论李侗“洒落气象”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354 |
| 颗粒名称: | 论李侗“洒落气象”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12 |
| 页码: | 250-261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论述了《延平答问》书中有二十三处涉及“洒落”、“洒然”或“脱然”。李侗的“洒落”思想及修为对朱熹的影响是深刻的。 |
| 关键词: | 李侗 洒落 朱熹 |
内容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被尊为延平先生。他与朱熹之父朱松均为理学家杨时的高足罗从彦的门下弟子,李侗实得其传。朱熹于李侗为世代有交情的通家子,又从学于李侗前后达十年之久,亲炙者六次。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朱熹赴同安主簿任顺路拜见李侗;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中旬朱熹同安主簿任满归来后,再前往南平受学,至三月而返;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朱熹又拜见李侗于南平,数月而归;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正月,朱熹拜谒李侗于建安(今建瓯市)遂与李侗俱归延平受教,至三月而归;隆兴元年(1163)夏、秋,李侗往江西铅山县其长子李友直处,去来途经崇安(今武夷山市),均与朱熹相会,朱熹还率弟子陪恩师畅游武夷山。随后李侗应福唐(今福清市)守汪应辰之请,赴福唐讲论,病发,于十月十五日逝于府治学馆,于是与朱熹隔生死。李侗生前对朱熹面授前后有数月之久,又有二十四通书信往复答疑解难,后来朱熹将其整理成《延平答问》,书中有二十三处涉及“洒落”、“洒然”或“脱然”。李侗的“洒落”思想及修为对朱熹的影响是深刻的。
一、李侗的“洒落”思想
李侗“洒落”思想的产生是有一定背景的,他说:“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因此,李侗把“洒落”作为一个重点问题加以强调,并提出了达到“洒落”的基本路径。
(一)“洒落气象”的提出
李侗曾说:“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什么是“洒落”呢?李侗在庚辰(1160)五月八日写给朱熹的信中说:“某尝以谓遇事若能无毫发固滞,便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大公,无彼己之偏倚,庶几于理道一贯。若见事不彻,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滞,皆不可也。……非理道明,心与气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说也。”可见“洒落”的特征在于明道理且道理一贯,达到心与气合,见事透彻,外事潇洒磊落,不偏不倚,通达晓畅:什么是“气象”呢?“气象”即指具体的自然万物的外在物象,又指具有内在意蕴的美学范畴。当指后者时,其意与“境界”一词相似,泛指人的精神品格,包括气度、风度、风范所达到的高度。李侗非常赞赏周敦颐的“洒落气象”,他说:“尝爱黄鲁直作濂溪诗序云:春陵周茂叔(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学者至此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庶几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进。愿更存养如此。”李侗对周敦颐的洒落气象的赞赏溢于言表,他要求学者要以周敦颐为榜样。他认为一个人具备洒落的精神境界必然会影响其言行举止。
(二)“洒落气象”的路径
要达到“洒落”的境界,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在长期的实践中,李侗形成了一套“洒落”修养的方法。
首先,先博学而后致约。李侗说:“不博无以致约,故闻见以多为贵。”遇事以无疑为善,这是因为“若是生疑,即恐滞碍。”闻见多了,见事透彻,自然疑殆就少了。博学的同时又要择精守约:所致之约就是儒家普遍适用的道统,李侗说:“所谓道者,是犹可通行者也。”为此,李侗建议多看儒家经典,对于这些经典中的精华,“玩味久之,必有会心处”。为了达到多闻见的目的,李侗主张让学者们群居终日,交相切磨,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这是因为学者看儒家经典过程中可以通过互相启发,领会其中微辞奥旨,甚至详考其事,“玩味所书抑扬予夺之处,看如何。积道理多,庶几渐见之。大率难得,学者无相启发处,终愦愦不能洒落尔”。
其次,于涵养处着力。李侗说:“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这是因为所学之知识并不能马上就能适合自身,需要领会其中的道理且一以贯之,才能应事洒落,无幽不穷。这就需将从师友中获得的道理往来于心中不断回味,他说:“夕所得于师友者,往来于心,求所以脱然处。”又说:“今之学者虽能存养,知有此理,然旦昼之间一有懈焉,遇事应接举处不觉打发机械,即离间而差矣。唯存养熟,理道明,习气渐尔消铄,道理油然而生,然后可进,亦不易也。”说明学者虽然知道存养的道理,但是不能坚持不懈。如果持守的意志不坚,就很容易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扰。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吻合浑然、体用无间。人们得不到进步,大概就是缺少涵养的缘故。所以,李侗说:“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又说:“大凡人理义之心何尝无,惟持守之即在尔。……湛然虚明,气象自然可见。……涵养须于此持守可尔……伊川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但敬不明于理,则敬特出于勉强而无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诚矣。……恐前数说方是学者下功夫处。不如此则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渐渐融释,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必理与心为一,庶几洒落矣。”说明通过涵养持敬,融释,从而对事物有透彻的理解,达到心与理一,不受制于外,才能称为“洒落”。
再者,以静坐默识的体悟方法来实现心与理一。静坐默识的体悟方法并非李侗的发明,默识心通是“道南学派”极力推崇的修养意向。李侗说:“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静矣。”又说:“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因为“处事扰扰,便似内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处理会,久之知觉渐渐可就道理矣”。又说:“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见其效。若欲于此进步,须把断诸路头,静坐默识,使之泥滓渐渐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说也,更熟思之。”李侗强调静坐修心主要目的在于收摄身心,心无旁骛,消除私欲,从而有利于实现心与理一,避免两者的脱节,以利于应事中节。朱熹曾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黄宗羲也说:“罗豫章师龟山,李延平师豫章,皆以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想其观字,亦如言圣人之能反观,非费思求索之谓,必有默会自得处。”又说:“‘静坐中观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是静中见性之法。要之,观者即是未发者也,观是不思,思则发矣。此为初学者引而致之之善诱也。”陈来先生在《朱子哲学研究》中指出:“所谓体验未发,是要求体验者超越一切思维和情感,以达到一种特别的心理体验。在这种高度沉静的修养中,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内心,成功的体验者常常会突发地获得一种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浑然感受。”当然这种体验未发的静坐功夫异于禅定,明道曾说:“习忘可以养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学道则异于是。”李侗的静坐不是心中虚无一物,而是要“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是时时处处主于天理、存养天理。
最后,不离日用,反身而诚,贵在自得。李侗非常关注修己之学。而修己之学离不开日用工夫,所以,李侗说:“唯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又说:“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皆可勉而进矣。若植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几希。”在李侗看来,读书人对圣贤之言都应在日用处下功夫,在人生中消融,化为自身的德行,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的口耳之学。他尤其注重领会儒家经典的言外之意,特别是基于直觉的经典中与己心相会之处:他说:“须是认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又说:“吾辈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必虑一澄然之时略绰一见,与心会处,便是正理。”他提倡如颜子那种闻言悟理、心契神受的自得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而洒落与自得又是连在一起的,李侗认为:“大率须见洒然处,然后为得。”而只有本着诚意持敬之心,反身以诚,才能实现自得,李侗说:“昔尝得之师友绪余,以谓学问有未惬适处,只求诸心。若反身而诚,清通和乐之象见,即是自得处。更望勉力,以此而已。”说明通过内省,以至诚之心立身行事,达到清通和乐之境,便是自得,便是洒落。
二、李侗的“洒落气象”
李侗受朱熹的父亲朱松雅重,基于他有着“求之当世,殆绝伦比”的处世风范与品性。同门友沙县邓迪曾评价说:“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应学臣沈函之请,为一大批著名理学家御书赐额,其中,为李侗题额“静中气象”,这是对李侗洒落境界的切中评价。李侗的“洒落气象”具体表现为学术通明、道德纯备以及人生态度上的超然远引。
(一)学术通明
李侗对儒家经典非常精通,朱熹曾说:“(李侗)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见其为一物而不违乎心目之间也。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其于《语》、《孟》他经,无不贯达(一本作通)。苟有疑问答之必极其趣。……其辨析精微,毫厘毕察。尝语问者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又说:“其语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毕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然一闻其说,则知其诐淫邪遁之所以然者。盖辨之于锱铢眇忽之间,而儒释之邪正分矣。”以上李侗的这些观点,给朱熹留下深刻的印象,确实说明了李侗的学术造诣深厚,已达贯通洒落的境界。李侗虽然不著书却不影响他作为朱熹老师的资格,正如颜子不著书,并不影响颜子作为“亚圣”(明代改为“复圣”)一样。清代延平知府金州周元文曾说:“(朱子)尝于集注中称述之,至云:‘默坐体验,洒然融洽。’盖其辨晰经书,推见至隐,虽虞廷之精一,孔门之一贯,不过是也。”
(二)道德纯备
李侗为人处世有极佳的品性。朱熹评价说:“其事亲诚孝,左右无违。仲兄性刚多忤,先生事之,致诚尽敬,更得其欢心焉。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与族姻故,恩意笃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处之有道,量入为出。宾祭谨饬,租赋必为邻里先,亲戚或贫不能婚嫁,为之经理。节衣食以赈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如也。年长者事之尽礼,少者贱者接之各尽其道。以故乡人爱敬,暴悍化服,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浅深,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李侗待人处世能达到以上境界,主要在于能够以尽己及物之心作为日常生活的一贯之理:他引用伊川的话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体会于一人之身,不过只是尽己及物之心而已。”又说:“盖天下之理无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则凡出于此者,虽品节万殊,曲折万变,莫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而各有条理,如川脉络之不可乱。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细而品类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经训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无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养益熟,精明纯一,触类洞然:泛应曲酬,发必中节。”“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常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可见,李侗的“洒落气象”的形成是他从日常生活中下功夫,长期涵养持守融释的结果。没有高贵的身份,一样可以成为道德纯备的圣贤。
(三)超然远引人
们常说禀性难移,可是李侗却能够做到变化气质,而且不干利禄,超然远引。实际上,少时的李侗十分豪迈,朱熹说:“尝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迥。”又说:“早岁闻道即弃场屋,超然远引,若无意于当世。然忧时论事,感激动人。”李侗得豫章所传之学后,退居山野,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李侗志于圣人绝学,务求诣其极,体验四十余年,遁世不见,无意于从政,俨然如一田夫野老,却无怨无悔。
李侗通过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的长期历练之后,神采精明,没有颓堕之气。他“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
寻常唤人,唤之不至,声必厉:侗唤之不至,声不加于前。其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然甚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他即便饮食或有不充,而怡然自得;他“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励,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李侗的个性已形成徐缓、中和、晓彻、清纯、怡然的超脱气象。
三、李侗的“洒落气象”对朱熹的影响
李侗在给罗博文的书信中说:“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极疑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李侗看到了朱熹是可造之才,因此对他悉心传授,而李侗的“洒落气象”对朱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为朱熹树立了洒落的榜样
朱熹深受李侗的言传身教的影响,在学术思想和人生态度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学术思想上,李侗“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的情怀和点拨,已使朱熹心智开悟,从而实现“逃禅归儒”学术转向,这为朱熹以后的终身辟佛奠定了基调;李侗“教熹看圣贤言语,熹将圣贤书读之,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乃返博归约,就平实处为学,于道日进”,为朱熹后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指引了方向。朱熹对《四书集注》的精确解释,与李侗对儒家经典洒然无碍解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侗曾特别指出了朱熹学术中的一些窒碍之处,例如,他曾说:“深测圣人之心,一个体段甚好,但更有少碍”;“谕及所疑数处,详味之,所见皆正当,可喜。但于洒落处恐未免滞碍。”等等。在接到朱熹不洒落处已渐融释告知之后,李侗称赞说:“承谕,近日学履甚适,向所耽恋不洒落处,今已渐融释。此便是道理进之效,甚善甚善。”朱熹对李侗的逐件“融释”不洒落之处的方法颇受启发:要达到心中“洒落”之功,须融释生活中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通过对每一件事情的透彻理会,经过日积月累,心中自然能够明了洒落了。朱熹说:“旧见李先生说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便理会一件。融释二字,下得极好:”朱熹后来在仕途上屡屡辞官,具有深厚的隐士情结,这无疑又是受到了李侗淡泊名利、超然远引人格潜移默化的感召。
(二)坚定了朱熹成为圣贤的决心
不仅如此,李侗还寄希望于朱熹能够成为治道的圣人。如果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达到圣人的洒落处,就会有失,只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才是洒然无窒的。李侗说:“圣人廓然明达,无所不可。非道大德宏者不能尔也……未至此,于所疑处即有碍。”又说:“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精粗不二,衮同尽此理,则非圣人不能是也。”李侗强调圣人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循序渐进达到,他说:“某窃以谓圣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为说,必十年乃一进者;若使困而知学,积十年之久,日孳孳而不倦者,是亦可以变化气质而必一进也。若以卤莽灭裂之学而不用心焉,虽十年亦只是如此,则是自暴自弃之人尔。言十年之渐次所以警乎学者,虽中才于夫子之道,皆可积习勉力而至焉。圣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李侗认为即使是中等才智的人,通过努力学习,变化气质,十年一进,都是可以成为圣人的。朱熹十数岁时当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时,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李侗勉励朱熹成圣,并告诉十年一进的方法,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朱熹成圣的信心。
(三)启发了朱熹继续探索致“中和”的修养方法
“洒落”的一个特征就是应事中节,为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加强致中和的修养方法:虽然朱熹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好章句训诂之学,不得尽心于李侗的“默会心通”的修养方法,直到李侗去世都还没有完全参透,未能体验到胸次洒落。朱熹曾说:“旧闻李先生论此(未发已发)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今乃知其为人深切,然恨不能尽记其曲折矣……但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磋过,孤负此翁耳。”但这一修养方法成为朱熹后来继续“中和”问题讨论的重要话头。在李侗过世不久,朱熹听说张南轩得衡山胡氏(胡宏)之学,于是前往访问:在壬辰八月《中和旧说序》中,他说:“余平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李先生没。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时,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朱熹逐渐认识到“中和旧说”是有问题的:“非惟心、性之名命之未当,而日用工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因为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日用工夫,也只是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这就缺少了平时涵养这一段工夫,于是,“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处,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因而,朱熹结合二程思想的分析并整合自己过去的心性观,形成了“中和”新说,即“未发为性,已发为情”,而“心统性情”。在新确立的“心性”关系里,“心”不仅存在于“已发”时,也存在于“未发”时,而且“已发未发”只是一个工夫,了无间隔。他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说:“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朱熹于是有了“鸢飞鱼跃”的心灵体验。
(四)“洒落”成为朱熹“圣贤气象”的中心话语
钱穆认为朱熹、吕祖谦在《近思录》中提出的“圣贤气象”是宋代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而“圣贤气象”的提出无疑是受了李侗的“洒落气象”的启发。“洒落”成为朱熹解释“圣贤气象”的重要词语,如《朱子语类》云:“集注谓曾点‘气象从容’,便是鼓瑟处;词意洒落,便是下面答言志……‘异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从容洒落处了。”朱熹针对曾点既见得天理流行,胸中洒落,而行有不掩,做工夫却有欠缺的不足进行了克服,形成了:“幔亭之风”,“‘幔亭之风’是朱熹与生徒们以武夷山诗意栖居为背景反映出来的,追求自得其乐和自由精神的圣贤气象。”朱熹在武夷精舍期间潇洒啸咏,完成《四书集注》,迎来诗歌创作的高峰和人生的顶峰。“幔亭之风”已对“曾点气象”实现了理性超越,真正达到了体用无间,洒然融释的境界。
四、结语
李侗的洒落修养已达很高的境界,可是他还是孜孜以求,永无止境。在庚辰五月八日给朱熹的书信中,他谦虚地说:“某晚景别无他,唯求道之心甚切。虽间能窥测一二,竟未有洒落处。以此兀坐,殊愦愦不快。”可见,“洒落”一直是李侗一生追求的理想。李侗如此重视洒落,并对朱熹等门人悉心教导,无非是想为社会培养出尽可能多的儒家式君子,以力纠当时社会知识分子不够洒落之偏。自南宋以来至今已近千年,“洒落”仍是有志于遨游于自由精神境界的人们所追求的理想。谁不想言行举止超然神采,风度翩翩,自然大方?谁不想洞彻万物,做事恰到好处,完美无瑕?谁不想拥有一个心境达观,超凡脱俗,不为世事所累的潇洒人生?接受自身改变不了的,改变自身能力所及的,不再为琐事而烦扰,不再为小事而糊涂,做个洒落的、身心加健康的人,将赋予人生以更多的意义。有韵致的洒落是一种对万物的洞察和生命的热情,是一种人生理性的豁达,是一种内涵与外露统一的表象,也是精神超越的折光。
一、李侗的“洒落”思想
李侗“洒落”思想的产生是有一定背景的,他说:“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因此,李侗把“洒落”作为一个重点问题加以强调,并提出了达到“洒落”的基本路径。
(一)“洒落气象”的提出
李侗曾说:“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什么是“洒落”呢?李侗在庚辰(1160)五月八日写给朱熹的信中说:“某尝以谓遇事若能无毫发固滞,便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大公,无彼己之偏倚,庶几于理道一贯。若见事不彻,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滞,皆不可也。……非理道明,心与气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说也。”可见“洒落”的特征在于明道理且道理一贯,达到心与气合,见事透彻,外事潇洒磊落,不偏不倚,通达晓畅:什么是“气象”呢?“气象”即指具体的自然万物的外在物象,又指具有内在意蕴的美学范畴。当指后者时,其意与“境界”一词相似,泛指人的精神品格,包括气度、风度、风范所达到的高度。李侗非常赞赏周敦颐的“洒落气象”,他说:“尝爱黄鲁直作濂溪诗序云:春陵周茂叔(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学者至此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庶几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进。愿更存养如此。”李侗对周敦颐的洒落气象的赞赏溢于言表,他要求学者要以周敦颐为榜样。他认为一个人具备洒落的精神境界必然会影响其言行举止。
(二)“洒落气象”的路径
要达到“洒落”的境界,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在长期的实践中,李侗形成了一套“洒落”修养的方法。
首先,先博学而后致约。李侗说:“不博无以致约,故闻见以多为贵。”遇事以无疑为善,这是因为“若是生疑,即恐滞碍。”闻见多了,见事透彻,自然疑殆就少了。博学的同时又要择精守约:所致之约就是儒家普遍适用的道统,李侗说:“所谓道者,是犹可通行者也。”为此,李侗建议多看儒家经典,对于这些经典中的精华,“玩味久之,必有会心处”。为了达到多闻见的目的,李侗主张让学者们群居终日,交相切磨,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这是因为学者看儒家经典过程中可以通过互相启发,领会其中微辞奥旨,甚至详考其事,“玩味所书抑扬予夺之处,看如何。积道理多,庶几渐见之。大率难得,学者无相启发处,终愦愦不能洒落尔”。
其次,于涵养处着力。李侗说:“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这是因为所学之知识并不能马上就能适合自身,需要领会其中的道理且一以贯之,才能应事洒落,无幽不穷。这就需将从师友中获得的道理往来于心中不断回味,他说:“夕所得于师友者,往来于心,求所以脱然处。”又说:“今之学者虽能存养,知有此理,然旦昼之间一有懈焉,遇事应接举处不觉打发机械,即离间而差矣。唯存养熟,理道明,习气渐尔消铄,道理油然而生,然后可进,亦不易也。”说明学者虽然知道存养的道理,但是不能坚持不懈。如果持守的意志不坚,就很容易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扰。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吻合浑然、体用无间。人们得不到进步,大概就是缺少涵养的缘故。所以,李侗说:“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又说:“大凡人理义之心何尝无,惟持守之即在尔。……湛然虚明,气象自然可见。……涵养须于此持守可尔……伊川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但敬不明于理,则敬特出于勉强而无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诚矣。……恐前数说方是学者下功夫处。不如此则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渐渐融释,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必理与心为一,庶几洒落矣。”说明通过涵养持敬,融释,从而对事物有透彻的理解,达到心与理一,不受制于外,才能称为“洒落”。
再者,以静坐默识的体悟方法来实现心与理一。静坐默识的体悟方法并非李侗的发明,默识心通是“道南学派”极力推崇的修养意向。李侗说:“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静矣。”又说:“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因为“处事扰扰,便似内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处理会,久之知觉渐渐可就道理矣”。又说:“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见其效。若欲于此进步,须把断诸路头,静坐默识,使之泥滓渐渐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说也,更熟思之。”李侗强调静坐修心主要目的在于收摄身心,心无旁骛,消除私欲,从而有利于实现心与理一,避免两者的脱节,以利于应事中节。朱熹曾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黄宗羲也说:“罗豫章师龟山,李延平师豫章,皆以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想其观字,亦如言圣人之能反观,非费思求索之谓,必有默会自得处。”又说:“‘静坐中观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是静中见性之法。要之,观者即是未发者也,观是不思,思则发矣。此为初学者引而致之之善诱也。”陈来先生在《朱子哲学研究》中指出:“所谓体验未发,是要求体验者超越一切思维和情感,以达到一种特别的心理体验。在这种高度沉静的修养中,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内心,成功的体验者常常会突发地获得一种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浑然感受。”当然这种体验未发的静坐功夫异于禅定,明道曾说:“习忘可以养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学道则异于是。”李侗的静坐不是心中虚无一物,而是要“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是时时处处主于天理、存养天理。
最后,不离日用,反身而诚,贵在自得。李侗非常关注修己之学。而修己之学离不开日用工夫,所以,李侗说:“唯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又说:“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皆可勉而进矣。若植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几希。”在李侗看来,读书人对圣贤之言都应在日用处下功夫,在人生中消融,化为自身的德行,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的口耳之学。他尤其注重领会儒家经典的言外之意,特别是基于直觉的经典中与己心相会之处:他说:“须是认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又说:“吾辈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必虑一澄然之时略绰一见,与心会处,便是正理。”他提倡如颜子那种闻言悟理、心契神受的自得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而洒落与自得又是连在一起的,李侗认为:“大率须见洒然处,然后为得。”而只有本着诚意持敬之心,反身以诚,才能实现自得,李侗说:“昔尝得之师友绪余,以谓学问有未惬适处,只求诸心。若反身而诚,清通和乐之象见,即是自得处。更望勉力,以此而已。”说明通过内省,以至诚之心立身行事,达到清通和乐之境,便是自得,便是洒落。
二、李侗的“洒落气象”
李侗受朱熹的父亲朱松雅重,基于他有着“求之当世,殆绝伦比”的处世风范与品性。同门友沙县邓迪曾评价说:“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应学臣沈函之请,为一大批著名理学家御书赐额,其中,为李侗题额“静中气象”,这是对李侗洒落境界的切中评价。李侗的“洒落气象”具体表现为学术通明、道德纯备以及人生态度上的超然远引。
(一)学术通明
李侗对儒家经典非常精通,朱熹曾说:“(李侗)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见其为一物而不违乎心目之间也。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其于《语》、《孟》他经,无不贯达(一本作通)。苟有疑问答之必极其趣。……其辨析精微,毫厘毕察。尝语问者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又说:“其语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毕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然一闻其说,则知其诐淫邪遁之所以然者。盖辨之于锱铢眇忽之间,而儒释之邪正分矣。”以上李侗的这些观点,给朱熹留下深刻的印象,确实说明了李侗的学术造诣深厚,已达贯通洒落的境界。李侗虽然不著书却不影响他作为朱熹老师的资格,正如颜子不著书,并不影响颜子作为“亚圣”(明代改为“复圣”)一样。清代延平知府金州周元文曾说:“(朱子)尝于集注中称述之,至云:‘默坐体验,洒然融洽。’盖其辨晰经书,推见至隐,虽虞廷之精一,孔门之一贯,不过是也。”
(二)道德纯备
李侗为人处世有极佳的品性。朱熹评价说:“其事亲诚孝,左右无违。仲兄性刚多忤,先生事之,致诚尽敬,更得其欢心焉。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与族姻故,恩意笃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处之有道,量入为出。宾祭谨饬,租赋必为邻里先,亲戚或贫不能婚嫁,为之经理。节衣食以赈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如也。年长者事之尽礼,少者贱者接之各尽其道。以故乡人爱敬,暴悍化服,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浅深,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李侗待人处世能达到以上境界,主要在于能够以尽己及物之心作为日常生活的一贯之理:他引用伊川的话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体会于一人之身,不过只是尽己及物之心而已。”又说:“盖天下之理无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则凡出于此者,虽品节万殊,曲折万变,莫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而各有条理,如川脉络之不可乱。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细而品类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经训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无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养益熟,精明纯一,触类洞然:泛应曲酬,发必中节。”“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常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可见,李侗的“洒落气象”的形成是他从日常生活中下功夫,长期涵养持守融释的结果。没有高贵的身份,一样可以成为道德纯备的圣贤。
(三)超然远引人
们常说禀性难移,可是李侗却能够做到变化气质,而且不干利禄,超然远引。实际上,少时的李侗十分豪迈,朱熹说:“尝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迥。”又说:“早岁闻道即弃场屋,超然远引,若无意于当世。然忧时论事,感激动人。”李侗得豫章所传之学后,退居山野,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李侗志于圣人绝学,务求诣其极,体验四十余年,遁世不见,无意于从政,俨然如一田夫野老,却无怨无悔。
李侗通过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的长期历练之后,神采精明,没有颓堕之气。他“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
寻常唤人,唤之不至,声必厉:侗唤之不至,声不加于前。其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然甚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他即便饮食或有不充,而怡然自得;他“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励,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李侗的个性已形成徐缓、中和、晓彻、清纯、怡然的超脱气象。
三、李侗的“洒落气象”对朱熹的影响
李侗在给罗博文的书信中说:“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极疑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李侗看到了朱熹是可造之才,因此对他悉心传授,而李侗的“洒落气象”对朱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为朱熹树立了洒落的榜样
朱熹深受李侗的言传身教的影响,在学术思想和人生态度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学术思想上,李侗“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的情怀和点拨,已使朱熹心智开悟,从而实现“逃禅归儒”学术转向,这为朱熹以后的终身辟佛奠定了基调;李侗“教熹看圣贤言语,熹将圣贤书读之,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乃返博归约,就平实处为学,于道日进”,为朱熹后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指引了方向。朱熹对《四书集注》的精确解释,与李侗对儒家经典洒然无碍解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侗曾特别指出了朱熹学术中的一些窒碍之处,例如,他曾说:“深测圣人之心,一个体段甚好,但更有少碍”;“谕及所疑数处,详味之,所见皆正当,可喜。但于洒落处恐未免滞碍。”等等。在接到朱熹不洒落处已渐融释告知之后,李侗称赞说:“承谕,近日学履甚适,向所耽恋不洒落处,今已渐融释。此便是道理进之效,甚善甚善。”朱熹对李侗的逐件“融释”不洒落之处的方法颇受启发:要达到心中“洒落”之功,须融释生活中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通过对每一件事情的透彻理会,经过日积月累,心中自然能够明了洒落了。朱熹说:“旧见李先生说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便理会一件。融释二字,下得极好:”朱熹后来在仕途上屡屡辞官,具有深厚的隐士情结,这无疑又是受到了李侗淡泊名利、超然远引人格潜移默化的感召。
(二)坚定了朱熹成为圣贤的决心
不仅如此,李侗还寄希望于朱熹能够成为治道的圣人。如果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达到圣人的洒落处,就会有失,只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才是洒然无窒的。李侗说:“圣人廓然明达,无所不可。非道大德宏者不能尔也……未至此,于所疑处即有碍。”又说:“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精粗不二,衮同尽此理,则非圣人不能是也。”李侗强调圣人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循序渐进达到,他说:“某窃以谓圣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为说,必十年乃一进者;若使困而知学,积十年之久,日孳孳而不倦者,是亦可以变化气质而必一进也。若以卤莽灭裂之学而不用心焉,虽十年亦只是如此,则是自暴自弃之人尔。言十年之渐次所以警乎学者,虽中才于夫子之道,皆可积习勉力而至焉。圣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李侗认为即使是中等才智的人,通过努力学习,变化气质,十年一进,都是可以成为圣人的。朱熹十数岁时当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时,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李侗勉励朱熹成圣,并告诉十年一进的方法,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朱熹成圣的信心。
(三)启发了朱熹继续探索致“中和”的修养方法
“洒落”的一个特征就是应事中节,为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加强致中和的修养方法:虽然朱熹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好章句训诂之学,不得尽心于李侗的“默会心通”的修养方法,直到李侗去世都还没有完全参透,未能体验到胸次洒落。朱熹曾说:“旧闻李先生论此(未发已发)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今乃知其为人深切,然恨不能尽记其曲折矣……但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磋过,孤负此翁耳。”但这一修养方法成为朱熹后来继续“中和”问题讨论的重要话头。在李侗过世不久,朱熹听说张南轩得衡山胡氏(胡宏)之学,于是前往访问:在壬辰八月《中和旧说序》中,他说:“余平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李先生没。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时,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朱熹逐渐认识到“中和旧说”是有问题的:“非惟心、性之名命之未当,而日用工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因为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日用工夫,也只是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这就缺少了平时涵养这一段工夫,于是,“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处,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因而,朱熹结合二程思想的分析并整合自己过去的心性观,形成了“中和”新说,即“未发为性,已发为情”,而“心统性情”。在新确立的“心性”关系里,“心”不仅存在于“已发”时,也存在于“未发”时,而且“已发未发”只是一个工夫,了无间隔。他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说:“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朱熹于是有了“鸢飞鱼跃”的心灵体验。
(四)“洒落”成为朱熹“圣贤气象”的中心话语
钱穆认为朱熹、吕祖谦在《近思录》中提出的“圣贤气象”是宋代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而“圣贤气象”的提出无疑是受了李侗的“洒落气象”的启发。“洒落”成为朱熹解释“圣贤气象”的重要词语,如《朱子语类》云:“集注谓曾点‘气象从容’,便是鼓瑟处;词意洒落,便是下面答言志……‘异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从容洒落处了。”朱熹针对曾点既见得天理流行,胸中洒落,而行有不掩,做工夫却有欠缺的不足进行了克服,形成了:“幔亭之风”,“‘幔亭之风’是朱熹与生徒们以武夷山诗意栖居为背景反映出来的,追求自得其乐和自由精神的圣贤气象。”朱熹在武夷精舍期间潇洒啸咏,完成《四书集注》,迎来诗歌创作的高峰和人生的顶峰。“幔亭之风”已对“曾点气象”实现了理性超越,真正达到了体用无间,洒然融释的境界。
四、结语
李侗的洒落修养已达很高的境界,可是他还是孜孜以求,永无止境。在庚辰五月八日给朱熹的书信中,他谦虚地说:“某晚景别无他,唯求道之心甚切。虽间能窥测一二,竟未有洒落处。以此兀坐,殊愦愦不快。”可见,“洒落”一直是李侗一生追求的理想。李侗如此重视洒落,并对朱熹等门人悉心教导,无非是想为社会培养出尽可能多的儒家式君子,以力纠当时社会知识分子不够洒落之偏。自南宋以来至今已近千年,“洒落”仍是有志于遨游于自由精神境界的人们所追求的理想。谁不想言行举止超然神采,风度翩翩,自然大方?谁不想洞彻万物,做事恰到好处,完美无瑕?谁不想拥有一个心境达观,超凡脱俗,不为世事所累的潇洒人生?接受自身改变不了的,改变自身能力所及的,不再为琐事而烦扰,不再为小事而糊涂,做个洒落的、身心加健康的人,将赋予人生以更多的意义。有韵致的洒落是一种对万物的洞察和生命的热情,是一种人生理性的豁达,是一种内涵与外露统一的表象,也是精神超越的折光。
附注
李侗:《李延平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刘京菊:《承洛启闽——道南学派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朱杰人:《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吴栻:(民国)《南平县志》,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
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蓝宗荣:《论朱熹“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与实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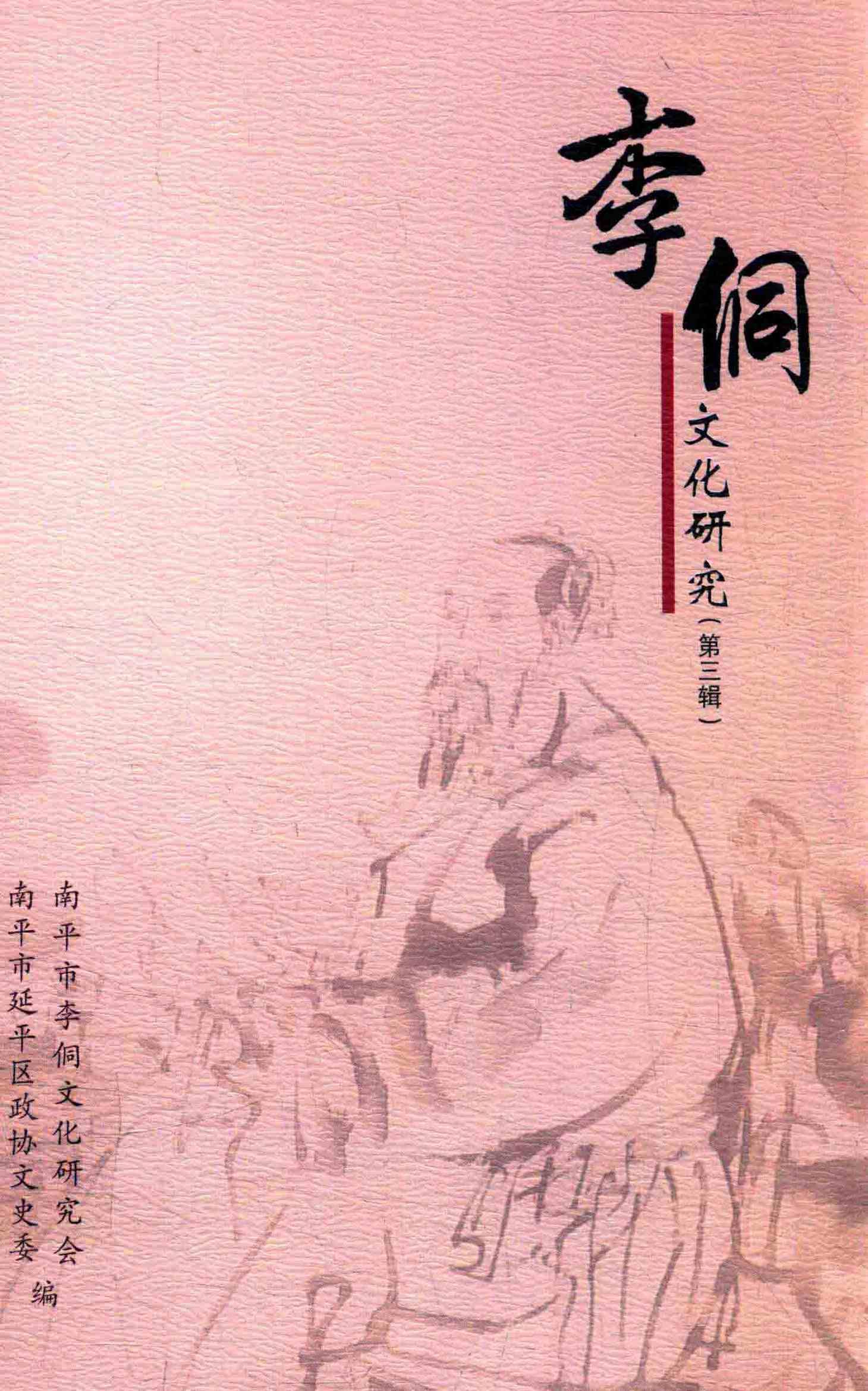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
相关人物
蓝宗荣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李侗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