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与“心法”:以《延平答问》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349 |
| 颗粒名称: | 师承与“心法”:以《延平答问》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 其他题名: | 兼论明清之际朱子学的地位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40-249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记述了以《延平答问》序跋为中心的考察,其中包括内容一、从序跋看《延平答问》的版本刊刻、流传过程,关系,三、从序跋看《延平答问》是一部怎样的书,四、从序跋看明清之际朱子学地位的再提升。 |
| 关键词: | 李侗 《延平答问》 考察 |
内容
《延平答问》(初为一卷本)是朱熹辑订的,收录的是他与其师李侗(延平)之间平时论学的往来书札,时间自宋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六月(时年朱子二十八岁)至隆兴元年(1163)癸未(时年朱子三十四岁),共七年。后来,朱熹门人又将其平时论述李延平的语录、《延平先生李公行状》、《祭延平李先生文》等收入别为《附录》一卷并刊行于世。自此以后一直到民国这八百多年里,出现了不少刻印于不同时期的《延平答问》的不同版本,而每一个刻本都留有刊刻者或是当时的文士名流所作的序、跋。据陆建华、严佐之校点的《延平答问》所收的《附录》,所录的历代刻本序跋或记共有二十一篇,其中,宋代二篇、明代三篇、清代八篇、民国一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延平答问提要》一篇,此外,还收录了历代藏书家所藏《延平答问》所作的“记”六篇。当然在《附录》中还有另外两篇序未有提到,就是清周亮工和李佐圣受李葆初之请为顺治本《延平答问》所作的序(此两序详见《南平县志》卷十六)。从这些序跋中可以直观感受到:《延平答问》在清代的刻印是较频繁的,而对这些序跋作一全面考察,从中可以窥见李侗、朱熹的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等重要的讯息,可以了解《延平答问》版本刻印与流传情况以及《延平答问》一书的性质与作用,特别是序跋背后所承载的与当时学术动态相关联的学术流变。这也给我们研究《延平答问》文本本身或以《延平答问》研究李延平和朱子二人的思想提供了又一新的角度。
一、从序跋看《延平答问》的版本刊刻、流传过程
就已知而言,《延平答问》在宋代有三个版本:嘉定七年(1214)北海王耕道姑孰郡斋本、嘉定九年(1216)曹彦约益昌学宫刻本、建阳麻沙印本。其中嘉定“姑孰本”的跋文是由朱子门人及孙婿赵师夏(致道)所作,该跋文在后世学者中多有推崇。况且王氏“姑孰本”乃后来历代各刊本的“祖本”,与其最近的曹氏“益昌本”即是承其而重刻的,这一点曹氏在他自己所作的《延平答问跋》中就已点明,他说:“《延平答问》一编,始得当涂印本于黄岩赵师夏致道……”而文中所提到的“当涂印本”即指王耕道的“姑孰本”,因“当涂”当时属江苏管辖。到了明代,也有不少《延平答问》的刻本,这其中最具意义的当属周木刻本,原因在于“周木本”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宋嘉定刻本,下启后来历次刻本(后来宋本已佚失),这可从周木在他亲自撰写的《延平答问序》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说:
木思睹有年,遍求于人而不可得,深愧寡陋,未考《元史》从祀之详。成化乙巳,乃复上请于朝,并乞校颁其书,羽翼正学。有司置议,事不果行。既六年,乃得延平郡庠近刻本而读之,承传舛讹,益增疑惧。又三年,始求得嘉定间刻本而校正焉,比近本既多《后录》,而复僭为《补录》,以附于后,刻之严郡,传示将来,俾知朱子又得于先生,而先生有功于朱子,诚如雷霆日月之不可掩矣。
当然,在该序文中周木还提及了主旨颁书和为搜寻《延平答问》版本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另外,周木还辑录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与李延平相关的论述而“复僭为《补录》”。由于宋本的佚失,周木刻本就成了以后诸刻本的“模本”了,如稍后的“正德李习本”、“万历熊尚文刻本”两个明代刻本都与“周木本”是一脉相承的。到了清代,几个重要的《延平答问》刻本,如清顺治年间(1644~1661)李延平裔孙李孔文刻本、清康熙年间(1662~1722)张伯行《正谊堂全书》本、吕氏宝诰堂本以及清乾隆年间(1736~1795)《四库全书》本也都与“周木本”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
二、从《延平答问》序跋看李延平、朱子的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
检视《延平答问》历代各序跋,作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李延平、朱子二人的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朱子门人暨孙婿赵师夏为北海王耕道所刻宋嘉定姑孰本所作的首个《延平答问跋》就曾提到:
延平李先生之学,得之仲素罗先生;罗先生之学,得之龟山杨先生。龟山盖伊洛之高弟也。……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
从上述可知,朱子的师承脉络是:伊洛(程颢、程颐)→杨龟山(时)→罗仲素(从彦)→李延平→朱子。当然,赵师夏在这篇跋文中提到李延平在师承上所做的贡献,认为“今文公先生之言布满天下,光明俊伟”是“实延平先生一言之绪也”。清代南平知县苏渭生在《清乾隆补刻本延平答问跋》中也说:“自龟山得濂洛之传,而道学之统闽中为盛。顾上承杨、罗而下开考亭(即指朱熹),则延平李先生之功为甚钜。”从赵师夏作跋以后,历代为《延平答问》作序或跋的作者也都会提及师承和学术渊源,而且更加的推崇和重视。明代周木在《延平答问序》中说:
先生之学得之豫章,豫章得之龟山,龟山实得之于伊洛,伊洛之学则又得于濂洛。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虽聋瞽之人,有不可掩者。
这里,周木将这种师承已上溯到了周濂溪(敦颐),而且认为这是“道统”的正传。至清代,承续周木此提法的有顺治间为顺治本《延平答问》作序(实名为《李延平先生文集序》)的周亮工,他在序文中多次提到:“尝稽考亭……及受学于李延平先生之门,为学乃始敛就平实”,“知先生,则愈知考亭矣。濂洛之学,至考亭而集其成”;“昔人以世无二程,无复知有濂溪。然则若无考亭,将不知有先生矣。”周元文在《清康熙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序》中也提“传道之正宗”,他说:
窃闻秦汉而降,道统不绝如线,迨至有宋,二程子发其宗指,朱子集其大成,而圣道以明。程子得杨龟山先生,目之曰:“吾道南矣。”继之者为罗仲素先生,又传而为李愿中先生,而后有朱子。其间师弟相承,后先继起,则杨、罗、李三先生实为传道之正宗。
而光绪五年(1879)巡延(延平)建(建阳)邵(邵武)使者广敏在《清光绪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序》中更是讲道:
粤稽道统相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迄思孟,燦著于群经。降而下之,荀与杨也,择焉不精,语焉不详,道统于是乎少微矣。紫阳出,数百年坠绪忽焉复振,究其渊源,则延平先生所传也。先生得濂洛正派,即绍洙泗真传。
综合上述可知,从宋代开始推崇李延平和朱子的门人学者都非常重视他们二人的师承关系与学术渊源,而且到明清之际以及整个清时期,更是将李、朱二人的师承与学术源流从上追溯至二程及周濂溪,亦即从“道南学派”上溯到整个“道统”,并且将朱子的地位从“道南真传”提升至得“道统正宗”,这固然与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有关,然其中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何在?这要联系明清之际的整个学术史环境来考察。
因行文关系,将此点放到后面论述。
三、从序跋看《延平答问》是一部怎样的书
我们知道,《延平答问》是朱子辑录了他与老师李延平之间平日论学往来的书信。至于辑订的初衷,历来都认为该书就是一本老师与学生之间普通的学习问答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较明确说《延平答问》是“书札往来问答”“后朱子辑而录之”。另外,从《延平答问》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的书名也可窥见一斑,《延平答问》从朱子辑订时起就未曾明确书的名称,如《朱文公文集》中有一处以“延平先生语录”而作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称“延平问答”、“延平李先生答问”、“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延平语”等。其实,这提法在《延平答问》历代刻本的序跋中也多有提及,明弘治间(1488~1505)周木在他所刻本《延平答问序》的开头就说:“《延平答问》者,子朱子述其师延平李先生答其平日之问,以明其传之有自也。”明正德间(1506~1521)李习(李侗裔孙)在他所刻本《延平答问跋》中也说:“紫阳朱夫子受学于老祖文靖公之门,尝以平日答问要语编录成书,流布天下。”周木与李习二人都认为《延平答问》是李、朱二人的“平日答问”。总之,对于《延平答问》一书的性质都普遍认为属于“问答”类的书。
但到后来特别是明末清初时,学者对于《延平答问》书的性质(即属何类书)有了新的观点和提法,将《延平答问》提升为一本传授“心法”的书,明万历间(1573~1620)的熊尚文在他所刻《延平答问序》中首次提出这样的观点,只是他用了“心传”一词,他说:“庶先生平日所得于豫章,而紫阳氏所藉以演心传于万祀者,是集稍觇一斑矣。”至清代,就都比较普遍的认同甚至推崇这种说法。康熙间(1662-1722)延平知府周元文在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序》中说:“程子曰:‘《中庸》一书,乃也氏传授心法。’则是书(指《延平答问》)也,其即紫阳所受之心法欤?”周氏之里正式使用“心法”一词,并且将《延平答问》与《中庸》并提,其寓意可见一斑。与周元文同时的南平县知县邓炎在同本的《延平答问跋》中亦说:“而《答问》一编,则李、朱二夫子传授心法,其讲学精奥,洵继往开来,不容泯没者也。”此后继承“心法”说的还有乾隆间(1736~1795)钟紫帏补刻本《延平答问跋》中说:“因忆《延平答问》一书,乃朱子授受衣钵。”光绪二年(1876)延平知府张其曜在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跋》开头说“《延平答问》一书,先儒所授受,实后学之法程,凡以阐明斯道者,无微不显。”光绪五年(1879)知延平府事的张国正在同本《延平答问序》中更是提“圣贤心法”,他说:“《延平答问》者,子朱子辑其师延平李先生平日传授之言,盖圣贤心法也。”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自明末首提“紫阳演心传”,到“紫阳受心法”、“朱子授受衣钵”、“先儒授受法程”,到最后的“圣贤之心法”,足以证明《延平答问》在明末清初及清以后的理学乃至儒学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与推崇,当然这与当时朱子地位的再次得到提升与推崇以及明清之际的学术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从序跋看明清之际朱子学地位的再提升
综合上文所述,从《延平答问》历代刻本的序跋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讯息,即在明清之际,朱子学学者们以传刻《延平答问》作为捍卫朱子及其理学地位的形式,使之不至于在“心学”兴起的浪潮中衰微。《延平答问》各序跋的作者将朱子的师承渊源追溯至周濂溪,并且推崇朱子为“道南学派”乃至整个“道统”流传的“正宗”与关键人物;更甚者是将《延平答问》这样的师生间“答问往来书札”尊奉为“圣贤之心法”。固然一本书的作用不会很大,但放于当时的思想和学术环境,且又是朱子亲自辑订的书,是具有重要的时代与学术(特别对于程朱理学来讲)意义的。当然,这种提升的过程是漫长的,凝结着诸多尊崇程朱学者的心血。究其原因,就必定会联系到明清之际那场重要的学术变迁运动。
首先,当时尊程朱学者极力抬升朱子地位及推崇《延平答问》为“心法”之书,与“阳明学”的盛行成为“显学”而“朱子学”的衰微有关。在明代的前中期,因明王朝的“定朱学于一尊”的举措,朱子理学仍然处于思想学术的统治地位,但也是从明代初期开始,朱子理学的发展有了心学化的趋向。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陈献章与湛若水二人,但最终集心学之大成的就是王阳明,他一开始也尊奉程朱,后来“龙场悟道”并逐渐形成了以“心”为中心的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赢得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而盛行。相反,在这一时期,朱子学虽还是统治之学,但由于心学的兴起而声势锐减变得衰微不堪。当然,这里面有朱子学自身理论与实践上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张岂之曾概括为:“一是明政府一方面‘定朱学于一尊’,而在实际层面却从一己私利出发,采取极端不合理的措施;二是朱学在‘格外在之物与伦理实践’之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三是朱学自身的流变呈现出注重居敬躬行、心上理会的向里工夫,即有向心学接近与注重心学的趋向。”也与当时一批尊朱子学的学者的思想认识变化有关。如薛瑄就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在他看来,朱子学不再是一种需要研究的思想形态,而只是一种只要进行道德实践即可类似与准宗教性的信仰体系。然鉴于当时这种学术环境,明清之际的一批坚守朱子学学者、士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受当时普遍流行心学及心法之类伦说的启发,一方面将朱子作为从“道南之传”抬升至接续整个“道学”继承人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是将《延平答问》作为整个理学以及道学的传授心诀而尊为“心法”,旨在推动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广泛传播,抬升与巩固朱子学的统治地位。
其次,在明末清初的那场思想变动中,尊崇朱子学并努力维护他们的影响和地位的,就不得不提到顾宪成、高攀龙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东林学派。上面曾提到,朱子学经南宋以后的兴盛,到明代已逐渐衰微,被阳明学的兴盛所冲击。但正如历史一样有盛必有衰,等到了王阳明去世后,阳明学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并暴露出了心学的弊端,从而就出现了学术上的反动。而顾宪成、高攀龙等在此时“广邀同道,集会讲学”并以东林书院为中心“传播学术、评议时政”,形成了具有独特思想特征的东林学派。从东林学派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自始自终是“学宗程朱”的,朱文杰说:“东林学派为儒家的正统学派,他们恪守程朱正宗。”而且与“濂洛关闽”之学有着渊源关系,其中当属周敦颐影响最大。当然,有学者认为顾、高等东林学派人是从“王学”向“朱学”的回归的学派,如陈时龙说:“东林学派源出于心学但代表了向程朱学回归的趋向的学派。”陈祖武在《顾炎武评传》中也说:“在晚明学术界,顾宪成、高攀龙以向朱学的回归,试图重振没落的理学。”但就是这种“回归”,为朱子学以及朱子地位的再次提升创造了有益的思想条件和学术环境。另一方面,始终坚守朱子学的学者也受到东林学派“崇朱辟王”的激励,积极而广泛地通过刊刻一些朱子的书籍来进一步宣传朱子学,并提升朱子在理学乃至整个道统上的地位。这可以从上述的自明末至清代《延平答问》的多个刻本,以及各刻本序跋中对于朱子师承渊源的抬升,将《延平答问》视为理学及整个道统的“圣贤心法”,就可以略见一二。
总之,《延平答问》一经问世,历代的刻本及为之作序跋者不在少数,特别是明末清初以及整个清代属最多。更有甚者,许多尊崇朱子学的学者借助于当时的学术流变,将《延平答问》看作理学乃至整个道统所传授的“圣贤之心法”,进一步明确与提升了李侗在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也维护了朱子作为道统的正宗传承人地位。从而,使朱子学在被“心学”的兴盛而一度消沉后,又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和能量,回归到正统的“显学”的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作者系江西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从序跋看《延平答问》的版本刊刻、流传过程
就已知而言,《延平答问》在宋代有三个版本:嘉定七年(1214)北海王耕道姑孰郡斋本、嘉定九年(1216)曹彦约益昌学宫刻本、建阳麻沙印本。其中嘉定“姑孰本”的跋文是由朱子门人及孙婿赵师夏(致道)所作,该跋文在后世学者中多有推崇。况且王氏“姑孰本”乃后来历代各刊本的“祖本”,与其最近的曹氏“益昌本”即是承其而重刻的,这一点曹氏在他自己所作的《延平答问跋》中就已点明,他说:“《延平答问》一编,始得当涂印本于黄岩赵师夏致道……”而文中所提到的“当涂印本”即指王耕道的“姑孰本”,因“当涂”当时属江苏管辖。到了明代,也有不少《延平答问》的刻本,这其中最具意义的当属周木刻本,原因在于“周木本”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宋嘉定刻本,下启后来历次刻本(后来宋本已佚失),这可从周木在他亲自撰写的《延平答问序》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说:
木思睹有年,遍求于人而不可得,深愧寡陋,未考《元史》从祀之详。成化乙巳,乃复上请于朝,并乞校颁其书,羽翼正学。有司置议,事不果行。既六年,乃得延平郡庠近刻本而读之,承传舛讹,益增疑惧。又三年,始求得嘉定间刻本而校正焉,比近本既多《后录》,而复僭为《补录》,以附于后,刻之严郡,传示将来,俾知朱子又得于先生,而先生有功于朱子,诚如雷霆日月之不可掩矣。
当然,在该序文中周木还提及了主旨颁书和为搜寻《延平答问》版本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另外,周木还辑录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与李延平相关的论述而“复僭为《补录》”。由于宋本的佚失,周木刻本就成了以后诸刻本的“模本”了,如稍后的“正德李习本”、“万历熊尚文刻本”两个明代刻本都与“周木本”是一脉相承的。到了清代,几个重要的《延平答问》刻本,如清顺治年间(1644~1661)李延平裔孙李孔文刻本、清康熙年间(1662~1722)张伯行《正谊堂全书》本、吕氏宝诰堂本以及清乾隆年间(1736~1795)《四库全书》本也都与“周木本”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
二、从《延平答问》序跋看李延平、朱子的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
检视《延平答问》历代各序跋,作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李延平、朱子二人的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朱子门人暨孙婿赵师夏为北海王耕道所刻宋嘉定姑孰本所作的首个《延平答问跋》就曾提到:
延平李先生之学,得之仲素罗先生;罗先生之学,得之龟山杨先生。龟山盖伊洛之高弟也。……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
从上述可知,朱子的师承脉络是:伊洛(程颢、程颐)→杨龟山(时)→罗仲素(从彦)→李延平→朱子。当然,赵师夏在这篇跋文中提到李延平在师承上所做的贡献,认为“今文公先生之言布满天下,光明俊伟”是“实延平先生一言之绪也”。清代南平知县苏渭生在《清乾隆补刻本延平答问跋》中也说:“自龟山得濂洛之传,而道学之统闽中为盛。顾上承杨、罗而下开考亭(即指朱熹),则延平李先生之功为甚钜。”从赵师夏作跋以后,历代为《延平答问》作序或跋的作者也都会提及师承和学术渊源,而且更加的推崇和重视。明代周木在《延平答问序》中说:
先生之学得之豫章,豫章得之龟山,龟山实得之于伊洛,伊洛之学则又得于濂洛。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虽聋瞽之人,有不可掩者。
这里,周木将这种师承已上溯到了周濂溪(敦颐),而且认为这是“道统”的正传。至清代,承续周木此提法的有顺治间为顺治本《延平答问》作序(实名为《李延平先生文集序》)的周亮工,他在序文中多次提到:“尝稽考亭……及受学于李延平先生之门,为学乃始敛就平实”,“知先生,则愈知考亭矣。濂洛之学,至考亭而集其成”;“昔人以世无二程,无复知有濂溪。然则若无考亭,将不知有先生矣。”周元文在《清康熙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序》中也提“传道之正宗”,他说:
窃闻秦汉而降,道统不绝如线,迨至有宋,二程子发其宗指,朱子集其大成,而圣道以明。程子得杨龟山先生,目之曰:“吾道南矣。”继之者为罗仲素先生,又传而为李愿中先生,而后有朱子。其间师弟相承,后先继起,则杨、罗、李三先生实为传道之正宗。
而光绪五年(1879)巡延(延平)建(建阳)邵(邵武)使者广敏在《清光绪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序》中更是讲道:
粤稽道统相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迄思孟,燦著于群经。降而下之,荀与杨也,择焉不精,语焉不详,道统于是乎少微矣。紫阳出,数百年坠绪忽焉复振,究其渊源,则延平先生所传也。先生得濂洛正派,即绍洙泗真传。
综合上述可知,从宋代开始推崇李延平和朱子的门人学者都非常重视他们二人的师承关系与学术渊源,而且到明清之际以及整个清时期,更是将李、朱二人的师承与学术源流从上追溯至二程及周濂溪,亦即从“道南学派”上溯到整个“道统”,并且将朱子的地位从“道南真传”提升至得“道统正宗”,这固然与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有关,然其中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何在?这要联系明清之际的整个学术史环境来考察。
因行文关系,将此点放到后面论述。
三、从序跋看《延平答问》是一部怎样的书
我们知道,《延平答问》是朱子辑录了他与老师李延平之间平日论学往来的书信。至于辑订的初衷,历来都认为该书就是一本老师与学生之间普通的学习问答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较明确说《延平答问》是“书札往来问答”“后朱子辑而录之”。另外,从《延平答问》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的书名也可窥见一斑,《延平答问》从朱子辑订时起就未曾明确书的名称,如《朱文公文集》中有一处以“延平先生语录”而作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称“延平问答”、“延平李先生答问”、“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延平语”等。其实,这提法在《延平答问》历代刻本的序跋中也多有提及,明弘治间(1488~1505)周木在他所刻本《延平答问序》的开头就说:“《延平答问》者,子朱子述其师延平李先生答其平日之问,以明其传之有自也。”明正德间(1506~1521)李习(李侗裔孙)在他所刻本《延平答问跋》中也说:“紫阳朱夫子受学于老祖文靖公之门,尝以平日答问要语编录成书,流布天下。”周木与李习二人都认为《延平答问》是李、朱二人的“平日答问”。总之,对于《延平答问》一书的性质都普遍认为属于“问答”类的书。
但到后来特别是明末清初时,学者对于《延平答问》书的性质(即属何类书)有了新的观点和提法,将《延平答问》提升为一本传授“心法”的书,明万历间(1573~1620)的熊尚文在他所刻《延平答问序》中首次提出这样的观点,只是他用了“心传”一词,他说:“庶先生平日所得于豫章,而紫阳氏所藉以演心传于万祀者,是集稍觇一斑矣。”至清代,就都比较普遍的认同甚至推崇这种说法。康熙间(1662-1722)延平知府周元文在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序》中说:“程子曰:‘《中庸》一书,乃也氏传授心法。’则是书(指《延平答问》)也,其即紫阳所受之心法欤?”周氏之里正式使用“心法”一词,并且将《延平答问》与《中庸》并提,其寓意可见一斑。与周元文同时的南平县知县邓炎在同本的《延平答问跋》中亦说:“而《答问》一编,则李、朱二夫子传授心法,其讲学精奥,洵继往开来,不容泯没者也。”此后继承“心法”说的还有乾隆间(1736~1795)钟紫帏补刻本《延平答问跋》中说:“因忆《延平答问》一书,乃朱子授受衣钵。”光绪二年(1876)延平知府张其曜在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跋》开头说“《延平答问》一书,先儒所授受,实后学之法程,凡以阐明斯道者,无微不显。”光绪五年(1879)知延平府事的张国正在同本《延平答问序》中更是提“圣贤心法”,他说:“《延平答问》者,子朱子辑其师延平李先生平日传授之言,盖圣贤心法也。”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自明末首提“紫阳演心传”,到“紫阳受心法”、“朱子授受衣钵”、“先儒授受法程”,到最后的“圣贤之心法”,足以证明《延平答问》在明末清初及清以后的理学乃至儒学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与推崇,当然这与当时朱子地位的再次得到提升与推崇以及明清之际的学术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从序跋看明清之际朱子学地位的再提升
综合上文所述,从《延平答问》历代刻本的序跋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讯息,即在明清之际,朱子学学者们以传刻《延平答问》作为捍卫朱子及其理学地位的形式,使之不至于在“心学”兴起的浪潮中衰微。《延平答问》各序跋的作者将朱子的师承渊源追溯至周濂溪,并且推崇朱子为“道南学派”乃至整个“道统”流传的“正宗”与关键人物;更甚者是将《延平答问》这样的师生间“答问往来书札”尊奉为“圣贤之心法”。固然一本书的作用不会很大,但放于当时的思想和学术环境,且又是朱子亲自辑订的书,是具有重要的时代与学术(特别对于程朱理学来讲)意义的。当然,这种提升的过程是漫长的,凝结着诸多尊崇程朱学者的心血。究其原因,就必定会联系到明清之际那场重要的学术变迁运动。
首先,当时尊程朱学者极力抬升朱子地位及推崇《延平答问》为“心法”之书,与“阳明学”的盛行成为“显学”而“朱子学”的衰微有关。在明代的前中期,因明王朝的“定朱学于一尊”的举措,朱子理学仍然处于思想学术的统治地位,但也是从明代初期开始,朱子理学的发展有了心学化的趋向。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陈献章与湛若水二人,但最终集心学之大成的就是王阳明,他一开始也尊奉程朱,后来“龙场悟道”并逐渐形成了以“心”为中心的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赢得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而盛行。相反,在这一时期,朱子学虽还是统治之学,但由于心学的兴起而声势锐减变得衰微不堪。当然,这里面有朱子学自身理论与实践上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张岂之曾概括为:“一是明政府一方面‘定朱学于一尊’,而在实际层面却从一己私利出发,采取极端不合理的措施;二是朱学在‘格外在之物与伦理实践’之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三是朱学自身的流变呈现出注重居敬躬行、心上理会的向里工夫,即有向心学接近与注重心学的趋向。”也与当时一批尊朱子学的学者的思想认识变化有关。如薛瑄就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在他看来,朱子学不再是一种需要研究的思想形态,而只是一种只要进行道德实践即可类似与准宗教性的信仰体系。然鉴于当时这种学术环境,明清之际的一批坚守朱子学学者、士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受当时普遍流行心学及心法之类伦说的启发,一方面将朱子作为从“道南之传”抬升至接续整个“道学”继承人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是将《延平答问》作为整个理学以及道学的传授心诀而尊为“心法”,旨在推动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广泛传播,抬升与巩固朱子学的统治地位。
其次,在明末清初的那场思想变动中,尊崇朱子学并努力维护他们的影响和地位的,就不得不提到顾宪成、高攀龙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东林学派。上面曾提到,朱子学经南宋以后的兴盛,到明代已逐渐衰微,被阳明学的兴盛所冲击。但正如历史一样有盛必有衰,等到了王阳明去世后,阳明学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并暴露出了心学的弊端,从而就出现了学术上的反动。而顾宪成、高攀龙等在此时“广邀同道,集会讲学”并以东林书院为中心“传播学术、评议时政”,形成了具有独特思想特征的东林学派。从东林学派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自始自终是“学宗程朱”的,朱文杰说:“东林学派为儒家的正统学派,他们恪守程朱正宗。”而且与“濂洛关闽”之学有着渊源关系,其中当属周敦颐影响最大。当然,有学者认为顾、高等东林学派人是从“王学”向“朱学”的回归的学派,如陈时龙说:“东林学派源出于心学但代表了向程朱学回归的趋向的学派。”陈祖武在《顾炎武评传》中也说:“在晚明学术界,顾宪成、高攀龙以向朱学的回归,试图重振没落的理学。”但就是这种“回归”,为朱子学以及朱子地位的再次提升创造了有益的思想条件和学术环境。另一方面,始终坚守朱子学的学者也受到东林学派“崇朱辟王”的激励,积极而广泛地通过刊刻一些朱子的书籍来进一步宣传朱子学,并提升朱子在理学乃至整个道统上的地位。这可以从上述的自明末至清代《延平答问》的多个刻本,以及各刻本序跋中对于朱子师承渊源的抬升,将《延平答问》视为理学及整个道统的“圣贤心法”,就可以略见一二。
总之,《延平答问》一经问世,历代的刻本及为之作序跋者不在少数,特别是明末清初以及整个清代属最多。更有甚者,许多尊崇朱子学的学者借助于当时的学术流变,将《延平答问》看作理学乃至整个道统所传授的“圣贤之心法”,进一步明确与提升了李侗在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也维护了朱子作为道统的正宗传承人地位。从而,使朱子学在被“心学”的兴盛而一度消沉后,又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和能量,回归到正统的“显学”的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作者系江西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
附注
朱子从游李延平的时间,若从其绍兴二十三年(1153)始见算起到李延平隆兴元年(1163)去世,前后共有十年之久。
赵师夏:《延平答问序跋》,《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周亮工:《李延平先生文集序》,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朱熹与闽学渊源》,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上),桂林:文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朱文杰:《吴桂森和他的(息斋笔记)》,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东林学术研讨会论文资料选》,1998年。
陈时龙:《晚明书院结群现象研究——东林书院网络的构成、宗旨与形成》,《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
陈祖武:《顾炎武评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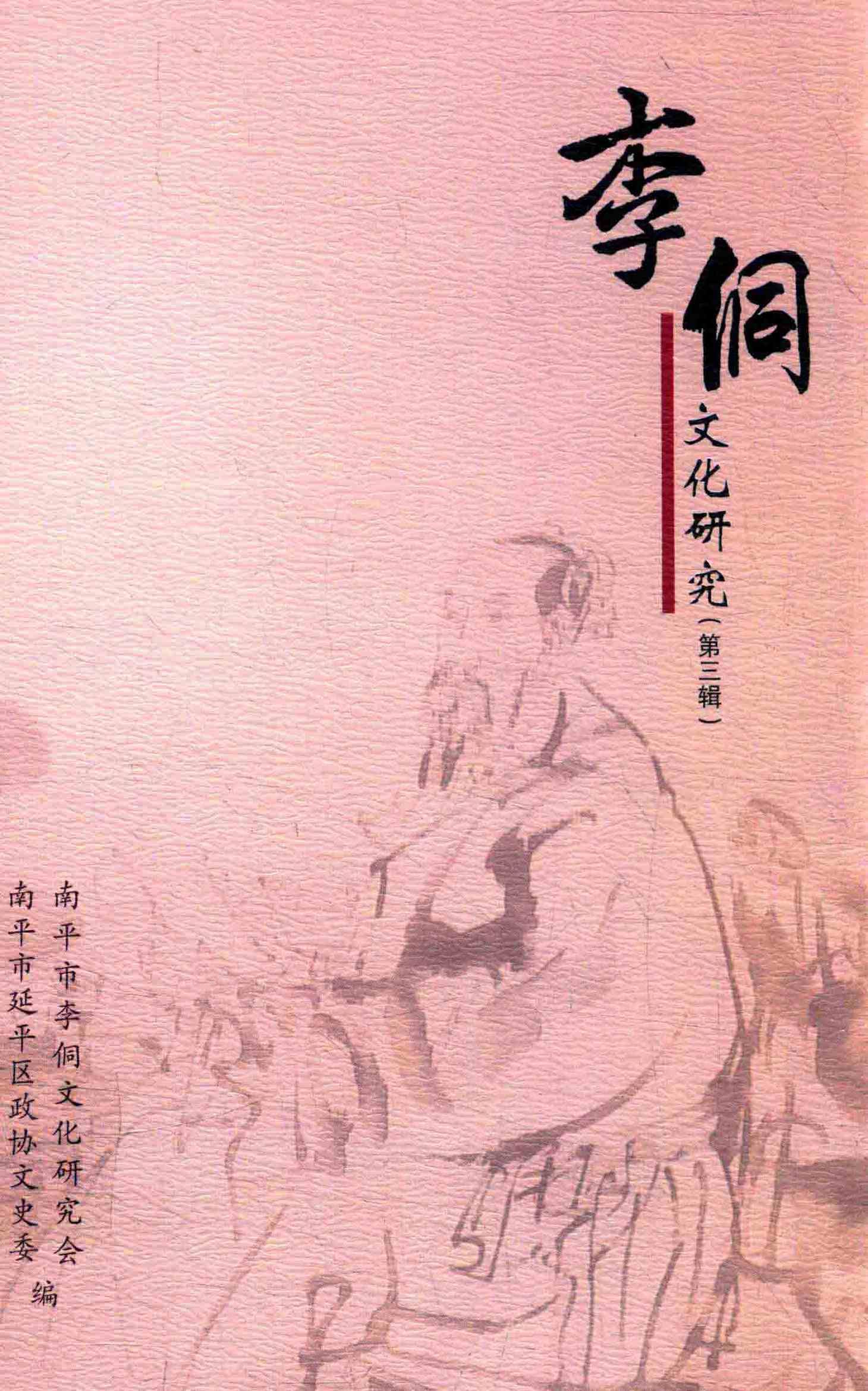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
相关人物
胡泉雨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李侗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