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延平答问:儒学新路向的肇端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318 |
| 颗粒名称: | 二、延平答问:儒学新路向的肇端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16 |
| 页码: | 147-162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记述了朱子拜李延平为师,朱子儒佛公案的结束。所以说,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成为整个朱子世界及其理论创造活动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了。这样一来,可以说对象化的视角、具体的事理关怀以及实然世界的背景,也就必然蕴含着朱子的一条探索儒学、推进儒学的新思路。 |
| 关键词: | 李侗 朱子 儒学 |
内容
拜李延平为师,固然标志着朱子儒佛公案的结束,但对于真正的为己之学来说,却又不过是一个初始的入门。由于朱子异常勤奋,此前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读书学习方面的经验,也积累了不少的相关学理性的知识,因而在拜延平为师之后,他也就必然要经历一个疏导、滤汰与重新拣择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在他感到延平自有其真、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基础时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由他所编订的《延平答问》就上起于丁丑年(朱子二十八岁),一直到癸未年(朱子三十四岁)延平去世。而这些答问,实际上也就成为延平在其一生的最后七年间与朱子所展开的一种思想交流与学术对话了。所以,在《延平答问》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延平的为学进路与思想规模,而且也能看出朱子对延平的理解以及其为学规模之逐渐地形成。也就是说,在从丁丑到癸未这七年间,延平与朱子二人的思想状况,大体也就表现在《延平答问》一书中。
关于《延平答问》的研究情况,如果以笔者所见为限,那么自然应当首推牟宗三先生的梳理与诠释最为精辟透彻,尤其是其关于延平思想体系之“超越的体证”、“日用身心的落实”以及“默坐澄心”之具体入手这三个关键环节的分析,本身也就足以撑开延平的整个思想构架与为学规模了;至于其关于孟子“终始条理”的诠释,虽然也是顺着延平的思路展开的,但又远远超过了延平本人的思想构架,而具有对整个儒家心性之学之智慧形态及其普遍性、共通性意义的揭示意味。但由于牟先生煌煌三大巨册的《心体与性体》首先是以梳理整个理学的发展脉略与总体走向为目标的,而其第三册虽然也以朱子为核心,但其走向又是以对朱子之“别子为宗”的定性为方向的。这样一来,虽然他也细致地梳理了延平的思想构架,并且也不断地以《论》、《孟》、《庸》、《易》充实之,但却是将其作为裁定朱子之“别子为宗”的文本依据与超越的标准来运用的。这样一来,朱子就不再是思想的主体,而仅仅成为其所需要裁定、需要批评的对象了。刘述先先生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固然是将整个《延平答问》纳入到“朱子从学延平的经过”这一具体的过程中来考察的,并且尽量以“同情的心态”来理解朱子,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牟先生完全将朱子对象化、裁定化的缺弱。但由于刘先生的整体思路仍然是以牟先生为准的,所以,虽然其关于朱子之史实、史料的考订更为精详,过程的梳理也更为细致,但对于朱子之思想主体的地位以及其为学新思路之萌芽仍然关注不够。
有鉴于此,笔者关于《延平答问》的分析将不再聚焦于延平思路本身的澄清,因为关于这一方面的看法笔者并无超过牟宗三之处,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先将其作为分析朱子思想之总体背景加以悬置(当然必要时也会加以征引)。除此之外,关于“朱子从学延平”的具体经过,笔者也并不比刘述先先生知道得更多,所以这里特意将刘先生对“朱子从学延平的经过”之梳理作为基础,然后再逐层展开对朱子思路的分析。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首先能够还原出朱子在这一过程中之思想主体的地位,虽然就“答问”这种形式而言,朱子无疑是请教者,而延平才是“答问”的主体,但反过来看,朱子毕竟又是提问者;而在朱子之“问”及其对延平之“答”的理解中,显然已经有一种新的为学思路隐然贯注其中。其次,虽然笔者也承认朱子与延平在基本思路上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并且将这一分歧作为把握朱子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但笔者分析的重心将主要放在对朱子新思路之澄清与凸显上。这也就是笔者特别以“儒学新路向的肇端”来命名这一节的主要缘由。
由此出发,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在朱子“师事”延平之前,其不同的为学进路或者说其对儒家学理的理解就已经形成自己的基本思路了。所以,其与延平关于“孝亲”、“起予”与“体用”等关系的问答与辨析,也就已经表现出了不同为学进路的端绪。比如:
问:“‘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东坡谓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使事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此可见孝子之心,与‘几谏’事亦相类。”
先生曰:“‘三年无改’,前辈论之详矣。类皆执文泥迹,有所迁就,失之。须是认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所谓道者,是犹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过,若稍稍有不惬意处,即率意改之,则孝子之心何在。……东坡之语有所激而然,是亦有意也。事只有个可与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处,自应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隐忍迁就,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此意虽未有害,第恐处心如此,即骎骎然所失处却多。吾辈欲求寡过,且仅守格法为不差也。‘几谏’事亦恐不相类,更思之。”
问:“向以‘亦足以发’之义求教,因引‘起予’为证,蒙批谕云,‘亦足以发’与‘起予’不类。熹反复思之,于此二者,但见有浅深之异,而未见全不相似处,乞赐详喻。”
先生曰:“颜子气象与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气象于胸中,然后体会夫子之言‘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之语气象如何。颜子沉潜淳粹,于圣人体段已具,故闻夫子之言,即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则于语默日用动容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也。子夏因问《诗》,如不得‘绘事后素’之言,即‘礼后’之意未必到,似有因问此一事,而夫子印可之意。此所以不类也,不知是如此否?偶追忆前日所问处,意不来,又未知向日因如何疑而及此也,更俟他日熟论。”
问“礼之用,和为贵”一章之义。
先生曰:“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礼之道,虽以和为贵,然必须体其源流之所自来而节文之,则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无隆杀之辨;‘知和而和’,于节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则礼之体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礼之严至拘碍者、和而失其节者,皆非知礼者也。故有子以是语门人,使知其节尔。”
这里首先要请读者原谅这一大段过长的引文。因为这三段问答不仅表现了延平对儒家学理的准确把握,而且也表现着其细致入微的理论辨析能力;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三问本身又典型地表现出朱子把握问题的基本视角和主要方法。比如关于孝亲之“三年无改于父道”的问题,朱子首先是将其作为一种客观而又必须合宜的事理来探讨的,所以他认为应当与“事父母几谏”属于同样的道理;而其之所以提出要“隐忍迁就”,也主要是为了外在的“合宜”,从而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但在延平看来,所谓“三年无改于父道”实际上首先是一个仁人孝子的孝亲之心以及其“忍与不忍”的问题,但这一孝亲之心同时也必然有其“可与不可”之超越维度的依据和标准,所以说“若大段有害处,自应即改何疑”。——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即为仁的原则;而这一原则与作为其具体落实或具体表现的“几谏”本身就不在同一层面。朱子视二者为“相类”,说明他已经将超越的原则与作为具体落实之“合宜”的标准一律作为外在世界中平列的事理来对比了,因而恰恰忽略了其相互内在本质上的差别。至于“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也是同样的关系。虽然朱子已“蒙批谕”并且也经过反复的思索,但他仍然认为“见有浅深之异,而未见全不相似处”,这说明他确实没有看到二者在本质上的差别,所以延平也就不得不明确指出,颜子是“于圣人体段已具”,其“默识心通”“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而子夏则不过是一种“偶及”或“误中”而已,至于其真实的基础,恐怕连“‘礼后’之意未必到”,这样一来,二者自然也就成为根本“不类”的关系了。朱子之所以不断地犯这种“不类”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将儒家做人的道理对象化、事理化了,从而总是作为一种平面的、等值的外在事理来推寻。正因为其将人生道理外在化、对象化复又平面化,所以他自然看不出其间的本质差别,从而又存在着将所有的事理都加以平面化、等值化之嫌,这也正是其不断地犯“不类”之过的原因。
关于礼之“和为贵”的问题,朱子也同样是将其作为一种外在的“合宜”标准来探讨的,所以延平也就必须先以“隆杀之辨”将其双向撑开,并明确指出其“‘知和而和’,于节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因为对儒学而言,礼虽然有“和”的作用,但却绝不是为了“和”而和,更不是因为有“和”的需要才制礼作乐的,如果只看到“和”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体其源流”,就必然会导致“礼之体用”两失的弊端此外再如:
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记孔子事,又记孔子之言于下以发明之,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也。
先生曰:“某尝闻罗先生:‘祭如在,及见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见之者’以至诚之意与鬼神交,庶几享之若诚心不至,于礼有失焉,则神不享矣,虽祭也何为!”
显然,在这里,朱子只将“祭如在”理解为一个文理连接之表达技巧的问题,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场景描述的问题,但在延平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表达技巧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外在的场景描述问题,而首先是一个主体诚敬之心足与不足的问题,不仅如此,“祭”的本质也就在于要不断地扩充其主体的诚敬之心,——由“见之者”及于“不及见之者”。如果只看到表达技巧或场景描述的层面,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也没有看到其关键所在,所以在这里,延平也就必须以重言的方式提醒朱子:“若诚心不至,于礼有失焉,则神不享矣,虽祭也何为!”
上述几段,大体上都是出于庚辰以前的书札,而朱子发问之最鲜明的特征,也就在于他比较关注语言文字之间的文理表达问题,进而关注外在事理的层面,以期达到事事“合宜”的目的,但他却没有注意到所谓孝心以及礼仪之内在根源及其超越维度的依据问题。所以,直到己卯年(朱子三十岁),延平仍然催书朱子,并明确地提醒他说:“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对于延平来说,如果朱子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不足,他当然无须对朱子说这样的话;但对于朱子来说,这却可能就是来自师长辈之最为重要的敲打与提撕了。因为如果没有对儒家超越而又内在——所谓体用两层世世界以及其纵向立体关系的准确把握,只牵制于语言文字之间,或者只关心所谓外在节目时序之如何“合宜”的问题,那么这样的理解思路,说到底也就不过是星星点点的“偶及”或“误中”而已。
庚辰年以后,朱子与延平的答问显然进了一层,而延平也屡屡提醒朱子,比如:“示谕夜气说甚详,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节寻求,即恐有差。大凡吾辈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虑一澄然之时,略绰一见于心会处,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滞碍”。此段延平并没有征引朱子关于夜气说的具体理解,应当说大概理路已经不差,但延平对朱子“不可更生枝节寻求”的叮咛,显然是针对其喜欢从语言文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关的。再比如:“承谕心与气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会心与气,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会融释,不如此,不见所谓气、所谓心,浑然一体流浃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别那个是心,那个是气,即劳攘尔。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语病无疑。若更非是,无惜劲论,吾侪正要如此。”凡此,当然都是延平对朱子在理解思路上的敲打提撕,而从这些提撕来看,大概延平也发现朱子喜欢进行具体细节包括从所谓语言文理方面进行分析,由于这种分析往往存在着节外生枝的可能,且常常陷于“不类”的境地,所以延平明确地提醒他“不可更生枝节寻求”、“若更分别那个是心,那个是气,即劳攘尔”,而应当全力去把握心与气之所谓“浑然一体流浃也”。
除此之外,延平还经常以他自己早年的从学经历来提醒朱子。比如:
某自少年从罗先生问学,彼时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闻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静处寻求。至今淟汩忧患,磨灭甚矣。四五十年间,每于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尝忘废,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无进步处。常切静坐思之,疑于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焉。向来尝与夏丈言语间稍无间,因得一次举此意质之,渠乃以释氏之语来相淘,终有纤奸打讹处,全不是吾儒气味,旨意大段各别,当俟他日相见剧论可知。大率今人与古人学殊不同。……元晦更潜心于此,勿以老迈为戒,而怠于此道。……盖弟子形容圣人,有所难言尔。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谓发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圣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圣人。此三句只好浑然作一气象看,则见圣人浑是道理,不见有身世之碍,故不知老之将至尔。元晦更以此意推广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极际气象,终是难形容也。……故孔子不居,因事而见尔。若常以不居其圣横在肚里,则非所以言圣人矣。如何如何?
这两段可以说是延平对朱子的具体指点,前者在于通过“默坐澄心”以时时返归于自己的“初心”(即后来象山所谓的“发明本心”),尤其是“每于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掇”、“疑于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焉”,这当然都是具体的反省,亦即所谓“默坐澄心”的工夫;而后者则主要在于形容圣人气象,批评朱子所谓“发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并明确指出“圣人自道理中流出”、“圣人浑是道理,不见有身世之碍”,所以不能仅仅以所谓“求道之切”来形容圣人的“发愤忘食”;更不能先将所谓“不居其圣”作为一种客观外在的标准“横在肚里”。因为如此一来,也就“非所以言圣人矣”,——即既不足以揭示圣人之与道理的浑一无间,更不足以体贴圣人之“浑是道理”的气象了。所有这些话头,当然都是提撕、指点朱子之意,至于朱子能否真正由“默坐澄心”返归于自己的“初心”,能否由“圣人自道理中流出”而更加体味“圣人与我同类”的道理,从而达到所谓“不见有身世之碍”的地步,则确实很难说、但从延平的这些叮咛提撕来看,则正可以反证朱子其时对“圣人”之对象化理解与“澄心”之事理化推究的理解方式。
随着交往的增多,延平对朱子在为学路径上的不足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书扎问答中,延平也就时时提及朱子在这些方面的缺弱,要他注意扭转。比如: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书云:……若欲进此学,须是尽放弃平日习气,更鞭饬所不及处,使之脱然有自得处,始是道理少进。承谕应接少暇即体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觉之效,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无惜详及,庶几彼此得以自警也。壬午五月十四日书云:承谕处事扰扰,便似内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从这些问答来看,延平所见不可谓不准,其考虑也不可谓不细。比如像“须是尽放弃平日习气,更鞭饬所不及处”以及对朱子自我检讨的所谓“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与“此乃知觉之效”等等敲打,都说明延平对朱子当时的状态看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更重要的是,延平还时时根据朱子的自我描述,给他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治方法,比如“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等等,也都是就具体的工夫进路而言的。但朱子当时却固执于自己的“旧习”,从而也就仍将延平这种指点工夫进路的话语仅仅作为一场学理来推究了。从这一点来看,朱子确实有负其师之命。
能够为这一看法提供佐证的是,《答薛仕龙》与《答江元适》都是朱子受学于延平时的书札;而在这些书札中,每当朱子受到批评或“困而自悔”时,他当然也会反省,但他的反省却往往是这样展开的:
熹自少愚钝,事事不能及人,顾常侧闻先生君子之余教,粗知有志于学……比乃困而自悔,始复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而亦未有闻也。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显然,所谓“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以及其反省的所谓“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等等,其实也都是在朱子深感为学不进的情况下出现的,自然也都代表着朱子的某种“反省”;而其具体的落实表现,则又只是所谓“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无怪乎他感觉自己是“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因为他的这种“反省”实际上只是对“句读文义”的反思,充其量也只是对自己“视听言动”的再掂量,根本就没有进入到所谓“初心”或“本心”的层面。当然,这也表现出朱子一贯的学习方法,——他确实对“句读文义”与“知识章句”比较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牟宗三就径直批评他根本是文不对题,根本不理解延平的思路。牟先生分析说:
延平所说的“体用合”,“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是着重在由超越体证之抽象状态达至日用处(分殊处)之具体呈现。但朱子后来所常说至日用处下工夫,却是着重在下学上达,与日用处理会道理、致知格物,此即丧失延平实体之具体呈现义(由体达用)之纵贯义。
……但延平之说此语,吾想却是根据其“体用合”,“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而来,而朱子却只重在日用处之认知的意义。同是“日用处”,它可指点到践履上通体达用,道之具体呈现,道在眼前,此所谓“日用处熟”;它也可以指点到知解上就日用处下学上达,格物致知。此是一个交叉路口,而朱子却偏重在后者。
……此即是将“日用处”之平实、切实,只转向下学上达、致知格物处讲,只成为认知意义的平实、切实。此是“静神养气”之静涵静摄系统下之平实切实。
牟宗三的这些批评,当然都是一种超越的解析,其用语虽然严厉,但在点破朱子将道德实践语境下道德理性之纵贯落实义扭转为平列的认知积累义方面,我们却不能不佩服其将问题看得准确,看得透彻。
此后,朱子与延平的两段对话即表现了朱子的为学进境,而延平的叮咛提携也同样表现了其对理论问题的敏锐与警觉:
先生曰:谢上蔡云:“‘吾尝习忘以养生。’明道曰:‘施之养则可,于道则有害。习忘可以养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学道则异于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谓乎?且出入起居,宁无事者?正心待之,则先事而迎,忘则涉乎去念,助则近于留情。故圣人心如鉴,所以异于释氏心也。”上蔡录明道此语,于学者甚有力。盖寻常于静处体认下工夫,即于闹处使不著,盖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谢先生确实于日用处便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事上作工夫学。)即恐明道此语亦未必引得出来。此语录所以极好玩索,近方看见如此意思显然。元晦于此更思看如何?唯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某辄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问:熹又问《孟子》“养气”一章,向者虽蒙曲折面诲,而愚意竟未见一总会处,近日求之,颇见大体,只是要得心气合而已。故说“持其志,无暴其气”,“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皆是紧切处。只是要得这里所存主处分明,则一身之气,自然一时奔凑翕聚,向这里来……
先生曰: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不然,心是心,气是气,不见所谓集义处,终不能合一也……然心气合一之象,更用体察,令分晓路脉方是。某寻常觉得于畔援心羡之时,未必皆是正理,亦心与气合,到此若仿佛有此气象,一差则所失多矣、其所谓浩然之气耶!某窃谓孟子所谓养气者,自有一端绪,须从知言处养来,乃不差。
这两段对话实际上都是从现实的日用工夫出发以直接指向超越的体证而言的。上一段从“习忘”与“养生”的关系出发引入儒家的“养心”与“养志”,而以孟子的“勿忘勿助”为标准,并要求将其落实于日用工夫之间;其特别警策之处在于“唯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这就成为一种理论思辩的工夫了。所以,儒家所谓日用处工夫主要是指将道德理性落实于日用事为间而言的。下一段则主要在于分析如何理解孟子的“养气”,朱子能够理解到养气就是要心与气合,所以有所谓“这里所存主处分明,则一身之气,自然一时奔凑翕聚,向这里来”,对于这一理解,延平当然感到高兴。但延平的提醒则在于:所谓“于畔援心羡之时……亦心与气合”,但却“未必皆是正理”。所以,所谓心与气合,并不是要合心于气、合理于欲,也不是二者的浑沦不分,而是必须合气于心、合欲于理;这样一种方向,其实也就是孟子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所以延平说必须从孟子的“知言”养来,方无大差,不然的话,就极有可能会成为所谓心随气走、志随气转的物欲横流了。
对于延平的立场、观点及其基本思路,我们这里已经无需多言,因为已经有牟宗三、刘述先两位先生的细致分析与准确把握在前了,——仅从其对朱子之反复的叮咛提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气象。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朱子,从朱子与延平的这一系列问答以及延平对朱子的叮咛提撕中能够表现出朱子的何种气象呢?因为从“师事”延平起,朱子就已经三十出头,其理智也大体成熟;仅从其读书学习——“业儒”及其所受的熏陶来看,也已经超过二十年,——起码已经积累了多年的读书学习经验。在这种条件下,其具体观点当然是可以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其认知世界、把握事物的视角与方法则大体上已经定型了。那么,从《延平答问》中,我们究竟能够看出朱子那些比较稳定的因素呢?
首先,由于朱子很早就以“业儒”自期,而在他的成长经历中,所谓“业儒”也就主要表现为读书学习,又由于朱子异常勤奋、顽强,因而其学习也就更多地致力于所谓“文理密察”一面,延平之所以提醒他“于言外求意乃通”,并不断地批评他的思考是“不类”,就是因为他把文本把得太死,把文理看得太重。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就已经决定了他对文本世界的对象性视角;而从具体认知的角度看,他又严格地杜绝自我体究式的主体介入方式,从而也就排除了主体与文本“融液一体”之可能。仅从其对圣人“发愤忘食”之“求道之切”的理解中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从对象的角度来“打量”圣人而不是真正以自我介入的方式来“体贴”圣人的。如果说宋明理学中就只有这一种进路,那我们自然无从比较;但如果我们将其与王阳明稍加比较,则朱子为学进路的这一对象性特点就显得格外分明。请看王阳明是如何学习书法的:
先生尝示学者曰:“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凝思静虑,抑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物,多举此为证。
这显然是“用心”型的学习。如果我们将这种“用心”型的学习与朱子稍加比较,那么朱子显然是属于“用脑”型的学习。王阳明这种“用心”型的学习方法固然并不万能,并且也有其局限性,但这种方法却能够使“我”与古帖以及我之心与手迅速地融液一体,而朱子却不仅要自觉地将“我”与圣人分开,而且还要将圣人与道理分开,——圣人也不过是“发愤忘食”、“求道之切”而已。如此一来,所谓文本也就真正成为他的对象世界了。
其次,在朱子与延平这一长达数年的“对话”中,朱子又典型地表现出其对由文本所蕴含的“事理”之特别关注的兴趣,他之所以常常陶醉于文本与文理的世界,不惜在上下文之间强行索解以至于旁征博引地加以说明,因而屡屡被延平批评为“不类”,不能“于言外求意”,一方面说明他确实对作为对象之文本世界把的特别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对象世界往往是以“平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之所以常常陷入“不类”的比喻,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对象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平面,其所谓万事一理、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的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从平面的视角展开的。那么,世界本身的立体性哪里去了呢?此则更有原因,待讨论思想谱系时再具体说明,但就其对“事理”之特别关注以及其完全将对象世界平面化而言,则又确实是朱子在与延平“对话”中的一大特点。
再次,在《延平答问》中,朱子所有的问题都隐然含括了一个既存在于主体之外同时又包括主体于其中的所谓客观世界,而朱子本人、包括所有的人其实都既是这一世界的认知者与揭示者,同时又始终是这一世界发展的产物与具体的参与者。对于这样一个总体背景,牟宗三常常以“朴素实在论”视之,而大陆学界则常常将其定位为客观唯心主义,其实这都存在着简单类比之过,究其原因,则主要集中在朱子对这一“客观世界”的肯定与承认上。我们这里暂且不管其客观世界的形成以及其如何才能成立的问题,但在朱子的思路中,这一世界的客观存在却一直是他,包括所有人的认知活动得以存在、得以发展的前提基础这一点却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所以说,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成为整个朱子世界及其理论创造活动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了。这样一来,可以说对象化的视角、具体的事理关怀以及实然世界的背景,也就必然蕴含着朱子的一条探索儒学、推进儒学的新思路。
在朱子看来,只要这个世界不会改变,那么其探索世界的进路与方法也就不会改变;而对李延平来说,虽然他也极为认真地指点朱子、提撕朱子,但只要朱子这一“世界”的规模与性质不会改变,那么延平对朱子所有的指点、提撕也就极有可能会陷于“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的格局。就是说,只要其“世界”的规模与性质是确定的,那么其对这个世界的研究与诠释进路也就必然是确定的。可惜延平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理论视野,因而他也无法看到人由自身的习惯性经验所自发形成之背景世界的力量,这也就使得他的指点、提撕只具有文献解读或工夫修养——所谓涵养的意义,而根本无法触动朱子,无法改变朱子的“世界”。当然,这同时也就在宋明理学中留下了或者说存在着开辟一个新世界之可能,所有这些,又将随着朱子在理论探讨上的不断发展与不断成长而逐渐明晰起来。
关于《延平答问》的研究情况,如果以笔者所见为限,那么自然应当首推牟宗三先生的梳理与诠释最为精辟透彻,尤其是其关于延平思想体系之“超越的体证”、“日用身心的落实”以及“默坐澄心”之具体入手这三个关键环节的分析,本身也就足以撑开延平的整个思想构架与为学规模了;至于其关于孟子“终始条理”的诠释,虽然也是顺着延平的思路展开的,但又远远超过了延平本人的思想构架,而具有对整个儒家心性之学之智慧形态及其普遍性、共通性意义的揭示意味。但由于牟先生煌煌三大巨册的《心体与性体》首先是以梳理整个理学的发展脉略与总体走向为目标的,而其第三册虽然也以朱子为核心,但其走向又是以对朱子之“别子为宗”的定性为方向的。这样一来,虽然他也细致地梳理了延平的思想构架,并且也不断地以《论》、《孟》、《庸》、《易》充实之,但却是将其作为裁定朱子之“别子为宗”的文本依据与超越的标准来运用的。这样一来,朱子就不再是思想的主体,而仅仅成为其所需要裁定、需要批评的对象了。刘述先先生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固然是将整个《延平答问》纳入到“朱子从学延平的经过”这一具体的过程中来考察的,并且尽量以“同情的心态”来理解朱子,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牟先生完全将朱子对象化、裁定化的缺弱。但由于刘先生的整体思路仍然是以牟先生为准的,所以,虽然其关于朱子之史实、史料的考订更为精详,过程的梳理也更为细致,但对于朱子之思想主体的地位以及其为学新思路之萌芽仍然关注不够。
有鉴于此,笔者关于《延平答问》的分析将不再聚焦于延平思路本身的澄清,因为关于这一方面的看法笔者并无超过牟宗三之处,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先将其作为分析朱子思想之总体背景加以悬置(当然必要时也会加以征引)。除此之外,关于“朱子从学延平”的具体经过,笔者也并不比刘述先先生知道得更多,所以这里特意将刘先生对“朱子从学延平的经过”之梳理作为基础,然后再逐层展开对朱子思路的分析。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首先能够还原出朱子在这一过程中之思想主体的地位,虽然就“答问”这种形式而言,朱子无疑是请教者,而延平才是“答问”的主体,但反过来看,朱子毕竟又是提问者;而在朱子之“问”及其对延平之“答”的理解中,显然已经有一种新的为学思路隐然贯注其中。其次,虽然笔者也承认朱子与延平在基本思路上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并且将这一分歧作为把握朱子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但笔者分析的重心将主要放在对朱子新思路之澄清与凸显上。这也就是笔者特别以“儒学新路向的肇端”来命名这一节的主要缘由。
由此出发,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在朱子“师事”延平之前,其不同的为学进路或者说其对儒家学理的理解就已经形成自己的基本思路了。所以,其与延平关于“孝亲”、“起予”与“体用”等关系的问答与辨析,也就已经表现出了不同为学进路的端绪。比如:
问:“‘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东坡谓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使事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此可见孝子之心,与‘几谏’事亦相类。”
先生曰:“‘三年无改’,前辈论之详矣。类皆执文泥迹,有所迁就,失之。须是认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所谓道者,是犹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过,若稍稍有不惬意处,即率意改之,则孝子之心何在。……东坡之语有所激而然,是亦有意也。事只有个可与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处,自应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隐忍迁就,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此意虽未有害,第恐处心如此,即骎骎然所失处却多。吾辈欲求寡过,且仅守格法为不差也。‘几谏’事亦恐不相类,更思之。”
问:“向以‘亦足以发’之义求教,因引‘起予’为证,蒙批谕云,‘亦足以发’与‘起予’不类。熹反复思之,于此二者,但见有浅深之异,而未见全不相似处,乞赐详喻。”
先生曰:“颜子气象与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气象于胸中,然后体会夫子之言‘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之语气象如何。颜子沉潜淳粹,于圣人体段已具,故闻夫子之言,即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则于语默日用动容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也。子夏因问《诗》,如不得‘绘事后素’之言,即‘礼后’之意未必到,似有因问此一事,而夫子印可之意。此所以不类也,不知是如此否?偶追忆前日所问处,意不来,又未知向日因如何疑而及此也,更俟他日熟论。”
问“礼之用,和为贵”一章之义。
先生曰:“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礼之道,虽以和为贵,然必须体其源流之所自来而节文之,则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无隆杀之辨;‘知和而和’,于节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则礼之体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礼之严至拘碍者、和而失其节者,皆非知礼者也。故有子以是语门人,使知其节尔。”
这里首先要请读者原谅这一大段过长的引文。因为这三段问答不仅表现了延平对儒家学理的准确把握,而且也表现着其细致入微的理论辨析能力;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三问本身又典型地表现出朱子把握问题的基本视角和主要方法。比如关于孝亲之“三年无改于父道”的问题,朱子首先是将其作为一种客观而又必须合宜的事理来探讨的,所以他认为应当与“事父母几谏”属于同样的道理;而其之所以提出要“隐忍迁就”,也主要是为了外在的“合宜”,从而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但在延平看来,所谓“三年无改于父道”实际上首先是一个仁人孝子的孝亲之心以及其“忍与不忍”的问题,但这一孝亲之心同时也必然有其“可与不可”之超越维度的依据和标准,所以说“若大段有害处,自应即改何疑”。——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即为仁的原则;而这一原则与作为其具体落实或具体表现的“几谏”本身就不在同一层面。朱子视二者为“相类”,说明他已经将超越的原则与作为具体落实之“合宜”的标准一律作为外在世界中平列的事理来对比了,因而恰恰忽略了其相互内在本质上的差别。至于“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也是同样的关系。虽然朱子已“蒙批谕”并且也经过反复的思索,但他仍然认为“见有浅深之异,而未见全不相似处”,这说明他确实没有看到二者在本质上的差别,所以延平也就不得不明确指出,颜子是“于圣人体段已具”,其“默识心通”“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而子夏则不过是一种“偶及”或“误中”而已,至于其真实的基础,恐怕连“‘礼后’之意未必到”,这样一来,二者自然也就成为根本“不类”的关系了。朱子之所以不断地犯这种“不类”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将儒家做人的道理对象化、事理化了,从而总是作为一种平面的、等值的外在事理来推寻。正因为其将人生道理外在化、对象化复又平面化,所以他自然看不出其间的本质差别,从而又存在着将所有的事理都加以平面化、等值化之嫌,这也正是其不断地犯“不类”之过的原因。
关于礼之“和为贵”的问题,朱子也同样是将其作为一种外在的“合宜”标准来探讨的,所以延平也就必须先以“隆杀之辨”将其双向撑开,并明确指出其“‘知和而和’,于节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因为对儒学而言,礼虽然有“和”的作用,但却绝不是为了“和”而和,更不是因为有“和”的需要才制礼作乐的,如果只看到“和”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体其源流”,就必然会导致“礼之体用”两失的弊端此外再如:
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记孔子事,又记孔子之言于下以发明之,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也。
先生曰:“某尝闻罗先生:‘祭如在,及见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见之者’以至诚之意与鬼神交,庶几享之若诚心不至,于礼有失焉,则神不享矣,虽祭也何为!”
显然,在这里,朱子只将“祭如在”理解为一个文理连接之表达技巧的问题,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场景描述的问题,但在延平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表达技巧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外在的场景描述问题,而首先是一个主体诚敬之心足与不足的问题,不仅如此,“祭”的本质也就在于要不断地扩充其主体的诚敬之心,——由“见之者”及于“不及见之者”。如果只看到表达技巧或场景描述的层面,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也没有看到其关键所在,所以在这里,延平也就必须以重言的方式提醒朱子:“若诚心不至,于礼有失焉,则神不享矣,虽祭也何为!”
上述几段,大体上都是出于庚辰以前的书札,而朱子发问之最鲜明的特征,也就在于他比较关注语言文字之间的文理表达问题,进而关注外在事理的层面,以期达到事事“合宜”的目的,但他却没有注意到所谓孝心以及礼仪之内在根源及其超越维度的依据问题。所以,直到己卯年(朱子三十岁),延平仍然催书朱子,并明确地提醒他说:“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对于延平来说,如果朱子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不足,他当然无须对朱子说这样的话;但对于朱子来说,这却可能就是来自师长辈之最为重要的敲打与提撕了。因为如果没有对儒家超越而又内在——所谓体用两层世世界以及其纵向立体关系的准确把握,只牵制于语言文字之间,或者只关心所谓外在节目时序之如何“合宜”的问题,那么这样的理解思路,说到底也就不过是星星点点的“偶及”或“误中”而已。
庚辰年以后,朱子与延平的答问显然进了一层,而延平也屡屡提醒朱子,比如:“示谕夜气说甚详,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节寻求,即恐有差。大凡吾辈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虑一澄然之时,略绰一见于心会处,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滞碍”。此段延平并没有征引朱子关于夜气说的具体理解,应当说大概理路已经不差,但延平对朱子“不可更生枝节寻求”的叮咛,显然是针对其喜欢从语言文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关的。再比如:“承谕心与气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会心与气,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会融释,不如此,不见所谓气、所谓心,浑然一体流浃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别那个是心,那个是气,即劳攘尔。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语病无疑。若更非是,无惜劲论,吾侪正要如此。”凡此,当然都是延平对朱子在理解思路上的敲打提撕,而从这些提撕来看,大概延平也发现朱子喜欢进行具体细节包括从所谓语言文理方面进行分析,由于这种分析往往存在着节外生枝的可能,且常常陷于“不类”的境地,所以延平明确地提醒他“不可更生枝节寻求”、“若更分别那个是心,那个是气,即劳攘尔”,而应当全力去把握心与气之所谓“浑然一体流浃也”。
除此之外,延平还经常以他自己早年的从学经历来提醒朱子。比如:
某自少年从罗先生问学,彼时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闻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静处寻求。至今淟汩忧患,磨灭甚矣。四五十年间,每于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尝忘废,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无进步处。常切静坐思之,疑于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焉。向来尝与夏丈言语间稍无间,因得一次举此意质之,渠乃以释氏之语来相淘,终有纤奸打讹处,全不是吾儒气味,旨意大段各别,当俟他日相见剧论可知。大率今人与古人学殊不同。……元晦更潜心于此,勿以老迈为戒,而怠于此道。……盖弟子形容圣人,有所难言尔。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谓发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圣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圣人。此三句只好浑然作一气象看,则见圣人浑是道理,不见有身世之碍,故不知老之将至尔。元晦更以此意推广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极际气象,终是难形容也。……故孔子不居,因事而见尔。若常以不居其圣横在肚里,则非所以言圣人矣。如何如何?
这两段可以说是延平对朱子的具体指点,前者在于通过“默坐澄心”以时时返归于自己的“初心”(即后来象山所谓的“发明本心”),尤其是“每于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掇”、“疑于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焉”,这当然都是具体的反省,亦即所谓“默坐澄心”的工夫;而后者则主要在于形容圣人气象,批评朱子所谓“发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并明确指出“圣人自道理中流出”、“圣人浑是道理,不见有身世之碍”,所以不能仅仅以所谓“求道之切”来形容圣人的“发愤忘食”;更不能先将所谓“不居其圣”作为一种客观外在的标准“横在肚里”。因为如此一来,也就“非所以言圣人矣”,——即既不足以揭示圣人之与道理的浑一无间,更不足以体贴圣人之“浑是道理”的气象了。所有这些话头,当然都是提撕、指点朱子之意,至于朱子能否真正由“默坐澄心”返归于自己的“初心”,能否由“圣人自道理中流出”而更加体味“圣人与我同类”的道理,从而达到所谓“不见有身世之碍”的地步,则确实很难说、但从延平的这些叮咛提撕来看,则正可以反证朱子其时对“圣人”之对象化理解与“澄心”之事理化推究的理解方式。
随着交往的增多,延平对朱子在为学路径上的不足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书扎问答中,延平也就时时提及朱子在这些方面的缺弱,要他注意扭转。比如: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书云:……若欲进此学,须是尽放弃平日习气,更鞭饬所不及处,使之脱然有自得处,始是道理少进。承谕应接少暇即体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觉之效,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无惜详及,庶几彼此得以自警也。壬午五月十四日书云:承谕处事扰扰,便似内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从这些问答来看,延平所见不可谓不准,其考虑也不可谓不细。比如像“须是尽放弃平日习气,更鞭饬所不及处”以及对朱子自我检讨的所谓“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与“此乃知觉之效”等等敲打,都说明延平对朱子当时的状态看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更重要的是,延平还时时根据朱子的自我描述,给他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治方法,比如“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等等,也都是就具体的工夫进路而言的。但朱子当时却固执于自己的“旧习”,从而也就仍将延平这种指点工夫进路的话语仅仅作为一场学理来推究了。从这一点来看,朱子确实有负其师之命。
能够为这一看法提供佐证的是,《答薛仕龙》与《答江元适》都是朱子受学于延平时的书札;而在这些书札中,每当朱子受到批评或“困而自悔”时,他当然也会反省,但他的反省却往往是这样展开的:
熹自少愚钝,事事不能及人,顾常侧闻先生君子之余教,粗知有志于学……比乃困而自悔,始复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而亦未有闻也。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显然,所谓“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以及其反省的所谓“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等等,其实也都是在朱子深感为学不进的情况下出现的,自然也都代表着朱子的某种“反省”;而其具体的落实表现,则又只是所谓“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无怪乎他感觉自己是“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因为他的这种“反省”实际上只是对“句读文义”的反思,充其量也只是对自己“视听言动”的再掂量,根本就没有进入到所谓“初心”或“本心”的层面。当然,这也表现出朱子一贯的学习方法,——他确实对“句读文义”与“知识章句”比较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牟宗三就径直批评他根本是文不对题,根本不理解延平的思路。牟先生分析说:
延平所说的“体用合”,“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是着重在由超越体证之抽象状态达至日用处(分殊处)之具体呈现。但朱子后来所常说至日用处下工夫,却是着重在下学上达,与日用处理会道理、致知格物,此即丧失延平实体之具体呈现义(由体达用)之纵贯义。
……但延平之说此语,吾想却是根据其“体用合”,“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而来,而朱子却只重在日用处之认知的意义。同是“日用处”,它可指点到践履上通体达用,道之具体呈现,道在眼前,此所谓“日用处熟”;它也可以指点到知解上就日用处下学上达,格物致知。此是一个交叉路口,而朱子却偏重在后者。
……此即是将“日用处”之平实、切实,只转向下学上达、致知格物处讲,只成为认知意义的平实、切实。此是“静神养气”之静涵静摄系统下之平实切实。
牟宗三的这些批评,当然都是一种超越的解析,其用语虽然严厉,但在点破朱子将道德实践语境下道德理性之纵贯落实义扭转为平列的认知积累义方面,我们却不能不佩服其将问题看得准确,看得透彻。
此后,朱子与延平的两段对话即表现了朱子的为学进境,而延平的叮咛提携也同样表现了其对理论问题的敏锐与警觉:
先生曰:谢上蔡云:“‘吾尝习忘以养生。’明道曰:‘施之养则可,于道则有害。习忘可以养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学道则异于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谓乎?且出入起居,宁无事者?正心待之,则先事而迎,忘则涉乎去念,助则近于留情。故圣人心如鉴,所以异于释氏心也。”上蔡录明道此语,于学者甚有力。盖寻常于静处体认下工夫,即于闹处使不著,盖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谢先生确实于日用处便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事上作工夫学。)即恐明道此语亦未必引得出来。此语录所以极好玩索,近方看见如此意思显然。元晦于此更思看如何?唯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某辄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问:熹又问《孟子》“养气”一章,向者虽蒙曲折面诲,而愚意竟未见一总会处,近日求之,颇见大体,只是要得心气合而已。故说“持其志,无暴其气”,“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皆是紧切处。只是要得这里所存主处分明,则一身之气,自然一时奔凑翕聚,向这里来……
先生曰: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不然,心是心,气是气,不见所谓集义处,终不能合一也……然心气合一之象,更用体察,令分晓路脉方是。某寻常觉得于畔援心羡之时,未必皆是正理,亦心与气合,到此若仿佛有此气象,一差则所失多矣、其所谓浩然之气耶!某窃谓孟子所谓养气者,自有一端绪,须从知言处养来,乃不差。
这两段对话实际上都是从现实的日用工夫出发以直接指向超越的体证而言的。上一段从“习忘”与“养生”的关系出发引入儒家的“养心”与“养志”,而以孟子的“勿忘勿助”为标准,并要求将其落实于日用工夫之间;其特别警策之处在于“唯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这就成为一种理论思辩的工夫了。所以,儒家所谓日用处工夫主要是指将道德理性落实于日用事为间而言的。下一段则主要在于分析如何理解孟子的“养气”,朱子能够理解到养气就是要心与气合,所以有所谓“这里所存主处分明,则一身之气,自然一时奔凑翕聚,向这里来”,对于这一理解,延平当然感到高兴。但延平的提醒则在于:所谓“于畔援心羡之时……亦心与气合”,但却“未必皆是正理”。所以,所谓心与气合,并不是要合心于气、合理于欲,也不是二者的浑沦不分,而是必须合气于心、合欲于理;这样一种方向,其实也就是孟子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所以延平说必须从孟子的“知言”养来,方无大差,不然的话,就极有可能会成为所谓心随气走、志随气转的物欲横流了。
对于延平的立场、观点及其基本思路,我们这里已经无需多言,因为已经有牟宗三、刘述先两位先生的细致分析与准确把握在前了,——仅从其对朱子之反复的叮咛提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气象。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朱子,从朱子与延平的这一系列问答以及延平对朱子的叮咛提撕中能够表现出朱子的何种气象呢?因为从“师事”延平起,朱子就已经三十出头,其理智也大体成熟;仅从其读书学习——“业儒”及其所受的熏陶来看,也已经超过二十年,——起码已经积累了多年的读书学习经验。在这种条件下,其具体观点当然是可以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其认知世界、把握事物的视角与方法则大体上已经定型了。那么,从《延平答问》中,我们究竟能够看出朱子那些比较稳定的因素呢?
首先,由于朱子很早就以“业儒”自期,而在他的成长经历中,所谓“业儒”也就主要表现为读书学习,又由于朱子异常勤奋、顽强,因而其学习也就更多地致力于所谓“文理密察”一面,延平之所以提醒他“于言外求意乃通”,并不断地批评他的思考是“不类”,就是因为他把文本把得太死,把文理看得太重。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就已经决定了他对文本世界的对象性视角;而从具体认知的角度看,他又严格地杜绝自我体究式的主体介入方式,从而也就排除了主体与文本“融液一体”之可能。仅从其对圣人“发愤忘食”之“求道之切”的理解中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从对象的角度来“打量”圣人而不是真正以自我介入的方式来“体贴”圣人的。如果说宋明理学中就只有这一种进路,那我们自然无从比较;但如果我们将其与王阳明稍加比较,则朱子为学进路的这一对象性特点就显得格外分明。请看王阳明是如何学习书法的:
先生尝示学者曰:“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凝思静虑,抑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物,多举此为证。
这显然是“用心”型的学习。如果我们将这种“用心”型的学习与朱子稍加比较,那么朱子显然是属于“用脑”型的学习。王阳明这种“用心”型的学习方法固然并不万能,并且也有其局限性,但这种方法却能够使“我”与古帖以及我之心与手迅速地融液一体,而朱子却不仅要自觉地将“我”与圣人分开,而且还要将圣人与道理分开,——圣人也不过是“发愤忘食”、“求道之切”而已。如此一来,所谓文本也就真正成为他的对象世界了。
其次,在朱子与延平这一长达数年的“对话”中,朱子又典型地表现出其对由文本所蕴含的“事理”之特别关注的兴趣,他之所以常常陶醉于文本与文理的世界,不惜在上下文之间强行索解以至于旁征博引地加以说明,因而屡屡被延平批评为“不类”,不能“于言外求意”,一方面说明他确实对作为对象之文本世界把的特别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对象世界往往是以“平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之所以常常陷入“不类”的比喻,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对象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平面,其所谓万事一理、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的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从平面的视角展开的。那么,世界本身的立体性哪里去了呢?此则更有原因,待讨论思想谱系时再具体说明,但就其对“事理”之特别关注以及其完全将对象世界平面化而言,则又确实是朱子在与延平“对话”中的一大特点。
再次,在《延平答问》中,朱子所有的问题都隐然含括了一个既存在于主体之外同时又包括主体于其中的所谓客观世界,而朱子本人、包括所有的人其实都既是这一世界的认知者与揭示者,同时又始终是这一世界发展的产物与具体的参与者。对于这样一个总体背景,牟宗三常常以“朴素实在论”视之,而大陆学界则常常将其定位为客观唯心主义,其实这都存在着简单类比之过,究其原因,则主要集中在朱子对这一“客观世界”的肯定与承认上。我们这里暂且不管其客观世界的形成以及其如何才能成立的问题,但在朱子的思路中,这一世界的客观存在却一直是他,包括所有人的认知活动得以存在、得以发展的前提基础这一点却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所以说,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成为整个朱子世界及其理论创造活动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了。这样一来,可以说对象化的视角、具体的事理关怀以及实然世界的背景,也就必然蕴含着朱子的一条探索儒学、推进儒学的新思路。
在朱子看来,只要这个世界不会改变,那么其探索世界的进路与方法也就不会改变;而对李延平来说,虽然他也极为认真地指点朱子、提撕朱子,但只要朱子这一“世界”的规模与性质不会改变,那么延平对朱子所有的指点、提撕也就极有可能会陷于“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的格局。就是说,只要其“世界”的规模与性质是确定的,那么其对这个世界的研究与诠释进路也就必然是确定的。可惜延平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理论视野,因而他也无法看到人由自身的习惯性经验所自发形成之背景世界的力量,这也就使得他的指点、提撕只具有文献解读或工夫修养——所谓涵养的意义,而根本无法触动朱子,无法改变朱子的“世界”。当然,这同时也就在宋明理学中留下了或者说存在着开辟一个新世界之可能,所有这些,又将随着朱子在理论探讨上的不断发展与不断成长而逐渐明晰起来。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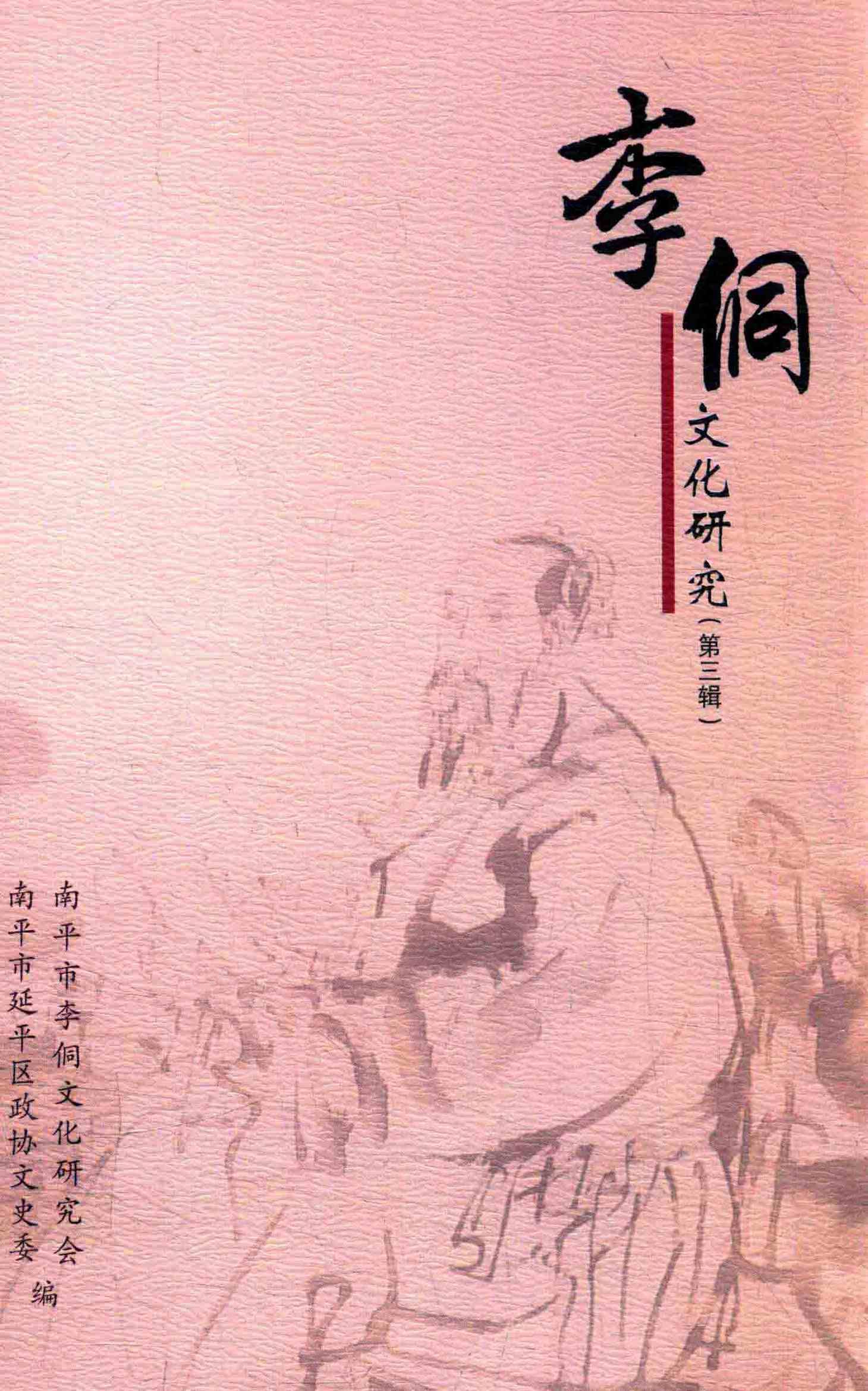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