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道李延平:佛与儒之抉择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317 |
| 颗粒名称: | 一、问道李延平:佛与儒之抉择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13 |
| 页码: | 135-147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记述了李侗与朱子儒佛之辨。朱子在与李延平的交往中,从怀疑、不服到虽然告别佛老,却仍然质疑不已的过程终于完成;而对朱子来说,不管其对李延平的思想理解到何种程度、接受到何种程度,而其师弟关系之确立则已经如缫丝抽茧般地完成了。 |
| 关键词: | 李侗 朱子 儒佛之辨 |
内容
从十九岁进士及第一直到二十四岁任同安主簿,朱子有一长达五年,较为闲暇、可以自由支配的“待次”时间,其间除了回祖籍婺源祭扫祖坟以外,朱熹基本上用来读书、访学与交友。因为此时他已经彻底摆脱了科举场屋之累,所以完全可以随性所适,尽情地展现其个人的禀赋与志趣。那么,在这较为闲暇的几年里,朱熹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关于其在这几年里比较突出的活动,《朱熹年谱长编》有如下记载:
绍兴二十年(1150),道谦自衡阳归密庵,朱熹屡至山中,与道谦朝夕咨参问道,书牍往还学禅。
绍兴二十一年,建斋室名“牧斋”,日读《六经》百氏之书,谦谦自牧。
绍兴二十二年,往武夷山冲佑观访道,斋心焚修。
四月,访密庵道谦,遂长途行役,由建阳直至顺昌,宿山寺,登云际阁……至五月而返。
归来斋居,更耽读佛经,心怀道谦,究味禅悦。
秋间耽读道经,学长生飞仙之术。
冬间,斋居修道,作焚修室,抑《步虚词》,仿道士步虚焚修。
绍兴二十三年(1153),春间,斋居晨昏诵读道经……作《牧斋记》,为其牧斋三年读儒经与出入佛老之总结。
五月,赴泉州同安县主簿任,经武夷山访冲佑观道士。述基本上概括了朱子在赴同安任之前四年多时间里的读书交往活动。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与禅师道谦的交往以及读佛老之书为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活动。但虽然如此,朱熹仍在《牧斋记》中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困惑:“余为是斋而居之三年矣,饥寒危迫之虑,未尝一日弛于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劳,疾病之忧,则无一日不取六经百氏之书以诵之于此也。以其志之笃、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业益加进,而不知智益昏而业益堕也。”对于这种困惑,由于百思不得其解,因而他当时甚至怀疑自己“凡所为早夜孜孜以冀事业之成而诏道德之进者,亦可谓妄矣”。这说明,即使是勤读《六经》百氏之书,朱熹当时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为己之学”。
正是这样一种深深的困惑,使朱熹不得不对自己从师求学以来的思想经历屡加反省,甚至连其幼年以来便一直记挂心中的“为己之学”也必须进行一番重新审视。自然,这也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理与自我总结活动。比如:
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
上述两段自然可以说是朱子在见李延平之前的一个思想总结。前一段主要总结其从学三君子以来的思想经历,而其结论则除了对儒家文献的泛泛了解以及科举考试时的“胡说”以外,“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当然,这里的“未有所得”主要是从“为己之学”上着眼的,——从“为己之学”的角度看,朱子当时对儒学的了解自然是“未知入手处”。后一段则主要叙述其如何用禅的“意思去胡说”,却竟然得到了功名,但对于他一直孜孜以求的“为己之学”来说,却仍然没有落到实处。因而,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去“见李先生”。这说明,自早年从其父亲的家教中得到“为己之学”的指点和启发后,这种“为己之学”就一直是朱子读书、业儒包括科考与习禅的方向与动力。因而在“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未知入手处”的情况下,其四处结交、上下求索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
这种状况也表现在他与朝野士夫的交往中。随着进士及第并进入朝廷官员的系列,朱熹的交往圈子日益扩大,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乡野书生,都在他的交游之列,但探索“为己之学”却始终像“定盘针”一样铭刻在他的心头;只要一谈到他自己,其对“为己之学”的探讨经历也就成为朱熹自报家门的独特方式了: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独闻古人为己之学而心窃好之,又以为是乃人之所当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从事焉,庶几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责,初不敢为异以求名也。
熹自少愚钝,事事不能及人,顾常侧闻先生君子之余教,粗知有志于学,而求之不得其术,盖舍近求远,处下窥高,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复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而亦未有闻也。
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熹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则又未及卒业而具有山颓梁坏之叹,怅怅然如盲之无目,擿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以是窃有意于朋友之助。上述几段,都是在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写于不同对象的书札,但其核心亦即所谓最终目标则始终只有一个,这就是要探讨儒家的“为己之学”,不过其具体叙述则因不同的对象而各有不同的侧重而已。《与留丞相书》中所谓的“是乃人之所当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从事焉”,其实正是对“为己之学”的一种准确解释;配之以“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责”,则既是对“为己之学”之所以是“人之所当为而立所可勉”的再解释,同时也是对周敦颐“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活用。而《答薛仕龙》书中所提到的“粗知有志于学,而求之不得其术,……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则是指其对佛老之学的浸染;至于“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在朱熹看来,则既是其对传统所谓“业儒”方式的复归,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直最为熟悉的读书和学习方法。而《答江元适》书中的“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则是对其为学方向之最初发端的明确揭示;至于“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则又显然是指他受教于李延平并受到延平批评的情形。至于《答何叔京》书中的“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则可以说是对其思想成熟前精神状况的一个总体说明。而在所有这些自我介绍中,“为己之学”始终是其进行自我评价的一个基本标准。
上述种种自我评价,实际上也包括其受教于李延平以后的情形,因为这些书信也都是其受教于延平以后所作。但最为确定的一点是,“为己之学”既是他四处结交以寻求共同探讨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其上下求索的圆心。所以,以此格之,朱子当时之所以要走向李延平,其实正是为了探讨真正的“为己之学”。
延平姓李,名侗,字愿中,福建南剑州剑浦人。因久居延平,世称延平先生。延平是洛学的三传,罗从彦的高足,因而也算是朱子父亲朱松的同门友。朱子幼时就见过李延平,而其父朱松对延平的评价尤其高。李默的《朱子年谱》就这样介绍李延平:
初,龟山先生倡道东南,从游甚众,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罗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讳侗,字愿中,受学罗公,实得其传,同门皆以为不及,然乐道不仕,人罕知之。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韦斋深以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将赴同安,特往见之。
显然,由于朱熹小时候就见过或闻知李延平的情况,加之其父亲对延平一直又非常推崇,所以,在朱熹摸索“为己之学”而又始终不得其门的情况下,其拜访李延平,用意也就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一定要弄清其自幼年以来一直无法释怀的“为己之学”的问题。
但这一往见却并不是很投缘。由于朱子此前已经有过一段对禅的钻研经历,并深受禅师的肯定和褒奖,因而由习禅而来的所谓“昭昭灵灵的境界”自然也就标志着他的最新认识。但朱熹的这些习禅所得却非但没有得到李延平的肯定,反而受到了明确的批评。请看朱子关于初见李延平时的几段回忆:
某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
上述几段其实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回忆,这就是初见李延平,而朱子当时所凭籍的实际上也就主要是其前几年的习禅所得,——是即所谓“说得无限道理”。可这些“无限道理”却让李先生给彻底否定了,——从最初的“不是”到“极言其不是”,简直就是一种明确的、不容置疑的否定态度。对当时的朱子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但在当时,无论是李延平的学养还是其在学界的声望,抑或是朱子本人的自信(正是其极不自信才有延平之行的)程度,都不容许他轻忽来自延平的批评。自然,这也就出现了一个对佛禅与儒学之反复比对、反复权衡与反复掂量的过程。其始,朱子甚至怀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但李延平明确的“不是”以及“极言其不是”,又是根本不容置疑的,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权且放过,且看下文的心态。但也就在这种状况下,朱子也就开始了其缓慢、逐步但又十分坚定地由禅而儒的思想转向过程。
要准确断定这一过程的具体始末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思想的转变毕竟不是做科学实验,也不是解方程,就连朱子本人也未必说得清他究竟是何时彻底实现其由禅而儒之转向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自从见李延平始,朱子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思想转变过程;而其完结同时又是和另外一件大事紧密相连的,这就是朱子究竟是何时开始正式拜李延平为师的?因为自从朱子的高足兼女婿黄榦在其所著的《朱文公行状》与同为朱子高足兼孙婿的赵师夏在《延平答问跋》中分别提出两种不同的说法后,朱子究竟何时拜延平为师的问题也就成为朱子研究中的一个大公案。由此之后,似乎每一位朱子研究者也都必须首先对此问题有所表态,有所择取,然后才可以展开对朱子思想的分析与叙述,所以,王懋竑在重修《朱子年谱》时就将旧谱中的“癸酉时受学于延平李先生”改为“始见李先生于延平”。这就是说,始见李延平并不意味着拜延平为师。但由于其具体细节已经无法详考,因而由此以来,在朱子究竟何时拜延平为师这一问题上,也就形成了一种各异其说的格局。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陈来先生的看法极有道理,他指出:“何时受学的问题,它的真正意义应该在于朱熹何时‘尽弃异学’,而不单纯在朱子何时执贽行弟子礼。”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因为如果离开了“尽弃异学”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也就仪仅成为一个朱子究竟是何时开始向延平“执贽行弟子礼”的问题了,自然,这也就仅仅成为一个朱子与延平之私交以及朱子主观上如何认定延平而不再是关于朱子思想本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了。实际上,只有前一个方面,即朱子究竟是何时实现其“尽弃异学”的转变,才真正是一个有思想史意义的话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笔者认为牟宗三先生的看法最为透彻,而刘述先先生的考订又最为精详,从而也就最具有思想史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朱子的研究就要从其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其事实的真伪,而是说其看法既符合思想本身发展的一般逻辑,同时也与历史事实比较吻合。原因在于,自从赵师夏在《延平答问跋》中提出朱子初见延平乃是“以父执事延平”而并不是“执弟子礼”以来,由于这一看法本身就以二人当时之思想差别为基础,——比如儒与禅之不同视角以及其对儒学的不同理解等等,而且又确实存在着思想史的根据,因而很快也就成为各家所公认的把握朱子思想发展的一大关节,包括其如何接受延平的思想以及其究竟何时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等等。这说明,自从这一问题提出后,它似乎也就成为朱子研究中的一个“铁案”了;而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其价值也就在于如何从这一“铁案”出发,以合情合理地说明朱子思想之发展与转变的具体过程了。
在现行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看法中,除了大家公认或共同接受的赵师夏之关于朱子初见延平并非就是师事以外,究竟朱子何时开始拜延平为师,则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比如钱穆先生认为“己亥一年(朱子26岁),乃为朱子一意归向儒学更为确定之年”,但在朱子何时拜延平为师的问题上,则钱穆与牟宗三又一致认为一直要到庚辰年(朱子31岁)“始受学焉”;而束景南先生又认为从丁丑年(朱子28岁)“李侗有答书”开始就应当算是受学,因而“从学延平李侗于此始”;陈来先生则认为“戊寅(朱子29岁)‘尽弃异学而师事焉’当可无疑”,因为这与朱子同安官余“始知不欺”的思想转变是一致的。上述说法当然都各有其道理。但由于笔者并不长于具体细节的考证,所以这里特意借助陈来先生的标准,先将“执弟子礼”与“尽弃异学”分开,以首先确定一个自己对前人观点之不同择取的基本平台。如果仅从“执弟子礼”的角度看,则笔者愿意接受束景南先生的看法,因为系统的书札问答毕竟可以说是师弟关系开始确立的表现。但是,如果从“尽弃异学”——在彻底告别禅学、告别佛老的基础上真正“师事”延平来看,则笔者更愿意接受牟宗三与钱穆两位先生所公认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由于牟先生的根据主要在于《年谱》、《行状》与《朱子文集》中关于“受教”、“受学”的直接记载,但却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辨析,而此后的刘述先先生则对牟宗三的观点作出了颇具特色然而又非常确凿的补正,所以笔者这里先简介刘述先先生的观点,同时也借以表达笔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取舍。
刘述先先生考证的特色在于他先依据赵师夏的概括,将朱子“以父执事延平”、受延平思想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与佛老的诀别直到最后直接“师事”延平层层分开,然后再以朱子思想之逐步发展来统一这一过程。所以,刘述先先征引赵师夏的跋以作为其全部考订的基本出发点:
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问学。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也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
这就是这一问题的缘起,赵师夏也叙述得非常明白,这就是先将“以父执事延平”与“师事”延平分开,并认为二者之间应当有一个过程;至于其过程的完成,则自然也就是所谓“尽弃所学而师事焉”。但是,关于“尽弃所学”的“师事”标准,刘述先同时又引入了赵师夏的另一段话:
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谓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
这一段既是延平所谓的儒佛之辨,自然也应当成为朱子彻底告别佛老从而“师事”延平的一个理论标准,而这一标准同时又确实可以证之于朱子思想发展的过程本身。如此一来,则朱子接受理一分殊的过程,似乎也就既是朱子告别佛老的过程,同时也将成为其开始“师事”延平的过程了。
应当承认,刘述先先生这一过程性标准的提出既客观地忠实于以上各种不同的说法,同时也比较符合儒佛本身的区别以及一般人思想发展的逻辑。但刘先生分析这一过程的特色则在于他将朱子早年的诗作进行了总体的排队与比较性的分析,——他先征引并分析其早年诗作中的仙气与禅味,以证明朱子其时确实接受了佛老的熏陶,然后再辨析其后来诗作中的儒家气象,尤其是将朱子二十二岁时的“何不栖空山”与二十七岁时的“何必栖空山”加以比较,也就明确地揭示了朱熹思想上的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这正可以说是朱子对禅学彻底告别的证明,当然同时也是其归本儒学的起始。所以,刘述先得出结论说: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这一年(甲戌,朱子25岁)和下年己亥之间诗量锐减。此下进入诗集第二卷,诗风乃与第一卷中诗大异。大概就是在这两年间,朱子且将圣人书来读,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逐渐归向儒学,释老的情调越来越减少,故诗吟特少。从这些迹象看来,甲戌已亥两年是朱子思想转变有关键性的两年,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注意和考察。
这当然只是一个初步的划分,以分清朱子究竟是如何在延平的影响下告别佛老的。接下来,刘述先又通过《延平答问》与朱子早年诗作的互证,以层层厘析朱子对延平从“怀疑”到“相得”、“沉潜”然后“正式受学”的过程。
刘述先先生的考证甚为细密,其间还采取了诗作与书札互证的方式,让人有不能不服之感。笔者这里既然是简介刘先生的考订结果,所以不想在征引材料方面作过多停留,只想摘取几个关键性环节以显现刘先生这一考订的基本思路与大概线索就行了。比如关于朱子初见延平的情形,在征引了朱子的相关回忆后,刘述先评价说:
朱子当时所说正是禅的昭昭灵灵的意思,但不为延平所首肯。朱子反倒怀疑延平理会此未得。由此可见朱子初见延平不只没有拜师之意,对他实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延平这种坚执的态度对朱子是新鲜的,而他大约也感觉到自己所学的确太杂,“我只是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所以姑且顺从延平的意思把禅搁下,专心儒学。
这是刘述先对朱子初见李延平的一段分析。而其结论,则无论是对应于朱子的“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以及此后的“将那禅来权已阁起……且将圣人之书来读”,还是对应于赵师夏在《延平答问跋》中所说的“以父执事延平”来看,应当说都是令人信服的。
朱子在丁丑年(朱子二十八岁)始与延平有书札往还,但戊寅(朱子二十九岁)以后,朱子与延平书札转密,而延平的答问也越来越多。刘述先在征引并分析了延平最初的三通书札之后评价说:
这样的口气显然还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口气。大抵延平答问前半所问多有关《论语》,《春秋》次之,间或及《孟子》,朱子有时以二苏语、孟之说质之于延平。
由于这里所要确定的是延平与朱子究竟是否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师弟关系,因而其关系的认定不仅取决于朱子如何对待延平,而且也取决于延平如何看待朱子。刘述先能够从延平对朱子的答问中分析出其当时尚“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口气”,也正如其能从朱子的早年诗作中分析出朱子的禅味以及其后来与禅的彻底诀别一样,让人不得不佩服其用心的深细。但问题并没有完结,刘述先接着又征引了朱子此期的《存斋记》,指出其虽然也在顺着孟子的思路前进,并且也已经不是禅的那一套,“但也和延平所教由《中庸》入体验未发时气象的一套很不相同”。这就又反过来,从朱子的角度来反证其时二人确实还不是师弟关系。
直到庚辰年朱子三十一岁时,由于其有“送籍溪胡丈赴馆供职”之作,而其诗中又有“留取幽人卧空谷”之句,其实朱子当时意在讽“先生不必起”,但却已经远远不是佛老的避世之意了,并且由此还引起了胡宏的关注与品评,刘述先这才分析说:“学问的进境到了一个地步,不作进一步的追求是不可能的。这一年的冬天朱子见李延平,乃正式受学。”与此同时,延平也在与其早年的弟子罗博文的书札中写道:
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这里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其师弟关系已经渗透于言语文字之间了;而延平向其早年的弟子罗博文介绍朱子的情况,也意味着将朱子介绍于其同门;至于“吾党”,则既有与朱子相对比的涵义,同时又有明确的“引进”之意。这时候,朱子与延平的师弟关系,显然已经成为双方所共同认可的了。当然这里还必须作一点补充性的说明,朱子既然提醒胡宪“不必起”,同时又主张“留取幽人卧空谷”,而这一“幽人”又不是指佛老的遗世独立,那就说明朱子此时的为学志向已经非常坚定了;而延平的评价实际上又是从为师的角度对这一志向的充分认可,所以下来也就有了“这一年的冬天朱子见李延平,乃正式受学”的结论。
但刘先生的考证还没有完,在征引了朱子此后的回忆与诗作之后,刘述先总结说:
看来此诗乃在延平时所作。此年诗惟前引送胡籍溪及寄两题四首,以及挽范直阁一题两首而已。大概在庚辰以前的两年之中,朱子既不作诗,也不读佛书,只一心读圣贤书;延平所谓能就里面体认,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也可由此诗得到一些消息。
朱子既经一番苦学,到次年辛已,乃又恢复大量作诗,以记述自己的进境以及心中的体会。
至此,朱子在与李延平的交往中,从怀疑、不服到虽然告别佛老,却仍然质疑不已的过程终于完成;而对朱子来说,不管其对李延平的思想理解到何种程度、接受到何种程度,而其师弟关系之确立则已经如缫丝抽茧般地完成了。
对于刘述先先生的这一考订,笔者还想补充一点题外的看法,这就是朱子与延平的师弟关系确实不可能确立得太早。因为以延平对儒家学理掌握之精深与把握之坚定来看,他也不可能容忍既已与朱子确立了明确的师弟关系,如何又能够坐视朱子在根本进路上与他完全不相应的理解呢?尤其是那种根本不到位的理解。对李延平这样的一代宗师而言,他既然能够从朱子“说得无限道理”中当下指出其“不是”,如何不能看出朱子对以延平为代表的儒学内省路线之全然不到位——所谓凑泊性的理解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延平只有先充分肯定其“进学甚力”,然后才能慢慢加以引导。可惜的是,延平很快就去世了。当然对朱子来说,这种根本不到位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就体现着其有所创新的研究进路了。
绍兴二十年(1150),道谦自衡阳归密庵,朱熹屡至山中,与道谦朝夕咨参问道,书牍往还学禅。
绍兴二十一年,建斋室名“牧斋”,日读《六经》百氏之书,谦谦自牧。
绍兴二十二年,往武夷山冲佑观访道,斋心焚修。
四月,访密庵道谦,遂长途行役,由建阳直至顺昌,宿山寺,登云际阁……至五月而返。
归来斋居,更耽读佛经,心怀道谦,究味禅悦。
秋间耽读道经,学长生飞仙之术。
冬间,斋居修道,作焚修室,抑《步虚词》,仿道士步虚焚修。
绍兴二十三年(1153),春间,斋居晨昏诵读道经……作《牧斋记》,为其牧斋三年读儒经与出入佛老之总结。
五月,赴泉州同安县主簿任,经武夷山访冲佑观道士。述基本上概括了朱子在赴同安任之前四年多时间里的读书交往活动。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与禅师道谦的交往以及读佛老之书为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活动。但虽然如此,朱熹仍在《牧斋记》中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困惑:“余为是斋而居之三年矣,饥寒危迫之虑,未尝一日弛于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劳,疾病之忧,则无一日不取六经百氏之书以诵之于此也。以其志之笃、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业益加进,而不知智益昏而业益堕也。”对于这种困惑,由于百思不得其解,因而他当时甚至怀疑自己“凡所为早夜孜孜以冀事业之成而诏道德之进者,亦可谓妄矣”。这说明,即使是勤读《六经》百氏之书,朱熹当时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为己之学”。
正是这样一种深深的困惑,使朱熹不得不对自己从师求学以来的思想经历屡加反省,甚至连其幼年以来便一直记挂心中的“为己之学”也必须进行一番重新审视。自然,这也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理与自我总结活动。比如:
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
上述两段自然可以说是朱子在见李延平之前的一个思想总结。前一段主要总结其从学三君子以来的思想经历,而其结论则除了对儒家文献的泛泛了解以及科举考试时的“胡说”以外,“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当然,这里的“未有所得”主要是从“为己之学”上着眼的,——从“为己之学”的角度看,朱子当时对儒学的了解自然是“未知入手处”。后一段则主要叙述其如何用禅的“意思去胡说”,却竟然得到了功名,但对于他一直孜孜以求的“为己之学”来说,却仍然没有落到实处。因而,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去“见李先生”。这说明,自早年从其父亲的家教中得到“为己之学”的指点和启发后,这种“为己之学”就一直是朱子读书、业儒包括科考与习禅的方向与动力。因而在“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未知入手处”的情况下,其四处结交、上下求索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
这种状况也表现在他与朝野士夫的交往中。随着进士及第并进入朝廷官员的系列,朱熹的交往圈子日益扩大,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乡野书生,都在他的交游之列,但探索“为己之学”却始终像“定盘针”一样铭刻在他的心头;只要一谈到他自己,其对“为己之学”的探讨经历也就成为朱熹自报家门的独特方式了: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独闻古人为己之学而心窃好之,又以为是乃人之所当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从事焉,庶几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责,初不敢为异以求名也。
熹自少愚钝,事事不能及人,顾常侧闻先生君子之余教,粗知有志于学,而求之不得其术,盖舍近求远,处下窥高,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复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而亦未有闻也。
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熹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则又未及卒业而具有山颓梁坏之叹,怅怅然如盲之无目,擿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以是窃有意于朋友之助。上述几段,都是在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写于不同对象的书札,但其核心亦即所谓最终目标则始终只有一个,这就是要探讨儒家的“为己之学”,不过其具体叙述则因不同的对象而各有不同的侧重而已。《与留丞相书》中所谓的“是乃人之所当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从事焉”,其实正是对“为己之学”的一种准确解释;配之以“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责”,则既是对“为己之学”之所以是“人之所当为而立所可勉”的再解释,同时也是对周敦颐“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活用。而《答薛仕龙》书中所提到的“粗知有志于学,而求之不得其术,……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则是指其对佛老之学的浸染;至于“退而求之于句读文义之间,谨之于视听言动之际”,在朱熹看来,则既是其对传统所谓“业儒”方式的复归,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直最为熟悉的读书和学习方法。而《答江元适》书中的“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则是对其为学方向之最初发端的明确揭示;至于“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则又显然是指他受教于李延平并受到延平批评的情形。至于《答何叔京》书中的“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则可以说是对其思想成熟前精神状况的一个总体说明。而在所有这些自我介绍中,“为己之学”始终是其进行自我评价的一个基本标准。
上述种种自我评价,实际上也包括其受教于李延平以后的情形,因为这些书信也都是其受教于延平以后所作。但最为确定的一点是,“为己之学”既是他四处结交以寻求共同探讨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其上下求索的圆心。所以,以此格之,朱子当时之所以要走向李延平,其实正是为了探讨真正的“为己之学”。
延平姓李,名侗,字愿中,福建南剑州剑浦人。因久居延平,世称延平先生。延平是洛学的三传,罗从彦的高足,因而也算是朱子父亲朱松的同门友。朱子幼时就见过李延平,而其父朱松对延平的评价尤其高。李默的《朱子年谱》就这样介绍李延平:
初,龟山先生倡道东南,从游甚众,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罗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讳侗,字愿中,受学罗公,实得其传,同门皆以为不及,然乐道不仕,人罕知之。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韦斋深以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将赴同安,特往见之。
显然,由于朱熹小时候就见过或闻知李延平的情况,加之其父亲对延平一直又非常推崇,所以,在朱熹摸索“为己之学”而又始终不得其门的情况下,其拜访李延平,用意也就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一定要弄清其自幼年以来一直无法释怀的“为己之学”的问题。
但这一往见却并不是很投缘。由于朱子此前已经有过一段对禅的钻研经历,并深受禅师的肯定和褒奖,因而由习禅而来的所谓“昭昭灵灵的境界”自然也就标志着他的最新认识。但朱熹的这些习禅所得却非但没有得到李延平的肯定,反而受到了明确的批评。请看朱子关于初见李延平时的几段回忆:
某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
上述几段其实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回忆,这就是初见李延平,而朱子当时所凭籍的实际上也就主要是其前几年的习禅所得,——是即所谓“说得无限道理”。可这些“无限道理”却让李先生给彻底否定了,——从最初的“不是”到“极言其不是”,简直就是一种明确的、不容置疑的否定态度。对当时的朱子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但在当时,无论是李延平的学养还是其在学界的声望,抑或是朱子本人的自信(正是其极不自信才有延平之行的)程度,都不容许他轻忽来自延平的批评。自然,这也就出现了一个对佛禅与儒学之反复比对、反复权衡与反复掂量的过程。其始,朱子甚至怀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但李延平明确的“不是”以及“极言其不是”,又是根本不容置疑的,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权且放过,且看下文的心态。但也就在这种状况下,朱子也就开始了其缓慢、逐步但又十分坚定地由禅而儒的思想转向过程。
要准确断定这一过程的具体始末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思想的转变毕竟不是做科学实验,也不是解方程,就连朱子本人也未必说得清他究竟是何时彻底实现其由禅而儒之转向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自从见李延平始,朱子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思想转变过程;而其完结同时又是和另外一件大事紧密相连的,这就是朱子究竟是何时开始正式拜李延平为师的?因为自从朱子的高足兼女婿黄榦在其所著的《朱文公行状》与同为朱子高足兼孙婿的赵师夏在《延平答问跋》中分别提出两种不同的说法后,朱子究竟何时拜延平为师的问题也就成为朱子研究中的一个大公案。由此之后,似乎每一位朱子研究者也都必须首先对此问题有所表态,有所择取,然后才可以展开对朱子思想的分析与叙述,所以,王懋竑在重修《朱子年谱》时就将旧谱中的“癸酉时受学于延平李先生”改为“始见李先生于延平”。这就是说,始见李延平并不意味着拜延平为师。但由于其具体细节已经无法详考,因而由此以来,在朱子究竟何时拜延平为师这一问题上,也就形成了一种各异其说的格局。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陈来先生的看法极有道理,他指出:“何时受学的问题,它的真正意义应该在于朱熹何时‘尽弃异学’,而不单纯在朱子何时执贽行弟子礼。”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因为如果离开了“尽弃异学”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也就仪仅成为一个朱子究竟是何时开始向延平“执贽行弟子礼”的问题了,自然,这也就仅仅成为一个朱子与延平之私交以及朱子主观上如何认定延平而不再是关于朱子思想本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了。实际上,只有前一个方面,即朱子究竟是何时实现其“尽弃异学”的转变,才真正是一个有思想史意义的话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笔者认为牟宗三先生的看法最为透彻,而刘述先先生的考订又最为精详,从而也就最具有思想史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朱子的研究就要从其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其事实的真伪,而是说其看法既符合思想本身发展的一般逻辑,同时也与历史事实比较吻合。原因在于,自从赵师夏在《延平答问跋》中提出朱子初见延平乃是“以父执事延平”而并不是“执弟子礼”以来,由于这一看法本身就以二人当时之思想差别为基础,——比如儒与禅之不同视角以及其对儒学的不同理解等等,而且又确实存在着思想史的根据,因而很快也就成为各家所公认的把握朱子思想发展的一大关节,包括其如何接受延平的思想以及其究竟何时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等等。这说明,自从这一问题提出后,它似乎也就成为朱子研究中的一个“铁案”了;而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其价值也就在于如何从这一“铁案”出发,以合情合理地说明朱子思想之发展与转变的具体过程了。
在现行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看法中,除了大家公认或共同接受的赵师夏之关于朱子初见延平并非就是师事以外,究竟朱子何时开始拜延平为师,则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比如钱穆先生认为“己亥一年(朱子26岁),乃为朱子一意归向儒学更为确定之年”,但在朱子何时拜延平为师的问题上,则钱穆与牟宗三又一致认为一直要到庚辰年(朱子31岁)“始受学焉”;而束景南先生又认为从丁丑年(朱子28岁)“李侗有答书”开始就应当算是受学,因而“从学延平李侗于此始”;陈来先生则认为“戊寅(朱子29岁)‘尽弃异学而师事焉’当可无疑”,因为这与朱子同安官余“始知不欺”的思想转变是一致的。上述说法当然都各有其道理。但由于笔者并不长于具体细节的考证,所以这里特意借助陈来先生的标准,先将“执弟子礼”与“尽弃异学”分开,以首先确定一个自己对前人观点之不同择取的基本平台。如果仅从“执弟子礼”的角度看,则笔者愿意接受束景南先生的看法,因为系统的书札问答毕竟可以说是师弟关系开始确立的表现。但是,如果从“尽弃异学”——在彻底告别禅学、告别佛老的基础上真正“师事”延平来看,则笔者更愿意接受牟宗三与钱穆两位先生所公认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由于牟先生的根据主要在于《年谱》、《行状》与《朱子文集》中关于“受教”、“受学”的直接记载,但却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辨析,而此后的刘述先先生则对牟宗三的观点作出了颇具特色然而又非常确凿的补正,所以笔者这里先简介刘述先先生的观点,同时也借以表达笔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取舍。
刘述先先生考证的特色在于他先依据赵师夏的概括,将朱子“以父执事延平”、受延平思想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与佛老的诀别直到最后直接“师事”延平层层分开,然后再以朱子思想之逐步发展来统一这一过程。所以,刘述先先征引赵师夏的跋以作为其全部考订的基本出发点:
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问学。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也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
这就是这一问题的缘起,赵师夏也叙述得非常明白,这就是先将“以父执事延平”与“师事”延平分开,并认为二者之间应当有一个过程;至于其过程的完成,则自然也就是所谓“尽弃所学而师事焉”。但是,关于“尽弃所学”的“师事”标准,刘述先同时又引入了赵师夏的另一段话:
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谓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
这一段既是延平所谓的儒佛之辨,自然也应当成为朱子彻底告别佛老从而“师事”延平的一个理论标准,而这一标准同时又确实可以证之于朱子思想发展的过程本身。如此一来,则朱子接受理一分殊的过程,似乎也就既是朱子告别佛老的过程,同时也将成为其开始“师事”延平的过程了。
应当承认,刘述先先生这一过程性标准的提出既客观地忠实于以上各种不同的说法,同时也比较符合儒佛本身的区别以及一般人思想发展的逻辑。但刘先生分析这一过程的特色则在于他将朱子早年的诗作进行了总体的排队与比较性的分析,——他先征引并分析其早年诗作中的仙气与禅味,以证明朱子其时确实接受了佛老的熏陶,然后再辨析其后来诗作中的儒家气象,尤其是将朱子二十二岁时的“何不栖空山”与二十七岁时的“何必栖空山”加以比较,也就明确地揭示了朱熹思想上的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这正可以说是朱子对禅学彻底告别的证明,当然同时也是其归本儒学的起始。所以,刘述先得出结论说: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这一年(甲戌,朱子25岁)和下年己亥之间诗量锐减。此下进入诗集第二卷,诗风乃与第一卷中诗大异。大概就是在这两年间,朱子且将圣人书来读,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逐渐归向儒学,释老的情调越来越减少,故诗吟特少。从这些迹象看来,甲戌已亥两年是朱子思想转变有关键性的两年,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注意和考察。
这当然只是一个初步的划分,以分清朱子究竟是如何在延平的影响下告别佛老的。接下来,刘述先又通过《延平答问》与朱子早年诗作的互证,以层层厘析朱子对延平从“怀疑”到“相得”、“沉潜”然后“正式受学”的过程。
刘述先先生的考证甚为细密,其间还采取了诗作与书札互证的方式,让人有不能不服之感。笔者这里既然是简介刘先生的考订结果,所以不想在征引材料方面作过多停留,只想摘取几个关键性环节以显现刘先生这一考订的基本思路与大概线索就行了。比如关于朱子初见延平的情形,在征引了朱子的相关回忆后,刘述先评价说:
朱子当时所说正是禅的昭昭灵灵的意思,但不为延平所首肯。朱子反倒怀疑延平理会此未得。由此可见朱子初见延平不只没有拜师之意,对他实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延平这种坚执的态度对朱子是新鲜的,而他大约也感觉到自己所学的确太杂,“我只是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所以姑且顺从延平的意思把禅搁下,专心儒学。
这是刘述先对朱子初见李延平的一段分析。而其结论,则无论是对应于朱子的“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以及此后的“将那禅来权已阁起……且将圣人之书来读”,还是对应于赵师夏在《延平答问跋》中所说的“以父执事延平”来看,应当说都是令人信服的。
朱子在丁丑年(朱子二十八岁)始与延平有书札往还,但戊寅(朱子二十九岁)以后,朱子与延平书札转密,而延平的答问也越来越多。刘述先在征引并分析了延平最初的三通书札之后评价说:
这样的口气显然还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口气。大抵延平答问前半所问多有关《论语》,《春秋》次之,间或及《孟子》,朱子有时以二苏语、孟之说质之于延平。
由于这里所要确定的是延平与朱子究竟是否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师弟关系,因而其关系的认定不仅取决于朱子如何对待延平,而且也取决于延平如何看待朱子。刘述先能够从延平对朱子的答问中分析出其当时尚“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口气”,也正如其能从朱子的早年诗作中分析出朱子的禅味以及其后来与禅的彻底诀别一样,让人不得不佩服其用心的深细。但问题并没有完结,刘述先接着又征引了朱子此期的《存斋记》,指出其虽然也在顺着孟子的思路前进,并且也已经不是禅的那一套,“但也和延平所教由《中庸》入体验未发时气象的一套很不相同”。这就又反过来,从朱子的角度来反证其时二人确实还不是师弟关系。
直到庚辰年朱子三十一岁时,由于其有“送籍溪胡丈赴馆供职”之作,而其诗中又有“留取幽人卧空谷”之句,其实朱子当时意在讽“先生不必起”,但却已经远远不是佛老的避世之意了,并且由此还引起了胡宏的关注与品评,刘述先这才分析说:“学问的进境到了一个地步,不作进一步的追求是不可能的。这一年的冬天朱子见李延平,乃正式受学。”与此同时,延平也在与其早年的弟子罗博文的书札中写道:
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这里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其师弟关系已经渗透于言语文字之间了;而延平向其早年的弟子罗博文介绍朱子的情况,也意味着将朱子介绍于其同门;至于“吾党”,则既有与朱子相对比的涵义,同时又有明确的“引进”之意。这时候,朱子与延平的师弟关系,显然已经成为双方所共同认可的了。当然这里还必须作一点补充性的说明,朱子既然提醒胡宪“不必起”,同时又主张“留取幽人卧空谷”,而这一“幽人”又不是指佛老的遗世独立,那就说明朱子此时的为学志向已经非常坚定了;而延平的评价实际上又是从为师的角度对这一志向的充分认可,所以下来也就有了“这一年的冬天朱子见李延平,乃正式受学”的结论。
但刘先生的考证还没有完,在征引了朱子此后的回忆与诗作之后,刘述先总结说:
看来此诗乃在延平时所作。此年诗惟前引送胡籍溪及寄两题四首,以及挽范直阁一题两首而已。大概在庚辰以前的两年之中,朱子既不作诗,也不读佛书,只一心读圣贤书;延平所谓能就里面体认,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也可由此诗得到一些消息。
朱子既经一番苦学,到次年辛已,乃又恢复大量作诗,以记述自己的进境以及心中的体会。
至此,朱子在与李延平的交往中,从怀疑、不服到虽然告别佛老,却仍然质疑不已的过程终于完成;而对朱子来说,不管其对李延平的思想理解到何种程度、接受到何种程度,而其师弟关系之确立则已经如缫丝抽茧般地完成了。
对于刘述先先生的这一考订,笔者还想补充一点题外的看法,这就是朱子与延平的师弟关系确实不可能确立得太早。因为以延平对儒家学理掌握之精深与把握之坚定来看,他也不可能容忍既已与朱子确立了明确的师弟关系,如何又能够坐视朱子在根本进路上与他完全不相应的理解呢?尤其是那种根本不到位的理解。对李延平这样的一代宗师而言,他既然能够从朱子“说得无限道理”中当下指出其“不是”,如何不能看出朱子对以延平为代表的儒学内省路线之全然不到位——所谓凑泊性的理解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延平只有先充分肯定其“进学甚力”,然后才能慢慢加以引导。可惜的是,延平很快就去世了。当然对朱子来说,这种根本不到位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就体现着其有所创新的研究进路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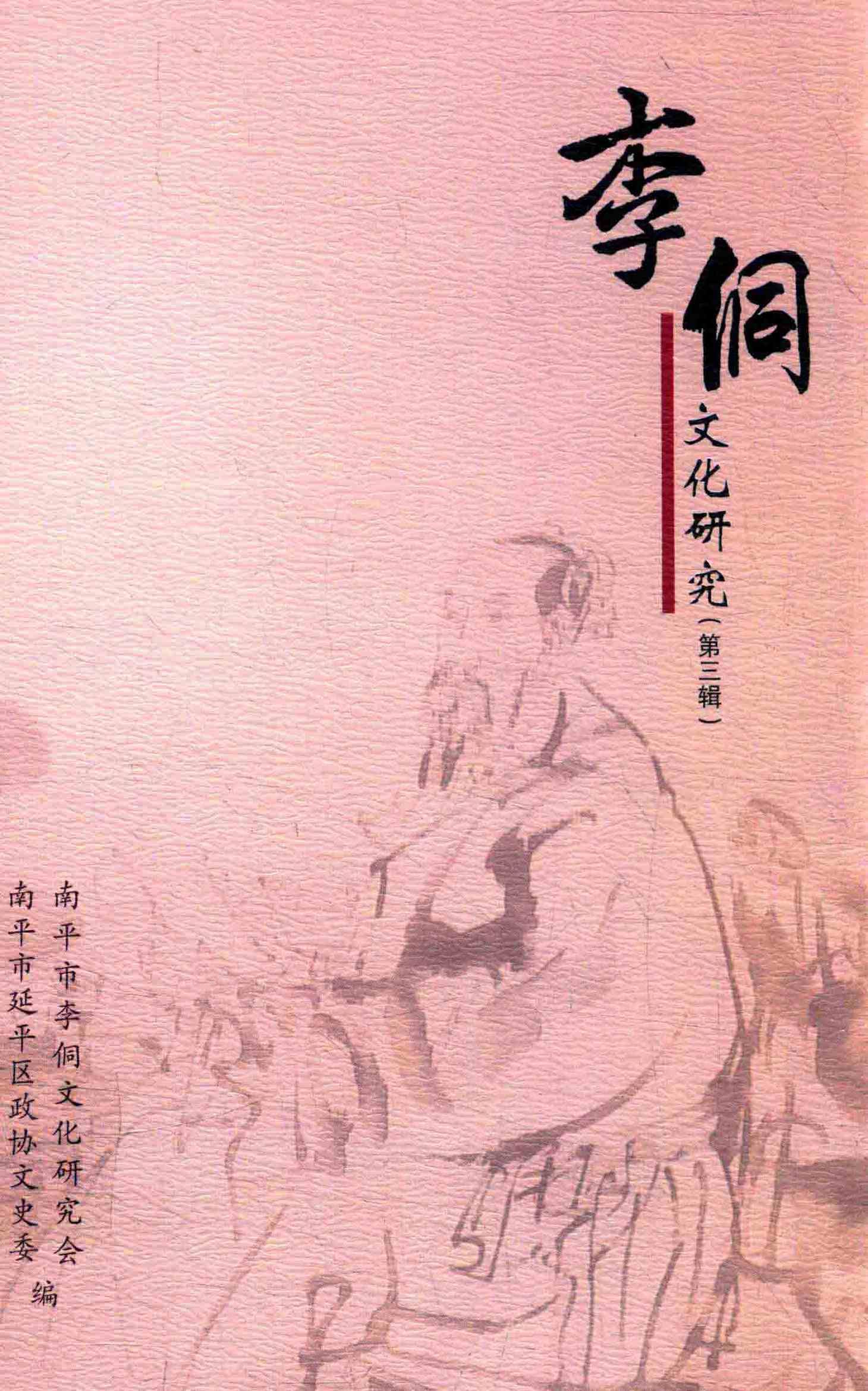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