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南剑三先生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312 |
| 颗粒名称: | 朱熹与南剑三先生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8 |
| 页码: | 127-134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记述了朱熹与杨时、罗从彦、李侗思想。杨、罗、李三先生这个中间环节,朱熹要从“杂博”的学识中、要从佛道思想中摆脱出来,必将经历不同的路程。总之杨时“道南”导致朱熹“闽学”——理学体系的完成,南剑三先生实开闽学之先河。 |
| 关键词: | 朱熹 南涧三先生 |
内容
二程思想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四传而得朱熹。宋儒杨时、罗从彦、李侗,都是闽之延平(今属福建南平市)人。延平在宋朝称南剑州,杨、罗、李被称为“南剑三先生”。朱熹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学术界议论不一,有的指出朱熹对三先生是不满意的,笔者认为确实如此,但尚需做具体分析。有的断言,二程思想经杨时“道南”,再经罗从彦至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应如何看待朱熹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下面从几个侧面做点粗浅的探讨。
一、从朱熹的师承关系说起
朱熹的父亲朱松师事过杨时的学生延平罗从彦,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据《延平府志》记载:“松公事之余,读书力学,无一息少废”,“口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他与闽中名儒广为交游。朱熹十四岁以前,在福建尤溪和建瓯时的家学,就接受理学思想影响。民间传说,他和其他小孩玩耍时,坐在沙滩上画八卦。他小时候就考虑天外是什么东西,想得几乎成疾。(《尤溪县志》《建瓯县志》)这些都说明他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朱松及其学友言行的熏陶。
朱熹十四岁丧父,他十四至二十四岁在崇安县五夫里,求学于朱松的好友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三先生之门。刘屏山学《易》得“不远复”为己之三字符,“佩服周旋,罔敢失坠”(《五夫里刘氏宗谱》)。刘白水在蔡京用事、伊洛之学不行之际,求得其书,每深夜“潜抄默诵之”(《宋史·刘勉之传》)。胡籍溪系当时大儒胡安国(武夷)从子,他还和刘白水一起拜曾与程颐游的谯定为师,“一意为学,不为人知……力田卖药,以奉其亲,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日众”(《宋史·胡宪传》)。三先生都是理学的崇信者,但正如《宋元学案》所指出的,皆“不能不杂于禅”。三先生相互过从讲学时,朱熹皆侍读左右。“两汉帝王胄,三刘文献家”(朱熹为刘家祠堂所写的对联)的刘氏家族刘子羽、刘子翚兄弟给朱熹提供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和丰富的藏书,使朱熹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学习上“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这段时间,朱熹又与僧、道有一定来往,因而也受到了僧、道思想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朱熹已打下了知识“杂博”的基础。
朱熹二十四岁到同安任主簿,路过延平,拜见朱松的同门学友李侗,由于知识“杂博”和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严重,所论均为李侗所反对。李侗交代朱熹要读“圣贤”书、遵“圣贤”语言才是道理。三年主簿兼管教育的经历,使他反复回味李侗之言,体会到李侗指点“其不我欺”。他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语类》卷104)朱熹把儒家思想表达为“这边”,把禅、道思想称为“那边”,在两者间做了泾渭分明的区分,并偏向了儒学。同安为官后六年间,直到朱熹三十四岁李侗去世那年止,朱熹拜李侗为师,经常往返于五夫里与剑浦(延平)之间,从李侗处闻“理一分殊”之说,得到理学思想的专门灌输。
在二十四至三十四岁这一阶段,朱熹思想发生“逃禅归儒”的转变,并注心于对“理一分殊”的探讨,这显然是李侗的开导所致。朱熹对师恩是念念不忘的,他在《祭延平李先生文》中云:“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相期日深,见励弥切……”在《又祭文》中说:“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学未传心,言徒在耳……”(《文集》卷87)所以全祖望说:“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此言实不为过。
朱松和李侗,这两个与青少年时代的朱熹关系密切的人物,都是罗从彦的学生,罗从彦求学于二程高弟杨时,因此,二程四传而得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所以,从师承关系上讲,南剑三先生是二程到朱熹的中间环节,二程思想能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与南剑三先生的“道南”一脉相承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朱熹本人也是直言不讳的。探讨朱熹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果忽略了家学、青少年时代的师弟子关系,尤其是否认李侗对青年朱熹的影响,是很难把问题说清楚的。
二、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褒贬
朱熹对杨、罗、李三先生思想的评议有许多贬词。他批评杨时“张皇佛氏之势”甚至说杨时“似别立一家”(《语类》卷101),这种批判是非常严厉的二朱熹引李侗语说罗从彦的“《春秋》说”不及胡安国(《语类》卷102),认为罗与杨(时)、游(酢)一样,少时先去看庄、列文字,后来虽学河洛之学,“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语类》卷101)。朱熹还认为李侗不让读《正蒙》之类的书,“终是短于辩证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语类》卷10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朱熹这些言论应怎样看待?笔者认为,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某些思想是有批评的;他对其理由长及前辈,敢于指出其短,或批评其与自己思想不一致之处,从总结学术思想的角度看,这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思想不受前人之言的束缚,才能使自己在思考问题时不拘泥于前说而有所前进。
还应看到,朱熹总是站在维护其师长及前辈的立场上来评价他们的。他对南剑三先生也有许多溢美之词,对他们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
譬如对杨时“晚出”一事虽有微词,但他认为:“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又如对杨时诗文,他认为“才说得有意思,便无收杀”,学生问他“是道理不透否”,他认为“虽然,亦是气质弱,然公平无病”。他说:“龟山天资高,朴实简易。”(《语类》卷101)甚至称颂杨时“功符孟子,德续无声”(《龟山集》卷首《文靖公像赞》)。把杨时与孟子相提并论,可谓至矣。
朱熹说罗从彦“严毅清苦,殊可畏”(《语类》卷102)。又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学其徒,望门以趋。惟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文靖公像赞》)其言辞流露出对罗从彦传道、为人和治学态度的仰慕。
朱熹说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语类》卷102)。他还说:“旧见李先生云:‘初向罗先生学《春秋》,觉说得自好。后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说有未安处。’”可见,李侗对杨、罗也是有议论的,这种议论得失之举深深地影响着朱熹。熹直接师从李侗,他的《挽延平李先生》诗云:“河洛传心后,毫厘复易差。淫辞方眩俗,夫子独名家。”“夫子独名家”突出一个“独”字,可见李侗在朱熹心目中是有很高地位的。朱熹对李侗固然有所批评,但他对李侗还是十分敬重和热爱的。李侗去世,朱熹哭道:“歧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斩板今来此,怀经痛所遭。有疑无与析,挥泪首频搔。”(《文集》卷2《挽延平李先生》)哀痛之音溢于言表。
杨时“道南”,二传李侗而为朱熹师,这一线“道脉”,朱熹是重视的。他对南剑三先生的褒贬,是为了总结、扬弃和继承他们的学术思想,是以维护师道为目的的。由此可见,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思想是既有批评又有肯定的,只看到朱熹批评南剑三先生一面已有不妥,而断言杨时“道南”至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的说法更是既不符合史实,也不利于理清朱熹思想演变的脉络。
三、从杨罗李的思想看朱熹的继承
南剑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他们对理学的传播,应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分析,这应该由专论去完成。本文只选择几个问题说明他们与朱熹的关系。
杨时用“天理”来说明世界的基本出发点。他说:“天下只是一理”(《龟山集》卷13);“天理之常,匪往匪来兮,虽寿天兮何伤”(《龟山集》卷28)。他不但讲理气关系,而且对气具有动静、屈伸、阖辟、往来的特点和作用做了发挥,并且用“气”解释天地、人物的产生;认为“天地即轻清、重浊之气的升降”所形成的,“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龟山集》卷13)他说:“通天下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龟山集》卷24)杨时用二气解释天地万物的产生,活灵活现,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毫不放松的,他说:“(气)有阖有辟,变由是生,其变无常,非易而何?”“通阖辟于一息兮,尸者其谁?盖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龟山集》卷13)据载,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朱熹十分赞赏地说:“此说极好,只是一阴阳,做出许般性。”(《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在理学关系上,杨时不仅吸收了二程的观点,而且受到张载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其哲学思想的其他方面,诸如格物致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方面,杨时思想都有折中二程、兼收他家思想的表现。难怪杨时刚死,就得到“网罗百家,驰骋千古”(绍兴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宋高宗皇帝赠杨时左大中大夫诰,翰林学士直史馆范冲行词)的美誉。杨时的这种“网罗百家”的学风为朱熹所继承,朱熹自称“会众说而折其中”(《中庸章句序》)。后人称二程朱熹学说为朱学派、程朱理学;认为朱熹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是孔子之后又一个集大成者,以二程思想为主流,并吸收和融汇其他学派的思想,是闽学的一大特点,就这个特点看,杨时实导闽学之前路。
“所造亦只是在善人有恒之间”(《宋元学案·豫章学案》)的罗从彦,在其《圣宋遵尧录》《杂著》《议论要语》等著作中,贯穿了立“正学”、摒“邪说”的道统论思想。罗从彦很赞同杨时所说的“学者先明‘五经’,然后学《春秋》,则其用利矣”,因为“五经论其理,《春秋》见之行事。《春秋》,圣人之用也”。罗从彦言必称孔孟,并认为“知《大学》之渊源,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中庸》之书……此圣学之渊源,六经之奥旨”。(《罗豫章集》卷12)立五经、四书为经典,是两宋理学“道统论”的重要表现。这个由二程开其端,杨时继续发挥,罗从彦身体力行的事业,是由朱熹来完成的。朱熹力主“道统论”,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语类》卷93)朱熹完成《四书集注》、组织五经诠释,可谓捍卫道统不遗余力。从这方面看,罗从彦和朱熹的继承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
李侗对朱熹耐心诱导,向他灌输“理一分殊”说,这从朱熹记叙的《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书来看是一目了然的。程颐答杨时时提出的“理一分殊”说,杨时心领神会,“释然无疑”,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龟山集》卷20)李侗在引导朱熹理解“理一分殊”说时,认为应该“在知字上用著力”,并指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要见一视同仁气象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在李侗指引下,朱熹侃侃而谈,大段议论。李侗在关键处精心“提破”。在李侗看来,天地万物“有有血气者,有无血气者”,本乎一源,“更应在此体究”。他指示朱熹对“理一”“须从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看为可”。朱熹对“分殊”的推演,李侗批曰:“推测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尝不见道也。某心甚慰。”朱熹从学于李侗,李侗给罗博文的信中说:“渠初从谦开善(僧人一笔者注)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处。”李侗称赞朱熹“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论难体认至切,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益深矣”。(《延平答问》)李侗对朱熹的启迪和诱导,对朱熹接受、继承和发展二程的思想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综上所述,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经历了几代人。杨时,“道南”为理学在福建播下种子,历经“最无气焰”(《宋元学案·豫章学案》)的罗从彦和“不著书、不作文”(《李延平集》卷3)的李侗,最终出现理学的完整体系“朱子之学”即“闽学”。这是理学长期酝酿直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杨时的思想“似别立一家”(《语类》卷101),但却是很关键的中间环节,从这里可以吸收经验教训、酝酿新的突破。罗从彦、李侗虽学术成就不大,但传道有功。失掉杨、罗、李三先生这个中间环节,朱熹要从“杂博”的学识中、要从佛道思想中摆脱出来,必将经历不同的路程。总之杨时“道南”导致朱熹“闽学”——理学体系的完成,南剑三先生实开闽学之先河。
一、从朱熹的师承关系说起
朱熹的父亲朱松师事过杨时的学生延平罗从彦,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据《延平府志》记载:“松公事之余,读书力学,无一息少废”,“口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他与闽中名儒广为交游。朱熹十四岁以前,在福建尤溪和建瓯时的家学,就接受理学思想影响。民间传说,他和其他小孩玩耍时,坐在沙滩上画八卦。他小时候就考虑天外是什么东西,想得几乎成疾。(《尤溪县志》《建瓯县志》)这些都说明他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朱松及其学友言行的熏陶。
朱熹十四岁丧父,他十四至二十四岁在崇安县五夫里,求学于朱松的好友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三先生之门。刘屏山学《易》得“不远复”为己之三字符,“佩服周旋,罔敢失坠”(《五夫里刘氏宗谱》)。刘白水在蔡京用事、伊洛之学不行之际,求得其书,每深夜“潜抄默诵之”(《宋史·刘勉之传》)。胡籍溪系当时大儒胡安国(武夷)从子,他还和刘白水一起拜曾与程颐游的谯定为师,“一意为学,不为人知……力田卖药,以奉其亲,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日众”(《宋史·胡宪传》)。三先生都是理学的崇信者,但正如《宋元学案》所指出的,皆“不能不杂于禅”。三先生相互过从讲学时,朱熹皆侍读左右。“两汉帝王胄,三刘文献家”(朱熹为刘家祠堂所写的对联)的刘氏家族刘子羽、刘子翚兄弟给朱熹提供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和丰富的藏书,使朱熹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学习上“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这段时间,朱熹又与僧、道有一定来往,因而也受到了僧、道思想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朱熹已打下了知识“杂博”的基础。
朱熹二十四岁到同安任主簿,路过延平,拜见朱松的同门学友李侗,由于知识“杂博”和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严重,所论均为李侗所反对。李侗交代朱熹要读“圣贤”书、遵“圣贤”语言才是道理。三年主簿兼管教育的经历,使他反复回味李侗之言,体会到李侗指点“其不我欺”。他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语类》卷104)朱熹把儒家思想表达为“这边”,把禅、道思想称为“那边”,在两者间做了泾渭分明的区分,并偏向了儒学。同安为官后六年间,直到朱熹三十四岁李侗去世那年止,朱熹拜李侗为师,经常往返于五夫里与剑浦(延平)之间,从李侗处闻“理一分殊”之说,得到理学思想的专门灌输。
在二十四至三十四岁这一阶段,朱熹思想发生“逃禅归儒”的转变,并注心于对“理一分殊”的探讨,这显然是李侗的开导所致。朱熹对师恩是念念不忘的,他在《祭延平李先生文》中云:“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相期日深,见励弥切……”在《又祭文》中说:“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学未传心,言徒在耳……”(《文集》卷87)所以全祖望说:“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此言实不为过。
朱松和李侗,这两个与青少年时代的朱熹关系密切的人物,都是罗从彦的学生,罗从彦求学于二程高弟杨时,因此,二程四传而得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所以,从师承关系上讲,南剑三先生是二程到朱熹的中间环节,二程思想能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与南剑三先生的“道南”一脉相承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朱熹本人也是直言不讳的。探讨朱熹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果忽略了家学、青少年时代的师弟子关系,尤其是否认李侗对青年朱熹的影响,是很难把问题说清楚的。
二、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褒贬
朱熹对杨、罗、李三先生思想的评议有许多贬词。他批评杨时“张皇佛氏之势”甚至说杨时“似别立一家”(《语类》卷101),这种批判是非常严厉的二朱熹引李侗语说罗从彦的“《春秋》说”不及胡安国(《语类》卷102),认为罗与杨(时)、游(酢)一样,少时先去看庄、列文字,后来虽学河洛之学,“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语类》卷101)。朱熹还认为李侗不让读《正蒙》之类的书,“终是短于辩证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语类》卷10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朱熹这些言论应怎样看待?笔者认为,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某些思想是有批评的;他对其理由长及前辈,敢于指出其短,或批评其与自己思想不一致之处,从总结学术思想的角度看,这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思想不受前人之言的束缚,才能使自己在思考问题时不拘泥于前说而有所前进。
还应看到,朱熹总是站在维护其师长及前辈的立场上来评价他们的。他对南剑三先生也有许多溢美之词,对他们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
譬如对杨时“晚出”一事虽有微词,但他认为:“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又如对杨时诗文,他认为“才说得有意思,便无收杀”,学生问他“是道理不透否”,他认为“虽然,亦是气质弱,然公平无病”。他说:“龟山天资高,朴实简易。”(《语类》卷101)甚至称颂杨时“功符孟子,德续无声”(《龟山集》卷首《文靖公像赞》)。把杨时与孟子相提并论,可谓至矣。
朱熹说罗从彦“严毅清苦,殊可畏”(《语类》卷102)。又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学其徒,望门以趋。惟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文靖公像赞》)其言辞流露出对罗从彦传道、为人和治学态度的仰慕。
朱熹说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语类》卷102)。他还说:“旧见李先生云:‘初向罗先生学《春秋》,觉说得自好。后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说有未安处。’”可见,李侗对杨、罗也是有议论的,这种议论得失之举深深地影响着朱熹。熹直接师从李侗,他的《挽延平李先生》诗云:“河洛传心后,毫厘复易差。淫辞方眩俗,夫子独名家。”“夫子独名家”突出一个“独”字,可见李侗在朱熹心目中是有很高地位的。朱熹对李侗固然有所批评,但他对李侗还是十分敬重和热爱的。李侗去世,朱熹哭道:“歧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斩板今来此,怀经痛所遭。有疑无与析,挥泪首频搔。”(《文集》卷2《挽延平李先生》)哀痛之音溢于言表。
杨时“道南”,二传李侗而为朱熹师,这一线“道脉”,朱熹是重视的。他对南剑三先生的褒贬,是为了总结、扬弃和继承他们的学术思想,是以维护师道为目的的。由此可见,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思想是既有批评又有肯定的,只看到朱熹批评南剑三先生一面已有不妥,而断言杨时“道南”至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的说法更是既不符合史实,也不利于理清朱熹思想演变的脉络。
三、从杨罗李的思想看朱熹的继承
南剑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他们对理学的传播,应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分析,这应该由专论去完成。本文只选择几个问题说明他们与朱熹的关系。
杨时用“天理”来说明世界的基本出发点。他说:“天下只是一理”(《龟山集》卷13);“天理之常,匪往匪来兮,虽寿天兮何伤”(《龟山集》卷28)。他不但讲理气关系,而且对气具有动静、屈伸、阖辟、往来的特点和作用做了发挥,并且用“气”解释天地、人物的产生;认为“天地即轻清、重浊之气的升降”所形成的,“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龟山集》卷13)他说:“通天下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龟山集》卷24)杨时用二气解释天地万物的产生,活灵活现,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毫不放松的,他说:“(气)有阖有辟,变由是生,其变无常,非易而何?”“通阖辟于一息兮,尸者其谁?盖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龟山集》卷13)据载,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朱熹十分赞赏地说:“此说极好,只是一阴阳,做出许般性。”(《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在理学关系上,杨时不仅吸收了二程的观点,而且受到张载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其哲学思想的其他方面,诸如格物致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方面,杨时思想都有折中二程、兼收他家思想的表现。难怪杨时刚死,就得到“网罗百家,驰骋千古”(绍兴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宋高宗皇帝赠杨时左大中大夫诰,翰林学士直史馆范冲行词)的美誉。杨时的这种“网罗百家”的学风为朱熹所继承,朱熹自称“会众说而折其中”(《中庸章句序》)。后人称二程朱熹学说为朱学派、程朱理学;认为朱熹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是孔子之后又一个集大成者,以二程思想为主流,并吸收和融汇其他学派的思想,是闽学的一大特点,就这个特点看,杨时实导闽学之前路。
“所造亦只是在善人有恒之间”(《宋元学案·豫章学案》)的罗从彦,在其《圣宋遵尧录》《杂著》《议论要语》等著作中,贯穿了立“正学”、摒“邪说”的道统论思想。罗从彦很赞同杨时所说的“学者先明‘五经’,然后学《春秋》,则其用利矣”,因为“五经论其理,《春秋》见之行事。《春秋》,圣人之用也”。罗从彦言必称孔孟,并认为“知《大学》之渊源,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中庸》之书……此圣学之渊源,六经之奥旨”。(《罗豫章集》卷12)立五经、四书为经典,是两宋理学“道统论”的重要表现。这个由二程开其端,杨时继续发挥,罗从彦身体力行的事业,是由朱熹来完成的。朱熹力主“道统论”,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语类》卷93)朱熹完成《四书集注》、组织五经诠释,可谓捍卫道统不遗余力。从这方面看,罗从彦和朱熹的继承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
李侗对朱熹耐心诱导,向他灌输“理一分殊”说,这从朱熹记叙的《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书来看是一目了然的。程颐答杨时时提出的“理一分殊”说,杨时心领神会,“释然无疑”,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龟山集》卷20)李侗在引导朱熹理解“理一分殊”说时,认为应该“在知字上用著力”,并指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要见一视同仁气象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在李侗指引下,朱熹侃侃而谈,大段议论。李侗在关键处精心“提破”。在李侗看来,天地万物“有有血气者,有无血气者”,本乎一源,“更应在此体究”。他指示朱熹对“理一”“须从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看为可”。朱熹对“分殊”的推演,李侗批曰:“推测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尝不见道也。某心甚慰。”朱熹从学于李侗,李侗给罗博文的信中说:“渠初从谦开善(僧人一笔者注)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处。”李侗称赞朱熹“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论难体认至切,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益深矣”。(《延平答问》)李侗对朱熹的启迪和诱导,对朱熹接受、继承和发展二程的思想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综上所述,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经历了几代人。杨时,“道南”为理学在福建播下种子,历经“最无气焰”(《宋元学案·豫章学案》)的罗从彦和“不著书、不作文”(《李延平集》卷3)的李侗,最终出现理学的完整体系“朱子之学”即“闽学”。这是理学长期酝酿直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杨时的思想“似别立一家”(《语类》卷101),但却是很关键的中间环节,从这里可以吸收经验教训、酝酿新的突破。罗从彦、李侗虽学术成就不大,但传道有功。失掉杨、罗、李三先生这个中间环节,朱熹要从“杂博”的学识中、要从佛道思想中摆脱出来,必将经历不同的路程。总之杨时“道南”导致朱熹“闽学”——理学体系的完成,南剑三先生实开闽学之先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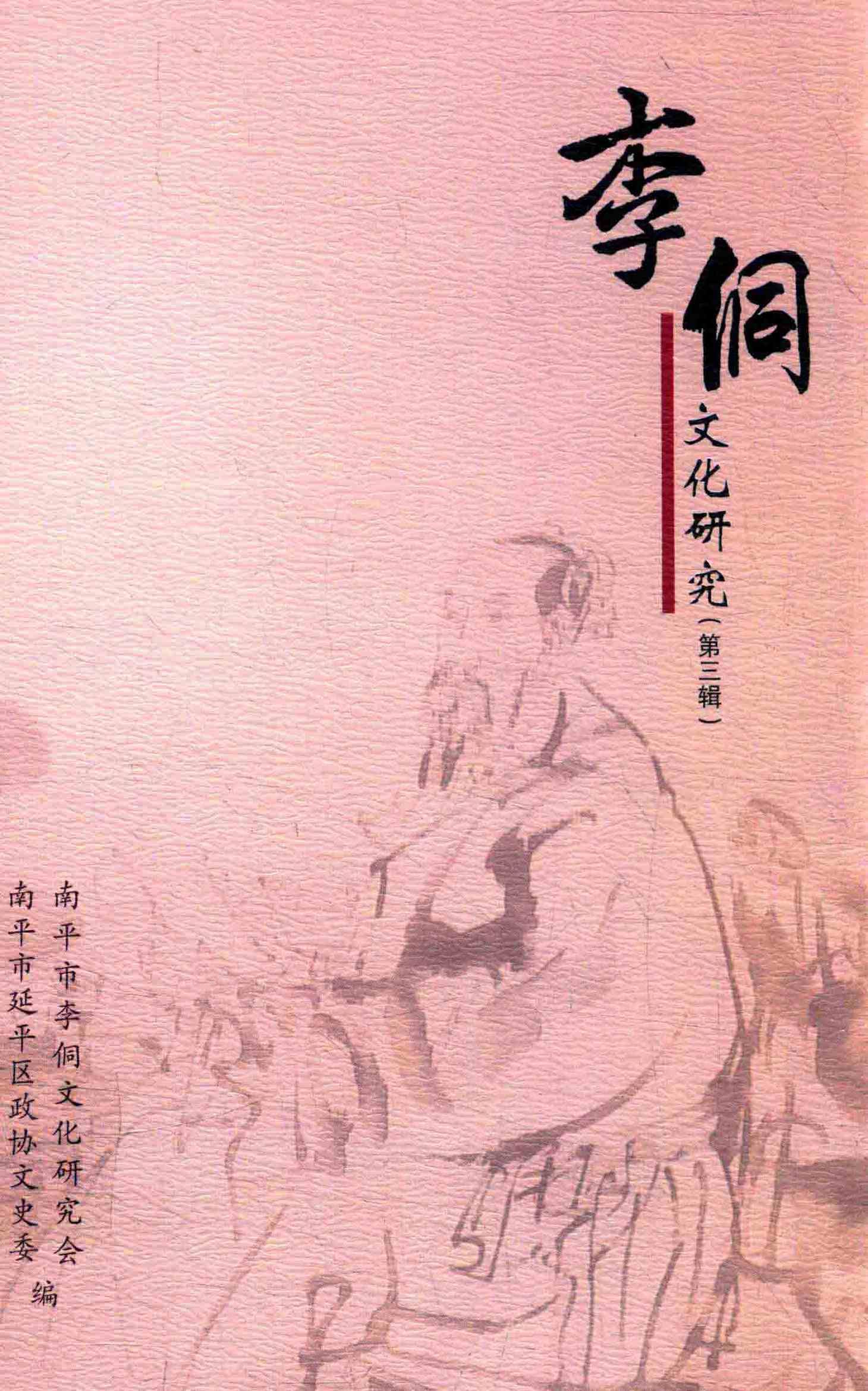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
相关人物
何乃川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