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熹未契李侗“未发气象”。而主“心贯未发涵养已发省察”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291 |
| 颗粒名称: | (三)朱熹未契李侗“未发气象”。而主“心贯未发涵养已发省察”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5 |
| 页码: | 38-42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记述了这里很形象地说明了朱熹的“心统性情”。朱熹由古代的尊天上升到讲理。孔子时而释天为自然界,含糊其辞。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断定天是有意志的。朱熹认为,天不外是苍苍之形体,而天意是理。这就摒弃了原先对天认识的宗教神秘色彩。他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天即理。是朱熹理学的哲学本色。由此,他把人们对天的认识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
| 关键词: | 李侗 朱熹 哲学 |
内容
朱熹早年依据李侗的教导,体会所谓“未发气象”,始终未能契入逆觉体证之路。朱熹后来回忆说: 当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及其也,渐次昏暗淡泊;又久则遂泯灭,而顽然如初无所睹。此无他,所见者,非卓然真见遗体之全,特因闻见揣度而知故耳。
这说明朱熹对李侗所谓“未发”说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并且还提出批评,如说“罗先生说(按指教人静坐)终恐有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李侗“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若一向如此(按指静坐),又似坐禅入定”,等等。这样,朱熹对程颢、杨时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未有真实契会。今人刘述先说: 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延平)即为朱子之业师但朱予并未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来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朱子所发展的是一心性情之三分架局。性即是理,而心是情,心统性情。这套思想的背景则是一理气二元不离不杂之形上学。理是超越而永恒的。气则是内在而具体的。性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爱、情是气。心是气之精爽者,具众理而应万事。
这就是朱熹别走蹊径直承程颐的思路。朱熹曾说,“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程颐)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 朱熹的思想结构是“心统性情、理气不离不杂”。他认为,性是理,心是气之灵,情是心气之发或之变,此便是“心性情三分”。仁只是性、只是理,恻隐之心与爱之情则属于气:谓“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表示仁不是心、不是爱,只是“爱之所以然的理,而为心所当具之德”。这样,仁只成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理,而不再是具体的活泼泼的生生之仁。仁这个“理”,必须通过心知之明的静涵后方能为心所具;仁这个“德”亦须通过心气之摄具此理,方能成为心自身之德。这就是说,德由理而转成,理不寓于心则不能成德。“心统性情”,统为统摄、统贯义,非统帅、统属义。心统性。是认知地、关联地统摄性而彰显之。这是心即统贯于“未发”之性。心统情,是行动地统摄情而敷施发用。这是心发出情,心统贯于“已发”之情。
对于朱熹的“心统性情”说,金春峰说: 用比喻说,朱熹讲的“心统性情”,犹如一自动切削车床。
车床的切削活动是情,属于形而下之经营造作;其自动切削活动之原理,相当于性;车床相当于心,是具此理而统性情者。自动车床之切削活动是中性无色的,其活动之“所以然”之理亦是中性无色的,因而是一纯自然系统。冯(友兰)先生说,朱熹讲的情犹如飞机之灾际的运动,飞机之所以如此运动之规律或所以然是“理”,心则是此理之认知者。但心仅能认识此飞机之“理”,而非统飞机活动之“情” 这里很形象地说明了朱熹的“心统性情”。朱熹由古代的尊天上升到讲理。孔子时而释天为自然界,含糊其辞。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断定天是有意志的。朱熹认为,天不外是苍苍之形体,而天意是理。这就摒弃了原先对天认识的宗教神秘色彩。他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天即理。是朱熹理学的哲学本色。由此,他把人们对天的认识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朱熹进一步指出,理离不开气,理气是不离不杂的。理属形而上,气属形而下,这个介限不能混杂;而理寓于气,理离开了气就无挂搭处。朱熹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有理,然后有气;必禀此性,然后有形。
在朱熹看来,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是静态的形而上实有,只存有不活动,不能妙运气化生生;气则能依理而行,凝结造作。
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有一套修养工夫;因心不是理,为了使心能够合乎理,需要涵养。不是涵养本心性体,而是肃整庄敬之心,汰滤私意杂念。通过逐渐涵养,达到“镜明止水”、心静明理。这叫作“涵养敬心”。静时涵养敬心,以求近合“未发”之“中”;动时察识情变,以期至“中节”之“和”。这叫作“静养动察”。无论静时动时,皆以“敬”贯串;敬既立于存 养之时,即涵养于“未发”;亦行于省察之间,即察识于“已发”。这叫作“敬贯动静”。而由察识工夫再推进一步,便是致知格物以穷理。
朱熹后学明确把朱熹这套修养功夫概括为治心之学。如明初朱子学家陈真晟(1411-1473)的《心学图说》。陈真晟说:
先讲求夫心要。心要既明则于圣学工夫已思过半矣,盖其心体是静坚固而能自立,则光明洞达作得主宰。所以一心有主,万事有纲,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之要得矣,然后可依节目补小学、大学工夫,而其尤急务则专在于致知诚意而已,皆不外乎一敬以为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功,则皆有自得之实矣。
陈真晟《心学图说》的心学思想是: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是谓之(善)性(五常之性);性为利欲所惑,“法天之当然是性之复”;复性需主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即知行,此即是一动一静在于理质言之,就是天理——善性、复性——敬(存心)、义(知行)。他认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二者为为学之要。主敬即存心,择义即致知。道体极乎其大,非存心无以极其大;道体极其微,非致知无以尽其微。静而涵养致知,动而慎独诚意,使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己,则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是美之至因外美而益充内美,发而为至美。这是陈真晟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发掘。
对于朱子学的心学,清张伯行在讲到陈真晟时有段深刻的分析: 或问余曰:“陈布衣(陈真晟)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之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尧舜以讫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迄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则为敬,在释氏言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 明人郑普在《布衣陈先生传》中把陈真晟的思想体系概括为“治心修身”四字,是十分确当的。陈真晟在《答耿斋周轸举人书》中说“治心修身”是程朱之学的要法,是治程朱之学的入门要道。
这说明朱熹对李侗所谓“未发”说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并且还提出批评,如说“罗先生说(按指教人静坐)终恐有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李侗“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若一向如此(按指静坐),又似坐禅入定”,等等。这样,朱熹对程颢、杨时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未有真实契会。今人刘述先说: 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延平)即为朱子之业师但朱予并未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来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朱子所发展的是一心性情之三分架局。性即是理,而心是情,心统性情。这套思想的背景则是一理气二元不离不杂之形上学。理是超越而永恒的。气则是内在而具体的。性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爱、情是气。心是气之精爽者,具众理而应万事。
这就是朱熹别走蹊径直承程颐的思路。朱熹曾说,“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程颐)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 朱熹的思想结构是“心统性情、理气不离不杂”。他认为,性是理,心是气之灵,情是心气之发或之变,此便是“心性情三分”。仁只是性、只是理,恻隐之心与爱之情则属于气:谓“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表示仁不是心、不是爱,只是“爱之所以然的理,而为心所当具之德”。这样,仁只成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理,而不再是具体的活泼泼的生生之仁。仁这个“理”,必须通过心知之明的静涵后方能为心所具;仁这个“德”亦须通过心气之摄具此理,方能成为心自身之德。这就是说,德由理而转成,理不寓于心则不能成德。“心统性情”,统为统摄、统贯义,非统帅、统属义。心统性。是认知地、关联地统摄性而彰显之。这是心即统贯于“未发”之性。心统情,是行动地统摄情而敷施发用。这是心发出情,心统贯于“已发”之情。
对于朱熹的“心统性情”说,金春峰说: 用比喻说,朱熹讲的“心统性情”,犹如一自动切削车床。
车床的切削活动是情,属于形而下之经营造作;其自动切削活动之原理,相当于性;车床相当于心,是具此理而统性情者。自动车床之切削活动是中性无色的,其活动之“所以然”之理亦是中性无色的,因而是一纯自然系统。冯(友兰)先生说,朱熹讲的情犹如飞机之灾际的运动,飞机之所以如此运动之规律或所以然是“理”,心则是此理之认知者。但心仅能认识此飞机之“理”,而非统飞机活动之“情” 这里很形象地说明了朱熹的“心统性情”。朱熹由古代的尊天上升到讲理。孔子时而释天为自然界,含糊其辞。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断定天是有意志的。朱熹认为,天不外是苍苍之形体,而天意是理。这就摒弃了原先对天认识的宗教神秘色彩。他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天即理。是朱熹理学的哲学本色。由此,他把人们对天的认识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朱熹进一步指出,理离不开气,理气是不离不杂的。理属形而上,气属形而下,这个介限不能混杂;而理寓于气,理离开了气就无挂搭处。朱熹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有理,然后有气;必禀此性,然后有形。
在朱熹看来,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是静态的形而上实有,只存有不活动,不能妙运气化生生;气则能依理而行,凝结造作。
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有一套修养工夫;因心不是理,为了使心能够合乎理,需要涵养。不是涵养本心性体,而是肃整庄敬之心,汰滤私意杂念。通过逐渐涵养,达到“镜明止水”、心静明理。这叫作“涵养敬心”。静时涵养敬心,以求近合“未发”之“中”;动时察识情变,以期至“中节”之“和”。这叫作“静养动察”。无论静时动时,皆以“敬”贯串;敬既立于存 养之时,即涵养于“未发”;亦行于省察之间,即察识于“已发”。这叫作“敬贯动静”。而由察识工夫再推进一步,便是致知格物以穷理。
朱熹后学明确把朱熹这套修养功夫概括为治心之学。如明初朱子学家陈真晟(1411-1473)的《心学图说》。陈真晟说:
先讲求夫心要。心要既明则于圣学工夫已思过半矣,盖其心体是静坚固而能自立,则光明洞达作得主宰。所以一心有主,万事有纲,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之要得矣,然后可依节目补小学、大学工夫,而其尤急务则专在于致知诚意而已,皆不外乎一敬以为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功,则皆有自得之实矣。
陈真晟《心学图说》的心学思想是: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是谓之(善)性(五常之性);性为利欲所惑,“法天之当然是性之复”;复性需主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即知行,此即是一动一静在于理质言之,就是天理——善性、复性——敬(存心)、义(知行)。他认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二者为为学之要。主敬即存心,择义即致知。道体极乎其大,非存心无以极其大;道体极其微,非致知无以尽其微。静而涵养致知,动而慎独诚意,使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己,则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是美之至因外美而益充内美,发而为至美。这是陈真晟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发掘。
对于朱子学的心学,清张伯行在讲到陈真晟时有段深刻的分析: 或问余曰:“陈布衣(陈真晟)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之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尧舜以讫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迄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则为敬,在释氏言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 明人郑普在《布衣陈先生传》中把陈真晟的思想体系概括为“治心修身”四字,是十分确当的。陈真晟在《答耿斋周轸举人书》中说“治心修身”是程朱之学的要法,是治程朱之学的入门要道。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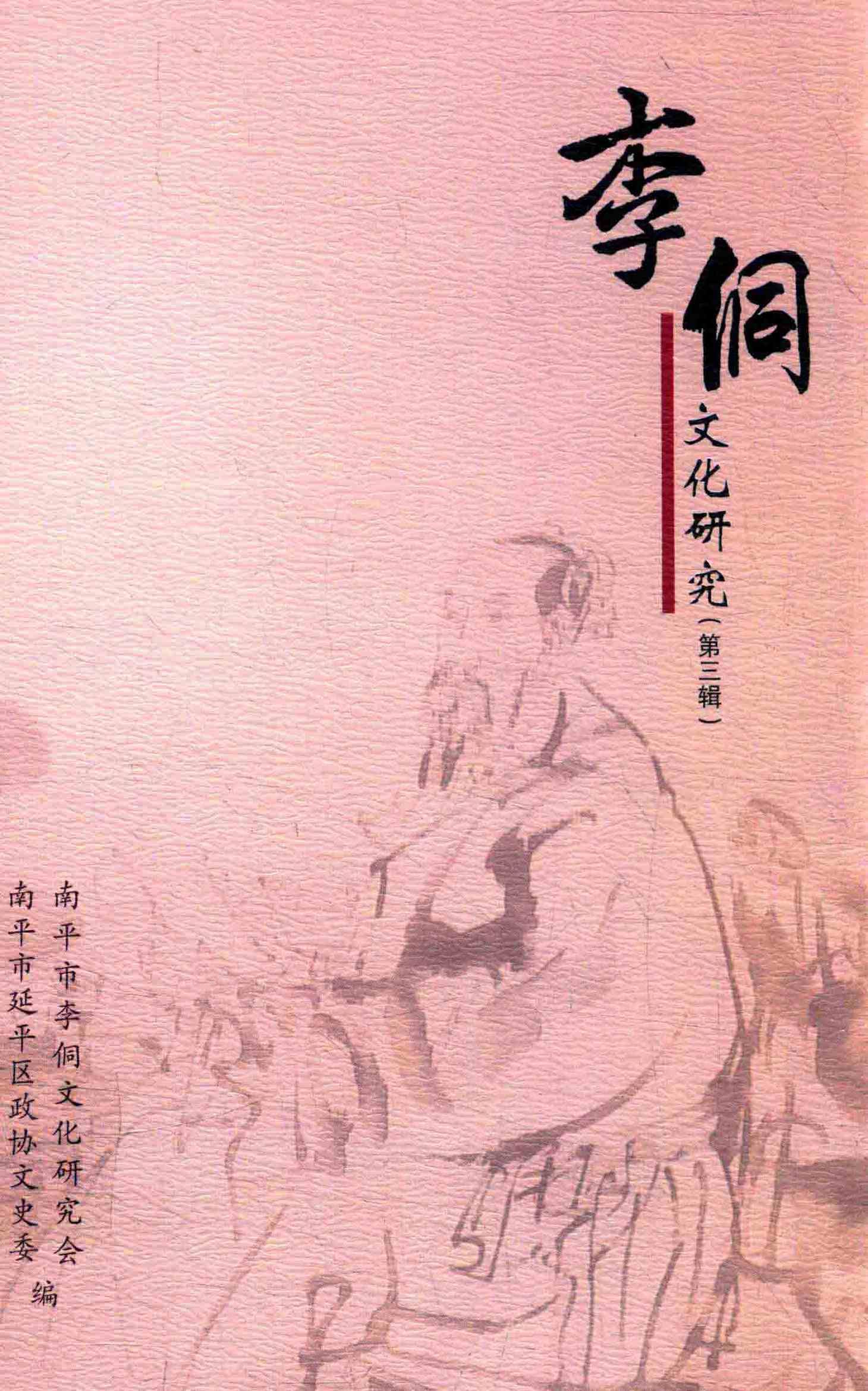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
相关地名
李侗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