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李侗是杨时的二传弟子,他24岁从郡人罗从彦学,之后传给一代宗师朱熹。虽然李侗“不著书,不作文”,但他的“语默动静,端详闲泰”深得学者推崇,人们用“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称誉李侗,清初康熙帝更御书“静中气象”称誉其精神品格。不过,近年来学者对李侗的研究多偏重于理学对朱熹的影响,而对其“静中气象”的文化蕴涵却未作深入的考察。笔者认为,李侗对朱熹理学的影响固然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包含着李侗“静中气象”的为学功夫。因此,有必要对李侗“静中气象”文化蕴涵作深入的考察,以洞察这位理学宗师精神品格的概貌。
“气象”一词是传统儒学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泛指人的精神品格,包括气度、气质、风度、风范等,是对儒家中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的褒扬。如程子在《论语》注中说:“先观二子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天地气象。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第93页,岳麓书社2004年)孔子和颜渊、子路三人各谈志向,程子认为孔子的志向比颜渊、子路高,因为他的志向具有“圣贤气象”。“气象”既有称誉人的整体精神,也用于褒扬某一方面的精神境界,如二程说“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朱熹、吕祖谦编,查洪德注译《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第43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只注书名),这是对诸葛亮人格精神的高度概括;“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同上,第430页),这是对孟子岩骨之风的称赞。“南剑三先生”、“延平四贤”中,除了李侗被称誉为“静中气象”外,还有杨时的“和平气象”;而罗从彦的“奥学清节”,实际上也是一种“气象”,二者都是褒扬某一方面的精神品格。
“静中气象”是康熙帝对李侗道德情操和精神品格的高度褒扬,但“静中”有何“气象”,这个“气象”具有什么文化蕴涵没有说明,只能从文本中李侗的生活、治学中加以考察:笔者认为,李侗的“静中气象”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静中气象”是一个偏正词组,“气象”是中心词,“静中”是对中心词的限定,因此“静”是“气象”的过程,是“气象”的酿造;“气象”是“静”的结果,是“静”的呈现。李侗之“静”是其理学的表现方式,其中蕴含着深邃的为学功夫。
一、“静中”存养功夫
传统儒学期望建立大同社会,而建立大同社会须从一个个家庭开始,从个人修身开始,而存养是修身的重要门径。李侗的“静中气象”首先表现在存养功夫,而“静”是其存养的重要方式。
“静”是中国古代道释儒三教中有着特殊含义的修身方法,道教以静虚作为养生方法,强调静中体道入道、长生不老;禅宗以禅定作为修身功夫,强调心一境性、见性成佛。汉代以后至唐代,出现道释儒三教合一、三教并立的局面,儒家学者多受影响。虽然宋代的理学家反对道佛,但在体悟儒家义理之前有过沉迷道释的经历,并且认为以静修身方法有会通处。
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汉字之一,许慎《说文》:“静,审也。从青,争声。”徐锴注解说:“丹青明审也。”王筠句读:“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可见,静的最初意思是“明审”。其它义项如安静、宁静、无声之静、贞正之静、洁净之静等都是由此引伸出来的。《礼记》是一部先秦至两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有人还将其视为一部儒学论文汇编,其中“乐记”记载:“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王安石解释说,“性者,有生之大本”。(《王安石集》卷六十八《论议·原性》)性即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以下简称《语类》)可见,静是人的本性,人生之初性本静。
李侗之“静”来源于先前的数位理学家,而这些理学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佛老倾向。《宋元学案·豫章学案》说:“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二程在创立理学过程中,就曾悟得佛学,援佛会儒,其中对佛教静坐修身方法颇为推崇,程颢就说“性静者可以为学”(《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第105页),并且“性静”可以通过静坐进修而成。《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载:谢良佐“往扶沟见明道受学,甚笃。明道一日谓之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杨时受学于二程,受佛教影响也颇深,虽然程颐称赞杨时和上蔡(谢良佐)坚守儒学,不流于夷狄,但这只是程颐一时之见,事实上杨、谢二人都杂夹佛学,并且程度相当。清人全祖望说:“龟山之夹杂异学,亦不下于上蔡。”(《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异学”就是佛学,因为它来源于异域印度,不是中国所产。《宋元学案》同时说杨时是位醇儒,又说“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同上)罗从彦初学于吴仪,崇宁初到将乐师事杨时。因得知洛阳二程,“鬻田裹量(粮),往洛见伊川”,之后又从杨时学。建炎四年,授惠州博罗县主簿。任满,入罗浮山静坐,以穷经为学。罗从彦认为“佛氏之学,端有悟入处。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同上,卷三十九《豫章学案》)他肯定赵普对太宗所言可“以尧、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同上)可见,静坐是一种会通道释儒三教的修身方法,而且罗从彦直承二程和杨时静坐修身进德方法后又传给了李侗。
不过,二程在穷理方法上有所区别,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同上),“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语类》卷十八)李侗强调正心诚意的“主静”,并以静修身,以静养心,他说罗从彦教他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不惟于进学有方,亦是养心之要。”(《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继承师说,并作深入阐发,他说:“天性生生之机,无时或息,故放失之后,少间又发,第人不肯认定,以此作主宰耳。认得此心,便是养。”(同上)当然,李侗对以静养心有一个认识过程。他初师罗从彦时,对罗氏的静坐方法颇有疑议。朱熹说:“尝见李先生说,‘旧见罗先生云:‘说《春秋》颇觉未甚惬意,不知到罗浮极静后,义理会得如何。’某心尝疑之以今观之,是如此。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义理出?’”(同上)罗浮即罗浮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的岭南道教名山,文人墨客、方士道人多于此优游闲养、隐居和修炼。李侗觉得即便罗从彦达到道人的静虚后,能否贯通儒家的义理还是值得怀疑。但李侗亲炙罗从彦多年,承其师衣钵。李侗说“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同上)这种存养功夫深得罗从彦称许,认为李侗修身存养,能够“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存养须“静”,而“静”须除却杂念,专念一虑。李侗得罗从彦真传之后,40多年谢绝世故,一心默坐澄心,即使“箪瓢屡空,怡然有以自适也”。(《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认为,问学之道.不在多言,“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同上),学者应在存养涵养处下功夫。而“静”就是不为他事干扰,才能“截然不可犯”。(《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朱熹对李侗的涵养观察十分细致,他说“李先生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朱熹还例举李侗生活中走路、叫人、观壁上字三个例子:说一般人走近路稍缓,走远路稍急,而李侗却近远无别;一般人叫人叫两三声不到声必厉,而李先生叫人不到却声不加于前;朱熹见壁上有字必抬头察看,而李先生静坐时不看,看则走近视之。可见,李侗治学方法是口到、眼到、心到,默坐澄心,静处存养,然后细细揣磨。李侗还提出要“静中”养气,而养气要心气合一,心之所向,全气随之。他说:“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不然,心是心,气是气,不见所谓集义处,终不能合一也。”(同上)
李侗师事罗从彦,除了所学有《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外,还练就了存养涵养修身功夫。沙县邓迪在朱松面前夸奖说:“愿中(李侗之字)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后人还把宋黄庭坚称赞周茂叔(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用来称誉李侗:这些既是对李侗存养气象的赞赏,也是对李侗人生品格的肯定。
二、“静中”格物功夫
“静”作为理学哲学思想体系的概念,与“动”相结合,构成宇宙本体论的两极。“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极立焉”。(周敦颐《太极图说》)
李侗之“静”,是哲学上所说的相对之“静”,而哲学之“静”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人们把李侗的“静中”精神品格称为“澄心”。澄心就是使心情清静的状态,源出《文子·上义》:“老子曰:‘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晋代陆机《文赋》:“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澄心定意为的是格物致知,理学家的格物先从“理一分殊”开始。杨时南传理学,对“理一分殊”“豁然无疑”(《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但杨时的理解是“知其理一,知其分殊”(《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其认识论具有均衡性。
默坐澄心的李侗也强调格物致知,但方法是在“静中”格物,从文本看,李侗之“静”呈现出诸多格物致知的气象。李侗在穷“理一分殊”之理时不同意杨时的看法,他不仅很有见地地提出“理一分殊”是儒家与佛教的根本区别:“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同上),而且强调“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同上)在理学家眼里,“理一分殊”被视为体用之学,李侗勉力朱熹要在体用上下功夫。他说:“近日涵养,必见应事脱然处否?须就事兼体用下工夫,久久纯熟,渐可见浑然气象矣。勉之!勉之!”(同上)李侗既细察形上之体,又注重形下之用,比杨时的理解更进一步,也更具时代意义。因为,理学家之所以将理学思想上升为本体地位,最终的目的在于治用,与《尚书》所说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相契。李侗强调格物致知,要反复推究其理,“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也不能“以口舌争也”。(同上)
“静”既是存养功夫,也是格物致知功夫。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上蔡亦言多着静不妨”。(同上)但静动须互发,有静有动,方可格物以至其知。“静”是学者入门之功,如果喘汗未定,没有冥心至静,难见端倪。但“不是道理只在静处”、“若一向静中担阁,便为有病”(同上),必须冥心至静后动静合一。
儒家之静不是道教的无为之静,而是内向修身的明审之静。李侗继承先辈理学家格物致知的动静观,动中有静,静而不滞。朱熹师从李侗时,就见“先生(李侗)终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无颓堕之气”。(同上)李侗的动静观强调五个方面:一是多在“静”中思。罗从彦教育李侗:“学道以思为主。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书》曰:‘思作睿,睿作圣。’‘惟狂克念作圣。’佛家一切反是。”(同上)心的功能是思考、思维。李侗从中得到启发,以静养心,在静中思考,思考通于微密,一心向圣。二是要有琢磨之功。朱熹见证了李侗性格气质的变化过程:“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同上)又说:“李先生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琢磨之功。”(同上)可见,少年时期的李侗血气方刚、豪迈英勇,通过修身养性,性格趋静,并以此为格物之方。上述记载还让我们看到宋代闽北有趣的社会生活和李侗静默澄心后的性格。(1)出行骑马。闽北地方志书记载当地地理为山行水处,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舟船,而李侗出行则骑马,而且速度之快。(2)静默澄心后的李侗一改往日豪迈、喜饮酒的性格,转而变成一位深沉蕴藉而又超凡脱俗的学者,连走路都委蛇慢步、随顺顺应、雍容自得,一幅憨态可掬之貌。三是力戒只求文字。李侗要求,学习不能只求文字,或只是强记硬诵,以资诵说,否则等于“玩物丧志”。因此他要求“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四是循序少进。李侗不仅随人深浅施教,对学生问答不倦,而且提出熟读精思的为学功夫,“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同上)五是要融会贯通。李侗认为,格物致知要在日用之间消化吸收,才能有了然之悟。他说:“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同上)师生之间、学友之间要相互切磋,心境才能洒脱畅快,学问才能融释贯通。
总之,李侗继承理学家的动静观,动静相互交替,又相互发明,在静默存养间,静中勤思,静中琢磨,体现出深厚的格物致知功夫。
三、“静中”体认功夫
李侗把“静”作为修养功夫,在“静”中格物致知,致知在穷理,于事事物物中体认理或天理,这是李侗“静中”功夫的根本目的。
“理一分殊”是理学家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框架,理学家们试图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天理的哲学意义,以此作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准则。但是“理一”好理解,“分殊”难理解,究其原因是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太极者,理也。就是说宇宙总起来有一个共通的理,万事万物又各有其特殊之理,“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伊川易传》卷三)是理学家的孜孜追求。因此,李侗告诉学者只讲“理一”,而不讲其“分之殊”,会“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但是,当时未入理学门墙的朱熹对此多为不解,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在赴同安主簿任途经延平拜李侗为师时,对他的观点就“疑而不服”。(《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朱熹认为:“天下之理,一而已,何为多事若是!”(同上)同安任满后,朱熹返回武夷山五夫治学,反复研究思考李延平所谓“理一易”“分殊难”,才明白李侗之言是正确的。
“理一分殊”被称为体用之学,“体”就是宇宙本体论的本,用就是“分殊”,理学家研究这一哲学命题在于“理”能够贯穿于“理一分殊”始终,即本如何通达于治用,治用如何呈现本体思想。《文子·上义》:“老子曰:‘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在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反于虚无,可谓达矣。’”李侗“静中气象”的本质说到底就是静中体认天理:他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同上)黄宗羲说朱熹为学时常“思延平(李侗)默坐澄心,其起手皆从理一。穷理者,穷此一也。所谓万殊者,直达之而已矣。若不见理一,则茫然不知何者为殊,殊亦殊个甚么,为学次第,鲜有不紊乱者。”(同上)也就是说,为学次第以理一为先,分殊为后,凡事先有一个理,然后“直达”万殊,而万殊之理,又“末复合为一理”。(《二程遗书》卷十四)
理或理一,在自然为规律,在社会则为准则,而仁是本体论的核心,义是仁的表现。“‘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二句乃是于发用处该摄本体而言,因此端绪而下工夫以推寻之处也”。(《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提出学者要“理会分殊”,就是本体的仁在“分殊”发用时要复合无间。他说:“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同上)因此,李侗认为在探索义理时,要扫去纷乱窒塞处,教胸中空荡荡,才能自觉有下落处。久而久之,便能“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同上)朱熹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同上)中节就是中和、适度,“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周敦颐《通书·师第七》)未发是性,性即理,是人天生的资质,已发为情为用。喜怒哀乐未发时不喜不怒、无哀无乐、不偏不倚的心境,叫“中节”;“发而皆中节”叫“和”,就是朱熹《中和说二》中说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如果不能虚一而静,气胜于心,就不能成己成物,未发时不适度,已发就谈不上和。李侗说:“虚一而静。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同上,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因能悟理一之本,即使“品节万殊,曲折万变”,没有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理,如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同上)李侗的“融释”类似于佛教华严宗的“圆融”,是天人合一、性情融合的最佳境界。朱熹解释李侗动静体仁说:“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则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则感而未尝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同上,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
分明“理一分殊”在于治用。李侗虽一生未做官,且40多年闲居乡村,似乎过着寂然像一个田夫野老的生活,但他的思维并非游离于世事之外。他在“静中”观察世事,洞察世事,虽平常闲居,若无意于世事,但内心却伤时忧国,谈论时事感激动人。南宋鄞县人王深宁(即王应麟)说:“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同上,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的治用措施具体有二:一是振三纲、明义利。他曾说:“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意思是说三纲、义利不能在社会上形成“上下之气”,要求朝廷要加以重视,使内外一体。但李侗把义利不分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说明他的思想具有保守的一面。二是提出“三本”。理学家所说的本有“大本”、“小本”,如儒家把人伦看成是体用之道,是“学问之大原”,而人伦中又以孝为先,是“百行之原”、“五伦之本”。李侗根据当时“上下之气间隔”、义利不分衍生的社会弊端,提出天下有三本:即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三者缺一不立。在这里,父生、师教、君治是小本,通过小本之治,也能实现一定时期社会的有序发展。难怪李侗不仅强调明“理一”,更要理会“分殊”。没有深入体察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事物的矛盾,难以理会物物之“太极”。因此,朱熹评论李侗:“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民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同上)李侗静中体认天理具有相当的水平。
总之,李侗的“静中气象”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诸多文化蕴涵,“静中”体现的是存养格致功夫,“气象”是存养格致功夫的显现,最终目标是体认天体,实现儒家提倡的社会大同。
(罗小平:福建省南平市台办调研室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朱子文化》2011年第4期)
“气象”一词是传统儒学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泛指人的精神品格,包括气度、气质、风度、风范等,是对儒家中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的褒扬。如程子在《论语》注中说:“先观二子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天地气象。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第93页,岳麓书社2004年)孔子和颜渊、子路三人各谈志向,程子认为孔子的志向比颜渊、子路高,因为他的志向具有“圣贤气象”。“气象”既有称誉人的整体精神,也用于褒扬某一方面的精神境界,如二程说“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朱熹、吕祖谦编,查洪德注译《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第43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只注书名),这是对诸葛亮人格精神的高度概括;“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同上,第430页),这是对孟子岩骨之风的称赞。“南剑三先生”、“延平四贤”中,除了李侗被称誉为“静中气象”外,还有杨时的“和平气象”;而罗从彦的“奥学清节”,实际上也是一种“气象”,二者都是褒扬某一方面的精神品格。
“静中气象”是康熙帝对李侗道德情操和精神品格的高度褒扬,但“静中”有何“气象”,这个“气象”具有什么文化蕴涵没有说明,只能从文本中李侗的生活、治学中加以考察:笔者认为,李侗的“静中气象”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静中气象”是一个偏正词组,“气象”是中心词,“静中”是对中心词的限定,因此“静”是“气象”的过程,是“气象”的酿造;“气象”是“静”的结果,是“静”的呈现。李侗之“静”是其理学的表现方式,其中蕴含着深邃的为学功夫。
一、“静中”存养功夫
传统儒学期望建立大同社会,而建立大同社会须从一个个家庭开始,从个人修身开始,而存养是修身的重要门径。李侗的“静中气象”首先表现在存养功夫,而“静”是其存养的重要方式。
“静”是中国古代道释儒三教中有着特殊含义的修身方法,道教以静虚作为养生方法,强调静中体道入道、长生不老;禅宗以禅定作为修身功夫,强调心一境性、见性成佛。汉代以后至唐代,出现道释儒三教合一、三教并立的局面,儒家学者多受影响。虽然宋代的理学家反对道佛,但在体悟儒家义理之前有过沉迷道释的经历,并且认为以静修身方法有会通处。
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汉字之一,许慎《说文》:“静,审也。从青,争声。”徐锴注解说:“丹青明审也。”王筠句读:“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可见,静的最初意思是“明审”。其它义项如安静、宁静、无声之静、贞正之静、洁净之静等都是由此引伸出来的。《礼记》是一部先秦至两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有人还将其视为一部儒学论文汇编,其中“乐记”记载:“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王安石解释说,“性者,有生之大本”。(《王安石集》卷六十八《论议·原性》)性即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以下简称《语类》)可见,静是人的本性,人生之初性本静。
李侗之“静”来源于先前的数位理学家,而这些理学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佛老倾向。《宋元学案·豫章学案》说:“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二程在创立理学过程中,就曾悟得佛学,援佛会儒,其中对佛教静坐修身方法颇为推崇,程颢就说“性静者可以为学”(《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第105页),并且“性静”可以通过静坐进修而成。《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载:谢良佐“往扶沟见明道受学,甚笃。明道一日谓之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杨时受学于二程,受佛教影响也颇深,虽然程颐称赞杨时和上蔡(谢良佐)坚守儒学,不流于夷狄,但这只是程颐一时之见,事实上杨、谢二人都杂夹佛学,并且程度相当。清人全祖望说:“龟山之夹杂异学,亦不下于上蔡。”(《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异学”就是佛学,因为它来源于异域印度,不是中国所产。《宋元学案》同时说杨时是位醇儒,又说“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同上)罗从彦初学于吴仪,崇宁初到将乐师事杨时。因得知洛阳二程,“鬻田裹量(粮),往洛见伊川”,之后又从杨时学。建炎四年,授惠州博罗县主簿。任满,入罗浮山静坐,以穷经为学。罗从彦认为“佛氏之学,端有悟入处。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同上,卷三十九《豫章学案》)他肯定赵普对太宗所言可“以尧、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同上)可见,静坐是一种会通道释儒三教的修身方法,而且罗从彦直承二程和杨时静坐修身进德方法后又传给了李侗。
不过,二程在穷理方法上有所区别,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同上),“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语类》卷十八)李侗强调正心诚意的“主静”,并以静修身,以静养心,他说罗从彦教他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不惟于进学有方,亦是养心之要。”(《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继承师说,并作深入阐发,他说:“天性生生之机,无时或息,故放失之后,少间又发,第人不肯认定,以此作主宰耳。认得此心,便是养。”(同上)当然,李侗对以静养心有一个认识过程。他初师罗从彦时,对罗氏的静坐方法颇有疑议。朱熹说:“尝见李先生说,‘旧见罗先生云:‘说《春秋》颇觉未甚惬意,不知到罗浮极静后,义理会得如何。’某心尝疑之以今观之,是如此。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义理出?’”(同上)罗浮即罗浮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的岭南道教名山,文人墨客、方士道人多于此优游闲养、隐居和修炼。李侗觉得即便罗从彦达到道人的静虚后,能否贯通儒家的义理还是值得怀疑。但李侗亲炙罗从彦多年,承其师衣钵。李侗说“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同上)这种存养功夫深得罗从彦称许,认为李侗修身存养,能够“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存养须“静”,而“静”须除却杂念,专念一虑。李侗得罗从彦真传之后,40多年谢绝世故,一心默坐澄心,即使“箪瓢屡空,怡然有以自适也”。(《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认为,问学之道.不在多言,“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同上),学者应在存养涵养处下功夫。而“静”就是不为他事干扰,才能“截然不可犯”。(《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朱熹对李侗的涵养观察十分细致,他说“李先生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朱熹还例举李侗生活中走路、叫人、观壁上字三个例子:说一般人走近路稍缓,走远路稍急,而李侗却近远无别;一般人叫人叫两三声不到声必厉,而李先生叫人不到却声不加于前;朱熹见壁上有字必抬头察看,而李先生静坐时不看,看则走近视之。可见,李侗治学方法是口到、眼到、心到,默坐澄心,静处存养,然后细细揣磨。李侗还提出要“静中”养气,而养气要心气合一,心之所向,全气随之。他说:“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不然,心是心,气是气,不见所谓集义处,终不能合一也。”(同上)
李侗师事罗从彦,除了所学有《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外,还练就了存养涵养修身功夫。沙县邓迪在朱松面前夸奖说:“愿中(李侗之字)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后人还把宋黄庭坚称赞周茂叔(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用来称誉李侗:这些既是对李侗存养气象的赞赏,也是对李侗人生品格的肯定。
二、“静中”格物功夫
“静”作为理学哲学思想体系的概念,与“动”相结合,构成宇宙本体论的两极。“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极立焉”。(周敦颐《太极图说》)
李侗之“静”,是哲学上所说的相对之“静”,而哲学之“静”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人们把李侗的“静中”精神品格称为“澄心”。澄心就是使心情清静的状态,源出《文子·上义》:“老子曰:‘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晋代陆机《文赋》:“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澄心定意为的是格物致知,理学家的格物先从“理一分殊”开始。杨时南传理学,对“理一分殊”“豁然无疑”(《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但杨时的理解是“知其理一,知其分殊”(《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其认识论具有均衡性。
默坐澄心的李侗也强调格物致知,但方法是在“静中”格物,从文本看,李侗之“静”呈现出诸多格物致知的气象。李侗在穷“理一分殊”之理时不同意杨时的看法,他不仅很有见地地提出“理一分殊”是儒家与佛教的根本区别:“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同上),而且强调“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同上)在理学家眼里,“理一分殊”被视为体用之学,李侗勉力朱熹要在体用上下功夫。他说:“近日涵养,必见应事脱然处否?须就事兼体用下工夫,久久纯熟,渐可见浑然气象矣。勉之!勉之!”(同上)李侗既细察形上之体,又注重形下之用,比杨时的理解更进一步,也更具时代意义。因为,理学家之所以将理学思想上升为本体地位,最终的目的在于治用,与《尚书》所说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相契。李侗强调格物致知,要反复推究其理,“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也不能“以口舌争也”。(同上)
“静”既是存养功夫,也是格物致知功夫。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上蔡亦言多着静不妨”。(同上)但静动须互发,有静有动,方可格物以至其知。“静”是学者入门之功,如果喘汗未定,没有冥心至静,难见端倪。但“不是道理只在静处”、“若一向静中担阁,便为有病”(同上),必须冥心至静后动静合一。
儒家之静不是道教的无为之静,而是内向修身的明审之静。李侗继承先辈理学家格物致知的动静观,动中有静,静而不滞。朱熹师从李侗时,就见“先生(李侗)终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无颓堕之气”。(同上)李侗的动静观强调五个方面:一是多在“静”中思。罗从彦教育李侗:“学道以思为主。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书》曰:‘思作睿,睿作圣。’‘惟狂克念作圣。’佛家一切反是。”(同上)心的功能是思考、思维。李侗从中得到启发,以静养心,在静中思考,思考通于微密,一心向圣。二是要有琢磨之功。朱熹见证了李侗性格气质的变化过程:“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同上)又说:“李先生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琢磨之功。”(同上)可见,少年时期的李侗血气方刚、豪迈英勇,通过修身养性,性格趋静,并以此为格物之方。上述记载还让我们看到宋代闽北有趣的社会生活和李侗静默澄心后的性格。(1)出行骑马。闽北地方志书记载当地地理为山行水处,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舟船,而李侗出行则骑马,而且速度之快。(2)静默澄心后的李侗一改往日豪迈、喜饮酒的性格,转而变成一位深沉蕴藉而又超凡脱俗的学者,连走路都委蛇慢步、随顺顺应、雍容自得,一幅憨态可掬之貌。三是力戒只求文字。李侗要求,学习不能只求文字,或只是强记硬诵,以资诵说,否则等于“玩物丧志”。因此他要求“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四是循序少进。李侗不仅随人深浅施教,对学生问答不倦,而且提出熟读精思的为学功夫,“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同上)五是要融会贯通。李侗认为,格物致知要在日用之间消化吸收,才能有了然之悟。他说:“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同上)师生之间、学友之间要相互切磋,心境才能洒脱畅快,学问才能融释贯通。
总之,李侗继承理学家的动静观,动静相互交替,又相互发明,在静默存养间,静中勤思,静中琢磨,体现出深厚的格物致知功夫。
三、“静中”体认功夫
李侗把“静”作为修养功夫,在“静”中格物致知,致知在穷理,于事事物物中体认理或天理,这是李侗“静中”功夫的根本目的。
“理一分殊”是理学家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框架,理学家们试图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天理的哲学意义,以此作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准则。但是“理一”好理解,“分殊”难理解,究其原因是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太极者,理也。就是说宇宙总起来有一个共通的理,万事万物又各有其特殊之理,“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伊川易传》卷三)是理学家的孜孜追求。因此,李侗告诉学者只讲“理一”,而不讲其“分之殊”,会“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但是,当时未入理学门墙的朱熹对此多为不解,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在赴同安主簿任途经延平拜李侗为师时,对他的观点就“疑而不服”。(《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朱熹认为:“天下之理,一而已,何为多事若是!”(同上)同安任满后,朱熹返回武夷山五夫治学,反复研究思考李延平所谓“理一易”“分殊难”,才明白李侗之言是正确的。
“理一分殊”被称为体用之学,“体”就是宇宙本体论的本,用就是“分殊”,理学家研究这一哲学命题在于“理”能够贯穿于“理一分殊”始终,即本如何通达于治用,治用如何呈现本体思想。《文子·上义》:“老子曰:‘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在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反于虚无,可谓达矣。’”李侗“静中气象”的本质说到底就是静中体认天理:他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同上)黄宗羲说朱熹为学时常“思延平(李侗)默坐澄心,其起手皆从理一。穷理者,穷此一也。所谓万殊者,直达之而已矣。若不见理一,则茫然不知何者为殊,殊亦殊个甚么,为学次第,鲜有不紊乱者。”(同上)也就是说,为学次第以理一为先,分殊为后,凡事先有一个理,然后“直达”万殊,而万殊之理,又“末复合为一理”。(《二程遗书》卷十四)
理或理一,在自然为规律,在社会则为准则,而仁是本体论的核心,义是仁的表现。“‘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二句乃是于发用处该摄本体而言,因此端绪而下工夫以推寻之处也”。(《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提出学者要“理会分殊”,就是本体的仁在“分殊”发用时要复合无间。他说:“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同上)因此,李侗认为在探索义理时,要扫去纷乱窒塞处,教胸中空荡荡,才能自觉有下落处。久而久之,便能“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同上)朱熹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同上)中节就是中和、适度,“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周敦颐《通书·师第七》)未发是性,性即理,是人天生的资质,已发为情为用。喜怒哀乐未发时不喜不怒、无哀无乐、不偏不倚的心境,叫“中节”;“发而皆中节”叫“和”,就是朱熹《中和说二》中说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如果不能虚一而静,气胜于心,就不能成己成物,未发时不适度,已发就谈不上和。李侗说:“虚一而静。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同上,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因能悟理一之本,即使“品节万殊,曲折万变”,没有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理,如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同上)李侗的“融释”类似于佛教华严宗的“圆融”,是天人合一、性情融合的最佳境界。朱熹解释李侗动静体仁说:“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则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则感而未尝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同上,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
分明“理一分殊”在于治用。李侗虽一生未做官,且40多年闲居乡村,似乎过着寂然像一个田夫野老的生活,但他的思维并非游离于世事之外。他在“静中”观察世事,洞察世事,虽平常闲居,若无意于世事,但内心却伤时忧国,谈论时事感激动人。南宋鄞县人王深宁(即王应麟)说:“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同上,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的治用措施具体有二:一是振三纲、明义利。他曾说:“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意思是说三纲、义利不能在社会上形成“上下之气”,要求朝廷要加以重视,使内外一体。但李侗把义利不分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说明他的思想具有保守的一面。二是提出“三本”。理学家所说的本有“大本”、“小本”,如儒家把人伦看成是体用之道,是“学问之大原”,而人伦中又以孝为先,是“百行之原”、“五伦之本”。李侗根据当时“上下之气间隔”、义利不分衍生的社会弊端,提出天下有三本:即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三者缺一不立。在这里,父生、师教、君治是小本,通过小本之治,也能实现一定时期社会的有序发展。难怪李侗不仅强调明“理一”,更要理会“分殊”。没有深入体察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事物的矛盾,难以理会物物之“太极”。因此,朱熹评论李侗:“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民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同上)李侗静中体认天理具有相当的水平。
总之,李侗的“静中气象”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诸多文化蕴涵,“静中”体现的是存养格致功夫,“气象”是存养格致功夫的显现,最终目标是体认天体,实现儒家提倡的社会大同。
(罗小平:福建省南平市台办调研室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朱子文化》2011年第4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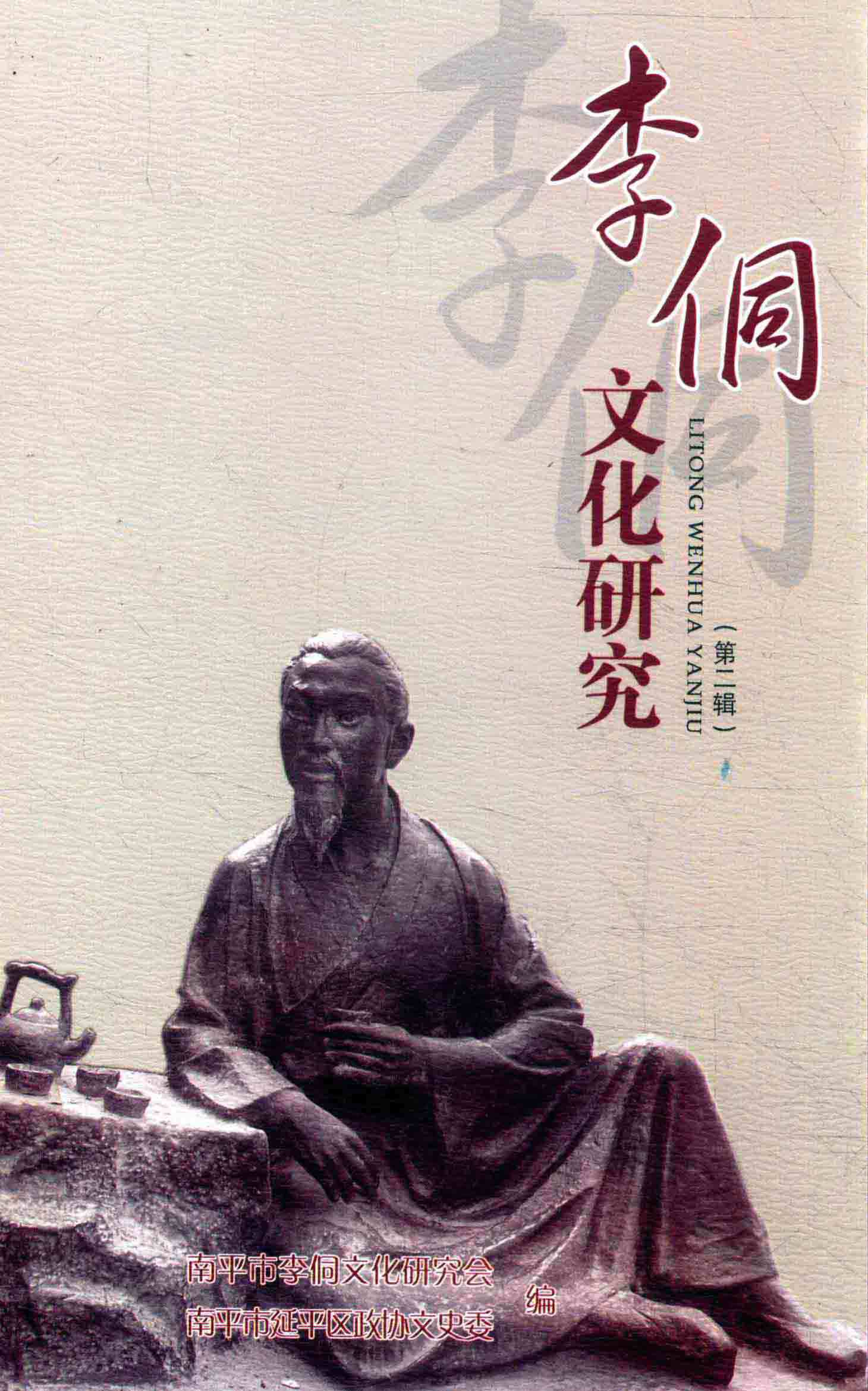
相关人物
罗小平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