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侗“理一分殊”思想新探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第二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160 |
| 颗粒名称: | 李侗“理一分殊”思想新探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8 |
| 页码: | 40-4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李侗“理一分殊”思想新探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思想。 |
| 关键词: | 李侗 理一分殊 思想 |
内容
宋理学大家李侗(1093-1163)字愿中,号延平先生,宋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李侗与朱熹之父朱松是同门好友,闻杨时之弟子罗从彦在杨时处得二程之“不传之学”,于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二十四岁时,慕名而拜罗从彦为师。从而,李侗成为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舍利禄而习二程之理学。李侗继承二程及其杨时、罗从彦理学思想基础上,对理学进行了潜心研究,特别是“理一分殊”学说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思想,这为从二程理学向朱熹闽学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因他的巨大贡献,在宋明理学史上,李侗、杨时及罗从彦被后人称之为“南剑三先生”。
一、“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
“理一分殊”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黎昕《杨时“理一分殊”说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福建论坛》,1986年第2期,第49-53页)早在理学之开山鼻祖周敦颐就曾对“义理”作过重要阐述,之后这一思想成为张载、程颢、程颐等一大批宋明理学家备受推崇的重要思想。李侗处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也即二程与朱熹理学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恰恰是理学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理一分殊”学说也就必然成为李侗哲学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宋明理学史上,“理一分殊”首先是程颐解答杨时对张载《西铭》之疑问而提出来的。而在杨时看来《西铭》虽然对古之圣贤的思想与要义作了大致阐释,但是仅仅言体忽视其用,这将势必会导致墨家的兼爱学说。杨时在《龟山集》卷十六指出:“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正谓此耳。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程颐针对杨时之疑问,作了答复,他认为《西铭》非墨家兼爱之学说,而是“明理一而分殊”。(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9页)同时,程颐具体阐述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在学理上存在的差别。他说:“《西铭》之论,则未然,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同上,第609页)在程颐看来,尽管儒家的仁爱同墨家兼爱都是要求人克己之私,对他人要无私无欲,使他人感受到仁爱,但是从实质和理论上存在根本差别,这表现在儒家仁爱观点体现了“理一”思想,而墨家兼爱观点所体现的是“二本无分”思想。这一差别不仅导致了儒家墨家在学术理论体系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这也是杨时没有真正领悟《西铭》要义的根源,也就是说尽管杨时对《西铭》进行了反复的解读,但是始终没有领悟到其中所蕴涵的“体”与“用”的主旨。杨时在程颐“理一分殊”学说的基础上对此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他独特的“理一分殊”之理论。杨时指出:“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则无事乎推矣。无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何谓称物?远近亲殊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在此,杨时澄清了原来对《西铭》要义之理解与墨家之兼爱相互混淆的观点,从而得出“理一”针对于天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都能以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之心态互相对待,而“分殊”则是相对于这些所有的事物又不能不分主次和亲疏远近用同一种方式对待的独特的观念,他把这独特的观念称之为圣人称物而平施。李侗继承这一观点指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李侗认为,天地万事万物的本原是理,称为“理一”,这个万物之理又是各不相同,称为“分殊”,于是这就解决了“理不患其不一”的问题。在李侗看来,最主要的问题不在“理一”,而在“分殊”。后者朱熹对“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则为墨氏兼爱;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则为杨氏为我。所以言分殊,而见理一底自在那里;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夹杂”,“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朱熹《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4页)可见,朱熹对于李侗“理一分殊”学说是非常重视的。“理一分殊”学说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正是程颐在解答杨时关于《西铭》“言体而不及用”之质疑而提出来,杨时对其进行了阐发,之后经过李侗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与创造性的发挥,使得“理一分殊”学说成为之后理学家重点研究探讨的内容。
二、李侗对“理一分殊”思想的拓展
李侗作为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其“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理学的发展可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离开李侗来谈论朱熹理学贡献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李侗对于“理一分殊”学说的独特阐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一分殊与太极之关系。“理一分殊”思想与佛教华严宗等有着渊源关系,按照学术界一致的意见,华严宗、禅宗以及周敦颐和邵雍的太极学说都曾对此思想有所论及。(朱修春、林凤珍《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32-34页)然而,“理”还没有上升为哲学之最高范畴。在宋代,理学之开山鼻祖周敦颐在《通书》中说“一实万分”,之后张载在《西铭》提出“民胞物与”。在南宋绍圣三年(1096),杨时针对张载《西铭》之要义提出质疑,并与程颐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程颐在解答杨时之疑问时把“理一分殊”作为哲学概念正式提出来,并对《西铭》中之要义进行了深入阐发。杨时就张载《西铭》中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对这种大爱无疆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他看来《西铭》中虽然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提及“仁之用”,也就是说只言“体”而没有言“用”,这样的话就与墨家的爱无差等的兼爱学说类同。程颐就《西铭》之体用问题答复杨时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9页)在程颐看来,理一分殊之思想非墨家之兼爱学说。此后,杨时对“理一分殊”学说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他视野下的“理一分殊”理论。杨时的“理一分殊”思想为他的弟子李侗所继承,李侗进一步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阐释了理一分殊的命题。他认为,太极就是最高之理,是至理之源。他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阂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兖同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与此同时,李侗以二程所提出的最高范畴理去探讨“太极动而生阳”即太极化生万物,描绘出一幅由太极到阴阳到万物与人的壮丽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李侗把理贯穿始终,太极即理,理即太极,两者融为一体,它是统治一切万物之本原。李侗把“太极”与“理”紧密联系起来,使理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内涵。但是,这个所谓的本体是一种精神上的本体。然而,我们不可否认,李侗在太极化生万物的过程中蕴涵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之后朱熹继承杨时、李侗这些观点,用“无形而有理”来阐释“无极而太极”,提出“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朱熹《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2页)在朱熹看来,太极不仅是一理而且也是众理的统一,太极不仅包含着万物整体而且万物又各具于一太极。
(二)理一分殊与仁义之关系。在杨时与程颐就《西铭》之要义共同探讨过程中,杨时就《西铭》中许多未能理解或者说还很混淆的观点及时得到了澄清,并在此基础上杨时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把“理”与封建伦理道德紧密联系起来。在杨时看来,理一与分殊之关系不仅仅是体与用的关系,而且也是仁与义之关系。杨时指出:“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杨时认为,仁义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杨时提出分殊不明,理一不精的观点。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各有不同,不能以相同的方式看待。杨时说“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同上,第269-270页)在此,杨时不仅澄清了原来自己对《西铭》中之要义“言体而不及用”的错误观念,赞成并接受了程颐《西铭》中理一分殊与仁与义相一致的观点而且在程颐的“理一分殊”思想的基础上,他把“理一分殊”思想引入社会现实的道德伦常关系当中,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阐释,论证了亲疏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李侗继承杨时这一思想,在李侗看来,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天理”之体观,他不赞成只是从人身上来看仁也不支持仅仅从天理未发上来看仁,而是认为应该从所有一切有血气的与无血气的人和物,并且“须是兼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为可”(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这样来看仁才可以、才能实现人、万事万物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说“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辩,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同上,第328页)在李侗看来,这个仁自始自终存在于事物的一切发展过程之中,并为人物所固有,它不仅体现了未发也体现了已发。李侗在教导朱熹体认杨时“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是着重强调“要在知字上用著力也”(同上,第332页),也就是要知一切有血气者与无血气者皆根源于理,天地万物也皆属此理。而仁是理的体观,它存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中,而其中由于各自所禀气质存在差异,便具有了各自不同的形式,因而,要知仁、天理现,就要在知上著力。同时,李侗把仁义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他更加注重“亦是如何通过践履,对仁‘下工夫令透彻’‘见得本源毫发之分殊’,进而知‘本源体用兼举处’从而解决‘理一’与‘分殊’,仁与义的同一性问题。”(何乃川、陈进国《论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第52-57页)李侗曾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作过一个评价,朱熹说:“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二句乃是发用处该摄本体而言,……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离乎义之内也。然者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义。”先生(李侗)勾断批云:‘推测到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患不见道也,甚慰甚慰。’”(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从这里可看出,朱熹继承和发挥了杨时、李侗的思想。李侗强调为得之加以涵养,就是要人们摒弃私欲,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就能达到仁。总而言之,李侗的上述阐释其目的也是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阐释,他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看作“天理”之体观,进一步论证了亲疏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把儒家伦理道德抬到了至圣的高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李侗作为从二程理学向朱熹理学转变的重要中介人物,为理学向南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李侗没有同朱熹一样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但是他的理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理一分殊”学说对朱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李侗及其理学思想,任何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如果忽视李侗的理学思想和地位,那么对理学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善的。
(王晓君: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一、“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
“理一分殊”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黎昕《杨时“理一分殊”说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福建论坛》,1986年第2期,第49-53页)早在理学之开山鼻祖周敦颐就曾对“义理”作过重要阐述,之后这一思想成为张载、程颢、程颐等一大批宋明理学家备受推崇的重要思想。李侗处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也即二程与朱熹理学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恰恰是理学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理一分殊”学说也就必然成为李侗哲学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宋明理学史上,“理一分殊”首先是程颐解答杨时对张载《西铭》之疑问而提出来的。而在杨时看来《西铭》虽然对古之圣贤的思想与要义作了大致阐释,但是仅仅言体忽视其用,这将势必会导致墨家的兼爱学说。杨时在《龟山集》卷十六指出:“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正谓此耳。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程颐针对杨时之疑问,作了答复,他认为《西铭》非墨家兼爱之学说,而是“明理一而分殊”。(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9页)同时,程颐具体阐述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在学理上存在的差别。他说:“《西铭》之论,则未然,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同上,第609页)在程颐看来,尽管儒家的仁爱同墨家兼爱都是要求人克己之私,对他人要无私无欲,使他人感受到仁爱,但是从实质和理论上存在根本差别,这表现在儒家仁爱观点体现了“理一”思想,而墨家兼爱观点所体现的是“二本无分”思想。这一差别不仅导致了儒家墨家在学术理论体系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这也是杨时没有真正领悟《西铭》要义的根源,也就是说尽管杨时对《西铭》进行了反复的解读,但是始终没有领悟到其中所蕴涵的“体”与“用”的主旨。杨时在程颐“理一分殊”学说的基础上对此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他独特的“理一分殊”之理论。杨时指出:“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则无事乎推矣。无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何谓称物?远近亲殊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在此,杨时澄清了原来对《西铭》要义之理解与墨家之兼爱相互混淆的观点,从而得出“理一”针对于天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都能以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之心态互相对待,而“分殊”则是相对于这些所有的事物又不能不分主次和亲疏远近用同一种方式对待的独特的观念,他把这独特的观念称之为圣人称物而平施。李侗继承这一观点指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李侗认为,天地万事万物的本原是理,称为“理一”,这个万物之理又是各不相同,称为“分殊”,于是这就解决了“理不患其不一”的问题。在李侗看来,最主要的问题不在“理一”,而在“分殊”。后者朱熹对“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则为墨氏兼爱;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则为杨氏为我。所以言分殊,而见理一底自在那里;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夹杂”,“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朱熹《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4页)可见,朱熹对于李侗“理一分殊”学说是非常重视的。“理一分殊”学说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正是程颐在解答杨时关于《西铭》“言体而不及用”之质疑而提出来,杨时对其进行了阐发,之后经过李侗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与创造性的发挥,使得“理一分殊”学说成为之后理学家重点研究探讨的内容。
二、李侗对“理一分殊”思想的拓展
李侗作为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其“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理学的发展可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离开李侗来谈论朱熹理学贡献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李侗对于“理一分殊”学说的独特阐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一分殊与太极之关系。“理一分殊”思想与佛教华严宗等有着渊源关系,按照学术界一致的意见,华严宗、禅宗以及周敦颐和邵雍的太极学说都曾对此思想有所论及。(朱修春、林凤珍《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32-34页)然而,“理”还没有上升为哲学之最高范畴。在宋代,理学之开山鼻祖周敦颐在《通书》中说“一实万分”,之后张载在《西铭》提出“民胞物与”。在南宋绍圣三年(1096),杨时针对张载《西铭》之要义提出质疑,并与程颐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程颐在解答杨时之疑问时把“理一分殊”作为哲学概念正式提出来,并对《西铭》中之要义进行了深入阐发。杨时就张载《西铭》中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对这种大爱无疆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他看来《西铭》中虽然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提及“仁之用”,也就是说只言“体”而没有言“用”,这样的话就与墨家的爱无差等的兼爱学说类同。程颐就《西铭》之体用问题答复杨时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9页)在程颐看来,理一分殊之思想非墨家之兼爱学说。此后,杨时对“理一分殊”学说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他视野下的“理一分殊”理论。杨时的“理一分殊”思想为他的弟子李侗所继承,李侗进一步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阐释了理一分殊的命题。他认为,太极就是最高之理,是至理之源。他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阂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兖同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与此同时,李侗以二程所提出的最高范畴理去探讨“太极动而生阳”即太极化生万物,描绘出一幅由太极到阴阳到万物与人的壮丽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李侗把理贯穿始终,太极即理,理即太极,两者融为一体,它是统治一切万物之本原。李侗把“太极”与“理”紧密联系起来,使理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内涵。但是,这个所谓的本体是一种精神上的本体。然而,我们不可否认,李侗在太极化生万物的过程中蕴涵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之后朱熹继承杨时、李侗这些观点,用“无形而有理”来阐释“无极而太极”,提出“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朱熹《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2页)在朱熹看来,太极不仅是一理而且也是众理的统一,太极不仅包含着万物整体而且万物又各具于一太极。
(二)理一分殊与仁义之关系。在杨时与程颐就《西铭》之要义共同探讨过程中,杨时就《西铭》中许多未能理解或者说还很混淆的观点及时得到了澄清,并在此基础上杨时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把“理”与封建伦理道德紧密联系起来。在杨时看来,理一与分殊之关系不仅仅是体与用的关系,而且也是仁与义之关系。杨时指出:“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杨时认为,仁义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杨时提出分殊不明,理一不精的观点。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各有不同,不能以相同的方式看待。杨时说“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同上,第269-270页)在此,杨时不仅澄清了原来自己对《西铭》中之要义“言体而不及用”的错误观念,赞成并接受了程颐《西铭》中理一分殊与仁与义相一致的观点而且在程颐的“理一分殊”思想的基础上,他把“理一分殊”思想引入社会现实的道德伦常关系当中,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阐释,论证了亲疏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李侗继承杨时这一思想,在李侗看来,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天理”之体观,他不赞成只是从人身上来看仁也不支持仅仅从天理未发上来看仁,而是认为应该从所有一切有血气的与无血气的人和物,并且“须是兼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为可”(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这样来看仁才可以、才能实现人、万事万物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说“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辩,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同上,第328页)在李侗看来,这个仁自始自终存在于事物的一切发展过程之中,并为人物所固有,它不仅体现了未发也体现了已发。李侗在教导朱熹体认杨时“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是着重强调“要在知字上用著力也”(同上,第332页),也就是要知一切有血气者与无血气者皆根源于理,天地万物也皆属此理。而仁是理的体观,它存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中,而其中由于各自所禀气质存在差异,便具有了各自不同的形式,因而,要知仁、天理现,就要在知上著力。同时,李侗把仁义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他更加注重“亦是如何通过践履,对仁‘下工夫令透彻’‘见得本源毫发之分殊’,进而知‘本源体用兼举处’从而解决‘理一’与‘分殊’,仁与义的同一性问题。”(何乃川、陈进国《论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第52-57页)李侗曾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作过一个评价,朱熹说:“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二句乃是发用处该摄本体而言,……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离乎义之内也。然者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义。”先生(李侗)勾断批云:‘推测到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患不见道也,甚慰甚慰。’”(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从这里可看出,朱熹继承和发挥了杨时、李侗的思想。李侗强调为得之加以涵养,就是要人们摒弃私欲,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就能达到仁。总而言之,李侗的上述阐释其目的也是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阐释,他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看作“天理”之体观,进一步论证了亲疏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把儒家伦理道德抬到了至圣的高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李侗作为从二程理学向朱熹理学转变的重要中介人物,为理学向南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李侗没有同朱熹一样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但是他的理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理一分殊”学说对朱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李侗及其理学思想,任何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如果忽视李侗的理学思想和地位,那么对理学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善的。
(王晓君: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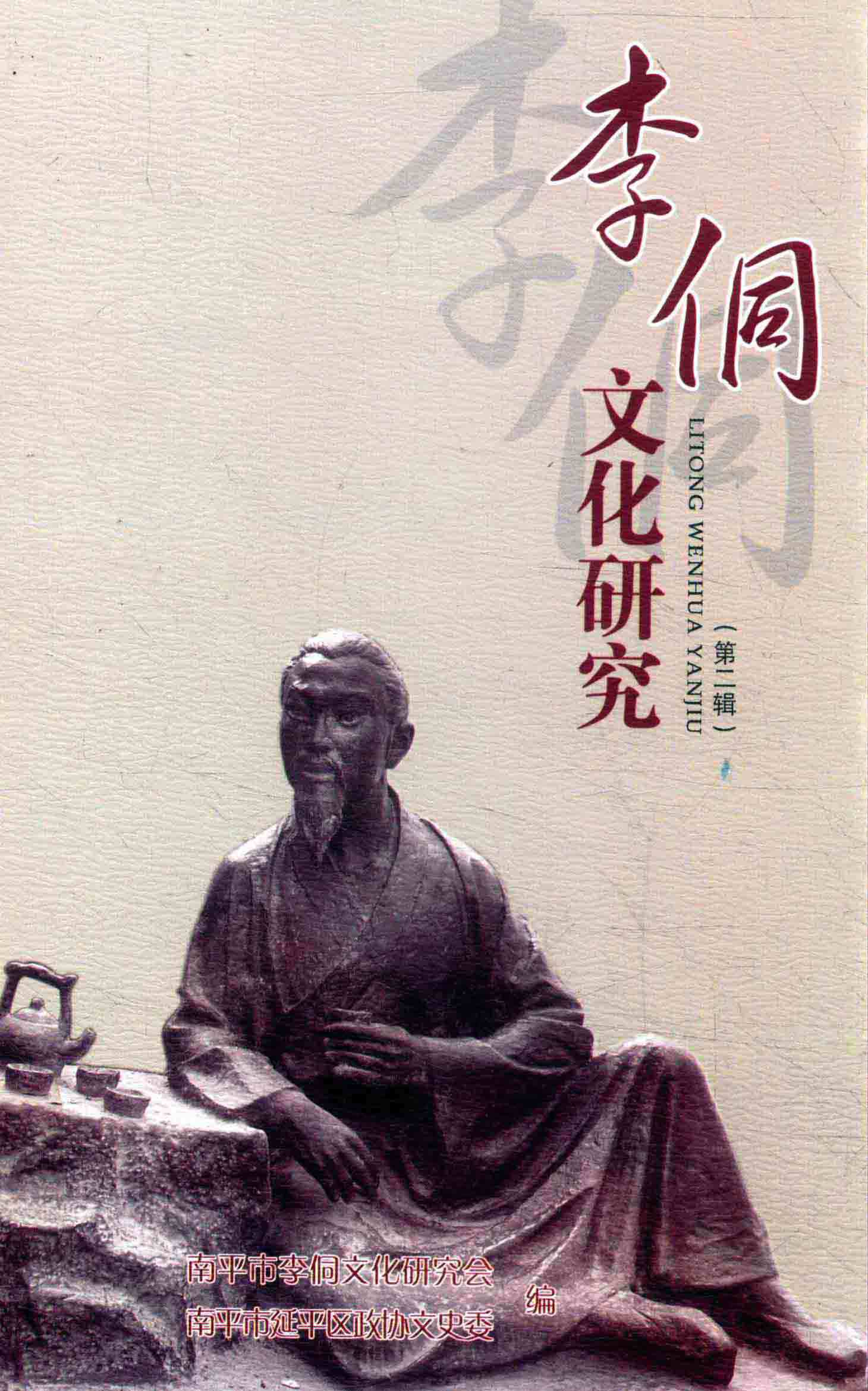
相关人物
王晓君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