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主张“罗从彦是沙县人”的材料分析
| 内容出处: | 《罗从彦故里行实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3934 |
| 颗粒名称: | 三、对主张“罗从彦是沙县人”的材料分析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18 |
| 页码: | 23-41 |
| 摘要: | 本节收录行状、墓志铭、文集、碑刻、行实、时人传记,等材料用以证明宋代理学家罗从彦世沙县人的事实。 |
| 关键词: | 罗从彦 宋代 沙县 |
内容
在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人们普遍采信那些与人物活动年代相接近的文字资料,如:行状、墓志铭、文集、碑刻、行实、时人传记,等等。因此多年以来,在证实“罗从彦究竟是延平人还是沙县人”的地域纷争中,“沙县派”学者奉若瑰宝的相关资料,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文字中:
1.宋·吴点《宋故殿撰罗公(畸)墓志铭》
2004年2月22日,沙县城西一工业开发区出土了一方《宋故殿撰罗公(畸)墓志铭》,明确记载了罗畸(1057—1124)的家世源流及生平信息,称“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罗周文)卒于沙县尉,因家焉。曾祖世口口口口口闻,祖觉,擢进士第,终广德军理掾。父安中,有辞藻,以公贵,累赠中奉大夫”。②这是一支在谱系记载上与罗从彦完全不同的罗氏支脉,但是不少“沙县派”学者却仅凭盛木一句“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③以及本地县志的单方记载,就决然断言说:
此碑的发现,可以佐证罗从彦籍贯,关于罗从彦及其沙县罗氏一族的籍贯,沙县、南平、永安、明溪等县、市文史界多有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我们看新出土的近900年前的墓志铭赫然写道:罗畸“南剑州沙县人也”。罗畸宋代沙县城关人,与闽学四贤之一罗从彦是同祖父的堂兄弟,依此,罗从彦是沙县人已是铁案。①
随着罗从彦堂叔父,宋·右文殿修撰罗畸墓志铭的出土,以碑铭文物有力佐证了罗从彦的籍贯。因罗畸与罗从彦同出沙县罗氏始祖罗沂(谱名罗周文)一脉无争议,既然罗畸墓志铭明确他是沙县人,那么,罗从彦为沙县人的争议应从此尘埃落定。②
罗畸墓志铭明确指出“罗畸,南剑州沙县人也,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卒于沙县尉”。因为罗从彦与罗畸同出沙县罗氏始祖罗沂一脉,那么罗从彦籍贯是沙县也就确信无疑。③
2004年2月22日,宋殿撰罗畸墓志铭的出土,以实物史料,铁证罗畸是唐沙县尉罗沂七世孙,佐证朱熹撰“罗博文行状”的真实和权威!各种版本《豫章文集》均有一致的宋盛木(宋罗博文好友)撰“题义恩祠记”,文中确认罗从彦为沙县开基祖罗沂字周文八世孙,从而确定罗畸与罗从彦的“叔侄关系”,将修正两地罗氏族谱中的误差。④
对此,我们权且不说仅凭《罗畸墓志铭》“罗公讳畸,字畴老,南剑州沙县人”和《沙县县志》、《题义恩祠壁》有关“罗畸,字畴老,沙县城关人,罗从彦的同祖父堂兄弟”和“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的相关叙述就直接得出“罗从彦是沙县人”的逻辑推导到底可靠不可靠,单就其县志同页所说:“罗从彦,字仲素,沙县城西洞天岩人。先祖原居江西南昌,旧属豫章郡,故世称豫章先生。为罗姓迁沙始祖唐元和十五年(820)沙县尉罗周文(罗沂)的第十二代后裔。”⑤《罗畸墓志铭》所说:“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罗周文)卒于沙县尉,因家焉。”《题义恩祠壁》所说:“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就可发现,“沙县派”学者不但不能在这些文字解读上做到对罗从彦的生平研究慎而又慎,而且在实践中也缺乏一定的调查发现,以致对于此碑有可能造成的谱系震动,竟然如此未知未察。
比如,为了将罗从彦说成是沙县人并且与罗畸关系密切。沙县《豫章郡·闽沙罗氏族谱》早已煞费苦心修订了这样两条传承谱系,即:
“罗周文→赠→吏伯→肆→熙载→庆矩→觉→安中→文弼→世南→神继→从彦→敦叙”
“罗周文→赠→吏伯→肆→熙载→庆矩→觉→安中→文韬→世炯→神述→畴(罗畸)→彦洁→博文”①
但是,这个铁板钉钉的《罗畸墓志铭》一出,却完全颠覆了《闽沙罗氏族谱》的世系排列,出现了这样一个“令人崩溃”的排序结果:
罗周文(罗畸七世祖,谱名罗沂)→(六世祖,名讳缺)→(五世祖,名讳缺,高祖)→(四世祖,名讳缺,曾祖)→觉→安中→畸→彦温、彦远、彦洁(下据朱熹《罗博文行状》,则应接:彦温→博文)
不知这个经由《罗畸墓志铭》揭示的“罗畸为罗安中之子,从罗周文到罗畸仅有七世,安中之后根本没有‘文’字辈罗氏子孙”的如山铁证,究竟还能和罗从彦世系产生怎样的特殊解读。
因此,为了让读者能够进一步弄清事实,在对《罗畸墓志铭》、《罗博文行状》和《罗博文墓志铭》进行解读时,究竟能不能毫无争议地得出“沙县派”学者所主张的“罗畸与罗从彦同出沙县罗氏始祖罗沂(罗周文)一脉无争议”“罗从彦为沙县开基祖罗沂、字周文八世孙”“罗畸与罗从彦是叔侄关系”“罗畸是罗从彦堂叔父”等结论,笔者特将三文照录如下,以鉴评判。
附一:宋·吴点《宋故殿撰罗公(畸)墓志铭》②(口为碑中缺字)
中奉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文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吴点撰
朝请大夫、知吉州军、州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兼管内劝农事、借紫金鱼袋陈城书
朝请大夫、权发遣南剑州军、州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兼管内劝农事、借紫金鱼袋林遹篆盖
口口口口口博学恬进之君子罗公讳畸,字畴老,南剑州沙县人也。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卒于沙县尉,因家焉。曾祖世口口口口闻,祖觉,擢进士第,终广德军理掾。父安中,有辞藻,以公贵,累赠中奉大夫。
公幼警敏,自始就学,婉如夙习,日口口口口口,出群异甚。弱冠游上庠,声誉轰然不可掩。熙宁九年(1076)登科,调福州司理参军。部使者阻威,厉民伤士类,不畏口论。公浩然有归志,投檄访医,奉双亲之暇,杜门读书弥十年。着《史海》百余卷,于古今无所不窥。自六经、百氏传记、天文地理、医技能之说,靡不该(古通:概)括。
相继丁内外艰,居丧尽礼,孝诚感格。兽驯墓侧,芝草生于庐。服除,叹曰:吾养不及亲矣!当移口口口口报。乃调滁州司法参军,明谳(审理案件)狱,疑濵(古通:滨)死,而平反者十余人。州将谓公守法为立异,欲劾之。公委曲辩论,不口口口口口口深相知,力荐于朝。任满到阙(古通:缺),会庙堂议设科目,代制举。公首中其选,名益彰。执政欲寘(置)之馆阁,力丐外官,除华口口口(州教授,据《沙县志》补),口则一遵太学教导之法。华人素尚气峙,崖岸为高,初未驯服。徐相告曰:罗公以规矩成我,非苦我也。俱勉而为善,世风丕变。其后,陕右诸郡舍法所取,唯华人应格为多。除太学録,迁博士,又迁太常博士、兵部郎官。大臣荐对从容,移刻,擢秘书少监,愈益恬晦。所乐者,徧(古通:遍)读人间未见之书,其余弗少贬也。居职最淹久,作《蓬山志》五卷,凡芸阁兴废始末,图书文籍之盛,与夫一时荣耀。希阔事,不待搜索,开卷炳然。
崇宁中(1102—1106),辟雍落成,有口口口儒臣许赋诗颂,献者无虑。数百口口口口臣次其高下奏,公为第一。口口口特令进官。初莅华学(注:华州学宫简称),举行释菜礼,既罢去,留俸给百斛,遗职事,诸生俾继承勿替为奉常。论孔子冠冕,当以王者口口旒为定制。至于十哲像设之位,亦加订正,朝廷并颁行于天下。尝猝然被命,作《奠献乐章》二十余首,落笔而成,识者口口口。
大观初(1107—1110),扰章恳外,凡三请,除殿撰,知庐州。未几,移知福州。所至必先问民疾苦,虽值旱蝗,随车雨足,人赖以安。异时,口口守将口移易僧舍,上下干请为市,公力革其敝(古通:弊),却权贵,书简游谒者,一不敢造前。暇日,按行府宅,至逍遥堂,视其榜,口建安刘口所立也。因作“仰止轩”,以景慕焉。已而,得宫祠还里,即所居,疏池沼,辟斋舫,唯诗书之娱.对宾客,剧(古通:只)谈古人忠口口口之美,未尝辄口声乐也。好施药剂,急人患难,凡久于弓口殡,力未能营措者,悉助而葬之。绝口不言人过,虽有诈者,不逆也。
宣和二年(1120),擢知虔州,公既拜命,慨然曰:“坐縻禄廪岁月甚久,每窃自愧,今敢辞劳乎。”虔于江西,俗素犷悍,为州口尚威,峻刑罚,公独以静镇之。居数月,囹圄亦空。本朝清献赵公治虔,政甚简易,严而不苛。尝瞰章、贡二水,为台于其口口而新之,绘其遗像而祠焉。欲以慰邦人之思也。州既治,乃清宫观,亟求玄章,再未上报。忽一日,夙兴盥漱,具衣冠,端口口口,于家世、子孙之事,无片言及之。享年六十有八。州人为之罢市而巷哭,贫者鬻衣致奠焉。盖公慈祥淳厚,至诚口口,虽赣号难治,亦不待岁月之久也。尤喜内典清心养气之学,无世俗嗜好萦其胸中,故由初迄终,其完如此。有书《讲口》五卷、《道山集》三十卷、《五经发题》五卷、《芸阁秘録》四十卷、《洞霄録》十卷,其余遗稿,在人尤多。
初娶张氏,口部郎中绎之女,口宜人。口娶陈氏、奉议郎璞之女,封宜人。三男,子彦温,从事郎、邵武军刑曹。彦远、彦洁皆将仕郎。女,一人,适进士张敦复。以宣和六年(1124)三月初一日己酉,葬于傺村先茔之侧。尚书兵部郎中张哿状公行甚详,可传不朽矣!彦温过听,乃误以志铭见委,屡辞莫敢承,又走人千里来浙东,其请益坚,终难以辞,辄论次而铭之,曰铭:学以求志,仕非慕禄,养德弥邵,位则不足;名高口绅,惠泽在民,口违于神,垂裕后人。
平津徐福摹上石
附二:宋·朱熹《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绯鱼袋罗公(博文)行状》①
公讳博文,字宗约,一字宗礼,南剑州沙县人。曾祖安中,赠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邓氏。祖畸,朝请郎,右文殿修撰。妣宜人张氏,宜人陈氏。父彦温,右从事郎,知建州瓯宁县事,赠右承议郎。妣太孺人邓氏,太孺人黄氏。罗氏,世为豫章人,唐长庆中(821—824),有为沙县尉以卒者,子孙因家焉。至五世孙觉始举进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显重于世。又再世而得公,复以道学行谊克世其家,有闻于时。然位卑数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识者恨之。
盖公少有异质,生岁始周,家人示以啐盘,公一无所顾,独扶服前取书之论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叹异,为文以记其事,且曰:“是儿当复以文学大吾门,且复闻道,而不为章句之习也。”十余岁,遭瓯宁府君之丧,哀毁如成人。治丧葬又皆必诚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补将仕郎,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户参军。治仓庾谨出纳,尽去宿弊,后皆可法。
再调静江府观察支使,桂管为岭檄以西一都会,民物繁伙,常时幕府已不胜事。至公为当路所知,事待公决者尤多。公财处从容,人未尝见其疾言遽色,而事无不各得其理者。时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窜斥,系踵南来,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廪奉,则鬻衣以济其乏。用荐者,改右宣议郎、知赣州瑞金县事,转宣教郎。
始至,岁歉,公度民且饥,则先事为备,多所储积。及饥,发廪赈赡,事无巨细,必躬临之,不以勤劳为惮。其至诚恻怛,虽壹主于惠爱无所计,惜而厝置,织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赖以全,而公又请推其馀,以及旁县。县故多盗,公饬巡徼,设方略,得渠帅数人置诸法,而境内帖然。在官余九月,会故丞相魏国张忠献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请以为干办公事。用上嗣位覃恩转通直郎,赐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数千人以归。和籴建康以实军,又以公与其事。未几,得穀亦巨万计。
张公再入相,宾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制置全蜀,奏辟公参议官以行,军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虚心好问,公亦推诚启告,反复殚尽,必归于至当而后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为多也。尝衔命汉中,劳抚将士,宣抚使以礼致遗,为钱三百万。公不欲受,而难于辞却。还次汉州,州方治贡院不能就,以五十万予之,余悉输成都公币。(罗博文)取河南程(颐、颢)夫子之遗文,与他名臣论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锓板,用之略尽。而横渠张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贫不自振。公访得之,为言汪公。延置府学,蜀士知所劝焉。东方士大夫游宦蜀土,贫不能归,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业之,赖以济者甚众。累迁承议郎,秩满,自请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命下,而汪公亦召还,公复从东。至嘉州留宿,与同舍会集笑语如常时。一日,忽语人曰:“吾将逝矣,然幸大事已竟,无可憾也。”遂就寝,酬酢从容,了不异平日,独无一语及其私,俄而遂化。
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盖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装以理丧事,则囊中独有书数十帙,余金足以归其丧而已。相与咨叹,以为不可及,遂以柩归。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沙县严地祖茔之旁。公娶陈氏,了斋先生之兄孙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问,曰辟。孙男八人,女七人,皆幼。
公资禀和粹,沈静寡欲,其处已待人,一主于诚敬。平居愉怡,人莫见其喜愠之色。闻人之善,称慕如不可及,至其有过,则常若有所隐避,而不忍言也。视人患难困乏,如切其身,经营周救,必尽其力。年未三十,即屏远声色,一榻萧然,惟乐善不倦如嗜欲。闻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几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胜,概多所登历,而于佛、老子之学,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诚笃好之,而不知公之所志,与其所学,有不在是也。盖尝从张忠献公问行已之大方,张公为手书所为敬说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终身不懈。又从同郡李愿中先生游。闻河洛所传之要,多所发明,于是喟然而叹曰:儒佛之异,亡他,公与私之间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坚。在桂州时,汪公盖方通判州事,知公所为,日就公语,且亟称道其为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员外郎刘公芮,亦方隐,居州之西山,躬耕励志,人罕识之。公独以坐曹决事之余,日往从之游。刘公名家子,及见前辈,多识前言往行,顾独恨得公晚,及闻公卒,哭之恸,为寝疾不食者数日,此岂势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业之美,固当有于为世,而充养有素,神观清明,人亦不谓其止于此也。呜呼!其可谓不幸也已。
熹尝受学李先生之门,先生为熹道公之为人甚详,于其从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张公高明闳大有余,而宗礼以精密详练佐之,幕府无过事矣。”时熹未识公也。及先生殁,乃获从公游,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后益信先生为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数千里,书问岁亦一再至,所以劝励从学者殊厚,日夜望公之还,几得复相与讲其旧学,而公乃以丧归。熹既痛公之不幸,不及大为时用,又伤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诸孤既号哭受弗,则以公从弟颐所叙官阀梗概一通授熹,使状次之,将以请铭于作者。熹谊不获辞,既趣以就事矣。惟是从游之晚,于公之行治有不尽知,大惧阙漏放失,将无以补采择为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财之。谨状。时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枢密院编修官朱熹状。
附三:宋·汪应辰《沙县罗宗约墓志铭》①
宗约罗氏,讳博文,曾祖安中,赠中奉大夫,妣恭人邓氏。祖畸,朝请郎、右文殿修撰,妣张氏、陈氏,皆宜人。父彦温,右从事郎,知建宁府瓯宁县事,赠右承议郎,妣邓氏、黄氏,皆赠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长庆中有为南剑沙县尉者,因家焉。五世孙觉始举进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显重于世。至宗约,复以道学行谊,克世其家焉。
宗约生有异质,家人试以晬盘,一无所顾,独匍匐取书册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叹异,为文以记其事。年十余,遭瓯宁府君丧,哀毁如成人。治丧必诚必信。用右文公奏补官,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户参军。临事不苟,无巨细皆有条理。再调静江府观察大使,桂管为岭檄以西一都会,府事既已丛剧,而连帅监司,亦多委以事,宗约皆从容置办。时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窜斥,系踵南来,宗约悉善遇之。至或鬻衣以济其乏。改右宣义郎、知赣州瑞金县事。始至岁歉,宗约先事储积,既而发廪赈赡,事皆躬临之。其至诚恻怛,虽一主于惠爱无所惜,而措置纤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县故多盗,宗约设方略,得首恶数人,置诸法,境内帖然。会故丞相魏国张忠献公都督江淮,请以为干办公事。其募兵和籴,皆不扰而济。张公再入相,宾客例出幕府,以宗约知和州,未赴,而四川制置使奏辟为参议官,宗约详审精密,每论事反复殚尽,归于至当而后已。尝至兴州劳将士,宣抚使以礼致遗,为钱三百万。宗约不欲受而难于辞。还次汉州,州方治贡院,以五十万助之,余悉输制置司公帑。横渠张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贫不自振。宗约访得之,为言于帅,延至府学,蜀士知所劝焉。士之游宦蜀土,贫不能归者,宗约出捐俸钱周之,赖以济者甚众。累迁承议郎,秩满,得请主管台州崇道观,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来问者,宗约虽疾病,而拱手端坐无惰容,盖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将逝矣,然幸大事已竟,无可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行聚而哭之,解其装以理丧事,则独有书数千卷,余金仅足以归其柩而已。相与咨叹,以为不可及。十有二月壬寅,葬于沙县岩地祖茔之旁。
宗约娶陈氏,了斋先生之兄孙女也。子男二人,曰问,曰辟;孙男八人,女七人,皆幼。
宗约资禀和粹,沈静寡欲。其处已待人,一以诚敬。平居怡愉,人莫见其喜愠之色。闻人之善,称慕如不及;至其有过,则常若有所隐避而不忍言也。视人患难困乏,如切其身。年几三十,既丧其藕,屏远声色,一榻萧然,惟乐善不倦如嗜欲。闻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几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愿中,受业于龟山先生杨文靖公,宗约从之游,多所发明。于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亦坚矣。然宗约之为人,虽笃意学问,而不为文词;虽力行善事,而不徼名誉;虽爱众亲仁,而非以为取悦也。故世知宗约者亦鲜矣。其孤以枢密院编修朱熹元晦所为行状,以来请铭,余与元晦盖皆知宗约者。
铭曰:汲汲其求,兢兢其持。保此无憾,全而归之。
2.宋·罗博文《书议论要语卷后》
在《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沙县版)》收录的、由李侗门生罗博文所撰写的《书议论要语卷后》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伯祖(祖父的兄长,父亲的伯父)先生《议论要语》,得之于眉人(指上寿之人)石安民大任(称指担任重要职务者)。其仲父道叟公辙,绍兴乙卯(1135)尝为延平学官,获此,题云:“传之郡人彭君”。今先生已(原字为“云”,今据上下文之意改)亡,无所取证,恐兵火之后飘散未可知。观其议论高致,真有用之学,致主庇民修身养心,尽在于斯于是,知先生之学不为空言也。归,当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审订之。时乾道丙戌(1166)十月寓成都燕堂,罗博文敬书。①
这份难得的、似乎能够完全说明“罗博文与罗从彦具有亲属关系,罗博文是沙县人,因此罗从彦也是沙县人”的《书议论要语卷后》,自宋以来一直就被主张“罗从彦是沙县人”的历代学人勤加应用,最终形成了代代相传、互相征引的“亲缘认定”。比如,明代叶联芳《重修沙县志》,沿用该说法称:“罗畸(罗博文祖父),字畴老,从彦之从父(祖父亲兄弟的儿子)兄弟。”②明代方志学家黄仲昭修撰《八闽通志》,也明确表述罗畸是“从彦之从父兄弟”,罗博文是“殿撰畸之孙”③。而清人李清馥在编纂《闽中理学渊源考》时,虽然一方面继续照录着“罗博文云:延平先生之传,乃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学,源流深远”④;一方面却把“伯祖”改成“从祖”(祖父的亲兄弟。如果从祖年长于祖父,则为伯祖;如果从祖年幼于祖父,则为叔祖),称:“罗博文,字宗礼,一字宗约。祖畸,太常博士,从祖为仲素先生。博文用祖荫补将仕郎福州司户参军,再调静江府观察支使。”⑤
随后,乾隆版《罗氏族谱》在其自编的《豫章文集》里,又“不知不觉”将原来的“伯祖”撰改成“余祖”,干脆将自己从“同祖父之兄弟”的后裔直接变成了“同祖父”的嫡系后裔,硬生生把自己加塞到另一个祖宗的队伍里,让人啼笑皆非。对此,民国十七年(1928)沙县罗氏后裔罗克涵在主编《沙县志》时,就已经发现并及时订正了乾隆版《罗氏族谱》的错误,重新称:“罗畸,字畴老,从彦之从父(祖父的亲兄弟的儿子)兄弟。”⑥但是,现在版的《沙县志》却不知为何还是将其书写成:“罗畸,字畴老,沙县城关人,罗从彦的同祖父堂兄弟。”“罗从彦,字仲素,沙县城西洞天岩人。先祖原居江西南昌,旧属豫章郡,故世称豫章先生。为罗姓迁沙始祖唐元和十五年(820)沙县尉罗周文的第十二代后裔。”①不仅又将二人从“叔伯侄”的关系强变成“堂兄弟”关系,而且还把罗从彦确定为“罗周文(罗沂)的第十二代后裔”,根本不顾只把罗周文称为“七世祖”的罗畸会作何感想.可见这其中受乾隆版《罗氏族谱》错误影响的缘由和动机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
那么,事实上的罗从彦和罗博文关系,是不是就真如罗博文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某(我)伯祖”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从罗博文留下的历史线索中去寻找答案。
考察史料,笔者发现历代典籍除了罗博文这唯一一个处处将自己与罗从彦联系在一起的、开口即言“某伯祖”的“傍名人”典型外,其他亲密如罗从彦与李侗(师生)、罗从彦与延年(师生)、李侗与罗博文(师生)、李侗与朱熹(师生)、朱熹与罗博文(学友)、陈渊与罗从彦(学友)、陈渊与罗博文(姻亲),重要如《罗从彦行状》《罗博文行状》《罗博文墓志铭》《默堂(陈渊)文集》《罗从彦墓志铭》等,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篇相关记载能够再次明确提到罗博文与罗从彦的亲属关系,这难道不会令人匪夷所思吗?更何况,在这篇从来没有被人质疑过的罗博文短文中,笔者又无意发现了一对并不具有亲属关系的石姓名人“石安民”和“石公辙”.不知为何竟被罗博文(抑或是假托罗博文之人)硬生生地牵连在一起,变成了关系密切的“叔侄二人”:
伯祖先生《议论要语》,得之于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叟公辙……
要知道,古代是以伯、仲、叔、季来表示兄弟间的排行顺序的.“仲父”本指父亲弟弟中的年龄最长者②。“石公辙”既是“石安民”之仲父,二人就理当为同籍之人。然而这里参照上下文意思所提到的石安民,却是罗博文在广西任上所结识的上级官僚、广西桂林临桂人石安民③,其于绍兴十五年(1145)中进士,1170年知制诰学士并留题广西贵港南山寺④,是一个有据可查的、地地道道的广西人;而石公辙,则是绍兴二年(1132)罗从彦准备就任广东惠州博罗县县尉时,以南剑州太守周侯绾之命主持当年南剑州州学释菜大典的、如假包换的浙江绍兴新昌籍特奏名状元石公辙①,其作为一个大器晚成的特科状元的传奇经历,甚至还绘声绘色地出现在了同为浙江(婺州)人的方勺笔下:
大梁二相祠,世传游、夏也。士有未遇,上书乞灵,往往见梦,虽远必应。越人石公辙妙年乡举,抵京,梦帘中出一纸,只“邻州”二字。石后累举,年逾五十,不得已,就特奏名,遂为第一,例赐出身。是时,上驻跸临安府也。②
试想一下,二人如果真是只由“罗博文”亲笔勾连成叔侄关系的话,那么这样的错误也就不是一般的错误了。
因此,为小心印证、避免错判这一重要的人物关系,笔者尽可能多地搜集到了与石公辙有关的宋代史料,发现这个被确认为“石安民仲父”的浙江人石公辙与广西人石安民之间,着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交往问题”,是很难按照情理解释的两个“有叔侄关系的人”:
第一,石公辙在绍兴二年(1132)以特奏名第一人的身份就任南剑州州学教授时,已经年逾五十,其在南剑州任上所得到的几不多传的罗从彦《议论要语》,为什么只愿意“传之郡人彭君”而非自己“博学多能的侄儿”,这在情理上应该作何解释?
第二,“郡人彭君”在得到罗从彦的《议论要语》后,却为何要将其转传于广西人石安民而不是来自于同郡的“罗从彦族亲罗博文”?
第三,石安民在得到这本珍贵的《议论要语》后,又为何还要将其转传给罗博文,这期间的关系瓜葛究竟为何不肯交待清楚?要知道,这份由罗博文最后得到的、被转来转去留有题字的罗从彦《议论要语》,很有可能是一份原本而非抄本!
由此可见,仅就石公辙与石安民的身份关系而言,罗博文的这份《书议论要语卷后》就有诸多值得存疑的地方,更何况那个生怕别人都不知道的“某(我)伯祖”之说呢!
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疑问外,我们还能清楚看到的事实就是,罗博文撰写这份《书议论要语卷后》的时间为乾道丙戌年(1166)十月,此时,他还寓居在成都燕堂,离去世尚有两年。其文所说的“归,当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审订之”的重要设想,最终也因为他的卒于途中而无法达成所愿。为此,清代黄宗羲在编订《宋元学案》时,就专门对此考证说:
朱子与宗约(罗博文),在延平(李侗)门人,最为契合。然朱子之交宗约,在延平殁后,宗约寻又入蜀,其相与不过一二年耳!宗约于蜀中得豫章《议论要语》,曰:“归,当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审订之。”则其所推服,朱子而外,无人焉。乃宗约卒于途中,此言遂成虚语,可叹哉!①
由此看来,不论罗博文自称的“某(我)伯祖罗从彦”,也不论其所传得于石安民、石公辙的《议论要语》也罢,朱熹其实都没对此做出明确审定,孰是孰非,当然也就不好做出明确判断。故明天启篁路村重修《罗氏宗谱》在收录罗博文写给罗从彦的《元祖文质公赞》时,也仅仅只将其身份标注为“族侄”。
附四:宋·石公辙《志释菜事》②
教授石公辙
绍兴二年壬子,州学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罗县尉罗从彦以太守周侯绾之命,领袖诸生宗昇、张元侯、符藻、廖援、张维、廖拱同行释菜之礼,有洙泗断断气象。而吾友吕君仁舍人以诗见褒,不免有过情之誉。然意在纪实,谨刻石而龛诸夫子庙壁,俾来者有感发焉。
会稽③石公辙道叟谨志
3.宋·盛木《题义恩祠壁》
《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沙县版)》除了收录一篇能够“表明罗从彦与罗博文身份关系”的《书议论要语卷后》外,同时还收录了一篇能够“表明罗从彦与罗畸身份关系”的《题义恩祠壁》,其文明确说到:
从彦,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罗主簿,先生官也。先生姓罗氏,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罗畸曾任右文殿修撰,故以官名称呼其为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即二人的五世祖①是兄弟)。……先生(罗从彦)无嗣,诸经解遗文在诸从学者家。《春秋解》,昔宗约处见之,此先生之文也。先生同殿撰公肄业于义恩寺,后绘先生遗像从祀于先世香火之侧。盖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故也。宗约官桂林,(盛)木自广西从宗约归延平。宗约西行改秩(改变官吏的职位或品级。多指提升),馆木此寺以俟其归。尝闻宗约讲及先生道学梗概,今拜先生遗像起敬起慕之余,拾旧所闻,辄敢僭易。书于祠侧之壁,复系之以辞云:“先生之学,精一之学。先生之传,伊洛之传。至道无文,至学无词。以心传心,天地不知。先生之道,天人之师。其道光大,有俟他时。朅来瞻慕,后学得依。”时绍兴乙亥(1155)十月廿日东里盛木任叔题。②
初读此文,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是:
第一,河南东里人(今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寺王村)盛木是罗博文的好朋友,其对罗博文的家族世系表现得相当熟悉,历代典籍也只有他非常明确地提到:“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罗从彦)无嗣,诸经解遗文在诸从学者家。”
第二,罗从彦与罗畸不仅“五世祖是兄弟”,而且二人还是同学,他们在一起学习的兼有学校功能的“义恩祠”(祠在沙县北九都),为罗从彦的八世祖捨田所创(一说为罗畸七世祖罗周文所创,详见沙县罗从彦纪念馆宣传栏),奉祀有先世香火,可惜未题其名讳。
第三,绍兴乙亥年(1155)十月,盛木跟随年已40岁③的罗博文从桂林任上返回延平时,恰遇罗博文被提拔任用——“……再调静江府④观察支使,桂管为岭檄以西一都会,民物繁伙,常时幕府已不胜事。至公为当路所知,事待公决者尤多。公财处从容,人未尝见其疾言遽色,而事无不各得其理者。时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窜斥,系踵南来,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廪奉,则鬻衣以济其乏。用荐者,改右宣议郎、知赣州瑞金县事,转宣教郎”。①因此单行的盛木只好借居在义恩祠等待着罗博文的回返。
然而深读此文,我们却可以发现:
第一,不知为何,留文不多的罗博文特别爱向他人强调自己与罗从彦的亲缘关系,尽管他的其他亲友中也不乏有不同凡响者;尽管直到他自己去世时(1168),罗从彦也都还没能成为一个享有盛名的人。
第二,所有那些引发后人议论的重大问题,盛木都已“非常具有先见”且“非常巧妙”地告知了大家。比如,对于“罗从彦到底是延平人还是沙县人”,盛木说的清晰而又婉转:“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因此,只要罗博文或罗畸被确认为沙县人无疑,那么罗从彦自然也就要是沙县人。再比如,对于“罗从彦到底有否子嗣”,盛木的回答更加直截了当:“先生(罗从彦)无嗣,诸经解遗文在诸从学者家。”这些关键信息以如此“毋庸置疑”的语气密集出现,难道不会让人感觉有点太过蹊跷?要知道,那份明确说明罗从彦有其嫡传子嗣的《豫章罗先生墓志铭》,正是罗从彦的正传弟子李侗亲笔所撰,而李侗又是罗博文所最最敬重的学术导师,三人间单凭这样亲近的师生关系,就绝不可能把罗从彦有无子嗣的重大问题简单搞错。那么,盛木此言从何而来?
第三,盛木只是沙县人罗博文“官桂林”时所结识的一个好朋友而已,他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前“自广西从宗约(罗博文)归延平”,又恰巧碰上宗约“西行改秩”时,必须长期留在义恩祠的合理理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依据上文所引朱熹《罗博文行状》可以知道,罗博文从桂林任上离职后,就在他人推荐下“改右宣议郎、知赣州瑞金县事,转宣教郎”。因此,依照广西、福建与江西的地理位置判断,原本要带着好友“归延平”的罗博文既然是“西行改秩”而不是“东行改秩”,那么他就应该是已经回到福建而后再决定“西行”前往江西,根本不太可能是自己直接前往江西而让盛木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借居在人生地不熟的沙县义恩祠苦苦干熬。更何况,根据文内所表达的行程安排,沙县人罗博文如果只是要带着好友“归沙县”看看“沙县人罗从彦”的话,那么他的目的其实已经完成(义恩祠就在沙县境内),根本没必要再“馆木此寺以俟其归”。因此,唯一能够说明盛木要居留在沙县义恩祠并耐心等待罗博文回来的真正原因,就是盛木希望罗博文回来后,能够继续带着他“归延平”拜访罗从彦故地,这其实也是他一开始就要表达的目的所在,只是从来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罢了。
第四,如果“义恩祠”真是罗从彦的八世祖捨田所创,祠内又奉祀有罗从彦的“先世香火”,那么,“义恩祠”就应该算是罗从彦的家祠,而对于罗从彦的家祠,仅仅只是作为罗从彦“五世兄弟”后裔的罗博文,究竟有没有资格把自己的朋友安排到罗从彦的家祠里长时久候?
第五,如果“义恩祠”真是罗从彦的八世祖捨田所创,祠内又奉祀有罗从彦的“先世香火”和“先生遗像”,那么,其父罗神继、其祖父罗世南、其曾祖父罗文弼、其八世祖罗某某的神牌是不是也应该位列其中?既如此,其先祖名讳又为何不能够被清楚点出?
第六,如果“义恩祠”真是罗从彦的八世祖捨田所创,那么,参照《南平县志》“罗从彦,据谱八世祖京城(即京成,疑为笔误),自豫章避难来家剑浦,生子二人,一徙沙县,一止镡城”①的说法,是不是不仅“沙县罗氏确有一支是从剑浦县迁徙而去”的说法可以得到证实,而且其所谓的“先生八世祖”的名讳也可以被证实就是罗京成?更何况,对于“沙县还有没有存在一支从剑浦县迁徙过去的京成公后裔”的调查工作,其实早在罗从彦五世孙罗良佐要兴修族谱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良佐公,讳良佐,字尧卿,……历官汀州教授。先淳祐八年(1248),曾适沙阳,访殿撰畴老公宗派,值干戈告变,途中有儆,不果,虚回。至晚年,询及故老,遍阅年谱及言行录数卷,即编成宗谱,大有伦次。其规模宏远,前为元宗,后为鼻祖,信夫。”②
第七,参照古人称谓习惯,如果盛木所说“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祖真是兄弟的话,那么吴点《宋故殿撰罗公(畸)墓志铭》提到的“罗公讳畸,字畴老,南剑州沙县人也。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卒于沙县尉,因家焉。”③与李侗《豫章罗先生墓志铭》提到的“数传来,惟罗最蕃衍,迁徙靡一。于时或沙或剑。而剑宗为先生远祖京成公。初居剑郭,久之,复居溪南篁乡。其曾大父文弼,大父世南,父神继,奕叶潜鳞,代有齿德”④不就成了大相径庭、互为矛盾的两种记载了?如:罗周文(罗畸七世祖,谱名罗沂,785—873)→(六世祖,名讳缺)→(五世祖,名讳缺,高祖)→(四世祖,名讳缺,曾祖)→罗觉(罗畸三世祖,祖父)→罗安中(罗畸二世祖,父亲)→罗畸(本位,第一世,1057—1124)→罗彦温(儿,第二世,亦称一世孙)→罗博文(孙,第三世,亦称二世孙,1116—1168)。
罗周偁(罗从彦十世祖①,842—?)→罗仪贞(九世祖,862—961)→罗京成(八世祖,875—929)→(七世祖,名讳缺)→(六世祖,名讳缺)→(五世祖,名讳缺,高祖)→罗文弼(罗从彦四世祖,曾祖)→罗世南(罗从彦三世祖,祖父)→罗神继(罗从彦二世祖,父亲)→罗从彦(本位,第一世,1072—1135)→罗敦叙(儿,第二世,亦称一世孙,1096—1133)→罗振宗(孙,第三世,亦称二世孙,1134—1194)。
如此看来,罗从彦与罗畸二人的辈分关系怎么都不能构成是“五世兄弟”。因此,在两篇石刻墓志铭都不可能有假的情况下,最大的谬误就只能来自于与罗氏关系最为疏远的、仅以文字传世的《题义恩祠壁》。此外,罗氏通谱网不知何以为凭点明的罗从彦八世祖名讳,也同样令人感到不知所措:“豫章先生祠……一在沙县洞天岩西麓。五世孙天泽请邑司建。……一在沙县义恩祠,祀八世祖熙载。”②
综上可见,盛木这篇看似言之凿凿的《题义恩祠壁》,的确存在诸多不能解释的存疑之处,如果我们单单仅凭其言就轻易得出有关罗从彦地籍、后裔的关键信息,那是一定很难令人信服的。
4.民国·翁国梁《洞天岩志》
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一月,沙县前行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翁国梁先生所作的《洞天岩志》,该书《自跋》一文对于编撰此书的缘由说明是:“余寓沙阳将一载,爰撰《洞天岩志》三万言,网罗遗文旧事,以存掌故;并录神奇,里巷琐言,以供谈助。凡山川、人物、艺文、古迹,总汇叙述,经纬条贯,便于寻检,且明本末,创志书之新格。沙邑人士为欲阐扬桑梓文献,保存古迹名胜,此书得以出版,而黄颂慈、洪可良、陈绍忠、林衡山诸君,与有力焉。”③
笔者通过对全书的详细阅读以及对网上资料的收集了解,得知该书的作者翁国梁,号春雪,其时曾就职于福建省立医学院,非常热衷于对地方民俗和地方史志的研究,是一名负有相当知名度的年轻教师:其书名题署者为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可谓是时运相亲;其书后附录的“本书作者其他编著”共40本,可谓是著作等身;其各个书目后所附着的题序或题笺,赫然出现着顾颉刚、于右任、郁达夫、蔡元培、容肇祖(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林森(国民政府主席)、丁文江(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鼎鼎大名,可谓是往来风雅;其在书目附录后所摘录的“名家书评”,分别来自江西教育厅长程时煃、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闽浙监察使(1935年兼任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福建民政厅长高登艇、福建教育厅长郑贞文、海军上将李世甲等官家政客,可谓是交游广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涉猎全面、了解事物无所不包的文化名家,却在跟随福建省军事、文化、教育机构内迁永安、沙县的一年间,留下了他在游览洞天岩后立志“且明本末,创志书之新格”的《洞天岩志》,对罗从彦与沙县的关系问题做了这样考订:
按豫章先生,旧以为剑浦罗源里人,后居沙县,盖先生始祖自豫章来,原迁沙县,后迁罗源,后又归沙县。据先生集载,绍兴乙亥东里盛木,博文友也,《题义恩祠壁》云:“是祠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先生同殿撰畸肄业于此”,此则先生复居沙阳明矣。又集载,先生录《龟山语录》云:“第四卷《毗陵所闻》,注云:‘辛卯(1111)七月,自沙县来,至十月去。’《萧山所闻》注云:‘壬辰(1112)五月又自沙县来,至八月去。’”若非居沙县,何曰“自沙县来也。”今考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之麓,至郡寇乱后,罗氏始衰,废其所游息。颜乐斋、濯缨亭等景,正在洞天瀑布之滨,且得与默堂相倡和。闻罗源里无泉石之奇,必非其所也。其葬罗源,第以李公扶柩至延平,故袝之祖墓侧耳。①
文中为着力证明“罗从彦是沙县人”,不惜援引了几个因果不对的逻辑判断,但最终给人的感觉却只是证明“罗从彦曾经住在沙县而已”,其具体说法如下:
第一,沙县人罗从彦因为先居剑浦、后居沙县,因此过去有人认为罗从彦是剑浦人。但实际情况却是:罗从彦始祖自豫章来,原迁沙县,后迁罗源,后又归沙县。罗博文好友盛木《题义恩祠壁》所说“是祠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先生同殿撰畸肄业于此”,就是罗从彦复居沙县的明证。
原文表述:按豫章先生,旧以为剑浦罗源里人,后居沙县,盖先生始祖自豫章来,原迁沙县,后迁罗源,后又归沙县。据先生集载,绍兴乙亥东里盛木,博文友也,《题义恩祠壁》云:“是祠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先生同殿撰畸肄业于此”,此则先生复居沙阳明矣。
第二,罗从彦所录《龟山语录》有多处注明其拜师龟山(杨时)时,都是“自沙县来”,如果不是住在沙县,又怎么可以说是“自沙县来”呢?
原文表述:先生录《龟山语录》云:“第四卷《毗陵所闻》,注云:‘辛卯(1111)七月,自沙县来,至十月去。’《萧山所闻》注云:‘壬辰(1112)五月又自沙县来,至八月去。’”若非居沙县,何曰“自沙县来也。”
第三,在罗从彦和陈渊诗作中多次出现的颜乐斋、濯缨亭、寄傲轩等建筑都只出现在洞天岩附近,剑浦县罗源里因为没有“泉石之奇”,因此一定不是罗从彦的所居之地,至于他为什么会最后归葬于罗源里,只是因为李侗要把他的灵柩扶归至延平(今南平市延平区)他的先祖旁祭祀而已。
原文表述:颜乐斋、濯缨亭等景,正在洞天瀑布之滨,且得与默堂相倡和。闻罗源里无泉石之奇,必非其所也。其葬罗源,第以李公扶柩至延平故袝之祖墓侧耳。
阅读翁国梁按语中所作的这些逻辑判断,很容易让人产生“不管罗从彦之前是哪里人,只要证明他是住在沙县的,那他就是沙县人”的荒谬结论。而在中国,任凭谁都知道,一个人的祖籍和地籍都只能有一个,如果有人只是要以一时之“居”来定籍的话,那么已经无法开口的罗从彦就会被强行冠以“延平人、沙县人、连城人、博罗人”等多个地籍。由此可见,仅仅因为某人“居在某地”就可以抛开所有因素来断定“某人是某地人”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罗氏通谱网登载的《福建罗氏源流初探》虽然也还依据某些错谬之事来主张罗从彦是沙县人,但却依旧不得不承认:
罗从彦,是福建著名的罗氏名人,字仲素,时学者尊称豫章先生,南剑州人沙县人。(《福建通志》考证其为沙县人,盖据晚年定居而言,祖籍而言,但其生在南平罗源乡,墓在南平)。宋绍兴二年(1132)特科进士,授博罗县主薄。是宋代理学(集儒、佛、道于一体)的重要人物。①
1.宋·吴点《宋故殿撰罗公(畸)墓志铭》
2004年2月22日,沙县城西一工业开发区出土了一方《宋故殿撰罗公(畸)墓志铭》,明确记载了罗畸(1057—1124)的家世源流及生平信息,称“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罗周文)卒于沙县尉,因家焉。曾祖世口口口口口闻,祖觉,擢进士第,终广德军理掾。父安中,有辞藻,以公贵,累赠中奉大夫”。②这是一支在谱系记载上与罗从彦完全不同的罗氏支脉,但是不少“沙县派”学者却仅凭盛木一句“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③以及本地县志的单方记载,就决然断言说:
此碑的发现,可以佐证罗从彦籍贯,关于罗从彦及其沙县罗氏一族的籍贯,沙县、南平、永安、明溪等县、市文史界多有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我们看新出土的近900年前的墓志铭赫然写道:罗畸“南剑州沙县人也”。罗畸宋代沙县城关人,与闽学四贤之一罗从彦是同祖父的堂兄弟,依此,罗从彦是沙县人已是铁案。①
随着罗从彦堂叔父,宋·右文殿修撰罗畸墓志铭的出土,以碑铭文物有力佐证了罗从彦的籍贯。因罗畸与罗从彦同出沙县罗氏始祖罗沂(谱名罗周文)一脉无争议,既然罗畸墓志铭明确他是沙县人,那么,罗从彦为沙县人的争议应从此尘埃落定。②
罗畸墓志铭明确指出“罗畸,南剑州沙县人也,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卒于沙县尉”。因为罗从彦与罗畸同出沙县罗氏始祖罗沂一脉,那么罗从彦籍贯是沙县也就确信无疑。③
2004年2月22日,宋殿撰罗畸墓志铭的出土,以实物史料,铁证罗畸是唐沙县尉罗沂七世孙,佐证朱熹撰“罗博文行状”的真实和权威!各种版本《豫章文集》均有一致的宋盛木(宋罗博文好友)撰“题义恩祠记”,文中确认罗从彦为沙县开基祖罗沂字周文八世孙,从而确定罗畸与罗从彦的“叔侄关系”,将修正两地罗氏族谱中的误差。④
对此,我们权且不说仅凭《罗畸墓志铭》“罗公讳畸,字畴老,南剑州沙县人”和《沙县县志》、《题义恩祠壁》有关“罗畸,字畴老,沙县城关人,罗从彦的同祖父堂兄弟”和“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的相关叙述就直接得出“罗从彦是沙县人”的逻辑推导到底可靠不可靠,单就其县志同页所说:“罗从彦,字仲素,沙县城西洞天岩人。先祖原居江西南昌,旧属豫章郡,故世称豫章先生。为罗姓迁沙始祖唐元和十五年(820)沙县尉罗周文(罗沂)的第十二代后裔。”⑤《罗畸墓志铭》所说:“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罗周文)卒于沙县尉,因家焉。”《题义恩祠壁》所说:“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就可发现,“沙县派”学者不但不能在这些文字解读上做到对罗从彦的生平研究慎而又慎,而且在实践中也缺乏一定的调查发现,以致对于此碑有可能造成的谱系震动,竟然如此未知未察。
比如,为了将罗从彦说成是沙县人并且与罗畸关系密切。沙县《豫章郡·闽沙罗氏族谱》早已煞费苦心修订了这样两条传承谱系,即:
“罗周文→赠→吏伯→肆→熙载→庆矩→觉→安中→文弼→世南→神继→从彦→敦叙”
“罗周文→赠→吏伯→肆→熙载→庆矩→觉→安中→文韬→世炯→神述→畴(罗畸)→彦洁→博文”①
但是,这个铁板钉钉的《罗畸墓志铭》一出,却完全颠覆了《闽沙罗氏族谱》的世系排列,出现了这样一个“令人崩溃”的排序结果:
罗周文(罗畸七世祖,谱名罗沂)→(六世祖,名讳缺)→(五世祖,名讳缺,高祖)→(四世祖,名讳缺,曾祖)→觉→安中→畸→彦温、彦远、彦洁(下据朱熹《罗博文行状》,则应接:彦温→博文)
不知这个经由《罗畸墓志铭》揭示的“罗畸为罗安中之子,从罗周文到罗畸仅有七世,安中之后根本没有‘文’字辈罗氏子孙”的如山铁证,究竟还能和罗从彦世系产生怎样的特殊解读。
因此,为了让读者能够进一步弄清事实,在对《罗畸墓志铭》、《罗博文行状》和《罗博文墓志铭》进行解读时,究竟能不能毫无争议地得出“沙县派”学者所主张的“罗畸与罗从彦同出沙县罗氏始祖罗沂(罗周文)一脉无争议”“罗从彦为沙县开基祖罗沂、字周文八世孙”“罗畸与罗从彦是叔侄关系”“罗畸是罗从彦堂叔父”等结论,笔者特将三文照录如下,以鉴评判。
附一:宋·吴点《宋故殿撰罗公(畸)墓志铭》②(口为碑中缺字)
中奉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文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吴点撰
朝请大夫、知吉州军、州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兼管内劝农事、借紫金鱼袋陈城书
朝请大夫、权发遣南剑州军、州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兼管内劝农事、借紫金鱼袋林遹篆盖
口口口口口博学恬进之君子罗公讳畸,字畴老,南剑州沙县人也。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卒于沙县尉,因家焉。曾祖世口口口口闻,祖觉,擢进士第,终广德军理掾。父安中,有辞藻,以公贵,累赠中奉大夫。
公幼警敏,自始就学,婉如夙习,日口口口口口,出群异甚。弱冠游上庠,声誉轰然不可掩。熙宁九年(1076)登科,调福州司理参军。部使者阻威,厉民伤士类,不畏口论。公浩然有归志,投檄访医,奉双亲之暇,杜门读书弥十年。着《史海》百余卷,于古今无所不窥。自六经、百氏传记、天文地理、医技能之说,靡不该(古通:概)括。
相继丁内外艰,居丧尽礼,孝诚感格。兽驯墓侧,芝草生于庐。服除,叹曰:吾养不及亲矣!当移口口口口报。乃调滁州司法参军,明谳(审理案件)狱,疑濵(古通:滨)死,而平反者十余人。州将谓公守法为立异,欲劾之。公委曲辩论,不口口口口口口深相知,力荐于朝。任满到阙(古通:缺),会庙堂议设科目,代制举。公首中其选,名益彰。执政欲寘(置)之馆阁,力丐外官,除华口口口(州教授,据《沙县志》补),口则一遵太学教导之法。华人素尚气峙,崖岸为高,初未驯服。徐相告曰:罗公以规矩成我,非苦我也。俱勉而为善,世风丕变。其后,陕右诸郡舍法所取,唯华人应格为多。除太学録,迁博士,又迁太常博士、兵部郎官。大臣荐对从容,移刻,擢秘书少监,愈益恬晦。所乐者,徧(古通:遍)读人间未见之书,其余弗少贬也。居职最淹久,作《蓬山志》五卷,凡芸阁兴废始末,图书文籍之盛,与夫一时荣耀。希阔事,不待搜索,开卷炳然。
崇宁中(1102—1106),辟雍落成,有口口口儒臣许赋诗颂,献者无虑。数百口口口口臣次其高下奏,公为第一。口口口特令进官。初莅华学(注:华州学宫简称),举行释菜礼,既罢去,留俸给百斛,遗职事,诸生俾继承勿替为奉常。论孔子冠冕,当以王者口口旒为定制。至于十哲像设之位,亦加订正,朝廷并颁行于天下。尝猝然被命,作《奠献乐章》二十余首,落笔而成,识者口口口。
大观初(1107—1110),扰章恳外,凡三请,除殿撰,知庐州。未几,移知福州。所至必先问民疾苦,虽值旱蝗,随车雨足,人赖以安。异时,口口守将口移易僧舍,上下干请为市,公力革其敝(古通:弊),却权贵,书简游谒者,一不敢造前。暇日,按行府宅,至逍遥堂,视其榜,口建安刘口所立也。因作“仰止轩”,以景慕焉。已而,得宫祠还里,即所居,疏池沼,辟斋舫,唯诗书之娱.对宾客,剧(古通:只)谈古人忠口口口之美,未尝辄口声乐也。好施药剂,急人患难,凡久于弓口殡,力未能营措者,悉助而葬之。绝口不言人过,虽有诈者,不逆也。
宣和二年(1120),擢知虔州,公既拜命,慨然曰:“坐縻禄廪岁月甚久,每窃自愧,今敢辞劳乎。”虔于江西,俗素犷悍,为州口尚威,峻刑罚,公独以静镇之。居数月,囹圄亦空。本朝清献赵公治虔,政甚简易,严而不苛。尝瞰章、贡二水,为台于其口口而新之,绘其遗像而祠焉。欲以慰邦人之思也。州既治,乃清宫观,亟求玄章,再未上报。忽一日,夙兴盥漱,具衣冠,端口口口,于家世、子孙之事,无片言及之。享年六十有八。州人为之罢市而巷哭,贫者鬻衣致奠焉。盖公慈祥淳厚,至诚口口,虽赣号难治,亦不待岁月之久也。尤喜内典清心养气之学,无世俗嗜好萦其胸中,故由初迄终,其完如此。有书《讲口》五卷、《道山集》三十卷、《五经发题》五卷、《芸阁秘録》四十卷、《洞霄録》十卷,其余遗稿,在人尤多。
初娶张氏,口部郎中绎之女,口宜人。口娶陈氏、奉议郎璞之女,封宜人。三男,子彦温,从事郎、邵武军刑曹。彦远、彦洁皆将仕郎。女,一人,适进士张敦复。以宣和六年(1124)三月初一日己酉,葬于傺村先茔之侧。尚书兵部郎中张哿状公行甚详,可传不朽矣!彦温过听,乃误以志铭见委,屡辞莫敢承,又走人千里来浙东,其请益坚,终难以辞,辄论次而铭之,曰铭:学以求志,仕非慕禄,养德弥邵,位则不足;名高口绅,惠泽在民,口违于神,垂裕后人。
平津徐福摹上石
附二:宋·朱熹《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绯鱼袋罗公(博文)行状》①
公讳博文,字宗约,一字宗礼,南剑州沙县人。曾祖安中,赠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邓氏。祖畸,朝请郎,右文殿修撰。妣宜人张氏,宜人陈氏。父彦温,右从事郎,知建州瓯宁县事,赠右承议郎。妣太孺人邓氏,太孺人黄氏。罗氏,世为豫章人,唐长庆中(821—824),有为沙县尉以卒者,子孙因家焉。至五世孙觉始举进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显重于世。又再世而得公,复以道学行谊克世其家,有闻于时。然位卑数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识者恨之。
盖公少有异质,生岁始周,家人示以啐盘,公一无所顾,独扶服前取书之论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叹异,为文以记其事,且曰:“是儿当复以文学大吾门,且复闻道,而不为章句之习也。”十余岁,遭瓯宁府君之丧,哀毁如成人。治丧葬又皆必诚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补将仕郎,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户参军。治仓庾谨出纳,尽去宿弊,后皆可法。
再调静江府观察支使,桂管为岭檄以西一都会,民物繁伙,常时幕府已不胜事。至公为当路所知,事待公决者尤多。公财处从容,人未尝见其疾言遽色,而事无不各得其理者。时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窜斥,系踵南来,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廪奉,则鬻衣以济其乏。用荐者,改右宣议郎、知赣州瑞金县事,转宣教郎。
始至,岁歉,公度民且饥,则先事为备,多所储积。及饥,发廪赈赡,事无巨细,必躬临之,不以勤劳为惮。其至诚恻怛,虽壹主于惠爱无所计,惜而厝置,织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赖以全,而公又请推其馀,以及旁县。县故多盗,公饬巡徼,设方略,得渠帅数人置诸法,而境内帖然。在官余九月,会故丞相魏国张忠献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请以为干办公事。用上嗣位覃恩转通直郎,赐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数千人以归。和籴建康以实军,又以公与其事。未几,得穀亦巨万计。
张公再入相,宾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制置全蜀,奏辟公参议官以行,军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虚心好问,公亦推诚启告,反复殚尽,必归于至当而后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为多也。尝衔命汉中,劳抚将士,宣抚使以礼致遗,为钱三百万。公不欲受,而难于辞却。还次汉州,州方治贡院不能就,以五十万予之,余悉输成都公币。(罗博文)取河南程(颐、颢)夫子之遗文,与他名臣论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锓板,用之略尽。而横渠张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贫不自振。公访得之,为言汪公。延置府学,蜀士知所劝焉。东方士大夫游宦蜀土,贫不能归,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业之,赖以济者甚众。累迁承议郎,秩满,自请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命下,而汪公亦召还,公复从东。至嘉州留宿,与同舍会集笑语如常时。一日,忽语人曰:“吾将逝矣,然幸大事已竟,无可憾也。”遂就寝,酬酢从容,了不异平日,独无一语及其私,俄而遂化。
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盖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装以理丧事,则囊中独有书数十帙,余金足以归其丧而已。相与咨叹,以为不可及,遂以柩归。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沙县严地祖茔之旁。公娶陈氏,了斋先生之兄孙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问,曰辟。孙男八人,女七人,皆幼。
公资禀和粹,沈静寡欲,其处已待人,一主于诚敬。平居愉怡,人莫见其喜愠之色。闻人之善,称慕如不可及,至其有过,则常若有所隐避,而不忍言也。视人患难困乏,如切其身,经营周救,必尽其力。年未三十,即屏远声色,一榻萧然,惟乐善不倦如嗜欲。闻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几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胜,概多所登历,而于佛、老子之学,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诚笃好之,而不知公之所志,与其所学,有不在是也。盖尝从张忠献公问行已之大方,张公为手书所为敬说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终身不懈。又从同郡李愿中先生游。闻河洛所传之要,多所发明,于是喟然而叹曰:儒佛之异,亡他,公与私之间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坚。在桂州时,汪公盖方通判州事,知公所为,日就公语,且亟称道其为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员外郎刘公芮,亦方隐,居州之西山,躬耕励志,人罕识之。公独以坐曹决事之余,日往从之游。刘公名家子,及见前辈,多识前言往行,顾独恨得公晚,及闻公卒,哭之恸,为寝疾不食者数日,此岂势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业之美,固当有于为世,而充养有素,神观清明,人亦不谓其止于此也。呜呼!其可谓不幸也已。
熹尝受学李先生之门,先生为熹道公之为人甚详,于其从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张公高明闳大有余,而宗礼以精密详练佐之,幕府无过事矣。”时熹未识公也。及先生殁,乃获从公游,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后益信先生为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数千里,书问岁亦一再至,所以劝励从学者殊厚,日夜望公之还,几得复相与讲其旧学,而公乃以丧归。熹既痛公之不幸,不及大为时用,又伤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诸孤既号哭受弗,则以公从弟颐所叙官阀梗概一通授熹,使状次之,将以请铭于作者。熹谊不获辞,既趣以就事矣。惟是从游之晚,于公之行治有不尽知,大惧阙漏放失,将无以补采择为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财之。谨状。时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枢密院编修官朱熹状。
附三:宋·汪应辰《沙县罗宗约墓志铭》①
宗约罗氏,讳博文,曾祖安中,赠中奉大夫,妣恭人邓氏。祖畸,朝请郎、右文殿修撰,妣张氏、陈氏,皆宜人。父彦温,右从事郎,知建宁府瓯宁县事,赠右承议郎,妣邓氏、黄氏,皆赠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长庆中有为南剑沙县尉者,因家焉。五世孙觉始举进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显重于世。至宗约,复以道学行谊,克世其家焉。
宗约生有异质,家人试以晬盘,一无所顾,独匍匐取书册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叹异,为文以记其事。年十余,遭瓯宁府君丧,哀毁如成人。治丧必诚必信。用右文公奏补官,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户参军。临事不苟,无巨细皆有条理。再调静江府观察大使,桂管为岭檄以西一都会,府事既已丛剧,而连帅监司,亦多委以事,宗约皆从容置办。时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窜斥,系踵南来,宗约悉善遇之。至或鬻衣以济其乏。改右宣义郎、知赣州瑞金县事。始至岁歉,宗约先事储积,既而发廪赈赡,事皆躬临之。其至诚恻怛,虽一主于惠爱无所惜,而措置纤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县故多盗,宗约设方略,得首恶数人,置诸法,境内帖然。会故丞相魏国张忠献公都督江淮,请以为干办公事。其募兵和籴,皆不扰而济。张公再入相,宾客例出幕府,以宗约知和州,未赴,而四川制置使奏辟为参议官,宗约详审精密,每论事反复殚尽,归于至当而后已。尝至兴州劳将士,宣抚使以礼致遗,为钱三百万。宗约不欲受而难于辞。还次汉州,州方治贡院,以五十万助之,余悉输制置司公帑。横渠张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贫不自振。宗约访得之,为言于帅,延至府学,蜀士知所劝焉。士之游宦蜀土,贫不能归者,宗约出捐俸钱周之,赖以济者甚众。累迁承议郎,秩满,得请主管台州崇道观,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来问者,宗约虽疾病,而拱手端坐无惰容,盖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将逝矣,然幸大事已竟,无可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行聚而哭之,解其装以理丧事,则独有书数千卷,余金仅足以归其柩而已。相与咨叹,以为不可及。十有二月壬寅,葬于沙县岩地祖茔之旁。
宗约娶陈氏,了斋先生之兄孙女也。子男二人,曰问,曰辟;孙男八人,女七人,皆幼。
宗约资禀和粹,沈静寡欲。其处已待人,一以诚敬。平居怡愉,人莫见其喜愠之色。闻人之善,称慕如不及;至其有过,则常若有所隐避而不忍言也。视人患难困乏,如切其身。年几三十,既丧其藕,屏远声色,一榻萧然,惟乐善不倦如嗜欲。闻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几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愿中,受业于龟山先生杨文靖公,宗约从之游,多所发明。于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亦坚矣。然宗约之为人,虽笃意学问,而不为文词;虽力行善事,而不徼名誉;虽爱众亲仁,而非以为取悦也。故世知宗约者亦鲜矣。其孤以枢密院编修朱熹元晦所为行状,以来请铭,余与元晦盖皆知宗约者。
铭曰:汲汲其求,兢兢其持。保此无憾,全而归之。
2.宋·罗博文《书议论要语卷后》
在《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沙县版)》收录的、由李侗门生罗博文所撰写的《书议论要语卷后》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伯祖(祖父的兄长,父亲的伯父)先生《议论要语》,得之于眉人(指上寿之人)石安民大任(称指担任重要职务者)。其仲父道叟公辙,绍兴乙卯(1135)尝为延平学官,获此,题云:“传之郡人彭君”。今先生已(原字为“云”,今据上下文之意改)亡,无所取证,恐兵火之后飘散未可知。观其议论高致,真有用之学,致主庇民修身养心,尽在于斯于是,知先生之学不为空言也。归,当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审订之。时乾道丙戌(1166)十月寓成都燕堂,罗博文敬书。①
这份难得的、似乎能够完全说明“罗博文与罗从彦具有亲属关系,罗博文是沙县人,因此罗从彦也是沙县人”的《书议论要语卷后》,自宋以来一直就被主张“罗从彦是沙县人”的历代学人勤加应用,最终形成了代代相传、互相征引的“亲缘认定”。比如,明代叶联芳《重修沙县志》,沿用该说法称:“罗畸(罗博文祖父),字畴老,从彦之从父(祖父亲兄弟的儿子)兄弟。”②明代方志学家黄仲昭修撰《八闽通志》,也明确表述罗畸是“从彦之从父兄弟”,罗博文是“殿撰畸之孙”③。而清人李清馥在编纂《闽中理学渊源考》时,虽然一方面继续照录着“罗博文云:延平先生之传,乃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学,源流深远”④;一方面却把“伯祖”改成“从祖”(祖父的亲兄弟。如果从祖年长于祖父,则为伯祖;如果从祖年幼于祖父,则为叔祖),称:“罗博文,字宗礼,一字宗约。祖畸,太常博士,从祖为仲素先生。博文用祖荫补将仕郎福州司户参军,再调静江府观察支使。”⑤
随后,乾隆版《罗氏族谱》在其自编的《豫章文集》里,又“不知不觉”将原来的“伯祖”撰改成“余祖”,干脆将自己从“同祖父之兄弟”的后裔直接变成了“同祖父”的嫡系后裔,硬生生把自己加塞到另一个祖宗的队伍里,让人啼笑皆非。对此,民国十七年(1928)沙县罗氏后裔罗克涵在主编《沙县志》时,就已经发现并及时订正了乾隆版《罗氏族谱》的错误,重新称:“罗畸,字畴老,从彦之从父(祖父的亲兄弟的儿子)兄弟。”⑥但是,现在版的《沙县志》却不知为何还是将其书写成:“罗畸,字畴老,沙县城关人,罗从彦的同祖父堂兄弟。”“罗从彦,字仲素,沙县城西洞天岩人。先祖原居江西南昌,旧属豫章郡,故世称豫章先生。为罗姓迁沙始祖唐元和十五年(820)沙县尉罗周文的第十二代后裔。”①不仅又将二人从“叔伯侄”的关系强变成“堂兄弟”关系,而且还把罗从彦确定为“罗周文(罗沂)的第十二代后裔”,根本不顾只把罗周文称为“七世祖”的罗畸会作何感想.可见这其中受乾隆版《罗氏族谱》错误影响的缘由和动机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
那么,事实上的罗从彦和罗博文关系,是不是就真如罗博文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某(我)伯祖”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从罗博文留下的历史线索中去寻找答案。
考察史料,笔者发现历代典籍除了罗博文这唯一一个处处将自己与罗从彦联系在一起的、开口即言“某伯祖”的“傍名人”典型外,其他亲密如罗从彦与李侗(师生)、罗从彦与延年(师生)、李侗与罗博文(师生)、李侗与朱熹(师生)、朱熹与罗博文(学友)、陈渊与罗从彦(学友)、陈渊与罗博文(姻亲),重要如《罗从彦行状》《罗博文行状》《罗博文墓志铭》《默堂(陈渊)文集》《罗从彦墓志铭》等,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篇相关记载能够再次明确提到罗博文与罗从彦的亲属关系,这难道不会令人匪夷所思吗?更何况,在这篇从来没有被人质疑过的罗博文短文中,笔者又无意发现了一对并不具有亲属关系的石姓名人“石安民”和“石公辙”.不知为何竟被罗博文(抑或是假托罗博文之人)硬生生地牵连在一起,变成了关系密切的“叔侄二人”:
伯祖先生《议论要语》,得之于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叟公辙……
要知道,古代是以伯、仲、叔、季来表示兄弟间的排行顺序的.“仲父”本指父亲弟弟中的年龄最长者②。“石公辙”既是“石安民”之仲父,二人就理当为同籍之人。然而这里参照上下文意思所提到的石安民,却是罗博文在广西任上所结识的上级官僚、广西桂林临桂人石安民③,其于绍兴十五年(1145)中进士,1170年知制诰学士并留题广西贵港南山寺④,是一个有据可查的、地地道道的广西人;而石公辙,则是绍兴二年(1132)罗从彦准备就任广东惠州博罗县县尉时,以南剑州太守周侯绾之命主持当年南剑州州学释菜大典的、如假包换的浙江绍兴新昌籍特奏名状元石公辙①,其作为一个大器晚成的特科状元的传奇经历,甚至还绘声绘色地出现在了同为浙江(婺州)人的方勺笔下:
大梁二相祠,世传游、夏也。士有未遇,上书乞灵,往往见梦,虽远必应。越人石公辙妙年乡举,抵京,梦帘中出一纸,只“邻州”二字。石后累举,年逾五十,不得已,就特奏名,遂为第一,例赐出身。是时,上驻跸临安府也。②
试想一下,二人如果真是只由“罗博文”亲笔勾连成叔侄关系的话,那么这样的错误也就不是一般的错误了。
因此,为小心印证、避免错判这一重要的人物关系,笔者尽可能多地搜集到了与石公辙有关的宋代史料,发现这个被确认为“石安民仲父”的浙江人石公辙与广西人石安民之间,着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交往问题”,是很难按照情理解释的两个“有叔侄关系的人”:
第一,石公辙在绍兴二年(1132)以特奏名第一人的身份就任南剑州州学教授时,已经年逾五十,其在南剑州任上所得到的几不多传的罗从彦《议论要语》,为什么只愿意“传之郡人彭君”而非自己“博学多能的侄儿”,这在情理上应该作何解释?
第二,“郡人彭君”在得到罗从彦的《议论要语》后,却为何要将其转传于广西人石安民而不是来自于同郡的“罗从彦族亲罗博文”?
第三,石安民在得到这本珍贵的《议论要语》后,又为何还要将其转传给罗博文,这期间的关系瓜葛究竟为何不肯交待清楚?要知道,这份由罗博文最后得到的、被转来转去留有题字的罗从彦《议论要语》,很有可能是一份原本而非抄本!
由此可见,仅就石公辙与石安民的身份关系而言,罗博文的这份《书议论要语卷后》就有诸多值得存疑的地方,更何况那个生怕别人都不知道的“某(我)伯祖”之说呢!
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疑问外,我们还能清楚看到的事实就是,罗博文撰写这份《书议论要语卷后》的时间为乾道丙戌年(1166)十月,此时,他还寓居在成都燕堂,离去世尚有两年。其文所说的“归,当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审订之”的重要设想,最终也因为他的卒于途中而无法达成所愿。为此,清代黄宗羲在编订《宋元学案》时,就专门对此考证说:
朱子与宗约(罗博文),在延平(李侗)门人,最为契合。然朱子之交宗约,在延平殁后,宗约寻又入蜀,其相与不过一二年耳!宗约于蜀中得豫章《议论要语》,曰:“归,当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审订之。”则其所推服,朱子而外,无人焉。乃宗约卒于途中,此言遂成虚语,可叹哉!①
由此看来,不论罗博文自称的“某(我)伯祖罗从彦”,也不论其所传得于石安民、石公辙的《议论要语》也罢,朱熹其实都没对此做出明确审定,孰是孰非,当然也就不好做出明确判断。故明天启篁路村重修《罗氏宗谱》在收录罗博文写给罗从彦的《元祖文质公赞》时,也仅仅只将其身份标注为“族侄”。
附四:宋·石公辙《志释菜事》②
教授石公辙
绍兴二年壬子,州学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罗县尉罗从彦以太守周侯绾之命,领袖诸生宗昇、张元侯、符藻、廖援、张维、廖拱同行释菜之礼,有洙泗断断气象。而吾友吕君仁舍人以诗见褒,不免有过情之誉。然意在纪实,谨刻石而龛诸夫子庙壁,俾来者有感发焉。
会稽③石公辙道叟谨志
3.宋·盛木《题义恩祠壁》
《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沙县版)》除了收录一篇能够“表明罗从彦与罗博文身份关系”的《书议论要语卷后》外,同时还收录了一篇能够“表明罗从彦与罗畸身份关系”的《题义恩祠壁》,其文明确说到:
从彦,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罗主簿,先生官也。先生姓罗氏,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罗畸曾任右文殿修撰,故以官名称呼其为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即二人的五世祖①是兄弟)。……先生(罗从彦)无嗣,诸经解遗文在诸从学者家。《春秋解》,昔宗约处见之,此先生之文也。先生同殿撰公肄业于义恩寺,后绘先生遗像从祀于先世香火之侧。盖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故也。宗约官桂林,(盛)木自广西从宗约归延平。宗约西行改秩(改变官吏的职位或品级。多指提升),馆木此寺以俟其归。尝闻宗约讲及先生道学梗概,今拜先生遗像起敬起慕之余,拾旧所闻,辄敢僭易。书于祠侧之壁,复系之以辞云:“先生之学,精一之学。先生之传,伊洛之传。至道无文,至学无词。以心传心,天地不知。先生之道,天人之师。其道光大,有俟他时。朅来瞻慕,后学得依。”时绍兴乙亥(1155)十月廿日东里盛木任叔题。②
初读此文,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是:
第一,河南东里人(今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寺王村)盛木是罗博文的好朋友,其对罗博文的家族世系表现得相当熟悉,历代典籍也只有他非常明确地提到:“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罗从彦)无嗣,诸经解遗文在诸从学者家。”
第二,罗从彦与罗畸不仅“五世祖是兄弟”,而且二人还是同学,他们在一起学习的兼有学校功能的“义恩祠”(祠在沙县北九都),为罗从彦的八世祖捨田所创(一说为罗畸七世祖罗周文所创,详见沙县罗从彦纪念馆宣传栏),奉祀有先世香火,可惜未题其名讳。
第三,绍兴乙亥年(1155)十月,盛木跟随年已40岁③的罗博文从桂林任上返回延平时,恰遇罗博文被提拔任用——“……再调静江府④观察支使,桂管为岭檄以西一都会,民物繁伙,常时幕府已不胜事。至公为当路所知,事待公决者尤多。公财处从容,人未尝见其疾言遽色,而事无不各得其理者。时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窜斥,系踵南来,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廪奉,则鬻衣以济其乏。用荐者,改右宣议郎、知赣州瑞金县事,转宣教郎”。①因此单行的盛木只好借居在义恩祠等待着罗博文的回返。
然而深读此文,我们却可以发现:
第一,不知为何,留文不多的罗博文特别爱向他人强调自己与罗从彦的亲缘关系,尽管他的其他亲友中也不乏有不同凡响者;尽管直到他自己去世时(1168),罗从彦也都还没能成为一个享有盛名的人。
第二,所有那些引发后人议论的重大问题,盛木都已“非常具有先见”且“非常巧妙”地告知了大家。比如,对于“罗从彦到底是延平人还是沙县人”,盛木说的清晰而又婉转:“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因此,只要罗博文或罗畸被确认为沙县人无疑,那么罗从彦自然也就要是沙县人。再比如,对于“罗从彦到底有否子嗣”,盛木的回答更加直截了当:“先生(罗从彦)无嗣,诸经解遗文在诸从学者家。”这些关键信息以如此“毋庸置疑”的语气密集出现,难道不会让人感觉有点太过蹊跷?要知道,那份明确说明罗从彦有其嫡传子嗣的《豫章罗先生墓志铭》,正是罗从彦的正传弟子李侗亲笔所撰,而李侗又是罗博文所最最敬重的学术导师,三人间单凭这样亲近的师生关系,就绝不可能把罗从彦有无子嗣的重大问题简单搞错。那么,盛木此言从何而来?
第三,盛木只是沙县人罗博文“官桂林”时所结识的一个好朋友而已,他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前“自广西从宗约(罗博文)归延平”,又恰巧碰上宗约“西行改秩”时,必须长期留在义恩祠的合理理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依据上文所引朱熹《罗博文行状》可以知道,罗博文从桂林任上离职后,就在他人推荐下“改右宣议郎、知赣州瑞金县事,转宣教郎”。因此,依照广西、福建与江西的地理位置判断,原本要带着好友“归延平”的罗博文既然是“西行改秩”而不是“东行改秩”,那么他就应该是已经回到福建而后再决定“西行”前往江西,根本不太可能是自己直接前往江西而让盛木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借居在人生地不熟的沙县义恩祠苦苦干熬。更何况,根据文内所表达的行程安排,沙县人罗博文如果只是要带着好友“归沙县”看看“沙县人罗从彦”的话,那么他的目的其实已经完成(义恩祠就在沙县境内),根本没必要再“馆木此寺以俟其归”。因此,唯一能够说明盛木要居留在沙县义恩祠并耐心等待罗博文回来的真正原因,就是盛木希望罗博文回来后,能够继续带着他“归延平”拜访罗从彦故地,这其实也是他一开始就要表达的目的所在,只是从来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罢了。
第四,如果“义恩祠”真是罗从彦的八世祖捨田所创,祠内又奉祀有罗从彦的“先世香火”,那么,“义恩祠”就应该算是罗从彦的家祠,而对于罗从彦的家祠,仅仅只是作为罗从彦“五世兄弟”后裔的罗博文,究竟有没有资格把自己的朋友安排到罗从彦的家祠里长时久候?
第五,如果“义恩祠”真是罗从彦的八世祖捨田所创,祠内又奉祀有罗从彦的“先世香火”和“先生遗像”,那么,其父罗神继、其祖父罗世南、其曾祖父罗文弼、其八世祖罗某某的神牌是不是也应该位列其中?既如此,其先祖名讳又为何不能够被清楚点出?
第六,如果“义恩祠”真是罗从彦的八世祖捨田所创,那么,参照《南平县志》“罗从彦,据谱八世祖京城(即京成,疑为笔误),自豫章避难来家剑浦,生子二人,一徙沙县,一止镡城”①的说法,是不是不仅“沙县罗氏确有一支是从剑浦县迁徙而去”的说法可以得到证实,而且其所谓的“先生八世祖”的名讳也可以被证实就是罗京成?更何况,对于“沙县还有没有存在一支从剑浦县迁徙过去的京成公后裔”的调查工作,其实早在罗从彦五世孙罗良佐要兴修族谱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良佐公,讳良佐,字尧卿,……历官汀州教授。先淳祐八年(1248),曾适沙阳,访殿撰畴老公宗派,值干戈告变,途中有儆,不果,虚回。至晚年,询及故老,遍阅年谱及言行录数卷,即编成宗谱,大有伦次。其规模宏远,前为元宗,后为鼻祖,信夫。”②
第七,参照古人称谓习惯,如果盛木所说“先生(罗从彦)与宗约(罗博文)王父(祖父)殿撰公”五世祖真是兄弟的话,那么吴点《宋故殿撰罗公(畸)墓志铭》提到的“罗公讳畸,字畴老,南剑州沙县人也。其先居豫章,七世祖沂卒于沙县尉,因家焉。”③与李侗《豫章罗先生墓志铭》提到的“数传来,惟罗最蕃衍,迁徙靡一。于时或沙或剑。而剑宗为先生远祖京成公。初居剑郭,久之,复居溪南篁乡。其曾大父文弼,大父世南,父神继,奕叶潜鳞,代有齿德”④不就成了大相径庭、互为矛盾的两种记载了?如:罗周文(罗畸七世祖,谱名罗沂,785—873)→(六世祖,名讳缺)→(五世祖,名讳缺,高祖)→(四世祖,名讳缺,曾祖)→罗觉(罗畸三世祖,祖父)→罗安中(罗畸二世祖,父亲)→罗畸(本位,第一世,1057—1124)→罗彦温(儿,第二世,亦称一世孙)→罗博文(孙,第三世,亦称二世孙,1116—1168)。
罗周偁(罗从彦十世祖①,842—?)→罗仪贞(九世祖,862—961)→罗京成(八世祖,875—929)→(七世祖,名讳缺)→(六世祖,名讳缺)→(五世祖,名讳缺,高祖)→罗文弼(罗从彦四世祖,曾祖)→罗世南(罗从彦三世祖,祖父)→罗神继(罗从彦二世祖,父亲)→罗从彦(本位,第一世,1072—1135)→罗敦叙(儿,第二世,亦称一世孙,1096—1133)→罗振宗(孙,第三世,亦称二世孙,1134—1194)。
如此看来,罗从彦与罗畸二人的辈分关系怎么都不能构成是“五世兄弟”。因此,在两篇石刻墓志铭都不可能有假的情况下,最大的谬误就只能来自于与罗氏关系最为疏远的、仅以文字传世的《题义恩祠壁》。此外,罗氏通谱网不知何以为凭点明的罗从彦八世祖名讳,也同样令人感到不知所措:“豫章先生祠……一在沙县洞天岩西麓。五世孙天泽请邑司建。……一在沙县义恩祠,祀八世祖熙载。”②
综上可见,盛木这篇看似言之凿凿的《题义恩祠壁》,的确存在诸多不能解释的存疑之处,如果我们单单仅凭其言就轻易得出有关罗从彦地籍、后裔的关键信息,那是一定很难令人信服的。
4.民国·翁国梁《洞天岩志》
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一月,沙县前行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翁国梁先生所作的《洞天岩志》,该书《自跋》一文对于编撰此书的缘由说明是:“余寓沙阳将一载,爰撰《洞天岩志》三万言,网罗遗文旧事,以存掌故;并录神奇,里巷琐言,以供谈助。凡山川、人物、艺文、古迹,总汇叙述,经纬条贯,便于寻检,且明本末,创志书之新格。沙邑人士为欲阐扬桑梓文献,保存古迹名胜,此书得以出版,而黄颂慈、洪可良、陈绍忠、林衡山诸君,与有力焉。”③
笔者通过对全书的详细阅读以及对网上资料的收集了解,得知该书的作者翁国梁,号春雪,其时曾就职于福建省立医学院,非常热衷于对地方民俗和地方史志的研究,是一名负有相当知名度的年轻教师:其书名题署者为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可谓是时运相亲;其书后附录的“本书作者其他编著”共40本,可谓是著作等身;其各个书目后所附着的题序或题笺,赫然出现着顾颉刚、于右任、郁达夫、蔡元培、容肇祖(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林森(国民政府主席)、丁文江(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鼎鼎大名,可谓是往来风雅;其在书目附录后所摘录的“名家书评”,分别来自江西教育厅长程时煃、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闽浙监察使(1935年兼任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福建民政厅长高登艇、福建教育厅长郑贞文、海军上将李世甲等官家政客,可谓是交游广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涉猎全面、了解事物无所不包的文化名家,却在跟随福建省军事、文化、教育机构内迁永安、沙县的一年间,留下了他在游览洞天岩后立志“且明本末,创志书之新格”的《洞天岩志》,对罗从彦与沙县的关系问题做了这样考订:
按豫章先生,旧以为剑浦罗源里人,后居沙县,盖先生始祖自豫章来,原迁沙县,后迁罗源,后又归沙县。据先生集载,绍兴乙亥东里盛木,博文友也,《题义恩祠壁》云:“是祠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先生同殿撰畸肄业于此”,此则先生复居沙阳明矣。又集载,先生录《龟山语录》云:“第四卷《毗陵所闻》,注云:‘辛卯(1111)七月,自沙县来,至十月去。’《萧山所闻》注云:‘壬辰(1112)五月又自沙县来,至八月去。’”若非居沙县,何曰“自沙县来也。”今考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之麓,至郡寇乱后,罗氏始衰,废其所游息。颜乐斋、濯缨亭等景,正在洞天瀑布之滨,且得与默堂相倡和。闻罗源里无泉石之奇,必非其所也。其葬罗源,第以李公扶柩至延平,故袝之祖墓侧耳。①
文中为着力证明“罗从彦是沙县人”,不惜援引了几个因果不对的逻辑判断,但最终给人的感觉却只是证明“罗从彦曾经住在沙县而已”,其具体说法如下:
第一,沙县人罗从彦因为先居剑浦、后居沙县,因此过去有人认为罗从彦是剑浦人。但实际情况却是:罗从彦始祖自豫章来,原迁沙县,后迁罗源,后又归沙县。罗博文好友盛木《题义恩祠壁》所说“是祠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先生同殿撰畸肄业于此”,就是罗从彦复居沙县的明证。
原文表述:按豫章先生,旧以为剑浦罗源里人,后居沙县,盖先生始祖自豫章来,原迁沙县,后迁罗源,后又归沙县。据先生集载,绍兴乙亥东里盛木,博文友也,《题义恩祠壁》云:“是祠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先生同殿撰畸肄业于此”,此则先生复居沙阳明矣。
第二,罗从彦所录《龟山语录》有多处注明其拜师龟山(杨时)时,都是“自沙县来”,如果不是住在沙县,又怎么可以说是“自沙县来”呢?
原文表述:先生录《龟山语录》云:“第四卷《毗陵所闻》,注云:‘辛卯(1111)七月,自沙县来,至十月去。’《萧山所闻》注云:‘壬辰(1112)五月又自沙县来,至八月去。’”若非居沙县,何曰“自沙县来也。”
第三,在罗从彦和陈渊诗作中多次出现的颜乐斋、濯缨亭、寄傲轩等建筑都只出现在洞天岩附近,剑浦县罗源里因为没有“泉石之奇”,因此一定不是罗从彦的所居之地,至于他为什么会最后归葬于罗源里,只是因为李侗要把他的灵柩扶归至延平(今南平市延平区)他的先祖旁祭祀而已。
原文表述:颜乐斋、濯缨亭等景,正在洞天瀑布之滨,且得与默堂相倡和。闻罗源里无泉石之奇,必非其所也。其葬罗源,第以李公扶柩至延平故袝之祖墓侧耳。
阅读翁国梁按语中所作的这些逻辑判断,很容易让人产生“不管罗从彦之前是哪里人,只要证明他是住在沙县的,那他就是沙县人”的荒谬结论。而在中国,任凭谁都知道,一个人的祖籍和地籍都只能有一个,如果有人只是要以一时之“居”来定籍的话,那么已经无法开口的罗从彦就会被强行冠以“延平人、沙县人、连城人、博罗人”等多个地籍。由此可见,仅仅因为某人“居在某地”就可以抛开所有因素来断定“某人是某地人”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罗氏通谱网登载的《福建罗氏源流初探》虽然也还依据某些错谬之事来主张罗从彦是沙县人,但却依旧不得不承认:
罗从彦,是福建著名的罗氏名人,字仲素,时学者尊称豫章先生,南剑州人沙县人。(《福建通志》考证其为沙县人,盖据晚年定居而言,祖籍而言,但其生在南平罗源乡,墓在南平)。宋绍兴二年(1132)特科进士,授博罗县主薄。是宋代理学(集儒、佛、道于一体)的重要人物。①
附注
②苏闽曙《沙县宋故殿撰罗公墓志铭考释》,《福建文博》2011年第2期,第73页。
③(宋)盛木《题义恩祠壁》,《豫章文集·卷十六·附录下》,《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72—773页。
①http://www.luoshi.net/newsl/shownews.asp?NewsID=1686罗氏通谱网:沙县资讯网沙村一雄编辑《沙县发现宋故殿撰罗畸墓志铭》
②http://luoshi.net/newsl/shownews.asp?NewsID=1697罗氏通谱网:罗训森《机缘巧合宋·右文殿修撰罗畸墓志铭》
③苏闽曙《沙县宋故殿撰罗公墓志铭考释》,《福建文博》2011年第2期,第73页。
④罗焕南《罗从彦后裔考略》,罗训森主编《中华罗氏通谱》第七期(内刊)2004年11月28日版,第58页;http://www.luoshi.net/NEWSl/shownews.asp?NewsID=3747罗氏通谱网亦有全文刊载。
⑤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154&index=1271&李启宇主编《沙县志·第三十三篇人物·第一章传记》,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
①沙县《豫章郡·闽沙罗氏族谱》卷二《文弼系·世系部》第1页。
②苏闽曙《沙县宋故殿撰罗公墓志铭考释》,《福建文博》2011年第2期,第7072页。
①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绯鱼袋罗公(博文)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22—4526页。
①(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二·沙县罗宗约墓志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805—806页。
①(宋)罗博文《书议论要语卷后》,《豫章文集·卷十六·附录下》,《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73页。
②张卿子点校《重修沙县志·洞天岩志》第一部分(明)叶联芳《沙县县志·卷之八·人物》,据嘉靖乙巳年刻本重刊,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③(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六十九·人物》(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654页。
④徐公喜点校,(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文靖李延平先生侗学派·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⑤徐公喜点校,(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文靖李延平先生侗学派·承议郎罗宗礼先生博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84—85页。
⑥(民国)罗克涵纂、梁伯荫修《沙县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3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据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影印。
①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154&index=1271&李启宇主编《沙县志·第三十三篇人物·第一章传记》,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
②《释名释亲属》解释为:“父之弟曰仲父。仲,平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
③石安民,生卒年待考。宋代官吏。字惠叔,广西桂林临桂人。宋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曾任象州判官,执法严明,决狱明恕。后分教廉、藤二州,提倡德教,文风大振。早年曾从沈晦、胡寅游,受知于张浚。能文善诗,博学多能,与其弟安行、安时并称“三石”。后知吉阳军(即今海南三亚。宋置崖州,后改曰吉阳军,明复为崖州),未赴而卒。其事迹参《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五、《宋元学案补遗》卷四十一。
④http://www.gxgg.gov.cn/news/2011-07/16558.htm《贵港市(广西)南山寺大事编年表》:1170年,知制诰学士、临桂石安民来游,留题丹灶对面。1173年,郡守、桂林人唐弼,书石安民诗跋摩崖。
①石公辙,字道叟,浙江绍兴新昌人,绍兴二年壬子科(1132)以特奏名第一人赐同进士出身(该年榜首为张九成),就任南剑州州学教授,曾以南剑州太守周侯绾之命主持当年八月落成的州学释菜大典。是年,以南剑州特奏名进士就任广东惠州博罗县县尉的罗从彦参加了该典礼。南剑州州学教授任后,石公辙又仕至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财用云。其族中兄弟石公弼、石公揆等也都是两宋之交的著名人物。
②(宋)方勺《泊宅编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延平门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298页:承议罗先生博文。
②(宋)石公辙《志释菜事》,《豫章文集卷十七外集》,《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77页。
③会稽,中国古郡名,位于长江下游江南一带,秦朝置。西汉末年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浙江大部以及福建地区,是当时辖境最为广阔的一郡,隶属于监察区扬州刺史部。三国吴时,分会稽郡置临海郡(今浙江东南部)、建安郡(今福建)、东阳郡(今浙江衢州、金华一带)。西晋至南朝末年,会稽郡仅辖今绍兴、宁波一带。隋文帝灭陈,废会稽郡,置吴州。隋炀帝改吴州为越州,后又改为会稽郡。唐初置越州,唐玄宗改越州为会稽郡,唐肃宗时复为越州,会稽郡遂不复存在,之后作为越州、绍兴的别称。
①五世即从本位起,上及父、祖、曾祖、高祖。
②(宋)盛木《题义恩祠壁》,《豫章文集·卷十六·附录下》,《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72—773页。
③参见朱熹所撰罗博文行状可知,罗博文逝于1168年,享年53岁,故该年罗博文40岁。
④静江是广西省桂林市的古称。宋高宗赵构登基之前,尝领静江军节度使。南宋绍兴三年(1133),升桂州为静江府,元改广西行中书省静江路,故桂林在南宋、元时期又称为“静江”。洪武五年(1372),明朝政府改静江府为桂林府,从此正式确定了桂林的名称并沿用至今。
①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绯鱼袋罗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23页。
①(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九·选举志第十三》,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476页。
②(宋)篁路村《罗氏宗谱·第五世祖良佐公行实》
③苏闽曙《沙县宋故殿撰罗公墓志铭考释》,《福建文博》2011年第2期,第73页。
④(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七艺文志》,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847—849页。
①据沙县罗从彦纪念馆资料、篁路村《罗氏宗谱》和罗焕南《福建罗氏源流考》、林荣发《三明罗氏源流概况》可知,罗周文生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元和十五年(820)改任沙县县尉;罗周偁生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与罗周文相差57岁,其后代罗京成生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是罗周偁的三传子孙。
②http://www.luoshi.net/newsl/shownews.asp?NewsID=1694罗氏通谱网:《罗氏祠庙》,录自罗水保、罗奎宗提供《罗氏文献》藏本。
③张卿子点校《重修沙县志·洞天岩志》第二部分(民国)翁国梁《洞天岩志》,据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重刊,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①张卿子点校《重修沙县志·洞天岩志》第二部分(民国)翁国梁《洞天岩志》,据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重刊,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①http://www.luoshi.net/newsl/shownews.asp?NewsID=707罗氏通谱网:罗训森《福建罗氏源流初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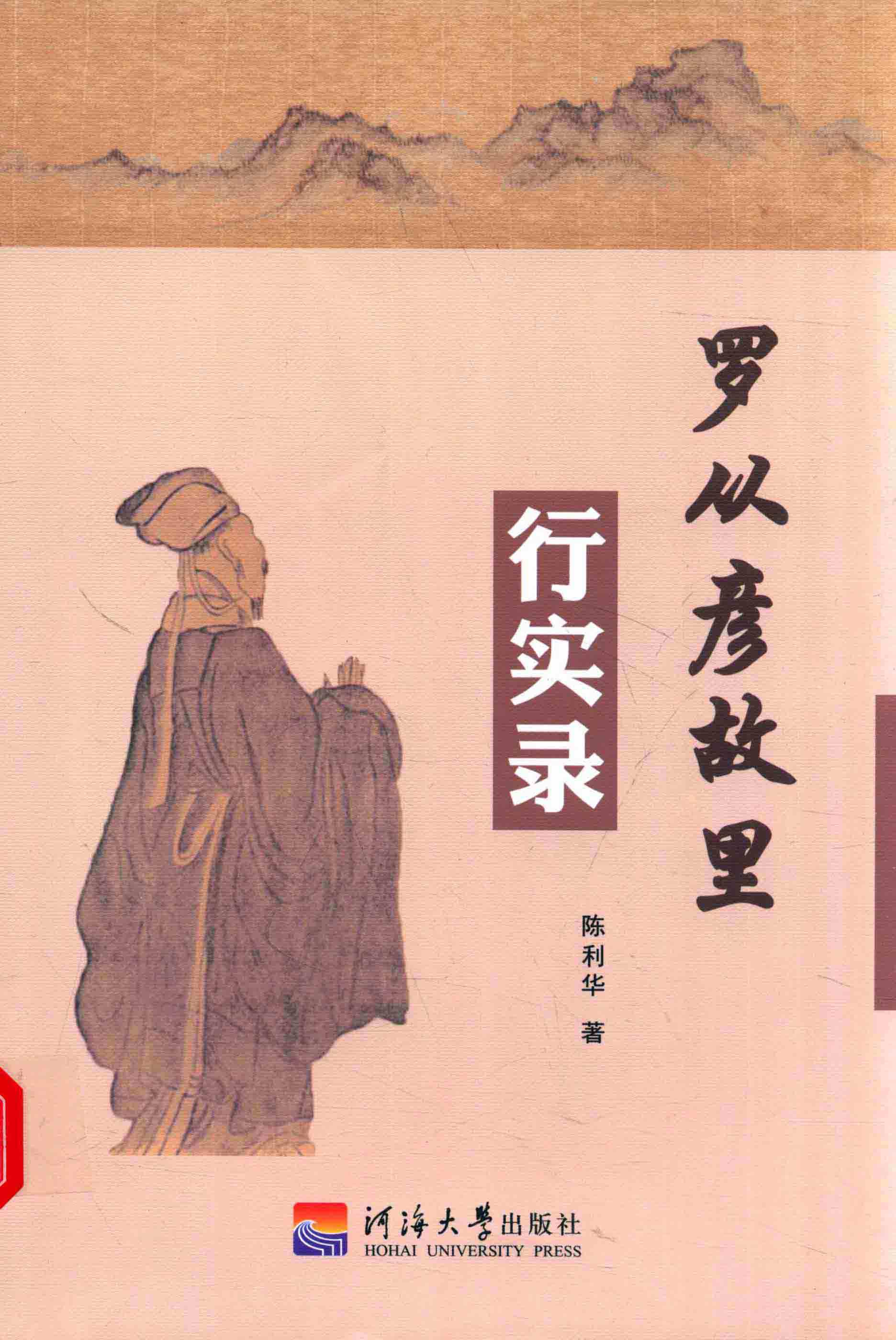
《罗从彦故里行实录》
出版者:河海大学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北宋理学大师、道南学派第二传人罗从彦的生平事迹、学派研究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及罗从彦的故里的建筑、名俗和历史文化发展与现代情况。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