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学家轻视文学吗?
| 内容出处: |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1224 |
| 颗粒名称: | (五)理学家轻视文学吗?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7 |
| 页码: | 377-38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宋代理学家虽以心性为务,但其视“理”于心外,而与所谓“心学家”产生分野。这一状况造成了“理学家视文艺为末流”的说法,成为一时之“公论”。在中国学界,讨论宋代文论者多把视野的核心聚焦在欧阳修、江西诗派、《沧浪诗话》等问题上。晚近以来影响较大的若干部教材,莫不如是。相比之下,理学家的文论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可有可无的陪衬或点缀。 |
| 关键词: | 朱子文化 诗词 文学 |
内容
宋代理学家虽以心性为务,但其视“理”于心外,而与所谓“心学家”产生分野。这一状况造成了“理学家视文艺为末流”的说法,成为一时之“公论”。在中国学界,讨论宋代文论者多把视野的核心聚焦在欧阳修、江西诗派、《沧浪诗话》等问题上。晚近以来影响较大的若干部教材,莫不如是。①相比之下,理学家的文论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可有可无的陪衬或点缀。
这不仅与文学实践史上如朱子等人“以诗名”的状况不符,也未必符合中国文论发展的实际状况。宋代以降,占据中国文学理论主潮的,恐怕不是严羽等处于文坛边缘评论家——同为闽北人的严羽,连一部起码的传记都没有留下。在理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之后(宋、元),中国文论的发展其实是以理学标准为框架的;可是,这在当代中国文论教材中很难寻觅到论述的笔墨。中国文论的历史书写,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理论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对宋代理学的“刻板印象”与文学概念既定模式的生硬运用。此处所言的“刻板印象”,是指“理学家轻视文艺”已成为中国文论史的定论。这种简明扼要的“结论”式命题,把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处理;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即理学美学或理学文学得到的关注极其之少——就文论系统的研究成果而言,宋代理学文论显不及其他朝代或同代其他流派的研究之繁荣;就理学系统的研究而言,理学文论又不及其他学科领域,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成果显著。
具体到朱子身上,据林庆彰和莫砺锋的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际学界关于朱子的研究著述达2254种,而文学研究不过寥寥三四十种。②就文学概念既定模式的裁剪作用而言,不同时代对“什么是文学”或“什么是文论”问题的回答,乃是确立其时文学、文论史书写基本范式的关键。与中国古代“诗言志”和“诗缘情”并举的状况不同①,当代中国文学经历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话语“洗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形成了以个人抒情对抗宏大叙事的先锋文学传统。在这套话语体系中,“文学”的价值天平倾向着“表现说”的立场,加之西方传入的形式意识,各种实验文学纷纷登台。用这种“文学”概念来裁剪文学实践,必然有因不符合“抒情”或“语言形式”要求而被淘汰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观念——理学家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便是典型。
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编撰才更多把严羽等在历史语境中并不显赫的人物作为一代文学精神的高标——这在后人的评价体系中当然不成问题,但如果将其视为历史真实的书写,则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
“理学家轻视文学”的论断其来有自,将其视为一种“刻板印象”并不是要推翻它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从历史来看,“理学家轻视文(学)”有着充足的论据。自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始,“重道轻文”就是典型之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②此外,二程、邵雍、张栻等人都有过相关类似的论述,兹不多举。
但问题在于,周敦颐这段已被无数次引用的话语之“文”,实乃与今日之所说“文学”不是一回事。在周子的运用中,“文”主要是统指能够承担道德意义的文字组织形式,即“文字”,虽然它包括作为“艺”的“文辞”,但“文辞”是不是就等于“文学”,恐怕还难以下定论。“文”之多义,需从其源头说起。
“文”或“文学”在中国古代起源于笔画符号。《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①,指的乃是自然界的斑纹或人工图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最多不过是“有文采的文字组织”而已。然而,这种代表着“美”的文字形态,在中国却有着相当深厚的民间崇拜传统。尤其在道教因素参与下,“文字”竟成了“随运开度,普成天地之功”的基本法则②。故《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③就此来说,周敦颐所言的“文辞”者,所指大抵是“文字”;周敦颐所说的“文以载道”,其实乃是“文章载道”或“文字载道”,而非“文学载道”。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周敦颐这番话语的针对对象是那些对“文字”的魔力有着过分崇拜的士子④,而非善于以文抒情的文人。
一般认为,“文字”之为“文学”,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其一是“文学”讲求文采,善于运用隐喻、反讽、悖论、朦胧等修辞形式对文字的组合加以变形,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⑤其二是“文学”讲求情感,要求在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活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⑥这二者的结合,便是本节前文所言的“话语蕴藉”,也就是“文学”应该在文字的字面意思之外,含有更为深刻的有待读者加以理解和阐释的意义,特别是需要加以体会的情感。而作为理学家口号的“文以载道”恰恰是要求文章作品在其字面意思之外必须有更深层次的“道”的要求,“道”蕴藉、隐藏在“文”之中,并借助“文”而进入读者的内心深处,呼唤起深远的回音——“美则爱,爱则传焉”。如果用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加以阐释,可以说无论是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还是程颐的“作文害道”,或者朱子的“道本文枝”,其根本反对的乃是“以辞害意”,而非“以情害意”。故程颐云:“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①说到这里,道理已经毕现,即“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刻板印象来自于今人对“文学”在中国古代语境中的误读,“理学家轻视”的“文学”是讲求文采的“文”(辞),而非“话语蕴藉”。不过,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理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却还有更深一层的复杂性。他们虽然不普遍反对一切文字组合形式,但对其所表之情感却有特殊的要求。文学作品表达情感,作者的情感能够通过文学阅读传达给接受者,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被称为“感兴”。文学具有鼓动性情的“感兴”作用,接受者有可能被文学文本所表达的情感牵引而丧失主体性意识,这正是理学家们所担忧的。但这一功效是可以反作用的,亦即是通过文学文本传递“正确”的情感,来引导读者挺拔其高度自觉的自我主体性。从朱子诗歌题目多次出现“感兴”二字——如前文所引《斋居感兴》多首,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理学诗人对此是有着高度自觉的。
邵雍说:“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这似乎可以视为理学家视文学为洪水猛兽,惟恐“以情害意”的证据。但邵雍笔锋一转,“古者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覆载在水也,不在人也;载则为利,覆则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②这就是说,“情之溺人”的关键在于所“溺”之“情”的性质;倘使主体能够“以物观物”“情累都忘”,则所留之“诗”便有益于“天下大义”;于是,个人的主体性不是丧失,而是得到了升华。这一点在周敦颐、二程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曰:“《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①可以说,“文学”的两重特性(文采、情感)在理学家那里都不是清晰可辨的。这不仅增加了后人对理学家文艺观理解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理学家自身的矛盾人格。而“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刻板印象在文学史对朱子的评价上,尤为明显。本节所述今人的朱子文学研究之弱便是明证。今以朱子诗歌创作为例,加上上文的理论澄清,或可破除“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于万一。不过,也如前文所言,“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论断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需要将既定的刻板印象引入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才有可能使其从内部得以破解。诗歌(文学)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艺术。理学家重视后者尤胜前者。对此,朱子有着高度的自觉。于此可以再举一例。朱子虽也有“游戏文字”,但从其创作大量诗歌的题目来看,他并不重视文字(文辞)。与一般诗人篇目的用心不同,朱子诗歌的题目很多是在叙事,交代作诗的前因后果,文字多得令人称奇。
仅举两例,如《丁丑冬在温陵陪敦宗李丈与一二道人同和东坡惠州梅花诗皆一再往反昨日见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再和一篇呈诸友兄一笑同赋》与《昨承诸兄临辱不揆以薄酒蔬食延驻都骑明日视壁间所张墨刻有亡去者人以为德庆丈之庾也驰问遣索蒙需拙诗辄赋所怀往奉一笑而尊犍刻可以归于我矣》1其诗歌的内容都没有其题目长。这恰说明朱子重视的是诗歌的内容,亦即是其传递的情感,如“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之感;而非文字堆砌的巧妙与所谓“艺术”。同样以此二例,还值得一说的是诗名中都有“一笑”两字,这在一千多首朱子诗中,并非仅见,但却多于长诗名之中。再如《去岁蒙学古分惠兰花清赏既歇复以根业归之故——而学古预有今岁之约近闻颇已著花辄赋小诗以寻前约幸一笑》《宋丈示及红梅腊梅借韵两诗辄复和呈以发一笑》《圭父约为金斗之游次韵献疑聊发一笑》《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诸名胜为落星之游分韵得往字率尔赋呈聊发一笑》《读十二辰诗卷掇其余作此聊奉一笑》等。这些处处可见的“一笑”,足可说明朱子对诗歌文字的不在意,而其“一笑”之作多见于“分韵”(赋韵)文字,更可见文字技法在朱子那里不过是点缀而已。
于此可以说明的是,理学家轻视文学,其意主要在于轻视文学之技法(文辞),而警惕文学之情感偏向,乃是理学之本,非仅文学受累,举凡释家、道家莫不在其警惕的范围之内。因此,笼统说“理学家轻视文学”,实则是一种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今人出于自我对“文学”概念理解的误读。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子,不但不轻视文学,更亲身实践,热衷文学创作。如果不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理解朱子,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朱子之后的理学文论)将无法得到深入的阐释,而浮于“理学家轻视文学”或“理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矛盾的”等论断的表面,更无助于将问题引向历史的深处。朱子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文本是复杂的,对其进行阐释也有多种角度,但无论如何,轻率的刻板的判断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作为诠释主体的朱子本人之态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性情、理想、志业、感兴等生命价值观,是必须给予充分考虑的。
这不仅与文学实践史上如朱子等人“以诗名”的状况不符,也未必符合中国文论发展的实际状况。宋代以降,占据中国文学理论主潮的,恐怕不是严羽等处于文坛边缘评论家——同为闽北人的严羽,连一部起码的传记都没有留下。在理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之后(宋、元),中国文论的发展其实是以理学标准为框架的;可是,这在当代中国文论教材中很难寻觅到论述的笔墨。中国文论的历史书写,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理论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对宋代理学的“刻板印象”与文学概念既定模式的生硬运用。此处所言的“刻板印象”,是指“理学家轻视文艺”已成为中国文论史的定论。这种简明扼要的“结论”式命题,把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处理;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即理学美学或理学文学得到的关注极其之少——就文论系统的研究成果而言,宋代理学文论显不及其他朝代或同代其他流派的研究之繁荣;就理学系统的研究而言,理学文论又不及其他学科领域,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成果显著。
具体到朱子身上,据林庆彰和莫砺锋的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际学界关于朱子的研究著述达2254种,而文学研究不过寥寥三四十种。②就文学概念既定模式的裁剪作用而言,不同时代对“什么是文学”或“什么是文论”问题的回答,乃是确立其时文学、文论史书写基本范式的关键。与中国古代“诗言志”和“诗缘情”并举的状况不同①,当代中国文学经历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话语“洗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形成了以个人抒情对抗宏大叙事的先锋文学传统。在这套话语体系中,“文学”的价值天平倾向着“表现说”的立场,加之西方传入的形式意识,各种实验文学纷纷登台。用这种“文学”概念来裁剪文学实践,必然有因不符合“抒情”或“语言形式”要求而被淘汰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观念——理学家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便是典型。
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编撰才更多把严羽等在历史语境中并不显赫的人物作为一代文学精神的高标——这在后人的评价体系中当然不成问题,但如果将其视为历史真实的书写,则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
“理学家轻视文学”的论断其来有自,将其视为一种“刻板印象”并不是要推翻它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从历史来看,“理学家轻视文(学)”有着充足的论据。自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始,“重道轻文”就是典型之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②此外,二程、邵雍、张栻等人都有过相关类似的论述,兹不多举。
但问题在于,周敦颐这段已被无数次引用的话语之“文”,实乃与今日之所说“文学”不是一回事。在周子的运用中,“文”主要是统指能够承担道德意义的文字组织形式,即“文字”,虽然它包括作为“艺”的“文辞”,但“文辞”是不是就等于“文学”,恐怕还难以下定论。“文”之多义,需从其源头说起。
“文”或“文学”在中国古代起源于笔画符号。《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①,指的乃是自然界的斑纹或人工图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最多不过是“有文采的文字组织”而已。然而,这种代表着“美”的文字形态,在中国却有着相当深厚的民间崇拜传统。尤其在道教因素参与下,“文字”竟成了“随运开度,普成天地之功”的基本法则②。故《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③就此来说,周敦颐所言的“文辞”者,所指大抵是“文字”;周敦颐所说的“文以载道”,其实乃是“文章载道”或“文字载道”,而非“文学载道”。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周敦颐这番话语的针对对象是那些对“文字”的魔力有着过分崇拜的士子④,而非善于以文抒情的文人。
一般认为,“文字”之为“文学”,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其一是“文学”讲求文采,善于运用隐喻、反讽、悖论、朦胧等修辞形式对文字的组合加以变形,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⑤其二是“文学”讲求情感,要求在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活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⑥这二者的结合,便是本节前文所言的“话语蕴藉”,也就是“文学”应该在文字的字面意思之外,含有更为深刻的有待读者加以理解和阐释的意义,特别是需要加以体会的情感。而作为理学家口号的“文以载道”恰恰是要求文章作品在其字面意思之外必须有更深层次的“道”的要求,“道”蕴藉、隐藏在“文”之中,并借助“文”而进入读者的内心深处,呼唤起深远的回音——“美则爱,爱则传焉”。如果用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加以阐释,可以说无论是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还是程颐的“作文害道”,或者朱子的“道本文枝”,其根本反对的乃是“以辞害意”,而非“以情害意”。故程颐云:“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①说到这里,道理已经毕现,即“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刻板印象来自于今人对“文学”在中国古代语境中的误读,“理学家轻视”的“文学”是讲求文采的“文”(辞),而非“话语蕴藉”。不过,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理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却还有更深一层的复杂性。他们虽然不普遍反对一切文字组合形式,但对其所表之情感却有特殊的要求。文学作品表达情感,作者的情感能够通过文学阅读传达给接受者,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被称为“感兴”。文学具有鼓动性情的“感兴”作用,接受者有可能被文学文本所表达的情感牵引而丧失主体性意识,这正是理学家们所担忧的。但这一功效是可以反作用的,亦即是通过文学文本传递“正确”的情感,来引导读者挺拔其高度自觉的自我主体性。从朱子诗歌题目多次出现“感兴”二字——如前文所引《斋居感兴》多首,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理学诗人对此是有着高度自觉的。
邵雍说:“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这似乎可以视为理学家视文学为洪水猛兽,惟恐“以情害意”的证据。但邵雍笔锋一转,“古者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覆载在水也,不在人也;载则为利,覆则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②这就是说,“情之溺人”的关键在于所“溺”之“情”的性质;倘使主体能够“以物观物”“情累都忘”,则所留之“诗”便有益于“天下大义”;于是,个人的主体性不是丧失,而是得到了升华。这一点在周敦颐、二程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曰:“《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①可以说,“文学”的两重特性(文采、情感)在理学家那里都不是清晰可辨的。这不仅增加了后人对理学家文艺观理解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理学家自身的矛盾人格。而“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刻板印象在文学史对朱子的评价上,尤为明显。本节所述今人的朱子文学研究之弱便是明证。今以朱子诗歌创作为例,加上上文的理论澄清,或可破除“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于万一。不过,也如前文所言,“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论断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需要将既定的刻板印象引入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才有可能使其从内部得以破解。诗歌(文学)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艺术。理学家重视后者尤胜前者。对此,朱子有着高度的自觉。于此可以再举一例。朱子虽也有“游戏文字”,但从其创作大量诗歌的题目来看,他并不重视文字(文辞)。与一般诗人篇目的用心不同,朱子诗歌的题目很多是在叙事,交代作诗的前因后果,文字多得令人称奇。
仅举两例,如《丁丑冬在温陵陪敦宗李丈与一二道人同和东坡惠州梅花诗皆一再往反昨日见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再和一篇呈诸友兄一笑同赋》与《昨承诸兄临辱不揆以薄酒蔬食延驻都骑明日视壁间所张墨刻有亡去者人以为德庆丈之庾也驰问遣索蒙需拙诗辄赋所怀往奉一笑而尊犍刻可以归于我矣》1其诗歌的内容都没有其题目长。这恰说明朱子重视的是诗歌的内容,亦即是其传递的情感,如“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之感;而非文字堆砌的巧妙与所谓“艺术”。同样以此二例,还值得一说的是诗名中都有“一笑”两字,这在一千多首朱子诗中,并非仅见,但却多于长诗名之中。再如《去岁蒙学古分惠兰花清赏既歇复以根业归之故——而学古预有今岁之约近闻颇已著花辄赋小诗以寻前约幸一笑》《宋丈示及红梅腊梅借韵两诗辄复和呈以发一笑》《圭父约为金斗之游次韵献疑聊发一笑》《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诸名胜为落星之游分韵得往字率尔赋呈聊发一笑》《读十二辰诗卷掇其余作此聊奉一笑》等。这些处处可见的“一笑”,足可说明朱子对诗歌文字的不在意,而其“一笑”之作多见于“分韵”(赋韵)文字,更可见文字技法在朱子那里不过是点缀而已。
于此可以说明的是,理学家轻视文学,其意主要在于轻视文学之技法(文辞),而警惕文学之情感偏向,乃是理学之本,非仅文学受累,举凡释家、道家莫不在其警惕的范围之内。因此,笼统说“理学家轻视文学”,实则是一种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今人出于自我对“文学”概念理解的误读。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子,不但不轻视文学,更亲身实践,热衷文学创作。如果不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理解朱子,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朱子之后的理学文论)将无法得到深入的阐释,而浮于“理学家轻视文学”或“理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矛盾的”等论断的表面,更无助于将问题引向历史的深处。朱子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文本是复杂的,对其进行阐释也有多种角度,但无论如何,轻率的刻板的判断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作为诠释主体的朱子本人之态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性情、理想、志业、感兴等生命价值观,是必须给予充分考虑的。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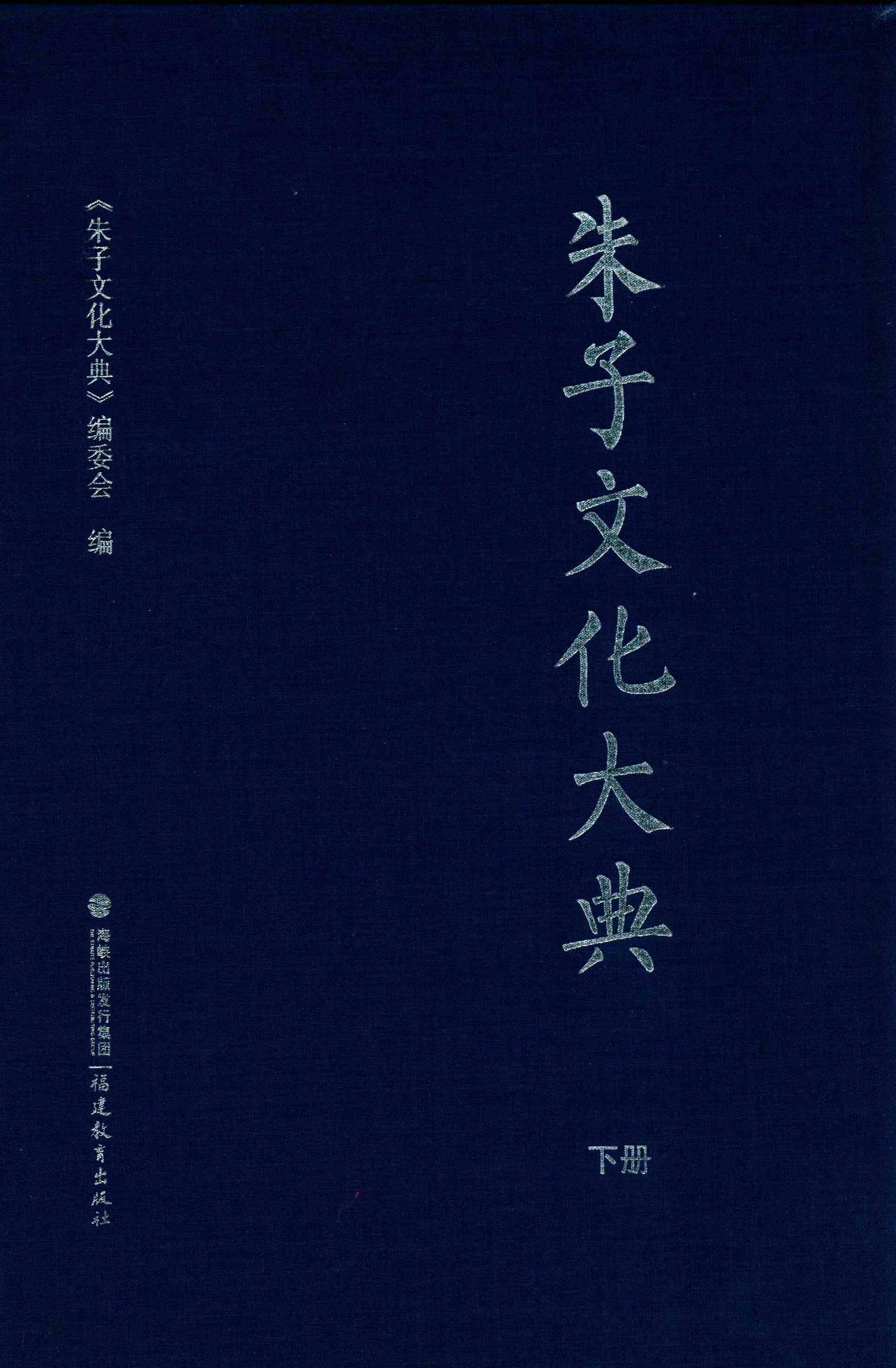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介绍朱子生平,包括家世、从学、讲学、论道、政绩等内容。中册阐述朱子文化源流,包括朱子理学形成的历史背景、朱子的理学思想、朱子的经学思想、朱子的教育思想等内容。下册着重介绍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