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
| 内容出处: |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1220 |
| 颗粒名称: | (一)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5 |
| 页码: | 360-36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在朱子诗歌研究史上,对朱子诗歌创作进行宏观描述,是许多前人业已进行过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历史性的描述”与“分类学的描述”两种类型:前者把朱子诗歌创作的五十年分为若干阶段,分别分析朱子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诗歌作品风格、意义等;后者则是对朱子诗歌文本做理趣诗、山水诗、感事诗等类型学的分析。 |
| 关键词: | 朱子文化 文化鉴赏 诗词 |
内容
自孔子云“三十而立”开始,“而立之年”就被中国人视为是个体思想确定与成熟的标志性时间点。在三十岁那一年前后,朱子以“绝不作诗”为题写了一首诗:“神心洞玄鉴,好恶审薫莸。云何反自诳,闵默还包羞。今辰仲冬节,寤叹得隐忧。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朋来自兹始,群阴邈难留。行迷亦已远,及此旋吾辀。”(《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这一首诗长长的题目详细交代了朱子作此诗的缘由——三十岁前后的朱子,正处于“弃禅归儒”的关键期;三十岁那年,他正式受学延平李侗,脱离了在同安任主簿时沉溺佛老世界的精神状态,决心以儒为业,趋向圣贤之道。可以说,此时的朱子正是在转向的关节点上。因此,从语言上看,此诗仍然大量使用了庄、禅术语,如“神心”“玄鉴”“朋来”“群阴”等;而从诗歌所表达的意愿上看,朱子则直抒对“反自诳”的“包羞”“隐忧”,并决意“及此旋吾辀”,亦即是调转船头,脱离空灵,朝向儒学。可这一套思想、情感乃是通过极具诗意的道家话语系统表现出来的。“绝不作诗”的意愿以诗的文体形式加以表达,否定审美情感的志向以审美话语为载体,此诚朱子自谓“盖不得已而有言”也,亦颇似戒烟者自云“再吸一支以纪戒烟之始”。
在这一事件中,朱子发誓“绝不作诗”的原因初看是“多言害道”;此语类似程颐所谓“作文害道”,但又明显超出了“作文害道”的范畴。在程颐看来,“作文害道”的问题在于“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①。程颐这种因“用功”而造成的“害道”,实则仍在技术层面,并未真正涉及文道关系问题。而朱子所谓“多言害道”,乃是由于阅读《大学·诚意》篇而生发的感慨。《大学·诚意》云:“毋自欺也……君子必诚其意”,这显然是诗中“云何反自诳”的出处。也就是说,朱子在此认识的“多言害道”问题已经远较程颐“作文害道”来得深刻,他看出了诗性语言能够塑造和引导人的情感与思维,甚至有可能混淆主体意识的“好恶”观念,蒙蔽“玄鉴”。然而,朱子一生尊崇道统,实在不可能充分意识到“语言”本身的力量,光大自己独特的观点,从而推翻程颐的“作文害道”论。
他也常常陷入程颐的说辞之中,如其曰:“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②无论如何,以此为例,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态度集中于文(语言)道(情感、志向)关系上,并长期存在于其创作实践中。
时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有云:“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酬唱至百余篇。忽矍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③这以鲜明的例证,说出了朱子在当时世人眼中的形象——不仅作诗,而且诗名甚大。可是,朱子却以此为辱。自我认识与社会形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此可见一斑,而朱子的自我期许与自我行为之间的巨大矛盾,也可从此显出。朱子对待诗歌,态度终究暧昧。
还可以再举一例。朱子三十八岁那年与张栻同游南岳,那是其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阶段。数月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朱子成诗一百三十多首①。这百余首诗篇来得并不容易,朱子之矛盾心态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有详细记载:丙戌至株洲,熹与伯崇、择之取道东归,而敬夫自此西还长沙矣。
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岳宫至株洲凡百有八十里,其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来所见,无非诗者。而前日既有约矣,然亦念夫别日之迫,而前日所讲,盖有既开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与思绎讨论,以毕其说,则其于诗,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谂于众曰:“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惩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然而今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然则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皆应曰:“诺”。既而敬夫以诗赠吾,三人亦各答赋以见意。熹则又进而言曰:“前日之约已过矣,然其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忘也。何则?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故前日戒惧警省之意,虽曰小过,然亦所当过也。由是而扩充之,庶几乎其寡过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书之,以诏毋忘。……自今暇日时出而观焉,其亦足以当盘盂几杖之戒也!②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朱子与张栻在南岳酬唱之后,“既有约矣”(约定不作诗),因此,即使“自岳宫至株洲凡百有八十里”,其间所见“无非诗者”,但他却没有作诗;而在株洲,两人即将别离,“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于是朱子宣布“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而这并不意味朱子认为诗可作,他仍殷殷切切地“进而言曰”,“戒惧警省之意”不可忘。“刚刚极南岳唱酬之欢,却又宣布戒诗之约;刚刚宣布戒约,却又要求罢去;罢去未几天,却又重申戒惧警省之意。这里重申戒惧警省之意,紧接着东归一路,又有《东归乱稿集》问世。”①这种反复的情形,将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例证之外需要讨论的是朱子于此提出的“戒诗”之缘由。比八年前的“多言害道”更加深入,这次朱子认为,“戒诗”是为了“戒惧警省”。不过,朱子所标举的理由,不过是“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营惑耳目、感移心意”等来自《大学·诚意》中所谓“君子慎独”的一套说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次提出要警惕的不是所有诗歌,而是诗之“流”。在其“流”之前的那些“宣畅湮郁,优柔平中”的诗,则“非有不善”,是值得肯定的。
可见,朱子之所以反对诗,其理论立足点大异于程颐的技术层面。在朱子看来,符合“道”之要求的情感的诗是可作、可读的,而“作诗”这种文学实践本身是语词的“游戏”,人的情感有可能被语词所控制,从而丧失了主体意识(丧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诗”这一行为本身是危险的,特别是在“离群索居”的时候,主体意识未得他者的“辅仁”而尤为薄弱,极易被“营惑”“感移”。可以说,朱子已经发现了诗歌(文学)具有语言(文)和情感(道)的双重属性;而在程颐那里,诗歌还仅是一种语言的“玩物”而已。朱子是在话语蕴藉的意义上来理解“诗歌”的,他对诗歌(文学)的认识,已经远远高于程颐等前辈理学家了②。
若非以当代文学理论家比拟,大致可认为朱子所赞赏的诗歌与罗兰·巴特所倡导的“可读的文本”(悦之文)近似,而其所反对的诗歌与巴特所谓“可写的文本”(醉之文)又有可以比拟之处。在巴特看来,可读的文本是古典文学,而可写的文本是先锋文学,前者是“欣快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而后者则是“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或许已至某种厌烦的地步),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①当然,这种比较是颇为牵强的,但却可见出朱子文论之深刻。
朱子对诗歌(文学)有如此深刻而复杂的认识,就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所以,在“文学是话语蕴藉”的意义上重新认识朱子诗歌文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朱子诗歌研究史上,对朱子诗歌创作进行宏观描述,是许多前人业已进行过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历史性的描述”与“分类学的描述”两种类型:前者把朱子诗歌创作的五十年分为若干阶段,分别分析朱子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诗歌作品风格、意义等;后者则是对朱子诗歌文本做理趣诗、山水诗、感事诗等类型学的分析。按照索绪尔区分的“历时”与“共时”范畴,前者可以认为是“历时性”的综述,而后者则是“共时性”的综述。从前者可以看出朱子诗歌创作五十年间的不同变化,后者可以归纳朱子诗歌不同类型的特征。但这两种方法却各有利弊:历时地看,朱子诗歌是一个变动不居、不断调动的文本层次;就其整体来说,又缺乏对其分阶段思想进阶的把握,而缺乏对某首诗歌创作语境的了解,对其解读就难免有所偏颇。因此,这两种分析方法应该适当加以结合,或者分别加以诠释,以形成互文,才能使朱子诗歌文本得到有机的分析、组合,进而呈现出整体全貌。
在这一事件中,朱子发誓“绝不作诗”的原因初看是“多言害道”;此语类似程颐所谓“作文害道”,但又明显超出了“作文害道”的范畴。在程颐看来,“作文害道”的问题在于“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①。程颐这种因“用功”而造成的“害道”,实则仍在技术层面,并未真正涉及文道关系问题。而朱子所谓“多言害道”,乃是由于阅读《大学·诚意》篇而生发的感慨。《大学·诚意》云:“毋自欺也……君子必诚其意”,这显然是诗中“云何反自诳”的出处。也就是说,朱子在此认识的“多言害道”问题已经远较程颐“作文害道”来得深刻,他看出了诗性语言能够塑造和引导人的情感与思维,甚至有可能混淆主体意识的“好恶”观念,蒙蔽“玄鉴”。然而,朱子一生尊崇道统,实在不可能充分意识到“语言”本身的力量,光大自己独特的观点,从而推翻程颐的“作文害道”论。
他也常常陷入程颐的说辞之中,如其曰:“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②无论如何,以此为例,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态度集中于文(语言)道(情感、志向)关系上,并长期存在于其创作实践中。
时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有云:“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酬唱至百余篇。忽矍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③这以鲜明的例证,说出了朱子在当时世人眼中的形象——不仅作诗,而且诗名甚大。可是,朱子却以此为辱。自我认识与社会形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此可见一斑,而朱子的自我期许与自我行为之间的巨大矛盾,也可从此显出。朱子对待诗歌,态度终究暧昧。
还可以再举一例。朱子三十八岁那年与张栻同游南岳,那是其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阶段。数月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朱子成诗一百三十多首①。这百余首诗篇来得并不容易,朱子之矛盾心态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有详细记载:丙戌至株洲,熹与伯崇、择之取道东归,而敬夫自此西还长沙矣。
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岳宫至株洲凡百有八十里,其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来所见,无非诗者。而前日既有约矣,然亦念夫别日之迫,而前日所讲,盖有既开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与思绎讨论,以毕其说,则其于诗,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谂于众曰:“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惩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然而今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然则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皆应曰:“诺”。既而敬夫以诗赠吾,三人亦各答赋以见意。熹则又进而言曰:“前日之约已过矣,然其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忘也。何则?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故前日戒惧警省之意,虽曰小过,然亦所当过也。由是而扩充之,庶几乎其寡过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书之,以诏毋忘。……自今暇日时出而观焉,其亦足以当盘盂几杖之戒也!②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朱子与张栻在南岳酬唱之后,“既有约矣”(约定不作诗),因此,即使“自岳宫至株洲凡百有八十里”,其间所见“无非诗者”,但他却没有作诗;而在株洲,两人即将别离,“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于是朱子宣布“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而这并不意味朱子认为诗可作,他仍殷殷切切地“进而言曰”,“戒惧警省之意”不可忘。“刚刚极南岳唱酬之欢,却又宣布戒诗之约;刚刚宣布戒约,却又要求罢去;罢去未几天,却又重申戒惧警省之意。这里重申戒惧警省之意,紧接着东归一路,又有《东归乱稿集》问世。”①这种反复的情形,将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例证之外需要讨论的是朱子于此提出的“戒诗”之缘由。比八年前的“多言害道”更加深入,这次朱子认为,“戒诗”是为了“戒惧警省”。不过,朱子所标举的理由,不过是“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营惑耳目、感移心意”等来自《大学·诚意》中所谓“君子慎独”的一套说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次提出要警惕的不是所有诗歌,而是诗之“流”。在其“流”之前的那些“宣畅湮郁,优柔平中”的诗,则“非有不善”,是值得肯定的。
可见,朱子之所以反对诗,其理论立足点大异于程颐的技术层面。在朱子看来,符合“道”之要求的情感的诗是可作、可读的,而“作诗”这种文学实践本身是语词的“游戏”,人的情感有可能被语词所控制,从而丧失了主体意识(丧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诗”这一行为本身是危险的,特别是在“离群索居”的时候,主体意识未得他者的“辅仁”而尤为薄弱,极易被“营惑”“感移”。可以说,朱子已经发现了诗歌(文学)具有语言(文)和情感(道)的双重属性;而在程颐那里,诗歌还仅是一种语言的“玩物”而已。朱子是在话语蕴藉的意义上来理解“诗歌”的,他对诗歌(文学)的认识,已经远远高于程颐等前辈理学家了②。
若非以当代文学理论家比拟,大致可认为朱子所赞赏的诗歌与罗兰·巴特所倡导的“可读的文本”(悦之文)近似,而其所反对的诗歌与巴特所谓“可写的文本”(醉之文)又有可以比拟之处。在巴特看来,可读的文本是古典文学,而可写的文本是先锋文学,前者是“欣快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而后者则是“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或许已至某种厌烦的地步),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①当然,这种比较是颇为牵强的,但却可见出朱子文论之深刻。
朱子对诗歌(文学)有如此深刻而复杂的认识,就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所以,在“文学是话语蕴藉”的意义上重新认识朱子诗歌文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朱子诗歌研究史上,对朱子诗歌创作进行宏观描述,是许多前人业已进行过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历史性的描述”与“分类学的描述”两种类型:前者把朱子诗歌创作的五十年分为若干阶段,分别分析朱子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诗歌作品风格、意义等;后者则是对朱子诗歌文本做理趣诗、山水诗、感事诗等类型学的分析。按照索绪尔区分的“历时”与“共时”范畴,前者可以认为是“历时性”的综述,而后者则是“共时性”的综述。从前者可以看出朱子诗歌创作五十年间的不同变化,后者可以归纳朱子诗歌不同类型的特征。但这两种方法却各有利弊:历时地看,朱子诗歌是一个变动不居、不断调动的文本层次;就其整体来说,又缺乏对其分阶段思想进阶的把握,而缺乏对某首诗歌创作语境的了解,对其解读就难免有所偏颇。因此,这两种分析方法应该适当加以结合,或者分别加以诠释,以形成互文,才能使朱子诗歌文本得到有机的分析、组合,进而呈现出整体全貌。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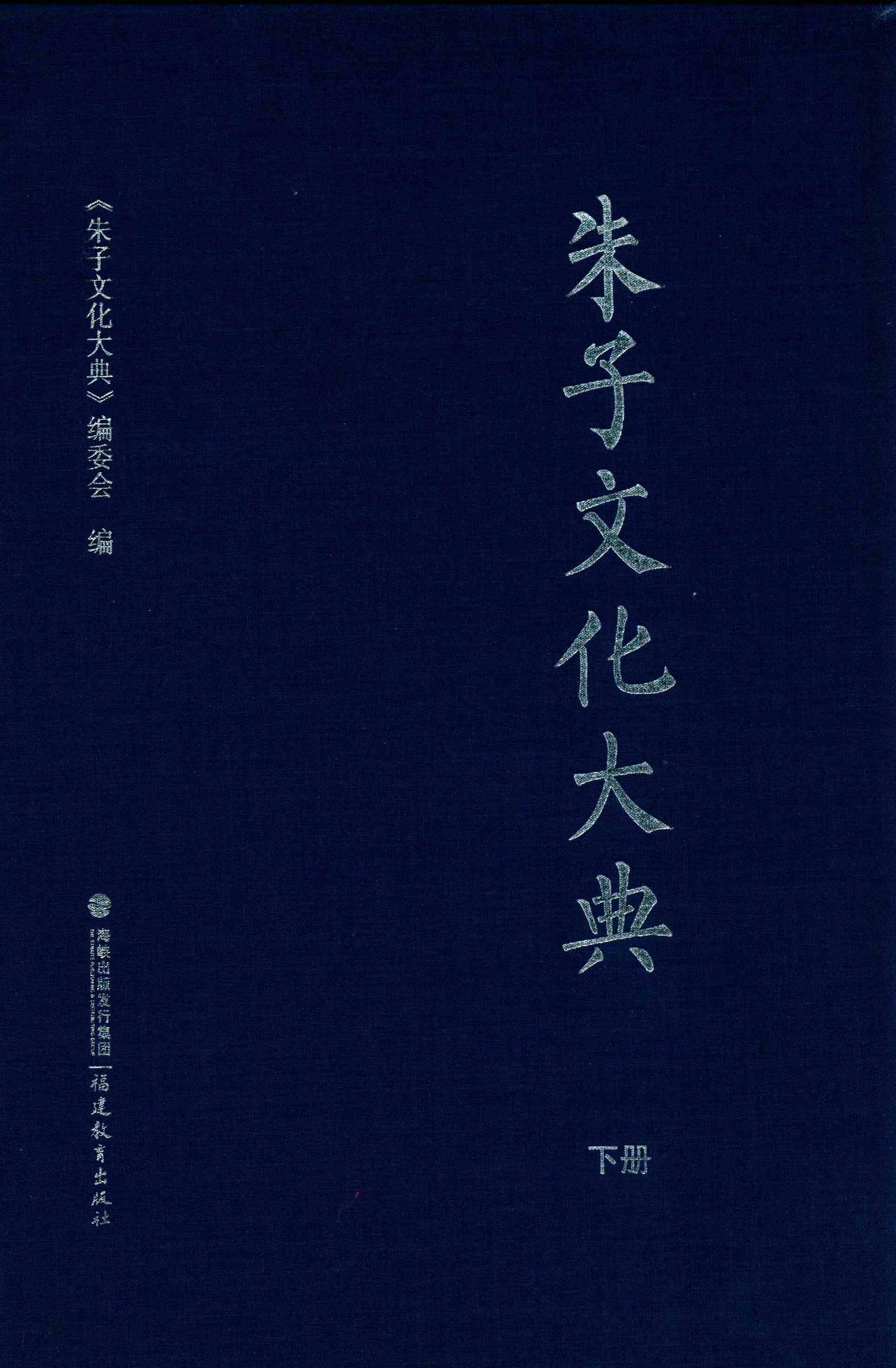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介绍朱子生平,包括家世、从学、讲学、论道、政绩等内容。中册阐述朱子文化源流,包括朱子理学形成的历史背景、朱子的理学思想、朱子的经学思想、朱子的教育思想等内容。下册着重介绍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