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子诗词概论
| 内容出处: |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1219 |
| 颗粒名称: | 一 朱子诗词概论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25 |
| 页码: | 359-38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对朱子诗词概论,朱子一生喜好诗文,诗歌的创作生涯长达五十余年。就今现存朱子诗歌作品篇目来说,至少有一千四百多首诗和近二十首词。 |
| 关键词: | 朱子文化 文化鉴赏 诗词 |
内容
朱子一生喜好诗文,诗歌的创作生涯长达五十余年。就今现存朱子诗歌作品篇目来说,至少有一千四百多首诗和近二十首词。①在数量上,朱子的诗作少于同时期的陆游九千余首、杨万里四千余首,但却远多于前朝李白九百多首、同期辛弃疾六百多首,接近唐代诗人杜甫存诗一千四百多首。这一数字的简单对比可以说明,诗歌在朱子精神生活中绝非配角,它贯穿着朱子的一生,伴随其哲学从模糊走向明晰;甚至可以说,文学创作深刻影响着朱子的人格建构与思维方式。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子的诗人声名一直没有得到今人足够的重视,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朱子是反对诗歌、轻视诗歌的。而与之相应的,是“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在传统学术史上近乎刻板的印象——即使就朱子自身而言,他也不愿意被人以“诗人”身份视之。问题究竟为何?本节尝试从朱子对待诗歌的创作态度入手,概述朱子一生的诗歌创作实践,并力图对其艺术价值作出较为公允的评判。在此基础上,本节将对“朱子反对写诗”或“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命题做一定分析。显然,这是一个思想史问题,而对待此问题并不能以“朱子自己也作诗”这一基本事实加以简单的否定。论者需要做的是深入分析朱子创作的诗歌文本及其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分析朱子的诗歌理论,综合其艺术实践加以评判。
(一)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自孔子云“三十而立”开始,“而立之年”就被中国人视为是个体思想确定与成熟的标志性时间点。在三十岁那一年前后,朱子以“绝不作诗”为题写了一首诗:“神心洞玄鉴,好恶审薫莸。云何反自诳,闵默还包羞。今辰仲冬节,寤叹得隐忧。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朋来自兹始,群阴邈难留。行迷亦已远,及此旋吾辀。”(《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这一首诗长长的题目详细交代了朱子作此诗的缘由——三十岁前后的朱子,正处于“弃禅归儒”的关键期;三十岁那年,他正式受学延平李侗,脱离了在同安任主簿时沉溺佛老世界的精神状态,决心以儒为业,趋向圣贤之道。可以说,此时的朱子正是在转向的关节点上。因此,从语言上看,此诗仍然大量使用了庄、禅术语,如“神心”“玄鉴”“朋来”“群阴”等;而从诗歌所表达的意愿上看,朱子则直抒对“反自诳”的“包羞”“隐忧”,并决意“及此旋吾辀”,亦即是调转船头,脱离空灵,朝向儒学。可这一套思想、情感乃是通过极具诗意的道家话语系统表现出来的。“绝不作诗”的意愿以诗的文体形式加以表达,否定审美情感的志向以审美话语为载体,此诚朱子自谓“盖不得已而有言”也,亦颇似戒烟者自云“再吸一支以纪戒烟之始”。
在这一事件中,朱子发誓“绝不作诗”的原因初看是“多言害道”;此语类似程颐所谓“作文害道”,但又明显超出了“作文害道”的范畴。在程颐看来,“作文害道”的问题在于“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①。程颐这种因“用功”而造成的“害道”,实则仍在技术层面,并未真正涉及文道关系问题。而朱子所谓“多言害道”,乃是由于阅读《大学·诚意》篇而生发的感慨。《大学·诚意》云:“毋自欺也……君子必诚其意”,这显然是诗中“云何反自诳”的出处。也就是说,朱子在此认识的“多言害道”问题已经远较程颐“作文害道”来得深刻,他看出了诗性语言能够塑造和引导人的情感与思维,甚至有可能混淆主体意识的“好恶”观念,蒙蔽“玄鉴”。然而,朱子一生尊崇道统,实在不可能充分意识到“语言”本身的力量,光大自己独特的观点,从而推翻程颐的“作文害道”论。
他也常常陷入程颐的说辞之中,如其曰:“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②无论如何,以此为例,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态度集中于文(语言)道(情感、志向)关系上,并长期存在于其创作实践中。
时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有云:“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酬唱至百余篇。忽矍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③这以鲜明的例证,说出了朱子在当时世人眼中的形象——不仅作诗,而且诗名甚大。可是,朱子却以此为辱。自我认识与社会形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此可见一斑,而朱子的自我期许与自我行为之间的巨大矛盾,也可从此显出。朱子对待诗歌,态度终究暧昧。
还可以再举一例。朱子三十八岁那年与张栻同游南岳,那是其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阶段。数月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朱子成诗一百三十多首①。这百余首诗篇来得并不容易,朱子之矛盾心态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有详细记载:丙戌至株洲,熹与伯崇、择之取道东归,而敬夫自此西还长沙矣。
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岳宫至株洲凡百有八十里,其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来所见,无非诗者。而前日既有约矣,然亦念夫别日之迫,而前日所讲,盖有既开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与思绎讨论,以毕其说,则其于诗,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谂于众曰:“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惩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然而今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然则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皆应曰:“诺”。既而敬夫以诗赠吾,三人亦各答赋以见意。熹则又进而言曰:“前日之约已过矣,然其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忘也。何则?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故前日戒惧警省之意,虽曰小过,然亦所当过也。由是而扩充之,庶几乎其寡过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书之,以诏毋忘。……自今暇日时出而观焉,其亦足以当盘盂几杖之戒也!②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朱子与张栻在南岳酬唱之后,“既有约矣”(约定不作诗),因此,即使“自岳宫至株洲凡百有八十里”,其间所见“无非诗者”,但他却没有作诗;而在株洲,两人即将别离,“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于是朱子宣布“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而这并不意味朱子认为诗可作,他仍殷殷切切地“进而言曰”,“戒惧警省之意”不可忘。“刚刚极南岳唱酬之欢,却又宣布戒诗之约;刚刚宣布戒约,却又要求罢去;罢去未几天,却又重申戒惧警省之意。这里重申戒惧警省之意,紧接着东归一路,又有《东归乱稿集》问世。”①这种反复的情形,将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例证之外需要讨论的是朱子于此提出的“戒诗”之缘由。比八年前的“多言害道”更加深入,这次朱子认为,“戒诗”是为了“戒惧警省”。不过,朱子所标举的理由,不过是“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营惑耳目、感移心意”等来自《大学·诚意》中所谓“君子慎独”的一套说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次提出要警惕的不是所有诗歌,而是诗之“流”。在其“流”之前的那些“宣畅湮郁,优柔平中”的诗,则“非有不善”,是值得肯定的。
可见,朱子之所以反对诗,其理论立足点大异于程颐的技术层面。在朱子看来,符合“道”之要求的情感的诗是可作、可读的,而“作诗”这种文学实践本身是语词的“游戏”,人的情感有可能被语词所控制,从而丧失了主体意识(丧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诗”这一行为本身是危险的,特别是在“离群索居”的时候,主体意识未得他者的“辅仁”而尤为薄弱,极易被“营惑”“感移”。可以说,朱子已经发现了诗歌(文学)具有语言(文)和情感(道)的双重属性;而在程颐那里,诗歌还仅是一种语言的“玩物”而已。朱子是在话语蕴藉的意义上来理解“诗歌”的,他对诗歌(文学)的认识,已经远远高于程颐等前辈理学家了②。
若非以当代文学理论家比拟,大致可认为朱子所赞赏的诗歌与罗兰·巴特所倡导的“可读的文本”(悦之文)近似,而其所反对的诗歌与巴特所谓“可写的文本”(醉之文)又有可以比拟之处。在巴特看来,可读的文本是古典文学,而可写的文本是先锋文学,前者是“欣快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而后者则是“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或许已至某种厌烦的地步),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①当然,这种比较是颇为牵强的,但却可见出朱子文论之深刻。
朱子对诗歌(文学)有如此深刻而复杂的认识,就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所以,在“文学是话语蕴藉”的意义上重新认识朱子诗歌文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朱子诗歌研究史上,对朱子诗歌创作进行宏观描述,是许多前人业已进行过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历史性的描述”与“分类学的描述”两种类型:前者把朱子诗歌创作的五十年分为若干阶段,分别分析朱子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诗歌作品风格、意义等;后者则是对朱子诗歌文本做理趣诗、山水诗、感事诗等类型学的分析。按照索绪尔区分的“历时”与“共时”范畴,前者可以认为是“历时性”的综述,而后者则是“共时性”的综述。从前者可以看出朱子诗歌创作五十年间的不同变化,后者可以归纳朱子诗歌不同类型的特征。但这两种方法却各有利弊:历时地看,朱子诗歌是一个变动不居、不断调动的文本层次;就其整体来说,又缺乏对其分阶段思想进阶的把握,而缺乏对某首诗歌创作语境的了解,对其解读就难免有所偏颇。因此,这两种分析方法应该适当加以结合,或者分别加以诠释,以形成互文,才能使朱子诗歌文本得到有机的分析、组合,进而呈现出整体全貌。
(二)朱子诗歌创作的历史阶段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对研究对象展开分类,对朱子诗歌创作历程的分阶已经有多种见解。从已有分析上看,这一历时性分析的视角大多以朱子生平历程为分界点,集中在其赴同安任职、知南康军、筑室建阳考亭等几件生平大事上。如蔡厚示、杨国学等人将朱子的诗歌创作分为早期(1148—1165,十九至三十五岁)、中期(1165—1194,三十五至六十四岁)、晚期(1194—1200,六十四至七十一岁)三期②,而吴长庚先生则将其分为准备阶段(十九至二十七岁)、高潮阶段(二十七至五十岁)、成熟阶段(五十至五十三岁)和终老阶段(五十三至七十一岁)四个阶段等。③这种历史分阶方式的优势在于便于处理朱子诗歌所表述的事实性内容及其所直接表述的情感,从而对朱子诗歌文本展开审美价值、艺术风格的评判。但这种分析方法也有简单使用“社会决定论”的弊端,即单纯用作者生平经历来理解其文学创作。要知道,不少诗歌是激于一时之情感勃发而作的,未必真与作者的生平经历(特别是重大事件)有必然关联。
与其使用朱子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期标准,不如转而思考朱子诗歌创作与其哲学体系分段进展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与诗歌类似,都是朱子精神世界的长期表征与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前文已述,朱子对文学创作作为话语蕴藉的功能极有认识,他不可能不在其诗歌中传递与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事实上,这也正是后人对宋诗的基本认识:“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①,或是“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②。因此,或可尝试使用朱子哲学的分阶,来对其诗歌加以历时性分析。
朱子诗歌文本与其哲学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这本应在对朱子诗歌文本的历时性分阶中得到较为清晰的揭示。可是,目前文献中这一视角的研究还不充分。郭齐根据朱子对道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将朱子诗歌创作以三十五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又辅以六个创作高峰期,这种分类方式是比较吻合其哲学标准的。③但显而易见的是,郭齐的这一分阶方法失之过简,仅有三十五岁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另外,所谓“创造高峰期”往往是由于某一事件(如南岳访张栻)而造成的,与朱子的哲学体系的发展并无必然关联。因此,这一分阶标准虽方向有创新价值,但其具体操作则仍可加以商榷。
本小节根据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④,将其诗歌文本创作分为“入儒”(1148—1169,十九至三十九岁)、“求衡”(1169—1177,三十九至四十七岁)、“人本”(1177—1189,四十七至五十九岁)与“存真”(1189—1200,五十九至七十一岁)四个阶段。这一分阶大体与朱子哲学的形成、发展、成熟和趋于化境的历程相应。以下分而述之。
朱子自述青少年时节,“某旧时亦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①。在这一时期,朱子开始了诗歌创作。而这些诗歌恰好又可以印证朱子从少年的器宇轩昂到初仕同安的苦闷,进而结交泉州名士、出入佛老,最后投身儒门,完成“弃禅归儒”的思想变迁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说,朱子在“入儒”阶段所积累的各种思想、认识、观念最终都构成了其哲学体系得以建立的学理基础——有的是以潜流或对立面的形式出现的,如禅学。因此,从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能较为明显地看出青少年时期的朱子思想变迁之情感因素。如中进士之后,朱子曾有长达五年的时间在家待职,青年的踌躇满志在闲散中消磨,逐渐出现“不恨岁月遒,但惜芳华姿。严霜萎百草,坐恐及兹时”(《古意》)的心态变化;而在同安任上,朱子孤寂之心亦时时涌起:“远宦去乡井,终日无一欢。援琴不能操,临殇起长叹。”(《寄黄子衡》)尽管这种心态可以在短暂的山水游乐中得到舒缓,如“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涉涧水作》);或在朝廷对抗金兵获胜的消息中得到暂时的喜悦,如“东京盛德符高祖,说与中原父老知”(《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其五》),但这些外来的刺激性放松毕竟无法成为朱子如此重视心性修为者愿意寄托精神的对象。因此,他在赴京城诠试前后进一步沉溺佛老,在其后自编诗集《牧斋净稿》中,记录了这段“望山怀释侣,盥手阅仙经”(《夏日》)的时光。
出仕同安是朱子思想的转折点,这与儒学事功的性质是相契的。朱子在同安任上整顿赋税,清点田亩经界,“一置身于同安尘世社会,他的儒家积极经世治邦的现实精神的一面高昂起来”了②。也正是在这前后,朱子正式拜李侗为师,将书斋“牧斋”改名“困学”,开始了艰难的由禅“入儒”的求学经历。其诗曰:“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在“入儒”阶段末,朱子迎来了一生中诗歌创作最高潮,即前文所提及的、常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的“朱张会讲”。在南岳及其归途的四个月时间中,朱子成诗一百三十余篇,编成《南岳唱酬集》和《东归乱稿》两部诗集。这两部诗集中所收朱子诗,充分显示了朱子儒学思想第一次升华前的样貌,全力促成了朱子在己丑年(乾道五年,1169)提出“中和新说”,史称“己丑之悟”。至此,朱子的哲学思想才逐渐成熟——“己丑之悟从根本上确立了朱子的学术面貌”①。
“求衡”阶段是朱子哲学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朱子潜居寒泉、云谷等地“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卜居》),潜心探讨本体论与宇宙观,完成十余部学术著作;并通过书信与湖湘派展开论辩,与吕祖谦相与讲习,参与鹅湖之会等大量学术活动。在这些活动的间隙,或有感于学术思想的魅力,朱子才偶有诗篇创作记录自己的思想历程,如《云谷杂诗十二首·讲道》云“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而在短短的八年中,朱子的哲学思想也出现了多次变化,其经学体系也在与他人的不断论争中走向完善。尤其重要的是,与陆氏兄弟的鹅湖之辩,构成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不同为学、修心取向在朱子心中的对立。这一对立推动着朱子找到“敬知双修”的进学路径,从而不断在以知识为本的基础上,于“道问学”与“尊德性”间寻找一种平衡。而与此同时,反道学声音也甚嚣尘上,可以说,此时的朱子之“求衡”同样也发生在自我与俗世之间,究竟是应该继续内心平和地读书求学,还是要愤世嫉俗的入世事功?从其教诲学生吴楫(字公济)的诗:“欲知陋巷忧时乐,只向韦编绝处寻”(《公济和诗见闵耽书勉以教外之乐以诗请问》)或可见一斑。而也许正是在前一思想的影响下,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淳熙二年,1175),朱子与吕祖谦游百丈、登芦峰,又一次爆发了诗歌创造的“小宇宙”,构成了其创作生涯中的高潮之一;其《百丈山记》一文,也由此而成千古名篇。
在“求衡”阶段中,朱子对待诗歌的态度始终随着其哲学体系的逐步完善而出现变化。他既对诗歌(文学)语言与道学情感之间的矛盾存在疑惑:“诗篇眼界何终极,道学心期未遽央。安得追寻二三子,舞雩风月共徜徉”(《择之寄示深卿唱和乌石南湖佳句辄次元韵》);又有因对自创道学体系的自信,而对诗歌作用的宽容:“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风弄月兴何长。从容咏叹无今古,此乐从兹乐未央”(《抄二南寄平父因题此诗》)。可以说,朱子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仅贯彻了他对文学乃是一种话语蕴藉的认识,而且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表征了文学的这一特性,使之具有与其哲学互诠的价值。“求衡”阶段的结束以淳熙四年(1177)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为标志,这被学者称为朱子“生平学问的第一次总结”①。此后,朱子再次出仕南康,道学体系从偏向理论构建,转向了更终极的指向,即出现了人本色彩。
在朱子哲学基本定型之际,朝中纷争不断,交替上下台的宰辅们轮番劝请朱子出山;连吕祖谦也来信劝说,“承领上意……使世见儒者之效,于斯文非小补也”(《吕东莱文集》卷三)。尽管朱子本人更愿意在深山之中继续完善其道学体系,三番两次上书请辞,如《寄籍溪胡丈及刘共父二首·其一》一诗曰:“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可是,省札时时催促,朱子也只好应命,于淳熙六年(1179)初从命抵达南康,出任知军;其后又转浙东提举。时诗人王质有诗云:“晦庵今年登五十……晦庵不急苍生急。”(《赠黄君》)朱子上奏请求免税、赈济灾荒,兴建白鹿洞书院,砥砺士风,写下了大量感时忧民的诗篇:“况复逢旱魃,农亩无余收。赤子亦何辜,黄屋劳深忧。”(《秋日告病斋居奉怀黄子厚刘平父及山间诸兄友》)在这些诗篇中,朱子的底层“人本”倾向是显豁的,可以认为也是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使命在诗歌中的直接显现。
与此同时,朱子在政事之余畅游江西,“把郡事余暇全部用在了登山唱酬上,两年中他几乎游遍了庐山每一处胜地,写下百余首诗篇”,甚至“俨然以诗坛盟主开导士子,要想改变积重难返的江西诗风”②。可以说,“人本”阶段的朱子山水诗已经达到了其一生的巅峰。“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陶公醉石归去来馆》),朱子的这些诗一方面师法其父朱松所崇尚的“简淡”笔力,另一方面也受到江西诗人诸如辛弃疾、陆游等人交往的影响,在清景中蕴含了道学生机至乐的一面。此类诗风,在朱子卸任提举,跧伏武夷山中所作诸如《九曲棹歌》等诗篇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亦可视为一种潜在的“人本”倾向:理学的终极指向分内外两个维度,其内向性的目的在于实现主体精神的自由解脱,即“鸢飞鱼跃”之境;而其外向性目的则是重构现实伦理世界。
可以认为,朱子“人本”阶段的诗作,大多可以体现这种哲学意图。
“人本”阶段后期,朱子在武夷山同当时诸派展开了全面的论战,对手包括永康学派陈亮、江西陆学、吕祖俭等,此外还有与程迥、郭雍、林栗等人就《周易》象数占学的多次论战。所有这些一方面导致了朱子其后《戊申封事》的政治失败,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朱子对自己生平学问进行第二次总结。根据束景南的分析,朱子这一次的总结在“周敦颐的太极学与邵雍先天学的基础上展开”,主要表现有《周易本义》的成书、反对《毛诗》传统旧说、批判王学礼学和“人本主义的四书学”。因此,在“人本”阶段中,朱子诗歌创作始终伴随着其哲学再次走向更高层面的成熟与深刻,表现了朱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情感变化。如淳熙七年(1180)接连所作《戏赠胜私老友》与《代胜私下一转语》两首诗,前后情感的变化颇可见出其个人意志与事功事为之间的变化①。可以说,正是经过了“人本”阶段的充分酝酿、积淀,“存真”阶段的朱子诗歌仍能有极大的韵味。
“存真”阶段是朱子一生的离乱结局。他秉持“人本”思想,再次出山知漳州,被地方腐朽的吏治碰得一败涂地;随后长子朱塾去世,朱子返回建阳考亭,打算于此终老。然其兼济天下的儒者身份,又时时怂恿他写下:“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壬子三月二十七日闻迅雷有感》)一类的诗句。随后,朱子以六十五岁高龄出任潭州知州,赴湖南执行长沙百日新政,修复岳麓书院。紧接着又转入为新君赵扩“侍讲”(帝师)。在这来回奔波中,年迈朱子已然有所失落。在进京途中,他写下了多首“野老寻真浑有意,道人谢客亦何心。一樽底处酬佳节,俯仰山林慨古今”(《崇真观》)之类向往道家神仙境界的诗篇。然而,朱子在朝任职仅四十六日便被逐出宫廷,所有重建人间伦理的政治理想一时破灭。朱子返回建阳,悠悠又是一副离世孤立的神情:“归来眩奇语,更欲穷窈窕。却寻两翁意,宴坐得观照。”(《伏读尤美轩诗卷谨赋一篇寄呈伯时季路二兄》)在武夷山停留的那一晚,漫天飞雪,朱子填词《好事近》,叫门人歌唱:“春色欲来时,先散满天风雪……中原佳气郁葱葱,河山壮宫阙。丞相功成千载,映黄流清澈。”就在这首尚有乐观情绪的诗之后,朱子未曾料到的“庆元党禁”开始了:道学被诬为“伪学”“逆党”,朱子罢职、大弟子蔡元定贬死道州。面对大难,朱子诗曰:“老去光华奸党籍,向来羞辱侍臣冠。极知此道无终否,且喜闲身得暂安。”(《蒙恩许遂休致陈昭远丈以诗见贺已和答之复赋一首》)此后,朱子在心性修为上转入禅道风范,以“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与非”(《鹧鸪天》)以自勉;而在日常生活中,则以编订《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文学作品为务。这一时期,朱子的诗歌文本皆以表达空灵、隐忧的真实情感为主。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朱子已经完全把情感作为诗歌创作的核心,即本节所言之“存真”。如果从其话语蕴藉的文学观而言,朱子已经能够做到使诗歌表征的情感符合“道”之要求,在诗歌评论中也不再言及文道矛盾,这就是孔子所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亦可认为是理学家文学创作的“化境”。
(三)朱子诗歌文本的文体类型在对朱子诗歌创作历时性分析基础上,再以共时性的分类学视角切入朱子的诗歌文本,才有可能为朱子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建立起以话语蕴藉为标准的横纵坐标分析框架。前者的着眼点往往在于朱子单篇诗歌创作的目的和顺序,关注诗歌表达情感与朱子哲学体系变化之间的关联;而共时性视角则将关注重心从历史线索转移到文本本身,从而获得对朱子诗歌更富形式感的深刻解读。
朱子诗歌文本的文体类型,不是诗歌形式主义的分类(如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等),而是以诗歌所描述的对象为标准所确立的类型学划分。这是传统文学研究的常见分类方式。前人关于朱子诗歌的这种分类研究,也十分常见;尤其在对朱子诗歌艺术成就的研究方面。申美子将朱子诗歌分为述理诗、交游诗、感事诗、杂咏诗五类①,朱杰人则侧重山水风景诗、交游诗和哲理诗三类②;郭齐在《论朱熹诗》中也根据朱子诗歌内容,将其区分为叙事诗、抒情诗、理学诗(禅诗、道诗)等③。此外,还有根据作诗目的进行的划分,如酬唱诗、题画诗、吊亡诗、以诗代柬等。事实上,如是应景之作在朱子诗歌中占据着不小的篇幅。
本文将朱子诗歌中易于归类的感事诗(例如战事)、抒情诗(例如对一些日常事物和景物的欣赏)、哲理诗(与朱子哲学最为相关)做一概要,而朱子偶尔一些“游戏笔墨”(如回文词、嵌字格),由于代表性不强,暂且忽略。
就感事诗而言,大致可以所感对象之不同,分为两类:感时世之变迁与感民间之疾苦。前者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南宋大败金兵,正值而立之年的朱子闻捷报写下《感事抒怀十六韵》和《次子有闻捷韵四首》等诗作,其中“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次子有闻捷韵四首·其二》)等壮志豪情,充分显示了理学士子面对家国变故时的雄壮胸怀和铮铮铁骨;而《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其二》中,“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
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之句既鲜明地表明了朱子主战派的立场,同时也直抒作为书生的无奈和自责等复杂情绪。再如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受职差监河南鸿庆宫(河南此时已沦陷金朝)时作《拜鸿庆宫有感》:“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这首诗从诗人接受官职时的丰富联想出发,从侧面反映出朱子深厚的家国情怀。而正是慷慨激昂的这类诗作,切中了南宋的时代旋律,为朱子赢得了与陆游等诗人齐名的声誉;但它们主要作于朱子青年时,为数并不多。
后者主要是朱子任地方官员的感叹。尽管朱子“仕于外者仅九考”,但却多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他曾多次奉旨在福建、浙江等地赈济灾荒,目睹天灾人祸,触目而惊心地写下大量关怀民间疾苦的诗歌,其中以作于赈济崇安水灾饥荒时期写的《杉木长涧四首》(1168)最为著名。此诗风格古朴,情感充沛,显示了诗人对凄楚百姓的无限怜悯,更有对“食肉徒”的鄙夷和怒斥:“赙恤岂不勤,丧养何能供”(《杉木长涧四首·其一》),“县官发廪存鳏孤,民气未觉回昭苏”(《杉木长涧四首·其三》),“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杉木长涧四首·其四》)。与此相似的还有《邵武道中》(1151)“劳生尚行役,游子能不悲”,《冬雨不止》(1153)“田家秋成意,落落乖所期。旷望独兴怀,戚戚愁寒饥”,等等。这些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多通过语言上的修辞,把浓郁的情感隐藏在精巧的文字之中,融合叙事、抒情为一,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价值。而作于崇安大水期间的《苦雨用俳谐体》,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意象写作,表达了诗人的现实关怀:“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白死禾”——一位以“天道”为信仰的理学家,仰天斥责“天公”的无情;这样一幅画面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儒生对待自然、民瘼的态度和儒学作为宗教的暧昧性。
从抒情诗看,朱子诗歌中的情感显然是以“温柔敦厚”为标准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中既有未入仕时踌躇满志的《远游篇》:“举座且停酒,听我歌远游。远游何所至?咫尺视九州……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又有厌倦官场沉浮而向往清幽归隐生活的《夜坐有感》:“秋堂天气清,坐久寒露滴。幽独不自怜,兹心竟谁识?”正如论者所言,“这些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像少用那样乐天知命,心满意足,而是有所追求,有所不满,以敏感的目光关注着生命的流程”①。这当然与朱子哲学“心性论”中对已发之“情”的认识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恰恰表现出朱子不同于其他理学诗人的关键所在。
朱子抒情诗中表征隐幽情感的诗歌往往与书写山水的诗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朱子诗歌文本中极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林佳蓉称为“隐退山林的心境取向”②。从本质上讲,朱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朱子诗(尤其山水诗)是典型的文人诗。因此,朱子山水诗歌在意趣、旨归上仍脱离不了所谓隐逸、寄托、忧国、怀人等范畴。根据“陌生化”理论,极有可能造成“朱子山水诗平庸”的印象。但朱子山水诗有两点特征是平庸之作所不具备的:其一是对山水的真爱。朱子的弟子吴寿昌说:“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燕居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①。
这种对自然挚爱,当然是朱子性格因素使然,而理学家对“天道”的认识也是重要原因。其二是朱子山水诗中体现出的对自然天道的内化理解(体认),使得其诗具有宏大、悠远之气象。例如“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醉下祝融峰作》),此诗豪情堪比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再如“离离浮远树,杳杳没孤鸿。若问明朝事,西山暗霭中”(《舟中晚赋》),一派悠远淡然的景色衬托诗人的旷达心襟。
以上两点特征造就了朱子山水诗的独特魅力,故陈霆《渚山堂词话·序》云:“晦庵朱子,世大儒也,江水浸云,晚朝飞画等调,曾不讳言。”②此外,朱子抒情诗中还有对禅道老庄的欣赏,这与朱子的哲理诗关系密切。在宋代儒、释、道三教融一之后,“道”或“天道”其实成为三种宗教情感所共同崇拜的对象,只是各自突出“道”的不同属性及由此引申出的不同情感意趣。朱子一生出入佛老集中于青年与晚年时期,此类抒情诗也大多作于这段时期。早年朱子禅道诗在感情上往往透露出一种清新的真挚,而在哲理上则更多侧重说教,如《诵经》(1154):“坐厌尘累积,脱躧味幽玄。
静披笈中素,流味东华篇。朝昏一俯仰,岁月如奔川。世纷未云遣,仗此息诸缘。”类似诗歌还有《久雨斋居诵经》和《读道书作六首》(1153)等③。
而晚年的朱子禅道诗则更多流露出精神上的悲怆气息,禅理也显得更为通透而空灵,如《香茶供养黄檗长老悟公故人之塔并以小诗见意二首·其二》(1199):“一别人间万事空,他年何处却相逢。不须更话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二峰。”哲理诗是朱子诗歌中较为独特的部分,一般诗人并不写哲理诗,此即蔡模在《文公先生感兴诗注序》中所言:“不徒以诗为诗,而以理为诗。”以诗歌的形式阐释哲学或伦理学观念,这是朱子等理学家诗作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例如《斋居感兴二十首》其四云:“静观灵台妙,万化此从出。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今人张毅评价道:“这其实已不是什么诗,因摒去情感而专涉理路,无诗的美感可言,只能算是押韵的理学语录。”①事实上,所谓“美感”本是人言人殊之物,把事理用诗歌的形式加以表征,尤其是朱子意识到“情”有变“性”、转识成智的可能时,这种形式本身即具有了某种情趣,可以与读者有相应契之处,当然可以视为一种“美感”;更遑论诗歌语言本身的“陌生化”效果在形式主义之后即被公认为“文学性”的重要来源。以《斋居感兴二十首》其四为例,此诗写的人心性万妙,把说理放在了诗歌的韵律与形式之中,有设问、有隐喻,显然是为了让读者在俯仰吟诵的感兴接受中体认“心性”。这种独特的理学传播方式,不仅在于押韵,更在于朱子诗题所言的“感兴”,也就是在唤起文学情感间传递理学观念。在朱子所写的哲理诗中,《观书有感》《偶题三首》等都是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
总体而言,朱子诗歌内容丰富,但所表达的情感形式却不复杂。朱子善于把复杂的哲学以简单的情感为表现形式,再加以讲求修辞的文字为载体,从而表现出文学艺术的美。在这个意义上,清人陈〓《宋十五家诗选》“朱子诗高秀绝伦,如峨眉天半,不可攀跻。至其英华发外,又觉光风霁月,粹然有道之言,千载下可想其胸次也”②之论,并不过分。另外,值得说明的是,以上划分,感事、抒情、哲理三种文体类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界限。同一首诗,在不同学者看来,可以划入不同的文体类型之中,乃是常事:感事之中亦有浓烈的情感,抒情也往往由事而生,哲理更是贯穿在朱子诗歌创作实践的始终。但这种边界模糊的划分,仍有助于窥视朱子诗歌文本的全貌,从宏观上把握朱子诗歌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四)朱子诗歌的艺术评价历来对朱子诗歌作品褒贬不一,扬之者称“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李淦《文章精义》),贬之者讥为“有韵的哲学讲义”①。前者固然有所夸大,后者则是以偏概全的无根之论。而晚近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对朱子往往付诸阙如;中国文学理论史也多对其诗文评不著一字,这更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从艺术角度评价朱子诗歌,是当代朱子诗歌研究的重点,于此前人之述备矣。②本文特拈出三点值得特别重视之处,分述如下。
首先是朱子诗歌文风古朴、典雅,同时又蕴含着沉雄之气,具有凝练的美感。朱子早岁学习汉魏古诗,亦步亦趋地练习写作:“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③这极大地影响了朱子一生的诗歌风格,与其后推崇陶渊明、韦应物、陈师道的诗作有着必然的关系。与此同时,这种诗风与朱子在审美意趣上以阳刚、崇高为旨也有关联。朱子说:“刚健中正……阳刚自是全体,岂得不中正!”④以朱子为代表的道学派诗人雄浑而经天纬地的诗歌观,在南宋江西诗派“神头鬼面”的风气中,其实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其次是朱子诗歌视野开阔,胸次洒然,有着一般风雅诗人所不能及的高远之气。这也是朱子反复强调的:“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⑤这一说法遭到不少诗学家的反对,尤其是主情派诗学家,他们认为诗歌不应说理,而应抒情;这当然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对文学有着极为深刻认识的朱子,于此不可能不察。事实上,朱子强调诗歌说理是建立在抒情性的基础之上的。朱子在《诗集传序》中说诗歌之所以创作的缘由是:“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①这是很典型的“诗言情”论,而其又说:“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②,更直接彰显了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就其实而言,这种“诗言情”的论调并不深刻,早在汉代“诗大序”中就有相似论述。朱子超越同时代诗论之处在于,他坚持认为:“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③在这一基础上,朱子在《楚辞后语·序》中提出:“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或言“‘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④这些极其深刻的美学论断,总结了朱子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艺术品格。因此,论者言其诗云:“浑涵万有,无事模镌,自然声振,非浅学之所能窥。”⑤虽有所夸大,亦不失为正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朱子诗歌中蕴含着大量日常生活与文人雅趣相结合的文本,显示了朱子道学平易近人的一面。世人多以肃穆视朱子,而其自己也坚持“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⑥的《写照铭》作为人生准则;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也说“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⑦。但在诗歌之中,朱子的文人情趣,甚至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都一览无余;他甚至有十九首词作传世,这在当时诗歌正统极为盛行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因此,清人焦循说:“谈者多谓词不可学,以其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朱晦翁、真西山俱不废词,词何不可学之有?”⑧如果说仅有词作不足以证实朱子性格中富有情趣之意,他的纯粹笔墨游戏的回文词、嵌名诗则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朱子有《菩萨蛮》回文词两首,其一云:“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全词正逆序均可读通,诗意盎然,颇费心机。清人邹祗谟说:“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①,可以看出朱子的独特创意。此外,朱子还有五首禽言诗,模仿禽鸟啼叫之声而为的民间歌调,写出了民间生活的情趣;《九曲棹歌》十首,则以渔民歌谣风格,写出文人归隐的生命情绪;《训蒙绝句》百篇,更是以学者思想直接整合当时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这些文字形式突出的诗歌文本,为数众多,显示了朱子作为理学家的乡土气息,也淬炼出他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与前文所谓“人本”取向之间有着可资参见的形式与内容之关联。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子是一个文人气息极其浓郁的学者,他的诗人气质与生俱来。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朱子诗歌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也不仅具有以诗证史的史料价值,它还具有哲学价值。以现今朱子文学研究来看,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朱子诗歌文本进行与时俱进的、富有时代意味的美学与哲学阐释,还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分析和思考。而于此可以尝试回答的是,本节开篇提出的一个疑问。
(五)理学家轻视文学吗?宋代理学家虽以心性为务,但其视“理”于心外,而与所谓“心学家”产生分野。这一状况造成了“理学家视文艺为末流”的说法,成为一时之“公论”。在中国学界,讨论宋代文论者多把视野的核心聚焦在欧阳修、江西诗派、《沧浪诗话》等问题上。晚近以来影响较大的若干部教材,莫不如是。①相比之下,理学家的文论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可有可无的陪衬或点缀。
这不仅与文学实践史上如朱子等人“以诗名”的状况不符,也未必符合中国文论发展的实际状况。宋代以降,占据中国文学理论主潮的,恐怕不是严羽等处于文坛边缘评论家——同为闽北人的严羽,连一部起码的传记都没有留下。在理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之后(宋、元),中国文论的发展其实是以理学标准为框架的;可是,这在当代中国文论教材中很难寻觅到论述的笔墨。中国文论的历史书写,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理论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对宋代理学的“刻板印象”与文学概念既定模式的生硬运用。此处所言的“刻板印象”,是指“理学家轻视文艺”已成为中国文论史的定论。这种简明扼要的“结论”式命题,把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处理;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即理学美学或理学文学得到的关注极其之少——就文论系统的研究成果而言,宋代理学文论显不及其他朝代或同代其他流派的研究之繁荣;就理学系统的研究而言,理学文论又不及其他学科领域,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成果显著。
具体到朱子身上,据林庆彰和莫砺锋的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际学界关于朱子的研究著述达2254种,而文学研究不过寥寥三四十种。②就文学概念既定模式的裁剪作用而言,不同时代对“什么是文学”或“什么是文论”问题的回答,乃是确立其时文学、文论史书写基本范式的关键。与中国古代“诗言志”和“诗缘情”并举的状况不同①,当代中国文学经历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话语“洗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形成了以个人抒情对抗宏大叙事的先锋文学传统。在这套话语体系中,“文学”的价值天平倾向着“表现说”的立场,加之西方传入的形式意识,各种实验文学纷纷登台。用这种“文学”概念来裁剪文学实践,必然有因不符合“抒情”或“语言形式”要求而被淘汰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观念——理学家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便是典型。
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编撰才更多把严羽等在历史语境中并不显赫的人物作为一代文学精神的高标——这在后人的评价体系中当然不成问题,但如果将其视为历史真实的书写,则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
“理学家轻视文学”的论断其来有自,将其视为一种“刻板印象”并不是要推翻它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从历史来看,“理学家轻视文(学)”有着充足的论据。自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始,“重道轻文”就是典型之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②此外,二程、邵雍、张栻等人都有过相关类似的论述,兹不多举。
但问题在于,周敦颐这段已被无数次引用的话语之“文”,实乃与今日之所说“文学”不是一回事。在周子的运用中,“文”主要是统指能够承担道德意义的文字组织形式,即“文字”,虽然它包括作为“艺”的“文辞”,但“文辞”是不是就等于“文学”,恐怕还难以下定论。“文”之多义,需从其源头说起。
“文”或“文学”在中国古代起源于笔画符号。《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①,指的乃是自然界的斑纹或人工图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最多不过是“有文采的文字组织”而已。然而,这种代表着“美”的文字形态,在中国却有着相当深厚的民间崇拜传统。尤其在道教因素参与下,“文字”竟成了“随运开度,普成天地之功”的基本法则②。故《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③就此来说,周敦颐所言的“文辞”者,所指大抵是“文字”;周敦颐所说的“文以载道”,其实乃是“文章载道”或“文字载道”,而非“文学载道”。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周敦颐这番话语的针对对象是那些对“文字”的魔力有着过分崇拜的士子④,而非善于以文抒情的文人。
一般认为,“文字”之为“文学”,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其一是“文学”讲求文采,善于运用隐喻、反讽、悖论、朦胧等修辞形式对文字的组合加以变形,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⑤其二是“文学”讲求情感,要求在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活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⑥这二者的结合,便是本节前文所言的“话语蕴藉”,也就是“文学”应该在文字的字面意思之外,含有更为深刻的有待读者加以理解和阐释的意义,特别是需要加以体会的情感。而作为理学家口号的“文以载道”恰恰是要求文章作品在其字面意思之外必须有更深层次的“道”的要求,“道”蕴藉、隐藏在“文”之中,并借助“文”而进入读者的内心深处,呼唤起深远的回音——“美则爱,爱则传焉”。如果用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加以阐释,可以说无论是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还是程颐的“作文害道”,或者朱子的“道本文枝”,其根本反对的乃是“以辞害意”,而非“以情害意”。故程颐云:“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①说到这里,道理已经毕现,即“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刻板印象来自于今人对“文学”在中国古代语境中的误读,“理学家轻视”的“文学”是讲求文采的“文”(辞),而非“话语蕴藉”。不过,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理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却还有更深一层的复杂性。他们虽然不普遍反对一切文字组合形式,但对其所表之情感却有特殊的要求。文学作品表达情感,作者的情感能够通过文学阅读传达给接受者,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被称为“感兴”。文学具有鼓动性情的“感兴”作用,接受者有可能被文学文本所表达的情感牵引而丧失主体性意识,这正是理学家们所担忧的。但这一功效是可以反作用的,亦即是通过文学文本传递“正确”的情感,来引导读者挺拔其高度自觉的自我主体性。从朱子诗歌题目多次出现“感兴”二字——如前文所引《斋居感兴》多首,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理学诗人对此是有着高度自觉的。
邵雍说:“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这似乎可以视为理学家视文学为洪水猛兽,惟恐“以情害意”的证据。但邵雍笔锋一转,“古者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覆载在水也,不在人也;载则为利,覆则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②这就是说,“情之溺人”的关键在于所“溺”之“情”的性质;倘使主体能够“以物观物”“情累都忘”,则所留之“诗”便有益于“天下大义”;于是,个人的主体性不是丧失,而是得到了升华。这一点在周敦颐、二程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曰:“《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①可以说,“文学”的两重特性(文采、情感)在理学家那里都不是清晰可辨的。这不仅增加了后人对理学家文艺观理解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理学家自身的矛盾人格。而“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刻板印象在文学史对朱子的评价上,尤为明显。本节所述今人的朱子文学研究之弱便是明证。今以朱子诗歌创作为例,加上上文的理论澄清,或可破除“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于万一。不过,也如前文所言,“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论断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需要将既定的刻板印象引入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才有可能使其从内部得以破解。诗歌(文学)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艺术。理学家重视后者尤胜前者。对此,朱子有着高度的自觉。于此可以再举一例。朱子虽也有“游戏文字”,但从其创作大量诗歌的题目来看,他并不重视文字(文辞)。与一般诗人篇目的用心不同,朱子诗歌的题目很多是在叙事,交代作诗的前因后果,文字多得令人称奇。
仅举两例,如《丁丑冬在温陵陪敦宗李丈与一二道人同和东坡惠州梅花诗皆一再往反昨日见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再和一篇呈诸友兄一笑同赋》与《昨承诸兄临辱不揆以薄酒蔬食延驻都骑明日视壁间所张墨刻有亡去者人以为德庆丈之庾也驰问遣索蒙需拙诗辄赋所怀往奉一笑而尊犍刻可以归于我矣》1其诗歌的内容都没有其题目长。这恰说明朱子重视的是诗歌的内容,亦即是其传递的情感,如“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之感;而非文字堆砌的巧妙与所谓“艺术”。同样以此二例,还值得一说的是诗名中都有“一笑”两字,这在一千多首朱子诗中,并非仅见,但却多于长诗名之中。再如《去岁蒙学古分惠兰花清赏既歇复以根业归之故——而学古预有今岁之约近闻颇已著花辄赋小诗以寻前约幸一笑》《宋丈示及红梅腊梅借韵两诗辄复和呈以发一笑》《圭父约为金斗之游次韵献疑聊发一笑》《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诸名胜为落星之游分韵得往字率尔赋呈聊发一笑》《读十二辰诗卷掇其余作此聊奉一笑》等。这些处处可见的“一笑”,足可说明朱子对诗歌文字的不在意,而其“一笑”之作多见于“分韵”(赋韵)文字,更可见文字技法在朱子那里不过是点缀而已。
于此可以说明的是,理学家轻视文学,其意主要在于轻视文学之技法(文辞),而警惕文学之情感偏向,乃是理学之本,非仅文学受累,举凡释家、道家莫不在其警惕的范围之内。因此,笼统说“理学家轻视文学”,实则是一种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今人出于自我对“文学”概念理解的误读。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子,不但不轻视文学,更亲身实践,热衷文学创作。如果不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理解朱子,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朱子之后的理学文论)将无法得到深入的阐释,而浮于“理学家轻视文学”或“理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矛盾的”等论断的表面,更无助于将问题引向历史的深处。朱子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文本是复杂的,对其进行阐释也有多种角度,但无论如何,轻率的刻板的判断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作为诠释主体的朱子本人之态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性情、理想、志业、感兴等生命价值观,是必须给予充分考虑的。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子的诗人声名一直没有得到今人足够的重视,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朱子是反对诗歌、轻视诗歌的。而与之相应的,是“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在传统学术史上近乎刻板的印象——即使就朱子自身而言,他也不愿意被人以“诗人”身份视之。问题究竟为何?本节尝试从朱子对待诗歌的创作态度入手,概述朱子一生的诗歌创作实践,并力图对其艺术价值作出较为公允的评判。在此基础上,本节将对“朱子反对写诗”或“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命题做一定分析。显然,这是一个思想史问题,而对待此问题并不能以“朱子自己也作诗”这一基本事实加以简单的否定。论者需要做的是深入分析朱子创作的诗歌文本及其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分析朱子的诗歌理论,综合其艺术实践加以评判。
(一)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自孔子云“三十而立”开始,“而立之年”就被中国人视为是个体思想确定与成熟的标志性时间点。在三十岁那一年前后,朱子以“绝不作诗”为题写了一首诗:“神心洞玄鉴,好恶审薫莸。云何反自诳,闵默还包羞。今辰仲冬节,寤叹得隐忧。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朋来自兹始,群阴邈难留。行迷亦已远,及此旋吾辀。”(《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这一首诗长长的题目详细交代了朱子作此诗的缘由——三十岁前后的朱子,正处于“弃禅归儒”的关键期;三十岁那年,他正式受学延平李侗,脱离了在同安任主簿时沉溺佛老世界的精神状态,决心以儒为业,趋向圣贤之道。可以说,此时的朱子正是在转向的关节点上。因此,从语言上看,此诗仍然大量使用了庄、禅术语,如“神心”“玄鉴”“朋来”“群阴”等;而从诗歌所表达的意愿上看,朱子则直抒对“反自诳”的“包羞”“隐忧”,并决意“及此旋吾辀”,亦即是调转船头,脱离空灵,朝向儒学。可这一套思想、情感乃是通过极具诗意的道家话语系统表现出来的。“绝不作诗”的意愿以诗的文体形式加以表达,否定审美情感的志向以审美话语为载体,此诚朱子自谓“盖不得已而有言”也,亦颇似戒烟者自云“再吸一支以纪戒烟之始”。
在这一事件中,朱子发誓“绝不作诗”的原因初看是“多言害道”;此语类似程颐所谓“作文害道”,但又明显超出了“作文害道”的范畴。在程颐看来,“作文害道”的问题在于“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①。程颐这种因“用功”而造成的“害道”,实则仍在技术层面,并未真正涉及文道关系问题。而朱子所谓“多言害道”,乃是由于阅读《大学·诚意》篇而生发的感慨。《大学·诚意》云:“毋自欺也……君子必诚其意”,这显然是诗中“云何反自诳”的出处。也就是说,朱子在此认识的“多言害道”问题已经远较程颐“作文害道”来得深刻,他看出了诗性语言能够塑造和引导人的情感与思维,甚至有可能混淆主体意识的“好恶”观念,蒙蔽“玄鉴”。然而,朱子一生尊崇道统,实在不可能充分意识到“语言”本身的力量,光大自己独特的观点,从而推翻程颐的“作文害道”论。
他也常常陷入程颐的说辞之中,如其曰:“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②无论如何,以此为例,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态度集中于文(语言)道(情感、志向)关系上,并长期存在于其创作实践中。
时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有云:“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酬唱至百余篇。忽矍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③这以鲜明的例证,说出了朱子在当时世人眼中的形象——不仅作诗,而且诗名甚大。可是,朱子却以此为辱。自我认识与社会形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此可见一斑,而朱子的自我期许与自我行为之间的巨大矛盾,也可从此显出。朱子对待诗歌,态度终究暧昧。
还可以再举一例。朱子三十八岁那年与张栻同游南岳,那是其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阶段。数月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朱子成诗一百三十多首①。这百余首诗篇来得并不容易,朱子之矛盾心态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有详细记载:丙戌至株洲,熹与伯崇、择之取道东归,而敬夫自此西还长沙矣。
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岳宫至株洲凡百有八十里,其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来所见,无非诗者。而前日既有约矣,然亦念夫别日之迫,而前日所讲,盖有既开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与思绎讨论,以毕其说,则其于诗,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谂于众曰:“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惩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然而今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然则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皆应曰:“诺”。既而敬夫以诗赠吾,三人亦各答赋以见意。熹则又进而言曰:“前日之约已过矣,然其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忘也。何则?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故前日戒惧警省之意,虽曰小过,然亦所当过也。由是而扩充之,庶几乎其寡过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书之,以诏毋忘。……自今暇日时出而观焉,其亦足以当盘盂几杖之戒也!②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朱子与张栻在南岳酬唱之后,“既有约矣”(约定不作诗),因此,即使“自岳宫至株洲凡百有八十里”,其间所见“无非诗者”,但他却没有作诗;而在株洲,两人即将别离,“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于是朱子宣布“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而这并不意味朱子认为诗可作,他仍殷殷切切地“进而言曰”,“戒惧警省之意”不可忘。“刚刚极南岳唱酬之欢,却又宣布戒诗之约;刚刚宣布戒约,却又要求罢去;罢去未几天,却又重申戒惧警省之意。这里重申戒惧警省之意,紧接着东归一路,又有《东归乱稿集》问世。”①这种反复的情形,将朱子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例证之外需要讨论的是朱子于此提出的“戒诗”之缘由。比八年前的“多言害道”更加深入,这次朱子认为,“戒诗”是为了“戒惧警省”。不过,朱子所标举的理由,不过是“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营惑耳目、感移心意”等来自《大学·诚意》中所谓“君子慎独”的一套说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次提出要警惕的不是所有诗歌,而是诗之“流”。在其“流”之前的那些“宣畅湮郁,优柔平中”的诗,则“非有不善”,是值得肯定的。
可见,朱子之所以反对诗,其理论立足点大异于程颐的技术层面。在朱子看来,符合“道”之要求的情感的诗是可作、可读的,而“作诗”这种文学实践本身是语词的“游戏”,人的情感有可能被语词所控制,从而丧失了主体意识(丧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诗”这一行为本身是危险的,特别是在“离群索居”的时候,主体意识未得他者的“辅仁”而尤为薄弱,极易被“营惑”“感移”。可以说,朱子已经发现了诗歌(文学)具有语言(文)和情感(道)的双重属性;而在程颐那里,诗歌还仅是一种语言的“玩物”而已。朱子是在话语蕴藉的意义上来理解“诗歌”的,他对诗歌(文学)的认识,已经远远高于程颐等前辈理学家了②。
若非以当代文学理论家比拟,大致可认为朱子所赞赏的诗歌与罗兰·巴特所倡导的“可读的文本”(悦之文)近似,而其所反对的诗歌与巴特所谓“可写的文本”(醉之文)又有可以比拟之处。在巴特看来,可读的文本是古典文学,而可写的文本是先锋文学,前者是“欣快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而后者则是“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或许已至某种厌烦的地步),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①当然,这种比较是颇为牵强的,但却可见出朱子文论之深刻。
朱子对诗歌(文学)有如此深刻而复杂的认识,就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所以,在“文学是话语蕴藉”的意义上重新认识朱子诗歌文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朱子诗歌研究史上,对朱子诗歌创作进行宏观描述,是许多前人业已进行过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历史性的描述”与“分类学的描述”两种类型:前者把朱子诗歌创作的五十年分为若干阶段,分别分析朱子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诗歌作品风格、意义等;后者则是对朱子诗歌文本做理趣诗、山水诗、感事诗等类型学的分析。按照索绪尔区分的“历时”与“共时”范畴,前者可以认为是“历时性”的综述,而后者则是“共时性”的综述。从前者可以看出朱子诗歌创作五十年间的不同变化,后者可以归纳朱子诗歌不同类型的特征。但这两种方法却各有利弊:历时地看,朱子诗歌是一个变动不居、不断调动的文本层次;就其整体来说,又缺乏对其分阶段思想进阶的把握,而缺乏对某首诗歌创作语境的了解,对其解读就难免有所偏颇。因此,这两种分析方法应该适当加以结合,或者分别加以诠释,以形成互文,才能使朱子诗歌文本得到有机的分析、组合,进而呈现出整体全貌。
(二)朱子诗歌创作的历史阶段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对研究对象展开分类,对朱子诗歌创作历程的分阶已经有多种见解。从已有分析上看,这一历时性分析的视角大多以朱子生平历程为分界点,集中在其赴同安任职、知南康军、筑室建阳考亭等几件生平大事上。如蔡厚示、杨国学等人将朱子的诗歌创作分为早期(1148—1165,十九至三十五岁)、中期(1165—1194,三十五至六十四岁)、晚期(1194—1200,六十四至七十一岁)三期②,而吴长庚先生则将其分为准备阶段(十九至二十七岁)、高潮阶段(二十七至五十岁)、成熟阶段(五十至五十三岁)和终老阶段(五十三至七十一岁)四个阶段等。③这种历史分阶方式的优势在于便于处理朱子诗歌所表述的事实性内容及其所直接表述的情感,从而对朱子诗歌文本展开审美价值、艺术风格的评判。但这种分析方法也有简单使用“社会决定论”的弊端,即单纯用作者生平经历来理解其文学创作。要知道,不少诗歌是激于一时之情感勃发而作的,未必真与作者的生平经历(特别是重大事件)有必然关联。
与其使用朱子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期标准,不如转而思考朱子诗歌创作与其哲学体系分段进展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与诗歌类似,都是朱子精神世界的长期表征与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前文已述,朱子对文学创作作为话语蕴藉的功能极有认识,他不可能不在其诗歌中传递与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事实上,这也正是后人对宋诗的基本认识:“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①,或是“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②。因此,或可尝试使用朱子哲学的分阶,来对其诗歌加以历时性分析。
朱子诗歌文本与其哲学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这本应在对朱子诗歌文本的历时性分阶中得到较为清晰的揭示。可是,目前文献中这一视角的研究还不充分。郭齐根据朱子对道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将朱子诗歌创作以三十五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又辅以六个创作高峰期,这种分类方式是比较吻合其哲学标准的。③但显而易见的是,郭齐的这一分阶方法失之过简,仅有三十五岁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另外,所谓“创造高峰期”往往是由于某一事件(如南岳访张栻)而造成的,与朱子的哲学体系的发展并无必然关联。因此,这一分阶标准虽方向有创新价值,但其具体操作则仍可加以商榷。
本小节根据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④,将其诗歌文本创作分为“入儒”(1148—1169,十九至三十九岁)、“求衡”(1169—1177,三十九至四十七岁)、“人本”(1177—1189,四十七至五十九岁)与“存真”(1189—1200,五十九至七十一岁)四个阶段。这一分阶大体与朱子哲学的形成、发展、成熟和趋于化境的历程相应。以下分而述之。
朱子自述青少年时节,“某旧时亦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①。在这一时期,朱子开始了诗歌创作。而这些诗歌恰好又可以印证朱子从少年的器宇轩昂到初仕同安的苦闷,进而结交泉州名士、出入佛老,最后投身儒门,完成“弃禅归儒”的思想变迁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说,朱子在“入儒”阶段所积累的各种思想、认识、观念最终都构成了其哲学体系得以建立的学理基础——有的是以潜流或对立面的形式出现的,如禅学。因此,从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能较为明显地看出青少年时期的朱子思想变迁之情感因素。如中进士之后,朱子曾有长达五年的时间在家待职,青年的踌躇满志在闲散中消磨,逐渐出现“不恨岁月遒,但惜芳华姿。严霜萎百草,坐恐及兹时”(《古意》)的心态变化;而在同安任上,朱子孤寂之心亦时时涌起:“远宦去乡井,终日无一欢。援琴不能操,临殇起长叹。”(《寄黄子衡》)尽管这种心态可以在短暂的山水游乐中得到舒缓,如“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涉涧水作》);或在朝廷对抗金兵获胜的消息中得到暂时的喜悦,如“东京盛德符高祖,说与中原父老知”(《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其五》),但这些外来的刺激性放松毕竟无法成为朱子如此重视心性修为者愿意寄托精神的对象。因此,他在赴京城诠试前后进一步沉溺佛老,在其后自编诗集《牧斋净稿》中,记录了这段“望山怀释侣,盥手阅仙经”(《夏日》)的时光。
出仕同安是朱子思想的转折点,这与儒学事功的性质是相契的。朱子在同安任上整顿赋税,清点田亩经界,“一置身于同安尘世社会,他的儒家积极经世治邦的现实精神的一面高昂起来”了②。也正是在这前后,朱子正式拜李侗为师,将书斋“牧斋”改名“困学”,开始了艰难的由禅“入儒”的求学经历。其诗曰:“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在“入儒”阶段末,朱子迎来了一生中诗歌创作最高潮,即前文所提及的、常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的“朱张会讲”。在南岳及其归途的四个月时间中,朱子成诗一百三十余篇,编成《南岳唱酬集》和《东归乱稿》两部诗集。这两部诗集中所收朱子诗,充分显示了朱子儒学思想第一次升华前的样貌,全力促成了朱子在己丑年(乾道五年,1169)提出“中和新说”,史称“己丑之悟”。至此,朱子的哲学思想才逐渐成熟——“己丑之悟从根本上确立了朱子的学术面貌”①。
“求衡”阶段是朱子哲学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朱子潜居寒泉、云谷等地“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卜居》),潜心探讨本体论与宇宙观,完成十余部学术著作;并通过书信与湖湘派展开论辩,与吕祖谦相与讲习,参与鹅湖之会等大量学术活动。在这些活动的间隙,或有感于学术思想的魅力,朱子才偶有诗篇创作记录自己的思想历程,如《云谷杂诗十二首·讲道》云“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而在短短的八年中,朱子的哲学思想也出现了多次变化,其经学体系也在与他人的不断论争中走向完善。尤其重要的是,与陆氏兄弟的鹅湖之辩,构成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不同为学、修心取向在朱子心中的对立。这一对立推动着朱子找到“敬知双修”的进学路径,从而不断在以知识为本的基础上,于“道问学”与“尊德性”间寻找一种平衡。而与此同时,反道学声音也甚嚣尘上,可以说,此时的朱子之“求衡”同样也发生在自我与俗世之间,究竟是应该继续内心平和地读书求学,还是要愤世嫉俗的入世事功?从其教诲学生吴楫(字公济)的诗:“欲知陋巷忧时乐,只向韦编绝处寻”(《公济和诗见闵耽书勉以教外之乐以诗请问》)或可见一斑。而也许正是在前一思想的影响下,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淳熙二年,1175),朱子与吕祖谦游百丈、登芦峰,又一次爆发了诗歌创造的“小宇宙”,构成了其创作生涯中的高潮之一;其《百丈山记》一文,也由此而成千古名篇。
在“求衡”阶段中,朱子对待诗歌的态度始终随着其哲学体系的逐步完善而出现变化。他既对诗歌(文学)语言与道学情感之间的矛盾存在疑惑:“诗篇眼界何终极,道学心期未遽央。安得追寻二三子,舞雩风月共徜徉”(《择之寄示深卿唱和乌石南湖佳句辄次元韵》);又有因对自创道学体系的自信,而对诗歌作用的宽容:“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风弄月兴何长。从容咏叹无今古,此乐从兹乐未央”(《抄二南寄平父因题此诗》)。可以说,朱子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仅贯彻了他对文学乃是一种话语蕴藉的认识,而且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表征了文学的这一特性,使之具有与其哲学互诠的价值。“求衡”阶段的结束以淳熙四年(1177)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为标志,这被学者称为朱子“生平学问的第一次总结”①。此后,朱子再次出仕南康,道学体系从偏向理论构建,转向了更终极的指向,即出现了人本色彩。
在朱子哲学基本定型之际,朝中纷争不断,交替上下台的宰辅们轮番劝请朱子出山;连吕祖谦也来信劝说,“承领上意……使世见儒者之效,于斯文非小补也”(《吕东莱文集》卷三)。尽管朱子本人更愿意在深山之中继续完善其道学体系,三番两次上书请辞,如《寄籍溪胡丈及刘共父二首·其一》一诗曰:“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可是,省札时时催促,朱子也只好应命,于淳熙六年(1179)初从命抵达南康,出任知军;其后又转浙东提举。时诗人王质有诗云:“晦庵今年登五十……晦庵不急苍生急。”(《赠黄君》)朱子上奏请求免税、赈济灾荒,兴建白鹿洞书院,砥砺士风,写下了大量感时忧民的诗篇:“况复逢旱魃,农亩无余收。赤子亦何辜,黄屋劳深忧。”(《秋日告病斋居奉怀黄子厚刘平父及山间诸兄友》)在这些诗篇中,朱子的底层“人本”倾向是显豁的,可以认为也是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使命在诗歌中的直接显现。
与此同时,朱子在政事之余畅游江西,“把郡事余暇全部用在了登山唱酬上,两年中他几乎游遍了庐山每一处胜地,写下百余首诗篇”,甚至“俨然以诗坛盟主开导士子,要想改变积重难返的江西诗风”②。可以说,“人本”阶段的朱子山水诗已经达到了其一生的巅峰。“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陶公醉石归去来馆》),朱子的这些诗一方面师法其父朱松所崇尚的“简淡”笔力,另一方面也受到江西诗人诸如辛弃疾、陆游等人交往的影响,在清景中蕴含了道学生机至乐的一面。此类诗风,在朱子卸任提举,跧伏武夷山中所作诸如《九曲棹歌》等诗篇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亦可视为一种潜在的“人本”倾向:理学的终极指向分内外两个维度,其内向性的目的在于实现主体精神的自由解脱,即“鸢飞鱼跃”之境;而其外向性目的则是重构现实伦理世界。
可以认为,朱子“人本”阶段的诗作,大多可以体现这种哲学意图。
“人本”阶段后期,朱子在武夷山同当时诸派展开了全面的论战,对手包括永康学派陈亮、江西陆学、吕祖俭等,此外还有与程迥、郭雍、林栗等人就《周易》象数占学的多次论战。所有这些一方面导致了朱子其后《戊申封事》的政治失败,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朱子对自己生平学问进行第二次总结。根据束景南的分析,朱子这一次的总结在“周敦颐的太极学与邵雍先天学的基础上展开”,主要表现有《周易本义》的成书、反对《毛诗》传统旧说、批判王学礼学和“人本主义的四书学”。因此,在“人本”阶段中,朱子诗歌创作始终伴随着其哲学再次走向更高层面的成熟与深刻,表现了朱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情感变化。如淳熙七年(1180)接连所作《戏赠胜私老友》与《代胜私下一转语》两首诗,前后情感的变化颇可见出其个人意志与事功事为之间的变化①。可以说,正是经过了“人本”阶段的充分酝酿、积淀,“存真”阶段的朱子诗歌仍能有极大的韵味。
“存真”阶段是朱子一生的离乱结局。他秉持“人本”思想,再次出山知漳州,被地方腐朽的吏治碰得一败涂地;随后长子朱塾去世,朱子返回建阳考亭,打算于此终老。然其兼济天下的儒者身份,又时时怂恿他写下:“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壬子三月二十七日闻迅雷有感》)一类的诗句。随后,朱子以六十五岁高龄出任潭州知州,赴湖南执行长沙百日新政,修复岳麓书院。紧接着又转入为新君赵扩“侍讲”(帝师)。在这来回奔波中,年迈朱子已然有所失落。在进京途中,他写下了多首“野老寻真浑有意,道人谢客亦何心。一樽底处酬佳节,俯仰山林慨古今”(《崇真观》)之类向往道家神仙境界的诗篇。然而,朱子在朝任职仅四十六日便被逐出宫廷,所有重建人间伦理的政治理想一时破灭。朱子返回建阳,悠悠又是一副离世孤立的神情:“归来眩奇语,更欲穷窈窕。却寻两翁意,宴坐得观照。”(《伏读尤美轩诗卷谨赋一篇寄呈伯时季路二兄》)在武夷山停留的那一晚,漫天飞雪,朱子填词《好事近》,叫门人歌唱:“春色欲来时,先散满天风雪……中原佳气郁葱葱,河山壮宫阙。丞相功成千载,映黄流清澈。”就在这首尚有乐观情绪的诗之后,朱子未曾料到的“庆元党禁”开始了:道学被诬为“伪学”“逆党”,朱子罢职、大弟子蔡元定贬死道州。面对大难,朱子诗曰:“老去光华奸党籍,向来羞辱侍臣冠。极知此道无终否,且喜闲身得暂安。”(《蒙恩许遂休致陈昭远丈以诗见贺已和答之复赋一首》)此后,朱子在心性修为上转入禅道风范,以“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与非”(《鹧鸪天》)以自勉;而在日常生活中,则以编订《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文学作品为务。这一时期,朱子的诗歌文本皆以表达空灵、隐忧的真实情感为主。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朱子已经完全把情感作为诗歌创作的核心,即本节所言之“存真”。如果从其话语蕴藉的文学观而言,朱子已经能够做到使诗歌表征的情感符合“道”之要求,在诗歌评论中也不再言及文道矛盾,这就是孔子所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亦可认为是理学家文学创作的“化境”。
(三)朱子诗歌文本的文体类型在对朱子诗歌创作历时性分析基础上,再以共时性的分类学视角切入朱子的诗歌文本,才有可能为朱子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建立起以话语蕴藉为标准的横纵坐标分析框架。前者的着眼点往往在于朱子单篇诗歌创作的目的和顺序,关注诗歌表达情感与朱子哲学体系变化之间的关联;而共时性视角则将关注重心从历史线索转移到文本本身,从而获得对朱子诗歌更富形式感的深刻解读。
朱子诗歌文本的文体类型,不是诗歌形式主义的分类(如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等),而是以诗歌所描述的对象为标准所确立的类型学划分。这是传统文学研究的常见分类方式。前人关于朱子诗歌的这种分类研究,也十分常见;尤其在对朱子诗歌艺术成就的研究方面。申美子将朱子诗歌分为述理诗、交游诗、感事诗、杂咏诗五类①,朱杰人则侧重山水风景诗、交游诗和哲理诗三类②;郭齐在《论朱熹诗》中也根据朱子诗歌内容,将其区分为叙事诗、抒情诗、理学诗(禅诗、道诗)等③。此外,还有根据作诗目的进行的划分,如酬唱诗、题画诗、吊亡诗、以诗代柬等。事实上,如是应景之作在朱子诗歌中占据着不小的篇幅。
本文将朱子诗歌中易于归类的感事诗(例如战事)、抒情诗(例如对一些日常事物和景物的欣赏)、哲理诗(与朱子哲学最为相关)做一概要,而朱子偶尔一些“游戏笔墨”(如回文词、嵌字格),由于代表性不强,暂且忽略。
就感事诗而言,大致可以所感对象之不同,分为两类:感时世之变迁与感民间之疾苦。前者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南宋大败金兵,正值而立之年的朱子闻捷报写下《感事抒怀十六韵》和《次子有闻捷韵四首》等诗作,其中“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次子有闻捷韵四首·其二》)等壮志豪情,充分显示了理学士子面对家国变故时的雄壮胸怀和铮铮铁骨;而《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其二》中,“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
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之句既鲜明地表明了朱子主战派的立场,同时也直抒作为书生的无奈和自责等复杂情绪。再如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受职差监河南鸿庆宫(河南此时已沦陷金朝)时作《拜鸿庆宫有感》:“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这首诗从诗人接受官职时的丰富联想出发,从侧面反映出朱子深厚的家国情怀。而正是慷慨激昂的这类诗作,切中了南宋的时代旋律,为朱子赢得了与陆游等诗人齐名的声誉;但它们主要作于朱子青年时,为数并不多。
后者主要是朱子任地方官员的感叹。尽管朱子“仕于外者仅九考”,但却多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他曾多次奉旨在福建、浙江等地赈济灾荒,目睹天灾人祸,触目而惊心地写下大量关怀民间疾苦的诗歌,其中以作于赈济崇安水灾饥荒时期写的《杉木长涧四首》(1168)最为著名。此诗风格古朴,情感充沛,显示了诗人对凄楚百姓的无限怜悯,更有对“食肉徒”的鄙夷和怒斥:“赙恤岂不勤,丧养何能供”(《杉木长涧四首·其一》),“县官发廪存鳏孤,民气未觉回昭苏”(《杉木长涧四首·其三》),“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杉木长涧四首·其四》)。与此相似的还有《邵武道中》(1151)“劳生尚行役,游子能不悲”,《冬雨不止》(1153)“田家秋成意,落落乖所期。旷望独兴怀,戚戚愁寒饥”,等等。这些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多通过语言上的修辞,把浓郁的情感隐藏在精巧的文字之中,融合叙事、抒情为一,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价值。而作于崇安大水期间的《苦雨用俳谐体》,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意象写作,表达了诗人的现实关怀:“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白死禾”——一位以“天道”为信仰的理学家,仰天斥责“天公”的无情;这样一幅画面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儒生对待自然、民瘼的态度和儒学作为宗教的暧昧性。
从抒情诗看,朱子诗歌中的情感显然是以“温柔敦厚”为标准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中既有未入仕时踌躇满志的《远游篇》:“举座且停酒,听我歌远游。远游何所至?咫尺视九州……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又有厌倦官场沉浮而向往清幽归隐生活的《夜坐有感》:“秋堂天气清,坐久寒露滴。幽独不自怜,兹心竟谁识?”正如论者所言,“这些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像少用那样乐天知命,心满意足,而是有所追求,有所不满,以敏感的目光关注着生命的流程”①。这当然与朱子哲学“心性论”中对已发之“情”的认识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恰恰表现出朱子不同于其他理学诗人的关键所在。
朱子抒情诗中表征隐幽情感的诗歌往往与书写山水的诗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朱子诗歌文本中极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林佳蓉称为“隐退山林的心境取向”②。从本质上讲,朱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朱子诗(尤其山水诗)是典型的文人诗。因此,朱子山水诗歌在意趣、旨归上仍脱离不了所谓隐逸、寄托、忧国、怀人等范畴。根据“陌生化”理论,极有可能造成“朱子山水诗平庸”的印象。但朱子山水诗有两点特征是平庸之作所不具备的:其一是对山水的真爱。朱子的弟子吴寿昌说:“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燕居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①。
这种对自然挚爱,当然是朱子性格因素使然,而理学家对“天道”的认识也是重要原因。其二是朱子山水诗中体现出的对自然天道的内化理解(体认),使得其诗具有宏大、悠远之气象。例如“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醉下祝融峰作》),此诗豪情堪比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再如“离离浮远树,杳杳没孤鸿。若问明朝事,西山暗霭中”(《舟中晚赋》),一派悠远淡然的景色衬托诗人的旷达心襟。
以上两点特征造就了朱子山水诗的独特魅力,故陈霆《渚山堂词话·序》云:“晦庵朱子,世大儒也,江水浸云,晚朝飞画等调,曾不讳言。”②此外,朱子抒情诗中还有对禅道老庄的欣赏,这与朱子的哲理诗关系密切。在宋代儒、释、道三教融一之后,“道”或“天道”其实成为三种宗教情感所共同崇拜的对象,只是各自突出“道”的不同属性及由此引申出的不同情感意趣。朱子一生出入佛老集中于青年与晚年时期,此类抒情诗也大多作于这段时期。早年朱子禅道诗在感情上往往透露出一种清新的真挚,而在哲理上则更多侧重说教,如《诵经》(1154):“坐厌尘累积,脱躧味幽玄。
静披笈中素,流味东华篇。朝昏一俯仰,岁月如奔川。世纷未云遣,仗此息诸缘。”类似诗歌还有《久雨斋居诵经》和《读道书作六首》(1153)等③。
而晚年的朱子禅道诗则更多流露出精神上的悲怆气息,禅理也显得更为通透而空灵,如《香茶供养黄檗长老悟公故人之塔并以小诗见意二首·其二》(1199):“一别人间万事空,他年何处却相逢。不须更话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二峰。”哲理诗是朱子诗歌中较为独特的部分,一般诗人并不写哲理诗,此即蔡模在《文公先生感兴诗注序》中所言:“不徒以诗为诗,而以理为诗。”以诗歌的形式阐释哲学或伦理学观念,这是朱子等理学家诗作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例如《斋居感兴二十首》其四云:“静观灵台妙,万化此从出。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今人张毅评价道:“这其实已不是什么诗,因摒去情感而专涉理路,无诗的美感可言,只能算是押韵的理学语录。”①事实上,所谓“美感”本是人言人殊之物,把事理用诗歌的形式加以表征,尤其是朱子意识到“情”有变“性”、转识成智的可能时,这种形式本身即具有了某种情趣,可以与读者有相应契之处,当然可以视为一种“美感”;更遑论诗歌语言本身的“陌生化”效果在形式主义之后即被公认为“文学性”的重要来源。以《斋居感兴二十首》其四为例,此诗写的人心性万妙,把说理放在了诗歌的韵律与形式之中,有设问、有隐喻,显然是为了让读者在俯仰吟诵的感兴接受中体认“心性”。这种独特的理学传播方式,不仅在于押韵,更在于朱子诗题所言的“感兴”,也就是在唤起文学情感间传递理学观念。在朱子所写的哲理诗中,《观书有感》《偶题三首》等都是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
总体而言,朱子诗歌内容丰富,但所表达的情感形式却不复杂。朱子善于把复杂的哲学以简单的情感为表现形式,再加以讲求修辞的文字为载体,从而表现出文学艺术的美。在这个意义上,清人陈〓《宋十五家诗选》“朱子诗高秀绝伦,如峨眉天半,不可攀跻。至其英华发外,又觉光风霁月,粹然有道之言,千载下可想其胸次也”②之论,并不过分。另外,值得说明的是,以上划分,感事、抒情、哲理三种文体类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界限。同一首诗,在不同学者看来,可以划入不同的文体类型之中,乃是常事:感事之中亦有浓烈的情感,抒情也往往由事而生,哲理更是贯穿在朱子诗歌创作实践的始终。但这种边界模糊的划分,仍有助于窥视朱子诗歌文本的全貌,从宏观上把握朱子诗歌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四)朱子诗歌的艺术评价历来对朱子诗歌作品褒贬不一,扬之者称“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李淦《文章精义》),贬之者讥为“有韵的哲学讲义”①。前者固然有所夸大,后者则是以偏概全的无根之论。而晚近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对朱子往往付诸阙如;中国文学理论史也多对其诗文评不著一字,这更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从艺术角度评价朱子诗歌,是当代朱子诗歌研究的重点,于此前人之述备矣。②本文特拈出三点值得特别重视之处,分述如下。
首先是朱子诗歌文风古朴、典雅,同时又蕴含着沉雄之气,具有凝练的美感。朱子早岁学习汉魏古诗,亦步亦趋地练习写作:“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③这极大地影响了朱子一生的诗歌风格,与其后推崇陶渊明、韦应物、陈师道的诗作有着必然的关系。与此同时,这种诗风与朱子在审美意趣上以阳刚、崇高为旨也有关联。朱子说:“刚健中正……阳刚自是全体,岂得不中正!”④以朱子为代表的道学派诗人雄浑而经天纬地的诗歌观,在南宋江西诗派“神头鬼面”的风气中,其实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其次是朱子诗歌视野开阔,胸次洒然,有着一般风雅诗人所不能及的高远之气。这也是朱子反复强调的:“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⑤这一说法遭到不少诗学家的反对,尤其是主情派诗学家,他们认为诗歌不应说理,而应抒情;这当然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对文学有着极为深刻认识的朱子,于此不可能不察。事实上,朱子强调诗歌说理是建立在抒情性的基础之上的。朱子在《诗集传序》中说诗歌之所以创作的缘由是:“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①这是很典型的“诗言情”论,而其又说:“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②,更直接彰显了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就其实而言,这种“诗言情”的论调并不深刻,早在汉代“诗大序”中就有相似论述。朱子超越同时代诗论之处在于,他坚持认为:“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③在这一基础上,朱子在《楚辞后语·序》中提出:“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或言“‘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④这些极其深刻的美学论断,总结了朱子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艺术品格。因此,论者言其诗云:“浑涵万有,无事模镌,自然声振,非浅学之所能窥。”⑤虽有所夸大,亦不失为正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朱子诗歌中蕴含着大量日常生活与文人雅趣相结合的文本,显示了朱子道学平易近人的一面。世人多以肃穆视朱子,而其自己也坚持“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⑥的《写照铭》作为人生准则;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也说“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⑦。但在诗歌之中,朱子的文人情趣,甚至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都一览无余;他甚至有十九首词作传世,这在当时诗歌正统极为盛行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因此,清人焦循说:“谈者多谓词不可学,以其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朱晦翁、真西山俱不废词,词何不可学之有?”⑧如果说仅有词作不足以证实朱子性格中富有情趣之意,他的纯粹笔墨游戏的回文词、嵌名诗则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朱子有《菩萨蛮》回文词两首,其一云:“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全词正逆序均可读通,诗意盎然,颇费心机。清人邹祗谟说:“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①,可以看出朱子的独特创意。此外,朱子还有五首禽言诗,模仿禽鸟啼叫之声而为的民间歌调,写出了民间生活的情趣;《九曲棹歌》十首,则以渔民歌谣风格,写出文人归隐的生命情绪;《训蒙绝句》百篇,更是以学者思想直接整合当时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这些文字形式突出的诗歌文本,为数众多,显示了朱子作为理学家的乡土气息,也淬炼出他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与前文所谓“人本”取向之间有着可资参见的形式与内容之关联。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子是一个文人气息极其浓郁的学者,他的诗人气质与生俱来。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朱子诗歌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也不仅具有以诗证史的史料价值,它还具有哲学价值。以现今朱子文学研究来看,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朱子诗歌文本进行与时俱进的、富有时代意味的美学与哲学阐释,还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分析和思考。而于此可以尝试回答的是,本节开篇提出的一个疑问。
(五)理学家轻视文学吗?宋代理学家虽以心性为务,但其视“理”于心外,而与所谓“心学家”产生分野。这一状况造成了“理学家视文艺为末流”的说法,成为一时之“公论”。在中国学界,讨论宋代文论者多把视野的核心聚焦在欧阳修、江西诗派、《沧浪诗话》等问题上。晚近以来影响较大的若干部教材,莫不如是。①相比之下,理学家的文论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可有可无的陪衬或点缀。
这不仅与文学实践史上如朱子等人“以诗名”的状况不符,也未必符合中国文论发展的实际状况。宋代以降,占据中国文学理论主潮的,恐怕不是严羽等处于文坛边缘评论家——同为闽北人的严羽,连一部起码的传记都没有留下。在理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之后(宋、元),中国文论的发展其实是以理学标准为框架的;可是,这在当代中国文论教材中很难寻觅到论述的笔墨。中国文论的历史书写,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理论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对宋代理学的“刻板印象”与文学概念既定模式的生硬运用。此处所言的“刻板印象”,是指“理学家轻视文艺”已成为中国文论史的定论。这种简明扼要的“结论”式命题,把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处理;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即理学美学或理学文学得到的关注极其之少——就文论系统的研究成果而言,宋代理学文论显不及其他朝代或同代其他流派的研究之繁荣;就理学系统的研究而言,理学文论又不及其他学科领域,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成果显著。
具体到朱子身上,据林庆彰和莫砺锋的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际学界关于朱子的研究著述达2254种,而文学研究不过寥寥三四十种。②就文学概念既定模式的裁剪作用而言,不同时代对“什么是文学”或“什么是文论”问题的回答,乃是确立其时文学、文论史书写基本范式的关键。与中国古代“诗言志”和“诗缘情”并举的状况不同①,当代中国文学经历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话语“洗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形成了以个人抒情对抗宏大叙事的先锋文学传统。在这套话语体系中,“文学”的价值天平倾向着“表现说”的立场,加之西方传入的形式意识,各种实验文学纷纷登台。用这种“文学”概念来裁剪文学实践,必然有因不符合“抒情”或“语言形式”要求而被淘汰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观念——理学家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便是典型。
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编撰才更多把严羽等在历史语境中并不显赫的人物作为一代文学精神的高标——这在后人的评价体系中当然不成问题,但如果将其视为历史真实的书写,则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
“理学家轻视文学”的论断其来有自,将其视为一种“刻板印象”并不是要推翻它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从历史来看,“理学家轻视文(学)”有着充足的论据。自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始,“重道轻文”就是典型之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②此外,二程、邵雍、张栻等人都有过相关类似的论述,兹不多举。
但问题在于,周敦颐这段已被无数次引用的话语之“文”,实乃与今日之所说“文学”不是一回事。在周子的运用中,“文”主要是统指能够承担道德意义的文字组织形式,即“文字”,虽然它包括作为“艺”的“文辞”,但“文辞”是不是就等于“文学”,恐怕还难以下定论。“文”之多义,需从其源头说起。
“文”或“文学”在中国古代起源于笔画符号。《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①,指的乃是自然界的斑纹或人工图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最多不过是“有文采的文字组织”而已。然而,这种代表着“美”的文字形态,在中国却有着相当深厚的民间崇拜传统。尤其在道教因素参与下,“文字”竟成了“随运开度,普成天地之功”的基本法则②。故《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③就此来说,周敦颐所言的“文辞”者,所指大抵是“文字”;周敦颐所说的“文以载道”,其实乃是“文章载道”或“文字载道”,而非“文学载道”。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周敦颐这番话语的针对对象是那些对“文字”的魔力有着过分崇拜的士子④,而非善于以文抒情的文人。
一般认为,“文字”之为“文学”,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其一是“文学”讲求文采,善于运用隐喻、反讽、悖论、朦胧等修辞形式对文字的组合加以变形,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⑤其二是“文学”讲求情感,要求在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活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⑥这二者的结合,便是本节前文所言的“话语蕴藉”,也就是“文学”应该在文字的字面意思之外,含有更为深刻的有待读者加以理解和阐释的意义,特别是需要加以体会的情感。而作为理学家口号的“文以载道”恰恰是要求文章作品在其字面意思之外必须有更深层次的“道”的要求,“道”蕴藉、隐藏在“文”之中,并借助“文”而进入读者的内心深处,呼唤起深远的回音——“美则爱,爱则传焉”。如果用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加以阐释,可以说无论是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还是程颐的“作文害道”,或者朱子的“道本文枝”,其根本反对的乃是“以辞害意”,而非“以情害意”。故程颐云:“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①说到这里,道理已经毕现,即“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刻板印象来自于今人对“文学”在中国古代语境中的误读,“理学家轻视”的“文学”是讲求文采的“文”(辞),而非“话语蕴藉”。不过,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理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却还有更深一层的复杂性。他们虽然不普遍反对一切文字组合形式,但对其所表之情感却有特殊的要求。文学作品表达情感,作者的情感能够通过文学阅读传达给接受者,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被称为“感兴”。文学具有鼓动性情的“感兴”作用,接受者有可能被文学文本所表达的情感牵引而丧失主体性意识,这正是理学家们所担忧的。但这一功效是可以反作用的,亦即是通过文学文本传递“正确”的情感,来引导读者挺拔其高度自觉的自我主体性。从朱子诗歌题目多次出现“感兴”二字——如前文所引《斋居感兴》多首,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理学诗人对此是有着高度自觉的。
邵雍说:“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这似乎可以视为理学家视文学为洪水猛兽,惟恐“以情害意”的证据。但邵雍笔锋一转,“古者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覆载在水也,不在人也;载则为利,覆则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②这就是说,“情之溺人”的关键在于所“溺”之“情”的性质;倘使主体能够“以物观物”“情累都忘”,则所留之“诗”便有益于“天下大义”;于是,个人的主体性不是丧失,而是得到了升华。这一点在周敦颐、二程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曰:“《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①可以说,“文学”的两重特性(文采、情感)在理学家那里都不是清晰可辨的。这不仅增加了后人对理学家文艺观理解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理学家自身的矛盾人格。而“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刻板印象在文学史对朱子的评价上,尤为明显。本节所述今人的朱子文学研究之弱便是明证。今以朱子诗歌创作为例,加上上文的理论澄清,或可破除“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于万一。不过,也如前文所言,“理学家轻视文学”这一论断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需要将既定的刻板印象引入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才有可能使其从内部得以破解。诗歌(文学)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艺术。理学家重视后者尤胜前者。对此,朱子有着高度的自觉。于此可以再举一例。朱子虽也有“游戏文字”,但从其创作大量诗歌的题目来看,他并不重视文字(文辞)。与一般诗人篇目的用心不同,朱子诗歌的题目很多是在叙事,交代作诗的前因后果,文字多得令人称奇。
仅举两例,如《丁丑冬在温陵陪敦宗李丈与一二道人同和东坡惠州梅花诗皆一再往反昨日见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再和一篇呈诸友兄一笑同赋》与《昨承诸兄临辱不揆以薄酒蔬食延驻都骑明日视壁间所张墨刻有亡去者人以为德庆丈之庾也驰问遣索蒙需拙诗辄赋所怀往奉一笑而尊犍刻可以归于我矣》1其诗歌的内容都没有其题目长。这恰说明朱子重视的是诗歌的内容,亦即是其传递的情感,如“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之感;而非文字堆砌的巧妙与所谓“艺术”。同样以此二例,还值得一说的是诗名中都有“一笑”两字,这在一千多首朱子诗中,并非仅见,但却多于长诗名之中。再如《去岁蒙学古分惠兰花清赏既歇复以根业归之故——而学古预有今岁之约近闻颇已著花辄赋小诗以寻前约幸一笑》《宋丈示及红梅腊梅借韵两诗辄复和呈以发一笑》《圭父约为金斗之游次韵献疑聊发一笑》《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诸名胜为落星之游分韵得往字率尔赋呈聊发一笑》《读十二辰诗卷掇其余作此聊奉一笑》等。这些处处可见的“一笑”,足可说明朱子对诗歌文字的不在意,而其“一笑”之作多见于“分韵”(赋韵)文字,更可见文字技法在朱子那里不过是点缀而已。
于此可以说明的是,理学家轻视文学,其意主要在于轻视文学之技法(文辞),而警惕文学之情感偏向,乃是理学之本,非仅文学受累,举凡释家、道家莫不在其警惕的范围之内。因此,笼统说“理学家轻视文学”,实则是一种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今人出于自我对“文学”概念理解的误读。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子,不但不轻视文学,更亲身实践,热衷文学创作。如果不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理解朱子,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朱子之后的理学文论)将无法得到深入的阐释,而浮于“理学家轻视文学”或“理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矛盾的”等论断的表面,更无助于将问题引向历史的深处。朱子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文本是复杂的,对其进行阐释也有多种角度,但无论如何,轻率的刻板的判断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作为诠释主体的朱子本人之态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性情、理想、志业、感兴等生命价值观,是必须给予充分考虑的。
附注
①关于朱子存诗的篇目数几乎无法统计,除了《朱文公文集》第一至第十卷收入诗歌1203首外,《别集》《遗集》《外集》中尚有若干篇,而这些篇目中相互重叠者又有不少;遑论散见于各地方志、宗族族谱等文献中的朱子诗。而就确定的篇目来看,依据常见文献《朱子大全》与《朱熹集》,朱子存诗当有1413首;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主要选自这一范围,并适当参考业已经过专家确定的朱子佚文诗篇。参见林佳蓉:《承担与自在之间——从朱熹的诗歌论其生命趋向的依违》,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5—8页;确定的朱子佚文诗篇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第239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第3333页。
③〔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朱文公论诗》,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页。
①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383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南岳游山后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05页。
①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页。
②根据童庆炳等人的意见,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话语蕴藉”,即“文学活动的蕴蓄深厚而又余味深长的语言与意义状况”。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①Roland Barthes,The pleasure of the text,Oxford:Blackwell 1990,p15.②蔡厚示:《诗词拾翠》(叁集),东京名家社2003年版,第127—138页;杨国学主编:《武夷文学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88页。
③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第4—10页。
①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
②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77年12年31日第一版。
③郭齐:《论朱熹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④朱子思想成熟的阶段划分,主要参考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20页。
②束景南:《朱子大传》,第128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1页。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第383页。
②束景南:《朱子大传》,第471页。
①〔宋〕朱熹撰,郭齐笺注:《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700—701页。
①申美子:《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
②朱杰人:《朱子诗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③郭齐:《论朱熹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①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②林佳蓉:《承担与自在之间——从朱熹的诗歌论其生命趋向的依违》,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296—318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七《朱子四·内任》,第2674页。
②〔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朱熹撰,郭齐笺注:《朱熹诗词编年笺注》,第41页。
①张毅:《苏轼与朱熹》,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②〔清〕陈〓:《宋十五家诗选·朱熹》,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参见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1—2页。
②朱杰人:《朱子诗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郭齐:《论朱熹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等。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01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九《易五·乾下》,第1730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07页。
①〔宋〕朱熹集撰:《诗集传·序》,赵长征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第3333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杨宋卿》,《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28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巩仲至》,《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97页。
⑤〔清〕吴之振:《宋诗钞》卷六十《朱子文公集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写照铭》,《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95页。
⑦〔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61页。
⑧〔清〕焦循:《雕菰楼词话》,清道光刻本。
①〔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如李壮鹰、李春青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春青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其中这些教材中均会论述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而它恰恰是被认为彻底反理学美学的一种诗论话语系统。换言之,中国学者对“美学”或“诗学”的概念仍然是以表现论或抒情论为主导,理学文论被视为“伦理本位”倾向,心性与情感在今人的论述中成为水火不容的两种态度。见李壮鹰、李春青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257页。
②参见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1—2页。
①“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表示诗歌是言说诗人的志向的;“诗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表示诗歌是抒发诗人的情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言志”与“缘情”长期存在着对立。
②〔宋〕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通书·文辞第二十八》,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36页。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13页。
②〔宋〕张君房:《云笈七笺》卷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1页。
③〔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自唐以来,中国科举设“辞赋”,以文名天下而加官晋爵者,十分普遍。这在社会整体风气上引导了当时的氛围,民间对文字的崇拜与巫术、祈祷、社团等宗教类现象相交织,形成一时风气。参见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270页。
⑤参见(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23页。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第239页。
②〔宋〕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三《二先生语三》,《二程集》,第59页。事实上,周敦颐的《爱莲说》和二程的一些诗作(如程颢的《秋日》、程颐的《春日偶成》等),表现了符合儒家中和思想的情感,至今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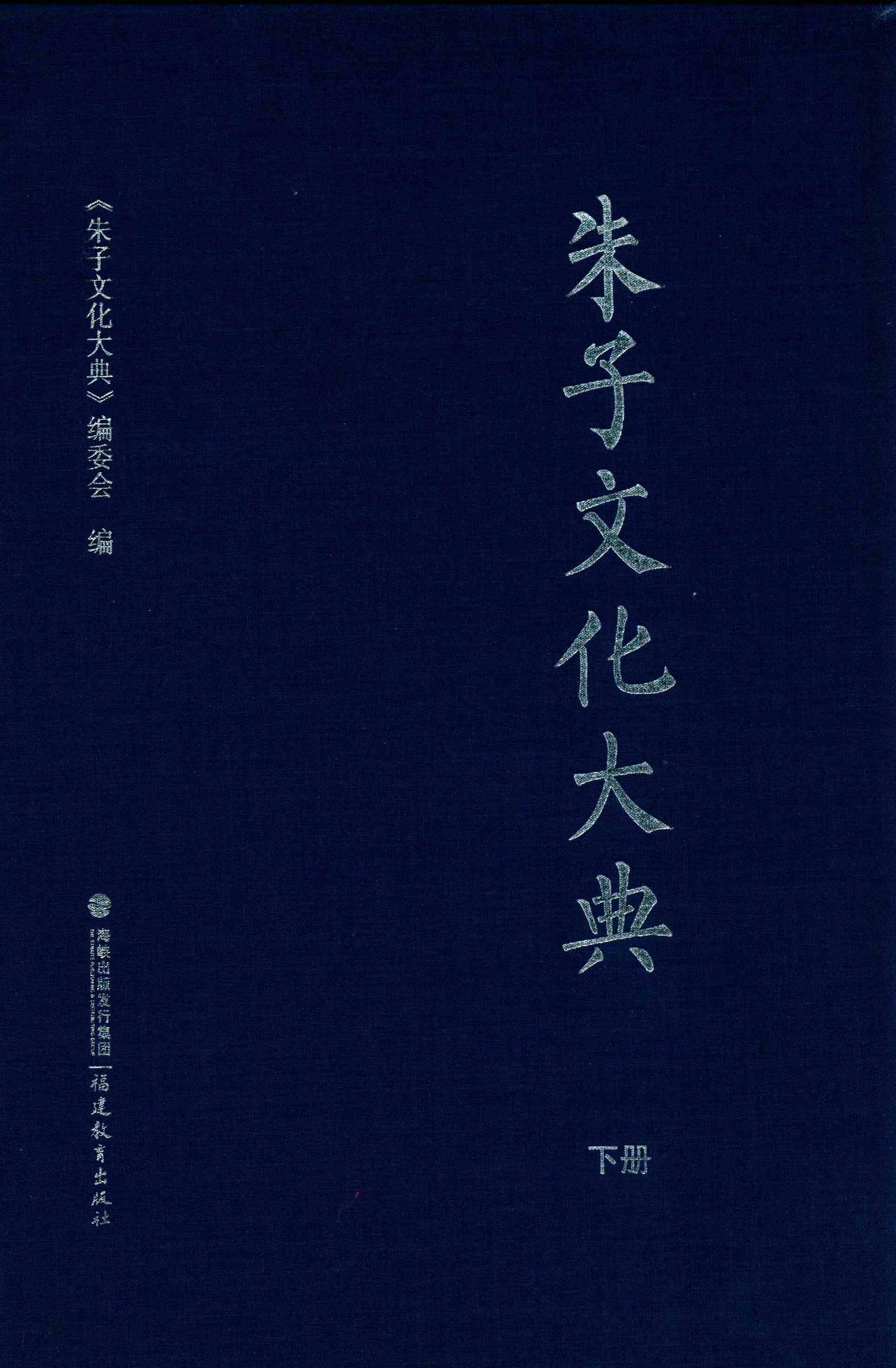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介绍朱子生平,包括家世、从学、讲学、论道、政绩等内容。中册阐述朱子文化源流,包括朱子理学形成的历史背景、朱子的理学思想、朱子的经学思想、朱子的教育思想等内容。下册着重介绍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