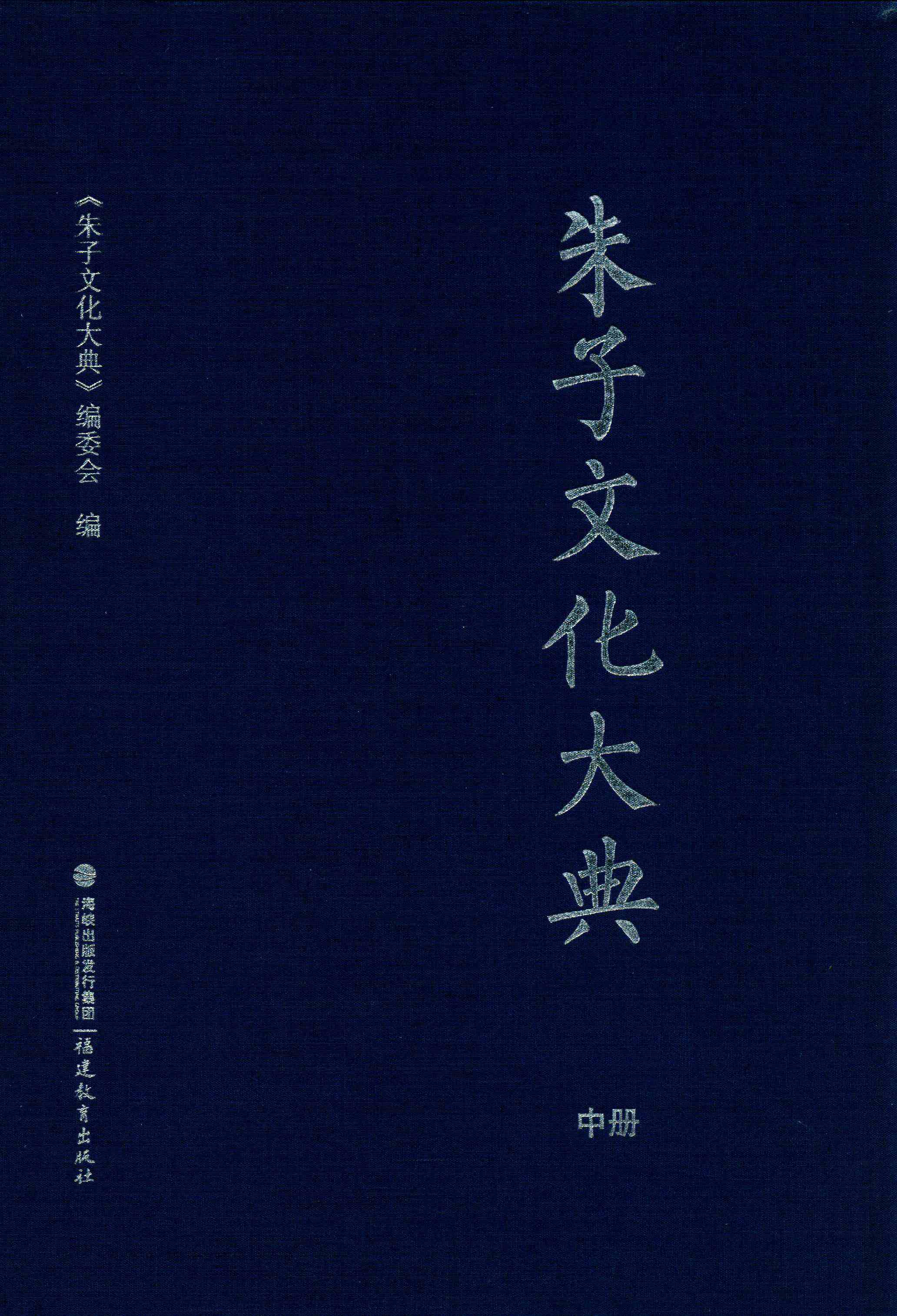(二)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相结合
| 内容出处: | 《朱子文化大典 中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0711 |
| 颗粒名称: | (二)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相结合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4 |
| 页码: | 91-94 |
| 摘要: | 在朱子经学思想体系里,当经文本义在阐发义理时,朱子求经文本义与其以义理解经具有统一性;当经文本义不在直接阐发义理时,朱子求经文本义与其以义理解经具有二重性。前者表现为治“四书”,后者表现为治“六经”。这与其经传相分又相合的思想相关联,体现了朱子经学与理学的结合,亦是为阐发义理作论证。如上所论,朱子在治《易》《诗》《礼》诸经方面,把探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之上。既重视原典,以符合圣人作经之本意;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义理解说之。 |
| 关键词: | 朱熹 经学思想 经文 |
内容
在朱子经学思想体系里,当经文本义在阐发义理时,朱子求经文本义与其以义理解经具有统一性;当经文本义不在直接阐发义理时,朱子求经文本义与其以义理解经具有二重性。前者表现为治“四书”,后者表现为治“六经”。因其具有一定的二重性,朱子又强调在区分本义与推说义的前提下,把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这与其经传相分又相合的思想相关联,体现了朱子经学与理学的结合,亦是为阐发义理作论证。
朱子经学虽以“四书”为“六经”之基础,但朱子在“四书”学这个基础上,仍对“六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述,在不少方面对诸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朱子既注意探求经文之本义,又重在以义理解经;既不仅仅停留在探求本义的阶段,又不以推说之义理取代经文之本义,而是把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所阐发之义理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这体现了朱子经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治“六经”上,朱子既不是单纯求本义,亦不是单纯讲义理,而是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以本义推说义理,以义理解说经文。在治《周易》方面,朱子首先指出《易经》的本义为占卜,批评易学之义理学派只重义理的发挥,轻视以至不讲《易》的占卜本义的偏向,主张经传相分;同时又提出在分别经传,明确《易》之本义为卜筮的前提下,把经传结合起来,以义理解经,在卜筮本义的基础上,通过象数阐发义理。他说:“《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圣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便以义理说出来。”①朱子大致把易学的发展分为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两个阶段,前者以《易经》的产生和形成为主,包括伏羲之图、象,文王、周公之辞等;后者以《易传》的产生和发展为主,包括孔子赞《易》,作十翼,教之以义理,以及伊川《易传》以义理说《易》等。朱子又主张把卜筮和义理两个阶段统一起来,把象数学与义理学相结合,统一于一以贯之之《易》道。具体表现在朱子以义理解《易》,主张在掌握本义的前提下以传释经,推说义理,以义理沟通经传,通过占卜之辞,即象以求理。他说:“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①理的获得,须建立在《易》之图、象、数、卜筮的基础上,如朱子依据《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以及周敦颐、邵雍之图书象数学,阐发其作为易学纲领的太极说,“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②。又在其太极说的基础上,阐发其哲学、理学思想。可见朱子的哲学、理学离不开其易学等经学思想,而朱子的易学又是其本义说与义理说相结合的统一体和产物。
在治《诗经》学方面,亦体现了朱子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相结合的经学特色。一方面,朱子突出一个“情”字,指出诗人作《诗》,其本意自在“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之间,另在《诗》三百篇中,有部分淫奔之诗,其本义为淫佚之情;另一方面,朱子又以义理解《诗》,主张于讽诵中见义理,并以道德理性谴责淫乱之情,表现出其《诗》学与理学的结合。朱子在探明《诗》文之本义的前提下以义理解《诗》,主要表现在重视《诗》之“二南”、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和以天理论注解《诗》之雅、颂上。
朱子以《周南》《召南》作为其整个《诗经》学的根本,认为一部《诗经》唯有在“二南”之中最能反映文王之治美好的风俗,而风俗之盛则是理义的表现。他从“二南”之诗的实际描写出发,加以义理化归纳和解说,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强调得其性情之正,以为诗学之本。虽然包括“二南”在内的整个《诗经》充满了自然的情爱描写,朱子也客观地承认《诗》“发乎情”,但朱子对一部“发乎情”的《诗经》,从“二南”入手,建立起以义理解《诗》的体系,来作为解整部《诗》的典范和指导思想。凡符合义理的,朱子便加以肯定和赞美,以为后世之法;凡不合义理的,则加以贬斥,直视为淫奔之诗,以为后世之戒。在朱子看来,“二南”之诗虽有关于情性的自然描写,但由于“二南”被文王之化,其后妃、夫人、女子等虽发乎情,却能够守之以礼义,故能得性情之正,而与放纵情感不同。故朱子要求“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①。强调以义理解《诗》,颐养性情,以为诗学之本。
关于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朱子于变风的郑卫之诗中,找出二十多篇淫奔之诗,批评其不合于义理的男女之情。如他注《风雨》篇云:“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②指出《静女》篇为“淫奔期会之诗”③,《遵大路》篇是讲“淫妇为人所弃”④。而在《桑中》篇的注解里,朱子批判了“卫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窃妻妾”⑤的诗文描写。朱子在解《诗》中,以理学之义理为标准,对男女之情持严谨态度,既适当地肯定合乎礼义的男女之情,更对不合礼义的男女自然之情爱及贵族“相窃妻妾”的淫乱行为提出批判,这是朱子以义理解《诗》的表现。
在治《礼》书方面,朱子以《仪礼》为经,为本,为事;以《礼记》为传,为末,为理,认为理是后起的。既强调《仪礼》与《礼记》的经传、本末、事理之分,又重视二者的结合,把理安著在《仪礼》所载之事中,即理的阐发须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天理通过具体的礼仪之事表现出来。从而把经学与理学相结合。朱子指出:“《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乃其义说耳。”⑥作为本经的《仪礼》讲的是“仪法度数”,即具体的礼仪之事,这即是《仪礼》的本义;而作为传文的《礼记》则是言理之书,通过对礼仪之事的解说,以发明义理。这与其《周易》经传的区分类似。他说:“《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顿处。”①朱子继承二程,将《大学》《中庸》两篇说理之书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列入“四书”,予以高度重视。但他又认为,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礼记》所发明的理,不得脱离《仪礼》所载洒扫应对进退饮食居处的具体仪节之事而孤立存在,否则《礼记》所发明的理便无安顿处。也就是说,理体现在具体的仪节事物中,凡行事合乎礼,这即是理。从而把理与事、义理与本义结合起来。
如上所论,朱子在治《易》《诗》《礼》诸经方面,把探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之上。既重视原典,以符合圣人作经之本意;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义理解说之。在注经的形式下,把继承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为发明义理作论证。这不仅体现了朱子经学的一个特点,亦是中国经学发展的一种形式和表现。
朱子经学虽以“四书”为“六经”之基础,但朱子在“四书”学这个基础上,仍对“六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述,在不少方面对诸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朱子既注意探求经文之本义,又重在以义理解经;既不仅仅停留在探求本义的阶段,又不以推说之义理取代经文之本义,而是把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所阐发之义理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这体现了朱子经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治“六经”上,朱子既不是单纯求本义,亦不是单纯讲义理,而是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以本义推说义理,以义理解说经文。在治《周易》方面,朱子首先指出《易经》的本义为占卜,批评易学之义理学派只重义理的发挥,轻视以至不讲《易》的占卜本义的偏向,主张经传相分;同时又提出在分别经传,明确《易》之本义为卜筮的前提下,把经传结合起来,以义理解经,在卜筮本义的基础上,通过象数阐发义理。他说:“《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圣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便以义理说出来。”①朱子大致把易学的发展分为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两个阶段,前者以《易经》的产生和形成为主,包括伏羲之图、象,文王、周公之辞等;后者以《易传》的产生和发展为主,包括孔子赞《易》,作十翼,教之以义理,以及伊川《易传》以义理说《易》等。朱子又主张把卜筮和义理两个阶段统一起来,把象数学与义理学相结合,统一于一以贯之之《易》道。具体表现在朱子以义理解《易》,主张在掌握本义的前提下以传释经,推说义理,以义理沟通经传,通过占卜之辞,即象以求理。他说:“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①理的获得,须建立在《易》之图、象、数、卜筮的基础上,如朱子依据《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以及周敦颐、邵雍之图书象数学,阐发其作为易学纲领的太极说,“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②。又在其太极说的基础上,阐发其哲学、理学思想。可见朱子的哲学、理学离不开其易学等经学思想,而朱子的易学又是其本义说与义理说相结合的统一体和产物。
在治《诗经》学方面,亦体现了朱子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相结合的经学特色。一方面,朱子突出一个“情”字,指出诗人作《诗》,其本意自在“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之间,另在《诗》三百篇中,有部分淫奔之诗,其本义为淫佚之情;另一方面,朱子又以义理解《诗》,主张于讽诵中见义理,并以道德理性谴责淫乱之情,表现出其《诗》学与理学的结合。朱子在探明《诗》文之本义的前提下以义理解《诗》,主要表现在重视《诗》之“二南”、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和以天理论注解《诗》之雅、颂上。
朱子以《周南》《召南》作为其整个《诗经》学的根本,认为一部《诗经》唯有在“二南”之中最能反映文王之治美好的风俗,而风俗之盛则是理义的表现。他从“二南”之诗的实际描写出发,加以义理化归纳和解说,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强调得其性情之正,以为诗学之本。虽然包括“二南”在内的整个《诗经》充满了自然的情爱描写,朱子也客观地承认《诗》“发乎情”,但朱子对一部“发乎情”的《诗经》,从“二南”入手,建立起以义理解《诗》的体系,来作为解整部《诗》的典范和指导思想。凡符合义理的,朱子便加以肯定和赞美,以为后世之法;凡不合义理的,则加以贬斥,直视为淫奔之诗,以为后世之戒。在朱子看来,“二南”之诗虽有关于情性的自然描写,但由于“二南”被文王之化,其后妃、夫人、女子等虽发乎情,却能够守之以礼义,故能得性情之正,而与放纵情感不同。故朱子要求“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①。强调以义理解《诗》,颐养性情,以为诗学之本。
关于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朱子于变风的郑卫之诗中,找出二十多篇淫奔之诗,批评其不合于义理的男女之情。如他注《风雨》篇云:“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②指出《静女》篇为“淫奔期会之诗”③,《遵大路》篇是讲“淫妇为人所弃”④。而在《桑中》篇的注解里,朱子批判了“卫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窃妻妾”⑤的诗文描写。朱子在解《诗》中,以理学之义理为标准,对男女之情持严谨态度,既适当地肯定合乎礼义的男女之情,更对不合礼义的男女自然之情爱及贵族“相窃妻妾”的淫乱行为提出批判,这是朱子以义理解《诗》的表现。
在治《礼》书方面,朱子以《仪礼》为经,为本,为事;以《礼记》为传,为末,为理,认为理是后起的。既强调《仪礼》与《礼记》的经传、本末、事理之分,又重视二者的结合,把理安著在《仪礼》所载之事中,即理的阐发须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天理通过具体的礼仪之事表现出来。从而把经学与理学相结合。朱子指出:“《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乃其义说耳。”⑥作为本经的《仪礼》讲的是“仪法度数”,即具体的礼仪之事,这即是《仪礼》的本义;而作为传文的《礼记》则是言理之书,通过对礼仪之事的解说,以发明义理。这与其《周易》经传的区分类似。他说:“《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顿处。”①朱子继承二程,将《大学》《中庸》两篇说理之书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列入“四书”,予以高度重视。但他又认为,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礼记》所发明的理,不得脱离《仪礼》所载洒扫应对进退饮食居处的具体仪节之事而孤立存在,否则《礼记》所发明的理便无安顿处。也就是说,理体现在具体的仪节事物中,凡行事合乎礼,这即是理。从而把理与事、义理与本义结合起来。
如上所论,朱子在治《易》《诗》《礼》诸经方面,把探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之上。既重视原典,以符合圣人作经之本意;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义理解说之。在注经的形式下,把继承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为发明义理作论证。这不仅体现了朱子经学的一个特点,亦是中国经学发展的一种形式和表现。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