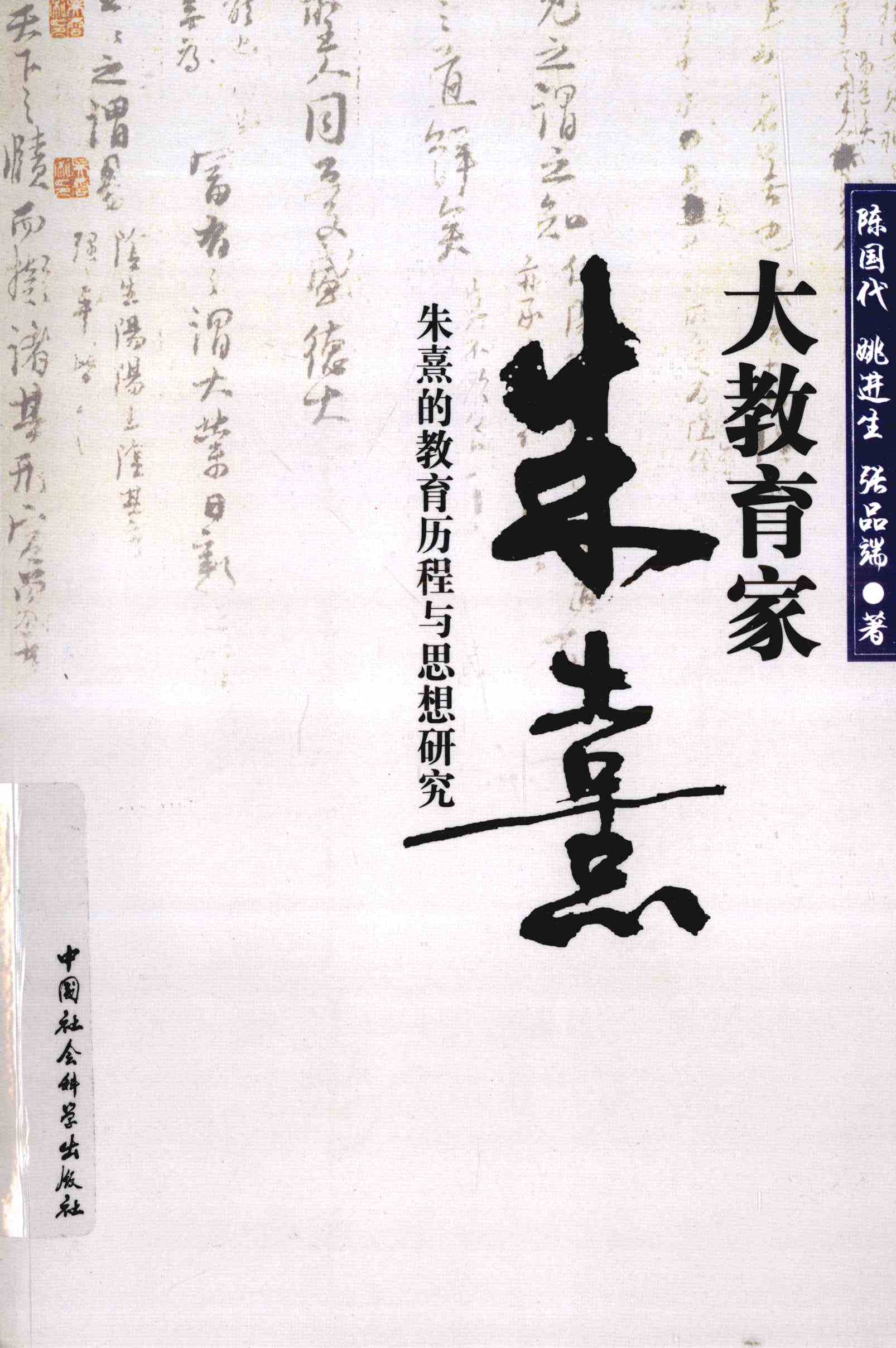朱熹的教育与影响
| 内容出处: | 《大教育教朱熹》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0108 |
| 颗粒名称: | 朱熹的教育与影响 |
| 分类号: | G40-09;B244.7 |
| 页数: | 5 |
| 页码: | 230-234 |
| 摘要: | 朱熹一生两次入湘来到潭州,其重道德教化也与此密切关联。朱熹与张栻之会,相与讲释所疑,以明千年道学,以扶纲常,以正人心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岳麓与城南仅一河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两岸。据随行入湘的范念德讲,朱熹和张栻讨论得十分热烈, “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即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却坚持讨论,以求达成共识。朱熹在长沙编成《州县释奠仪图》,其后由邵囦于长沙郡斋刻印,同时刻印的还有《三家礼范》、《稽古录》、《诗集传》,作为整顿士风学风的基本读物,希望通过“礼”的力量,用三纲五常来拯救世风、使人性复善。 |
| 关键词: | 朱熹 教育 潭州 |
内容
朱熹一生两次入湘来到潭州,其重道德教化也与此密切关联。
第一次是在乾道三年八月(1167年)访张栻,在事先与吕祖谦商量后,由刘珙、张孝祥作了安排,主教张栻、守臣张孝祥为朱熹的到来和讲学活动提供良好条件。八月中旬,朱熹携门生林择之、范念德赴潭州,于九月八日到达长沙,住在张栻的城南书院的南轩,朱熹与张栻往返于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之间,就此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的学问交流。朱熹与张栻之会,相与讲释所疑,以明千年道学,以扶纲常,以正人心的总目标是一致的。“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这次入湘,也是朱熹与湖湘众学者进行广泛交流的好机会,与此同时,朱熹发现“岳麓学者未知向方,往往骋空言而远实理”,主教于岳麓书院的张栻显然失责。 朱熹与各地学者不断进行交流、论辩,这也可以看成是其学问修正与扩容的过程。朱熹所建立的闽学,与胡氏、张氏师徒所建立的湖湘学,都源自北宋二程所建立的洛学,基本倾向相同,张栻是继胡安国、胡宏之后的湖湘学派的领军人物,与朱熹的交情很深,常有书信往来,探讨理学的基本问题,且有许多共识。
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两个月,理学界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而展开。朱、张对“中和”、“太极”、“仁”等一系列理学问题,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张栻的城南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岳麓与城南仅一河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两岸。据随行入湘的范念德讲,朱熹和张栻讨论得十分热烈, “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即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却坚持讨论,以求达成共识。朱熹在给程洵的信中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往左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 据清康熙《岳麓志》记载,朱熹到长沙访南轩,讲学岳麓,其内容是孟子学说,目的是“以致克己求仁之功”,两人又论《中庸》要义有一月,朱熹亲书“忠孝廉节”四大字于讲堂。朱熹上岳麓,是否登坛为诸生讲授,开讲的内容是什么,王懋竑以为于朱子《朱子全书》、《朱子语类》无考,而陈荣捷则作合理推测,朱熹会在书院里讲学。书院会讲制度的确立,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会讲”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体现了书院内“百家争鸣”的特色。会讲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辨析异同,推动了书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研究和教学的结合。朱张会讲开辟了理学中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和融合,也对后来岳麓书院的学术发展和教学活动起了推动作用。朱熹在潭州的首次讲学活动时间虽短,但朱张会讲激发了湖湘学的迅速传播,并使湖南教育中心由衡山向北转移到了长沙岳麓。
朱熹在潭州的第二次讲学活动是从绍熙五年的五月开始的。朱熹到长沙后,竟发现昔日讲学之地的繁盛已不复存在,“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这是湖湘学派领袖人物张栻过早离开人世、新的领军人物尚未树立起来的后果。朱熹“深以讲学教人之务为寄”,因此,在从政的同时仍重视教育,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分内的重要任务来抓,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教育事业,决意兴复岳麓书院和倡修湘西精舍,并亲自登台讲授,培养士子。朱熹对建设和发展书院及州学、活跃湖湘学风、确立会讲制度以及授业生徒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熹在《潭州到任谢表》中写道:“学兼岳麓,壤带洞庭,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他在潭州的教育活动,主要体现在整顿岳麓书院、增置学田、揭示学规和亲自讲授等方面。
朱熹在任上颁有《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由此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士风和建设书院。其一是聘请黎贵臣充任书院讲书职事,又聘郑一之为学录,掌管学规和辅助教授。其二是增加生员名额,扩大招收名额至四十八名,可以不由课试而进,其廪给予郡庠相等。把书院作为“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其三是更建位于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该书院,乾道初曾由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有的房屋三十年来因故久圮,朱熹选择地势高而干燥的地方作为建筑地,决定进行大规模修复、扩建书院房屋以容纳更多的学生。其四是解决书院的经费问题,为岳麓书院置学田五十顷。经过朱熹的有效治理和严厉督促,岳麓书院很快得以复兴。朱熹在离任时,又托继任者王蔺修复与岳麓书院关系紧密的湘西书院。 朱熹兴学,对书院教育影响最大的是颁行《书院教条》。这个学规还是朱熹在淳熙间任南康知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学规中,朱熹明确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总方针是实施以“五教”为主要内容的五伦——伦理教育,强调了书院教育必须为社会伦理服务的前提。以此明确学者到书院来是为何而学、为谁而学,规范生徒行为,唤醒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学规反复要求生徒讲明义理,修养心性,力图体现其理学教育的根本特点。学规进而提出修身、处世、接物之要,作为生徒实际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准绳。其中所包含的重人格教育、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学风。朱熹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实际上指示了书院教学的全部过程。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意欲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书院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特色,都与这个“为学之序”密切相关。
朱熹知潭州时,“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朱熹,把《四书集注》作为岳麓书院的主要教材,始终坚持亲自执教,讲论重点集中于读书之须涵泳,须要浃洽。据廖谦记载,朱熹不仅经常在寓所向来访的学生授课,而且还亲自到岳麓书院督课,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一次,朱熹到书院后,采取抽签的方式让两位学生讲《大学》的语意,被抽查的学生都讲不清楚。朱熹便对诸生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并指出书院如果不如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建书院,在书院读书就是要读懂圣贤教人的道理,而不要模仿官学追求科举考试死读书、死背时文,要学子理会学问,“不理会学问,与蚩蚩横目之氓何异!”朱熹严肃认真、周到恳恻的教育作风,对学生的思想、学术都影响至深。
朱熹在长沙编成《州县释奠仪图》,其后由邵囦于长沙郡斋刻印,同时刻印的还有《三家礼范》、《稽古录》、《诗集传》,作为整顿士风学风的基本读物,希望通过“礼”的力量,用三纲五常来拯救世风、使人性复善。
第一次是在乾道三年八月(1167年)访张栻,在事先与吕祖谦商量后,由刘珙、张孝祥作了安排,主教张栻、守臣张孝祥为朱熹的到来和讲学活动提供良好条件。八月中旬,朱熹携门生林择之、范念德赴潭州,于九月八日到达长沙,住在张栻的城南书院的南轩,朱熹与张栻往返于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之间,就此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的学问交流。朱熹与张栻之会,相与讲释所疑,以明千年道学,以扶纲常,以正人心的总目标是一致的。“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这次入湘,也是朱熹与湖湘众学者进行广泛交流的好机会,与此同时,朱熹发现“岳麓学者未知向方,往往骋空言而远实理”,主教于岳麓书院的张栻显然失责。 朱熹与各地学者不断进行交流、论辩,这也可以看成是其学问修正与扩容的过程。朱熹所建立的闽学,与胡氏、张氏师徒所建立的湖湘学,都源自北宋二程所建立的洛学,基本倾向相同,张栻是继胡安国、胡宏之后的湖湘学派的领军人物,与朱熹的交情很深,常有书信往来,探讨理学的基本问题,且有许多共识。
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两个月,理学界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而展开。朱、张对“中和”、“太极”、“仁”等一系列理学问题,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张栻的城南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岳麓与城南仅一河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两岸。据随行入湘的范念德讲,朱熹和张栻讨论得十分热烈, “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即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却坚持讨论,以求达成共识。朱熹在给程洵的信中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往左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 据清康熙《岳麓志》记载,朱熹到长沙访南轩,讲学岳麓,其内容是孟子学说,目的是“以致克己求仁之功”,两人又论《中庸》要义有一月,朱熹亲书“忠孝廉节”四大字于讲堂。朱熹上岳麓,是否登坛为诸生讲授,开讲的内容是什么,王懋竑以为于朱子《朱子全书》、《朱子语类》无考,而陈荣捷则作合理推测,朱熹会在书院里讲学。书院会讲制度的确立,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会讲”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体现了书院内“百家争鸣”的特色。会讲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辨析异同,推动了书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研究和教学的结合。朱张会讲开辟了理学中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和融合,也对后来岳麓书院的学术发展和教学活动起了推动作用。朱熹在潭州的首次讲学活动时间虽短,但朱张会讲激发了湖湘学的迅速传播,并使湖南教育中心由衡山向北转移到了长沙岳麓。
朱熹在潭州的第二次讲学活动是从绍熙五年的五月开始的。朱熹到长沙后,竟发现昔日讲学之地的繁盛已不复存在,“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这是湖湘学派领袖人物张栻过早离开人世、新的领军人物尚未树立起来的后果。朱熹“深以讲学教人之务为寄”,因此,在从政的同时仍重视教育,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分内的重要任务来抓,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教育事业,决意兴复岳麓书院和倡修湘西精舍,并亲自登台讲授,培养士子。朱熹对建设和发展书院及州学、活跃湖湘学风、确立会讲制度以及授业生徒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熹在《潭州到任谢表》中写道:“学兼岳麓,壤带洞庭,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他在潭州的教育活动,主要体现在整顿岳麓书院、增置学田、揭示学规和亲自讲授等方面。
朱熹在任上颁有《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由此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士风和建设书院。其一是聘请黎贵臣充任书院讲书职事,又聘郑一之为学录,掌管学规和辅助教授。其二是增加生员名额,扩大招收名额至四十八名,可以不由课试而进,其廪给予郡庠相等。把书院作为“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其三是更建位于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该书院,乾道初曾由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有的房屋三十年来因故久圮,朱熹选择地势高而干燥的地方作为建筑地,决定进行大规模修复、扩建书院房屋以容纳更多的学生。其四是解决书院的经费问题,为岳麓书院置学田五十顷。经过朱熹的有效治理和严厉督促,岳麓书院很快得以复兴。朱熹在离任时,又托继任者王蔺修复与岳麓书院关系紧密的湘西书院。 朱熹兴学,对书院教育影响最大的是颁行《书院教条》。这个学规还是朱熹在淳熙间任南康知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学规中,朱熹明确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总方针是实施以“五教”为主要内容的五伦——伦理教育,强调了书院教育必须为社会伦理服务的前提。以此明确学者到书院来是为何而学、为谁而学,规范生徒行为,唤醒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学规反复要求生徒讲明义理,修养心性,力图体现其理学教育的根本特点。学规进而提出修身、处世、接物之要,作为生徒实际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准绳。其中所包含的重人格教育、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学风。朱熹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实际上指示了书院教学的全部过程。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意欲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书院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特色,都与这个“为学之序”密切相关。
朱熹知潭州时,“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朱熹,把《四书集注》作为岳麓书院的主要教材,始终坚持亲自执教,讲论重点集中于读书之须涵泳,须要浃洽。据廖谦记载,朱熹不仅经常在寓所向来访的学生授课,而且还亲自到岳麓书院督课,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一次,朱熹到书院后,采取抽签的方式让两位学生讲《大学》的语意,被抽查的学生都讲不清楚。朱熹便对诸生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并指出书院如果不如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建书院,在书院读书就是要读懂圣贤教人的道理,而不要模仿官学追求科举考试死读书、死背时文,要学子理会学问,“不理会学问,与蚩蚩横目之氓何异!”朱熹严肃认真、周到恳恻的教育作风,对学生的思想、学术都影响至深。
朱熹在长沙编成《州县释奠仪图》,其后由邵囦于长沙郡斋刻印,同时刻印的还有《三家礼范》、《稽古录》、《诗集传》,作为整顿士风学风的基本读物,希望通过“礼”的力量,用三纲五常来拯救世风、使人性复善。
相关地名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