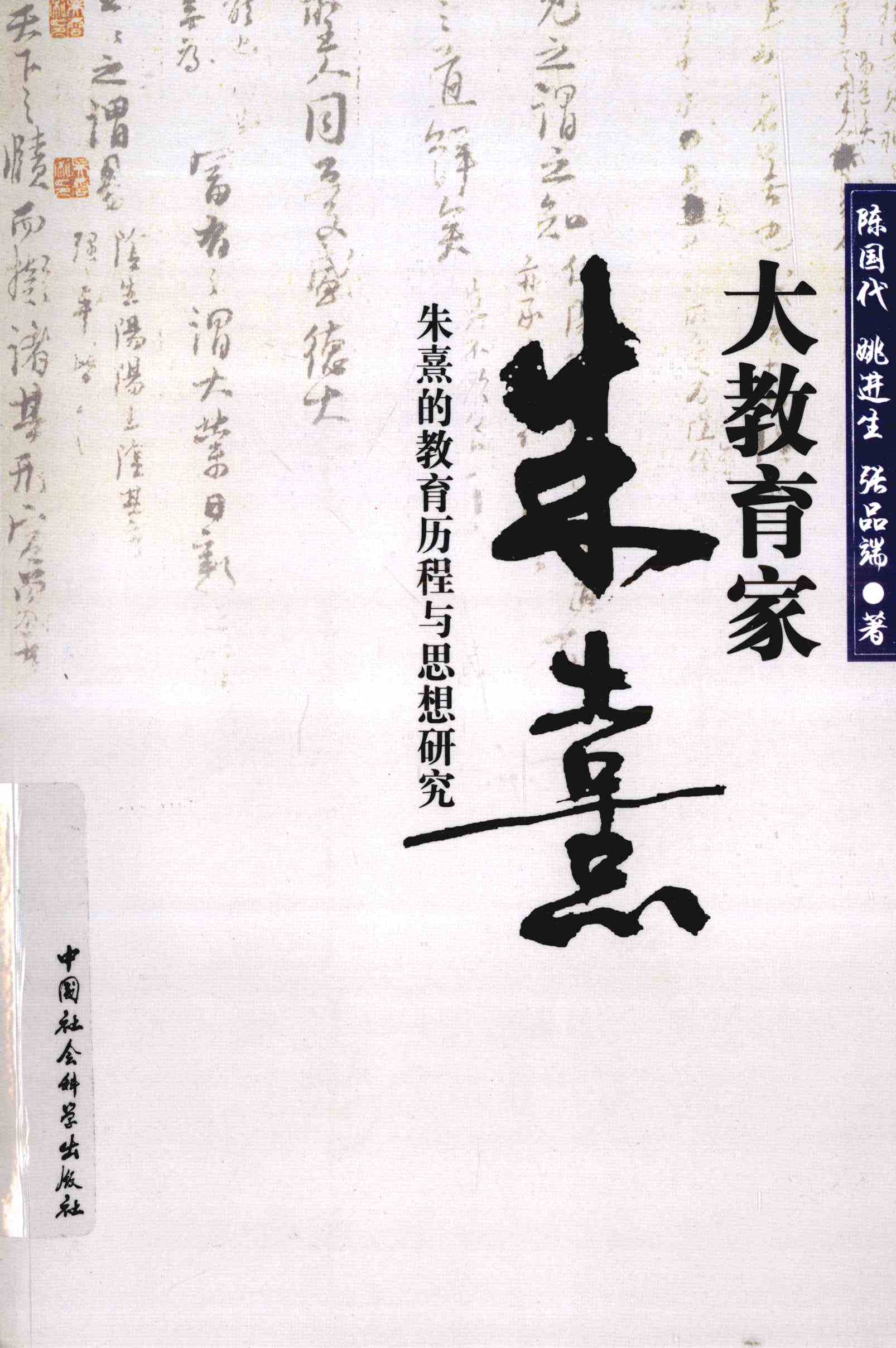朱熹绍熙五年在玉山讲学活动
| 内容出处: | 《大教育教朱熹》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0104 |
| 颗粒名称: | 朱熹绍熙五年在玉山讲学活动 |
| 分类号: | G40-09;B244.7 |
| 页数: | 7 |
| 页码: | 217-223 |
| 摘要: | 南宋绍熙五年,患心病不能打理朝政的宋光宗赵惇传位给儿子赵扩。二十七岁的赵扩仓促登基,立为宁宗。大约在绍熙五年闰十月二十六日朱熹归闽,时有林用中、余大猷、吴南、赵善期、王汉、李杞、喻仲可、朱耀卿、陈秀参等人随行。上述人物皆为从学者。朱熹于十一月十一日到玉山县,县宰司马迈率领诸生迎接朱熹一行,并邀请朱熹到县庠宾位讲座。朱熹登坛为县学诸生演讲,“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县宰当即录下讲义,寄给朱熹,经整理后,再由县令刻印发行。 |
| 关键词: | 朱熹 南宋绍熙五年 讲学活动 |
内容
南宋绍熙五年,患心病不能打理朝政的宋光宗赵惇传位给儿子赵扩。二十七岁的赵扩仓促登基,立为宁宗。新帝以为“欲进修德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经黄裳、彭龟年等人举荐,将赴任潭州才三个月的朱熹从湖南安抚使任上召入京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是朱熹生平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京官,入侍经筵四十六日,宁宗在新贵韩侂胄的挑拨离间下就以“悯卿耄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为名,内批朱熹差遣宫观,罢去侍讲,将朱熹赶出了京师。大约在绍熙五年闰十月二十六日朱熹归闽,时有林用中、余大猷、吴南、赵善期、王汉、李杞、喻仲可、朱耀卿、陈秀参等人随行。经钱塘曇山再访郑次山(郑涛)园亭。在曇山仙人洞石壁题留“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徘徊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宜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参、李良仲、喻可中俱来”。上述人物皆为从学者。 朱熹于十一月十一日到玉山县,县宰司马迈率领诸生迎接朱熹一行,并邀请朱熹到县庠宾位讲座。朱熹登坛为县学诸生演讲,“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县宰当即录下讲义,寄给朱熹,经整理后,再由县令刻印发行。今将《玉山讲义》录下: 先生曰:“熹此来得观学校鼎新,又有灵芝之瑞,足见贤宰承流宣化,兴学诲人之美意,不胜慰喜。又承特设讲座,俾为诸君诵说,虽不敢当,然区区所闻,亦不得不为诸君言之。盖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大学问。诸君肄业于此,朝夕讲明于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须有疑。今日幸得相会,正好商量,彼此之间,皆当有益。” 时有程珙起而且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之,非圣贤所说,性字更不必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发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义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义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 珙又请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著便仁,何也?” 先生曰:“说中说极,今人多错会了他文义,今亦未暇一一详说。但至孔门,方说仁字,则是列圣相传到此,方渐次说亲切处耳。夫子所以贤于尧舜,于此亦可见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须更于自己分上,实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说过,无益于事也。”先生因举《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谓性者,适固已言之矣。今复以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职。朝廷所命之职,无非使之行法治已,岂有不善?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尧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气禀清明,自无物欲之蔽,故为尧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学者知性善,则知尧舜之圣,非是强为。识得尧舜做处,则便识得性善底规模样子。而凡吾日用之间所以去人欲复天理者,皆吾分内当然之事,其势至顺而无难。此孟子所以首为文公言之,而又称尧舜以实之也。但当战国之时,圣教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圣贤之可学。闻是说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复致疑于其间。若文公则虽未能尽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与进善之萌芽也,孟子故于其去而复来迎而谓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盖古今贤愚同此一性,则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笃信力行,则天下之理虽有至难,犹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为之不难乎?然或气禀昏愚而物欲深固,则其势虽顺且易,亦须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后可以复其初。故孟子又引《商书》之言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则虽本甚易而反为至难矣。’此章之言虽甚简约,然其反复曲折,开晓学者最为深切。诸君更宜熟读深思,反复玩味,就日用间便著实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贤圣教人,始终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细,无有或遗。
故才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工,然亦不是判然两事也。《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记得昔日参见端明汪公,见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显而未尝少有自满之色,日以师友前辈多识前言往行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则自近世名卿鲜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诸君视之,文人行耳,其遗风余烈尚未远也。又知县大夫,当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至忠洁公扈从北狩,固守臣节,不污伪命,又以忠义闻于当世,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倘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道义风节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诸君留意以副贤大夫教诲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讲徒为空言,则区区之望也。” 朱熹在《玉山讲义》中表彰的温国文正公,即司马光;端明汪公,即汪应辰。
汪应辰(1118—1176年),字圣锡,原名汪洋,乃汪涓之弟,信州玉山人。幼年聪慧,五岁能读书应对,语惊众人。因家境贫寒,常从他人处借书,过目不忘。从名儒喻樗、吕居仁、张九成、胡安国等游。十八岁时登绍兴五年(1 135年)乙卯科进士第一,宋高宗皇帝赐名应辰,授镇东军签判,深得宰相赵鼎的爱惜,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八年,上书反对议和,以言事忤秦桧,出通判建州。秦桧为相,汪应辰遭受迫害并被流放岭南十七年。桧死,始得复召入朝,为吏部郎官。绍兴三十年后升为秘书少监。绍兴三十二年十月,以左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权户部侍郎调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路经建安,读朱熹诗文,叹为远器,与朱熹相见,即与陈康伯、陈俊卿、凌景夏向朝廷举荐朱熹。隆兴元年四月召朱熹到福州,讨论北伐用兵等事宜。隆兴二年二月、四月,两次邀请朱熹到福州讨论和战问题及论辩儒佛。当年五月准备入朝奏事,七月由福州北上,过崇安与朱熹见面,入朝后,除敷文阁直学士,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状荐举朱熹自代。乾道三四年间官益州太守。乾道四年六月,应诏入朝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因勇于任事,敢于兴利除弊而得罪权贵,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仍屡遭弹劾,遂以病为由,力请致仕。著有《二经雅言》、《唐书列传辨证》、《文定集》等。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病卒,谥文定。
而在座听讲主动提问者程珙,字仲璧,号柳湖,为饶州德兴人程端蒙之族孙,早在淳熙三年在婺源执礼拜师问学于朱熹。同朱熹有书信问答,朱熹作《答程珙》书。其主讲于柳湖书院,传播理学,与董铢、王过齐名。著有《易说》。
明代叶公回校订之《朱子年谱》云:朱熹“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此乃先生晚年教人亲切之训,读者宜深味之。” 当代著名学者束景南先生评价《玉山讲义》“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作的一次最精约明晰的理论概括”。
故才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工,然亦不是判然两事也。《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记得昔日参见端明汪公,见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显而未尝少有自满之色,日以师友前辈多识前言往行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则自近世名卿鲜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诸君视之,文人行耳,其遗风余烈尚未远也。又知县大夫,当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至忠洁公扈从北狩,固守臣节,不污伪命,又以忠义闻于当世,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倘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道义风节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诸君留意以副贤大夫教诲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讲徒为空言,则区区之望也。” 朱熹在《玉山讲义》中表彰的温国文正公,即司马光;端明汪公,即汪应辰。
汪应辰(1118—1176年),字圣锡,原名汪洋,乃汪涓之弟,信州玉山人。幼年聪慧,五岁能读书应对,语惊众人。因家境贫寒,常从他人处借书,过目不忘。从名儒喻樗、吕居仁、张九成、胡安国等游。十八岁时登绍兴五年(1 135年)乙卯科进士第一,宋高宗皇帝赐名应辰,授镇东军签判,深得宰相赵鼎的爱惜,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八年,上书反对议和,以言事忤秦桧,出通判建州。秦桧为相,汪应辰遭受迫害并被流放岭南十七年。桧死,始得复召入朝,为吏部郎官。绍兴三十年后升为秘书少监。绍兴三十二年十月,以左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权户部侍郎调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路经建安,读朱熹诗文,叹为远器,与朱熹相见,即与陈康伯、陈俊卿、凌景夏向朝廷举荐朱熹。隆兴元年四月召朱熹到福州,讨论北伐用兵等事宜。隆兴二年二月、四月,两次邀请朱熹到福州讨论和战问题及论辩儒佛。当年五月准备入朝奏事,七月由福州北上,过崇安与朱熹见面,入朝后,除敷文阁直学士,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状荐举朱熹自代。乾道三四年间官益州太守。乾道四年六月,应诏入朝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因勇于任事,敢于兴利除弊而得罪权贵,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仍屡遭弹劾,遂以病为由,力请致仕。著有《二经雅言》、《唐书列传辨证》、《文定集》等。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病卒,谥文定。
而在座听讲主动提问者程珙,字仲璧,号柳湖,为饶州德兴人程端蒙之族孙,早在淳熙三年在婺源执礼拜师问学于朱熹。同朱熹有书信问答,朱熹作《答程珙》书。其主讲于柳湖书院,传播理学,与董铢、王过齐名。著有《易说》。
明代叶公回校订之《朱子年谱》云:朱熹“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此乃先生晚年教人亲切之训,读者宜深味之。” 当代著名学者束景南先生评价《玉山讲义》“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作的一次最精约明晰的理论概括”。
相关地名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