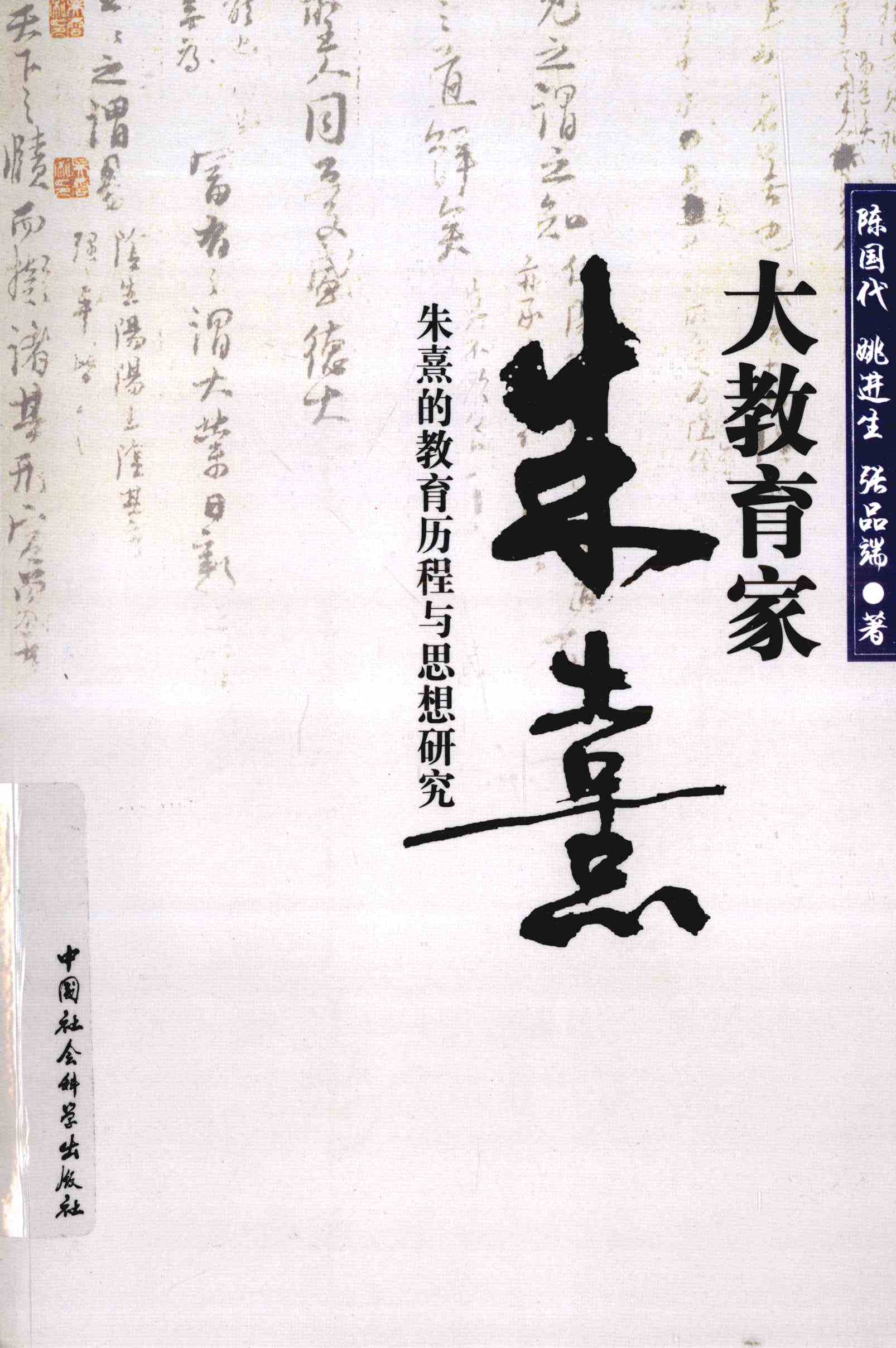第五节 玉山讲座明宗义 格致正诚天下平
| 内容出处: | 《大教育教朱熹》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0102 |
| 颗粒名称: | 第五节 玉山讲座明宗义 格致正诚天下平 |
| 并列题名: | 朱熹在玉山讲学活动拾零 |
| 分类号: | G40-09;B244.7 |
| 页数: | 18 |
| 页码: | 210-227 |
| 摘要: | 朱熹生平多次路经玉山县境,如朱熹进士及第后的绍兴十九年底回婺源故里省亲扫墓时路经铅山、上饶、玉山。淳熙三年朱熹赴婺源展墓,应诏赴京城奏事路过玉山。任浙东提举的朱熹写信给在金华的长子朱塾,朱熹卸浙东提举任后路过玉山县,并同段钧、赵善期陪朱熹游县西北怀玉中的南山。朱熹淳熙间在玉山讲学活动任南康知军的朱熹,朱熹携女婿黄榦离开崇安北上,与南康知军朱熹认识而从游。朱熹赴京城奏事路过玉山,朱熹要长子朱塾出面邀约浙东各派学者到玉山相会。 |
| 关键词: | 朱熹 玉山 讲论活动 |
内容
玉山县位于信州与衢州之间,与上饶、永丰、常山相邻。南宋时期,玉山县属江南东路管辖。从武夷山出闽到杭州城,一般得过玉山县。玉山县因境内西北部有怀玉山而得名,而怀玉山又因“玉帝遗玉于此”而得名,它绵延赣浙皖三省,北部的三清山玉京峰是其主峰,现在已开辟成旅游观光区。
有文献记载,朱熹生平多次路经玉山县境,如朱熹进士及第后的绍兴十九年底回婺源故里省亲扫墓时路经铅山、上饶、玉山。淳熙三年朱熹赴婺源展墓,经玉山往绍德庵一祭汪应辰。淳熙八年,卸任南康知军的朱熹,应诏赴京城奏事路过玉山。淳熙九年九月四日,任浙东提举的朱熹写信给在金华的长子朱塾,邀约浙东各派学者到玉山相会,即淳熙九年九月重阳节,朱熹卸浙东提举任后路过玉山县,有徐文卿与之初识、聚会,并同段钧、赵善期陪朱熹游县西北怀玉中的南山。淳熙十五年三月,朱熹应诏北上,在玉山县稽留四十余日,至五月十七日方离开。绍熙五年十一月戊戌,朱熹离开临安,过三衢,十一日至玉山县,应县宰之请讲学于县庠,等等。 本文对朱熹在玉山的讲学活动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梳理,分为淳熙间讲学、绍熙间讲学两个部分叙述,同时介绍朱熹交往的对象资料,以资参考。
朱熹淳熙间在玉山讲学活动任南康知军的朱熹,因救灾措施得力,赈济工作及时,使得一军三县二十万的灾民困顿得纾,于是得到朝廷嘉奖,得以转官,淳熙八年四月十九日回家,七月除秘阁,九月改除提举浙东茶盐常平公事,十一月二日应诏赴京城奏事。朱熹携女婿黄榦离开崇安北上,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延和殿面奏孝宗皇帝。翁婿路过玉山县,与刘允迪见面,未做长时间的逗留。
刘允迪,字德华,信州玉山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及第,曾任德安县宰,为政惠爱以得民心。淳熙六年至八年间,与南康知军朱熹认识而从游。淳熙八年其待次家中,于义学教授族子弟及乡人,朱熹赴京城奏事路过玉山,与之见面论学。
淳熙九年九月四日,朱熹要长子朱塾出面邀约浙东各派学者到玉山相会,前来的有吕祖俭、汪伯时、汪逵、潘景愈、潘景宪、康文虎、叶适、高应朝、刘炳等人。众人聚首,讲论学问。束景南先生说聚会地点在衢州府常山县。其后的重阳节,朱熹在众弟子的簇拥下来到信州府玉山县留数日,凭吊汪应辰遗迹、留连怀玉山水,在玉山的徐文卿、徐焕、段钧、赵善期前来聚会,并陪同朱熹游南山、登紫霄峰,留南山一日,且有留名。朱熹在玉山的活动,由门人写信告诉远在长沙的赵蕃。未及随杖履而行的诗人赵蕃有四首诗专门反映了这次的聚会与游玩,诗收载于《淳熙稿》卷十中。其中有:闻道朱夫子,南山尽日留。经行还阻见,会合信难谋。湛辈我无与,颜徒君好修。题名凡几字,好为刻岩幽。 徐文卿,字斯远,号樟丘,徐人杰之子,信州府玉山人。淳熙九年重阳节,与卸浙东提举任后路过玉山县的朱熹初识、聚会,并同段钧、赵善期陪朱熹游南山。此后的淳熙十六年九月,徐文卿又问学于武夷精舍。其早年嗜游山水,绍熙二年与赵蕃等人唱和,诗学与赵蕃、韩淲齐名。庆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到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见朱熹,并赠玉砚,朱熹为作《怀玉砚铭》。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进士及第,未授官而死。著有《萧秋诗集》。叶适作《徐斯远文集序》。
徐焕,字彦章,信州玉山人。曾在玉山道上与朱熹见面,探讨“子夏为狷介,只是把论交处说”。后来又问学于建阳考亭,参与讨论天体运行问题。与朱熹书信往来,朱熹作《答徐彦章》书四通。其与赵蕃友善,有诗作往来酬唱,官福州福清县。著有《周官辨略》等。
段钧,字元衡,其先邯郸人,南渡后侨居信州上饶。淳熙六年与南康知军朱熹同僚,四月共游,栖贤摩崖石刻留名。七月同游三峡,朱熹有《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佥判教授二同僚星子令尹约周君段君同游三峡过山房登折桂分韵赋诗得万字辄成十韵呈诸同游》,重阳节,与朱熹等人登高,作诗酬唱。淳熙九年九月重九,与卸浙东提举任后路过江西玉山的朱熹聚会,并同徐文卿、赵成父陪朱熹游南山。其与赵蕃兄弟等友善,赵有《段元衡出示与晦翁九日登紫霄峰诗及手帖并及贾八十兄诗既敬读之得三绝句》。赵善期,字诚父、成父,号定庵,赵蕃之弟,宋太宗七世孙,迁居信州玉山县。以荫入仕,淳熙六年,为巴州化城丞。淳熙九年九月与卸任后路过信州玉山的朱熹聚会,并同段钧、徐文卿等陪朱熹游南山。此后的绍熙五年,陪朱熹从杭州南归,在郑次山亭园有题名“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徘徊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宜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参、李良仲、喻可中俱来。”赵善期后官至通判,善作词。叶适有《赵成父筑亭上饶即用东里旧圃榜曰鱼计》。
上述诸人的资料透露了朱熹的行踪。而在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已被朝廷闲置整整六年的朱熹得到朝臣杨万里、周必大的举荐,除江西提刑,朱熹不得辞,应诏北上,由门人李闳祖、陈文蔚陪同,但在途徘徊不前,观望朝中时局变化,密切关注时势的演变,四月初四到达玉山,在此稽留至五月十七日方离开。这是一次为时特别长的盘桓逗留,四十余日里,朱熹都到过什么地方呢?在做些什么事? 在玉山古道上,朱熹接纳了徐昭然,向他面授主一学说。抛弃陆学而专心一意学禅的刘尧夫也来谒见,遭到朱熹诘责。最引人注意的是四月中旬与离开朝中来到玉山的杨万里邂逅。这是朱熹与杨万里的初次见面,以弟昆相呼,两人神往已久,谈论甚多,各自发表对朝政的看法,两人的观点基本一致,为他们日后的交往奠定了基础。而朱熹在玉山遇到翰林学士洪迈,两人为太极之说展开争论,留下一段悬案。为进一步了解该群体的讲论及影响,现简单介绍诸人资料如下,读者或可从中寻找到朱熹在玉山的所作所为。 徐昭然,字子融,号潜斋,信州铅山人,朱熹门人。淳熙十五年三月,受学于铅山县境永平驿,时朱熹过此徘徊不前。后随同往玉山,留止月余,随行聆教,受益匪浅。同年七月闭馆同余大雅到五夫受学,次年在武夷精舍续学。朱熹称其“志气刚决,操守非他人所及,文章痛快直截,无支离缠绕之弊”。朱熹曾指出其认心为性近似佛氏的错处。朱熹以其老成有守,欲延之家塾,为诸子师范。绍熙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朱熹罢侍讲归,子融还与陈文蔚、黄子功护送朱熹自上饶登临分水岭,在分水铺留一宿而别。徐昭然还于鹅湖寺旁结舍,聚徒讲学。其与陈文蔚过从甚密,后来陈文蔚曾书其遗事,介绍其从学朱熹的经过。
刘尧夫在十七岁时就成为陆九渊等人弟子。淳熙五年七月经吕祖谦引荐,入闽访朱熹,到崇安五夫从学数日,言陆氏之非,为朱熹所责,以为“子静之学即有未当,尧夫不可如此诋之。”淳熙六年三月同陆九龄拜访赴任南康军、路过信州铅山县留宿于观音寺的朱熹,却不参与朱陆讲论,因不满两人极论无猜,只在一旁学道家打坐,遭朱熹批评。淳熙十五年四月,在信州玉山县,见到入朝奏事而又徘徊不前的朱熹。次年学禅,出家为僧,未几病卒。这是朱熹辟佛中始终未能将之改造过来的典型人物之一。
杨万里(1125—1207年),字廷秀、庭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调零陵尉。张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遂以诚斋名书房。隆兴初知奉新县,以荐为国子监博士。后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主张抗金,正直敢言。早年未识朱熹,从张栻处听说朱熹学问并仰望之。淳熙十二年五月,官吏部郎中,以朱熹“学传二程,才雄一世,虽赋性近于狷介,临事过于果锐,若处以儒学之官,涵养成就,必为异才”而向时宰王淮荐举。淳熙十四年七月向周必大举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又向孝宗皇帝上《旱谟应诏上疏》,直接为朱熹因弹劾唐仲友被闲置六年鸣不平。淳熙十五年四月中旬因争议高庙配飨被罢出朝,遭排斥到筠州为官,在玉山与将入朝奏事的朱熹初次见面。杨万里支持朱熹的学说思想,并希望朱熹能为世所用。
此后的淳熙十六年八月自筠州入都,官秘书监,十月特过武夷山,同朱熹相会论政。绍熙元年正月有咏武夷精舍组诗寄给朱熹。同年十一月,出为江东漕运官。绍熙三年八月,得罪时相,罢职,奉祠归里,退隐南溪。次年十月寄诗、礼物给朱熹。绍熙五年四月,与朱熹见之于吉水朝元岭南溪,得朱熹以“廉介清洁,直是少”之评。庆元元年二月,复信朱熹,表示乐知天命,高蹈不仕之志。庆元三年名列庆元党籍。后来的开禧间为宝谟阁学士,二年于病中书韩侂胄罪状,次年愤极而卒,谥文节。著有《千虑策》、《诚斋易传》、《诚斋诗话》、《诚斋乐府》、《诚斋诗集》、《诚斋集》等。
洪迈(1123—1202年),字景庐,号容斋,洪皓之季子,饶州鄱阳人。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 145年)中进士第,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出为福州教授。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绍兴二十九年八月为吏部员外郎,与校书郎王淮同舍相好。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次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其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其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士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七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隆兴元年知泉州,次年离任。乾道二年,知吉州。淳熙六年,后改知赣州,到任,重视教育,建学馆,造浮桥,便利民。淳熙七年,知建宁府,富民有睚眦杀人衷刃篡狱者,久拒捕,迈正其罪,黥流岭外,五月放罢。淳熙十一年知婺州,大兴水利。后孝宗召对,洪迈建议于淮东抗金边备要地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并应补充水军,加强守备,得到孝宗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淳熙十三年入史馆主修《四朝帝纪》,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拜翰林学士。
淳熙十五年五月,洪迈出知镇江,由鄱阳北上,六月中旬,在玉山相遇从临安归闽的朱熹,出示《四朝国史》,在《周敦颐传》中,将周敦颐所言“无极而太极”改为“自无极而太极”,使无极、太极本是同一关系的理,分为有先后生成的关系,朱熹对此深为不满,要其拿出依据并修改之,但遭到拒绝。
此后的淳熙十五年九月,洪迈改知太平府,密友沈继祖作《送洪内翰知太平府》。绍熙元年为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次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著有《史记法语》、《经子法语》、《南朝史精义》、《容斋五笔》、《野处类稿》、《夷坚志》等。
文中小插曲: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作《丞相魏国陈正献公行状》,直斥洪迈为奸佞小人。在庆元二年底党禁开始,道学魁首朱熹遭受政治迫害,而风烛残年的洪迈开始奋起反扑,以道听途说虚构了浙东提举朱熹严刑拷打台州营妓严蕊的故事,收入在《夷坚志》中流布开来。朱熹比洪迈早二年弃世,故无以辩白去污。自古文人相轻,由此可见一斑。降至当今,仍有小文人拾人旧唾,说“我读史书,知道了朱熹的一些逸闻趣事。比如,当年他在提举浙东刑狱任上,眼馋那位美貌有才的营妓严蕊。可是人家严蕊名花有主,爱的却是老先生的同事、台州知州唐仲友。严蕊虽是个妓女,却颇忠实自己的感情,坚决不从。朱老先生一怒之下,向皇帝赵扩递上奏章,弹劾唐仲友。又以有伤风化罪将严蕊关进大牢,严刑拷打。大有‘我摸不得,谁敢去摸’之气概”。自号读史书的人,却只关注一些逸闻趣事,却没有将朱熹的身份弄明白,对历史事件也没有弄清楚,连皇帝是赵眘、还是赵扩都分辨不清,却横加指责前贤,于是有“我一听别人骂朱熹就特别高兴”,实乃浅薄至极。写《齐东野语》的宋人周密不可能再生,写《二刻拍案惊奇》的明人凌濛初也不可能再生,大文豪鲁迅先生过世了多年,不知罗思鼎是否尚健在?希望那些爱在网上活跃发表“高见”之人,去读读南昌大学历史系俞兆鹏教授的文章《从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贪官与营妓的关系》,也许会有所受益。朱熹绍熙五年在玉山讲学活动南宋绍熙五年,患心病不能打理朝政的宋光宗赵惇传位给儿子赵扩。二十七岁的赵扩仓促登基,立为宁宗。新帝以为“欲进修德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经黄裳、彭龟年等人举荐,将赴任潭州才三个月的朱熹从湖南安抚使任上召入京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是朱熹生平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京官,入侍经筵四十六日,宁宗在新贵韩侂胄的挑拨离间下就以“悯卿耄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为名,内批朱熹差遣宫观,罢去侍讲,将朱熹赶出了京师。大约在绍熙五年闰十月二十六日朱熹归闽,时有林用中、余大猷、吴南、赵善期、王汉、李杞、喻仲可、朱耀卿、陈秀参等人随行。经钱塘曇山再访郑次山(郑涛)园亭。在曇山仙人洞石壁题留“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徘徊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宜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参、李良仲、喻可中俱来”。上述人物皆为从学者。 朱熹于十一月十一日到玉山县,县宰司马迈率领诸生迎接朱熹一行,并邀请朱熹到县庠宾位讲座。朱熹登坛为县学诸生演讲,“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县宰当即录下讲义,寄给朱熹,经整理后,再由县令刻印发行。今将《玉山讲义》录下: 先生曰:“熹此来得观学校鼎新,又有灵芝之瑞,足见贤宰承流宣化,兴学诲人之美意,不胜慰喜。又承特设讲座,俾为诸君诵说,虽不敢当,然区区所闻,亦不得不为诸君言之。盖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大学问。诸君肄业于此,朝夕讲明于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须有疑。今日幸得相会,正好商量,彼此之间,皆当有益。” 时有程珙起而且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之,非圣贤所说,性字更不必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发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义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义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 珙又请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著便仁,何也?” 先生曰:“说中说极,今人多错会了他文义,今亦未暇一一详说。但至孔门,方说仁字,则是列圣相传到此,方渐次说亲切处耳。夫子所以贤于尧舜,于此亦可见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须更于自己分上,实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说过,无益于事也。”先生因举《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谓性者,适固已言之矣。今复以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职。朝廷所命之职,无非使之行法治已,岂有不善?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尧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气禀清明,自无物欲之蔽,故为尧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学者知性善,则知尧舜之圣,非是强为。识得尧舜做处,则便识得性善底规模样子。而凡吾日用之间所以去人欲复天理者,皆吾分内当然之事,其势至顺而无难。此孟子所以首为文公言之,而又称尧舜以实之也。但当战国之时,圣教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圣贤之可学。闻是说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复致疑于其间。若文公则虽未能尽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与进善之萌芽也,孟子故于其去而复来迎而谓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盖古今贤愚同此一性,则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笃信力行,则天下之理虽有至难,犹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为之不难乎?然或气禀昏愚而物欲深固,则其势虽顺且易,亦须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后可以复其初。故孟子又引《商书》之言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则虽本甚易而反为至难矣。’此章之言虽甚简约,然其反复曲折,开晓学者最为深切。诸君更宜熟读深思,反复玩味,就日用间便著实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贤圣教人,始终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细,无有或遗。
故才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工,然亦不是判然两事也。《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记得昔日参见端明汪公,见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显而未尝少有自满之色,日以师友前辈多识前言往行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则自近世名卿鲜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诸君视之,文人行耳,其遗风余烈尚未远也。又知县大夫,当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至忠洁公扈从北狩,固守臣节,不污伪命,又以忠义闻于当世,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倘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道义风节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诸君留意以副贤大夫教诲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讲徒为空言,则区区之望也。” 朱熹在《玉山讲义》中表彰的温国文正公,即司马光;端明汪公,即汪应辰。
汪应辰(1118—1176年),字圣锡,原名汪洋,乃汪涓之弟,信州玉山人。幼年聪慧,五岁能读书应对,语惊众人。因家境贫寒,常从他人处借书,过目不忘。从名儒喻樗、吕居仁、张九成、胡安国等游。十八岁时登绍兴五年(1 135年)乙卯科进士第一,宋高宗皇帝赐名应辰,授镇东军签判,深得宰相赵鼎的爱惜,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八年,上书反对议和,以言事忤秦桧,出通判建州。秦桧为相,汪应辰遭受迫害并被流放岭南十七年。桧死,始得复召入朝,为吏部郎官。绍兴三十年后升为秘书少监。绍兴三十二年十月,以左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权户部侍郎调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路经建安,读朱熹诗文,叹为远器,与朱熹相见,即与陈康伯、陈俊卿、凌景夏向朝廷举荐朱熹。隆兴元年四月召朱熹到福州,讨论北伐用兵等事宜。隆兴二年二月、四月,两次邀请朱熹到福州讨论和战问题及论辩儒佛。当年五月准备入朝奏事,七月由福州北上,过崇安与朱熹见面,入朝后,除敷文阁直学士,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状荐举朱熹自代。乾道三四年间官益州太守。乾道四年六月,应诏入朝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因勇于任事,敢于兴利除弊而得罪权贵,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仍屡遭弹劾,遂以病为由,力请致仕。著有《二经雅言》、《唐书列传辨证》、《文定集》等。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病卒,谥文定。
而在座听讲主动提问者程珙,字仲璧,号柳湖,为饶州德兴人程端蒙之族孙,早在淳熙三年在婺源执礼拜师问学于朱熹。同朱熹有书信问答,朱熹作《答程珙》书。其主讲于柳湖书院,传播理学,与董铢、王过齐名。著有《易说》。
明代叶公回校订之《朱子年谱》云:朱熹“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此乃先生晚年教人亲切之训,读者宜深味之。” 当代著名学者束景南先生评价《玉山讲义》“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作的一次最精约明晰的理论概括”。与朱熹有关的玉山草堂书院接下来,我们来考察朱熹与玉山有关的书院。就笔者所接触的文献,提到书院有草堂书院、怀玉书院(或曰怀玉山书院)与朱熹有关,但讲学时间却模糊不清。
方志所载草堂书院在江西玉山县北怀玉山下,乃后人为了纪念朱熹与众门生游宿、讲学于怀玉山中,建了草堂书院。传朱子讲学于此,题山下酒舍一联云:泉飞白石堪为酒,灶傍青山不买柴。后人建青山绿树亭、源头活水亭,堂庑号舍具备。又言怀玉书院位于江西玉山县怀玉山金刚岭之阳。北宋杨亿曾建“怀玉精舍”于此。“淳熙间,朱子与陆九渊、汪应辰诸贤讲学其间,有司及门人拓建书院,置田以供四方来学者”。
关于草堂书院、怀玉山书院的沿革,可参考历代《记文》。
南唐之际,玉山县令杨文逸为应梦验,为刚出世的孙子杨亿选择读书之处,择怀玉山金刚峰下的法海寺一间房作为杨亿的读书处,后称之为杨亿精舍。杨亿文采横溢,十一岁中进士,后成为西昆体诗集大成者,一直为京官到老。南宋谏议大夫尹穑客居怀玉山时又选杨亿精舍作为书斋,号为“方斋”,后人乃立为书院。
明代嘉靖年间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在《怀玉山书院记》中说:“金刚峰下为怀玉寺,稍南,为草堂书院,宋朱子讲学其中。”清乾隆江西布政使汤聘在《端明书院记》中说玉山县城端明书院与县北金刚峰朱子讲学之怀玉书院巍然并峙,“盖朱子即杨文公读书之处建书院以讲学,颜曰‘草堂’。后人更之,曰‘怀玉’”。清代学者蒋士铨在《怀玉山志》序中说:“书院本唐法海寺基,迨朱陆讲学于此,乃立为书院。”由法海寺→杨亿读书处→精舍→草堂、讲学其中→怀玉书院的综合表述可以看出,玉山草堂书院与怀玉山书院则为一也。也就是徐公喜先生所言“明清时的怀玉书院,实际上就是宋时的草堂书院”。那么“江西玉山县北怀玉山下”与“江西玉山县怀玉山金刚岭之阳”也就是同一个地点,惜乎,笔者游玉山三清山时未得拜谒之。
方彦寿先生在《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中将怀玉书院列为朱熹讲学过的书院,并从《朱子全书》考察到朱熹曾与吕祖谦有“怀玉之约”。淳熙元年,朱熹在写给吕氏的信中说:“秋冬间无事,或可出入。甚思承教……闻怀玉山水甚胜,若会于彼,道里均矣。”但到了秋冬间,两人均因故不能践约前往。《答吕伯恭》书第三十六云:“怀玉之约迟以明年,无所不可。”淳熙二年的江西鹅湖之会后,“怀玉之约”仍未成行,故朱熹在《答吕伯恭》书第四十则云:“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鹅湖追逐入怀玉深山坐数日也。”(徐公喜先生文章有“吾痛不得自鹅湖,遂入怀玉,深山静坐数月”,引文与此不同)也就是说,朱熹未能追随吕祖谦赴怀玉山,引以为憾。
徐公喜先生在《朱熹<玉山讲义>的价值》一文中说朱熹未讲明讲学的地点,又说“当代学者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也只是说朱熹应玉山县宰司马氏邀请为县庠诸生做了一次讲学。对于朱熹在何地作《玉山讲义》并没有具体的论断。从现有的史料看,朱熹应当是在怀玉山中的草堂书院。草堂书院因朱熹讲学于此而出名,但是并不是如同有的旧志所说为朱熹所建”。
此说有两点欠妥,即“朱熹未讲明地点”和“束景南并没有具体的论断”。这在徐先生引用朱熹给林德久信中就说道:“昨在玉山学中,与诸生说话,司马宰令人录来。当时无人剧论,说得不痛快,归来偶与一朋友说,却说得详尽,因并两次所言,录以报之。”就将地点说明了,玉山学中,就是指玉山县学。朱熹在《讲义》开首便有“熹此来得观学校鼎新”,就明言县学。因此说,将地点认作怀玉山中的草堂书院,显然也就错了。
徐先生否认草堂书院“旧志所说为朱熹所建”是正确的,但对“有司及门人拓建书院”一句却没有说明,忽略了光绪版《江西通志》所言朱熹门人对草堂的建设作用。
明代嘉靖年间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在《怀玉山书院记》中说:“金刚峰下为怀玉寺,稍南,为草堂书院,宋朱子讲学其中。”没有指明朱熹讲学于草堂书院的具体时间,或为淳熙二年,或为淳熙九年,或为淳熙十五年,或为绍熙五年,未究其详。
方彦寿认为光绪《江西通志》称朱熹与陆九渊、汪应辰曾讲学其间,证据不足,“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笔者认为,朱、陆、汪同时讲学于其中,显然缺少有力证据,鹅湖之会是在淳熙二年五月二十八、九日至六月八日之间举行的学术交流,会期约十天,之后,未见朱熹和陆九渊往玉山见汪应辰当面论学,朱熹写信给吕祖谦已经表达清楚,此后也无机会与陆九渊聚首面论于玉山。但不排除汪应辰、朱熹、陆九渊三人不同时期分别讲学于其中的可能。
淳熙九年九月,朱熹卸任浙东提举,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由衢州常山来到信州玉山县留数日,凭吊汪应辰遗迹、流连怀玉山水,有玉山方面的徐文卿、徐焕、段钧、赵善期等人前来聚会。诗人赵蕃所作《成父书来,报朱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杖履为恨,辄成鄙句,寄斯远、彦章,且示成父》和《段元衡出示与晦翁九日登紫霄峰诗及手帖及贾十八兄诗,既敬读之,得三绝句》,诗末有“晦翁比自浙东归,过玉山留数日”。赵蕃所言的南山,在玉山县西北怀玉山山脚下。依诗人章泉之说,可给出怀玉山中草堂书院与朱熹的关系。
而淳熙十五年夏四月初四,朱熹到达玉山,至五月十七日方离开玉山,其间稽留四十余日,与众弟子及杨万里会见与讲论,亦有可能从容游览怀玉山、讲学于怀玉中。但绍熙五年朱熹只讲学于县庠,未见有登览怀玉山讲学的记载。
因此,朱熹在怀玉山草堂书院的讲学活动,最明确的时间应是淳熙九年重阳节,最不能忽略的是淳熙十五年夏间。
有文献记载,朱熹生平多次路经玉山县境,如朱熹进士及第后的绍兴十九年底回婺源故里省亲扫墓时路经铅山、上饶、玉山。淳熙三年朱熹赴婺源展墓,经玉山往绍德庵一祭汪应辰。淳熙八年,卸任南康知军的朱熹,应诏赴京城奏事路过玉山。淳熙九年九月四日,任浙东提举的朱熹写信给在金华的长子朱塾,邀约浙东各派学者到玉山相会,即淳熙九年九月重阳节,朱熹卸浙东提举任后路过玉山县,有徐文卿与之初识、聚会,并同段钧、赵善期陪朱熹游县西北怀玉中的南山。淳熙十五年三月,朱熹应诏北上,在玉山县稽留四十余日,至五月十七日方离开。绍熙五年十一月戊戌,朱熹离开临安,过三衢,十一日至玉山县,应县宰之请讲学于县庠,等等。 本文对朱熹在玉山的讲学活动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梳理,分为淳熙间讲学、绍熙间讲学两个部分叙述,同时介绍朱熹交往的对象资料,以资参考。
朱熹淳熙间在玉山讲学活动任南康知军的朱熹,因救灾措施得力,赈济工作及时,使得一军三县二十万的灾民困顿得纾,于是得到朝廷嘉奖,得以转官,淳熙八年四月十九日回家,七月除秘阁,九月改除提举浙东茶盐常平公事,十一月二日应诏赴京城奏事。朱熹携女婿黄榦离开崇安北上,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延和殿面奏孝宗皇帝。翁婿路过玉山县,与刘允迪见面,未做长时间的逗留。
刘允迪,字德华,信州玉山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及第,曾任德安县宰,为政惠爱以得民心。淳熙六年至八年间,与南康知军朱熹认识而从游。淳熙八年其待次家中,于义学教授族子弟及乡人,朱熹赴京城奏事路过玉山,与之见面论学。
淳熙九年九月四日,朱熹要长子朱塾出面邀约浙东各派学者到玉山相会,前来的有吕祖俭、汪伯时、汪逵、潘景愈、潘景宪、康文虎、叶适、高应朝、刘炳等人。众人聚首,讲论学问。束景南先生说聚会地点在衢州府常山县。其后的重阳节,朱熹在众弟子的簇拥下来到信州府玉山县留数日,凭吊汪应辰遗迹、留连怀玉山水,在玉山的徐文卿、徐焕、段钧、赵善期前来聚会,并陪同朱熹游南山、登紫霄峰,留南山一日,且有留名。朱熹在玉山的活动,由门人写信告诉远在长沙的赵蕃。未及随杖履而行的诗人赵蕃有四首诗专门反映了这次的聚会与游玩,诗收载于《淳熙稿》卷十中。其中有:闻道朱夫子,南山尽日留。经行还阻见,会合信难谋。湛辈我无与,颜徒君好修。题名凡几字,好为刻岩幽。 徐文卿,字斯远,号樟丘,徐人杰之子,信州府玉山人。淳熙九年重阳节,与卸浙东提举任后路过玉山县的朱熹初识、聚会,并同段钧、赵善期陪朱熹游南山。此后的淳熙十六年九月,徐文卿又问学于武夷精舍。其早年嗜游山水,绍熙二年与赵蕃等人唱和,诗学与赵蕃、韩淲齐名。庆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到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见朱熹,并赠玉砚,朱熹为作《怀玉砚铭》。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进士及第,未授官而死。著有《萧秋诗集》。叶适作《徐斯远文集序》。
徐焕,字彦章,信州玉山人。曾在玉山道上与朱熹见面,探讨“子夏为狷介,只是把论交处说”。后来又问学于建阳考亭,参与讨论天体运行问题。与朱熹书信往来,朱熹作《答徐彦章》书四通。其与赵蕃友善,有诗作往来酬唱,官福州福清县。著有《周官辨略》等。
段钧,字元衡,其先邯郸人,南渡后侨居信州上饶。淳熙六年与南康知军朱熹同僚,四月共游,栖贤摩崖石刻留名。七月同游三峡,朱熹有《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佥判教授二同僚星子令尹约周君段君同游三峡过山房登折桂分韵赋诗得万字辄成十韵呈诸同游》,重阳节,与朱熹等人登高,作诗酬唱。淳熙九年九月重九,与卸浙东提举任后路过江西玉山的朱熹聚会,并同徐文卿、赵成父陪朱熹游南山。其与赵蕃兄弟等友善,赵有《段元衡出示与晦翁九日登紫霄峰诗及手帖并及贾八十兄诗既敬读之得三绝句》。赵善期,字诚父、成父,号定庵,赵蕃之弟,宋太宗七世孙,迁居信州玉山县。以荫入仕,淳熙六年,为巴州化城丞。淳熙九年九月与卸任后路过信州玉山的朱熹聚会,并同段钧、徐文卿等陪朱熹游南山。此后的绍熙五年,陪朱熹从杭州南归,在郑次山亭园有题名“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徘徊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宜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参、李良仲、喻可中俱来。”赵善期后官至通判,善作词。叶适有《赵成父筑亭上饶即用东里旧圃榜曰鱼计》。
上述诸人的资料透露了朱熹的行踪。而在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已被朝廷闲置整整六年的朱熹得到朝臣杨万里、周必大的举荐,除江西提刑,朱熹不得辞,应诏北上,由门人李闳祖、陈文蔚陪同,但在途徘徊不前,观望朝中时局变化,密切关注时势的演变,四月初四到达玉山,在此稽留至五月十七日方离开。这是一次为时特别长的盘桓逗留,四十余日里,朱熹都到过什么地方呢?在做些什么事? 在玉山古道上,朱熹接纳了徐昭然,向他面授主一学说。抛弃陆学而专心一意学禅的刘尧夫也来谒见,遭到朱熹诘责。最引人注意的是四月中旬与离开朝中来到玉山的杨万里邂逅。这是朱熹与杨万里的初次见面,以弟昆相呼,两人神往已久,谈论甚多,各自发表对朝政的看法,两人的观点基本一致,为他们日后的交往奠定了基础。而朱熹在玉山遇到翰林学士洪迈,两人为太极之说展开争论,留下一段悬案。为进一步了解该群体的讲论及影响,现简单介绍诸人资料如下,读者或可从中寻找到朱熹在玉山的所作所为。 徐昭然,字子融,号潜斋,信州铅山人,朱熹门人。淳熙十五年三月,受学于铅山县境永平驿,时朱熹过此徘徊不前。后随同往玉山,留止月余,随行聆教,受益匪浅。同年七月闭馆同余大雅到五夫受学,次年在武夷精舍续学。朱熹称其“志气刚决,操守非他人所及,文章痛快直截,无支离缠绕之弊”。朱熹曾指出其认心为性近似佛氏的错处。朱熹以其老成有守,欲延之家塾,为诸子师范。绍熙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朱熹罢侍讲归,子融还与陈文蔚、黄子功护送朱熹自上饶登临分水岭,在分水铺留一宿而别。徐昭然还于鹅湖寺旁结舍,聚徒讲学。其与陈文蔚过从甚密,后来陈文蔚曾书其遗事,介绍其从学朱熹的经过。
刘尧夫在十七岁时就成为陆九渊等人弟子。淳熙五年七月经吕祖谦引荐,入闽访朱熹,到崇安五夫从学数日,言陆氏之非,为朱熹所责,以为“子静之学即有未当,尧夫不可如此诋之。”淳熙六年三月同陆九龄拜访赴任南康军、路过信州铅山县留宿于观音寺的朱熹,却不参与朱陆讲论,因不满两人极论无猜,只在一旁学道家打坐,遭朱熹批评。淳熙十五年四月,在信州玉山县,见到入朝奏事而又徘徊不前的朱熹。次年学禅,出家为僧,未几病卒。这是朱熹辟佛中始终未能将之改造过来的典型人物之一。
杨万里(1125—1207年),字廷秀、庭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调零陵尉。张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遂以诚斋名书房。隆兴初知奉新县,以荐为国子监博士。后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主张抗金,正直敢言。早年未识朱熹,从张栻处听说朱熹学问并仰望之。淳熙十二年五月,官吏部郎中,以朱熹“学传二程,才雄一世,虽赋性近于狷介,临事过于果锐,若处以儒学之官,涵养成就,必为异才”而向时宰王淮荐举。淳熙十四年七月向周必大举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又向孝宗皇帝上《旱谟应诏上疏》,直接为朱熹因弹劾唐仲友被闲置六年鸣不平。淳熙十五年四月中旬因争议高庙配飨被罢出朝,遭排斥到筠州为官,在玉山与将入朝奏事的朱熹初次见面。杨万里支持朱熹的学说思想,并希望朱熹能为世所用。
此后的淳熙十六年八月自筠州入都,官秘书监,十月特过武夷山,同朱熹相会论政。绍熙元年正月有咏武夷精舍组诗寄给朱熹。同年十一月,出为江东漕运官。绍熙三年八月,得罪时相,罢职,奉祠归里,退隐南溪。次年十月寄诗、礼物给朱熹。绍熙五年四月,与朱熹见之于吉水朝元岭南溪,得朱熹以“廉介清洁,直是少”之评。庆元元年二月,复信朱熹,表示乐知天命,高蹈不仕之志。庆元三年名列庆元党籍。后来的开禧间为宝谟阁学士,二年于病中书韩侂胄罪状,次年愤极而卒,谥文节。著有《千虑策》、《诚斋易传》、《诚斋诗话》、《诚斋乐府》、《诚斋诗集》、《诚斋集》等。
洪迈(1123—1202年),字景庐,号容斋,洪皓之季子,饶州鄱阳人。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 145年)中进士第,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出为福州教授。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绍兴二十九年八月为吏部员外郎,与校书郎王淮同舍相好。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次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其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其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士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七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隆兴元年知泉州,次年离任。乾道二年,知吉州。淳熙六年,后改知赣州,到任,重视教育,建学馆,造浮桥,便利民。淳熙七年,知建宁府,富民有睚眦杀人衷刃篡狱者,久拒捕,迈正其罪,黥流岭外,五月放罢。淳熙十一年知婺州,大兴水利。后孝宗召对,洪迈建议于淮东抗金边备要地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并应补充水军,加强守备,得到孝宗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淳熙十三年入史馆主修《四朝帝纪》,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拜翰林学士。
淳熙十五年五月,洪迈出知镇江,由鄱阳北上,六月中旬,在玉山相遇从临安归闽的朱熹,出示《四朝国史》,在《周敦颐传》中,将周敦颐所言“无极而太极”改为“自无极而太极”,使无极、太极本是同一关系的理,分为有先后生成的关系,朱熹对此深为不满,要其拿出依据并修改之,但遭到拒绝。
此后的淳熙十五年九月,洪迈改知太平府,密友沈继祖作《送洪内翰知太平府》。绍熙元年为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次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著有《史记法语》、《经子法语》、《南朝史精义》、《容斋五笔》、《野处类稿》、《夷坚志》等。
文中小插曲: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作《丞相魏国陈正献公行状》,直斥洪迈为奸佞小人。在庆元二年底党禁开始,道学魁首朱熹遭受政治迫害,而风烛残年的洪迈开始奋起反扑,以道听途说虚构了浙东提举朱熹严刑拷打台州营妓严蕊的故事,收入在《夷坚志》中流布开来。朱熹比洪迈早二年弃世,故无以辩白去污。自古文人相轻,由此可见一斑。降至当今,仍有小文人拾人旧唾,说“我读史书,知道了朱熹的一些逸闻趣事。比如,当年他在提举浙东刑狱任上,眼馋那位美貌有才的营妓严蕊。可是人家严蕊名花有主,爱的却是老先生的同事、台州知州唐仲友。严蕊虽是个妓女,却颇忠实自己的感情,坚决不从。朱老先生一怒之下,向皇帝赵扩递上奏章,弹劾唐仲友。又以有伤风化罪将严蕊关进大牢,严刑拷打。大有‘我摸不得,谁敢去摸’之气概”。自号读史书的人,却只关注一些逸闻趣事,却没有将朱熹的身份弄明白,对历史事件也没有弄清楚,连皇帝是赵眘、还是赵扩都分辨不清,却横加指责前贤,于是有“我一听别人骂朱熹就特别高兴”,实乃浅薄至极。写《齐东野语》的宋人周密不可能再生,写《二刻拍案惊奇》的明人凌濛初也不可能再生,大文豪鲁迅先生过世了多年,不知罗思鼎是否尚健在?希望那些爱在网上活跃发表“高见”之人,去读读南昌大学历史系俞兆鹏教授的文章《从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贪官与营妓的关系》,也许会有所受益。朱熹绍熙五年在玉山讲学活动南宋绍熙五年,患心病不能打理朝政的宋光宗赵惇传位给儿子赵扩。二十七岁的赵扩仓促登基,立为宁宗。新帝以为“欲进修德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经黄裳、彭龟年等人举荐,将赴任潭州才三个月的朱熹从湖南安抚使任上召入京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是朱熹生平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京官,入侍经筵四十六日,宁宗在新贵韩侂胄的挑拨离间下就以“悯卿耄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为名,内批朱熹差遣宫观,罢去侍讲,将朱熹赶出了京师。大约在绍熙五年闰十月二十六日朱熹归闽,时有林用中、余大猷、吴南、赵善期、王汉、李杞、喻仲可、朱耀卿、陈秀参等人随行。经钱塘曇山再访郑次山(郑涛)园亭。在曇山仙人洞石壁题留“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徘徊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宜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参、李良仲、喻可中俱来”。上述人物皆为从学者。 朱熹于十一月十一日到玉山县,县宰司马迈率领诸生迎接朱熹一行,并邀请朱熹到县庠宾位讲座。朱熹登坛为县学诸生演讲,“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县宰当即录下讲义,寄给朱熹,经整理后,再由县令刻印发行。今将《玉山讲义》录下: 先生曰:“熹此来得观学校鼎新,又有灵芝之瑞,足见贤宰承流宣化,兴学诲人之美意,不胜慰喜。又承特设讲座,俾为诸君诵说,虽不敢当,然区区所闻,亦不得不为诸君言之。盖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大学问。诸君肄业于此,朝夕讲明于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须有疑。今日幸得相会,正好商量,彼此之间,皆当有益。” 时有程珙起而且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之,非圣贤所说,性字更不必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发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义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义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 珙又请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著便仁,何也?” 先生曰:“说中说极,今人多错会了他文义,今亦未暇一一详说。但至孔门,方说仁字,则是列圣相传到此,方渐次说亲切处耳。夫子所以贤于尧舜,于此亦可见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须更于自己分上,实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说过,无益于事也。”先生因举《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谓性者,适固已言之矣。今复以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职。朝廷所命之职,无非使之行法治已,岂有不善?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尧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气禀清明,自无物欲之蔽,故为尧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学者知性善,则知尧舜之圣,非是强为。识得尧舜做处,则便识得性善底规模样子。而凡吾日用之间所以去人欲复天理者,皆吾分内当然之事,其势至顺而无难。此孟子所以首为文公言之,而又称尧舜以实之也。但当战国之时,圣教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圣贤之可学。闻是说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复致疑于其间。若文公则虽未能尽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与进善之萌芽也,孟子故于其去而复来迎而谓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盖古今贤愚同此一性,则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笃信力行,则天下之理虽有至难,犹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为之不难乎?然或气禀昏愚而物欲深固,则其势虽顺且易,亦须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后可以复其初。故孟子又引《商书》之言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则虽本甚易而反为至难矣。’此章之言虽甚简约,然其反复曲折,开晓学者最为深切。诸君更宜熟读深思,反复玩味,就日用间便著实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贤圣教人,始终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细,无有或遗。
故才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工,然亦不是判然两事也。《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记得昔日参见端明汪公,见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显而未尝少有自满之色,日以师友前辈多识前言往行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则自近世名卿鲜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诸君视之,文人行耳,其遗风余烈尚未远也。又知县大夫,当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至忠洁公扈从北狩,固守臣节,不污伪命,又以忠义闻于当世,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倘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道义风节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诸君留意以副贤大夫教诲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讲徒为空言,则区区之望也。” 朱熹在《玉山讲义》中表彰的温国文正公,即司马光;端明汪公,即汪应辰。
汪应辰(1118—1176年),字圣锡,原名汪洋,乃汪涓之弟,信州玉山人。幼年聪慧,五岁能读书应对,语惊众人。因家境贫寒,常从他人处借书,过目不忘。从名儒喻樗、吕居仁、张九成、胡安国等游。十八岁时登绍兴五年(1 135年)乙卯科进士第一,宋高宗皇帝赐名应辰,授镇东军签判,深得宰相赵鼎的爱惜,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八年,上书反对议和,以言事忤秦桧,出通判建州。秦桧为相,汪应辰遭受迫害并被流放岭南十七年。桧死,始得复召入朝,为吏部郎官。绍兴三十年后升为秘书少监。绍兴三十二年十月,以左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权户部侍郎调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路经建安,读朱熹诗文,叹为远器,与朱熹相见,即与陈康伯、陈俊卿、凌景夏向朝廷举荐朱熹。隆兴元年四月召朱熹到福州,讨论北伐用兵等事宜。隆兴二年二月、四月,两次邀请朱熹到福州讨论和战问题及论辩儒佛。当年五月准备入朝奏事,七月由福州北上,过崇安与朱熹见面,入朝后,除敷文阁直学士,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状荐举朱熹自代。乾道三四年间官益州太守。乾道四年六月,应诏入朝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因勇于任事,敢于兴利除弊而得罪权贵,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仍屡遭弹劾,遂以病为由,力请致仕。著有《二经雅言》、《唐书列传辨证》、《文定集》等。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病卒,谥文定。
而在座听讲主动提问者程珙,字仲璧,号柳湖,为饶州德兴人程端蒙之族孙,早在淳熙三年在婺源执礼拜师问学于朱熹。同朱熹有书信问答,朱熹作《答程珙》书。其主讲于柳湖书院,传播理学,与董铢、王过齐名。著有《易说》。
明代叶公回校订之《朱子年谱》云:朱熹“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此乃先生晚年教人亲切之训,读者宜深味之。” 当代著名学者束景南先生评价《玉山讲义》“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作的一次最精约明晰的理论概括”。与朱熹有关的玉山草堂书院接下来,我们来考察朱熹与玉山有关的书院。就笔者所接触的文献,提到书院有草堂书院、怀玉书院(或曰怀玉山书院)与朱熹有关,但讲学时间却模糊不清。
方志所载草堂书院在江西玉山县北怀玉山下,乃后人为了纪念朱熹与众门生游宿、讲学于怀玉山中,建了草堂书院。传朱子讲学于此,题山下酒舍一联云:泉飞白石堪为酒,灶傍青山不买柴。后人建青山绿树亭、源头活水亭,堂庑号舍具备。又言怀玉书院位于江西玉山县怀玉山金刚岭之阳。北宋杨亿曾建“怀玉精舍”于此。“淳熙间,朱子与陆九渊、汪应辰诸贤讲学其间,有司及门人拓建书院,置田以供四方来学者”。
关于草堂书院、怀玉山书院的沿革,可参考历代《记文》。
南唐之际,玉山县令杨文逸为应梦验,为刚出世的孙子杨亿选择读书之处,择怀玉山金刚峰下的法海寺一间房作为杨亿的读书处,后称之为杨亿精舍。杨亿文采横溢,十一岁中进士,后成为西昆体诗集大成者,一直为京官到老。南宋谏议大夫尹穑客居怀玉山时又选杨亿精舍作为书斋,号为“方斋”,后人乃立为书院。
明代嘉靖年间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在《怀玉山书院记》中说:“金刚峰下为怀玉寺,稍南,为草堂书院,宋朱子讲学其中。”清乾隆江西布政使汤聘在《端明书院记》中说玉山县城端明书院与县北金刚峰朱子讲学之怀玉书院巍然并峙,“盖朱子即杨文公读书之处建书院以讲学,颜曰‘草堂’。后人更之,曰‘怀玉’”。清代学者蒋士铨在《怀玉山志》序中说:“书院本唐法海寺基,迨朱陆讲学于此,乃立为书院。”由法海寺→杨亿读书处→精舍→草堂、讲学其中→怀玉书院的综合表述可以看出,玉山草堂书院与怀玉山书院则为一也。也就是徐公喜先生所言“明清时的怀玉书院,实际上就是宋时的草堂书院”。那么“江西玉山县北怀玉山下”与“江西玉山县怀玉山金刚岭之阳”也就是同一个地点,惜乎,笔者游玉山三清山时未得拜谒之。
方彦寿先生在《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中将怀玉书院列为朱熹讲学过的书院,并从《朱子全书》考察到朱熹曾与吕祖谦有“怀玉之约”。淳熙元年,朱熹在写给吕氏的信中说:“秋冬间无事,或可出入。甚思承教……闻怀玉山水甚胜,若会于彼,道里均矣。”但到了秋冬间,两人均因故不能践约前往。《答吕伯恭》书第三十六云:“怀玉之约迟以明年,无所不可。”淳熙二年的江西鹅湖之会后,“怀玉之约”仍未成行,故朱熹在《答吕伯恭》书第四十则云:“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鹅湖追逐入怀玉深山坐数日也。”(徐公喜先生文章有“吾痛不得自鹅湖,遂入怀玉,深山静坐数月”,引文与此不同)也就是说,朱熹未能追随吕祖谦赴怀玉山,引以为憾。
徐公喜先生在《朱熹<玉山讲义>的价值》一文中说朱熹未讲明讲学的地点,又说“当代学者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也只是说朱熹应玉山县宰司马氏邀请为县庠诸生做了一次讲学。对于朱熹在何地作《玉山讲义》并没有具体的论断。从现有的史料看,朱熹应当是在怀玉山中的草堂书院。草堂书院因朱熹讲学于此而出名,但是并不是如同有的旧志所说为朱熹所建”。
此说有两点欠妥,即“朱熹未讲明地点”和“束景南并没有具体的论断”。这在徐先生引用朱熹给林德久信中就说道:“昨在玉山学中,与诸生说话,司马宰令人录来。当时无人剧论,说得不痛快,归来偶与一朋友说,却说得详尽,因并两次所言,录以报之。”就将地点说明了,玉山学中,就是指玉山县学。朱熹在《讲义》开首便有“熹此来得观学校鼎新”,就明言县学。因此说,将地点认作怀玉山中的草堂书院,显然也就错了。
徐先生否认草堂书院“旧志所说为朱熹所建”是正确的,但对“有司及门人拓建书院”一句却没有说明,忽略了光绪版《江西通志》所言朱熹门人对草堂的建设作用。
明代嘉靖年间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在《怀玉山书院记》中说:“金刚峰下为怀玉寺,稍南,为草堂书院,宋朱子讲学其中。”没有指明朱熹讲学于草堂书院的具体时间,或为淳熙二年,或为淳熙九年,或为淳熙十五年,或为绍熙五年,未究其详。
方彦寿认为光绪《江西通志》称朱熹与陆九渊、汪应辰曾讲学其间,证据不足,“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笔者认为,朱、陆、汪同时讲学于其中,显然缺少有力证据,鹅湖之会是在淳熙二年五月二十八、九日至六月八日之间举行的学术交流,会期约十天,之后,未见朱熹和陆九渊往玉山见汪应辰当面论学,朱熹写信给吕祖谦已经表达清楚,此后也无机会与陆九渊聚首面论于玉山。但不排除汪应辰、朱熹、陆九渊三人不同时期分别讲学于其中的可能。
淳熙九年九月,朱熹卸任浙东提举,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由衢州常山来到信州玉山县留数日,凭吊汪应辰遗迹、流连怀玉山水,有玉山方面的徐文卿、徐焕、段钧、赵善期等人前来聚会。诗人赵蕃所作《成父书来,报朱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杖履为恨,辄成鄙句,寄斯远、彦章,且示成父》和《段元衡出示与晦翁九日登紫霄峰诗及手帖及贾十八兄诗,既敬读之,得三绝句》,诗末有“晦翁比自浙东归,过玉山留数日”。赵蕃所言的南山,在玉山县西北怀玉山山脚下。依诗人章泉之说,可给出怀玉山中草堂书院与朱熹的关系。
而淳熙十五年夏四月初四,朱熹到达玉山,至五月十七日方离开玉山,其间稽留四十余日,与众弟子及杨万里会见与讲论,亦有可能从容游览怀玉山、讲学于怀玉中。但绍熙五年朱熹只讲学于县庠,未见有登览怀玉山讲学的记载。
因此,朱熹在怀玉山草堂书院的讲学活动,最明确的时间应是淳熙九年重阳节,最不能忽略的是淳熙十五年夏间。
附注
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57—58页。 ②星球地图出版社编:《中国地图册》,星球地图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①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748—749页。
①《朱子语类》卷120。
①俞文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①(清)吴庆坻:《蕉廊脞录·曇山朱文公题名》。②洪嘉植:《朱熹年谱》。
①《朱子全书》卷74。
①光绪《江西通志》卷82。
①《朱子全书·答吕伯恭书三十五》。②《朱子全书》卷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