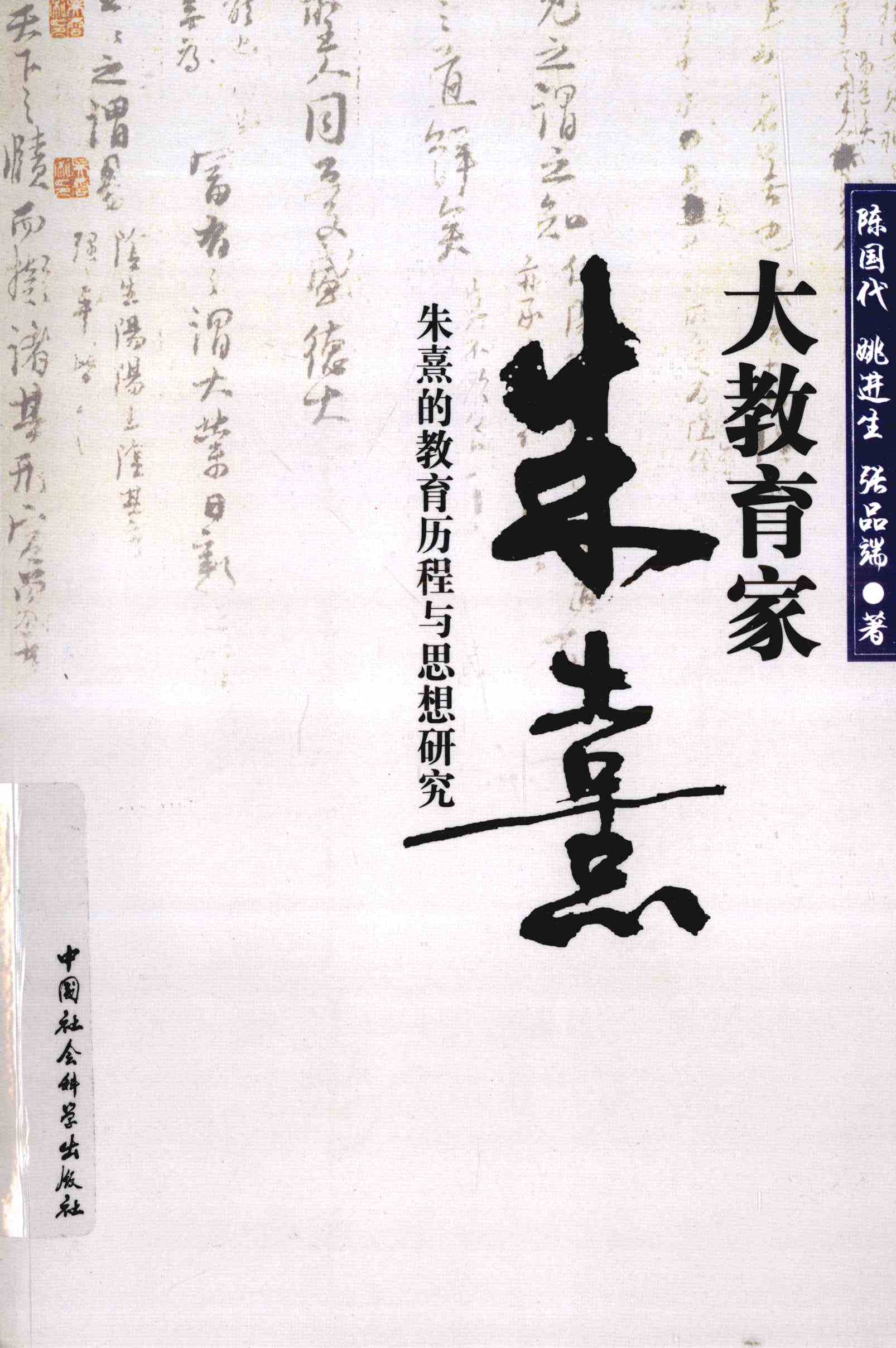第四节 匡庐山下旌旗举 白鹿洞规天道明
| 内容出处: | 《大教育教朱熹》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0098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匡庐山下旌旗举 白鹿洞规天道明 |
| 其他题名: |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讲学活动 |
| 分类号: | G40-09;B244.7 |
| 页数: | 17 |
| 页码: | 193-209 |
| 摘要: | 朱熹在离开泉州同安县主簿任之后,向朝廷申请奉祠得到准许,约有十五年的时间按规定领微薄的祠禄养家,将身心投入到注释经典古籍与教学课徒的活动中,先后在紫阳楼、六经堂、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讲学,与闽地学者、湖湘学者、浙东学者、金溪学者探讨学问,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待哺饥民偏恋德,老翁犹作小儿啼。篇首所举朱熹不愿出山为宦,并非居奇以自售,也非高蹈遁世,其长期不欲再宦自有其理由,不在此细加讨论。朱熹听从刘清之的劝说,颁布《晓谕兄弟争财产事》,使父子复合者数家,境内词讼锐减。当年九月,朱熹又任命学录杨日新为书院堂长,主持日常工作。 |
| 关键词: | 朱熹 白鹿洞书院 讲论活动 |
内容
朱熹在离开泉州同安县主簿任之后,向朝廷申请奉祠得到准许,约有十五年的时间按规定领微薄的祠禄养家,将身心投入到注释经典古籍与教学课徒的活动中,先后在紫阳楼、六经堂、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讲学,与闽地学者、湖湘学者、浙东学者、金溪学者探讨学问,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
淳熙三年(1176年)六月,参知政事龚茂良与吏部尚书韩元吉大力举荐朱熹,欲让朱熹出山入朝为官,而朱熹辞之不应。淳熙五年三月,史浩除右相,荐引朱熹,八月十七日尚书省下札除朱熹知南康军,朱熹辞不受,十月又命其径直赴南康任。十一月赵雄为右相,十二月及次年三月省札再催朱熹赴任。诸多朝臣如此重视举荐,朝廷如此再三催促,朱熹不得不领命上任,于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携带小儿子朱在、外甥魏愉起程,由门生黄榦、丁克、王翰(瀚)陪同,二月四日至信州铅山县,三月三十日到达位于鄱阳湖畔的南康军治所所在地星子县开始工作。在任两年多时间,至淳熙八年闰三月,朱熹因修举荒政有功,民无流殍,得到转官,改除直秘阁、江西提举而离任,淳熙八年四月十九日回到崇安五夫家。朱熹离开南康前,江东提举尤袤作诗《送朱晦庵南归》,诗云:二年摩手抚疮痍,思与庐山五老齐。合侍玉皇香案侧,却持华节大江西。鼎新白鹿诸生学,筑就长江万丈堤。待哺饥民偏恋德,老翁犹作小儿啼。
篇首所举朱熹不愿出山为宦,并非居奇以自售,也非高蹈遁世,其长期不欲再宦自有其理由,不在此细加讨论。而尤袤的这首送别诗,概括了朱熹两年来在南康军的为政之业绩,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本文将从朱熹执政与教育两大方面说之。朱熹在南康军的官宦政绩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年三月,五十岁的朱熹到南康任所。南康军管辖星子、都昌、新昌三县,本军治所设在星子县,其背负庐山云峰,前踞茫茫彭蠡。朱熹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
朱熹听从刘清之的劝说,颁布《晓谕兄弟争财产事》,使父子复合者数家,境内词讼锐减。
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诣旱伤田段地头,对账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县令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桑法》。翌年五月至七月,滴雨未下,严重干旱,土田龟裂,禾苗枯死,人心惶惶。朱熹究心措置赈灾。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至年底,已做好赈济准备。朱熹受辛弃疾帅湖南时提出“劫禾者斩,闭粜者配”八字荒政之法的启发,制订一套更加缜密的救政之法,从淳熙八年正月开始,在本军所辖的三县设三十五个济粜场,按等级分发救济粮食,让饥民度过年关与春荒,全活二十万民众。
教化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朱熹发布宽恤民力、敦厉风俗的牒文,委命僚属杨教授、毛司户负责,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境内的先贤遗迹进行收集整理并予以表彰。他们寻访陶侃、谢安、陶潜、周敦颐、司马暠、司马延义、熊仁赡、刘涣、刘恕、陈瓘、李常等人的事迹,作为敦化风俗的榜样。朱熹寻访陶侃、陈瓘的遗迹,分别为武功超卓的晋太傅谢安、高风亮节的征士陶潜、道学开山祖周敦颐立祠,修复司马暠、司马延义、熊仁赡、刘涣、刘恕的坟墓,旌表累世嫠妇守节的义门洪氏,把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作为说教的典范,来挽救衰世的颓风。淳熙六年五月刻印修订后的《太极通书》,在学宫讲堂东建成濂溪祠堂,以二程配享周敦颐,在讲堂西建五贤祠,奉祀陶潜、刘涣、刘恕、李常、陈瓘等,又注《孝经·庶人章》以示俗,“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朱熹“入学讲说,自《中庸》、《大学章句》外,又出《太极讲义》一编,以示学者。” 因此,朱熹在南康军任上的施政大纲就是减税免役以宽民力、厚教化以敦风俗、砥士风以美人伦,主要的业绩体现在注重民生、注重风化和注重教育上。朱熹在南康军的教育实践朱熹在南康军,注重教育,体现在要求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接受读经教育,还体现在整顿军学、修复白鹿洞书院以及亲自讲学上。
为了振兴儒教,与佛道争夺教育阵地,提倡宽松的讲学风气,朱熹把目光投注到书院上。于是,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着意要尽快修复毁于兵火、业已荒废的白鹿洞书院。这座书院曾经与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兵燹后栋宇荡然不存,只留下一片残败的废墟。古籍所载白鹿洞方位淳熙六年十月,朱熹带着僚属寻访白鹿洞遗址,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找到了遗址。白鹿洞在庐山五老峰南二十余里,这里秀峰环抱,远离市井尘嚣,是个群居讲学、隐遁著述的好处所,原为唐贞元中(785—805年)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避兵乱而隐居读书之处。
李氏曾养一白鹿自随。唐宝历中(825—827年)李渤升任江州刺史时,于原来读书处建筑台榭,取名白鹿洞。南唐升元中(937—943年)就白鹿洞修建校舍,扩大规模,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任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号称庐山国学。其后书院得到朝廷的重视不断发展,至北宋时改称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虽然规模不大,但学生自学读书、教师质疑问难、师生共同探讨学问等书院教学的基本特点已经形成,培养了大批人才,因此影响很大。后来,由于官方只重视南康军学建设而忽视对白鹿洞书院的投资与管理,使得白鹿洞书院逐渐冷落下来,以至于后来“而洞之书院遂废”。在朱熹看来,修复白鹿洞书院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之一。他在向朝廷提交的《申修白鹿洞书院状》中指出:“窃惟庐山山水之胜,甲于东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有不兴葺。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学精舍。又蒙圣朝恩赐褒显,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如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 于是,朱熹亲自主持书院修复工作,在门人刘清之、杨方的帮助下,由军学教授杨大法和星子县令王仲杰负责,白鹿洞书院很快得以修复,至淳熙七年三月十八日,建成屋宇二十余间,先招收生员二十人,增置学田赡养学员。朱熹自兼洞主,亲任导师,举行释菜仪式后正式执教讲学其中,当天开讲,“讲义只是《中庸》首章《中庸或问》中语。”后来朱熹还以洞主的名义出了一道《白鹿书堂策问》:孔子殁,七十子丧,杨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后其得肆,千有余年,诸生皆诵说孔子。而独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号为以道鸣者,然于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无称焉,或尊其功以为不在禹下。其归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数子者后议其前,或以为同门而异户,或无称焉,或以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与于斯道之传者。其于扬墨,或微议其失,或无称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说矣。朱熹要求学生认真思考后回答孟子是如何继承圣统的,以此来加强道统意识,强化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感,以宣扬儒家思想,与佛道抗争。
朱熹还亲自手书一副对联贴在白鹿洞的彝伦堂上: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仁智独得之天。
当年九月,朱熹又任命学录杨日新为书院堂长,主持日常工作。朱熹还请好友吕祖谦为之撰《白鹿洞书院记》,自己则作《白鹿洞赋》以明兴建书院的根本宗旨。后来在编排《朱子全书》时,置于前首为《虞帝庙迎送神乐歌词》,该赋仅次之。
朱熹还于淳熙八年三月上书奏请孝宗皇帝,请为书院赐额,又奏请朝廷赐予宋高宗御书《石经》及国子监刊刻的《九经注疏》及《论语》、《孟子》等书,①同时发文各地征集图书,向各路广求藏书,得到好友陈俊卿、陆游、钱佃、王师愈、尤袤、张子颜等官员的支持,陆续将书籍赠送,故白鹿洞书院收获颇丰。其中有个典型的例子,吉州庐陵人刘仁季,求朱熹为其亡父刘靖之作传,而赠以先人所藏《汉书》四十四通作为酬答,朱熹将此转赠给白鹿洞书院,藏之以备学者看读②。
特别有影响力的是朱熹制定了书院教育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文末,朱熹还加了按语: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按:古代书写由从右到左,竖向排版) 也许在淳熙六年春三月,朱熹在信州铅山观音寺与来访的陆九龄相聚面论,陆九龄已转变为学态度,每交谈,必引用《论语》为证,且告诉朱熹:“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今人自小即教做对,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皆坏其性质。某尝示欲做一小学规,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须有益。”其欲定学规之说,显然启发了朱熹。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该学规的真实含义,我们对文中相关文句的出处进行梳理。
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为: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原文为: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期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出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原文为: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乾损益动》第三十一) 处事之要。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则云: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原文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原文为: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表面上看,朱熹制定的这一著名的学规,多采自《中庸》、《论语》、《孟子》、《春秋》、《汉书》、《周敦颐文集》与董仲舒的名言以为伦常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看似简单,然其说明则讲明义理,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神髓,也是朱熹《四书》学的精华,故被广泛尊崇并推广,屡屡作为私人书院、官立学校的教规,成为历史上教育之金规玉律,影响不衰。
从朱熹所作的大量文章及吕祖谦的《白鹿洞书院记》,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动机、过程、规模、制度等等。而白鹿洞书院的前途与影响,还有赖于后继者的不懈努力。李燔、张洽、黄榦、陈宓为朱熹的得力门人,李燔、张洽二人相继为白鹿洞书院堂长,黄榦、陈宓讲学于其间。后儒胡居仁、王守仁、蔡宗兖、邹守益等人于白鹿洞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亦有不菲的贡献。
学规是各级学校管理的重要依据,宋代中央太学及州县学校、私立学校都有制定相应的学规进行管理。
太学是宋代的最高学府,设有国子祭酒、司业、博士、丞、主簿、正、录等学官,各级官员各司其职进行管理,使学校能正常运行。太学的学规是针对生徒犯错误及其错误的不同程度而制定的处罚措施,分为五等:一是关暇数月,不许出入;二是前廊关暇;三是迁斋,由一斋迁到另一斋,被迁入斋可接受亦可拒纳,若拒纳,则立告公堂,方许退还;四是居“讼斋”,自宿自省;五是罚以夏楚,屏斥终身不齿。另外,还规定外舍生如入学五年不预校订,及不曾请列国学解送或不曾公试入等第者,到年终检校时,酌即除籍。其管理模式显然有其严格的一面,否则,管不住众多的纨绔子弟。
州县学校之学规,也是对生徒入学、授课、告假及违纪等事项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学规,与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之学规存在很大的反差。
朱熹所制定的学规,即前面已经讲到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也称白鹿洞书院揭示或白鹿洞书院教条, “是教条,不是官司约束,”是典型的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大学教育的总纲领,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南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书院差不多都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白鹿洞教规也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教育纲领。其影响所及,远传海外的韩国、日本。本文择选部分历史人物对白鹿洞书院教规的重视与传播来展现该教规的影响。
刘爚,建宁府建阳人。登第入仕多年,于嘉定二年被召入朝议事,任吏部郎中,除浙西提刑,嘉定四年,调任国子监司业。当年四月,上殿奏乞开伪学之禁,以正士学本原,并请刊行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学宫教材,并将朱熹手订的《白鹿洞学规》颁示国子监和太学,从而为朱熹的学问由民间走向官学铺平了道路。
陈宓知南剑时建延平书院,依朱子的白鹿洞教规而行。
叶武子(?—1246年),字诚之、成之,号息庵,邵武人。淳熙十三年游乡校,学《周礼》于永嘉徐元德。绍熙二年与李方子叶贺孙等同受学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又为朱熹门人。补太学生。开禧三年,朝议有欲以韩侂胄首和敌者,诚之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国体何?”率同舍叩阍,以国体所系力争之。登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甲戌科进士第,历官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程,刻《四书集注章句》以授之。历国子正,知处州,有异政,入为宗学博士,仍依白鹿洞学规勉励宗子向学。 吴昌裔(1183—1240年),字季永,吴泳之弟,潼川人,迁居新安歙县向杲。早孤,与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时好,与兄得程颐、张载、朱熹诸儒书,研读不倦。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及第,闻汉阳守黄榦得朱熹之正学,往从之学。后调眉州教授,揭《白鹿洞学规》以教人。累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避,著直声。出为大理少卿,以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改知嘉兴府,历知赣、婺州,以宝章阁待制致仕。
上四人为宋代学者;下二人则为元代学者: 黎献,字子文,号拙翁,元季广州东莞人。性警敏,笃学问。弱冠授徒,一依紫阳白鹿洞学规以为教。
翁森,字秀卿,号一瓢,台州仙居人。宋亡,立志不仕,隐居教授。元至元年间,于县东南崇教里建安洲书院,取朱熹《白鹿洞学规》以为训,以儒术教化乡人,从学者甚众。翰林学士陈刚中曾为之作《安洲乡学记》。
薛瑄和胡居仁则是明代著名学者。
薛瑄(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平阳府河津人。少工诗赋,后从魏希文、范汝舟治理学,即尽焚所作诗赋。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及第,擢广东道御史。旋居父丧,悉遵古礼。宣德中除服,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正统元年,出为山东佥事提学,以《白鹿洞学规》开示诸生,亲为讲授。
胡居仁(1434—1484年),字叔心,号敬斋,饶州余干人。幼时聪敏异常,广涉群书。及壮,师事吴与弼,饱读儒家经典,尤致力于程朱理学,与陈献章、娄谅、谢复、郑侃等人交游,进行学术探讨。主张“以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平生致力于教育,于家乡南谷筑室讲学,又应提学使李龄、钟成之请,两次主讲白鹿洞书院,姚文灏又聘其为桐源书院讲师,从教二十余年,治学严谨,务求学以致用。手订学规,有《续白鹿洞学规》与《白鹿洞讲义》传世。
延至清代,亦有朱用纯、窦克勤、任德成等人推重《白鹿洞学规》。
朱用纯(1627—1699年),字致一,号柏庐,朱集璜之子,苏州府昆山人。始终未入仕,教授乡里,仿白鹿洞规,设讲约,从者皆兴起,授来学者以《小学》、《近思录》,确守程朱理学,知行并进,而诚于至敬。将朱熹平生治家言论,编成《治家格言》,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
窦克勤(1653—1708年),字敏修,号静庵、遯斋,河南柘城人。师事理学家汤试,试谓师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职,劝其就教职。又拜孙奇逢弟子耿介为师。选为泌阳教谕,立五社学,置之师,仿《白鹿洞学规》,订《泌阳学条规》,各设“规过劝善簿”,月朔考核。又立童子社学,授以《孝经》、《小学》、《四书》、《五经》等。
任德成(1693—1772年),字象元,苏州府吴江人。从游于任启运门下,宗朱子学说,平生尊奉朱熹《白鹿洞学规》检摄言行。尝取自汉迄明能与《白鹿洞学规》相互发明的先哲格言,辑为《读白鹿洞规大义》。
据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录》载,降至清末,德宗皇帝下诏建立京师大学堂,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还以“朱子白鹿洞揭示”及教员管理员学生规则榜示全堂。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遵守朱子学规。
在海外,有朝鲜李退溪尊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以教育学者。
李退溪即李滉(1501—1570年),字景浩,朝鲜李朝时人,著有《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圣学十图》、《启蒙传疑》、《三经四书释义》、《四端七情录》、《增补退溪全书》等。其出生于诗书官宦世家,在父兄的严格教育下,从小就受到了程朱性理文化的熏陶。其一生淡泊名利,超然于党争之外,以研究朱子学为毕生事业,创立退溪学派,建立四端七情说,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海东朱子”、“东方百世之师”,朝鲜儒学泰斗。他办伊山书院、陶山书堂,把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书院教育的基本理论根据。
受朝鲜李滉著作《自省录》的启发与影响,日本的山崎闇斋也开始研究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庆安三年(1650年)十一月作《白鹿洞学规集注》,与同志者讲习之。于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在日本逐渐传播开来。山崎闇斋(1618—1682年)字敬义,日本京都人。幼入佛寺,约二十五岁归儒后,笃信程朱理学,创立崎门学派,传播朱子理学,为德川幕府时期著名儒学大家。
就今日教育来看,朱熹所制定的学规依然有价值。在白鹿洞书院受学的学者从淳熙六年三月至淳熙八年四月,大约有近百名学者向朱熹问学或聆听大儒的教诲。朱熹作为白鹿洞的新洞主,在主持白鹿洞书院一年半的时间里,给四方而来的学者讲学,对“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
我们对朱熹文集、白鹿洞书院志、各地方志和庐山金石志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有包定、包扬、包约、蔡念成、蔡元定、曹建、曹彦纯、曹彦约、陈士直、陈秬、陈秠、陈克己、陈祖永、程端蒙、邓绹、邓絅、丁克、段钧、傅公弼、冯琦、郭植、胡泳、胡莘、胡子先、胡仲开、黄榦、黄灏、金朋悦、金去伪、李吕、李燔、李秉文、李辉、李深之、李埜、林用中、林允中、林夔孙、刘贲、刘清之、刘尧夫、刘孟容、刘允迪、刘仁季、吕炳、吕熠、吕焘、吕炎、吕焕、彭蠡、彭浔、彭方、彭楼、祁真卿、盛璲、万人杰、汪清卿、王阮、王光朝、王瀚、王仲杰、吴兼善、吴唐卿、许子春、熊兆、薛洪、严敬、杨方、杨三益、叶永卿、于革、余隅、余大雅、余洁、余宋杰、余琦、俞洁己、俞子寿、赵希汉、赵子明、张彦先、张扬卿、周谟、周仲亨、周仿、周颖、周颐、周得之、周伯熊、周直卿、僧志南;以及朱熹次子朱埜、小儿子朱在、外甥魏愉等,在南康军追随朱熹或问学于白鹿洞书院。朱熹要求门生探讨儒家学说,不要花精力谈论佛老之学,写诗以告诫:“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参与白鹿洞书院建设与管理的朱熹的僚属杨王休、杨大法、杨日新、王仲杰、毛大年、赵胜、郭坚,也是边工作边问学。这些学者来自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安徽等不同地区,后来又分散到各地,或从政,或从教,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宣扬与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的中坚力量蔡元定、杨方、黄灏、武臣张彦先(致远),后来在韩侂胄执政的庆元间被列入庆元党籍而遭受打击。
淳熙八年二月,陆九渊率其门生路谦亨、陆麟之、朱克家、周清叟、熊鉴、胥训实等数人从金溪到南康军访朱熹,朱熹则尽地主之谊,请陆九渊上白鹿洞书院开讲座。陆九渊在淳熙二年鹅湖之会之后,通过门生、陆九龄等作前导,与朱熹进行联系,当九龄死后,九渊主动到南康拜见朱熹,并请朱熹为其亡兄书写《墓志铭》。朱熹请陆九渊上白鹿洞书院开讲,陆氏讲论《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讲得透彻精彩,获得朱熹赞赏,当即表示要留下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刻石纪念。
淳熙八年闰三月二十八日,朱熹任满两周年离任,朝廷依陈俊卿、周必大之荐,除朱熹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领旨拜命,率领刘清之、张扬卿、王阮、周颐、林用中、赵希汉、陈祖永、祁真卿、吴兼善、许子春、胡莘、王光朝、余隅、陈士直、黄榦、张彦先、僧志南和书院诸生向庐山山北进发,到了太平兴国宫,有江州州学教授翁名卿同游,欧景文和二十多名诸生一起来迎,四月六日到达濂溪书堂,朝拜周敦颐遗像,周敦颐的曾孙周正卿、周彦卿、玄孙周焘设宴款待。朱熹在途与登堂的演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延伸。
北宋五子中,周敦颐是被朱熹推崇且得以亲临其讲学之所直接拜谒其遗像的唯一者。这当然是受限于赵宋江山的沦陷,南宋之人无法越过战事区直接到中原行祭祀活动,只有遥祭以寄托精神之不灭。我们还可以结合朱熹的大量著作来看朱熹对道学开山祖的敬仰之情。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在担任南康军知军期间,率先修复白鹿洞书院,招收生徒,聘请教师,制订学规,奏请赐额,征集图书,增置学田,亲自讲学,以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学者,受众甚多,这也使得白鹿洞书院成为办学的典范,特别是《学规》,影响更见深远。
从朱熹教育历程来划判,此期的书院建设与讲学活动,无疑是朱熹教育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淳熙三年(1176年)六月,参知政事龚茂良与吏部尚书韩元吉大力举荐朱熹,欲让朱熹出山入朝为官,而朱熹辞之不应。淳熙五年三月,史浩除右相,荐引朱熹,八月十七日尚书省下札除朱熹知南康军,朱熹辞不受,十月又命其径直赴南康任。十一月赵雄为右相,十二月及次年三月省札再催朱熹赴任。诸多朝臣如此重视举荐,朝廷如此再三催促,朱熹不得不领命上任,于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携带小儿子朱在、外甥魏愉起程,由门生黄榦、丁克、王翰(瀚)陪同,二月四日至信州铅山县,三月三十日到达位于鄱阳湖畔的南康军治所所在地星子县开始工作。在任两年多时间,至淳熙八年闰三月,朱熹因修举荒政有功,民无流殍,得到转官,改除直秘阁、江西提举而离任,淳熙八年四月十九日回到崇安五夫家。朱熹离开南康前,江东提举尤袤作诗《送朱晦庵南归》,诗云:二年摩手抚疮痍,思与庐山五老齐。合侍玉皇香案侧,却持华节大江西。鼎新白鹿诸生学,筑就长江万丈堤。待哺饥民偏恋德,老翁犹作小儿啼。
篇首所举朱熹不愿出山为宦,并非居奇以自售,也非高蹈遁世,其长期不欲再宦自有其理由,不在此细加讨论。而尤袤的这首送别诗,概括了朱熹两年来在南康军的为政之业绩,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本文将从朱熹执政与教育两大方面说之。朱熹在南康军的官宦政绩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年三月,五十岁的朱熹到南康任所。南康军管辖星子、都昌、新昌三县,本军治所设在星子县,其背负庐山云峰,前踞茫茫彭蠡。朱熹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
朱熹听从刘清之的劝说,颁布《晓谕兄弟争财产事》,使父子复合者数家,境内词讼锐减。
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诣旱伤田段地头,对账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县令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桑法》。翌年五月至七月,滴雨未下,严重干旱,土田龟裂,禾苗枯死,人心惶惶。朱熹究心措置赈灾。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至年底,已做好赈济准备。朱熹受辛弃疾帅湖南时提出“劫禾者斩,闭粜者配”八字荒政之法的启发,制订一套更加缜密的救政之法,从淳熙八年正月开始,在本军所辖的三县设三十五个济粜场,按等级分发救济粮食,让饥民度过年关与春荒,全活二十万民众。
教化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朱熹发布宽恤民力、敦厉风俗的牒文,委命僚属杨教授、毛司户负责,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境内的先贤遗迹进行收集整理并予以表彰。他们寻访陶侃、谢安、陶潜、周敦颐、司马暠、司马延义、熊仁赡、刘涣、刘恕、陈瓘、李常等人的事迹,作为敦化风俗的榜样。朱熹寻访陶侃、陈瓘的遗迹,分别为武功超卓的晋太傅谢安、高风亮节的征士陶潜、道学开山祖周敦颐立祠,修复司马暠、司马延义、熊仁赡、刘涣、刘恕的坟墓,旌表累世嫠妇守节的义门洪氏,把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作为说教的典范,来挽救衰世的颓风。淳熙六年五月刻印修订后的《太极通书》,在学宫讲堂东建成濂溪祠堂,以二程配享周敦颐,在讲堂西建五贤祠,奉祀陶潜、刘涣、刘恕、李常、陈瓘等,又注《孝经·庶人章》以示俗,“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朱熹“入学讲说,自《中庸》、《大学章句》外,又出《太极讲义》一编,以示学者。” 因此,朱熹在南康军任上的施政大纲就是减税免役以宽民力、厚教化以敦风俗、砥士风以美人伦,主要的业绩体现在注重民生、注重风化和注重教育上。朱熹在南康军的教育实践朱熹在南康军,注重教育,体现在要求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接受读经教育,还体现在整顿军学、修复白鹿洞书院以及亲自讲学上。
为了振兴儒教,与佛道争夺教育阵地,提倡宽松的讲学风气,朱熹把目光投注到书院上。于是,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着意要尽快修复毁于兵火、业已荒废的白鹿洞书院。这座书院曾经与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兵燹后栋宇荡然不存,只留下一片残败的废墟。古籍所载白鹿洞方位淳熙六年十月,朱熹带着僚属寻访白鹿洞遗址,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找到了遗址。白鹿洞在庐山五老峰南二十余里,这里秀峰环抱,远离市井尘嚣,是个群居讲学、隐遁著述的好处所,原为唐贞元中(785—805年)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避兵乱而隐居读书之处。
李氏曾养一白鹿自随。唐宝历中(825—827年)李渤升任江州刺史时,于原来读书处建筑台榭,取名白鹿洞。南唐升元中(937—943年)就白鹿洞修建校舍,扩大规模,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任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号称庐山国学。其后书院得到朝廷的重视不断发展,至北宋时改称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虽然规模不大,但学生自学读书、教师质疑问难、师生共同探讨学问等书院教学的基本特点已经形成,培养了大批人才,因此影响很大。后来,由于官方只重视南康军学建设而忽视对白鹿洞书院的投资与管理,使得白鹿洞书院逐渐冷落下来,以至于后来“而洞之书院遂废”。在朱熹看来,修复白鹿洞书院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之一。他在向朝廷提交的《申修白鹿洞书院状》中指出:“窃惟庐山山水之胜,甲于东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有不兴葺。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学精舍。又蒙圣朝恩赐褒显,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如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 于是,朱熹亲自主持书院修复工作,在门人刘清之、杨方的帮助下,由军学教授杨大法和星子县令王仲杰负责,白鹿洞书院很快得以修复,至淳熙七年三月十八日,建成屋宇二十余间,先招收生员二十人,增置学田赡养学员。朱熹自兼洞主,亲任导师,举行释菜仪式后正式执教讲学其中,当天开讲,“讲义只是《中庸》首章《中庸或问》中语。”后来朱熹还以洞主的名义出了一道《白鹿书堂策问》:孔子殁,七十子丧,杨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后其得肆,千有余年,诸生皆诵说孔子。而独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号为以道鸣者,然于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无称焉,或尊其功以为不在禹下。其归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数子者后议其前,或以为同门而异户,或无称焉,或以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与于斯道之传者。其于扬墨,或微议其失,或无称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说矣。朱熹要求学生认真思考后回答孟子是如何继承圣统的,以此来加强道统意识,强化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感,以宣扬儒家思想,与佛道抗争。
朱熹还亲自手书一副对联贴在白鹿洞的彝伦堂上: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仁智独得之天。
当年九月,朱熹又任命学录杨日新为书院堂长,主持日常工作。朱熹还请好友吕祖谦为之撰《白鹿洞书院记》,自己则作《白鹿洞赋》以明兴建书院的根本宗旨。后来在编排《朱子全书》时,置于前首为《虞帝庙迎送神乐歌词》,该赋仅次之。
朱熹还于淳熙八年三月上书奏请孝宗皇帝,请为书院赐额,又奏请朝廷赐予宋高宗御书《石经》及国子监刊刻的《九经注疏》及《论语》、《孟子》等书,①同时发文各地征集图书,向各路广求藏书,得到好友陈俊卿、陆游、钱佃、王师愈、尤袤、张子颜等官员的支持,陆续将书籍赠送,故白鹿洞书院收获颇丰。其中有个典型的例子,吉州庐陵人刘仁季,求朱熹为其亡父刘靖之作传,而赠以先人所藏《汉书》四十四通作为酬答,朱熹将此转赠给白鹿洞书院,藏之以备学者看读②。
特别有影响力的是朱熹制定了书院教育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文末,朱熹还加了按语: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按:古代书写由从右到左,竖向排版) 也许在淳熙六年春三月,朱熹在信州铅山观音寺与来访的陆九龄相聚面论,陆九龄已转变为学态度,每交谈,必引用《论语》为证,且告诉朱熹:“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今人自小即教做对,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皆坏其性质。某尝示欲做一小学规,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须有益。”其欲定学规之说,显然启发了朱熹。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该学规的真实含义,我们对文中相关文句的出处进行梳理。
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为: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原文为: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期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出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原文为: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乾损益动》第三十一) 处事之要。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则云: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原文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原文为: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表面上看,朱熹制定的这一著名的学规,多采自《中庸》、《论语》、《孟子》、《春秋》、《汉书》、《周敦颐文集》与董仲舒的名言以为伦常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看似简单,然其说明则讲明义理,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神髓,也是朱熹《四书》学的精华,故被广泛尊崇并推广,屡屡作为私人书院、官立学校的教规,成为历史上教育之金规玉律,影响不衰。
从朱熹所作的大量文章及吕祖谦的《白鹿洞书院记》,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动机、过程、规模、制度等等。而白鹿洞书院的前途与影响,还有赖于后继者的不懈努力。李燔、张洽、黄榦、陈宓为朱熹的得力门人,李燔、张洽二人相继为白鹿洞书院堂长,黄榦、陈宓讲学于其间。后儒胡居仁、王守仁、蔡宗兖、邹守益等人于白鹿洞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亦有不菲的贡献。
学规是各级学校管理的重要依据,宋代中央太学及州县学校、私立学校都有制定相应的学规进行管理。
太学是宋代的最高学府,设有国子祭酒、司业、博士、丞、主簿、正、录等学官,各级官员各司其职进行管理,使学校能正常运行。太学的学规是针对生徒犯错误及其错误的不同程度而制定的处罚措施,分为五等:一是关暇数月,不许出入;二是前廊关暇;三是迁斋,由一斋迁到另一斋,被迁入斋可接受亦可拒纳,若拒纳,则立告公堂,方许退还;四是居“讼斋”,自宿自省;五是罚以夏楚,屏斥终身不齿。另外,还规定外舍生如入学五年不预校订,及不曾请列国学解送或不曾公试入等第者,到年终检校时,酌即除籍。其管理模式显然有其严格的一面,否则,管不住众多的纨绔子弟。
州县学校之学规,也是对生徒入学、授课、告假及违纪等事项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学规,与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之学规存在很大的反差。
朱熹所制定的学规,即前面已经讲到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也称白鹿洞书院揭示或白鹿洞书院教条, “是教条,不是官司约束,”是典型的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大学教育的总纲领,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南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书院差不多都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白鹿洞教规也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教育纲领。其影响所及,远传海外的韩国、日本。本文择选部分历史人物对白鹿洞书院教规的重视与传播来展现该教规的影响。
刘爚,建宁府建阳人。登第入仕多年,于嘉定二年被召入朝议事,任吏部郎中,除浙西提刑,嘉定四年,调任国子监司业。当年四月,上殿奏乞开伪学之禁,以正士学本原,并请刊行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学宫教材,并将朱熹手订的《白鹿洞学规》颁示国子监和太学,从而为朱熹的学问由民间走向官学铺平了道路。
陈宓知南剑时建延平书院,依朱子的白鹿洞教规而行。
叶武子(?—1246年),字诚之、成之,号息庵,邵武人。淳熙十三年游乡校,学《周礼》于永嘉徐元德。绍熙二年与李方子叶贺孙等同受学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又为朱熹门人。补太学生。开禧三年,朝议有欲以韩侂胄首和敌者,诚之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国体何?”率同舍叩阍,以国体所系力争之。登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甲戌科进士第,历官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程,刻《四书集注章句》以授之。历国子正,知处州,有异政,入为宗学博士,仍依白鹿洞学规勉励宗子向学。 吴昌裔(1183—1240年),字季永,吴泳之弟,潼川人,迁居新安歙县向杲。早孤,与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时好,与兄得程颐、张载、朱熹诸儒书,研读不倦。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及第,闻汉阳守黄榦得朱熹之正学,往从之学。后调眉州教授,揭《白鹿洞学规》以教人。累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避,著直声。出为大理少卿,以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改知嘉兴府,历知赣、婺州,以宝章阁待制致仕。
上四人为宋代学者;下二人则为元代学者: 黎献,字子文,号拙翁,元季广州东莞人。性警敏,笃学问。弱冠授徒,一依紫阳白鹿洞学规以为教。
翁森,字秀卿,号一瓢,台州仙居人。宋亡,立志不仕,隐居教授。元至元年间,于县东南崇教里建安洲书院,取朱熹《白鹿洞学规》以为训,以儒术教化乡人,从学者甚众。翰林学士陈刚中曾为之作《安洲乡学记》。
薛瑄和胡居仁则是明代著名学者。
薛瑄(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平阳府河津人。少工诗赋,后从魏希文、范汝舟治理学,即尽焚所作诗赋。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及第,擢广东道御史。旋居父丧,悉遵古礼。宣德中除服,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正统元年,出为山东佥事提学,以《白鹿洞学规》开示诸生,亲为讲授。
胡居仁(1434—1484年),字叔心,号敬斋,饶州余干人。幼时聪敏异常,广涉群书。及壮,师事吴与弼,饱读儒家经典,尤致力于程朱理学,与陈献章、娄谅、谢复、郑侃等人交游,进行学术探讨。主张“以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平生致力于教育,于家乡南谷筑室讲学,又应提学使李龄、钟成之请,两次主讲白鹿洞书院,姚文灏又聘其为桐源书院讲师,从教二十余年,治学严谨,务求学以致用。手订学规,有《续白鹿洞学规》与《白鹿洞讲义》传世。
延至清代,亦有朱用纯、窦克勤、任德成等人推重《白鹿洞学规》。
朱用纯(1627—1699年),字致一,号柏庐,朱集璜之子,苏州府昆山人。始终未入仕,教授乡里,仿白鹿洞规,设讲约,从者皆兴起,授来学者以《小学》、《近思录》,确守程朱理学,知行并进,而诚于至敬。将朱熹平生治家言论,编成《治家格言》,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
窦克勤(1653—1708年),字敏修,号静庵、遯斋,河南柘城人。师事理学家汤试,试谓师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职,劝其就教职。又拜孙奇逢弟子耿介为师。选为泌阳教谕,立五社学,置之师,仿《白鹿洞学规》,订《泌阳学条规》,各设“规过劝善簿”,月朔考核。又立童子社学,授以《孝经》、《小学》、《四书》、《五经》等。
任德成(1693—1772年),字象元,苏州府吴江人。从游于任启运门下,宗朱子学说,平生尊奉朱熹《白鹿洞学规》检摄言行。尝取自汉迄明能与《白鹿洞学规》相互发明的先哲格言,辑为《读白鹿洞规大义》。
据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录》载,降至清末,德宗皇帝下诏建立京师大学堂,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还以“朱子白鹿洞揭示”及教员管理员学生规则榜示全堂。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遵守朱子学规。
在海外,有朝鲜李退溪尊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以教育学者。
李退溪即李滉(1501—1570年),字景浩,朝鲜李朝时人,著有《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圣学十图》、《启蒙传疑》、《三经四书释义》、《四端七情录》、《增补退溪全书》等。其出生于诗书官宦世家,在父兄的严格教育下,从小就受到了程朱性理文化的熏陶。其一生淡泊名利,超然于党争之外,以研究朱子学为毕生事业,创立退溪学派,建立四端七情说,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海东朱子”、“东方百世之师”,朝鲜儒学泰斗。他办伊山书院、陶山书堂,把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书院教育的基本理论根据。
受朝鲜李滉著作《自省录》的启发与影响,日本的山崎闇斋也开始研究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庆安三年(1650年)十一月作《白鹿洞学规集注》,与同志者讲习之。于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在日本逐渐传播开来。山崎闇斋(1618—1682年)字敬义,日本京都人。幼入佛寺,约二十五岁归儒后,笃信程朱理学,创立崎门学派,传播朱子理学,为德川幕府时期著名儒学大家。
就今日教育来看,朱熹所制定的学规依然有价值。在白鹿洞书院受学的学者从淳熙六年三月至淳熙八年四月,大约有近百名学者向朱熹问学或聆听大儒的教诲。朱熹作为白鹿洞的新洞主,在主持白鹿洞书院一年半的时间里,给四方而来的学者讲学,对“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
我们对朱熹文集、白鹿洞书院志、各地方志和庐山金石志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有包定、包扬、包约、蔡念成、蔡元定、曹建、曹彦纯、曹彦约、陈士直、陈秬、陈秠、陈克己、陈祖永、程端蒙、邓绹、邓絅、丁克、段钧、傅公弼、冯琦、郭植、胡泳、胡莘、胡子先、胡仲开、黄榦、黄灏、金朋悦、金去伪、李吕、李燔、李秉文、李辉、李深之、李埜、林用中、林允中、林夔孙、刘贲、刘清之、刘尧夫、刘孟容、刘允迪、刘仁季、吕炳、吕熠、吕焘、吕炎、吕焕、彭蠡、彭浔、彭方、彭楼、祁真卿、盛璲、万人杰、汪清卿、王阮、王光朝、王瀚、王仲杰、吴兼善、吴唐卿、许子春、熊兆、薛洪、严敬、杨方、杨三益、叶永卿、于革、余隅、余大雅、余洁、余宋杰、余琦、俞洁己、俞子寿、赵希汉、赵子明、张彦先、张扬卿、周谟、周仲亨、周仿、周颖、周颐、周得之、周伯熊、周直卿、僧志南;以及朱熹次子朱埜、小儿子朱在、外甥魏愉等,在南康军追随朱熹或问学于白鹿洞书院。朱熹要求门生探讨儒家学说,不要花精力谈论佛老之学,写诗以告诫:“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参与白鹿洞书院建设与管理的朱熹的僚属杨王休、杨大法、杨日新、王仲杰、毛大年、赵胜、郭坚,也是边工作边问学。这些学者来自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安徽等不同地区,后来又分散到各地,或从政,或从教,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宣扬与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的中坚力量蔡元定、杨方、黄灏、武臣张彦先(致远),后来在韩侂胄执政的庆元间被列入庆元党籍而遭受打击。
淳熙八年二月,陆九渊率其门生路谦亨、陆麟之、朱克家、周清叟、熊鉴、胥训实等数人从金溪到南康军访朱熹,朱熹则尽地主之谊,请陆九渊上白鹿洞书院开讲座。陆九渊在淳熙二年鹅湖之会之后,通过门生、陆九龄等作前导,与朱熹进行联系,当九龄死后,九渊主动到南康拜见朱熹,并请朱熹为其亡兄书写《墓志铭》。朱熹请陆九渊上白鹿洞书院开讲,陆氏讲论《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讲得透彻精彩,获得朱熹赞赏,当即表示要留下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刻石纪念。
淳熙八年闰三月二十八日,朱熹任满两周年离任,朝廷依陈俊卿、周必大之荐,除朱熹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领旨拜命,率领刘清之、张扬卿、王阮、周颐、林用中、赵希汉、陈祖永、祁真卿、吴兼善、许子春、胡莘、王光朝、余隅、陈士直、黄榦、张彦先、僧志南和书院诸生向庐山山北进发,到了太平兴国宫,有江州州学教授翁名卿同游,欧景文和二十多名诸生一起来迎,四月六日到达濂溪书堂,朝拜周敦颐遗像,周敦颐的曾孙周正卿、周彦卿、玄孙周焘设宴款待。朱熹在途与登堂的演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延伸。
北宋五子中,周敦颐是被朱熹推崇且得以亲临其讲学之所直接拜谒其遗像的唯一者。这当然是受限于赵宋江山的沦陷,南宋之人无法越过战事区直接到中原行祭祀活动,只有遥祭以寄托精神之不灭。我们还可以结合朱熹的大量著作来看朱熹对道学开山祖的敬仰之情。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在担任南康军知军期间,率先修复白鹿洞书院,招收生徒,聘请教师,制订学规,奏请赐额,征集图书,增置学田,亲自讲学,以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学者,受众甚多,这也使得白鹿洞书院成为办学的典范,特别是《学规》,影响更见深远。
从朱熹教育历程来划判,此期的书院建设与讲学活动,无疑是朱熹教育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附注
①《朱子全书》卷99。②曹彦约:《昌谷集》卷20,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①《朱子全书·答吕伯恭书八十五》。
①《朱子全书》卷74。白鹿洞书院(李梦阳手书)①邓刚、李淑兰:《庐山国学与白鹿洞书院的课程设置》所举九经为五代中冯道等人主持刻印的《诗》、《书》、《易》、《礼记》、《礼仪》、《周礼》、《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参见闵正国主编的《中国书院论坛》第三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②吴怿:《白鹿洞书院藏书述略》所言有误,参见闵正国主编《中国书院论坛》第三辑,第206页。
①《勉斋集·朱子行状》。
相关地名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