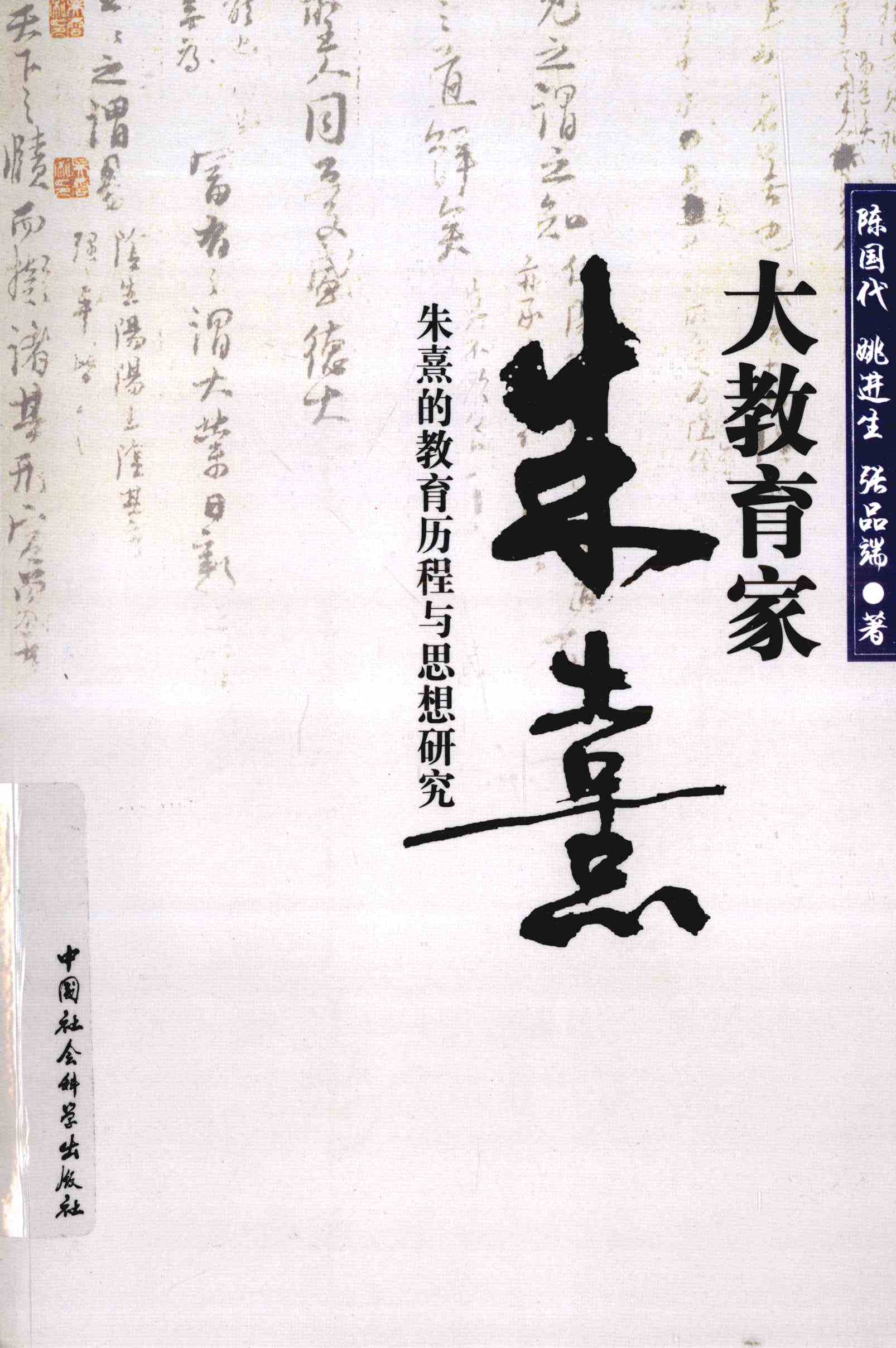第七节 温陵佛事寻常有 野店子规格外亲
| 内容出处: | 《大教育教朱熹》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0064 |
| 颗粒名称: | 第七节 温陵佛事寻常有 野店子规格外亲 |
| 其他题名: | 朱熹在泉南讲学活动拾零 |
| 分类号: | G40-09;B244.7 |
| 页数: | 14 |
| 页码: | 103-116 |
| 摘要: | 本文则采撷其在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地的教育活动之花絮以飨读者。朱熹的读书与访学活动绍兴二十六年春,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朱熹寓居剧头铺,弄明白了明道先生程颢解说“朱熹向旅馆中人借得《孟子》一书,朱熹又访得泉州人曾恬(乃程门高弟上蔡先生谢良佐的弟子),这是朱熹进士及第之后辗转师事延平先生李侗期间在泉州攻读圣贤书(儒家经典著作)、接续二程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时期。朱熹初仕泉州同安县主簿,向惠安县丞郑昭叔讨教行经界法的经验,同安主簿朱熹登其门拜访,朱熹便与友生讲习。 |
| 关键词: | 朱熹 泉南 讲学 |
内容
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以城北泉山而得名,旧亦称温陵。南宋时泉州管辖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同安诸县。
绍兴二十三年至绍熙二年(1 153—1 191年)年间,朱熹或因仕宦、或因私交,步履多涉泉州之境,往来泉州各地,开展讲学活动,其任同安主簿时讲学活动,已有专章介绍,在此不复。本文则采撷其在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地的教育活动之花絮以飨读者。朱熹的读书与访学活动绍兴二十六年春,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由泉州府抽调到府,分配任务后,被派往德化按事。朱熹寓居剧头铺,春寒夜冷,借着烛光苦读《论语》,闻杜鹃啼叫到天明,弄明白了明道先生程颢解说“子夏之门人小子”章的意思而沾沾自喜。
绍兴二十六年八月上旬,朱熹到泉州府等待离任的批文。在泉州官邸,朱熹向旅馆中人借得《孟子》一书,潜心研读,终于晓得“养气”一章的语脉,为后来集解《孟子》奠定了基础。朱熹又访得泉州人曾恬(乃程门高弟上蔡先生谢良佐的弟子),从其家获得谢上蔡语录,潜心研读。这是朱熹进士及第之后辗转师事延平先生李侗期间在泉州攻读圣贤书(儒家经典著作)、接续二程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时期。
朱熹初仕泉州同安县主簿,工作认真,清查版籍田税时发现许多问题,找到根结所在,在于经界之举未行,欲行经界以正本原。朱熹后来回顾说:“熹绍兴二十三、四年间,备员泉州同安主簿,是时已见本州不曾经界。县道催理税物,不登乡司,例以逃绝为词,官司便谓不可追究。徐考其实,则人户虽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处,但或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为邻至宗亲后来占据,阴结乡吏,隐而不言耳。固尝画策,以请于县。一时均割虽亦颇多,然本源未正,弊随目生,终不能有以为久远之利。”于是在当年秋收后,特地到泉州所属的惠安县城,向惠安县丞郑昭叔讨教行经界法的经验。
朱熹在同安担任主簿,听说邻县永春有个贤令尹黄瑀,治县有政声,特别是其公廉强介,察见微隐,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他县民有冤讼,率请委公以决。其条教科指,操验稽决,人皆传诵以为法。其禁令要束,大抵皆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之意。其言明白简切,其达之也,远近幽隐,无不暨焉。黄璃(1109—1168年),字德藻,福州府长乐县青山人氏,迁居闽县。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四年,知泉州永春县。同安主簿朱熹登其门拜访,见令尹正危坐堂上,批阅学宫弟子课程,庭中阒然无人声。朱熹“问公所以为此者,公不鄙,告语甚悉”,受益匪浅。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仕于同安满四周年,替任的人终未至,罢归,十一月又到泉州住陈良杰家数月,命友生之嗜学者与居,名室为“畏垒庵”,与陈养正、吕少卫等游,当年十二月五日作《恕斋记》。“恕斋”是陈养正读书之堂,吕少卫题名,养正则请朱熹为之作记。在畏垒庵,有嗜学者相伴,朱熹便与友生讲习,讲习经典著作,探讨儒家思想之奥蕴,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朱熹在同安县学讲学活动的延伸。
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初,朱熹南下福州携门人林用中同往泉州,十月下旬,朱、林到后,与休斋陈知柔追游于莲花峰、九日山、凉峰、凤风山、云台山之间。在泉州,多与泉中旧识、雅士如许升、黄伟优游、讲论。又与陈知柔、黄维之一起前往泉州吊唁傅自得。在此过程中,朱熹向追随者讲授儒家思想。朱熹在泉州各地的讲学活动乾隆《泉州府志·学校》序中有曰:“学校之设,以培养人才而固邦本,广以习之,优以奖之,拜圣亲师,罽以约束之。历代以来,制寖备矣。泉自常衮倡学,欧阳詹应其选,迨后来朱紫阳过化之区,蔡文庄诞生之地,跻于前哲配享庙廷,所谓瓜瓞之绵,其后愈大者也。”可见朱熹的教化之功,大矣! 在今泉州市区北门模范巷第三医院内,有抬匾式石坊表横梁,上刻有行楷“小山丛竹”、“晦翁书”字样。朱熹在淳熙元年甲午(1174年)四十五岁时方用“晦翁”之字,以“晦翁书”三字看,此为朱熹中晚年的墨迹,最大的可能是淳熙间旧地重游时所题。
朱熹早在离开同安主簿任之前,曾数至泉州郡城,抵则必登城隍庙后小山,称其山川之美,山上有亭,亭边种竹,朱熹称小山丛竹亭,与同游者讲学论道于其中。这是朱熹在担任同安主簿兼管学事期间讲学活动的延伸。由于朱熹讲学的方式方法不同寻常,讲问内容超越举子应试范围,对培养学者独立思考、人生信仰、价值取向有莫深的影响,许多人喜欢听其课,朱熹受聘讲学的机会也多,特别在类似赋闲的等待继任者的时间内,朱熹讲学于泉州城周围的书堂、精舍之属,将其早期思想传授给泉州的士子们。
明代嘉靖年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建小山丛竹亭,更名“过化”,且镂刻朱熹遗像以崇之。清康熙四十年,通判徐之霖于府城隍庙旁建书院——小山丛竹书院,并亲自撰《重兴朱夫子小山丛竹亭记》。
朱熹平生至少有三次到永春县。第一次是在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十二月,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期间,曾奉泉州府檄往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一带公干,顺便访永春县令黄璃,主动向其学习戢吏奸、恤民隐的为官之法。第二次是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九月。当年七月朱熹任同安簿三年秩满,八月在泉州府等候朝廷批书之际,游历泉州府永春县,到永春岱山岩、大剧铺等地访问同年进士苏升,与故交陈知柔登环翠亭。第三次是在淳熙十年初冬间朱熹再游永春,访同年进士陈光,得与陈知柔讲学于怀古堂,登临环翠亭,赋诗唱和,其乐融融。朱熹喜欢游山水,交名流,其往游永春访贤问儒,乃为第一要义。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晚春,二十七岁的朱熹奉檄从同安往外邑体究公事,即出差到德化县,在《朱子语类》卷49、卷104中均有此次外出的记载。
朱熹奉檄走外邑体究公事的时间在绍兴二十六年春三月,而诗中讲一官今是五年期,从绍兴二十三年算起,朱熹仕泉南满五年应是在绍兴二十七年,实际上此“五年”为虚指。这段时间,是朱熹尊延平李侗先生之意,苦读儒家经典著作《孟子》的时期,是在泉南佛国觉醒而始弃佛崇儒的关键时期。五代至北宋时期,古典经学衰微没落,给佛教和道教的复兴繁盛留下广大的文化空间。北宋诸帝王对佛老的提倡,更是助长了佛老思想的蔓延与浸润,使得人们精神委靡,对江山沦陷、二帝蒙辱而不思报复,登上帝王宝座的赵构日夜都怕谈恢复、迎二帝归,一旦迎回二帝便会动摇自己主宰江山的统治地位,而攀附于赵构的群小也怕失去荣华富贵的享受,于是高唱儒佛道兼修并行,士大夫们心醉神迷于佛老说教,以佛道文化作为儒文化的两翼,在沉闷的空气中悠悠飞翔,而伴随的是人心败坏,社会退化,弊端百出,民不聊生。朱熹师事武夷三先生后,曾有出入佛老十余年的心路历程,在同安为官期间,面对现实生活,开始渐渐相信不是提倡贪生畏死的佛老之学,而是提倡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才是拯救南宋衰世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支柱。这一觉醒,对于朱熹来说十分重要。他任县簿兼主学事,所以将许多精力花在整顿县学教育上,希望通过振兴儒学来解决社会问题,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而改变社会现状。朱熹曾多次到晋江石井(今安海)寻访其父旧事,拜访父执,与当地的名流耆士讲论经义,勉劝镇人为学,把良好的为学风气带到了安海,而使民沾其德,咸知向学。
绍熙二年(1191年)四月底,朱熹辞任漳州太守归,北过晋江,端午节在洛阳下生院为叶仲微、叶德符父子慕堂诗作跋。其时既有大批的追随者,也有当地士子问学,故说朱熹对泉南、对安海的教育是有重大的贡献。于是后来有人建石井书院、立朱祠作为纪念朱松、朱熹、朱在祖孙三代的重要场所。
朱熹于绍兴间仕于同安、淳熙间吊唁泉州友人、绍熙间官于漳州,皆经过惠安之境。惠安城北门外有泗州,其位于主要交通干线。据史料记载,从云峰山到泗州山都是极为兴盛的佛教圣地。泗洲山麓有座著名的德济庵,该庵始建于唐朝咸通年间,因“有僧得浮木,夜有光,刻为佛像,立精庐奉之”。其后屡有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以至有前后三殿、拜亭、制药司、织做司等建筑群,鼎盛时比丘尼达99人。庵堂依山傍石,后有天然石洞,洞内石壁刻有诗文;上有观音岩,岩上雕刻观音像。山顶巨石有“天开岩”及“山海奇观”等巨幅手书石刻。
绍熙二年正月,朱熹以丧嫡长子之痛请求辞官,四月底得旨允许辞官回家。有资料表明,廖德明与陈易、郑可学、周弼、蔡念诚等人同期随从朱熹北归,闻朱熹论学问传授之次第。五月在惠安泗州,聆听朱熹论儒释之异,即“儒理实,佛理空”。自从佛教进驻中土,便快速滋长起来,与本土文化进行较量与领地的争夺,遭到儒家学者的普遍性批评而时有收敛,但在南宋,由于士大夫们推波助澜,帝王不断分封各地已故高僧之头衔,各地名山遍立寺院,达官贵人沉迷佛事,庶民也燃香点烛虔诚膜拜,整个社会风气低迷。
朱熹秉承二程辟佛之说,平生常与学者论儒释之异,以警醒受学者。魏以降,儒家学说受到佛道的挑战,儒释道三家之学开始了互相排斥到逐步融合的进程。至唐宋时期,道学影响减弱,而佛学影响由于帝王和许多读书人的介入与鼓动,则成扩张之势。士大夫崇佛之风日益浓烈,特别是许多人出入佛老,美其名曰儒释道三者兼修,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儒者谈禅论道,释老广交上层社会,大有与儒学争夺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之势。朱熹的前辈、同辈中也不乏佛老的信徒,故早年研读释老之书的朱熹,在受李侗的指教后,主动将二氏之书搁起,潜心于儒家学说以明为人之大本,为后来大力辟佛、特别是辟禅奠定基础。朱熹的排佛思想,在乾道、淳熙间不断与人论辩、不断反思、不断总结自己学问的过程中达到高潮,并写进《四书集注》中的相关章节里。
朱熹的排佛思想还形成一个体系,朱子学专家束景南先生总结说该体系包含有三个内在层次:一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迷信,他是视为愚妄彻底否定,佛教以世俗宗教迷信所宣扬的一切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极乐世界、吃斋礼佛、念经成佛等等,他都一概摈弃:二是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他是作为异端从总体上排斥,即他所说的“大本不同”,但在个别观点上同儒说相合或部分相合的则加以改造吸收,如静坐之于主敬,禁欲之于人欲,论性之于论心,论心之于论意之类;三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哲学,他是注重吸取其缜密的思辨方法,用来表述和论证儒家的命题、观点与思想。朱熹辟佛斥道,更深一层的意义,恐怕是对北宋诸帝王大力提倡佛道进行的批判。没有统治者大力提倡培植,佛道就不会无限制地扩张、渗透,民心不会丧乱,士大夫也不会贪生惧死,北宋也不会轻易被灭亡。南宋帝王不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依然秉承祖宗遗旨,甚至将和议确立为国策,帝王将相贪生怕死而求苟安,士林中弥漫着贪惰恶习,志士恢复大计屡遭打压,士气由此而一蹶不振,亡国之势已露端倪。
朱熹过惠安,参观庵寺,见佛事鼎盛而人易被其玄说所迷,而发辟佛之说。在《朱子语类》卷第126论释氏中,廖德明记录:“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包扬则记曰:“佛以空为见,其见已错,所以错。”以空而言,客观存在的、人眼所见的,皆为空,人活着有何意义?佛存在又有何意义?这种学说,很容易导致人的思维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所以,朱熹不能不在教导士子时反复论说儒佛之异。庆元二年二月,朱熹在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为向浯《遗戒》作跋,仍在倡导抵触佛教为亡者设道场的末俗之陋。
朱熹是儒家思想的卫道者,其倡人伦、守礼法,要求人们诚心正意,要求人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志有为,而不似道家追求个人的长生不老的一味贪生,也不似僧徒将自身看成是个寄生的臭皮囊的虚无幻灭,其教人从日常生活中体认天理之所在,把握好人活世上的方向,让人脚踏实地地生活在现实的世界。朱熹的泉州籍门人朱熹的教学活动,为泉州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其门人有同安籍的许升、王力行、许子春、陈齐仲、戴迈、吕侁、杨宋卿;永春籍的陈易;南安籍的蔡和、杨景陆、诸葛廷瑞、诸葛廷材、李亢宗;惠安籍的刘镜、张巽;晋江籍的杨至、杨履正、高禾、林峦、傅伯成、傅伯寿、傅伯拱等,陈景初、陈景仁、储用等人也属朱熹门人之列。在此对这些人资料做些简单介绍。
许升(1141—1185年),字顺之,号存斋,许漠之子,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其年方十三岁,到县学拜朱熹为师。许升学习用功,专心致志,深得喜欢。绍兴二十八年随朱熹到崇安五夫继续求学,覃思研精,学力大究,九月卒业归家。后遍交四方之士,论道肄业。隆兴至乾道初,参与朱熹的儒佛争论。乾道二年秋末,朱熹《答许顺之》信中有新作《方塘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淳熙元年,许升到建阳寒泉精舍续学。淳熙十年十月,朱熹与林用中至泉州时,其多从游,故曰其是朱熹得意门生,也是朱熹宣传儒学、创建理学的得力助手,有紫阳始教之高弟的美称。在家乡办存斋书堂,广招学士,培养雕琢成器之才。曾尊师旨意,校订《程氏语录》。著有《孟子说》、《礼记文解》、《易解》等。淳熙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朱熹作《祭许顺之文》。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朱熹为同安县主簿期间的入门弟子。乾道四年八月参与讨论观过知仁之说。淳熙间与陈易、杨至、杨履正、刘镜皆从朱熹学。绍熙二年续学于漳州,苦学善问,深得旨趣,被朱熹品评为“明敏有余而少持重”,受朱熹邀请参与校订《二程遗书》。著有《朱子传授支派图》、《辛亥问答》等。
许子春,字景阳,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于泉州同安县学受学于朱熹。淳熙八年就教于九江濂溪书堂,同年闰三月,与朱熹等人同游寻真观。随后,朱熹卸任南康太守时畅游庐山,其与刘清之、张扬卿、王阮、周颐、林用中、赵希汉、陈祖永、吴兼善、祁真卿、胡莘、王朝、余隅、陈士直、黄榦、张彦先、僧志南等人陪同。朱熹有书信致之。
陈齐仲,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间在同安受学于任县主簿的朱熹。乾道二年,致书朱熹问格物致知等问题,朱熹作《答陈齐仲》复其所问。后参与修订朱熹的《孟子集解》。
杨宋卿,泉州府同安人。县学诸生,专攻诗赋。绍兴二十四年问学朱熹于同安县学,后与朱熹讨论诗学,朱熹有《答杨宋卿》书。
傅伯成(1143—1226年),字景初,号竹隐,傅自得次子,泉州晋江人。绍兴间年尚小,听从父命拜同安主簿朱熹为师。后登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第,调连江尉。试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历知闽清县、连江县。淳熙元年,傅自得改知建宁府,其侍父于侧,再问学于朱熹。庆元初,召为将作监,进太府寺丞。庆元三年以朝散大夫知漳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朱熹之意而遵行之,创惠民局以济民病,革优人淫戏。后历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成都路提点刑狱。入为工部侍郎,开禧间以沮开边出为湖广总领。反对韩侂胄诋毁大儒,又反对韩侂胄用兵,抵罪。嘉定元年官左谏议大夫,抗疏十有三,皆军国大义。左迁权吏部侍郎,嘉定二年,知建宁府,有治声,后知镇江府,全活饥民甚众。嘉定八年除宝谟阁直学士,寻加宝文阁学士、龙图阁学士。著有《傅忠简奏议》、《耋志》、《竹隐居士集》等。宝庆二年卒,谥忠简。陈宓作《祭傅忠简文》,刘克庄作《龙学竹隐傅公行状》。
傅伯寿(1138—1223年),字景仁,傅自得长子,绍兴间拜同安主簿朱熹为师。登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第,乾道八年再举博学宏词科。淳熙二年为著作佐郎,次年九月除著作郎。淳熙四年六月作为龚茂良党人被放罢,当年九月,与袁枢、梁瑑、吴英等人访朱熹于武夷山下,并共游九曲溪。淳熙十五年至绍熙元年初为漳州太守,以公帑刻朱熹的《楚辞叶韵》。绍熙元年除礼部郎中,绍熙三年,出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绍熙五年,改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因朱熹以其为故家子弟而不荐举之,遭其怨恨,后投韩侂胄,致身通显。庆元元年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宁宗命,制告词给朱熹,告词中有“大逊如慢,小逊如伪”等语,其后,小人始敢直诋朱熹。其弟伯成屡引义责之,卒不听。庆元六年,出知建宁府,朱熹殁后,不许生徒前往建阳送葬。嘉泰元年六月放罢。次年,为翰林学士。三年,为吏部尚书,兼秘书省检阅文字,兼实录院修撰。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主修《高宗实录》、《孝宗实录》、《光宗实录》,著有《傅枢密文集》。 林峦,泉州晋江人。绍兴二十三年为同安县学诸生,刻意词章,拜同安主簿朱熹为师学习。其能推所闻以讲学闾里。乾道四年参与校订《二程遗书》。曾与朱熹书信往来,朱熹作《答林峦书》二通,劝其不要刻意词章,回到经学义理的正路上。
高禾(1156—1225年),字颖叔,泉州府晋江人。登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进士第,历知福清、仙游、惠州。绍熙间倅漳州,禾执弟子礼问学于漳州知州朱熹,而成朱熹门人,卑以恭,熹深器之。后官至兵部郎中。有乡人游宦,落难以死,其孤孱弱无依,公率诸司合力贿之以举其榇。
杨履正,字子顺,泉州府晋江人。绍熙元年与陈易、杨至、王力行、刘镜皆从学朱熹于漳州,朱熹称其为学缜密,多有书信往来问答。居乡里,有从其学者数百人。
杨至,字至之,泉州府晋江人。为朱熹门生,以文学名于时,与李唐咨皆文采发越,灿烂可观,蔡元定以女妻之。淳熙间,在武夷精舍就学,绍熙二年问学于漳州。绍熙五年四月,同黄义刚、?渊等人随朱熹赴长沙任入湖南。庆元间在建阳考亭续学。朱熹称其讲论精细。辑《晦翁语录》,撰有《圣人至教图》、《天道至德图》等。
杨景陆,字伯淳,泉州南安县人。朱熹曾因行役按事经其乡,住宿其家中,其得亲炙以成学。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及第,官建宁司法参军。著有《汉唐通鉴》、 《史志解》、《春秋解》。
诸葛廷瑞(?—1195年),字麟之,诸葛季文之子,其先南阳人,居泉州南安。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及第。乾道三年以左宣议郎为建宁府崇安县令,登朱熹之门受学,故其为政以教化为先。次年崇安县发生大饥荒,延请朱熹、刘汝愚协同赈灾,在县学内建赵抃、胡安国祠,到五夫请朱熹为作《祀二贤学宫记》,朱熹作《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言及其开仓赈灾事。诸葛廷瑞后来改判明州,又知惠州。后历起居舍人,淳熙十六年,以工部员外郎充吊祭金国使。金伴使以三节人衣带服饰为非,请易之,并露刃恐以祸福,廷瑞宁死不从。使还,除吏部侍郎。在朝屡有奏章进言,多被采纳。后官至兵部侍郎兼太子少保,庆元初卒。
诸葛廷材,字诚之,诸葛廷瑞之弟。授徒里中,究心学问,与朱熹论陆九渊之学。晦翁答书勉其虚心熟讲,勿以气盛粗心害道。自此,务为修身切已之学,卒成名儒,著有《六经诸子诸解》。
李亢宗,字子能,泉州府南安人。绍熙间于漳州问学于朱熹门下。其刻志问学,服习俭素,无贵介习气,朱熹称之。有书信致朱熹问学。官至县丞,卒,陈宓作《祭李县丞亢宗文》。
陈易,字俊之,号缓之,陈知柔之季子,泉州永春县人。幼孤力学,淳熙四年以明经登乡荐。绍熙元年于漳州问学于朱熹门下,次年四月与郑可学、周弼、蔡念诚等人闻朱熹论学问传授之次第。登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第,官终福州怀安县丞。庆元五年续学于建阳考亭,朱熹称其与陈淳为学颇得蹊径次第。
陈易崇尚伊洛之学,不眉浮屠,参酌古礼,乡闾化之。晋江蔡和以儒名恒请质焉,先时漳泉士泥章句自熹导源于前,易与淳继之,由是濂洛关闽之学大行。或问熹延平验中于未发之前,是何气象?易曰: “持守卫良久,亦自可见。”著有《论语解》、《孟子解》等。
蔡和,字廷杰,号白石,泉州府南安人。其家颇为殷实,以耕读为乐。绍兴间朱熹官同安簿,过蔡岭,闻其名,特访之。晚则心慕朱熹之学,以亲老不能远行,推举陈淳往受业,而以书请质之,故列为朱熹门人。其丧祭酌参古礼,乡闾化之。李方子、真德秀皆雅敬之。著有《易说》、《家训集鉴》等。
惠安人刘镜和张巽也是朱熹的门人,后人尊他们为紫阳高弟。
刘镜,字叔光,淳熙十四年秋曾偕张巽往武夷精舍问学质疑于朱熹。每天从事于涵养体察、躬行践履,久益明净,称朱门高弟。刘镜与杨至、陈易、杨履正为学友。其厌科举之习,无心仕宦,在龙津之原建别业授徒。嘉定后庆元党禁解除,其与张巽大力宣扬、传播朱子理学。卒后,被奉祀于乡贤祠中。
张巽,字子文、深道,为张寓之子。张寓知临江军,与张栻讲学,故淳熙间张寓谴张巽从学于张栻门下,及归,张栻赠诗且致属望。当张栻过世后,张巽作诗三律挽之,并守心丧三年。
淳熙间晦翁之学盛行,张巽与朱熹门人杨至、陈易、刘镜论学,许多问题未释然,于是淳熙十四年秋同刘镜走武夷山,谒朱熹于武夷精舍,问学质疑,始得引导,专心于涵养体察,日久心智益明净。张巽善诗,临别时作《武夷留别朱晦翁先生》诗:千灯圣道谁能几,若卓先贤问一遗。巨麓清扬知多少,石钟自况示精微。山中夜冷雪客立,洞口秋深雁望飞。此际殷勤分手去,明春策杖扣仙扉。
其力尊师教“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回惠安后,张巽在锦溪上建草堂,与刘镜在惠安传播理学思想。
降至明代,泉州地区出现了朱子学研究的兴盛局面,乃源于南宋时期大批的朱熹门人的传道授业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绍兴二十三年至绍熙二年(1 153—1 191年)年间,朱熹或因仕宦、或因私交,步履多涉泉州之境,往来泉州各地,开展讲学活动,其任同安主簿时讲学活动,已有专章介绍,在此不复。本文则采撷其在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地的教育活动之花絮以飨读者。朱熹的读书与访学活动绍兴二十六年春,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由泉州府抽调到府,分配任务后,被派往德化按事。朱熹寓居剧头铺,春寒夜冷,借着烛光苦读《论语》,闻杜鹃啼叫到天明,弄明白了明道先生程颢解说“子夏之门人小子”章的意思而沾沾自喜。
绍兴二十六年八月上旬,朱熹到泉州府等待离任的批文。在泉州官邸,朱熹向旅馆中人借得《孟子》一书,潜心研读,终于晓得“养气”一章的语脉,为后来集解《孟子》奠定了基础。朱熹又访得泉州人曾恬(乃程门高弟上蔡先生谢良佐的弟子),从其家获得谢上蔡语录,潜心研读。这是朱熹进士及第之后辗转师事延平先生李侗期间在泉州攻读圣贤书(儒家经典著作)、接续二程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时期。
朱熹初仕泉州同安县主簿,工作认真,清查版籍田税时发现许多问题,找到根结所在,在于经界之举未行,欲行经界以正本原。朱熹后来回顾说:“熹绍兴二十三、四年间,备员泉州同安主簿,是时已见本州不曾经界。县道催理税物,不登乡司,例以逃绝为词,官司便谓不可追究。徐考其实,则人户虽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处,但或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为邻至宗亲后来占据,阴结乡吏,隐而不言耳。固尝画策,以请于县。一时均割虽亦颇多,然本源未正,弊随目生,终不能有以为久远之利。”于是在当年秋收后,特地到泉州所属的惠安县城,向惠安县丞郑昭叔讨教行经界法的经验。
朱熹在同安担任主簿,听说邻县永春有个贤令尹黄瑀,治县有政声,特别是其公廉强介,察见微隐,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他县民有冤讼,率请委公以决。其条教科指,操验稽决,人皆传诵以为法。其禁令要束,大抵皆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之意。其言明白简切,其达之也,远近幽隐,无不暨焉。黄璃(1109—1168年),字德藻,福州府长乐县青山人氏,迁居闽县。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四年,知泉州永春县。同安主簿朱熹登其门拜访,见令尹正危坐堂上,批阅学宫弟子课程,庭中阒然无人声。朱熹“问公所以为此者,公不鄙,告语甚悉”,受益匪浅。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仕于同安满四周年,替任的人终未至,罢归,十一月又到泉州住陈良杰家数月,命友生之嗜学者与居,名室为“畏垒庵”,与陈养正、吕少卫等游,当年十二月五日作《恕斋记》。“恕斋”是陈养正读书之堂,吕少卫题名,养正则请朱熹为之作记。在畏垒庵,有嗜学者相伴,朱熹便与友生讲习,讲习经典著作,探讨儒家思想之奥蕴,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朱熹在同安县学讲学活动的延伸。
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初,朱熹南下福州携门人林用中同往泉州,十月下旬,朱、林到后,与休斋陈知柔追游于莲花峰、九日山、凉峰、凤风山、云台山之间。在泉州,多与泉中旧识、雅士如许升、黄伟优游、讲论。又与陈知柔、黄维之一起前往泉州吊唁傅自得。在此过程中,朱熹向追随者讲授儒家思想。朱熹在泉州各地的讲学活动乾隆《泉州府志·学校》序中有曰:“学校之设,以培养人才而固邦本,广以习之,优以奖之,拜圣亲师,罽以约束之。历代以来,制寖备矣。泉自常衮倡学,欧阳詹应其选,迨后来朱紫阳过化之区,蔡文庄诞生之地,跻于前哲配享庙廷,所谓瓜瓞之绵,其后愈大者也。”可见朱熹的教化之功,大矣! 在今泉州市区北门模范巷第三医院内,有抬匾式石坊表横梁,上刻有行楷“小山丛竹”、“晦翁书”字样。朱熹在淳熙元年甲午(1174年)四十五岁时方用“晦翁”之字,以“晦翁书”三字看,此为朱熹中晚年的墨迹,最大的可能是淳熙间旧地重游时所题。
朱熹早在离开同安主簿任之前,曾数至泉州郡城,抵则必登城隍庙后小山,称其山川之美,山上有亭,亭边种竹,朱熹称小山丛竹亭,与同游者讲学论道于其中。这是朱熹在担任同安主簿兼管学事期间讲学活动的延伸。由于朱熹讲学的方式方法不同寻常,讲问内容超越举子应试范围,对培养学者独立思考、人生信仰、价值取向有莫深的影响,许多人喜欢听其课,朱熹受聘讲学的机会也多,特别在类似赋闲的等待继任者的时间内,朱熹讲学于泉州城周围的书堂、精舍之属,将其早期思想传授给泉州的士子们。
明代嘉靖年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建小山丛竹亭,更名“过化”,且镂刻朱熹遗像以崇之。清康熙四十年,通判徐之霖于府城隍庙旁建书院——小山丛竹书院,并亲自撰《重兴朱夫子小山丛竹亭记》。
朱熹平生至少有三次到永春县。第一次是在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十二月,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期间,曾奉泉州府檄往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一带公干,顺便访永春县令黄璃,主动向其学习戢吏奸、恤民隐的为官之法。第二次是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九月。当年七月朱熹任同安簿三年秩满,八月在泉州府等候朝廷批书之际,游历泉州府永春县,到永春岱山岩、大剧铺等地访问同年进士苏升,与故交陈知柔登环翠亭。第三次是在淳熙十年初冬间朱熹再游永春,访同年进士陈光,得与陈知柔讲学于怀古堂,登临环翠亭,赋诗唱和,其乐融融。朱熹喜欢游山水,交名流,其往游永春访贤问儒,乃为第一要义。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晚春,二十七岁的朱熹奉檄从同安往外邑体究公事,即出差到德化县,在《朱子语类》卷49、卷104中均有此次外出的记载。
朱熹奉檄走外邑体究公事的时间在绍兴二十六年春三月,而诗中讲一官今是五年期,从绍兴二十三年算起,朱熹仕泉南满五年应是在绍兴二十七年,实际上此“五年”为虚指。这段时间,是朱熹尊延平李侗先生之意,苦读儒家经典著作《孟子》的时期,是在泉南佛国觉醒而始弃佛崇儒的关键时期。五代至北宋时期,古典经学衰微没落,给佛教和道教的复兴繁盛留下广大的文化空间。北宋诸帝王对佛老的提倡,更是助长了佛老思想的蔓延与浸润,使得人们精神委靡,对江山沦陷、二帝蒙辱而不思报复,登上帝王宝座的赵构日夜都怕谈恢复、迎二帝归,一旦迎回二帝便会动摇自己主宰江山的统治地位,而攀附于赵构的群小也怕失去荣华富贵的享受,于是高唱儒佛道兼修并行,士大夫们心醉神迷于佛老说教,以佛道文化作为儒文化的两翼,在沉闷的空气中悠悠飞翔,而伴随的是人心败坏,社会退化,弊端百出,民不聊生。朱熹师事武夷三先生后,曾有出入佛老十余年的心路历程,在同安为官期间,面对现实生活,开始渐渐相信不是提倡贪生畏死的佛老之学,而是提倡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才是拯救南宋衰世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支柱。这一觉醒,对于朱熹来说十分重要。他任县簿兼主学事,所以将许多精力花在整顿县学教育上,希望通过振兴儒学来解决社会问题,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而改变社会现状。朱熹曾多次到晋江石井(今安海)寻访其父旧事,拜访父执,与当地的名流耆士讲论经义,勉劝镇人为学,把良好的为学风气带到了安海,而使民沾其德,咸知向学。
绍熙二年(1191年)四月底,朱熹辞任漳州太守归,北过晋江,端午节在洛阳下生院为叶仲微、叶德符父子慕堂诗作跋。其时既有大批的追随者,也有当地士子问学,故说朱熹对泉南、对安海的教育是有重大的贡献。于是后来有人建石井书院、立朱祠作为纪念朱松、朱熹、朱在祖孙三代的重要场所。
朱熹于绍兴间仕于同安、淳熙间吊唁泉州友人、绍熙间官于漳州,皆经过惠安之境。惠安城北门外有泗州,其位于主要交通干线。据史料记载,从云峰山到泗州山都是极为兴盛的佛教圣地。泗洲山麓有座著名的德济庵,该庵始建于唐朝咸通年间,因“有僧得浮木,夜有光,刻为佛像,立精庐奉之”。其后屡有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以至有前后三殿、拜亭、制药司、织做司等建筑群,鼎盛时比丘尼达99人。庵堂依山傍石,后有天然石洞,洞内石壁刻有诗文;上有观音岩,岩上雕刻观音像。山顶巨石有“天开岩”及“山海奇观”等巨幅手书石刻。
绍熙二年正月,朱熹以丧嫡长子之痛请求辞官,四月底得旨允许辞官回家。有资料表明,廖德明与陈易、郑可学、周弼、蔡念诚等人同期随从朱熹北归,闻朱熹论学问传授之次第。五月在惠安泗州,聆听朱熹论儒释之异,即“儒理实,佛理空”。自从佛教进驻中土,便快速滋长起来,与本土文化进行较量与领地的争夺,遭到儒家学者的普遍性批评而时有收敛,但在南宋,由于士大夫们推波助澜,帝王不断分封各地已故高僧之头衔,各地名山遍立寺院,达官贵人沉迷佛事,庶民也燃香点烛虔诚膜拜,整个社会风气低迷。
朱熹秉承二程辟佛之说,平生常与学者论儒释之异,以警醒受学者。魏以降,儒家学说受到佛道的挑战,儒释道三家之学开始了互相排斥到逐步融合的进程。至唐宋时期,道学影响减弱,而佛学影响由于帝王和许多读书人的介入与鼓动,则成扩张之势。士大夫崇佛之风日益浓烈,特别是许多人出入佛老,美其名曰儒释道三者兼修,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儒者谈禅论道,释老广交上层社会,大有与儒学争夺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之势。朱熹的前辈、同辈中也不乏佛老的信徒,故早年研读释老之书的朱熹,在受李侗的指教后,主动将二氏之书搁起,潜心于儒家学说以明为人之大本,为后来大力辟佛、特别是辟禅奠定基础。朱熹的排佛思想,在乾道、淳熙间不断与人论辩、不断反思、不断总结自己学问的过程中达到高潮,并写进《四书集注》中的相关章节里。
朱熹的排佛思想还形成一个体系,朱子学专家束景南先生总结说该体系包含有三个内在层次:一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迷信,他是视为愚妄彻底否定,佛教以世俗宗教迷信所宣扬的一切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极乐世界、吃斋礼佛、念经成佛等等,他都一概摈弃:二是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他是作为异端从总体上排斥,即他所说的“大本不同”,但在个别观点上同儒说相合或部分相合的则加以改造吸收,如静坐之于主敬,禁欲之于人欲,论性之于论心,论心之于论意之类;三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哲学,他是注重吸取其缜密的思辨方法,用来表述和论证儒家的命题、观点与思想。朱熹辟佛斥道,更深一层的意义,恐怕是对北宋诸帝王大力提倡佛道进行的批判。没有统治者大力提倡培植,佛道就不会无限制地扩张、渗透,民心不会丧乱,士大夫也不会贪生惧死,北宋也不会轻易被灭亡。南宋帝王不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依然秉承祖宗遗旨,甚至将和议确立为国策,帝王将相贪生怕死而求苟安,士林中弥漫着贪惰恶习,志士恢复大计屡遭打压,士气由此而一蹶不振,亡国之势已露端倪。
朱熹过惠安,参观庵寺,见佛事鼎盛而人易被其玄说所迷,而发辟佛之说。在《朱子语类》卷第126论释氏中,廖德明记录:“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包扬则记曰:“佛以空为见,其见已错,所以错。”以空而言,客观存在的、人眼所见的,皆为空,人活着有何意义?佛存在又有何意义?这种学说,很容易导致人的思维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所以,朱熹不能不在教导士子时反复论说儒佛之异。庆元二年二月,朱熹在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为向浯《遗戒》作跋,仍在倡导抵触佛教为亡者设道场的末俗之陋。
朱熹是儒家思想的卫道者,其倡人伦、守礼法,要求人们诚心正意,要求人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志有为,而不似道家追求个人的长生不老的一味贪生,也不似僧徒将自身看成是个寄生的臭皮囊的虚无幻灭,其教人从日常生活中体认天理之所在,把握好人活世上的方向,让人脚踏实地地生活在现实的世界。朱熹的泉州籍门人朱熹的教学活动,为泉州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其门人有同安籍的许升、王力行、许子春、陈齐仲、戴迈、吕侁、杨宋卿;永春籍的陈易;南安籍的蔡和、杨景陆、诸葛廷瑞、诸葛廷材、李亢宗;惠安籍的刘镜、张巽;晋江籍的杨至、杨履正、高禾、林峦、傅伯成、傅伯寿、傅伯拱等,陈景初、陈景仁、储用等人也属朱熹门人之列。在此对这些人资料做些简单介绍。
许升(1141—1185年),字顺之,号存斋,许漠之子,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其年方十三岁,到县学拜朱熹为师。许升学习用功,专心致志,深得喜欢。绍兴二十八年随朱熹到崇安五夫继续求学,覃思研精,学力大究,九月卒业归家。后遍交四方之士,论道肄业。隆兴至乾道初,参与朱熹的儒佛争论。乾道二年秋末,朱熹《答许顺之》信中有新作《方塘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淳熙元年,许升到建阳寒泉精舍续学。淳熙十年十月,朱熹与林用中至泉州时,其多从游,故曰其是朱熹得意门生,也是朱熹宣传儒学、创建理学的得力助手,有紫阳始教之高弟的美称。在家乡办存斋书堂,广招学士,培养雕琢成器之才。曾尊师旨意,校订《程氏语录》。著有《孟子说》、《礼记文解》、《易解》等。淳熙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朱熹作《祭许顺之文》。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朱熹为同安县主簿期间的入门弟子。乾道四年八月参与讨论观过知仁之说。淳熙间与陈易、杨至、杨履正、刘镜皆从朱熹学。绍熙二年续学于漳州,苦学善问,深得旨趣,被朱熹品评为“明敏有余而少持重”,受朱熹邀请参与校订《二程遗书》。著有《朱子传授支派图》、《辛亥问答》等。
许子春,字景阳,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于泉州同安县学受学于朱熹。淳熙八年就教于九江濂溪书堂,同年闰三月,与朱熹等人同游寻真观。随后,朱熹卸任南康太守时畅游庐山,其与刘清之、张扬卿、王阮、周颐、林用中、赵希汉、陈祖永、吴兼善、祁真卿、胡莘、王朝、余隅、陈士直、黄榦、张彦先、僧志南等人陪同。朱熹有书信致之。
陈齐仲,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间在同安受学于任县主簿的朱熹。乾道二年,致书朱熹问格物致知等问题,朱熹作《答陈齐仲》复其所问。后参与修订朱熹的《孟子集解》。
杨宋卿,泉州府同安人。县学诸生,专攻诗赋。绍兴二十四年问学朱熹于同安县学,后与朱熹讨论诗学,朱熹有《答杨宋卿》书。
傅伯成(1143—1226年),字景初,号竹隐,傅自得次子,泉州晋江人。绍兴间年尚小,听从父命拜同安主簿朱熹为师。后登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第,调连江尉。试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历知闽清县、连江县。淳熙元年,傅自得改知建宁府,其侍父于侧,再问学于朱熹。庆元初,召为将作监,进太府寺丞。庆元三年以朝散大夫知漳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朱熹之意而遵行之,创惠民局以济民病,革优人淫戏。后历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成都路提点刑狱。入为工部侍郎,开禧间以沮开边出为湖广总领。反对韩侂胄诋毁大儒,又反对韩侂胄用兵,抵罪。嘉定元年官左谏议大夫,抗疏十有三,皆军国大义。左迁权吏部侍郎,嘉定二年,知建宁府,有治声,后知镇江府,全活饥民甚众。嘉定八年除宝谟阁直学士,寻加宝文阁学士、龙图阁学士。著有《傅忠简奏议》、《耋志》、《竹隐居士集》等。宝庆二年卒,谥忠简。陈宓作《祭傅忠简文》,刘克庄作《龙学竹隐傅公行状》。
傅伯寿(1138—1223年),字景仁,傅自得长子,绍兴间拜同安主簿朱熹为师。登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第,乾道八年再举博学宏词科。淳熙二年为著作佐郎,次年九月除著作郎。淳熙四年六月作为龚茂良党人被放罢,当年九月,与袁枢、梁瑑、吴英等人访朱熹于武夷山下,并共游九曲溪。淳熙十五年至绍熙元年初为漳州太守,以公帑刻朱熹的《楚辞叶韵》。绍熙元年除礼部郎中,绍熙三年,出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绍熙五年,改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因朱熹以其为故家子弟而不荐举之,遭其怨恨,后投韩侂胄,致身通显。庆元元年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宁宗命,制告词给朱熹,告词中有“大逊如慢,小逊如伪”等语,其后,小人始敢直诋朱熹。其弟伯成屡引义责之,卒不听。庆元六年,出知建宁府,朱熹殁后,不许生徒前往建阳送葬。嘉泰元年六月放罢。次年,为翰林学士。三年,为吏部尚书,兼秘书省检阅文字,兼实录院修撰。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主修《高宗实录》、《孝宗实录》、《光宗实录》,著有《傅枢密文集》。 林峦,泉州晋江人。绍兴二十三年为同安县学诸生,刻意词章,拜同安主簿朱熹为师学习。其能推所闻以讲学闾里。乾道四年参与校订《二程遗书》。曾与朱熹书信往来,朱熹作《答林峦书》二通,劝其不要刻意词章,回到经学义理的正路上。
高禾(1156—1225年),字颖叔,泉州府晋江人。登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进士第,历知福清、仙游、惠州。绍熙间倅漳州,禾执弟子礼问学于漳州知州朱熹,而成朱熹门人,卑以恭,熹深器之。后官至兵部郎中。有乡人游宦,落难以死,其孤孱弱无依,公率诸司合力贿之以举其榇。
杨履正,字子顺,泉州府晋江人。绍熙元年与陈易、杨至、王力行、刘镜皆从学朱熹于漳州,朱熹称其为学缜密,多有书信往来问答。居乡里,有从其学者数百人。
杨至,字至之,泉州府晋江人。为朱熹门生,以文学名于时,与李唐咨皆文采发越,灿烂可观,蔡元定以女妻之。淳熙间,在武夷精舍就学,绍熙二年问学于漳州。绍熙五年四月,同黄义刚、?渊等人随朱熹赴长沙任入湖南。庆元间在建阳考亭续学。朱熹称其讲论精细。辑《晦翁语录》,撰有《圣人至教图》、《天道至德图》等。
杨景陆,字伯淳,泉州南安县人。朱熹曾因行役按事经其乡,住宿其家中,其得亲炙以成学。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及第,官建宁司法参军。著有《汉唐通鉴》、 《史志解》、《春秋解》。
诸葛廷瑞(?—1195年),字麟之,诸葛季文之子,其先南阳人,居泉州南安。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及第。乾道三年以左宣议郎为建宁府崇安县令,登朱熹之门受学,故其为政以教化为先。次年崇安县发生大饥荒,延请朱熹、刘汝愚协同赈灾,在县学内建赵抃、胡安国祠,到五夫请朱熹为作《祀二贤学宫记》,朱熹作《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言及其开仓赈灾事。诸葛廷瑞后来改判明州,又知惠州。后历起居舍人,淳熙十六年,以工部员外郎充吊祭金国使。金伴使以三节人衣带服饰为非,请易之,并露刃恐以祸福,廷瑞宁死不从。使还,除吏部侍郎。在朝屡有奏章进言,多被采纳。后官至兵部侍郎兼太子少保,庆元初卒。
诸葛廷材,字诚之,诸葛廷瑞之弟。授徒里中,究心学问,与朱熹论陆九渊之学。晦翁答书勉其虚心熟讲,勿以气盛粗心害道。自此,务为修身切已之学,卒成名儒,著有《六经诸子诸解》。
李亢宗,字子能,泉州府南安人。绍熙间于漳州问学于朱熹门下。其刻志问学,服习俭素,无贵介习气,朱熹称之。有书信致朱熹问学。官至县丞,卒,陈宓作《祭李县丞亢宗文》。
陈易,字俊之,号缓之,陈知柔之季子,泉州永春县人。幼孤力学,淳熙四年以明经登乡荐。绍熙元年于漳州问学于朱熹门下,次年四月与郑可学、周弼、蔡念诚等人闻朱熹论学问传授之次第。登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第,官终福州怀安县丞。庆元五年续学于建阳考亭,朱熹称其与陈淳为学颇得蹊径次第。
陈易崇尚伊洛之学,不眉浮屠,参酌古礼,乡闾化之。晋江蔡和以儒名恒请质焉,先时漳泉士泥章句自熹导源于前,易与淳继之,由是濂洛关闽之学大行。或问熹延平验中于未发之前,是何气象?易曰: “持守卫良久,亦自可见。”著有《论语解》、《孟子解》等。
蔡和,字廷杰,号白石,泉州府南安人。其家颇为殷实,以耕读为乐。绍兴间朱熹官同安簿,过蔡岭,闻其名,特访之。晚则心慕朱熹之学,以亲老不能远行,推举陈淳往受业,而以书请质之,故列为朱熹门人。其丧祭酌参古礼,乡闾化之。李方子、真德秀皆雅敬之。著有《易说》、《家训集鉴》等。
惠安人刘镜和张巽也是朱熹的门人,后人尊他们为紫阳高弟。
刘镜,字叔光,淳熙十四年秋曾偕张巽往武夷精舍问学质疑于朱熹。每天从事于涵养体察、躬行践履,久益明净,称朱门高弟。刘镜与杨至、陈易、杨履正为学友。其厌科举之习,无心仕宦,在龙津之原建别业授徒。嘉定后庆元党禁解除,其与张巽大力宣扬、传播朱子理学。卒后,被奉祀于乡贤祠中。
张巽,字子文、深道,为张寓之子。张寓知临江军,与张栻讲学,故淳熙间张寓谴张巽从学于张栻门下,及归,张栻赠诗且致属望。当张栻过世后,张巽作诗三律挽之,并守心丧三年。
淳熙间晦翁之学盛行,张巽与朱熹门人杨至、陈易、刘镜论学,许多问题未释然,于是淳熙十四年秋同刘镜走武夷山,谒朱熹于武夷精舍,问学质疑,始得引导,专心于涵养体察,日久心智益明净。张巽善诗,临别时作《武夷留别朱晦翁先生》诗:千灯圣道谁能几,若卓先贤问一遗。巨麓清扬知多少,石钟自况示精微。山中夜冷雪客立,洞口秋深雁望飞。此际殷勤分手去,明春策杖扣仙扉。
其力尊师教“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回惠安后,张巽在锦溪上建草堂,与刘镜在惠安传播理学思想。
降至明代,泉州地区出现了朱子学研究的兴盛局面,乃源于南宋时期大批的朱熹门人的传道授业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相关地名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