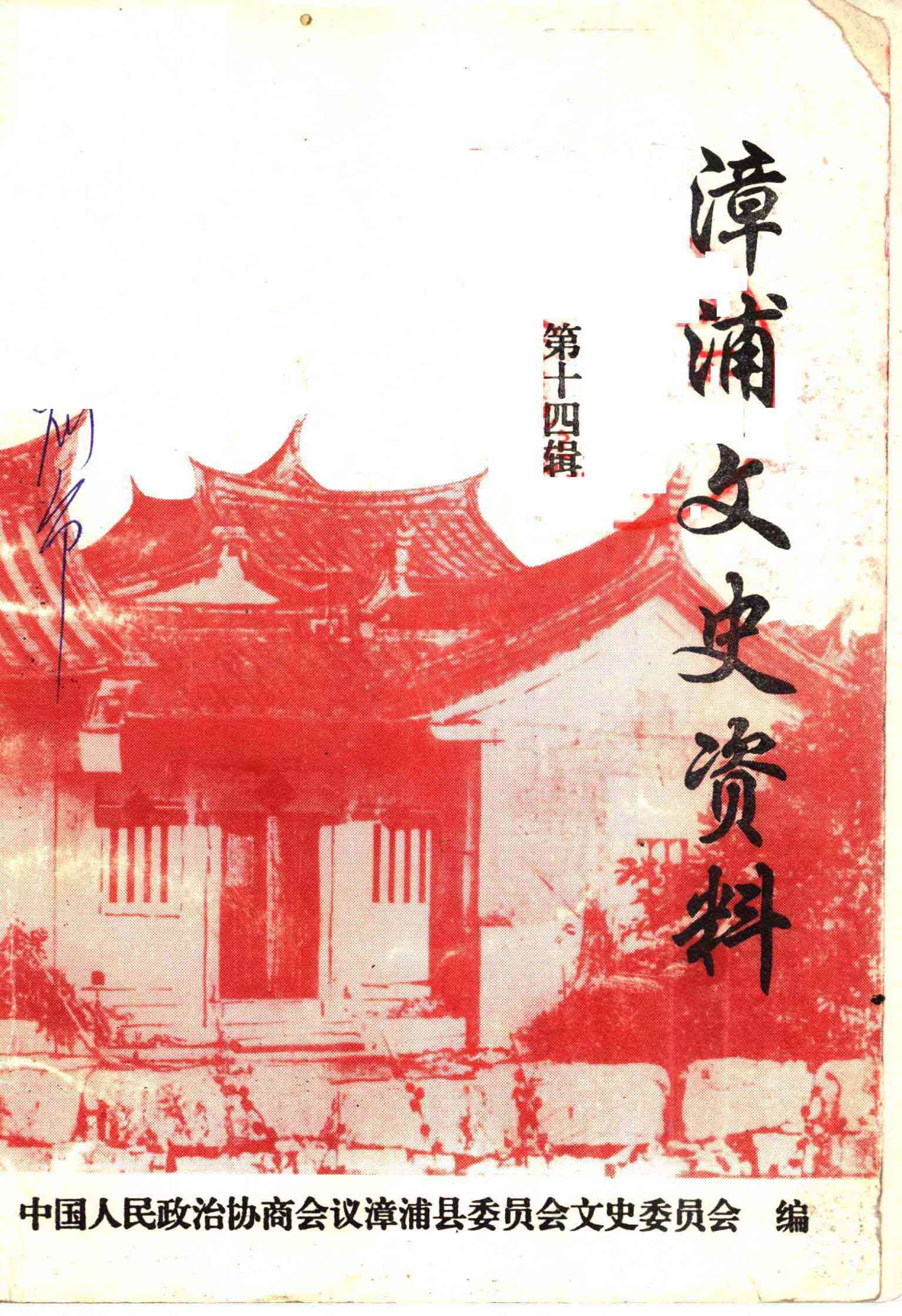抗战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所历所见
| 内容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763 |
| 颗粒名称: | 抗战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所历所见 |
| 分类号: | G455 |
| 页数: | 7 |
| 页码: | 87-93 |
| 摘要: | 本文主要描述了在抗战时期,学校和学生们的经历。学生们在晨呼队中高唱抗日歌曲,进行防空演习,躲避日机轰炸,甚至停学成为见习农民。 |
| 关键词: | 抗战 学校 防空演习 |
内容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序幕拉开了。这一年我刚七岁,父亲送我到西街三房巷张隆古先生办的私塾念“四书五经”。刚念过《论语》,《中庸》、《孟子》三本书,私塾便停办了,原因是政府为适应抗日形势,通令各地开办国民学校,禁办私塾。我便转到武营中心小学,插读二年级。这已是一九三八年了。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晨呼队”,除一年级外,各级男女生都得参加。每天早晨天未亮,我顶着凛冽的寒风,先到古井头葛婶店前,用二个铜片买一碗糖粥吃,再到学校集中,然后由老师带队,出校门从西街、府前街,转到北街、麦市街,沿街高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雄壮嘹亮的歌声、满腔的热血激情,驱散人们身上的寒气。晨呼队的后面跟着县长吕思义,吕手持“动葛”(手杖),沿街敲门撞户,喊老百姓起床,几乎天天如此,妇女背地里多叫他“神经县长”。晨呼队最后到兴教广场参加升旗。升旗后回家早餐,餐后再入学上课。
那时,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课外活动内容,就是“防空演习”。学校划定班级疏散地点,“乱钟”一响,师生马上离校跑到指定地点隐蔽防空。我们班原指定隐蔽点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内,数次演习都去那里。农历四月廿五日那天,我们听到县府大钟紧敲声及学校的乱钟,急忙冲出学校后门,抬头看见飞得很低的日机,已在礼拜堂方向的上空,我急转身向高厝巷,一口气跑到城边桃仔园(现北市场蔬菜公司),突然听到恐怖刺耳的飞机呼啸声,急忙按演习时老师讲的,俯卧地上,掩耳张口。“轰轰轰”一连串的炸弹爆炸声,声声震动着大地,也震动着我的身心。我身边有些妇女,紧紧捂着孩子的嘴巴,怕哭声引来飞机,口中叼念着,天公保佑,佛祖保庇,炸弹不要落在这里。好不容易在心惊胆战中挨到飞机走了,警报解除了,才急忙回家,看到家中一切依旧,方能开口说话。这时,街上传开了,炸弹炸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左右,炸死了蔡发祥、蔡恢等数人,死者四肢五脏悬挂树梢、檐口,惨不忍睹。以后钟声一响,我便从高厝巷往北门兜方向跑。那时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不快,轰炸还要打围找目标,因此,飞机飞到头上立即卧倒地上,飞机一过身,立即拔腿再走,经常走三、四里路到羊寮(今朝阳)、楼仔顶村。
当时,“防空哨”设在鸡笼山(现气象台),警报器用挂在县府前东侧钟楼上的大铜钟。防空哨一接敌机犯境情报,立即电告敲钟者,敲钟者立即赶到钟楼,登楼撞钟。连续紧接撞钟为敌机入境警报;如慢慢地一声一声则是解除警报。后来,可能因钟楼延缓时间,改用一部金属手摇“警螺”(汽笛)以代替大钟。
城内居民一听到警报,便急奔城外疏散或躲进防空洞、防空壕。那年七月廿九日(俗为“尾中元”),日机投弹炸在市场(现旧文化馆)东侧防空壕(今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几个人堵死在里边。自此很多人不敢躲入防空洞。
这一年,日机犯境非常频繁,有时一天要走避数次。学校只好采取疏散上课,我们班到王顶蔡俊德校长家上课,也曾到西门外大树下(现城关粮站)上课。城里居民也改变生活方式,天朦朦亮就吃早餐,太阳未出时就出城躲日机。中午就地野炊,穷困之家午餐只好免了。黄昏后庆幸一天平安过去,才陆续回家。
县府后衙(现宾馆)几株大榕树上栖着几千只乌鸦,曾有乌鸦半夜“反巢”隔日敌机犯境情况,群众将乌鸦当“预警器”。七月上旬,乌鸦夜夜反巢,居民搞得失魂落魄,日夜不宁,既不能安居,更无法乐业。我父亲是手艺工人,他上半辈子有二怕,一怕日本飞机;一怕抓壮丁。警报一响,他面如土色,连跑也跑不动,只好在家宅后龙眼树下挖一条防空壕。在城内、躲防空壕也是担惊受怕,父亲便到城郊附近农村去联系住房,准备搬到农村中去。
农历九月初六、初七两天,日机连续轰炸县城数处,每次都有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城内居民纷纷搬到农乡亲友家。家长也不敢让子女去上学。武营中心小学也搬到霞潭村,我们全家搬到罗北考湖村。起初,每天跟着堂兄走三、四里路到霞潭去上学。不多久,学校没学生上课,老师也走了。堂兄到东门他外婆家,我也停学了。
在考湖村,父亲断了手艺营生,就租了一些土地,我们成了见习农民。见习农民种地比正式农民还讲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摘绿豆。父亲说,太阳出来一晒,豆英就爆裂,因此,采绿豆就得在大阳出来前。中午,农民都回家休息,父亲要我跟他留在地里锄草,说中午阳光强,锄掉的草不易复苏。我还常跟祖父进城卖蕃薯,两担蕃薯可卖一百多个铜镭,吃一碗“水面”5镭,祖孙吃后,再把家里的肥料挑到农村地里。当地农民说我们生产的作物不比他们少。但我的学业却荒废了。一九四〇年空袭减少了,祖父母先回家,不久,全家回城。学校复课了,我也复学。
吕思义县长走了,学校不再搞晨呼了。但小学生还得接受军训。军训很正规,每个学生要做一套黑布中山装,黑学生帽,束腰皮带,高年级同学要打绑腿。女生一律剪短发。学校利用劳作课,中年级每人做一把木大刀,油漆后系上红布带。高年级每人做一支木驳壳枪。西街顶陈克昌先生任学校军事训练教官。体育老师教舞大刀,陈教官教步兵操,教打野战。有一次,高年级同学到野外操演野战,曾鼎同学被土制手榴弹炸得血流满脸,用担架抬回校。
武营中心小学不少老师是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演“文明戏”(话剧),绘宣传抗日画。蔡俊德、郑秀贞夫妇、蔡启昌、林清秀夫妇、曾敏英、张淡月、许其和等老师,还有校外的柯汉扬、蔡维汉、邱珍五等先生组织的“抗敌剧团”,经常下乡演“文明戏”宣传抗日,高年级不少同学跟着剧团下乡,充当配角或跑龙套。有一次,我和戴壬癸同学被曾敏英老师叫上台凑个群众角色。兴教广场的戏台原是露天的,为了演文明戏宜传抗日,县政府拨款盖瓦顶大戏台,连带左右两大房间,演戏时作化妆室、休息室。平时则作我们的教室。
抗战时期,我们小学生不但自己要读书,还要当民众夜校的小先生。我被分配在县府内县堂(现历史博物馆)识字班当先生,还有同班女同学教唱抗日歌曲。每天晚餐后,手提小油灯挨家挨户叫学员上学,学员多是中青年妇女。
小学生参加的会竟多不胜数。全县在兴教广场开“一元献机抗日”大会,我们全校都去参加,有些同学在家长支持下,上台献金戒指、银圆,有各界人士、妇女上台献首饰、钞票,我们在台下鼓掌、唱抗日歌曲。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县幼儿园后大路边),我们同学每人献几个铜镭放在碑基底下。每星期一是“纪念周”例会,我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列队到兴教广场唱抗日歌曲,听县长训话。
当时的老师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记得有一年儿童节,每个同学分到一份礼物,有糖果、饼干,还有一节果蔗。蔡校长手拿甘蔗问大家:同学们,这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甘蔗。校长笑着说:不,这是用来打日本飞机的高射炮……。在五年级时,学校举办美术展览,老师要求学生画有抗日内容的图画。我和王乾三、叶集锋,从学校图书室借来很多张“日寇暴行图”,我们每人临摹了好几张参加展览,老师还表扬我们。
后来,敌机侵犯骚扰减少了,社会上涌起抓汉奸、抓壮丁潮流。老师告诉我们,汉奸装成乞丐、小贩、难民,到处向水井投毒,学生要协助政府抓汉奸,随时随地注意可疑的人。社会上也传得人心惶惶,公共场所的水井都要加盖上锁。肃奸成为一个新运动,文明戏演“抓汉奸”,街头标语、漫画也都是肃奸内容的。有一次,兴教广场演“文明戏”,归侨,修脚踏车的乌番师傅,客串扮汉奸黄秋岳,“黄犯”五花大绑,背插斩标,身后左右站立两名持枪法警。“黄犯”用潮曲清唱通敌叛国的罪状,由城关民乐演奏手们伴奏。曲完执行枪决,“啪”一声,“黄犯”从台上栽下台来,观众人心大快,“消灭汉奸”,“枪毙卖国贼”!喊声响彻云霄。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忽然听到要枪决“资敌犯”胡百虎,大家丢下课本跑到街上观看。
社会上到处在抽壮丁,按规定,三抽二,二抽一,单丁缓役,但有钱人尽管兄弟多,可以用钱雇壮丁,当官的怕中签的壮丁逃跑,保内壮丁抓阄,一中签马上像犯人一样被缚起来押关在联保办事处(后改乡镇公所),家属三餐去送饭。接兵部队一期接着一期来接收。接兵部队在城关一些祠堂设“新兵招待所”,实是关壮丁的牢狱。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的父兄被抓丁,家无劳力,不得不失学。当兵上前线抗击日寇,原是国民应尽义务,理应踊跃应征,为何要用绳子缚,铁丝捆,发现逃跑,不是当场击毙,就抓回活活打死?那一年署假,武菅中心小学被接兵部队“借”去关壮丁。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路过窗下,突然听见内边惨叫声,便停足往内窥视,见二个壮丁赤裸身子被按在石板上,当官的指挥其他壮丁逐个用扁挑轮打,终于打得不叫不动了。我家隔巷刘祠堂,也是关壮丁的地方,经常在半夜听见惨叫声,天刚亮就可看见荷枪的士兵,押着壮丁抬着裹草席的尸体出城去。还有一次,关在兴教寺的壮丁,集体逃跑,当官的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打死十余人,横尸榕树下。这些现象老百姓看在眼里,更觉得当壮丁的可怕。
国民党政府只管抽壮丁,不管壮丁家里生活如何,妻孥子女死活如何,壮丁抓到“招待所”,吃不饱,穿不暖,动辄遭受毒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往上送时,每人牢牢捆缚,还用铁丝扎成一串,拉屎撒尿还要挨枪托、皮鞭毒打。用这种手段抓来的兵怎能打仗,怎能不跑呢?当然,自愿去当兵的人也有。我同班一位姓李的同学,在家庭得不到温暖,未到16岁去“卖壮丁”(顶替他人入伍,价钱约2至3担花生油)。六年级一位姓洪的同学,顶替其胞兄入伍,未经什么训练就被押送到安徽,补入前线部队,参加九华山会战,队伍打散了,他靠着这小学文化知识,孤身千里跑回漳浦,考上漳浦中学。1944年,政府派人到学校招募“远征军”,说是要到缅甸、印度参加盟军抗日,还招“华安军”等,学校不少同学报名参加。只有这样当兵才免受“新兵招待所”虐待,且受光荣欢送。
我们小学毕业那年,潮汕地区被日本侵占,大批难民逃到闽南,来漳浦的为数更多。不久,全县突然发生瘟疫(霍乱),死亡数千人。我们班里同学就死了三男一女,这可以说是间接死于战乱。
上了初中不久,形势又趋紧张,二、三年级同学疏散到石榴崎溪一带上课,我们一年级则是上早,晚课,每人自备一盏小油灯,每天两头摸黑去上学,好在此况时间不长。
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天,忽传占据厦门的日军数百名,从海澄港尾登陆向漳浦而来。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居民纷纷离家疏散出城,学校也宣布停课,学生随家庭疏散。我们与邻居几户疏散到罗山大埔村。那一夜,约11点钟,突然来了一股“追击”日寇的国军七十五师,有数名“便衣”会说本地话。把我们几家驱赶集中在一间房屋内,抢去了我们很多东西。“便衣”又叫十几个妇女帮他们把抓来的鸡鸭宰剥烧煮。天亮了他们要走了,我问其中一人:你们追日本怎么追到这里?那人说,我们是从文周岭过来的。我明白了,日寇流窜是走佛昙、赤湖、旧镇、城关的大路,国军是走湖西、赤土、万安、文周岭、罗北弯弯曲曲山路,这条路线距大路约二、三十华里。完全可避免与日军遭遇。
日军窜入城内抓去一些老百姓当挑夫,即离城往盘陀方向而去。次日我们回家,听说日军过盘陀时被盟军飞机炸死一些人马。挑夫有的乘机选出日军魔掌,回了家,有的被日军打死,有的被盟国飞机炸死。
中国有句古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战乱是何等可怕可悲可恨,和平是何等可贵。要得到和平,国家就必须加强现代化建设,否则落后就要挨打。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晨呼队”,除一年级外,各级男女生都得参加。每天早晨天未亮,我顶着凛冽的寒风,先到古井头葛婶店前,用二个铜片买一碗糖粥吃,再到学校集中,然后由老师带队,出校门从西街、府前街,转到北街、麦市街,沿街高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雄壮嘹亮的歌声、满腔的热血激情,驱散人们身上的寒气。晨呼队的后面跟着县长吕思义,吕手持“动葛”(手杖),沿街敲门撞户,喊老百姓起床,几乎天天如此,妇女背地里多叫他“神经县长”。晨呼队最后到兴教广场参加升旗。升旗后回家早餐,餐后再入学上课。
那时,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课外活动内容,就是“防空演习”。学校划定班级疏散地点,“乱钟”一响,师生马上离校跑到指定地点隐蔽防空。我们班原指定隐蔽点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内,数次演习都去那里。农历四月廿五日那天,我们听到县府大钟紧敲声及学校的乱钟,急忙冲出学校后门,抬头看见飞得很低的日机,已在礼拜堂方向的上空,我急转身向高厝巷,一口气跑到城边桃仔园(现北市场蔬菜公司),突然听到恐怖刺耳的飞机呼啸声,急忙按演习时老师讲的,俯卧地上,掩耳张口。“轰轰轰”一连串的炸弹爆炸声,声声震动着大地,也震动着我的身心。我身边有些妇女,紧紧捂着孩子的嘴巴,怕哭声引来飞机,口中叼念着,天公保佑,佛祖保庇,炸弹不要落在这里。好不容易在心惊胆战中挨到飞机走了,警报解除了,才急忙回家,看到家中一切依旧,方能开口说话。这时,街上传开了,炸弹炸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左右,炸死了蔡发祥、蔡恢等数人,死者四肢五脏悬挂树梢、檐口,惨不忍睹。以后钟声一响,我便从高厝巷往北门兜方向跑。那时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不快,轰炸还要打围找目标,因此,飞机飞到头上立即卧倒地上,飞机一过身,立即拔腿再走,经常走三、四里路到羊寮(今朝阳)、楼仔顶村。
当时,“防空哨”设在鸡笼山(现气象台),警报器用挂在县府前东侧钟楼上的大铜钟。防空哨一接敌机犯境情报,立即电告敲钟者,敲钟者立即赶到钟楼,登楼撞钟。连续紧接撞钟为敌机入境警报;如慢慢地一声一声则是解除警报。后来,可能因钟楼延缓时间,改用一部金属手摇“警螺”(汽笛)以代替大钟。
城内居民一听到警报,便急奔城外疏散或躲进防空洞、防空壕。那年七月廿九日(俗为“尾中元”),日机投弹炸在市场(现旧文化馆)东侧防空壕(今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几个人堵死在里边。自此很多人不敢躲入防空洞。
这一年,日机犯境非常频繁,有时一天要走避数次。学校只好采取疏散上课,我们班到王顶蔡俊德校长家上课,也曾到西门外大树下(现城关粮站)上课。城里居民也改变生活方式,天朦朦亮就吃早餐,太阳未出时就出城躲日机。中午就地野炊,穷困之家午餐只好免了。黄昏后庆幸一天平安过去,才陆续回家。
县府后衙(现宾馆)几株大榕树上栖着几千只乌鸦,曾有乌鸦半夜“反巢”隔日敌机犯境情况,群众将乌鸦当“预警器”。七月上旬,乌鸦夜夜反巢,居民搞得失魂落魄,日夜不宁,既不能安居,更无法乐业。我父亲是手艺工人,他上半辈子有二怕,一怕日本飞机;一怕抓壮丁。警报一响,他面如土色,连跑也跑不动,只好在家宅后龙眼树下挖一条防空壕。在城内、躲防空壕也是担惊受怕,父亲便到城郊附近农村去联系住房,准备搬到农村中去。
农历九月初六、初七两天,日机连续轰炸县城数处,每次都有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城内居民纷纷搬到农乡亲友家。家长也不敢让子女去上学。武营中心小学也搬到霞潭村,我们全家搬到罗北考湖村。起初,每天跟着堂兄走三、四里路到霞潭去上学。不多久,学校没学生上课,老师也走了。堂兄到东门他外婆家,我也停学了。
在考湖村,父亲断了手艺营生,就租了一些土地,我们成了见习农民。见习农民种地比正式农民还讲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摘绿豆。父亲说,太阳出来一晒,豆英就爆裂,因此,采绿豆就得在大阳出来前。中午,农民都回家休息,父亲要我跟他留在地里锄草,说中午阳光强,锄掉的草不易复苏。我还常跟祖父进城卖蕃薯,两担蕃薯可卖一百多个铜镭,吃一碗“水面”5镭,祖孙吃后,再把家里的肥料挑到农村地里。当地农民说我们生产的作物不比他们少。但我的学业却荒废了。一九四〇年空袭减少了,祖父母先回家,不久,全家回城。学校复课了,我也复学。
吕思义县长走了,学校不再搞晨呼了。但小学生还得接受军训。军训很正规,每个学生要做一套黑布中山装,黑学生帽,束腰皮带,高年级同学要打绑腿。女生一律剪短发。学校利用劳作课,中年级每人做一把木大刀,油漆后系上红布带。高年级每人做一支木驳壳枪。西街顶陈克昌先生任学校军事训练教官。体育老师教舞大刀,陈教官教步兵操,教打野战。有一次,高年级同学到野外操演野战,曾鼎同学被土制手榴弹炸得血流满脸,用担架抬回校。
武营中心小学不少老师是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演“文明戏”(话剧),绘宣传抗日画。蔡俊德、郑秀贞夫妇、蔡启昌、林清秀夫妇、曾敏英、张淡月、许其和等老师,还有校外的柯汉扬、蔡维汉、邱珍五等先生组织的“抗敌剧团”,经常下乡演“文明戏”宣传抗日,高年级不少同学跟着剧团下乡,充当配角或跑龙套。有一次,我和戴壬癸同学被曾敏英老师叫上台凑个群众角色。兴教广场的戏台原是露天的,为了演文明戏宜传抗日,县政府拨款盖瓦顶大戏台,连带左右两大房间,演戏时作化妆室、休息室。平时则作我们的教室。
抗战时期,我们小学生不但自己要读书,还要当民众夜校的小先生。我被分配在县府内县堂(现历史博物馆)识字班当先生,还有同班女同学教唱抗日歌曲。每天晚餐后,手提小油灯挨家挨户叫学员上学,学员多是中青年妇女。
小学生参加的会竟多不胜数。全县在兴教广场开“一元献机抗日”大会,我们全校都去参加,有些同学在家长支持下,上台献金戒指、银圆,有各界人士、妇女上台献首饰、钞票,我们在台下鼓掌、唱抗日歌曲。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县幼儿园后大路边),我们同学每人献几个铜镭放在碑基底下。每星期一是“纪念周”例会,我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列队到兴教广场唱抗日歌曲,听县长训话。
当时的老师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记得有一年儿童节,每个同学分到一份礼物,有糖果、饼干,还有一节果蔗。蔡校长手拿甘蔗问大家:同学们,这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甘蔗。校长笑着说:不,这是用来打日本飞机的高射炮……。在五年级时,学校举办美术展览,老师要求学生画有抗日内容的图画。我和王乾三、叶集锋,从学校图书室借来很多张“日寇暴行图”,我们每人临摹了好几张参加展览,老师还表扬我们。
后来,敌机侵犯骚扰减少了,社会上涌起抓汉奸、抓壮丁潮流。老师告诉我们,汉奸装成乞丐、小贩、难民,到处向水井投毒,学生要协助政府抓汉奸,随时随地注意可疑的人。社会上也传得人心惶惶,公共场所的水井都要加盖上锁。肃奸成为一个新运动,文明戏演“抓汉奸”,街头标语、漫画也都是肃奸内容的。有一次,兴教广场演“文明戏”,归侨,修脚踏车的乌番师傅,客串扮汉奸黄秋岳,“黄犯”五花大绑,背插斩标,身后左右站立两名持枪法警。“黄犯”用潮曲清唱通敌叛国的罪状,由城关民乐演奏手们伴奏。曲完执行枪决,“啪”一声,“黄犯”从台上栽下台来,观众人心大快,“消灭汉奸”,“枪毙卖国贼”!喊声响彻云霄。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忽然听到要枪决“资敌犯”胡百虎,大家丢下课本跑到街上观看。
社会上到处在抽壮丁,按规定,三抽二,二抽一,单丁缓役,但有钱人尽管兄弟多,可以用钱雇壮丁,当官的怕中签的壮丁逃跑,保内壮丁抓阄,一中签马上像犯人一样被缚起来押关在联保办事处(后改乡镇公所),家属三餐去送饭。接兵部队一期接着一期来接收。接兵部队在城关一些祠堂设“新兵招待所”,实是关壮丁的牢狱。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的父兄被抓丁,家无劳力,不得不失学。当兵上前线抗击日寇,原是国民应尽义务,理应踊跃应征,为何要用绳子缚,铁丝捆,发现逃跑,不是当场击毙,就抓回活活打死?那一年署假,武菅中心小学被接兵部队“借”去关壮丁。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路过窗下,突然听见内边惨叫声,便停足往内窥视,见二个壮丁赤裸身子被按在石板上,当官的指挥其他壮丁逐个用扁挑轮打,终于打得不叫不动了。我家隔巷刘祠堂,也是关壮丁的地方,经常在半夜听见惨叫声,天刚亮就可看见荷枪的士兵,押着壮丁抬着裹草席的尸体出城去。还有一次,关在兴教寺的壮丁,集体逃跑,当官的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打死十余人,横尸榕树下。这些现象老百姓看在眼里,更觉得当壮丁的可怕。
国民党政府只管抽壮丁,不管壮丁家里生活如何,妻孥子女死活如何,壮丁抓到“招待所”,吃不饱,穿不暖,动辄遭受毒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往上送时,每人牢牢捆缚,还用铁丝扎成一串,拉屎撒尿还要挨枪托、皮鞭毒打。用这种手段抓来的兵怎能打仗,怎能不跑呢?当然,自愿去当兵的人也有。我同班一位姓李的同学,在家庭得不到温暖,未到16岁去“卖壮丁”(顶替他人入伍,价钱约2至3担花生油)。六年级一位姓洪的同学,顶替其胞兄入伍,未经什么训练就被押送到安徽,补入前线部队,参加九华山会战,队伍打散了,他靠着这小学文化知识,孤身千里跑回漳浦,考上漳浦中学。1944年,政府派人到学校招募“远征军”,说是要到缅甸、印度参加盟军抗日,还招“华安军”等,学校不少同学报名参加。只有这样当兵才免受“新兵招待所”虐待,且受光荣欢送。
我们小学毕业那年,潮汕地区被日本侵占,大批难民逃到闽南,来漳浦的为数更多。不久,全县突然发生瘟疫(霍乱),死亡数千人。我们班里同学就死了三男一女,这可以说是间接死于战乱。
上了初中不久,形势又趋紧张,二、三年级同学疏散到石榴崎溪一带上课,我们一年级则是上早,晚课,每人自备一盏小油灯,每天两头摸黑去上学,好在此况时间不长。
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天,忽传占据厦门的日军数百名,从海澄港尾登陆向漳浦而来。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居民纷纷离家疏散出城,学校也宣布停课,学生随家庭疏散。我们与邻居几户疏散到罗山大埔村。那一夜,约11点钟,突然来了一股“追击”日寇的国军七十五师,有数名“便衣”会说本地话。把我们几家驱赶集中在一间房屋内,抢去了我们很多东西。“便衣”又叫十几个妇女帮他们把抓来的鸡鸭宰剥烧煮。天亮了他们要走了,我问其中一人:你们追日本怎么追到这里?那人说,我们是从文周岭过来的。我明白了,日寇流窜是走佛昙、赤湖、旧镇、城关的大路,国军是走湖西、赤土、万安、文周岭、罗北弯弯曲曲山路,这条路线距大路约二、三十华里。完全可避免与日军遭遇。
日军窜入城内抓去一些老百姓当挑夫,即离城往盘陀方向而去。次日我们回家,听说日军过盘陀时被盟军飞机炸死一些人马。挑夫有的乘机选出日军魔掌,回了家,有的被日军打死,有的被盟国飞机炸死。
中国有句古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战乱是何等可怕可悲可恨,和平是何等可贵。要得到和平,国家就必须加强现代化建设,否则落后就要挨打。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