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百年的漳州鸦片烟毒
| 内容出处: | 《漳州芗城文史资料第四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4549 |
| 颗粒名称: | 肆虐百年的漳州鸦片烟毒 |
| 分类号: | F752.95 |
| 页数: | 14 |
| 页码: | 104-117 |
| 摘要: |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腐败政府——满清皇朝的大门,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道光末年漳州也有了鸦片烟馆公开营业。国民党统治时期,鸦片烟祸愈烈,众多吸毒成瘾的烟民,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因吸毒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因吸毒而道德沦丧,流为盗贼;在苦难的旧社会,烟毒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建国初期,共产党、人民政府进行了清毒运动,将肆虐百年、历经两代的鸦片祸害肃清了。现在就个人的见闻及对知情老人的访问,将漳州百年烟祸综合记述,既不完整、亦恐多有错误。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政出多门,于是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已遍及城乡了。 |
| 关键词: | 鸦片 贸易史 漳州 |
内容
鸦片战争后(1842),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腐败政府——满清皇朝的大门,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漳州也有了鸦片烟馆公开营业。国民党统治时期,鸦片烟祸愈烈,众多吸毒成瘾的烟民,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因吸毒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因吸毒而道德沦丧,流为盗贼;在苦难的旧社会,烟毒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建国初期,共产党、人民政府进行了清毒运动,将肆虐百年、历经两代的鸦片祸害肃清了。现在就个人的见闻及对知情老人的访问,将漳州百年烟祸综合记述,既不完整、亦恐多有错误。
(一)清末民初烟馆公开经营
漳州自清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就有几家经营鸦片烟馆,供人吸食。起初是那些达官贵人、官宦士绅、富家子弟,手捧鸦片枪,躺在烟榻上吸毒,不久,贩夫走卒、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也逐渐入馆吸毒了。
当时,鸦片烟馆公开营业,门前进入者不少。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政出多门,于是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已遍及城乡了。
清末民初,漳州城区开设烟馆有二十多家,其招牌字号有:双合盛、合盛、协成、兴隆、德兴、珍香、惠馨、顺和⋯⋯。分布在打锡巷、东桥亭、下营、龙眼营、上坂、新府路、双门顶,还有东门马公庙、南门竹巷下、西门西街、北门糖市等街区。
烟馆的特点是各家门前都挂一竹帘,上写本馆字号,屋檐前挂一盏方形玻璃灯,写上红字为标帜,烟馆里面烟味浓郁灯光荧荧、抽吸之声籁籁,烟鬼们吞云吐雾、个个有飘飘欲仙之态。
各家烟馆,大体上在屋子里有厅有房,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一般可供五、六人,小榻二、三人横躺吸食,各置有烟盘,其中配有烟枪、烟灯、烟杆、茶具等。
烟枪是用甘蔗套上竹筒所制,配上烟嘴、烟斗即成。当时有两句形容烟枪的顺口溜说:“甘蔗入竹广(筒),吸了才会爽”(闽南方言)。上层社会私家使用的烟枪,那就比较考究、精致,例如有用象牙或玉石镶成,烟盘用宣枝嵌花,铜质的烟灯灯台,清水玻璃灯罩。富人士绅人家,一般备有二、三套烟具,以备招待客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对鸦片“寓禁于征”,鸦片烟馆则“挂羊头卖狗肉”,改头换面,一夜之间,所有“鸦片馆”可以变成“戒烟所”了。
据熟悉经营烟馆的某老人告诉笔者,他说:鸦片烟馆这种行业,生意也不是那么容易做,俗话说“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争着干”。鸦片生意利润较丰,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一方面。民国时期,政令多受,朝令夕改是常事,令人很难捉摸,从整个时期来说,公开经营,是民国十二年(1923)张毅统治漳州那一阵子,到民国二十年(1931)福建省成立所谓“禁烟查缉处”,鸦片税额招商承包;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又改为“寓禁于征”,这期间大半都是在躲躲闪闪或半掩门的情况下经营的。公开经营鸦片铺既是非法的,那么就有风险,稍有不慎便会财本无归,得罪了官长,还有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再说“婆婆”、“奶奶”多,谁都不能得罪,特别是做为靠山的“菩萨”,逢年过节、初一、十五都必须“烧香、上供”。此外,还有警察,侦探、流氓、地痞之流,都必须应付,否则,经营鸦片者就别想过得安稳的日子。这些反映,则道出了旧社会鸦片毒在漳州漫延的内幕了。
(二)鸦片的贩卖和走私
清末民初,漳州最大的顶盘鸦片经营者之一是“烈昌北溪馆”,原是经营纸馆,因鸦片利润高而兼营,址在马坪街(今延安南路门牌55号,该处现为漳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专门经营云南鸦片烟土,批发给二、三盘烟商,每两大洋(银元)二元左右,二、三盘烟商在经过掺杂之后,零售每叶(鸦片膏除了盒庄外、零售就用竹叶包裹,每叶重约一钱)售价小洋二、三角(抗日战争期间每叶涨至一元左右),质量较好的铜盒庄“福寿膏”每盒约一两,售价三元上下,半两庄二元左右。设灯供吸的三盘商烟膏零售每钱五、六角。不过,鸦片价格并不统一,时有变动。
民国二十三年间(1934),国民党政府为了搜括“剿匪”经费,在全国实行鸦片“寓禁于征”的政策。鸦片公卖,叫做“特货”,归商人承包,闽南经销“特货”的专权,由厦门人叶清和(厦门著名的“鸦片大王”)经营的“鹭通公司”包揽,叶清和能够承包经营“特货”权,靠的是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关系。当时“鹭通公司”设于厦门升平路惠通巷门牌7号,漳州的鸦片大部份由鹭通公司倾销,该公司后来扩大为“裕闽公司”,并在闽南各县遍设所谓“代理处”。其时,漳州地区的龙溪县代理处为“龙通公司”,由缉私队长亚才代理;海澄县为“德通公司”,由高仰山任经理;南靖县是“靖通公司”,由张德辉任经理。
此外,厦门地区还有“协和行”(址在厦门镇邦路),“源兴行”(址在厦门开元路),“五丰公司”和“神州药房”(址在鼓浪屿)也分别通过走私渠道及销售网络在漳州一带进行销售活动。
除了上述厦门这几家鸦片公司外,还有日本台湾浪人“十八大哥”首领林滚派人专门包运鸦片来漳,广东潮汕也有贩卖鸦片的走水(水客)走私来漳贩售。与此同时,在漳州西北部、长泰县岩溪、平和县九峰等地农民还种植罂粟(鸦片原果),长泰匪首叶文龙不但组织一批人种罂粟,还就地炼制鸦片。这些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厦门和广东的潮汕相继沦陷,但鸦片的来源与销售仍畅通无阻。日寇在厦门设立“福裕鸦片公司”,由日本浪人开设的“金合成船务公司”,用两艘“交通船”往返漳厦之间,他们勾结漳州的不法分子载运鸦片毒品到石码(今龙海市),以套取内地的粮食和副食品资敌。
鸦片的贩卖,除了那些烟馆,特货公司批另兼营外,尚有许许多多个体私贩,如马公庙“鸦片福仔”,公爷街美仔(女性)、县后斑井、新桥头阿南、圆圈边广和隆老纪等多人,他们不开设门市而私下出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鸦片的销售与吸毒不如以前那么公开,但私下运销与吸毒仍然不断。当时漳州最大的毒贩是李春辉,此人操纵着漳州地区大部份的鸦片交易,他活动十分隐蔽,从不直接出面,而漳州所有鸦片毒品的行销,基本都是通过其手下的地下网络进行交易的。据过去有一家报纸披露,在漳州一带曾经发生过利用死婴走私鸦片,他们将死婴内脏挖出,藏入鸦片,用小被包好,以逃避检查。可见烟贩们唯利是图,手段极端残忍恶劣。
(三)民国时期的“禁政”
民国时期是怎样进行禁烟的?
辛亥革命(1911)漳州光复后,当时的漳州参议员会设立各局、课,其中民事局特别设置“禁烟”一职,由吴松亭负责。虽有机构和议事,但因积习难改,实际上工作并无开展,不久,该机构也随着政局变动而解散。
民国七年(1918),陈炯明率粤军入闽,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推行新政,高喊禁烟,革除陋习等口号,但事实上在所辖的二十一县中,创设所谓“田亩捐”,又名“义捐”,实即鸦片捐,当时漳州有些农民曾为不种鸦片而捐款甚重不能交纳,推派代表进谒陈炯明陈情请予减轻,陈炯明却答说:“我们所征的是田亩捐,种植鸦片可听其自由,但捐款不能减”。这说明陈炯明只要收田亩捐,种鸦片也可以,而吸毒更有何妨!
军阀张毅自民国十二年(1923)起统治漳州的几年间,他废除原有禁令,允许烟馆公开营业,一时间,旧新烟馆遍布市内各角落,其时张正天为防务局长,于正税之外勒收烟(鸦片)捐,田亩捐(烟苗),为了勒收田亩捐,公开的胁迫农民种植罂粟,如有违抗便遭残杀。当时,漳州一群爱国青年组织“震中学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该组织青年卜益友出面请除“三害”,即烟(鸦片)、赌(赌博)、花(妓女)三害,其后卜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以枪杀。
民国十四年(1925)漳州成立了“漳属禁烟办事处”,以漳州人陈兆龙(又名彬侯,系同盟会漳州第一任会长)为主任,张寿河为禁烟总检查,陈、张二人颇有抱负,也想做一点有益大众的事,但因政局不稳,加上地方恶势力顽抗阻挠,有令难行,禁而不止。
民国十七年,张贞(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入漳,在驻漳的数年间(1928—1933),表面上三令五申要肃毒禁烟,可是田亩捐(种植鸦片捐)也是他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项目,何况他那些旅、团长中也有几个瘾君子,对于禁烟一事,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由泛滥下去,彼此皆大欢喜。
民国二十年(1931)福建省成立“禁烟查缉处”,以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规定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当时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本人就是一个吸大烟享受腐化的典型官僚,所谓禁烟只是自我标榜,而实际却是公开买卖鸦片,以招商承包鸦片税。这期间漳州也随之以征代禁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福建省主席改由十九路军的蒋光鼐担任,蒋又兼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漳州也同时设置“禁烟督察员”,但刚成立不久,十九路军进行闽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将福建改为四个省,即闽海省、兴泉省、龙漳省、延建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禁烟一事谁也顾不上,这又给予毒贩子以可乘之机,买卖鸦片和吸毒没有人过问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政府对鸦片实行“寓禁于征”的公卖政策,通过“公卖”征收重税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勘乱”经费。事实上“寓禁于征”只是巧立名目,从鸦片收取更高税额,在“禁政”之中变个手法罢了。不久,陈仪、刘建绪相继主闽,“禁烟”调子唱得高一些,就漳州的情况看,表面上政令是严加禁止,但是烟毒泛滥之势不减,只是不象以前那么公开而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民党提出对鸦片“六年禁绝计划”,而且把每年的“六月三日”定为戒烟节说的颇为冠冕堂皇,但是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实际做起来却另外一回事。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间,在南靖曾发生一起鸦片“贼抢贼”的丑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福建上膏局龙岩分局,有一批“川土”鸦片,计十一箱三百多斤,伪装成包裹邮件,从龙岩运到南靖水潮,然后由省保安团派一军官率士兵八人押运,准备运往漳州出售,事被南靖金山人吴昂成(时任汀漳师管区连长,因请假回龙山)获悉,认为发财机会到了,便纠集亲信十多人,到龙山、雁竹两乡交界处地名“九丛松柏”地方埋伏,当运鸦片的帆船抵达该处,吴指挥同伙鸣枪喊话,命令交出鸦片,吴抢劫得手后,把这批鸦片分别运往和溪、华安、漳州等地销赃。事后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电令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严查,但这是明摆的“贼抢贼”丑事,谁也不愿出头损角,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综观国民党统治中国三十几年间,对鸦片烟毒口头上说禁,而实际上国民党内的官员和军队却始终在自由抽吸,甚至他们还利用查缉鸦片、征收鸦片捐税从中牟取钱财。由此,鸦片烟毒也是不断地在各地运销和任人抽吸。笔者曾经亲眼目睹这样的事实:
1949年秋,国民党刘汝明第八兵团,被解放军追击,撤逃至漳州一带,其一四三师王守谦部驻守南靖山城时,军心惶惶不安,而这个师所部三个团长都是老烟枪,公然躺在民宅(他们占住民居)横榻上吸食鸦片,此时此地国民党军队还是不忘鸦片,悠然自得在大庭广众中吞云吐雾。(四)吸食鸦片的祸害
“鸦片”,漳州人俗称“阿片”,也叫“阿芙蓉”,又称“洋药”,是一种棕黑色的膏状物,含有吗啡成份,偶而少量服用,具有镇痛、止咳、止泻等药效,若长期服用,不但成瘾,且祸害极大。
染上鸦片烟瘾的人,由于长期吸食而发生慢性中毒,身体形状逐渐变化,脸色灰暗,双颊深陷,颧骨高耸、瘦骨嶙峋、眼神呆滞无光,精神萎靡不振,走起路来,趿着鞋子,有气无力;倘遇烟瘾犯时,更是呻吟不绝,肌肉抽搐,坐立不安,呵欠连连,鼻涕流淌,形同鬼魅,有些严重的即躺在床上或地上打滚,叫苦连天。
在旧社会,起初抽吸鸦片的,多是一些官宦、士绅、巨富、商贾,他们把抽吸鸦片当作消遣解闷的手段、寻欢作乐的方式。虽然也有一些市井小民、劳动苦力者吸用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才染上这弊害。如当苦力的拉黄包车,抬轿子,搬运工人⋯⋯,他们由于劳动强度大,超时劳作(一天连续劳作十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温饱不易,身体孱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不得不在劳动之余,吸上几口鸦片,以振作精神,继续劳作。然而抽吸鸦片者,一旦成瘾,不吸就无法干活,于是越吸身体越坏,体力越下降,生活变得越困苦。另方面,在旧社会医疗条件很差,医疗费用昂贵情况下,有些人因生病,以鸦片作麻醉、镇痛为药用,这对一般的胃病、肚子疼、腹泻等小病,也起了治标的疗效。不过从表面上似乎也能镇痛治病,但只要吸了几次,其骨子里就要中毒,成了瘾则非吸不可了。在旧社会里,有不少官僚豪绅、富商巨贾和公子哥儿,因吸食鸦片,把钱财化成缭绕的烟雾,结果家破人亡;也有一些穷人因染上烟毒而终生潦倒,行乞街头,抛尸田野。因此,凡有识之士,则视鸦片为猛兽、为魔鬼,深恶痛绝。漳州民间对鸦片的危害曾流传以下绝句:“此与杀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枪”。另有付对联也以形象化语言无情的揭露了鸦片烟毒的祸害:
“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动!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舍,不见烟火冲天。”
(五)瘾君子族的众生相
瘾君子一族,人数不少,形形色色,情况各异,笔者就漳州地区选出几个嗜烟如命的人物,介绍于下:
瘾君子一:曹本章,是满清政府最后一任的龙溪县太爷,辛亥革命漳州光复,先是逃离漳州,洪宪中又返回漳州任汀漳龙道尹。是一把“老枪”,鸦片烟瘾很深,他一贯躺在烟榻之上办公,边抽吸鸦片,边听师爷陈述案情,除了必须对外应酬外,几乎整天不离烟榻,如果因奉召晋见上司,便偷偷备上烟丸,作为烟瘾犯时吞服,以免当场露馅。
瘾君子二:叶宾,清末民初漳州最负盛名的中医,精于医学,素有一剂知,二剂已起人沉疴。他早年当师爷时便染上烟瘾,弃政从医后,未能戒掉恶习,因而生活散慢,每日须在上午九点钟以后才起床,过瘾后约十点左右开诊,日限十人,其余时间不管候诊病家情形如何,病症是否危急,病家怎么恳求,概不过问,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医术高明,医德不佳。
瘾君子三:榜舍,东门街(今新华东路)人,祖上为士宦人家,其后代名叫阿榜;原先家庭富裕,人们称他为“榜舍“。他抽吸鸦片成瘾后,每吸一口鸦片喷烟后,就喝杯浓茶并配食专门特制的“红龟粿”。吸了鸦片必然要好吃懒作,他后来闹穷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迫于无奈,只好蒸制红龟粿沿街叫卖。曾几何时,阿榜还是个有钱哥儿,人们尊称他“榜舍”,后来人们鄙视他叫“榜舍龟”。
瘾君子四:黄锥,原是南乡农民,后入城在塔仔脚码头当搬运工,早年染上吸毒恶习,后因无钱过烟瘾,竟将亲生骨肉十二岁的女儿卖给人家为童养媳。在当时,象黄锥这样因吸毒而逼死老婆、卖儿卖女的事,是时有发生的。
瘾君子五:老猴,原名尤振祥,家住芳华南路,据说祖辈是龙溪县东隅地保。满清时代,地保之职原属世袭,民国时期,此例废除,他没能沿袭地保之职,却把鸦片烟瘾遗袭下来。父母亡故后,他单身一人,由于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平日只备有一对红烛,一包鞭炮,探得某家、某户或某商店有红白喜丧事,如结婚、寿诞、开张等喜庆,便登门虚作贺仪,索取红包;或遇某家办、丧事,趁其出殡途中虚设路祭,假事吊丧,以获得祭仪。偶尔某家因养猪丢失或儿童走失,老猴为了挣点钱度日,他被雇手持一面纸招,敲打铜锣、沿街喊叫招回失物或孩子。从而人们给他绰号为“叫大哮”,这就是抽大烟的懒汉尤振祥穷苦潦倒的下场。
瘾君子六:王顺和,下井街人,其父在南门经营五谷行,家教无方,平日任他吸食鸦片和进出妓女馆。其父死后,家财很快被挥霍荡尽。因常年抽吸鸦片,烟毒太深,全身瘦骨嶙峋,精神萎靡,不能从事劳动,平日趿着一双破鞋,或到旅社客栈,或入厕所寻找别人丢下的烟屁股以度瘾。人们常说,抽了鸦片,人变为鬼,王顺和就是这样变的。
(六)百年烟毒,三个月肃清
建国后,共产党、人民政府鉴于鸦片不仅是毒害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的毒品,而且也是沾污中国人一百余年的民族耻辱,必须坚决肃清。1951年前后,漳州已经发现了不少的吸毒者,并先先后后抓了不少的鸦片烟贩,收缴几千两毒品,但由于当时尚无完整的政策措施和周密的工作步骤,只是断断续续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尚未能彻底禁绝。
1952年7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清毒工作做为中心工作来抓,全党全民一齐动手,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运动月,要求全面彻底地肃清鸦片烟毒。1952年秋,龙溪地区(即今漳州市)依据福建省委关于开展清毒运动的政策和要求,即成立龙溪地区清毒办公室专门机构,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摸底后,确定以平和、龙溪和漳州(即今芗城区)三县市作为全区的清毒重点,其他各县也要配合进行。
平和县是种植罂粟的产区,漳州和石码(今龙海市)两地是毒贩的中转站和吸毒者较多的地方。当时作重点是对的。实际上漳州与石码也早已作了准备,等待命令立即行动。
八月二十四晚十二点,全区各县同时行动,一举将所有大小毒贩和抽吸鸦片的烟民逮捕、集中。平和、漳州两地收缴鸦片烟膏一千多两,烟灯、烟枪一百多付,集中烟民二百多人,抓到毒贩三十多人,战果辉煌。
随后,各县(市)清毒宣传大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既教育了广大群众,又迫使漏网的毒犯主动地进行坦白交待。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消灭了毒品销售的社会基础,并将居住于漳州的二百多烟民,全部集中到旧龙溪地方法院(即今南昌路芗城区文明办所在地,此前,吸毒者也集中一部份在公园边经历巷“安息日会”教堂内)。依照上级规定,对集中的烟民进行清毒教育,交待清毒政策,采取自我教育形式,由烟民们自诉抽吸鸦片的危害,经过一个月的集中,以强迫戒烟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办法,在大部分人有一定悔悟情况下,经过严肃地办理“约法三章”的手续后,才放他们回家恢复正常生活。据以后观察,这些人都能改掉劣习,分别在各个行业从事正当职业和积极劳动着,其中如著名西医陈志纲,在彻底戒除毒瘾后,被选为人民代民,还当上了“漳州工人疗养院”院长。原来是个烟毒很深瘾君子的老猴(尤振祥),接受教育并戒除烟瘾后,肩挑竹筐,做着收购废品的生意,生活有保障,还成了家,精神风貌全变了,他自己编了几句顺口溜自娱:“老猴戒烟翻了身,鸡毛肉骨担上肩,三顿吃饱有酒饮,闲时看戏看绍兴(即越剧);旧底(即过去)吸食鸦片苦,现在成家也娶媒(娶老婆)”。形象地诉说了戒烟后的幸福生活。
严禁鸦片是顺人心、合民意的大好事,清毒工作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漳州经过三个月的清毒,彻底清除了肆虐百年、祸害漳州人民的鸦片烟毒。为了铲除毒根,警戒后人,龙溪地区暨漳州市依照清毒政策规定,于1952年9月15日在漳州召开公审大会,分别情况处理了一批贩毒分子,将大毒犯李春辉执行处决,漳州广和隆店主老纪判徒刑四年送苏北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安置在漳州饮食公司工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彻底解决了这项历史重任,洗刷了帝国主义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历史耻辱,全部肃清了肆虐百年,毒害漳州人民的鸦片烟毒。
注:
①参阅《南靖文史资料》第九辑陈奇芳写《一桩骇人听闻的鸦片抢劫案》。
②参阅《漳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庄德秀写《回忆漳州地区的清毒运动》。
(一)清末民初烟馆公开经营
漳州自清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就有几家经营鸦片烟馆,供人吸食。起初是那些达官贵人、官宦士绅、富家子弟,手捧鸦片枪,躺在烟榻上吸毒,不久,贩夫走卒、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也逐渐入馆吸毒了。
当时,鸦片烟馆公开营业,门前进入者不少。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政出多门,于是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已遍及城乡了。
清末民初,漳州城区开设烟馆有二十多家,其招牌字号有:双合盛、合盛、协成、兴隆、德兴、珍香、惠馨、顺和⋯⋯。分布在打锡巷、东桥亭、下营、龙眼营、上坂、新府路、双门顶,还有东门马公庙、南门竹巷下、西门西街、北门糖市等街区。
烟馆的特点是各家门前都挂一竹帘,上写本馆字号,屋檐前挂一盏方形玻璃灯,写上红字为标帜,烟馆里面烟味浓郁灯光荧荧、抽吸之声籁籁,烟鬼们吞云吐雾、个个有飘飘欲仙之态。
各家烟馆,大体上在屋子里有厅有房,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一般可供五、六人,小榻二、三人横躺吸食,各置有烟盘,其中配有烟枪、烟灯、烟杆、茶具等。
烟枪是用甘蔗套上竹筒所制,配上烟嘴、烟斗即成。当时有两句形容烟枪的顺口溜说:“甘蔗入竹广(筒),吸了才会爽”(闽南方言)。上层社会私家使用的烟枪,那就比较考究、精致,例如有用象牙或玉石镶成,烟盘用宣枝嵌花,铜质的烟灯灯台,清水玻璃灯罩。富人士绅人家,一般备有二、三套烟具,以备招待客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对鸦片“寓禁于征”,鸦片烟馆则“挂羊头卖狗肉”,改头换面,一夜之间,所有“鸦片馆”可以变成“戒烟所”了。
据熟悉经营烟馆的某老人告诉笔者,他说:鸦片烟馆这种行业,生意也不是那么容易做,俗话说“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争着干”。鸦片生意利润较丰,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一方面。民国时期,政令多受,朝令夕改是常事,令人很难捉摸,从整个时期来说,公开经营,是民国十二年(1923)张毅统治漳州那一阵子,到民国二十年(1931)福建省成立所谓“禁烟查缉处”,鸦片税额招商承包;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又改为“寓禁于征”,这期间大半都是在躲躲闪闪或半掩门的情况下经营的。公开经营鸦片铺既是非法的,那么就有风险,稍有不慎便会财本无归,得罪了官长,还有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再说“婆婆”、“奶奶”多,谁都不能得罪,特别是做为靠山的“菩萨”,逢年过节、初一、十五都必须“烧香、上供”。此外,还有警察,侦探、流氓、地痞之流,都必须应付,否则,经营鸦片者就别想过得安稳的日子。这些反映,则道出了旧社会鸦片毒在漳州漫延的内幕了。
(二)鸦片的贩卖和走私
清末民初,漳州最大的顶盘鸦片经营者之一是“烈昌北溪馆”,原是经营纸馆,因鸦片利润高而兼营,址在马坪街(今延安南路门牌55号,该处现为漳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专门经营云南鸦片烟土,批发给二、三盘烟商,每两大洋(银元)二元左右,二、三盘烟商在经过掺杂之后,零售每叶(鸦片膏除了盒庄外、零售就用竹叶包裹,每叶重约一钱)售价小洋二、三角(抗日战争期间每叶涨至一元左右),质量较好的铜盒庄“福寿膏”每盒约一两,售价三元上下,半两庄二元左右。设灯供吸的三盘商烟膏零售每钱五、六角。不过,鸦片价格并不统一,时有变动。
民国二十三年间(1934),国民党政府为了搜括“剿匪”经费,在全国实行鸦片“寓禁于征”的政策。鸦片公卖,叫做“特货”,归商人承包,闽南经销“特货”的专权,由厦门人叶清和(厦门著名的“鸦片大王”)经营的“鹭通公司”包揽,叶清和能够承包经营“特货”权,靠的是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关系。当时“鹭通公司”设于厦门升平路惠通巷门牌7号,漳州的鸦片大部份由鹭通公司倾销,该公司后来扩大为“裕闽公司”,并在闽南各县遍设所谓“代理处”。其时,漳州地区的龙溪县代理处为“龙通公司”,由缉私队长亚才代理;海澄县为“德通公司”,由高仰山任经理;南靖县是“靖通公司”,由张德辉任经理。
此外,厦门地区还有“协和行”(址在厦门镇邦路),“源兴行”(址在厦门开元路),“五丰公司”和“神州药房”(址在鼓浪屿)也分别通过走私渠道及销售网络在漳州一带进行销售活动。
除了上述厦门这几家鸦片公司外,还有日本台湾浪人“十八大哥”首领林滚派人专门包运鸦片来漳,广东潮汕也有贩卖鸦片的走水(水客)走私来漳贩售。与此同时,在漳州西北部、长泰县岩溪、平和县九峰等地农民还种植罂粟(鸦片原果),长泰匪首叶文龙不但组织一批人种罂粟,还就地炼制鸦片。这些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厦门和广东的潮汕相继沦陷,但鸦片的来源与销售仍畅通无阻。日寇在厦门设立“福裕鸦片公司”,由日本浪人开设的“金合成船务公司”,用两艘“交通船”往返漳厦之间,他们勾结漳州的不法分子载运鸦片毒品到石码(今龙海市),以套取内地的粮食和副食品资敌。
鸦片的贩卖,除了那些烟馆,特货公司批另兼营外,尚有许许多多个体私贩,如马公庙“鸦片福仔”,公爷街美仔(女性)、县后斑井、新桥头阿南、圆圈边广和隆老纪等多人,他们不开设门市而私下出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鸦片的销售与吸毒不如以前那么公开,但私下运销与吸毒仍然不断。当时漳州最大的毒贩是李春辉,此人操纵着漳州地区大部份的鸦片交易,他活动十分隐蔽,从不直接出面,而漳州所有鸦片毒品的行销,基本都是通过其手下的地下网络进行交易的。据过去有一家报纸披露,在漳州一带曾经发生过利用死婴走私鸦片,他们将死婴内脏挖出,藏入鸦片,用小被包好,以逃避检查。可见烟贩们唯利是图,手段极端残忍恶劣。
(三)民国时期的“禁政”
民国时期是怎样进行禁烟的?
辛亥革命(1911)漳州光复后,当时的漳州参议员会设立各局、课,其中民事局特别设置“禁烟”一职,由吴松亭负责。虽有机构和议事,但因积习难改,实际上工作并无开展,不久,该机构也随着政局变动而解散。
民国七年(1918),陈炯明率粤军入闽,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推行新政,高喊禁烟,革除陋习等口号,但事实上在所辖的二十一县中,创设所谓“田亩捐”,又名“义捐”,实即鸦片捐,当时漳州有些农民曾为不种鸦片而捐款甚重不能交纳,推派代表进谒陈炯明陈情请予减轻,陈炯明却答说:“我们所征的是田亩捐,种植鸦片可听其自由,但捐款不能减”。这说明陈炯明只要收田亩捐,种鸦片也可以,而吸毒更有何妨!
军阀张毅自民国十二年(1923)起统治漳州的几年间,他废除原有禁令,允许烟馆公开营业,一时间,旧新烟馆遍布市内各角落,其时张正天为防务局长,于正税之外勒收烟(鸦片)捐,田亩捐(烟苗),为了勒收田亩捐,公开的胁迫农民种植罂粟,如有违抗便遭残杀。当时,漳州一群爱国青年组织“震中学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该组织青年卜益友出面请除“三害”,即烟(鸦片)、赌(赌博)、花(妓女)三害,其后卜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以枪杀。
民国十四年(1925)漳州成立了“漳属禁烟办事处”,以漳州人陈兆龙(又名彬侯,系同盟会漳州第一任会长)为主任,张寿河为禁烟总检查,陈、张二人颇有抱负,也想做一点有益大众的事,但因政局不稳,加上地方恶势力顽抗阻挠,有令难行,禁而不止。
民国十七年,张贞(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入漳,在驻漳的数年间(1928—1933),表面上三令五申要肃毒禁烟,可是田亩捐(种植鸦片捐)也是他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项目,何况他那些旅、团长中也有几个瘾君子,对于禁烟一事,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由泛滥下去,彼此皆大欢喜。
民国二十年(1931)福建省成立“禁烟查缉处”,以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规定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当时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本人就是一个吸大烟享受腐化的典型官僚,所谓禁烟只是自我标榜,而实际却是公开买卖鸦片,以招商承包鸦片税。这期间漳州也随之以征代禁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福建省主席改由十九路军的蒋光鼐担任,蒋又兼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漳州也同时设置“禁烟督察员”,但刚成立不久,十九路军进行闽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将福建改为四个省,即闽海省、兴泉省、龙漳省、延建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禁烟一事谁也顾不上,这又给予毒贩子以可乘之机,买卖鸦片和吸毒没有人过问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政府对鸦片实行“寓禁于征”的公卖政策,通过“公卖”征收重税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勘乱”经费。事实上“寓禁于征”只是巧立名目,从鸦片收取更高税额,在“禁政”之中变个手法罢了。不久,陈仪、刘建绪相继主闽,“禁烟”调子唱得高一些,就漳州的情况看,表面上政令是严加禁止,但是烟毒泛滥之势不减,只是不象以前那么公开而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民党提出对鸦片“六年禁绝计划”,而且把每年的“六月三日”定为戒烟节说的颇为冠冕堂皇,但是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实际做起来却另外一回事。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间,在南靖曾发生一起鸦片“贼抢贼”的丑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福建上膏局龙岩分局,有一批“川土”鸦片,计十一箱三百多斤,伪装成包裹邮件,从龙岩运到南靖水潮,然后由省保安团派一军官率士兵八人押运,准备运往漳州出售,事被南靖金山人吴昂成(时任汀漳师管区连长,因请假回龙山)获悉,认为发财机会到了,便纠集亲信十多人,到龙山、雁竹两乡交界处地名“九丛松柏”地方埋伏,当运鸦片的帆船抵达该处,吴指挥同伙鸣枪喊话,命令交出鸦片,吴抢劫得手后,把这批鸦片分别运往和溪、华安、漳州等地销赃。事后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电令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严查,但这是明摆的“贼抢贼”丑事,谁也不愿出头损角,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综观国民党统治中国三十几年间,对鸦片烟毒口头上说禁,而实际上国民党内的官员和军队却始终在自由抽吸,甚至他们还利用查缉鸦片、征收鸦片捐税从中牟取钱财。由此,鸦片烟毒也是不断地在各地运销和任人抽吸。笔者曾经亲眼目睹这样的事实:
1949年秋,国民党刘汝明第八兵团,被解放军追击,撤逃至漳州一带,其一四三师王守谦部驻守南靖山城时,军心惶惶不安,而这个师所部三个团长都是老烟枪,公然躺在民宅(他们占住民居)横榻上吸食鸦片,此时此地国民党军队还是不忘鸦片,悠然自得在大庭广众中吞云吐雾。(四)吸食鸦片的祸害
“鸦片”,漳州人俗称“阿片”,也叫“阿芙蓉”,又称“洋药”,是一种棕黑色的膏状物,含有吗啡成份,偶而少量服用,具有镇痛、止咳、止泻等药效,若长期服用,不但成瘾,且祸害极大。
染上鸦片烟瘾的人,由于长期吸食而发生慢性中毒,身体形状逐渐变化,脸色灰暗,双颊深陷,颧骨高耸、瘦骨嶙峋、眼神呆滞无光,精神萎靡不振,走起路来,趿着鞋子,有气无力;倘遇烟瘾犯时,更是呻吟不绝,肌肉抽搐,坐立不安,呵欠连连,鼻涕流淌,形同鬼魅,有些严重的即躺在床上或地上打滚,叫苦连天。
在旧社会,起初抽吸鸦片的,多是一些官宦、士绅、巨富、商贾,他们把抽吸鸦片当作消遣解闷的手段、寻欢作乐的方式。虽然也有一些市井小民、劳动苦力者吸用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才染上这弊害。如当苦力的拉黄包车,抬轿子,搬运工人⋯⋯,他们由于劳动强度大,超时劳作(一天连续劳作十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温饱不易,身体孱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不得不在劳动之余,吸上几口鸦片,以振作精神,继续劳作。然而抽吸鸦片者,一旦成瘾,不吸就无法干活,于是越吸身体越坏,体力越下降,生活变得越困苦。另方面,在旧社会医疗条件很差,医疗费用昂贵情况下,有些人因生病,以鸦片作麻醉、镇痛为药用,这对一般的胃病、肚子疼、腹泻等小病,也起了治标的疗效。不过从表面上似乎也能镇痛治病,但只要吸了几次,其骨子里就要中毒,成了瘾则非吸不可了。在旧社会里,有不少官僚豪绅、富商巨贾和公子哥儿,因吸食鸦片,把钱财化成缭绕的烟雾,结果家破人亡;也有一些穷人因染上烟毒而终生潦倒,行乞街头,抛尸田野。因此,凡有识之士,则视鸦片为猛兽、为魔鬼,深恶痛绝。漳州民间对鸦片的危害曾流传以下绝句:“此与杀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枪”。另有付对联也以形象化语言无情的揭露了鸦片烟毒的祸害:
“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动!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舍,不见烟火冲天。”
(五)瘾君子族的众生相
瘾君子一族,人数不少,形形色色,情况各异,笔者就漳州地区选出几个嗜烟如命的人物,介绍于下:
瘾君子一:曹本章,是满清政府最后一任的龙溪县太爷,辛亥革命漳州光复,先是逃离漳州,洪宪中又返回漳州任汀漳龙道尹。是一把“老枪”,鸦片烟瘾很深,他一贯躺在烟榻之上办公,边抽吸鸦片,边听师爷陈述案情,除了必须对外应酬外,几乎整天不离烟榻,如果因奉召晋见上司,便偷偷备上烟丸,作为烟瘾犯时吞服,以免当场露馅。
瘾君子二:叶宾,清末民初漳州最负盛名的中医,精于医学,素有一剂知,二剂已起人沉疴。他早年当师爷时便染上烟瘾,弃政从医后,未能戒掉恶习,因而生活散慢,每日须在上午九点钟以后才起床,过瘾后约十点左右开诊,日限十人,其余时间不管候诊病家情形如何,病症是否危急,病家怎么恳求,概不过问,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医术高明,医德不佳。
瘾君子三:榜舍,东门街(今新华东路)人,祖上为士宦人家,其后代名叫阿榜;原先家庭富裕,人们称他为“榜舍“。他抽吸鸦片成瘾后,每吸一口鸦片喷烟后,就喝杯浓茶并配食专门特制的“红龟粿”。吸了鸦片必然要好吃懒作,他后来闹穷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迫于无奈,只好蒸制红龟粿沿街叫卖。曾几何时,阿榜还是个有钱哥儿,人们尊称他“榜舍”,后来人们鄙视他叫“榜舍龟”。
瘾君子四:黄锥,原是南乡农民,后入城在塔仔脚码头当搬运工,早年染上吸毒恶习,后因无钱过烟瘾,竟将亲生骨肉十二岁的女儿卖给人家为童养媳。在当时,象黄锥这样因吸毒而逼死老婆、卖儿卖女的事,是时有发生的。
瘾君子五:老猴,原名尤振祥,家住芳华南路,据说祖辈是龙溪县东隅地保。满清时代,地保之职原属世袭,民国时期,此例废除,他没能沿袭地保之职,却把鸦片烟瘾遗袭下来。父母亡故后,他单身一人,由于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平日只备有一对红烛,一包鞭炮,探得某家、某户或某商店有红白喜丧事,如结婚、寿诞、开张等喜庆,便登门虚作贺仪,索取红包;或遇某家办、丧事,趁其出殡途中虚设路祭,假事吊丧,以获得祭仪。偶尔某家因养猪丢失或儿童走失,老猴为了挣点钱度日,他被雇手持一面纸招,敲打铜锣、沿街喊叫招回失物或孩子。从而人们给他绰号为“叫大哮”,这就是抽大烟的懒汉尤振祥穷苦潦倒的下场。
瘾君子六:王顺和,下井街人,其父在南门经营五谷行,家教无方,平日任他吸食鸦片和进出妓女馆。其父死后,家财很快被挥霍荡尽。因常年抽吸鸦片,烟毒太深,全身瘦骨嶙峋,精神萎靡,不能从事劳动,平日趿着一双破鞋,或到旅社客栈,或入厕所寻找别人丢下的烟屁股以度瘾。人们常说,抽了鸦片,人变为鬼,王顺和就是这样变的。
(六)百年烟毒,三个月肃清
建国后,共产党、人民政府鉴于鸦片不仅是毒害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的毒品,而且也是沾污中国人一百余年的民族耻辱,必须坚决肃清。1951年前后,漳州已经发现了不少的吸毒者,并先先后后抓了不少的鸦片烟贩,收缴几千两毒品,但由于当时尚无完整的政策措施和周密的工作步骤,只是断断续续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尚未能彻底禁绝。
1952年7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清毒工作做为中心工作来抓,全党全民一齐动手,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运动月,要求全面彻底地肃清鸦片烟毒。1952年秋,龙溪地区(即今漳州市)依据福建省委关于开展清毒运动的政策和要求,即成立龙溪地区清毒办公室专门机构,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摸底后,确定以平和、龙溪和漳州(即今芗城区)三县市作为全区的清毒重点,其他各县也要配合进行。
平和县是种植罂粟的产区,漳州和石码(今龙海市)两地是毒贩的中转站和吸毒者较多的地方。当时作重点是对的。实际上漳州与石码也早已作了准备,等待命令立即行动。
八月二十四晚十二点,全区各县同时行动,一举将所有大小毒贩和抽吸鸦片的烟民逮捕、集中。平和、漳州两地收缴鸦片烟膏一千多两,烟灯、烟枪一百多付,集中烟民二百多人,抓到毒贩三十多人,战果辉煌。
随后,各县(市)清毒宣传大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既教育了广大群众,又迫使漏网的毒犯主动地进行坦白交待。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消灭了毒品销售的社会基础,并将居住于漳州的二百多烟民,全部集中到旧龙溪地方法院(即今南昌路芗城区文明办所在地,此前,吸毒者也集中一部份在公园边经历巷“安息日会”教堂内)。依照上级规定,对集中的烟民进行清毒教育,交待清毒政策,采取自我教育形式,由烟民们自诉抽吸鸦片的危害,经过一个月的集中,以强迫戒烟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办法,在大部分人有一定悔悟情况下,经过严肃地办理“约法三章”的手续后,才放他们回家恢复正常生活。据以后观察,这些人都能改掉劣习,分别在各个行业从事正当职业和积极劳动着,其中如著名西医陈志纲,在彻底戒除毒瘾后,被选为人民代民,还当上了“漳州工人疗养院”院长。原来是个烟毒很深瘾君子的老猴(尤振祥),接受教育并戒除烟瘾后,肩挑竹筐,做着收购废品的生意,生活有保障,还成了家,精神风貌全变了,他自己编了几句顺口溜自娱:“老猴戒烟翻了身,鸡毛肉骨担上肩,三顿吃饱有酒饮,闲时看戏看绍兴(即越剧);旧底(即过去)吸食鸦片苦,现在成家也娶媒(娶老婆)”。形象地诉说了戒烟后的幸福生活。
严禁鸦片是顺人心、合民意的大好事,清毒工作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漳州经过三个月的清毒,彻底清除了肆虐百年、祸害漳州人民的鸦片烟毒。为了铲除毒根,警戒后人,龙溪地区暨漳州市依照清毒政策规定,于1952年9月15日在漳州召开公审大会,分别情况处理了一批贩毒分子,将大毒犯李春辉执行处决,漳州广和隆店主老纪判徒刑四年送苏北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安置在漳州饮食公司工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彻底解决了这项历史重任,洗刷了帝国主义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历史耻辱,全部肃清了肆虐百年,毒害漳州人民的鸦片烟毒。
注:
①参阅《南靖文史资料》第九辑陈奇芳写《一桩骇人听闻的鸦片抢劫案》。
②参阅《漳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庄德秀写《回忆漳州地区的清毒运动》。
附注
注:
①参阅《南靖文史资料》第九辑陈奇芳写《一桩骇人听闻的鸦片抢劫案》。
②参阅《漳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庄德秀写《回忆漳州地区的清毒运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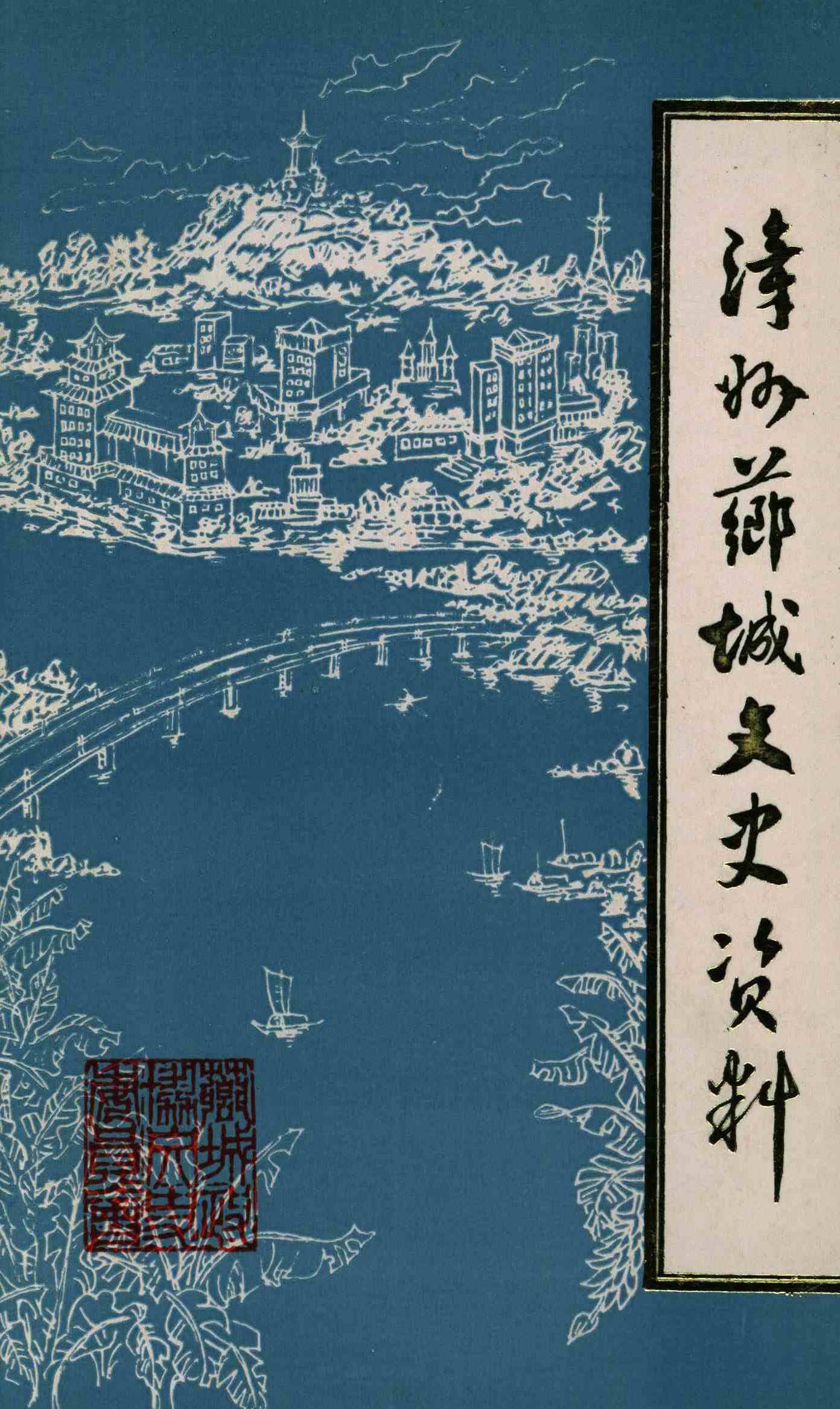
相关人物
黄叶沱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漳州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