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仪式观视域中的港里村妈祖信俗传播
| 内容出处: | 《传播学视野下的妈祖文化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620020220000472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仪式观视域中的港里村妈祖信俗传播 |
| 分类号: | B933 |
| 页数: | 17 |
| 页码: | 109-125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仪式观视域中的港里村妈祖信俗传播情况,包括传播仪式观、传播仪式观视域中的妈祖信俗传播与共同体建构两部分内容。 |
| 关键词: | 文化传播 妈祖信俗 仪式观 |
内容
对于传播仪式观的考察,要结合具体的实践才能够得以深入而全面地展开。如前所述,凯瑞的仪式传播观的六个核心概念:文化、传播、仪式、技术、新闻和会话,这些概念无不与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在妈祖文化作为文化传播的过程之中,这六种社会实践活动怎样具体而微地与传播仪式观进行了勾连,我们选取了一个村落——位于莆田湄洲湾北岸的港里村,以港里村妈祖信俗传播为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具体地探讨传播仪式观。
一、传播仪式观
台湾知名学者,与林美容教授并称“妈祖婆”的张珣教授在其《妈祖·信仰的追寻》一书中,就人类学对于宗教现象的研究特点提出了如下观点:被当做文化象征(宗教、节庆、伦理、价值)来处理;其组织视同社会组织之一,探究的是其间的分合纠结;分析仪式应该注意其传递文化理念与规范社会秩序的价值;重视集体的情感认同甚于个人的神秘经验之唤起。①
对于中国的社会实践而言,相比于官方色彩浓厚的儒、释、道三教,各种活跃在乡间田垄的地方性神明,更贴近百姓的生活,更受欢迎,妈祖信俗即其中较有特色和有影响力者之一。作为百姓日常生活基本层面的民间信仰,是我们考察和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图像”的重点与焦点所在。那么,民间信仰产生的机制、功能和影响如何?一些学者已经从自己的角度试着回答这些问题,认为民问信仰的寺庙或者宗祠,常常成为一个社区的“祭祀圈”或城镇的“信仰圈”的中心,有效地推动了城乡社区自我组织的形成和自我管理的完善。②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民间信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身份认同感的产生与发展。本节将从传播学角度出发,以港里村为例,来研究妈祖信俗。但是,由于田野调查的工作不足,相关资料的欠缺,本节所呈现的仅是一个初步的理解与思路的概述。
对于民间信仰仪式与族群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更倾向于将仪式看作是一个族群使用象征符号的一种习惯或集中使用象征符号的形式。为了进一步阐释象征符号是如何在信众中间产生互动,以及如何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文化的认同感,我们引入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凯瑞在其《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出,传播学研究视角可以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两大类。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具有深厚的宗教渊源: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它(传播的仪式观)“并不看重布道、说教和教海的作用,为的是强调祷告者、圣歌及典礼的重要性”因此,“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
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①以这样一种观念来理解传播问题,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作为一个非常庞杂、难以把握的概念,“民间信仰”显然是多面向的。出于选择切入点的考虑,我们特别关注妈祖信俗中重要的“仪式”环节,以妈祖信俗核心传播区之一港里村的妈祖信俗传播为研究对象,研究它是如何在文化认同乃至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上发挥作用的。涂尔干曾强调,信仰,特别是仪式,是一种加强传统上个人之间的社会纽带的方式;②格尔茨进一步说明,它涉及生活准则及世界观的融合,形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③杜威则相信传播扮演着重要的认识角色,不是把知识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简单角色,而是创造知识的丰富意义。这源于他对传播的独特理解:传播是人类生活唯一的手段和目的。作为手段,它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中解放出来,并能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作为目的,它使人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传播值得人们当作手段,因为它是使人类生活丰富多彩、意义广泛的唯一手段;它值得人们当作生活的目的,因为它能把人从孤独中解救
出来,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①
在这里,公众存在于“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中,它通过参与式传播融入共同体生活之中,这种以传播创造社会共同体的理念,为我们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信仰仪式开启了一个崭新视角。“在一个高度互动的传播系统中,已经不可能划分‘来源’和‘受众’,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变革了受众研究的思维空间,着眼于在人与人的互动与意义分享的层面探讨媒介效果,在主体间的整合意义上建构受众。”②作为一种可能的致思取向,它关涉主体间的传播关系,也关涉多级主体间的意义分享。本节拟由观察符号互动与族群秩序、祭祀仪式与文化认同而体察妈祖信俗传播与妈祖文化共同体建构之问的微妙关系,并且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种理想境界的妈祖文化共同体建构与村民日常生活中妈祖信俗仪式化之间存在的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背离的关系?
二、传播仪式观视域中的妈祖信俗传播与共同体建构
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族群是那些体质类型或因习俗的相似性,或因殖民或移民的记忆,而对共同的血统享有主观信仰的人群。而认同则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术语,指帮助个体在个体自身生活中产生秩序,并帮助个体置身于群体之中或卷入与集体的认同。③学界对于族群认同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族源认同、语言认同、宗教认同、生活习俗认同、性格特征认同。显然,本书着力探讨的是族群的文化认同,具体而言即研究妈祖信俗传播与仪式中的认同乃至妈祖文化共同体之关系。
首先是时间维度,研究妈祖信俗、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的历史传承。通过对神活传说之生产、加工、流传的解释,对族谱记载的故事、警语、祖训、族范的解读,对游神仪式、祭祀习俗演变的解析,试图说明民间信仰在时间上的延续、传播,形成了港里社区居民的共同历史记忆,产生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神”这些观念,从而强化了彼此的认同。
其次是空间维度,研究妈祖宫庙、祠堂,及其他庙宇在港里社区中的空间散布。通过实地考察,确认各庙宇、祠堂的地理位置,绘制地图,对照各村的行政划分,我们发现自然村的分界与民间信仰“祭祀圈”的分界基本吻合,并且有着鲜明的层次感。天后祖祠、福慧寺、五帝庙、吴祖社、新兴社、灵慈东宫、灵慈西宫、接水亭、鳌层宫、开元宫、小港开山宫、黄氏祠堂、钱楼社、姨妈府、泰山大哥府等各宫庙与自然村之间均有其相对应的关系。族群边界与民间信仰边界的基本重合,初步印证了本研究的基本假设。
最后一个维度,则是研究在共时空下举行的各种民间信仰仪式与族群认同有着怎样的联系。仪式,向来是人类学家考察一个社区内人们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截面,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仪式是宗教活动最主要的层面,华莱士则把仪式看作是宗教的主要现象,即行动中的宗教。①中国学者在研究民间信仰问题时,也十分看重仪式在维持传统乡土社会秩序、促进村落内部凝聚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刘晓春在对客家村落的研究中提到,以家族为单位所举行的仪式表演既提高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也促进了家族成员基于共同的家族利益对外协作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助。显然,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如何运用传播的仪式观来看待妈祖信俗中的仪式,则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
褚建芳在《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一书中认为,民间信仰仪式“最明显、最集中地反映和表达了当地人们对人与世界的理解、解释与看法,并揭示了他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以及整体运作规范、逻辑与秩序”,而人类学对于民间信仰仪式的研究,大体上有三种取向,一是把仪式看作情感表达的场合,二是将其看作戏剧表演或游戏,三是把仪式看成是人与神圣力量的交流过程。②我们视民间信仰仪式为一种交流的方式,但认为它未必仅限于人与神之间的交流,某种程度上,参与仪式的人们之间也存在交流的过程(未必只是语言交流);究其根本,人神交流、人人交流,都可以归结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象征符号互动——当然,本书的最终目的不仅局限于研究民间信仰中交流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仪式的“符号秩序”的生产、互动,进而研究人与人之间、人与传统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他们可以建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一种独立存在的自我认同”“这种意义系统渗透在家庭和地区的日常生活当中”日常,①,家庭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被这种意义的范式所渗透和支撑,老辈人通过这种意义范式讨论他们所分享的情境体验。在社会化进程中,尤其在家庭与社区的范围之内,这种意义系统在年青一代的成长过程中被再生产,并构成想象的基本框架,透过这一框架,他们接近其社会经验。就其要者,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民间信仰仪式中的祭祀品、祭祀仪式以及仪式进程中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探讨港里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象征符号互动问题。
仪式,向来是人类学家考察一个社区内人们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截面,既然选择仪式,尤其是仪式中的象征符号互动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那么就港里村的民间仪式本身而言,它的哪些方面体现了我们所关注的“交流”的问题呢?
在港里村,除“妈祖回娘家”“海祭妈祖”习俗外,尚有“妈祖元宵”、港里“大月半”、福慧寺“廿二拖”、五月初五烧瘟船等习俗,以及港里遗存的结婚闹洞房“做经文”和“寿旦喜庆”等古已有之的民俗。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梳理,以及对自身田野生活体验的总结,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民间信仰仪式中的祭品、祭祀仪式,以及仪式进程中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象征符号互动问题。
(一)祭品
研究祭祀品,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研究人与神之间的交流。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人与神之间的交流是不平等地位者之间的信息交流,需要通过一个中介物来实现,而这个中介物就是人们在仪式中向神进献的祭祀品”。②
有学者认为,所谓祭品,如贡品、鞭炮、香烛等,实际上是人们向神明献上的贿赂,企图以较小的代价换得较大的利益,如平安、得子、高升等。祭祀品不单纯是利益的交易,也体现了人对于神明的虔诚之心和敬畏之感,“如果不为仪式花足够的钱就等于是对命运、祖先和神的不尊,这反过来就等于是对自己幸福的潜在威胁”。①
我们在港里村发现,这种“贿赂”神的现象十分普遍。无论祭祖还是拜神,村民一般会选择在初一、十五或者神、社节日,尤其是年初正月期间,为神明备上果、糖等祭品,焚香许愿,承诺如果愿望得到实现,就会以更丰富的祭品来还愿,否则会引来其他村民的非议,因为他们认为不“还神”会惹神明生气,降祸到村里,殃及池鱼。祭品都要遵循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品类、数量都有讲究。如胡乱向神献祭品,会被人耻笑,也可能会得罪村里在这方面的权威长者。因此,各家准备祭品的人选,一般是年纪较大的妇女,她们在祭祀这一方面往往博学而稳重。
而褚建芳在其著作中则从财产合法性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云南傣族村落佛教信仰中“献卤”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意涵。他反复提及“卤”和“阿祚”两个概念(均为傣语),认为人和神之间存在一种“道义互惠”关系,表现为三个层次的“施”与“报”。表面上看,“卤”可以认为是信众向佛进献的斋饭、鲜花、香烛等物品,以求得佛给予信众的“阿祚”(翻译成汉语就是“福分”)。这是第一层面的施与报的关系。然而,在献卤的仪式过程中,祭祀品的所有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转移,它仍然是属于献卤的人——拿回去吃掉或者扔掉。既然认为祭祀品的所有权在人神交流的过程中没有被让渡,那么信众向佛送出了什么?而佛又向信众回报了什么?实际上,信众是通过祭祀品这个中介物表达自己对佛的尊敬和服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诚心”;反过来,佛则报以“阿祚”,表示认可。用作者的话来说,“在献祭仪式中,作为供品的物质实体本身并不重要,它们只是把献祭的人和所祭拜的神祇联系起来的中介物,起到了表达或者传递信息的作用”。②这是第二个层面上的施与报的关系。当然,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出发,将祭祀品视作传递人神之间亲善友好信息的中介,显然是不够深刻的。那么,祭祀品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究竟在人神交流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涂尔干看来,人类的财产权仅仅是神的财产权的替代物。人们需要通过定期举行仪式,取得神对其财产使用权的认可,从而维持和确认其合法性。祭祀品的象征意义在于,财产的合法性有着神圣的起源,人与神之间的从属关系是这一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人们通过定期向神奉献祭祀品表示对该从属关系的服膺,从而获取当世财产的合法性,以及来世财产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三个层面上施与报的关系。这里的“神”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是世俗人间道德与力量完美结合的理想人物,是地方社会规范的抽象化的道德模范”。①也就是说,人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集体或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通过象征符号互动确立起来的人神之间的神圣契约与神圣秩序,一旦流传开来,成为族群中大多数人所遵从的原则,显然有利于一个族群内部的和谐稳定和统一。
具体到妈祖信俗的祭祀仪式中,“妈祖回娘家”和“海祭妈祖”祭祀习俗并列为天后祖祠的“春秋两祭”,是港里村所有祭祀活动中最盛者,活动中所使用的祭品之多、材质之好、造型之精美更是无以复加。而最能体现当地人继承中原汉族遗风的祭品,当属“少牢”。所谓少牢,指的是“古代祭祀燕烹用羊、豕各一者”。根据《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自宋以降,各朝谕祭妈祖的仪式均非常隆重。《明史·礼志》记:“降香遣官仪:祀前一日清晨,皇帝披弁服,升奉天殿,捧香者以香授献官(奉旨主祭者),献官捧由中陛降中道,出至午门外,置(香)龙亭内,仪仗鼓吹导引至祭所,后定:祭之日降香,如常仪。中严(祭庙森严)以待献官,祭毕,复命,解严还宫。”又记:永乐七年(1409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诸庙皆少牢(羊一、猪一)。”《清史稿·礼志》记:“凡列祀典者,有司(地方官)随时致严(虔)。用羊一、猪一、果五盘、帛一、樽一、爵三,读祝叩拜如故事。”
港里村民一直恪守这一礼制,称之为“猪羊祭”,祭祀用的猪和羊各一只②。而准备祭品的花费,则是由林氏后裔捐款,交董事会统一管理。祭祀完毕,董事会义工将祭品分发至各户人家,共同享用。这样的做法代代传承,成为族群中所有人遵从的原则,在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的同时又规范着族群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有利于族群内部的和谐稳定和统一。
(二)祭祀仪式
在论及港里村的祖先崇拜、妈祖信俗的祭祀仪式之前,我们必须先对“祭祀仪式”这一个概念进行界定。所谓“祭祀仪式”指的是民间信仰仪式的各种程序,包括跪拜、进香、摇签、卜杯、敬酒等等。社,会人类学家特纳(VictorTunner)认为,这些祭祀仪式会带来个人的超脱感、安慰、安全甚至狂喜,或对一起参加仪式的人的亲切感;法国早期人类学家范瑾尼(A.VanGennep)则
提出,祭祀仪式的目的是帮助人在一生中比较容易地通过一些关口,如生、老、病、死这些过程。①
本书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出发,虽然也赞同祭祀仪式具有上述功能,但我们更关注作为象征符号,它们是如何促进人与社会(社区)之间的互动,进而产生文化上的认同。
前面提到的祭祀品主要反映的是人神之间的交流,而祭祀仪式则是在人神交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多人与人之间交流层面。下面则以最为常见的“卜杯”和“摇签”这两种仪式以及新近增加的“头炷香”仪式来说明。
莆田妈祖宫庙中,常用一对木制或竹制的半月形,一面平坦、一面隆起的法器,向妈祖问卜。每片“筶”有两面,光滑平整的一面为阳,呈半圆柱体弧形的一面为阴。而两片“筶”搭配组合,就会出现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阴一阳,称为“圣筶”,好兆头;两片都是阳面,为“阳筶”,运气不好不坏;两片都是阴面,则为“阴筶”,很不吉祥。
在莆田当地广为流传的是这样一则与少年妈祖林默有关的故事。在贤良港妈祖祖祠不远处,有一地名地鼎,是古时铸鼎(莆田人称铁锅为鼎)之地,该地铸的鼎质量非常好,故而有名。相传,有一天,少女林默去看铸鼎,不料师傅却连续三次铸不成,发现有个女孩子在旁边观看之后,要赶她走,小林默说:“走可以,但我要一点烧红的铁砂。”师傅当即满足她的要求,她遂用双手捧起烧红的铁砂回家,双手安然无恙,而手中的铁砂则冷却成了一对筶杯。
笔者曾多次看到满脸虔诚的人们(以妇女居多)在妈祖像前进香、跪拜,通过“掷筶”和“摇签”向妈祖询问某事是否可行。卜得圣杯,则欢天喜地,允诺事成之后必来筶谢;否则,也会向妈祖谢恩,感谢她的庇佑。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到的象征符号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下人们的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表征。正如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所说,文化就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他同时指出,文化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①因此,我们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来看“掷筶”这种文化现象时,应当“毫无负担”地将其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来考察仪式中的交流问题。“掷筶”表面上是人神之间交流的信息传递工具,但就更深层的意义而言,它象征了人类对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朴素认识和敬畏。它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对于自身以及这个世界的觉悟,并且对此深信不疑。在同一时空中,参与祭祀仪式的人们对于自身和世界具有近似或共通的感知,因而彼此之间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又由于仪式具有“表演性”和“重复性”,既使得仪式本身得到超越时空的传承,也让其象征的世界观得以“集体记忆”的形式流传后世。因此,人与人之间借助祭祀仪式这种象征符号实现了交流和文化传承。在这样一个创造、分享、修正和保存现实的过程中,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认同也就得到了强化,并为重塑族群的共同文化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摇签”仪式也可以看作是促进族群认同的象征符号互动。陈进国指出,抽签(即“摇签”)是中国民间社会流行的一种签卜术。我们所了解的港里社区的祭祀仪式中的“摇签”用的是竹制灵签,在27根竹签上分别写上编号,放入一个竹筒;信众跪在神像前,,口中许愿,双手握竹筒摇动,直到摇出一根签,再将其交给解签人(一般为庙祝);解签人根据灵签上的编号,根据签书中对应的签诗来判断吉凶祸福。与前文提及的“卜杯”仪式一样,“摇签”首先也是一种人神之间交流的工具,“摇签”仪式通过信众与神明之间的“有效对话,使”神明的“真正意志”得以呈现,从而建立人和神之间的合作关系,强化人们对时空秩序、道德秩序和生命秩序的认可或信守。②更进一步来说,通过对这些秩序的象征性确认,人和人之间(既包括今人与今人之间,也包括今人和古人)也分享了感知和经验,成为一个共同体。如陈进国所说,“摇签”仪式象征性地提供了维持民间社会生活的文化稳定力量。①
凯瑞曾非常睿智地指出,“真实”(real)不断地调适和重建,以适应人类的目标,包括人类本身的改造。而科学并不是一套被赋予特权和基础的再现,科学只不过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交流。②陈进国也提出:“现代人实在没有理由和资格,带着独断论的思维和‘上帝’的眼光,持续地对中国的古人和民众体察世界的智慧、情趣表现出细想的乃至批评的无端的骄傲,尽管民众的诗性智慧也充满着诧异和算计。”③在现代社会中,“掷筶”“摇签”等祭祀仪式不被科学所认可,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荒谬、没有意义的。相反,这些祭祀仪式作为象征符号互动,确实曾经有效地促进族群内部的认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且,它在今后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仍将发挥重要的正面作用。
我们通过田野观察发现,无论是迄今已经中断70余年的天后祖祠巡游仪式,还是现在仍如火如荼、热闹举办的社庙迎神巡境仪式、“妈祖元宵”参神仪式、“妈祖同娘家”仪式、“海祭妈祖”仪式,都说明妈祖信俗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占据了非常普遍而重要的地位。每逢初一、十五日或神、社节日,善男信女们披红戴绿,身背香袋,上各处神庙上香磕头、烧银纸、放鞭炮,全村香烟缭绕,神韵非常。每逢大节日(如神庙主祀神的生忌日),更是热闹非凡。有供奉礼品,大鼓大吹的,有演莆戏的,有朝拜神明的,有办酒筵请客的。男女老少忙得不亦乐乎,可称一大奇观。④
在近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回娘家”仪式与九月初九日“海祭妈祖”仪式中,都增加了“头炷香”的项目。祖祠董事在仪式前会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华人华侨、本地民营企业家或村民的捐款或知悉其捐款意向,遂于仪式中安排认捐人或其代表在董事长带领下在祭台上祭拜妈祖,而其他信众则只能在祭台下祭拜。尽管仪式中不会当众公布捐款数额,但据我们的调查,能够在这两大仪式中向妈祖敬献“头炷香”者的捐款数额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而且,有的还连续数次敬献“头炷香”。
在这样一个仪式中,如若我们视敬献“头炷香”者的捐款为一种祭祀品的话,那么,其象征意义就在于,敬献“头炷香”者在祈求神明认可其财产具有神圣的起源,人与神之间的从属关系是这一合法性的根本所在。“头炷香”的敬献者们正是通过这一仪式来表示对该从属关系的服膺,从而获取当世财产的合法性以及来世财产的可能性。①
(三)仪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民间信仰仪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考察一个社区、一个族群内部认同感的重要侧面。在港里村,妈祖祖祠更因其所具备的林氏祖祠功能而更加凸显其由人神关系所延伸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林姓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是商代王朝子姓后裔,殷少师比干之子受姓为林。据《敕封天后志·天后本支世系考》,妈祖是唐邵州刺使林蕴的七世孙女。蕴公生一子愿。愿生邕、同、圉、赋。圉迁居忠门[懿宗咸通十年(869年)追谥蕴公“忠烈”诏赐毳服,旌表其闾,故其子孙所居地名忠门]。旋又迁更南沿海的新安里黄螺,港,以蕴公曾应贤良科,故易名贤良港。圉公官唐威武军节度武勇将军,生保吉、保安。保吉仕后周,授统军兵马使,年老辞官归隐贤良港,葬风林山。配闻氏生一子名孚。孚公袭世勋,官福建总管。生一子惟悫。惟悫公官闽都巡检,配王氏,生一子六女。子名洪毅,其第六女名默娘,即林祖姑妈祖。洪毅卒于宋开宝八年海难,遗一子。后裔分衍上林、下林、上厝、后厝、港尾、地鼎六房,因清代截界政策而迁居外地甚多,分派惠安外厝、岭头等地。
因而,今居港里的两千多林氏后裔族人都会在祭拜妈祖时,到祠内祀妈祖父母和林蕴以下列祖的后殿,后殿的照壁上刻有明代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林俊撰写的《族范》,从《族范》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林姓子孙洁身自好、保持“忠孝”家风的决心和传承妈祖仁慈博爱的胸襟。《族范》照录如下:
族范
凡林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尊幼有序,礼义廉耻,兼修四维。士农工商,各守一业。
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动必端,言必谨。事君必忠敬,居官必廉慎,乡里必和平。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毋富而骄,毋贫而滥,毋信妇言伤骨肉,毋言人过长薄风;毋忌嫉贤能,伤人害物;毋出入公府,营私召怨。毋奸盗谲诈,饮博斗讼;毋满盈不戒,妙微不谨;毋坏名丧节,灾己辱先。善者嘉之,贫难、死丧、疾病周恤之,不善者劝悔之,不改、与众弃之。不许入祠,以共绵诗礼仁厚之泽。敬之,戒之,毋忽!
邵州蕴公廿二世孙明太子少保、刑部尚书谥贞肃讳俊公撰
《族范》为邵州蕴公廿二世孙(材行房)明太子少保、刑部尚书谥贞肃讳俊公撰,为开先祠祭祀时对族众宣读的,故邵州派下各房祭祠例须宣读《族范》。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少保公之子林达篆书石刻尚存(真迹存放于莆田市博物馆)。
这种当众宣读“族范”的仪式的象征意义在于向所有在场的村民表明:我们都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神明、祖先的崇拜,遵从同样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敬老、孝道),因此我们认同彼此,“都是港里人”“都是同一个祖先”。此即莫斯(Mauss)所言,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被推广到了人与人的关系。
不仅仅如此,还有一份《林氏家训》更使我们对于这个家族的发展史有了更加探入的了解,作为一个家族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是弥足珍贵的。
林氏家范①
(一)国法当守
法乃治国之本,纪为立身准则。吾林氏族人,当守纪法。守法剐身行自由,违法当守处罚。凡一切规矩,都从国法中来。合法则据理力争,不法须自行认错。不可逾之、违之、犯之。
(二)家规当尊
家有法度,代有设施。为吾子孙,奉亲孝,事长悌,和妯娌,爱子孙。叙天伦之理。尽尊卑之分,上行下效,理势必然。更戒嗜酒、戒浮赌、戒争讼、戒窃盗。不以恶凌善,不以强恃弱。勿以大压小,勿以富欺贫。莫以权夺理,莫无理取闹。为正人君子,家规当遵。
(三)师尊当敬
人非生而能慧,学则可以医愚。学能明理,明理以致用。非学无以广才,非思无以研精。学必尊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为吾子孙,虚怀若谷,尊师重道,学必有成。
(四)交友当正
人生皆有急难之时,友朋之间相互周济,诚为乐事,此交友广则成事易也。然处事贵在知人。知己朋友,则可借以辅吾仁,矫吾失,薰吾德,正吾行。如他山之石,互相切磋。励我以道义,博羲以学问。此所谓益友也。垢不择其人,则惟导恶习,趋下流。意气用事,骄奢相攀,足以危身破家,此所谓损友也。更有言貌称真心似蛇蝎者,不可不防。当慎之远之。此谓交友当正也。
(五)处世当明
人居社会,关系纷繁,待人接物,处世分叫。器量大,操守璃。见识远,谋虑长。是非辨,大小分。行事必审其当否。听人说是非。莫亲信,亦莫亲答。诺则必行。处乡邻以敦厚谦和为心,若有缓急,自当量力助之,不可存求报之心。此谓处世如胸中泾渭,自当分明。
(六)业当勤俭
士农工商,均为常业,不论何门,都应各安其分,惟勤是务,不起妄想。读勤者智足,艺勤者技良,耕勤者粮丰,商勤者财富。选行,必专一行,当守一行之道德。勤能创业,俭可守家。当量其所入度其所处,未可浪费。俭以养德。清心寡欲则无不足。为吾子孙,勤俭当勉。
(七)族宜当敦
吾族大而枝繁叶茂,不能无智愚、贤与不肖之辈,且念皆祖宗一脉所承,未教不可视为愚。不可弃之于不教。不可因争吵而失大义,因小事而闹成大事。若事虽大而情可谅,法可伸,理可容者,须宽宏以待而处之,所谓君子有容人之量,可令其改过自新,奋发自勉,曲成其美。凡有族人来往,不论远近,当一体相待,不可因亲疏而简慢之。须相敬相爱,急难相恤,斯无愧于敦本追源之念。
(八)教子有方
凡教子者,须择严师以训导之,寻良友以切磋之。束其心志,专心读书为上,勿放荡偷闲,莫巧言欺之,勿以善小而使其不为,恶小而使其为之。为父母者自甘模范,并勤于引导施教,善于启迪开智,听其善言,观其善行,使知其所信。
(九)祭祀当诚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无祖宗,身从何处?须常怀先祖稼穑之艰,创业之难。尊祖敬宗,人之常情。节时佳日,缅怀祭祀,其心当真。鸦尚反哺,羊能跪乳,况人之不如乎?为吾子孙,须常记之。
(十)宝藏谱牒
谱牒者,所记祖宗之功德也,传千万世源流。世人视金为宝,殊不知谱牒尤为至宝。国家以史重,缄之金匮,子孙以谱为贵,藏于家庙。为子孙者,应代续族谱,记当世族人之功德,以承接先祖真脉之传,启迪子孙后代,何其贵也。此谱牒所当宝藏也。
在港里村,每年正月十五当晚,还有一个“会神”“参神”仪式向我们展示神与神之间的关系。贤良港古寺、古祠、古庙多,全村大小寺、庙、祠、社、亭、府16个,其中有福慧寺、五帝庙、吴祖社、天后祖祠、新兴社、灵慈东宫、灵慈西宫、接水亭、鳌层宫、开元宫、小港开山宫、黄氏祠堂、钱楼社、姨妈府、泰山大哥府等。每年正月十五晚,各宫庙福首(亦称炉主)率合境人丁迎神出巡,途经各社庙参拜邻社之神,最后由吴祖社、灵慈西宫、新兴社等三个林姓族人宫庙汇聚于港里村天后祖祠后山之洞山坪会齐,摆上神案,由福首率吹鼓手到各社神前相互参拜。这种社庙间的“会神”“参神”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神的交往,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增进联谊,从而促进宗族间的和睦团结,这种以“参神”形式出现的“妈祖元宵”仪式活动也是贤良港传统文化中遗存下来的一种文化景观。①
以往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研究民间信仰问题时,经常会用到“祭祀圈”这个概念。“祭祀圈”由日本学者冈田谦于1938年提出,指的是“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②林美容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仰圈”的概念,将前者的“地域”特征推广为“组织”特征。①无论是“祭祀圈”还是“信仰圈”,都是在一个社区(或族群)的整体层面上,来讨论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
港里村的民间信仰活动中,形成了以妈祖崇拜为核心的祭祀圈,村民因参与仪式而产生“有份”感觉。我们认为,祭祀圈理论在讨论“有份”的群体归属感问题时,未能探究象征符号互动中人们因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不同,而对仪式有着不同的解读,产生不同程度的“有份”感。因此,本书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从更微观的“仪式—秩序”生产层面,研究个人在族群中扮演的角色、相互间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使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来表述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印证了族群中人和人之间存在地位差异的社会关系结构。至于这种“差序格局”在族群中的维系,就不得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概念。儒家思想认为,“礼达而分定”。《左传》亦提出,“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意思是说,“礼”是一种因社会成员身份地位不同而有差异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只要不同的人严格遵守不同的“礼”,就能各得其所,社会也因此安定繁荣。同时,“礼”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礼数”,指具体的礼节仪式。我们认为“礼数”是对社会等级制度和伦理秩序(即更大层面上的“礼”)的抽象化,或者是象征符号。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每一个人也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行使不同的礼数;而仪式中人的角色和关系,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符号,它隐喻、象征着个人在族群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人的社会关系。在民间信仰仪式中,最显著的是信众与神明之间施与报的从属关系,其象征意义我们在前文已有论及,此不赘述。此外,乡老也在民间信仰仪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通常负责领导、策划、组织,决定仪式的规模大小、交由什么人来承办、经费该如何处置等等。它象征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家长制度。与之相似的还有仪式中“老大”抑或“精英”们(村里有身份地位、经验丰富的年长男性),对应的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长老统治”。陈进国认为,寺庙解签人是扮演着“神媒”或“神的代理人”角色,既是神圣意志的转述者,也是地方知识的传播者。①与之相似还有僧侣、道士、神婆等等。它象征着社会中的知识阶层,他们负责沟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帮助人们解释现象、提供建议。在村落活动中,新婚男性在“添丁”(有了儿子)之后,会积极参加抬神像的仪式,在一种半狂欢的状态下,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向众人宣告自己的“成年”。它反映的是传统社会对于男性角色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样,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要求也在仪式中有所隐喻——女性一般不能参与仪式的组织、决策过程;有的地方以“不祥”“不洁”为由拒绝女性参与到仪式中来,甚至某些地方的风俗是不允许女性看到、触摸神像;甚至家中添了男丁,按照风俗要向村中各户分发“丁饼”,而生了女儿则无须这样的仪式。男女间的不平等,由此可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港里村,无论是祭拜祖先、祭拜妈祖还是其他神灵,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的信众,大多是女性。她们准备祭品、焚香跪拜、口念祝词,丝毫没有忌讳。尽管女性成为祭祀活动参与者的主体,但男性依然在祭祀的组织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扮演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在我们了解到的港里村各类仪式中,无一不是由男性主导。这一点,从董事会成员的性别构成即可得出基本判断(目前董事会的90名成员中,女性仅8位,而18名常务董事中更是仅有1位女性)。这种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却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出现的:港里村一直是一个传统渔村,土地面积本来就少,码头遭废弃后,除少数村民仍从事农业生产外,很多村民外出经商、打工,一旦在外立稳脚跟,就会将家人接去,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且小家庭得以团聚,但家中老人多以水土不服、眷恋故土而留守家园,留守女性也多为老人,且数量多于男性。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仪式中的权力博弈、知识占有、男女有别,都能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找到对应的“原型”。也就是说,民间信仰仪式中神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角色定位,都不过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角色定位的象征性重复,用格尔茨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扮演”。作为仪式的礼数是对作为社会约定俗成规则之“礼”的确认和练习;参与其中的人们,在象征符号互动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完成了对族群、对其他成员的认同。在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之下,人们安守本分,传统乡土社会得到了整合与延续。
三、结论与展望
民间信仰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的整合,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和团结。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口耳相传,构成了村民的共同历史记忆,产生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神”这些观念,从而强化了彼此的认同:神庙祠堂在空间上的散布,赋予了神明的地域性特征,强化了同一祭祀圈内村民之间的认同,形成各个层级的具有对内团结、对外竞争的社区团体:而仪式可以看作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象征符号互动,祭祀品、祭祀仪式、仪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同一时空下象征符号互动的载体,形成了所谓的“在场”“归属”之感,从而维持传统乡土社会秩序、促进村落内部凝聚力。
我们将民间信仰看作是一种传播现象,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它,正是因为它的传承、散播以及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互动,使得它具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将社区团结在一起,使村民产生一种归属感。而这种力量始于交流,不单是言语的交流,而是分享记忆、分享空间、分享同一时空下的参与感;这种力量的意义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动物,“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在做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我们先是用符号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居住在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中”。①
一、传播仪式观
台湾知名学者,与林美容教授并称“妈祖婆”的张珣教授在其《妈祖·信仰的追寻》一书中,就人类学对于宗教现象的研究特点提出了如下观点:被当做文化象征(宗教、节庆、伦理、价值)来处理;其组织视同社会组织之一,探究的是其间的分合纠结;分析仪式应该注意其传递文化理念与规范社会秩序的价值;重视集体的情感认同甚于个人的神秘经验之唤起。①
对于中国的社会实践而言,相比于官方色彩浓厚的儒、释、道三教,各种活跃在乡间田垄的地方性神明,更贴近百姓的生活,更受欢迎,妈祖信俗即其中较有特色和有影响力者之一。作为百姓日常生活基本层面的民间信仰,是我们考察和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图像”的重点与焦点所在。那么,民间信仰产生的机制、功能和影响如何?一些学者已经从自己的角度试着回答这些问题,认为民问信仰的寺庙或者宗祠,常常成为一个社区的“祭祀圈”或城镇的“信仰圈”的中心,有效地推动了城乡社区自我组织的形成和自我管理的完善。②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民间信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身份认同感的产生与发展。本节将从传播学角度出发,以港里村为例,来研究妈祖信俗。但是,由于田野调查的工作不足,相关资料的欠缺,本节所呈现的仅是一个初步的理解与思路的概述。
对于民间信仰仪式与族群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更倾向于将仪式看作是一个族群使用象征符号的一种习惯或集中使用象征符号的形式。为了进一步阐释象征符号是如何在信众中间产生互动,以及如何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文化的认同感,我们引入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凯瑞在其《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出,传播学研究视角可以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两大类。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具有深厚的宗教渊源: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它(传播的仪式观)“并不看重布道、说教和教海的作用,为的是强调祷告者、圣歌及典礼的重要性”因此,“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
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①以这样一种观念来理解传播问题,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作为一个非常庞杂、难以把握的概念,“民间信仰”显然是多面向的。出于选择切入点的考虑,我们特别关注妈祖信俗中重要的“仪式”环节,以妈祖信俗核心传播区之一港里村的妈祖信俗传播为研究对象,研究它是如何在文化认同乃至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上发挥作用的。涂尔干曾强调,信仰,特别是仪式,是一种加强传统上个人之间的社会纽带的方式;②格尔茨进一步说明,它涉及生活准则及世界观的融合,形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③杜威则相信传播扮演着重要的认识角色,不是把知识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简单角色,而是创造知识的丰富意义。这源于他对传播的独特理解:传播是人类生活唯一的手段和目的。作为手段,它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中解放出来,并能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作为目的,它使人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传播值得人们当作手段,因为它是使人类生活丰富多彩、意义广泛的唯一手段;它值得人们当作生活的目的,因为它能把人从孤独中解救
出来,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①
在这里,公众存在于“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中,它通过参与式传播融入共同体生活之中,这种以传播创造社会共同体的理念,为我们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信仰仪式开启了一个崭新视角。“在一个高度互动的传播系统中,已经不可能划分‘来源’和‘受众’,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变革了受众研究的思维空间,着眼于在人与人的互动与意义分享的层面探讨媒介效果,在主体间的整合意义上建构受众。”②作为一种可能的致思取向,它关涉主体间的传播关系,也关涉多级主体间的意义分享。本节拟由观察符号互动与族群秩序、祭祀仪式与文化认同而体察妈祖信俗传播与妈祖文化共同体建构之问的微妙关系,并且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种理想境界的妈祖文化共同体建构与村民日常生活中妈祖信俗仪式化之间存在的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背离的关系?
二、传播仪式观视域中的妈祖信俗传播与共同体建构
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族群是那些体质类型或因习俗的相似性,或因殖民或移民的记忆,而对共同的血统享有主观信仰的人群。而认同则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术语,指帮助个体在个体自身生活中产生秩序,并帮助个体置身于群体之中或卷入与集体的认同。③学界对于族群认同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族源认同、语言认同、宗教认同、生活习俗认同、性格特征认同。显然,本书着力探讨的是族群的文化认同,具体而言即研究妈祖信俗传播与仪式中的认同乃至妈祖文化共同体之关系。
首先是时间维度,研究妈祖信俗、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的历史传承。通过对神活传说之生产、加工、流传的解释,对族谱记载的故事、警语、祖训、族范的解读,对游神仪式、祭祀习俗演变的解析,试图说明民间信仰在时间上的延续、传播,形成了港里社区居民的共同历史记忆,产生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神”这些观念,从而强化了彼此的认同。
其次是空间维度,研究妈祖宫庙、祠堂,及其他庙宇在港里社区中的空间散布。通过实地考察,确认各庙宇、祠堂的地理位置,绘制地图,对照各村的行政划分,我们发现自然村的分界与民间信仰“祭祀圈”的分界基本吻合,并且有着鲜明的层次感。天后祖祠、福慧寺、五帝庙、吴祖社、新兴社、灵慈东宫、灵慈西宫、接水亭、鳌层宫、开元宫、小港开山宫、黄氏祠堂、钱楼社、姨妈府、泰山大哥府等各宫庙与自然村之间均有其相对应的关系。族群边界与民间信仰边界的基本重合,初步印证了本研究的基本假设。
最后一个维度,则是研究在共时空下举行的各种民间信仰仪式与族群认同有着怎样的联系。仪式,向来是人类学家考察一个社区内人们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截面,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仪式是宗教活动最主要的层面,华莱士则把仪式看作是宗教的主要现象,即行动中的宗教。①中国学者在研究民间信仰问题时,也十分看重仪式在维持传统乡土社会秩序、促进村落内部凝聚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刘晓春在对客家村落的研究中提到,以家族为单位所举行的仪式表演既提高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也促进了家族成员基于共同的家族利益对外协作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助。显然,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如何运用传播的仪式观来看待妈祖信俗中的仪式,则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
褚建芳在《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一书中认为,民间信仰仪式“最明显、最集中地反映和表达了当地人们对人与世界的理解、解释与看法,并揭示了他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以及整体运作规范、逻辑与秩序”,而人类学对于民间信仰仪式的研究,大体上有三种取向,一是把仪式看作情感表达的场合,二是将其看作戏剧表演或游戏,三是把仪式看成是人与神圣力量的交流过程。②我们视民间信仰仪式为一种交流的方式,但认为它未必仅限于人与神之间的交流,某种程度上,参与仪式的人们之间也存在交流的过程(未必只是语言交流);究其根本,人神交流、人人交流,都可以归结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象征符号互动——当然,本书的最终目的不仅局限于研究民间信仰中交流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仪式的“符号秩序”的生产、互动,进而研究人与人之间、人与传统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他们可以建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一种独立存在的自我认同”“这种意义系统渗透在家庭和地区的日常生活当中”日常,①,家庭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被这种意义的范式所渗透和支撑,老辈人通过这种意义范式讨论他们所分享的情境体验。在社会化进程中,尤其在家庭与社区的范围之内,这种意义系统在年青一代的成长过程中被再生产,并构成想象的基本框架,透过这一框架,他们接近其社会经验。就其要者,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民间信仰仪式中的祭祀品、祭祀仪式以及仪式进程中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探讨港里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象征符号互动问题。
仪式,向来是人类学家考察一个社区内人们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截面,既然选择仪式,尤其是仪式中的象征符号互动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那么就港里村的民间仪式本身而言,它的哪些方面体现了我们所关注的“交流”的问题呢?
在港里村,除“妈祖回娘家”“海祭妈祖”习俗外,尚有“妈祖元宵”、港里“大月半”、福慧寺“廿二拖”、五月初五烧瘟船等习俗,以及港里遗存的结婚闹洞房“做经文”和“寿旦喜庆”等古已有之的民俗。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梳理,以及对自身田野生活体验的总结,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民间信仰仪式中的祭品、祭祀仪式,以及仪式进程中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象征符号互动问题。
(一)祭品
研究祭祀品,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研究人与神之间的交流。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人与神之间的交流是不平等地位者之间的信息交流,需要通过一个中介物来实现,而这个中介物就是人们在仪式中向神进献的祭祀品”。②
有学者认为,所谓祭品,如贡品、鞭炮、香烛等,实际上是人们向神明献上的贿赂,企图以较小的代价换得较大的利益,如平安、得子、高升等。祭祀品不单纯是利益的交易,也体现了人对于神明的虔诚之心和敬畏之感,“如果不为仪式花足够的钱就等于是对命运、祖先和神的不尊,这反过来就等于是对自己幸福的潜在威胁”。①
我们在港里村发现,这种“贿赂”神的现象十分普遍。无论祭祖还是拜神,村民一般会选择在初一、十五或者神、社节日,尤其是年初正月期间,为神明备上果、糖等祭品,焚香许愿,承诺如果愿望得到实现,就会以更丰富的祭品来还愿,否则会引来其他村民的非议,因为他们认为不“还神”会惹神明生气,降祸到村里,殃及池鱼。祭品都要遵循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品类、数量都有讲究。如胡乱向神献祭品,会被人耻笑,也可能会得罪村里在这方面的权威长者。因此,各家准备祭品的人选,一般是年纪较大的妇女,她们在祭祀这一方面往往博学而稳重。
而褚建芳在其著作中则从财产合法性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云南傣族村落佛教信仰中“献卤”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意涵。他反复提及“卤”和“阿祚”两个概念(均为傣语),认为人和神之间存在一种“道义互惠”关系,表现为三个层次的“施”与“报”。表面上看,“卤”可以认为是信众向佛进献的斋饭、鲜花、香烛等物品,以求得佛给予信众的“阿祚”(翻译成汉语就是“福分”)。这是第一层面的施与报的关系。然而,在献卤的仪式过程中,祭祀品的所有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转移,它仍然是属于献卤的人——拿回去吃掉或者扔掉。既然认为祭祀品的所有权在人神交流的过程中没有被让渡,那么信众向佛送出了什么?而佛又向信众回报了什么?实际上,信众是通过祭祀品这个中介物表达自己对佛的尊敬和服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诚心”;反过来,佛则报以“阿祚”,表示认可。用作者的话来说,“在献祭仪式中,作为供品的物质实体本身并不重要,它们只是把献祭的人和所祭拜的神祇联系起来的中介物,起到了表达或者传递信息的作用”。②这是第二个层面上的施与报的关系。当然,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出发,将祭祀品视作传递人神之间亲善友好信息的中介,显然是不够深刻的。那么,祭祀品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究竟在人神交流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涂尔干看来,人类的财产权仅仅是神的财产权的替代物。人们需要通过定期举行仪式,取得神对其财产使用权的认可,从而维持和确认其合法性。祭祀品的象征意义在于,财产的合法性有着神圣的起源,人与神之间的从属关系是这一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人们通过定期向神奉献祭祀品表示对该从属关系的服膺,从而获取当世财产的合法性,以及来世财产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三个层面上施与报的关系。这里的“神”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是世俗人间道德与力量完美结合的理想人物,是地方社会规范的抽象化的道德模范”。①也就是说,人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集体或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通过象征符号互动确立起来的人神之间的神圣契约与神圣秩序,一旦流传开来,成为族群中大多数人所遵从的原则,显然有利于一个族群内部的和谐稳定和统一。
具体到妈祖信俗的祭祀仪式中,“妈祖回娘家”和“海祭妈祖”祭祀习俗并列为天后祖祠的“春秋两祭”,是港里村所有祭祀活动中最盛者,活动中所使用的祭品之多、材质之好、造型之精美更是无以复加。而最能体现当地人继承中原汉族遗风的祭品,当属“少牢”。所谓少牢,指的是“古代祭祀燕烹用羊、豕各一者”。根据《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自宋以降,各朝谕祭妈祖的仪式均非常隆重。《明史·礼志》记:“降香遣官仪:祀前一日清晨,皇帝披弁服,升奉天殿,捧香者以香授献官(奉旨主祭者),献官捧由中陛降中道,出至午门外,置(香)龙亭内,仪仗鼓吹导引至祭所,后定:祭之日降香,如常仪。中严(祭庙森严)以待献官,祭毕,复命,解严还宫。”又记:永乐七年(1409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诸庙皆少牢(羊一、猪一)。”《清史稿·礼志》记:“凡列祀典者,有司(地方官)随时致严(虔)。用羊一、猪一、果五盘、帛一、樽一、爵三,读祝叩拜如故事。”
港里村民一直恪守这一礼制,称之为“猪羊祭”,祭祀用的猪和羊各一只②。而准备祭品的花费,则是由林氏后裔捐款,交董事会统一管理。祭祀完毕,董事会义工将祭品分发至各户人家,共同享用。这样的做法代代传承,成为族群中所有人遵从的原则,在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的同时又规范着族群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有利于族群内部的和谐稳定和统一。
(二)祭祀仪式
在论及港里村的祖先崇拜、妈祖信俗的祭祀仪式之前,我们必须先对“祭祀仪式”这一个概念进行界定。所谓“祭祀仪式”指的是民间信仰仪式的各种程序,包括跪拜、进香、摇签、卜杯、敬酒等等。社,会人类学家特纳(VictorTunner)认为,这些祭祀仪式会带来个人的超脱感、安慰、安全甚至狂喜,或对一起参加仪式的人的亲切感;法国早期人类学家范瑾尼(A.VanGennep)则
提出,祭祀仪式的目的是帮助人在一生中比较容易地通过一些关口,如生、老、病、死这些过程。①
本书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出发,虽然也赞同祭祀仪式具有上述功能,但我们更关注作为象征符号,它们是如何促进人与社会(社区)之间的互动,进而产生文化上的认同。
前面提到的祭祀品主要反映的是人神之间的交流,而祭祀仪式则是在人神交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多人与人之间交流层面。下面则以最为常见的“卜杯”和“摇签”这两种仪式以及新近增加的“头炷香”仪式来说明。
莆田妈祖宫庙中,常用一对木制或竹制的半月形,一面平坦、一面隆起的法器,向妈祖问卜。每片“筶”有两面,光滑平整的一面为阳,呈半圆柱体弧形的一面为阴。而两片“筶”搭配组合,就会出现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阴一阳,称为“圣筶”,好兆头;两片都是阳面,为“阳筶”,运气不好不坏;两片都是阴面,则为“阴筶”,很不吉祥。
在莆田当地广为流传的是这样一则与少年妈祖林默有关的故事。在贤良港妈祖祖祠不远处,有一地名地鼎,是古时铸鼎(莆田人称铁锅为鼎)之地,该地铸的鼎质量非常好,故而有名。相传,有一天,少女林默去看铸鼎,不料师傅却连续三次铸不成,发现有个女孩子在旁边观看之后,要赶她走,小林默说:“走可以,但我要一点烧红的铁砂。”师傅当即满足她的要求,她遂用双手捧起烧红的铁砂回家,双手安然无恙,而手中的铁砂则冷却成了一对筶杯。
笔者曾多次看到满脸虔诚的人们(以妇女居多)在妈祖像前进香、跪拜,通过“掷筶”和“摇签”向妈祖询问某事是否可行。卜得圣杯,则欢天喜地,允诺事成之后必来筶谢;否则,也会向妈祖谢恩,感谢她的庇佑。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到的象征符号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下人们的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表征。正如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所说,文化就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他同时指出,文化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①因此,我们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来看“掷筶”这种文化现象时,应当“毫无负担”地将其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来考察仪式中的交流问题。“掷筶”表面上是人神之间交流的信息传递工具,但就更深层的意义而言,它象征了人类对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朴素认识和敬畏。它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对于自身以及这个世界的觉悟,并且对此深信不疑。在同一时空中,参与祭祀仪式的人们对于自身和世界具有近似或共通的感知,因而彼此之间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又由于仪式具有“表演性”和“重复性”,既使得仪式本身得到超越时空的传承,也让其象征的世界观得以“集体记忆”的形式流传后世。因此,人与人之间借助祭祀仪式这种象征符号实现了交流和文化传承。在这样一个创造、分享、修正和保存现实的过程中,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认同也就得到了强化,并为重塑族群的共同文化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摇签”仪式也可以看作是促进族群认同的象征符号互动。陈进国指出,抽签(即“摇签”)是中国民间社会流行的一种签卜术。我们所了解的港里社区的祭祀仪式中的“摇签”用的是竹制灵签,在27根竹签上分别写上编号,放入一个竹筒;信众跪在神像前,,口中许愿,双手握竹筒摇动,直到摇出一根签,再将其交给解签人(一般为庙祝);解签人根据灵签上的编号,根据签书中对应的签诗来判断吉凶祸福。与前文提及的“卜杯”仪式一样,“摇签”首先也是一种人神之间交流的工具,“摇签”仪式通过信众与神明之间的“有效对话,使”神明的“真正意志”得以呈现,从而建立人和神之间的合作关系,强化人们对时空秩序、道德秩序和生命秩序的认可或信守。②更进一步来说,通过对这些秩序的象征性确认,人和人之间(既包括今人与今人之间,也包括今人和古人)也分享了感知和经验,成为一个共同体。如陈进国所说,“摇签”仪式象征性地提供了维持民间社会生活的文化稳定力量。①
凯瑞曾非常睿智地指出,“真实”(real)不断地调适和重建,以适应人类的目标,包括人类本身的改造。而科学并不是一套被赋予特权和基础的再现,科学只不过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交流。②陈进国也提出:“现代人实在没有理由和资格,带着独断论的思维和‘上帝’的眼光,持续地对中国的古人和民众体察世界的智慧、情趣表现出细想的乃至批评的无端的骄傲,尽管民众的诗性智慧也充满着诧异和算计。”③在现代社会中,“掷筶”“摇签”等祭祀仪式不被科学所认可,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荒谬、没有意义的。相反,这些祭祀仪式作为象征符号互动,确实曾经有效地促进族群内部的认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且,它在今后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仍将发挥重要的正面作用。
我们通过田野观察发现,无论是迄今已经中断70余年的天后祖祠巡游仪式,还是现在仍如火如荼、热闹举办的社庙迎神巡境仪式、“妈祖元宵”参神仪式、“妈祖同娘家”仪式、“海祭妈祖”仪式,都说明妈祖信俗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占据了非常普遍而重要的地位。每逢初一、十五日或神、社节日,善男信女们披红戴绿,身背香袋,上各处神庙上香磕头、烧银纸、放鞭炮,全村香烟缭绕,神韵非常。每逢大节日(如神庙主祀神的生忌日),更是热闹非凡。有供奉礼品,大鼓大吹的,有演莆戏的,有朝拜神明的,有办酒筵请客的。男女老少忙得不亦乐乎,可称一大奇观。④
在近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回娘家”仪式与九月初九日“海祭妈祖”仪式中,都增加了“头炷香”的项目。祖祠董事在仪式前会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华人华侨、本地民营企业家或村民的捐款或知悉其捐款意向,遂于仪式中安排认捐人或其代表在董事长带领下在祭台上祭拜妈祖,而其他信众则只能在祭台下祭拜。尽管仪式中不会当众公布捐款数额,但据我们的调查,能够在这两大仪式中向妈祖敬献“头炷香”者的捐款数额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而且,有的还连续数次敬献“头炷香”。
在这样一个仪式中,如若我们视敬献“头炷香”者的捐款为一种祭祀品的话,那么,其象征意义就在于,敬献“头炷香”者在祈求神明认可其财产具有神圣的起源,人与神之间的从属关系是这一合法性的根本所在。“头炷香”的敬献者们正是通过这一仪式来表示对该从属关系的服膺,从而获取当世财产的合法性以及来世财产的可能性。①
(三)仪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民间信仰仪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考察一个社区、一个族群内部认同感的重要侧面。在港里村,妈祖祖祠更因其所具备的林氏祖祠功能而更加凸显其由人神关系所延伸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林姓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是商代王朝子姓后裔,殷少师比干之子受姓为林。据《敕封天后志·天后本支世系考》,妈祖是唐邵州刺使林蕴的七世孙女。蕴公生一子愿。愿生邕、同、圉、赋。圉迁居忠门[懿宗咸通十年(869年)追谥蕴公“忠烈”诏赐毳服,旌表其闾,故其子孙所居地名忠门]。旋又迁更南沿海的新安里黄螺,港,以蕴公曾应贤良科,故易名贤良港。圉公官唐威武军节度武勇将军,生保吉、保安。保吉仕后周,授统军兵马使,年老辞官归隐贤良港,葬风林山。配闻氏生一子名孚。孚公袭世勋,官福建总管。生一子惟悫。惟悫公官闽都巡检,配王氏,生一子六女。子名洪毅,其第六女名默娘,即林祖姑妈祖。洪毅卒于宋开宝八年海难,遗一子。后裔分衍上林、下林、上厝、后厝、港尾、地鼎六房,因清代截界政策而迁居外地甚多,分派惠安外厝、岭头等地。
因而,今居港里的两千多林氏后裔族人都会在祭拜妈祖时,到祠内祀妈祖父母和林蕴以下列祖的后殿,后殿的照壁上刻有明代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林俊撰写的《族范》,从《族范》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林姓子孙洁身自好、保持“忠孝”家风的决心和传承妈祖仁慈博爱的胸襟。《族范》照录如下:
族范
凡林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尊幼有序,礼义廉耻,兼修四维。士农工商,各守一业。
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动必端,言必谨。事君必忠敬,居官必廉慎,乡里必和平。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毋富而骄,毋贫而滥,毋信妇言伤骨肉,毋言人过长薄风;毋忌嫉贤能,伤人害物;毋出入公府,营私召怨。毋奸盗谲诈,饮博斗讼;毋满盈不戒,妙微不谨;毋坏名丧节,灾己辱先。善者嘉之,贫难、死丧、疾病周恤之,不善者劝悔之,不改、与众弃之。不许入祠,以共绵诗礼仁厚之泽。敬之,戒之,毋忽!
邵州蕴公廿二世孙明太子少保、刑部尚书谥贞肃讳俊公撰
《族范》为邵州蕴公廿二世孙(材行房)明太子少保、刑部尚书谥贞肃讳俊公撰,为开先祠祭祀时对族众宣读的,故邵州派下各房祭祠例须宣读《族范》。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少保公之子林达篆书石刻尚存(真迹存放于莆田市博物馆)。
这种当众宣读“族范”的仪式的象征意义在于向所有在场的村民表明:我们都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神明、祖先的崇拜,遵从同样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敬老、孝道),因此我们认同彼此,“都是港里人”“都是同一个祖先”。此即莫斯(Mauss)所言,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被推广到了人与人的关系。
不仅仅如此,还有一份《林氏家训》更使我们对于这个家族的发展史有了更加探入的了解,作为一个家族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是弥足珍贵的。
林氏家范①
(一)国法当守
法乃治国之本,纪为立身准则。吾林氏族人,当守纪法。守法剐身行自由,违法当守处罚。凡一切规矩,都从国法中来。合法则据理力争,不法须自行认错。不可逾之、违之、犯之。
(二)家规当尊
家有法度,代有设施。为吾子孙,奉亲孝,事长悌,和妯娌,爱子孙。叙天伦之理。尽尊卑之分,上行下效,理势必然。更戒嗜酒、戒浮赌、戒争讼、戒窃盗。不以恶凌善,不以强恃弱。勿以大压小,勿以富欺贫。莫以权夺理,莫无理取闹。为正人君子,家规当遵。
(三)师尊当敬
人非生而能慧,学则可以医愚。学能明理,明理以致用。非学无以广才,非思无以研精。学必尊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为吾子孙,虚怀若谷,尊师重道,学必有成。
(四)交友当正
人生皆有急难之时,友朋之间相互周济,诚为乐事,此交友广则成事易也。然处事贵在知人。知己朋友,则可借以辅吾仁,矫吾失,薰吾德,正吾行。如他山之石,互相切磋。励我以道义,博羲以学问。此所谓益友也。垢不择其人,则惟导恶习,趋下流。意气用事,骄奢相攀,足以危身破家,此所谓损友也。更有言貌称真心似蛇蝎者,不可不防。当慎之远之。此谓交友当正也。
(五)处世当明
人居社会,关系纷繁,待人接物,处世分叫。器量大,操守璃。见识远,谋虑长。是非辨,大小分。行事必审其当否。听人说是非。莫亲信,亦莫亲答。诺则必行。处乡邻以敦厚谦和为心,若有缓急,自当量力助之,不可存求报之心。此谓处世如胸中泾渭,自当分明。
(六)业当勤俭
士农工商,均为常业,不论何门,都应各安其分,惟勤是务,不起妄想。读勤者智足,艺勤者技良,耕勤者粮丰,商勤者财富。选行,必专一行,当守一行之道德。勤能创业,俭可守家。当量其所入度其所处,未可浪费。俭以养德。清心寡欲则无不足。为吾子孙,勤俭当勉。
(七)族宜当敦
吾族大而枝繁叶茂,不能无智愚、贤与不肖之辈,且念皆祖宗一脉所承,未教不可视为愚。不可弃之于不教。不可因争吵而失大义,因小事而闹成大事。若事虽大而情可谅,法可伸,理可容者,须宽宏以待而处之,所谓君子有容人之量,可令其改过自新,奋发自勉,曲成其美。凡有族人来往,不论远近,当一体相待,不可因亲疏而简慢之。须相敬相爱,急难相恤,斯无愧于敦本追源之念。
(八)教子有方
凡教子者,须择严师以训导之,寻良友以切磋之。束其心志,专心读书为上,勿放荡偷闲,莫巧言欺之,勿以善小而使其不为,恶小而使其为之。为父母者自甘模范,并勤于引导施教,善于启迪开智,听其善言,观其善行,使知其所信。
(九)祭祀当诚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无祖宗,身从何处?须常怀先祖稼穑之艰,创业之难。尊祖敬宗,人之常情。节时佳日,缅怀祭祀,其心当真。鸦尚反哺,羊能跪乳,况人之不如乎?为吾子孙,须常记之。
(十)宝藏谱牒
谱牒者,所记祖宗之功德也,传千万世源流。世人视金为宝,殊不知谱牒尤为至宝。国家以史重,缄之金匮,子孙以谱为贵,藏于家庙。为子孙者,应代续族谱,记当世族人之功德,以承接先祖真脉之传,启迪子孙后代,何其贵也。此谱牒所当宝藏也。
在港里村,每年正月十五当晚,还有一个“会神”“参神”仪式向我们展示神与神之间的关系。贤良港古寺、古祠、古庙多,全村大小寺、庙、祠、社、亭、府16个,其中有福慧寺、五帝庙、吴祖社、天后祖祠、新兴社、灵慈东宫、灵慈西宫、接水亭、鳌层宫、开元宫、小港开山宫、黄氏祠堂、钱楼社、姨妈府、泰山大哥府等。每年正月十五晚,各宫庙福首(亦称炉主)率合境人丁迎神出巡,途经各社庙参拜邻社之神,最后由吴祖社、灵慈西宫、新兴社等三个林姓族人宫庙汇聚于港里村天后祖祠后山之洞山坪会齐,摆上神案,由福首率吹鼓手到各社神前相互参拜。这种社庙间的“会神”“参神”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神的交往,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增进联谊,从而促进宗族间的和睦团结,这种以“参神”形式出现的“妈祖元宵”仪式活动也是贤良港传统文化中遗存下来的一种文化景观。①
以往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研究民间信仰问题时,经常会用到“祭祀圈”这个概念。“祭祀圈”由日本学者冈田谦于1938年提出,指的是“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②林美容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仰圈”的概念,将前者的“地域”特征推广为“组织”特征。①无论是“祭祀圈”还是“信仰圈”,都是在一个社区(或族群)的整体层面上,来讨论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
港里村的民间信仰活动中,形成了以妈祖崇拜为核心的祭祀圈,村民因参与仪式而产生“有份”感觉。我们认为,祭祀圈理论在讨论“有份”的群体归属感问题时,未能探究象征符号互动中人们因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不同,而对仪式有着不同的解读,产生不同程度的“有份”感。因此,本书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从更微观的“仪式—秩序”生产层面,研究个人在族群中扮演的角色、相互间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使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来表述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印证了族群中人和人之间存在地位差异的社会关系结构。至于这种“差序格局”在族群中的维系,就不得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概念。儒家思想认为,“礼达而分定”。《左传》亦提出,“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意思是说,“礼”是一种因社会成员身份地位不同而有差异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只要不同的人严格遵守不同的“礼”,就能各得其所,社会也因此安定繁荣。同时,“礼”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礼数”,指具体的礼节仪式。我们认为“礼数”是对社会等级制度和伦理秩序(即更大层面上的“礼”)的抽象化,或者是象征符号。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每一个人也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行使不同的礼数;而仪式中人的角色和关系,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符号,它隐喻、象征着个人在族群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人的社会关系。在民间信仰仪式中,最显著的是信众与神明之间施与报的从属关系,其象征意义我们在前文已有论及,此不赘述。此外,乡老也在民间信仰仪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通常负责领导、策划、组织,决定仪式的规模大小、交由什么人来承办、经费该如何处置等等。它象征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家长制度。与之相似的还有仪式中“老大”抑或“精英”们(村里有身份地位、经验丰富的年长男性),对应的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长老统治”。陈进国认为,寺庙解签人是扮演着“神媒”或“神的代理人”角色,既是神圣意志的转述者,也是地方知识的传播者。①与之相似还有僧侣、道士、神婆等等。它象征着社会中的知识阶层,他们负责沟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帮助人们解释现象、提供建议。在村落活动中,新婚男性在“添丁”(有了儿子)之后,会积极参加抬神像的仪式,在一种半狂欢的状态下,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向众人宣告自己的“成年”。它反映的是传统社会对于男性角色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样,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要求也在仪式中有所隐喻——女性一般不能参与仪式的组织、决策过程;有的地方以“不祥”“不洁”为由拒绝女性参与到仪式中来,甚至某些地方的风俗是不允许女性看到、触摸神像;甚至家中添了男丁,按照风俗要向村中各户分发“丁饼”,而生了女儿则无须这样的仪式。男女间的不平等,由此可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港里村,无论是祭拜祖先、祭拜妈祖还是其他神灵,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的信众,大多是女性。她们准备祭品、焚香跪拜、口念祝词,丝毫没有忌讳。尽管女性成为祭祀活动参与者的主体,但男性依然在祭祀的组织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扮演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在我们了解到的港里村各类仪式中,无一不是由男性主导。这一点,从董事会成员的性别构成即可得出基本判断(目前董事会的90名成员中,女性仅8位,而18名常务董事中更是仅有1位女性)。这种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却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出现的:港里村一直是一个传统渔村,土地面积本来就少,码头遭废弃后,除少数村民仍从事农业生产外,很多村民外出经商、打工,一旦在外立稳脚跟,就会将家人接去,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且小家庭得以团聚,但家中老人多以水土不服、眷恋故土而留守家园,留守女性也多为老人,且数量多于男性。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仪式中的权力博弈、知识占有、男女有别,都能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找到对应的“原型”。也就是说,民间信仰仪式中神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角色定位,都不过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角色定位的象征性重复,用格尔茨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扮演”。作为仪式的礼数是对作为社会约定俗成规则之“礼”的确认和练习;参与其中的人们,在象征符号互动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完成了对族群、对其他成员的认同。在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之下,人们安守本分,传统乡土社会得到了整合与延续。
三、结论与展望
民间信仰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的整合,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和团结。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口耳相传,构成了村民的共同历史记忆,产生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神”这些观念,从而强化了彼此的认同:神庙祠堂在空间上的散布,赋予了神明的地域性特征,强化了同一祭祀圈内村民之间的认同,形成各个层级的具有对内团结、对外竞争的社区团体:而仪式可以看作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象征符号互动,祭祀品、祭祀仪式、仪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同一时空下象征符号互动的载体,形成了所谓的“在场”“归属”之感,从而维持传统乡土社会秩序、促进村落内部凝聚力。
我们将民间信仰看作是一种传播现象,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它,正是因为它的传承、散播以及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互动,使得它具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将社区团结在一起,使村民产生一种归属感。而这种力量始于交流,不单是言语的交流,而是分享记忆、分享空间、分享同一时空下的参与感;这种力量的意义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动物,“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在做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我们先是用符号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居住在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中”。①
附注
①张珣:《妈祖·信仰的追寻》,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14页。
②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①[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③[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
①单波:《译者序》,迪金森等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②单波:《译者序》,迪金森等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③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①周云水:《一个客家村落的民间信仰和文化认同——赣南背部石城客家宗教仪式的人类学探讨》,《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
②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3页。
①[英]迪金森等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②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①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书店年1997年版,第248页。
②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①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
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
②在莆田许多地方,由于许多信众希冀和期许妈祖的庇佑,祭祀用的猪和羊数量并无限制,多则各十数只,祭拜妈祖之情切,着实令人惊叹。
①周云水:《一个客家村落的民间信仰和文化认同——赣南背部石城客家宗教仪式的人类学探讨》,《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
①[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②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①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②[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③陈进国:《信仰、仪式与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④叶明生:《莆田贤良港妈祖信仰、祭祀仪式与音乐研究》,《海峡两岸·传统视野下的妈祖信仰文化考察活动资料汇编》,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2012年,第59页。
①根据叶明生先生的分析,头炷香的产生缘由不外四点:(1)对神表示最大的虔诚;(2)显示投注者的社区地位;(3)祈神给予更大的保护或庇佑;(4)内心忏悔及祈神禳除灾殃之举。
①傅世强:《我为林家拍族谱》,嘉木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0页。
①叶明生:《莆田贤良港妈祖信仰、祭祀仪式与音乐研究》,《海峡两岸·传统视野下的妈祖信仰文化考察活动资料汇编》,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2012年,第23页。
②张宏明:《民间宗教祭祀中的义务性和自愿性——祭祀圈和信仰圈辨析》,《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
①鄂崇荣:《土族民间祭祀圈与信仰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
①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①[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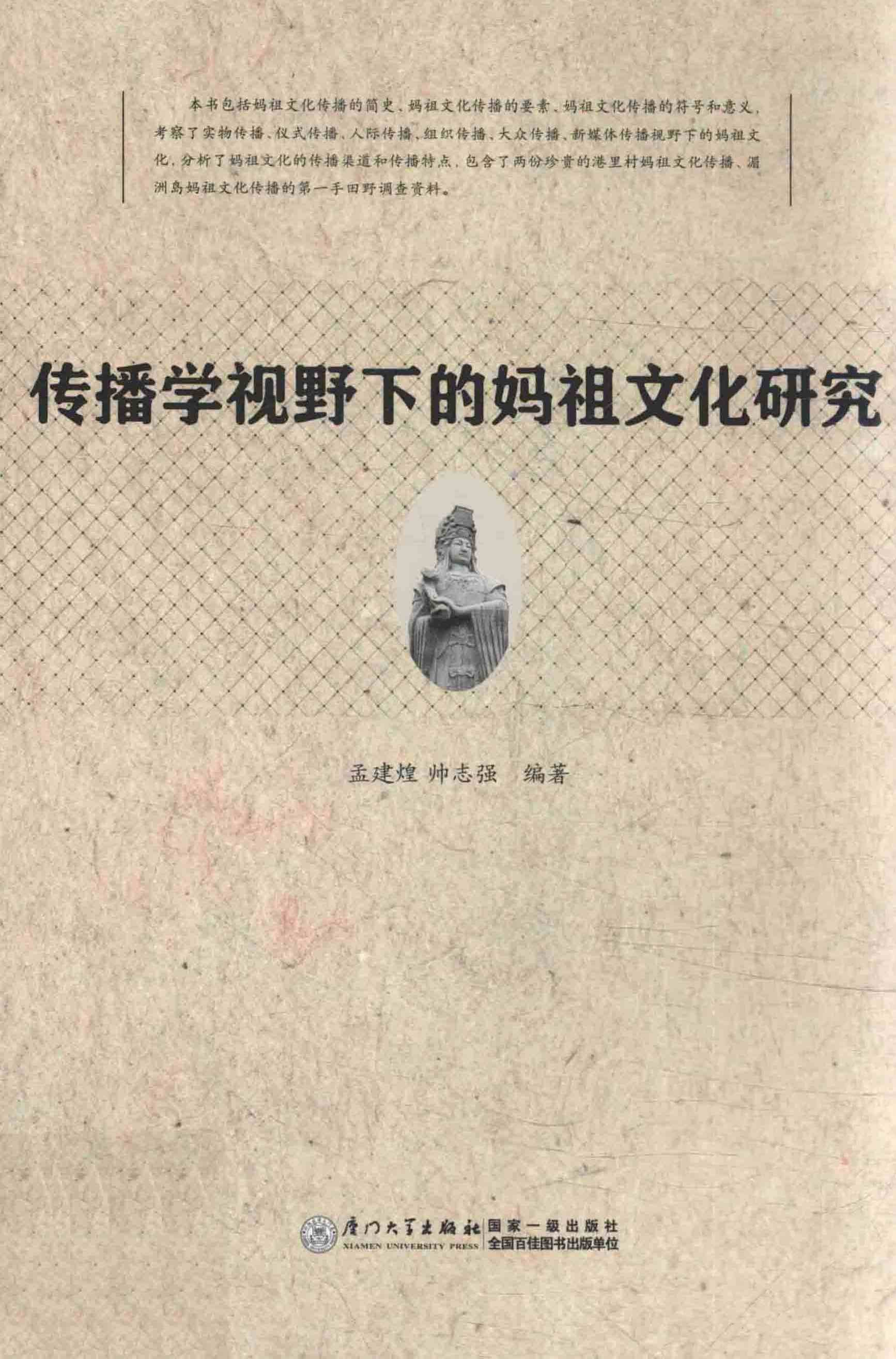
《传播学视野下的妈祖文化研究》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包括妈祖文化传播的简史、妈祖文化传播的要素、妈祖文化传播的符号和意义,考察了实物传播、仪式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体传播视野下的妈祖文化,分析了妈祖文化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特点,包含了两份珍贵的港里村妈祖文化传播、湄洲岛妈祖文化传播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