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符号与信息传播
| 内容出处: | 《传播学视野下的妈祖文化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620020220000462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符号与信息传播 |
| 分类号: | B933 |
| 页数: | 10 |
| 页码: | 37-46 |
| 摘要: | 信息的传播离不开符号,那么符号是什么?符号与信息传播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符号在人类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把符号的这种功能称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支配着索绪尔的整个语言的语言学系统。那么事物X便是事物Y的符号,Y便是X指代的事物或表述的意义。 |
| 关键词: | 文化传播 妈祖文化 符号 |
内容
一、符号与信息
信息的传播离不开符号,那么符号是什么?符号与信息传播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符号在人类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1,符号的概念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伴随着人类的各种活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就是借助于符号才能得以形成的。在认知体系中,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式;另一方面它是意义的载体,是精神的一种外化形式。符号与被反映物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意义来实现的。例如,“紫禁城”在政治上是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符号总是具有意义的符号,意义也总是以一定符号形式来呈现的。总的来说,符号的意思就是一种“特征纪念”,就像绰号是为了让人容易记住、方便辨认的称呼。你记张三李四可能麻烦,但你记“大胡子”“小眼镜儿”就方便多了,所以符号也可以说是由人的认识习惯造成的。
由此可见,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美国的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皮尔斯说:“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种真实的或复制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且它可以用另一个我称为解释者的符号去加以解释,以传达可能在此之前尚未知道的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①
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把符号的这种功能称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他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比如英语的“tree”这个单词,它的发音就是它的“能指”,而“树”的概念就是“所指”。“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树”这个词中,树的概念和“树”的特定发音不是必然结合在一起的,“树”在英文中的读音和在法文、拉丁文中的读音明显不同,但都能表达了“树”的意思。这就是符号的任意性原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支配着索绪尔的整个语言的语言学系统。
在传播学中,符号具有极为广泛的含义。日本学者永井成男认为,只要在事物X和事物Y之间存在着某种指代或表述关系,“X能够指代或表述Y”,那么事物X便是事物Y的符号,Y便是X指代的事物或表述的意义。从这个定义而言,符号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感觉到的声音、动作、形状、颜色、气味甚至物体,只要它们能够携带信息或表述某种特定的意义,都属于符号的范畴。①
由此可以看出,符号学所研究的符号就是能传递某种信息的事物,实际上也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媒介。正是从这个角度,有些学者才认为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英国著名学者特伦斯·霍克斯曾说,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域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从长远看来,两者都应被囊括在第三个容量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被称作传播(Communication)。②
符号在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通过编码、解码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递。具体地说,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再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是一种双边的、相互影响的过程。在传播学理论中,传播学者对信息传播中符号的意义及运用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2.符号的基本特征
(1)抽象性
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把符号理解为由特殊抽象到普遍的一种形式。“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这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那里,被称为“反思”。即人能够从漂浮不定的感性之流中抽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进行研究。这种抽象能力在动物中是没有的。这就说明关系的思想是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符号体系,“关系”的思想根本不可能。所以“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
(2)普遍性
所谓普遍性是指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括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这一特性表明人的符号功能不受任何感性材料的限制。此一时、彼一时、此地、彼地,其意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由于每物都有一个名称,普遍适用就是人类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比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唯独人类能打开文化世界大门的奥秘之所在。
(3)多变性
一个符号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极其多变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内,用不同的词表达某种思想和观念。“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的,而是灵活多变的。”卡西尔认为,正是符号的这三大特性使符号超越于信号。卡西尔以巴甫洛夫所作的狗的第二信号系统实验为例来予以说明。他认为:“铃声”作为“信号”是一个物理事实,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相反,人的“符号”不是“事实性的”而是“理想性的”,它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而符号是“指称者”,信号有着某种物理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是观念性的,意义性的存在,具有功能性的价值。人类由于有了这个特殊的功能,才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世界所给予的影响做出事实上的反应,而且能对世界所给予的影响做出事实上的反应,而且能对世界做出主动的创造与解释。正是有了这个符号功能,才使人从动物的纯粹自然世界升华到人的文化世界。
3.符号的分类关于符号的分类,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为三种,即图像符号、索引符号与象征符号。
图像符号是一种与指涉对象有某些相似性的符号。皮尔斯说:“一个图像符号是一种仅以其自身特征相涉于它所指涉的对象的符号。”①换句话说,图像符号以其与对象相关或分享的某种品质,而“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它们指涉的对象。例如,一张照片,一幅地图,或一个简单的形象性标志,甚至包括厕所门上的男女剪影,都是“看起来”像它们所指涉的对象。口技或音乐中的各种模拟效果音,语言中的象声词,都是“听起来”像它们指涉的对象。至于视觉、听觉并用的影视艺术,其传递的符号和消息文本,也大多是图像性的符号。
索引符号是一种与其指涉对象有着某种直接联系或内在关系的符号,又称标志、指征。皮尔斯说:“一个索引符号以实际地为对象所影响而相涉于它所指涉的对象。”“当符号的个体存在与其对象确实发生关联时”,即为索引符号。①如烟之于火,闪电之于雷鸣,打喷嚏之于受凉感冒等。在通常情况下,因为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事实上或“受影响”的因果联系,故前者皆可被视作后者的索引符号。这种符号往往以人们不曾意识到的“强制”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象。
象征符号是一种与其指涉对象没有自然的、必然性联系的符号。它之所以成为一种对象的再现,完全是由于某种规则或约定俗成的惯例。皮尔斯说:“一个象征符号是一种某种普遍观念的协作联合,它的运作能使象征符号指涉于相关对象。”换言之,“当符号在或多或少的肯定程度上,被出自惯例读解为代表某对象时”,它便可被“称之为象征符号”。②口语中的大部分词汇,书面拼音文字,大部分数字,大部分法定的或公认的标志,相对其对象而言,通常是约定俗成的,或文化性的。其间没有什么必然的根据来解释它为什么“代表”这个对象而不“代表”那个对象,例如,“牛”这个词为什么只能代表牛而不能代表马,这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再如,十字路口的“红灯”为什么表示停,“绿灯”为什么表示行,这也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完全是由交通规则规定的,是一定的惯例、习俗、规则使它们成为象征符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符号学关于符号类别的研究对传播的编码、译码是大有裨益的,它既可以指导人们选择正确的符码传递信息,也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译码、释码,从而更好地接收、理解信息。
4.符号的基本功能
交际是符号的基本功能之一,符号的交际功能赋予了符号世界强大的生命力。从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人类的交际行为是指人们运用符号传情达意,进行人际间的讯息交流和讯息共享的行为协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符号具有不同的编码和解码规则。符号情境是人们运用符号进行认知和交际的具体情境,它在交际中主要起限制作用和解释作用。动首先表现为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反馈的过程也伴随着在符号解读基础上的再次符号化活动。
(2)传达功能
意义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形式,由符号承载,才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传播和保存。比如,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如果没有《论语》,我们就无法接触到他的精神世界,其思想也就无法传世至今。
(3)思考功能
思考是内在意识活动,是内在的信息处理过程。思考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符号、在各种符号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思维离不开语言,也就离不开符号。
二、符号学与传播学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中的semiotikos。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诗学》、《工具论》等著作中,都对符号有过相关的论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开始使用“符号学”这一术语。现代符号学研究,萌生于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皮尔斯和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奠基人。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指出:符号学是“将表明符号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语言学不过是符号这门总的学科中的一部分”。索绪尔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提出,创立了符号学。之后符号学逐渐形成两大流派,即以研究逻辑为主的流派和以研究语言为主的流派,而且涉及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影响非常广泛和深入,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科学。此后,符号学才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符号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符号学理论,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认识论、社会生物学、宗教学、神话、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现在,世界各国和符号学家正在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研究动物语言、宗教语言、法律语言、政治语言、广告语言等。
从符号学研究范畴看,它以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字、图像、动作、音乐、物品,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仪式或表演,在更大的范围理解,一个事件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后,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符号。因此,符号学的研究涉及意义表达的一切领域。在大众传播日益发展和广泛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项目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的符号性和用各种符号建构意义的方方面面,已引起人们的充分注视。罗兰·巴尔特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还不敢肯定除了人类语言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具有某种广泛性的符号系统..所有的符号系统都与语言纠缠不清。
1.符号学的产生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实用和审美两种需求,并且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设计活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符号行为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从甲骨文到图腾图案,都记载古人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的信息。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符号不断地被发掘和运用,并且不断丰富。日本学者持上彦指出,当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之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为“符号”。
索绪尔在其对现代语言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
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首先,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符号学理论认为,人的思维是由认识表象开始的,事物的表象被记录到大脑中形成概念,而后大脑皮层将这些来源于实际生活经验的概念加以归纳、整理并进行储存,从而使外部世界乃至自身思维世界的各种对象和过程均在大脑中形成各自对应的映像;这些映像以狭义语言为基础,又表现为可视图形、文字、语言、肢体动作、音乐等广义语言。这种狭义与广义语言的结合即为符号。
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
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道:“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作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泽成法文)和法国哲学家梅尔洛·庞蒂的《感觉现象学》(1945年)。
2.传播学与符号学是两门互相交叉的学科
从名称上看,传播学与符号学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但进一步分析,却又发现两者有许多明显的交叉。有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与符号学从某些方面说与符号学研究是同义语。传播学与符号学这两个学科名称术语有时甚至可以互换。①这种观点得到了来自符号学传统和传播学传统两个领域的不同角度的确证。例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吉罗的《符号学概论》,将符号学与传播学几乎视为同一对象来处理。以至于中文译者在译序中谈道,“首先,符号学属于传播学,而传播的构成要素也适用于符号学”。②随后,吉罗在全书开篇第一章即将符号功能界定为“靠讯息来传播观念”,并将雅柯布森的模式视为对传播学理论的一种延展。③更多的情况,符号学者与传播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将对方视为要素之一。即符号学将传播视为符号过程的一个环节,而传播学则常常将符号视为传播的信息方式。再看传播学领域,施拉姆那部经典的《传播学概论》中辟专章写“传播的符号”。他认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独立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④国内学者也基本上接受了该观点,并以此来定义传播学。例如,陈力丹认为,“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⑤
应当说,符号学与传播学的结合,最“快速简洁”的办法就是从传播内容入手,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难道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文本分析”或者说“语义分析”层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发现国内首先引进或提倡“符传播学”的学者中,这种基于批判取向的符号文本分析似乎成了“传播符号学”的典型方法。①
品牌战略专家、传媒符号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胡易容在《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中为新闻传播学科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一传媒符号学。“传媒符号学”,即集传播学和符号学精粹于一体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但“传媒符号学”研究一直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原因有二:一是传媒符号学研究集中于文本分析,二是学界习惯将符号学方法作为传媒的“批评理论”。
其实,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有一部分是相同的。这两门学科都研究符号,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应包括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组成部分。语形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各种关系,语义学主要研究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主要研究符号和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传播学关于编码、译码、释码的研究也要涉及这三方面的内容。编码就是传播者把要传递的信息转化成符号,因为传播者要传递的信息(包括思想、感情)仅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在自己的大脑里,别人是无法知晓的。要想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别人,就要把它们转化成文字、声音、表情、姿势等各种各样的符号,变成别人凭各种感官就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译码是编码的逆变换,即接受者把接收到的符号再转换成信息,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释码。显然编码者要考虑语形、语义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符号?怎样组织符号才能准确地传达意义,才能使对方(指受传者)正确地理解意义?译码、释码者也要考虑语义、语用的问题: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什么?对方(指传者)使用这些符号表达什么意思?
传播学和符号学也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内容。传播学除了研究传播的媒介、符号以外,还要研究传播的过程、传播的技巧、传播的效果、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传播与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符号学是不研究的。
同样,人类传播所使用的符号也只是符号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符号学还研究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动植物的刺激反应过程,高级生物的知觉和倾向性方式,灵长目动物的相互作用以及机器中的信息加工等内容。例如,美国当代著名的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A.Sebeok)创立的动物符号学就是研究各种动物(如蜜蜂、鸟、猩猩等)之间的信息传递问题。显然,这些内容传播学是不研究的。
既然如此,传播学可否称为“符号传播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李思屈在《传媒业的产业融合与传播符号学的新视域》一文中认为:传播学应然并正在走向一门“传播符号学”。①
“传播符号学”的概念最早由费斯克在《传播符号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两大派别,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前者视传播为讯息的传递,关注的焦点在于传送者和接收者如何进行译码和编码,以及传送者如何使用传播媒介和管道。它探讨传播的效果和正确性问题。后者则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传播学和符号学是两门相互交叉的学科。③传播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其外部模式容易观察,也相对容易以量化的形式加以描述。然而,当各种传播技术相互交融,使传播现象弥漫于各个领域和大众的日常生活,“内容”产品正在溢出过去的“传媒业”边界的时候,传播的“内容”一符号与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这就为传播符号学的发展提供了外在动力。内在的发展逻辑与外在的社会需求相契合,是一门学科焕发生机的重要条件。
传播的本质是对意义的生产、传递与消费。不同文化浸淫下的消费者对同一部作品的消费感受会有不同,这非但不是信息传递的失败,恰是符号与意义消费的价值所在:传媒产品正是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意义文本,来丰富人们的生命体验。对意义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接近“符号消费”的研究焦点,深入到当前新型传媒产业发展的核心。传播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将成为我们适应、当前传媒产业实践的融合变化,进一步推进传播学发展的一种新的视野与思路。
信息的传播离不开符号,那么符号是什么?符号与信息传播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符号在人类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1,符号的概念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伴随着人类的各种活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就是借助于符号才能得以形成的。在认知体系中,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式;另一方面它是意义的载体,是精神的一种外化形式。符号与被反映物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意义来实现的。例如,“紫禁城”在政治上是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符号总是具有意义的符号,意义也总是以一定符号形式来呈现的。总的来说,符号的意思就是一种“特征纪念”,就像绰号是为了让人容易记住、方便辨认的称呼。你记张三李四可能麻烦,但你记“大胡子”“小眼镜儿”就方便多了,所以符号也可以说是由人的认识习惯造成的。
由此可见,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美国的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皮尔斯说:“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种真实的或复制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且它可以用另一个我称为解释者的符号去加以解释,以传达可能在此之前尚未知道的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①
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把符号的这种功能称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他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比如英语的“tree”这个单词,它的发音就是它的“能指”,而“树”的概念就是“所指”。“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树”这个词中,树的概念和“树”的特定发音不是必然结合在一起的,“树”在英文中的读音和在法文、拉丁文中的读音明显不同,但都能表达了“树”的意思。这就是符号的任意性原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支配着索绪尔的整个语言的语言学系统。
在传播学中,符号具有极为广泛的含义。日本学者永井成男认为,只要在事物X和事物Y之间存在着某种指代或表述关系,“X能够指代或表述Y”,那么事物X便是事物Y的符号,Y便是X指代的事物或表述的意义。从这个定义而言,符号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感觉到的声音、动作、形状、颜色、气味甚至物体,只要它们能够携带信息或表述某种特定的意义,都属于符号的范畴。①
由此可以看出,符号学所研究的符号就是能传递某种信息的事物,实际上也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媒介。正是从这个角度,有些学者才认为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英国著名学者特伦斯·霍克斯曾说,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域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从长远看来,两者都应被囊括在第三个容量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被称作传播(Communication)。②
符号在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通过编码、解码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递。具体地说,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再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是一种双边的、相互影响的过程。在传播学理论中,传播学者对信息传播中符号的意义及运用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2.符号的基本特征
(1)抽象性
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把符号理解为由特殊抽象到普遍的一种形式。“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这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那里,被称为“反思”。即人能够从漂浮不定的感性之流中抽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进行研究。这种抽象能力在动物中是没有的。这就说明关系的思想是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符号体系,“关系”的思想根本不可能。所以“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
(2)普遍性
所谓普遍性是指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括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这一特性表明人的符号功能不受任何感性材料的限制。此一时、彼一时、此地、彼地,其意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由于每物都有一个名称,普遍适用就是人类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比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唯独人类能打开文化世界大门的奥秘之所在。
(3)多变性
一个符号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极其多变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内,用不同的词表达某种思想和观念。“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的,而是灵活多变的。”卡西尔认为,正是符号的这三大特性使符号超越于信号。卡西尔以巴甫洛夫所作的狗的第二信号系统实验为例来予以说明。他认为:“铃声”作为“信号”是一个物理事实,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相反,人的“符号”不是“事实性的”而是“理想性的”,它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而符号是“指称者”,信号有着某种物理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是观念性的,意义性的存在,具有功能性的价值。人类由于有了这个特殊的功能,才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世界所给予的影响做出事实上的反应,而且能对世界所给予的影响做出事实上的反应,而且能对世界做出主动的创造与解释。正是有了这个符号功能,才使人从动物的纯粹自然世界升华到人的文化世界。
3.符号的分类关于符号的分类,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为三种,即图像符号、索引符号与象征符号。
图像符号是一种与指涉对象有某些相似性的符号。皮尔斯说:“一个图像符号是一种仅以其自身特征相涉于它所指涉的对象的符号。”①换句话说,图像符号以其与对象相关或分享的某种品质,而“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它们指涉的对象。例如,一张照片,一幅地图,或一个简单的形象性标志,甚至包括厕所门上的男女剪影,都是“看起来”像它们所指涉的对象。口技或音乐中的各种模拟效果音,语言中的象声词,都是“听起来”像它们指涉的对象。至于视觉、听觉并用的影视艺术,其传递的符号和消息文本,也大多是图像性的符号。
索引符号是一种与其指涉对象有着某种直接联系或内在关系的符号,又称标志、指征。皮尔斯说:“一个索引符号以实际地为对象所影响而相涉于它所指涉的对象。”“当符号的个体存在与其对象确实发生关联时”,即为索引符号。①如烟之于火,闪电之于雷鸣,打喷嚏之于受凉感冒等。在通常情况下,因为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事实上或“受影响”的因果联系,故前者皆可被视作后者的索引符号。这种符号往往以人们不曾意识到的“强制”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象。
象征符号是一种与其指涉对象没有自然的、必然性联系的符号。它之所以成为一种对象的再现,完全是由于某种规则或约定俗成的惯例。皮尔斯说:“一个象征符号是一种某种普遍观念的协作联合,它的运作能使象征符号指涉于相关对象。”换言之,“当符号在或多或少的肯定程度上,被出自惯例读解为代表某对象时”,它便可被“称之为象征符号”。②口语中的大部分词汇,书面拼音文字,大部分数字,大部分法定的或公认的标志,相对其对象而言,通常是约定俗成的,或文化性的。其间没有什么必然的根据来解释它为什么“代表”这个对象而不“代表”那个对象,例如,“牛”这个词为什么只能代表牛而不能代表马,这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再如,十字路口的“红灯”为什么表示停,“绿灯”为什么表示行,这也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完全是由交通规则规定的,是一定的惯例、习俗、规则使它们成为象征符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符号学关于符号类别的研究对传播的编码、译码是大有裨益的,它既可以指导人们选择正确的符码传递信息,也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译码、释码,从而更好地接收、理解信息。
4.符号的基本功能
交际是符号的基本功能之一,符号的交际功能赋予了符号世界强大的生命力。从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人类的交际行为是指人们运用符号传情达意,进行人际间的讯息交流和讯息共享的行为协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符号具有不同的编码和解码规则。符号情境是人们运用符号进行认知和交际的具体情境,它在交际中主要起限制作用和解释作用。动首先表现为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反馈的过程也伴随着在符号解读基础上的再次符号化活动。
(2)传达功能
意义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形式,由符号承载,才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传播和保存。比如,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如果没有《论语》,我们就无法接触到他的精神世界,其思想也就无法传世至今。
(3)思考功能
思考是内在意识活动,是内在的信息处理过程。思考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符号、在各种符号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思维离不开语言,也就离不开符号。
二、符号学与传播学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中的semiotikos。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诗学》、《工具论》等著作中,都对符号有过相关的论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开始使用“符号学”这一术语。现代符号学研究,萌生于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皮尔斯和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奠基人。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指出:符号学是“将表明符号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语言学不过是符号这门总的学科中的一部分”。索绪尔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提出,创立了符号学。之后符号学逐渐形成两大流派,即以研究逻辑为主的流派和以研究语言为主的流派,而且涉及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影响非常广泛和深入,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科学。此后,符号学才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符号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符号学理论,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认识论、社会生物学、宗教学、神话、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现在,世界各国和符号学家正在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研究动物语言、宗教语言、法律语言、政治语言、广告语言等。
从符号学研究范畴看,它以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字、图像、动作、音乐、物品,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仪式或表演,在更大的范围理解,一个事件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后,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符号。因此,符号学的研究涉及意义表达的一切领域。在大众传播日益发展和广泛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项目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的符号性和用各种符号建构意义的方方面面,已引起人们的充分注视。罗兰·巴尔特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还不敢肯定除了人类语言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具有某种广泛性的符号系统..所有的符号系统都与语言纠缠不清。
1.符号学的产生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实用和审美两种需求,并且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设计活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符号行为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从甲骨文到图腾图案,都记载古人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的信息。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符号不断地被发掘和运用,并且不断丰富。日本学者持上彦指出,当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之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为“符号”。
索绪尔在其对现代语言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
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首先,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符号学理论认为,人的思维是由认识表象开始的,事物的表象被记录到大脑中形成概念,而后大脑皮层将这些来源于实际生活经验的概念加以归纳、整理并进行储存,从而使外部世界乃至自身思维世界的各种对象和过程均在大脑中形成各自对应的映像;这些映像以狭义语言为基础,又表现为可视图形、文字、语言、肢体动作、音乐等广义语言。这种狭义与广义语言的结合即为符号。
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
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道:“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作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泽成法文)和法国哲学家梅尔洛·庞蒂的《感觉现象学》(1945年)。
2.传播学与符号学是两门互相交叉的学科
从名称上看,传播学与符号学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但进一步分析,却又发现两者有许多明显的交叉。有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与符号学从某些方面说与符号学研究是同义语。传播学与符号学这两个学科名称术语有时甚至可以互换。①这种观点得到了来自符号学传统和传播学传统两个领域的不同角度的确证。例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吉罗的《符号学概论》,将符号学与传播学几乎视为同一对象来处理。以至于中文译者在译序中谈道,“首先,符号学属于传播学,而传播的构成要素也适用于符号学”。②随后,吉罗在全书开篇第一章即将符号功能界定为“靠讯息来传播观念”,并将雅柯布森的模式视为对传播学理论的一种延展。③更多的情况,符号学者与传播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将对方视为要素之一。即符号学将传播视为符号过程的一个环节,而传播学则常常将符号视为传播的信息方式。再看传播学领域,施拉姆那部经典的《传播学概论》中辟专章写“传播的符号”。他认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独立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④国内学者也基本上接受了该观点,并以此来定义传播学。例如,陈力丹认为,“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⑤
应当说,符号学与传播学的结合,最“快速简洁”的办法就是从传播内容入手,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难道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文本分析”或者说“语义分析”层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发现国内首先引进或提倡“符传播学”的学者中,这种基于批判取向的符号文本分析似乎成了“传播符号学”的典型方法。①
品牌战略专家、传媒符号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胡易容在《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中为新闻传播学科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一传媒符号学。“传媒符号学”,即集传播学和符号学精粹于一体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但“传媒符号学”研究一直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原因有二:一是传媒符号学研究集中于文本分析,二是学界习惯将符号学方法作为传媒的“批评理论”。
其实,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有一部分是相同的。这两门学科都研究符号,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应包括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组成部分。语形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各种关系,语义学主要研究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主要研究符号和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传播学关于编码、译码、释码的研究也要涉及这三方面的内容。编码就是传播者把要传递的信息转化成符号,因为传播者要传递的信息(包括思想、感情)仅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在自己的大脑里,别人是无法知晓的。要想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别人,就要把它们转化成文字、声音、表情、姿势等各种各样的符号,变成别人凭各种感官就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译码是编码的逆变换,即接受者把接收到的符号再转换成信息,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释码。显然编码者要考虑语形、语义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符号?怎样组织符号才能准确地传达意义,才能使对方(指受传者)正确地理解意义?译码、释码者也要考虑语义、语用的问题: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什么?对方(指传者)使用这些符号表达什么意思?
传播学和符号学也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内容。传播学除了研究传播的媒介、符号以外,还要研究传播的过程、传播的技巧、传播的效果、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传播与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符号学是不研究的。
同样,人类传播所使用的符号也只是符号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符号学还研究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动植物的刺激反应过程,高级生物的知觉和倾向性方式,灵长目动物的相互作用以及机器中的信息加工等内容。例如,美国当代著名的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A.Sebeok)创立的动物符号学就是研究各种动物(如蜜蜂、鸟、猩猩等)之间的信息传递问题。显然,这些内容传播学是不研究的。
既然如此,传播学可否称为“符号传播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李思屈在《传媒业的产业融合与传播符号学的新视域》一文中认为:传播学应然并正在走向一门“传播符号学”。①
“传播符号学”的概念最早由费斯克在《传播符号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两大派别,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前者视传播为讯息的传递,关注的焦点在于传送者和接收者如何进行译码和编码,以及传送者如何使用传播媒介和管道。它探讨传播的效果和正确性问题。后者则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传播学和符号学是两门相互交叉的学科。③传播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其外部模式容易观察,也相对容易以量化的形式加以描述。然而,当各种传播技术相互交融,使传播现象弥漫于各个领域和大众的日常生活,“内容”产品正在溢出过去的“传媒业”边界的时候,传播的“内容”一符号与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这就为传播符号学的发展提供了外在动力。内在的发展逻辑与外在的社会需求相契合,是一门学科焕发生机的重要条件。
传播的本质是对意义的生产、传递与消费。不同文化浸淫下的消费者对同一部作品的消费感受会有不同,这非但不是信息传递的失败,恰是符号与意义消费的价值所在:传媒产品正是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意义文本,来丰富人们的生命体验。对意义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接近“符号消费”的研究焦点,深入到当前新型传媒产业发展的核心。传播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将成为我们适应、当前传媒产业实践的融合变化,进一步推进传播学发展的一种新的视野与思路。
附注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①转引自陈道德:《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
②[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①[美]皮尔斯:《逻辑学作为符号学:符号理论》,转引自陈道德:《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①[美]皮尔斯:《逻辑学作为符号学:符号理论》,转引自陈道德:《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②[美]皮尔斯:《逻辑学作为符号学:符号理论》,转引自陈道德:《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①PaulBouissac.EncyclopediaofSemiot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133.
②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译序,第7页。
③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④威尔伯·施拉姆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⑤赵毅衡、蒋荣昌:《符号与传媒》,第五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①赵星植:《评李彬〈传播符号论〉》,http://www.semiotics.net.cn/cbfhxts_show.asp?id=1839,访问日期:2012年10月15日。
①李思屈:《传媒业的产业融合与传播符号学的新视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②约翰·费斯克著,张锦华译:《传播符号学理论》,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③陈道德:《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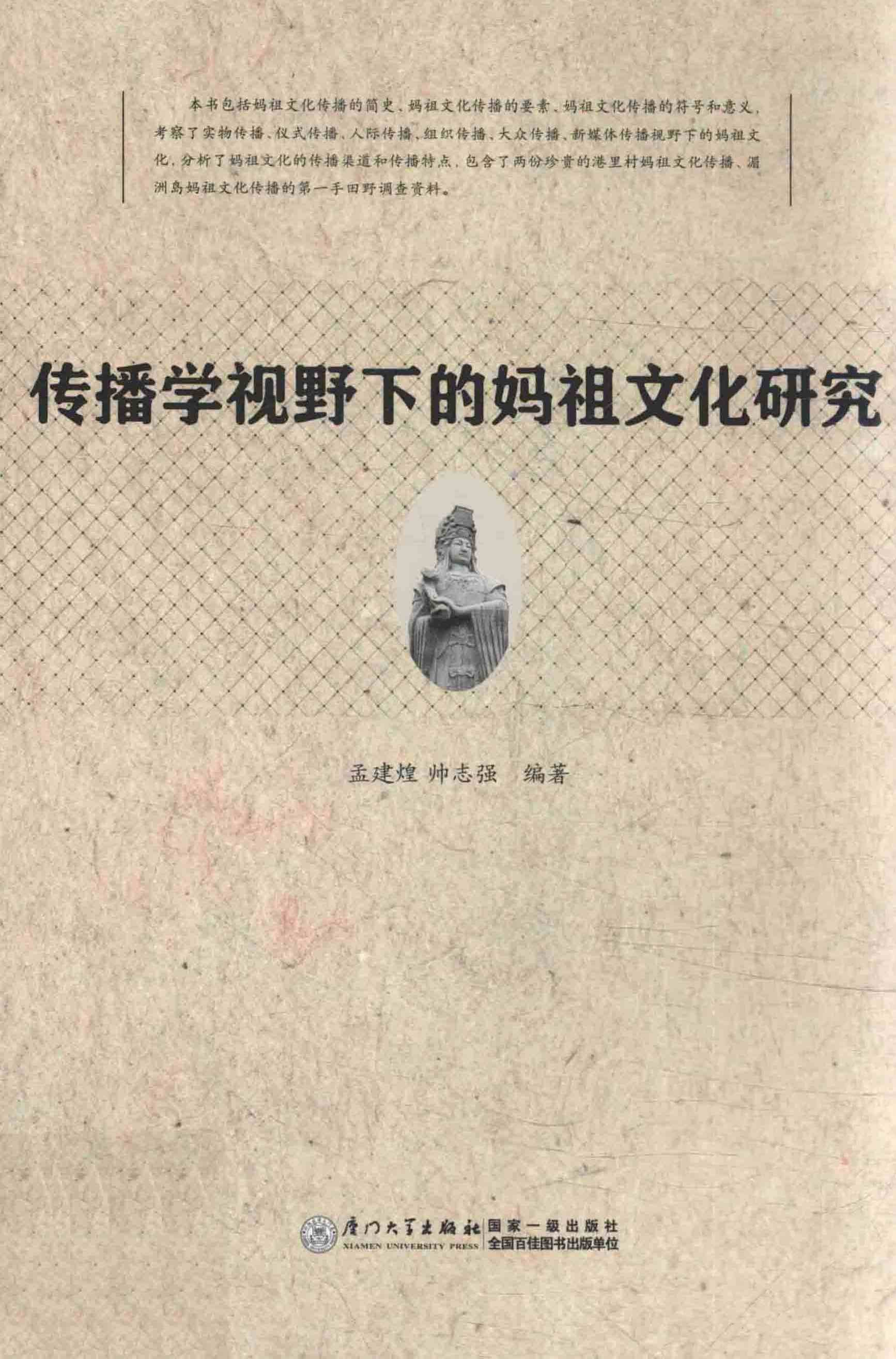
《传播学视野下的妈祖文化研究》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包括妈祖文化传播的简史、妈祖文化传播的要素、妈祖文化传播的符号和意义,考察了实物传播、仪式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体传播视野下的妈祖文化,分析了妈祖文化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特点,包含了两份珍贵的港里村妈祖文化传播、湄洲岛妈祖文化传播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