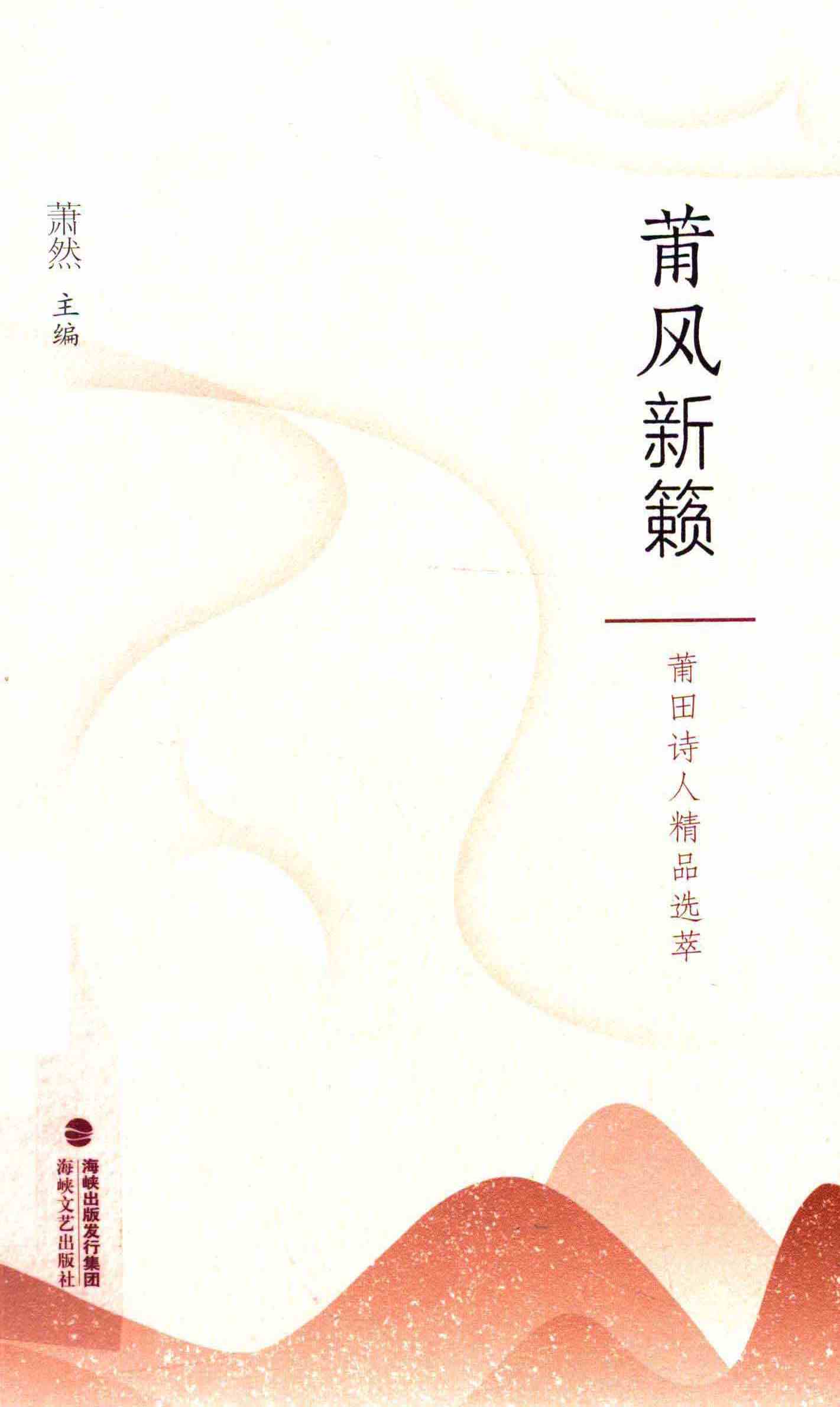内容
一、诗乡与诗人的归来
莆田别称莆阳,地处福建中东部沿海,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自西晋衣冠南渡以来,中原文化的垂青很快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诗歌之花:唐代有南湖三兄弟、江采苹和黄滔,宋代有蔡襄、陈俊卿和刘克庄,明清有林尧英、郑纪、陈池养和郭尚先等,其中郑露和江采苹更是公认的八闽第一位男诗人和女诗人。在清人郑王臣所编撰的《莆风清籁集》中,就收录了此地自唐至清近两千位乡贤的三千余首诗作,首次集中且系统地展示了莆阳诗群的渊源和流派。此后,莆田又涌现出郭风、彭燕郊等优秀诗人,他们以自己的经典作品在近当代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这看似一脉相承的诗路,也曾在许多次的廷变、兵燹或天灾中经受剧烈激荡,随之产生式微与回归的轮回。莆阳诗群的上一次兴盛,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朦胧诗的启迪,本土的一批青年诗人开始以诗歌为故乡抒情。不久之后,青年们返归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加之下一代的断层,诗歌渐成模糊的轮廓。直到近些年,在各个年龄层的莆田诗人自觉的身份认同和群体集结下,莆阳诗群才得以重拾回归的旗纛;在诗风兴盛、诗人担当和诗学奠立这三大标准的鼎足上,莆田这座城市正重新焕发诗乡的风采。
2013年11月,诗人梁征在莆田、新疆诗人交流活动上,曾将莆阳山水亲切地称为“甜美的沃土”。在莆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此间大小乡镇,并以饱满的深情为莆田的老二十四景和新二十四景打造诗歌名片。这里的奇秀山水和独特人文,让这位来自北方的汉子有了一见如故和宾至如归的感觉:面对宁海桥的初升红日,他看到了“海的心是水/水的心是波/波的心是天/天的心是这轮宁海的初日”;面对天马山的晴岚,他“听到腾云驾雾的萧萧/自光彩中泻出一派嘶风水墨”;面对木兰溪的泱泱春水,他遥想起“千年钱妃的痴情倚盼/把一己悲欢投进了惊涛骇浪/留下一生的神奇和瞬间的壮怀”;面对夹漈草堂的书声松风,他由衷赞叹“苍老的是石头/长寿的是学说/一个永不风化的灵魂/像莆阳山水一样鲜活”。梁征在诗里与山水对话,与古人对话,他将莆阳所赋予的这段人生际遇,转化为“人兴业茂,清风明月”的诗意蓝图回馈这座古城。
于是更多的人听见了诗乡洪亮的召唤。出生于闽东的莆籍诗人哈雷,是一位诗歌布道者。回到祖籍地,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河道边上/猛烈地听到龙眼催熟的声音”,因为“喝过无数兰溪水/手握着一颗又一颗滚烫的荔枝/但一直叫不出家乡的名字”,而发出“人有其土,木兰溪,我是你不肖的儿子”的感慨。因此,他开始沿着延寿溪的涓流,踏上了返乡之旅:“我爱你的地方,必须是缓缓流动河水/暮色苍茫,归鸟漫天,两岸青蛙在草丛中鼓腹长吟”。在他的行吟中,故乡从一个遥远的符号愈发清晰真实,好像一位慈母“总是一针一线穿引着我所有的挂念/襟江带水地润湿了我的全部容颜/并用一个词描述家的意义”。不仅于此,在2010至2013年的短短数年间,诗人哈雷先后成功策划了“映像·妈祖”“映像·仙游”“映像·莆阳”及“映像·涵江”等系列大型诗歌活动,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华语诗人共同聚焦莆阳,诗写莆阳,在莆阳的诗事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前者相比,诗人南夫与本少爷的归来则有着更加恰如其分的理由——他们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并且都有过在外闯荡事业的相似经历。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在外莆田人坚毅隐忍、敢拼善闯的地域性格,更有着离家千里心系故土的殷殷牵系;这份牵系,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里先后选择了回归家园。南夫是活跃在莆田本土的屈指可数的“50后”诗人,如今,他幽居沿海老家,抱着承欢膝下的小孙子,过着“用诗人乘以后海/等于一枚/金质徽章”的“富农生活”。他的诗歌自然、流畅,不刻意修辞,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痛苦于传统的瓦解,忧患于乡村的崩塌,嬉笑怒骂皆有诗性光芒。本少爷是突围诗社的荣誉社长,在外多年,凭着一身的才气和义气,与国内众多诗人有过交集,也是莆田为数不多的作品荣登《人民文学》的实力诗人。他的诗歌世界中,有着一座“雨落在上面/仿佛万千诗人”即将投奔的“诗江湖”;他的江湖里,既有着“多情人小安”的儿女情长,也有着“我正在发育。/那些年它们不得不顺从我”的意气风发,有“不知今晚厦门的月亮/是否照着我们/还照着千年前的李杜”的兄弟情深,还有着“诗人决绝离去/留下双瞳剪水/来是空言去绝踪”的快意恩仇。这些年,他更是致力于加强莆田民间诗歌力量的对外交流和群体展示,先后在《诗歌月刊》《诗潮》《天津诗人》等刊物上集中推荐莆阳诗群,从民间行为上为莆田在福建的诗群土壤中争取应有的位置。
除此之外,还有朱谷忠、杨健民、田荔琴、郑重、西楼、杨雪帆、萧然、王鸿、林春荣、岸子、程剑平等的“归来”,以及“80后”的莆田诗人陈上、霞浦诗人黄加芳和武汉诗人但薇的汇入。外籍在莆诗人、莆籍在外诗人和莆田本土诗人,丰富着莆阳诗群的组成结构,这种多元、开放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承担着复兴莆田诗脉的重任。
二、诗群与诗写的归来
20世纪80年代,诗人郑重等在莆仙地区埋下了一粒诗歌的种子。在他与叶弦鸣、杨振辉等人的奔走与组织下,兰溪诗社应运而生,凝聚了吴建华、朱金明、朱金芳、郭明理、陈舟、李峰、严凯、郑国贤、郑清为、施清泉、赖振锋、张青青、邱庆政、王林、谢选首、麦冬、罗西、萧然等一大批中坚力量,成为了这里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现代诗群。诗社成立伊始,受到了省内外诗歌界的广泛关注,出版了莆田地区首份新诗诗报——《兰溪》,邀请了郭风、蔡其矫、谢冕、刘登翰、俞兆平、杨健民、谢春池、舒婷、陈仲义、章武、朱谷忠等诸多名家担纲顾问,并得到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建省文化厅厅长许怀中先生的来信祝贺——这段闪亮的经历,已经成为许多人珍贵的集体记忆。作为当年兰溪诗社的主要召集人兼副社长,郑重的诗歌成就不仅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升华,更在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精神领袖。尽管如此,诗人哈雷仍将其称为一位“十分低调”的“归来的诗写者”,他从郑重“遵循内心的召唤”的表达中,发现了他诗歌“安静的品质”。无独有偶,评论家孙绍振读到了郑重诗歌中“极度自由”的一面:“以孤独的姿态远行,寻找着相似的倒影,并最终抵达更为柔软的自己。它们是三颗被丢入水中的石子,通过层层漾开的涟漪,打开了其作品里广阔的诗境。”我们看到,郑重的诗和他的人生阅历是彼此捆绑又相互映照的,时而讴歌壮美山河:“到漠北去,以一粒沙的名义/叩击大漠的胸膛/追逐戈壁的浩瀚”;时而探寻低处之美:“风打开翅膀/一只雀,把檐角抓得更紧/如披着风衣的词/翻开了方向”;时而转述生命体验:“盘旋出生命之轻/又俯冲出欲望之重”;时而表达纯粹哲思:“能把一只鸟说成鸟的人/一定能长出一片/树林般的羽翼”。相同的是,他那由“不屈的脾气,奔跑的个性和青春的刚毅”所组成的激情始终透出纸面,难怪令同样来自仙游的诗人王清铭啧啧称奇,谓之“奇气”。
就在兰溪诗社横空出世的年代,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群活跃在莆田秀屿的诗人,开始站在海天交接处,从日复一日的潮汐中索取咏叹的诗句;他们颂唱的源点——南日岛,也在外人的印象中化身一座诗之岛。诗人杨雪帆这么描写道:“这是天神栖息过的岛屿/澄静的午夜,宏亮的晨晖/以及琥珀色的傍晚/朝圣者把石砌的马道修向海洋”;他的老乡张紫宸延续着他笔下的神性,并嫁接在岛上的一切意象之上:“幸福的女人像棵马尾松/被劈成柴,塞进炉膛/烧成袅袅的灰和烟”。然而,现代化的冲击,让诗人王鸿看到了今日南日岛的矛盾:“这才是真实的南日——永远的是非之地/最沉寂也最嘈杂,最纯洁也最肮脏/最温情也最残酷,最平静也最凶险”,他以一种庐山之外的视野和一种抚摸尘世的大悲悯,洞察了当前多数乡村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时的茫然;同样深陷矛盾思考中的张玉泉则这么形容自己:“没有屋檐的阳台上/湿漉漉地站着一个/俯视大地的人”,多年来,从岛内到岛外,从海边到山区,张玉泉萃取于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的诗歌,正如其人:“尚待时日移到西山下/夕阳泛红,大地静息/我们就停止忧虑/放下今生”,带着一种回归的成熟和睿智。在他们的共同发声下,秀屿诗群凝聚了南夫、岸子、林落木、谢顺航、肖海英、麦田、南木、张旗、陈北、黄披星、陈言等人,并与行走在兰溪诗社流域的诗人们形成掎角之势,不断壮大莆田的诗歌力量。
如今的莆阳诗群,早已去除了原先模糊的地域阻隔,在信息和交流更为便利的年代,一扫年龄断层引发的惶恐担忧。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莆田的“80后”“90后”和“00后”诗人,如巫小茶、张坚、段裂、陈言、陈美者、陈海媛、刘永辉、倪伟李、李智强、欧逸舟、石瞒芋、上官朝夕、陈上、黄加芳、年微漾、但薇、蔡书琴、艾溅果、谢世明、许莉、周凌瀚、彭月婷、守树、晏禾、马彬辉、陈俊杰、吉嘉琦、李彤遥等人,都以不俗的创作实力和独特的作品特质为人们所期待。
而诗群的回归,首先必有赖于个体诗写的回归。这其中,以诗人萧然的归来最为瞩目。时光回到20世纪80年代,早在那时,年仅十几岁的萧然就开始发表诗歌及散文,并依靠出众的才华,在福建省内崭露头角。当年,萧然加入福建省作协时年仅22岁,成为莆田地区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次年,又出版首部诗集《静夜无痕》,引起巨大反响。然而,不落窠臼的性格,让正处在风生水起的创作道路上的他自我否定,接下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光阴里,萧然先后南下广东,又北上京城,点滴积累生命的沉淀。尽管暌违诗歌写作,也刻意回避诗群,但萧然始终以年轻时的诗心和性情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并享受生活。2014年底,在友人的劝说鼓舞下,萧然带来了他的第二部诗集——《不是去向是归途》。经历过时光交错和人生起伏后的萧然,带着一种抱朴守拙的超凡,他的诗歌尽可能多地删减了冗余的修辞和铺垫,只留下直击人心的锋刃,一如他的朋友在久别重逢时不约而同的发问:“当年萧然的那一袭飘飘长发哪里去了?”他从商业场的丛林法则中认识到了“一匹误陷兽夹的狼/是怎样咬断自己的腿”的残酷,却仍以最大的善意和悲悯,与这个时代达成和解,因为“猎人和猎物/都是一匹狼的生死之交”;而这也暴露了他无比虔诚的佛教信仰,他获得了“虚幻和真相/悬浮在云朵之上/彼此确认”的人生观,让一切复杂的虚像都回归简单的本质,从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另一方面,常年的羁旅生涯,让他的乡愁水涨船高,而他依然恪守节制,“使用修辞手法/省略掉战争,掌控好笔画的/宽度和深度,才能避免把木兰溪/写成黄河”;他爱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乡、妻儿和亲人,既不自大也不自卑,进而理解他人对故乡、妻儿和亲人的爱,理解乡愁、爱情和亲情背后隐藏着的苦难与悲怆,悟出了爱这个国家,就要“大声说出高山/说出大海,说出漠河,说出曾母暗沙/说出喜马拉雅真实的海拔”。在“萧然式归来”的影响下,王清铭、纪朝阳、柯友珊、方志忠、韩冰、郑朝阳、郭清锋、林寞、段裂、墨予、林养、李德辉、郑建华、程沧海、墨荷等一批诗人,也纷纷擦亮蒙尘的诗笔,掷出闪光的诗句。
三、诗运与诗学的归来
诚然,诗人和诗作是一个诗群的主体,而诗群的前进,则需要诗歌运动的助推;反观诗歌运动的背后,亦是诗人们个体担当和诗道精神的流露。在莆田文学界,几乎每个人都对云里风文学奖耳熟能详,在自1994年以来的漫长岁月中,莆籍华侨云里风先生以其充沛饱满的热情和报效桑梓的情怀,激励了一代代的青年才俊,其中不乏诗人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云里风文学奖在设置上的地域局限,使得它未能在全省范围形成更大的影响。
青年诗人张坚有感于此,决定做一些修订和补充。2008年,由他出资设立的首届“张坚诗歌奖”面向福建全省优秀诗人进行公开征稿,次年又进一步放开,改为面向全国。如今,“张坚诗歌奖”的评选工程已经进行到了第七届,影响力也在逐年攀升。在“拒绝平庸晦涩,评选实力诗人,力推新锐天才”的宗旨的引领下,“张坚诗歌奖”已发掘出多位诗坛新秀,其评委阵容更是涵盖了非马、古月、李少君、唐力、汤养宗、哈雷、陈先发、何小竹、曾宏、安琪等众多知名诗人。该奖项还曾先后三次分别在莆田市区、莆田西天尾镇和厦门曾厝〓举办盛大的颁奖仪式,每次都邀请了数十位各地诗人共同参与见证。特别是2009年春节的首届莆仙诗人联谊会,第一次提出了“莆阳诗群”的概念;此后不久,《诗歌月刊》2010年第2期上半月刊首度集结推出了莆田诗群作品展,标志着该诗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认。而张坚本人也长期坚持诗歌创作,曾出版有《有风或者无风》《水土不服》等诗集,借以安放漂泊在外的莆阳情结。
在诗歌创作呈现集体井喷的状态下,诗集的出版显得水到渠成。一本诗集是一位诗人最有效的名片,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外界对诗人印象的评判,而决定好坏标准的,不仅在于诗作的质量,也在于诗集在编排、校对、设计和印刷上的匠心独运。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林滨副社长,多年来以一位乡亲的情感,密切关注莆田诗群的成长,经他亲自操刀或协调出版的莆阳诗群诗集有孙绍振主编的《诗歌哈雷》、梁征的《木兰春涨》、郑重的《时间的羽翼》、萧然的《不是去向是归途》、王鸿的《尘世的抚摸》、黄披星的《不下雪的城市》、倪伟李的《纸上的硝烟》、年微漾的《一号楼》、陈上的《再造星辰》以及诗歌采风合集《映像莆阳》《诗韵涵江》等,在幕后为这一群体默默付出。
在诗歌氛围的共振下,出生于1987年的年轻诗人陈上,有了重启兰溪诗社的想法。学生时代,对外国文学的痴迷,成为他开启诗写道路的滥觞。他自比“初夏的朗诵者”,要在冰与火的围攻下守候诗歌的宗教;他的诗歌浑如印象派画作,带有一种意象的华彩,让人沉醉其间。他甚至擦掉了人们对于故乡习惯性的水墨式勾勒,改以一种更具冲击力的色调重新定义:“在这片海身上,时光重新开始流浪。/并且可以生长往事。/一片海只能埋没一次。/苏醒即是新生。”苏醒,也真的带来了新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莆田市作协副秘书长和《海峡诗人》杂志副主编,积极对外输送莆阳诗群的新鲜血液;不久后的兰溪诗社,也将在他的有力策划下,完成一次关于记忆和情感的时间穿越。
学者杨健民的方式则更为前卫,借着微信产品的东风,他提出了在微信朋友圈中进行同题诗歌写作的创意,并马上得到热烈响应。这种简便直接的沟通方式,让多数人重燃诗歌创作的激情,催生了不少优秀作品。诗人田荔琴在这种方式的诗写体验中,感悟到“生命的内存/比电脑宽厚”,说出了多数人共同的心声。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一个诗群的扎根若仅以一时的风气为依托,必然无法长久;它还需要诗歌美学的奠立和支撑,并以此为后来的写作提供经验和参考。莆阳诗群的诗作,有游历、有乡愁、有感悟、有纪实,题材上与其他地域的诗群并无太大差别,因此,从中提炼出一些独具一格的美学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担任《东南学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杨健民,是造诣很高的学者,更是莆阳诗群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观察者。在场是最好的解读。年轻时,杨健民先生以一部《艺术感觉论》,开创了美学领域的崭新课题;现在,对莆田诗人的专注,使得他总能发现他们身上的特立之处,并以此作为这部著述的进一步佐证。在《梁征与他的“寻找”》一文中,他一眼便敏锐地发现“梁征对于山水的抒情方式,已经从物象意义进入了一种透彻的参悟”;这种“禅思和妙悟”近乎一次次的“唤醒”,所有递呈表面的物象感官因此产生位移,更接近其“幽深的渊薮”。在陈上的诗歌面前,他毫不避讳地直言“在这个时候谈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当前多数诗人热衷于“挑战新的艺术偶像,撕裂了磨炼、推敲与精益求精的传统,这些反叛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然而,陈上“借用意象结构曲折地表现微妙的情绪结构”的表现手法,使他看到了其诗歌中安全、节制的珍贵品质,从而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并由衷发出“诗若安好,便是存在”的赞叹。推及萧然的创作,他则抛出了“诗歌的可能性意义区域”这一命题,认为“诗歌在所有写作中具有的可能性空间,就在于它是一切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是最具哲学意义的献给灵魂的礼物”;因此,“诗即是思”,是某种对于诗歌形式的解离后的“深度的理性”,只有保持这种理性,才会给读者以一直都想要“踩着”和“触碰着”的冲动。不难看出,杨健民先生对诗人的思考有着更高的期望,只有思考,一个诗人才能超越经验,在现实世界的背面规避引力和阻碍,获得真正的自由。
对于莆阳诗群,我好像说了不少,却好像还远远不够。对这个“归来的诗群”的重新定义,并非一次画地为牢式的自我狂欢,相反,这里的每个个体,其实又都是其他地域的原籍或在地诗人;而且,每位诗人的写作,也都是彼此独立的,正如诗人哈雷在年微漾诗集《一号楼》序言中所提及的:“所有的写作都是个人化的,诗歌更重要的是气质型写作。”只是,借助于身份认同,我们更容易因为某些共同属性而相互慰藉,更容易形成一股群体气质,从而走得更远。
借杨健民先生的话,就是:“诗若安好,便是存在!”
莆田别称莆阳,地处福建中东部沿海,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自西晋衣冠南渡以来,中原文化的垂青很快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诗歌之花:唐代有南湖三兄弟、江采苹和黄滔,宋代有蔡襄、陈俊卿和刘克庄,明清有林尧英、郑纪、陈池养和郭尚先等,其中郑露和江采苹更是公认的八闽第一位男诗人和女诗人。在清人郑王臣所编撰的《莆风清籁集》中,就收录了此地自唐至清近两千位乡贤的三千余首诗作,首次集中且系统地展示了莆阳诗群的渊源和流派。此后,莆田又涌现出郭风、彭燕郊等优秀诗人,他们以自己的经典作品在近当代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这看似一脉相承的诗路,也曾在许多次的廷变、兵燹或天灾中经受剧烈激荡,随之产生式微与回归的轮回。莆阳诗群的上一次兴盛,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朦胧诗的启迪,本土的一批青年诗人开始以诗歌为故乡抒情。不久之后,青年们返归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加之下一代的断层,诗歌渐成模糊的轮廓。直到近些年,在各个年龄层的莆田诗人自觉的身份认同和群体集结下,莆阳诗群才得以重拾回归的旗纛;在诗风兴盛、诗人担当和诗学奠立这三大标准的鼎足上,莆田这座城市正重新焕发诗乡的风采。
2013年11月,诗人梁征在莆田、新疆诗人交流活动上,曾将莆阳山水亲切地称为“甜美的沃土”。在莆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此间大小乡镇,并以饱满的深情为莆田的老二十四景和新二十四景打造诗歌名片。这里的奇秀山水和独特人文,让这位来自北方的汉子有了一见如故和宾至如归的感觉:面对宁海桥的初升红日,他看到了“海的心是水/水的心是波/波的心是天/天的心是这轮宁海的初日”;面对天马山的晴岚,他“听到腾云驾雾的萧萧/自光彩中泻出一派嘶风水墨”;面对木兰溪的泱泱春水,他遥想起“千年钱妃的痴情倚盼/把一己悲欢投进了惊涛骇浪/留下一生的神奇和瞬间的壮怀”;面对夹漈草堂的书声松风,他由衷赞叹“苍老的是石头/长寿的是学说/一个永不风化的灵魂/像莆阳山水一样鲜活”。梁征在诗里与山水对话,与古人对话,他将莆阳所赋予的这段人生际遇,转化为“人兴业茂,清风明月”的诗意蓝图回馈这座古城。
于是更多的人听见了诗乡洪亮的召唤。出生于闽东的莆籍诗人哈雷,是一位诗歌布道者。回到祖籍地,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河道边上/猛烈地听到龙眼催熟的声音”,因为“喝过无数兰溪水/手握着一颗又一颗滚烫的荔枝/但一直叫不出家乡的名字”,而发出“人有其土,木兰溪,我是你不肖的儿子”的感慨。因此,他开始沿着延寿溪的涓流,踏上了返乡之旅:“我爱你的地方,必须是缓缓流动河水/暮色苍茫,归鸟漫天,两岸青蛙在草丛中鼓腹长吟”。在他的行吟中,故乡从一个遥远的符号愈发清晰真实,好像一位慈母“总是一针一线穿引着我所有的挂念/襟江带水地润湿了我的全部容颜/并用一个词描述家的意义”。不仅于此,在2010至2013年的短短数年间,诗人哈雷先后成功策划了“映像·妈祖”“映像·仙游”“映像·莆阳”及“映像·涵江”等系列大型诗歌活动,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华语诗人共同聚焦莆阳,诗写莆阳,在莆阳的诗事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前者相比,诗人南夫与本少爷的归来则有着更加恰如其分的理由——他们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并且都有过在外闯荡事业的相似经历。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在外莆田人坚毅隐忍、敢拼善闯的地域性格,更有着离家千里心系故土的殷殷牵系;这份牵系,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里先后选择了回归家园。南夫是活跃在莆田本土的屈指可数的“50后”诗人,如今,他幽居沿海老家,抱着承欢膝下的小孙子,过着“用诗人乘以后海/等于一枚/金质徽章”的“富农生活”。他的诗歌自然、流畅,不刻意修辞,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痛苦于传统的瓦解,忧患于乡村的崩塌,嬉笑怒骂皆有诗性光芒。本少爷是突围诗社的荣誉社长,在外多年,凭着一身的才气和义气,与国内众多诗人有过交集,也是莆田为数不多的作品荣登《人民文学》的实力诗人。他的诗歌世界中,有着一座“雨落在上面/仿佛万千诗人”即将投奔的“诗江湖”;他的江湖里,既有着“多情人小安”的儿女情长,也有着“我正在发育。/那些年它们不得不顺从我”的意气风发,有“不知今晚厦门的月亮/是否照着我们/还照着千年前的李杜”的兄弟情深,还有着“诗人决绝离去/留下双瞳剪水/来是空言去绝踪”的快意恩仇。这些年,他更是致力于加强莆田民间诗歌力量的对外交流和群体展示,先后在《诗歌月刊》《诗潮》《天津诗人》等刊物上集中推荐莆阳诗群,从民间行为上为莆田在福建的诗群土壤中争取应有的位置。
除此之外,还有朱谷忠、杨健民、田荔琴、郑重、西楼、杨雪帆、萧然、王鸿、林春荣、岸子、程剑平等的“归来”,以及“80后”的莆田诗人陈上、霞浦诗人黄加芳和武汉诗人但薇的汇入。外籍在莆诗人、莆籍在外诗人和莆田本土诗人,丰富着莆阳诗群的组成结构,这种多元、开放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承担着复兴莆田诗脉的重任。
二、诗群与诗写的归来
20世纪80年代,诗人郑重等在莆仙地区埋下了一粒诗歌的种子。在他与叶弦鸣、杨振辉等人的奔走与组织下,兰溪诗社应运而生,凝聚了吴建华、朱金明、朱金芳、郭明理、陈舟、李峰、严凯、郑国贤、郑清为、施清泉、赖振锋、张青青、邱庆政、王林、谢选首、麦冬、罗西、萧然等一大批中坚力量,成为了这里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现代诗群。诗社成立伊始,受到了省内外诗歌界的广泛关注,出版了莆田地区首份新诗诗报——《兰溪》,邀请了郭风、蔡其矫、谢冕、刘登翰、俞兆平、杨健民、谢春池、舒婷、陈仲义、章武、朱谷忠等诸多名家担纲顾问,并得到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建省文化厅厅长许怀中先生的来信祝贺——这段闪亮的经历,已经成为许多人珍贵的集体记忆。作为当年兰溪诗社的主要召集人兼副社长,郑重的诗歌成就不仅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升华,更在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精神领袖。尽管如此,诗人哈雷仍将其称为一位“十分低调”的“归来的诗写者”,他从郑重“遵循内心的召唤”的表达中,发现了他诗歌“安静的品质”。无独有偶,评论家孙绍振读到了郑重诗歌中“极度自由”的一面:“以孤独的姿态远行,寻找着相似的倒影,并最终抵达更为柔软的自己。它们是三颗被丢入水中的石子,通过层层漾开的涟漪,打开了其作品里广阔的诗境。”我们看到,郑重的诗和他的人生阅历是彼此捆绑又相互映照的,时而讴歌壮美山河:“到漠北去,以一粒沙的名义/叩击大漠的胸膛/追逐戈壁的浩瀚”;时而探寻低处之美:“风打开翅膀/一只雀,把檐角抓得更紧/如披着风衣的词/翻开了方向”;时而转述生命体验:“盘旋出生命之轻/又俯冲出欲望之重”;时而表达纯粹哲思:“能把一只鸟说成鸟的人/一定能长出一片/树林般的羽翼”。相同的是,他那由“不屈的脾气,奔跑的个性和青春的刚毅”所组成的激情始终透出纸面,难怪令同样来自仙游的诗人王清铭啧啧称奇,谓之“奇气”。
就在兰溪诗社横空出世的年代,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群活跃在莆田秀屿的诗人,开始站在海天交接处,从日复一日的潮汐中索取咏叹的诗句;他们颂唱的源点——南日岛,也在外人的印象中化身一座诗之岛。诗人杨雪帆这么描写道:“这是天神栖息过的岛屿/澄静的午夜,宏亮的晨晖/以及琥珀色的傍晚/朝圣者把石砌的马道修向海洋”;他的老乡张紫宸延续着他笔下的神性,并嫁接在岛上的一切意象之上:“幸福的女人像棵马尾松/被劈成柴,塞进炉膛/烧成袅袅的灰和烟”。然而,现代化的冲击,让诗人王鸿看到了今日南日岛的矛盾:“这才是真实的南日——永远的是非之地/最沉寂也最嘈杂,最纯洁也最肮脏/最温情也最残酷,最平静也最凶险”,他以一种庐山之外的视野和一种抚摸尘世的大悲悯,洞察了当前多数乡村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时的茫然;同样深陷矛盾思考中的张玉泉则这么形容自己:“没有屋檐的阳台上/湿漉漉地站着一个/俯视大地的人”,多年来,从岛内到岛外,从海边到山区,张玉泉萃取于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的诗歌,正如其人:“尚待时日移到西山下/夕阳泛红,大地静息/我们就停止忧虑/放下今生”,带着一种回归的成熟和睿智。在他们的共同发声下,秀屿诗群凝聚了南夫、岸子、林落木、谢顺航、肖海英、麦田、南木、张旗、陈北、黄披星、陈言等人,并与行走在兰溪诗社流域的诗人们形成掎角之势,不断壮大莆田的诗歌力量。
如今的莆阳诗群,早已去除了原先模糊的地域阻隔,在信息和交流更为便利的年代,一扫年龄断层引发的惶恐担忧。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莆田的“80后”“90后”和“00后”诗人,如巫小茶、张坚、段裂、陈言、陈美者、陈海媛、刘永辉、倪伟李、李智强、欧逸舟、石瞒芋、上官朝夕、陈上、黄加芳、年微漾、但薇、蔡书琴、艾溅果、谢世明、许莉、周凌瀚、彭月婷、守树、晏禾、马彬辉、陈俊杰、吉嘉琦、李彤遥等人,都以不俗的创作实力和独特的作品特质为人们所期待。
而诗群的回归,首先必有赖于个体诗写的回归。这其中,以诗人萧然的归来最为瞩目。时光回到20世纪80年代,早在那时,年仅十几岁的萧然就开始发表诗歌及散文,并依靠出众的才华,在福建省内崭露头角。当年,萧然加入福建省作协时年仅22岁,成为莆田地区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次年,又出版首部诗集《静夜无痕》,引起巨大反响。然而,不落窠臼的性格,让正处在风生水起的创作道路上的他自我否定,接下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光阴里,萧然先后南下广东,又北上京城,点滴积累生命的沉淀。尽管暌违诗歌写作,也刻意回避诗群,但萧然始终以年轻时的诗心和性情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并享受生活。2014年底,在友人的劝说鼓舞下,萧然带来了他的第二部诗集——《不是去向是归途》。经历过时光交错和人生起伏后的萧然,带着一种抱朴守拙的超凡,他的诗歌尽可能多地删减了冗余的修辞和铺垫,只留下直击人心的锋刃,一如他的朋友在久别重逢时不约而同的发问:“当年萧然的那一袭飘飘长发哪里去了?”他从商业场的丛林法则中认识到了“一匹误陷兽夹的狼/是怎样咬断自己的腿”的残酷,却仍以最大的善意和悲悯,与这个时代达成和解,因为“猎人和猎物/都是一匹狼的生死之交”;而这也暴露了他无比虔诚的佛教信仰,他获得了“虚幻和真相/悬浮在云朵之上/彼此确认”的人生观,让一切复杂的虚像都回归简单的本质,从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另一方面,常年的羁旅生涯,让他的乡愁水涨船高,而他依然恪守节制,“使用修辞手法/省略掉战争,掌控好笔画的/宽度和深度,才能避免把木兰溪/写成黄河”;他爱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乡、妻儿和亲人,既不自大也不自卑,进而理解他人对故乡、妻儿和亲人的爱,理解乡愁、爱情和亲情背后隐藏着的苦难与悲怆,悟出了爱这个国家,就要“大声说出高山/说出大海,说出漠河,说出曾母暗沙/说出喜马拉雅真实的海拔”。在“萧然式归来”的影响下,王清铭、纪朝阳、柯友珊、方志忠、韩冰、郑朝阳、郭清锋、林寞、段裂、墨予、林养、李德辉、郑建华、程沧海、墨荷等一批诗人,也纷纷擦亮蒙尘的诗笔,掷出闪光的诗句。
三、诗运与诗学的归来
诚然,诗人和诗作是一个诗群的主体,而诗群的前进,则需要诗歌运动的助推;反观诗歌运动的背后,亦是诗人们个体担当和诗道精神的流露。在莆田文学界,几乎每个人都对云里风文学奖耳熟能详,在自1994年以来的漫长岁月中,莆籍华侨云里风先生以其充沛饱满的热情和报效桑梓的情怀,激励了一代代的青年才俊,其中不乏诗人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云里风文学奖在设置上的地域局限,使得它未能在全省范围形成更大的影响。
青年诗人张坚有感于此,决定做一些修订和补充。2008年,由他出资设立的首届“张坚诗歌奖”面向福建全省优秀诗人进行公开征稿,次年又进一步放开,改为面向全国。如今,“张坚诗歌奖”的评选工程已经进行到了第七届,影响力也在逐年攀升。在“拒绝平庸晦涩,评选实力诗人,力推新锐天才”的宗旨的引领下,“张坚诗歌奖”已发掘出多位诗坛新秀,其评委阵容更是涵盖了非马、古月、李少君、唐力、汤养宗、哈雷、陈先发、何小竹、曾宏、安琪等众多知名诗人。该奖项还曾先后三次分别在莆田市区、莆田西天尾镇和厦门曾厝〓举办盛大的颁奖仪式,每次都邀请了数十位各地诗人共同参与见证。特别是2009年春节的首届莆仙诗人联谊会,第一次提出了“莆阳诗群”的概念;此后不久,《诗歌月刊》2010年第2期上半月刊首度集结推出了莆田诗群作品展,标志着该诗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认。而张坚本人也长期坚持诗歌创作,曾出版有《有风或者无风》《水土不服》等诗集,借以安放漂泊在外的莆阳情结。
在诗歌创作呈现集体井喷的状态下,诗集的出版显得水到渠成。一本诗集是一位诗人最有效的名片,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外界对诗人印象的评判,而决定好坏标准的,不仅在于诗作的质量,也在于诗集在编排、校对、设计和印刷上的匠心独运。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林滨副社长,多年来以一位乡亲的情感,密切关注莆田诗群的成长,经他亲自操刀或协调出版的莆阳诗群诗集有孙绍振主编的《诗歌哈雷》、梁征的《木兰春涨》、郑重的《时间的羽翼》、萧然的《不是去向是归途》、王鸿的《尘世的抚摸》、黄披星的《不下雪的城市》、倪伟李的《纸上的硝烟》、年微漾的《一号楼》、陈上的《再造星辰》以及诗歌采风合集《映像莆阳》《诗韵涵江》等,在幕后为这一群体默默付出。
在诗歌氛围的共振下,出生于1987年的年轻诗人陈上,有了重启兰溪诗社的想法。学生时代,对外国文学的痴迷,成为他开启诗写道路的滥觞。他自比“初夏的朗诵者”,要在冰与火的围攻下守候诗歌的宗教;他的诗歌浑如印象派画作,带有一种意象的华彩,让人沉醉其间。他甚至擦掉了人们对于故乡习惯性的水墨式勾勒,改以一种更具冲击力的色调重新定义:“在这片海身上,时光重新开始流浪。/并且可以生长往事。/一片海只能埋没一次。/苏醒即是新生。”苏醒,也真的带来了新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莆田市作协副秘书长和《海峡诗人》杂志副主编,积极对外输送莆阳诗群的新鲜血液;不久后的兰溪诗社,也将在他的有力策划下,完成一次关于记忆和情感的时间穿越。
学者杨健民的方式则更为前卫,借着微信产品的东风,他提出了在微信朋友圈中进行同题诗歌写作的创意,并马上得到热烈响应。这种简便直接的沟通方式,让多数人重燃诗歌创作的激情,催生了不少优秀作品。诗人田荔琴在这种方式的诗写体验中,感悟到“生命的内存/比电脑宽厚”,说出了多数人共同的心声。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一个诗群的扎根若仅以一时的风气为依托,必然无法长久;它还需要诗歌美学的奠立和支撑,并以此为后来的写作提供经验和参考。莆阳诗群的诗作,有游历、有乡愁、有感悟、有纪实,题材上与其他地域的诗群并无太大差别,因此,从中提炼出一些独具一格的美学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担任《东南学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杨健民,是造诣很高的学者,更是莆阳诗群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观察者。在场是最好的解读。年轻时,杨健民先生以一部《艺术感觉论》,开创了美学领域的崭新课题;现在,对莆田诗人的专注,使得他总能发现他们身上的特立之处,并以此作为这部著述的进一步佐证。在《梁征与他的“寻找”》一文中,他一眼便敏锐地发现“梁征对于山水的抒情方式,已经从物象意义进入了一种透彻的参悟”;这种“禅思和妙悟”近乎一次次的“唤醒”,所有递呈表面的物象感官因此产生位移,更接近其“幽深的渊薮”。在陈上的诗歌面前,他毫不避讳地直言“在这个时候谈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当前多数诗人热衷于“挑战新的艺术偶像,撕裂了磨炼、推敲与精益求精的传统,这些反叛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然而,陈上“借用意象结构曲折地表现微妙的情绪结构”的表现手法,使他看到了其诗歌中安全、节制的珍贵品质,从而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并由衷发出“诗若安好,便是存在”的赞叹。推及萧然的创作,他则抛出了“诗歌的可能性意义区域”这一命题,认为“诗歌在所有写作中具有的可能性空间,就在于它是一切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是最具哲学意义的献给灵魂的礼物”;因此,“诗即是思”,是某种对于诗歌形式的解离后的“深度的理性”,只有保持这种理性,才会给读者以一直都想要“踩着”和“触碰着”的冲动。不难看出,杨健民先生对诗人的思考有着更高的期望,只有思考,一个诗人才能超越经验,在现实世界的背面规避引力和阻碍,获得真正的自由。
对于莆阳诗群,我好像说了不少,却好像还远远不够。对这个“归来的诗群”的重新定义,并非一次画地为牢式的自我狂欢,相反,这里的每个个体,其实又都是其他地域的原籍或在地诗人;而且,每位诗人的写作,也都是彼此独立的,正如诗人哈雷在年微漾诗集《一号楼》序言中所提及的:“所有的写作都是个人化的,诗歌更重要的是气质型写作。”只是,借助于身份认同,我们更容易因为某些共同属性而相互慰藉,更容易形成一股群体气质,从而走得更远。
借杨健民先生的话,就是:“诗若安好,便是存在!”
相关人物
年微漾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