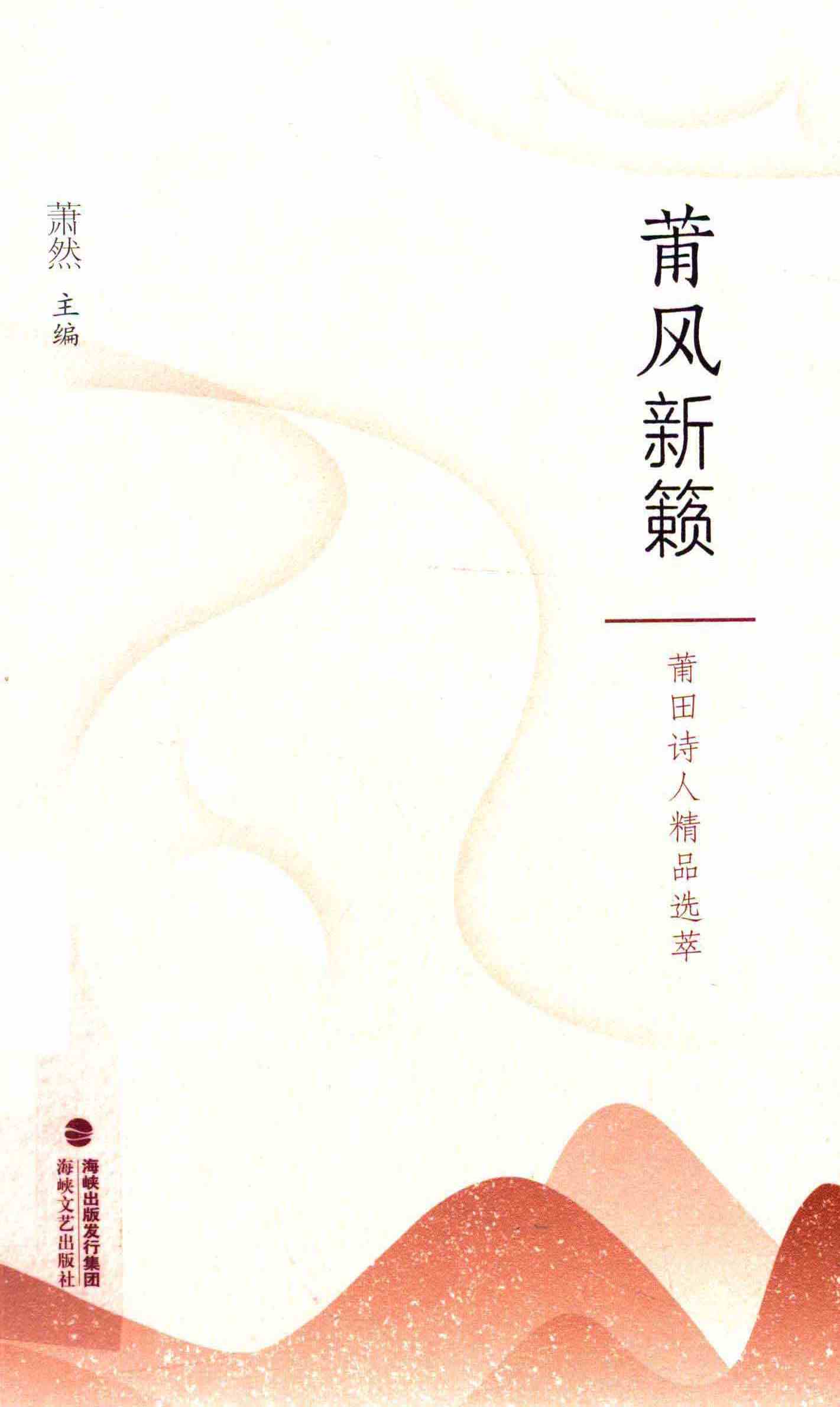内容
“兰溪”是一个故事,一个蕴涵着莆阳诗坛传奇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群在兰溪边上成长的青年,发起成立了“兰溪诗社”。那一天,我和谢冕、俞兆平、谢春池、朱谷忠等站在兰溪岸边,眯着眼望着他们。这是一场目光的伏击:正中、杨振辉、郭明理、朱金芳、罗西、萧然……一群被诗的荷尔蒙激荡得浑身勃发的年轻人,在兰溪边上吟诗,把诗歌一句一句地扔进兰溪,扔出一种浩大、一种活力。他们悠游在诗的丛林里,用语言冲击着语言,以想象碰撞着想象。记得谢冕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痛快至极!”
几年以后,“兰溪”突然沉寂了,一种凋谢的不朽穿越时空暌隔的深刻伦理,给后来者带来了认知的陌生。我一直在寻找“兰溪”,寻找那些诗人。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影响的焦虑由此而生。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批诗人躲在世纪的不同角落,以最匍匐的姿势,蕴蓄着最昂扬的力量。其实,没有人能够忘却“兰溪”,忘却那些诗人。我沿着岁月的纹路,一个一个地寻找并回溯。每一次悠远的回溯,都让我兴奋无比。因为他们依然属于诗,属于高远、属于深邃。正中找到了,多年的从政经历,面容刻上了时间的羽翼,望之若刚,忽焉若柔,诗变得沧桑而“思不群”;罗西找到了,他的华丽转身,诗的语词始终飘忽着,望之若色,忽焉若情;萧然找到了,从长发飘飘到光头党,望之若秋,忽焉若春,诗歌还是那么伟岸,“一个人的立春”还是那么悲壮……他们是“兰溪”留下的最初的坚守,正在母亲河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诗行。他们是兰溪诗歌的精虫,留下了兰溪诗歌的生命智慧和生命意志。
许多人都喜欢说“诗性智慧”四个字,其实,“兰溪”创设之初,倒不具有多大的“诗性智慧”,而在于它渗透着一种“诗性精神”。我一直以为,精神比智慧更具有量级。“诗性精神”是诗人的一粒春药,它的普遍意义就在于它交给诗人的,是对于人和物象的认知能力——知性,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力量和感慨,是一种击中精神内里的“为什么”与“何以可能”,是一种生命元素。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兰溪诗社”,是莆阳大地第一次出现的“诗的觉醒”,那么,今天由正中、萧然、陈上、年微漾、南夫、张坚、沧海、本少爷、石瞒芋、公子剑等重启“兰溪”,则是开创了莆阳的新的“魏晋风度”时代。重返“兰溪”,我们回到了一个“诗歌共同体”,回到了一个属于莆阳自身的“诗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自性、多样、共生。由此,我想起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什么是花?什么是雾?这些东西已经构成了“兰溪”的文学经验,也是莆阳诗歌的原动力和精神模板。时至今天,我的确无法为莆阳诗群概括出怎样具体的精神风格,因为它们既是自性的,又是多样的;既是多样的,又是共生的;这里面包含着诗歌自身的闪烁性和不确定性。
小说家阎连科说,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些感受黑暗的人。那么诗人呢?——我始终对这个问题带有深深的追问。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诗人能感受美好、温暖和明亮,也能感受不安、忧郁和焦虑。然而无论如何,诗歌是关注日常的。只有日常,才是诗的第一现场,才是我们的初心和底线。
“兰溪”有着过去的文本,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兰溪”还将开辟新的文本,这将是一个超越性的历史的开始。诗是不可言说的,它终究是一种“神意”、一种寄寓、一种拔出任何思维空间和想象的凛冽性和锐利感。读得懂也好,读不懂也罢,诗还是诗,它就在那里活着,在那里蹦哒着。
有人说,当代诗歌正趋于“碎片化”。碎片化没有什么不好。在某种理念甚至是空的理念之下,那些魔幻加上才气的诗的碎片化,可能一下子让人搞不懂什么是它真正要表达的意义,然而它很可能就是窥探诗的另一个内奥的窗户。我始终觉得,诗可以去追寻某些不完美的细节,它一旦被表达出来,就可能比那些完美的事物还要美丽。一位有才气的诗人,他可以在不完美中创造完美,可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可以在汹涌而至的孤寂乃至窒息中滑出庞大的语词之网,挣扎出诗性存在的充满质感的缝隙。很简单,这就如同哲学思想——它往往就产生在身边的一饮一啄之中。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已经出笼,人们对其中的获奖诗歌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诗歌终于归位,回归诗歌本体。一句话,诗能够让人读懂了。“读懂”是什么?“读懂”就是把诗歌交给读者,把诗人内在的欲望和精神力量,把那些生命的搏动和关于生存的意义交给读者。诗歌是个体意象的产物,也是诗人生命情感和生命智慧的产物。如果说当代诗歌正在被定位于一个新的起点或零的刻度,那么诗歌将重新在先验的文化原型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化符码。这个思考,是基于对当前的诗坛现象的一种审视。当今时代,诗人的大规模增殖已成古怪,那么多玄想的灵魂涌出,究竟是诗神的迷悟还是诗歌的颠覆?我想它不会是好事。诗坛熙熙攘攘,等着领受各种桂冠。这些“诗人”从公共生存文化主流中分离而出,类似于新新人类的一次令人咋舌的降临。另一个可怕的现象是,诗人的自大妄想症广泛蔓延,可以随意地把顾城、舒婷、北岛和海子推到另一个诗歌记忆库,甚至从此可以置之不理。某文化批评家尖锐地指出:“形形色色的理论宣言喷薄而出,宇宙的磁心、亚磁心以及子磁心可疑地存现,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自称是天体运动的领袖或先锋,孱弱的诗篇戴上强悍的形而上面具向邻人发出恫吓。”这同样不会是好事。我们并不排斥诗歌各种派别的产生,但是诗的各种“派”能否在诗坛鹤立,则完全取决于那些骄傲而可爱的诗的小鸟儿能否找到自己的羽翼,而不是以那种好斗的公牛般的架势徒增诗坛的混乱。我想,无论是宏大叙事、主体意象还是创造世界,无论是孤芳自赏、缓解焦虑还是自我疗伤,好的诗歌一定是出自生命情感、生命意志和生命智慧的灵魂孔道的。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即将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一个有8000人参加的世界级盛会讨论的竟然是“做人”这两个字,表明了何为人的问题与如何做人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共识。兰溪诗社的发起人之一萧然在“莆阳诗群”的微信群里说:“诗人其实应该拆成‘诗’和‘人’两个字,人是主语,诗只是标签,诗是由人的人格力量、思想的高度、情怀的广度和文化的深度决定,并非写一些分行排列装神弄鬼愤世嫉俗的文字就叫诗人。”我十分赞同这个见解,它可以视作兰溪诗歌的一个文化期待和审美期待。
“兰溪”依然游荡着20世纪的诗的精灵。到了21世纪,莆阳一批新的诗人应运而生,留下了一串长长的如同诗句的名单,他们活得有趣、诗写得有趣。有趣一定是诗的飘逸与豪迈,也是诗情的喷涌和律动!
祝愿“兰溪”重启,祝愿莆风有新籁!诗的兰溪无论奔流到海,还是半路拐弯,都是诗的存在。我必须重复我的一句话:诗若安好,便是存在。
2018年8月12日于福州
(杨健民,福建仙游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若干学术著作、散文随笔集。现居福州。)
几年以后,“兰溪”突然沉寂了,一种凋谢的不朽穿越时空暌隔的深刻伦理,给后来者带来了认知的陌生。我一直在寻找“兰溪”,寻找那些诗人。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影响的焦虑由此而生。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批诗人躲在世纪的不同角落,以最匍匐的姿势,蕴蓄着最昂扬的力量。其实,没有人能够忘却“兰溪”,忘却那些诗人。我沿着岁月的纹路,一个一个地寻找并回溯。每一次悠远的回溯,都让我兴奋无比。因为他们依然属于诗,属于高远、属于深邃。正中找到了,多年的从政经历,面容刻上了时间的羽翼,望之若刚,忽焉若柔,诗变得沧桑而“思不群”;罗西找到了,他的华丽转身,诗的语词始终飘忽着,望之若色,忽焉若情;萧然找到了,从长发飘飘到光头党,望之若秋,忽焉若春,诗歌还是那么伟岸,“一个人的立春”还是那么悲壮……他们是“兰溪”留下的最初的坚守,正在母亲河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诗行。他们是兰溪诗歌的精虫,留下了兰溪诗歌的生命智慧和生命意志。
许多人都喜欢说“诗性智慧”四个字,其实,“兰溪”创设之初,倒不具有多大的“诗性智慧”,而在于它渗透着一种“诗性精神”。我一直以为,精神比智慧更具有量级。“诗性精神”是诗人的一粒春药,它的普遍意义就在于它交给诗人的,是对于人和物象的认知能力——知性,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力量和感慨,是一种击中精神内里的“为什么”与“何以可能”,是一种生命元素。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兰溪诗社”,是莆阳大地第一次出现的“诗的觉醒”,那么,今天由正中、萧然、陈上、年微漾、南夫、张坚、沧海、本少爷、石瞒芋、公子剑等重启“兰溪”,则是开创了莆阳的新的“魏晋风度”时代。重返“兰溪”,我们回到了一个“诗歌共同体”,回到了一个属于莆阳自身的“诗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自性、多样、共生。由此,我想起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什么是花?什么是雾?这些东西已经构成了“兰溪”的文学经验,也是莆阳诗歌的原动力和精神模板。时至今天,我的确无法为莆阳诗群概括出怎样具体的精神风格,因为它们既是自性的,又是多样的;既是多样的,又是共生的;这里面包含着诗歌自身的闪烁性和不确定性。
小说家阎连科说,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些感受黑暗的人。那么诗人呢?——我始终对这个问题带有深深的追问。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诗人能感受美好、温暖和明亮,也能感受不安、忧郁和焦虑。然而无论如何,诗歌是关注日常的。只有日常,才是诗的第一现场,才是我们的初心和底线。
“兰溪”有着过去的文本,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兰溪”还将开辟新的文本,这将是一个超越性的历史的开始。诗是不可言说的,它终究是一种“神意”、一种寄寓、一种拔出任何思维空间和想象的凛冽性和锐利感。读得懂也好,读不懂也罢,诗还是诗,它就在那里活着,在那里蹦哒着。
有人说,当代诗歌正趋于“碎片化”。碎片化没有什么不好。在某种理念甚至是空的理念之下,那些魔幻加上才气的诗的碎片化,可能一下子让人搞不懂什么是它真正要表达的意义,然而它很可能就是窥探诗的另一个内奥的窗户。我始终觉得,诗可以去追寻某些不完美的细节,它一旦被表达出来,就可能比那些完美的事物还要美丽。一位有才气的诗人,他可以在不完美中创造完美,可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可以在汹涌而至的孤寂乃至窒息中滑出庞大的语词之网,挣扎出诗性存在的充满质感的缝隙。很简单,这就如同哲学思想——它往往就产生在身边的一饮一啄之中。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已经出笼,人们对其中的获奖诗歌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诗歌终于归位,回归诗歌本体。一句话,诗能够让人读懂了。“读懂”是什么?“读懂”就是把诗歌交给读者,把诗人内在的欲望和精神力量,把那些生命的搏动和关于生存的意义交给读者。诗歌是个体意象的产物,也是诗人生命情感和生命智慧的产物。如果说当代诗歌正在被定位于一个新的起点或零的刻度,那么诗歌将重新在先验的文化原型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化符码。这个思考,是基于对当前的诗坛现象的一种审视。当今时代,诗人的大规模增殖已成古怪,那么多玄想的灵魂涌出,究竟是诗神的迷悟还是诗歌的颠覆?我想它不会是好事。诗坛熙熙攘攘,等着领受各种桂冠。这些“诗人”从公共生存文化主流中分离而出,类似于新新人类的一次令人咋舌的降临。另一个可怕的现象是,诗人的自大妄想症广泛蔓延,可以随意地把顾城、舒婷、北岛和海子推到另一个诗歌记忆库,甚至从此可以置之不理。某文化批评家尖锐地指出:“形形色色的理论宣言喷薄而出,宇宙的磁心、亚磁心以及子磁心可疑地存现,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自称是天体运动的领袖或先锋,孱弱的诗篇戴上强悍的形而上面具向邻人发出恫吓。”这同样不会是好事。我们并不排斥诗歌各种派别的产生,但是诗的各种“派”能否在诗坛鹤立,则完全取决于那些骄傲而可爱的诗的小鸟儿能否找到自己的羽翼,而不是以那种好斗的公牛般的架势徒增诗坛的混乱。我想,无论是宏大叙事、主体意象还是创造世界,无论是孤芳自赏、缓解焦虑还是自我疗伤,好的诗歌一定是出自生命情感、生命意志和生命智慧的灵魂孔道的。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即将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一个有8000人参加的世界级盛会讨论的竟然是“做人”这两个字,表明了何为人的问题与如何做人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共识。兰溪诗社的发起人之一萧然在“莆阳诗群”的微信群里说:“诗人其实应该拆成‘诗’和‘人’两个字,人是主语,诗只是标签,诗是由人的人格力量、思想的高度、情怀的广度和文化的深度决定,并非写一些分行排列装神弄鬼愤世嫉俗的文字就叫诗人。”我十分赞同这个见解,它可以视作兰溪诗歌的一个文化期待和审美期待。
“兰溪”依然游荡着20世纪的诗的精灵。到了21世纪,莆阳一批新的诗人应运而生,留下了一串长长的如同诗句的名单,他们活得有趣、诗写得有趣。有趣一定是诗的飘逸与豪迈,也是诗情的喷涌和律动!
祝愿“兰溪”重启,祝愿莆风有新籁!诗的兰溪无论奔流到海,还是半路拐弯,都是诗的存在。我必须重复我的一句话:诗若安好,便是存在。
2018年8月12日于福州
(杨健民,福建仙游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若干学术著作、散文随笔集。现居福州。)
相关人物
杨建民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