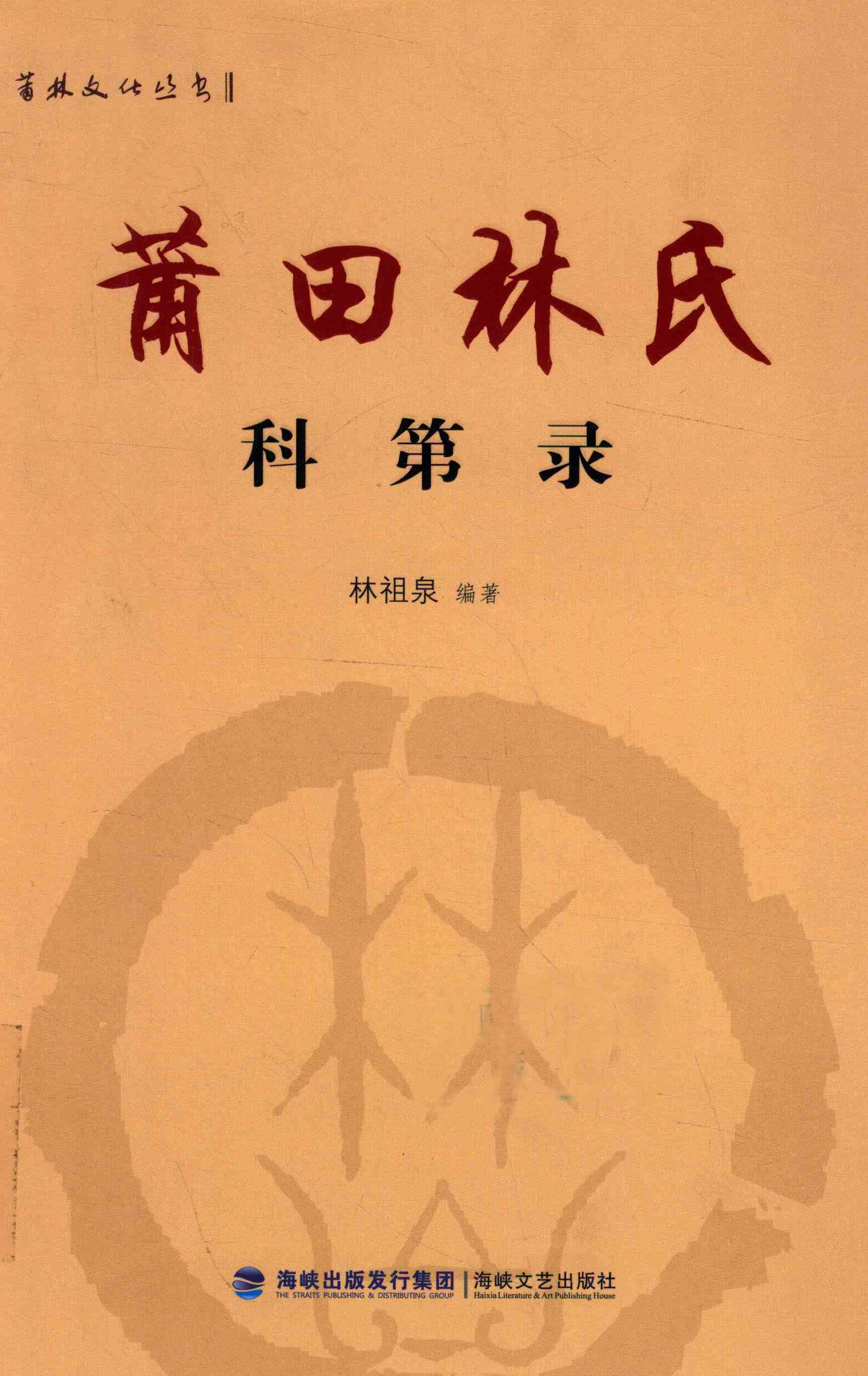内容
林姓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自商末周初繁衍发展,迄今3000多年,历100余代。中华林姓主体为子姓后裔,殷少师比干之后人。据唐代林宝《元和姓纂》中称: “林,殷太丁之子比干之后。比干为纣王所灭,其子坚逃难于长林之山,遂姓林氏。”武王伐纣,灭殷商而立周朝,以比干忠谏死,封其墓,赐其子坚姓林,命为三监,食采博陵。林坚即为林氏受姓始祖,比干则被奉为林氏太始祖。
有关文献记载,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宗室及衣冠望族相继徙居入闽。林禄奉敕守晋安郡,迁居晋安,为林姓开闽始祖。传四世林恪为入莆始祖。传九世林原次,生三子:林既、林茂、林诜。林既初居北螺村,因乱迁居莒溪(今属莆田市城厢区),后定居长城(今属莆田市荔城区),史称 “长城金紫林”。林茂曾孙林玄泰,唐永昌元年(689),举茂才,官任瀛州(今属河北)刺史。其子林万宠,唐开元八年(720),明经及第,官至饶阳(今属河北)太守,生三子:林韬、林披、林昌。林韬之孙林攒,唐德宗立双阙以旌表其孝,时号“阙下林家”;林披,唐天宝十一年(752),明经及第,官任检校太子詹事、苏州(今属江苏)别驾,赠睦州(今属浙江)刺史,由北螺迁居澄渚乌石(今属莆田市荔城区),生九子:林苇、林藻、林著、林荐、林晔、林蕴、林蒙、林迈、林蔇,皆官刺史,世称 “九牧林家 ”;林昌之子林萍,迁居仙游游洋,称之 “游洋林家 ”。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中部的莆田,史称“兴化”“兴安”,为八闽名郡。它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明《兴化府志》载,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分南安地置莆田县,属丰州(今福州),寻废,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析南安地置丰州(今泉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圣历二年(699),析莆田地置清源县,两县同属武荣州(今泉州)。不久,废武荣州,两县隶属泉州(今福州)。久视元年(700)复置武荣州,莆田、清源两县复属武荣州。景云二年(711)改武荣州为泉州,莆田、清源两县属泉州。天宝元年(742)改泉州为清源郡,清源县改名仙游县。乾元元年(758)改清源郡为泉州,莆田、仙游(统称“莆仙”)两县隶属泉州。五代保大七年(949)改泉州为清源军,莆田、仙游两县隶属清源军。
《兴化府志》又载:“兴化为郡(别称莆阳、莆中),建置自宋始。”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割据漳州、泉州(含莆田、仙游)地区近20年的仙游人陈洪进,因“纳土归宋”有功而官至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但在他统治期间,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游洋人林居裔领导的农民起义。林居裔“聚众数万人(号称十万)抗宋,自称西平王 ”,围攻泉州城,后被朝廷派官军镇压。
次年,宋太宗翻阅《泉福图志》,“念游洋洞地险,思欲以德化之”,下诏割永福(今永泰)、福唐(今福清)合游洋、百丈2镇计14个里,设兴化县,后置太平军,军治、县治均在游洋镇。太平兴国五年(980),从泉州析出莆田、仙游两县入太平军,改名兴化军,管辖兴化、莆田、仙游3个县,为“八闽”之一。后因游洋镇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太平兴国八年(983),福建转运使杨克让奏准朝廷把军治从游洋迁至莆田县城。宋末升兴化军为兴安州。元代改兴安州为兴化路。明代改兴化路为兴化府。正统十三年(1448)裁撤兴化县,乃辖莆、仙两县。清代沿用明制,仍名兴化府。
林姓是莆田的第二大姓,“莆田林”开创了林氏家族在我国东南沿海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中华林姓家族的最大支系。按照当今人口数量排序,林姓居全国第17位、福建的第2位。莆田素有“陈林半天下”之称,截至2016年底,林姓人口有近50万人。莆田林氏的4个分支,分别是“九牧林”“金紫林”“阙下林”和“游洋林”。“游洋林”在宋代一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迁往漳州等地。明末清初,“游洋林”后人随郑成功攻打台湾,又迁往台湾雾峰。因此,莆田林氏也是台湾雾峰林氏家族的先祖。
莆田林氏又是一个文化层次很高的官宦世家,家风鼎盛,人才辈出,延绵百世而不衰,真可谓“诗书簪缨之名门望族”。据史料统计,自唐代第一位进士林藻至清代末科进士张琴的1000多年间,莆田共涌现出文武进士(含诸科、特奏名等)近2400人、明经17人和举人2265人。其中,林姓文武进士(含诸科、特奏名等)就有308人,明经14人,举人458人,分别占莆田总数的13%、82%和20%,蔚为科举奇观,高居诸姓之首,故时人有 “无林不开榜”之语。“科举”一词,来源于“分科举人”,就是“分科目选举人才”,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名称。科举也叫开科取士,是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世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我国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元朝初期几十年的不曾开科,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不断更选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的影响,是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的。
从整体来看,隋朝以前莆田的教育还处在萌芽状态。郑露三兄弟倡学在南山的 “开莆来学”,不仅开创了莆田教育之先河,而且也代表了福建文教曙光的来临,莆田的人文教育活动在唐代逐步开展。《兴化府志》云:“唐世设科取士..其科之目十有二:曰秀才,曰明经,曰进士,曰俊士..当时秀才科最高,鲜有应者;士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唐贞元(785—805)之后,福建 “岁贡士与内州等”,一改过去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状况,及第者络绎不绝。
《中国科举史》载,唐代从武德五年(622)至天祐四年(907)285年间,共举行262科考试,录取进士6656人。据《福建教育史》的统计,唐代福建56位可考的进士中,莆仙籍就有11人,约占20%。其中,林氏进士1人(林藻),约占莆田总数的10%。而按《新唐书》所记载,当时莆仙两地的人口数仅占全省的11%。终唐一朝,莆田人在《新唐书》中立传的只有林攒、林蕴两位,均为林氏家族。又据《兴化府志》统计,唐代莆田有17人明经及第,林家子弟就占14人,为莆田总数的82%。
谁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这是以往有过不少误解和争议的问题。明代周华在《游洋志 ·人物》中记载: “金鲤,字伯龙,清源东里白鹤人,登武德二年庚辰进士第(按:武德三年才是庚辰年)。”为此,在莆田市的第一轮修志中,不少编写者都沿用 “金鲤是莆田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的说法。如新编《莆田县志》载 “金鲤,唐武德三年(620)进士”;新编《仙游县志》载 “金鲤,唐武德二年(619)进士 ”;新编《莆田市志》与新编《莆田县志》的记载也是一样的。还有《兴化进士》《莆田史话》《莆田市名人志》等邑人出版的书籍,均持同样的观点,以至于后来的一些文史研究者以讹传讹。
其实,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是唐贞元七年(791)及第的林藻,他也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二个进士。关于林藻进士及第之事,地方志书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宋《仙溪志》卷二 “进士题名”载: “唐重进士科,莆始于林藻、欧阳詹,仙游始于陈乘、杨在尧、陈光义。”这是林藻为莆田第一位进士的最早记载,而此书没有金鲤登第的任何信息。又如明《八闽通志》卷七十二 “人物”亦云: “林藻字纬乾,贞元七年(791)登进士第,郡人登第自(林)藻始。”也就是说莆田的第一位进士是林藻。
《八闽通志》是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的地方志,《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 “福建自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后,记舆地者不下数十家,唯明黄仲昭《八闽通志》颇称善本。”该《志》 “不仿效其他省志通例,在通志之上冠以正式省名的做法,在地方志中别具一格,后来王应山纂《闽大记》《闽都记》,何乔远纂《闽书》,也都袭用此法..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有的且是未见于其他志乘的,体例也比较齐整,为我省编纂各级地方志之所本”。同样,在明《闽大记》《闽书》等方志中均没有金鲤登第的记载。
从古籍文献记载看,唐武德四年(621)发布开科举士的敕令后,至武德五年(622)十月,诸州经过考试贡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交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考试,取中秀才1人、进士4人。该科进士头名为孙伏伽,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姓名可考的状元,与孙伏伽同进士的还有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等3人。因唐代科举始于武德五年,所以,金鲤根本不可能登武德二年(619)庚辰进士第。
宋代在中国科举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创立的殿试制度,使分级考试逐层选拔臻于完备。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不但为同时代的辽、金所仿效,而且为后来的元、明、清各朝所沿袭。同样,宋代的兴化军在莆田科举史上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有宋一代,莆地虽偏居福建东南沿海一隅,但科甲鼎盛,俊秀如林,成为无可争议的科考发达之地,成为名扬天下的 “文献之邦”。
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宋代从建隆元年(960)至咸淳十年(1274)314年间,共举行118科考试,录取进士97300人,其中正奏名进士42457人,诸科进士16366人,特奏者进士38477。又据《福建教育史》的记载,宋代福建籍进士有7144人(不含诸科、特奏名等),名列全国正奏名进士第一位。为此,《宋史》会将 “登科第者尤多”列为福建的重要特点。然只有3个县的兴化军正如《兴化府志》所载,就有进士1756人,其中正奏名进士1014人(占福建进士总数的14%),特奏者进士582人,诸科进士63人,其他科进士97人。而林氏进士有205人,其中正奏名进士125人,占莆田总数的12%;特奏名进士60人,占莆田总数的10%;诸科进士8人,占莆田总数的13%;其他科进士12人,占莆田总数的12%。
值得一提的是,在由唐至清朝的历科进士中,唯独宋代于正奏名进士之外,还有特奏名进士。何谓特奏名?《宋史 ·选举志》云: “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这就是说,所谓特奏名,就是凡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解试、省试,即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并赐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
特奏名的设立,使科举考试更具吸引力,它不仅意味着取士名额的增加与扩大,而且也使读书人应举的前程显得更加光明。然特奏名的两个主要条件是 “举数”和 “年甲 ”,而不是才学高下,所谓 “退者俟乎再来”,则为每一个科场失意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一般士子就不会轻易放弃举业铤而走险。
对此,南宋人王栐在《燕翼贻谋录》卷一 “进士特奏”中有如下一段精彩论述: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籍。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开宝三年(790),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三月庚午诏曰: ‘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泪没消磨其中,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 ”可见宋代统治者创立特奏名制度,主要是吸取了唐末王仙芝等人因进士不第而犯上作乱的教训,特意大量增加取士名额,使潦倒场屋、屡试不中的广大举人心存一线希望,通过陪同正式考生参加殿试(即 “附试”)的机会,博取功名,进入仕途,不致积愤造反。
据宋朝文献资料载,北宋前期,一般是曾经省试进士五举或六举、诸科七举或八举、年龄在50以上,特予奏名。北宋中期,一般是曾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年50以上,曾经省试进士五举年50、诸科六举年60以上,特予奏名。北宋后期,一般是 “进士五举、诸科六举曾经御试下,进士六举、诸科七举省试下,年50以上;进士七举、诸科八举曾经御试下,进士九举、诸科十举省试下,年40以上”,特许奏名。南宋时期,特奏名,就是凡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解试、省试,即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并赐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
特奏名的设立,使科举考试更具吸引力,它不仅意味着取士名额的增加与扩大,而且也使读书人应举的前程显得更加光明。然特奏名的两个主要条件是 “举数”和 “年甲 ”,而不是才学高下,所谓 “退者俟乎再来”,则为每一个科场失意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一般士子就不会轻易放弃举业铤而走险。
对此,南宋人王栐在《燕翼贻谋录》卷一 “进士特奏”中有如下一段精彩论述: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籍。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开宝三年(790),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三月庚午诏曰: ‘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泪没消磨其中,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 ”可见宋代统治者创立特奏名制度,主要是吸取了唐末王仙芝等人因进士不第而犯上作乱的教训,特意大量增加取士名额,使潦倒场屋、屡试不中的广大举人心存一线希望,通过陪同正式考生参加殿试(即 “附试”)的机会,博取功名,进入仕途,不致积愤造反。
据宋朝文献资料载,北宋前期,一般是曾经省试进士五举或六举、诸科七举或八举、年龄在50以上,特予奏名。北宋中期,一般是曾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年50以上,曾经省试进士五举年50、诸科六举年60以上,特予奏名。北宋后期,一般是 “进士五举、诸科六举曾经御试下,进士六举、诸科七举省试下,年50以上;进士七举、诸科八举曾经御试下,进士九举、诸科十举省试下,年40以上”,特许奏名。南宋时期,“进士六举曾经御试、八举曾经省试,并年40以上;进士四举曾经御试、五举曾经省试,并年50以上 ”,特许奏名。总之,北宋后期较严,而南宋时期稍宽。
凡特奏名者,不论殿试成绩如何,均赐予一定的出身或官衔。在太祖、太宗朝,尚未分等第,均赐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一般分为三等,赐本科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诸州长史、文学、助教。英、神、哲、徽四朝,一般分为五等,第一等赐同本科出身、假承务郎(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学,第四等下州文学,第五等诸州助教。南宋时,仍分为五等,一般第一等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二、三名赐同学究出身,第一等第四名以下赐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将仕郎),第三、四、五等与英、神、哲、徽朝的三、四、五等相同。
作为笼络士子的一种手段,特奏名办法出台后,在维持宋朝境内安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然而特奏名入仕者任官比正奏名进士低,多数是授州府官学助教一职,这虽有促进官办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但特奏名制度也使科举的选贤任能功能变为选贤任能与养士抚庸相辅并行了。如两宋贡举共取士97300人,其中特奏名者即达38477人,约占40%。据《兴化府志》的统计,从宋元丰五年(1082)黄裳榜起至咸淳十年(1274)王龙泽榜止,192年间莆田特奏名进士共计582人;而从宋建隆元年(960)杨砺榜起至咸淳十年(1274)王龙泽榜止,314年间莆田正奏名进士只有1014人。由此可见,宋代莆田特奏名进士之多。
综上所述,宋代莆田只有特奏名进士,而没有特奏名状元。遗憾的是,近年来邑人出版的《宋代莆阳名人志》《莆田史话》《莆田市名人志》等书籍,却提出了 “莆田有特奏名状元8人”的新说法。其实,这个所谓特奏名状元,就是特奏名 “第一人”。如林洵美,绍兴十五年(1145)特奏名“第一人”,特赐同进士出身,任潮阳(今属广东)知县。众所周知,“状元及第”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由唐至清朝,唯进士科第一才能称 “状元 ”,才能称 “大魁天下”,其他各科第一,均无 “状元”之名。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中只标明进士科第一人为状元,明经或制科第一均不称状元。进士第一始称状元,唐代如此,宋代亦然。本文特此指出,以正视听。
此外,莆田林氏还涌现出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 “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等奇特现象。更有意思的是,兴化军有20对兄弟双双同科及第,其中林氏家族就有2对,即林宋臣、林宋弼(1132年)和林岳、林准(1160年),占总数的10%;甚至还出现林汝大、林栋(1271年)父子同科及第的现象,的确实属罕见。
纵观宋代莆田科举之盛,究其原因有五:一是朝廷以文治国,重视科举取士是莆田科举鼎盛的政治背景。赵宋自立国后,实行以人文为主体的治国方略。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文治。尤其是宋太宗做了皇帝之后,迅速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可以说,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宋朝廷不仅扩大录取名额,而且还通过改革科举考试方式,使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乃至上层农民的子弟,都可以不受家庭地位的影响,在考场上凭学识取得官位。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莆田大量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数亦文亦仕,既参与国家管理,又著书立说。当然,莆田林氏进士也不例外。
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而立传的林氏进士有5名,占莆田总数的21%。在莆田出仕官员中,官至六部尚书(正部长级)者13名,林氏家族就有2名,即林大鼐、林英,占总数的15%;官至六部侍郎(副部长级)者15名,林氏家族也占了2席,即林光朝、林彬之,占总数的13%据不完全统计,仅林氏进士著书立说的就有林璃的《太玄经注》十卷、《太玄经释文》一卷、《唐书纯粹》一百卷;林英的《晦庵童训》一册;林伸的《东轩文集》十卷、《春秋三传正经》;林豫的《笔锋草录》二十卷、《杂说》十卷、《杂文》十卷;林冲之的《木雁居士集》;林震的《林震集句诗》七卷、《林震文集》一百卷、《礼问》三十卷、《易传》十卷、《易数》三十卷、《易问》五卷、《经语千字文》一卷;林宋卿的《道山诗庄》《涪陵集》《湖北事宜》《督府集议》;林大鼐的《铁砚文集;◆林枅的《林枅诗文集》二十卷;林一鹗的《民谣集》;林虙的《诗解补缺》《礼经总括》《释奠解》《西汉发微》《元丰圣训》二十卷、《西汉诏令》十二卷;林光朝的《艾轩集》十卷;林榕的《四明居士诗》五卷;林井的《捐躯录》《平燕十略》;林磻的《典故钩玄》六十卷;林彬之的《囿山集》《海溪善政编》;林成季的《艾轩家传》一卷;林自的《周易解》《庄子解》《林自诗文集》十卷;林彖的《萍斋诗集》;林光世的《水村易镜》《景定嘉言》二卷等。
二是宋代大量人口南迁,福建经济的发展为莆田科举鼎盛奠定了物质基础。两宋是福建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时期,首先得益于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大量人口的南迁,使福建路、兴化军受益。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兴化的农业、手工业和海运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特别是木兰陂的建成不仅抵御洪水和海潮的灾害,保障农田灌溉,扩大耕地面积,而且使兴化平原的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木兰陂是当时福建规模最大,乃至在全国也算得上十分宏伟的水利工程,它的修成跟林氏家族也有关系。
三是宋代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莆田科举鼎盛的形成构建浓厚的文化氛围。宋室南渡后,整个文化中心向南方转移,在北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身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这些人到来后备受重用,自然形成了崇儒重文的社会风尚。尤其是宋代莆田的藏书家多、藏书量丰富,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如进士林伸,好聚书,官俸所入多用于买书,所蓄数千卷。有人见其如此便说: “你为何不替子孙考虑,却将钱都去买书? ”林伸答道: “吾蓄书数千卷,苟有贤子孙,足矣;不贤,多财适为累耳! ”又如进士林霆,博学而深研象数,与邑人郑樵为金石之交,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 “吾为汝曹(你们)获(留)良产矣。”因此,许多莆田士人捐金帛购书籍唯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也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藏书,才使得莆田文人辈出,著述如林,名作迭起。
四是地方吏民重教兴学是莆田科举鼎盛最重要的因素。北宋在经历范仲淹的 “庆历兴学”(1041—1048),王安石的 “熙宁、元丰兴学”(1071—1078)和蔡京的 “崇宁兴学”(1102—1106)等三次兴学运动后,基本上确立州(府、军)、县二级官办教育体系。但兴化军早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就已经形成军学和县学的二级教育网络,这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官办学校 “制度宏伟、雄冠一时 ”,出现 “学宫壮伟甲于闽郡”的动人局面。办学高峰时期,军学校舍 “凡四百八十间 ”,参加兴化军贡试的学子多达近7000人,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这与当时各地官学屡兴屡废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官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文化教育中心。
但对 “儒风特盛”的兴化军来说,这只是一方面,而更广泛、深厚的科举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的私学教育中。宋代莆田的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据方志记载,兴化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就达30所之多。仅林氏家族就有5所,占莆田总数的17%。
如林光朝在黄石东井(今属莆田市荔城区)创办 “红泉义学”,又称 “东井书堂 ”,正如邑人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所说:“初艾轩(光朝)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代邑人探花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林)蕴、(林)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除此之外,林光朝还与其族人林充、林褒在谷城山的松隐岩、国清塘旁的濯缨亭和五侯山之西的涌泉岩等地,创办草堂,传道讲学;林安中在西天尾澄渚村(今属莆田市荔城区)创办澄渚梯云斋,“将以教一族之英俊,来四方之明彦 ”;林彖在龙华寺(今属仙游县龙华镇),创办龙华书堂。同时,林氏家族还涌现出如林迪、林光朝、林立之、林彖等一批教育名家。
五是地狭人稠、以儒为业也是莆田科举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北方大量人口的南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由于移民的急剧增加,人地矛盾在兴化军尤为突出。正如郑樵在《通志》中所言: “吾莆地狭人贫,惟以读书为业。”对于莆田存在人口过剩的现象,林光朝在《艾轩集》中记叙当时的情景: “莆之郡二百年,虽以州名,其实一县也,原轸如绳,廛里如栉,十室五六,无田可耕。”然而,在 “地狭人稠,为生艰难”的情况下,聪明的莆田人却另拓谋生之路,诸如从事技艺、经商、出家以及向海外移民等,其中也包括不少人以读书为业,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希望一朝金榜题名,摆脱这种困境。莆田人的古训 “家贫子读书 ”,就是当时最真实生动的写照。
终宋一世,莆田林氏进士在清廉为官、学术造诣、家风传承等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
例如,名留史册的清官兄弟林孝渊和林孝泽。《兴化府志》载,林孝渊担任泉州通判兼泉州提举市舶司时,有一天,负责查验货物的官吏,按照惯例拿回来一盒龙脑(香料)。林孝渊知道后,命令收归官库。的确,按惯例市舶司的官吏可以收纳一匣的龙脑,并不犯法。但他清廉自守,认为官物属于国家,而私物则是商人货物。这种所谓惯例必须取缔,于是下令归还 “舶库”。
《九日山志》也载,林孝渊曾登泉州九日山并留下两块摩崖石刻,其一: “长乐林述中,陈大年,莆阳林全一(孝渊),嘉禾(厦门)鲁巨山同登姜相峰,过此徘徊久之,丙午(1126)十月十一。”其二: “靖康改元初冬,提举常平等事林遹述中,循按泉南。同提举市舶鲁詹巨山,太守陈元老大年,通判林孝渊全一,会食延福寺。遍览名胜,登山绝顶,极目遐旷,俛仰陈迹,徘徊久之。”这是靖康元年(1126),几位同僚到延福寺聚餐后登游九日山的记游石刻。同是这几个人,两块摩崖石刻却如此分开刻字,似为表示公私分明之意。由于前段系私事游览,姓氏前没有加上官衔;而后段为同僚公事聚会,故姓氏前加上官衔。
无独有偶,这种清廉之风在弟弟林孝泽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兴化府志》记载,他担任广东提举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事务。有个外国商妇蒲氏,其儿子所贩卖的货物,因违反朝廷的贸易法而被扣押。
于是拿着海外奇异珍宝贿赂宫官,为儿子求情,企图打破朝廷的有关禁令,并得到了皇帝侍从的帮助。林孝泽说: “过去三佛斋国(印尼苏门答腊古国)因不按规定时间前来请求进贡,清明的君主尚且谢绝,并遣送使臣回国。如今因一位商妇,要使朝廷废弃已实行二百年的往来贸易法,怎么可以呢? ”于是向朝廷上书力争,坚持不予放行。
后来,他以左朝请郎知漳州。一日傍晚,林孝泽视事完毕回住所,属吏拿着火烛送到室内,他却说: “这是官府使用的火烛,怎么可以用在私室? ”急命拿走。《八闽通志》称赞道: “(他)清介特甚,至不用官烛于私室。”再如,承前启后的理学名家林光朝。他少时聪明好学,拜邑人大学问家林霆为师。然而科举仕途之路却并不顺利,先后两次入京参加礼部会试,均落榜不第。但他并不气馁,离京返乡途中,便在浙江钱塘、吴兴一带从师求学,“过吴中,从陆子正游而得洛学(理学) ”。他研读程学,“学通六经,旁贯百氏 ”。
沿及南宋,讲学之风日盛。林光朝在长达20多年的传道授业中,继承程子之学,在闽中一带传播,盛名天下,桃李遍地。他所创立的学术思想即为其弟子所承传,并形成颇具阵容的红泉学派,自成理学于一家。
《闽书》载,红泉学派的门徒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其(林光朝)后,纲山林公亦之,乐轩陈公藻,先后起而继之。乐轩(林亦之),家长乐;纲山(陈藻),居福清,岁来讲学东井,风声所被,气习所薰,人皆有邹鲁之风 ”。《莆阳比事》也载,林光朝学生刘夙、刘朔于绍兴年间(1131—1162)相继登进士第后,在浙江衢州和温州一带任职和教授。还有不少弟子在各地创书院。传播理学,如弟子洪天赐、刘克刚等,他们在授学宗旨上亦继承了艾轩(林光朝)的思想,在学术论坛上大显身手,有的寻其源,有的扬起波,各有千秋。
林光朝是一个对宋代理学的形成、传播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尤其是宋朝南渡后,对东南半壁理学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红泉学派兴起于二程、朱陆之间,在传播洛学上,承前启后。
宋初尊崇儒学,重视孔孟之道。至宋仁宗继位,遂推行义理之学,胡瑗、孙复、石介开其先河,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至宋神宗年间(1068—1085),又有周的门徒程颢、程颐等,一传再传,蔚成理学一大学派。正如清人蒋垣所说: “濂溪周子敦颐,继孔孟绝学于仁宗间,以《太极图》《通书》授程伯子颢、叔子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季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惇、杨时成德尤著。杨时闽之将乐人..杨时归闽,受业者多,东南推其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弘传之张栻,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表现在政治上,学派中又各有门户,造成朝廷中党派纷争。程氏兄弟的“洛学”派在受到三次沉重打击之后,只好兵分三路,进入闽、浙、赣,潜移民间。于是,洛学在南渡前后形成中辍局面。另一方面,时人称为 “国之大儒”的朱熹尚未兴起,当林光朝倡道讲学于红泉之际,朱熹还处在孩提时代。当朱熹正式师事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门下专心于儒学时,林光朝已登隆兴进士第。
同时,从二程洛学入闽线索看,一是洛学道南系的先河杨时、游酢。杨时一传罗从彦,二传李侗,三传朱熹;游则无门人。二是程学传至胡安国,国传其子胡寅、胡宁、胡宏,并传侄子胡宪。三是通过程门高弟伊焞、王苹传给陆子正,再传给林光朝。“和靖高弟如吕、如王、如祁,皆无门人可见,监官陆氏(子正)独能传入艾轩,于是红泉东井学派兴焉”。上述前两条线的程门高弟皆是闽北人,属当地的建宁府、延平府。他们传播洛学的地域都在闽北,使闽北成为福建学术的一大中心,闽文化的大本营。
但是,从这些闽学之先的年表看,他们均卒于北宋或南宋初,唯有闽中这一线路,传承程学正宗的林光朝,正处中年时期。因此,红泉学派为南宋理学的勃兴无疑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恰如《黄四如集序》中所言: “濂洛中微,考亭未兴,艾轩林公光朝,倡道莆阳,从如归市,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宋史》亦载: “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林)光朝始。”邑人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也赞扬道: “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可以肯定,林光朝的理学思想对青年时期的朱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建立的一个封建朝代,不但实现了辽、西夏和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完全入主中原的愿望,而且建立了疆土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但蒙古民族“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个性并未完全改变,因而对科举取士制度最初并不在意,统治阶级和士人社会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也存在极大的分歧。经过许多儒臣的竭力倡议,才在元皇庆二年(1313)建立了科举制度,此时距1279年元世祖攻灭南宋已经有34年之久,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中断时间是最长的。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一些蒙古和色目贵族还是力图加以罢止,采行科举取士制度之争并未结束,其中元统三年(1335)的科举停罢之争是最为激烈的一次,以致出现1336年和1339年的两次停罢。
由于元军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汉人尤其是福建人民大开杀戒,沿途尸横遍野,生灵涂炭,文化教育设施也多数遭到摧毁和破坏,致使福建尤其是莆田的科举式微,进入一个中落时期,读书为官者寥寥无几。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元代从延祐二年(1315)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51年间(其中缺少2科,即1336年和1339年),举行16科考试(每3年开一科),共录取进士1139人。又据《八闽通志》和《兴化府志》的记载,元代福建进士有36人,其中兴化籍7人,约占福建总数的20%;而林氏进士2人,约占莆田总数的29%。元代福建举人有70人,其中兴化籍9人,约占福建总数的13%;而林氏举人2人,占莆田总数的22%。
林济孙、林亨是不是元代的状元?这也是一直在莆田有过争议的一个问题。清乾隆《仙游县志》载: “至元六年(1340)林济孙榜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升侍讲。”又载: “至正三年(1343)林亨榜进士第一,官至朝奉大夫。”清同治《福建通志》和民国《福建通志》均有相同的记载。为此,在莆田市的第一轮修志中,不少编写者都沿用 “林济孙、林亨是元代状元”的说法,如新编《仙游县志》和新编《莆田市志》。还有《莆田文化丛书 ·文化概谈》《兴化进士》《莆田史话》《莆田市名人志》等邑人出版的书籍,也持这一观点,以至于误导了不少读者。
其实,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从史志记载来看,不仅《元史》没有记载 “林济孙、林亨是元代状元”的史实,而且《八闽通志》《闽书》《闽大记》《兴化府志》等明代志书也均未记载此事;从登第时间上来看,元代共举行16科考试(停罢的是1336年和1339年),接下去的是1342年才对。而林济孙、林亨中状元的时间却是至元六年(1340)和至正三年(1343),这两年恰恰没有开科。众所周知,元代科举分为右榜和左榜,右榜状元必须是蒙古和色目人,左榜状元才是汉人和南人。因此,每次开科会出现 “一科两状元”的特殊情况。况且,左榜状元16人有名有姓,有籍可查,没有一个是福建人。所以,经过考证确认,林济孙、林亨既不是元代进士,更不是元代状元。清乾隆《仙游县志》、清同治《福建通志》和民国《福建通志》等志书关于 “林济孙、林亨是元代状元”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
星移斗转,朝代更替。到了明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以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之唐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统治者求贤若渴,除了下诏招贤,还于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令各行省连试三年。由于朝廷刚刚建立,缺少官吏,因此乡试中式的举人都免除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拔为官。以上政策、措施,极大鼓舞了士人的读书求取功名之心,而扩招必然增加应试名额,增加了中举的可能性。最高统治者还将各地科举的兴盛程度作为考核官吏的一大手段,鞭策了在任官吏重视当地的教育,而无视教育或劝教不善者,则坚决给予惩罚。终明一代,莆田历任地方官多能以身作则,倡学乡里。对于学校缺乏办学经费,官吏或慷慨解囊,或拨寺产补给学田,或出库银以赡生徒。随着兴化经济的日益繁荣,在传统的重教兴学的社会氛围熏陶下,莆田又重现了科举强区、人才辈出的盛况,进入再一个昌盛时期。
按《中国状元大典》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272年间,共举行91科考试,录取进士24636人。又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明代福建进士有2395人,其中兴化籍535人,占福建总数的22%,而林氏进士89人,约占莆田总数的17%;明代福建状元有11人,其中兴化籍2人,占福建总数的18%,而林氏状元1人(林环),占莆田总数的50%;明代福建探花有10人,其中兴化籍4人,占福建总数的40%,而林氏探花1人(林文),占莆田总数的25%。
关于明代莆田状元,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传说。清末邑人进士张琴编的《莆田县志》说:明永乐四年(1406)丙戌科莆田人林环殿试第一,但同科进士、林环同乡陈实却恃才不服,扬言考官录取不公。明成祖召而诘问,陈实答言: “臣百问百答,从无纰漏,缘何不取? ”皇上怒其不恭,欲制其狂气,乃命大学士解缙出题云: “孔门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云台二十八将,将将何功? ”成祖亲临考问,陈实一一对答不误,文采亦佳。但林环更是应对如流,毫无遗漏。因二人不分上下,皇帝乃加罪陈实,充军三边。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兴化府人才济济。同时,林环也以无可争辩的才华得到明成祖的青睐,他的确是莆田林氏杰出人才的代表,史家评他: “负材学,晓世务,特为文庙所器,一时儒硕亦厚望之。”如果说明代会试是全国各省举人之间文化水准的大较量的话,那么乡试则是省内各府县秀才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智力的大竞赛。明代乡试已固定成为省级地方考试层级,举人出身即可授予官职,因此竞争十分激烈,乡试中举也比前代更为荣耀风光。由于想要参加乡试的生员(秀才)太多,为了控制参试人数,明代曾规定每举1名,只允许30名科举生员参加乡试。限于录取比例太低,中举的机会是相当少的,中举率大约在4%,故俗有 “金举人,银进士 ”之谣。
正是从竞争的激烈程度来看,举人比进士还更难能可贵,才会有 “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据《福建教育史》统计,明代福建举人有8325人,其中兴化籍1692人,占福建总数的20%,而林氏举人312人,占莆田总数的18%;明代福建乡试解元有90人,其中兴化籍30人,占福建总数的33%,而林氏解元4人(林时望、林同、林文俊、林东海),占莆田总数的13%。因为莆田在福建乡试中,中举人数多次占全省的近一半,故有 “一邑半榜 ”之誉。
有明一代,莆田不仅科甲鼎盛,侔于中州,而且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从政者重臣高官选出,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等奇特现象。莆田人在《明史》中立传的有4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36名,而立传的林氏进士有6名,占莆田总数的17%。在莆田出仕官员中,四品(知府)以上的官员多达300多人。
而任明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俊、林云同、林尧俞、林兰友,占莆田总数的27%;任明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侍郎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富、林文俊、林铭鼎、林佳鼎,占莆田总数的27%;任都察院的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的有15人,其中林氏7人,即林元甫、林茂达、林有孚、林大辂、林润、林贽、林一柱,占莆田总数的47%。任左右布政使的有27人,其中林氏5人,即林豫、林应标、林烶章、林澄源、林恭章,占莆田总数的19%;任正副按察使的有34人,其中林氏8人,即林坦、林时、林长繁、林民悦、林铭几、林有年、林斌、林烇章,占莆田总数的24%。上述一人多历数职,这里只列其较高的一职,且无法将四品以上林氏官员的名字一一列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十年(1531)莆田知县王钜建县衙,把衙门外南端 “善俗坊”改为 “文献名邦”,后遭倭寇烧毁。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县徐执策重建县衙,并在县巷南北两端分别建竖 “海滨邹鲁”和 “莆阳文献”两个木坊。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孙继有又将这两坊改名为 “文献名邦”和 “壶兰雄邑 ”。从此,莆田正式誉称为 “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所谓 “文献名邦 ”,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解说: “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指历史典籍和贤能人才辈出的著名乡邦(地方)。
而 “海滨邹鲁”,其中 “邹”是指孟子的家乡,“鲁”是指孔子的家乡,两者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邦国之一。莆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虽为小邑,但儒风特盛,无论是从教育发达、科名鼎盛来看,还是从文化氛围、学术成就来说,把 “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这两顶桂冠戴之莆阳,都不为过。因为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公论,如宋真宗敕书所说 “闽越之地,邹鲁之儒”,宋度宗盛赞 “莆,文献之邦也”,宋邑人黄灏讲 “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邑人状元黄公度在《兴化军学记》中所载 “习俗好尚,实有东周齐鲁遗风”等等。所以,明代兴化成为 “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千百年间重视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对此盛事,清乾隆《莆田县志 ·人物志》序言中写道: “莆僻处海滨,齐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故欤?盖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确实,“文献名邦 ” “海滨邹鲁”的深刻内涵,远远不止于科甲之盛,人才之众,更重要的还在于兴化人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就以著述来说,仅明一代,就有著作900多部,现存120多部。
据不完全统计,仅林氏进士、举人撰写的书籍就有林洪的《竹庵存稿》十卷;林环的《■斋集》十卷;林文的《澹轩集》五十卷;林诚的《奏疏》五卷;林俊的《西征集》《见素文集》二十八卷;林茂达的《翠庭集》;林塾的《石泉集》《拾遗书》;林富的《省吾遗集》《奏议》二卷、《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林文俊的《内黄县志》《方斋存稿》十卷;林达的《自考集》《编年纪略》;林大辂的《愧瘖集》;林樯的《诗集》二卷;林应骢的《梦槎奇游集》二卷;林云同的《读书园集》《退斋文集》《韶州府志》;林东海的《四书经集解》,林华的《岳麓口义》十卷;林万潮的《赣州集》;林应箕的《百一诗稿》;林兆金的《东山樵稿》;林润的《愿治疏稿》;林澄源的《悟往吟》《经传讲义》《古易论》;林兆珂的《批点左传》《楚辞》《参同契》《毛诗多识编》七卷、《考工记述注》二卷、《撞弓述注》二卷、《宙合编》八卷、《李诗钞述注》十六卷、《杜诗钞述注》十六卷和《衡州府志》十五卷;林尧俞的《溪堂集》四卷、《万历兴化府志》;林恭章的《静宇逸稿》;林铭鼎的《新锓林会魁》《书经逢源集注》六卷;林铭几的《南窗遗稿》;林兰友的《迷迷草》;林嵋的《蟛蜞集》十二卷;林士敏的《芹边集》《匡庐小稿》;林喦的《万竹居士集》;林长懋的《竹庄集》;林勤的《朴庵集》六卷;林同的《大学中庸训说》《书经讲义》;林智的《蛙鸣集》;林宪的《鸥沙集》十卷;林大猷的《思轩稿》;林有年的《寒谷集》《东山诸集》《东莞县志》《瑞金县志》《武义县志》《安溪县志》《仙游县志》《福清县志》;林墰的《西麓稿》;林汝永的《南崧集》;林应采的《东皋吟稿》;林炳章的《宠荣堂稿》;林兆箕的《学适堂集》;林烇章的《伊蒿稿》;林錝的《石莲集》;林宪曾的《西源集》;林谐的《觉未轩集》;林齐圣的《闲有堂集》;林尊宾的《雁圉集》四卷;林说的《寸草堂集》等。
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1522—1566),日本倭寇的侵扰打破了莆田人民安宁祥和的生活,战乱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邑人关佛心在《莆田倭祸记》序言中这样写道:“莆田立县千三百年,最大之兵祸,厥惟明代之倭寇。”倭患在生命、财产上侵扰莆田人民,还毁坏学校、公祠,破坏读书人赖以生存与读书的社会环境及物质条件。
《莆田倭祸记》在《屠城记》一章中又描述道: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城陷..被焚毁之衙署、祠院庐一览:莆田儒学、兴化儒学..黄仲昭祠、林苇祠..士绅之遭难者:甲科以上十七人,乙榜数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倭患造成兴化府科举日益萎靡,据清乾隆《莆田县志》统计,嘉靖二十二年(1543)乡举中莆田中举33人,二十五(1546)年为27人,二十八年(1549)为20人,三十一年(1552)为21人,三十四年(1555)为22人,三十七年(1558)降至19人,四十年(1561)和四十三年(1564)仅剩15人。进士名额到嘉靖末年,每榜也只有2至3人。莆田的科举事业跌到了底谷。
清朝的科举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朝廷加强思想控制和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种重要手段。“四书五经”照样是科举取士的准则和学校教学的依据。人们的思想被死死地控制在理学的囹圄之中,应试文章只能用僵死的八股文 “代圣贤立言 ”,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梁启超痛斥说,“民之愚,国之弱 ”,皆有八股取士造成。由于明中后期倭寇“屠城”和明末战乱对莆田经济、教育巨大破坏等一系列原因,清代莆田的科举已是 “强弩之末 ”。莆田士人热衷科举、想进朝廷为官者不多,越来越少。
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258年间,共举行112科考试,录取进士26888人。又据《福建教育史》的记载,清代福建进士有1421人,其中兴化府64人,约占福建总数的5%左右,而林氏进士9人,约占莆田总数的14%;清代福建举人有10391人,其中兴化籍564人,占福建总数的5%;而林氏举人143人,占莆田总数的25%。1905年5月,清朝廷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也出于改变教育落后的状况,无可奈何发布诏谕,“从丙午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至此延续13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科举停罢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1905年废科举,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尤其在清末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科举停罢不仅对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震撼,而且在世界上的反响也相当强烈。美国学者威尔 ·杜兰说: “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和官制改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 “学而优则仕”的考试选人办法,虽有其局限性,但肯定比 “学而劣则仕”或者 “不学而仕”好,这或许就是科举制度存在1000多年的最大合理性。人们因而得出结论:科举是十分适合中国古代国情的一种制度。
有关文献记载,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宗室及衣冠望族相继徙居入闽。林禄奉敕守晋安郡,迁居晋安,为林姓开闽始祖。传四世林恪为入莆始祖。传九世林原次,生三子:林既、林茂、林诜。林既初居北螺村,因乱迁居莒溪(今属莆田市城厢区),后定居长城(今属莆田市荔城区),史称 “长城金紫林”。林茂曾孙林玄泰,唐永昌元年(689),举茂才,官任瀛州(今属河北)刺史。其子林万宠,唐开元八年(720),明经及第,官至饶阳(今属河北)太守,生三子:林韬、林披、林昌。林韬之孙林攒,唐德宗立双阙以旌表其孝,时号“阙下林家”;林披,唐天宝十一年(752),明经及第,官任检校太子詹事、苏州(今属江苏)别驾,赠睦州(今属浙江)刺史,由北螺迁居澄渚乌石(今属莆田市荔城区),生九子:林苇、林藻、林著、林荐、林晔、林蕴、林蒙、林迈、林蔇,皆官刺史,世称 “九牧林家 ”;林昌之子林萍,迁居仙游游洋,称之 “游洋林家 ”。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中部的莆田,史称“兴化”“兴安”,为八闽名郡。它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明《兴化府志》载,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分南安地置莆田县,属丰州(今福州),寻废,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析南安地置丰州(今泉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圣历二年(699),析莆田地置清源县,两县同属武荣州(今泉州)。不久,废武荣州,两县隶属泉州(今福州)。久视元年(700)复置武荣州,莆田、清源两县复属武荣州。景云二年(711)改武荣州为泉州,莆田、清源两县属泉州。天宝元年(742)改泉州为清源郡,清源县改名仙游县。乾元元年(758)改清源郡为泉州,莆田、仙游(统称“莆仙”)两县隶属泉州。五代保大七年(949)改泉州为清源军,莆田、仙游两县隶属清源军。
《兴化府志》又载:“兴化为郡(别称莆阳、莆中),建置自宋始。”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割据漳州、泉州(含莆田、仙游)地区近20年的仙游人陈洪进,因“纳土归宋”有功而官至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但在他统治期间,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游洋人林居裔领导的农民起义。林居裔“聚众数万人(号称十万)抗宋,自称西平王 ”,围攻泉州城,后被朝廷派官军镇压。
次年,宋太宗翻阅《泉福图志》,“念游洋洞地险,思欲以德化之”,下诏割永福(今永泰)、福唐(今福清)合游洋、百丈2镇计14个里,设兴化县,后置太平军,军治、县治均在游洋镇。太平兴国五年(980),从泉州析出莆田、仙游两县入太平军,改名兴化军,管辖兴化、莆田、仙游3个县,为“八闽”之一。后因游洋镇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太平兴国八年(983),福建转运使杨克让奏准朝廷把军治从游洋迁至莆田县城。宋末升兴化军为兴安州。元代改兴安州为兴化路。明代改兴化路为兴化府。正统十三年(1448)裁撤兴化县,乃辖莆、仙两县。清代沿用明制,仍名兴化府。
林姓是莆田的第二大姓,“莆田林”开创了林氏家族在我国东南沿海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中华林姓家族的最大支系。按照当今人口数量排序,林姓居全国第17位、福建的第2位。莆田素有“陈林半天下”之称,截至2016年底,林姓人口有近50万人。莆田林氏的4个分支,分别是“九牧林”“金紫林”“阙下林”和“游洋林”。“游洋林”在宋代一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迁往漳州等地。明末清初,“游洋林”后人随郑成功攻打台湾,又迁往台湾雾峰。因此,莆田林氏也是台湾雾峰林氏家族的先祖。
莆田林氏又是一个文化层次很高的官宦世家,家风鼎盛,人才辈出,延绵百世而不衰,真可谓“诗书簪缨之名门望族”。据史料统计,自唐代第一位进士林藻至清代末科进士张琴的1000多年间,莆田共涌现出文武进士(含诸科、特奏名等)近2400人、明经17人和举人2265人。其中,林姓文武进士(含诸科、特奏名等)就有308人,明经14人,举人458人,分别占莆田总数的13%、82%和20%,蔚为科举奇观,高居诸姓之首,故时人有 “无林不开榜”之语。“科举”一词,来源于“分科举人”,就是“分科目选举人才”,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名称。科举也叫开科取士,是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世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我国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元朝初期几十年的不曾开科,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不断更选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的影响,是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的。
从整体来看,隋朝以前莆田的教育还处在萌芽状态。郑露三兄弟倡学在南山的 “开莆来学”,不仅开创了莆田教育之先河,而且也代表了福建文教曙光的来临,莆田的人文教育活动在唐代逐步开展。《兴化府志》云:“唐世设科取士..其科之目十有二:曰秀才,曰明经,曰进士,曰俊士..当时秀才科最高,鲜有应者;士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唐贞元(785—805)之后,福建 “岁贡士与内州等”,一改过去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状况,及第者络绎不绝。
《中国科举史》载,唐代从武德五年(622)至天祐四年(907)285年间,共举行262科考试,录取进士6656人。据《福建教育史》的统计,唐代福建56位可考的进士中,莆仙籍就有11人,约占20%。其中,林氏进士1人(林藻),约占莆田总数的10%。而按《新唐书》所记载,当时莆仙两地的人口数仅占全省的11%。终唐一朝,莆田人在《新唐书》中立传的只有林攒、林蕴两位,均为林氏家族。又据《兴化府志》统计,唐代莆田有17人明经及第,林家子弟就占14人,为莆田总数的82%。
谁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这是以往有过不少误解和争议的问题。明代周华在《游洋志 ·人物》中记载: “金鲤,字伯龙,清源东里白鹤人,登武德二年庚辰进士第(按:武德三年才是庚辰年)。”为此,在莆田市的第一轮修志中,不少编写者都沿用 “金鲤是莆田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的说法。如新编《莆田县志》载 “金鲤,唐武德三年(620)进士”;新编《仙游县志》载 “金鲤,唐武德二年(619)进士 ”;新编《莆田市志》与新编《莆田县志》的记载也是一样的。还有《兴化进士》《莆田史话》《莆田市名人志》等邑人出版的书籍,均持同样的观点,以至于后来的一些文史研究者以讹传讹。
其实,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是唐贞元七年(791)及第的林藻,他也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二个进士。关于林藻进士及第之事,地方志书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宋《仙溪志》卷二 “进士题名”载: “唐重进士科,莆始于林藻、欧阳詹,仙游始于陈乘、杨在尧、陈光义。”这是林藻为莆田第一位进士的最早记载,而此书没有金鲤登第的任何信息。又如明《八闽通志》卷七十二 “人物”亦云: “林藻字纬乾,贞元七年(791)登进士第,郡人登第自(林)藻始。”也就是说莆田的第一位进士是林藻。
《八闽通志》是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的地方志,《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 “福建自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后,记舆地者不下数十家,唯明黄仲昭《八闽通志》颇称善本。”该《志》 “不仿效其他省志通例,在通志之上冠以正式省名的做法,在地方志中别具一格,后来王应山纂《闽大记》《闽都记》,何乔远纂《闽书》,也都袭用此法..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有的且是未见于其他志乘的,体例也比较齐整,为我省编纂各级地方志之所本”。同样,在明《闽大记》《闽书》等方志中均没有金鲤登第的记载。
从古籍文献记载看,唐武德四年(621)发布开科举士的敕令后,至武德五年(622)十月,诸州经过考试贡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交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考试,取中秀才1人、进士4人。该科进士头名为孙伏伽,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姓名可考的状元,与孙伏伽同进士的还有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等3人。因唐代科举始于武德五年,所以,金鲤根本不可能登武德二年(619)庚辰进士第。
宋代在中国科举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创立的殿试制度,使分级考试逐层选拔臻于完备。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不但为同时代的辽、金所仿效,而且为后来的元、明、清各朝所沿袭。同样,宋代的兴化军在莆田科举史上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有宋一代,莆地虽偏居福建东南沿海一隅,但科甲鼎盛,俊秀如林,成为无可争议的科考发达之地,成为名扬天下的 “文献之邦”。
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宋代从建隆元年(960)至咸淳十年(1274)314年间,共举行118科考试,录取进士97300人,其中正奏名进士42457人,诸科进士16366人,特奏者进士38477。又据《福建教育史》的记载,宋代福建籍进士有7144人(不含诸科、特奏名等),名列全国正奏名进士第一位。为此,《宋史》会将 “登科第者尤多”列为福建的重要特点。然只有3个县的兴化军正如《兴化府志》所载,就有进士1756人,其中正奏名进士1014人(占福建进士总数的14%),特奏者进士582人,诸科进士63人,其他科进士97人。而林氏进士有205人,其中正奏名进士125人,占莆田总数的12%;特奏名进士60人,占莆田总数的10%;诸科进士8人,占莆田总数的13%;其他科进士12人,占莆田总数的12%。
值得一提的是,在由唐至清朝的历科进士中,唯独宋代于正奏名进士之外,还有特奏名进士。何谓特奏名?《宋史 ·选举志》云: “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这就是说,所谓特奏名,就是凡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解试、省试,即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并赐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
特奏名的设立,使科举考试更具吸引力,它不仅意味着取士名额的增加与扩大,而且也使读书人应举的前程显得更加光明。然特奏名的两个主要条件是 “举数”和 “年甲 ”,而不是才学高下,所谓 “退者俟乎再来”,则为每一个科场失意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一般士子就不会轻易放弃举业铤而走险。
对此,南宋人王栐在《燕翼贻谋录》卷一 “进士特奏”中有如下一段精彩论述: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籍。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开宝三年(790),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三月庚午诏曰: ‘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泪没消磨其中,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 ”可见宋代统治者创立特奏名制度,主要是吸取了唐末王仙芝等人因进士不第而犯上作乱的教训,特意大量增加取士名额,使潦倒场屋、屡试不中的广大举人心存一线希望,通过陪同正式考生参加殿试(即 “附试”)的机会,博取功名,进入仕途,不致积愤造反。
据宋朝文献资料载,北宋前期,一般是曾经省试进士五举或六举、诸科七举或八举、年龄在50以上,特予奏名。北宋中期,一般是曾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年50以上,曾经省试进士五举年50、诸科六举年60以上,特予奏名。北宋后期,一般是 “进士五举、诸科六举曾经御试下,进士六举、诸科七举省试下,年50以上;进士七举、诸科八举曾经御试下,进士九举、诸科十举省试下,年40以上”,特许奏名。南宋时期,特奏名,就是凡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解试、省试,即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并赐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
特奏名的设立,使科举考试更具吸引力,它不仅意味着取士名额的增加与扩大,而且也使读书人应举的前程显得更加光明。然特奏名的两个主要条件是 “举数”和 “年甲 ”,而不是才学高下,所谓 “退者俟乎再来”,则为每一个科场失意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一般士子就不会轻易放弃举业铤而走险。
对此,南宋人王栐在《燕翼贻谋录》卷一 “进士特奏”中有如下一段精彩论述: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籍。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开宝三年(790),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三月庚午诏曰: ‘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泪没消磨其中,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 ”可见宋代统治者创立特奏名制度,主要是吸取了唐末王仙芝等人因进士不第而犯上作乱的教训,特意大量增加取士名额,使潦倒场屋、屡试不中的广大举人心存一线希望,通过陪同正式考生参加殿试(即 “附试”)的机会,博取功名,进入仕途,不致积愤造反。
据宋朝文献资料载,北宋前期,一般是曾经省试进士五举或六举、诸科七举或八举、年龄在50以上,特予奏名。北宋中期,一般是曾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年50以上,曾经省试进士五举年50、诸科六举年60以上,特予奏名。北宋后期,一般是 “进士五举、诸科六举曾经御试下,进士六举、诸科七举省试下,年50以上;进士七举、诸科八举曾经御试下,进士九举、诸科十举省试下,年40以上”,特许奏名。南宋时期,“进士六举曾经御试、八举曾经省试,并年40以上;进士四举曾经御试、五举曾经省试,并年50以上 ”,特许奏名。总之,北宋后期较严,而南宋时期稍宽。
凡特奏名者,不论殿试成绩如何,均赐予一定的出身或官衔。在太祖、太宗朝,尚未分等第,均赐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一般分为三等,赐本科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诸州长史、文学、助教。英、神、哲、徽四朝,一般分为五等,第一等赐同本科出身、假承务郎(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学,第四等下州文学,第五等诸州助教。南宋时,仍分为五等,一般第一等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二、三名赐同学究出身,第一等第四名以下赐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将仕郎),第三、四、五等与英、神、哲、徽朝的三、四、五等相同。
作为笼络士子的一种手段,特奏名办法出台后,在维持宋朝境内安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然而特奏名入仕者任官比正奏名进士低,多数是授州府官学助教一职,这虽有促进官办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但特奏名制度也使科举的选贤任能功能变为选贤任能与养士抚庸相辅并行了。如两宋贡举共取士97300人,其中特奏名者即达38477人,约占40%。据《兴化府志》的统计,从宋元丰五年(1082)黄裳榜起至咸淳十年(1274)王龙泽榜止,192年间莆田特奏名进士共计582人;而从宋建隆元年(960)杨砺榜起至咸淳十年(1274)王龙泽榜止,314年间莆田正奏名进士只有1014人。由此可见,宋代莆田特奏名进士之多。
综上所述,宋代莆田只有特奏名进士,而没有特奏名状元。遗憾的是,近年来邑人出版的《宋代莆阳名人志》《莆田史话》《莆田市名人志》等书籍,却提出了 “莆田有特奏名状元8人”的新说法。其实,这个所谓特奏名状元,就是特奏名 “第一人”。如林洵美,绍兴十五年(1145)特奏名“第一人”,特赐同进士出身,任潮阳(今属广东)知县。众所周知,“状元及第”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由唐至清朝,唯进士科第一才能称 “状元 ”,才能称 “大魁天下”,其他各科第一,均无 “状元”之名。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中只标明进士科第一人为状元,明经或制科第一均不称状元。进士第一始称状元,唐代如此,宋代亦然。本文特此指出,以正视听。
此外,莆田林氏还涌现出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 “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等奇特现象。更有意思的是,兴化军有20对兄弟双双同科及第,其中林氏家族就有2对,即林宋臣、林宋弼(1132年)和林岳、林准(1160年),占总数的10%;甚至还出现林汝大、林栋(1271年)父子同科及第的现象,的确实属罕见。
纵观宋代莆田科举之盛,究其原因有五:一是朝廷以文治国,重视科举取士是莆田科举鼎盛的政治背景。赵宋自立国后,实行以人文为主体的治国方略。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文治。尤其是宋太宗做了皇帝之后,迅速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可以说,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宋朝廷不仅扩大录取名额,而且还通过改革科举考试方式,使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乃至上层农民的子弟,都可以不受家庭地位的影响,在考场上凭学识取得官位。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莆田大量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数亦文亦仕,既参与国家管理,又著书立说。当然,莆田林氏进士也不例外。
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而立传的林氏进士有5名,占莆田总数的21%。在莆田出仕官员中,官至六部尚书(正部长级)者13名,林氏家族就有2名,即林大鼐、林英,占总数的15%;官至六部侍郎(副部长级)者15名,林氏家族也占了2席,即林光朝、林彬之,占总数的13%据不完全统计,仅林氏进士著书立说的就有林璃的《太玄经注》十卷、《太玄经释文》一卷、《唐书纯粹》一百卷;林英的《晦庵童训》一册;林伸的《东轩文集》十卷、《春秋三传正经》;林豫的《笔锋草录》二十卷、《杂说》十卷、《杂文》十卷;林冲之的《木雁居士集》;林震的《林震集句诗》七卷、《林震文集》一百卷、《礼问》三十卷、《易传》十卷、《易数》三十卷、《易问》五卷、《经语千字文》一卷;林宋卿的《道山诗庄》《涪陵集》《湖北事宜》《督府集议》;林大鼐的《铁砚文集;◆林枅的《林枅诗文集》二十卷;林一鹗的《民谣集》;林虙的《诗解补缺》《礼经总括》《释奠解》《西汉发微》《元丰圣训》二十卷、《西汉诏令》十二卷;林光朝的《艾轩集》十卷;林榕的《四明居士诗》五卷;林井的《捐躯录》《平燕十略》;林磻的《典故钩玄》六十卷;林彬之的《囿山集》《海溪善政编》;林成季的《艾轩家传》一卷;林自的《周易解》《庄子解》《林自诗文集》十卷;林彖的《萍斋诗集》;林光世的《水村易镜》《景定嘉言》二卷等。
二是宋代大量人口南迁,福建经济的发展为莆田科举鼎盛奠定了物质基础。两宋是福建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时期,首先得益于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大量人口的南迁,使福建路、兴化军受益。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兴化的农业、手工业和海运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特别是木兰陂的建成不仅抵御洪水和海潮的灾害,保障农田灌溉,扩大耕地面积,而且使兴化平原的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木兰陂是当时福建规模最大,乃至在全国也算得上十分宏伟的水利工程,它的修成跟林氏家族也有关系。
三是宋代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莆田科举鼎盛的形成构建浓厚的文化氛围。宋室南渡后,整个文化中心向南方转移,在北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身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这些人到来后备受重用,自然形成了崇儒重文的社会风尚。尤其是宋代莆田的藏书家多、藏书量丰富,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如进士林伸,好聚书,官俸所入多用于买书,所蓄数千卷。有人见其如此便说: “你为何不替子孙考虑,却将钱都去买书? ”林伸答道: “吾蓄书数千卷,苟有贤子孙,足矣;不贤,多财适为累耳! ”又如进士林霆,博学而深研象数,与邑人郑樵为金石之交,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 “吾为汝曹(你们)获(留)良产矣。”因此,许多莆田士人捐金帛购书籍唯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也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藏书,才使得莆田文人辈出,著述如林,名作迭起。
四是地方吏民重教兴学是莆田科举鼎盛最重要的因素。北宋在经历范仲淹的 “庆历兴学”(1041—1048),王安石的 “熙宁、元丰兴学”(1071—1078)和蔡京的 “崇宁兴学”(1102—1106)等三次兴学运动后,基本上确立州(府、军)、县二级官办教育体系。但兴化军早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就已经形成军学和县学的二级教育网络,这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官办学校 “制度宏伟、雄冠一时 ”,出现 “学宫壮伟甲于闽郡”的动人局面。办学高峰时期,军学校舍 “凡四百八十间 ”,参加兴化军贡试的学子多达近7000人,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这与当时各地官学屡兴屡废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官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文化教育中心。
但对 “儒风特盛”的兴化军来说,这只是一方面,而更广泛、深厚的科举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的私学教育中。宋代莆田的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据方志记载,兴化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就达30所之多。仅林氏家族就有5所,占莆田总数的17%。
如林光朝在黄石东井(今属莆田市荔城区)创办 “红泉义学”,又称 “东井书堂 ”,正如邑人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所说:“初艾轩(光朝)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代邑人探花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林)蕴、(林)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除此之外,林光朝还与其族人林充、林褒在谷城山的松隐岩、国清塘旁的濯缨亭和五侯山之西的涌泉岩等地,创办草堂,传道讲学;林安中在西天尾澄渚村(今属莆田市荔城区)创办澄渚梯云斋,“将以教一族之英俊,来四方之明彦 ”;林彖在龙华寺(今属仙游县龙华镇),创办龙华书堂。同时,林氏家族还涌现出如林迪、林光朝、林立之、林彖等一批教育名家。
五是地狭人稠、以儒为业也是莆田科举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北方大量人口的南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由于移民的急剧增加,人地矛盾在兴化军尤为突出。正如郑樵在《通志》中所言: “吾莆地狭人贫,惟以读书为业。”对于莆田存在人口过剩的现象,林光朝在《艾轩集》中记叙当时的情景: “莆之郡二百年,虽以州名,其实一县也,原轸如绳,廛里如栉,十室五六,无田可耕。”然而,在 “地狭人稠,为生艰难”的情况下,聪明的莆田人却另拓谋生之路,诸如从事技艺、经商、出家以及向海外移民等,其中也包括不少人以读书为业,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希望一朝金榜题名,摆脱这种困境。莆田人的古训 “家贫子读书 ”,就是当时最真实生动的写照。
终宋一世,莆田林氏进士在清廉为官、学术造诣、家风传承等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
例如,名留史册的清官兄弟林孝渊和林孝泽。《兴化府志》载,林孝渊担任泉州通判兼泉州提举市舶司时,有一天,负责查验货物的官吏,按照惯例拿回来一盒龙脑(香料)。林孝渊知道后,命令收归官库。的确,按惯例市舶司的官吏可以收纳一匣的龙脑,并不犯法。但他清廉自守,认为官物属于国家,而私物则是商人货物。这种所谓惯例必须取缔,于是下令归还 “舶库”。
《九日山志》也载,林孝渊曾登泉州九日山并留下两块摩崖石刻,其一: “长乐林述中,陈大年,莆阳林全一(孝渊),嘉禾(厦门)鲁巨山同登姜相峰,过此徘徊久之,丙午(1126)十月十一。”其二: “靖康改元初冬,提举常平等事林遹述中,循按泉南。同提举市舶鲁詹巨山,太守陈元老大年,通判林孝渊全一,会食延福寺。遍览名胜,登山绝顶,极目遐旷,俛仰陈迹,徘徊久之。”这是靖康元年(1126),几位同僚到延福寺聚餐后登游九日山的记游石刻。同是这几个人,两块摩崖石刻却如此分开刻字,似为表示公私分明之意。由于前段系私事游览,姓氏前没有加上官衔;而后段为同僚公事聚会,故姓氏前加上官衔。
无独有偶,这种清廉之风在弟弟林孝泽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兴化府志》记载,他担任广东提举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事务。有个外国商妇蒲氏,其儿子所贩卖的货物,因违反朝廷的贸易法而被扣押。
于是拿着海外奇异珍宝贿赂宫官,为儿子求情,企图打破朝廷的有关禁令,并得到了皇帝侍从的帮助。林孝泽说: “过去三佛斋国(印尼苏门答腊古国)因不按规定时间前来请求进贡,清明的君主尚且谢绝,并遣送使臣回国。如今因一位商妇,要使朝廷废弃已实行二百年的往来贸易法,怎么可以呢? ”于是向朝廷上书力争,坚持不予放行。
后来,他以左朝请郎知漳州。一日傍晚,林孝泽视事完毕回住所,属吏拿着火烛送到室内,他却说: “这是官府使用的火烛,怎么可以用在私室? ”急命拿走。《八闽通志》称赞道: “(他)清介特甚,至不用官烛于私室。”再如,承前启后的理学名家林光朝。他少时聪明好学,拜邑人大学问家林霆为师。然而科举仕途之路却并不顺利,先后两次入京参加礼部会试,均落榜不第。但他并不气馁,离京返乡途中,便在浙江钱塘、吴兴一带从师求学,“过吴中,从陆子正游而得洛学(理学) ”。他研读程学,“学通六经,旁贯百氏 ”。
沿及南宋,讲学之风日盛。林光朝在长达20多年的传道授业中,继承程子之学,在闽中一带传播,盛名天下,桃李遍地。他所创立的学术思想即为其弟子所承传,并形成颇具阵容的红泉学派,自成理学于一家。
《闽书》载,红泉学派的门徒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其(林光朝)后,纲山林公亦之,乐轩陈公藻,先后起而继之。乐轩(林亦之),家长乐;纲山(陈藻),居福清,岁来讲学东井,风声所被,气习所薰,人皆有邹鲁之风 ”。《莆阳比事》也载,林光朝学生刘夙、刘朔于绍兴年间(1131—1162)相继登进士第后,在浙江衢州和温州一带任职和教授。还有不少弟子在各地创书院。传播理学,如弟子洪天赐、刘克刚等,他们在授学宗旨上亦继承了艾轩(林光朝)的思想,在学术论坛上大显身手,有的寻其源,有的扬起波,各有千秋。
林光朝是一个对宋代理学的形成、传播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尤其是宋朝南渡后,对东南半壁理学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红泉学派兴起于二程、朱陆之间,在传播洛学上,承前启后。
宋初尊崇儒学,重视孔孟之道。至宋仁宗继位,遂推行义理之学,胡瑗、孙复、石介开其先河,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至宋神宗年间(1068—1085),又有周的门徒程颢、程颐等,一传再传,蔚成理学一大学派。正如清人蒋垣所说: “濂溪周子敦颐,继孔孟绝学于仁宗间,以《太极图》《通书》授程伯子颢、叔子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季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惇、杨时成德尤著。杨时闽之将乐人..杨时归闽,受业者多,东南推其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弘传之张栻,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表现在政治上,学派中又各有门户,造成朝廷中党派纷争。程氏兄弟的“洛学”派在受到三次沉重打击之后,只好兵分三路,进入闽、浙、赣,潜移民间。于是,洛学在南渡前后形成中辍局面。另一方面,时人称为 “国之大儒”的朱熹尚未兴起,当林光朝倡道讲学于红泉之际,朱熹还处在孩提时代。当朱熹正式师事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门下专心于儒学时,林光朝已登隆兴进士第。
同时,从二程洛学入闽线索看,一是洛学道南系的先河杨时、游酢。杨时一传罗从彦,二传李侗,三传朱熹;游则无门人。二是程学传至胡安国,国传其子胡寅、胡宁、胡宏,并传侄子胡宪。三是通过程门高弟伊焞、王苹传给陆子正,再传给林光朝。“和靖高弟如吕、如王、如祁,皆无门人可见,监官陆氏(子正)独能传入艾轩,于是红泉东井学派兴焉”。上述前两条线的程门高弟皆是闽北人,属当地的建宁府、延平府。他们传播洛学的地域都在闽北,使闽北成为福建学术的一大中心,闽文化的大本营。
但是,从这些闽学之先的年表看,他们均卒于北宋或南宋初,唯有闽中这一线路,传承程学正宗的林光朝,正处中年时期。因此,红泉学派为南宋理学的勃兴无疑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恰如《黄四如集序》中所言: “濂洛中微,考亭未兴,艾轩林公光朝,倡道莆阳,从如归市,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宋史》亦载: “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林)光朝始。”邑人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也赞扬道: “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可以肯定,林光朝的理学思想对青年时期的朱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建立的一个封建朝代,不但实现了辽、西夏和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完全入主中原的愿望,而且建立了疆土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但蒙古民族“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个性并未完全改变,因而对科举取士制度最初并不在意,统治阶级和士人社会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也存在极大的分歧。经过许多儒臣的竭力倡议,才在元皇庆二年(1313)建立了科举制度,此时距1279年元世祖攻灭南宋已经有34年之久,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中断时间是最长的。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一些蒙古和色目贵族还是力图加以罢止,采行科举取士制度之争并未结束,其中元统三年(1335)的科举停罢之争是最为激烈的一次,以致出现1336年和1339年的两次停罢。
由于元军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汉人尤其是福建人民大开杀戒,沿途尸横遍野,生灵涂炭,文化教育设施也多数遭到摧毁和破坏,致使福建尤其是莆田的科举式微,进入一个中落时期,读书为官者寥寥无几。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元代从延祐二年(1315)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51年间(其中缺少2科,即1336年和1339年),举行16科考试(每3年开一科),共录取进士1139人。又据《八闽通志》和《兴化府志》的记载,元代福建进士有36人,其中兴化籍7人,约占福建总数的20%;而林氏进士2人,约占莆田总数的29%。元代福建举人有70人,其中兴化籍9人,约占福建总数的13%;而林氏举人2人,占莆田总数的22%。
林济孙、林亨是不是元代的状元?这也是一直在莆田有过争议的一个问题。清乾隆《仙游县志》载: “至元六年(1340)林济孙榜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升侍讲。”又载: “至正三年(1343)林亨榜进士第一,官至朝奉大夫。”清同治《福建通志》和民国《福建通志》均有相同的记载。为此,在莆田市的第一轮修志中,不少编写者都沿用 “林济孙、林亨是元代状元”的说法,如新编《仙游县志》和新编《莆田市志》。还有《莆田文化丛书 ·文化概谈》《兴化进士》《莆田史话》《莆田市名人志》等邑人出版的书籍,也持这一观点,以至于误导了不少读者。
其实,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从史志记载来看,不仅《元史》没有记载 “林济孙、林亨是元代状元”的史实,而且《八闽通志》《闽书》《闽大记》《兴化府志》等明代志书也均未记载此事;从登第时间上来看,元代共举行16科考试(停罢的是1336年和1339年),接下去的是1342年才对。而林济孙、林亨中状元的时间却是至元六年(1340)和至正三年(1343),这两年恰恰没有开科。众所周知,元代科举分为右榜和左榜,右榜状元必须是蒙古和色目人,左榜状元才是汉人和南人。因此,每次开科会出现 “一科两状元”的特殊情况。况且,左榜状元16人有名有姓,有籍可查,没有一个是福建人。所以,经过考证确认,林济孙、林亨既不是元代进士,更不是元代状元。清乾隆《仙游县志》、清同治《福建通志》和民国《福建通志》等志书关于 “林济孙、林亨是元代状元”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
星移斗转,朝代更替。到了明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以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之唐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统治者求贤若渴,除了下诏招贤,还于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令各行省连试三年。由于朝廷刚刚建立,缺少官吏,因此乡试中式的举人都免除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拔为官。以上政策、措施,极大鼓舞了士人的读书求取功名之心,而扩招必然增加应试名额,增加了中举的可能性。最高统治者还将各地科举的兴盛程度作为考核官吏的一大手段,鞭策了在任官吏重视当地的教育,而无视教育或劝教不善者,则坚决给予惩罚。终明一代,莆田历任地方官多能以身作则,倡学乡里。对于学校缺乏办学经费,官吏或慷慨解囊,或拨寺产补给学田,或出库银以赡生徒。随着兴化经济的日益繁荣,在传统的重教兴学的社会氛围熏陶下,莆田又重现了科举强区、人才辈出的盛况,进入再一个昌盛时期。
按《中国状元大典》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272年间,共举行91科考试,录取进士24636人。又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明代福建进士有2395人,其中兴化籍535人,占福建总数的22%,而林氏进士89人,约占莆田总数的17%;明代福建状元有11人,其中兴化籍2人,占福建总数的18%,而林氏状元1人(林环),占莆田总数的50%;明代福建探花有10人,其中兴化籍4人,占福建总数的40%,而林氏探花1人(林文),占莆田总数的25%。
关于明代莆田状元,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传说。清末邑人进士张琴编的《莆田县志》说:明永乐四年(1406)丙戌科莆田人林环殿试第一,但同科进士、林环同乡陈实却恃才不服,扬言考官录取不公。明成祖召而诘问,陈实答言: “臣百问百答,从无纰漏,缘何不取? ”皇上怒其不恭,欲制其狂气,乃命大学士解缙出题云: “孔门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云台二十八将,将将何功? ”成祖亲临考问,陈实一一对答不误,文采亦佳。但林环更是应对如流,毫无遗漏。因二人不分上下,皇帝乃加罪陈实,充军三边。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兴化府人才济济。同时,林环也以无可争辩的才华得到明成祖的青睐,他的确是莆田林氏杰出人才的代表,史家评他: “负材学,晓世务,特为文庙所器,一时儒硕亦厚望之。”如果说明代会试是全国各省举人之间文化水准的大较量的话,那么乡试则是省内各府县秀才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智力的大竞赛。明代乡试已固定成为省级地方考试层级,举人出身即可授予官职,因此竞争十分激烈,乡试中举也比前代更为荣耀风光。由于想要参加乡试的生员(秀才)太多,为了控制参试人数,明代曾规定每举1名,只允许30名科举生员参加乡试。限于录取比例太低,中举的机会是相当少的,中举率大约在4%,故俗有 “金举人,银进士 ”之谣。
正是从竞争的激烈程度来看,举人比进士还更难能可贵,才会有 “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据《福建教育史》统计,明代福建举人有8325人,其中兴化籍1692人,占福建总数的20%,而林氏举人312人,占莆田总数的18%;明代福建乡试解元有90人,其中兴化籍30人,占福建总数的33%,而林氏解元4人(林时望、林同、林文俊、林东海),占莆田总数的13%。因为莆田在福建乡试中,中举人数多次占全省的近一半,故有 “一邑半榜 ”之誉。
有明一代,莆田不仅科甲鼎盛,侔于中州,而且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从政者重臣高官选出,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等奇特现象。莆田人在《明史》中立传的有4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36名,而立传的林氏进士有6名,占莆田总数的17%。在莆田出仕官员中,四品(知府)以上的官员多达300多人。
而任明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俊、林云同、林尧俞、林兰友,占莆田总数的27%;任明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侍郎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富、林文俊、林铭鼎、林佳鼎,占莆田总数的27%;任都察院的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的有15人,其中林氏7人,即林元甫、林茂达、林有孚、林大辂、林润、林贽、林一柱,占莆田总数的47%。任左右布政使的有27人,其中林氏5人,即林豫、林应标、林烶章、林澄源、林恭章,占莆田总数的19%;任正副按察使的有34人,其中林氏8人,即林坦、林时、林长繁、林民悦、林铭几、林有年、林斌、林烇章,占莆田总数的24%。上述一人多历数职,这里只列其较高的一职,且无法将四品以上林氏官员的名字一一列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十年(1531)莆田知县王钜建县衙,把衙门外南端 “善俗坊”改为 “文献名邦”,后遭倭寇烧毁。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县徐执策重建县衙,并在县巷南北两端分别建竖 “海滨邹鲁”和 “莆阳文献”两个木坊。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孙继有又将这两坊改名为 “文献名邦”和 “壶兰雄邑 ”。从此,莆田正式誉称为 “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所谓 “文献名邦 ”,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解说: “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指历史典籍和贤能人才辈出的著名乡邦(地方)。
而 “海滨邹鲁”,其中 “邹”是指孟子的家乡,“鲁”是指孔子的家乡,两者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邦国之一。莆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虽为小邑,但儒风特盛,无论是从教育发达、科名鼎盛来看,还是从文化氛围、学术成就来说,把 “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这两顶桂冠戴之莆阳,都不为过。因为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公论,如宋真宗敕书所说 “闽越之地,邹鲁之儒”,宋度宗盛赞 “莆,文献之邦也”,宋邑人黄灏讲 “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邑人状元黄公度在《兴化军学记》中所载 “习俗好尚,实有东周齐鲁遗风”等等。所以,明代兴化成为 “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千百年间重视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对此盛事,清乾隆《莆田县志 ·人物志》序言中写道: “莆僻处海滨,齐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故欤?盖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确实,“文献名邦 ” “海滨邹鲁”的深刻内涵,远远不止于科甲之盛,人才之众,更重要的还在于兴化人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就以著述来说,仅明一代,就有著作900多部,现存120多部。
据不完全统计,仅林氏进士、举人撰写的书籍就有林洪的《竹庵存稿》十卷;林环的《■斋集》十卷;林文的《澹轩集》五十卷;林诚的《奏疏》五卷;林俊的《西征集》《见素文集》二十八卷;林茂达的《翠庭集》;林塾的《石泉集》《拾遗书》;林富的《省吾遗集》《奏议》二卷、《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林文俊的《内黄县志》《方斋存稿》十卷;林达的《自考集》《编年纪略》;林大辂的《愧瘖集》;林樯的《诗集》二卷;林应骢的《梦槎奇游集》二卷;林云同的《读书园集》《退斋文集》《韶州府志》;林东海的《四书经集解》,林华的《岳麓口义》十卷;林万潮的《赣州集》;林应箕的《百一诗稿》;林兆金的《东山樵稿》;林润的《愿治疏稿》;林澄源的《悟往吟》《经传讲义》《古易论》;林兆珂的《批点左传》《楚辞》《参同契》《毛诗多识编》七卷、《考工记述注》二卷、《撞弓述注》二卷、《宙合编》八卷、《李诗钞述注》十六卷、《杜诗钞述注》十六卷和《衡州府志》十五卷;林尧俞的《溪堂集》四卷、《万历兴化府志》;林恭章的《静宇逸稿》;林铭鼎的《新锓林会魁》《书经逢源集注》六卷;林铭几的《南窗遗稿》;林兰友的《迷迷草》;林嵋的《蟛蜞集》十二卷;林士敏的《芹边集》《匡庐小稿》;林喦的《万竹居士集》;林长懋的《竹庄集》;林勤的《朴庵集》六卷;林同的《大学中庸训说》《书经讲义》;林智的《蛙鸣集》;林宪的《鸥沙集》十卷;林大猷的《思轩稿》;林有年的《寒谷集》《东山诸集》《东莞县志》《瑞金县志》《武义县志》《安溪县志》《仙游县志》《福清县志》;林墰的《西麓稿》;林汝永的《南崧集》;林应采的《东皋吟稿》;林炳章的《宠荣堂稿》;林兆箕的《学适堂集》;林烇章的《伊蒿稿》;林錝的《石莲集》;林宪曾的《西源集》;林谐的《觉未轩集》;林齐圣的《闲有堂集》;林尊宾的《雁圉集》四卷;林说的《寸草堂集》等。
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1522—1566),日本倭寇的侵扰打破了莆田人民安宁祥和的生活,战乱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邑人关佛心在《莆田倭祸记》序言中这样写道:“莆田立县千三百年,最大之兵祸,厥惟明代之倭寇。”倭患在生命、财产上侵扰莆田人民,还毁坏学校、公祠,破坏读书人赖以生存与读书的社会环境及物质条件。
《莆田倭祸记》在《屠城记》一章中又描述道: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城陷..被焚毁之衙署、祠院庐一览:莆田儒学、兴化儒学..黄仲昭祠、林苇祠..士绅之遭难者:甲科以上十七人,乙榜数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倭患造成兴化府科举日益萎靡,据清乾隆《莆田县志》统计,嘉靖二十二年(1543)乡举中莆田中举33人,二十五(1546)年为27人,二十八年(1549)为20人,三十一年(1552)为21人,三十四年(1555)为22人,三十七年(1558)降至19人,四十年(1561)和四十三年(1564)仅剩15人。进士名额到嘉靖末年,每榜也只有2至3人。莆田的科举事业跌到了底谷。
清朝的科举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朝廷加强思想控制和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种重要手段。“四书五经”照样是科举取士的准则和学校教学的依据。人们的思想被死死地控制在理学的囹圄之中,应试文章只能用僵死的八股文 “代圣贤立言 ”,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梁启超痛斥说,“民之愚,国之弱 ”,皆有八股取士造成。由于明中后期倭寇“屠城”和明末战乱对莆田经济、教育巨大破坏等一系列原因,清代莆田的科举已是 “强弩之末 ”。莆田士人热衷科举、想进朝廷为官者不多,越来越少。
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258年间,共举行112科考试,录取进士26888人。又据《福建教育史》的记载,清代福建进士有1421人,其中兴化府64人,约占福建总数的5%左右,而林氏进士9人,约占莆田总数的14%;清代福建举人有10391人,其中兴化籍564人,占福建总数的5%;而林氏举人143人,占莆田总数的25%。1905年5月,清朝廷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也出于改变教育落后的状况,无可奈何发布诏谕,“从丙午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至此延续13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科举停罢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1905年废科举,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尤其在清末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科举停罢不仅对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震撼,而且在世界上的反响也相当强烈。美国学者威尔 ·杜兰说: “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和官制改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 “学而优则仕”的考试选人办法,虽有其局限性,但肯定比 “学而劣则仕”或者 “不学而仕”好,这或许就是科举制度存在1000多年的最大合理性。人们因而得出结论:科举是十分适合中国古代国情的一种制度。
相关地名
莆田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