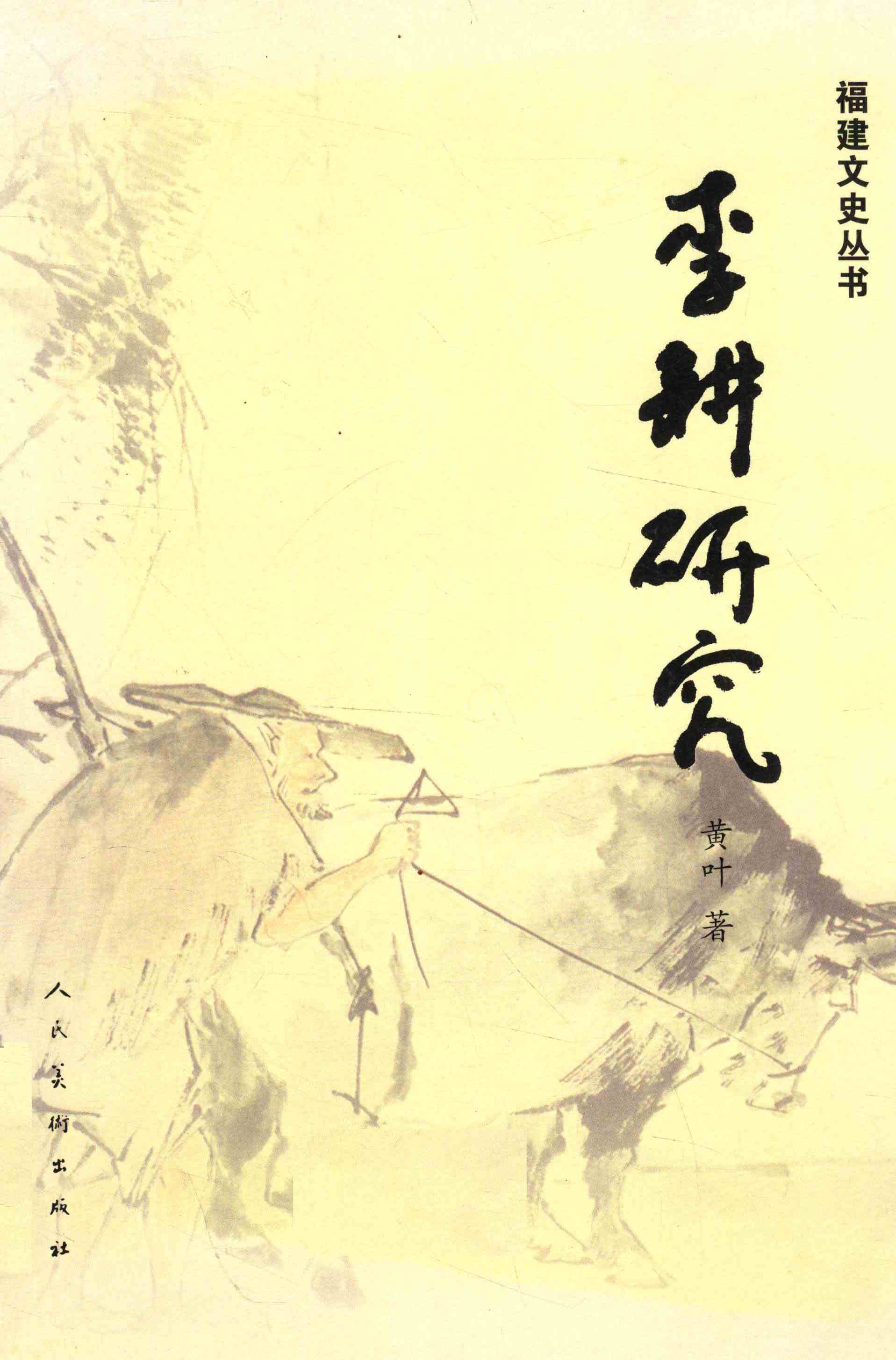内容
2002年,我在“莆仙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仙游画家“二李”述评》(后收入《八闽文化研究丛书、莆仙文化研究》,2003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该文就李霞、李耕先生的艺术及其风格形成的因素和价值、影响等做了一次简单的梳理和阐述。将同一地区、同一流派的代表性画家纳入同一框架分别予以评述,从自然、人文环境、师承和从艺道路,个人性格气质等同与不同中审视两者各自的艺术风格和人生。运用这一方法来找出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梳理环境和画家本身与艺术风格的关系,以及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独具地域特色的仙游文化,应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2014年7月7日,“福建省中职骨干教师培训班”在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开学,本人应邀作了“李霞、李耕国画风格比较”专题讲座,实际上,该讲座是对《仙游画家“二李”述评》的延续和深化,着重从中国画作品构成元素中去寻找两人表现形式的差异和论述双方艺术的不同点。我想,面对学员听众,通过具体分析会比空泛的理论表述更深刻,更具说服力。
本文便是对这一讲座稿的整理和充实,特别是把在本次讲座中因时间关系没有提到的仙游另一位代表性画家黄羲先生一并纳入,使得这一地方绘画流派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完整的体系,外界也能从仙游古典人物传统的“同”中看到“异”,从静态的、固化的流派体解到动态的流变和发展,并通过普遍性与特殊性、不变与变的回环观照,获得更清晰的镜头和更全面、深入的认知和理解。无疑,这对于仙游古典人物画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对长期处于低谷或者说被边缘化的中国画古典人物研究和创作,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借鉴、启示甚至推动作用。
一
以年龄和资历论,李霞长于李耕,又早出道,因此我们先谈李霞。首先从构成中国画风格的最主要元素——笔墨去切入。
李霞笔墨雄放旷迈,古穆浑厚,这一特征在写意巨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代表作有《关公》《钟馗》、“八仙”(四条屏)、“忠、孝、廉、节”(四条屏)、《麻姑》《寿星》等。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霞画面笔墨构成效果,首先得益于他所使用的自制鸡颖笔。鸡颖笔既有羊毫贮墨多,又有狼毫弹性强的特殊性能,易控制,好发挥,由之使李霞的线条能够在重按轻提、上下其手的往来变化中显示出一气呵成、连绵不断的气韵,在畅快通达中保持了线条轻重粗细的韵律节奏。李霞作写意巨幅,多用吸墨性能强的夹宣,以增益墨色温厚之气。在体现其雄迈风格的以粗、重、大、长线条为特征的信笔挥写时,凭着中锋使转的运笔功力与锋颖的弹性,做到先行的,作为主干的阔笔不粘不滞;后续的,作为辅翼的细线不枯不薄。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李霞作巨幅时,务需将宣纸裱糊于墙壁上竖立作画,却能控制到毫颖贮墨如此饱满而不致流淌下来,这与行笔速度之疾以及落纸时先以粗线阔笔构就主体,然后辅以细线的笔迹运行速度和顺序有直接关系。而这些笔墨构成特征,也有意无意促成了李霞雄阔酣畅、大气磅礴风格的形成,这从《富贵寿考》(图1) 中行笔轨迹可以得到证明。
李霞旷迈雄放的另一表现是在人物画创作过程中对形与神关系的拿捏,(也可以引申为笔墨所发挥再现与表现功能的理解与应用上)这从他的《髓石子自序》中已有所表白:“国画尚笔法精神,西法尚透视写生,时趋不同,各有所长”。基于此,他在实施线条对人物形体描绘时才敢于把追求笔墨气韵之生动凌驾于对形体准确性的斤斤计较和过分附就之上,颇有点像善诗者的“不因辞害意”。如《铁拐李》(图2) 对画面笔墨主体的宽大衣袖衣纹线条处理,便带有较多主观成分,也就是将笔墨气韵及其形式美感作为展示自己功力和宣示艺术立场的一角舞台,从而把师法黄慎以草书入画体式发挥到极致。须知,李霞所处时代,西学东渐之风正炽,而人物画创作一般又侧重于写实,这一以笔墨神采气韵去调取观众视觉神经,对具体形态一些细枝末节的淡化甚至大胆删削,正是中国画写意传统中“遗貌取神”“得意忘形”的践履,也是李霞魄力与气度、胆识与性格的一种表现。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所指出的李霞风格的雄迈旷放、古穆浑厚无非是出自他作品尺幅之大,线条的粗阔疏放等外在形式上,那就有点误解了。
李霞作品的大气磅礴,绝不能视同为那些虚张声势的笔墨演示,而是紧随着蓄力重按、阔笔悍写之后,能够有效地利用鸡颖笔毫的超强弹性,就在笔尖恢复原状的当儿乘势而下,或急起直追,或舒缓从容,于长拉短拽、迂回穿插中各臻其妙。这些灵动活泼、轻松随意元素的注入,顿使原本在粗壮硕大主线重压下显得有些沉闷的“局”顿时被带活起来,笔墨也丰富起来。
仙游九鲤湖以瀑布成九漈而名扬天下。我想,李霞画中的大笔,岂不是雷霆万钧的“珠帘漈”? 而数笔作为辅助、映衬的细线,又恰如旁边从草丛石缝中溢出涓涓细流的“玉柱漈”,诚所谓“珠帘玉柱,瀑流交映”!李霞的艺术创作不正是大自然的翻版和老子朴素辩证法的实践?一般认为,举凡一幅写意画,其所用阔笔大线条,犹如书写榜书,纵有浪漫情怀,亦难能心手如一,若欲抒发性灵得其酣畅飞动之势殊为不易,故只能诉诸沉稳拙厚以彰显其腕底功力,寄寓雄迈之气。而李霞的巨幅写意,阔笔粗放间的回环使转能于拙厚凝重中达到不粘不滞的气脉通畅,确实显示了李霞的不凡功力。然而从李霞重、拙笔墨所捎带的洒落遒劲、收放自如的细线,又可以体味到李霞“致广大”后的“尽精微”——既有运斤成风气势,又有春蚕吐丝的和缓与柔韧,大而能放,细亦不弱。我曾在《铅华扫尽见精微——李霞〈孟母择邻图〉解赏》一文中就提到:“李霞以擅写巨幅,喜运阔笔,画面以恢宏博大闻名,但从这幅尺幅不大(指《孟母择邻图》)的立轴中那扫尽铅华和细腻精微的笔墨中,我们看到了画家的另一面。”算是提示人们对李霞另一风格的关注。下面我要介绍的是李霞工细笔一路的代表作《十八罗汉过江图》(图3)。
《十八罗汉过江图》为水墨长卷,李霞1935年65岁时作于上海。该卷人物及其衣纹,罗汉坐骑虎、狮、象与天上云龙、各种法器、江面波浪以及岸际窠石山坡、虬松枯树,一例古法森严;线条勾画一丝不苟,规整而不失灵动;人物古穆奇逸、意态从容;笔墨淡淡荡荡,一派祥和,整体格调协和古雅。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李龙眠、贯休、吴彬、曾鲸等前辈大家的不同程度影响,还可以领略到李霞在践行:“窃意专攻写意,恐流粗率;专攻线纹,恐失拘牵”(《髓石子自序》) 时于线纹这一端力求“不失拘牵”的出色表现,其画风的严谨,画技的精湛,画格的淳雅,深获当时艺术素养深厚的政界大佬推许,为之题跋的有林森、于右任、许世英、黄葆戉等,殊为难得。
趋于工谨细致,可归入兼工带写一路的作品还有载于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四聘”(《耕稼登庸》《钓璜待聘》《秦穆求贤》《三顾草庐》)四条屏,比较特别的是该套作品乃是把山水作为画面主体,而人物不是十分显眼,若当作李霞的山水画也无不可。其中山水画法直追宋元,高古浑穆,与图中的人物风格浑然一体。说明了《髓石子自序》中所称其“间赏博考历代名家画迹”的同时亦下过一定功夫去实践。而晚年创作的“廿四孝”组画,“用笔灵动随性,书卷气浓厚,人物多以细线勾出,比例准确,衣纹纵横争折,夹带左右,人情世态表现十分鲜活,尊卑贵贱,老幼妇孺,各具身份,室内陈设、器皿透视合理,图案纹饰变化丰富,农舍、庭院取自生活所见,自然亲切,背景用小写意手法画出,与人物运线对比,益觉生动。”(黄羡《雄浑古穆、意趣超然——画家李霞的艺术成就》载台湾省《历史文物》2007.04)李霞作为以画画谋生的职业画家,必然会考虑到不同层次的买家和不同的场所及用途。其巨幅作品以笔墨旷迈雄放,人物形象的沉稳端庄所显示的正大富贵之气为富户豪门所喜爱,作品悬挂在高宅大院的厅堂,十分匹配。工谨画法乃是顾及到人物画所不应回避的叙事功能,对历史故事的描述乃是人物画创作的应有之义,由于叙事题材在故事情节表现上有对真实性、完整性、生动性的特殊要求,限定了其表述方式也必须趋于循规蹈矩、严谨严肃,对故事的发生地和背景当有所交代,所以配景也不能太过大意和粗疏,这就是李霞作品既有大幅巨幛的大气磅礴,又有一般规格之精细工谨的由来。不过,基于李霞的性情气质、审美取向和深厚功力,有些作品虽然尺幅不大,笔画工细,结构严谨,但仍然不失其旷达雄浑与沉郁酣畅之气。
海派巨擘吴昌硕曾称李霞为“人物第一家”,可以想见两人应有一定的情缘。李霞衣纹勾画还引入了吴昌硕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法。当然,李霞私淑黄慎,尤以草书入画传其衣钵,得其神髓,因此其草书也承袭了黄慎的神采风韵,跌宕起伏而流转自如。从他的衣纹线条中,古人推重书法行笔的“折钗股”“屋漏痕”“高山坠石”“万岁枯藤”等形迹随处可见。
从阔笔讲到细线,从拙厚讲到灵动,从疏放讲到严谨,线条的粗细长短、浓淡枯润、纵横曲直的排列、组合、穿插、腾挪和对比中编织出笔墨平面上的形式美,又从线条运行的起止、疾徐、顿挫、轻重、去留中演示出一笔一画的韵律美,这就是李霞的线条特色,但这仅仅止于狭义的笔墨层面。下面,我们再谈李霞的人物造型。
李霞塑造的人物形象,古穆端肃而风骨魁奇,其立式造型多呈倒锥形,即上身宽博,下身逐渐收紧收窄,有很强的雕塑感和形式感。尤以《麻姑》(参见P114《李耕写意人物画综论》图57)最为典型,已然成了李霞作品的独特符号,想必应与李霞的海派情结有关,李霞生前出版的两本画册都是在上海印刻,这在印刷业不发达的当时颇为稀罕,海派艺术对李霞势必形成一定影响。十分明显,李霞的麻姑造型与钱慧安十分相似。这一倾向于静态的造型正契合了李霞所欲建立的沉、厚、稳的画面基调,更为李霞运笔时习惯性的自上而下注气(巨幅宣纸裱于墙上直立作画笔迹运行的必然趋势)提供纵向之势(静态的倒锥型或直立式造型必以纵向线条来支撑),这样,也就产生了李霞人物画又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李霞的人物画表现形式上正好对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外静内动”形态——即为了凝神聚气,成其浑穆壮美之势,李霞的人物造型大多保持稳重、沉静这一基本特征,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先是用阔笔箍住整体轮廓,尽量避免气力外泄。故此,李霞用笔较少向四周发散辐射,笔墨的变化、线条的流动,一般都是在大轮廓之内进行。这在他的代表作如巨幅关公、麻姑、钟馗、寿星等造像式人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鉴于此,我对过去曾将李霞与李耕艺术风格比之为五代时期花鸟画两大流派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后又将他们的艺术风格推及到儒道两家思想的高度予以归类,认为李霞偏于儒家,重规矩、尊古法,作品庙堂气浓厚,是入世的。而李耕不管是人生态度或艺术追求,都倾向于道家回归自然、向往自由、崇尚朴素的思想,因此他的创作不拘成法,极具个性,展现的是江湖朴野之风。通过对二人作品的进一步认识,觉得还有必要申明:“就笔墨、造型等具体运作程式而言,李霞从中有意无意地演绎着道家的圆浑、内敛、古穆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而李耕挥毫恣肆、率直硬朗的锋芒毕露,奇趣横生、灵气四溅的才气外溢,反倒表露出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意态,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构图在古代南齐谢赫的中国画六法中又称“经营位置”,先人于此已创造了诸多图法并加以理论的诠释并形成范式,总绕不开用老子朴素辩证法来处理虚实、浓淡、简繁、疏密、横直、远近等的关系,只不过作者在实践应用过程中,根据不同内容和形式,对这些关系处理的机巧和灵活度各个有所不同罢了。李霞画风偏于纯正沉稳,因此构图上也相应地四平八稳,甚少有惊人之举和独创图式。他的出彩部分,或者说最具震撼力的地方,是用笔的高人一筹及其人物形象塑造与笔墨、构图等整体画面的高度协和,并从这一协和中升华出中华文化的端肃之体、正大之气!我在《仙游画家“二李”述评》中还顺便提到了“李霞在传统颜料使用和色彩火候的把握上也堪称大匠。他的作品是研究传统色彩学的极好范本” 。虽然写意画并不十分在意颜色问题,但对李霞中国画风格的综合评述,我想还得再次提到他的用色。也许是前期水墨晕染功夫的到位之故,李霞在画面上所罩颜色,尤其是朱砂、赭石一类暖色,与墨气每每能浑融一体,了无涂抹痕迹,更无一丝一毫的火气和轻薄妖艳之气,予人感觉的是自然沉淀晕化下的醇厚、温润、丰腴、平和。
二
李耕画风奇特,个性张扬,富新意、善变化。如果说李霞以稳重、宏大、深厚、旷放等来构筑他的艺术世界,那么李耕则是以奇肆、朴野、超逸、爽朗贯穿着他的艺术主线。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差别是:李霞中国画风格自始至终没有太大变化,其演进脉络呈直线渐进式,如果真要找出变化,那就是从早期的“稚嫩”走向后期的“成熟、老到”。而李耕风格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变化,呈跳跃式、波动状的发展轨迹。例如20世纪20年代前的年轻时期画风酷似李霞,人物造型也是倒锥形上宽下窄,衣纹勾画也用宽笔粗线,由于李耕是左手笔,挟笔多现欹侧之势,因此起笔或转折时露圭角,峭削而凌厉,如《东坡笠屐》(图4),此与李霞的中锋阔笔的飞白不尽相同。但又不难看出两人共同承袭黄慎而笔迹出现的一些差别。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李耕画风又是一变,笔墨恣肆奔放。及至30年代末又来一个脱胎换骨,造型由原来的束缚转向疏朗、生动,风格已渐脱前人的桎梏而现出自己的特点。即一改原来的狂肆张扬、略觉乖张的意笔大写,转而为平淡从容的以细线勾写为主的兼工带写法式,到这个时期,“李耕体”写意和“李耕体”工笔才定形下来(图5),从此不断迈向成熟。最终成为代表李耕风格的最主要体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李耕在不拘成法的强烈创新意识支配下,其作品多为通过细线勾勒抒发自己写意情怀的“兼工带写”法式和外形较为均匀工谨而不失写意性的“工笔画”,但一直也不放弃形式上更抒情,笔墨上更放纵、更富变化,人物形态更有趣,形象更夸张的大写意,或以水墨没骨泼写,或以粗线简写。此类大写意尽管与兼工带写的小写意在表现形式上有别,但写意精神却是相通的,李耕的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依然十分明显,如《十八罗汉》册页之一(图6)。
李霞作品以大写意为主,而李耕作品以小写意为主。上面说到李耕大写意,那仅仅是李耕的附产品,且基本上都是小品册页,这与李霞大写意多为大幅巨制,又形成一个有趣的反差。
而在线条的组合与笔墨变化上,李霞是以衣褶线纹结构与组合上的轻重、粗细、浓淡等线条形状的对比和行笔的顿挫曲屈、往来回环来体现笔墨形式美感(倾于工整细谨的作品除外),而李耕则在勾画衣褶线条时不刻意于粗细轻重的变化关系,而是一例用细线如硬笔速写般的一气呵成,其美感全部体现在线条组合的疏密与长短分布,再推及到挥写时的状态上,线与线之间的交织,穿插把对表现客体形神、动态的描写和作者的即时情感,超凡才思、精湛工夫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用细线率性勾画显然与李耕画幅尺寸不大有一定关系。如此两人同为竖立作画,而因画幅和毛笔性能不同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颇值研究。即如我评述其《八仙醉酒》所指出的:“通过线条的主导和牵引,编织出八仙的各自醉态,一群瘫在地上、烂醉如泥的人物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凭借线条以急就章的分行布白,演奏出上下左右逆来顺往、纵横交错的乐章,达成既有独立存在,又彼此关联的组合……线条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写形、传神、抒情、达意、聚气、载道。”该《八仙醉酒》的线条,就是我所说最能代表李耕风格一一线条一如工笔般没有明显粗细变化,但又充满着写意激情的别具一格的兼工带写法式。
相较于李霞的“稳”“正”,李耕的“变”“奇”能提供给大家的看点更多。接下去,再看看李耕的人物造型。
李耕的人物造型与李霞最大区别是,李耕动、奇,李霞静、正。毫无疑义,画家一种风格的确立,其中所有构成元素必然会不期然而然地与整体风格同步或者说相对应。唯其如此,风格的构成才不会有松散感、拼贴感,画面整体才会显的自然、妥帖、协调。李霞的造型如此,李耕的人物造型亦如是,即处处体现了“奇”与“变”。所谓人物造型的“奇”,就是指形体动态通过艺术夸张,使之更生动,更具艺术感染力。李耕造型的奇,最常见的是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来演绎:一是经常把站立姿势的高士和罗汉的身材比例拔高一至两个头(图7),这与李霞较为循规蹈矩、遵循既定的人体比例迥然有别,从中可以看到李耕乐于“标新立异”的思维(李耕这种修长高挑的人体比例在前人作品中罕有先例)。至于李耕为什么喜欢将人物比例拔高,凭我推测,可能是出于对罗汉西人形象身材高大的强化,而高士文人画得伟岸高挑一些可彰显其清高儒雅之气(与陈洪绶、金农的缩短人体比例以显示古拙相反)。还有一个原因是李耕勾画衣纹线条以细与长为基本特征,当然这与他将宣纸裱糊于墙壁上竖立作画形成的“势”有关。竖立作画线条的运行不受拘束,宜作长枪大戟式的挥写,虽然李霞也喜作长线条,不过李霞长而不细、线条弧度大,而李耕长而细的线条爽利硬朗喜欢长驱直下,如此有修长人物造型加上宽袍大袖,就会给作者进入“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创作状态时提供尽情发挥的余地。
二是通过夸张的造型来强化人物曲线美和作品的张力。具体样式主要有反弓形、弓形、“S”形。反弓形在修长身材的基础上再以挺胸腆肚来体现对象的轩昂之气或富贵之态,一般适用于高官贵胄贤达名士之流,其中最具曲线美的是人物侧身造型,能够集轩昂、高贵和优雅、飘逸于一身,比用正面或半侧身来表现更具典范性。弓形造型适用于表现老人或一些流传中已有定格的特形者,如老农民、老渔翁和某些仙、佛人物等。李耕画的老农民和老渔翁,其耸肩驼背的造型极夸张之能事,不仅能让人感受出历经沧桑、环境压迫的身世,更能够借助身体的大弧度以形成满弓待发之势,把作者顽强、坚毅、特立独行的品性,通过表现客体异乎常态的造型传诉出来。
三是捕捉生活中最典型、最生动和最契合观众审美心理,易于引发观众获得审美意趣的神情动态,通过艺术提炼作为“画眼”,使大家在中国画高雅形式中,分享到人性普遍认同的乐趣和乡土味、生活化的温情。奇中带趣,也是李耕艺术的一大特点,这不但缘于他对日常生活感受的真切和观察的细微,更得益于作为艺术家的奇异灵感、奇高天赋和奇绝的笔墨驾驭能力。审慎李耕所塑造每一个人物的一举手一投足,既有日常生活中各种动态的自然、随顺,也有艺术表现的概括和夸张,既合乎常识、常理、常情,又有滋、有味、有趣。为表述心理活动时信笔写出的斜乜眼、撇嘴、张嘴、蹙眉等五官细微变化,也绝不会让人觉得是那么稀松平常以致熟视无睹,而是以形体动态与神情和笔墨的高度协调统一生发出的“趣”来吸引你的视线,调动你的神经,引发你的联想,激起你对艺术的美妙之感。不信请看李耕描写生活常态的“四快”(呵欠、挠痒、通耳、喷嚏),憨态可掬的笑弥勒,奇形异状的罗汉,其风趣、诙谐、天真、顽劣,定教你会为之忍俊不禁,心理放松呢。(图8“四快”之一《通耳》)说实话,李霞人物造型的倒锥形、雕塑感、异乎寻常的大气、魁梧,不能不说也有奇的一面,但与李耕的奇相较,只能归之为与奇相对的正、稳一格了。
不可否认,“变”与“奇”本来就有必然联系,没有变,何来奇? 李耕以“变”来成就他的“奇”。下面,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谈一谈李耕艺术的另一看点,那就是“变”。
“变”在李耕作品中,又可分为多个层面。前面提到衣纹线条勾画和笔墨运用时,李耕惯用的以细线勾画为主的兼工带写一式时的“线形基本不变,但在组合与运行时极尽韵律变化之能事”,应视为变的一个方面或层面。李耕的变,还体现在敢于超越前人又不断超越自己的变,还有同题作品画面从不重复和雷同的变。这也是李耕与李霞,或者说与众多画家的不同之处。
超越前人,是指李耕的风格与画史上任何一家一法不同。如果把风格构成元素一一分开审视,也就是说,李耕的绘画语言进入成熟阶段,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有如苏词的“自是一家”。他用笔的洒脱、硬朗、坚实、朴野,造型上人体比例的拔高和夸张的大胆,动态神情的生动自然又奇趣横生,以大众化、通俗化艺术语言演绎高雅的、被奉为阳春白雪的水墨写意画,把平民思想融进道释和文人高士题材中去,他的感悟力、敏感度、创造性、异质思维使其在汲收古法的基础上能够“脱窠臼,出新意”,这许许多多特别之处,才成就其“独树一帜”与“自成一派”!超越自己,是指李耕在创作中从不重复自己,其中包括他一生中经历几个阶段画风的变化。与众多画家不同的是,他的画风从早期到晚期的变不仅仅体现在笔墨从幼稚走向成熟之变,更主要的是在艺术语言上的不断翻新,不断“脱胎换骨”。再者,就是他的同题作品画面从不雷同,例如他画过不计其数的弥勒佛,但从来没有出现过雷同重复现象,从中足证其创造力、想象力的非同一般,更可以感受出作为一个以画画为生的职业画师严谨、认真、拒绝平庸、不流俗套、追求卓越的创作态度和对艺术的一往深情。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画家,题材重复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画面的重复,李耕的可贵正在于此!人物画创作最难突破的是千人一面,尤其是没有历史影像可资借鉴、参考,仅靠文学作品描述或民间流传作为版本依据的古典人物画创作,局限于每一个画家的思维惯性和创作模式,人物形象描写极易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人物的形体外貌趋同化,必然导致界限的模糊,(除了某些特定人物如关公、弥勒佛、济颠、铁拐李、南极寿星等) 很多人物只能是靠服饰和道具的不同来加以辨识确认。但李耕就不一样,他笔下的人物,仙就是仙,佛就是佛,高士隐者、高官显胄、平民百姓等俱各气质不同,界限分明,即使同为女性,观音与麻姑,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神女仙妃与贤母民妇,虽一例端庄朴实,但骨子里透现出的不同性情气质依然清晰可辨。这些都得益于李耕对各个人物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笔墨语言运用的恰到好处。
除此之外,画面配景的山水、树木、烟云、屋宇和器物,李耕也做足了“变”的文章。例如他的树木主干用侧锋一笔上推或下贯,大面积留白的断云边缘不刻意于晕染过渡,对画面虚实切割的大胆果断,还有善于借助局部浓墨来强化对比效果,以调理整体、收拾局面等的随机应变能力,即使是构图——这一早已被前人形成法则,范式相对稳定,(如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等关系以及几种既成的布局图谱) 已经鲜有人能够突破的框架之内,李耕也能够做到新意迭出,其敢于造险又善于化险为夷和出奇制胜之高妙每每令人叹为观止!
三
最后谈一谈黄羲。
黄羲在仙游三画家中身份比较特殊,因为他少年时曾有过追随李耕学画的经历,几年后又转而师事李霞。有趣的是,师徒三人年龄相差各14岁(李霞生于1871年,李耕生于1885年,黄羲生于1899年),也可以算为同时代人,却由于师徒关系,黄羲又常常被认为是李霞、李耕的下一辈。
鉴于他们三人的艺术各有千秋,且黄羲又接受和从事过现代美术教育,所以他的画虽保持了仙游(或福建) 的地方流派显著特色,但已与现代审美取向和创作理念达成某些对接,成为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人物。因此将黄羲与李霞、李耕纳入同一体系去研究,置于同一平面去审视,不仅能为仙游传统人物画增添不少光彩,也给这一传统画派如何融入现代元素和适应时代要求,提供了重要借鉴。我们要深刻认识黄羲承前启后的意义,对他的艺术,尤其是对他绘画风格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把传统人物画衣褶线纹的表现形式应用到现代美术教育所重视的人体写实中去,特别是能在实践过程及其效果上达到自然而然的无缝对接,这就是黄羲的极高明之处。当然,选择这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是黄羲的聪明之举。因为,就对纯正传统笔墨掌握的火候言之,他无意,当然也无须做李霞第二;就画才、灵气以及对当地民间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李耕无疑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和条件。同时,环境、时势、本身性格等因素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跟在两位前辈后面亦步亦趋。正在这时,上苍为他做了最好的安排,那就是当时西洋画法被大量引用到美术教育中,黄羲赶上这个时代,成了既获得过传统技法严格训练,又接受到现代美术教育的左右逢源、中西共享的娇子。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昌明艺术专科学校和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美术学院聘请任教,吴昌硕、王一亭、诸闻韵、潘天寿、黄宾虹的垂青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折芦描是黄羲最常用,也是运用得最为得心应手的一种传统衣纹描法。
大概是该描法运笔的起承转合、线条的粗细浓淡变化对勾画人体各式动作所形成衣纹折褶既能接近真实,又富有传统用笔追求的韵律和变化意趣吧。
黄羲折芦描特点是起笔爽劲利索,转折明快自然,落墨精准,线条刚柔相济,不矫不饰又不粘不滞,与他的温润水墨、明净色彩、优雅准确造型共同编织成清新秀逸、严谨闳约的画风。因此,他的这一有如清风朗月的风格,在表现女性题材,尤其是既具传统仕女幽婉娴淑、矜持古雅特质,又捎带着仙家潇洒出尘、超逸虚灵的麻姑形象,更是入情入理,出神入化,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见图9)。另外,由于黄羲具备了现代绘画中的人体写实基础和透视、光影知识,对仙佛、高士的塑造较之李霞、李耕也另有一种韵味。例如他笔下的弥勒、钟馗,用笔墨勾画点染出的脸庞和人体,骨感清晰、肌理分明,但又不等同于素描加色彩那么僵硬机械,而是“取笔力生动为魂,以形象轮廓为魄”(黄羲语) 是充满了笔情墨趣的“中国式传神写照”。(见图10《钟馗》)我在《为闽派注入新鲜血液的画家——黄羲》(载《中国书画报》2016第21期) 中将黄羲古典人物画创作特点概括为:“一是继承了传统国画把线描作为主要表现载体的正脉,然后又合乎情理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体结构等相关知识,通过线条和笔墨的转折、粗细、长短、浓淡等平面组合和穿插来表现人物动态变化所产生的衣褶线纹,解决透视、结构上‘立体’的形问题;二是通过线条运行的轻重、疾徐、顿挫等节奏韵律来抒发个人情感,获得与表现对象气质神情的相互贯通,以达成传统意义上的‘以形写神’。”这一运用严谨、认真、毫不含糊的态度去对待人物的形,借助传统线条的意写、兴会去解决形与神、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自然地使得他与李霞、李耕在审美追求、笔墨构成上各有侧重、各呈风采。应该说,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点——不仅仅表现在笔墨上的清雅与浑厚、洒脱与严谨,而有着更为深层的、本质上的区别。
(四)
最后,我就上述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总结。
艺术风格是艺术家创作个性与艺术作品的语言、情意交互作用所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整体艺术特色。因此,我们在谈到李霞、李耕、黄羲三画家风格时,除了从笔墨的或浑穆厚重、或洒脱奇肆、或清新秀逸等外在形式去审视,更需要去探究笔墨后面那些深层次问题,如作者的创作理念、审美追求、表述形式,还有作者的性格气质、学养阅历、成长环境等等。唯其如此,风格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存在和表层的形象,也才会透过风格这一现象去发现和发掘更具实质意义的无穷信息和无尽玄机。基于此,我才对这一看似简单,只需一目了然即可定调的三人不同画风中,牵引出许多相关话题。毫无疑义,倘若李霞没有身上的豪迈之气和游历四方、广交名士的经历,也就没有他的胆识之高和气魄之大,进而决定了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的选择及其笔墨气势的形成。如果李耕不植根本土、立足民间、自强自立、依靠非凡的悟性和坚毅的品性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志趣,他的作品也就不会如此地既接地气,又能新意迭出、奇趣横生! 同样,如果黄羲不走出仙游,寻找传统与现代对接之路,黄羲也就不会成为现在的黄羲,也许,仙游这一绘画流派在他身上,依然只局限在闽派的单向延续而看不到发展的另一种形式。
从同一性中看到多样性,仙游的画家群,也就不会因地域的局限和民间的身份而自惭形秽了。
本文发表于2017年第3期《中国书画报》
2014年7月7日,“福建省中职骨干教师培训班”在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开学,本人应邀作了“李霞、李耕国画风格比较”专题讲座,实际上,该讲座是对《仙游画家“二李”述评》的延续和深化,着重从中国画作品构成元素中去寻找两人表现形式的差异和论述双方艺术的不同点。我想,面对学员听众,通过具体分析会比空泛的理论表述更深刻,更具说服力。
本文便是对这一讲座稿的整理和充实,特别是把在本次讲座中因时间关系没有提到的仙游另一位代表性画家黄羲先生一并纳入,使得这一地方绘画流派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完整的体系,外界也能从仙游古典人物传统的“同”中看到“异”,从静态的、固化的流派体解到动态的流变和发展,并通过普遍性与特殊性、不变与变的回环观照,获得更清晰的镜头和更全面、深入的认知和理解。无疑,这对于仙游古典人物画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对长期处于低谷或者说被边缘化的中国画古典人物研究和创作,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借鉴、启示甚至推动作用。
一
以年龄和资历论,李霞长于李耕,又早出道,因此我们先谈李霞。首先从构成中国画风格的最主要元素——笔墨去切入。
李霞笔墨雄放旷迈,古穆浑厚,这一特征在写意巨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代表作有《关公》《钟馗》、“八仙”(四条屏)、“忠、孝、廉、节”(四条屏)、《麻姑》《寿星》等。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霞画面笔墨构成效果,首先得益于他所使用的自制鸡颖笔。鸡颖笔既有羊毫贮墨多,又有狼毫弹性强的特殊性能,易控制,好发挥,由之使李霞的线条能够在重按轻提、上下其手的往来变化中显示出一气呵成、连绵不断的气韵,在畅快通达中保持了线条轻重粗细的韵律节奏。李霞作写意巨幅,多用吸墨性能强的夹宣,以增益墨色温厚之气。在体现其雄迈风格的以粗、重、大、长线条为特征的信笔挥写时,凭着中锋使转的运笔功力与锋颖的弹性,做到先行的,作为主干的阔笔不粘不滞;后续的,作为辅翼的细线不枯不薄。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李霞作巨幅时,务需将宣纸裱糊于墙壁上竖立作画,却能控制到毫颖贮墨如此饱满而不致流淌下来,这与行笔速度之疾以及落纸时先以粗线阔笔构就主体,然后辅以细线的笔迹运行速度和顺序有直接关系。而这些笔墨构成特征,也有意无意促成了李霞雄阔酣畅、大气磅礴风格的形成,这从《富贵寿考》(图1) 中行笔轨迹可以得到证明。
李霞旷迈雄放的另一表现是在人物画创作过程中对形与神关系的拿捏,(也可以引申为笔墨所发挥再现与表现功能的理解与应用上)这从他的《髓石子自序》中已有所表白:“国画尚笔法精神,西法尚透视写生,时趋不同,各有所长”。基于此,他在实施线条对人物形体描绘时才敢于把追求笔墨气韵之生动凌驾于对形体准确性的斤斤计较和过分附就之上,颇有点像善诗者的“不因辞害意”。如《铁拐李》(图2) 对画面笔墨主体的宽大衣袖衣纹线条处理,便带有较多主观成分,也就是将笔墨气韵及其形式美感作为展示自己功力和宣示艺术立场的一角舞台,从而把师法黄慎以草书入画体式发挥到极致。须知,李霞所处时代,西学东渐之风正炽,而人物画创作一般又侧重于写实,这一以笔墨神采气韵去调取观众视觉神经,对具体形态一些细枝末节的淡化甚至大胆删削,正是中国画写意传统中“遗貌取神”“得意忘形”的践履,也是李霞魄力与气度、胆识与性格的一种表现。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所指出的李霞风格的雄迈旷放、古穆浑厚无非是出自他作品尺幅之大,线条的粗阔疏放等外在形式上,那就有点误解了。
李霞作品的大气磅礴,绝不能视同为那些虚张声势的笔墨演示,而是紧随着蓄力重按、阔笔悍写之后,能够有效地利用鸡颖笔毫的超强弹性,就在笔尖恢复原状的当儿乘势而下,或急起直追,或舒缓从容,于长拉短拽、迂回穿插中各臻其妙。这些灵动活泼、轻松随意元素的注入,顿使原本在粗壮硕大主线重压下显得有些沉闷的“局”顿时被带活起来,笔墨也丰富起来。
仙游九鲤湖以瀑布成九漈而名扬天下。我想,李霞画中的大笔,岂不是雷霆万钧的“珠帘漈”? 而数笔作为辅助、映衬的细线,又恰如旁边从草丛石缝中溢出涓涓细流的“玉柱漈”,诚所谓“珠帘玉柱,瀑流交映”!李霞的艺术创作不正是大自然的翻版和老子朴素辩证法的实践?一般认为,举凡一幅写意画,其所用阔笔大线条,犹如书写榜书,纵有浪漫情怀,亦难能心手如一,若欲抒发性灵得其酣畅飞动之势殊为不易,故只能诉诸沉稳拙厚以彰显其腕底功力,寄寓雄迈之气。而李霞的巨幅写意,阔笔粗放间的回环使转能于拙厚凝重中达到不粘不滞的气脉通畅,确实显示了李霞的不凡功力。然而从李霞重、拙笔墨所捎带的洒落遒劲、收放自如的细线,又可以体味到李霞“致广大”后的“尽精微”——既有运斤成风气势,又有春蚕吐丝的和缓与柔韧,大而能放,细亦不弱。我曾在《铅华扫尽见精微——李霞〈孟母择邻图〉解赏》一文中就提到:“李霞以擅写巨幅,喜运阔笔,画面以恢宏博大闻名,但从这幅尺幅不大(指《孟母择邻图》)的立轴中那扫尽铅华和细腻精微的笔墨中,我们看到了画家的另一面。”算是提示人们对李霞另一风格的关注。下面我要介绍的是李霞工细笔一路的代表作《十八罗汉过江图》(图3)。
《十八罗汉过江图》为水墨长卷,李霞1935年65岁时作于上海。该卷人物及其衣纹,罗汉坐骑虎、狮、象与天上云龙、各种法器、江面波浪以及岸际窠石山坡、虬松枯树,一例古法森严;线条勾画一丝不苟,规整而不失灵动;人物古穆奇逸、意态从容;笔墨淡淡荡荡,一派祥和,整体格调协和古雅。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李龙眠、贯休、吴彬、曾鲸等前辈大家的不同程度影响,还可以领略到李霞在践行:“窃意专攻写意,恐流粗率;专攻线纹,恐失拘牵”(《髓石子自序》) 时于线纹这一端力求“不失拘牵”的出色表现,其画风的严谨,画技的精湛,画格的淳雅,深获当时艺术素养深厚的政界大佬推许,为之题跋的有林森、于右任、许世英、黄葆戉等,殊为难得。
趋于工谨细致,可归入兼工带写一路的作品还有载于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四聘”(《耕稼登庸》《钓璜待聘》《秦穆求贤》《三顾草庐》)四条屏,比较特别的是该套作品乃是把山水作为画面主体,而人物不是十分显眼,若当作李霞的山水画也无不可。其中山水画法直追宋元,高古浑穆,与图中的人物风格浑然一体。说明了《髓石子自序》中所称其“间赏博考历代名家画迹”的同时亦下过一定功夫去实践。而晚年创作的“廿四孝”组画,“用笔灵动随性,书卷气浓厚,人物多以细线勾出,比例准确,衣纹纵横争折,夹带左右,人情世态表现十分鲜活,尊卑贵贱,老幼妇孺,各具身份,室内陈设、器皿透视合理,图案纹饰变化丰富,农舍、庭院取自生活所见,自然亲切,背景用小写意手法画出,与人物运线对比,益觉生动。”(黄羡《雄浑古穆、意趣超然——画家李霞的艺术成就》载台湾省《历史文物》2007.04)李霞作为以画画谋生的职业画家,必然会考虑到不同层次的买家和不同的场所及用途。其巨幅作品以笔墨旷迈雄放,人物形象的沉稳端庄所显示的正大富贵之气为富户豪门所喜爱,作品悬挂在高宅大院的厅堂,十分匹配。工谨画法乃是顾及到人物画所不应回避的叙事功能,对历史故事的描述乃是人物画创作的应有之义,由于叙事题材在故事情节表现上有对真实性、完整性、生动性的特殊要求,限定了其表述方式也必须趋于循规蹈矩、严谨严肃,对故事的发生地和背景当有所交代,所以配景也不能太过大意和粗疏,这就是李霞作品既有大幅巨幛的大气磅礴,又有一般规格之精细工谨的由来。不过,基于李霞的性情气质、审美取向和深厚功力,有些作品虽然尺幅不大,笔画工细,结构严谨,但仍然不失其旷达雄浑与沉郁酣畅之气。
海派巨擘吴昌硕曾称李霞为“人物第一家”,可以想见两人应有一定的情缘。李霞衣纹勾画还引入了吴昌硕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法。当然,李霞私淑黄慎,尤以草书入画传其衣钵,得其神髓,因此其草书也承袭了黄慎的神采风韵,跌宕起伏而流转自如。从他的衣纹线条中,古人推重书法行笔的“折钗股”“屋漏痕”“高山坠石”“万岁枯藤”等形迹随处可见。
从阔笔讲到细线,从拙厚讲到灵动,从疏放讲到严谨,线条的粗细长短、浓淡枯润、纵横曲直的排列、组合、穿插、腾挪和对比中编织出笔墨平面上的形式美,又从线条运行的起止、疾徐、顿挫、轻重、去留中演示出一笔一画的韵律美,这就是李霞的线条特色,但这仅仅止于狭义的笔墨层面。下面,我们再谈李霞的人物造型。
李霞塑造的人物形象,古穆端肃而风骨魁奇,其立式造型多呈倒锥形,即上身宽博,下身逐渐收紧收窄,有很强的雕塑感和形式感。尤以《麻姑》(参见P114《李耕写意人物画综论》图57)最为典型,已然成了李霞作品的独特符号,想必应与李霞的海派情结有关,李霞生前出版的两本画册都是在上海印刻,这在印刷业不发达的当时颇为稀罕,海派艺术对李霞势必形成一定影响。十分明显,李霞的麻姑造型与钱慧安十分相似。这一倾向于静态的造型正契合了李霞所欲建立的沉、厚、稳的画面基调,更为李霞运笔时习惯性的自上而下注气(巨幅宣纸裱于墙上直立作画笔迹运行的必然趋势)提供纵向之势(静态的倒锥型或直立式造型必以纵向线条来支撑),这样,也就产生了李霞人物画又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李霞的人物画表现形式上正好对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外静内动”形态——即为了凝神聚气,成其浑穆壮美之势,李霞的人物造型大多保持稳重、沉静这一基本特征,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先是用阔笔箍住整体轮廓,尽量避免气力外泄。故此,李霞用笔较少向四周发散辐射,笔墨的变化、线条的流动,一般都是在大轮廓之内进行。这在他的代表作如巨幅关公、麻姑、钟馗、寿星等造像式人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鉴于此,我对过去曾将李霞与李耕艺术风格比之为五代时期花鸟画两大流派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后又将他们的艺术风格推及到儒道两家思想的高度予以归类,认为李霞偏于儒家,重规矩、尊古法,作品庙堂气浓厚,是入世的。而李耕不管是人生态度或艺术追求,都倾向于道家回归自然、向往自由、崇尚朴素的思想,因此他的创作不拘成法,极具个性,展现的是江湖朴野之风。通过对二人作品的进一步认识,觉得还有必要申明:“就笔墨、造型等具体运作程式而言,李霞从中有意无意地演绎着道家的圆浑、内敛、古穆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而李耕挥毫恣肆、率直硬朗的锋芒毕露,奇趣横生、灵气四溅的才气外溢,反倒表露出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意态,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构图在古代南齐谢赫的中国画六法中又称“经营位置”,先人于此已创造了诸多图法并加以理论的诠释并形成范式,总绕不开用老子朴素辩证法来处理虚实、浓淡、简繁、疏密、横直、远近等的关系,只不过作者在实践应用过程中,根据不同内容和形式,对这些关系处理的机巧和灵活度各个有所不同罢了。李霞画风偏于纯正沉稳,因此构图上也相应地四平八稳,甚少有惊人之举和独创图式。他的出彩部分,或者说最具震撼力的地方,是用笔的高人一筹及其人物形象塑造与笔墨、构图等整体画面的高度协和,并从这一协和中升华出中华文化的端肃之体、正大之气!我在《仙游画家“二李”述评》中还顺便提到了“李霞在传统颜料使用和色彩火候的把握上也堪称大匠。他的作品是研究传统色彩学的极好范本” 。虽然写意画并不十分在意颜色问题,但对李霞中国画风格的综合评述,我想还得再次提到他的用色。也许是前期水墨晕染功夫的到位之故,李霞在画面上所罩颜色,尤其是朱砂、赭石一类暖色,与墨气每每能浑融一体,了无涂抹痕迹,更无一丝一毫的火气和轻薄妖艳之气,予人感觉的是自然沉淀晕化下的醇厚、温润、丰腴、平和。
二
李耕画风奇特,个性张扬,富新意、善变化。如果说李霞以稳重、宏大、深厚、旷放等来构筑他的艺术世界,那么李耕则是以奇肆、朴野、超逸、爽朗贯穿着他的艺术主线。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差别是:李霞中国画风格自始至终没有太大变化,其演进脉络呈直线渐进式,如果真要找出变化,那就是从早期的“稚嫩”走向后期的“成熟、老到”。而李耕风格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变化,呈跳跃式、波动状的发展轨迹。例如20世纪20年代前的年轻时期画风酷似李霞,人物造型也是倒锥形上宽下窄,衣纹勾画也用宽笔粗线,由于李耕是左手笔,挟笔多现欹侧之势,因此起笔或转折时露圭角,峭削而凌厉,如《东坡笠屐》(图4),此与李霞的中锋阔笔的飞白不尽相同。但又不难看出两人共同承袭黄慎而笔迹出现的一些差别。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李耕画风又是一变,笔墨恣肆奔放。及至30年代末又来一个脱胎换骨,造型由原来的束缚转向疏朗、生动,风格已渐脱前人的桎梏而现出自己的特点。即一改原来的狂肆张扬、略觉乖张的意笔大写,转而为平淡从容的以细线勾写为主的兼工带写法式,到这个时期,“李耕体”写意和“李耕体”工笔才定形下来(图5),从此不断迈向成熟。最终成为代表李耕风格的最主要体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李耕在不拘成法的强烈创新意识支配下,其作品多为通过细线勾勒抒发自己写意情怀的“兼工带写”法式和外形较为均匀工谨而不失写意性的“工笔画”,但一直也不放弃形式上更抒情,笔墨上更放纵、更富变化,人物形态更有趣,形象更夸张的大写意,或以水墨没骨泼写,或以粗线简写。此类大写意尽管与兼工带写的小写意在表现形式上有别,但写意精神却是相通的,李耕的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依然十分明显,如《十八罗汉》册页之一(图6)。
李霞作品以大写意为主,而李耕作品以小写意为主。上面说到李耕大写意,那仅仅是李耕的附产品,且基本上都是小品册页,这与李霞大写意多为大幅巨制,又形成一个有趣的反差。
而在线条的组合与笔墨变化上,李霞是以衣褶线纹结构与组合上的轻重、粗细、浓淡等线条形状的对比和行笔的顿挫曲屈、往来回环来体现笔墨形式美感(倾于工整细谨的作品除外),而李耕则在勾画衣褶线条时不刻意于粗细轻重的变化关系,而是一例用细线如硬笔速写般的一气呵成,其美感全部体现在线条组合的疏密与长短分布,再推及到挥写时的状态上,线与线之间的交织,穿插把对表现客体形神、动态的描写和作者的即时情感,超凡才思、精湛工夫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用细线率性勾画显然与李耕画幅尺寸不大有一定关系。如此两人同为竖立作画,而因画幅和毛笔性能不同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颇值研究。即如我评述其《八仙醉酒》所指出的:“通过线条的主导和牵引,编织出八仙的各自醉态,一群瘫在地上、烂醉如泥的人物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凭借线条以急就章的分行布白,演奏出上下左右逆来顺往、纵横交错的乐章,达成既有独立存在,又彼此关联的组合……线条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写形、传神、抒情、达意、聚气、载道。”该《八仙醉酒》的线条,就是我所说最能代表李耕风格一一线条一如工笔般没有明显粗细变化,但又充满着写意激情的别具一格的兼工带写法式。
相较于李霞的“稳”“正”,李耕的“变”“奇”能提供给大家的看点更多。接下去,再看看李耕的人物造型。
李耕的人物造型与李霞最大区别是,李耕动、奇,李霞静、正。毫无疑义,画家一种风格的确立,其中所有构成元素必然会不期然而然地与整体风格同步或者说相对应。唯其如此,风格的构成才不会有松散感、拼贴感,画面整体才会显的自然、妥帖、协调。李霞的造型如此,李耕的人物造型亦如是,即处处体现了“奇”与“变”。所谓人物造型的“奇”,就是指形体动态通过艺术夸张,使之更生动,更具艺术感染力。李耕造型的奇,最常见的是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来演绎:一是经常把站立姿势的高士和罗汉的身材比例拔高一至两个头(图7),这与李霞较为循规蹈矩、遵循既定的人体比例迥然有别,从中可以看到李耕乐于“标新立异”的思维(李耕这种修长高挑的人体比例在前人作品中罕有先例)。至于李耕为什么喜欢将人物比例拔高,凭我推测,可能是出于对罗汉西人形象身材高大的强化,而高士文人画得伟岸高挑一些可彰显其清高儒雅之气(与陈洪绶、金农的缩短人体比例以显示古拙相反)。还有一个原因是李耕勾画衣纹线条以细与长为基本特征,当然这与他将宣纸裱糊于墙壁上竖立作画形成的“势”有关。竖立作画线条的运行不受拘束,宜作长枪大戟式的挥写,虽然李霞也喜作长线条,不过李霞长而不细、线条弧度大,而李耕长而细的线条爽利硬朗喜欢长驱直下,如此有修长人物造型加上宽袍大袖,就会给作者进入“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创作状态时提供尽情发挥的余地。
二是通过夸张的造型来强化人物曲线美和作品的张力。具体样式主要有反弓形、弓形、“S”形。反弓形在修长身材的基础上再以挺胸腆肚来体现对象的轩昂之气或富贵之态,一般适用于高官贵胄贤达名士之流,其中最具曲线美的是人物侧身造型,能够集轩昂、高贵和优雅、飘逸于一身,比用正面或半侧身来表现更具典范性。弓形造型适用于表现老人或一些流传中已有定格的特形者,如老农民、老渔翁和某些仙、佛人物等。李耕画的老农民和老渔翁,其耸肩驼背的造型极夸张之能事,不仅能让人感受出历经沧桑、环境压迫的身世,更能够借助身体的大弧度以形成满弓待发之势,把作者顽强、坚毅、特立独行的品性,通过表现客体异乎常态的造型传诉出来。
三是捕捉生活中最典型、最生动和最契合观众审美心理,易于引发观众获得审美意趣的神情动态,通过艺术提炼作为“画眼”,使大家在中国画高雅形式中,分享到人性普遍认同的乐趣和乡土味、生活化的温情。奇中带趣,也是李耕艺术的一大特点,这不但缘于他对日常生活感受的真切和观察的细微,更得益于作为艺术家的奇异灵感、奇高天赋和奇绝的笔墨驾驭能力。审慎李耕所塑造每一个人物的一举手一投足,既有日常生活中各种动态的自然、随顺,也有艺术表现的概括和夸张,既合乎常识、常理、常情,又有滋、有味、有趣。为表述心理活动时信笔写出的斜乜眼、撇嘴、张嘴、蹙眉等五官细微变化,也绝不会让人觉得是那么稀松平常以致熟视无睹,而是以形体动态与神情和笔墨的高度协调统一生发出的“趣”来吸引你的视线,调动你的神经,引发你的联想,激起你对艺术的美妙之感。不信请看李耕描写生活常态的“四快”(呵欠、挠痒、通耳、喷嚏),憨态可掬的笑弥勒,奇形异状的罗汉,其风趣、诙谐、天真、顽劣,定教你会为之忍俊不禁,心理放松呢。(图8“四快”之一《通耳》)说实话,李霞人物造型的倒锥形、雕塑感、异乎寻常的大气、魁梧,不能不说也有奇的一面,但与李耕的奇相较,只能归之为与奇相对的正、稳一格了。
不可否认,“变”与“奇”本来就有必然联系,没有变,何来奇? 李耕以“变”来成就他的“奇”。下面,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谈一谈李耕艺术的另一看点,那就是“变”。
“变”在李耕作品中,又可分为多个层面。前面提到衣纹线条勾画和笔墨运用时,李耕惯用的以细线勾画为主的兼工带写一式时的“线形基本不变,但在组合与运行时极尽韵律变化之能事”,应视为变的一个方面或层面。李耕的变,还体现在敢于超越前人又不断超越自己的变,还有同题作品画面从不重复和雷同的变。这也是李耕与李霞,或者说与众多画家的不同之处。
超越前人,是指李耕的风格与画史上任何一家一法不同。如果把风格构成元素一一分开审视,也就是说,李耕的绘画语言进入成熟阶段,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有如苏词的“自是一家”。他用笔的洒脱、硬朗、坚实、朴野,造型上人体比例的拔高和夸张的大胆,动态神情的生动自然又奇趣横生,以大众化、通俗化艺术语言演绎高雅的、被奉为阳春白雪的水墨写意画,把平民思想融进道释和文人高士题材中去,他的感悟力、敏感度、创造性、异质思维使其在汲收古法的基础上能够“脱窠臼,出新意”,这许许多多特别之处,才成就其“独树一帜”与“自成一派”!超越自己,是指李耕在创作中从不重复自己,其中包括他一生中经历几个阶段画风的变化。与众多画家不同的是,他的画风从早期到晚期的变不仅仅体现在笔墨从幼稚走向成熟之变,更主要的是在艺术语言上的不断翻新,不断“脱胎换骨”。再者,就是他的同题作品画面从不雷同,例如他画过不计其数的弥勒佛,但从来没有出现过雷同重复现象,从中足证其创造力、想象力的非同一般,更可以感受出作为一个以画画为生的职业画师严谨、认真、拒绝平庸、不流俗套、追求卓越的创作态度和对艺术的一往深情。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画家,题材重复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画面的重复,李耕的可贵正在于此!人物画创作最难突破的是千人一面,尤其是没有历史影像可资借鉴、参考,仅靠文学作品描述或民间流传作为版本依据的古典人物画创作,局限于每一个画家的思维惯性和创作模式,人物形象描写极易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人物的形体外貌趋同化,必然导致界限的模糊,(除了某些特定人物如关公、弥勒佛、济颠、铁拐李、南极寿星等) 很多人物只能是靠服饰和道具的不同来加以辨识确认。但李耕就不一样,他笔下的人物,仙就是仙,佛就是佛,高士隐者、高官显胄、平民百姓等俱各气质不同,界限分明,即使同为女性,观音与麻姑,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神女仙妃与贤母民妇,虽一例端庄朴实,但骨子里透现出的不同性情气质依然清晰可辨。这些都得益于李耕对各个人物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笔墨语言运用的恰到好处。
除此之外,画面配景的山水、树木、烟云、屋宇和器物,李耕也做足了“变”的文章。例如他的树木主干用侧锋一笔上推或下贯,大面积留白的断云边缘不刻意于晕染过渡,对画面虚实切割的大胆果断,还有善于借助局部浓墨来强化对比效果,以调理整体、收拾局面等的随机应变能力,即使是构图——这一早已被前人形成法则,范式相对稳定,(如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等关系以及几种既成的布局图谱) 已经鲜有人能够突破的框架之内,李耕也能够做到新意迭出,其敢于造险又善于化险为夷和出奇制胜之高妙每每令人叹为观止!
三
最后谈一谈黄羲。
黄羲在仙游三画家中身份比较特殊,因为他少年时曾有过追随李耕学画的经历,几年后又转而师事李霞。有趣的是,师徒三人年龄相差各14岁(李霞生于1871年,李耕生于1885年,黄羲生于1899年),也可以算为同时代人,却由于师徒关系,黄羲又常常被认为是李霞、李耕的下一辈。
鉴于他们三人的艺术各有千秋,且黄羲又接受和从事过现代美术教育,所以他的画虽保持了仙游(或福建) 的地方流派显著特色,但已与现代审美取向和创作理念达成某些对接,成为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人物。因此将黄羲与李霞、李耕纳入同一体系去研究,置于同一平面去审视,不仅能为仙游传统人物画增添不少光彩,也给这一传统画派如何融入现代元素和适应时代要求,提供了重要借鉴。我们要深刻认识黄羲承前启后的意义,对他的艺术,尤其是对他绘画风格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把传统人物画衣褶线纹的表现形式应用到现代美术教育所重视的人体写实中去,特别是能在实践过程及其效果上达到自然而然的无缝对接,这就是黄羲的极高明之处。当然,选择这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是黄羲的聪明之举。因为,就对纯正传统笔墨掌握的火候言之,他无意,当然也无须做李霞第二;就画才、灵气以及对当地民间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李耕无疑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和条件。同时,环境、时势、本身性格等因素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跟在两位前辈后面亦步亦趋。正在这时,上苍为他做了最好的安排,那就是当时西洋画法被大量引用到美术教育中,黄羲赶上这个时代,成了既获得过传统技法严格训练,又接受到现代美术教育的左右逢源、中西共享的娇子。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昌明艺术专科学校和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美术学院聘请任教,吴昌硕、王一亭、诸闻韵、潘天寿、黄宾虹的垂青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折芦描是黄羲最常用,也是运用得最为得心应手的一种传统衣纹描法。
大概是该描法运笔的起承转合、线条的粗细浓淡变化对勾画人体各式动作所形成衣纹折褶既能接近真实,又富有传统用笔追求的韵律和变化意趣吧。
黄羲折芦描特点是起笔爽劲利索,转折明快自然,落墨精准,线条刚柔相济,不矫不饰又不粘不滞,与他的温润水墨、明净色彩、优雅准确造型共同编织成清新秀逸、严谨闳约的画风。因此,他的这一有如清风朗月的风格,在表现女性题材,尤其是既具传统仕女幽婉娴淑、矜持古雅特质,又捎带着仙家潇洒出尘、超逸虚灵的麻姑形象,更是入情入理,出神入化,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见图9)。另外,由于黄羲具备了现代绘画中的人体写实基础和透视、光影知识,对仙佛、高士的塑造较之李霞、李耕也另有一种韵味。例如他笔下的弥勒、钟馗,用笔墨勾画点染出的脸庞和人体,骨感清晰、肌理分明,但又不等同于素描加色彩那么僵硬机械,而是“取笔力生动为魂,以形象轮廓为魄”(黄羲语) 是充满了笔情墨趣的“中国式传神写照”。(见图10《钟馗》)我在《为闽派注入新鲜血液的画家——黄羲》(载《中国书画报》2016第21期) 中将黄羲古典人物画创作特点概括为:“一是继承了传统国画把线描作为主要表现载体的正脉,然后又合乎情理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体结构等相关知识,通过线条和笔墨的转折、粗细、长短、浓淡等平面组合和穿插来表现人物动态变化所产生的衣褶线纹,解决透视、结构上‘立体’的形问题;二是通过线条运行的轻重、疾徐、顿挫等节奏韵律来抒发个人情感,获得与表现对象气质神情的相互贯通,以达成传统意义上的‘以形写神’。”这一运用严谨、认真、毫不含糊的态度去对待人物的形,借助传统线条的意写、兴会去解决形与神、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自然地使得他与李霞、李耕在审美追求、笔墨构成上各有侧重、各呈风采。应该说,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点——不仅仅表现在笔墨上的清雅与浑厚、洒脱与严谨,而有着更为深层的、本质上的区别。
(四)
最后,我就上述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总结。
艺术风格是艺术家创作个性与艺术作品的语言、情意交互作用所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整体艺术特色。因此,我们在谈到李霞、李耕、黄羲三画家风格时,除了从笔墨的或浑穆厚重、或洒脱奇肆、或清新秀逸等外在形式去审视,更需要去探究笔墨后面那些深层次问题,如作者的创作理念、审美追求、表述形式,还有作者的性格气质、学养阅历、成长环境等等。唯其如此,风格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存在和表层的形象,也才会透过风格这一现象去发现和发掘更具实质意义的无穷信息和无尽玄机。基于此,我才对这一看似简单,只需一目了然即可定调的三人不同画风中,牵引出许多相关话题。毫无疑义,倘若李霞没有身上的豪迈之气和游历四方、广交名士的经历,也就没有他的胆识之高和气魄之大,进而决定了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的选择及其笔墨气势的形成。如果李耕不植根本土、立足民间、自强自立、依靠非凡的悟性和坚毅的品性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志趣,他的作品也就不会如此地既接地气,又能新意迭出、奇趣横生! 同样,如果黄羲不走出仙游,寻找传统与现代对接之路,黄羲也就不会成为现在的黄羲,也许,仙游这一绘画流派在他身上,依然只局限在闽派的单向延续而看不到发展的另一种形式。
从同一性中看到多样性,仙游的画家群,也就不会因地域的局限和民间的身份而自惭形秽了。
本文发表于2017年第3期《中国书画报》
相关地名
莆田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