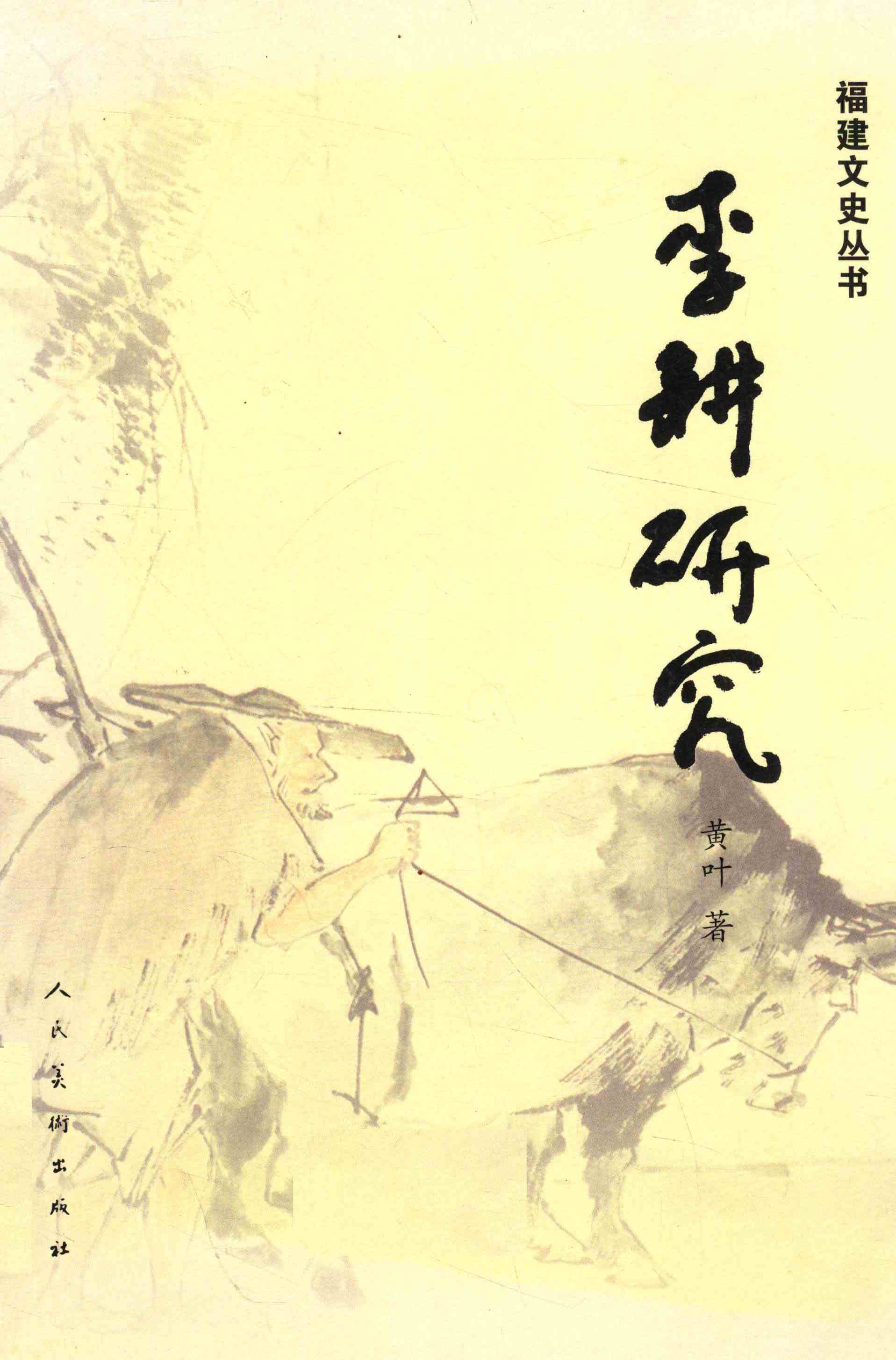内容
上一章节末尾“变化为宗”,是对李耕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怎样不断超越古人、超越他人、超越自己上去论述。本章列述李耕各个时期的不同风格,则是对李耕写意人物画风格演进轨迹的一番梳理,其间实际也包含了三个超越,尤其是“超越自己”这一最为重要的层面。
我们看到,李耕各个时期或曰各个阶段画风变化虽然十分明显,但演化脉胳却是清晰的,不像一些画家一生风格保持太过稳定而易于给人留下创造力不足,创新意识不强的印象;也不像一些画家为标新立异而忽左忽右地在“跳山头”,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最终在创作道路上形不成一条主线。(注意,这与艺术追求上的“转益多师”不可同日而语,善于转益多师者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一贯信念和主张,转益多师只是广征博取的一种方法或手段而已)因此,分析李耕各个时期画风的嬗变,对于研究李耕艺术是很重要的一环。
李耕写意人物画风格的嬗变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只能从存世的李耕作品最早创作时间,即20世纪初算起至20年代初期。这个时段,李耕正由寺庙壁画向卷轴画转型,也是李耕在乃父殁后,开始自己摸索、选择艺术道路和创作方向的节点。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李耕父亲说起。李耕父亲李墀,字步丹,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民间画师,一生以画寺庙壁画、雕塑神像和人物肖像为业,可惜真正属于他创作的作品似已绝迹,当然也就无从得知他的画究竟出自何家何法。但凭我推断,李墀受福建本土画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依据如下:一是由于福建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所限,经济、文化偏安一隅,受外地影响、渗透比较少,文化相互交流基本上囿于福建本土之间。距时较近的闽西上官周、黄慎、华喦在福建当地影响很大,要睹其原作机会相对多,学习方便。二是从他的弟子作品可以得以部分印证。例如至今保存较完整的仙游县游洋镇龙山书院朱学田壁画,闽派人物画特点就十分突出,朱氏与李墀既是邻居,又是及门弟子。另外与李耕同时代的当地另一著名人物画家李霞(比李耕年长14岁)早岁曾师从李墀学艺,对黄慎笔墨技法之用功可谓始终不渝,此应与当年李墀引导不无关系。李耕初学画时以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为范本(后来他自己课徒时也有同样要求),进入写意人物画创作初期画风又与李霞极为相似,盖因师出同门。依此类推,也可以得出李墀私淑于福建本土诸先辈的结论。
由于从小就跟随父亲学艺,李耕早年的作品必然会留下父辈的印记。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李耕的卷轴画作品留传很少,一是他当时主要是从事民间寺庙壁画;二是年代久远,偶有一些也损毁失落殆尽。笔者有幸,曾在藏家手头见过几幅,才得出李耕早期画风酷似李霞之结论。如《麻姑》《呵欠》(图55、56)和李霞作品《神仙富贵》《风尘三侠》(图57、58)。其中李耕所作仕女画作品,丰满的鸭蛋形脸庞和秀雅的五官(凤眼柳叶眉樱桃口),上半身宽下半身窄的倒锥式造型,乍一看也颇似沪上钱慧安(李霞的作品与钱氏亦逼肖,据说钱氏曾学过上官周,其间交集有待探究),但笔墨勾画却大不相同,钱慧安细笔偏工,衣褶走势多纵向收敛而很少横向放射,显得拘束谨持,如《一去苏台不复返》(图59),而李耕承袭黄慎意笔,工写互参,粗细混用。不过略嫌束缚的造型依然限制了用笔的纵横自如,且折芦描转折处时露圭角,稍嫌刻意,题款书法与黄慎肖似,郑板桥六分半书体也时在款项中出现。从中可透露出一点信息:随着社会进步,商贸往来渐趋频繁,当地获取资讯的途径增多,为李耕这一代人接触各方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江浙绘画的元素已开始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既然这一时期李耕卷轴画作品现在已难得一见,那么仙游县度尾镇瑞云祠尚存李耕1917年创作的壁画《林子行迹图》(林子本行实录) 人物画25幅,应该说是最能代表早期画风的唯一一组作品了。我所撰写《仙游现存李耕壁画及其艺术特色》一文,对该壁画艺术做了如下的归纳:“从技法层面审视,这个时期李耕绘画风格尚未显现出自己面目,基本上处在对前人画谱的学习、应用或者说领会阶段,人物造型、线条、意趣及其配景的山水树木除了大量吸收闽籍画家黄瘿瓢、上官周技法以外,前人画谱中其他各家技法也若隐若现地流露于笔痕墨迹间。与中晚期画风比较,不难看出早期用笔略觉拘谨和刻意,造型也有较明显的程式化倾向,构图则简略太甚,偏于空疏,画面单薄,但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又能窥见李耕对前人绘画技法努力继承的态度……”第二阶段应划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也是李耕初露锋芒,一鸣惊人的时期,其间作品开始获得徐悲鸿赏识:“有以奇拙胜者,首推李君耕,挥毫恣肆,可以追踪瘿瓢,其才则中原所无……”不过,对其中“有以奇拙胜者”的“奇拙”我一直感到困惑,当时李耕画风奇则奇矣,但“拙”字我不知徐悲鸿先生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对此,很多评论者都回避了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洪惠镇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人物画第一家——李耕》文中似乎也有过类似纠结,最后把李耕整体风格概括为“奇峭”,以表示与“奇拙”的不同。他是这样表述的:“……徐悲鸿见到他(李耕) 的画,谓其‘挥毫恣肆,追踪瘿瓢’,并以‘奇拙’形容其画风,甚为贴切。不过,后来李耕又有自己的创造,成熟后的画风自成一派,与黄慎的差异显著,不再是‘奇拙’可以概括全貌的了。仍能称得上‘奇拙’的作品不是太多,只有像《十八罗汉》册页里的某些画幅和他临终前画的5件绝笔画才是。绝笔尤其典型,书画俱拙……”又说:“……除了这类作品,不好称‘拙’。按文人画的标准而言,‘拙’与‘巧’、‘熟’相对,与‘生’为邻。李耕大量画作风格流畅熟练,近乎‘熟’而非‘生’‘拙’。上海美术评论家邵洛羊称李耕画风‘奇’‘古’‘古劲峭拔’比较接近。但是‘奇’‘峭’有之,‘古’也未必。因为李耕的人物,无论工笔写意都继承传统,笼统而言,当然是‘古’的,但以文人画所谓‘古’的标准衡量,仍与‘生’‘拙’为伍(金农的写意人物方为典型)。我想只用‘奇峭’二字,似更能说明他的画风。”显然,洪惠镇先生也不赞同将李耕国画风格归之于“拙”的一路,绕了一圈,无非是对徐悲鸿当年评价“奇拙”的“拙”字心存疑惑,勉强用了“甚为贴切”加以塞责。因为按照常理或者说中国画创作的发展规律,应该是“由熟入生”“由巧而走向拙”,这一点洪先生自己已说得十分清楚,并举例说明最能体现艺术臻于“拙”的化境是临终前五幅作品,这一见解既尊重事实又十分精辟! 不难想象,徐悲鸿初次见到李耕作品的1928年,李耕才四十多岁,对画家而言,正是年轻气盛,激情贲张时期,徐悲鸿从李耕画作中感觉出“挥毫恣肆”状态,深为其娴熟笔墨技巧所表现出的横溢才情和不同凡响的出奇制胜(奇是李耕作品自始至终的最大看点)功夫发出:“其才则中原所无”的由衷赞叹!但令人不解的是,基于徐悲鸿对中国画的鉴赏能力和地位,把一个崭露头角、正欲一展身手的画家作品定性为由熟入生,显得老气横秋的“拙”,而且还不是一时兴起的信口而出,(据说该篇评论文章还发表于《申报》上) 这是颇值商榷的。其实,只须核对李耕当时作品如《弥勒》(图60),自会心知肚明。对此我始终保持疑问,直到近期才突然冒出一个新的猜想:这一“拙”字是否为“崛”字之误? “看似寻常最奇崛”,奇崛也是评论文艺作品较常用的词语,百度百科对奇崛的基本解释是:1. 亦作“奇倔”;2. 奇特挺拔;3. 独特不凡;4. 谓笔墨刚健。如果以这几点来比照李耕当时的中国画作品风格,那倒是十分贴切的。李耕人物造型和用笔,都具有奇特挺拔之势;独特不凡,这里可以指才奇画也奇,对应了“其才则中原所无”;笔墨刚健,更是李耕画风的显著特点之一! 另一为人们所忽略的是,不管是普通话或莆仙方言,“拙”与“倔”发音都很接近,尤其是莆仙方言,两个字常常混淆,这是不是当时传话的口误? 依我看极有可能。问题是徐悲鸿这篇文章,至今尚未找到,在未见到原文前,这段话就一直是作为口头传下来的。由此容我再续一段小插曲:2001年,李耕中国画作品欲再度进京展览时,我趁机向主办方之一的仙游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议,请求派人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当年《申报》,复印回徐悲鸿评价李耕的原文。(关于徐悲鸿这篇文章的出处,根据1984年印发的《纪念李耕诞生100周年资料汇编》,有说是载于《申报》,有说是《大公报》,时间有1927年的,也有1928年,画展名称有“中法两国绘画联展”“中法绘画赛会”“东南五省绘画联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我查了《徐悲鸿年谱》,追寻徐悲鸿的行迹,确定时间为1928年暑期,展览名称为“福建省第一届美术作品展览”,但此文发自什么报刊,依然无从落实,只好先从《申报》找起) 我的建议获得了批准,随即派仙游县图书馆陈明善馆长只身赴上海图书馆查找,一个星期后无果而返。陈馆长是个负责任的同志,从浩瀚的资料中爬梳剔抉一番没有觅得原文,又特地登门拜访上海徐悲鸿研究会理论研究部主任、《徐悲鸿诞生100周年纪念文集》主编王震先生,得到“此语气出自徐悲鸿先生无疑”的书面证明。嗣后就没有继续考证,以至今天仍挂在我心头,曾想去查找一下《大公报》或福建当时的报纸和相关资料,因为1928年这次美术展览为福建省首届,规模空前,赶上徐悲鸿正好出差在榕,(时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之邀作《蔡公时被难图》,并为申请学生吕斯百、王临乙赴法留学名额说项,一说为黄孟圭特地邀请徐悲鸿来榕为“福建省第一届美术作品展览”剪彩)参观了画展,福建当地媒体当会作为重点报道。
这回是怪本人疏懒,到现在尚没有实际行动。
扯得有点远,还是回归正题。
总而言之,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李耕作品开始出现自己的面目,先前学过的黄慎风格到此只能觅得“踪迹”,故有徐悲鸿的“追踪”一词,也就是“挥毫恣肆”上还留有黄慎以草书入画的流风余韵或闽画习气,但已经注入了自己的感情,融入自己的创造,要不然怎会“其才则中原所无”? 而笔墨形式表面最能称得上写意画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其线条的概括力,笔墨的放纵,情感的宣泄,个性的张扬通过作品表露无遗,应属于本文前面所说的行草和草书类型,即每每兴之所至,行笔极为率性,尤敢涉险出奇,中、老侧、偏锋齐上,风扫云舒,飘逸潇洒,描法不拘一格,用墨于浓淡干湿间随意生发,极灵动变化之能事,落款书法尤见黄瘿瓢跌宕起伏之势,按现在说法是作品具有相当的“视觉冲击力”,如《张果老》(图61)。当然,其年轻气盛时所挟带的某些用笔流弊如圭角妄露,矜才使气,放而有余,收而不足等习气也显露出来。
第三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系李耕艺术成熟期。
若欲细分,这一阶段又可分做三个时段:一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是李耕由本来侧锋阔笔粗线为主的狂放、恣肆,追求画面整体的激越和动势开始转向稳健、劲峭、典雅、清逸的中锋细笔勾画为主,李耕日后最常用的钉头鼠尾描衣纹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见诸笔端,并一直被沿用到晚期。人物形体比例为配合细笔长线条美感的发挥而拉高,一些历史人物和仙佛形象,颀长、挺拔的体形愈发显示出优雅和清奇,书法亦转向婉约秀逸,深具儒者之风。是时李耕五十出头,正处在艺术创作高峰期。但颇为费解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耕的作品似乎流传极少,究竟出于何因有待考证。步入40年代,李耕力作频现,现今流传的好几套组画册页,工笔《十八学士登瀛洲》通景屏,《五百罗汉》长卷,新近发现描金《地狱变相》系列(即《十殿阎王》)等都创作于这一时段。由于将创作兴致部分移向工笔画,致使该时写意也捎带了工笔细写韵致,用笔相对纤细工谨,最能代表李耕写意人物画风格的兼工带写便成熟于此间。李耕夸张而富有奇趣的人物造型和形象,爽劲晓畅、随机生发的中锋线条间以偏、侧锋助势的笔墨,善于营造倾斜奇险之势的构图以达成既保持传统笔墨功力,又具现代视觉冲击力的奇峭画风也稳定下来,并逐步向着用笔的苍涩、老到、从容、超逸,用墨的沉稳、浑厚境界发展,及至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大家忙于适应新的社会形态,暂时失去了品赏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段时间的李耕,可能是鬻画无着,暂时放弃了卷轴画创作,使其能于闲睱之外重操旧业,于1950年应朋友之请在仙游县榜头镇几间“三教祠”画起了壁画,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详见《仙游现存李耕壁画及其艺术特色》篇)。此后不久,政权和社会趋稳,人民生活开始安定,李耕才重返画室进行国画创作。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段他创作了多套《诗经·豳风·七月》册页(图62),我将创作的时代背景视之为:《诗经》所表现的夏商周三代时期,农民在耕作中互助合作的劳动生产形态,(史家称为“公社”) 与土地改革时期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某种类似,因而促发了李耕创作该题材的意兴。还有一些描写农忙季节的劳动场面和《物质交流》系列,均属为时为事之作。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原因,李耕此时创作本意已不在卖画,所以作品中商品意识即所谓“市气”已完全消弥,因而除了《物资交流》(图63) 等为配合当时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意图向新的人物题材转型时暴露出古法惯性的难以克服,出现一些勉为其难的痕迹外,这时创作的古典人物画,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境,线条于不激不厉、优游不迫中愈显苍莽朴厚,了无此前的锋芒和机心的外露,作品深沉厚重,古穆大气,十分耐看。
第四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临终前,可归入晚年期。是时李耕的艺术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地位迅速上升,先后被选聘为仙游县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有关领导还经常亲临或派员上门慰问、探望,可谓关怀备至。50年代末政府又为之筹备成立李耕国画研究室,由他自己担任导师,收徒授艺,传承艺术。为报答党和政府关怀,李耕老当益壮,努力创作了不少呼应时代、有政治寓意的作品,例如创作《夏禹治水》《愚公移山》来表现人民改造自然、战天斗地的决心;作《苏东坡夜探石钟山》“颂党员兴调查研究之风” (李耕题识);作《文姬思汉》《文天祥》(图64)褒扬爱国主义精神;作《尧民击壤而歌》《黄帝梦游华胥国》等歌颂天下太平,人民幸福。并画有几幅毛泽东和鲁迅诗词用典句意,如《子在川上曰》(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魏武挥鞭》(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七律·自嘲》)等。另外,还保持他最拿手的《弥勒佛》创作,大概是指导学生的示范作品吧。颇为有趣的是,这时李耕画的弥勒佛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下颏布满了胡茬,以致有调侃者说,弥勒佛也跟着李耕一起老了。工笔画示范作品尚有一套4幅《十八学士》通景屏。进入晚期李耕笔墨更为古穆苍浑,由于视力衰退,有些作品上墨后觉得不甚满意,就用白粉覆盖,然后再上墨上色,如是涂涂画画,重重叠叠,粉、墨、色交互使用,愈见拙厚凝重,形成了这一阶段的风格特征。当然最堪称“朴拙圆满,浑若天成”的要数临终前5幅作品了。我曾将之比作弘一法师临终绝笔“悲欣交集”。
该5幅作品为《济颠》《弥勒》《伏虎》《呵欠》《搔痒》(详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李耕临终作品及其艺术的再认识》),可视之为李耕毕生事佛,生命走向涅槃,艺术进入化境的“舍利子”,其笔墨苍浑沉厚,形体比例依然保持准确,意态生动自然,韵味高古,神韵天然。处于弥留之际,能以澄澈清明心境和顽强毅力写出一贯的“形神兼备”作品,不能不说是长期历练形成潜在意识所发挥着的神奇效应。
从学习古人之法开始到熟练的挥洒自如,然后若有所悟而渐次收敛,转向理性的平和清逸,确立了个性鲜明,具有独特笔墨语言的“奇峭”画风,在这一基本面上进入“苍浑朴厚,从容随意”的升华,最后达到返璞归真的大化之境,这就是李耕艺术风格的嬗变轨迹,这一过程,也揭示了中国画创作以及真正的中国画家成长的普遍规律。
我们看到,李耕各个时期或曰各个阶段画风变化虽然十分明显,但演化脉胳却是清晰的,不像一些画家一生风格保持太过稳定而易于给人留下创造力不足,创新意识不强的印象;也不像一些画家为标新立异而忽左忽右地在“跳山头”,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最终在创作道路上形不成一条主线。(注意,这与艺术追求上的“转益多师”不可同日而语,善于转益多师者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一贯信念和主张,转益多师只是广征博取的一种方法或手段而已)因此,分析李耕各个时期画风的嬗变,对于研究李耕艺术是很重要的一环。
李耕写意人物画风格的嬗变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只能从存世的李耕作品最早创作时间,即20世纪初算起至20年代初期。这个时段,李耕正由寺庙壁画向卷轴画转型,也是李耕在乃父殁后,开始自己摸索、选择艺术道路和创作方向的节点。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李耕父亲说起。李耕父亲李墀,字步丹,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民间画师,一生以画寺庙壁画、雕塑神像和人物肖像为业,可惜真正属于他创作的作品似已绝迹,当然也就无从得知他的画究竟出自何家何法。但凭我推断,李墀受福建本土画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依据如下:一是由于福建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所限,经济、文化偏安一隅,受外地影响、渗透比较少,文化相互交流基本上囿于福建本土之间。距时较近的闽西上官周、黄慎、华喦在福建当地影响很大,要睹其原作机会相对多,学习方便。二是从他的弟子作品可以得以部分印证。例如至今保存较完整的仙游县游洋镇龙山书院朱学田壁画,闽派人物画特点就十分突出,朱氏与李墀既是邻居,又是及门弟子。另外与李耕同时代的当地另一著名人物画家李霞(比李耕年长14岁)早岁曾师从李墀学艺,对黄慎笔墨技法之用功可谓始终不渝,此应与当年李墀引导不无关系。李耕初学画时以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为范本(后来他自己课徒时也有同样要求),进入写意人物画创作初期画风又与李霞极为相似,盖因师出同门。依此类推,也可以得出李墀私淑于福建本土诸先辈的结论。
由于从小就跟随父亲学艺,李耕早年的作品必然会留下父辈的印记。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李耕的卷轴画作品留传很少,一是他当时主要是从事民间寺庙壁画;二是年代久远,偶有一些也损毁失落殆尽。笔者有幸,曾在藏家手头见过几幅,才得出李耕早期画风酷似李霞之结论。如《麻姑》《呵欠》(图55、56)和李霞作品《神仙富贵》《风尘三侠》(图57、58)。其中李耕所作仕女画作品,丰满的鸭蛋形脸庞和秀雅的五官(凤眼柳叶眉樱桃口),上半身宽下半身窄的倒锥式造型,乍一看也颇似沪上钱慧安(李霞的作品与钱氏亦逼肖,据说钱氏曾学过上官周,其间交集有待探究),但笔墨勾画却大不相同,钱慧安细笔偏工,衣褶走势多纵向收敛而很少横向放射,显得拘束谨持,如《一去苏台不复返》(图59),而李耕承袭黄慎意笔,工写互参,粗细混用。不过略嫌束缚的造型依然限制了用笔的纵横自如,且折芦描转折处时露圭角,稍嫌刻意,题款书法与黄慎肖似,郑板桥六分半书体也时在款项中出现。从中可透露出一点信息:随着社会进步,商贸往来渐趋频繁,当地获取资讯的途径增多,为李耕这一代人接触各方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江浙绘画的元素已开始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既然这一时期李耕卷轴画作品现在已难得一见,那么仙游县度尾镇瑞云祠尚存李耕1917年创作的壁画《林子行迹图》(林子本行实录) 人物画25幅,应该说是最能代表早期画风的唯一一组作品了。我所撰写《仙游现存李耕壁画及其艺术特色》一文,对该壁画艺术做了如下的归纳:“从技法层面审视,这个时期李耕绘画风格尚未显现出自己面目,基本上处在对前人画谱的学习、应用或者说领会阶段,人物造型、线条、意趣及其配景的山水树木除了大量吸收闽籍画家黄瘿瓢、上官周技法以外,前人画谱中其他各家技法也若隐若现地流露于笔痕墨迹间。与中晚期画风比较,不难看出早期用笔略觉拘谨和刻意,造型也有较明显的程式化倾向,构图则简略太甚,偏于空疏,画面单薄,但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又能窥见李耕对前人绘画技法努力继承的态度……”第二阶段应划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也是李耕初露锋芒,一鸣惊人的时期,其间作品开始获得徐悲鸿赏识:“有以奇拙胜者,首推李君耕,挥毫恣肆,可以追踪瘿瓢,其才则中原所无……”不过,对其中“有以奇拙胜者”的“奇拙”我一直感到困惑,当时李耕画风奇则奇矣,但“拙”字我不知徐悲鸿先生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对此,很多评论者都回避了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洪惠镇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人物画第一家——李耕》文中似乎也有过类似纠结,最后把李耕整体风格概括为“奇峭”,以表示与“奇拙”的不同。他是这样表述的:“……徐悲鸿见到他(李耕) 的画,谓其‘挥毫恣肆,追踪瘿瓢’,并以‘奇拙’形容其画风,甚为贴切。不过,后来李耕又有自己的创造,成熟后的画风自成一派,与黄慎的差异显著,不再是‘奇拙’可以概括全貌的了。仍能称得上‘奇拙’的作品不是太多,只有像《十八罗汉》册页里的某些画幅和他临终前画的5件绝笔画才是。绝笔尤其典型,书画俱拙……”又说:“……除了这类作品,不好称‘拙’。按文人画的标准而言,‘拙’与‘巧’、‘熟’相对,与‘生’为邻。李耕大量画作风格流畅熟练,近乎‘熟’而非‘生’‘拙’。上海美术评论家邵洛羊称李耕画风‘奇’‘古’‘古劲峭拔’比较接近。但是‘奇’‘峭’有之,‘古’也未必。因为李耕的人物,无论工笔写意都继承传统,笼统而言,当然是‘古’的,但以文人画所谓‘古’的标准衡量,仍与‘生’‘拙’为伍(金农的写意人物方为典型)。我想只用‘奇峭’二字,似更能说明他的画风。”显然,洪惠镇先生也不赞同将李耕国画风格归之于“拙”的一路,绕了一圈,无非是对徐悲鸿当年评价“奇拙”的“拙”字心存疑惑,勉强用了“甚为贴切”加以塞责。因为按照常理或者说中国画创作的发展规律,应该是“由熟入生”“由巧而走向拙”,这一点洪先生自己已说得十分清楚,并举例说明最能体现艺术臻于“拙”的化境是临终前五幅作品,这一见解既尊重事实又十分精辟! 不难想象,徐悲鸿初次见到李耕作品的1928年,李耕才四十多岁,对画家而言,正是年轻气盛,激情贲张时期,徐悲鸿从李耕画作中感觉出“挥毫恣肆”状态,深为其娴熟笔墨技巧所表现出的横溢才情和不同凡响的出奇制胜(奇是李耕作品自始至终的最大看点)功夫发出:“其才则中原所无”的由衷赞叹!但令人不解的是,基于徐悲鸿对中国画的鉴赏能力和地位,把一个崭露头角、正欲一展身手的画家作品定性为由熟入生,显得老气横秋的“拙”,而且还不是一时兴起的信口而出,(据说该篇评论文章还发表于《申报》上) 这是颇值商榷的。其实,只须核对李耕当时作品如《弥勒》(图60),自会心知肚明。对此我始终保持疑问,直到近期才突然冒出一个新的猜想:这一“拙”字是否为“崛”字之误? “看似寻常最奇崛”,奇崛也是评论文艺作品较常用的词语,百度百科对奇崛的基本解释是:1. 亦作“奇倔”;2. 奇特挺拔;3. 独特不凡;4. 谓笔墨刚健。如果以这几点来比照李耕当时的中国画作品风格,那倒是十分贴切的。李耕人物造型和用笔,都具有奇特挺拔之势;独特不凡,这里可以指才奇画也奇,对应了“其才则中原所无”;笔墨刚健,更是李耕画风的显著特点之一! 另一为人们所忽略的是,不管是普通话或莆仙方言,“拙”与“倔”发音都很接近,尤其是莆仙方言,两个字常常混淆,这是不是当时传话的口误? 依我看极有可能。问题是徐悲鸿这篇文章,至今尚未找到,在未见到原文前,这段话就一直是作为口头传下来的。由此容我再续一段小插曲:2001年,李耕中国画作品欲再度进京展览时,我趁机向主办方之一的仙游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议,请求派人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当年《申报》,复印回徐悲鸿评价李耕的原文。(关于徐悲鸿这篇文章的出处,根据1984年印发的《纪念李耕诞生100周年资料汇编》,有说是载于《申报》,有说是《大公报》,时间有1927年的,也有1928年,画展名称有“中法两国绘画联展”“中法绘画赛会”“东南五省绘画联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我查了《徐悲鸿年谱》,追寻徐悲鸿的行迹,确定时间为1928年暑期,展览名称为“福建省第一届美术作品展览”,但此文发自什么报刊,依然无从落实,只好先从《申报》找起) 我的建议获得了批准,随即派仙游县图书馆陈明善馆长只身赴上海图书馆查找,一个星期后无果而返。陈馆长是个负责任的同志,从浩瀚的资料中爬梳剔抉一番没有觅得原文,又特地登门拜访上海徐悲鸿研究会理论研究部主任、《徐悲鸿诞生100周年纪念文集》主编王震先生,得到“此语气出自徐悲鸿先生无疑”的书面证明。嗣后就没有继续考证,以至今天仍挂在我心头,曾想去查找一下《大公报》或福建当时的报纸和相关资料,因为1928年这次美术展览为福建省首届,规模空前,赶上徐悲鸿正好出差在榕,(时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之邀作《蔡公时被难图》,并为申请学生吕斯百、王临乙赴法留学名额说项,一说为黄孟圭特地邀请徐悲鸿来榕为“福建省第一届美术作品展览”剪彩)参观了画展,福建当地媒体当会作为重点报道。
这回是怪本人疏懒,到现在尚没有实际行动。
扯得有点远,还是回归正题。
总而言之,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李耕作品开始出现自己的面目,先前学过的黄慎风格到此只能觅得“踪迹”,故有徐悲鸿的“追踪”一词,也就是“挥毫恣肆”上还留有黄慎以草书入画的流风余韵或闽画习气,但已经注入了自己的感情,融入自己的创造,要不然怎会“其才则中原所无”? 而笔墨形式表面最能称得上写意画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其线条的概括力,笔墨的放纵,情感的宣泄,个性的张扬通过作品表露无遗,应属于本文前面所说的行草和草书类型,即每每兴之所至,行笔极为率性,尤敢涉险出奇,中、老侧、偏锋齐上,风扫云舒,飘逸潇洒,描法不拘一格,用墨于浓淡干湿间随意生发,极灵动变化之能事,落款书法尤见黄瘿瓢跌宕起伏之势,按现在说法是作品具有相当的“视觉冲击力”,如《张果老》(图61)。当然,其年轻气盛时所挟带的某些用笔流弊如圭角妄露,矜才使气,放而有余,收而不足等习气也显露出来。
第三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系李耕艺术成熟期。
若欲细分,这一阶段又可分做三个时段:一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是李耕由本来侧锋阔笔粗线为主的狂放、恣肆,追求画面整体的激越和动势开始转向稳健、劲峭、典雅、清逸的中锋细笔勾画为主,李耕日后最常用的钉头鼠尾描衣纹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见诸笔端,并一直被沿用到晚期。人物形体比例为配合细笔长线条美感的发挥而拉高,一些历史人物和仙佛形象,颀长、挺拔的体形愈发显示出优雅和清奇,书法亦转向婉约秀逸,深具儒者之风。是时李耕五十出头,正处在艺术创作高峰期。但颇为费解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耕的作品似乎流传极少,究竟出于何因有待考证。步入40年代,李耕力作频现,现今流传的好几套组画册页,工笔《十八学士登瀛洲》通景屏,《五百罗汉》长卷,新近发现描金《地狱变相》系列(即《十殿阎王》)等都创作于这一时段。由于将创作兴致部分移向工笔画,致使该时写意也捎带了工笔细写韵致,用笔相对纤细工谨,最能代表李耕写意人物画风格的兼工带写便成熟于此间。李耕夸张而富有奇趣的人物造型和形象,爽劲晓畅、随机生发的中锋线条间以偏、侧锋助势的笔墨,善于营造倾斜奇险之势的构图以达成既保持传统笔墨功力,又具现代视觉冲击力的奇峭画风也稳定下来,并逐步向着用笔的苍涩、老到、从容、超逸,用墨的沉稳、浑厚境界发展,及至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大家忙于适应新的社会形态,暂时失去了品赏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段时间的李耕,可能是鬻画无着,暂时放弃了卷轴画创作,使其能于闲睱之外重操旧业,于1950年应朋友之请在仙游县榜头镇几间“三教祠”画起了壁画,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详见《仙游现存李耕壁画及其艺术特色》篇)。此后不久,政权和社会趋稳,人民生活开始安定,李耕才重返画室进行国画创作。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段他创作了多套《诗经·豳风·七月》册页(图62),我将创作的时代背景视之为:《诗经》所表现的夏商周三代时期,农民在耕作中互助合作的劳动生产形态,(史家称为“公社”) 与土地改革时期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某种类似,因而促发了李耕创作该题材的意兴。还有一些描写农忙季节的劳动场面和《物质交流》系列,均属为时为事之作。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原因,李耕此时创作本意已不在卖画,所以作品中商品意识即所谓“市气”已完全消弥,因而除了《物资交流》(图63) 等为配合当时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意图向新的人物题材转型时暴露出古法惯性的难以克服,出现一些勉为其难的痕迹外,这时创作的古典人物画,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境,线条于不激不厉、优游不迫中愈显苍莽朴厚,了无此前的锋芒和机心的外露,作品深沉厚重,古穆大气,十分耐看。
第四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临终前,可归入晚年期。是时李耕的艺术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地位迅速上升,先后被选聘为仙游县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有关领导还经常亲临或派员上门慰问、探望,可谓关怀备至。50年代末政府又为之筹备成立李耕国画研究室,由他自己担任导师,收徒授艺,传承艺术。为报答党和政府关怀,李耕老当益壮,努力创作了不少呼应时代、有政治寓意的作品,例如创作《夏禹治水》《愚公移山》来表现人民改造自然、战天斗地的决心;作《苏东坡夜探石钟山》“颂党员兴调查研究之风” (李耕题识);作《文姬思汉》《文天祥》(图64)褒扬爱国主义精神;作《尧民击壤而歌》《黄帝梦游华胥国》等歌颂天下太平,人民幸福。并画有几幅毛泽东和鲁迅诗词用典句意,如《子在川上曰》(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魏武挥鞭》(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七律·自嘲》)等。另外,还保持他最拿手的《弥勒佛》创作,大概是指导学生的示范作品吧。颇为有趣的是,这时李耕画的弥勒佛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下颏布满了胡茬,以致有调侃者说,弥勒佛也跟着李耕一起老了。工笔画示范作品尚有一套4幅《十八学士》通景屏。进入晚期李耕笔墨更为古穆苍浑,由于视力衰退,有些作品上墨后觉得不甚满意,就用白粉覆盖,然后再上墨上色,如是涂涂画画,重重叠叠,粉、墨、色交互使用,愈见拙厚凝重,形成了这一阶段的风格特征。当然最堪称“朴拙圆满,浑若天成”的要数临终前5幅作品了。我曾将之比作弘一法师临终绝笔“悲欣交集”。
该5幅作品为《济颠》《弥勒》《伏虎》《呵欠》《搔痒》(详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李耕临终作品及其艺术的再认识》),可视之为李耕毕生事佛,生命走向涅槃,艺术进入化境的“舍利子”,其笔墨苍浑沉厚,形体比例依然保持准确,意态生动自然,韵味高古,神韵天然。处于弥留之际,能以澄澈清明心境和顽强毅力写出一贯的“形神兼备”作品,不能不说是长期历练形成潜在意识所发挥着的神奇效应。
从学习古人之法开始到熟练的挥洒自如,然后若有所悟而渐次收敛,转向理性的平和清逸,确立了个性鲜明,具有独特笔墨语言的“奇峭”画风,在这一基本面上进入“苍浑朴厚,从容随意”的升华,最后达到返璞归真的大化之境,这就是李耕艺术风格的嬗变轨迹,这一过程,也揭示了中国画创作以及真正的中国画家成长的普遍规律。
相关地名
莆田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