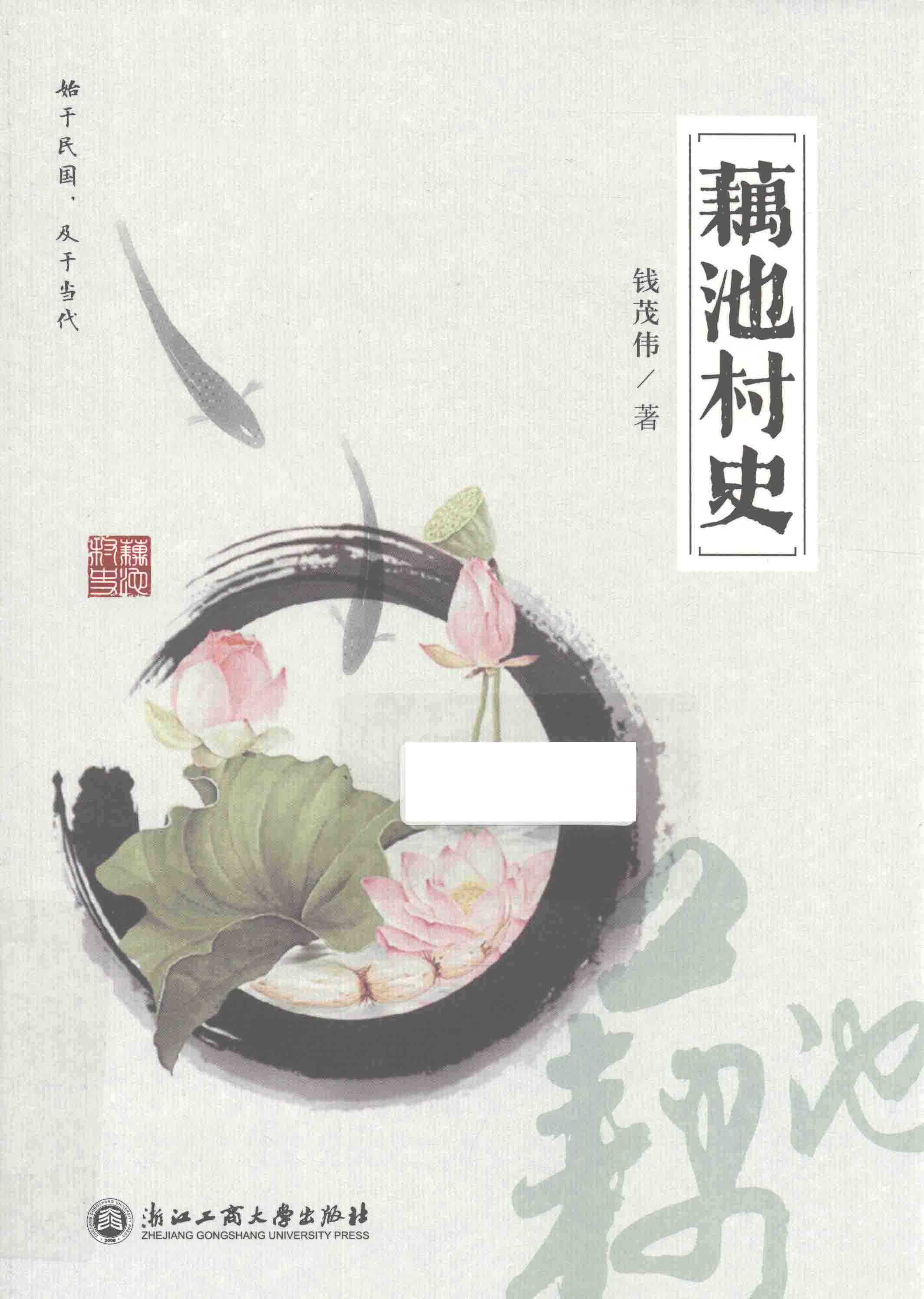内容
1953年以后,藕池村逐步走上了集体化之路。1958年至1961年,进行了大公社的探索。1962年至1982年,实行了20年左右的小公社。在公社、大队的管理下,以生产队的方式工作着。在那个年代,农业是根本,工业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其他副业一直相辅而行。
第一节/农业生产
一、生产方式
姜岳祥说:“土地改革后,田分好了,生产队也很小心的,公粮都要交的。”
从图6-1来看,当时的集体化农业生产,内部分工是十分详细的,有植保员、种子员、肥水管理员、田间观察记录员、畜牧负责人、会计员、现金保管员、粮食(实物)保管员、绿萍专管员、粪便管理员。
葛小其说:“那个时候女人也要去种田。男人在生产队干好活,再去自留地拔拔草。女的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管孩子、补衣服,女人比男人更苦。男人4点去拔秧,7点回来吃饭,女人已经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了。男人来吃完饭了,女人开始去种田了。生产队的话要做一个月,割早稻、种晚稻。个人种的话,十几天就够了。分田到户了,种的东西卖的钱都是自己的。生产队就是大锅饭,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肯做。女人平时还要做凉帽,像我们这个时代生的女人都是会做凉帽的。
“一个生产队一年总产量是比如1000斤,除去国家公粮、社员口粮及化肥、农药、牛,能节余200斤左右。一般100亩田,要分到组、分到人,除去生产成本,一个生产队一年还有几万块结余,要如何分呢?这个是按劳动力来分的,一般要按四个季来分,春季、早稻下、晚稻上、年终,春季少一点,早稻下了稍微多点。”
二、生产工具
姜岳祥说:“打稻机,大概是1961年开始有的,藕池一个点,板桥一个点,一个点买一部。田的话还是藕池多,板桥五百多亩田,藕池一千多亩田。藕池的两个队合着买了一部。那时候板桥买了一部,本来是要分给藕池的,板桥就找了农办副主任张忠林,他说:有是有,但现在别来买,让别人知道了不好,大家都要的话,我们也拿不出来,因为没有几部。我们说那什么时候好拿呢?他说等晚一点。就在晚上偷偷摸摸去,还是走小路,走大路难为情,也怕别人争,就这样买了一部打稻机。最早一个大队只有一部,过了三年,就很多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买了,一个生产队一部。有电动打稻机比较迟了,是七八十年代的事。作为队长,也种地,忙了要帮,开早工也要去,工作每天都要安排好。那时候是分任务的,你完成得早可以回去。后来分自留地了,你可以弄自留地去。”
三、拖拉机与农用船
1960年12月,藕池大队向邻近的建庄大队购买了一部机船,共2000元,当时只付了300元。其余款项约定1961年早稻期时分批还上,结果到了1963年5月仍没有还上,于是被建庄大队告上法庭。后来经过调解,藕池村同意分两批还上,才了了此事。由此也可见当时藕池大队经济之拮据。戚明华说:“那个时候都是船,每个生产队有2只船和2只牛,拖拉机有的时候是1976年左右了,1000多亩田靠一辆拖拉机。以前也没有石子路,要用船运着拖拉机到板桥,再搬到岸上使用。”
四、挑坟滩
徐繁荣说:“在生产队,我们挑坟滩、挑河泥,那时候最苦了。挑坟滩是分田到户前一两年,大概是1979年,那时候我们还小,挑得背都弯了,挑坟滩最苦了。区域都给你分好的,运气好一点的话,石块少一点,运气差一点的话,石块比较多,翻都翻不动。我们算苦了,但比起上辈人,我们至少有得吃了,但是劳力还是要出的。爸爸当了村里一个小领导,家里的事情就我们自己做了。做皎口水库的时候,我刚好要发育,一个小后生挑得背都弯了。”
五、进城积肥
姜岳祥说:“那时候很困难,那就动脑筋。要种菜籽、大麦和水稻,但是没有肥料,所以稻子种起来都小小的,只能扩大面积。一个生产队,105亩田,20%要种大麦,10%是菜籽。种点菜籽,肥料也没有的,这里离城里很近,就连夜去城里偷点大粪回来当肥料。那时候肥料还是要控制的,都是收集了后再卖给农民,我们生产队买来,还得分配的。以前就是给个条子写明几点走,撑着船过去等。最早船也是没有的,都是从地主那没收来的船。我们队以前就是用河泥当肥料,现在这样的河泥,以前碰都碰不到,有的话真的高兴死了。现在都填掉了,也不用积肥了。以前的粮站,也是一点点搞起来的。我们生产队有两只船,早晚饭吃好就去积肥了。粮食种得好了,我们也能富裕点。那时候都是晚上干这活,晚饭吃一点就去了。积过肥的河泥用来浇菜、浇麦、浇田,浇过了,产量是有点不一样的。”吴升月说:“那时候要积肥,就到宁波给别人倒马桶然后挑回来,积肥多产量也高,第6生产队,副队长就是徐定良,正队长是吴祝庆。副队长抓生产,他非常会做,积肥时,每天早上就出去到宁波倒马桶。人家肥积不来,我们是每天都有。积肥多,产量高,分红也多。”
姜冲德说:“以前化肥不怎么用的,因为是要花钱的,以前浇点氨水,尿素稍微放一点,这已经算是很好了,其他是没有的。一般都要到宁波城里去积肥,就是倒马桶的,以前都没有什么化肥的,都靠这些粪水的。”姜冲德又说:“我们经常晚上饭吃好去,半夜去弄肥。如果被抓,还要到大队里去打证明,要去讲好话的。以前从九中挑出来,走城隍庙过来,这么远的路。”
六、打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打水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行业。当时,有专门的人负责打水。江根星、叶金康、张昌浩、洪根庆等人,均打过水。姜岳祥说:“买第一台打水机的是板桥,那时候我28岁,当兵已经回来了,是1963年。那时候干旱,稻谷都晒死了,一点收成都没有。方家耷的张忠林是农办的,他说:打水机你们要吗?那时候都买不起,村里没有钱。板桥把口粮卖掉,才买了这个打水机,这是第一部。但是效果很好,粮食丰收。打水机的管子(口)是10寸的,可以机动的,藕池要用,可以借给藕池,这里打好,再去那边。此前的1959年,姚江大闸造好了,水拦起来,就可以灌溉了。慈溪、江北都要拿水,很多机器排着,你也打,我也要打。我们的水是从青林渡放过来的。”周利英说:“以前一直要打水的,从3月份开始打,一直打到田没有了为止。他们是大队打水员。”
七、抢收抢种
徐建波说:“我1982年开始也分到田了,我们第7生产队人少地多,地分到了17亩。我爷爷自己种不过来,又给了我们3亩,总共20亩。那个时候田都是靠人力种的,我爸还在铁厂上班,分田到户时,我才16岁,20亩田我一个人管不过来,真的很苦。我爸爸基本上早上5点起床,早工开好之后,再去上班。我做到18岁,也去铁厂上班了。我们家一共4个人,还有我妈和妹妹。当时妹妹小,已经读初中了,妹妹基本都是在家里烧饭,活基本上都是我们三个人做。‘双抢’也是很苦,基本都是凌晨二三点起床,做到晚上11点,一直做了六七年。后来,外地人来了,拿点田出来给人家种,才轻松一点了。”李小平说:“生产队时,我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是张昌浩,我们叫他‘老板’。张昌浩人是很好的,那时候田多人少。在规定时间,一定要种,要开夜工,要拔秧、开早工。当时还年轻,凌晨一两点起床拔秧田,两个人拼在一起干,一人一半。拔好以后,挑到地里,让妇女插秧。有一次,我和洪根庆拼的,他说你怎么拔不上来了呀,实际上我在打瞌睡了,睡着了。”徐仁定说:“像现在怎么可能想得到,那时候田种得都怕了。那时候天下雨,稻没有割,天晴了,共青团员3点钟就要去割,干到天亮。3亩田上午打好,下午就好种了。”周利英说:“以前当干部都是实干的,是要带头做的,且要比人家多做,如果比人家做得少,人家不服的。天亮后,以12点为界,分两个班,半天轮到一班。轮到你,就算是12点钟的时候,天最热,你也要去干的,下雨也要去,打雷也要去的。”
八、收入不高
周利英说:“那时候记工分,没有现钱,哪有现钱买菜啊。如果就男人,女人不做,工分容易超支。我们两个人都干,超支倒是没有。”史幼芳说:“我们农民有句话,田沿三尺高,跳出田沿就好。头想高烟囱,城市的烟囱高高的,都想到城市去。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买的,粮票还分地方粮票,有宁波粮票、浙江粮票、全国粮票。我们到上海去,要拿全国粮票的,浙江粮票都没有用的,饭都不能吃。宁波城市里的工人,带鱼都可以领大一点的,我们农村里分到的带鱼都是小小的。我记得我25岁时,有的东西还要用票买的。国家贫穷,老百姓也就这样了。农民每天背朝天种田,下雨也要淋,真的很辛苦。现在国家对农民也重视,国家也富强了,总归是好起来了,农民翻身出头了。”
九、种席草
杨国平说:“当年种席草时,收上后要晒好,在太阳底下,要三朝、四朝地晒,还要摇着船去宁波去晒呢。俗话说‘小暑割草,大暑割稻’,差不多是最热的时候割席草。后来是种日本席草,做榻榻米的,从田里割来,用泥粉弄过,再晒过,要晒过几天。这个草细,本地草比较粗。日本席草种植始于20世纪80年代,不过本地席草种也种的,但是比较少了。个人分田到户以后,大家都种日本席草了,因为种这个收入高”。姜芬琴说:“还有草帽和我们睡的席子,也是我们自己种的草做的。自己种的席草,晒干以后,一捆一捆给它捆好,然后用两根稻草做的绳子给它捆起来的。这个捆的技术也是很难的,因为席草晒干以后很滑的,如果捆不好的话,一拿就散掉了。我老爸捆的席草,又干净又好,从来不会散掉。”徐森林说:“天亮起来,大家饿着肚子去割席草,饭也没得吃。那时候有种黄桃的,有时候买点黄桃来当饭。席草还要把它晒干,还要去卖,那时候真的很苦的。等我们卖完了回来,人家早就在吃饭了。我们回到家里,还要放夜潮,那时候很苦的。”
此外,还有稻草。姜芬琴说:“我老爸(姜阿利)种出来的东西很精细的,泥土弄得像米粉一样精细。我们早稻割下来以后,稻草干了,拿回来要储存。那时候就靠烧稻草当燃料用的。稻草都是储存在屋子外面的,要给搭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堆。一般的农民都搭不好,搭到一定大小就要塌掉了。我老爸的草堆,可以搭到最大最高,像房子一样盖起来,不管多大的雨,里面都淋不进去的。要用的时候,不是从上面一捆捆拿的,而是在中间抽的。这么大的一个草堆,它是一捆捆都叠好的。如果草堆没有搭好的话,抽出来后,这个草堆就要塌下来了。我老爸搭的草堆,你去抽好了,它不会塌下来的,很厉害的,这也是一种技术,一种手艺。20世纪80年代,我们村里集体经济就是靠农田做出来的,可以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村里也没有很穷的人家。”
第二节/内河捕鱼
姚国华说:“父亲(姚信芳)也是捕鱼的。在藕池,捕鱼的有两户,一个是叶家(叶根财),一户是姚家。叶家是四兄弟,姚家也是四兄弟。以前我父亲也是很辛苦的,在河塘里捕鱼。我父亲有4个儿子2个女儿,以前人多,赚不到钱。我家捕鱼是从爷爷开始的。我父亲三个兄弟,都是捕鱼的,嫂子也是捕鱼的。那时候捕鱼的人,多数是住在船上的。房子也是有的,如果不去外面捕鱼了,就回家里来住。以前就一条船,小小的手摇船,在旁边的江河里捕鱼。开出去以后的话,可能要2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一般要背两袋米去。捕了鱼还要去卖掉,这个也要看行情的,经常卖不掉,臭了倒掉也是经常的。过去捕到好的螃蟹,我父亲就卖给藕池的老板,换一点米。现在我也不会捕鱼了。现在好的东西都很值钱,大的河鲫鱼要40块、50块一斤。
“父亲三兄弟里,大伯伯早就到沈家门修皮鞋去了,后来又回来捕鱼。捕鱼的人是苦的,钱又赚不到。我们家6个兄弟姐妹,你知道要吃多少饭吗?那时候男孩子最起码有3碗可以吃,那四个兄弟就12碗了。米是跟人家买的,我们家以前一个大大的米缸,要煮一锅的,不然不够吃。我们四兄弟原来也捕鱼,现在有一个在开五金厂。现在,最大的阿哥(姚昌华)还在捕鱼,还有一个阿弟(姚宝华)也是。老大天冷不捕了,天热就捕一捕鱼,因为他79岁了。老四是一直在捕鱼的。
“我们是在布政的,布政渔业队早就有了。我们户口在藕池,工作单位在布政。渔业队在板桥,有100多个人。以前老的渔业队在厂里干活,现在大家也都退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捕鱼的人合在一起,变成渔业大队了。我们分房子没有享受到的,因为分属不同的经济合作社。这也有道理,因为农民是有土地资源的,靠土地生活的。你们渔业是靠水资源,也可以去自己开发。我十多岁开始捕鱼的时候,这边水很多的,但是后来被拦起来了。我是1973年结婚的。结婚了以后,我还在捕鱼,老婆开始在五金厂上班,后来厂被个人承包去了,也出来一起去卖鱼。
“1983年到2011年,我一直当渔业社社长。渔业社是不分组的,我是属于‘半工半渔’的,上午到村里办事,下午出去捕鱼。一般来说,我能解决的我自己去做,我不能解决的就找村书记。那时候河塘是渔业社的主要经济来源,收入也是蛮可观的,承包河道,多少长度多少钱一年。在古林镇范围我管理不了,石碶街道也有。石碶也有渔业社的,但河塘是属于我们的。后来塘西造敬老院,把河塘填了。这事当时是石碶街道办的,河的面积是属于我们渔业队的,所以要到石碶街道去要点适当的赔偿,当时的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双方是共同协商的。我就讲了,多少总归要赔偿一点的,不赔偿是不可能的。”
陈利菊补充说:“那时候捕鱼,用丝网和小船作业。这个就是典型的内河捕鱼。捕鱼的行业不是很好做,只能养家糊口,跟农民种田一样,也没有什么花头的,也很苦的,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当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想让儿子和女儿生活能好一点,也要咬牙干。这个苦和种田的苦是不同,农民的苦是有季节的,我们是一年四季的。我们不怕下雨,但是怕响雷。”
第三节/村办企业
在大队时期,农业为主,工业为辅,是一条基本原则。两者之间,多少有一些矛盾。当时村中领导,往往将杨家路头工业区称为“梁山巢”。因为他们赚了钱,只会私分,上交村里的财政很少。
乡里有乡办企业,大队有队办企业。1971年可能是个高峰期,办厂都是1971年开始的。
一、藕池铁厂
铁厂,也被村人叫作锻压厂。1969年,永康商人来1队办铁厂加工。1971年,大队接手,独立办厂。徐信定当厂长,成员有张明芳、龚财良、李忠尧、陈再明、戚明亮、张小康等人。藕池为了办打铁厂,领导与技工曾去上海参与培训。
张小康说:“我那时候28岁(1969),有一个永康人到我们第一生产队来问:你们有会打铁的吗?我们给你办厂,你们生产队的人去工作,给生产队60元一个月。我们队长一听挺好的,就同意了。厂子是以打农具为主的。我当时在畜牧场,他们打铁厂有所发展了,炉灶开得多了,要叫更多的人去。生产队的人打铁毕竟是外行,不想打了,就来叫我来了。我想想打铁是吃技术饭的,就同意了。我在生产队里就是打铁,做了两年。两年下来,已经有点学会了。因为我做事非常勤快,永康人很喜欢我。结果,生产队里矛盾很大,说厂里这么早下班,农民早上4点钟还要下田。结果,这个厂开不下去了,就关掉了。
“大队书记江根星听说后就讲,大队去开,这个厂就给了大队。大队就开社员大会,社员全部报名想去。因为我的成分不好,是富农子女,就没有去报名。结果大队干部说,你为什么昨天没报名?我说报跟不报也是一样,到时候也要被淘汰下来的。他说,这个不用管的。过了八个月,永康那个老板说:张小康人很勤劳,这个人很好。结果,我又被他叫去了。我那时候29岁(1970)。我们藕池前一代,基本上个个都打过铁,但都没干长久,只有我一个人做得长。
“厂给了大队以后,大队人去厂里做工的人多了,工资就付不起了。我们村里书记说,从农业收入里调过去。还有一家米厂,去轧米,给4毛5分一天。这个时候塑料厂刚开始有,这个利润也蛮好,赚了一些钱。我们藕池铁厂没有设备,想来想去,都觉得做不下去。为什么呢?一天的时间,两个人只能打一段铁,三天打下来,没多少好做,所以很烦。买铁要到耐火厂去买的,买了以后,用船拖回来。耐火厂那边回来,要路过三江口的,因为太重,船有时候会翻,人没有淹死,算运气好了。我是一直打铁的,打到1986年实行厂长责任制,厂被承包了为止。我打铁18年,这样风风雨雨过来,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是从农民起家的。”
吴升月说:“1971年已经办打铁厂了,这是村里第一个厂,在藕池村庙里办,是机器打的。厂办了很多年,我老头1975年去了。这是藕池村第一个工厂,规模比较大,有二十几个职工,产品的销售也很好,那时候劳动力不紧张,生产队劳动不紧张,办厂能给村里增加收入。我老头那时候34岁了,下面的人都是18、19岁的小青年。厂一直到很晚才关。主要是做模具坯子,这个要用铁打出来,相当于做铸模的坯子,然后把这个坯子拿到模具厂去开模,他们不会开模,就只能打坯子。那时候是书记江根星、大队长姜岳海和我老头讨论出来要办这样一个厂,然后叫我老头去负责,他就从生产队走出来去办厂了。厂里都是拿工分,没有补贴的。”
1974年1月到1976年12月,徐信华回村铁厂工作,担任厂长。由此可知,徐信定走前,村中已经将徐信华安排为厂长了。
1978年,由李安明当厂长。李安明说:“1973年,村里叫我开拖拉机。到1977年,布政乡镇府把我叫去培养。1978年,藕池的锻压厂叫我去当厂长。①当时我妈是支委,大队开夜会说有个队办企业,非常不容易,这个厂的厂长没有人当。我妈就跟江书记说:这个厂长还是让我儿子去当。我妈夜会开回来跟我说:江书记同意让你去做这个厂的厂长。我答应了。我们有两班,一班是做钣金工,一班是做锻带,到宁波海洋有限公司造船的。我们电焊工去上班,4.8元一天,一班是我们村里的锻压厂打铁的。这个矛盾很大,他们4.8元一天,骑着自行车回来了。我们还在打铁,打完铁,还要造围墙。我跟江书记说,矛盾太大了。这个时候杨家路头还是坟滩,企业尚在起步阶段。江书记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还是以打铁为主,4.8元一天我也不赚了,并在一起。我们锻带以前两班,工作量很大,来不及。江书记说好的,就并在一起了。在海洋公司的那些人,平时空惯了,他们不会干活。我上白班,晚上我就去盯着。上夜班,我白天就去盯着,都是睡在厂里的。谁有不对的地方,我会指出来,如果真的不行,只能开除。有一个职工,每周有三四天总要提前走,招呼也不打一声。我告诉他,只允许每周有一天可以提早走。结果他屡教不改,我就让他不要来上班了。如果他写保证书愿意改过,那就再考虑一下。
“1985年至1988年,企业多了,有铁厂、保温材料厂、轨钢厂、翻砂厂、镊子厂。1986年,我当时到村里去了,做副书记,管全村的企业,人称‘工业社长’。铁厂培养史幼芳做厂长,我跑业务,慈溪、奉化到处走。当时,我阿姨的儿子吴安光做村书记。我做的时候不长,才一年多。
“到1994年,小型企业转制了,我和小兄弟就开始自己打铁了。上午做点活,下午送送货。我们当时有两个跑业务的人,我定了规则,跑的业务越多,奖励越多。当时奖励3%,跑业务的人是叔侄俩,叔叔业务能力、交际能力比较强,所以业务很多。弄到2002年左右,我们这个房子拆迁了,村里吴书记叫我不要弄了,去村里管拆迁。等房子造好之后,我就开始管物业了,比如房子漏了要修这些。我对工业这方面比较内行。企业要做大,就要有实力。”
葛小其说:“锻压厂在现在造庙的位置,是以前大庙拆光了后造的。八几年,那时还未开放,政策有点放松,就相继办了很多厂。我在厂里做了三年,1987、1988年左右,我开始管村里的事了,管管养猪等杂事。八几年,生产队已经分成组了,生产队长就空了,我就负责了村里的一些杂事。那时候新学堂是村办公室。”姜芬琴说:“锻造厂在藕池,工厂做在学校里的。我们村里的村办企业也算办得早了,其他村是没有的。人是不多的,只有十来个人。以前的厂,规模不大的。我一个三姐夫李忠尧就是在锻造厂,他的活干得很好。”
徐建波说:“我爸(徐月定)一直在铁厂上班,一直干到厂关闭为止。这个铁厂是1971年左右开始办的,这个时候厂里只有六七个人,一开始手工敲,后来用皮带榔头敲。我们徐家人都很实在,包括我在内,都是实话实说的人,我的家族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我爸一生也是为了企业,当时打铁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开始都是用手工打铁的,他是当时厂里的副厂长,是不可缺少的。我爸在铁厂做的时间是最久的一个。我爸这个人不怎么讲话,他很苦的,一直在做,他是师傅,就一直在打模板。以前模板都是一块块打出来的,才能开模子做产品,以前不像现在开模子,都可以用机器,以前是用很大的皮带榔头敲打的。我在铁厂也做过了,我做的时候,已经用空气锥了。我20岁到铁厂上班,做了4年。以前很难进去的,因为我爸爸在里面,照顾我,才让我去那里上班。具体干的活是给人家加工打毛坯。以前铁也很缺少的,材料也不能浪费。以前的皮带榔头都有几百斤的,要拉上去然后放下来。之后用空气锥了,自动化了。做铁厂真的很苦很热,也很危险,每个人都会烫伤。当榔头打下来,火花就会飞溅起来,就算戴着手套也会溅进去。一定要等那几下敲完,才能去脱手套。严重的时候,一层皮连带手套一起被脱了。我身上的疤就是工作时候留下的,这个是高风险工作。一开始厂里说打锄头铁把,后来给别人加工。”徐月定,1958年前在塘西益智小学读书,1959年在石碶中学读书,1961年务农,1964年加入共青团,1971年起在铁厂上班,1980年入党,后担任生产厂长。
铁厂迁移到杨家路头,是1974年的事。这与机耕路铺好有关。史幼芳说:“我是1971年下半年到大队企业的。我是第二批,当时大概4个人。此前,第一批大概五六个人。原来在庙里,后来机耕路铺好了,这条车路通了,大概1974年搬过去的。杨家路头的发展也蛮好,厂有十多间房子,后来有了资金,就造了一排楼房。我们本来是锻压厂,专门打机械零件、打塑料模板的,塑料模子要开的话,就需要这个模板的,等于是给大的国有企业做材料加工。
“那时候办厂困难有的,集体企业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在庙里的大树上把架子搭起来,用皮带拖榔头上去,然后掉下来。打铁,那是以前的土方法,没有什么技术性,也没有什么科学性。以前一开始是靠手工敲的,用八角榔头,农村钱也难赚。1987年,买了空气锤。空气锤买了以后,跟以前就不一样了,设备先进了,打铁就好打了。
“一开始是拿工分的,1971年进去,18块一月,后来大概是25块,然后再加一点,30块一个月。生产队有些人就有怨言了,队办企业有30块一个月,我们每天种田,一个月只有几块。我们1971年、1972年,毛30块一月。1980年,工资有60块了,很高了。特别是如果到外面去做钣金,那工资就更高了。1986年,就自己承包厂了,营业执照上法人代表是我,厂的名字是藕池锻压厂。自己承包了,资金可以自己安排。买点东西,要村里支部书记批,等于自主权还在村里。”
“1994年,转制了,自己办厂,改为新星不锈钢厂。改革开放之后,政策就两样了,最多时带过20多个人。我们做那种不锈钢,人家用锭子炼出来,打好,钢带就做不锈钢杯子,不锈钢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我们是第一道工序,就是先把锭子加热。后来厂区就用来造房子了,造商品房,后来就转到现在这里来,把地给他们了。生产不锈钢,因为是烧煤的,灰尘比较大,环保不达标,后来就关掉了,大概是2001年关掉的。”
据吴安光的说法,铁厂(锻压厂)是藕池第一家企业,也是最好的企业,当时村人以能进铁厂为荣。铁厂的职工也十分牛,觉得村里的钱都是靠他们赚来的。有时,旁边的小厂想在休息时间用一下他们的设备,让他们来开门,他们都是十分不耐烦的。
二、藕池水平仪厂
姜芬琴说:“办企业,我们这个村的思想倒是蛮进步的,很早的时候就办了两个厂,一个是锻造厂,一个是水平仪厂。水平仪厂是怎么办起来的呢?我老爸有一点文化,村里书记叫我老爸去做知青工作,有一个女知青是苏州来的,叫胡克荣,她有做水平仪的技术。我也不知道她原来的经历,反正她有这个技术,包括这个知青的妹妹也会做的。那时候厂也是很小的,用的是玻璃钢管,差不多2—3厘米粗的玻璃钢管,这是原材料,还有酒精灯,上面有酒精。酒精灯的火没有烟的,把玻璃钢管加热。有一个机器,用脚可以踩的,踩一会儿这个火可以调节大小。看起来操作简单,但里面包含了一定技术,控制不好就做不好的。水平仪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我们做泥工,这个墙直不直,把这个一放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不直的话,水平仪就不在中间了,就斜到一边去了。”姜爱珍说:“这个厂是一个知青厂,职工大多是知青。”这印证了姜芬琴的话,水平仪厂是由苏州来的知青为首办起来的。蔡菊英说:“父亲1969年过世后,我们家里日子也比较难过。1971年,我到皎口水库去。没有做多久,就回来了。没有多久,藕池头开厂了,开的是水表厂(水平仪厂),就是在火车轨道里面,一根水平尺滑来滑去的。吴老师的老公徐信定做厂长。这些厂的人住在我家里,我的胆子也锻炼大了。15、16岁时,我在厂里干活。后来,厂也关掉了。”从有关情况来看,徐信定为厂长是对的。蔡菊英是当事人,所以话更有权威性。吴升月也明确说,是她老公办的厂。当时有女工20多人。姜芬琴说:“后来村里不办了,拿到公社去办过,这边会做的人也跟过去了,像我大姐,还有我隔壁的徐爱珠,这些人都去这个厂做过了。”这个厂称为布政公社机械仪器厂。徐爱珠说:“我进厂时,十七八岁(1970年左右)。这家厂是苏州来的知青胡克荣、庄惠珠等人办起来了。胡克荣妹妹是苏州水平仪厂的,她会做。一段时间后,她妹妹也来帮忙。厂办在张昌浩家中。玻璃比较危险,掉到地上,脚容易伤着。1973年,胡克荣、庄惠珠到皎口水库去做了,厂也就停了。1975年,公社拿去办了。胡克荣与姜素琴作为师傅,也到布政工作。职工有二三十人。我做了15年,直到工厂关门。”也就是说,1989年关门。按徐爱珠的说法,水平仪厂在做皎口水库前,地点在张昌浩家。而蔡菊英的说法是,在做皎口水库后,地点在他家中。
三、藕池塑料厂
姜岳海当厂长,1974年创办。轧机是靠人掰的。姜岳祥说:“有三台轧机,分三班。多时有七八人。有生意做一下,无生意时停了。也就存在四五年时间。”陈惠信老婆张吉英也做过。陈惠信说:“当时很难进,他老婆是因为丈人张文良被牛踩死,出于照顾一下而进厂的。”此事发生于1978年,张文良被吴家大队的牛踩死的。
吴祝庆老婆王月娥也在此厂中做过。徐定良说:“姜岳海后来搞工业了,就跟农业不大接触了。工业也搞得不太好。”
四、藕池镊子厂
洪根庆当厂长,1975—1976年间创办。张杏芳说:“原来在藕池办企业,办得很好。他到上海也去过的,做钣金。以前有的厂要用桶的,是用铁做的,用电焊焊住,那个很苦的,用手敲的。”龚财良说:“我18岁时候打铁,一两年以后,再做钣金。当时要抓阄,有些人去打铁,我抓着钣金,就去做钣金了。我做钣金也做了五六年。到宁波那把洪根庆的业务接过来,再去做(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那时候还是记工分的。我们是社会工厂,到宁波,今天给这家做,明天给另外的做,这家厂活干好了,再到别的厂去,不是固定的,我们自己没有厂的。”龚财良1949年生,18岁时当为1966年。二年后,当为1968年。洪根庆做钣金时,接来做镊子的生意,就办了这个厂,大队包给他,做钣金、镊子。他管理两家厂,镊子厂大概15个人在做。洪桂棠、张方平等人做过。1982年,徐仁定接手。
五、藕池翻砂厂
第一任厂长是吴安光,第二任是林振华,第三任是龚财良,第四任是俞云华,第五任是周厚裕,第六任是徐仁定。
翻砂厂是1981年成立的。吴安光说:“1982年,分田到户了。田里的收入,一直没有提高上去。那时候,大队里的翻砂厂关门了,人家办不起来。当时是集体承包,超额完成任务就按比例分成。我就跟(江)书记提出来,是不是田可以不要分,但这个厂由我来承包。当时他说:田没有人种不行,你要去办厂就去办好了,但田也要分去的,田不分去,我叫谁种呢?所以,我田也分到了。翻砂厂就由我承包下来了,叫来林振华等人。当时上交大队里是3000块一年,这个账目是要公开的。超出部分,按比例分成,三成可以归厂里职工分配,七成归企业集体。当时我承包的时候,老书记(江根星)说:你刚刚从田里上来的,包翻砂厂,你做得了吗?我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反正3000块钱一年给你,有分成的话就拿一点。就这样承包来了。我当时经营翻砂厂的策略是,把主要的人员组织好,供销也弄好,自己亲自管理生产。那当时翻砂厂还是做得很好的。”
李和平说:“我是17岁(1982)进村翻砂厂的,翻砂是最土的一种铸造方法。那时候有二十多个人,厂长是林振华。我在厂里做了三年。藕池翻砂厂没有变样.我师父是老思想,不知道到外面去开发,收一点废铁来当原料,那产品当然做不好。三年后(1985),我从翻砂厂走出来了,到维多利厂上班。那时候厂里好一点业务会放到外面,让别人做,简单一点的拿回来,给厂里做。厂又瘫了。然后分开了,给俞云华承包了。后来鄞江铸造厂的周厚裕来藕池村承包,他能力有,弄得还可以,但毕竟是外地人,有些人老是整他,产品老是故意做报废,就又瘫了。然后就是徐仁定了,他是村里的党员,被派下来当厂长,他运气好,那时候好买断,钞票赚了一点。”
俞云华说:“25岁时,我也包过厂的,藕池村翻砂厂是我包来的。在全公社,工资我最高了。我是最早做承包的,时间在1985年。一年都不到,时间挺短的。那时候什么人可以来包呢,村里有领导背景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文化,我吃亏也吃亏在这。承包过去没关系,但是人事权没有的,就是人招进来或者开除出去的权力没有的。我这边来不及,他也不给你通融。人家有靠山,我没有靠山。我业务接过来,人家时间都讲好的。我这个人是讲信用的,人家说货一个礼拜要拿的,我们开炉子,开了以后,铁水要倒进去。工人不给你做,就这样坐着。我被逼得没路了,我等于失信了,我给人家好话讲尽。拿来业务,一个礼拜后要交活的。那个时候也不是国有企业,村办企业都这个样子的。现在的老板如果看你做得不对,可以把你辞退掉。你承包了,工人不肯给你干,因为都是他们村里自己人压着的价钱,我去了以后,价钱抬高了,原来的是上交2000,我那时候抬高到6000块。他们看到我就难看了。”
其后,徐仁定接任。徐仁定说:“1985年左右,我去翻砂厂了。我的娘舅都在宁波,所以到翻砂厂去跑业务。在段塘的钢锯厂,我也做了五六个月。然后村里就把我叫去,把我放在厂里。之后调到翻砂厂,让我做了副厂长,在翻砂厂好几年。翻砂厂是村里办的,是集体的,我们村里的总收入只有几万。”
六、布政轨钢厂
1983—1985年,葛小其任村金属提炼厂厂长。金属提炼厂,也被称为拉丝厂。
1989—1990年,在杨家路头,洪康华任轧钢厂厂长。张龙才说:“老洪叔叔(洪康华)年纪也大了,让我承包试试看。当时村里要求上交3万一年。当时3万块也算比较多了,还有工人工资和水电费用也要付,我就硬着头皮试试看。我的压力也很大,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事情。我老婆也算村里的干部,我第一年上交的还比较多一点,多了几千块。以前卖东西要到慈溪、象山、宁海去兜兜转转,当时坐公交车去慈溪等地,早早出去,晚晚回来,像赚什么大钱似的。生产效率也有一些,工人也不喜欢半个月在做,半个月在休息,最好天天干活,来不及就加班,业务也比较多。我当时跟生产厂长说:你辛苦一点,如果做得好,下半年多分一点钱,别人年底发二百、三百,我发五百。办厂也办了四五年,慢慢转制,卖给个人,大概是1994年。我们转制应该很早,那时住在新房子。转制过来,厂房是问村里买的,村里没有上心造,厂房砖头都是用乱七八糟的烂泥弄弄的,可以算危房。后来面积不够大,我们就弄个棚,慢慢把规模弄起来。当时买厂房花了20万,我向我大舅子去借钱。我大舅子做生意,有钱的,也没有收我利息。收购的材料,都是大钢厂、小钢厂淘汰的东西,都是没有人要的。”
七、藕池羽毛厂
林德庆、吴安光先后担任过羽毛厂厂长。于春玲说:“我是1979年正月初六结婚的。1982年,村里开了一家羽毛厂,有广州人来给我们做指导老师。这个厂是老江书记一手策划的,做的是鸡毛掸子,地点在新学堂,办公室下面就是羽毛厂。这个时候村里没有钱的,就是招收年轻的员工。羽毛厂有100位女员工,给大家二两鸡毛,让我们挑,看谁能挑得快且好,我是第一名,张兰芳是第二名。因为我在羽毛厂出手快的,且是团员,广州人开会经常与我照面,所以就注意到我了。广州人是讲普通话的,我能讲几句话,跟广州人沟通起来方便些。于是我被广州人认可,给厂里跑跑业务、当当翻译。我原先家里大人是团支部书记,开会要去参加,他们看我档案,觉得还行,就让我去厂里做车间主任。后来,那个女的广州师傅生病了,这个厂就注销了。厂就存在一年多,1983年左右就关门了。”徐贤君是当时的出纳。吴安光说:“当时鸡毛厂(羽毛厂)经济效益差,那时我是生产队长,书记把我叫过去说:‘这个厂怎么弄?要么你去弄看看?’那我也去弄了,搞了一年两年,一边当生产队长,一边还要让我去管理鸡毛厂。当时条件十分窘迫。有一次,广州客人从杭州来宁波,我到南站接他。从永宁桥乘6路公交车到段塘,要2角钱,5分一站。如果从永宁桥头到段塘,二人乘车的话,身上的钱不够。当时南站可以走出来,我们就步行到恒丰纱厂,再乘6路公交车到段塘下,钱刚刚好。等我接手一年之后,我看看不对。我跟老书记说,这家厂不要去弄了,弄不好了,后来就关掉了。”
八、窑厂
窑厂在保温厂里办,分了两间屋子。张杏芳说:“窑厂是通达公司办的厂,那时候搞稳产,泥土都挑不完,我们生产队,挑了很多,像我们两个生产队,田有30亩。砖头厂(窑厂)办在通达那个位置,办了五六年吧,大约在1979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别人的砖头做得好,它做的砖头松松的,人家砌墙不喜欢用这样的。后来田分到户了,砖头厂也就不弄了,被人家买走了。”张吉峰说:“厂是李自强弄的,是村里的,就是做砖。1985年,是村里办好,承包给别人的,承包的是是集仕港人。”
九、藕池保温厂
1983年左右,开保温材料厂,厂开在杨家路头,厂长是张杏芳。1980年起,张杏芳到铁厂当厂长。1985年1月起,陈惠信跑外勤。此前,1982—1984年,他担任村合作社副社长。1984年入党。张杏芳当了五六年厂长,后给陈惠信当了。陈惠信的说法是,他与张杏芳分了两个组,他做玻璃珠,张杏芳做保温材料。1991年起,他承包了三年。1994年,转制给他个人,杨家路头工业区关掉,迁入新办的藕池工业区中,他老婆(张吉英)管车间。1999年,老婆病死,工厂也关门了。
此外,藕池小学也办过校办厂,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板桥村人俞国忠承包,徐亚晨兼会计。1990年,徐亚晨第二次到藕池小学代课,兼校办厂会计。俞国忠1979—1983年当过兵。
藕池绝缘材料厂,1985—1986年,徐仁定任厂长,赵宏海任书记。
此外,有食品厂与海绵厂,是外来人办的。
20世纪70、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由于人才、技术、资金不足,普遍做不大。在转制过程中,内外间、集体与个体间的矛盾加剧。集体观念强的村人,不愿意为个体承包人服务,更不愿意为外乡老板服务,成心怠工,导致企业效率十分低。政企不分,导致企业机制不灵活。于是,出现转制风,直接将村办集体企业出售给个人。1994年,农业部颁布文件《关于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要求将乡镇企业转制。到了1994年,藕池村也实行转制,村办企业出售给个人,乡村不再直接办厂,而改为服务企业,通过投资工业区,引进外来企业,收取租金,获得红利。藕池一直没有出现大型企业,只有一些小企业。村办工业区模式,只能出现小企业,不可能出现大企业。
第四节/诸多副业
一、织草帽
织凉帽是藕池女人的一个特色手工行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都在织凉帽。姜芬琴说:“草席是自产自销的,打草帽,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不好的。大多数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打。我们打草帽,基本上都聚在一起打的,我有三个姐姐,一起干活有个伴,老是到生产队长、大队长徐定良家里打,坐了满满的一房间,大家说说笑话、说说事情,也很有趣的,这是一种氛围。到了晚上,我们还要打,打好差不多要10点钟了。一般晚上聚在一起的比较少,因为晚上没有电灯的,只有煤油灯,太暗。到了冬天,打草帽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打草帽是要用水的,特别是西风一吹,草干了,打一会儿,就要用水浸一浸。草浸了水以后,就很冷,我们的手就要生冻疮。第二个是天冷,草比较容易断掉,要接上去。最好就是5月初这个时候打草帽,草很软的,冬天就比较痛苦。
“第二个痛苦就是晚上打,晚上打草帽老是要打瞌睡,因为很累的,我们这个地方跟其他村里打草帽方法又不一样,其他村里打草帽有三根芯、四根芯,我们打草帽就是两根芯,中间隔了两条,很细的,三根芯、四根芯,绳子很粗,五根芯、六根芯打出来,边很宽的,一条一条的,一顶草帽没几条就打完了。我们草帽打得很细的,一个顶要打10多圈,边沿要打20多圈,平的这里要打10多圈,这样打下来,最起码要30、40圈。晚上6点钟晚饭吃好,要打到10点钟。这样,可以卖到2毛钱。如果打3根芯、4根芯的话,只卖6分钱。这是比较精细的。还有更精细的,用最好的草去打,可以卖到3毛钱或者3毛8分钱,这个是大帽子,打得慢的人要五六个小时,做得快的人也要三四个小时。像我的亲家母,前几天跟我说,他们一天能打4顶。我们这个时候最多一天打3顶,上午一顶,下午一顶,晚上一顶,这样3顶。我们一般情况下就只有打2顶、3顶。我们一开始,打的时候,特别是冬天,又比较冷,冬天又没有衣服穿的,穿着破棉袄,就容易打瞌睡。这不是速度慢下来了吗?没有打好睡不了,一定要打好,才能去睡,有时候打到11点,才去睡。冬天老是要打瞌睡,夏天晚上就是蚊子多,也打不快,又很热,容易出汗。反正打帽子,是挺痛苦。当时我就想,我一生什么时候不用打草帽了就好了。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又改进了材料,席草不打了,打皮斯克,那个很软的,也不脏。以前打席子草帽是很脏的,草是地上种的,怎么洗过都没用,打过以后,手、衣服都很脏的。我家的三姐,帽子质量打得最好,人家自己戴的帽子,都叫她打,她帽子打得很好。草帽戴在头上,下雨天,水不会滴进来。还有扇子,她也打得非常好。
“后来是用打纸草。好像慈溪还要早,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纸草了,我们还是比较晚的。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开始是草帽,工厂里会收,多少分量的草可以打几顶,数字给你写好,否则你乱打也不行的。后来是打纸草,纸草是硬的。反正就是打各种各样的花色出来,这个就贵了,5块钱一顶,要打好几天。它有点艺术感,有点花纹的,不像以前初级的东西,比较秀气了。我姐姐现在还在打,其实打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十个手指一直在动,对预防老年痴呆症也是有好处的,他们八十几岁的老人也有在打的。
“打草帽也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这是有现金收入的。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女同志只在割稻的时候帮助男同志干一下,其他的时间都是男同志去干活,女同志不去的,全部都是打草帽的。以前是大家集中起来打,很开心的,我们有时候打凉帽,也唱戏,以前唱样板戏、唱京剧,尤其喜欢《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三个。我们村里有高音喇叭的,广播好了以后就放京剧了,这些京剧,每一段台词我们都能背下来,都会唱。以前的东西少,每天都是听这些,就听得滚瓜烂熟了。”
李小平说:“赵宏海跟老婆两个人都在做,他们做得非常快。”有一天,笔者到赵宏海家中采访,确实看见他与老婆两人一起打凉帽。赵宏海说,他不喜欢搓麻将之类的活动,有空就打打凉帽。李小平又说:“我也会做凉帽。那时候家里条件都很差,记得凉帽是两三角一顶。那时候放学回来要割猪草,给猪吃好。然后要给草帽收边,草帽的底就是头,一般是大人先做好,藕池男孩子实际上这种活都会做。因为家里苦,大人把草帽打好,边圈的话,都要我们去做,底(头)开始到中部这个活我们做不了,男的就是收边,做旁边那一点,收边大多数男的都会做。会做的人做得很快,像我姐姐,她一天能编一顶多,现在好像是40块一顶,一个礼拜可以收入300多块。那时候没有地方可以赚钱,也没有地方打工,就是靠打草帽。唯一赚钱的路子就是打草帽。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是妇女主任,村里老百姓草帽做好,然后由她每周挑到西门工艺品厂去卖。卖了以后,把钱分给他们,算账是叫阿伟姐算。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就是挑着走过去。工艺品厂在西门口。那时候家庭手工艺就是打草帽,属于家庭手工业,原材料进来,成品出去。”
姜芬琴说:“我们一些女同志,都是从五六岁、七八岁开始打草帽的,很会打的。一些男孩子也会打。我们的隔壁邻居,他们跟我们家相反,他们有五个男孩子,我们有四个女孩子,他们家男孩子都会打草帽,都打得很好的。大家用打草帽赚来的钱来补贴生活费,日子也是过得蛮好的。我们有四姐妹,都会打草帽,还有我妈妈也打,五个人打草帽。这个钱是一个星期收入一次,一顶草帽2毛钱。这个草是农民自己种的,是生产队负责分的,材料也是要钱的,成本5分钱,卖掉是2毛钱,还赚1毛5分钱。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也不是很贫穷,还可以,蛮好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很勤劳、很会干活的,去要饭或者没饭吃的现象,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
二、畜牧业与兽医
在生产队时期,除了种田,也重视畜牧业,譬如养猪、养鸭、养鸡之类。当时,大队有牲畜场。生产队也会养鸭、养鸡。李安法说:“布政公社提倡一户一猪,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养猪,猪卖掉,钱拿来,可以在生产队领200斤谷子。当初在布政全公社是484头牛。那时候生产队也有的,农村里每户人家都有猪的。人家养猪不一定只有一只,人家家里人多,吃饭口粮也需要得多,养得多的也有可能的。如果你不养,村里的饲料都被别人拿光了。一只肉猪卖掉,生产队里可以拿200斤的饲料粮,就是200斤的谷子。生产队里这个没有限制的,票子拿来就可以拿谷子的。”周利英说:“还要养鸡,他(叶金康)是10级劳力,人家就说了:你10级劳力,不养鸡,难道叫我们9级、8级弄啊?
他就养了。”既然养了鸭鸡,又得上市出售。包泉德说:“地主富农经常吃亏,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生产队的鸭可以卖了,生产队长派人来了,说你装两袋鸭,四五只一篓。我还觉得是好事。一共有4个人去,鸭装好挑去,加起来有60斤,那时候我还挑得动。挑到兴宁桥,人很多,他们叫我负责打秤,我这个本事也好的,算账很快。其他的人,在家里很厉害,到外面没花头了,人家给一块不知道找多少钱。鸭卖掉了,卖得很快,到家里去太早了,人家会气不过,觉得你们钱这么好赚呀。队长说:我们去逛逛吧,‘茶罗面’(阳春面)去吃一碗。他们三个嘻嘻哈哈还在吃时,我又动脑筋了,走这么远的路,空篓我不挑了。最后找一个上厕所的借口,篓子最后由他人挑回来了。”
因为畜牧业,也带来了相关的畜牧兽医。杨国富、张加洋、李安法、李小平等做过兽医。李小平说:“六年级毕业以后读中学,是在礼嘉桥。我中学没有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先做兽医,大概是1976年、1977年,做了三年。那时候村里哪里有培训,原来有个兽医,就是我堂阿哥李安法,他原来是藕池村的兽医。那时候农村要发展就养猪,每个村都有兽医。后来布政乡把他叫去了,村里就没有兽医了,就我来做了。阿哥跟我讲,一般量量体温,发热时青霉素打打,药配一点。兽医做了三四年。后来年纪大了,要找对象了,兽医说出去不太好听,我就不做了。”
三、泥水匠
孙定根说:“我小阿姐的老公是做泥水匠的,他教过我怎么做,怎么打灶头。后来我做泥水匠,给人家造房子。那时候是给人家做,拿点工分,然后吃点饭,可以拿几个馒头回家给小孩子吃。我在村里帮人家造房子也造了很多的,很多人都来叫我,我就一直在做泥水匠。藕池有很多人要造房子,都是我造的。生产队忙的时候就做生产队的活,生产队空的时候帮人家造房子。
“我的打灶技术很高。当时是烧稻草的,不是现在这样烧煤气的。打灶的话,我在板桥做的,板桥有一个(俞)元根也做泥水匠的。那时候在大队做的话,仅拿一些工分的,他也在做的。后来他找到别的活了,有泥水活也来叫我。宋严王村那边叫我去打灶头,我说你也给我带过去。后来板桥有一户人家打灶,打好了,用的时候熄火了。那户主人家问我,我们家这个小灶,稻草点着火以后,灶
洞都没有塞进去就灭了,这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我说我给你去看看。我一看,灶头倒是打得蛮好的。我说,你拆是不要拆掉了,我给你改一下。就给它稍微拆了,改了一下,给它打好、排好,他说你真是有本事。然后这个名气就越做越大了,大家都叫我打灶。以前方家人碰到了会说:老孙,走,给我打灶去。从此以后,其他泥水活没有做了,专门打灶了。
“这个是要有经验的,没有经验没有用,打灶也是这样的。过去有一个盆子,烧柴火的,塞进去,很快的。后面不一样了,这里很宽,柴火塞进去,锅边就可以烧起来了。就是这样的造型,就是上面一点点收起来,锅圈拿过来划好,用水泥刀斩好,一块一块都放好。它下面位置很大的,锅边这样烧上去,烧得很快的。以前一个灶头两个灶洞,两个灶洞的当中有一个汤锅的,以前汤锅非常好用的,你一烧火,汤锅要热的,这个汤锅不放好,你烧火的时候,汤锅冰凉的有什么用呢?所以汤锅放好,这两个位置看好,火一烧,汤锅就热得快了,这个都要经验的,以前汤锅很流行的。灶头打在这里就不大动了,如果灶洞的小缝大了一点,就要修灶了,其他的基本上不动的,用的年数多了,有可能会裂掉。
“后来村里有一个新学堂,还有两个小房间在,要打地灶,我就去打了。地灶是做年糕的灶,我们还要打砻糠灶,米轧出来,做年糕用。它那个铁板是一块一块的,走进去,砻糠掉下去,这个东西会错开的,砻糠当柴火烧的。地灶,别的砻糠用不来的,你扔进去火就灭了。我问过姐夫,他说打地灶的话,烟囱打好以后,用稻草点火看看,如果塞进去火很大,就可以用了,如果没有火,那就不能用的。点起来以后火会走,灶屋弄好,火塞进去以后会变很大的。
“我老婆生下儿子(孙民冲)以后,我做泥水匠,他也做泥水匠,他很听话。后来我给人家去砌墙,他也去,人家说这个小孩真的好乖,墙砌得整整齐齐的。方益民家的最开始是我带着我儿子去做的,方益民后来另外造房子时,是我儿子带班的。方益民后来对我儿子非常客气的,房子起几间,包括其他一些设计,都是我儿子弄好的。一开始,藕池的人都在夸,你儿子厉害。后来积了一些钱,他就不干活了。
“板桥的梁苗反,是我把他带起来的,我做泥水他都跟着去。以前工资比较低的,最多2块一日,他就1块多一点。规矩我给他立好,你给人家干活,吃的东西要当心。他是经常喝酒。我就跟他说,你到外面去,第一,酒不要多喝,第二,饭菜不要乱吃。比方大黄鱼、小黄鱼放着,不要吃,有些菜是不能动的,一般的菜,一些菜羹什么的,你可以吃的。什么时候可以放开吃呢,上梁那一天,他把亲戚叫过来办酒席,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你不吃的话,也要被人家吃光的。村里谁要造房子了,我也给他做点工,拿一点工资。我做到2002年左右,60多岁了,就不做了。”
四、轧米
轧米,普通话称碾米。这是农村大米加工行业。当时,藕池有两个轧米厂,一是藕池,一是板桥。杨裕祥称:“碾米厂老早就有了,我读书的时候碾米机就已经有了,厂大概是1958年开始的。最早碾米的人姜全财(姜小云)、张昌浩,我是第三个人。整个藕池有两个人轧米(碾米),从早上一直碾到夜。”又有徐正章,也是轧米员。
孙定根说:“轧米那会儿,我快40岁(1975)了。等于老的米厂在的,我在板桥干活,(徐)定良认识了。轧米这个行业本来是轮不到我的,原来是(励)康财在轧的,后来龚武良轧,再后来龚武良也不做了,轧米的人没有了。我也没出去做泥水匠了,我说,我来给你们轧米。他同意了,我就去轧米了。轧米轧到改革开放为止。我轧米的时候,已经不做泥水匠了。我轧米轧得非常好,我良心也好的,后来轧米不用付钱的,就是米糠不让人家拿走,人家养牛养鸡的,就到我这里来买,有了就卖给他。后来改革开放了,新的机器来了,老的机器没有用了。后来吴纪芳在了,那年去轧米,下半年去算账,算下来以后,七扣八扣,等于我没有钱拿了。当时吴纪芳拿新的机器来,我还用着老机器。他轧了以后可以拿很多钱,我没有钱拿。吴纪芳也很好,他说:这是不行的,同样是轧米,一个拿这么多,一个没有钱拿。吴纪芳就说,结200块给我。他一句话,我拿100块也好,心里舒服了。后来我也用新机器了,又快又省力。后来改革开放,我就不轧米了。”
第一节/农业生产
一、生产方式
姜岳祥说:“土地改革后,田分好了,生产队也很小心的,公粮都要交的。”
从图6-1来看,当时的集体化农业生产,内部分工是十分详细的,有植保员、种子员、肥水管理员、田间观察记录员、畜牧负责人、会计员、现金保管员、粮食(实物)保管员、绿萍专管员、粪便管理员。
葛小其说:“那个时候女人也要去种田。男人在生产队干好活,再去自留地拔拔草。女的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管孩子、补衣服,女人比男人更苦。男人4点去拔秧,7点回来吃饭,女人已经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了。男人来吃完饭了,女人开始去种田了。生产队的话要做一个月,割早稻、种晚稻。个人种的话,十几天就够了。分田到户了,种的东西卖的钱都是自己的。生产队就是大锅饭,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肯做。女人平时还要做凉帽,像我们这个时代生的女人都是会做凉帽的。
“一个生产队一年总产量是比如1000斤,除去国家公粮、社员口粮及化肥、农药、牛,能节余200斤左右。一般100亩田,要分到组、分到人,除去生产成本,一个生产队一年还有几万块结余,要如何分呢?这个是按劳动力来分的,一般要按四个季来分,春季、早稻下、晚稻上、年终,春季少一点,早稻下了稍微多点。”
二、生产工具
姜岳祥说:“打稻机,大概是1961年开始有的,藕池一个点,板桥一个点,一个点买一部。田的话还是藕池多,板桥五百多亩田,藕池一千多亩田。藕池的两个队合着买了一部。那时候板桥买了一部,本来是要分给藕池的,板桥就找了农办副主任张忠林,他说:有是有,但现在别来买,让别人知道了不好,大家都要的话,我们也拿不出来,因为没有几部。我们说那什么时候好拿呢?他说等晚一点。就在晚上偷偷摸摸去,还是走小路,走大路难为情,也怕别人争,就这样买了一部打稻机。最早一个大队只有一部,过了三年,就很多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买了,一个生产队一部。有电动打稻机比较迟了,是七八十年代的事。作为队长,也种地,忙了要帮,开早工也要去,工作每天都要安排好。那时候是分任务的,你完成得早可以回去。后来分自留地了,你可以弄自留地去。”
三、拖拉机与农用船
1960年12月,藕池大队向邻近的建庄大队购买了一部机船,共2000元,当时只付了300元。其余款项约定1961年早稻期时分批还上,结果到了1963年5月仍没有还上,于是被建庄大队告上法庭。后来经过调解,藕池村同意分两批还上,才了了此事。由此也可见当时藕池大队经济之拮据。戚明华说:“那个时候都是船,每个生产队有2只船和2只牛,拖拉机有的时候是1976年左右了,1000多亩田靠一辆拖拉机。以前也没有石子路,要用船运着拖拉机到板桥,再搬到岸上使用。”
四、挑坟滩
徐繁荣说:“在生产队,我们挑坟滩、挑河泥,那时候最苦了。挑坟滩是分田到户前一两年,大概是1979年,那时候我们还小,挑得背都弯了,挑坟滩最苦了。区域都给你分好的,运气好一点的话,石块少一点,运气差一点的话,石块比较多,翻都翻不动。我们算苦了,但比起上辈人,我们至少有得吃了,但是劳力还是要出的。爸爸当了村里一个小领导,家里的事情就我们自己做了。做皎口水库的时候,我刚好要发育,一个小后生挑得背都弯了。”
五、进城积肥
姜岳祥说:“那时候很困难,那就动脑筋。要种菜籽、大麦和水稻,但是没有肥料,所以稻子种起来都小小的,只能扩大面积。一个生产队,105亩田,20%要种大麦,10%是菜籽。种点菜籽,肥料也没有的,这里离城里很近,就连夜去城里偷点大粪回来当肥料。那时候肥料还是要控制的,都是收集了后再卖给农民,我们生产队买来,还得分配的。以前就是给个条子写明几点走,撑着船过去等。最早船也是没有的,都是从地主那没收来的船。我们队以前就是用河泥当肥料,现在这样的河泥,以前碰都碰不到,有的话真的高兴死了。现在都填掉了,也不用积肥了。以前的粮站,也是一点点搞起来的。我们生产队有两只船,早晚饭吃好就去积肥了。粮食种得好了,我们也能富裕点。那时候都是晚上干这活,晚饭吃一点就去了。积过肥的河泥用来浇菜、浇麦、浇田,浇过了,产量是有点不一样的。”吴升月说:“那时候要积肥,就到宁波给别人倒马桶然后挑回来,积肥多产量也高,第6生产队,副队长就是徐定良,正队长是吴祝庆。副队长抓生产,他非常会做,积肥时,每天早上就出去到宁波倒马桶。人家肥积不来,我们是每天都有。积肥多,产量高,分红也多。”
姜冲德说:“以前化肥不怎么用的,因为是要花钱的,以前浇点氨水,尿素稍微放一点,这已经算是很好了,其他是没有的。一般都要到宁波城里去积肥,就是倒马桶的,以前都没有什么化肥的,都靠这些粪水的。”姜冲德又说:“我们经常晚上饭吃好去,半夜去弄肥。如果被抓,还要到大队里去打证明,要去讲好话的。以前从九中挑出来,走城隍庙过来,这么远的路。”
六、打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打水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行业。当时,有专门的人负责打水。江根星、叶金康、张昌浩、洪根庆等人,均打过水。姜岳祥说:“买第一台打水机的是板桥,那时候我28岁,当兵已经回来了,是1963年。那时候干旱,稻谷都晒死了,一点收成都没有。方家耷的张忠林是农办的,他说:打水机你们要吗?那时候都买不起,村里没有钱。板桥把口粮卖掉,才买了这个打水机,这是第一部。但是效果很好,粮食丰收。打水机的管子(口)是10寸的,可以机动的,藕池要用,可以借给藕池,这里打好,再去那边。此前的1959年,姚江大闸造好了,水拦起来,就可以灌溉了。慈溪、江北都要拿水,很多机器排着,你也打,我也要打。我们的水是从青林渡放过来的。”周利英说:“以前一直要打水的,从3月份开始打,一直打到田没有了为止。他们是大队打水员。”
七、抢收抢种
徐建波说:“我1982年开始也分到田了,我们第7生产队人少地多,地分到了17亩。我爷爷自己种不过来,又给了我们3亩,总共20亩。那个时候田都是靠人力种的,我爸还在铁厂上班,分田到户时,我才16岁,20亩田我一个人管不过来,真的很苦。我爸爸基本上早上5点起床,早工开好之后,再去上班。我做到18岁,也去铁厂上班了。我们家一共4个人,还有我妈和妹妹。当时妹妹小,已经读初中了,妹妹基本都是在家里烧饭,活基本上都是我们三个人做。‘双抢’也是很苦,基本都是凌晨二三点起床,做到晚上11点,一直做了六七年。后来,外地人来了,拿点田出来给人家种,才轻松一点了。”李小平说:“生产队时,我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是张昌浩,我们叫他‘老板’。张昌浩人是很好的,那时候田多人少。在规定时间,一定要种,要开夜工,要拔秧、开早工。当时还年轻,凌晨一两点起床拔秧田,两个人拼在一起干,一人一半。拔好以后,挑到地里,让妇女插秧。有一次,我和洪根庆拼的,他说你怎么拔不上来了呀,实际上我在打瞌睡了,睡着了。”徐仁定说:“像现在怎么可能想得到,那时候田种得都怕了。那时候天下雨,稻没有割,天晴了,共青团员3点钟就要去割,干到天亮。3亩田上午打好,下午就好种了。”周利英说:“以前当干部都是实干的,是要带头做的,且要比人家多做,如果比人家做得少,人家不服的。天亮后,以12点为界,分两个班,半天轮到一班。轮到你,就算是12点钟的时候,天最热,你也要去干的,下雨也要去,打雷也要去的。”
八、收入不高
周利英说:“那时候记工分,没有现钱,哪有现钱买菜啊。如果就男人,女人不做,工分容易超支。我们两个人都干,超支倒是没有。”史幼芳说:“我们农民有句话,田沿三尺高,跳出田沿就好。头想高烟囱,城市的烟囱高高的,都想到城市去。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买的,粮票还分地方粮票,有宁波粮票、浙江粮票、全国粮票。我们到上海去,要拿全国粮票的,浙江粮票都没有用的,饭都不能吃。宁波城市里的工人,带鱼都可以领大一点的,我们农村里分到的带鱼都是小小的。我记得我25岁时,有的东西还要用票买的。国家贫穷,老百姓也就这样了。农民每天背朝天种田,下雨也要淋,真的很辛苦。现在国家对农民也重视,国家也富强了,总归是好起来了,农民翻身出头了。”
九、种席草
杨国平说:“当年种席草时,收上后要晒好,在太阳底下,要三朝、四朝地晒,还要摇着船去宁波去晒呢。俗话说‘小暑割草,大暑割稻’,差不多是最热的时候割席草。后来是种日本席草,做榻榻米的,从田里割来,用泥粉弄过,再晒过,要晒过几天。这个草细,本地草比较粗。日本席草种植始于20世纪80年代,不过本地席草种也种的,但是比较少了。个人分田到户以后,大家都种日本席草了,因为种这个收入高”。姜芬琴说:“还有草帽和我们睡的席子,也是我们自己种的草做的。自己种的席草,晒干以后,一捆一捆给它捆好,然后用两根稻草做的绳子给它捆起来的。这个捆的技术也是很难的,因为席草晒干以后很滑的,如果捆不好的话,一拿就散掉了。我老爸捆的席草,又干净又好,从来不会散掉。”徐森林说:“天亮起来,大家饿着肚子去割席草,饭也没得吃。那时候有种黄桃的,有时候买点黄桃来当饭。席草还要把它晒干,还要去卖,那时候真的很苦的。等我们卖完了回来,人家早就在吃饭了。我们回到家里,还要放夜潮,那时候很苦的。”
此外,还有稻草。姜芬琴说:“我老爸(姜阿利)种出来的东西很精细的,泥土弄得像米粉一样精细。我们早稻割下来以后,稻草干了,拿回来要储存。那时候就靠烧稻草当燃料用的。稻草都是储存在屋子外面的,要给搭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堆。一般的农民都搭不好,搭到一定大小就要塌掉了。我老爸的草堆,可以搭到最大最高,像房子一样盖起来,不管多大的雨,里面都淋不进去的。要用的时候,不是从上面一捆捆拿的,而是在中间抽的。这么大的一个草堆,它是一捆捆都叠好的。如果草堆没有搭好的话,抽出来后,这个草堆就要塌下来了。我老爸搭的草堆,你去抽好了,它不会塌下来的,很厉害的,这也是一种技术,一种手艺。20世纪80年代,我们村里集体经济就是靠农田做出来的,可以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村里也没有很穷的人家。”
第二节/内河捕鱼
姚国华说:“父亲(姚信芳)也是捕鱼的。在藕池,捕鱼的有两户,一个是叶家(叶根财),一户是姚家。叶家是四兄弟,姚家也是四兄弟。以前我父亲也是很辛苦的,在河塘里捕鱼。我父亲有4个儿子2个女儿,以前人多,赚不到钱。我家捕鱼是从爷爷开始的。我父亲三个兄弟,都是捕鱼的,嫂子也是捕鱼的。那时候捕鱼的人,多数是住在船上的。房子也是有的,如果不去外面捕鱼了,就回家里来住。以前就一条船,小小的手摇船,在旁边的江河里捕鱼。开出去以后的话,可能要2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一般要背两袋米去。捕了鱼还要去卖掉,这个也要看行情的,经常卖不掉,臭了倒掉也是经常的。过去捕到好的螃蟹,我父亲就卖给藕池的老板,换一点米。现在我也不会捕鱼了。现在好的东西都很值钱,大的河鲫鱼要40块、50块一斤。
“父亲三兄弟里,大伯伯早就到沈家门修皮鞋去了,后来又回来捕鱼。捕鱼的人是苦的,钱又赚不到。我们家6个兄弟姐妹,你知道要吃多少饭吗?那时候男孩子最起码有3碗可以吃,那四个兄弟就12碗了。米是跟人家买的,我们家以前一个大大的米缸,要煮一锅的,不然不够吃。我们四兄弟原来也捕鱼,现在有一个在开五金厂。现在,最大的阿哥(姚昌华)还在捕鱼,还有一个阿弟(姚宝华)也是。老大天冷不捕了,天热就捕一捕鱼,因为他79岁了。老四是一直在捕鱼的。
“我们是在布政的,布政渔业队早就有了。我们户口在藕池,工作单位在布政。渔业队在板桥,有100多个人。以前老的渔业队在厂里干活,现在大家也都退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捕鱼的人合在一起,变成渔业大队了。我们分房子没有享受到的,因为分属不同的经济合作社。这也有道理,因为农民是有土地资源的,靠土地生活的。你们渔业是靠水资源,也可以去自己开发。我十多岁开始捕鱼的时候,这边水很多的,但是后来被拦起来了。我是1973年结婚的。结婚了以后,我还在捕鱼,老婆开始在五金厂上班,后来厂被个人承包去了,也出来一起去卖鱼。
“1983年到2011年,我一直当渔业社社长。渔业社是不分组的,我是属于‘半工半渔’的,上午到村里办事,下午出去捕鱼。一般来说,我能解决的我自己去做,我不能解决的就找村书记。那时候河塘是渔业社的主要经济来源,收入也是蛮可观的,承包河道,多少长度多少钱一年。在古林镇范围我管理不了,石碶街道也有。石碶也有渔业社的,但河塘是属于我们的。后来塘西造敬老院,把河塘填了。这事当时是石碶街道办的,河的面积是属于我们渔业队的,所以要到石碶街道去要点适当的赔偿,当时的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双方是共同协商的。我就讲了,多少总归要赔偿一点的,不赔偿是不可能的。”
陈利菊补充说:“那时候捕鱼,用丝网和小船作业。这个就是典型的内河捕鱼。捕鱼的行业不是很好做,只能养家糊口,跟农民种田一样,也没有什么花头的,也很苦的,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当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想让儿子和女儿生活能好一点,也要咬牙干。这个苦和种田的苦是不同,农民的苦是有季节的,我们是一年四季的。我们不怕下雨,但是怕响雷。”
第三节/村办企业
在大队时期,农业为主,工业为辅,是一条基本原则。两者之间,多少有一些矛盾。当时村中领导,往往将杨家路头工业区称为“梁山巢”。因为他们赚了钱,只会私分,上交村里的财政很少。
乡里有乡办企业,大队有队办企业。1971年可能是个高峰期,办厂都是1971年开始的。
一、藕池铁厂
铁厂,也被村人叫作锻压厂。1969年,永康商人来1队办铁厂加工。1971年,大队接手,独立办厂。徐信定当厂长,成员有张明芳、龚财良、李忠尧、陈再明、戚明亮、张小康等人。藕池为了办打铁厂,领导与技工曾去上海参与培训。
张小康说:“我那时候28岁(1969),有一个永康人到我们第一生产队来问:你们有会打铁的吗?我们给你办厂,你们生产队的人去工作,给生产队60元一个月。我们队长一听挺好的,就同意了。厂子是以打农具为主的。我当时在畜牧场,他们打铁厂有所发展了,炉灶开得多了,要叫更多的人去。生产队的人打铁毕竟是外行,不想打了,就来叫我来了。我想想打铁是吃技术饭的,就同意了。我在生产队里就是打铁,做了两年。两年下来,已经有点学会了。因为我做事非常勤快,永康人很喜欢我。结果,生产队里矛盾很大,说厂里这么早下班,农民早上4点钟还要下田。结果,这个厂开不下去了,就关掉了。
“大队书记江根星听说后就讲,大队去开,这个厂就给了大队。大队就开社员大会,社员全部报名想去。因为我的成分不好,是富农子女,就没有去报名。结果大队干部说,你为什么昨天没报名?我说报跟不报也是一样,到时候也要被淘汰下来的。他说,这个不用管的。过了八个月,永康那个老板说:张小康人很勤劳,这个人很好。结果,我又被他叫去了。我那时候29岁(1970)。我们藕池前一代,基本上个个都打过铁,但都没干长久,只有我一个人做得长。
“厂给了大队以后,大队人去厂里做工的人多了,工资就付不起了。我们村里书记说,从农业收入里调过去。还有一家米厂,去轧米,给4毛5分一天。这个时候塑料厂刚开始有,这个利润也蛮好,赚了一些钱。我们藕池铁厂没有设备,想来想去,都觉得做不下去。为什么呢?一天的时间,两个人只能打一段铁,三天打下来,没多少好做,所以很烦。买铁要到耐火厂去买的,买了以后,用船拖回来。耐火厂那边回来,要路过三江口的,因为太重,船有时候会翻,人没有淹死,算运气好了。我是一直打铁的,打到1986年实行厂长责任制,厂被承包了为止。我打铁18年,这样风风雨雨过来,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是从农民起家的。”
吴升月说:“1971年已经办打铁厂了,这是村里第一个厂,在藕池村庙里办,是机器打的。厂办了很多年,我老头1975年去了。这是藕池村第一个工厂,规模比较大,有二十几个职工,产品的销售也很好,那时候劳动力不紧张,生产队劳动不紧张,办厂能给村里增加收入。我老头那时候34岁了,下面的人都是18、19岁的小青年。厂一直到很晚才关。主要是做模具坯子,这个要用铁打出来,相当于做铸模的坯子,然后把这个坯子拿到模具厂去开模,他们不会开模,就只能打坯子。那时候是书记江根星、大队长姜岳海和我老头讨论出来要办这样一个厂,然后叫我老头去负责,他就从生产队走出来去办厂了。厂里都是拿工分,没有补贴的。”
1974年1月到1976年12月,徐信华回村铁厂工作,担任厂长。由此可知,徐信定走前,村中已经将徐信华安排为厂长了。
1978年,由李安明当厂长。李安明说:“1973年,村里叫我开拖拉机。到1977年,布政乡镇府把我叫去培养。1978年,藕池的锻压厂叫我去当厂长。①当时我妈是支委,大队开夜会说有个队办企业,非常不容易,这个厂的厂长没有人当。我妈就跟江书记说:这个厂长还是让我儿子去当。我妈夜会开回来跟我说:江书记同意让你去做这个厂的厂长。我答应了。我们有两班,一班是做钣金工,一班是做锻带,到宁波海洋有限公司造船的。我们电焊工去上班,4.8元一天,一班是我们村里的锻压厂打铁的。这个矛盾很大,他们4.8元一天,骑着自行车回来了。我们还在打铁,打完铁,还要造围墙。我跟江书记说,矛盾太大了。这个时候杨家路头还是坟滩,企业尚在起步阶段。江书记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还是以打铁为主,4.8元一天我也不赚了,并在一起。我们锻带以前两班,工作量很大,来不及。江书记说好的,就并在一起了。在海洋公司的那些人,平时空惯了,他们不会干活。我上白班,晚上我就去盯着。上夜班,我白天就去盯着,都是睡在厂里的。谁有不对的地方,我会指出来,如果真的不行,只能开除。有一个职工,每周有三四天总要提前走,招呼也不打一声。我告诉他,只允许每周有一天可以提早走。结果他屡教不改,我就让他不要来上班了。如果他写保证书愿意改过,那就再考虑一下。
“1985年至1988年,企业多了,有铁厂、保温材料厂、轨钢厂、翻砂厂、镊子厂。1986年,我当时到村里去了,做副书记,管全村的企业,人称‘工业社长’。铁厂培养史幼芳做厂长,我跑业务,慈溪、奉化到处走。当时,我阿姨的儿子吴安光做村书记。我做的时候不长,才一年多。
“到1994年,小型企业转制了,我和小兄弟就开始自己打铁了。上午做点活,下午送送货。我们当时有两个跑业务的人,我定了规则,跑的业务越多,奖励越多。当时奖励3%,跑业务的人是叔侄俩,叔叔业务能力、交际能力比较强,所以业务很多。弄到2002年左右,我们这个房子拆迁了,村里吴书记叫我不要弄了,去村里管拆迁。等房子造好之后,我就开始管物业了,比如房子漏了要修这些。我对工业这方面比较内行。企业要做大,就要有实力。”
葛小其说:“锻压厂在现在造庙的位置,是以前大庙拆光了后造的。八几年,那时还未开放,政策有点放松,就相继办了很多厂。我在厂里做了三年,1987、1988年左右,我开始管村里的事了,管管养猪等杂事。八几年,生产队已经分成组了,生产队长就空了,我就负责了村里的一些杂事。那时候新学堂是村办公室。”姜芬琴说:“锻造厂在藕池,工厂做在学校里的。我们村里的村办企业也算办得早了,其他村是没有的。人是不多的,只有十来个人。以前的厂,规模不大的。我一个三姐夫李忠尧就是在锻造厂,他的活干得很好。”
徐建波说:“我爸(徐月定)一直在铁厂上班,一直干到厂关闭为止。这个铁厂是1971年左右开始办的,这个时候厂里只有六七个人,一开始手工敲,后来用皮带榔头敲。我们徐家人都很实在,包括我在内,都是实话实说的人,我的家族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我爸一生也是为了企业,当时打铁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开始都是用手工打铁的,他是当时厂里的副厂长,是不可缺少的。我爸在铁厂做的时间是最久的一个。我爸这个人不怎么讲话,他很苦的,一直在做,他是师傅,就一直在打模板。以前模板都是一块块打出来的,才能开模子做产品,以前不像现在开模子,都可以用机器,以前是用很大的皮带榔头敲打的。我在铁厂也做过了,我做的时候,已经用空气锥了。我20岁到铁厂上班,做了4年。以前很难进去的,因为我爸爸在里面,照顾我,才让我去那里上班。具体干的活是给人家加工打毛坯。以前铁也很缺少的,材料也不能浪费。以前的皮带榔头都有几百斤的,要拉上去然后放下来。之后用空气锥了,自动化了。做铁厂真的很苦很热,也很危险,每个人都会烫伤。当榔头打下来,火花就会飞溅起来,就算戴着手套也会溅进去。一定要等那几下敲完,才能去脱手套。严重的时候,一层皮连带手套一起被脱了。我身上的疤就是工作时候留下的,这个是高风险工作。一开始厂里说打锄头铁把,后来给别人加工。”徐月定,1958年前在塘西益智小学读书,1959年在石碶中学读书,1961年务农,1964年加入共青团,1971年起在铁厂上班,1980年入党,后担任生产厂长。
铁厂迁移到杨家路头,是1974年的事。这与机耕路铺好有关。史幼芳说:“我是1971年下半年到大队企业的。我是第二批,当时大概4个人。此前,第一批大概五六个人。原来在庙里,后来机耕路铺好了,这条车路通了,大概1974年搬过去的。杨家路头的发展也蛮好,厂有十多间房子,后来有了资金,就造了一排楼房。我们本来是锻压厂,专门打机械零件、打塑料模板的,塑料模子要开的话,就需要这个模板的,等于是给大的国有企业做材料加工。
“那时候办厂困难有的,集体企业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在庙里的大树上把架子搭起来,用皮带拖榔头上去,然后掉下来。打铁,那是以前的土方法,没有什么技术性,也没有什么科学性。以前一开始是靠手工敲的,用八角榔头,农村钱也难赚。1987年,买了空气锤。空气锤买了以后,跟以前就不一样了,设备先进了,打铁就好打了。
“一开始是拿工分的,1971年进去,18块一月,后来大概是25块,然后再加一点,30块一个月。生产队有些人就有怨言了,队办企业有30块一个月,我们每天种田,一个月只有几块。我们1971年、1972年,毛30块一月。1980年,工资有60块了,很高了。特别是如果到外面去做钣金,那工资就更高了。1986年,就自己承包厂了,营业执照上法人代表是我,厂的名字是藕池锻压厂。自己承包了,资金可以自己安排。买点东西,要村里支部书记批,等于自主权还在村里。”
“1994年,转制了,自己办厂,改为新星不锈钢厂。改革开放之后,政策就两样了,最多时带过20多个人。我们做那种不锈钢,人家用锭子炼出来,打好,钢带就做不锈钢杯子,不锈钢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我们是第一道工序,就是先把锭子加热。后来厂区就用来造房子了,造商品房,后来就转到现在这里来,把地给他们了。生产不锈钢,因为是烧煤的,灰尘比较大,环保不达标,后来就关掉了,大概是2001年关掉的。”
据吴安光的说法,铁厂(锻压厂)是藕池第一家企业,也是最好的企业,当时村人以能进铁厂为荣。铁厂的职工也十分牛,觉得村里的钱都是靠他们赚来的。有时,旁边的小厂想在休息时间用一下他们的设备,让他们来开门,他们都是十分不耐烦的。
二、藕池水平仪厂
姜芬琴说:“办企业,我们这个村的思想倒是蛮进步的,很早的时候就办了两个厂,一个是锻造厂,一个是水平仪厂。水平仪厂是怎么办起来的呢?我老爸有一点文化,村里书记叫我老爸去做知青工作,有一个女知青是苏州来的,叫胡克荣,她有做水平仪的技术。我也不知道她原来的经历,反正她有这个技术,包括这个知青的妹妹也会做的。那时候厂也是很小的,用的是玻璃钢管,差不多2—3厘米粗的玻璃钢管,这是原材料,还有酒精灯,上面有酒精。酒精灯的火没有烟的,把玻璃钢管加热。有一个机器,用脚可以踩的,踩一会儿这个火可以调节大小。看起来操作简单,但里面包含了一定技术,控制不好就做不好的。水平仪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我们做泥工,这个墙直不直,把这个一放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不直的话,水平仪就不在中间了,就斜到一边去了。”姜爱珍说:“这个厂是一个知青厂,职工大多是知青。”这印证了姜芬琴的话,水平仪厂是由苏州来的知青为首办起来的。蔡菊英说:“父亲1969年过世后,我们家里日子也比较难过。1971年,我到皎口水库去。没有做多久,就回来了。没有多久,藕池头开厂了,开的是水表厂(水平仪厂),就是在火车轨道里面,一根水平尺滑来滑去的。吴老师的老公徐信定做厂长。这些厂的人住在我家里,我的胆子也锻炼大了。15、16岁时,我在厂里干活。后来,厂也关掉了。”从有关情况来看,徐信定为厂长是对的。蔡菊英是当事人,所以话更有权威性。吴升月也明确说,是她老公办的厂。当时有女工20多人。姜芬琴说:“后来村里不办了,拿到公社去办过,这边会做的人也跟过去了,像我大姐,还有我隔壁的徐爱珠,这些人都去这个厂做过了。”这个厂称为布政公社机械仪器厂。徐爱珠说:“我进厂时,十七八岁(1970年左右)。这家厂是苏州来的知青胡克荣、庄惠珠等人办起来了。胡克荣妹妹是苏州水平仪厂的,她会做。一段时间后,她妹妹也来帮忙。厂办在张昌浩家中。玻璃比较危险,掉到地上,脚容易伤着。1973年,胡克荣、庄惠珠到皎口水库去做了,厂也就停了。1975年,公社拿去办了。胡克荣与姜素琴作为师傅,也到布政工作。职工有二三十人。我做了15年,直到工厂关门。”也就是说,1989年关门。按徐爱珠的说法,水平仪厂在做皎口水库前,地点在张昌浩家。而蔡菊英的说法是,在做皎口水库后,地点在他家中。
三、藕池塑料厂
姜岳海当厂长,1974年创办。轧机是靠人掰的。姜岳祥说:“有三台轧机,分三班。多时有七八人。有生意做一下,无生意时停了。也就存在四五年时间。”陈惠信老婆张吉英也做过。陈惠信说:“当时很难进,他老婆是因为丈人张文良被牛踩死,出于照顾一下而进厂的。”此事发生于1978年,张文良被吴家大队的牛踩死的。
吴祝庆老婆王月娥也在此厂中做过。徐定良说:“姜岳海后来搞工业了,就跟农业不大接触了。工业也搞得不太好。”
四、藕池镊子厂
洪根庆当厂长,1975—1976年间创办。张杏芳说:“原来在藕池办企业,办得很好。他到上海也去过的,做钣金。以前有的厂要用桶的,是用铁做的,用电焊焊住,那个很苦的,用手敲的。”龚财良说:“我18岁时候打铁,一两年以后,再做钣金。当时要抓阄,有些人去打铁,我抓着钣金,就去做钣金了。我做钣金也做了五六年。到宁波那把洪根庆的业务接过来,再去做(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那时候还是记工分的。我们是社会工厂,到宁波,今天给这家做,明天给另外的做,这家厂活干好了,再到别的厂去,不是固定的,我们自己没有厂的。”龚财良1949年生,18岁时当为1966年。二年后,当为1968年。洪根庆做钣金时,接来做镊子的生意,就办了这个厂,大队包给他,做钣金、镊子。他管理两家厂,镊子厂大概15个人在做。洪桂棠、张方平等人做过。1982年,徐仁定接手。
五、藕池翻砂厂
第一任厂长是吴安光,第二任是林振华,第三任是龚财良,第四任是俞云华,第五任是周厚裕,第六任是徐仁定。
翻砂厂是1981年成立的。吴安光说:“1982年,分田到户了。田里的收入,一直没有提高上去。那时候,大队里的翻砂厂关门了,人家办不起来。当时是集体承包,超额完成任务就按比例分成。我就跟(江)书记提出来,是不是田可以不要分,但这个厂由我来承包。当时他说:田没有人种不行,你要去办厂就去办好了,但田也要分去的,田不分去,我叫谁种呢?所以,我田也分到了。翻砂厂就由我承包下来了,叫来林振华等人。当时上交大队里是3000块一年,这个账目是要公开的。超出部分,按比例分成,三成可以归厂里职工分配,七成归企业集体。当时我承包的时候,老书记(江根星)说:你刚刚从田里上来的,包翻砂厂,你做得了吗?我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反正3000块钱一年给你,有分成的话就拿一点。就这样承包来了。我当时经营翻砂厂的策略是,把主要的人员组织好,供销也弄好,自己亲自管理生产。那当时翻砂厂还是做得很好的。”
李和平说:“我是17岁(1982)进村翻砂厂的,翻砂是最土的一种铸造方法。那时候有二十多个人,厂长是林振华。我在厂里做了三年。藕池翻砂厂没有变样.我师父是老思想,不知道到外面去开发,收一点废铁来当原料,那产品当然做不好。三年后(1985),我从翻砂厂走出来了,到维多利厂上班。那时候厂里好一点业务会放到外面,让别人做,简单一点的拿回来,给厂里做。厂又瘫了。然后分开了,给俞云华承包了。后来鄞江铸造厂的周厚裕来藕池村承包,他能力有,弄得还可以,但毕竟是外地人,有些人老是整他,产品老是故意做报废,就又瘫了。然后就是徐仁定了,他是村里的党员,被派下来当厂长,他运气好,那时候好买断,钞票赚了一点。”
俞云华说:“25岁时,我也包过厂的,藕池村翻砂厂是我包来的。在全公社,工资我最高了。我是最早做承包的,时间在1985年。一年都不到,时间挺短的。那时候什么人可以来包呢,村里有领导背景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文化,我吃亏也吃亏在这。承包过去没关系,但是人事权没有的,就是人招进来或者开除出去的权力没有的。我这边来不及,他也不给你通融。人家有靠山,我没有靠山。我业务接过来,人家时间都讲好的。我这个人是讲信用的,人家说货一个礼拜要拿的,我们开炉子,开了以后,铁水要倒进去。工人不给你做,就这样坐着。我被逼得没路了,我等于失信了,我给人家好话讲尽。拿来业务,一个礼拜后要交活的。那个时候也不是国有企业,村办企业都这个样子的。现在的老板如果看你做得不对,可以把你辞退掉。你承包了,工人不肯给你干,因为都是他们村里自己人压着的价钱,我去了以后,价钱抬高了,原来的是上交2000,我那时候抬高到6000块。他们看到我就难看了。”
其后,徐仁定接任。徐仁定说:“1985年左右,我去翻砂厂了。我的娘舅都在宁波,所以到翻砂厂去跑业务。在段塘的钢锯厂,我也做了五六个月。然后村里就把我叫去,把我放在厂里。之后调到翻砂厂,让我做了副厂长,在翻砂厂好几年。翻砂厂是村里办的,是集体的,我们村里的总收入只有几万。”
六、布政轨钢厂
1983—1985年,葛小其任村金属提炼厂厂长。金属提炼厂,也被称为拉丝厂。
1989—1990年,在杨家路头,洪康华任轧钢厂厂长。张龙才说:“老洪叔叔(洪康华)年纪也大了,让我承包试试看。当时村里要求上交3万一年。当时3万块也算比较多了,还有工人工资和水电费用也要付,我就硬着头皮试试看。我的压力也很大,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事情。我老婆也算村里的干部,我第一年上交的还比较多一点,多了几千块。以前卖东西要到慈溪、象山、宁海去兜兜转转,当时坐公交车去慈溪等地,早早出去,晚晚回来,像赚什么大钱似的。生产效率也有一些,工人也不喜欢半个月在做,半个月在休息,最好天天干活,来不及就加班,业务也比较多。我当时跟生产厂长说:你辛苦一点,如果做得好,下半年多分一点钱,别人年底发二百、三百,我发五百。办厂也办了四五年,慢慢转制,卖给个人,大概是1994年。我们转制应该很早,那时住在新房子。转制过来,厂房是问村里买的,村里没有上心造,厂房砖头都是用乱七八糟的烂泥弄弄的,可以算危房。后来面积不够大,我们就弄个棚,慢慢把规模弄起来。当时买厂房花了20万,我向我大舅子去借钱。我大舅子做生意,有钱的,也没有收我利息。收购的材料,都是大钢厂、小钢厂淘汰的东西,都是没有人要的。”
七、藕池羽毛厂
林德庆、吴安光先后担任过羽毛厂厂长。于春玲说:“我是1979年正月初六结婚的。1982年,村里开了一家羽毛厂,有广州人来给我们做指导老师。这个厂是老江书记一手策划的,做的是鸡毛掸子,地点在新学堂,办公室下面就是羽毛厂。这个时候村里没有钱的,就是招收年轻的员工。羽毛厂有100位女员工,给大家二两鸡毛,让我们挑,看谁能挑得快且好,我是第一名,张兰芳是第二名。因为我在羽毛厂出手快的,且是团员,广州人开会经常与我照面,所以就注意到我了。广州人是讲普通话的,我能讲几句话,跟广州人沟通起来方便些。于是我被广州人认可,给厂里跑跑业务、当当翻译。我原先家里大人是团支部书记,开会要去参加,他们看我档案,觉得还行,就让我去厂里做车间主任。后来,那个女的广州师傅生病了,这个厂就注销了。厂就存在一年多,1983年左右就关门了。”徐贤君是当时的出纳。吴安光说:“当时鸡毛厂(羽毛厂)经济效益差,那时我是生产队长,书记把我叫过去说:‘这个厂怎么弄?要么你去弄看看?’那我也去弄了,搞了一年两年,一边当生产队长,一边还要让我去管理鸡毛厂。当时条件十分窘迫。有一次,广州客人从杭州来宁波,我到南站接他。从永宁桥乘6路公交车到段塘,要2角钱,5分一站。如果从永宁桥头到段塘,二人乘车的话,身上的钱不够。当时南站可以走出来,我们就步行到恒丰纱厂,再乘6路公交车到段塘下,钱刚刚好。等我接手一年之后,我看看不对。我跟老书记说,这家厂不要去弄了,弄不好了,后来就关掉了。”
八、窑厂
窑厂在保温厂里办,分了两间屋子。张杏芳说:“窑厂是通达公司办的厂,那时候搞稳产,泥土都挑不完,我们生产队,挑了很多,像我们两个生产队,田有30亩。砖头厂(窑厂)办在通达那个位置,办了五六年吧,大约在1979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别人的砖头做得好,它做的砖头松松的,人家砌墙不喜欢用这样的。后来田分到户了,砖头厂也就不弄了,被人家买走了。”张吉峰说:“厂是李自强弄的,是村里的,就是做砖。1985年,是村里办好,承包给别人的,承包的是是集仕港人。”
九、藕池保温厂
1983年左右,开保温材料厂,厂开在杨家路头,厂长是张杏芳。1980年起,张杏芳到铁厂当厂长。1985年1月起,陈惠信跑外勤。此前,1982—1984年,他担任村合作社副社长。1984年入党。张杏芳当了五六年厂长,后给陈惠信当了。陈惠信的说法是,他与张杏芳分了两个组,他做玻璃珠,张杏芳做保温材料。1991年起,他承包了三年。1994年,转制给他个人,杨家路头工业区关掉,迁入新办的藕池工业区中,他老婆(张吉英)管车间。1999年,老婆病死,工厂也关门了。
此外,藕池小学也办过校办厂,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板桥村人俞国忠承包,徐亚晨兼会计。1990年,徐亚晨第二次到藕池小学代课,兼校办厂会计。俞国忠1979—1983年当过兵。
藕池绝缘材料厂,1985—1986年,徐仁定任厂长,赵宏海任书记。
此外,有食品厂与海绵厂,是外来人办的。
20世纪70、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由于人才、技术、资金不足,普遍做不大。在转制过程中,内外间、集体与个体间的矛盾加剧。集体观念强的村人,不愿意为个体承包人服务,更不愿意为外乡老板服务,成心怠工,导致企业效率十分低。政企不分,导致企业机制不灵活。于是,出现转制风,直接将村办集体企业出售给个人。1994年,农业部颁布文件《关于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要求将乡镇企业转制。到了1994年,藕池村也实行转制,村办企业出售给个人,乡村不再直接办厂,而改为服务企业,通过投资工业区,引进外来企业,收取租金,获得红利。藕池一直没有出现大型企业,只有一些小企业。村办工业区模式,只能出现小企业,不可能出现大企业。
第四节/诸多副业
一、织草帽
织凉帽是藕池女人的一个特色手工行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都在织凉帽。姜芬琴说:“草席是自产自销的,打草帽,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不好的。大多数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打。我们打草帽,基本上都聚在一起打的,我有三个姐姐,一起干活有个伴,老是到生产队长、大队长徐定良家里打,坐了满满的一房间,大家说说笑话、说说事情,也很有趣的,这是一种氛围。到了晚上,我们还要打,打好差不多要10点钟了。一般晚上聚在一起的比较少,因为晚上没有电灯的,只有煤油灯,太暗。到了冬天,打草帽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打草帽是要用水的,特别是西风一吹,草干了,打一会儿,就要用水浸一浸。草浸了水以后,就很冷,我们的手就要生冻疮。第二个是天冷,草比较容易断掉,要接上去。最好就是5月初这个时候打草帽,草很软的,冬天就比较痛苦。
“第二个痛苦就是晚上打,晚上打草帽老是要打瞌睡,因为很累的,我们这个地方跟其他村里打草帽方法又不一样,其他村里打草帽有三根芯、四根芯,我们打草帽就是两根芯,中间隔了两条,很细的,三根芯、四根芯,绳子很粗,五根芯、六根芯打出来,边很宽的,一条一条的,一顶草帽没几条就打完了。我们草帽打得很细的,一个顶要打10多圈,边沿要打20多圈,平的这里要打10多圈,这样打下来,最起码要30、40圈。晚上6点钟晚饭吃好,要打到10点钟。这样,可以卖到2毛钱。如果打3根芯、4根芯的话,只卖6分钱。这是比较精细的。还有更精细的,用最好的草去打,可以卖到3毛钱或者3毛8分钱,这个是大帽子,打得慢的人要五六个小时,做得快的人也要三四个小时。像我的亲家母,前几天跟我说,他们一天能打4顶。我们这个时候最多一天打3顶,上午一顶,下午一顶,晚上一顶,这样3顶。我们一般情况下就只有打2顶、3顶。我们一开始,打的时候,特别是冬天,又比较冷,冬天又没有衣服穿的,穿着破棉袄,就容易打瞌睡。这不是速度慢下来了吗?没有打好睡不了,一定要打好,才能去睡,有时候打到11点,才去睡。冬天老是要打瞌睡,夏天晚上就是蚊子多,也打不快,又很热,容易出汗。反正打帽子,是挺痛苦。当时我就想,我一生什么时候不用打草帽了就好了。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又改进了材料,席草不打了,打皮斯克,那个很软的,也不脏。以前打席子草帽是很脏的,草是地上种的,怎么洗过都没用,打过以后,手、衣服都很脏的。我家的三姐,帽子质量打得最好,人家自己戴的帽子,都叫她打,她帽子打得很好。草帽戴在头上,下雨天,水不会滴进来。还有扇子,她也打得非常好。
“后来是用打纸草。好像慈溪还要早,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纸草了,我们还是比较晚的。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开始是草帽,工厂里会收,多少分量的草可以打几顶,数字给你写好,否则你乱打也不行的。后来是打纸草,纸草是硬的。反正就是打各种各样的花色出来,这个就贵了,5块钱一顶,要打好几天。它有点艺术感,有点花纹的,不像以前初级的东西,比较秀气了。我姐姐现在还在打,其实打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十个手指一直在动,对预防老年痴呆症也是有好处的,他们八十几岁的老人也有在打的。
“打草帽也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这是有现金收入的。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女同志只在割稻的时候帮助男同志干一下,其他的时间都是男同志去干活,女同志不去的,全部都是打草帽的。以前是大家集中起来打,很开心的,我们有时候打凉帽,也唱戏,以前唱样板戏、唱京剧,尤其喜欢《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三个。我们村里有高音喇叭的,广播好了以后就放京剧了,这些京剧,每一段台词我们都能背下来,都会唱。以前的东西少,每天都是听这些,就听得滚瓜烂熟了。”
李小平说:“赵宏海跟老婆两个人都在做,他们做得非常快。”有一天,笔者到赵宏海家中采访,确实看见他与老婆两人一起打凉帽。赵宏海说,他不喜欢搓麻将之类的活动,有空就打打凉帽。李小平又说:“我也会做凉帽。那时候家里条件都很差,记得凉帽是两三角一顶。那时候放学回来要割猪草,给猪吃好。然后要给草帽收边,草帽的底就是头,一般是大人先做好,藕池男孩子实际上这种活都会做。因为家里苦,大人把草帽打好,边圈的话,都要我们去做,底(头)开始到中部这个活我们做不了,男的就是收边,做旁边那一点,收边大多数男的都会做。会做的人做得很快,像我姐姐,她一天能编一顶多,现在好像是40块一顶,一个礼拜可以收入300多块。那时候没有地方可以赚钱,也没有地方打工,就是靠打草帽。唯一赚钱的路子就是打草帽。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是妇女主任,村里老百姓草帽做好,然后由她每周挑到西门工艺品厂去卖。卖了以后,把钱分给他们,算账是叫阿伟姐算。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就是挑着走过去。工艺品厂在西门口。那时候家庭手工艺就是打草帽,属于家庭手工业,原材料进来,成品出去。”
姜芬琴说:“我们一些女同志,都是从五六岁、七八岁开始打草帽的,很会打的。一些男孩子也会打。我们的隔壁邻居,他们跟我们家相反,他们有五个男孩子,我们有四个女孩子,他们家男孩子都会打草帽,都打得很好的。大家用打草帽赚来的钱来补贴生活费,日子也是过得蛮好的。我们有四姐妹,都会打草帽,还有我妈妈也打,五个人打草帽。这个钱是一个星期收入一次,一顶草帽2毛钱。这个草是农民自己种的,是生产队负责分的,材料也是要钱的,成本5分钱,卖掉是2毛钱,还赚1毛5分钱。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也不是很贫穷,还可以,蛮好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很勤劳、很会干活的,去要饭或者没饭吃的现象,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
二、畜牧业与兽医
在生产队时期,除了种田,也重视畜牧业,譬如养猪、养鸭、养鸡之类。当时,大队有牲畜场。生产队也会养鸭、养鸡。李安法说:“布政公社提倡一户一猪,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养猪,猪卖掉,钱拿来,可以在生产队领200斤谷子。当初在布政全公社是484头牛。那时候生产队也有的,农村里每户人家都有猪的。人家养猪不一定只有一只,人家家里人多,吃饭口粮也需要得多,养得多的也有可能的。如果你不养,村里的饲料都被别人拿光了。一只肉猪卖掉,生产队里可以拿200斤的饲料粮,就是200斤的谷子。生产队里这个没有限制的,票子拿来就可以拿谷子的。”周利英说:“还要养鸡,他(叶金康)是10级劳力,人家就说了:你10级劳力,不养鸡,难道叫我们9级、8级弄啊?
他就养了。”既然养了鸭鸡,又得上市出售。包泉德说:“地主富农经常吃亏,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生产队的鸭可以卖了,生产队长派人来了,说你装两袋鸭,四五只一篓。我还觉得是好事。一共有4个人去,鸭装好挑去,加起来有60斤,那时候我还挑得动。挑到兴宁桥,人很多,他们叫我负责打秤,我这个本事也好的,算账很快。其他的人,在家里很厉害,到外面没花头了,人家给一块不知道找多少钱。鸭卖掉了,卖得很快,到家里去太早了,人家会气不过,觉得你们钱这么好赚呀。队长说:我们去逛逛吧,‘茶罗面’(阳春面)去吃一碗。他们三个嘻嘻哈哈还在吃时,我又动脑筋了,走这么远的路,空篓我不挑了。最后找一个上厕所的借口,篓子最后由他人挑回来了。”
因为畜牧业,也带来了相关的畜牧兽医。杨国富、张加洋、李安法、李小平等做过兽医。李小平说:“六年级毕业以后读中学,是在礼嘉桥。我中学没有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先做兽医,大概是1976年、1977年,做了三年。那时候村里哪里有培训,原来有个兽医,就是我堂阿哥李安法,他原来是藕池村的兽医。那时候农村要发展就养猪,每个村都有兽医。后来布政乡把他叫去了,村里就没有兽医了,就我来做了。阿哥跟我讲,一般量量体温,发热时青霉素打打,药配一点。兽医做了三四年。后来年纪大了,要找对象了,兽医说出去不太好听,我就不做了。”
三、泥水匠
孙定根说:“我小阿姐的老公是做泥水匠的,他教过我怎么做,怎么打灶头。后来我做泥水匠,给人家造房子。那时候是给人家做,拿点工分,然后吃点饭,可以拿几个馒头回家给小孩子吃。我在村里帮人家造房子也造了很多的,很多人都来叫我,我就一直在做泥水匠。藕池有很多人要造房子,都是我造的。生产队忙的时候就做生产队的活,生产队空的时候帮人家造房子。
“我的打灶技术很高。当时是烧稻草的,不是现在这样烧煤气的。打灶的话,我在板桥做的,板桥有一个(俞)元根也做泥水匠的。那时候在大队做的话,仅拿一些工分的,他也在做的。后来他找到别的活了,有泥水活也来叫我。宋严王村那边叫我去打灶头,我说你也给我带过去。后来板桥有一户人家打灶,打好了,用的时候熄火了。那户主人家问我,我们家这个小灶,稻草点着火以后,灶
洞都没有塞进去就灭了,这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我说我给你去看看。我一看,灶头倒是打得蛮好的。我说,你拆是不要拆掉了,我给你改一下。就给它稍微拆了,改了一下,给它打好、排好,他说你真是有本事。然后这个名气就越做越大了,大家都叫我打灶。以前方家人碰到了会说:老孙,走,给我打灶去。从此以后,其他泥水活没有做了,专门打灶了。
“这个是要有经验的,没有经验没有用,打灶也是这样的。过去有一个盆子,烧柴火的,塞进去,很快的。后面不一样了,这里很宽,柴火塞进去,锅边就可以烧起来了。就是这样的造型,就是上面一点点收起来,锅圈拿过来划好,用水泥刀斩好,一块一块都放好。它下面位置很大的,锅边这样烧上去,烧得很快的。以前一个灶头两个灶洞,两个灶洞的当中有一个汤锅的,以前汤锅非常好用的,你一烧火,汤锅要热的,这个汤锅不放好,你烧火的时候,汤锅冰凉的有什么用呢?所以汤锅放好,这两个位置看好,火一烧,汤锅就热得快了,这个都要经验的,以前汤锅很流行的。灶头打在这里就不大动了,如果灶洞的小缝大了一点,就要修灶了,其他的基本上不动的,用的年数多了,有可能会裂掉。
“后来村里有一个新学堂,还有两个小房间在,要打地灶,我就去打了。地灶是做年糕的灶,我们还要打砻糠灶,米轧出来,做年糕用。它那个铁板是一块一块的,走进去,砻糠掉下去,这个东西会错开的,砻糠当柴火烧的。地灶,别的砻糠用不来的,你扔进去火就灭了。我问过姐夫,他说打地灶的话,烟囱打好以后,用稻草点火看看,如果塞进去火很大,就可以用了,如果没有火,那就不能用的。点起来以后火会走,灶屋弄好,火塞进去以后会变很大的。
“我老婆生下儿子(孙民冲)以后,我做泥水匠,他也做泥水匠,他很听话。后来我给人家去砌墙,他也去,人家说这个小孩真的好乖,墙砌得整整齐齐的。方益民家的最开始是我带着我儿子去做的,方益民后来另外造房子时,是我儿子带班的。方益民后来对我儿子非常客气的,房子起几间,包括其他一些设计,都是我儿子弄好的。一开始,藕池的人都在夸,你儿子厉害。后来积了一些钱,他就不干活了。
“板桥的梁苗反,是我把他带起来的,我做泥水他都跟着去。以前工资比较低的,最多2块一日,他就1块多一点。规矩我给他立好,你给人家干活,吃的东西要当心。他是经常喝酒。我就跟他说,你到外面去,第一,酒不要多喝,第二,饭菜不要乱吃。比方大黄鱼、小黄鱼放着,不要吃,有些菜是不能动的,一般的菜,一些菜羹什么的,你可以吃的。什么时候可以放开吃呢,上梁那一天,他把亲戚叫过来办酒席,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你不吃的话,也要被人家吃光的。村里谁要造房子了,我也给他做点工,拿一点工资。我做到2002年左右,60多岁了,就不做了。”
四、轧米
轧米,普通话称碾米。这是农村大米加工行业。当时,藕池有两个轧米厂,一是藕池,一是板桥。杨裕祥称:“碾米厂老早就有了,我读书的时候碾米机就已经有了,厂大概是1958年开始的。最早碾米的人姜全财(姜小云)、张昌浩,我是第三个人。整个藕池有两个人轧米(碾米),从早上一直碾到夜。”又有徐正章,也是轧米员。
孙定根说:“轧米那会儿,我快40岁(1975)了。等于老的米厂在的,我在板桥干活,(徐)定良认识了。轧米这个行业本来是轮不到我的,原来是(励)康财在轧的,后来龚武良轧,再后来龚武良也不做了,轧米的人没有了。我也没出去做泥水匠了,我说,我来给你们轧米。他同意了,我就去轧米了。轧米轧到改革开放为止。我轧米的时候,已经不做泥水匠了。我轧米轧得非常好,我良心也好的,后来轧米不用付钱的,就是米糠不让人家拿走,人家养牛养鸡的,就到我这里来买,有了就卖给他。后来改革开放了,新的机器来了,老的机器没有用了。后来吴纪芳在了,那年去轧米,下半年去算账,算下来以后,七扣八扣,等于我没有钱拿了。当时吴纪芳拿新的机器来,我还用着老机器。他轧了以后可以拿很多钱,我没有钱拿。吴纪芳也很好,他说:这是不行的,同样是轧米,一个拿这么多,一个没有钱拿。吴纪芳就说,结200块给我。他一句话,我拿100块也好,心里舒服了。后来我也用新机器了,又快又省力。后来改革开放,我就不轧米了。”
附注
①据李安民的党员档案修订和回忆,他1970年开拖拉机,1973年到布政乡,1974年或1977年进锻件厂。所谓“我包了两个厂,一个是砖瓦厂,一是手套厂”,实际上是“参加乡基本路线工作组,到针织厂”。
相关地名
藕池村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