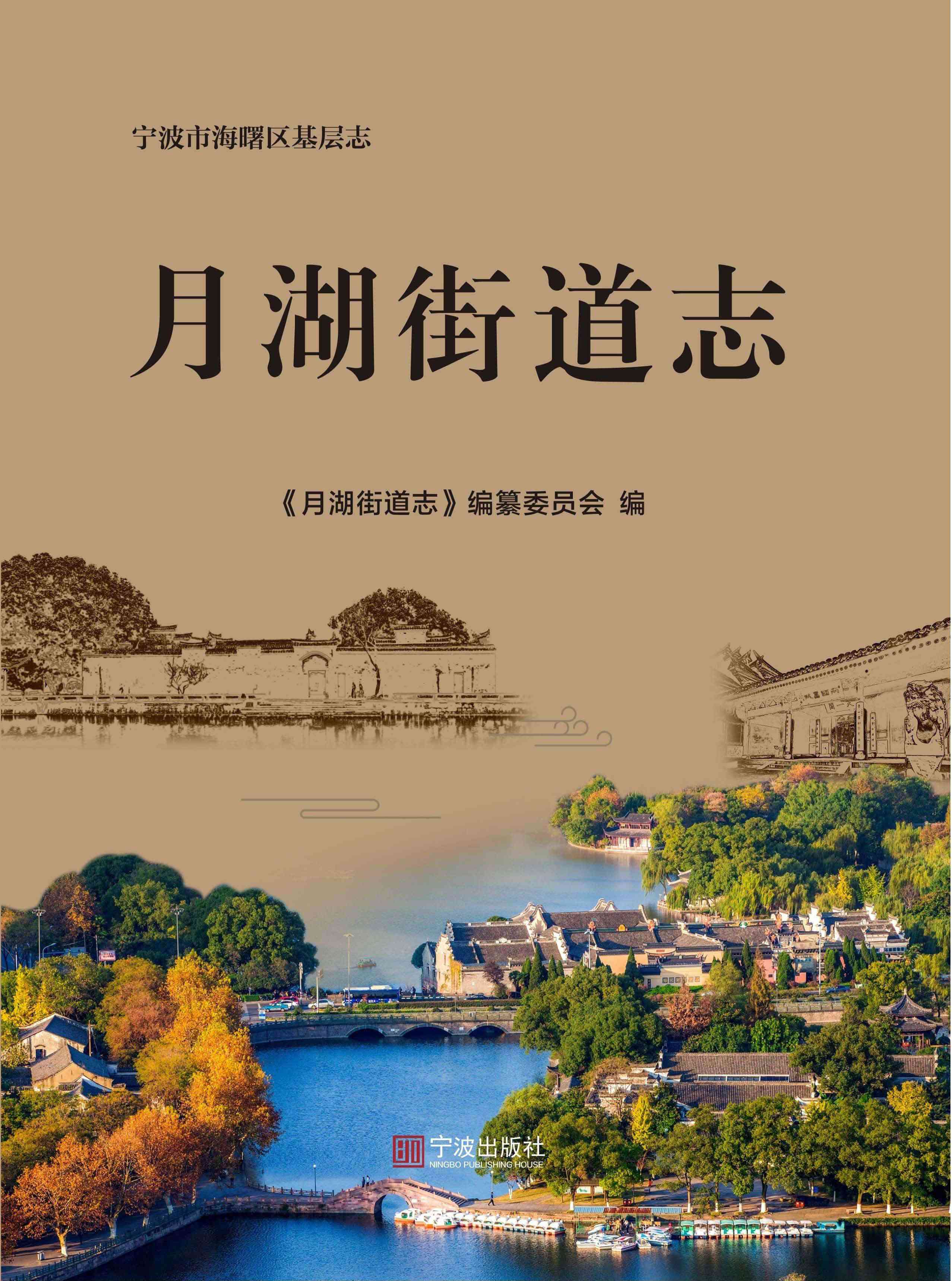内容
范钦建阁藏书后,其子孙严守祖训,书籍一直完整保存,并稍有增添。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局局长郑振铎在《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中称,“相传天一阁藏书原有七万余卷”(载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七期)。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修《四库全书》,要求各地进呈藏书。同年十一月,范钦八世孙范懋柱献书,天一阁藏书开始外流。此后,天一阁历尽劫难,至民国初遭窃,书籍仅存五分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劫难,日军进逼宁波,社会力量全面介入天一阁书籍保护,由省教育厅和省图书馆派员将书籍辗转押运至浙西龙泉保存,抗日战争胜利后运回天一阁。这次劫难,天一阁只失去两部方志。至20世纪50年代,陆续收回以前流散出去的藏书,甬上不少藏书家又向天一阁捐赠书籍,以至藏书数大增,至2015年藏书已达30万卷。
“其家奉司马公遗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有借钞者,主人延入,日资给之”(《颐采堂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40页)。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也提到“四方好事者时来借钞”(天一阁中厅刻板)。由此可见,天一阁书不出阁,但却是允许外人借阅、抄录的,开创了私家图书馆向外人开放的先河。明清士大夫直至近世学者莫不以登天一阁观书为幸事。范钦及他的继承者也刻印了一些天一阁藏书传布于世,以便人们阅读利用。由于年代久远,藏书霉变虫蛀日趋严重。1956年后,天一阁管理部门对大批藏书逐批进行了修补,使一些残破书籍得以继续保存,并对书籍进行数字化录入,使藏书内容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第一节 原有藏书
天一阁藏书自范钦开始。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将“范东明搜藏图书之来源”归结为4类:“一则为丰氏万卷楼之旧藏,二则为范大澈之故物,三则为东明所随时搜购,四则为多方借钞。”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民国二十四年11月《越风》)又增“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一类。这5类大致概括了天一阁初建时的藏书来源。
丰氏之书 丰氏藏书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中说:“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遗物也。”丰氏为甬上望族,是宁波南宋四姓之一,代有闻人。至丰坊聚书达5万卷,因名藏书楼为“万卷楼”。万卷楼藏书起自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4),这批书籍,从甬上流至绍兴,再到奉化,又到定海者,最后复归于甬上。丰坊晚年患“心疾”,凡宋崭写本,多被门生辈据为己有,幸存的仅十之四,又遭火灾,所剩无几。这最后剩下的一部分书与金石拓片都归到范钦之处。由此,天一阁藏书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
范大澈之书 范大澈为范钦的侄子。曾出使朝鲜,嗜好钞存异本,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9页)记载了范大澈抄书的规模:“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在长安邸中,所养书佣,多至二三十人,接几而食。既家居,筑室西皋,复与里中贤士大夫,品第所得者,垂二十年。”范大澈雇佣二三十人抄录书籍,数量巨大,有不少书籍是当时天一阁所未藏者。范大澈因没有从范钦处借到书,因此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金购置。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就叫范钦观看,范钦看后只好默认此书为天一阁所无。范大澈过世后,其藏书也逐渐流入天一阁。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见到阁中所藏之书,有不少有范大澈的印记(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346页)。
自购书 范钦曾在北京和七省为官,每到一地就购买书籍,当时明代已趋向衰乱,士大夫收藏的一些佳本有很多流出,范钦就在当地收集这些佳本。当时深负盛名的野竹斋沈辨之、茶梦庵姚舜咨的藏书,都被其收归己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范钦致仕隐居宁波,之后20余年继续收购书籍。范钦自己收购的书籍,在天一阁藏书中占据相当的分量。
传抄之书 明代抄书风气盛行。天一阁中所抄书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王世贞处抄来的。当时,范钦与王世贞相约,定期将家中藏书目录相互比较,各自从对方书目中找出自己所无之书抄录下来(事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和王世贞《答范司马简》)。王世贞的山园藏书号称达到3万卷,因此范钦在与王世贞的互相抄书中,得益良多。此外,天一阁也从海内故家借抄书籍。后人论明代抄本之精,天一阁名列其中。
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 明代,《登科录》与各省的《会试录》《乡试录》,往往赠送转索。范钦官迹所至,交游广泛,独具远识,于当代则蓄意征存,于前代复重值罗致,由此搜存了大量登科、乡会试、武举等录及进士履历。这方面书籍的收藏使当时的天一阁已经以“藏书最多”闻名。至今,天一阁中还藏有乡会试录1000余种。这些都是最可靠的传记资料。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二年(1933),赵万里两度登阁阅书,他在《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57页)中谈到,明代《登科录》在黄河流域各省旧家的祠堂里或有可能收藏,别处就很难见到同样的一册两册。当代,天一阁是收藏此类文献资料最多之处。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十分丰富,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在中国首屈一指。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阁藏明代地方志四百三十五种,其中见存者二百七十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这些地方志中以修于嘉靖者最多,计有130多种,占现存明代地方志总数270多种的半数以上;正德次之,计有23种;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崇祯者最少。天一阁的明代方志十之八九在国内找不到第二部,如弘治本《上海县志》、嘉靖本《武康县志》、正嘉间杨循吉所修的《吴邑志》都是存世极少的志书。嘉靖二十七年(1548)谢庭桂所修的《隆庆志》可称是孤本(以上据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这些珍本中除刻本之外,还有一些明抄本,如弘治《偃师县志》、正德《新乡县志》、嘉靖《钧州志》、嘉靖《涉县志》、嘉靖《长泰县志》、嘉靖《仁化县志》等都是在当时得不到刻本的情况下用蓝格棉纸抄录的,至今尤为珍贵。
范钦建阁后曾编《四明范氏书目》,此书中并未有藏书数字记载。范钦之子范大冲曾编《天一阁书目》(今藏天津图书馆),抄录书目有:“经类七种,体制音韵法书类四种,人物类十一种,目录类十种,氏族类二种,图志类四种,杂家类附小说各家八种,刑家类八种,兵家类四种,医家类二十二种,别集类三十五种,词典类二种,共计一百十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6页)范钦建阁初期,阁中藏书,各类文献未见确切数字。范钦之后,其子范大冲也曾新收书籍入阁。之后,曾孙范光文又增购阁中所无书籍(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47页),曾孙范光燮和玄孙范正辂也都曾为天一阁增添藏书。至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时,天一阁藏书实存4094部,53000余卷。
第二节 后续藏书
清光绪年间,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卷末附有“新藏书目”,编入当时新入藏的清末学者徐时栋、董沛、宗源瀚、薛福成、钱学嘉等人所撰成或所整理校刊之书46种,以区别于范氏原有藏书。此为后续藏书。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续增之书有124种,收录范围从清末延伸到此编目刊印时的古籍。
20世纪50年代,宁波藏书家张琴、张申之、刘楚芗、和世训、李蕴、徐馀藻都先后将所藏之书赠送给天一阁。1957年,宁波图书馆古籍部成立,这批古籍转至该馆收藏,天一阁也留下了数十种善本。1957年以后,地方藏书家或其家属遵藏书家遗愿捐赠给国家的入阁书籍达17万余卷。上海仪器厂副厂长张季言,镇海(今北仑区霞浦镇)人,以自己积蓄购书收藏。为纪念其启蒙老师张樵庄在清末办学的功绩,他将其上海愚园路寓所中藏书室以“樵斋”命名。后来拟在故乡霞浦建立“樵斋”图书馆。他去世后,其妻考虑霞浦较偏僻,于1957年7月将14162册、计57040卷图书连同书箱和张季言先生遗像全部捐赠给天一阁。1964年初,市政府实行私房改造,房管部门在西门郎官巷张氏祖宗堂阁楼上发现两大箱古书,其中有明嘉靖年间张时彻修纂的《宁波府志》原刻本。这些书籍是张孟契祖上所遗。“不久,张先生慷慨地把书籍捐赠给天一阁,共计一百三十八种,一百三十九部,一千三百九十三册,三千八百七十八卷,是入编赠书中数量最多的一家。”(据20世纪90年代任天一阁文保所所长的骆兆平《天一阁新藏书目序》,见《天一阁藏书史志》第117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家谱被当作“四旧”处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虞逸仲将这些家谱搜集起来,运回天一阁珍藏。虞逸仲等人还到宁波五中(今效实中学)、宁波女中、江北四中、宁波一中、灵桥废品收购仓库、濠河废品仓库、灵桥废品收购商店、江东东胜废品仓库、南门华伦造纸厂、姚江东风造纸厂、奉化棠岙棠云造纸厂、庄桥废品收购商店等处搜寻文物,并论斤以废纸价回收。在大堆废书废纸中发现天一阁原藏散出的明抄本《周易要义》零页,就把所有废纸搬回,一页一页寻找。居然将缺页全部找到,装订成册。朱赞卿(1885—1968),浙江萧山人,经济收入大半用于购买古籍与文物,晚年时嘱咐家人将自己的藏书和文物捐赠给天一阁。1979年9月,其家属将“别宥斋”藏书10余万卷和1700余件字画、文物赠送给天一阁。其藏书中有汲古阁影印宋抄本《集韵》、天一阁散佚明代方志《茶陵州志》《象山县志》稿等善本;书画有北宋黄庭坚墨迹《竹枝词》,明天一阁主人范钦手卷、徐文长《白燕诗轴》等珍品。同年10月,孙家溎家属赠送“蜗寄庐”14000余卷藏书给天一阁。孙家溎,字翔熊,号蜗庐主人,清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生,虽藏书数量不多,但版本精美,善本有元刻本《隋书》、明刻本《天一阁集》,全祖望批校明万历刻本《书经直解》等,共954部;字画有万斯同、郑梁、黄百家等名家的诗翰。1979年10月,杨容林家属将“清防阁”藏书古籍415部,字画25件捐赠给天一阁。杨容林,字容士,又名道宽,清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生。曾任宁波通利源油厂经理、太和酱园经理。他继承父亲杨臣勋“清防阁”藏书,又购入“二铭书屋”原藏碑帖,其中有善本书数十种,罕见的有明弘治十年(1497)刻本《诗林广记》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阮大铖《和箫集》等。
其他捐赠古籍、书画、文物的还有马廉、张申之、张炯伯、沈子槎、俞佐宸等人,古籍中不乏善本、孤本。至1987年底,阁藏古籍增至20余万卷,其中善本7万余卷。
天一阁还向社会各界、古旧书店、文物商店等处采购古籍,据1979年统计,共购得古籍图书9369部(占现有阁藏图书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毛抄《集韵》、明刻本《金连记》均为稀世之珍,此外还有《明代扇子画册》、半浦二老阁《郑氏家谱》一部24册。1962年6月,天一阁向市古籍书店购进书籍有《冯氏宗谱》《马港厅志》《邹县志》《黔西州志》《宋史新编》《故宫扇面集》等书籍及本纸(补书用纸)15公斤。
30年中,天一阁共访得原藏书185部,计710册3067卷(不分卷作一卷统计)。至此,早年散存在宁波当地的原天一阁藏书基本归阁。
至2007年,有古籍150216册,新方志13885册。
第三节 藏书保护
防火
范钦将藏书楼取名天一阁,取天一生水,以水制火之意,表达了免于火灾的愿望。藏书楼建成后,范钦着重书楼防火。首先,选择合理的位置,将藏书楼建在住所东面,远离厨房灶火。其次,建造防火设施,藏书楼建造之初,就在书楼附近凿一水池,蓄水备用。再则,制定了相应措施,严禁烟火入阁,这一禁令一直坚持了下来,藏书楼楼梯边一块“烟酒切忌登楼”禁牌直到现在依然挂着。清末,学者缪荃孙曾随宁波知府夏雨枝去天一阁,后来在《天一阁始末记》中写道:“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阁,约不携星火。”
防霉、防虫蛀
书籍要长期保存,防霉、防虫蛀也是必要之举。梅季书籍受潮,范氏有每年伏天晒书之举。虽然每年晒书,虫蛀、霉变仍然难免,这是书籍的又一个大害。范氏在书中夹芸草以防蛀,橱下放英石吸湿防霉。此事,清代寅著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给乾隆的奏章中就曾提及:“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英石产于广东英德县,是一种石灰岩石块。对英石和芸草的功效,众多研究天一阁的学者不同意其有吸湿和防蛀的功效。赵万里在《重整天一阁藏书纪略》中说:“我们发现好几个柜子里都有蠹虫,因此对于传统的保存图书的秘诀,发生疑问。故相传,阁里的书全部夹着芸草,可以防蛀;柜下镇着浮石,可以吸收水分。这完全是神话。”多次登天一阁编目的冯贞群也说:“案:嘉庆壬戌目中有霉蛀之本,则芸草避蠹、英石收湿之说实未足信,岂以时久而失其效耶?”阮元、麟庆对此持肯定态度。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唯此岿然独存。余两登此阁,阁不甚大,地颇卑湿,而书籍干燥无虫蛀,是可异也。”麟庆撰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天一观书》中说:“又有芸草一株,淡绿色,香尚馥郁,三百年来书不生蠹以此。”芸草,学名Cymbopogom distans,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书籍防虫物,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提及“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至于英石,地质工作者认为它并无吸潮作用。民国三十八年(1949),范氏天一阁阁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决定在书橱内散放樟脑丸4磅。
1975年,经广西第一图书馆推荐,天一阁开始试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出产的香草,效果良好。金秀香草,又名灵香草,亦即黄香草(Lysimachia foenum graecum),金秀县将香草寄至天一阁后,天一阁使用了24年,香草仍然香气扑鼻,而且对人体健康无害,对书籍纸张也没有副作用。
20世纪50年代开始,天一阁管理人员每年凡遇气候干燥的日子,都打开窗户和书橱门通风去湿,同时挨次检查,视书籍受潮和虫蛀情况分别处理。这项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并未中断。
防流散
为防书籍流散,范钦曾规定天一阁藏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其后除范懋柱曾向乾隆献书之外,范氏子孙一直恪守祖训。以后,社会逐渐介入天一阁管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详见本编第三章第二节)于8月15日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天一阁书籍运寄他处,以资安全”。17日,将全部明代地方志、登科录,以及其他善本45种移至鄞西茅草漕眺头范大冲墓庄(光禄庄)暂存。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5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再择阁中明以前版本及抄本,仿前式装箱移藏茅山司马庄”。13日早晨运抵鄞南茅山范钦墓庄(归云庄)。4月7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到会委员仅陈宝麟、冯贞群、叶谦谅(藏禹谟代)、范若鹏、范鹿其、范盈汶6人,浙江省教育厅和省立图书馆均派员列席。会议讨论“奉教育部令,天一阁藏书由范氏自行觅藏、仍虑未妥。战期内,应由教育厅代为迁移保管,战后负责交还”。是年4月,奉教育部令,将所藏宋元明抄本分装28箱,由办事员施永绚偕教育厅特派员周凯旋、浙江图书馆员史美诚共同押运至龙泉山中秘密保存。储藏方式、搬运费用均由省图书馆决定和承担。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天一阁藏书从龙泉运回阁中。
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2日,地方热心文化人士与范氏后裔200余人,在天一阁集会,共商管理办法,同时成立天一阁管理委员会。会址设在天一阁。天一阁管理委员会订有简章,以“筹集基金,缮葺阁屋,保存修补并流通古籍,及添购采访新旧图书、日报、杂志、考试名册、各大学同学录并其他有关文献文书”为宗旨,设委员27人,其中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总务、图书、劝募、会计甲级正副组长8人,共11人为常务委员会。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4月24日,历时2年,共召开全体会议2次,常务委员会议3次,存有会议记录3册。同月27日,范氏后人如柽、宝根、葆甫、康龄、鹿其、思慈召开会议,成立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公推范鹿其为主席。主席报告:“鹿其等鉴于先祖东明公藏书建阁以来,于兹已四百余年,历经被窃散佚,虫蚀鼠伤,其故厥在族人素主保守毫无组织所致,爰将发起保管委员会,以资永垂。”决议:“除昌、盛二房房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加推召南、芍㵐、若沂、巨棠为本会委员。”同时决定“以南塘河鱼荡租费收入作为常年经费,并向殷实子姓劝募之”。6月19日,又加推厚发、汶灏二人为委员。7月3日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晒书问题。决议:“(一)照例举行,(二)书橱内散放樟脑丸四磅,(三)规定七月二十四日起晒书,由本会全体委员担任之。”因藏书自浙西运回后,迄未整理,需在晒书期间进行核对,故历时10天。事后范鹿其说:“此次整书,检点下来,所缺方志约五部及零星残本。”8月21日召开第五次常会。讨论“本阁藏书楼门户及书橱锁钥过去与现在均由主委鹿其执管,应否仍由原人执管或数人分管,以明责任,而昭慎重”。决议“书橱锁钥,仍归鹿其掌管,总门锁钥由康龄、宝根二委员分执掌管,扶梯门及楼下边门锁钥由盈房执掌”。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存有会议记录1册,记事至8月21日止。
1962年,天一阁根据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对珍稀善本的保护方法,制作杏木匣子夹樟木板装箱,共350箱9000余斤,其中一类的地方志、登科录及珍贵书籍34箱1584斤。原拟随浙江图书馆藏书运至安吉、孝丰山区潜藏,后拟改随地、市档案馆运至四明山中藏放。因形势变化未外运。书籍修补
天一阁藏书年代久远,修复书籍成为天一阁书籍保管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在1958年后进行。据严春航《天一阁藏书修复记录》:自1958年9月17日至1961年6月10日共修补古籍59部192册。自1961年8月至1966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初编107种,其中凡破损者均加以修补。1964年6月15日—1965年5月6日,受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上海古籍书店代为修补天一阁藏书14部37册。1998年7月—2000年6月,上海图书馆代为修补古籍33部49册。天一阁工作人员也修补了大批古籍:1964—1971年,洪可尧修补古籍37部101册;1990—2000年,李大东修补古籍82部128册;1997年11月—2000年,王金玉修补古籍14部14册;1997年11月—2000年,施美君修补古籍22部22册;1997年11月—2000年,邱丹凤修补古籍18部18册;2000年10—12月,董捷修补古籍1部1册。
2010年新建古籍库房,配有温度湿度控制设备、空气净化设备、防盗报警装置、保安监控系统设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等现代化防火防虫防潮设备。
第四节 传抄与刻印
传抄
范钦在抄录别人家书籍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书供外人抄录,其中主要有王世贞。他与王世贞互相传抄自己所没有的对方藏书。除了与其他藏家互相抄录书籍外,天一阁藏书还供其他求抄者进阁抄录。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提到:“自易代以来,亦稍有阙失,然犹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者,时来借钞。”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载《颐采堂文集》)也记载:“或曰其家奉司马公遗训,代不分书,有钞借者,主人延入,日资给之,如邺侯父承休,聚书三万余卷,戒子孙,世间有求读者,别院供馔是也。”清康熙时自天一阁传抄的书籍数量更大。现在还保存在天一阁中的康熙间抄本《康熙中传抄天一阁书目》,记载了康熙十五年(1676)至二十五年(1686)之间,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期间外界传抄天一阁书籍的情况,所抄之书在66种以上。民国二十四年(1935),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订《天一阁藏书传钞简约》,规定捐款抄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一阁藏书抄录、复印更为规范,各界各学科都因此受益。
《天一阁藏书传钞简约》称:“初拟公开阅览,而阁中藏本衣脱钉亡,虫伤水渍,非大为修治,难以阅读。前年募集修阁余款,编印目录,保管开支,荡然无存。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学者欲求未见之书,但斥区区之金,可得秘笈,庶一举两得矣。”“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这一简约告之于世后,外界从天一阁传钞书籍数量没有确切统计。据1964年调查,温州市图书馆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向天一阁抄藏弘治《温州府志》22卷,抄本6册。云南文献会向天一阁抄得《正德云南志》40卷。上述抄本现在分别藏在温州市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
1949年后,至少全国各地有27个单位从天一阁抄录古籍(摘抄资料与拍摄照片不计在内),其中,1954—1983年,云南图书馆抄录乡试录10册,各种志书64卷,《商文毅公遗行集》1卷、《皇明恩命录》4卷。1957年,天津图书馆抄录《琼台志》44卷。1957—1958年,广东省中山图书抄录嘉靖《广州志》存37卷、嘉靖《德庆州志》等各种州志11种70余卷。1958年11月,甘肃图书馆抄录弘治《宁夏新志》8卷、嘉靖《宁夏新志》8卷。1959—1960年,安徽省科学院抄录明代安徽各种府志、州志、县志150余卷。1960年,瑞昌县地方党史、县志编辑办公室抄录隆庆《瑞昌县志》8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抄录“针灸四书”(《子午流注针经》《针经指南》《黄帝明堂灸经》和《灸膏肓腧穴法》的合称)。1963年,宁夏大学抄录弘治《宁夏新志》。1964年,湖南图书馆抄录嘉靖《澧州志》6卷(存5卷)、隆庆《宝庆府志》5卷;首都图书馆抄录隆庆《昌平州志》8卷(存6卷);江西丰城县志编委办公室抄录《丰乘》(存8卷);明进士题名录编印处抄录崇祯四年(1631)《进士登科录》1册、崇祯七年(1634)《进士登科录》1册。1966年,江西修水县图书馆抄录嘉靖《宁州志》18卷4册。1975年,广西第二图书馆抄录嘉靖《南宁府志》9卷3册。1975年广西第一图书馆抄录成化《平蛮录》及其他乡试录、《皇明实录》等书籍35册。1977年,浙江图书馆抄录嘉靖《浙江通志》29卷(补缺)、弘治《温州府志》22卷6册、嘉靖《定海县志》12卷4册。1979年,甘肃省图书馆抄录嘉靖《耀州志》1册、正德《凤翔府志》2册。1979年,河南禹县图书馆抄嘉靖《钧州志》2卷1册;山东图书馆抄录弘治《章丘县志》2册。1980年,山东图书馆抄录《德州志》2册、《宁海州志》2卷1册;江西武宁县档案馆抄录《武宁县志》6卷2册;广西第一图书馆抄录明刻《泰泉集选抄》12卷、《古今名山游记》选抄1卷、《名山胜概记》选抄1卷;湖北巴东档案馆抄录《巴东县志》3卷2册。1981年,河南太康县档案馆抄录《太康县志》,江西高安县县志编辑办公室抄录《瑞州府志》,河南息县档案馆抄录《息县志》(抄两部);湖北恩施博物馆抄录《巴东县志》。198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方志编辑委员会抄录嘉靖《耀州志》2卷1册。198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抄录《夜航船》10册。
各地学者从天一阁藏书中获益甚多。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弘治《赵州志》中,发现了有关石桥建筑的资料;著名古琴学专家查阜西带领一批中青年古琴工作者在天一阁发现了两部从未见过的明刻古琴谱《浙音释字琴谱》和《三教同声》。其间,天一阁有计划出版了一些善本、珍本,藏书内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现在,天一阁开展古籍数字化工程建设,引进相关软、硬件及配套设配,把已经整理好的古籍扫描,把古籍转换成电子书,设置古籍电子阅览室。2015年已有电子书籍约3万册。
刻印
明代中叶,坊刻及私人刻书蔚然成风。范钦也是一位积极的刻书者,他任随州知府时曾主持刻印《王彭衙诗》9卷(版佚,书藏南京图书馆),在袁州知府任上又刻《熊士选集》1卷(版佚,书藏北京图书馆)。范钦创建天一阁后,他的刻书事业形成规模。天一阁所刻的《稽古录》一书,署名的刻工就有52位。经范钦亲自校订并流传至今的有《范氏奇书》,计20种。至今阁中尚存明刻版片数百块。据骆兆平《天一阁刻书目录》:天一阁计刻书31种169卷。其中《法帖释文》一书,“天一阁现存各旧目均失载,而残板尚存,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148页)。1961—1966年,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选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线装本,“选刊”收入了107种地方志,1981年重印。1988年9月—1991年,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选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续),199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收入地方志109种。至此,除55种残缺藏本外,天一阁有关方志的藏书全部出版完毕。
天一阁还保存有不少印书的木版。计34卷,主要是天一阁刻印书籍的版片,其他还有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阮元《天一阁书目》、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等书籍的版片。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周易乾坤凿度》(2卷19片36面)、《天一阁碑目》(1卷,续增1卷,23版44面)、《三史统类臆断》(1卷8片16面)、《广成子解》(1卷3版6面)4种,仍保存完整,其余各种都有散佚。
专记
天一阁历劫
书籍的保护是个大难题,除了风侵、雨蚀、虫蛀霉变等自然原因而受损耗外,更多的损耗来自人为因素。自天一阁建阁起,经历数次劫难,以致在民国初期只剩下原藏书的1/5。民国十九年(1930),杨铁夫撰写的《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中称天一阁经历四厄:“太平一役,宁波当战冲,《河图》缀裤,《论语》代薪,是为一厄”;“民国建元亦受波及,捆载以去者,往往落诸江北教士之手,事后交涉,始许赎还,然已非完璧,是为二厄”;“然钻穴者,利其无人,苟得逾垣毁窗,遂可雍容进退,是为三厄”;“陈仓栈道,转移无形,况查验楼板中,明明有虚盖一穴,可容一人上下者乎?是为四厄”。这后两厄都可归之于偷盗,其实可合并为一。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重编序》中称天一阁遭遇五劫。这五劫中未列入辛亥革命期间天一阁所遭受的损失。抗日战争胜利后,天一阁藏书自浙西龙泉运回宁波,当时宁波的《时事公报》上《记天一阁》一文称,“其散亡最大者可分三期”:编《四库全书》遭受的损失、“太平军攻甬”时的损失和民国三年的遭窃。综合各种文献,天一阁藏书经历了下面几次重大劫难。
明末之乱,天一阁藏书颇有散失(郑振铎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七期),范钦手编的书目到这时已经失传,其他书籍散失十之一二。冯贞群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中称:“明清易代,稍有缺失,犹存十之八(经籍明历朝实录有之半于斯时流出)”。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流散。
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抚三宝从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手里提去不少藏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计算起来,共有638部。这一类书上,有一个明确的标识,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长方形朱记,朱记上的文字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书一部,计书几本。开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庵。这些应发还给天一阁的书中还有不少辗转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据骆兆平考校,进呈书总数为641种,计5762卷。至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代为天一阁藏书编目时,天一阁实有藏书4094部,53000余卷。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流散。
鸦片战争时期,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侵略军占据宁波,掠取《统一志》《舆地书》数十种而去。在此之前,范氏子侄抽出《图书集成》参考,阅毕未归,致使缺佚1500卷。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流散。
清咸丰十一年(1861)前后,当地窃贼利用太平军下宁波府之机,乘乱拆毁阁后墙垣,潜运天一阁藏书。这些书有些为江北岸外国传教士所得,有些论斤贱卖到奉化棠岙造纸者家中。
后被识家从造纸者家中转买。其中买得最多的一人,因遭受火灾,书籍尽毁。除书籍之外,阁中所藏的碑帖也多有流散。范钦后人范邦绥,与范氏族人多方购求,才使少量流散书籍回归阁中。有部分散落在宁波之外,收购的人不听赎取,当时的宁波知府边葆諴移文提赎,这些书才得以还藏阁中。这是天一阁书籍第四次遭受重大流散。
辛亥革命期间,因社会动荡,天一阁藏书也受到波及。一些歹徒进入天一阁,将藏书捆扎以后盗出阁外。这些书往往落于江北岸外国传教士之手。事后交涉,始许赎还,然而已有不少散失。此为杨铁夫所称的二厄,也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五次重大流散。
天一阁阁门封闭,在范氏的保管者认为这是十分严密的保护措施。但一些偷盗者恰恰能利用这个机会窃书。据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有某氏者时来甬上,与范氏后裔商购书不成。”民国二年(1913),此人就根据薛福成所编的书目选择自己所需书籍,向窃贼薛继位(冯贞群记作薛继渭)支付大笔钱财,唆使其到天一阁盗书。薛继位利用夜幕掩护,挖洞进入天一阁,登上屋顶,揭去瓦片,用绳子将自己吊入藏书楼。白天,窃贼在藏书楼上躺着睡觉;晚上,点起蜡烛按照唆使者的目录从书橱中拣书,然后装入皮箱运出阁外。这样一直持续了近10天(缪荃孙《天一阁失窃书目》则作“数十日“),范氏族人有不少在天一阁四周居住,但因为未曾到过阁中,而且隔着高墙,竟然毫不知情。陈训慈认为窃贼所盗书籍归于一人。但缪荃孙认为窃贼将书售给了上海各藏书家。至于窃贼偷书使天一阁藏书流失的数量。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中说:“丧失过半(赵万里曰:至少有1000种散出,宋元明集最多,明季杂史次之,《登科录》、地方志约去100余种)。越四年书又遭窃(为范氏追还,所失无几),此五劫也。”比较几种说法,失窃年代、窃贼姓名、盗窃手法略有不同,但都提到失窃书籍数量巨大。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六次重大流散。
至民国十九年(1930)秋,当时宁波市市长杨子毅,命杨铁夫等人前往天一阁调查,为编目做准备。合诸范氏自行清理所写书目,通计为书962种,共7991册,比薛目约得1/2。其中完璧者,尚有310种,比薛目约得1/4。杨铁夫《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中记述:“其中最完善者,为地志一类,百存九十五分以上。不知地理与他书异,他书宜古,地理宜今,明代志书,以之考古则有余,以之徵今则不足。”“《图书集成》尚存四千零七十四册,约得原书之半。《三才广志》,阮目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二百三十七册;至薛目时,存一百三十二册,今则止存四十二册。殆必有人以渐进之策,谋夺此书者。”民国二十四年(1935)冯贞群登阁编目,历时6个月,编成《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此目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问世,共10卷,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郑振铎《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中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贞群编了一部《天一阁劫余书目》,则所存不过一千五百九十一部,一万三千零三十八卷,较之薛目,又少了五百六十二部(较阮目少了二千五百零三部)。加上清代续加的《图书集成》等书二百二十七部,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卷;再加上范氏家著三十六部,一百十九卷,总共所藏总数为一千八百五十部,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二卷。”
第五节 藏书的整理出版和展览
天一阁有古籍藏书16万余册,内容丰富,为了让更多地人了解天一阁的藏书,天一阁近年来不断整理各类古籍,截至2015年底,已出版图书47种;开展各类藏书文化展览达97次。
“其家奉司马公遗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有借钞者,主人延入,日资给之”(《颐采堂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40页)。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也提到“四方好事者时来借钞”(天一阁中厅刻板)。由此可见,天一阁书不出阁,但却是允许外人借阅、抄录的,开创了私家图书馆向外人开放的先河。明清士大夫直至近世学者莫不以登天一阁观书为幸事。范钦及他的继承者也刻印了一些天一阁藏书传布于世,以便人们阅读利用。由于年代久远,藏书霉变虫蛀日趋严重。1956年后,天一阁管理部门对大批藏书逐批进行了修补,使一些残破书籍得以继续保存,并对书籍进行数字化录入,使藏书内容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第一节 原有藏书
天一阁藏书自范钦开始。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将“范东明搜藏图书之来源”归结为4类:“一则为丰氏万卷楼之旧藏,二则为范大澈之故物,三则为东明所随时搜购,四则为多方借钞。”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民国二十四年11月《越风》)又增“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一类。这5类大致概括了天一阁初建时的藏书来源。
丰氏之书 丰氏藏书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中说:“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遗物也。”丰氏为甬上望族,是宁波南宋四姓之一,代有闻人。至丰坊聚书达5万卷,因名藏书楼为“万卷楼”。万卷楼藏书起自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4),这批书籍,从甬上流至绍兴,再到奉化,又到定海者,最后复归于甬上。丰坊晚年患“心疾”,凡宋崭写本,多被门生辈据为己有,幸存的仅十之四,又遭火灾,所剩无几。这最后剩下的一部分书与金石拓片都归到范钦之处。由此,天一阁藏书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
范大澈之书 范大澈为范钦的侄子。曾出使朝鲜,嗜好钞存异本,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9页)记载了范大澈抄书的规模:“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在长安邸中,所养书佣,多至二三十人,接几而食。既家居,筑室西皋,复与里中贤士大夫,品第所得者,垂二十年。”范大澈雇佣二三十人抄录书籍,数量巨大,有不少书籍是当时天一阁所未藏者。范大澈因没有从范钦处借到书,因此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金购置。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就叫范钦观看,范钦看后只好默认此书为天一阁所无。范大澈过世后,其藏书也逐渐流入天一阁。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见到阁中所藏之书,有不少有范大澈的印记(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346页)。
自购书 范钦曾在北京和七省为官,每到一地就购买书籍,当时明代已趋向衰乱,士大夫收藏的一些佳本有很多流出,范钦就在当地收集这些佳本。当时深负盛名的野竹斋沈辨之、茶梦庵姚舜咨的藏书,都被其收归己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范钦致仕隐居宁波,之后20余年继续收购书籍。范钦自己收购的书籍,在天一阁藏书中占据相当的分量。
传抄之书 明代抄书风气盛行。天一阁中所抄书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王世贞处抄来的。当时,范钦与王世贞相约,定期将家中藏书目录相互比较,各自从对方书目中找出自己所无之书抄录下来(事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和王世贞《答范司马简》)。王世贞的山园藏书号称达到3万卷,因此范钦在与王世贞的互相抄书中,得益良多。此外,天一阁也从海内故家借抄书籍。后人论明代抄本之精,天一阁名列其中。
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 明代,《登科录》与各省的《会试录》《乡试录》,往往赠送转索。范钦官迹所至,交游广泛,独具远识,于当代则蓄意征存,于前代复重值罗致,由此搜存了大量登科、乡会试、武举等录及进士履历。这方面书籍的收藏使当时的天一阁已经以“藏书最多”闻名。至今,天一阁中还藏有乡会试录1000余种。这些都是最可靠的传记资料。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二年(1933),赵万里两度登阁阅书,他在《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57页)中谈到,明代《登科录》在黄河流域各省旧家的祠堂里或有可能收藏,别处就很难见到同样的一册两册。当代,天一阁是收藏此类文献资料最多之处。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十分丰富,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在中国首屈一指。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阁藏明代地方志四百三十五种,其中见存者二百七十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这些地方志中以修于嘉靖者最多,计有130多种,占现存明代地方志总数270多种的半数以上;正德次之,计有23种;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崇祯者最少。天一阁的明代方志十之八九在国内找不到第二部,如弘治本《上海县志》、嘉靖本《武康县志》、正嘉间杨循吉所修的《吴邑志》都是存世极少的志书。嘉靖二十七年(1548)谢庭桂所修的《隆庆志》可称是孤本(以上据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这些珍本中除刻本之外,还有一些明抄本,如弘治《偃师县志》、正德《新乡县志》、嘉靖《钧州志》、嘉靖《涉县志》、嘉靖《长泰县志》、嘉靖《仁化县志》等都是在当时得不到刻本的情况下用蓝格棉纸抄录的,至今尤为珍贵。
范钦建阁后曾编《四明范氏书目》,此书中并未有藏书数字记载。范钦之子范大冲曾编《天一阁书目》(今藏天津图书馆),抄录书目有:“经类七种,体制音韵法书类四种,人物类十一种,目录类十种,氏族类二种,图志类四种,杂家类附小说各家八种,刑家类八种,兵家类四种,医家类二十二种,别集类三十五种,词典类二种,共计一百十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6页)范钦建阁初期,阁中藏书,各类文献未见确切数字。范钦之后,其子范大冲也曾新收书籍入阁。之后,曾孙范光文又增购阁中所无书籍(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47页),曾孙范光燮和玄孙范正辂也都曾为天一阁增添藏书。至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时,天一阁藏书实存4094部,53000余卷。
第二节 后续藏书
清光绪年间,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卷末附有“新藏书目”,编入当时新入藏的清末学者徐时栋、董沛、宗源瀚、薛福成、钱学嘉等人所撰成或所整理校刊之书46种,以区别于范氏原有藏书。此为后续藏书。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续增之书有124种,收录范围从清末延伸到此编目刊印时的古籍。
20世纪50年代,宁波藏书家张琴、张申之、刘楚芗、和世训、李蕴、徐馀藻都先后将所藏之书赠送给天一阁。1957年,宁波图书馆古籍部成立,这批古籍转至该馆收藏,天一阁也留下了数十种善本。1957年以后,地方藏书家或其家属遵藏书家遗愿捐赠给国家的入阁书籍达17万余卷。上海仪器厂副厂长张季言,镇海(今北仑区霞浦镇)人,以自己积蓄购书收藏。为纪念其启蒙老师张樵庄在清末办学的功绩,他将其上海愚园路寓所中藏书室以“樵斋”命名。后来拟在故乡霞浦建立“樵斋”图书馆。他去世后,其妻考虑霞浦较偏僻,于1957年7月将14162册、计57040卷图书连同书箱和张季言先生遗像全部捐赠给天一阁。1964年初,市政府实行私房改造,房管部门在西门郎官巷张氏祖宗堂阁楼上发现两大箱古书,其中有明嘉靖年间张时彻修纂的《宁波府志》原刻本。这些书籍是张孟契祖上所遗。“不久,张先生慷慨地把书籍捐赠给天一阁,共计一百三十八种,一百三十九部,一千三百九十三册,三千八百七十八卷,是入编赠书中数量最多的一家。”(据20世纪90年代任天一阁文保所所长的骆兆平《天一阁新藏书目序》,见《天一阁藏书史志》第117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家谱被当作“四旧”处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虞逸仲将这些家谱搜集起来,运回天一阁珍藏。虞逸仲等人还到宁波五中(今效实中学)、宁波女中、江北四中、宁波一中、灵桥废品收购仓库、濠河废品仓库、灵桥废品收购商店、江东东胜废品仓库、南门华伦造纸厂、姚江东风造纸厂、奉化棠岙棠云造纸厂、庄桥废品收购商店等处搜寻文物,并论斤以废纸价回收。在大堆废书废纸中发现天一阁原藏散出的明抄本《周易要义》零页,就把所有废纸搬回,一页一页寻找。居然将缺页全部找到,装订成册。朱赞卿(1885—1968),浙江萧山人,经济收入大半用于购买古籍与文物,晚年时嘱咐家人将自己的藏书和文物捐赠给天一阁。1979年9月,其家属将“别宥斋”藏书10余万卷和1700余件字画、文物赠送给天一阁。其藏书中有汲古阁影印宋抄本《集韵》、天一阁散佚明代方志《茶陵州志》《象山县志》稿等善本;书画有北宋黄庭坚墨迹《竹枝词》,明天一阁主人范钦手卷、徐文长《白燕诗轴》等珍品。同年10月,孙家溎家属赠送“蜗寄庐”14000余卷藏书给天一阁。孙家溎,字翔熊,号蜗庐主人,清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生,虽藏书数量不多,但版本精美,善本有元刻本《隋书》、明刻本《天一阁集》,全祖望批校明万历刻本《书经直解》等,共954部;字画有万斯同、郑梁、黄百家等名家的诗翰。1979年10月,杨容林家属将“清防阁”藏书古籍415部,字画25件捐赠给天一阁。杨容林,字容士,又名道宽,清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生。曾任宁波通利源油厂经理、太和酱园经理。他继承父亲杨臣勋“清防阁”藏书,又购入“二铭书屋”原藏碑帖,其中有善本书数十种,罕见的有明弘治十年(1497)刻本《诗林广记》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阮大铖《和箫集》等。
其他捐赠古籍、书画、文物的还有马廉、张申之、张炯伯、沈子槎、俞佐宸等人,古籍中不乏善本、孤本。至1987年底,阁藏古籍增至20余万卷,其中善本7万余卷。
天一阁还向社会各界、古旧书店、文物商店等处采购古籍,据1979年统计,共购得古籍图书9369部(占现有阁藏图书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毛抄《集韵》、明刻本《金连记》均为稀世之珍,此外还有《明代扇子画册》、半浦二老阁《郑氏家谱》一部24册。1962年6月,天一阁向市古籍书店购进书籍有《冯氏宗谱》《马港厅志》《邹县志》《黔西州志》《宋史新编》《故宫扇面集》等书籍及本纸(补书用纸)15公斤。
30年中,天一阁共访得原藏书185部,计710册3067卷(不分卷作一卷统计)。至此,早年散存在宁波当地的原天一阁藏书基本归阁。
至2007年,有古籍150216册,新方志13885册。
第三节 藏书保护
防火
范钦将藏书楼取名天一阁,取天一生水,以水制火之意,表达了免于火灾的愿望。藏书楼建成后,范钦着重书楼防火。首先,选择合理的位置,将藏书楼建在住所东面,远离厨房灶火。其次,建造防火设施,藏书楼建造之初,就在书楼附近凿一水池,蓄水备用。再则,制定了相应措施,严禁烟火入阁,这一禁令一直坚持了下来,藏书楼楼梯边一块“烟酒切忌登楼”禁牌直到现在依然挂着。清末,学者缪荃孙曾随宁波知府夏雨枝去天一阁,后来在《天一阁始末记》中写道:“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阁,约不携星火。”
防霉、防虫蛀
书籍要长期保存,防霉、防虫蛀也是必要之举。梅季书籍受潮,范氏有每年伏天晒书之举。虽然每年晒书,虫蛀、霉变仍然难免,这是书籍的又一个大害。范氏在书中夹芸草以防蛀,橱下放英石吸湿防霉。此事,清代寅著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给乾隆的奏章中就曾提及:“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英石产于广东英德县,是一种石灰岩石块。对英石和芸草的功效,众多研究天一阁的学者不同意其有吸湿和防蛀的功效。赵万里在《重整天一阁藏书纪略》中说:“我们发现好几个柜子里都有蠹虫,因此对于传统的保存图书的秘诀,发生疑问。故相传,阁里的书全部夹着芸草,可以防蛀;柜下镇着浮石,可以吸收水分。这完全是神话。”多次登天一阁编目的冯贞群也说:“案:嘉庆壬戌目中有霉蛀之本,则芸草避蠹、英石收湿之说实未足信,岂以时久而失其效耶?”阮元、麟庆对此持肯定态度。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唯此岿然独存。余两登此阁,阁不甚大,地颇卑湿,而书籍干燥无虫蛀,是可异也。”麟庆撰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天一观书》中说:“又有芸草一株,淡绿色,香尚馥郁,三百年来书不生蠹以此。”芸草,学名Cymbopogom distans,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书籍防虫物,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提及“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至于英石,地质工作者认为它并无吸潮作用。民国三十八年(1949),范氏天一阁阁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决定在书橱内散放樟脑丸4磅。
1975年,经广西第一图书馆推荐,天一阁开始试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出产的香草,效果良好。金秀香草,又名灵香草,亦即黄香草(Lysimachia foenum graecum),金秀县将香草寄至天一阁后,天一阁使用了24年,香草仍然香气扑鼻,而且对人体健康无害,对书籍纸张也没有副作用。
20世纪50年代开始,天一阁管理人员每年凡遇气候干燥的日子,都打开窗户和书橱门通风去湿,同时挨次检查,视书籍受潮和虫蛀情况分别处理。这项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并未中断。
防流散
为防书籍流散,范钦曾规定天一阁藏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其后除范懋柱曾向乾隆献书之外,范氏子孙一直恪守祖训。以后,社会逐渐介入天一阁管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详见本编第三章第二节)于8月15日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天一阁书籍运寄他处,以资安全”。17日,将全部明代地方志、登科录,以及其他善本45种移至鄞西茅草漕眺头范大冲墓庄(光禄庄)暂存。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5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再择阁中明以前版本及抄本,仿前式装箱移藏茅山司马庄”。13日早晨运抵鄞南茅山范钦墓庄(归云庄)。4月7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到会委员仅陈宝麟、冯贞群、叶谦谅(藏禹谟代)、范若鹏、范鹿其、范盈汶6人,浙江省教育厅和省立图书馆均派员列席。会议讨论“奉教育部令,天一阁藏书由范氏自行觅藏、仍虑未妥。战期内,应由教育厅代为迁移保管,战后负责交还”。是年4月,奉教育部令,将所藏宋元明抄本分装28箱,由办事员施永绚偕教育厅特派员周凯旋、浙江图书馆员史美诚共同押运至龙泉山中秘密保存。储藏方式、搬运费用均由省图书馆决定和承担。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天一阁藏书从龙泉运回阁中。
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2日,地方热心文化人士与范氏后裔200余人,在天一阁集会,共商管理办法,同时成立天一阁管理委员会。会址设在天一阁。天一阁管理委员会订有简章,以“筹集基金,缮葺阁屋,保存修补并流通古籍,及添购采访新旧图书、日报、杂志、考试名册、各大学同学录并其他有关文献文书”为宗旨,设委员27人,其中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总务、图书、劝募、会计甲级正副组长8人,共11人为常务委员会。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4月24日,历时2年,共召开全体会议2次,常务委员会议3次,存有会议记录3册。同月27日,范氏后人如柽、宝根、葆甫、康龄、鹿其、思慈召开会议,成立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公推范鹿其为主席。主席报告:“鹿其等鉴于先祖东明公藏书建阁以来,于兹已四百余年,历经被窃散佚,虫蚀鼠伤,其故厥在族人素主保守毫无组织所致,爰将发起保管委员会,以资永垂。”决议:“除昌、盛二房房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加推召南、芍㵐、若沂、巨棠为本会委员。”同时决定“以南塘河鱼荡租费收入作为常年经费,并向殷实子姓劝募之”。6月19日,又加推厚发、汶灏二人为委员。7月3日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晒书问题。决议:“(一)照例举行,(二)书橱内散放樟脑丸四磅,(三)规定七月二十四日起晒书,由本会全体委员担任之。”因藏书自浙西运回后,迄未整理,需在晒书期间进行核对,故历时10天。事后范鹿其说:“此次整书,检点下来,所缺方志约五部及零星残本。”8月21日召开第五次常会。讨论“本阁藏书楼门户及书橱锁钥过去与现在均由主委鹿其执管,应否仍由原人执管或数人分管,以明责任,而昭慎重”。决议“书橱锁钥,仍归鹿其掌管,总门锁钥由康龄、宝根二委员分执掌管,扶梯门及楼下边门锁钥由盈房执掌”。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存有会议记录1册,记事至8月21日止。
1962年,天一阁根据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对珍稀善本的保护方法,制作杏木匣子夹樟木板装箱,共350箱9000余斤,其中一类的地方志、登科录及珍贵书籍34箱1584斤。原拟随浙江图书馆藏书运至安吉、孝丰山区潜藏,后拟改随地、市档案馆运至四明山中藏放。因形势变化未外运。书籍修补
天一阁藏书年代久远,修复书籍成为天一阁书籍保管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在1958年后进行。据严春航《天一阁藏书修复记录》:自1958年9月17日至1961年6月10日共修补古籍59部192册。自1961年8月至1966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初编107种,其中凡破损者均加以修补。1964年6月15日—1965年5月6日,受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上海古籍书店代为修补天一阁藏书14部37册。1998年7月—2000年6月,上海图书馆代为修补古籍33部49册。天一阁工作人员也修补了大批古籍:1964—1971年,洪可尧修补古籍37部101册;1990—2000年,李大东修补古籍82部128册;1997年11月—2000年,王金玉修补古籍14部14册;1997年11月—2000年,施美君修补古籍22部22册;1997年11月—2000年,邱丹凤修补古籍18部18册;2000年10—12月,董捷修补古籍1部1册。
2010年新建古籍库房,配有温度湿度控制设备、空气净化设备、防盗报警装置、保安监控系统设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等现代化防火防虫防潮设备。
第四节 传抄与刻印
传抄
范钦在抄录别人家书籍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书供外人抄录,其中主要有王世贞。他与王世贞互相传抄自己所没有的对方藏书。除了与其他藏家互相抄录书籍外,天一阁藏书还供其他求抄者进阁抄录。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提到:“自易代以来,亦稍有阙失,然犹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者,时来借钞。”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载《颐采堂文集》)也记载:“或曰其家奉司马公遗训,代不分书,有钞借者,主人延入,日资给之,如邺侯父承休,聚书三万余卷,戒子孙,世间有求读者,别院供馔是也。”清康熙时自天一阁传抄的书籍数量更大。现在还保存在天一阁中的康熙间抄本《康熙中传抄天一阁书目》,记载了康熙十五年(1676)至二十五年(1686)之间,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期间外界传抄天一阁书籍的情况,所抄之书在66种以上。民国二十四年(1935),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订《天一阁藏书传钞简约》,规定捐款抄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一阁藏书抄录、复印更为规范,各界各学科都因此受益。
《天一阁藏书传钞简约》称:“初拟公开阅览,而阁中藏本衣脱钉亡,虫伤水渍,非大为修治,难以阅读。前年募集修阁余款,编印目录,保管开支,荡然无存。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学者欲求未见之书,但斥区区之金,可得秘笈,庶一举两得矣。”“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这一简约告之于世后,外界从天一阁传钞书籍数量没有确切统计。据1964年调查,温州市图书馆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向天一阁抄藏弘治《温州府志》22卷,抄本6册。云南文献会向天一阁抄得《正德云南志》40卷。上述抄本现在分别藏在温州市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
1949年后,至少全国各地有27个单位从天一阁抄录古籍(摘抄资料与拍摄照片不计在内),其中,1954—1983年,云南图书馆抄录乡试录10册,各种志书64卷,《商文毅公遗行集》1卷、《皇明恩命录》4卷。1957年,天津图书馆抄录《琼台志》44卷。1957—1958年,广东省中山图书抄录嘉靖《广州志》存37卷、嘉靖《德庆州志》等各种州志11种70余卷。1958年11月,甘肃图书馆抄录弘治《宁夏新志》8卷、嘉靖《宁夏新志》8卷。1959—1960年,安徽省科学院抄录明代安徽各种府志、州志、县志150余卷。1960年,瑞昌县地方党史、县志编辑办公室抄录隆庆《瑞昌县志》8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抄录“针灸四书”(《子午流注针经》《针经指南》《黄帝明堂灸经》和《灸膏肓腧穴法》的合称)。1963年,宁夏大学抄录弘治《宁夏新志》。1964年,湖南图书馆抄录嘉靖《澧州志》6卷(存5卷)、隆庆《宝庆府志》5卷;首都图书馆抄录隆庆《昌平州志》8卷(存6卷);江西丰城县志编委办公室抄录《丰乘》(存8卷);明进士题名录编印处抄录崇祯四年(1631)《进士登科录》1册、崇祯七年(1634)《进士登科录》1册。1966年,江西修水县图书馆抄录嘉靖《宁州志》18卷4册。1975年,广西第二图书馆抄录嘉靖《南宁府志》9卷3册。1975年广西第一图书馆抄录成化《平蛮录》及其他乡试录、《皇明实录》等书籍35册。1977年,浙江图书馆抄录嘉靖《浙江通志》29卷(补缺)、弘治《温州府志》22卷6册、嘉靖《定海县志》12卷4册。1979年,甘肃省图书馆抄录嘉靖《耀州志》1册、正德《凤翔府志》2册。1979年,河南禹县图书馆抄嘉靖《钧州志》2卷1册;山东图书馆抄录弘治《章丘县志》2册。1980年,山东图书馆抄录《德州志》2册、《宁海州志》2卷1册;江西武宁县档案馆抄录《武宁县志》6卷2册;广西第一图书馆抄录明刻《泰泉集选抄》12卷、《古今名山游记》选抄1卷、《名山胜概记》选抄1卷;湖北巴东档案馆抄录《巴东县志》3卷2册。1981年,河南太康县档案馆抄录《太康县志》,江西高安县县志编辑办公室抄录《瑞州府志》,河南息县档案馆抄录《息县志》(抄两部);湖北恩施博物馆抄录《巴东县志》。198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方志编辑委员会抄录嘉靖《耀州志》2卷1册。198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抄录《夜航船》10册。
各地学者从天一阁藏书中获益甚多。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弘治《赵州志》中,发现了有关石桥建筑的资料;著名古琴学专家查阜西带领一批中青年古琴工作者在天一阁发现了两部从未见过的明刻古琴谱《浙音释字琴谱》和《三教同声》。其间,天一阁有计划出版了一些善本、珍本,藏书内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现在,天一阁开展古籍数字化工程建设,引进相关软、硬件及配套设配,把已经整理好的古籍扫描,把古籍转换成电子书,设置古籍电子阅览室。2015年已有电子书籍约3万册。
刻印
明代中叶,坊刻及私人刻书蔚然成风。范钦也是一位积极的刻书者,他任随州知府时曾主持刻印《王彭衙诗》9卷(版佚,书藏南京图书馆),在袁州知府任上又刻《熊士选集》1卷(版佚,书藏北京图书馆)。范钦创建天一阁后,他的刻书事业形成规模。天一阁所刻的《稽古录》一书,署名的刻工就有52位。经范钦亲自校订并流传至今的有《范氏奇书》,计20种。至今阁中尚存明刻版片数百块。据骆兆平《天一阁刻书目录》:天一阁计刻书31种169卷。其中《法帖释文》一书,“天一阁现存各旧目均失载,而残板尚存,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148页)。1961—1966年,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选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线装本,“选刊”收入了107种地方志,1981年重印。1988年9月—1991年,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选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续),199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收入地方志109种。至此,除55种残缺藏本外,天一阁有关方志的藏书全部出版完毕。
天一阁还保存有不少印书的木版。计34卷,主要是天一阁刻印书籍的版片,其他还有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阮元《天一阁书目》、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等书籍的版片。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周易乾坤凿度》(2卷19片36面)、《天一阁碑目》(1卷,续增1卷,23版44面)、《三史统类臆断》(1卷8片16面)、《广成子解》(1卷3版6面)4种,仍保存完整,其余各种都有散佚。
专记
天一阁历劫
书籍的保护是个大难题,除了风侵、雨蚀、虫蛀霉变等自然原因而受损耗外,更多的损耗来自人为因素。自天一阁建阁起,经历数次劫难,以致在民国初期只剩下原藏书的1/5。民国十九年(1930),杨铁夫撰写的《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中称天一阁经历四厄:“太平一役,宁波当战冲,《河图》缀裤,《论语》代薪,是为一厄”;“民国建元亦受波及,捆载以去者,往往落诸江北教士之手,事后交涉,始许赎还,然已非完璧,是为二厄”;“然钻穴者,利其无人,苟得逾垣毁窗,遂可雍容进退,是为三厄”;“陈仓栈道,转移无形,况查验楼板中,明明有虚盖一穴,可容一人上下者乎?是为四厄”。这后两厄都可归之于偷盗,其实可合并为一。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重编序》中称天一阁遭遇五劫。这五劫中未列入辛亥革命期间天一阁所遭受的损失。抗日战争胜利后,天一阁藏书自浙西龙泉运回宁波,当时宁波的《时事公报》上《记天一阁》一文称,“其散亡最大者可分三期”:编《四库全书》遭受的损失、“太平军攻甬”时的损失和民国三年的遭窃。综合各种文献,天一阁藏书经历了下面几次重大劫难。
明末之乱,天一阁藏书颇有散失(郑振铎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七期),范钦手编的书目到这时已经失传,其他书籍散失十之一二。冯贞群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中称:“明清易代,稍有缺失,犹存十之八(经籍明历朝实录有之半于斯时流出)”。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流散。
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抚三宝从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手里提去不少藏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计算起来,共有638部。这一类书上,有一个明确的标识,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长方形朱记,朱记上的文字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书一部,计书几本。开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庵。这些应发还给天一阁的书中还有不少辗转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据骆兆平考校,进呈书总数为641种,计5762卷。至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代为天一阁藏书编目时,天一阁实有藏书4094部,53000余卷。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流散。
鸦片战争时期,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侵略军占据宁波,掠取《统一志》《舆地书》数十种而去。在此之前,范氏子侄抽出《图书集成》参考,阅毕未归,致使缺佚1500卷。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流散。
清咸丰十一年(1861)前后,当地窃贼利用太平军下宁波府之机,乘乱拆毁阁后墙垣,潜运天一阁藏书。这些书有些为江北岸外国传教士所得,有些论斤贱卖到奉化棠岙造纸者家中。
后被识家从造纸者家中转买。其中买得最多的一人,因遭受火灾,书籍尽毁。除书籍之外,阁中所藏的碑帖也多有流散。范钦后人范邦绥,与范氏族人多方购求,才使少量流散书籍回归阁中。有部分散落在宁波之外,收购的人不听赎取,当时的宁波知府边葆諴移文提赎,这些书才得以还藏阁中。这是天一阁书籍第四次遭受重大流散。
辛亥革命期间,因社会动荡,天一阁藏书也受到波及。一些歹徒进入天一阁,将藏书捆扎以后盗出阁外。这些书往往落于江北岸外国传教士之手。事后交涉,始许赎还,然而已有不少散失。此为杨铁夫所称的二厄,也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五次重大流散。
天一阁阁门封闭,在范氏的保管者认为这是十分严密的保护措施。但一些偷盗者恰恰能利用这个机会窃书。据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有某氏者时来甬上,与范氏后裔商购书不成。”民国二年(1913),此人就根据薛福成所编的书目选择自己所需书籍,向窃贼薛继位(冯贞群记作薛继渭)支付大笔钱财,唆使其到天一阁盗书。薛继位利用夜幕掩护,挖洞进入天一阁,登上屋顶,揭去瓦片,用绳子将自己吊入藏书楼。白天,窃贼在藏书楼上躺着睡觉;晚上,点起蜡烛按照唆使者的目录从书橱中拣书,然后装入皮箱运出阁外。这样一直持续了近10天(缪荃孙《天一阁失窃书目》则作“数十日“),范氏族人有不少在天一阁四周居住,但因为未曾到过阁中,而且隔着高墙,竟然毫不知情。陈训慈认为窃贼所盗书籍归于一人。但缪荃孙认为窃贼将书售给了上海各藏书家。至于窃贼偷书使天一阁藏书流失的数量。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中说:“丧失过半(赵万里曰:至少有1000种散出,宋元明集最多,明季杂史次之,《登科录》、地方志约去100余种)。越四年书又遭窃(为范氏追还,所失无几),此五劫也。”比较几种说法,失窃年代、窃贼姓名、盗窃手法略有不同,但都提到失窃书籍数量巨大。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六次重大流散。
至民国十九年(1930)秋,当时宁波市市长杨子毅,命杨铁夫等人前往天一阁调查,为编目做准备。合诸范氏自行清理所写书目,通计为书962种,共7991册,比薛目约得1/2。其中完璧者,尚有310种,比薛目约得1/4。杨铁夫《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中记述:“其中最完善者,为地志一类,百存九十五分以上。不知地理与他书异,他书宜古,地理宜今,明代志书,以之考古则有余,以之徵今则不足。”“《图书集成》尚存四千零七十四册,约得原书之半。《三才广志》,阮目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二百三十七册;至薛目时,存一百三十二册,今则止存四十二册。殆必有人以渐进之策,谋夺此书者。”民国二十四年(1935)冯贞群登阁编目,历时6个月,编成《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此目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问世,共10卷,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郑振铎《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中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贞群编了一部《天一阁劫余书目》,则所存不过一千五百九十一部,一万三千零三十八卷,较之薛目,又少了五百六十二部(较阮目少了二千五百零三部)。加上清代续加的《图书集成》等书二百二十七部,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卷;再加上范氏家著三十六部,一百十九卷,总共所藏总数为一千八百五十部,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二卷。”
第五节 藏书的整理出版和展览
天一阁有古籍藏书16万余册,内容丰富,为了让更多地人了解天一阁的藏书,天一阁近年来不断整理各类古籍,截至2015年底,已出版图书47种;开展各类藏书文化展览达97次。
相关地名
月湖街道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