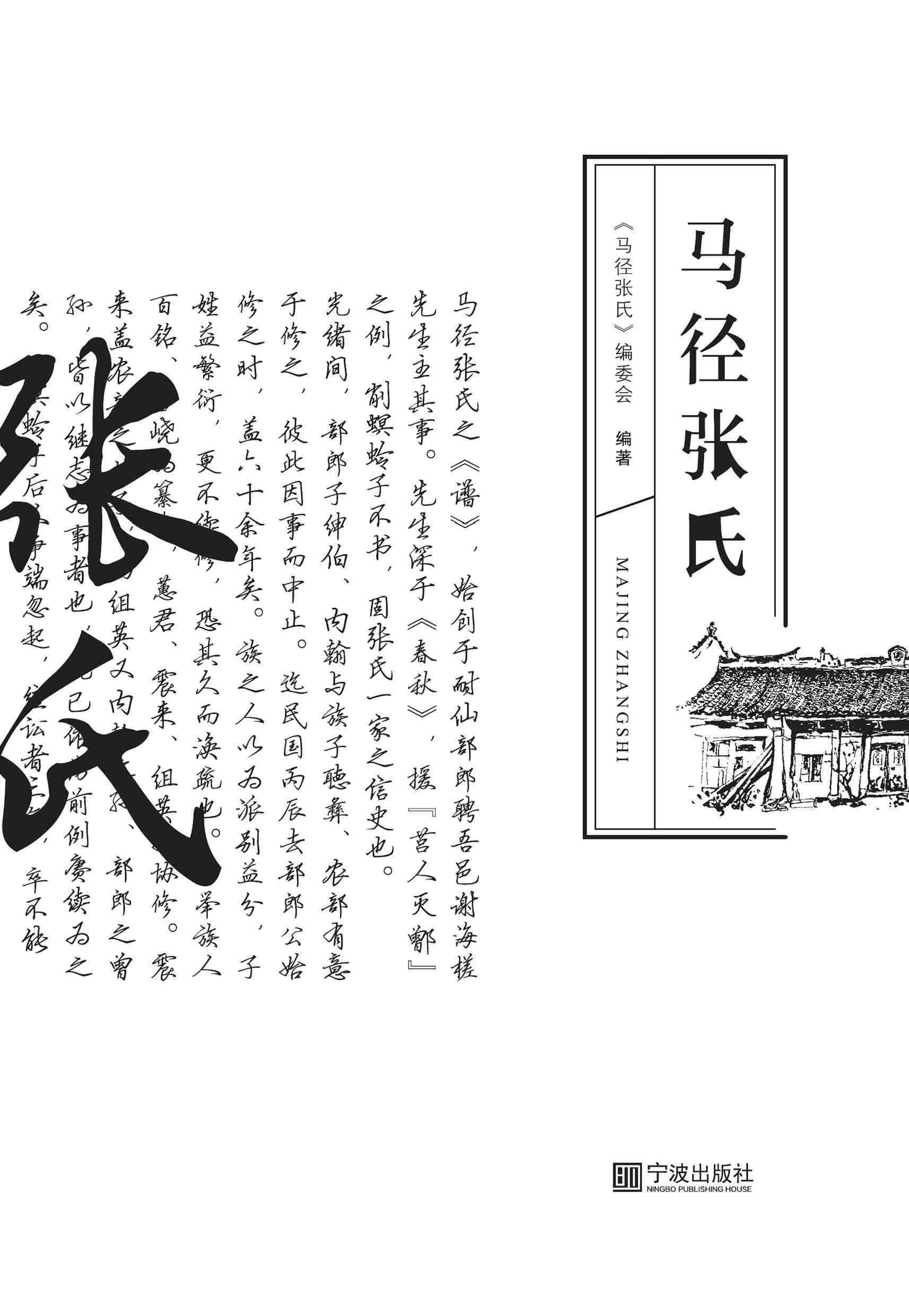内容
“如果说谁对我的金石篆刻、印泥制作影响最大,非张鲁庵莫属。我与他虽不是师生关系,却也没有一个老师会像他这样尽心尽力地帮我助我。”提起张鲁庵,著名书法家、金石篆刻家、印泥制作大师高式熊这样说。
谈及与张鲁庵的相识相知,高式熊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运气好,这位良师益友对他而言,宛如人生路上的明灯。
从赵叔孺到高式熊
20世纪30年代,刚过而立之年的张鲁庵来到上海,并长期寓居于此。当时的张鲁庵,已经开始广为收藏研究印章印谱,被时人称为“印痴”,来上海除了拓展产业,更是为了拜师、求学、广交朋友。
而在这里,他遇到了被称为“近世之赵孟頫”的赵叔孺。赵叔孺精通金石印刻,擅长花卉虫草、鞍马翎毛,其中尤精画马。机遇难得,张鲁庵立刻表达了拜入赵叔孺门下的意愿,令他惊喜的是,赵叔孺马上答应了。
他不知道的是,赵叔孺当时虽已是书画界泰斗,却乐善好施,有教无类,门下弟子众多。赵叔孺的弟子之一陈巨来曾说:“一班附庸风雅的仕女,纷然而至,拜列门墙,执弟子之礼,可谓群英杂凑,少长都全,有银行经理、钱庄阿大、朝鲜女学生、青楼女画家、纨绔子弟、没落者、留学者,及其没后,闻共得七十二贤之多云。”而这纨绔子弟,指的就是张鲁庵。
宽松的学习环境,让张鲁庵可以在经商的同时,研究金石篆刻和印泥技艺。或许这个“印痴”也当真与篆刻有缘,虽被称为纨绔子弟,他在赵叔孺的众多弟子中,却也十分出挑,与篆刻名家陈巨来、方介堪、沙孟海、叶露园等人同为当时上海艺林的翘楚,出版了《仿完白山人印谱》(1932年拓本)两卷等著作。
1942年和1944年,赵叔孺率门人两次举办“赵氏同门金石书画展览会”,轰动上海艺界。张鲁庵的金石篆刻、收藏的印章印谱和制作的精美印泥,在两次展览会上都大放异彩。
而在1941年,少年高式熊也通过赵叔孺的介绍,结识了张鲁庵。
当时,赵叔孺把张鲁庵编的《黄牧甫印谱》推荐给了初入篆刻之门的高式熊。但印谱5元的高价令高式熊难以承受,赵叔孺忙说:“你不必买,做这部印谱的人会送来的。”
过了些时日,张鲁庵寻上门来,自报家门:“我叫张咀英(张鲁庵号咀英),赵叔孺先生叫我来的,这印谱送给你。”当时的张鲁庵虚岁已经42岁,比高式熊大21岁。这一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自此成为忘年交。“几时我请你吃顿饭,你到我家里来看看。”初次见面,张鲁庵就邀请高式熊去他位于江阴路九福里的家里做客。
不久之后,高式熊正式登门拜访张鲁庵。一进门,他就吓了一跳:书房的四面书橱中全是印谱。而在张鲁庵家中,这样的书房共有三间。张鲁庵曾在《从师回忆录》中有过统计:“积年既久,所获渐多,共得古今印章四千余钮,历代印谱四百余种。”
不等高式熊回过神来,张鲁庵就大方地说:“今天是让你来看看我家环境的。你学篆刻,必须多看印谱,最好看原拓印谱。我看你家里不富裕,也买不起印谱,你不用买了,我的这些印谱印章就是你的。今后你要看什么,由我来安排。”
如今,高式熊已经年逾九旬,但他依旧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他的这种无私提携后人的举动,使我终生难忘。”
从此以后,高式熊成了张家的常客。他所用的图章石头、刻刀、印泥、印谱纸等,皆由张鲁庵提供。张鲁庵还在自己的书房里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写字台,并把房门钥匙给了高式熊,允许他自由进出。
“那是我刻章最得益的机会!”高式熊坦言。多年以后,他整理汇辑了《鲁庵所藏印谱简目》一册四卷及附卷,引起了书画界的轰动。内容囊括四百多部印谱的原拓本、印本及所有的名印谱。其中甚至还有陈介祺赠给吴大澂的那部一百册的《十钟山房印举》——这是张鲁庵花了八百两银子从吴大澂之孙吴湖帆手中购得的。
从药号小开到以商养文
不论是陈巨来,还是高式熊,谈及张鲁庵,总避不开“家境殷实”这四个字。因为父亲早逝,尚在襁褓中的张鲁庵被确立为杭州名药号“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在他9岁,仍在老家宁波马径村上学读书之时,就在名义上接手了“张同泰”药号的经营。
其实当时,张母杨氏才是药号实际的经营者。《张氏宗谱》收有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的《张母杨太君五十寿序》。序文说道:“张氏以商起家,尤善储药。自秦蜀岭外,珍异之草,谲怪之物,无所不至。北采辽东人参,输之其乡,以是雄于财。太君早岁持门户,能制奇赢,忠信重诺,使人乐为用。选材益良,懋迁过于旧数倍。”大意是说:“张同泰”在全国各地搜罗名贵药材,无所不至,无所不有,财力雄厚。杨氏年轻时就主持门户,深通经商之道,又讲究诚信,赢得手下效忠,使得生意比从前好出几倍。
而至张鲁庵成年,正式接手药号生意的时候,“张同泰”已经财源广进,成为与当时杭州城著名的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齐名的六大国药铺之一。
成家立业,张鲁庵亦在那一年结了婚。也就是从那时起,张同泰药号开始了以商养文的嬗变。
20世纪初,上海逐步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国际上,也称得上是大都市。上海的租界云集了全国知名的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文化名人交往频繁,文化盛事此起彼伏。
经商几年的张鲁庵开始逐步接触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圈子,心思活络的他十分向往上海的繁荣和发达。尤其是他在杭州的好友收藏家高野侯、高络园兄弟等陆续迁往上海发展后,向上海拓展产业,在这片文化海洋中拜师、求学、广交朋友的念头就在张鲁庵心中发芽了。
于是,张鲁庵多次到上海进行考察,最后选定了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房地产大王”哈同的产业慈淑大厦内开设“张同泰国药号益元参店分号”,专营名贵滋补药材。道地的用料,使“张同泰”在上海一炮打响。在经营上取得突破的时候,张鲁庵聘请了一位经理,自己索性当起了甩手掌柜。
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成绩,但这并不是张鲁庵迁居上海的最终目的。在拜赵叔孺为师后,他在每日修习金石篆刻外,仍延续着年少时收集印谱印章的爱好。到上海之后,藏品的广度和数量突飞猛进,再加上张鲁庵家赀丰厚,各种与金石篆刻有关的藏品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如一方邓石如所刻的五面印,张鲁庵考证后确认为真品,于是与前江苏抚台刘坤一的后裔多次商谈,花了500银圆买下。古玩商人们看到张鲁庵出手如此阔绰,都把他当成“纨绔子弟”“药号小开”,纷纷上门求售。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鲁庵每次都严格审定,只有确定了并非赝品,他才会出价收藏。而如果其中有珍品精品,或者孤本善本,他会主动加价购买。在这种以商养文的资金支持下,张鲁庵收藏的印谱就有400多部,收藏的历代印章更达到4000余方。其中何雪渔印章20方,并拓之成集,而当中的“放情诗酒”一方印,是杭城著名收藏大家魏家孙旧藏,当时的上海艺界得知后,纷纷把它捧为极品拱璧。
在庞大收藏品的支持下,张鲁庵的篆刻水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也成为公认的全国收集历代篆刻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收藏者,在当时,就已经有人称他为印谱收藏“海内第一家”。同时,《鲁庵印选》《鲁庵印谱》等10余本印谱图书接连出版,除了最珍贵的《十钟山房印举》百册拓本,明代万历年间的《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隆庆年间的《顾氏集古印谱》等印谱亦重回公众视野,大大丰富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篆刻文化。
鲁庵印泥国之瑰宝
作为一个“印人”,在治印过程中有三样重要的工具:一为印石,用田黄、鸡血、寿山石等名贵石材刻之,其印章可为子孙后世永久宝之,否则为无本之木;二为刻刀,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即印泥,别看都是红色,好的印泥与普通印泥的品质差别很大。好的印泥色泽鲜亮,经久不变色,钤在书画上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好的印章配好的印泥,好比宝马配金鞍。
张鲁庵痴迷金石刻印,在技艺磨炼中,深谙印谱、印石、刻刀、印泥四位一体,缺一不可。他为了在刻印时刻刀能用得得心应手,专门自己设计了刀形,花重金在德国求购了顶尖的“鹰力球”牌锋钢,制作专用刻刀。在印刀达到他所追求的“所向披靡”“随心所欲”的感觉后,他又对既有的印泥质量越来越不满意。当时,西方化学印泥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初印时色泽艳丽,但久而久之就会褪色;而很多使用传统工艺的印泥却因为配方失调,出现泥块薄稠不一的情况,影响使用。
好的印泥如同名墨,成为书画家追求的对象。张鲁庵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使用好的印泥,他开始潜心研制印泥。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番工夫在后来成为他的金字招牌。
制作印泥在篆刻艺术中虽属于“雕虫小技”,但要做好却不容易。从清乾隆时期起,最得行内人士青睐的只有福建漳州魏丽华家独家秘制的印泥。但是魏家的印泥秘方,累世相传,只传长房长媳,故外人绝难知晓秘方。而张鲁庵在杭州时,就试着研制印泥达十年之久。据说有一次为能做出满意的颜色,拟用红宝石做成分,他真将红宝石碾碎,后发现粉末是白色的,只好作罢。张鲁庵前后耗资数千大洋,却始终不能仿制出如魏家那样的极品印泥。
到了上海之后,条件完善了,机会也来了。当时他开始自号“印泥工人”,把家里弄得宛如一个实验室。他投入大量资金,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化学和物理专家陈灵生、余雪扬到家共同研究。同时,张鲁庵以每两16银圆的高价,从漳州魏家购进24两印泥。印泥到手后,他除了自存8两,其余16两分成4份,一份分析油性,一份分析颜料,一份分析艾绒成分,一份分析附加的药料成分。
从原料选择到配方比例的调整,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印泥终于制作成功。用其钤出的印蜕,色泽鲜明、历久不变;钤出的印文有立体感,很少受气温影响。
“即便连续印十方细元朱文,印文也不走样,这就是鲁庵印泥的厉害之处。”高式熊后来回忆说,“这个特制工艺秘方,从1号到56号,浸润了张鲁庵毕生的心血。因为这秘方里,含有多种中药和化学成分,再经过手工操作和自然氧化过程。此外,他根据上海的气候,配制的印泥热天不烂、寒天不硬,印色鲜艳雅丽、质薄匀净,所以也叫海派印泥。”
“鲁庵印泥”正是从那时起开始闻名天下,甚至产生了“一两黄金一两鲁庵印泥”的说法。当时,北京有一位从皇宫出来的印泥制作高手徐正庵,做的印泥被称为“天下第一”。“鲁庵印泥”问世后,书画家们自然关心哪一个更优,但一番比较下来,都觉得两种印泥难分伯仲,于是又有了“南张北徐”的说法。
在《潘伯鹰文存》之《小沧桑记》中,有一篇《印泥工人张鲁庵》的文章,作者认为张鲁庵成功的原因在于“认真”二字:“他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认真而已,因为认真,别人所不能体察到的细微关键,他能抓住。屡察屡改,以致他成了‘状元’。”
最令人称奇的是,不论是“鲁庵印泥”还是自制的优质刻刀,都不外售。当年,张大千、吴湖帆、徐森玉、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等篆刻书画名家都用着张鲁庵赠送的“鲁庵印泥”和刻刀。后来,上海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也先后用上了“鲁庵印泥”。再后来,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书画家也纷纷得到了张鲁庵赠送的印泥和刻刀。一时间,艺林同好们都以能获得一盒“鲁庵印泥”为生平乐事,以至于张大千离开大陆后,还设法托人为他捎去“鲁庵印泥”。
也许,对张鲁庵来说,大家用了觉得好,就是他最大的快乐,而他的快乐,与钱无关。“伊活络得不得了,样样都要白相相,真会白相,而且肯掼钞票,但做出来的印泥从来不卖的,就送送朋友,交关慷慨,还是小开脾气嘛!”高式熊这样评论这位亦师亦友的“药号小开”,而他自己平时用的刻刀,有两把也是张鲁庵制作赠送的。
当时,高式熊曾建议张鲁庵公开印泥方子,张鲁庵却说:“公开出来其实也没什么稀奇,只是没人重视罢了。”高式熊于是去联系博物馆、书法家协会、西泠印社等,果然各方都不重视。直到2008年,“鲁庵印泥制作技艺”才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漳州八宝印泥”一起,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宝级印泥。
乐善好施不做亡国奴
如果评价张鲁庵仅是一个爱好书画篆刻的“小开”,未免有失偏颇。张鲁庵自小家境殷实,虽出手阔绰,骨子里却有着一种文人风骨。
经营张同泰药号时,他要求药店采购的药材必须是原产地进购的顶级产品。比如常用的补气药黄芪,必须选产地为内蒙古和山西的;又如常用的清热解毒、调和用的中药材甘草,虽然多地皆有生产,他却派人远赴新疆收集,保证甘草的优良品质。
店里的药材好,价格自然不菲,但遇到家境困难的病人,药店却会减免药费。张鲁庵刚接手药店时,自然灾害频发,难民连续不断,每逢腊月初八或大灾之时,“张同泰”就会在孩儿巷支起两口大锅,熬制腊八粥,布施饥民。而到了端午节,“张同泰”又会在孩儿巷分送祛病香囊,为百姓防病治病。
就是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张同泰”济世利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张鲁庵自身又喜欢金石书画,他在沪杭两地商业界的名望日益高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次年,上海淞沪抗战失利,不久之后,杭州城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就在同年,张鲁庵暂时回到了杭州,看着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满目狼藉,他干脆关上了张同泰国药号的大门,闭门歇业。虽然做不到实质性的抗争,他也不想为日本侵略者粉饰门面。
然而,汉奸王五权却找到了他。当时,日军占领杭州城后,杭州原有的各行业同业公会悉数解散,日军苦于没有同业公会帮助,无法收取税费和控制各行业,就要求王五权限期成立各行业公会。而到恢复医店同业公会时,王五权就想起了当时最有声望和号召力的张鲁庵。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提出这个建议,张鲁庵立即拒绝了他。权衡利弊后,王五权以退为进,只说让张鲁庵再考虑考虑,悻悻离去。
之后发生的事,令张鲁庵始料未及。几天后,夫人带着儿子到西湖边的亲戚家游玩,到了华灯初上,却仍不见夫人和儿子归家的身影,张鲁庵立即派人到西湖边的亲戚家打听,那边却回复说夫人和孩子吃完午饭就坐黄包车回家了。张鲁庵急忙派人在杭州城内四处寻找,一直到下半夜依然杳无音信。他坐在客厅,一夜未寐。
第二天天刚亮,客厅的电话响了起来,张鲁庵忙接起电话,只听到一个阴沉的声音说:“张老板,你的夫人和儿子在我们这儿,现在他们很好,我们劝你不要一意孤行,不识时务,不然的话你就到西湖边收尸吧!”说完狠话,对方一下挂断了电话。
过了没多久,家人就来报,王五权和一个日本军人来访。王五权介绍,日本军人是管理杭州社会事务的沟部熊吉中将,听说张鲁庵夫人和儿子走失,特地来慰问,顺便商谈张鲁庵出任药店同业公会会长一事。此时,张鲁庵已经明白,妻儿已被日伪扣留做了人质。
心中一思忖,听着汉奸王五权和日军中将沟部熊吉言语中所带的威胁,张鲁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微微点了下头,应承了下来。果然,到了下午,王五权把夫人陆献芹和儿子送回了张宅,同时还不忘假惺惺地说:“皇军派了几个中队用大狼狗搜寻,终于在吴山找到了张太太和您儿子。”
见识了日寇和汉奸的卑鄙手段后,张鲁庵开始虚与委蛇。表面上他不做任何对抗,面对王五权“半个月内重建杭州药店同业公会”的要求,张鲁庵点头表示应承,同时开始起早贪黑,整天忙进忙出的日子,并不时向王五权汇报筹建情况。起初,王五权对张鲁庵颇有戒心,但到后来,见张鲁庵四处联系,各药店反响热烈的情况后,就渐渐放心了。
半个月后,张鲁庵找到了王五权的社会科办公室,对他说:“经过紧张的筹备,药店同业公会成立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按原计划,明天上午9时在市商会会议室召开成立会议,请王科长莅临指导。”当时的王五权,已经对张鲁庵完全放心,听取了成立计划后,立即到日军办公室去做了汇报。
而第二天早上,当王五权陪同沟部熊吉提前10分钟来到市商会会场时,却发现会场冷冷清清,完全没有召开会议的迹象。时间过了9点,会场里依旧只有王五权和沟部熊吉等人。这时王五权才发现事情不妙,立即派人到“张同泰”和张鲁庵家中寻找。然而偌大一个“张同泰”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张鲁庵家也人去楼空,踪迹全无。
原来,张鲁庵不愿意为虎作伥,他在取得王五权的信任之后,就立即行动了起来,暗暗遣散了全部员工,并将贵重物品悄悄转移了出去,同时把名贵药材做了妥当的安排。那天,他只身来到王五权办公室通知开会,只是为了麻痹王五权。在通知完后,他就连夜带着阖家老小,避走到了浙西山区乡下,隐姓埋名过起了乡野生活。
几年后,日寇在全国各地抗日战场中屡战屡败,盘踞在杭州的日伪政权惶惶不可终日,无心加强统治。张鲁庵在浙西山区得到消息后返回杭州,将“张同泰”重新营业起来。当时,张鲁庵除了经营药号和金石篆刻,还多次悄悄通过地下渠道,为抗日部队和游击队送医送药,尽了一份抗日爱国之力。
古道热肠于细微处见信义
上海解放之后,张鲁庵久居上海,金石印谱收藏也日益精进,“鲁庵印泥”更是形成了独特的技艺配方,在上海的金石书画界名声日隆。同时,他还担任了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秘书长。
1956年的一天,上海书法篆刻家田叔达和张维杨陪同一位年轻人到张鲁庵家中拜访,他们要把这位年轻人引荐给张鲁庵。这位年轻人名叫符骥良,当时30岁,自小喜欢金石书画,1950年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金石书画界逐步结交了一批同好,开始崭露头角。
一见到符骥良,张鲁庵就拿出印石、刻具让符骥良刻了一方“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的便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符骥良胸有成竹,用时不多,就刻好了一方便章。张鲁庵拿起刻好的便章,给予了好评。从此之后,他就把符骥良留在了身边,作为自己的助理。
当时,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有社员140多人,汇集了中国金石篆刻界的顶尖高手,而“鲁庵印泥”成为社员们的必用印泥,需求量大增。而此时的张鲁庵已体弱多病,难以承受长时间的印泥制作工作。为了满足社员的需求,张鲁庵开始带着符骥良一起参与制作。经过几年的言传身教,符骥良尽得张鲁庵的印泥制作技艺,成为“鲁庵印泥”的直接传承者。
高式熊曾说,用一个词形容张鲁庵,就是“古道热肠”。他不仅将“鲁庵印泥”的独门秘技传授给了符骥良和高式熊,他的高古人品,也长时间在艺界广为流传。
20世纪初寓居上海后,张鲁庵结识了上海众多的金石书画大家,其中有一位金石书画家叫杜镜吾,是张鲁庵好友,两人常相互切磋篆刻技艺,交流金石印谱书籍。两家住得不远,经常相互借书,来往频繁了,杜镜吾有时懒得出门,就让儿子杜启康到张鲁庵家送书还书。
1962年,张鲁庵因肝癌不幸逝世。这位中国“金石、印谱收藏第一人”的离开,引起了艺界轰动。而他在生前曾留下遗嘱,把他的毕生收藏全部捐献给杭州西泠印社。
就在张鲁庵葬礼举行过后,杜镜吾听说了张鲁庵要把所有收藏的珍贵金石、印谱捐赠出去的遗嘱,不禁对友人的义举感到钦佩。但几天后,他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两本珍贵印谱出借在张鲁庵家!这两本印谱是自己家的祖传珍本,平时根本不会外借他人,因为张鲁庵开口了,他才会借出去。这样一想,杜镜吾心中不免着急,自己祖传的两本珍谱,是否会被张鲁庵家属当作张鲁庵的藏品一并捐献出去呢?焦急之余,杜镜吾立刻写了一封信,让儿子杜启康赶往张鲁庵家中打听情况。
事出突然,杜启康在听了父亲的嘱咐后,一路小跑来到张鲁庵家,张鲁庵的第二任妻子叶宝琴接待了杜启康。杜启康首先对张鲁庵的逝世表示了哀悼,然后将父亲的信件交给了叶宝琴。接过信件看完后,叶宝琴忙说:“这件事是有的,若不是你父亲提起,我还忘了!这件事张先生生前已经关照过。你坐一下,我上楼去取!”
叶宝琴从楼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交给了杜启康。杜启康打开一看,正是父亲千叮嘱万吩咐的两本祖传印谱。这时,叶宝琴又递给杜启康一方黄绸礼盒,打开一看,礼盒中有一只青花印泥盒,盒中鲜红如血、光彩可鉴的“鲁庵印泥”足有一两多。
叶宝琴说:“老头子生前特地关照,这两本印谱是杜镜吾先生的心爱之物,一定要完璧归赵。老头子还叮嘱,杜先生是制印高手,务必把这盒珍藏多年的‘鲁庵印泥’送给老友,留作纪念。”
杜启康虽对金石篆刻没有研究,但耳濡目染,常听父亲杜镜吾赞叹“鲁庵印泥”如何了得,如何珍贵,也听说过一两“鲁庵印泥”足抵一两黄金的传闻。如今捧着这盒印泥,思及张鲁庵对自己父亲的情谊,顿时觉得重如千金。
回到家后,杜启康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父亲杜镜吾。杜镜吾拿着张鲁庵归还的印谱和赠送的“鲁庵印泥”,由衷钦佩起老友的为人。他连连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其实,对张鲁庵一生的成就,可以用“三印”来概括:历代印谱、印章收藏天下第一,创制“鲁庵印泥”贵为国宝。在张鲁庵下葬之时,夫人叶宝琴在丈夫的骨灰盒内放入了一小瓶精制蓖麻油,而这瓶蓖麻油正是“鲁庵印泥”配方的奥秘所在。
10多年的反复科学试验,张鲁庵终于创制出国宝“鲁庵印泥”,他毫无保留地把印泥制作技术传授给了符骥良和高式熊等后人;40余年收集的从古至今的珍贵印谱、印章,他也没有据为己有,出书拓谱,编册流传,更在死后把毕生收藏捐献出来。
在近现代金石篆刻界,张鲁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纽带。他从最初学习以赵次闲为代表的西泠印社诸人的技巧,到学习有“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美誉的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完白的治印艺术,再到拜师赵叔孺,授艺高式熊、符骥良,张鲁庵以一己之心力,一药号之财力,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篆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张鲁庵的一生,又何止“三印”?
谈及与张鲁庵的相识相知,高式熊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运气好,这位良师益友对他而言,宛如人生路上的明灯。
从赵叔孺到高式熊
20世纪30年代,刚过而立之年的张鲁庵来到上海,并长期寓居于此。当时的张鲁庵,已经开始广为收藏研究印章印谱,被时人称为“印痴”,来上海除了拓展产业,更是为了拜师、求学、广交朋友。
而在这里,他遇到了被称为“近世之赵孟頫”的赵叔孺。赵叔孺精通金石印刻,擅长花卉虫草、鞍马翎毛,其中尤精画马。机遇难得,张鲁庵立刻表达了拜入赵叔孺门下的意愿,令他惊喜的是,赵叔孺马上答应了。
他不知道的是,赵叔孺当时虽已是书画界泰斗,却乐善好施,有教无类,门下弟子众多。赵叔孺的弟子之一陈巨来曾说:“一班附庸风雅的仕女,纷然而至,拜列门墙,执弟子之礼,可谓群英杂凑,少长都全,有银行经理、钱庄阿大、朝鲜女学生、青楼女画家、纨绔子弟、没落者、留学者,及其没后,闻共得七十二贤之多云。”而这纨绔子弟,指的就是张鲁庵。
宽松的学习环境,让张鲁庵可以在经商的同时,研究金石篆刻和印泥技艺。或许这个“印痴”也当真与篆刻有缘,虽被称为纨绔子弟,他在赵叔孺的众多弟子中,却也十分出挑,与篆刻名家陈巨来、方介堪、沙孟海、叶露园等人同为当时上海艺林的翘楚,出版了《仿完白山人印谱》(1932年拓本)两卷等著作。
1942年和1944年,赵叔孺率门人两次举办“赵氏同门金石书画展览会”,轰动上海艺界。张鲁庵的金石篆刻、收藏的印章印谱和制作的精美印泥,在两次展览会上都大放异彩。
而在1941年,少年高式熊也通过赵叔孺的介绍,结识了张鲁庵。
当时,赵叔孺把张鲁庵编的《黄牧甫印谱》推荐给了初入篆刻之门的高式熊。但印谱5元的高价令高式熊难以承受,赵叔孺忙说:“你不必买,做这部印谱的人会送来的。”
过了些时日,张鲁庵寻上门来,自报家门:“我叫张咀英(张鲁庵号咀英),赵叔孺先生叫我来的,这印谱送给你。”当时的张鲁庵虚岁已经42岁,比高式熊大21岁。这一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自此成为忘年交。“几时我请你吃顿饭,你到我家里来看看。”初次见面,张鲁庵就邀请高式熊去他位于江阴路九福里的家里做客。
不久之后,高式熊正式登门拜访张鲁庵。一进门,他就吓了一跳:书房的四面书橱中全是印谱。而在张鲁庵家中,这样的书房共有三间。张鲁庵曾在《从师回忆录》中有过统计:“积年既久,所获渐多,共得古今印章四千余钮,历代印谱四百余种。”
不等高式熊回过神来,张鲁庵就大方地说:“今天是让你来看看我家环境的。你学篆刻,必须多看印谱,最好看原拓印谱。我看你家里不富裕,也买不起印谱,你不用买了,我的这些印谱印章就是你的。今后你要看什么,由我来安排。”
如今,高式熊已经年逾九旬,但他依旧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他的这种无私提携后人的举动,使我终生难忘。”
从此以后,高式熊成了张家的常客。他所用的图章石头、刻刀、印泥、印谱纸等,皆由张鲁庵提供。张鲁庵还在自己的书房里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写字台,并把房门钥匙给了高式熊,允许他自由进出。
“那是我刻章最得益的机会!”高式熊坦言。多年以后,他整理汇辑了《鲁庵所藏印谱简目》一册四卷及附卷,引起了书画界的轰动。内容囊括四百多部印谱的原拓本、印本及所有的名印谱。其中甚至还有陈介祺赠给吴大澂的那部一百册的《十钟山房印举》——这是张鲁庵花了八百两银子从吴大澂之孙吴湖帆手中购得的。
从药号小开到以商养文
不论是陈巨来,还是高式熊,谈及张鲁庵,总避不开“家境殷实”这四个字。因为父亲早逝,尚在襁褓中的张鲁庵被确立为杭州名药号“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在他9岁,仍在老家宁波马径村上学读书之时,就在名义上接手了“张同泰”药号的经营。
其实当时,张母杨氏才是药号实际的经营者。《张氏宗谱》收有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的《张母杨太君五十寿序》。序文说道:“张氏以商起家,尤善储药。自秦蜀岭外,珍异之草,谲怪之物,无所不至。北采辽东人参,输之其乡,以是雄于财。太君早岁持门户,能制奇赢,忠信重诺,使人乐为用。选材益良,懋迁过于旧数倍。”大意是说:“张同泰”在全国各地搜罗名贵药材,无所不至,无所不有,财力雄厚。杨氏年轻时就主持门户,深通经商之道,又讲究诚信,赢得手下效忠,使得生意比从前好出几倍。
而至张鲁庵成年,正式接手药号生意的时候,“张同泰”已经财源广进,成为与当时杭州城著名的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齐名的六大国药铺之一。
成家立业,张鲁庵亦在那一年结了婚。也就是从那时起,张同泰药号开始了以商养文的嬗变。
20世纪初,上海逐步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国际上,也称得上是大都市。上海的租界云集了全国知名的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文化名人交往频繁,文化盛事此起彼伏。
经商几年的张鲁庵开始逐步接触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圈子,心思活络的他十分向往上海的繁荣和发达。尤其是他在杭州的好友收藏家高野侯、高络园兄弟等陆续迁往上海发展后,向上海拓展产业,在这片文化海洋中拜师、求学、广交朋友的念头就在张鲁庵心中发芽了。
于是,张鲁庵多次到上海进行考察,最后选定了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房地产大王”哈同的产业慈淑大厦内开设“张同泰国药号益元参店分号”,专营名贵滋补药材。道地的用料,使“张同泰”在上海一炮打响。在经营上取得突破的时候,张鲁庵聘请了一位经理,自己索性当起了甩手掌柜。
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成绩,但这并不是张鲁庵迁居上海的最终目的。在拜赵叔孺为师后,他在每日修习金石篆刻外,仍延续着年少时收集印谱印章的爱好。到上海之后,藏品的广度和数量突飞猛进,再加上张鲁庵家赀丰厚,各种与金石篆刻有关的藏品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如一方邓石如所刻的五面印,张鲁庵考证后确认为真品,于是与前江苏抚台刘坤一的后裔多次商谈,花了500银圆买下。古玩商人们看到张鲁庵出手如此阔绰,都把他当成“纨绔子弟”“药号小开”,纷纷上门求售。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鲁庵每次都严格审定,只有确定了并非赝品,他才会出价收藏。而如果其中有珍品精品,或者孤本善本,他会主动加价购买。在这种以商养文的资金支持下,张鲁庵收藏的印谱就有400多部,收藏的历代印章更达到4000余方。其中何雪渔印章20方,并拓之成集,而当中的“放情诗酒”一方印,是杭城著名收藏大家魏家孙旧藏,当时的上海艺界得知后,纷纷把它捧为极品拱璧。
在庞大收藏品的支持下,张鲁庵的篆刻水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也成为公认的全国收集历代篆刻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收藏者,在当时,就已经有人称他为印谱收藏“海内第一家”。同时,《鲁庵印选》《鲁庵印谱》等10余本印谱图书接连出版,除了最珍贵的《十钟山房印举》百册拓本,明代万历年间的《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隆庆年间的《顾氏集古印谱》等印谱亦重回公众视野,大大丰富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篆刻文化。
鲁庵印泥国之瑰宝
作为一个“印人”,在治印过程中有三样重要的工具:一为印石,用田黄、鸡血、寿山石等名贵石材刻之,其印章可为子孙后世永久宝之,否则为无本之木;二为刻刀,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即印泥,别看都是红色,好的印泥与普通印泥的品质差别很大。好的印泥色泽鲜亮,经久不变色,钤在书画上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好的印章配好的印泥,好比宝马配金鞍。
张鲁庵痴迷金石刻印,在技艺磨炼中,深谙印谱、印石、刻刀、印泥四位一体,缺一不可。他为了在刻印时刻刀能用得得心应手,专门自己设计了刀形,花重金在德国求购了顶尖的“鹰力球”牌锋钢,制作专用刻刀。在印刀达到他所追求的“所向披靡”“随心所欲”的感觉后,他又对既有的印泥质量越来越不满意。当时,西方化学印泥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初印时色泽艳丽,但久而久之就会褪色;而很多使用传统工艺的印泥却因为配方失调,出现泥块薄稠不一的情况,影响使用。
好的印泥如同名墨,成为书画家追求的对象。张鲁庵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使用好的印泥,他开始潜心研制印泥。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番工夫在后来成为他的金字招牌。
制作印泥在篆刻艺术中虽属于“雕虫小技”,但要做好却不容易。从清乾隆时期起,最得行内人士青睐的只有福建漳州魏丽华家独家秘制的印泥。但是魏家的印泥秘方,累世相传,只传长房长媳,故外人绝难知晓秘方。而张鲁庵在杭州时,就试着研制印泥达十年之久。据说有一次为能做出满意的颜色,拟用红宝石做成分,他真将红宝石碾碎,后发现粉末是白色的,只好作罢。张鲁庵前后耗资数千大洋,却始终不能仿制出如魏家那样的极品印泥。
到了上海之后,条件完善了,机会也来了。当时他开始自号“印泥工人”,把家里弄得宛如一个实验室。他投入大量资金,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化学和物理专家陈灵生、余雪扬到家共同研究。同时,张鲁庵以每两16银圆的高价,从漳州魏家购进24两印泥。印泥到手后,他除了自存8两,其余16两分成4份,一份分析油性,一份分析颜料,一份分析艾绒成分,一份分析附加的药料成分。
从原料选择到配方比例的调整,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印泥终于制作成功。用其钤出的印蜕,色泽鲜明、历久不变;钤出的印文有立体感,很少受气温影响。
“即便连续印十方细元朱文,印文也不走样,这就是鲁庵印泥的厉害之处。”高式熊后来回忆说,“这个特制工艺秘方,从1号到56号,浸润了张鲁庵毕生的心血。因为这秘方里,含有多种中药和化学成分,再经过手工操作和自然氧化过程。此外,他根据上海的气候,配制的印泥热天不烂、寒天不硬,印色鲜艳雅丽、质薄匀净,所以也叫海派印泥。”
“鲁庵印泥”正是从那时起开始闻名天下,甚至产生了“一两黄金一两鲁庵印泥”的说法。当时,北京有一位从皇宫出来的印泥制作高手徐正庵,做的印泥被称为“天下第一”。“鲁庵印泥”问世后,书画家们自然关心哪一个更优,但一番比较下来,都觉得两种印泥难分伯仲,于是又有了“南张北徐”的说法。
在《潘伯鹰文存》之《小沧桑记》中,有一篇《印泥工人张鲁庵》的文章,作者认为张鲁庵成功的原因在于“认真”二字:“他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认真而已,因为认真,别人所不能体察到的细微关键,他能抓住。屡察屡改,以致他成了‘状元’。”
最令人称奇的是,不论是“鲁庵印泥”还是自制的优质刻刀,都不外售。当年,张大千、吴湖帆、徐森玉、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等篆刻书画名家都用着张鲁庵赠送的“鲁庵印泥”和刻刀。后来,上海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也先后用上了“鲁庵印泥”。再后来,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书画家也纷纷得到了张鲁庵赠送的印泥和刻刀。一时间,艺林同好们都以能获得一盒“鲁庵印泥”为生平乐事,以至于张大千离开大陆后,还设法托人为他捎去“鲁庵印泥”。
也许,对张鲁庵来说,大家用了觉得好,就是他最大的快乐,而他的快乐,与钱无关。“伊活络得不得了,样样都要白相相,真会白相,而且肯掼钞票,但做出来的印泥从来不卖的,就送送朋友,交关慷慨,还是小开脾气嘛!”高式熊这样评论这位亦师亦友的“药号小开”,而他自己平时用的刻刀,有两把也是张鲁庵制作赠送的。
当时,高式熊曾建议张鲁庵公开印泥方子,张鲁庵却说:“公开出来其实也没什么稀奇,只是没人重视罢了。”高式熊于是去联系博物馆、书法家协会、西泠印社等,果然各方都不重视。直到2008年,“鲁庵印泥制作技艺”才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漳州八宝印泥”一起,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宝级印泥。
乐善好施不做亡国奴
如果评价张鲁庵仅是一个爱好书画篆刻的“小开”,未免有失偏颇。张鲁庵自小家境殷实,虽出手阔绰,骨子里却有着一种文人风骨。
经营张同泰药号时,他要求药店采购的药材必须是原产地进购的顶级产品。比如常用的补气药黄芪,必须选产地为内蒙古和山西的;又如常用的清热解毒、调和用的中药材甘草,虽然多地皆有生产,他却派人远赴新疆收集,保证甘草的优良品质。
店里的药材好,价格自然不菲,但遇到家境困难的病人,药店却会减免药费。张鲁庵刚接手药店时,自然灾害频发,难民连续不断,每逢腊月初八或大灾之时,“张同泰”就会在孩儿巷支起两口大锅,熬制腊八粥,布施饥民。而到了端午节,“张同泰”又会在孩儿巷分送祛病香囊,为百姓防病治病。
就是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张同泰”济世利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张鲁庵自身又喜欢金石书画,他在沪杭两地商业界的名望日益高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次年,上海淞沪抗战失利,不久之后,杭州城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就在同年,张鲁庵暂时回到了杭州,看着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满目狼藉,他干脆关上了张同泰国药号的大门,闭门歇业。虽然做不到实质性的抗争,他也不想为日本侵略者粉饰门面。
然而,汉奸王五权却找到了他。当时,日军占领杭州城后,杭州原有的各行业同业公会悉数解散,日军苦于没有同业公会帮助,无法收取税费和控制各行业,就要求王五权限期成立各行业公会。而到恢复医店同业公会时,王五权就想起了当时最有声望和号召力的张鲁庵。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提出这个建议,张鲁庵立即拒绝了他。权衡利弊后,王五权以退为进,只说让张鲁庵再考虑考虑,悻悻离去。
之后发生的事,令张鲁庵始料未及。几天后,夫人带着儿子到西湖边的亲戚家游玩,到了华灯初上,却仍不见夫人和儿子归家的身影,张鲁庵立即派人到西湖边的亲戚家打听,那边却回复说夫人和孩子吃完午饭就坐黄包车回家了。张鲁庵急忙派人在杭州城内四处寻找,一直到下半夜依然杳无音信。他坐在客厅,一夜未寐。
第二天天刚亮,客厅的电话响了起来,张鲁庵忙接起电话,只听到一个阴沉的声音说:“张老板,你的夫人和儿子在我们这儿,现在他们很好,我们劝你不要一意孤行,不识时务,不然的话你就到西湖边收尸吧!”说完狠话,对方一下挂断了电话。
过了没多久,家人就来报,王五权和一个日本军人来访。王五权介绍,日本军人是管理杭州社会事务的沟部熊吉中将,听说张鲁庵夫人和儿子走失,特地来慰问,顺便商谈张鲁庵出任药店同业公会会长一事。此时,张鲁庵已经明白,妻儿已被日伪扣留做了人质。
心中一思忖,听着汉奸王五权和日军中将沟部熊吉言语中所带的威胁,张鲁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微微点了下头,应承了下来。果然,到了下午,王五权把夫人陆献芹和儿子送回了张宅,同时还不忘假惺惺地说:“皇军派了几个中队用大狼狗搜寻,终于在吴山找到了张太太和您儿子。”
见识了日寇和汉奸的卑鄙手段后,张鲁庵开始虚与委蛇。表面上他不做任何对抗,面对王五权“半个月内重建杭州药店同业公会”的要求,张鲁庵点头表示应承,同时开始起早贪黑,整天忙进忙出的日子,并不时向王五权汇报筹建情况。起初,王五权对张鲁庵颇有戒心,但到后来,见张鲁庵四处联系,各药店反响热烈的情况后,就渐渐放心了。
半个月后,张鲁庵找到了王五权的社会科办公室,对他说:“经过紧张的筹备,药店同业公会成立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按原计划,明天上午9时在市商会会议室召开成立会议,请王科长莅临指导。”当时的王五权,已经对张鲁庵完全放心,听取了成立计划后,立即到日军办公室去做了汇报。
而第二天早上,当王五权陪同沟部熊吉提前10分钟来到市商会会场时,却发现会场冷冷清清,完全没有召开会议的迹象。时间过了9点,会场里依旧只有王五权和沟部熊吉等人。这时王五权才发现事情不妙,立即派人到“张同泰”和张鲁庵家中寻找。然而偌大一个“张同泰”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张鲁庵家也人去楼空,踪迹全无。
原来,张鲁庵不愿意为虎作伥,他在取得王五权的信任之后,就立即行动了起来,暗暗遣散了全部员工,并将贵重物品悄悄转移了出去,同时把名贵药材做了妥当的安排。那天,他只身来到王五权办公室通知开会,只是为了麻痹王五权。在通知完后,他就连夜带着阖家老小,避走到了浙西山区乡下,隐姓埋名过起了乡野生活。
几年后,日寇在全国各地抗日战场中屡战屡败,盘踞在杭州的日伪政权惶惶不可终日,无心加强统治。张鲁庵在浙西山区得到消息后返回杭州,将“张同泰”重新营业起来。当时,张鲁庵除了经营药号和金石篆刻,还多次悄悄通过地下渠道,为抗日部队和游击队送医送药,尽了一份抗日爱国之力。
古道热肠于细微处见信义
上海解放之后,张鲁庵久居上海,金石印谱收藏也日益精进,“鲁庵印泥”更是形成了独特的技艺配方,在上海的金石书画界名声日隆。同时,他还担任了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秘书长。
1956年的一天,上海书法篆刻家田叔达和张维杨陪同一位年轻人到张鲁庵家中拜访,他们要把这位年轻人引荐给张鲁庵。这位年轻人名叫符骥良,当时30岁,自小喜欢金石书画,1950年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金石书画界逐步结交了一批同好,开始崭露头角。
一见到符骥良,张鲁庵就拿出印石、刻具让符骥良刻了一方“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的便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符骥良胸有成竹,用时不多,就刻好了一方便章。张鲁庵拿起刻好的便章,给予了好评。从此之后,他就把符骥良留在了身边,作为自己的助理。
当时,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有社员140多人,汇集了中国金石篆刻界的顶尖高手,而“鲁庵印泥”成为社员们的必用印泥,需求量大增。而此时的张鲁庵已体弱多病,难以承受长时间的印泥制作工作。为了满足社员的需求,张鲁庵开始带着符骥良一起参与制作。经过几年的言传身教,符骥良尽得张鲁庵的印泥制作技艺,成为“鲁庵印泥”的直接传承者。
高式熊曾说,用一个词形容张鲁庵,就是“古道热肠”。他不仅将“鲁庵印泥”的独门秘技传授给了符骥良和高式熊,他的高古人品,也长时间在艺界广为流传。
20世纪初寓居上海后,张鲁庵结识了上海众多的金石书画大家,其中有一位金石书画家叫杜镜吾,是张鲁庵好友,两人常相互切磋篆刻技艺,交流金石印谱书籍。两家住得不远,经常相互借书,来往频繁了,杜镜吾有时懒得出门,就让儿子杜启康到张鲁庵家送书还书。
1962年,张鲁庵因肝癌不幸逝世。这位中国“金石、印谱收藏第一人”的离开,引起了艺界轰动。而他在生前曾留下遗嘱,把他的毕生收藏全部捐献给杭州西泠印社。
就在张鲁庵葬礼举行过后,杜镜吾听说了张鲁庵要把所有收藏的珍贵金石、印谱捐赠出去的遗嘱,不禁对友人的义举感到钦佩。但几天后,他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两本珍贵印谱出借在张鲁庵家!这两本印谱是自己家的祖传珍本,平时根本不会外借他人,因为张鲁庵开口了,他才会借出去。这样一想,杜镜吾心中不免着急,自己祖传的两本珍谱,是否会被张鲁庵家属当作张鲁庵的藏品一并捐献出去呢?焦急之余,杜镜吾立刻写了一封信,让儿子杜启康赶往张鲁庵家中打听情况。
事出突然,杜启康在听了父亲的嘱咐后,一路小跑来到张鲁庵家,张鲁庵的第二任妻子叶宝琴接待了杜启康。杜启康首先对张鲁庵的逝世表示了哀悼,然后将父亲的信件交给了叶宝琴。接过信件看完后,叶宝琴忙说:“这件事是有的,若不是你父亲提起,我还忘了!这件事张先生生前已经关照过。你坐一下,我上楼去取!”
叶宝琴从楼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交给了杜启康。杜启康打开一看,正是父亲千叮嘱万吩咐的两本祖传印谱。这时,叶宝琴又递给杜启康一方黄绸礼盒,打开一看,礼盒中有一只青花印泥盒,盒中鲜红如血、光彩可鉴的“鲁庵印泥”足有一两多。
叶宝琴说:“老头子生前特地关照,这两本印谱是杜镜吾先生的心爱之物,一定要完璧归赵。老头子还叮嘱,杜先生是制印高手,务必把这盒珍藏多年的‘鲁庵印泥’送给老友,留作纪念。”
杜启康虽对金石篆刻没有研究,但耳濡目染,常听父亲杜镜吾赞叹“鲁庵印泥”如何了得,如何珍贵,也听说过一两“鲁庵印泥”足抵一两黄金的传闻。如今捧着这盒印泥,思及张鲁庵对自己父亲的情谊,顿时觉得重如千金。
回到家后,杜启康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父亲杜镜吾。杜镜吾拿着张鲁庵归还的印谱和赠送的“鲁庵印泥”,由衷钦佩起老友的为人。他连连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其实,对张鲁庵一生的成就,可以用“三印”来概括:历代印谱、印章收藏天下第一,创制“鲁庵印泥”贵为国宝。在张鲁庵下葬之时,夫人叶宝琴在丈夫的骨灰盒内放入了一小瓶精制蓖麻油,而这瓶蓖麻油正是“鲁庵印泥”配方的奥秘所在。
10多年的反复科学试验,张鲁庵终于创制出国宝“鲁庵印泥”,他毫无保留地把印泥制作技术传授给了符骥良和高式熊等后人;40余年收集的从古至今的珍贵印谱、印章,他也没有据为己有,出书拓谱,编册流传,更在死后把毕生收藏捐献出来。
在近现代金石篆刻界,张鲁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纽带。他从最初学习以赵次闲为代表的西泠印社诸人的技巧,到学习有“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美誉的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完白的治印艺术,再到拜师赵叔孺,授艺高式熊、符骥良,张鲁庵以一己之心力,一药号之财力,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篆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张鲁庵的一生,又何止“三印”?
相关人物
张鲁庵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