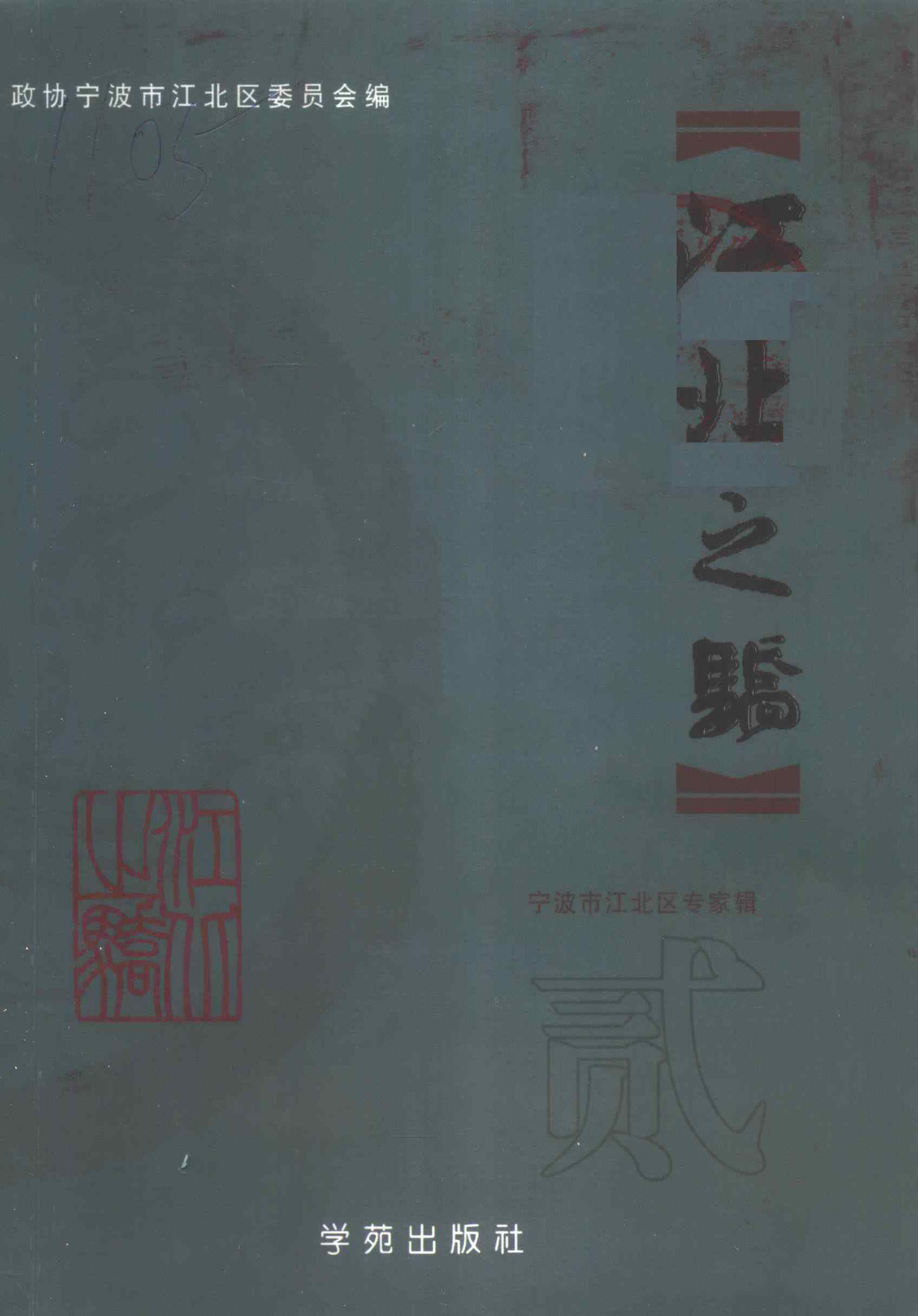内容
贝芝芬
记忆中的童年
我是宁波江北区慈城镇(原慈谿县)人,家住北门九曲弄7号。妈妈只生我和弟弟贝新源两个,弟弟比我小一岁多,我们的幼、童年是在抗日战争中渡过的。当日本鬼子把炸弹投向孔庙,妈妈带我们到黄山池墩外婆家避难,后来我和弟弟在那里的崇本小学上了学。我刚上学就参加演出,歌剧名:“面包歌”,剧中三个人:妈妈、女儿和一个要饭的小男孩。我演女儿(小红廖)。讲的是这小女孩在三岁时爸爸在抗日游击战中牺牲,过着“一顿三餐也很难得吃个饱”的日子,妈妈正等着小红廖放学回家吃饭,这时来了要饭的小男孩,妈妈把饭分给他吃,小红廖回来,大家就一起手拉手唱了起来,共同想往着有美好的未来。
崇本小学教师中有游击队(三五支队)里的人,我们懂得是游击队员在不怕流血牺牲奋勇打击日本鬼子。记得有位陈(还是姓郑?)老师,他像父亲般的关心我,当他要回游击队去前来家访,想把我带走,当时我妈妈正患“干血痨”,外婆外公刚相继去世,我那时才六岁,妈妈舍不得我走,弟弟也不让我走,陈老师就说以后再来接我。从此,我就一直等待这位老师能来接我,但他没有再来,也听不到他的音讯。
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我奔赴到哪里,在我心里一直装着崇本小学、北城小学、慈湖中学和我的老师,是他们辛勤培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这烽火漫天血腥遍野的年代里,妈妈靠给熟人帮家务、切鞋底、缝缝补补挣些钱,靠亲戚支援,和卖掉她的嫁妆来补贴家里开支,供我们上学。在最困难的时期,她自己吃糠和买便宜的已有烂斑的红薯充饥,那时我们已经懂事,我放学回家趁肚子饿就先拿过来吃,糠用水拌着吃很难咽下去,干的嚼着吃还可以,但吃不快,妈妈过来时总会抢过去,给我盛些饭吃。弟弟小时候身体较弱,好生病,所以我们都不让他吃这些。我和弟弟除了校服,没有穿过新衣服,连鞋袜都是亲戚他们孩子穿下来的。那年代穿下来的衣服已经很旧,鞋小挤脚,疼也得穿。我们家没有钱装电灯,晚上复习功课常常用菜油灯,在一盏菜油灯下,我和弟弟做功课,妈妈在一旁缝缝补补。妈妈不会讲更多的道理,她常说要我们好好学习,要学好本领。反反复复说这样一句话:“穷人志气高,乏好呀会好”。艰难岁月中的锻炼和革命的熏陶,使我们姐弟俩逐渐成长。
当我结婚有了孩子,我的爱人是航空兵师师长,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妈妈常常对孩子们讲我和弟弟小时候的故事,并告诉他们:“要吃苦中苦,才为人上人”,孩子们听外婆的话,从小爱劳动、能吃苦、勤学习,四个孩子都大学本科毕业,现都是高职称科技工作者。孩子们至今还记住外婆那纯朴、铭心的教导。
再见了妈妈!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弟弟和我都在慈湖中学读书,我们的班主任是陈华民老师,他不但教我们书,还教我们做人。慈湖中学里革命空气很高涨,上公民课的冯明老师常在上课时先告诉我们:解放军势如破竹,已经打到哪里来了,这里“解放”的日子快要到了。有一天,学校里有人给弟弟的书包里放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那天放学回家,我们一直看到半夜,开始有了对未来“新中国”的认识和对“理想”的追求。从这以后,我们常常讨论一些问题、不断提高认识水平。
1949年5月24日慈城解放。那一天上午,从东方山那边传来解放军炮声的时候,妈妈在客堂间的八仙桌上铺了厚厚的棉被,叫弟弟和我躲到桌子底下,她去厨房做午饭了。弟弟和我真想看看解放军进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偷偷跑出去,到了杨家弄,看到国民党兵换上了黑色便衣正在拼命逃。那年,我读初中二年级,弟弟读一年级。解放军住进了我们学校(大庙)里,在杨家弄祠堂里住着伤兵,每次放学路过,我们总会投去敬慕的目光,渴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人,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同学冯小英改名冯倩亚,我改名贝一平,报考宁波鄞县县立中学高中春季班,我们俩都被录取,她去上了高中(后来也参军)。我因妈妈借不到钱,劝我读完初中拿到文凭好找个工作。1950年毕业后,是王幼于老师把我引上革命道路,我参加了土改,在助征队工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弟弟在慈中入了团。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解放了的中国》,看的第一部故事片是《赵一曼》,从那时起,我就想往着自己将来能当一名解放军里的卫生兵,能扛着抢打敌人,上战场去抢救伤员。当我把这一追求告诉弟弟时,他说:“好!把我们的一切都献给祖国”。当时我们想到:我们俩都远离妈妈,她怎么受得了?我就劝弟弟留在妈妈身边。1951年7月15日,我们姐弟俩在同一天,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踏上征途,响应抗美援朝参军。当时我刚到上海东南药物职业学校实验室当练习生,我是瞒着妈妈从上海走的。当我参军后头10天里,我每天给妈妈写一封信,请她原谅女儿不告而别。后来妈妈告诉我,弟弟向她告别那天,他转身就快步走,头也不敢回。当时和战友们唱起《共青团员之歌》:“再见了妈妈!再见了亲爱的故乡!”的时候,心里总以为这一去也许再也回不来了而热泪盈眶。
志同道合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解放,全国各大报纸都广泛宣传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这一伟大的胜利,同时宣传了涌现出的一批英雄指战员,组织上给我介绍了其中的一位:张伟良,他是这次战斗中的空中带队长机。有一次他来病房看望战友,我在该科里当医生,科主任叫我给他送去一杯茶,我送去后就出来了。以后组织上找我谈时就说明了:这是组织安排让他看一看我。那个年代是“姑娘爱英雄、追英雄”的年代,不能说没有心动,但我考虑自己才20岁,刚毕业当上医生;他虽也才26岁,但已是航空兵师副师长,怕人家说我有“虚荣心”,我当时就没有表态,他也很快去苏联莫斯科红旗指挥学院学习。一年后,他们师的政委来住院,把我叫到他病房找我谈,我就把自己心里的顾虑说了。政委的话中,有两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动:一是他在这次执行任务中,敌人的炮弹钻到他飞机的肚子下没有爆炸,这就是说他险些为解放我们浙东沿海岛屿而付出年轻的生命;二是他因十二岁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性子急,脾气暴,要找一个性格比较柔和些的。我就写信向妈妈和弟弟说了这情况,得到了妈妈和弟弟的支持,我和张伟良就开始通信。他告诉我在战争年代里,他遭受到家破人亡的灾难,奶奶被鬼子杀害,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逃难和贫病交迫中去世,他很想有个“家”。1957年7月暑假,他回国飞行时我们结了婚。1959年,他毕业回国,我们有了一个家。那时,我的弟弟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每年暑、寒假都来,他称呼张伟良为“哥哥!”,张伟良也很喜欢有这样一位弟弟,妈妈也来,我们母子母女又团聚在一起。
现在我和张伟良已是将度金婚的年份了。我们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下一代也是两男两女: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他很满意,常常说:“日本鬼子和反动派毁了我的家;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我的家又兴旺起来。真是有国才有家!”。他确实脾气不好,在他“火”上来时我不作声,是我错,我就马上改;若是他错,等他火过了,我会转个弯儿向他指出。他说:他想和我吵架也吵不起来,结果还都是他“输”;孩子们都说:妈妈对爸爸是“以柔克刚”。这主要是我们有一个牢固的婚姻基础;志同道合。同路同歌
入伍后,弟弟和我开始都是陆军战士,弟弟在舟山,我在南京教导队集训,我们约好,到部队穿上军装戴上五角星时,要赶紧照一张像寄给亲爱的妈妈。1952年我们俩第一次立功(三等功),政府敲锣打鼓把两份立功喜报送到家里,妈妈给我们写的信里,字里行间露出了异常兴奋的心情,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1956年,我们同年入党。我是解放后军队系统培养的第一批军医;弟弟是祖国军事工程学院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核物理专家,我俩毕业成绩各科都全五分,优等生,而且自习能力比较好,这是故乡母校给我们打下的基础。不幸的是他在实验时得苯中毒、放射病;后来我也得了砷中毒致残,命运安排我们都得了职业病,而且都曾濒临死亡的边缘。因为他的病与他从事的专业密切相关,而当时这个专业是绝对保密的,他对我也一直保密,我一直不知道他学、干什么专业?他更不对医生说,所以很长时期里一直误诊误治。一般医生对“砷中毒”的诊治无经验,但我在医生误诊误治的情况下自己翻书,对号入了座。因当时我小女儿正准备要考大学,小儿子正在争取进重点高中,为了让他们集中精力学习,我不能说自己的病;我爱人已调往兰州,我不想增加他的思想负担,也不告诉他。晚上疼痛难忍,我怕穿鞋走有声音,就只穿袜子,轻轻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我只想坚持到孩子们都先后上了大学。我们姐弟俩在通讯中互相鼓励,坚持工作,下决心战胜病魔。我们还约好,退休后回家乡去发挥余热
1996年5月,当我的大女儿(广州军区总院副主任医师)突来电话;舅舅患脊柱内椎管肿瘤,要到她所在的医院开刀,说那边诊断是良性。开出来的情况会及时告诉我。
开刀的那天,我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但一直没有电话,我心里一直琢磨着,越想越预感有情况,等到晚上九点多,女儿来电话:“妈妈,舅舅开刀时,我一直在手术室,局部组织发黑,情况不太好,已做病理切片,报告还没有出来。我真不想告诉你,但又不得不告诉你”。我知道自己要死了,也没掉过一点眼泪,但这时我实在忍不住而哭了。我如果真的失去了弟弟,可能我再也振作不起来。我对女儿说:“你知道舅舅在我心中的份量,我不能没有他,一定要想办法!”。
三天后,女儿来电话说:是恶性的,要做放、化疗,但舅舅体质太弱,再是切片上还看不明白属那类型?脊髓细胞都变型,没敢上。手术后十天了还没上。我就立即买飞机票,张伟良陪我到北京找最有本事的专家咨询,拿了专家的医嘱后又飞往广州。
看到弟弟躺在床上的虚弱样子,我体会了“心碎”的感受,我轻轻地抚摸着他,问他,他露出小时候那腼腆的微笑,告诉我:“现在好多了,能躺下睡了”。女儿到家后告诉我:“舅舅手术前已有好多天不能躺,不能坐,只能站着,晚上用两个靠背椅子的背撑着打盹,连在飞机上也是站过来的”。可是他一直瞒着我。
和女儿商量,经医生同意,把我带去的“千佛草”给弟弟喝。一周后情况明显好转,先后上了放、化疗,查ECT正常后出院,回原单位医院继续治疗。由于放疗剂量过量而致放射病,好转后又一次放疗,再加上当时虚假广告的影响,广告甚至做到病房;在并发白血病时,又由于诊断和治疗上的原因(他病危时不让我去,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一直守着他,大女儿去偷看病历才明白,但一切已太晚了),而于1998年4月12日清晨病故。
张伟良和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1997年12月,在大学的医院里。去前女儿告诉我不要干扰那边的治疗,不要多问、多说,否则对他的治疗反而不利。当时他刚从白血病发作中抢救过来。情况还可以,能拿着拐棍在病房的走廊里走动。我想看看病历,向医生了解一下病情,血象怎么样?在吃什么药?这些都无法问,医生也不照面,无法知道。这一次去,我想问、想说的话很多,但怕给弟弟治病带来不利,又怕弟弟思想产生对病的顾虑和猜测,故而只是鼓励他一定要战胜疾病。他看我着急的样子,总说:“放心吧!没事的”。我告诉他以后的治疗千万要慎重,不能有半点出错,他点点头。但我马上感到这话怎么能对他说,应该对医生说,但现在的医生怎能听我说这种话!分别的时候,我下楼时感到腿发软、要哭,我爱人扶住我,我强忍住眼泪回过头去,想再看弟弟一眼,但弟弟已被扶向病房,留给我一个他最后的背影。
“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国防事业!”
1999年的元旦、春节之际,我给王幼于老师写贺年卡时,我还是把弟弟的名字签上了,我不忍心让敬爱的、已经年迈的王老师在双节的日子里受到失去学生之疼。后来他知道后安慰我,说我弟弟是以身殉职。王老师一次次给我写信关怀我,鼓励我。
弟弟走了,我和弟弟“回家乡发挥余热”的共同诺言,成了弟弟的遗言,现在虽只留下我一个人了,我也一定要去实现这个我们共同的心愿。
在1991年我到故乡母校参加校友会的时候,响应镇政府号召,在家乡搞了一个项目:“一种防治老年病延缓衰老的保健药酿”,就是我到广州总医院送给弟弟服的“千佛草”(商品名),2000年6月获国家发明专利。“千佛草”在国内外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在临床应用中进行跟踪观察,及本人和家里人连续服用十余年的亲身体会,对调理血糖、血脂、血粘度,提高自身抗病能力、延缓衰老和对疲劳综合症、产后及更年期妇女的调理方面,效果确实不错,我和老伴(76岁,战伤二等乙级残废)在这十余年来,没去医院看过病,每年体检,还没有发现主要疾病。在江北区有关领导的指点、帮助下,现已在黄夹岙建起了生产千佛草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中心,以确保产品质量。发掘祖国医学宝库,造福于人民,为家乡增光。
弟弟走的时候,上级对他的评语是:“贝新源同志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国防事业”。最近,接到《编委会》通知,我已被入选《新世纪中华国防专家人才传略》。
我虽是一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我不会贪图在家里享受安逸,今后我要继续努力,奏响生命之歌的尾声。
记忆中的童年
我是宁波江北区慈城镇(原慈谿县)人,家住北门九曲弄7号。妈妈只生我和弟弟贝新源两个,弟弟比我小一岁多,我们的幼、童年是在抗日战争中渡过的。当日本鬼子把炸弹投向孔庙,妈妈带我们到黄山池墩外婆家避难,后来我和弟弟在那里的崇本小学上了学。我刚上学就参加演出,歌剧名:“面包歌”,剧中三个人:妈妈、女儿和一个要饭的小男孩。我演女儿(小红廖)。讲的是这小女孩在三岁时爸爸在抗日游击战中牺牲,过着“一顿三餐也很难得吃个饱”的日子,妈妈正等着小红廖放学回家吃饭,这时来了要饭的小男孩,妈妈把饭分给他吃,小红廖回来,大家就一起手拉手唱了起来,共同想往着有美好的未来。
崇本小学教师中有游击队(三五支队)里的人,我们懂得是游击队员在不怕流血牺牲奋勇打击日本鬼子。记得有位陈(还是姓郑?)老师,他像父亲般的关心我,当他要回游击队去前来家访,想把我带走,当时我妈妈正患“干血痨”,外婆外公刚相继去世,我那时才六岁,妈妈舍不得我走,弟弟也不让我走,陈老师就说以后再来接我。从此,我就一直等待这位老师能来接我,但他没有再来,也听不到他的音讯。
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我奔赴到哪里,在我心里一直装着崇本小学、北城小学、慈湖中学和我的老师,是他们辛勤培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这烽火漫天血腥遍野的年代里,妈妈靠给熟人帮家务、切鞋底、缝缝补补挣些钱,靠亲戚支援,和卖掉她的嫁妆来补贴家里开支,供我们上学。在最困难的时期,她自己吃糠和买便宜的已有烂斑的红薯充饥,那时我们已经懂事,我放学回家趁肚子饿就先拿过来吃,糠用水拌着吃很难咽下去,干的嚼着吃还可以,但吃不快,妈妈过来时总会抢过去,给我盛些饭吃。弟弟小时候身体较弱,好生病,所以我们都不让他吃这些。我和弟弟除了校服,没有穿过新衣服,连鞋袜都是亲戚他们孩子穿下来的。那年代穿下来的衣服已经很旧,鞋小挤脚,疼也得穿。我们家没有钱装电灯,晚上复习功课常常用菜油灯,在一盏菜油灯下,我和弟弟做功课,妈妈在一旁缝缝补补。妈妈不会讲更多的道理,她常说要我们好好学习,要学好本领。反反复复说这样一句话:“穷人志气高,乏好呀会好”。艰难岁月中的锻炼和革命的熏陶,使我们姐弟俩逐渐成长。
当我结婚有了孩子,我的爱人是航空兵师师长,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妈妈常常对孩子们讲我和弟弟小时候的故事,并告诉他们:“要吃苦中苦,才为人上人”,孩子们听外婆的话,从小爱劳动、能吃苦、勤学习,四个孩子都大学本科毕业,现都是高职称科技工作者。孩子们至今还记住外婆那纯朴、铭心的教导。
再见了妈妈!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弟弟和我都在慈湖中学读书,我们的班主任是陈华民老师,他不但教我们书,还教我们做人。慈湖中学里革命空气很高涨,上公民课的冯明老师常在上课时先告诉我们:解放军势如破竹,已经打到哪里来了,这里“解放”的日子快要到了。有一天,学校里有人给弟弟的书包里放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那天放学回家,我们一直看到半夜,开始有了对未来“新中国”的认识和对“理想”的追求。从这以后,我们常常讨论一些问题、不断提高认识水平。
1949年5月24日慈城解放。那一天上午,从东方山那边传来解放军炮声的时候,妈妈在客堂间的八仙桌上铺了厚厚的棉被,叫弟弟和我躲到桌子底下,她去厨房做午饭了。弟弟和我真想看看解放军进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偷偷跑出去,到了杨家弄,看到国民党兵换上了黑色便衣正在拼命逃。那年,我读初中二年级,弟弟读一年级。解放军住进了我们学校(大庙)里,在杨家弄祠堂里住着伤兵,每次放学路过,我们总会投去敬慕的目光,渴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人,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同学冯小英改名冯倩亚,我改名贝一平,报考宁波鄞县县立中学高中春季班,我们俩都被录取,她去上了高中(后来也参军)。我因妈妈借不到钱,劝我读完初中拿到文凭好找个工作。1950年毕业后,是王幼于老师把我引上革命道路,我参加了土改,在助征队工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弟弟在慈中入了团。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解放了的中国》,看的第一部故事片是《赵一曼》,从那时起,我就想往着自己将来能当一名解放军里的卫生兵,能扛着抢打敌人,上战场去抢救伤员。当我把这一追求告诉弟弟时,他说:“好!把我们的一切都献给祖国”。当时我们想到:我们俩都远离妈妈,她怎么受得了?我就劝弟弟留在妈妈身边。1951年7月15日,我们姐弟俩在同一天,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踏上征途,响应抗美援朝参军。当时我刚到上海东南药物职业学校实验室当练习生,我是瞒着妈妈从上海走的。当我参军后头10天里,我每天给妈妈写一封信,请她原谅女儿不告而别。后来妈妈告诉我,弟弟向她告别那天,他转身就快步走,头也不敢回。当时和战友们唱起《共青团员之歌》:“再见了妈妈!再见了亲爱的故乡!”的时候,心里总以为这一去也许再也回不来了而热泪盈眶。
志同道合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解放,全国各大报纸都广泛宣传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这一伟大的胜利,同时宣传了涌现出的一批英雄指战员,组织上给我介绍了其中的一位:张伟良,他是这次战斗中的空中带队长机。有一次他来病房看望战友,我在该科里当医生,科主任叫我给他送去一杯茶,我送去后就出来了。以后组织上找我谈时就说明了:这是组织安排让他看一看我。那个年代是“姑娘爱英雄、追英雄”的年代,不能说没有心动,但我考虑自己才20岁,刚毕业当上医生;他虽也才26岁,但已是航空兵师副师长,怕人家说我有“虚荣心”,我当时就没有表态,他也很快去苏联莫斯科红旗指挥学院学习。一年后,他们师的政委来住院,把我叫到他病房找我谈,我就把自己心里的顾虑说了。政委的话中,有两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动:一是他在这次执行任务中,敌人的炮弹钻到他飞机的肚子下没有爆炸,这就是说他险些为解放我们浙东沿海岛屿而付出年轻的生命;二是他因十二岁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性子急,脾气暴,要找一个性格比较柔和些的。我就写信向妈妈和弟弟说了这情况,得到了妈妈和弟弟的支持,我和张伟良就开始通信。他告诉我在战争年代里,他遭受到家破人亡的灾难,奶奶被鬼子杀害,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逃难和贫病交迫中去世,他很想有个“家”。1957年7月暑假,他回国飞行时我们结了婚。1959年,他毕业回国,我们有了一个家。那时,我的弟弟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每年暑、寒假都来,他称呼张伟良为“哥哥!”,张伟良也很喜欢有这样一位弟弟,妈妈也来,我们母子母女又团聚在一起。
现在我和张伟良已是将度金婚的年份了。我们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下一代也是两男两女: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他很满意,常常说:“日本鬼子和反动派毁了我的家;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我的家又兴旺起来。真是有国才有家!”。他确实脾气不好,在他“火”上来时我不作声,是我错,我就马上改;若是他错,等他火过了,我会转个弯儿向他指出。他说:他想和我吵架也吵不起来,结果还都是他“输”;孩子们都说:妈妈对爸爸是“以柔克刚”。这主要是我们有一个牢固的婚姻基础;志同道合。同路同歌
入伍后,弟弟和我开始都是陆军战士,弟弟在舟山,我在南京教导队集训,我们约好,到部队穿上军装戴上五角星时,要赶紧照一张像寄给亲爱的妈妈。1952年我们俩第一次立功(三等功),政府敲锣打鼓把两份立功喜报送到家里,妈妈给我们写的信里,字里行间露出了异常兴奋的心情,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1956年,我们同年入党。我是解放后军队系统培养的第一批军医;弟弟是祖国军事工程学院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核物理专家,我俩毕业成绩各科都全五分,优等生,而且自习能力比较好,这是故乡母校给我们打下的基础。不幸的是他在实验时得苯中毒、放射病;后来我也得了砷中毒致残,命运安排我们都得了职业病,而且都曾濒临死亡的边缘。因为他的病与他从事的专业密切相关,而当时这个专业是绝对保密的,他对我也一直保密,我一直不知道他学、干什么专业?他更不对医生说,所以很长时期里一直误诊误治。一般医生对“砷中毒”的诊治无经验,但我在医生误诊误治的情况下自己翻书,对号入了座。因当时我小女儿正准备要考大学,小儿子正在争取进重点高中,为了让他们集中精力学习,我不能说自己的病;我爱人已调往兰州,我不想增加他的思想负担,也不告诉他。晚上疼痛难忍,我怕穿鞋走有声音,就只穿袜子,轻轻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我只想坚持到孩子们都先后上了大学。我们姐弟俩在通讯中互相鼓励,坚持工作,下决心战胜病魔。我们还约好,退休后回家乡去发挥余热
1996年5月,当我的大女儿(广州军区总院副主任医师)突来电话;舅舅患脊柱内椎管肿瘤,要到她所在的医院开刀,说那边诊断是良性。开出来的情况会及时告诉我。
开刀的那天,我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但一直没有电话,我心里一直琢磨着,越想越预感有情况,等到晚上九点多,女儿来电话:“妈妈,舅舅开刀时,我一直在手术室,局部组织发黑,情况不太好,已做病理切片,报告还没有出来。我真不想告诉你,但又不得不告诉你”。我知道自己要死了,也没掉过一点眼泪,但这时我实在忍不住而哭了。我如果真的失去了弟弟,可能我再也振作不起来。我对女儿说:“你知道舅舅在我心中的份量,我不能没有他,一定要想办法!”。
三天后,女儿来电话说:是恶性的,要做放、化疗,但舅舅体质太弱,再是切片上还看不明白属那类型?脊髓细胞都变型,没敢上。手术后十天了还没上。我就立即买飞机票,张伟良陪我到北京找最有本事的专家咨询,拿了专家的医嘱后又飞往广州。
看到弟弟躺在床上的虚弱样子,我体会了“心碎”的感受,我轻轻地抚摸着他,问他,他露出小时候那腼腆的微笑,告诉我:“现在好多了,能躺下睡了”。女儿到家后告诉我:“舅舅手术前已有好多天不能躺,不能坐,只能站着,晚上用两个靠背椅子的背撑着打盹,连在飞机上也是站过来的”。可是他一直瞒着我。
和女儿商量,经医生同意,把我带去的“千佛草”给弟弟喝。一周后情况明显好转,先后上了放、化疗,查ECT正常后出院,回原单位医院继续治疗。由于放疗剂量过量而致放射病,好转后又一次放疗,再加上当时虚假广告的影响,广告甚至做到病房;在并发白血病时,又由于诊断和治疗上的原因(他病危时不让我去,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一直守着他,大女儿去偷看病历才明白,但一切已太晚了),而于1998年4月12日清晨病故。
张伟良和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1997年12月,在大学的医院里。去前女儿告诉我不要干扰那边的治疗,不要多问、多说,否则对他的治疗反而不利。当时他刚从白血病发作中抢救过来。情况还可以,能拿着拐棍在病房的走廊里走动。我想看看病历,向医生了解一下病情,血象怎么样?在吃什么药?这些都无法问,医生也不照面,无法知道。这一次去,我想问、想说的话很多,但怕给弟弟治病带来不利,又怕弟弟思想产生对病的顾虑和猜测,故而只是鼓励他一定要战胜疾病。他看我着急的样子,总说:“放心吧!没事的”。我告诉他以后的治疗千万要慎重,不能有半点出错,他点点头。但我马上感到这话怎么能对他说,应该对医生说,但现在的医生怎能听我说这种话!分别的时候,我下楼时感到腿发软、要哭,我爱人扶住我,我强忍住眼泪回过头去,想再看弟弟一眼,但弟弟已被扶向病房,留给我一个他最后的背影。
“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国防事业!”
1999年的元旦、春节之际,我给王幼于老师写贺年卡时,我还是把弟弟的名字签上了,我不忍心让敬爱的、已经年迈的王老师在双节的日子里受到失去学生之疼。后来他知道后安慰我,说我弟弟是以身殉职。王老师一次次给我写信关怀我,鼓励我。
弟弟走了,我和弟弟“回家乡发挥余热”的共同诺言,成了弟弟的遗言,现在虽只留下我一个人了,我也一定要去实现这个我们共同的心愿。
在1991年我到故乡母校参加校友会的时候,响应镇政府号召,在家乡搞了一个项目:“一种防治老年病延缓衰老的保健药酿”,就是我到广州总医院送给弟弟服的“千佛草”(商品名),2000年6月获国家发明专利。“千佛草”在国内外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在临床应用中进行跟踪观察,及本人和家里人连续服用十余年的亲身体会,对调理血糖、血脂、血粘度,提高自身抗病能力、延缓衰老和对疲劳综合症、产后及更年期妇女的调理方面,效果确实不错,我和老伴(76岁,战伤二等乙级残废)在这十余年来,没去医院看过病,每年体检,还没有发现主要疾病。在江北区有关领导的指点、帮助下,现已在黄夹岙建起了生产千佛草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中心,以确保产品质量。发掘祖国医学宝库,造福于人民,为家乡增光。
弟弟走的时候,上级对他的评语是:“贝新源同志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国防事业”。最近,接到《编委会》通知,我已被入选《新世纪中华国防专家人才传略》。
我虽是一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我不会贪图在家里享受安逸,今后我要继续努力,奏响生命之歌的尾声。
相关地名
江北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