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
| 内容出处: |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图书 |
| 唯一号: | 112520020220002349 |
| 颗粒名称: | 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 |
| 分类号: | K827 |
| 页数: | 6 |
| 页码: | 558-563 |
| 摘要: | 本文冯定与毛泽东的二三事是2011年9月在北京天外天烤鸭店由冯贝叶口述展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情怀。 |
| 关键词: | 慈城镇 冯定 毛泽东 |
内容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冯定作为党的宣传干部,自然熟知并了解毛泽东,但他没有去过延安,与毛泽东没有直接来往。而以父亲的职位,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父亲,更谈不上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也就有了之后的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
1952年1月,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揭发出的资本家“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行为)问题也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国家财产被盗和干部受腐蚀等问题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以至非解决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于是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三反”和“五反”两个斗争就会合在一起了。这一年,中国仍处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当中,那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应当还有所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父亲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此很感兴趣。
他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认为:只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而没有看到他们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还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是片面的,在实践中立即消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是错误的、有害的。父亲所在的华东局由于实际领导运动,显然也看到了如再不解决这一问题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父亲把学习体会写成文章后,华东局一方面在内部组织人对这文章进行推敲和修改,另一方面向毛泽东报送了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
据母亲回忆,华东局组织修改父亲的文章时,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提出了几处修改的观点,而父亲不同意修改意见,但这年3月24日《解放日报》[1]发表时仍按张春桥的观点作了修改。父亲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据说毛泽东称赞了父亲的文章,同时批评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2]据此,陆定一同志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在检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在检讨报告上还为《学习》杂志代写了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3]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父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在预印的小样上亲笔做了多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修改是文章的题目[4]。同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此文。父母亲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与《学习》杂志上的文章进行对照发现,《学习》杂志修改的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修改的那几处,也就是发表的这篇文章与父亲原文观点基本相符,这是颇具戏剧性的情况。而当时的父母就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父亲的文章。现在这已为于光远同志在其回忆文章中证实。
这年下半年,父亲从上海华东局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一分院第一副院长。
4年后,父亲被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年,父亲两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是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父亲在日记中记载:
二月三日,雾霭,阴沉。早起。上午出席小组会,之后回家午餐,想好好地睡一下,但仍没有睡好。下午出席大会;之后至怀仁堂赴宴。宴前,先晤了陈云同志,他还记得1926年间在宝山路和我开过支部干事会的事;不久毛主席等来了,和宾客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看我一下,问我现在哪里工作;刘少奇同志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同志说他读过我的文章;都使我铭感不忘!宴会直至十一时余才散;回院就寝,已很晚了。
午后二时,去西苑大旅社等候开重要会议;三时余,接通知去怀仁堂;四时余,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等十来人出来,与科学工作者们合摄一像;我被预先告知站在毛主席背后左侧,他就坐前和我及其二三人握了手。
这是父亲在科学院讨论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会议期间见到毛泽东的情景记录。
这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马列学院一分院,据自传:当时,父亲有几个去向,一是任第二届赴越南整党顾问团团长,一是去郑州任新成立的郑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此外中共中央编译局也希望父亲去他们那工作。但由于情况多变,父亲的工作一直没定而没有上任。直到第二年1月22日,父亲接到中宣部张际春[1]的紧急电话,电话告诉父亲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北京大学教授马列主义。据说,去北大当教授是毛泽东的提议,而且让父亲什么职务都不要挂,只当一名教授,旨在加强党对北大学术方面的马列主义领导,由此父亲成了北大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教授。[2]一星期后,父亲到北大报到。尽管没有实职,父亲却经常参加校党委书记的碰头会,后再由校党委书记提名,父亲任校党委副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北大党委被撤销为止。
父亲去北大时,冯友兰[1]先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父亲住在燕南园,这是北大最好的教授宿舍区,十余幢松墙环绕的独门独院的西式小洋房,居住着全校多位一、二级教授,多是学界泰斗,吴文藻与冰心夫妇,还有雷洁琼、马寅初等,可以说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知名学者都在此住过。北大的燕南园后被称为精神圣地。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清华园迁到燕南园57号的。父亲的家是55号。55号与57号小洋房从地理方位上看呈对角而立,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小洋房的主人,两位冯教授因时代的特殊背景也有着某种“对立”的关系。不是吗?毛泽东提名调父亲到北京大学。毛泽东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争鸣,冯友兰可以讲唯心主义,冯定讲唯物主义,同冯友兰唱对台戏。而那时的北大校园似乎有一种具有调侃意味的说法:学唯物主义找冯定,学唯心主义找冯友兰,学帝王将相找翦伯赞。时至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2]
其实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文化部、文联等文艺界,继文艺界被点名批判之后,这股批判风又扫向了理论界,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哪还有出路可言呢?一年后,父亲遭到了点名批判。首次批判文章的题目是“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3]。众所周知,《红旗》杂志是党中央办的理论刊物,此文一登也就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对父亲开展了时间长达几个月的批判。之后,北大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对冯定同志著作的批评。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毛主席对冯定著作的批评。[1]
周培源怎么会知道毛泽东批评父亲著作的一席话呢?这年8月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参会科学家后,约于光远、周培源谈话时,毛泽东对周培源说:“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2]从此以后,对父亲的批判也就升级了……当时曾有人劝父亲:“做个检讨算了。”但父亲却不肯屈服,还说:“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3]
不做检讨英雄,就只能顶着“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更有意思的是,原本唱对台戏的两位冯教授,对台戏没唱成却双双被推上批判台,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批判冯定、冯友兰联络站”,后又被关在同一牛棚。有一次,冯友兰问父亲:“过去不是一直说‘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怎么现在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关到这里来了?对此我不能理解。”你猜,父亲怎么说?他说:“就像现在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也不能理解。”[4]燕园没摆成的擂台却在牛棚“如愿”了,不过那是两人私设的擂台舌战,还是被关在牛棚里的一位哲学系学生听到而公布于众的。
回顾历史,1963—1964年的“这场在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的批判,是受到毛泽东肯定和支持的,也是他‘反修防修的一个重大步骤。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野心家、阴谋家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根据薄一波同志的回忆录,批判父亲是由康生首先决定的,并向毛泽东送了不少材料”[5]。现根据“文革”后发表的文献来看,这些批判,毛泽东事前并不清楚,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曾多次对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林彪讲话稿做过批示、修改。一月后,此稿印发到县团级。其中第10页的“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画去了“冯定”的名字,并批道“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1]。这一批示在当年是绝密的,自然不能保佑父亲免于“文革”的灾难。就在如今,不是父亲的亲朋好友,也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些。
当年,自父亲被公开点名批判之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家人心里的委屈和难受更是难以言表,但一家人还祈盼父亲的问题总会被解决。然而,这仅仅是愿望,而且是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伊始,父亲被扣上“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批斗加剧……1975年,父亲因患胆结石病危,北大党委才宣布父亲解放。可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及“批邓”运动,这一“解放”决定遂又作废……又折腾了一年,至1977年父亲才获新生。
自被公开点名批判以来的十余年间,父亲长期处于被批斗、隔离审查、与世隔绝的状态,身心受到摧残,父亲晚年的脑软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如今,父亲、母亲俱已去世,再回首“文革”历史,连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不能免于这场灾难,而且全国亿万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还有些是家破人亡,对照此,我父母的遭遇,似乎算不得什么了,毕竟父母双双度过了严寒。在严寒,族叔公儿子冯彬曾来我家看望父母,不仅带一些可口的食品,且与父亲道故论道,还在精神上安慰父亲,父亲曾说:“与冯彬的交谈是我活下去的支持力。”
1952年1月,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揭发出的资本家“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行为)问题也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国家财产被盗和干部受腐蚀等问题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以至非解决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于是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三反”和“五反”两个斗争就会合在一起了。这一年,中国仍处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当中,那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应当还有所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父亲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此很感兴趣。
他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认为:只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而没有看到他们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还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是片面的,在实践中立即消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是错误的、有害的。父亲所在的华东局由于实际领导运动,显然也看到了如再不解决这一问题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父亲把学习体会写成文章后,华东局一方面在内部组织人对这文章进行推敲和修改,另一方面向毛泽东报送了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
据母亲回忆,华东局组织修改父亲的文章时,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提出了几处修改的观点,而父亲不同意修改意见,但这年3月24日《解放日报》[1]发表时仍按张春桥的观点作了修改。父亲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据说毛泽东称赞了父亲的文章,同时批评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2]据此,陆定一同志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在检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在检讨报告上还为《学习》杂志代写了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3]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父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在预印的小样上亲笔做了多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修改是文章的题目[4]。同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此文。父母亲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与《学习》杂志上的文章进行对照发现,《学习》杂志修改的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修改的那几处,也就是发表的这篇文章与父亲原文观点基本相符,这是颇具戏剧性的情况。而当时的父母就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父亲的文章。现在这已为于光远同志在其回忆文章中证实。
这年下半年,父亲从上海华东局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一分院第一副院长。
4年后,父亲被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年,父亲两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是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父亲在日记中记载:
二月三日,雾霭,阴沉。早起。上午出席小组会,之后回家午餐,想好好地睡一下,但仍没有睡好。下午出席大会;之后至怀仁堂赴宴。宴前,先晤了陈云同志,他还记得1926年间在宝山路和我开过支部干事会的事;不久毛主席等来了,和宾客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看我一下,问我现在哪里工作;刘少奇同志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同志说他读过我的文章;都使我铭感不忘!宴会直至十一时余才散;回院就寝,已很晚了。
午后二时,去西苑大旅社等候开重要会议;三时余,接通知去怀仁堂;四时余,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等十来人出来,与科学工作者们合摄一像;我被预先告知站在毛主席背后左侧,他就坐前和我及其二三人握了手。
这是父亲在科学院讨论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会议期间见到毛泽东的情景记录。
这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马列学院一分院,据自传:当时,父亲有几个去向,一是任第二届赴越南整党顾问团团长,一是去郑州任新成立的郑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此外中共中央编译局也希望父亲去他们那工作。但由于情况多变,父亲的工作一直没定而没有上任。直到第二年1月22日,父亲接到中宣部张际春[1]的紧急电话,电话告诉父亲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北京大学教授马列主义。据说,去北大当教授是毛泽东的提议,而且让父亲什么职务都不要挂,只当一名教授,旨在加强党对北大学术方面的马列主义领导,由此父亲成了北大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教授。[2]一星期后,父亲到北大报到。尽管没有实职,父亲却经常参加校党委书记的碰头会,后再由校党委书记提名,父亲任校党委副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北大党委被撤销为止。
父亲去北大时,冯友兰[1]先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父亲住在燕南园,这是北大最好的教授宿舍区,十余幢松墙环绕的独门独院的西式小洋房,居住着全校多位一、二级教授,多是学界泰斗,吴文藻与冰心夫妇,还有雷洁琼、马寅初等,可以说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知名学者都在此住过。北大的燕南园后被称为精神圣地。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清华园迁到燕南园57号的。父亲的家是55号。55号与57号小洋房从地理方位上看呈对角而立,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小洋房的主人,两位冯教授因时代的特殊背景也有着某种“对立”的关系。不是吗?毛泽东提名调父亲到北京大学。毛泽东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争鸣,冯友兰可以讲唯心主义,冯定讲唯物主义,同冯友兰唱对台戏。而那时的北大校园似乎有一种具有调侃意味的说法:学唯物主义找冯定,学唯心主义找冯友兰,学帝王将相找翦伯赞。时至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2]
其实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文化部、文联等文艺界,继文艺界被点名批判之后,这股批判风又扫向了理论界,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哪还有出路可言呢?一年后,父亲遭到了点名批判。首次批判文章的题目是“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3]。众所周知,《红旗》杂志是党中央办的理论刊物,此文一登也就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对父亲开展了时间长达几个月的批判。之后,北大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对冯定同志著作的批评。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毛主席对冯定著作的批评。[1]
周培源怎么会知道毛泽东批评父亲著作的一席话呢?这年8月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参会科学家后,约于光远、周培源谈话时,毛泽东对周培源说:“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2]从此以后,对父亲的批判也就升级了……当时曾有人劝父亲:“做个检讨算了。”但父亲却不肯屈服,还说:“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3]
不做检讨英雄,就只能顶着“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更有意思的是,原本唱对台戏的两位冯教授,对台戏没唱成却双双被推上批判台,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批判冯定、冯友兰联络站”,后又被关在同一牛棚。有一次,冯友兰问父亲:“过去不是一直说‘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怎么现在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关到这里来了?对此我不能理解。”你猜,父亲怎么说?他说:“就像现在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也不能理解。”[4]燕园没摆成的擂台却在牛棚“如愿”了,不过那是两人私设的擂台舌战,还是被关在牛棚里的一位哲学系学生听到而公布于众的。
回顾历史,1963—1964年的“这场在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的批判,是受到毛泽东肯定和支持的,也是他‘反修防修的一个重大步骤。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野心家、阴谋家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根据薄一波同志的回忆录,批判父亲是由康生首先决定的,并向毛泽东送了不少材料”[5]。现根据“文革”后发表的文献来看,这些批判,毛泽东事前并不清楚,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曾多次对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林彪讲话稿做过批示、修改。一月后,此稿印发到县团级。其中第10页的“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画去了“冯定”的名字,并批道“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1]。这一批示在当年是绝密的,自然不能保佑父亲免于“文革”的灾难。就在如今,不是父亲的亲朋好友,也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些。
当年,自父亲被公开点名批判之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家人心里的委屈和难受更是难以言表,但一家人还祈盼父亲的问题总会被解决。然而,这仅仅是愿望,而且是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伊始,父亲被扣上“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批斗加剧……1975年,父亲因患胆结石病危,北大党委才宣布父亲解放。可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及“批邓”运动,这一“解放”决定遂又作废……又折腾了一年,至1977年父亲才获新生。
自被公开点名批判以来的十余年间,父亲长期处于被批斗、隔离审查、与世隔绝的状态,身心受到摧残,父亲晚年的脑软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如今,父亲、母亲俱已去世,再回首“文革”历史,连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不能免于这场灾难,而且全国亿万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还有些是家破人亡,对照此,我父母的遭遇,似乎算不得什么了,毕竟父母双双度过了严寒。在严寒,族叔公儿子冯彬曾来我家看望父母,不仅带一些可口的食品,且与父亲道故论道,还在精神上安慰父亲,父亲曾说:“与冯彬的交谈是我活下去的支持力。”
附注
[1]《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解放日报》,1952年3月24日)
[2]详见于光远同志回忆录(《百年潮》2000年第10期)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144—148页;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0页
[4]详见冯贝叶、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百年潮》2000年第6期),或见《毛泽东剪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1]张际春(1900—1968),字晓岚,湖南宜章人,早年结业于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后参加井冈山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西南局组织部长兼纪检委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等职
[2]谢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一创者》,《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1页
[1]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2]陈薇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37页
[3]《红旗》杂志,第十七、十八期合刊,1964年9月23日
[1]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2]“文革”后,有些人的回忆中都提到毛泽东讲话中有这句话
[3]宗璞:《霞落燕园》,《中国作家》1986年第四期
[4]张义德:《怀念我的老师冯定教授》,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34—135页
[5]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37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57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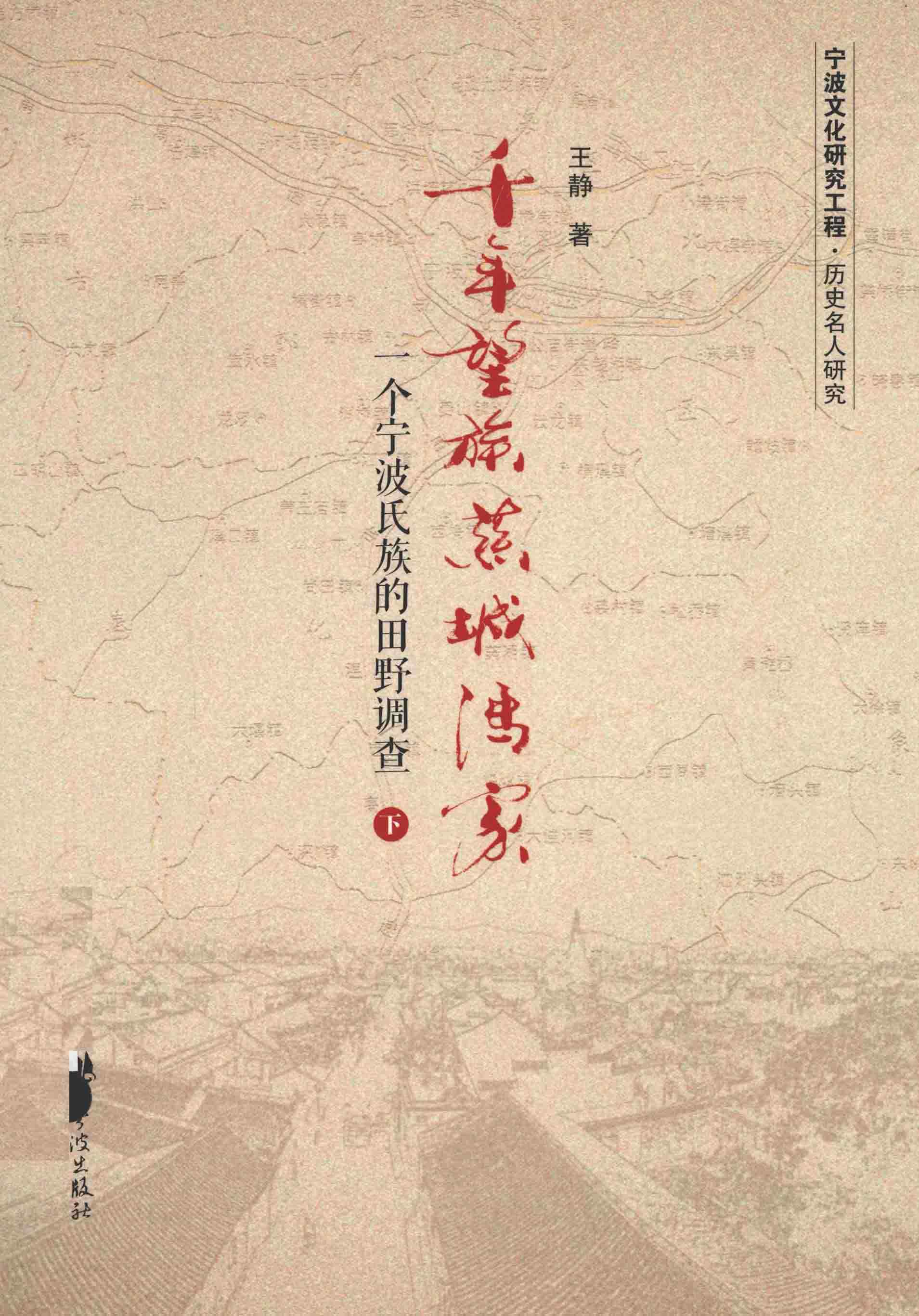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本书是以慈城冯氏众子姓及家族文化为对象,以慈城及海内外的家族文化为参照说明,以历史文献及口述史为依据,结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民俗学,对慈城冯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认为慈城冯氏以寻根、联宗等形式营造家族的精神家园,以凝聚众子姓之心是千年望族的内核,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得以绵延千年不绝的家族秘诀。
阅读
相关地名
慈城镇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