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房、客厅和我的人生
| 内容出处: |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图书 |
| 唯一号: | 112520020220002345 |
| 颗粒名称: | 父亲的书房、客厅和我的人生 |
| 分类号: | K820.9 |
| 页数: | 9 |
| 页码: | 536-544 |
| 摘要: | 本文冯昭奎父亲的书房、客厅和冯昭奎的人生是2014年2月在北京宁波宾由冯昭奎、冯昭珏、冯昭逢口述展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情怀。 |
| 关键词: | 慈城镇 书房 客厅 |
内容
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是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内的一个院子。当时我的大伯伯都良一家也住在那条胡同,离我家不远,两家来来往往,宛如一家人。
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曾是外交部宿舍,是由四个院落组成的大杂院,先后住过几十户外交部的司局级干部。我家位于最里面的院子,是个两层小楼,我家住一层楼。二层楼有一个阳台,据说这院的原主人是梅兰芳,早先(20世纪20年代)梅大师在这里接待过瑞典皇室贵宾,又在二楼的阳台练过嗓子。
乔冠华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前曾住在小楼的二层。我家搬进去时,二楼住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刚搬走。与小楼最近的一套平房,房客先后是黄华大使与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老师。当年的我,总觉得我家的邻居“很不简单”。孟用潜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曾任刘少奇主席的秘书;何老师参加革命比孟晚了十年,也在张闻天手下工作过,当时的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调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成为邻居何老师的“部下”。
我家进门是个不小的门厅,里面有四间房,父亲的书房兼父母的卧室,客厅兼招待客人的“宴会厅”,平时吃饭的房间和我们姐弟几人住的小房间;后面是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令我感到晦暗。
书房朝阳,总是充满阳光,暖意浓浓。靠窗是父亲的那张大书桌,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文件,其中有每天叠加的新华社
《参考资料》,分上午版、下午版,好像有时还有中午版,两三种版本的厚度都不逊于杂志。我读高中乃至进大学,每个周末回家,总喜欢进父亲的书房转悠,翻翻这看看那,尤其感兴趣的是那摞《参考资料》,而父亲却不想让我看,总说:“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
书桌的后面是几个大书柜,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图书”占了相当大的空间。当时的出版社除出版《世界知识》等三种国际问题杂志外,还出版有关国际问题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供党政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图书”,这些图书的扉页印有“本书供部级以上干部阅读”或“本书供局级以上干部阅读”的文字。我有时忍不住“偷读”这些书,不经意间“享受”了“局级”乃至“部级”以上干部的待遇,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有点诚惶诚恐。
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即便是听报告或开会做记录,也保持着工整的字迹。记得读过他做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笔记,我不知这笔记是否是他聆听毛泽东主席讲话的记录,觉得毛主席讲话好生动啊。不过,等到该文公开出版,才发现笔记的内容与出版物有差异。
父亲的书房没什么摆设。墙上仅挂着一块匾额,内容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诗,那是鲁迅先生为父亲题写的。茶几上有支克里姆林宫形状的小室温计,那是父亲访苏归来带回的。
紧连书房的客厅经常宾客满座,而进父亲书房的人却不多,常见的有两位,一位是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的姚臻叔叔,一位是我的堂兄冯彬。姚叔叔曾是父亲加入地下党后的单线领导之一,时主管国际宣传,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又是“独此一家”的权威性国际问题出版社。姚叔叔来我家,虽有叙旧,更多的是与父亲谈工作。记得1958年春,姚叔叔来得较频繁,好像是因为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不久,《世界知识》第12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此文后被《人民日报》转载,才知姚叔叔与父亲忙于讲话辑录稿的整理、发表。冯彬当时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经常向父亲讨教,父亲也乐意跟他聊。叔侄俩都爱抽烟,他俩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海阔天空地神侃。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暖融融,靠在一旁的我常常听得入神,全然不在乎满屋的烟雾。
不管父亲在不在家,我家常有客人,周末的客厅像“宴会厅”,而每到月底,母亲况密文就会对父亲说“钱用完了”,“清苦几天”,待到工资到手,又照旧宴请宾客,乐此不疲。可悲的是父母亲的热情好客竟被造反派批判是“大吃大喝”,当然这是后话。“主雅客来勤”,父亲常常在客厅高谈他的国际形势见解,而母亲总是张罗着用好酒好菜招待来客,赵朴初伯伯的“每忆高谈惊四筵”的诗句就是指当年我家客厅的情景。有一次,清华大学请父亲作国际形势报告,我和同学们排队进入清华大礼堂,迟到的学生只能在后面站着听,或者在阶梯教室听拉线广播。坐在球顶建筑物礼堂的我,就有一种幸运感,这样吸引全校师生的报告,我却可以在家里经常听到。
我家的客人除亲戚外,来得较多的是父亲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事,其中几位老同事是抗战胜利后与父亲在上海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共用一张旧写字台各司其职的人,他们是编辑、出版、发行《世界知识》的骨干人物。
另外一拨客人是民进的同志与朋友。父亲与赵朴初、雷洁琼早在1943年就是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讨论时局的“星期二聚餐会”成员。三年后,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前后,父亲与大伯(冯都良)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的住处接待或掩护沙文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冯定、孙冶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活动。
那时,我家在上海文安坊5号(现襄阳南路附近)三楼,二楼住的孙冶芳一家(当时我不知道我家是掩护孙),每天出门前,母亲总千叮万嘱我们在外面不要乱讲话,就怕父亲出意外,然而父亲还是出事了。大约我4岁的一天,日本宪兵闯入我家,我被杀气腾腾的场面吓得躲开,后从姐姐、哥哥的讲述中才知,是日本宪兵队侦查父亲工作的大用出版社,因抓不到进步作家楼适夷[1],就抓捕了父亲。父亲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不肯说出楼的去向,后由周建人(鲁迅的弟弟)及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对此,楼适夷后吟《忆仲足》一诗:
最忆储能冯仲足,照人肝胆明如月。
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做了多年民主党派的工作,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秘书长、民进北京市主任。赵朴初、雷洁琼、徐伯昕、杨东莼等民进会员,都是父亲的老朋友,赵伯伯被称为父亲的“铁哥们”,雷阿姨被称为父亲的“铁姐们”。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父亲千方百计地将心直口快、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雷阿姨“保”了下来。
可在“文化大革命”,身患癌症的父亲亦难逃一劫。尤其是1966年,肠癌并发肝癌的父亲已卧床不起,此刻的书房成了他的“病房”,来抄家的造反派在父亲的病床两头贴了“坦白交代,抗拒从严!”,“打倒某某某”,“打倒刘邓司令部在新闻战线的黑干将”等标语。等造反派走出家门,气愤的姐姐好提撕下一张标语,而父亲却让姐姐重新贴上。当时院子里还有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主要内容一是要交代与“修正主义分子”冯定的关系,一是批判父亲的“大吃大喝”……而父亲让我们要正确对待毛主席发动的群众运动。可当造反派诬蔑《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之时,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一字一句抗议:“说《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的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想想也是,父亲从1933年开始他的写作[1],第二年,追随胡愈之先生,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世界知识》的宗旨是为苦闷、彷徨的中国青年开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由此,父亲从作者、编辑到总编,为《世界知识》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而如今《世界知识》却被诬蔑为“卖国杂志”,父亲真的很伤心,很痛心。
由于心痛,由于病痛,往日被孙辈昵称为胖爷爷的父亲那宽厚、乐观的笑容不见了,书房的病床上只有叹息,只有呻吟……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一晚,我从外面回家,父亲看到我,眼睛顿时一亮,说:“阿平,你给我拉一段《魂断蓝桥》[2听听。”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自发现肠癌到上海做手术后,已有四年,住过好几次院,虽说健康状况一次比一次差,但父亲从没有直接表达过对家的依恋,对亲人的依恋。这次又将去住院,再次离开家,离开书房,父亲想借助这一乐曲来表达自己的心愿。而《魂断蓝桥》时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如果被大院的造反派听到,将又是一场灾难。然而,我们已不顾这些,为了父亲的心愿,一旁护理的母亲拿出一条厚窗帘,把它挂了起来;好提出门去院子看外面的动静;我拿出积满灰尘的小提琴,拂去浮尘,擦松香,调准弦音……当旋律从我的手指和弓弦之间滑出而回荡在父亲的书房之时,我的心灵如醉酒般地颤动起来,表达出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离别之情,我们彼此是那么的依恋,那么的不舍,又是那么的无可奈何。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们仨泪流满面,只见父亲闭上了眼睛,脸上有了瞬间的安宁。我喜欢音乐,父亲曾经多次给我音乐会的票子;父亲和大伯常听我拉的《茉莉花》。现在想想也是欣慰,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在父亲最后的书房,我的喜好给病痛与心痛的父亲带去瞬间安宁。
1966年的夏天,我工作的七机部二院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将抽调力量去贵州,我是其中一员。当时的领导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三线’一天不建设好,他就睡不着觉”,为了让毛主席能睡好觉,我们一批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坚决响应号召参加“三线”建设。我去北京医院与病重不起的父亲道别,说我要去参加“三线”建设,挺远的,在贵州遵义。父亲平静地说,“年轻人么,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
与父亲告别后,我随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军来到贵阳,在远离北京3000多公里的“064”指挥部,设计隐身山洞的半导体车间。其间,因惦记父亲的病情与同事谈起,一同事告诉我一好消息——上海一教授发明了治疗肝癌的新药。可还没来得及写信联系,这年11月30日,父亲带着双重的痛苦——病痛与心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书房,离开了伴随三十多的《世界知识》。当3000多公里之外的我接到“父病危”电报之时,竟还想着去上海替父亲买新药呢。到上海听一亲戚说出“您不用去”四个字,我才明白,那天与父亲在北京医院相见竟成我们父子的永别,“年轻人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是父亲对我的最后遗嘱。
从上海回到北京,父亲的遗体已火化。时是“文革”,父亲被批,而外交部的一些领导,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些同事还是“悄悄地”与父亲告别。13年后的初春,外交部为冯宾符、吴景崧、梁纯夫三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黄华、胡愈之夫妇、乔石夫妇、周建人、赵朴初、雷洁琼、孙冶方夫妇、宦鄉、于光远、冯定夫妇、孙起孟、萨空了、冯亦代、刘贯一、徐伯昕、陈翰伯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全体同志近300人出席了追悼会,1979年3月2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消息。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停刊被诬蔑的《世界知识》同年复刊,与读者再见面。还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如今的我子承父业,从工程师转行为日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员。
我觉得我的转行与父亲的DNA有密切关系,我家在无量大人胡同的父亲的书房是我学生时代的“第二课堂”,我从中感受真理之美,感受写作之趣。我觉得我的转行不仅是父亲职业的传承,而且是父亲意志的传承。我学的是俄语,大学毕业参加军垦农场劳动时,我从父亲当年自学英语受到启发,悄悄自学英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外语被视为崇洋媚外,我就搞到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每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从英文反推中文意思(因为中文语录天天读,大都记得住),记了很多英文词汇。回想当年自学英语的环境,真是不可思议,但我常以父亲自学英语、翻译《西行漫记》的那种精神自勉自励。正是父亲的榜样,1978年人事部组织的科技人员英语水平考试,我获得笔试67分、口试5﹣的成绩。那时考70分的科技人员可以不参加培训就可出国,我的笔试成绩虽差三分,但由于口试接近最高分,也被列入免于培训之列,于1979年选送到日本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为此我又自学了日语。
如果说自学外语是以父亲为榜样,那么喜欢写作也与父亲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从日本回国后,我将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写成科普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其中《软件的崛起》一文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并与我约谈,希望我去国家科委工作,当时我已达到了可读懂俄文、英文、日文的专业技术文章的水平,又有半导体和电子学的专业基础,而且最向往的工作就是能够安安静静地做些资料翻译工作,正好国家专利局招人,我便到专利局接待大厅填了应聘的表格,等了一个多月不见回音。世间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一次《世界知识》的作者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何倩,他建议我调到日本所,说到日本所也可以做喜欢的资料工作,于是我写信给日本所人事处,想不到一周后就有了回音,又过了一周就搞定了调动手续。此后,国家专利局也发来商调函,表示“热烈欢迎”,但为时已晚矣。
回想起来,真是有缘,由于父亲奉献了大半生精力的《世界知识》的“牵线”作用,我成了老邻居何方老师的部下。这一调动被同事戏称为“变身”,而我说是“半路出家”。人到中年的我,专门从事日本研究,我克服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不足等困难,靠着勤能补拙、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和行动,主要做了三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众所周知,转行到陌生的领域,总得找一条进入此领域的路径,我利用我所学专业和原工作的特点,将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作为第一个选题,撰写了一份题为“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的报告,发表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第二年就被评选为社科院“优秀报告”。去日本考察后,又撰写了“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的考察报告,被中央有关部门选作“县团级文件”发往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我的研究视野扩大到“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写下了《日本的新技术革命》、《日本经济的活力》、《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改革》等。其中《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分类出版了《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日本的零售业》、《中日流通业比较》、《AComparisonBetweenDistributioninChinaandJapan》四本专著,之后又出版了《走向技术立国之路》、《日本经济》等,迄今我已有12本个人著作。
在对日本的研究过程中,我自然而然想到了中日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日关系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路,来研究中日关系这一课题,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先后出版了《对话:北京与东京》、《日本:战略的贫困》、《中日关系报告》等书和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内部报告,这些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我退休后,被邀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日研究所所长(其实只是挂个名),2004年10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我接到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个重要会议,要我回京后马上向一位领导同志“报到”。我回北京后不久,就接到这位领导同志的电话,通知我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并让我告知其车牌号。我说,我是退休的普通研究人员,没有专车,只好乘出租车。对方说:“那我们就派人在中南海门口接你吧。”待到开会那天,我来到中南海门口,说明来意,警卫很快放行,我没等人来接,“趁机”在这个“最安静的公园”散了步。
进入会场,才知道是胡锦涛主席召集一次小型座谈会。胡主席还没有到,先进入会场的人打算到会场门口迎接,却不料胡主席身穿夹克,脚穿布鞋,走路很轻,已经进入会场。他绕椭圆形会议桌转了半圈,与发言者一一握手,然后在会议主持人旁边落座。我看与会者个个都身份不凡,暗嘱自己不要主动发言。没想到在第一位发言者讲完之后,胡主席就点了我的名:“冯昭奎,你讲讲吧。”按照会前有人特意给我打的招呼,我的发言用了40多分钟时间,比其他与会者的发言时间多出一倍。
因为写写写,我和我的文章引起了关注,既受到批评和指责又得到肯定和赞扬,其实我只是个书虫,只想努力说一些实话,为人做事都很呆板。1990年前后,院里要我当副所长,我拒绝了,但仍然被以一种“没得商量”的方式接到任命,我硬着头皮当了一届就主动辞职。2011年,因为在公共汽车站偶遇其他所的老朋友,告诉我院里正在评选学部委员,我就填了一份表格,出乎意料地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反正从工程师改行做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此后遇到的种种事情,都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也可以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我的祖父是旧时代的士大夫,父亲是新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我是他们的儿孙,继承了他们的基因,秉承了他们的性格。有意思的是,年过古稀的我至今仍以研究、写作国际问题为乐,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除了有时在书房里听听音乐,没有什么嗜好,每天就坐在书房里,不是看与研,就是思与写,这一切正是缘于父亲对我的启蒙、培养、熏陶。
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曾是外交部宿舍,是由四个院落组成的大杂院,先后住过几十户外交部的司局级干部。我家位于最里面的院子,是个两层小楼,我家住一层楼。二层楼有一个阳台,据说这院的原主人是梅兰芳,早先(20世纪20年代)梅大师在这里接待过瑞典皇室贵宾,又在二楼的阳台练过嗓子。
乔冠华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前曾住在小楼的二层。我家搬进去时,二楼住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刚搬走。与小楼最近的一套平房,房客先后是黄华大使与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老师。当年的我,总觉得我家的邻居“很不简单”。孟用潜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曾任刘少奇主席的秘书;何老师参加革命比孟晚了十年,也在张闻天手下工作过,当时的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调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成为邻居何老师的“部下”。
我家进门是个不小的门厅,里面有四间房,父亲的书房兼父母的卧室,客厅兼招待客人的“宴会厅”,平时吃饭的房间和我们姐弟几人住的小房间;后面是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令我感到晦暗。
书房朝阳,总是充满阳光,暖意浓浓。靠窗是父亲的那张大书桌,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文件,其中有每天叠加的新华社
《参考资料》,分上午版、下午版,好像有时还有中午版,两三种版本的厚度都不逊于杂志。我读高中乃至进大学,每个周末回家,总喜欢进父亲的书房转悠,翻翻这看看那,尤其感兴趣的是那摞《参考资料》,而父亲却不想让我看,总说:“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
书桌的后面是几个大书柜,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图书”占了相当大的空间。当时的出版社除出版《世界知识》等三种国际问题杂志外,还出版有关国际问题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供党政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图书”,这些图书的扉页印有“本书供部级以上干部阅读”或“本书供局级以上干部阅读”的文字。我有时忍不住“偷读”这些书,不经意间“享受”了“局级”乃至“部级”以上干部的待遇,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有点诚惶诚恐。
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即便是听报告或开会做记录,也保持着工整的字迹。记得读过他做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笔记,我不知这笔记是否是他聆听毛泽东主席讲话的记录,觉得毛主席讲话好生动啊。不过,等到该文公开出版,才发现笔记的内容与出版物有差异。
父亲的书房没什么摆设。墙上仅挂着一块匾额,内容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诗,那是鲁迅先生为父亲题写的。茶几上有支克里姆林宫形状的小室温计,那是父亲访苏归来带回的。
紧连书房的客厅经常宾客满座,而进父亲书房的人却不多,常见的有两位,一位是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的姚臻叔叔,一位是我的堂兄冯彬。姚叔叔曾是父亲加入地下党后的单线领导之一,时主管国际宣传,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又是“独此一家”的权威性国际问题出版社。姚叔叔来我家,虽有叙旧,更多的是与父亲谈工作。记得1958年春,姚叔叔来得较频繁,好像是因为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不久,《世界知识》第12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此文后被《人民日报》转载,才知姚叔叔与父亲忙于讲话辑录稿的整理、发表。冯彬当时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经常向父亲讨教,父亲也乐意跟他聊。叔侄俩都爱抽烟,他俩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海阔天空地神侃。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暖融融,靠在一旁的我常常听得入神,全然不在乎满屋的烟雾。
不管父亲在不在家,我家常有客人,周末的客厅像“宴会厅”,而每到月底,母亲况密文就会对父亲说“钱用完了”,“清苦几天”,待到工资到手,又照旧宴请宾客,乐此不疲。可悲的是父母亲的热情好客竟被造反派批判是“大吃大喝”,当然这是后话。“主雅客来勤”,父亲常常在客厅高谈他的国际形势见解,而母亲总是张罗着用好酒好菜招待来客,赵朴初伯伯的“每忆高谈惊四筵”的诗句就是指当年我家客厅的情景。有一次,清华大学请父亲作国际形势报告,我和同学们排队进入清华大礼堂,迟到的学生只能在后面站着听,或者在阶梯教室听拉线广播。坐在球顶建筑物礼堂的我,就有一种幸运感,这样吸引全校师生的报告,我却可以在家里经常听到。
我家的客人除亲戚外,来得较多的是父亲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事,其中几位老同事是抗战胜利后与父亲在上海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共用一张旧写字台各司其职的人,他们是编辑、出版、发行《世界知识》的骨干人物。
另外一拨客人是民进的同志与朋友。父亲与赵朴初、雷洁琼早在1943年就是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讨论时局的“星期二聚餐会”成员。三年后,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前后,父亲与大伯(冯都良)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的住处接待或掩护沙文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冯定、孙冶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活动。
那时,我家在上海文安坊5号(现襄阳南路附近)三楼,二楼住的孙冶芳一家(当时我不知道我家是掩护孙),每天出门前,母亲总千叮万嘱我们在外面不要乱讲话,就怕父亲出意外,然而父亲还是出事了。大约我4岁的一天,日本宪兵闯入我家,我被杀气腾腾的场面吓得躲开,后从姐姐、哥哥的讲述中才知,是日本宪兵队侦查父亲工作的大用出版社,因抓不到进步作家楼适夷[1],就抓捕了父亲。父亲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不肯说出楼的去向,后由周建人(鲁迅的弟弟)及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对此,楼适夷后吟《忆仲足》一诗:
最忆储能冯仲足,照人肝胆明如月。
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做了多年民主党派的工作,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秘书长、民进北京市主任。赵朴初、雷洁琼、徐伯昕、杨东莼等民进会员,都是父亲的老朋友,赵伯伯被称为父亲的“铁哥们”,雷阿姨被称为父亲的“铁姐们”。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父亲千方百计地将心直口快、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雷阿姨“保”了下来。
可在“文化大革命”,身患癌症的父亲亦难逃一劫。尤其是1966年,肠癌并发肝癌的父亲已卧床不起,此刻的书房成了他的“病房”,来抄家的造反派在父亲的病床两头贴了“坦白交代,抗拒从严!”,“打倒某某某”,“打倒刘邓司令部在新闻战线的黑干将”等标语。等造反派走出家门,气愤的姐姐好提撕下一张标语,而父亲却让姐姐重新贴上。当时院子里还有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主要内容一是要交代与“修正主义分子”冯定的关系,一是批判父亲的“大吃大喝”……而父亲让我们要正确对待毛主席发动的群众运动。可当造反派诬蔑《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之时,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一字一句抗议:“说《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的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想想也是,父亲从1933年开始他的写作[1],第二年,追随胡愈之先生,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世界知识》的宗旨是为苦闷、彷徨的中国青年开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由此,父亲从作者、编辑到总编,为《世界知识》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而如今《世界知识》却被诬蔑为“卖国杂志”,父亲真的很伤心,很痛心。
由于心痛,由于病痛,往日被孙辈昵称为胖爷爷的父亲那宽厚、乐观的笑容不见了,书房的病床上只有叹息,只有呻吟……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一晚,我从外面回家,父亲看到我,眼睛顿时一亮,说:“阿平,你给我拉一段《魂断蓝桥》[2听听。”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自发现肠癌到上海做手术后,已有四年,住过好几次院,虽说健康状况一次比一次差,但父亲从没有直接表达过对家的依恋,对亲人的依恋。这次又将去住院,再次离开家,离开书房,父亲想借助这一乐曲来表达自己的心愿。而《魂断蓝桥》时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如果被大院的造反派听到,将又是一场灾难。然而,我们已不顾这些,为了父亲的心愿,一旁护理的母亲拿出一条厚窗帘,把它挂了起来;好提出门去院子看外面的动静;我拿出积满灰尘的小提琴,拂去浮尘,擦松香,调准弦音……当旋律从我的手指和弓弦之间滑出而回荡在父亲的书房之时,我的心灵如醉酒般地颤动起来,表达出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离别之情,我们彼此是那么的依恋,那么的不舍,又是那么的无可奈何。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们仨泪流满面,只见父亲闭上了眼睛,脸上有了瞬间的安宁。我喜欢音乐,父亲曾经多次给我音乐会的票子;父亲和大伯常听我拉的《茉莉花》。现在想想也是欣慰,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在父亲最后的书房,我的喜好给病痛与心痛的父亲带去瞬间安宁。
1966年的夏天,我工作的七机部二院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将抽调力量去贵州,我是其中一员。当时的领导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三线’一天不建设好,他就睡不着觉”,为了让毛主席能睡好觉,我们一批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坚决响应号召参加“三线”建设。我去北京医院与病重不起的父亲道别,说我要去参加“三线”建设,挺远的,在贵州遵义。父亲平静地说,“年轻人么,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
与父亲告别后,我随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军来到贵阳,在远离北京3000多公里的“064”指挥部,设计隐身山洞的半导体车间。其间,因惦记父亲的病情与同事谈起,一同事告诉我一好消息——上海一教授发明了治疗肝癌的新药。可还没来得及写信联系,这年11月30日,父亲带着双重的痛苦——病痛与心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书房,离开了伴随三十多的《世界知识》。当3000多公里之外的我接到“父病危”电报之时,竟还想着去上海替父亲买新药呢。到上海听一亲戚说出“您不用去”四个字,我才明白,那天与父亲在北京医院相见竟成我们父子的永别,“年轻人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是父亲对我的最后遗嘱。
从上海回到北京,父亲的遗体已火化。时是“文革”,父亲被批,而外交部的一些领导,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些同事还是“悄悄地”与父亲告别。13年后的初春,外交部为冯宾符、吴景崧、梁纯夫三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黄华、胡愈之夫妇、乔石夫妇、周建人、赵朴初、雷洁琼、孙冶方夫妇、宦鄉、于光远、冯定夫妇、孙起孟、萨空了、冯亦代、刘贯一、徐伯昕、陈翰伯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全体同志近300人出席了追悼会,1979年3月2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消息。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停刊被诬蔑的《世界知识》同年复刊,与读者再见面。还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如今的我子承父业,从工程师转行为日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员。
我觉得我的转行与父亲的DNA有密切关系,我家在无量大人胡同的父亲的书房是我学生时代的“第二课堂”,我从中感受真理之美,感受写作之趣。我觉得我的转行不仅是父亲职业的传承,而且是父亲意志的传承。我学的是俄语,大学毕业参加军垦农场劳动时,我从父亲当年自学英语受到启发,悄悄自学英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外语被视为崇洋媚外,我就搞到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每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从英文反推中文意思(因为中文语录天天读,大都记得住),记了很多英文词汇。回想当年自学英语的环境,真是不可思议,但我常以父亲自学英语、翻译《西行漫记》的那种精神自勉自励。正是父亲的榜样,1978年人事部组织的科技人员英语水平考试,我获得笔试67分、口试5﹣的成绩。那时考70分的科技人员可以不参加培训就可出国,我的笔试成绩虽差三分,但由于口试接近最高分,也被列入免于培训之列,于1979年选送到日本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为此我又自学了日语。
如果说自学外语是以父亲为榜样,那么喜欢写作也与父亲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从日本回国后,我将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写成科普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其中《软件的崛起》一文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并与我约谈,希望我去国家科委工作,当时我已达到了可读懂俄文、英文、日文的专业技术文章的水平,又有半导体和电子学的专业基础,而且最向往的工作就是能够安安静静地做些资料翻译工作,正好国家专利局招人,我便到专利局接待大厅填了应聘的表格,等了一个多月不见回音。世间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一次《世界知识》的作者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何倩,他建议我调到日本所,说到日本所也可以做喜欢的资料工作,于是我写信给日本所人事处,想不到一周后就有了回音,又过了一周就搞定了调动手续。此后,国家专利局也发来商调函,表示“热烈欢迎”,但为时已晚矣。
回想起来,真是有缘,由于父亲奉献了大半生精力的《世界知识》的“牵线”作用,我成了老邻居何方老师的部下。这一调动被同事戏称为“变身”,而我说是“半路出家”。人到中年的我,专门从事日本研究,我克服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不足等困难,靠着勤能补拙、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和行动,主要做了三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众所周知,转行到陌生的领域,总得找一条进入此领域的路径,我利用我所学专业和原工作的特点,将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作为第一个选题,撰写了一份题为“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的报告,发表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第二年就被评选为社科院“优秀报告”。去日本考察后,又撰写了“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的考察报告,被中央有关部门选作“县团级文件”发往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我的研究视野扩大到“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写下了《日本的新技术革命》、《日本经济的活力》、《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改革》等。其中《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分类出版了《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日本的零售业》、《中日流通业比较》、《AComparisonBetweenDistributioninChinaandJapan》四本专著,之后又出版了《走向技术立国之路》、《日本经济》等,迄今我已有12本个人著作。
在对日本的研究过程中,我自然而然想到了中日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日关系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路,来研究中日关系这一课题,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先后出版了《对话:北京与东京》、《日本:战略的贫困》、《中日关系报告》等书和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内部报告,这些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我退休后,被邀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日研究所所长(其实只是挂个名),2004年10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我接到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个重要会议,要我回京后马上向一位领导同志“报到”。我回北京后不久,就接到这位领导同志的电话,通知我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并让我告知其车牌号。我说,我是退休的普通研究人员,没有专车,只好乘出租车。对方说:“那我们就派人在中南海门口接你吧。”待到开会那天,我来到中南海门口,说明来意,警卫很快放行,我没等人来接,“趁机”在这个“最安静的公园”散了步。
进入会场,才知道是胡锦涛主席召集一次小型座谈会。胡主席还没有到,先进入会场的人打算到会场门口迎接,却不料胡主席身穿夹克,脚穿布鞋,走路很轻,已经进入会场。他绕椭圆形会议桌转了半圈,与发言者一一握手,然后在会议主持人旁边落座。我看与会者个个都身份不凡,暗嘱自己不要主动发言。没想到在第一位发言者讲完之后,胡主席就点了我的名:“冯昭奎,你讲讲吧。”按照会前有人特意给我打的招呼,我的发言用了40多分钟时间,比其他与会者的发言时间多出一倍。
因为写写写,我和我的文章引起了关注,既受到批评和指责又得到肯定和赞扬,其实我只是个书虫,只想努力说一些实话,为人做事都很呆板。1990年前后,院里要我当副所长,我拒绝了,但仍然被以一种“没得商量”的方式接到任命,我硬着头皮当了一届就主动辞职。2011年,因为在公共汽车站偶遇其他所的老朋友,告诉我院里正在评选学部委员,我就填了一份表格,出乎意料地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反正从工程师改行做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此后遇到的种种事情,都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也可以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我的祖父是旧时代的士大夫,父亲是新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我是他们的儿孙,继承了他们的基因,秉承了他们的性格。有意思的是,年过古稀的我至今仍以研究、写作国际问题为乐,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除了有时在书房里听听音乐,没有什么嗜好,每天就坐在书房里,不是看与研,就是思与写,这一切正是缘于父亲对我的启蒙、培养、熏陶。
附注
[1]楼适夷(1905—2001),原名楼锡春,浙江余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中共党员。历任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代理主编,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新华日报》编委,《时代日报》编辑,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译文》编委
[1]据统计,1933—1937年,冯宾符先后用“仲足”、“宾符”、“奥松”、“艾纳”等笔名,在《东方杂志》、《申报》、《永生》、《半月》、《文化战线》、《国民周报》等发表100多篇时事政论(据《冯宾符年谱》)
[2]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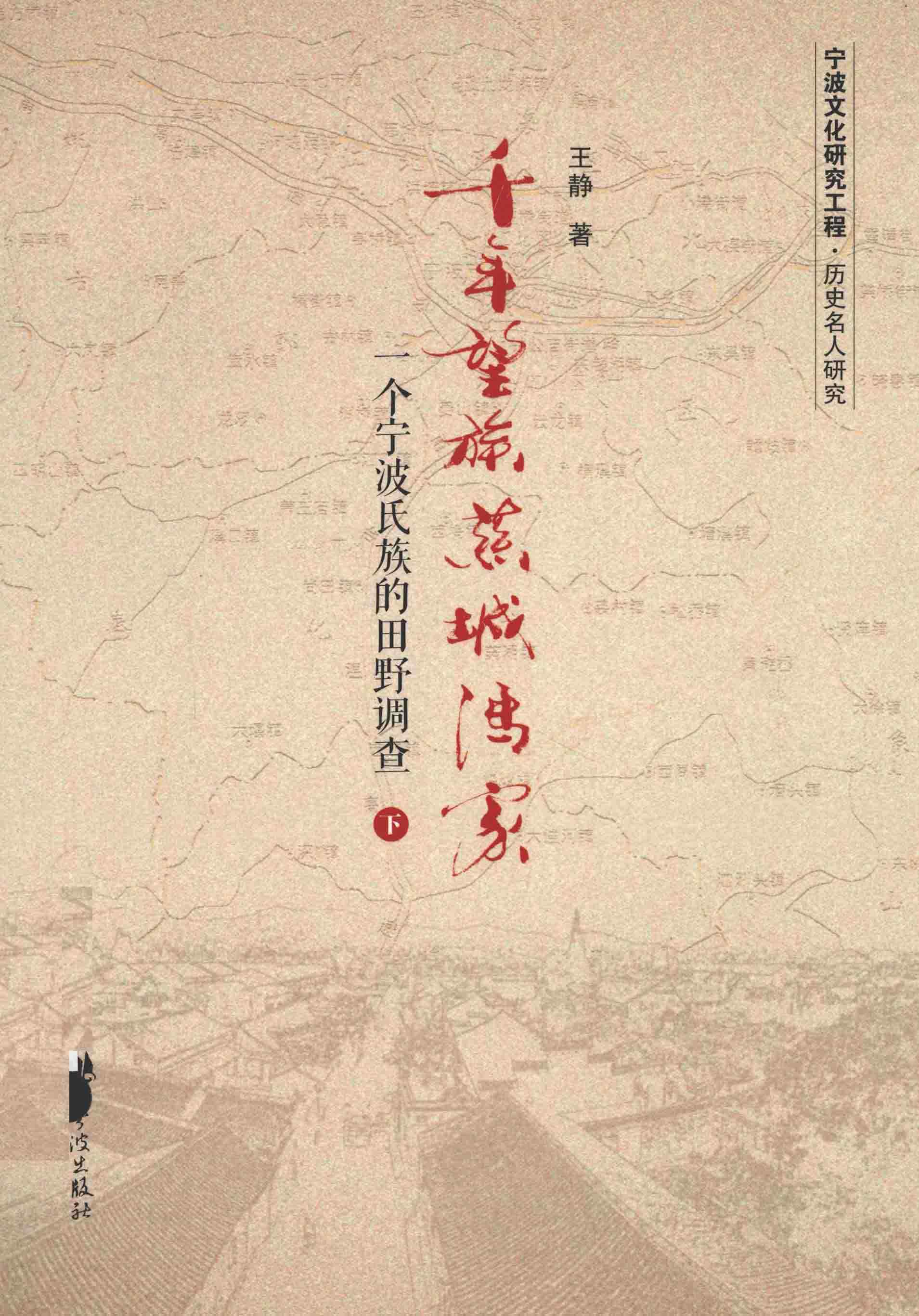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本书是以慈城冯氏众子姓及家族文化为对象,以慈城及海内外的家族文化为参照说明,以历史文献及口述史为依据,结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民俗学,对慈城冯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认为慈城冯氏以寻根、联宗等形式营造家族的精神家园,以凝聚众子姓之心是千年望族的内核,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得以绵延千年不绝的家族秘诀。
阅读
相关地名
慈城镇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