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冯家的媳妇
| 内容出处: |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图书 |
| 唯一号: | 112520020220002341 |
| 颗粒名称: | 我是冯家的媳妇 |
| 分类号: | K820.9 |
| 页数: | 7 |
| 页码: | 511-517 |
| 摘要: | 本文姚婉宜是冯家的媳妇是2011年5月在江苏昆山人民南路97号由姚婉宜口述关于政治方面。 |
| 关键词: | 慈城镇 冯家 媳妇 |
内容
我17岁嫁到冯家,是在太阳殿路33号,称槐花树门头冯家,后门走出是金刚井弄,对面是布政房,往北走是完节坊。这把椅子那时就已经在了,一共有四把旧藤椅,两把坏脱送掉了,两把带到了昆山。
我结婚是在1929年,原定在四月二十一(农历),正好遇到孙中山落葬[1],婚期只好提前到四月十七。那天冯家抬两房媳妇,是两兄弟同一天拜堂,即二哥与二嫂,我和丈夫开叔。二哥当时在宁波四明银行工作,二嫂韩淑宜是宁波人,家住宁波宝兴当弄;开叔在宁波保慎钱庄做事,我是庄桥姚家人,姨丈做的媒,所以好日酒[2]办在宁波。因为中午办酒,姨丈怕来不及,头天夜里(即提前一天)从庄桥乘火车到宁波,在江北岸开了旅馆(旅馆名不记得了),父母亲及众亲眷一同出来,第二天花轿到旅馆接新娘到办酒饭店(饭店名不记得了)。花轿早已把我抬到饭店了,而宁波人的规矩是下午两点才上轿,故一直不见二嫂的花轿到,而我要等二嫂的花轿到了方可落轿,一起拜堂。紧催慢催,二嫂的花轿12点多才到,二嫂娘家的外地客人及宁波客人同来。说是四月里,其实已经是夏天,结婚那天很热,花轿里还要摆一只火熜,芸香烧得“喷喷香”,真是“轰轰响”。头戴鹤帽,外罩戴头袱[1],天介热,急得姨丈在落轿杠时,直喊“先拕火熜”。拜堂后各人进房间。下午另乘轿子到火车站,从宁波回慈城家中再办晚上的仪式。慈城的结婚,男方花轿头夜已来,花轿蛮大,装饰高大,一般需8个人抬轿,往往抬到偏僻人少处,轿夫先将轿子拆卸掉一些部件,以减轻重量,临近男方家时再按原样装好。
第二天一早,在送娘子(堕民嫂)陪同下向长辈敬盖碗茶,给平辈和小辈泻糖茶。当时陪同的好像没啥讲究,只要讲得清冯家亲属关系就行,我是手拎一把镴茶壶,送娘子手端茶盘,先后到长辈、亲戚(包括住在附近的远堂亲戚)和近邻泻茶,当时桂珠姑(即外五房的冯一敏)太婆、太叔婆都在,接连敬茶三天。
我嫁到冯家时,太婆[2]还在,已经七十多岁。开叔是六兄弟,还有一姐姐,其中老四早夭。太婆、公婆、还未结婚的大哥、大姐和两小叔子住在前进房子,我家与二嫂家住在后进。前进是五楼五底,西面是君木叔公家,右面是阿拉家,太婆住楼下,公婆住楼上。后进也是冯家的房子,只是租给了人家,房客后在上海开钱庄,一家搬去上海。我家小孩多,就将三楼三底的楼下倒租过来,中间堂前安装了落地玻璃门,我们叫洋窗。
之后,冯家抬了三房媳妇。大嫂蔡觉予是镇海三官堂人,在宁波办的新式结婚,没戴红头袱,就像现在的旅行结婚;五嫂胡湘伊是余姚人,她乘火车到慈城,新郎(五叔)借保黎医院医生出诊的两顶轿子,在太湖路上的工商会办酒,下午娘家人回去后,再接新娘到槐花树门头的家中;六嫂陈端好是半浦人,因战时危机,日本人入侵,婚事十分简单,借普迪二校作结婚场所。我在娘家的小名是幼娟,妯娌们的小名依次是依心、阿三、阿秀,六嫂不知道,嫁到冯家后,都良叔给我改名为婉宜,我们妯娌都有文雅的名字。
太婆待我们孙媳妇很客气;婆婆爱唠叨。太婆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既不拜菩萨,又不念佛;婆婆是吃素念佛到处拜菩萨。1930年冬天,小脚太婆到大门外看望,被六弟不小心撞倒,摔断了腿,从此不能再起立。冯家有请安问候的规矩,每天早晚要向太婆、公婆请安。那天,二嫂请安回来说,太婆拉肚子。我听说就去前进看望太婆。太婆还说,不要紧,千钿难买六月拉,就是有点肚子痛。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当一回事,各自回房。睡到下半夜,婆婆从小门过来叫我们快起床,原来太婆半夜开始就上吐下泻……虽说如此,一家人没想到请医生,也不知道流行时疫病,等到第二天夜里,太婆就过世了。平时,我看公公待太婆不那么亲热,但太婆过世后,公公很伤心,既请和尚又请尼姑,连续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经,我们每天半夜两点上净茶,早晨上饭之后的一日三餐,据说这样祭祀母亲是很少的。做七时由六个尼姑念《金刚经》,平时每天念《弥陀经》,而且家里还专
完节坊,是慈城一个标志性的地名,也是一处古县城景点。诰封三代,连荫二子,在江南一邑的慈城,不时传颂着冯岳的喜事。冯岳官至尚书,诰封三代,门请厨工烧饭,当然其他的家务还是由妯娌一起做。
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服侍太婆、服侍公婆,引线(针线)生活[1]样样会做,做衣裳,做鞋子,开叔的长衫、棉袍,后来不穿这种衣服,又全部改成儿女穿的衣裳。婆婆要做式样考究的衣服时,就雇安甫(与我差不多年纪)小裁缝来做,而睡衫、裤、棉裤之类不那么要求样式的,她让我们媳妇做。婆婆还说:“你们庄桥人会做衣裳,阿拉洪塘人勿会做。”其实我做娘子[2]时,也只会缝纰头[3],只是嫁到冯家后开始学做衣裳,是和二嫂一起学的。进门不久,婆婆让我和二嫂给她做几件洋布衫,二嫂比我大三年,那次二嫂裁衣,等裁好摊开一看,尺寸弄错了。幸亏还有布料,我们怕婆婆责怪,悄悄收起裁错的衣片,又裁了一件新的做好。
我生育儿女六个(在慈城就有四个,其中老四1941年逃难时出生在上海),有时忙勿过来,十月里做棉袄的辰光,嫁到费家市费家的阿姐常常步行20多里路,约有三个钟头,来帮我做引线生活。春结毛线冬做衣,数十年,公婆、我们和孩子三代人身上穿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夜作,先让孩子睡在摇篮里,自己是一边用手做生活,一边还要用脚拐摇篮,等做到十一点钟再将孩子抱上床。我到昆山来时,还将慈城的藤盘、绕线板都带来了,绕线板还是红木镶象牙的当年,除了做衣裳,还要补袜子,因是洋纱袜子很会破,几乎是洗一水要补一次,实在不能补了,就贴袜底,用硬纸板剪成鞋底形状,将破袜底中间剪开,插入鞋底纸,两边翻上面来,再用新布一针针缝上去。有时,衣裳穿得褪色了,买来染粉自己染色,五嫂回娘家时常从余姚买来颜料粉。我们五妯娌间很和睦。
冯家是大户人家,除了公公名下的儿女外,光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内五房与外五房之分,我家、君木叔公,还有宁波一藏书家都属内五房,君木叔公一家住上海。上面提到的,现还住在太阳殿路的桂芝姑属外五房,前几年我们去慈城时碰到过。我们冯家属统宗祠,后来祠堂改为学堂,名称为尚志小学。统宗祠是大祠堂,一代一代子孙越来越多,陆续搬离分出去,下面又有了小祠堂,如绩高堂[1]。绩高堂在布政房旁边,我们又属于绩高堂。绩高堂族长是毛头太公,他年纪不算大,但辈分最高,吃饭时一人一桌,族人有“毛头太公吃独桌”之说。我们的神主牌不在绩高堂,而在完节坊魁字门头,那是太太公允骏公的房子。魁字门头在太湖路上,门牌是32号[2],不知现在是否已经改了,我生道容就是在那儿,平时我们进出都走太湖路,这是完节坊后门。从大门进完节坊,能看到两顶轿子,因年代久远已很破旧,像风凉轿,据说也是皇帝赐的,因为上代是读书人。完节坊内房子蛮奇怪,大门走进,一边是冯家,一边是周家,不知是冯家把房子卖给了周家,还是与周家有什么关系。我们当媳妇的又不好问。此外,公公还有远房的堂弟,公公叫仁宝,他叫仁元,仁元是这本书[3]主人舜华的父亲,舜华的哥哥伯华认公公为寄拜[4]阿爸。幼时已经寄拜,没看见寄拜仪式,可能这是我嫁到冯家之前的事。后来,我晓得公公婆婆会差人给伯华,即寄拜儿子送年夜饭,其中一碗鱼、一碗肉、一碗汤团和一碗糯米饭是一定要的,其他没定规,一直送到寄拜儿子长到16岁。每年大年初一,一早伯华三兄弟就来我家拜年,公公婆婆会给压岁钿。正月十五那天,三兄弟会来拜糖饼,也就是拜过祖宗神像后,分给他们糖饼(也称吉饼)。当年听说过树德堂,是否是槐花树门头神堂呢?不能确定。慈城冯家的寄拜、过继蛮讲究规矩的,一般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寄拜给弟弟(叔叔)家。因为有寄拜的关系,所以虽说是远房,但两家走得较近。
婆婆是洪塘人,她是五姐妹,父母早亡,由叔父洪念祖抚养长大,并择婿出嫁。婆婆的姐姐们分别嫁到慈城的桂家、徐家、孙家,均属富裕人家,而她嫁的冯家,相对较穷。据说姐姐们陪嫁的是真皮箱,而她的是纸面皮箱,俗称假皮箱,这使婆婆心里一直“勿是介”(慈城方言,意为不乐意)。婆婆的四姐,我叫四姨,嫁给半浦孙衡甫[1]做填房,我叫孙衡甫为姨丈,四姨与我蛮要好,90岁时还是在昆山做的生(过寿)。她没孩子,对外甥、外甥囡及孙辈都很关爱。
1940年逃难去上海,婆婆带着我们四妯娌(大嫂已跟大哥昌伯从慈城参加了新四军)、我的两个孩儿(当时大女儿留在姚家)、15岁的外甥(我阿姐的儿子),还有安甫一起与四姨乘四明公司的小货轮到上海。在煤业公司谋生的公公只租了公司的一间后厢房,而我们一下子去那么多人,最后由四姨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安甫租了煤业公司的一间房子,以做裁缝而在上海落脚。不幸的是我们安顿下来不到两个月,婆婆却离我们而去。因是战争动乱年代,丧事办得较为简单,第二年都良叔写了《冯母洪孺人家传》一文,书法家书写以示纪念。之后,六弟与五弟两夫妻先后参加了革命。六弟新婚不久,因为战争物价飞涨,六嫂谋到教书一职,可公公却认为女人不能出去工作,迫使六嫂也去了苏北。
老四1941年出生在上海,开叔时常失业,生活负担重,两个大的小孩要读书,1942年,我和二嫂带孩子们回到慈城。大叔冯钢参加新四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人民银行苏州分行行长等,开叔调到昆山银行工作,1952年才从慈城迁居昆山。解放后扫文盲,居委会让人教语文、教算术,我总算能看报了。如今耳聋听不到声音,还能看电视,比如看英国王子结婚蛮有意思,想起太婆、婆婆。我们都是冯家媳妇,我是最长寿的,也是最幸福了。
⊙我家和槐花树门头
口述者:冯士能出生年月:1938年8月职业:新闻工作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市临平路89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慈城的完节坊,成长在太阳殿路33号,现址是太阳殿路44号。慈城人称槐花树门头冯家。
我所知道的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君木先生、孟颛先生和我家的祖父辈们。孟颛先生辈分比君木先生低一辈,他的祖父是二房,君木先生的父亲是五房,我的高祖父是三房,他们是亲兄弟。四房的曾祖辈没有儿子,我家祖父的小弟过继到四房,我称小公公(参见表6.2.4)。
小公公的名字,刚听娘说叫仁甲,我看到过他。新中国成立前,小公公守护宝善堂,孤身一人,食宿都在宝善堂。1948年的一天,他喝老酒后抽烟,又糊里糊涂睡着了,结果烟头点燃了蚊帐而发生火警,所以曾经有一次宝善堂的火警是小公公闯的祸,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酿成火灾。
我的阿爷是三兄弟。阿爷的大弟劬勤住在太湖路,在大桥头北面(现已拆光),具体门牌忘了,家人称魁字门头[1],与完节坊相通。无论是太湖路的房子,还是太阳殿路的房子,其产权大多是祖上的公共房子[1],由孟颛公负责管理,因孟颛公长住在宁波,便委托大公公照料。我家祖孙三代人丁兴旺,都住在槐花树门头,一直住到离开慈城。
太阳殿路44号的老墙门,于慈城、于我们冯家有一种纪念意义。这个由前后两进正屋、偏屋轩子间构成的江南民居,因曾经居住过多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而被载入史册。我说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如君木先生和他的长子都良先生,君木先生和他的学生沙孟海先生,还有君木先生和他的族侄冯定,这些人物不仅仅是慈城名人、宁波名人,还是中国名人。
我家租的是后进,族人称后堂,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子,前进的五上五下称前堂。阿爷有六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阿爷、阿娘与儿孙们同居一堂,后来伯叔纷纷离家谋生。我的大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大伯母也跟随而去,当年后进楼下的西间堆放大伯用过的家具;二伯出门去了宁波;差不多同时,五叔也参加了革命;据说大伯有一次回慈城,新婚不久的小叔夫妻俩也跟着去了苏北,不幸的是没去几年,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小叔在苏北部队得了膨胀病(血吸虫病),后回上海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为不治之症,只能再回到慈城,不久去世。
大约在1946与1947年间,父亲受阿爷之命去苏北益林,现在是盐城市阜宁县益林乡“探亲”。据母亲回忆,当年大伯曾劝父亲留下来一起干,而我父亲却因家里有五个儿女(当时我的小妹还没出生)拖累而回上海。回来后,父亲悄悄与母亲说:北边[1]苦是苦,人倒蛮开心,是“穷开心”。母亲解释“穷开心”的意思,一是穷,生活艰苦,另外昆山土话中“穷”含“很”之意。父亲虽没留在苏北,但他在思想与行动上是支持大伯他们革命的。
当年的大伯在苏北根据地搞后勤工作,经常把苏北棉花之类的农副产品运到上海卖掉,将卖得的钱换钢材、药品运回苏北,就像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角色。因而他来上海时,一会儿穿西装,一会儿穿长衫,有时打扮得像大老板,有时打扮得像劳动者,而国民党当局已经注意到他了,所以《申报》刊登过一则新闻有大伯的名字[2],说“匪首冯昌伯潜入上海”之类的话。在解放战争时期,大伯采购的不少物资,如钢材、医药等全是当局禁品,有几次在吴淞口被查获,父亲听说大伯的物资被扣,就四处找人疏通关系。当年,都良阿爷也在上海,其与沙孟海、沙文汉两兄弟关系很好,沙文汉是地下党,而沙孟海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工作。父亲可能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帮助大伯的。
都良阿爷说过,慈城冯氏分两大脉络,有的崇儒,是读书人,比较清苦;还有一些冯家是做生意的,开药店,开钱庄,比较有钱。我的祖辈、父辈既不是做学问的,也不是开店办厂的,是职员,为人“打工”的。我小时候,家里生活过得清苦,这是因为我父亲经常失业,而失业缘起是父亲有参加新四军的兄弟,老板一旦晓得父亲的苏北背景就不敢再雇用。
在慈城,儿时的我们常盼信客[3]来。信客来,就是父亲带钱来了,家里有了钱,就能吃到荤腥了。后来我听母亲说,旧时的宁波,带鱼是不上桌请客的,而慈城人反之,不仅能上台面,还视其为吉利,因为带鱼的“带”字寓意带钞票。多吉利的带鱼哟,带鱼对慈城人来说是“讨口彩”的吉祥鱼。
在慈城,我家因父亲经常失业,自然少了生活来源,这就苦了母亲。
慈城冯氏有“败落乡绅不走样”的说法,不管家里怎么清苦,我娘总是让我们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这样母亲就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夏天布衫冬天棉,一年到头纳(慈城方言,音读漆)鞋底。想想也是,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让我们穿脚趾头“笃出”的鞋子,而做鞋的工序又那么多,从褙袼到绱鞋,要经多少道工序,光纳鞋底用的线,就够麻烦了。过去没现成的纳鞋底线,是从穿破的纱袜上拆出线,八并四,四并二,最后搓成纳鞋底线,我们都帮母亲搓过纳鞋底线。做鞋面也是如此,剪样、粘合、绲边,若是棉鞋还要衬棉花,而一双布鞋只能穿几个月。母亲一年到头要做多少双鞋子,我不曾统计过,但只要看我家那些大大小小的鞋楦,就明自母亲曾经的辛苦
在慈城,童年生活虽然紧绷绷的,但很快乐。冯家孩子多,那时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十几个,父辈兄弟敬老爱幼,互相融洽;下代兄弟姐妹也和睦相处,常常聚在一起玩游戏,乘风凉,猜谜语,哼儿歌。我母亲记性特别好,说起慈城民谚民谣一箩筐一箩筐的去年,我写了一篇《诱人的慈城民谣》,后刊登在《海上宁波人》杂志上,文中的谚语、童谣大多是听母亲说的。母亲没上过学,是父亲教她识的字,我读初小,她也拿我的国文课本去学,有时我读不出、写不出,反而是她教我母亲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据传,我家祖上(太太公辈)在东北营口投资开药店,好像是咸春堂,按股子分红,但到了祖父辈已没什么钱,只属“工薪阶层”上面我说过,祖父有六个儿子,而且是差不多年纪娶的媳妇年老的母亲还常说,冯家规矩重,做媳妇难。从早晨替公婆揩灯罩、擦水烟管开始,母亲和妯娌们每天承担一大堆家务,大伯母、婶婶等参加革命后,母亲几乎成了众家媳妇,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而世间总是多做事情多出错,也多招怪,可母亲从不怨天尤人,依旧乐呵呵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这样,母亲以她朴素的语言,勤劳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我很感激家乡慈城、家乡宁波,因为我是慈城冯氏子孙槐花树门头的家,因族人过世的过世,离开的离开,除了20世纪70年代都良阿爷回乡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房子有的空关,有的出租,1976年将年久失修的房屋卖了。可我们还总是惦念慈城,惦念老家,2006年母亲94岁那年,我们兄妹陪她重游故乡
这之前,因工作关系我去过宁波几次。1995年,我带领报社编辑、记者到宁波,在与宁波宣传部门交流如何办好党报时,向市领导承诺《解放日报》重点报道宁波的意向。[1]当时我提出这个设想,不光是因为上海与宁波地域相邻,血缘相近,经济相连,文化相融,也是我情感使然,因为我是来自宁波的游子,是来自慈城的游子。
我结婚是在1929年,原定在四月二十一(农历),正好遇到孙中山落葬[1],婚期只好提前到四月十七。那天冯家抬两房媳妇,是两兄弟同一天拜堂,即二哥与二嫂,我和丈夫开叔。二哥当时在宁波四明银行工作,二嫂韩淑宜是宁波人,家住宁波宝兴当弄;开叔在宁波保慎钱庄做事,我是庄桥姚家人,姨丈做的媒,所以好日酒[2]办在宁波。因为中午办酒,姨丈怕来不及,头天夜里(即提前一天)从庄桥乘火车到宁波,在江北岸开了旅馆(旅馆名不记得了),父母亲及众亲眷一同出来,第二天花轿到旅馆接新娘到办酒饭店(饭店名不记得了)。花轿早已把我抬到饭店了,而宁波人的规矩是下午两点才上轿,故一直不见二嫂的花轿到,而我要等二嫂的花轿到了方可落轿,一起拜堂。紧催慢催,二嫂的花轿12点多才到,二嫂娘家的外地客人及宁波客人同来。说是四月里,其实已经是夏天,结婚那天很热,花轿里还要摆一只火熜,芸香烧得“喷喷香”,真是“轰轰响”。头戴鹤帽,外罩戴头袱[1],天介热,急得姨丈在落轿杠时,直喊“先拕火熜”。拜堂后各人进房间。下午另乘轿子到火车站,从宁波回慈城家中再办晚上的仪式。慈城的结婚,男方花轿头夜已来,花轿蛮大,装饰高大,一般需8个人抬轿,往往抬到偏僻人少处,轿夫先将轿子拆卸掉一些部件,以减轻重量,临近男方家时再按原样装好。
第二天一早,在送娘子(堕民嫂)陪同下向长辈敬盖碗茶,给平辈和小辈泻糖茶。当时陪同的好像没啥讲究,只要讲得清冯家亲属关系就行,我是手拎一把镴茶壶,送娘子手端茶盘,先后到长辈、亲戚(包括住在附近的远堂亲戚)和近邻泻茶,当时桂珠姑(即外五房的冯一敏)太婆、太叔婆都在,接连敬茶三天。
我嫁到冯家时,太婆[2]还在,已经七十多岁。开叔是六兄弟,还有一姐姐,其中老四早夭。太婆、公婆、还未结婚的大哥、大姐和两小叔子住在前进房子,我家与二嫂家住在后进。前进是五楼五底,西面是君木叔公家,右面是阿拉家,太婆住楼下,公婆住楼上。后进也是冯家的房子,只是租给了人家,房客后在上海开钱庄,一家搬去上海。我家小孩多,就将三楼三底的楼下倒租过来,中间堂前安装了落地玻璃门,我们叫洋窗。
之后,冯家抬了三房媳妇。大嫂蔡觉予是镇海三官堂人,在宁波办的新式结婚,没戴红头袱,就像现在的旅行结婚;五嫂胡湘伊是余姚人,她乘火车到慈城,新郎(五叔)借保黎医院医生出诊的两顶轿子,在太湖路上的工商会办酒,下午娘家人回去后,再接新娘到槐花树门头的家中;六嫂陈端好是半浦人,因战时危机,日本人入侵,婚事十分简单,借普迪二校作结婚场所。我在娘家的小名是幼娟,妯娌们的小名依次是依心、阿三、阿秀,六嫂不知道,嫁到冯家后,都良叔给我改名为婉宜,我们妯娌都有文雅的名字。
太婆待我们孙媳妇很客气;婆婆爱唠叨。太婆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既不拜菩萨,又不念佛;婆婆是吃素念佛到处拜菩萨。1930年冬天,小脚太婆到大门外看望,被六弟不小心撞倒,摔断了腿,从此不能再起立。冯家有请安问候的规矩,每天早晚要向太婆、公婆请安。那天,二嫂请安回来说,太婆拉肚子。我听说就去前进看望太婆。太婆还说,不要紧,千钿难买六月拉,就是有点肚子痛。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当一回事,各自回房。睡到下半夜,婆婆从小门过来叫我们快起床,原来太婆半夜开始就上吐下泻……虽说如此,一家人没想到请医生,也不知道流行时疫病,等到第二天夜里,太婆就过世了。平时,我看公公待太婆不那么亲热,但太婆过世后,公公很伤心,既请和尚又请尼姑,连续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经,我们每天半夜两点上净茶,早晨上饭之后的一日三餐,据说这样祭祀母亲是很少的。做七时由六个尼姑念《金刚经》,平时每天念《弥陀经》,而且家里还专
完节坊,是慈城一个标志性的地名,也是一处古县城景点。诰封三代,连荫二子,在江南一邑的慈城,不时传颂着冯岳的喜事。冯岳官至尚书,诰封三代,门请厨工烧饭,当然其他的家务还是由妯娌一起做。
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服侍太婆、服侍公婆,引线(针线)生活[1]样样会做,做衣裳,做鞋子,开叔的长衫、棉袍,后来不穿这种衣服,又全部改成儿女穿的衣裳。婆婆要做式样考究的衣服时,就雇安甫(与我差不多年纪)小裁缝来做,而睡衫、裤、棉裤之类不那么要求样式的,她让我们媳妇做。婆婆还说:“你们庄桥人会做衣裳,阿拉洪塘人勿会做。”其实我做娘子[2]时,也只会缝纰头[3],只是嫁到冯家后开始学做衣裳,是和二嫂一起学的。进门不久,婆婆让我和二嫂给她做几件洋布衫,二嫂比我大三年,那次二嫂裁衣,等裁好摊开一看,尺寸弄错了。幸亏还有布料,我们怕婆婆责怪,悄悄收起裁错的衣片,又裁了一件新的做好。
我生育儿女六个(在慈城就有四个,其中老四1941年逃难时出生在上海),有时忙勿过来,十月里做棉袄的辰光,嫁到费家市费家的阿姐常常步行20多里路,约有三个钟头,来帮我做引线生活。春结毛线冬做衣,数十年,公婆、我们和孩子三代人身上穿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夜作,先让孩子睡在摇篮里,自己是一边用手做生活,一边还要用脚拐摇篮,等做到十一点钟再将孩子抱上床。我到昆山来时,还将慈城的藤盘、绕线板都带来了,绕线板还是红木镶象牙的当年,除了做衣裳,还要补袜子,因是洋纱袜子很会破,几乎是洗一水要补一次,实在不能补了,就贴袜底,用硬纸板剪成鞋底形状,将破袜底中间剪开,插入鞋底纸,两边翻上面来,再用新布一针针缝上去。有时,衣裳穿得褪色了,买来染粉自己染色,五嫂回娘家时常从余姚买来颜料粉。我们五妯娌间很和睦。
冯家是大户人家,除了公公名下的儿女外,光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内五房与外五房之分,我家、君木叔公,还有宁波一藏书家都属内五房,君木叔公一家住上海。上面提到的,现还住在太阳殿路的桂芝姑属外五房,前几年我们去慈城时碰到过。我们冯家属统宗祠,后来祠堂改为学堂,名称为尚志小学。统宗祠是大祠堂,一代一代子孙越来越多,陆续搬离分出去,下面又有了小祠堂,如绩高堂[1]。绩高堂在布政房旁边,我们又属于绩高堂。绩高堂族长是毛头太公,他年纪不算大,但辈分最高,吃饭时一人一桌,族人有“毛头太公吃独桌”之说。我们的神主牌不在绩高堂,而在完节坊魁字门头,那是太太公允骏公的房子。魁字门头在太湖路上,门牌是32号[2],不知现在是否已经改了,我生道容就是在那儿,平时我们进出都走太湖路,这是完节坊后门。从大门进完节坊,能看到两顶轿子,因年代久远已很破旧,像风凉轿,据说也是皇帝赐的,因为上代是读书人。完节坊内房子蛮奇怪,大门走进,一边是冯家,一边是周家,不知是冯家把房子卖给了周家,还是与周家有什么关系。我们当媳妇的又不好问。此外,公公还有远房的堂弟,公公叫仁宝,他叫仁元,仁元是这本书[3]主人舜华的父亲,舜华的哥哥伯华认公公为寄拜[4]阿爸。幼时已经寄拜,没看见寄拜仪式,可能这是我嫁到冯家之前的事。后来,我晓得公公婆婆会差人给伯华,即寄拜儿子送年夜饭,其中一碗鱼、一碗肉、一碗汤团和一碗糯米饭是一定要的,其他没定规,一直送到寄拜儿子长到16岁。每年大年初一,一早伯华三兄弟就来我家拜年,公公婆婆会给压岁钿。正月十五那天,三兄弟会来拜糖饼,也就是拜过祖宗神像后,分给他们糖饼(也称吉饼)。当年听说过树德堂,是否是槐花树门头神堂呢?不能确定。慈城冯家的寄拜、过继蛮讲究规矩的,一般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寄拜给弟弟(叔叔)家。因为有寄拜的关系,所以虽说是远房,但两家走得较近。
婆婆是洪塘人,她是五姐妹,父母早亡,由叔父洪念祖抚养长大,并择婿出嫁。婆婆的姐姐们分别嫁到慈城的桂家、徐家、孙家,均属富裕人家,而她嫁的冯家,相对较穷。据说姐姐们陪嫁的是真皮箱,而她的是纸面皮箱,俗称假皮箱,这使婆婆心里一直“勿是介”(慈城方言,意为不乐意)。婆婆的四姐,我叫四姨,嫁给半浦孙衡甫[1]做填房,我叫孙衡甫为姨丈,四姨与我蛮要好,90岁时还是在昆山做的生(过寿)。她没孩子,对外甥、外甥囡及孙辈都很关爱。
1940年逃难去上海,婆婆带着我们四妯娌(大嫂已跟大哥昌伯从慈城参加了新四军)、我的两个孩儿(当时大女儿留在姚家)、15岁的外甥(我阿姐的儿子),还有安甫一起与四姨乘四明公司的小货轮到上海。在煤业公司谋生的公公只租了公司的一间后厢房,而我们一下子去那么多人,最后由四姨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安甫租了煤业公司的一间房子,以做裁缝而在上海落脚。不幸的是我们安顿下来不到两个月,婆婆却离我们而去。因是战争动乱年代,丧事办得较为简单,第二年都良叔写了《冯母洪孺人家传》一文,书法家书写以示纪念。之后,六弟与五弟两夫妻先后参加了革命。六弟新婚不久,因为战争物价飞涨,六嫂谋到教书一职,可公公却认为女人不能出去工作,迫使六嫂也去了苏北。
老四1941年出生在上海,开叔时常失业,生活负担重,两个大的小孩要读书,1942年,我和二嫂带孩子们回到慈城。大叔冯钢参加新四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人民银行苏州分行行长等,开叔调到昆山银行工作,1952年才从慈城迁居昆山。解放后扫文盲,居委会让人教语文、教算术,我总算能看报了。如今耳聋听不到声音,还能看电视,比如看英国王子结婚蛮有意思,想起太婆、婆婆。我们都是冯家媳妇,我是最长寿的,也是最幸福了。
⊙我家和槐花树门头
口述者:冯士能出生年月:1938年8月职业:新闻工作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市临平路89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慈城的完节坊,成长在太阳殿路33号,现址是太阳殿路44号。慈城人称槐花树门头冯家。
我所知道的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君木先生、孟颛先生和我家的祖父辈们。孟颛先生辈分比君木先生低一辈,他的祖父是二房,君木先生的父亲是五房,我的高祖父是三房,他们是亲兄弟。四房的曾祖辈没有儿子,我家祖父的小弟过继到四房,我称小公公(参见表6.2.4)。
小公公的名字,刚听娘说叫仁甲,我看到过他。新中国成立前,小公公守护宝善堂,孤身一人,食宿都在宝善堂。1948年的一天,他喝老酒后抽烟,又糊里糊涂睡着了,结果烟头点燃了蚊帐而发生火警,所以曾经有一次宝善堂的火警是小公公闯的祸,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酿成火灾。
我的阿爷是三兄弟。阿爷的大弟劬勤住在太湖路,在大桥头北面(现已拆光),具体门牌忘了,家人称魁字门头[1],与完节坊相通。无论是太湖路的房子,还是太阳殿路的房子,其产权大多是祖上的公共房子[1],由孟颛公负责管理,因孟颛公长住在宁波,便委托大公公照料。我家祖孙三代人丁兴旺,都住在槐花树门头,一直住到离开慈城。
太阳殿路44号的老墙门,于慈城、于我们冯家有一种纪念意义。这个由前后两进正屋、偏屋轩子间构成的江南民居,因曾经居住过多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而被载入史册。我说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如君木先生和他的长子都良先生,君木先生和他的学生沙孟海先生,还有君木先生和他的族侄冯定,这些人物不仅仅是慈城名人、宁波名人,还是中国名人。
我家租的是后进,族人称后堂,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子,前进的五上五下称前堂。阿爷有六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阿爷、阿娘与儿孙们同居一堂,后来伯叔纷纷离家谋生。我的大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大伯母也跟随而去,当年后进楼下的西间堆放大伯用过的家具;二伯出门去了宁波;差不多同时,五叔也参加了革命;据说大伯有一次回慈城,新婚不久的小叔夫妻俩也跟着去了苏北,不幸的是没去几年,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小叔在苏北部队得了膨胀病(血吸虫病),后回上海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为不治之症,只能再回到慈城,不久去世。
大约在1946与1947年间,父亲受阿爷之命去苏北益林,现在是盐城市阜宁县益林乡“探亲”。据母亲回忆,当年大伯曾劝父亲留下来一起干,而我父亲却因家里有五个儿女(当时我的小妹还没出生)拖累而回上海。回来后,父亲悄悄与母亲说:北边[1]苦是苦,人倒蛮开心,是“穷开心”。母亲解释“穷开心”的意思,一是穷,生活艰苦,另外昆山土话中“穷”含“很”之意。父亲虽没留在苏北,但他在思想与行动上是支持大伯他们革命的。
当年的大伯在苏北根据地搞后勤工作,经常把苏北棉花之类的农副产品运到上海卖掉,将卖得的钱换钢材、药品运回苏北,就像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角色。因而他来上海时,一会儿穿西装,一会儿穿长衫,有时打扮得像大老板,有时打扮得像劳动者,而国民党当局已经注意到他了,所以《申报》刊登过一则新闻有大伯的名字[2],说“匪首冯昌伯潜入上海”之类的话。在解放战争时期,大伯采购的不少物资,如钢材、医药等全是当局禁品,有几次在吴淞口被查获,父亲听说大伯的物资被扣,就四处找人疏通关系。当年,都良阿爷也在上海,其与沙孟海、沙文汉两兄弟关系很好,沙文汉是地下党,而沙孟海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工作。父亲可能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帮助大伯的。
都良阿爷说过,慈城冯氏分两大脉络,有的崇儒,是读书人,比较清苦;还有一些冯家是做生意的,开药店,开钱庄,比较有钱。我的祖辈、父辈既不是做学问的,也不是开店办厂的,是职员,为人“打工”的。我小时候,家里生活过得清苦,这是因为我父亲经常失业,而失业缘起是父亲有参加新四军的兄弟,老板一旦晓得父亲的苏北背景就不敢再雇用。
在慈城,儿时的我们常盼信客[3]来。信客来,就是父亲带钱来了,家里有了钱,就能吃到荤腥了。后来我听母亲说,旧时的宁波,带鱼是不上桌请客的,而慈城人反之,不仅能上台面,还视其为吉利,因为带鱼的“带”字寓意带钞票。多吉利的带鱼哟,带鱼对慈城人来说是“讨口彩”的吉祥鱼。
在慈城,我家因父亲经常失业,自然少了生活来源,这就苦了母亲。
慈城冯氏有“败落乡绅不走样”的说法,不管家里怎么清苦,我娘总是让我们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这样母亲就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夏天布衫冬天棉,一年到头纳(慈城方言,音读漆)鞋底。想想也是,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让我们穿脚趾头“笃出”的鞋子,而做鞋的工序又那么多,从褙袼到绱鞋,要经多少道工序,光纳鞋底用的线,就够麻烦了。过去没现成的纳鞋底线,是从穿破的纱袜上拆出线,八并四,四并二,最后搓成纳鞋底线,我们都帮母亲搓过纳鞋底线。做鞋面也是如此,剪样、粘合、绲边,若是棉鞋还要衬棉花,而一双布鞋只能穿几个月。母亲一年到头要做多少双鞋子,我不曾统计过,但只要看我家那些大大小小的鞋楦,就明自母亲曾经的辛苦
在慈城,童年生活虽然紧绷绷的,但很快乐。冯家孩子多,那时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十几个,父辈兄弟敬老爱幼,互相融洽;下代兄弟姐妹也和睦相处,常常聚在一起玩游戏,乘风凉,猜谜语,哼儿歌。我母亲记性特别好,说起慈城民谚民谣一箩筐一箩筐的去年,我写了一篇《诱人的慈城民谣》,后刊登在《海上宁波人》杂志上,文中的谚语、童谣大多是听母亲说的。母亲没上过学,是父亲教她识的字,我读初小,她也拿我的国文课本去学,有时我读不出、写不出,反而是她教我母亲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据传,我家祖上(太太公辈)在东北营口投资开药店,好像是咸春堂,按股子分红,但到了祖父辈已没什么钱,只属“工薪阶层”上面我说过,祖父有六个儿子,而且是差不多年纪娶的媳妇年老的母亲还常说,冯家规矩重,做媳妇难。从早晨替公婆揩灯罩、擦水烟管开始,母亲和妯娌们每天承担一大堆家务,大伯母、婶婶等参加革命后,母亲几乎成了众家媳妇,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而世间总是多做事情多出错,也多招怪,可母亲从不怨天尤人,依旧乐呵呵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这样,母亲以她朴素的语言,勤劳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我很感激家乡慈城、家乡宁波,因为我是慈城冯氏子孙槐花树门头的家,因族人过世的过世,离开的离开,除了20世纪70年代都良阿爷回乡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房子有的空关,有的出租,1976年将年久失修的房屋卖了。可我们还总是惦念慈城,惦念老家,2006年母亲94岁那年,我们兄妹陪她重游故乡
这之前,因工作关系我去过宁波几次。1995年,我带领报社编辑、记者到宁波,在与宁波宣传部门交流如何办好党报时,向市领导承诺《解放日报》重点报道宁波的意向。[1]当时我提出这个设想,不光是因为上海与宁波地域相邻,血缘相近,经济相连,文化相融,也是我情感使然,因为我是来自宁波的游子,是来自慈城的游子。
附注
[1]据记载:1929年5月26日至6月1日,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灵榇从北京碧云寺奉安于南京中山陵,国民党做出了全国下半旗七日志哀,停止一切宴会娱乐七日之类的要求。是年农历四月二十一,阳历为5月29日[2]好日酒:方言,即婚宴
[1]戴头袱:旧时宁波女子出嫁时头上戴的红布。袱,音为篷
[2]太婆:曾祖母。这里口述者借用了孩子对曾祖母的称呼
[1]生活:方言,指工作
[2]娘子:方言,指未出嫁的女孩
[3]纰头:也称贴纰,方言,衣服边缘往里折叠的部分,纰音为皮
[1]据《冯氏福聚宗谱》,绩高堂之名在“彬行”出现(明天启版本,同治丙寅处重订)
[2]据《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清册》(1953年):太湖路32号户名冯劬]存,成分职员,实住2人
[3]这本书:《冯舜华纪念文集》,中建总公司编于1997年4月,后由其子冯皖民看望口述者时赠送
[4]寄拜:一般指为了期望孩子的健康成长,让孩子拜一个多福多寿的人为干爹;慈城冯氏的寄拜大多是寄拜给本家族内的兄弟,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可寄拜给弟弟家,也可寄拜给连襟(即孩子的姨丈)
[1]孙衡甫(1875—1944):又名遵法,慈城半浦人。光绪年间,在上海久源钱庄做学徒,后在信裕、恒隆、恒来、益昌等钱庄参股。1907年,投资创办上海泰来面粉厂。次年,投资四明银行。1910年后,历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主任、经理。1931年起,历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保险公司董事长,并投资上海浙江银行、统原银行、明华银行、苏州信孚银行、苏州电气厂、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穿山轮船公司、上海童涵春国药号、长江煤矿公司、上海宁益银团等,兼任股董等职,还投资上海市房地产业,建造1200幢里弄房屋(现延安西路与巨鹿路间的四明村);热心公益,捐资建造半浦小学,修建慈城至半浦的道路,宁波灵桥建设出资5000元大洋,占总造价的一半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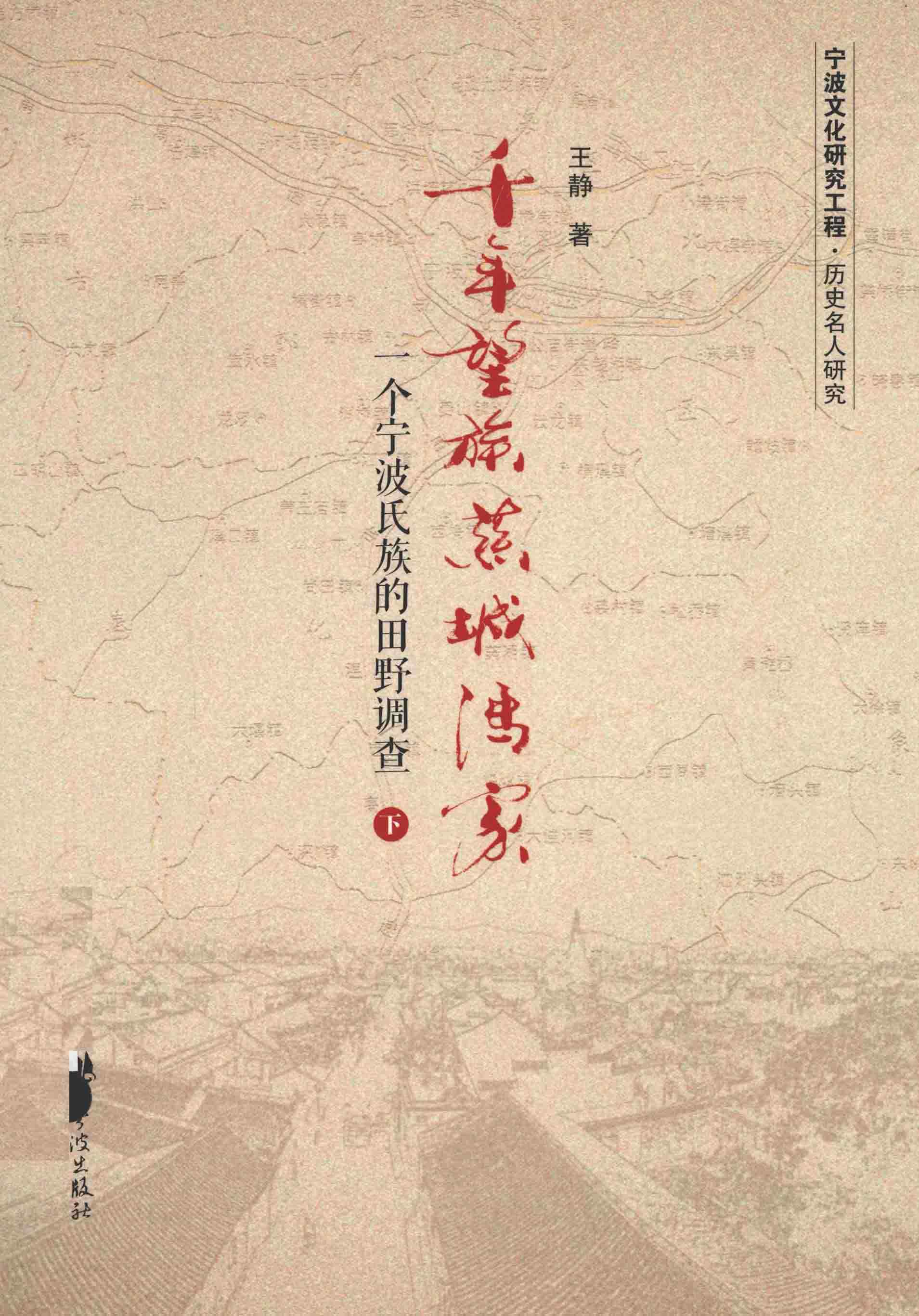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本书是以慈城冯氏众子姓及家族文化为对象,以慈城及海内外的家族文化为参照说明,以历史文献及口述史为依据,结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民俗学,对慈城冯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认为慈城冯氏以寻根、联宗等形式营造家族的精神家园,以凝聚众子姓之心是千年望族的内核,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得以绵延千年不绝的家族秘诀。
阅读
相关地名
慈城镇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