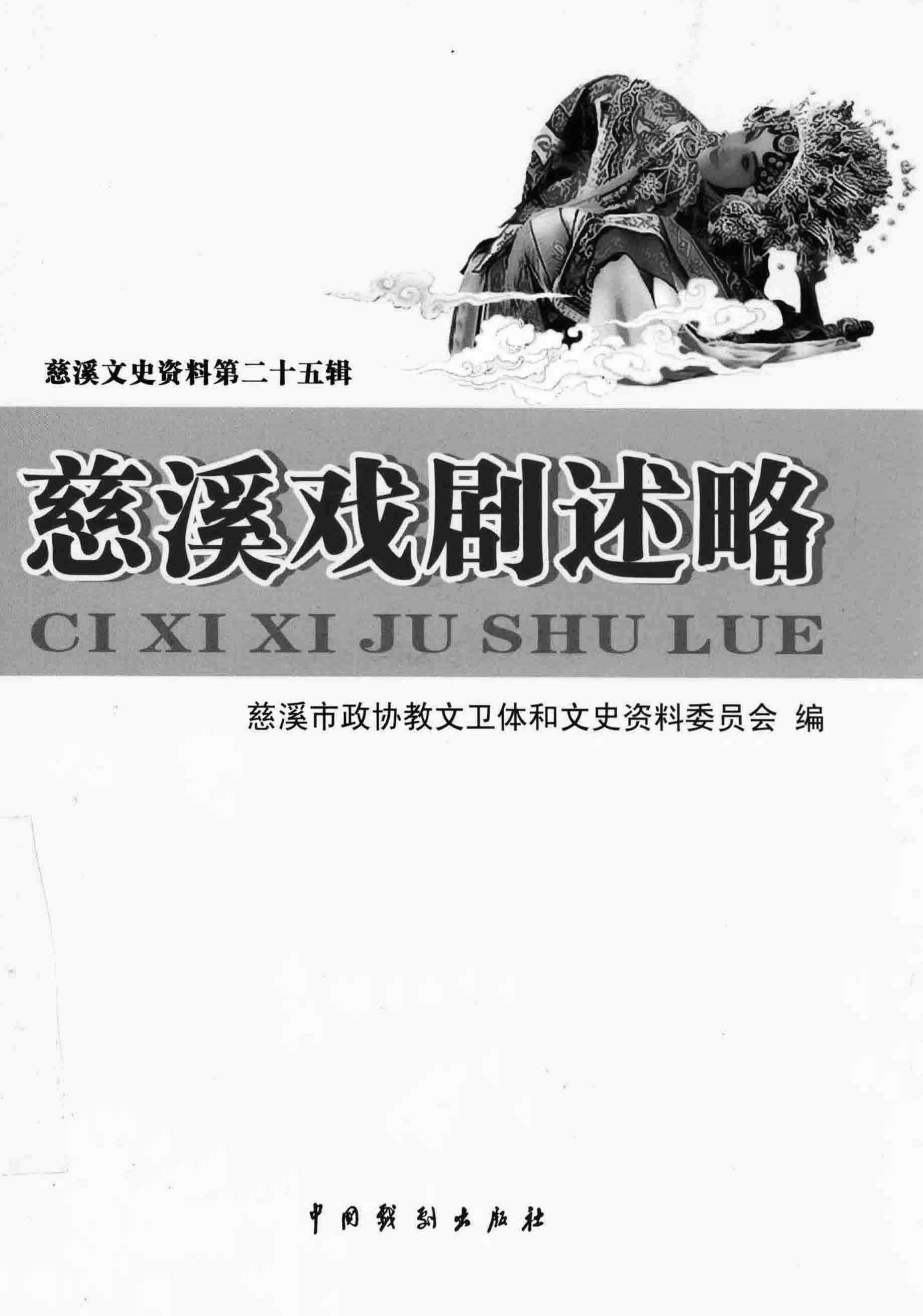内容
徐进,慈溪观海卫镇东山头村人,1923年11月17日出生。1943年春,考进袁雪芬领衔的剧团当编剧,写的第一个戏是《月缺难圆》。此后曾分别担任过芳华剧团、玉兰剧团、东山越艺社和云华剧团的编剧。创作了《木兰从军》、《葛嫩娘》、《天涯梦》及根据《天方夜谭》故事改编的传奇剧《沙漠王子》、现代戏《浪荡子》、《秋海棠》等剧目。上海解放不久,他参加了上海市地方戏剧研究班学习。1950年4月加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参与集体改编越剧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1958年,又将古典小说《红楼梦》改编成越剧《红楼梦》,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剧目赴京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成为剧院的优秀代表作。1962年,此剧又搬上了银幕。徐进从事越剧写作将近60年,一生中,创作或整理改编较有影响的剧目有:《盘夫索夫》、《劈山救母》、《织锦记》、《杏花村》、《金山战鼓》、《花中君子》和现代戏《三月春潮》等。还和林谷、谢晋一起创作了电影剧本《舞台姐妹》及续篇——《泪雨春花》。此外,还发表过许多论文如《词能达意,话如其人——戏曲语言唱词浅析》、《浅谈越剧艺术的个性特色》等,出版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徐进越剧作品选集》。
徐进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越剧院副院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一级编剧。他一生共创作了了58部戏,创作剧本数量之多在全国越剧界位居首位,有“越剧编剧状元”之称。2006年获上海市颁发的“百年越剧特殊贡献艺术家”荣誉奖牌。2010年10月15日,徐进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去世,享年86岁。
我的越剧情怀
徐进
我于1923年出生在浙江慈溪观城镇东山头。我父亲当过钱庄会计。后来长期失业。贫穷便向我家里袭来。我交不起学费,在当地的浙江慈溪锦堂乡村师范附属小学毕了业,没读完中学,便到上海谋生,进了一家西药房。从学徒到职员,干了几年。我感到贫穷虽可怕,但无知比贫穷更可怕。因而我在业余时间发奋读书,还到处看戏,特别是看家乡戏越剧。不仅看戏,还学写戏哩!也许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在石头上坐三年,石头也会发热”吧,我确实靠自学学得了一点知识。再加上西药房比封建性的店铺要“文明”一些,夜里还给学英文、读书。
1942年冬,有一天偶尔发现报上“好友电台”招考越剧编剧的广告,我去报名应考,居然被录取了,而且独占鳌头。事后才知虽以“好友电台”出面,其实招考者乃袁雪芬正开始进行越剧改革的早期的雪声剧团。
这场考试,使后来好多人戏称我为“状元公”,这场考试也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我就这样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担负越剧改革的工作,成为“越剧之家”中的一员。我为越剧写的第一个戏是袁雪芬主演的《月缺难圆》。那时,尽管戏是在小小的仅有三、四百个座位的“大来剧场”演出,尽管生活还是清贫得很,但我已经享受到艺术的乐趣,感觉到它的所谓“魅力”了。
此后,我在尹桂芳所在的芳华剧团,徐玉兰所在的玉兰剧团,范瑞娟、傅全香所在的东山越艺社,竺水招、戚雅仙所在的云华剧团,都担任过编剧或负责过剧务部。
我在解放前为这些剧团写了几十部戏。矮中取长的话,其中如《木兰从军》、《天涯梦》、《葛嫩姐》、《明月重圆夜》等,算是较好的了。由尹桂芳主演的、我根据《天方夜谭》故事改编的传奇剧《沙漠王子》和现代剧《浪荡子》、《秋海棠》,当时虽盛况空前,但现在看来,这些戏也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
我感到解放前我的作品曾一定程度地受到美国电影和中国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因为我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上海。但是正因为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我所吸收和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有它反封建、反暴政等另外的积极的一面。由于我受过老板的压迫,搞的又是当时被人瞧不起的地方戏曲,因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的反感,对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这一切,也必然会闯进我的作品中来。
清代著名的鼓词作家韩小窗有句曰:“小院闲步泼墨迟,牢骚笔写断魂词”这正是旧社会不少戏曲作者的写照,包括我在内。我曾在《记得时》这个戏的,演出说明书上写道:“我不喜欢高贵的人物,因此《记得时》里所跳跃的便是那些孤女、流浪者、牧童、老更夫..这一类带着泥土气息的角色。..幼年的故事写成幼稚的剧本,我不想给大人先生们赏识,我愿献给普通的越剧观众们。”我在某个历史故事剧的说明书上也发过这样的“牢骚”:“历史尚且可以捏造,一个历史以外的故事又算得了什么!”我还在现代戏《十字街头》里,让一个为生活所逼而犯法被判了刑的小职员,在法庭上喊出“这究竟是谁的罪”那种不平之鸣!我和南薇合作的以陈胜、吴广起义为背景写反对暴政的《天涯梦》,曾经触犯了反动当局,而被勒令删改。这些戏虽然“未必笑啼皆中节”,但有的则“敢言怒骂亦成文”。可我的作品真正有点社会影响的话,那是在解放之后。解放后,我一直深深感到党对我的培养,在我的编剧生涯里贯穿着、体现着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由于我是个清贫的靠自学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因而一解放就很自然地靠拢党,有翻身感,容易接受新的进步事物,当时上海的“剧影协会”组织写播音开篇,上街游行,迎接解放,我都兴奋地参加了;以致当我在街上碰到我们曾与之斗争过的一个剧场老板时,他竟一变往日嘴脸,而向我十分恭敬地点头哈腰,据说以为我们这些编导是地下党哩。在解放后的新事物面前,我感到一切是那么陌生而又新鲜,于是产生一种迫切需要了解和学习它的愿望。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就参加了当时军管会文管会办的上海地方戏剧研究班学习。第一次学到了社会发展史的启蒙知识,第一次懂得革命文艺的粗浅道理。1950年4月,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国家办的戏曲团体——华东文化部越剧实验剧团。我和当时云华剧团一部分同志,宁肯减低自己的工资,投入这一革命文艺团体的怀抱。
如果说,解放前我是毕业于“社会大学”的话,那么解放后,特别在50年代,我是在新的社会生活里学习、磨练。党把我放在沸腾的生活洪流里,让我锻炼,吸收知识,受到教育。1950年,我以“记者”的身份参观了松江县的土改试点,使我懂得了《白毛女》故事的巨大价值。1954年,我到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我才亲身感受到这些“兵”为什么能用小米加步枪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1957年底,我参加了上海市委组织的“万人检查团”,下乡检查郊县合作社情况,使我感性地接触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还参加了“五反”运动,掌握过一个老板集中学习的大组,认识了形形色色的老板高明的手腕。我还参加过肃反等等各种运动..这一切,不仅给作家提供了生活积累,增加了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改变着作家的世界观,旧的思想面貌潜移默化地被新的所代替。
“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我总觉得党是给了我很多实践、磨练、压担子的机会,甚至有时感到自己的肩膀只能压80斤,但党却有意要给挑100斤似的。例如在“五反”工作队时,有次队长(一个区委宣传部长)忽然说他不能去某个医学院作报告了,临时竟叫我代他去做一下。那时我还不是个党员(我在1955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水平又很低。我第一次对着话筒,向100多名大专学生战战兢兢地做了个有关“五反”的报告,我从语言贫乏、汗流浃背开始,直到滔滔不绝,辩才无碍。事后,我很感谢那位工作队长,他对我作了次大胆的培养。
说到培养,我不能不怀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而去世的前华东戏曲研究院的领导伊兵同志。他曾经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过一次关于我应当如何真正成为戏曲作家的问题。他再三叮嘱我:作为戏曲作家,你必须打好两个基础,一个是十分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学的基础,另一个是非常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而这两方面,你都是很不够的,正是在伊兵同志的指导下,我除了向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其它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学习外,我把打好基础的重点放在《梁祝》、《红楼梦》这两个戏的创作实践上。我认为只有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才能把《梁祝》这一民间传统戏和《红楼梦》这一古典文学的精髓学到手。
《梁祝》是依靠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保存、流传下来的,经过不少艺人的修改和丰富。如1942年越剧改革后,袁雪芬主演的《梁祝哀史》便作了初步整理。解放后,在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的组织下,以我为主,会同一些同志重新整理改编了它。我们做了很大的加工和重写,还新写了“乔装”、“逼婚”两场戏,并由我作了一系列修改后定稿。该剧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荣获剧本一等奖。
1953年春,《梁祝》由我和桑弧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摄制成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影片。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把影片带到日内瓦会议招待会上放映,使这一外国朋友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民间传说,和“绍兴歌剧”——越剧这一优美抒情的剧种,在国际上受到赞赏。1986年,我又将《梁祝》编写成5集电视连续剧,由上海电视台录制、播出。
我在1955年上海越剧院成立后不久开始改编《红楼梦》。不少人以为改编者是个老翁,其实我时年32岁。这之前我参加过全国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这之后又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工作者会议,说明我那时还是个青年编剧。
我开始刻苦地钻研《红楼梦》原著,做了不少摘记。一进入小说,真像打开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感到曹雪芹的知识是那么丰富。有多少东西可学啊!不仅是性格语言,艺术构思,艺术形象的创造,而且天文地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花鸟草木、园林建筑,甚至是医药常识等等,无所不有,这是我小学时代偷读它时无法体会到的。改编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红楼梦》小说确实在提高我的古典文学修养上起了良师益友的作用。
“欲知山上路,须问过来人”。我也向各种已有的《红楼梦》戏剧作品学习,如《红楼梦散套》、《红楼梦传奇》,以及鼓词、子弟书、评弹、京、川、锡、话等各剧种改编本,成功处学而习之,失败处引以为训。
在改编中,我碰到过无数困难挫折,也走过不少曲径弯道,有时真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找不到出路,深感“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苦战了两年,总算写成剧本。1957年搬上舞台。1959年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剧目赴京演出。也曾赴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泰国等演出。朝鲜国立民族剧院把它翻译成“唱剧”上演。又几次赴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演出。1986年9月该剧还参加了法国巴黎艺术节。该剧1962年就摄成影片,被“四人帮”压制。“文革”后复映时轰动了全国,从这里我得到了一点启示,那就是说,作家要给点压力的好,有时要给自己出点难题;唯其难,才会迫使你百倍努力,才会“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
越剧《红楼梦》还通过导演一次次排戏加工,演员的不断舞台实践,帮助了剧本进一步丰满起来。因此,这件艺术品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欣赏,是许多同志努力的结果。其中还意想不到地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总理生前不仅多次看了越剧《红楼梦》,甚至还和我、徐玉兰等一起去参观了传说就是大观园旧址的“恭王府”,并把我和徐玉兰介绍给闻讯包围拢来的一群大学生。这使我想起了有人说的“周总理他是真正尊重艺术、扶持艺术的知音”这句最恰当不过的话。
除了《梁祝》和《红楼梦》,我还整理了传统小戏《卖婆记》(解放初拍成小型影片)和《盘夫》(曾在《剧本》月刊发表),创作改编的剧本还有《劈山救母》、《金山战鼓》、《花中君子》、《瑞云》等。
当我随《红楼梦》剧组访问朝鲜时,在一次宴会上,一位朝鲜艺术家敬了我一杯酒,并说希望我也能写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其实,历年来我写的现代剧不算少,只是艺术质量不怎么高,自认为稍好的有1954年初根据赵树理小说改编的《小二黑结婚》,1957年创作的反映人民警察挽救失足青年的《生活的道路》,1974、1975年深入农村生活,创作了小戏《乡邮员》。粉碎“四人帮”后,与黄之一、陈鹏合作,创作了《三月春潮》,描写了周恩来同志1927年领导和指挥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使周总理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戏剧舞台上。这个戏赴京参加了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剧本和演出都获得了二等奖,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此外,大家都知道,我还和林谷、谢晋一起创作了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重见天日的故事影片《舞台姐妹》。1981年2月,《剧本》月刊又发表了我和薛允璜合作的它的续篇、8场越剧《泪雨春花》。但这个剧本因种种原因未曾排演,搁置下来了。
除编剧外,我还不断总结写作经验。1962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约7000多字的文章《从小说到戏——谈越剧〈红楼梦〉的改编》,并在各地的进修班、学习班或创作会议上讲课。不少报刊、杂志、电台也对我的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发表了评论。其中,戏剧理论家安葵以《革新的剧作家从传统中获得了优势》为题,发表了1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评介了我的剧本创作。
除编剧外,我曾在1978—1984年担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并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委员。现为一级编剧,越剧院艺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锣鼓长了没好戏”,只是最后还必须说几句:
我是十分热爱浙江,热爱慈溪家乡的,因为我出生在那里。我又在宁波读过中学。1958年,我在四明山区生活、采风,背过毛竹,被新四军三五支队的英雄事迹所激动,被浙东新嫁娘为什么要穿戴凤冠霞帔的民间故事所陶醉。1963年,我在浙西的新安江水力发电站生活过,还住在越剧发源地嵊县的“越剧之家”,和袁雪芬、林谷、谢晋讨论过《舞台姐妹》,还坐着脚划船荡漾于绍兴鉴湖,寻访过万年台、庙台等等各种各样的戏曲舞台。总之一句话:家乡浙江的丽山秀川、文化风物也曾经滋养过我,这也是我所永远不会忘记的。
徐进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越剧院副院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一级编剧。他一生共创作了了58部戏,创作剧本数量之多在全国越剧界位居首位,有“越剧编剧状元”之称。2006年获上海市颁发的“百年越剧特殊贡献艺术家”荣誉奖牌。2010年10月15日,徐进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去世,享年86岁。
我的越剧情怀
徐进
我于1923年出生在浙江慈溪观城镇东山头。我父亲当过钱庄会计。后来长期失业。贫穷便向我家里袭来。我交不起学费,在当地的浙江慈溪锦堂乡村师范附属小学毕了业,没读完中学,便到上海谋生,进了一家西药房。从学徒到职员,干了几年。我感到贫穷虽可怕,但无知比贫穷更可怕。因而我在业余时间发奋读书,还到处看戏,特别是看家乡戏越剧。不仅看戏,还学写戏哩!也许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在石头上坐三年,石头也会发热”吧,我确实靠自学学得了一点知识。再加上西药房比封建性的店铺要“文明”一些,夜里还给学英文、读书。
1942年冬,有一天偶尔发现报上“好友电台”招考越剧编剧的广告,我去报名应考,居然被录取了,而且独占鳌头。事后才知虽以“好友电台”出面,其实招考者乃袁雪芬正开始进行越剧改革的早期的雪声剧团。
这场考试,使后来好多人戏称我为“状元公”,这场考试也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我就这样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担负越剧改革的工作,成为“越剧之家”中的一员。我为越剧写的第一个戏是袁雪芬主演的《月缺难圆》。那时,尽管戏是在小小的仅有三、四百个座位的“大来剧场”演出,尽管生活还是清贫得很,但我已经享受到艺术的乐趣,感觉到它的所谓“魅力”了。
此后,我在尹桂芳所在的芳华剧团,徐玉兰所在的玉兰剧团,范瑞娟、傅全香所在的东山越艺社,竺水招、戚雅仙所在的云华剧团,都担任过编剧或负责过剧务部。
我在解放前为这些剧团写了几十部戏。矮中取长的话,其中如《木兰从军》、《天涯梦》、《葛嫩姐》、《明月重圆夜》等,算是较好的了。由尹桂芳主演的、我根据《天方夜谭》故事改编的传奇剧《沙漠王子》和现代剧《浪荡子》、《秋海棠》,当时虽盛况空前,但现在看来,这些戏也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
我感到解放前我的作品曾一定程度地受到美国电影和中国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因为我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上海。但是正因为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我所吸收和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有它反封建、反暴政等另外的积极的一面。由于我受过老板的压迫,搞的又是当时被人瞧不起的地方戏曲,因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的反感,对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这一切,也必然会闯进我的作品中来。
清代著名的鼓词作家韩小窗有句曰:“小院闲步泼墨迟,牢骚笔写断魂词”这正是旧社会不少戏曲作者的写照,包括我在内。我曾在《记得时》这个戏的,演出说明书上写道:“我不喜欢高贵的人物,因此《记得时》里所跳跃的便是那些孤女、流浪者、牧童、老更夫..这一类带着泥土气息的角色。..幼年的故事写成幼稚的剧本,我不想给大人先生们赏识,我愿献给普通的越剧观众们。”我在某个历史故事剧的说明书上也发过这样的“牢骚”:“历史尚且可以捏造,一个历史以外的故事又算得了什么!”我还在现代戏《十字街头》里,让一个为生活所逼而犯法被判了刑的小职员,在法庭上喊出“这究竟是谁的罪”那种不平之鸣!我和南薇合作的以陈胜、吴广起义为背景写反对暴政的《天涯梦》,曾经触犯了反动当局,而被勒令删改。这些戏虽然“未必笑啼皆中节”,但有的则“敢言怒骂亦成文”。可我的作品真正有点社会影响的话,那是在解放之后。解放后,我一直深深感到党对我的培养,在我的编剧生涯里贯穿着、体现着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由于我是个清贫的靠自学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因而一解放就很自然地靠拢党,有翻身感,容易接受新的进步事物,当时上海的“剧影协会”组织写播音开篇,上街游行,迎接解放,我都兴奋地参加了;以致当我在街上碰到我们曾与之斗争过的一个剧场老板时,他竟一变往日嘴脸,而向我十分恭敬地点头哈腰,据说以为我们这些编导是地下党哩。在解放后的新事物面前,我感到一切是那么陌生而又新鲜,于是产生一种迫切需要了解和学习它的愿望。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就参加了当时军管会文管会办的上海地方戏剧研究班学习。第一次学到了社会发展史的启蒙知识,第一次懂得革命文艺的粗浅道理。1950年4月,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国家办的戏曲团体——华东文化部越剧实验剧团。我和当时云华剧团一部分同志,宁肯减低自己的工资,投入这一革命文艺团体的怀抱。
如果说,解放前我是毕业于“社会大学”的话,那么解放后,特别在50年代,我是在新的社会生活里学习、磨练。党把我放在沸腾的生活洪流里,让我锻炼,吸收知识,受到教育。1950年,我以“记者”的身份参观了松江县的土改试点,使我懂得了《白毛女》故事的巨大价值。1954年,我到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我才亲身感受到这些“兵”为什么能用小米加步枪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1957年底,我参加了上海市委组织的“万人检查团”,下乡检查郊县合作社情况,使我感性地接触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还参加了“五反”运动,掌握过一个老板集中学习的大组,认识了形形色色的老板高明的手腕。我还参加过肃反等等各种运动..这一切,不仅给作家提供了生活积累,增加了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改变着作家的世界观,旧的思想面貌潜移默化地被新的所代替。
“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我总觉得党是给了我很多实践、磨练、压担子的机会,甚至有时感到自己的肩膀只能压80斤,但党却有意要给挑100斤似的。例如在“五反”工作队时,有次队长(一个区委宣传部长)忽然说他不能去某个医学院作报告了,临时竟叫我代他去做一下。那时我还不是个党员(我在1955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水平又很低。我第一次对着话筒,向100多名大专学生战战兢兢地做了个有关“五反”的报告,我从语言贫乏、汗流浃背开始,直到滔滔不绝,辩才无碍。事后,我很感谢那位工作队长,他对我作了次大胆的培养。
说到培养,我不能不怀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而去世的前华东戏曲研究院的领导伊兵同志。他曾经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过一次关于我应当如何真正成为戏曲作家的问题。他再三叮嘱我:作为戏曲作家,你必须打好两个基础,一个是十分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学的基础,另一个是非常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而这两方面,你都是很不够的,正是在伊兵同志的指导下,我除了向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其它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学习外,我把打好基础的重点放在《梁祝》、《红楼梦》这两个戏的创作实践上。我认为只有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才能把《梁祝》这一民间传统戏和《红楼梦》这一古典文学的精髓学到手。
《梁祝》是依靠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保存、流传下来的,经过不少艺人的修改和丰富。如1942年越剧改革后,袁雪芬主演的《梁祝哀史》便作了初步整理。解放后,在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的组织下,以我为主,会同一些同志重新整理改编了它。我们做了很大的加工和重写,还新写了“乔装”、“逼婚”两场戏,并由我作了一系列修改后定稿。该剧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荣获剧本一等奖。
1953年春,《梁祝》由我和桑弧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摄制成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影片。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把影片带到日内瓦会议招待会上放映,使这一外国朋友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民间传说,和“绍兴歌剧”——越剧这一优美抒情的剧种,在国际上受到赞赏。1986年,我又将《梁祝》编写成5集电视连续剧,由上海电视台录制、播出。
我在1955年上海越剧院成立后不久开始改编《红楼梦》。不少人以为改编者是个老翁,其实我时年32岁。这之前我参加过全国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这之后又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工作者会议,说明我那时还是个青年编剧。
我开始刻苦地钻研《红楼梦》原著,做了不少摘记。一进入小说,真像打开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感到曹雪芹的知识是那么丰富。有多少东西可学啊!不仅是性格语言,艺术构思,艺术形象的创造,而且天文地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花鸟草木、园林建筑,甚至是医药常识等等,无所不有,这是我小学时代偷读它时无法体会到的。改编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红楼梦》小说确实在提高我的古典文学修养上起了良师益友的作用。
“欲知山上路,须问过来人”。我也向各种已有的《红楼梦》戏剧作品学习,如《红楼梦散套》、《红楼梦传奇》,以及鼓词、子弟书、评弹、京、川、锡、话等各剧种改编本,成功处学而习之,失败处引以为训。
在改编中,我碰到过无数困难挫折,也走过不少曲径弯道,有时真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找不到出路,深感“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苦战了两年,总算写成剧本。1957年搬上舞台。1959年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剧目赴京演出。也曾赴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泰国等演出。朝鲜国立民族剧院把它翻译成“唱剧”上演。又几次赴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演出。1986年9月该剧还参加了法国巴黎艺术节。该剧1962年就摄成影片,被“四人帮”压制。“文革”后复映时轰动了全国,从这里我得到了一点启示,那就是说,作家要给点压力的好,有时要给自己出点难题;唯其难,才会迫使你百倍努力,才会“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
越剧《红楼梦》还通过导演一次次排戏加工,演员的不断舞台实践,帮助了剧本进一步丰满起来。因此,这件艺术品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欣赏,是许多同志努力的结果。其中还意想不到地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总理生前不仅多次看了越剧《红楼梦》,甚至还和我、徐玉兰等一起去参观了传说就是大观园旧址的“恭王府”,并把我和徐玉兰介绍给闻讯包围拢来的一群大学生。这使我想起了有人说的“周总理他是真正尊重艺术、扶持艺术的知音”这句最恰当不过的话。
除了《梁祝》和《红楼梦》,我还整理了传统小戏《卖婆记》(解放初拍成小型影片)和《盘夫》(曾在《剧本》月刊发表),创作改编的剧本还有《劈山救母》、《金山战鼓》、《花中君子》、《瑞云》等。
当我随《红楼梦》剧组访问朝鲜时,在一次宴会上,一位朝鲜艺术家敬了我一杯酒,并说希望我也能写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其实,历年来我写的现代剧不算少,只是艺术质量不怎么高,自认为稍好的有1954年初根据赵树理小说改编的《小二黑结婚》,1957年创作的反映人民警察挽救失足青年的《生活的道路》,1974、1975年深入农村生活,创作了小戏《乡邮员》。粉碎“四人帮”后,与黄之一、陈鹏合作,创作了《三月春潮》,描写了周恩来同志1927年领导和指挥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使周总理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戏剧舞台上。这个戏赴京参加了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剧本和演出都获得了二等奖,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此外,大家都知道,我还和林谷、谢晋一起创作了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重见天日的故事影片《舞台姐妹》。1981年2月,《剧本》月刊又发表了我和薛允璜合作的它的续篇、8场越剧《泪雨春花》。但这个剧本因种种原因未曾排演,搁置下来了。
除编剧外,我还不断总结写作经验。1962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约7000多字的文章《从小说到戏——谈越剧〈红楼梦〉的改编》,并在各地的进修班、学习班或创作会议上讲课。不少报刊、杂志、电台也对我的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发表了评论。其中,戏剧理论家安葵以《革新的剧作家从传统中获得了优势》为题,发表了1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评介了我的剧本创作。
除编剧外,我曾在1978—1984年担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并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委员。现为一级编剧,越剧院艺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锣鼓长了没好戏”,只是最后还必须说几句:
我是十分热爱浙江,热爱慈溪家乡的,因为我出生在那里。我又在宁波读过中学。1958年,我在四明山区生活、采风,背过毛竹,被新四军三五支队的英雄事迹所激动,被浙东新嫁娘为什么要穿戴凤冠霞帔的民间故事所陶醉。1963年,我在浙西的新安江水力发电站生活过,还住在越剧发源地嵊县的“越剧之家”,和袁雪芬、林谷、谢晋讨论过《舞台姐妹》,还坐着脚划船荡漾于绍兴鉴湖,寻访过万年台、庙台等等各种各样的戏曲舞台。总之一句话:家乡浙江的丽山秀川、文化风物也曾经滋养过我,这也是我所永远不会忘记的。
相关人物
徐进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慈溪市
相关地名
相关作品
《我的越剧情怀》
相关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