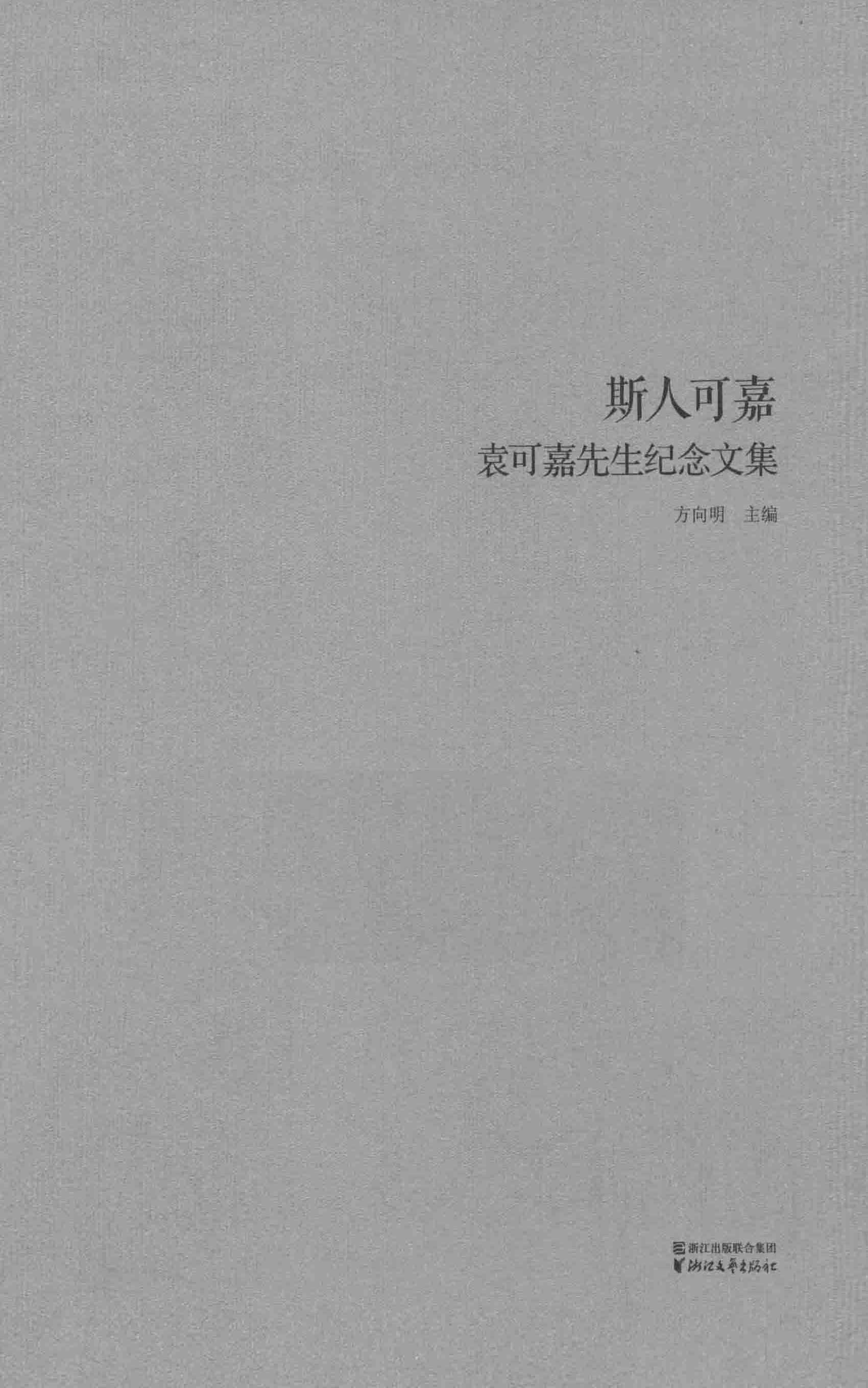内容
从时间上看,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处于一个历史关节点上:它是对于此前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次梳理和总结,更是对这一处于历史上升期、具有无限前景的“诗的新生代”①的歌赞和呼唤。但现实发展却强有力地扭转、改变了这一文化逻辑,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里现代主义诗歌失去了合法性,几近绝迹,“新诗现代化”理论也命运多舛,不是被批判便是被遗忘。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阶段,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伴随近年来从精英主义、理想主义氛围到消费主义、娱乐化的文化嬗递,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今,共和国时逢甲子,反观六十余年前袁可嘉有关“新诗现代化”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和识见,它们是超越了当时和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诗歌的主流认知的。同时,“新诗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也有某种互文性,两者的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和重合之处,两相对照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一些重要的、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与经验。
一
如其字面意义所示,“新诗现代化”强调的是新诗的“现代化”,这在袁可嘉的表述中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比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间接性”、“暗示性”、“戏剧化”、“戏剧主义”等。这种“现代化”从另外的角度讲,我们可以说它表达的是对于新诗“复杂性”的追求,这种“复杂”一方面是针对现代社会变幻莫测、错综暖昧的外部现实的,另一方面则是针对现代人纠缠莫辨、混沌交织的内心处境和心理现实的。面对变化了的现实状况,古典主义的“简单”、“单纯”已经很难担负起表达现代人的内心的任务,而只有多元、复杂、歧异、暖昧、混沌、反讽、悖沦、荒诞等等才能更为贴近现代人的生存,才更富有“及物性”和表现力。这是现代主义诗歌发生的内在根源,也是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他自己有如此的论述,“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新诗现代化)它不仅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即说它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似亦不过”①。
从“复杂性”的视角,我们可以予“新诗现代化”理论以一种不无意义的解读。关于“现代化”的新诗的特征,袁可嘉强调它是一种“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里面显然包含对于诗歌复杂性的体认和追求。他说:“表现在现代诗人作品中突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以及现代神话、现代诗剧所清晰呈现的对现代人生、文化的综合尝试都与批评理论所指出的方向同步齐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短句作为结论的结论,则我们似可说,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②关于新诗的戏剧化、戏剧主义,实际也包含异质因素的呈现、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和辩驳等,这也包含着敞开事物的复杂性,而摒弃对于思想与情绪简单、直接、粗暴的处理。袁可嘉在论述中介绍和引用了瑞恰慈关于“包含的诗”与“排斥的诗”的说法,“唯情的十九世纪的浪漫诗和唯理的十八世纪的假古典诗都是‘排斥的诗’,即是只能容纳一种单纯的,往往也是极端的,人生态度的诗,结果一则感伤,一则说教,诗品都不算高……只有莎翁的悲剧、多恩的玄学诗及艾略特以来的现代诗才称得上是‘包含的诗’;它们都包含冲突,矛盾,而象悲剧一样地终止于更高的调和。它们都有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特征”①。在另外的文章中,他所指出的显然是对于上述观点的延伸,“新诗的毛病表现为平行的二种: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二者都只是自我描写,都不足以说服读者或感动他人……那么,如何使这些意志和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笔者的答复即是本文的题目:《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和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②。关于具体的写作方法,他指出“戏剧效果的第一个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③关于现代诗的“晦涩”,这大概是它最为人诟病,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的问题,袁可嘉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辩护,他指出“正如文学上的‘浪漫’并不与‘浪荡’同义,‘古典’也非‘古板’,现代诗的晦涩也就不等于用文字捉迷藏,以别人的莫名作自己的得意。它之成为一个现代诗的通性与特性,虽都出于诗人的寓意,但绝非毫无辩白余地”。他从“现代诗人所处的厄境”与“传统价值的解体”、“现代诗人的一种偏爱:想从奇异的复杂获得奇异的丰富”、“情绪渗透”、“构造意象或运用隐喻明喻的特殊法则”、“故意荒唐地运用文字”等方面分析了“晦涩成因的五种主型”,指出“现代诗中晦涩的存在,一方面有它社会的,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也确有特殊的艺术价值”。④如果我们从“复杂性”角度来看,现代诗的“晦涩”问题也可得到解释:由于现代诗人对于事物更为深入的观照和理解,他们有着对于内在、复杂、深沉的追求,其文本构成了一个独异的世界,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对它的理解需要能力相当、与之相匹配的心智活动。晦涩的现代诗虽然有些难懂,可能为故弄玄虚者所利用,但更重要的是使得诗歌更复杂和丰富,也更有意味和表现力,因而这种“晦涩”是不容轻易否定的。
袁可嘉还谈到了诗歌与“民主”的关系,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有创见也很有建设性的观点,是他关于新诗“现代化”、“戏剧化”论述的发展,同时也与新诗的“复杂性”问题密切相关。他认为应该追求一种“民主文化”,“无论把民主定义为外观的文化模式或内在的意识形态,它都具有下述的儿种特征:它是辩证的(从不同中产生和谐),包含的(有关的因素都有独立的地位),戏剧的(通过矛盾冲突而得平衡),复杂的(因有不同存在),创造的(各部分都有充分生机),有机的(以部分配合全体而不失去独立性),现代的,而非直线的,简化的,排他的,反映的,机械的和原始的”。①这显然与巴赫金关于小说的“复调”与“对话”的论述有些相似,同样都是契合现代艺术精神的有识之见。“民主文化”是“从不同中求得和谐”,“民主”的,也是“现代”的,“民主文化是现代的文化,民主的诗也必须是现代的诗”,“我们所要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包括民主政治的现代民主文化,我们所要争取的诗也必然是现代化的民主的诗”。②这显然是一个颇为诱人、具有广阔前景的文化命题,而如果联系现实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无疑可以给人更多有意义的启示。
二
通过以上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到,袁可嘉的诗歌理论秉持的是纯正的文学立场。在这里,文学本身即是目的,它不是其他任何事物的附庸、工具、注脚,这在20世纪40年代混乱、焦灼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是头脑清醒、比较“另类”的。评论家蓝棣之为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写的评论文章中说:“他的着眼点,是在文学本身,在文学内部。他这一系列论文的价值,在于他执着地坚持了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①这确实道出了袁可嘉诗论的立足点和基本取向。袁可嘉在《我的文学观》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学的基本看法:“一个比较完美的文学观,如我在上面所指陈的,一定得包含社会学,心理学的和美学的三个方面;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的价值在对于社会的传达;从心理学来说,它的价值在个人的创造;从美学来说,它的价值在文字的艺术,而三者绝对是相辅相成,有机综合的,否则即不会有文学作品。”同时,他着重强调“尤为重要的,无论从哪一观点来看文学,我们的目的都在欣赏文学,研究文学,创造文学,而非别的”。②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之间,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人的文学”的“宗奉者”,是以人(生命)和文学(艺术)为本位的。当然,与个人主义传统长期浸淫下的西方文化观点有所不同(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袁可嘉诗论并非完全取法于西方,而是与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相关联的),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比较辩证、包容的,绝非一味的“西化”,“而我必须重复陈述一个根本的中心观念: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③。他是在尊重文学、尊重人的基础上同时注意发挥文学的政
”治作用并服务于人民的,而并没有落入为艺术而艺术、唯艺术是从的窠臼。袁可嘉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当然是正确的,是对于在坚持文学特质的前提下发挥其现实效用的比较全面的认识。
不过,现实却并没有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展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纯洁化”的要求一次次整肃、冲刷着人的头脑,“左”的甚至“极左”的文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新诗现代化”这种不无“自由化”倾向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清理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它自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而是被纳入了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的规划中,充当了为现实政治“鼓与呼”的“战士”与“歌手”角色,而绝无独立发展、自由探索的可能,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变得简单、直接、明朗、通俗,成了政治的图解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以当时的标准看,有“复杂性”追求的“新诗现代化”理论显然是“反动”、“错误”的:其痛苦、暖昧、绝望、混沌的思想是“不健康”的,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低级”的趣味;而其晦涩、多义、迂回的表达则是“无病呻吟”、“故弄玄虚”、“语言至上”的,所有这些都是与“进步”的、“人民”的文艺背道而驰的,是需要被铲除的“毒草”。或者说,文学被认为应该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新诗现代化”以及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被打入冷官也就成为必然。这一时期袁可嘉的文学活动主要从评论和创作转向了“研究”,他写作了如《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新批评派述评》《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①等文章,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以政治立场、阶级立场代替了文学立场,政治话语、阶级话语替换了文学话语,从而做出了与“新诗现代化”理论迥异的论断。多年以后,他在评价这些文章的时候反思道:“我已完全忘却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对待文艺现象的准则,忘却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染上了不分是非,一律骂倒的粗暴作风。这是我生平一大失误,事实证明,这种恶劣做法,既无益学术,也不利政治,这要到70年代后期才得到改正。这个惨痛教训是我一生难忘的。”②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现代主义诗歌不但没有往前发展,反而是大幅度后退的,这其中有意识形态因素的“敌对”作用,也有艺术观念和方式上不合“规范”的原因,但不管怎样,其“合法性”已然失去,偌大文坛已难觅其容身之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虽然没有完全绝迹,但确实是寥寥无几的,我们看到,在“十七年”与“文革”期间,大概只有“潜在写作”的若干人以秘密的、“非法”的方式写作了为数不多的现代主义诗歌。当然,这其中也有诗人写出了优异的足以传世之作(比如穆旦、食指),但总体上现代主义写作是寥落、冷清的,成就也不高。当然,不管精神控制多么严密,思想的禁区总会有人去僭越。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以“小圈子”的形式组成了若干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写作群体,这其中有比如郭世英、张鹤慈等的“X社”,张郎郎等的“太阳纵队”,芒克、多多、根子等的“白洋淀诗群”,黄翔、哑默等的“贵州诗人群”,这些群体有的仅露出些异质性的“苗头”便被打压下去,有的则由于管制的缝隙而在现代主义的道路上走出了相当的距离。不过总的来说进行这样的写作是有风险的,其影响范围并不大,公开发表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它们一直以“潜流”的形式存在,真正的“冲出历史地表”要等到70年代末的诗歌民刊《今天》,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呼唤、引领社会变革和文学变革的作用,并开启了新一轮的现代主义写作大潮。
历史往往是呈“之”字形行进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又一次发生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面向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开放”,与此前极权主义的文化发展模式相比较,此时显然有了更多的民主因素,在表达的自由度、文学的主体性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久被压抑的现代主义写作倾向也终于有了表达的可能。应该看到,这种现代主义的写作绝非外力引导的结果,而实在是自发、自然而然的,它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人的处境、人的内心相契合的,它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相似更多是“不谋而合”而非“崇洋媚外”。从“复杂性”角度讲,社会开始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允许对于事物更为复杂、深入的探寻和表达,允许人的主体性、文学主体性的探求,这无疑是现代主义诗歌出现的基础。就诗歌的技术层面来讲,袁可嘉所说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戏剧化”、“客观性与间接性”无疑也重新获得了合法性,并且得到了诗人们的青睐,新的写作蔚为大观,开辟出了崭新的写作气象。当然,对于这种“复杂性”的认知和接受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朦胧诗”一开始便是作为负面概念提出的,用以指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的“难懂”、“怪诞”、“玄虚”。①但毫无疑问,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在这一时期的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时代的主流,是包含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意义的,因而也是不可能被轻易扼杀、取缔的。这可以被视为40年代现代主义写作的一种延续和再出发,但较之40年代的诗歌探索,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压抑和遮蔽,80年代的现代主义写作(其主体多为与40年代后期的“九叶”诗人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显得更有活力、更富激情,显示出了创作能量的“爆炸”和创作的“井喷”现象。80年代中期,以《他们》《非非》《莽汉》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在“朦胧诗”之后登场,到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①可谓蔚为大观,这其中绝大多数为现代主义的写作,诗歌写作的可能性被极大丰富了。这一时期诗歌的现代主义写作其成就有目共睹,它们共同书写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新的篇章,丰富了当代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技法,提高了其艺术容量和艺术能力。由此,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生长性,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是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和现代理性的发展相联系的,它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认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人为的阻拒或扭转都是不符合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的,难逃失败的结局。当然,“复杂性”本身并非现代主义的唯一规定性本质,它只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复杂”本身便包含了异质、多元的成分,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复杂”的否定,而由“现代主义”发展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更是明显地包含了对“复杂”的反动:解构、反智、直白、无意义、调侃、游戏……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初见端倪,90年代已具规模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一方面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之的反叛和僭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难辨的。不过,面对当下中国的实际,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出疑问: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理性精神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而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这种状况下的解构、反智、调侃是否会造成理性精神的下降和人文素养的降低?在主体意识并不强大甚至尚未真正确立的情况下急于颠覆、解构个人主体,是否逾越阶段、提前加剧了“人的死亡”?一味的口语化、简单化、游戏化是否会落入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的陷阱而为其同化,并造成诗性内涵、诗歌精神的流失?这恐怕是当下诗歌所面临的不能说不重要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从“复杂性”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致经历了“追求——不被允许——再度追求”的过程,这其中与政治、民主、文学观念、艺术方法等都有多重的复杂联系,有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
一
如其字面意义所示,“新诗现代化”强调的是新诗的“现代化”,这在袁可嘉的表述中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比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间接性”、“暗示性”、“戏剧化”、“戏剧主义”等。这种“现代化”从另外的角度讲,我们可以说它表达的是对于新诗“复杂性”的追求,这种“复杂”一方面是针对现代社会变幻莫测、错综暖昧的外部现实的,另一方面则是针对现代人纠缠莫辨、混沌交织的内心处境和心理现实的。面对变化了的现实状况,古典主义的“简单”、“单纯”已经很难担负起表达现代人的内心的任务,而只有多元、复杂、歧异、暖昧、混沌、反讽、悖沦、荒诞等等才能更为贴近现代人的生存,才更富有“及物性”和表现力。这是现代主义诗歌发生的内在根源,也是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他自己有如此的论述,“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新诗现代化)它不仅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即说它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似亦不过”①。
从“复杂性”的视角,我们可以予“新诗现代化”理论以一种不无意义的解读。关于“现代化”的新诗的特征,袁可嘉强调它是一种“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里面显然包含对于诗歌复杂性的体认和追求。他说:“表现在现代诗人作品中突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以及现代神话、现代诗剧所清晰呈现的对现代人生、文化的综合尝试都与批评理论所指出的方向同步齐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短句作为结论的结论,则我们似可说,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②关于新诗的戏剧化、戏剧主义,实际也包含异质因素的呈现、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和辩驳等,这也包含着敞开事物的复杂性,而摒弃对于思想与情绪简单、直接、粗暴的处理。袁可嘉在论述中介绍和引用了瑞恰慈关于“包含的诗”与“排斥的诗”的说法,“唯情的十九世纪的浪漫诗和唯理的十八世纪的假古典诗都是‘排斥的诗’,即是只能容纳一种单纯的,往往也是极端的,人生态度的诗,结果一则感伤,一则说教,诗品都不算高……只有莎翁的悲剧、多恩的玄学诗及艾略特以来的现代诗才称得上是‘包含的诗’;它们都包含冲突,矛盾,而象悲剧一样地终止于更高的调和。它们都有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特征”①。在另外的文章中,他所指出的显然是对于上述观点的延伸,“新诗的毛病表现为平行的二种: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二者都只是自我描写,都不足以说服读者或感动他人……那么,如何使这些意志和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笔者的答复即是本文的题目:《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和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②。关于具体的写作方法,他指出“戏剧效果的第一个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③关于现代诗的“晦涩”,这大概是它最为人诟病,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的问题,袁可嘉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辩护,他指出“正如文学上的‘浪漫’并不与‘浪荡’同义,‘古典’也非‘古板’,现代诗的晦涩也就不等于用文字捉迷藏,以别人的莫名作自己的得意。它之成为一个现代诗的通性与特性,虽都出于诗人的寓意,但绝非毫无辩白余地”。他从“现代诗人所处的厄境”与“传统价值的解体”、“现代诗人的一种偏爱:想从奇异的复杂获得奇异的丰富”、“情绪渗透”、“构造意象或运用隐喻明喻的特殊法则”、“故意荒唐地运用文字”等方面分析了“晦涩成因的五种主型”,指出“现代诗中晦涩的存在,一方面有它社会的,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也确有特殊的艺术价值”。④如果我们从“复杂性”角度来看,现代诗的“晦涩”问题也可得到解释:由于现代诗人对于事物更为深入的观照和理解,他们有着对于内在、复杂、深沉的追求,其文本构成了一个独异的世界,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对它的理解需要能力相当、与之相匹配的心智活动。晦涩的现代诗虽然有些难懂,可能为故弄玄虚者所利用,但更重要的是使得诗歌更复杂和丰富,也更有意味和表现力,因而这种“晦涩”是不容轻易否定的。
袁可嘉还谈到了诗歌与“民主”的关系,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有创见也很有建设性的观点,是他关于新诗“现代化”、“戏剧化”论述的发展,同时也与新诗的“复杂性”问题密切相关。他认为应该追求一种“民主文化”,“无论把民主定义为外观的文化模式或内在的意识形态,它都具有下述的儿种特征:它是辩证的(从不同中产生和谐),包含的(有关的因素都有独立的地位),戏剧的(通过矛盾冲突而得平衡),复杂的(因有不同存在),创造的(各部分都有充分生机),有机的(以部分配合全体而不失去独立性),现代的,而非直线的,简化的,排他的,反映的,机械的和原始的”。①这显然与巴赫金关于小说的“复调”与“对话”的论述有些相似,同样都是契合现代艺术精神的有识之见。“民主文化”是“从不同中求得和谐”,“民主”的,也是“现代”的,“民主文化是现代的文化,民主的诗也必须是现代的诗”,“我们所要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包括民主政治的现代民主文化,我们所要争取的诗也必然是现代化的民主的诗”。②这显然是一个颇为诱人、具有广阔前景的文化命题,而如果联系现实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无疑可以给人更多有意义的启示。
二
通过以上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到,袁可嘉的诗歌理论秉持的是纯正的文学立场。在这里,文学本身即是目的,它不是其他任何事物的附庸、工具、注脚,这在20世纪40年代混乱、焦灼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是头脑清醒、比较“另类”的。评论家蓝棣之为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写的评论文章中说:“他的着眼点,是在文学本身,在文学内部。他这一系列论文的价值,在于他执着地坚持了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①这确实道出了袁可嘉诗论的立足点和基本取向。袁可嘉在《我的文学观》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学的基本看法:“一个比较完美的文学观,如我在上面所指陈的,一定得包含社会学,心理学的和美学的三个方面;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的价值在对于社会的传达;从心理学来说,它的价值在个人的创造;从美学来说,它的价值在文字的艺术,而三者绝对是相辅相成,有机综合的,否则即不会有文学作品。”同时,他着重强调“尤为重要的,无论从哪一观点来看文学,我们的目的都在欣赏文学,研究文学,创造文学,而非别的”。②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之间,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人的文学”的“宗奉者”,是以人(生命)和文学(艺术)为本位的。当然,与个人主义传统长期浸淫下的西方文化观点有所不同(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袁可嘉诗论并非完全取法于西方,而是与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相关联的),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比较辩证、包容的,绝非一味的“西化”,“而我必须重复陈述一个根本的中心观念: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③。他是在尊重文学、尊重人的基础上同时注意发挥文学的政
”治作用并服务于人民的,而并没有落入为艺术而艺术、唯艺术是从的窠臼。袁可嘉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当然是正确的,是对于在坚持文学特质的前提下发挥其现实效用的比较全面的认识。
不过,现实却并没有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展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纯洁化”的要求一次次整肃、冲刷着人的头脑,“左”的甚至“极左”的文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新诗现代化”这种不无“自由化”倾向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清理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它自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而是被纳入了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的规划中,充当了为现实政治“鼓与呼”的“战士”与“歌手”角色,而绝无独立发展、自由探索的可能,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变得简单、直接、明朗、通俗,成了政治的图解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以当时的标准看,有“复杂性”追求的“新诗现代化”理论显然是“反动”、“错误”的:其痛苦、暖昧、绝望、混沌的思想是“不健康”的,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低级”的趣味;而其晦涩、多义、迂回的表达则是“无病呻吟”、“故弄玄虚”、“语言至上”的,所有这些都是与“进步”的、“人民”的文艺背道而驰的,是需要被铲除的“毒草”。或者说,文学被认为应该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新诗现代化”以及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被打入冷官也就成为必然。这一时期袁可嘉的文学活动主要从评论和创作转向了“研究”,他写作了如《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新批评派述评》《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①等文章,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以政治立场、阶级立场代替了文学立场,政治话语、阶级话语替换了文学话语,从而做出了与“新诗现代化”理论迥异的论断。多年以后,他在评价这些文章的时候反思道:“我已完全忘却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对待文艺现象的准则,忘却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染上了不分是非,一律骂倒的粗暴作风。这是我生平一大失误,事实证明,这种恶劣做法,既无益学术,也不利政治,这要到70年代后期才得到改正。这个惨痛教训是我一生难忘的。”②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现代主义诗歌不但没有往前发展,反而是大幅度后退的,这其中有意识形态因素的“敌对”作用,也有艺术观念和方式上不合“规范”的原因,但不管怎样,其“合法性”已然失去,偌大文坛已难觅其容身之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虽然没有完全绝迹,但确实是寥寥无几的,我们看到,在“十七年”与“文革”期间,大概只有“潜在写作”的若干人以秘密的、“非法”的方式写作了为数不多的现代主义诗歌。当然,这其中也有诗人写出了优异的足以传世之作(比如穆旦、食指),但总体上现代主义写作是寥落、冷清的,成就也不高。当然,不管精神控制多么严密,思想的禁区总会有人去僭越。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以“小圈子”的形式组成了若干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写作群体,这其中有比如郭世英、张鹤慈等的“X社”,张郎郎等的“太阳纵队”,芒克、多多、根子等的“白洋淀诗群”,黄翔、哑默等的“贵州诗人群”,这些群体有的仅露出些异质性的“苗头”便被打压下去,有的则由于管制的缝隙而在现代主义的道路上走出了相当的距离。不过总的来说进行这样的写作是有风险的,其影响范围并不大,公开发表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它们一直以“潜流”的形式存在,真正的“冲出历史地表”要等到70年代末的诗歌民刊《今天》,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呼唤、引领社会变革和文学变革的作用,并开启了新一轮的现代主义写作大潮。
历史往往是呈“之”字形行进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又一次发生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面向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开放”,与此前极权主义的文化发展模式相比较,此时显然有了更多的民主因素,在表达的自由度、文学的主体性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久被压抑的现代主义写作倾向也终于有了表达的可能。应该看到,这种现代主义的写作绝非外力引导的结果,而实在是自发、自然而然的,它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人的处境、人的内心相契合的,它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相似更多是“不谋而合”而非“崇洋媚外”。从“复杂性”角度讲,社会开始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允许对于事物更为复杂、深入的探寻和表达,允许人的主体性、文学主体性的探求,这无疑是现代主义诗歌出现的基础。就诗歌的技术层面来讲,袁可嘉所说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戏剧化”、“客观性与间接性”无疑也重新获得了合法性,并且得到了诗人们的青睐,新的写作蔚为大观,开辟出了崭新的写作气象。当然,对于这种“复杂性”的认知和接受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朦胧诗”一开始便是作为负面概念提出的,用以指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的“难懂”、“怪诞”、“玄虚”。①但毫无疑问,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在这一时期的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时代的主流,是包含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意义的,因而也是不可能被轻易扼杀、取缔的。这可以被视为40年代现代主义写作的一种延续和再出发,但较之40年代的诗歌探索,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压抑和遮蔽,80年代的现代主义写作(其主体多为与40年代后期的“九叶”诗人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显得更有活力、更富激情,显示出了创作能量的“爆炸”和创作的“井喷”现象。80年代中期,以《他们》《非非》《莽汉》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在“朦胧诗”之后登场,到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①可谓蔚为大观,这其中绝大多数为现代主义的写作,诗歌写作的可能性被极大丰富了。这一时期诗歌的现代主义写作其成就有目共睹,它们共同书写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新的篇章,丰富了当代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技法,提高了其艺术容量和艺术能力。由此,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生长性,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是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和现代理性的发展相联系的,它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认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人为的阻拒或扭转都是不符合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的,难逃失败的结局。当然,“复杂性”本身并非现代主义的唯一规定性本质,它只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复杂”本身便包含了异质、多元的成分,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复杂”的否定,而由“现代主义”发展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更是明显地包含了对“复杂”的反动:解构、反智、直白、无意义、调侃、游戏……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初见端倪,90年代已具规模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一方面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之的反叛和僭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难辨的。不过,面对当下中国的实际,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出疑问: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理性精神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而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这种状况下的解构、反智、调侃是否会造成理性精神的下降和人文素养的降低?在主体意识并不强大甚至尚未真正确立的情况下急于颠覆、解构个人主体,是否逾越阶段、提前加剧了“人的死亡”?一味的口语化、简单化、游戏化是否会落入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的陷阱而为其同化,并造成诗性内涵、诗歌精神的流失?这恐怕是当下诗歌所面临的不能说不重要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从“复杂性”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致经历了“追求——不被允许——再度追求”的过程,这其中与政治、民主、文学观念、艺术方法等都有多重的复杂联系,有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
附注
①诗人、诗评家唐湜对20世纪40年代具有现代主义写作倾向的诗人群体的命名,见《诗的新生代》等文,《意度集》,平原社,1950年版。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11页。
②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页。
①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36页。
②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25页。
③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④袁可嘉:《诗与晦涩》,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1—100页。
①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2页。
②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1、50、51页。
①蓝棣之:《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见《论新诗现代化》附录,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2页。
②袁可嘉:《我的文学观》,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0、111页。
③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4页。
①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1962年第2期、1963年第3期。
②袁可嘉:《我与现代派》,见《诗探索》,2001年第3—4辑。
①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见《诗刊》1980年第8期。其中作为批判对象例证之一的便是“九叶”诗人杜运燮的作品《秋》。
①《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30日)。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