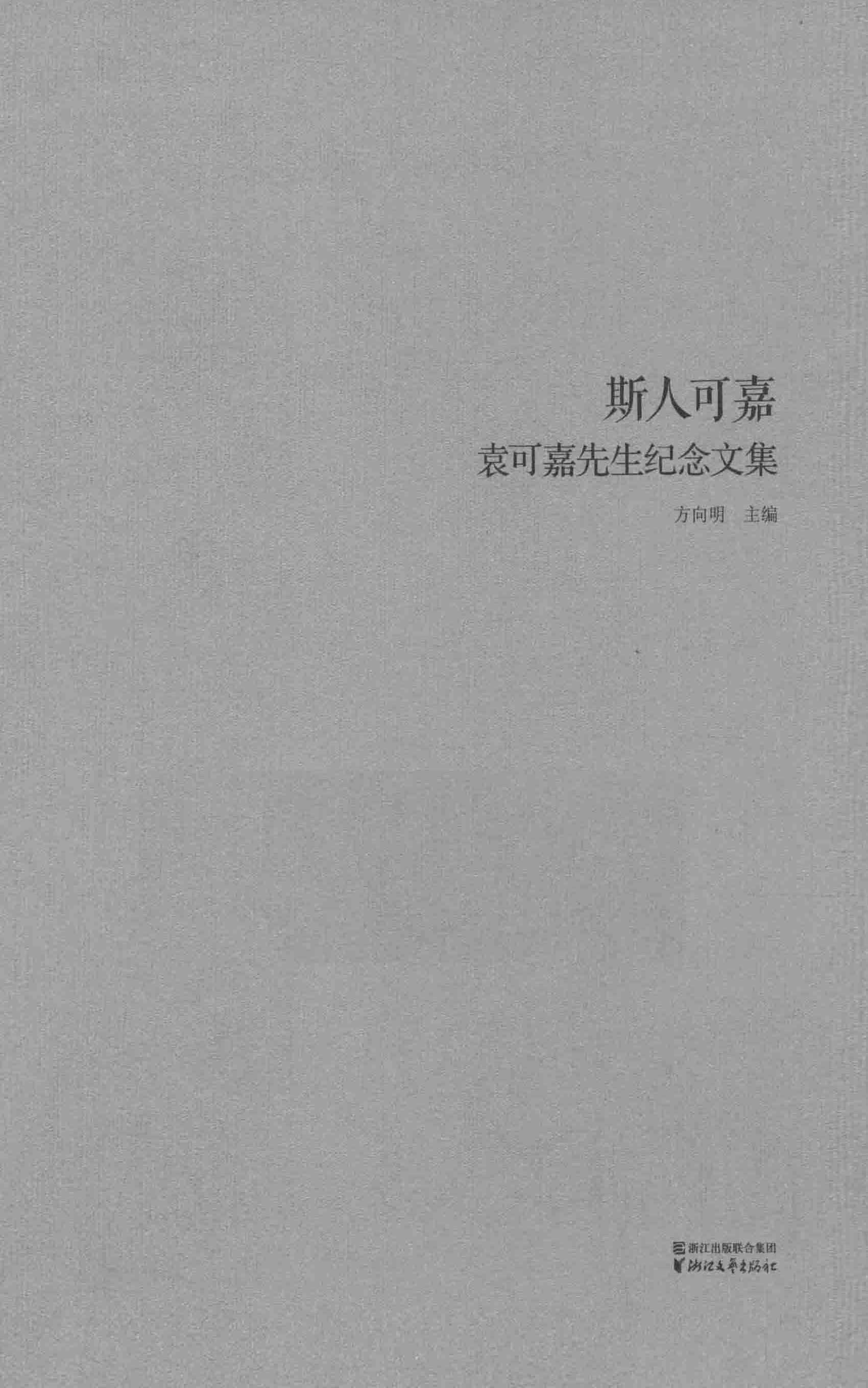内容
袁可嘉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的诗论结集《论新诗现代化》,由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今天重读,仍觉颇有新意,觉得其中蕴含着一些现代性的意义,蕴含着一种先行者的思想自觉。
无疑,袁可嘉当年提出的“新诗现代化”与当下文坛的现代性理论是不能等同的,两者之间的理论界定和思想内涵都有很大的差异。况且,现代性的问题是如此庞杂、如此繁复。我们知道,现代性与现代主义难解难分地纠葛在一起,“‘现代主义’一词是用作非常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同义词”,“‘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美学,涉及对现代性的一种特定的、常常是深刻矛盾的态度”。①于是,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和创作也就毫无疑义地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追求,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发展状态也就一定程度地体现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也知道,现代性又不等同于现代主义,它作为一种复合型命题,体现于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多个层面。这样一来,衡量中国文学发展或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内涵,也就不能仅仅用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尺,何况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状态又比较贫瘠、瘦弱。在这个意义上,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的现代性意义便凸现出来,它是历史发展顺序上的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诗歌三十年历程的顺势积累,又是横向时空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多种元素的会合交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启蒙现代性的历史升华、审美现代性的日臻成熟,也是两者之间的综合互补。
首先,袁可嘉展示给我们的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他说,现代诗论的构成是“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结合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于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意志的不时流露。”①
唐湜在回忆“九叶诗派”当时的文学活动时说,当时的袁可嘉是在“努力建立一个现代诗论的体系”。“现实、象征、玄学”的三者综合便是这样一种现代诗论体系。一方面,“现实、象征、玄学”的三者综合诞生于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诗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上。它既是对五四时期李金发等人象征诗派和30年代戴望舒等人现代诗派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他们的批判和改造。在以袁可嘉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看来,无论是李金发还是戴望舒,都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派,只是意象派或后期象征派而已。“真正的现代派诗只有在40年代才能产生,这里有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各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30年代根本没有像40年代这种极端冷酷、丑恶、严峻、复杂的现代现实,当时的诗人也不可能有现代人的意识、感觉、表现形式、语言形式等等来写诗。所以说,把戴望舒的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诗笼统地说成现代派诗。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因而使我们有信心在40年代建立真正的现代派诗。”②另一方面,这种“现实、象征、玄学”相结合的理论也是建立在40年代中国社会独特的语境之中,建立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元素的融合交汇之中。唐湜说:“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有着繁复错综的社会与政治斗争的现代世界,在大上海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现代社会,现实主义就必须加以发展与深化,那就是用现代化的表现手法、现代化的意象、现代化的节奏与色彩,即以现代化的新武器来打现代化的立体战争。”③
在“现实、象征、玄学”的理论体系中,核心是象征,而象征的核心则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诉求、思维方式和叙事艺术。袁可嘉表示:“现实、象征、玄学”的观点源于英国现代诗人、文学理论家立恰慈(瑞恰慈)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理论:“无论在诗歌批评,诗作的主题意识与表现方法三方面,现代诗歌都显示出高度综合的性质;批评以立恰慈的著作为核心,有‘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的提出;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表现在现代诗人作品中突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以及现代神话、现代诗剧所清晰呈现的对现代人生、文化的综合尝试都与批评理论所指出的方向同步齐趋。”①他解释,在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的关系之中,象征是魂,其渊源是“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因为,它能够表达“最大量意识状态”,它能够以“极度地扩展”与“极度地浓缩”两种方式来传达“最大量的经验活动”。前者以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的《尤力西斯》为代表,以二十五万字的篇幅写一天的活动;后者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代表,以寥寥四百行反映整个现代文明。虽然,前后两者表达着“扩展”与“凝缩”两个“绝对相反”的方向,但同样都是依赖于文字对于声音、节奏、意象所引发的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几无穷尽的联想”。这是与“概念逻辑”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甚至是迄今为止找不到一部作品能够与之相比的“细致复杂”的艺术。这种“最大量的经验活动”的艺术表现是如此地“恰当而有效”:过去如此丰富,眼前如此复杂,将来又充满了奇异的可能,一切历史、记忆、智慧、宗教和一切对于现实世界的感觉思维,都在这样“一个新的综合”里透露出各种形式的“消息”。可以说,以象征为核心的“新诗现代化”是“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是现代主义的叙事革命,它比“纯粹客观或纯粹主观”的表现、比“徒眩新奇,徒趋时尚”的形式都具有更广、更深、更重的意义,它代表着“新的感性的崛起”,建构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②
在“现实、象征、玄学”三者之中,现实是基础。袁可嘉说,当初他们“注意借鉴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但他们更注意反映广泛的现实生活,不局限于个人小天地,尤其反对颓废倾向;同样,他们虽然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但作为热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现代西方文艺家常有的那种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虚无主义情调”新诗现代化必须根植于现实生的现实,反映人的生命和人的心理的现实。这是一种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相对相成的有机结合,它能够使自我意识在“正确意义”下“扩大加深”,使文艺对于人生价值的“推广加深”。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和叙事行为的创新,现代性新诗还必须在“象征”和“现实”的前提下,运用抽象的哲理沉思与具象的敏锐感觉作为诗的智性手段。袁可嘉强调,现代主义诗歌艺术是一种“间接性”的艺术行为,是一种“感觉曲线”的形式方法。因为任何一个感觉敏锐、内心生活丰富的诗人在任何特定的时空内所产生的感觉形态都一定是多曲折、多变易的,而不可能是任何“一推到底的直线运动”形式。
袁可嘉解释,现代性新诗必须尊重诗作为艺术时的“诗的实质”。即,诗除了必须承担一般艺术的共同性以外,还必须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完成自己特定的艺术要求,这就是以多种形式的象征作为营造意象和表达情绪的手段,诸如“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等具体方法,都是诗中的意境创造、意象形成、辞藻锤炼、节奏呼应等极度复杂奥妙的有机综合过程,都是以象征为核心,以现实为基础的智性、玄学的表现。例如“感觉曲线”,是以与思想感觉相应的具体事物来代替那些“貌似坦白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这种迂回性的“间接的表明情绪”的方法,可以使读者在伴随丰富而来的错综复杂的“无形定义圈”内充分发挥自由的联想;例如“意象比喻”,是以“间接性”艺术去发现“表面极不相关而实质有类似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去创造“在突然扩大或缩小里清晰呈现”的特殊的“感觉与思想的结合”,去显示那种“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丰富”的艺术效果和复杂意义;例如“想象逻辑”,是在强调诗歌组织“高低起伏、层层连锁”的结构意识,它颠覆了传统诗歌“概念逻辑”的结构安排,通过“想象逻辑”,通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来表现诗情,来确立诗歌批评的标准;例如“间接性”的诗歌文字媒介,强调运用新的文字使用方来创造现代诗体,从而增加诗歌艺术的“弹性与韧性”,从而改变诗歌形式的“粗暴姿态”。①
其次,新诗现代化提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综合。袁可嘉认为,一个完美的文学观,必须有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理论内涵的支撑:“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的价值在于社会的传达;从心理学来说,它的价值在个人的创造;从美学来说,它的价值在文字的艺术,而三者绝对是相辅相成,有机综合的。”①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渗透的,既不是非单方面的存在,也不是外加的条件。在这里,社会学的观点不仅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心理学的认识也不仅指弗洛伊德学说的性和下意识,美学也不仅仅是克罗齐的直觉学说,而要求我们利用全部文化和学术的成果来接近文学,了解文学,研究文学,创造文学,以此建构的新诗现代化才是有机的、戏剧的、辩证的、综合的。
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三种理论视域的交汇出发,“人的文学”的理论内涵须包含两个本位的认识: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来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形式对照来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可见,“人的文学”坚信一切文学的创造、欣赏和批评都必须是以“生命本位”为本原的“心智活动”或“生命活动”。例如,在“人的文学”的“生命本位”的创作过程中,第一步,创造者要在自我生活领域中选择有意义的经验作为创作素材。第二步,有价值的经验素材通过“文学的艺术性格”的创造得到完美的表现。第三步,读者在读过好作品之后,生命更充实丰富了。于是,创造者和读者的“人性”和“人心”都“扩大”了,“伸展”了,感性更活泼,思想更深邃,继而出现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所以,以“生命本位”作为前提的“人的文学”既要尊重“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得”,又要尊重个体自我的意识活动的自动性。因为:“文学的价值既在创造生命,生命本身又是有机的综合整体,则文学所处理的经验领域的广度、高度、深度及表现方式的变化弹性自然都愈大愈好。”②与此相对,文坛上任何伦理教训的文学、感官享乐的文学以及政治宣传的文学都是对“人的文学”、人的生命的限制或扼杀。
同样,“人民的文学”的基本精神也包含两个本位的认识: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讲,它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与其他活动相对照而言,它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可以说,人民本位强调文学必须属于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歌颂和平与民主,抨击反动的恶势力。工具本位强调文学必须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领导,必须是战斗的,必须发挥宣传的功用。由此发展下去,过去士大夫的文学被淘汰了,今日市民的文学也被扬弃了,象征和玄学更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现实又现实”而且只是“某一种模型里的现实”。
面对相互矛盾的两极,袁可嘉强调,“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艺术本位”与“工具本位”必须进行综合。从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两者本身就不应该有争执,艺术本位与工具本位也应该互相协调。因为,“人”包含“人民”,文学服务于“人”与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况且,把创作对象扩大到普通人民大众的圈子里去,也是人本位或生命本位的目标,也是最大可能量意识状态活动的实现。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却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有些人以政治意识去抽空、压缩和简化文学,从而否定文学中的自然和美,否定爱情、友谊乃至个人心灵的描写,从而以“人民”否定了“人”,以“政治”否定了生命,最后“人”也就被简化为一个观念的几千万次翻版说明,或改头换面的公式运用。同样,“艺术本位”与“工具本位”在理论上也有互相协调的余地,因为即使承认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工具本位”也必须先做到“艺术本位”才能完成工具的使命。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些人以“工具”否定“艺术”,以“人民”否定“人”。于是,袁可嘉真诚地向“人民的文学”进言:人民的文学必须在不放弃人民本位的立场下放弃统一文学的野心;必须“适度”地认识和应用“阶级本位”;必须尊重文学的艺术本质而不能过分片面地迷信文学的工具性、战斗性;必须把自己的“主观的视野”扩大,而不能以“自己的尺度为唯一尺度来限制全体,否定全体”。①
再次,现代化强调新诗“戏剧主义”的综合。在袁可嘉看来,新诗的问题甚至包括新文学的问题不纯粹是内容的,也不纯粹是技巧的,而是超越了两者或源于两者融汇、转化之后的一种戏剧主义的综合。这种戏剧主义的形式,可以通过客观性与间接性的原则,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认识表现出来,可以通过“心理的了解”去从事“心理隐微的探索”,可以融汇“思想的成分”和“表现的灵敏”,在空间、时间、广度、深度诸多方面为新诗为新文学提供更大的“自由与弹性”。
新诗戏剧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体系,其理论构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新诗戏剧主义的批评标准是内在的,它不依赖诗篇以外的任何因素。它的批评内容,一方面是诗经验本身的质量,一方面是诗表现上的成败,前者是素材价值的估价,后者是艺术手腕的高低。(二)戏剧主义批评家认为诗的经验与表现、实质与形式是不可分的,诗的创造只是“一个连续的‘象征的行为’,绝无写好信(实质),然后塞入信袋(形式)的可笑情形”①。(三)新诗戏剧主义强调诗结构中的矛盾统一,强调诗的结构形式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如果没有这种“消融众多矛盾的统一性”,诗篇就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当然,这种“统一性”的诗歌结构形式,并不是传统、狭隘、平面的形态,而是艾略特的那种现代主义“想象逻辑”的结构,是“诗的情思”通过“意象连续发展后的想象的次序”。②袁可嘉说,在艾略特的诗歌形式中,我们看到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突兀片断,骤然读起来,令人莫名其妙,但如果把“诗情发展的曲线”在自己心中重描一遍,就会“恍然”悟到它们的奇异“配合”:或是在扩大某一行某一意象的意蕴,或是在加深某一情绪的起伏震荡,或是在加速某一观念的辩证运行。(四)戏剧主义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分析的批评体系。它以印象主义为主,与各种教条主义、权威主义尖锐对立,重视学力、智力和剥笋式的分析技术,常用带有机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以及讽刺感和辩证性的批评术语。
当然,新诗戏剧主义批评体系的建构也不是突兀的,它源于现代心理学、现代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字学多方面的理论基础。从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人生本身就是戏剧。所谓人生不过是前后绵延的“意识流”的总和,而意识流也不过是一串刺激与反映的连续、修正与配合。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自我主体各种不同的反应,导致各种不同的矛盾和冲突的表现,而人生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些矛盾冲突所带的冲动、刺激和反应。人生价值的高低也就由这些“协调不同质量的冲动”的“能力”而决定;从柯尔立克的想象学说和克罗齐的“直觉”说出发,想象特别是诗想象具有一种非凡的综合能力。在诗想象中,一切同与异、抽象与具体、观念与意象、殊相与共相、新奇与陈腐,一切异常的情绪激动,一切相反的不和谐因素都会在诗的具象和情趣之中井然有序地结合起来,使诗成为情趣与意象完美结合后的模式。在诗的想象中,诗的观念中原有的那种“抽象的”“死的”东西,一经化于诗中,便会生意盎然;从文字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诗的语言含有高度的象征性质,它可以随时接受意象、节奏、语气、态度等因素的修正补充,同时又都可以在诗的象征性表现中产生不同的张力,形成了一种立体的戏剧的象征行为。
最后,新诗现代化是中国现实土壤上的“西洋化”与“现代化”的综合。袁可嘉说,“现代化”是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是指空间上的变易,两者的混合为一,“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①。两者的综合便可以包容现代性的多种特性:从各种不同之中产生和谐的辩证性,包容各种具有独立地位的包含性,通过矛盾冲突而得到平衡的戏剧性,具有各种不同存在的复杂性,孕育着充分的生机的创造性,运用部分来配合全体而又不失去独立性的有机性,以及非直线的、简化的、排他的等。如袁可嘉所说:“现代化的诗是辩证的(作曲线行进),包含的(包含可能溶入诗中的种种经验),戏剧的(从矛盾到和谐),复杂的(因此有时也就晦涩的),创造的(‘诗是象征的行为’),有机的,现代的。”②
那么,如何实现现代性诗歌诸多特性的综合呢?袁可嘉提出了多种具体途径:第一,从外在现实主义走向内在现实主义。外在现实主义只关心民主的题材,只揭示“原则上的真理”、表面上的题材民主化和语言人民化。它只是一种“出发的起点”而不是“归宿的终极”。内在现实主义注重作者拥有的“拥抱全面人生经验的良机”,注重使用“最富有变化和弹性”的“戏剧的而非抒情”的语言来最适宜地表现“最大量的心神活动”。第二,从“机械地反映”到“有机地创造”。外在现实主义以为诗只是反映时代的相机,对准现实,一按快门,便完成了创作,如此“机械地反映”表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现实景象”、“迷糊空洞的集体愿望”,或者沦为一片“热情的松散泄沓”。而内在现实主义强调诗是“有机地创造”。这种创造性的诗歌表现的是艺术,是“诗经验的本身”完成的“整体价值”的感动。前者是“一架相机的活动”式的外在现实主义的重复,是量的增加。后者则是“接近人体的生命”的“价值的增益”,是“质的创建”的内在现实主义的“终极”表现。第三,从“抒情的运动”到“戏剧的行动”。抒情的诗是直线的宣泄,戏剧的诗是复杂经验的戏剧表达。随着现代人生的日趋丰富,单纯的热情宣泄显然不适应于奇异的现代世界,现代诗人重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热情的宣泄”。因为,热情可以借助惊叹号表达得淋漓尽致,复杂的现代经验是决非捶胸顿足所能表达出来的。现代主义的戏剧诗不是情感的“直线的运动”,它是“复杂的经验”的“有组织的表达”,是各种不同“一刹那的人生经验”的曲折、暗示、迂回的表现。以徐志摩的抒情诗与穆旦的戏剧诗相比较而言,前者分量轻、感情浓、意象华丽、节奏匀称,多注重情绪的重复和氛围的抒情气氛,是“浪漫的好诗”;后者分量重、情理交缠、意象突出,节奏突兀而多变,是“现代化了的诗”。时代发展的需求使我们不免偏爱后者。第四,从原始的到现代的。以卢梭、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强调回归自然、纯朴、平凡的原始倾向,虽然具有“消极矫正”的意义,却不能解决现代文化的难题。如果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现代社会发展并驾齐驱,新诗必须接受现代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加深自觉意识,而不是寄希望于简化的、单纯的传统,更不能借助“原始倾向”来“挽回”历史前进的车轮,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进程的压力将逼迫我们放弃“单纯的愿望”,大踏步走向现代。第五,从民主的政治热到民主的文化热。袁可嘉强调,民主的文化应该是现代的文化,民主的诗也应该是现代化的诗。它必须综合辩证的、戏剧的、复杂的、有机的、创造的多方面的特质。①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贯穿着客观现实与主观自我、政治认同与艺术本位、“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等两种价值取向、两种文学潮流的矛盾和对立。新文学伊始,从创造社提出个性、自我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会提出人生文学、平民文学的论争开始,发展到30年代及至40年代,两大阵营的论争和对抗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诸种浪漫派、象征派、现代派倡导的内心真实、主观情绪、生命意识的“人的文学”与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主张的政治性、现实性、大众性的“人民的文学”各持己见、针锋相对,甚至出现过许多偏激的言辞和行为。直至,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的问世,致使新文学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翻开了新的一章。它顺应现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立足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需求,融汇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的有机辩证关系,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艺术营养,创造了“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结合的“新的综合”的理论体系,使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相结合,书写了一种今天看来仍有新意的现代性视域下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综合。
无疑,袁可嘉当年提出的“新诗现代化”与当下文坛的现代性理论是不能等同的,两者之间的理论界定和思想内涵都有很大的差异。况且,现代性的问题是如此庞杂、如此繁复。我们知道,现代性与现代主义难解难分地纠葛在一起,“‘现代主义’一词是用作非常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同义词”,“‘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美学,涉及对现代性的一种特定的、常常是深刻矛盾的态度”。①于是,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和创作也就毫无疑义地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追求,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发展状态也就一定程度地体现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也知道,现代性又不等同于现代主义,它作为一种复合型命题,体现于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多个层面。这样一来,衡量中国文学发展或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内涵,也就不能仅仅用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尺,何况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状态又比较贫瘠、瘦弱。在这个意义上,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的现代性意义便凸现出来,它是历史发展顺序上的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诗歌三十年历程的顺势积累,又是横向时空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多种元素的会合交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启蒙现代性的历史升华、审美现代性的日臻成熟,也是两者之间的综合互补。
首先,袁可嘉展示给我们的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他说,现代诗论的构成是“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结合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于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意志的不时流露。”①
唐湜在回忆“九叶诗派”当时的文学活动时说,当时的袁可嘉是在“努力建立一个现代诗论的体系”。“现实、象征、玄学”的三者综合便是这样一种现代诗论体系。一方面,“现实、象征、玄学”的三者综合诞生于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诗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上。它既是对五四时期李金发等人象征诗派和30年代戴望舒等人现代诗派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他们的批判和改造。在以袁可嘉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看来,无论是李金发还是戴望舒,都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派,只是意象派或后期象征派而已。“真正的现代派诗只有在40年代才能产生,这里有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各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30年代根本没有像40年代这种极端冷酷、丑恶、严峻、复杂的现代现实,当时的诗人也不可能有现代人的意识、感觉、表现形式、语言形式等等来写诗。所以说,把戴望舒的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诗笼统地说成现代派诗。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因而使我们有信心在40年代建立真正的现代派诗。”②另一方面,这种“现实、象征、玄学”相结合的理论也是建立在40年代中国社会独特的语境之中,建立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元素的融合交汇之中。唐湜说:“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有着繁复错综的社会与政治斗争的现代世界,在大上海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现代社会,现实主义就必须加以发展与深化,那就是用现代化的表现手法、现代化的意象、现代化的节奏与色彩,即以现代化的新武器来打现代化的立体战争。”③
在“现实、象征、玄学”的理论体系中,核心是象征,而象征的核心则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诉求、思维方式和叙事艺术。袁可嘉表示:“现实、象征、玄学”的观点源于英国现代诗人、文学理论家立恰慈(瑞恰慈)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理论:“无论在诗歌批评,诗作的主题意识与表现方法三方面,现代诗歌都显示出高度综合的性质;批评以立恰慈的著作为核心,有‘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的提出;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表现在现代诗人作品中突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以及现代神话、现代诗剧所清晰呈现的对现代人生、文化的综合尝试都与批评理论所指出的方向同步齐趋。”①他解释,在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的关系之中,象征是魂,其渊源是“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因为,它能够表达“最大量意识状态”,它能够以“极度地扩展”与“极度地浓缩”两种方式来传达“最大量的经验活动”。前者以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的《尤力西斯》为代表,以二十五万字的篇幅写一天的活动;后者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代表,以寥寥四百行反映整个现代文明。虽然,前后两者表达着“扩展”与“凝缩”两个“绝对相反”的方向,但同样都是依赖于文字对于声音、节奏、意象所引发的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几无穷尽的联想”。这是与“概念逻辑”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甚至是迄今为止找不到一部作品能够与之相比的“细致复杂”的艺术。这种“最大量的经验活动”的艺术表现是如此地“恰当而有效”:过去如此丰富,眼前如此复杂,将来又充满了奇异的可能,一切历史、记忆、智慧、宗教和一切对于现实世界的感觉思维,都在这样“一个新的综合”里透露出各种形式的“消息”。可以说,以象征为核心的“新诗现代化”是“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是现代主义的叙事革命,它比“纯粹客观或纯粹主观”的表现、比“徒眩新奇,徒趋时尚”的形式都具有更广、更深、更重的意义,它代表着“新的感性的崛起”,建构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②
在“现实、象征、玄学”三者之中,现实是基础。袁可嘉说,当初他们“注意借鉴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但他们更注意反映广泛的现实生活,不局限于个人小天地,尤其反对颓废倾向;同样,他们虽然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但作为热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现代西方文艺家常有的那种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虚无主义情调”新诗现代化必须根植于现实生的现实,反映人的生命和人的心理的现实。这是一种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相对相成的有机结合,它能够使自我意识在“正确意义”下“扩大加深”,使文艺对于人生价值的“推广加深”。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和叙事行为的创新,现代性新诗还必须在“象征”和“现实”的前提下,运用抽象的哲理沉思与具象的敏锐感觉作为诗的智性手段。袁可嘉强调,现代主义诗歌艺术是一种“间接性”的艺术行为,是一种“感觉曲线”的形式方法。因为任何一个感觉敏锐、内心生活丰富的诗人在任何特定的时空内所产生的感觉形态都一定是多曲折、多变易的,而不可能是任何“一推到底的直线运动”形式。
袁可嘉解释,现代性新诗必须尊重诗作为艺术时的“诗的实质”。即,诗除了必须承担一般艺术的共同性以外,还必须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完成自己特定的艺术要求,这就是以多种形式的象征作为营造意象和表达情绪的手段,诸如“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等具体方法,都是诗中的意境创造、意象形成、辞藻锤炼、节奏呼应等极度复杂奥妙的有机综合过程,都是以象征为核心,以现实为基础的智性、玄学的表现。例如“感觉曲线”,是以与思想感觉相应的具体事物来代替那些“貌似坦白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这种迂回性的“间接的表明情绪”的方法,可以使读者在伴随丰富而来的错综复杂的“无形定义圈”内充分发挥自由的联想;例如“意象比喻”,是以“间接性”艺术去发现“表面极不相关而实质有类似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去创造“在突然扩大或缩小里清晰呈现”的特殊的“感觉与思想的结合”,去显示那种“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丰富”的艺术效果和复杂意义;例如“想象逻辑”,是在强调诗歌组织“高低起伏、层层连锁”的结构意识,它颠覆了传统诗歌“概念逻辑”的结构安排,通过“想象逻辑”,通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来表现诗情,来确立诗歌批评的标准;例如“间接性”的诗歌文字媒介,强调运用新的文字使用方来创造现代诗体,从而增加诗歌艺术的“弹性与韧性”,从而改变诗歌形式的“粗暴姿态”。①
其次,新诗现代化提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综合。袁可嘉认为,一个完美的文学观,必须有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理论内涵的支撑:“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的价值在于社会的传达;从心理学来说,它的价值在个人的创造;从美学来说,它的价值在文字的艺术,而三者绝对是相辅相成,有机综合的。”①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渗透的,既不是非单方面的存在,也不是外加的条件。在这里,社会学的观点不仅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心理学的认识也不仅指弗洛伊德学说的性和下意识,美学也不仅仅是克罗齐的直觉学说,而要求我们利用全部文化和学术的成果来接近文学,了解文学,研究文学,创造文学,以此建构的新诗现代化才是有机的、戏剧的、辩证的、综合的。
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三种理论视域的交汇出发,“人的文学”的理论内涵须包含两个本位的认识: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来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形式对照来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可见,“人的文学”坚信一切文学的创造、欣赏和批评都必须是以“生命本位”为本原的“心智活动”或“生命活动”。例如,在“人的文学”的“生命本位”的创作过程中,第一步,创造者要在自我生活领域中选择有意义的经验作为创作素材。第二步,有价值的经验素材通过“文学的艺术性格”的创造得到完美的表现。第三步,读者在读过好作品之后,生命更充实丰富了。于是,创造者和读者的“人性”和“人心”都“扩大”了,“伸展”了,感性更活泼,思想更深邃,继而出现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所以,以“生命本位”作为前提的“人的文学”既要尊重“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得”,又要尊重个体自我的意识活动的自动性。因为:“文学的价值既在创造生命,生命本身又是有机的综合整体,则文学所处理的经验领域的广度、高度、深度及表现方式的变化弹性自然都愈大愈好。”②与此相对,文坛上任何伦理教训的文学、感官享乐的文学以及政治宣传的文学都是对“人的文学”、人的生命的限制或扼杀。
同样,“人民的文学”的基本精神也包含两个本位的认识: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讲,它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与其他活动相对照而言,它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可以说,人民本位强调文学必须属于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歌颂和平与民主,抨击反动的恶势力。工具本位强调文学必须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领导,必须是战斗的,必须发挥宣传的功用。由此发展下去,过去士大夫的文学被淘汰了,今日市民的文学也被扬弃了,象征和玄学更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现实又现实”而且只是“某一种模型里的现实”。
面对相互矛盾的两极,袁可嘉强调,“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艺术本位”与“工具本位”必须进行综合。从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两者本身就不应该有争执,艺术本位与工具本位也应该互相协调。因为,“人”包含“人民”,文学服务于“人”与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况且,把创作对象扩大到普通人民大众的圈子里去,也是人本位或生命本位的目标,也是最大可能量意识状态活动的实现。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却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有些人以政治意识去抽空、压缩和简化文学,从而否定文学中的自然和美,否定爱情、友谊乃至个人心灵的描写,从而以“人民”否定了“人”,以“政治”否定了生命,最后“人”也就被简化为一个观念的几千万次翻版说明,或改头换面的公式运用。同样,“艺术本位”与“工具本位”在理论上也有互相协调的余地,因为即使承认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工具本位”也必须先做到“艺术本位”才能完成工具的使命。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些人以“工具”否定“艺术”,以“人民”否定“人”。于是,袁可嘉真诚地向“人民的文学”进言:人民的文学必须在不放弃人民本位的立场下放弃统一文学的野心;必须“适度”地认识和应用“阶级本位”;必须尊重文学的艺术本质而不能过分片面地迷信文学的工具性、战斗性;必须把自己的“主观的视野”扩大,而不能以“自己的尺度为唯一尺度来限制全体,否定全体”。①
再次,现代化强调新诗“戏剧主义”的综合。在袁可嘉看来,新诗的问题甚至包括新文学的问题不纯粹是内容的,也不纯粹是技巧的,而是超越了两者或源于两者融汇、转化之后的一种戏剧主义的综合。这种戏剧主义的形式,可以通过客观性与间接性的原则,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认识表现出来,可以通过“心理的了解”去从事“心理隐微的探索”,可以融汇“思想的成分”和“表现的灵敏”,在空间、时间、广度、深度诸多方面为新诗为新文学提供更大的“自由与弹性”。
新诗戏剧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体系,其理论构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新诗戏剧主义的批评标准是内在的,它不依赖诗篇以外的任何因素。它的批评内容,一方面是诗经验本身的质量,一方面是诗表现上的成败,前者是素材价值的估价,后者是艺术手腕的高低。(二)戏剧主义批评家认为诗的经验与表现、实质与形式是不可分的,诗的创造只是“一个连续的‘象征的行为’,绝无写好信(实质),然后塞入信袋(形式)的可笑情形”①。(三)新诗戏剧主义强调诗结构中的矛盾统一,强调诗的结构形式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如果没有这种“消融众多矛盾的统一性”,诗篇就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当然,这种“统一性”的诗歌结构形式,并不是传统、狭隘、平面的形态,而是艾略特的那种现代主义“想象逻辑”的结构,是“诗的情思”通过“意象连续发展后的想象的次序”。②袁可嘉说,在艾略特的诗歌形式中,我们看到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突兀片断,骤然读起来,令人莫名其妙,但如果把“诗情发展的曲线”在自己心中重描一遍,就会“恍然”悟到它们的奇异“配合”:或是在扩大某一行某一意象的意蕴,或是在加深某一情绪的起伏震荡,或是在加速某一观念的辩证运行。(四)戏剧主义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分析的批评体系。它以印象主义为主,与各种教条主义、权威主义尖锐对立,重视学力、智力和剥笋式的分析技术,常用带有机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以及讽刺感和辩证性的批评术语。
当然,新诗戏剧主义批评体系的建构也不是突兀的,它源于现代心理学、现代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字学多方面的理论基础。从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人生本身就是戏剧。所谓人生不过是前后绵延的“意识流”的总和,而意识流也不过是一串刺激与反映的连续、修正与配合。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自我主体各种不同的反应,导致各种不同的矛盾和冲突的表现,而人生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些矛盾冲突所带的冲动、刺激和反应。人生价值的高低也就由这些“协调不同质量的冲动”的“能力”而决定;从柯尔立克的想象学说和克罗齐的“直觉”说出发,想象特别是诗想象具有一种非凡的综合能力。在诗想象中,一切同与异、抽象与具体、观念与意象、殊相与共相、新奇与陈腐,一切异常的情绪激动,一切相反的不和谐因素都会在诗的具象和情趣之中井然有序地结合起来,使诗成为情趣与意象完美结合后的模式。在诗的想象中,诗的观念中原有的那种“抽象的”“死的”东西,一经化于诗中,便会生意盎然;从文字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诗的语言含有高度的象征性质,它可以随时接受意象、节奏、语气、态度等因素的修正补充,同时又都可以在诗的象征性表现中产生不同的张力,形成了一种立体的戏剧的象征行为。
最后,新诗现代化是中国现实土壤上的“西洋化”与“现代化”的综合。袁可嘉说,“现代化”是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是指空间上的变易,两者的混合为一,“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①。两者的综合便可以包容现代性的多种特性:从各种不同之中产生和谐的辩证性,包容各种具有独立地位的包含性,通过矛盾冲突而得到平衡的戏剧性,具有各种不同存在的复杂性,孕育着充分的生机的创造性,运用部分来配合全体而又不失去独立性的有机性,以及非直线的、简化的、排他的等。如袁可嘉所说:“现代化的诗是辩证的(作曲线行进),包含的(包含可能溶入诗中的种种经验),戏剧的(从矛盾到和谐),复杂的(因此有时也就晦涩的),创造的(‘诗是象征的行为’),有机的,现代的。”②
那么,如何实现现代性诗歌诸多特性的综合呢?袁可嘉提出了多种具体途径:第一,从外在现实主义走向内在现实主义。外在现实主义只关心民主的题材,只揭示“原则上的真理”、表面上的题材民主化和语言人民化。它只是一种“出发的起点”而不是“归宿的终极”。内在现实主义注重作者拥有的“拥抱全面人生经验的良机”,注重使用“最富有变化和弹性”的“戏剧的而非抒情”的语言来最适宜地表现“最大量的心神活动”。第二,从“机械地反映”到“有机地创造”。外在现实主义以为诗只是反映时代的相机,对准现实,一按快门,便完成了创作,如此“机械地反映”表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现实景象”、“迷糊空洞的集体愿望”,或者沦为一片“热情的松散泄沓”。而内在现实主义强调诗是“有机地创造”。这种创造性的诗歌表现的是艺术,是“诗经验的本身”完成的“整体价值”的感动。前者是“一架相机的活动”式的外在现实主义的重复,是量的增加。后者则是“接近人体的生命”的“价值的增益”,是“质的创建”的内在现实主义的“终极”表现。第三,从“抒情的运动”到“戏剧的行动”。抒情的诗是直线的宣泄,戏剧的诗是复杂经验的戏剧表达。随着现代人生的日趋丰富,单纯的热情宣泄显然不适应于奇异的现代世界,现代诗人重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热情的宣泄”。因为,热情可以借助惊叹号表达得淋漓尽致,复杂的现代经验是决非捶胸顿足所能表达出来的。现代主义的戏剧诗不是情感的“直线的运动”,它是“复杂的经验”的“有组织的表达”,是各种不同“一刹那的人生经验”的曲折、暗示、迂回的表现。以徐志摩的抒情诗与穆旦的戏剧诗相比较而言,前者分量轻、感情浓、意象华丽、节奏匀称,多注重情绪的重复和氛围的抒情气氛,是“浪漫的好诗”;后者分量重、情理交缠、意象突出,节奏突兀而多变,是“现代化了的诗”。时代发展的需求使我们不免偏爱后者。第四,从原始的到现代的。以卢梭、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强调回归自然、纯朴、平凡的原始倾向,虽然具有“消极矫正”的意义,却不能解决现代文化的难题。如果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现代社会发展并驾齐驱,新诗必须接受现代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加深自觉意识,而不是寄希望于简化的、单纯的传统,更不能借助“原始倾向”来“挽回”历史前进的车轮,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进程的压力将逼迫我们放弃“单纯的愿望”,大踏步走向现代。第五,从民主的政治热到民主的文化热。袁可嘉强调,民主的文化应该是现代的文化,民主的诗也应该是现代化的诗。它必须综合辩证的、戏剧的、复杂的、有机的、创造的多方面的特质。①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贯穿着客观现实与主观自我、政治认同与艺术本位、“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等两种价值取向、两种文学潮流的矛盾和对立。新文学伊始,从创造社提出个性、自我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会提出人生文学、平民文学的论争开始,发展到30年代及至40年代,两大阵营的论争和对抗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诸种浪漫派、象征派、现代派倡导的内心真实、主观情绪、生命意识的“人的文学”与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主张的政治性、现实性、大众性的“人民的文学”各持己见、针锋相对,甚至出现过许多偏激的言辞和行为。直至,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的问世,致使新文学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翻开了新的一章。它顺应现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立足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需求,融汇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的有机辩证关系,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艺术营养,创造了“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结合的“新的综合”的理论体系,使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相结合,书写了一种今天看来仍有新意的现代性视域下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综合。
附注
①[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0、336页。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页。
②唐祈:《唐祈诗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唐湜:《我的诗艺探索历程》,见《一叶诗谈》,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4页。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页。
②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11页。
③袁可嘉:《九叶集·序》,见《九叶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页。
①袁可嘉:《我的文学观》,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0页。
②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4页。
①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0—122页。
①袁可嘉:《谈戏剧主义》,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6页。
②袁可嘉:《谈戏剧主义》,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7页。
①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页。
②袁可嘉:《诗与民主》,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3页。
①袁可嘉:《诗与民主》,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4—51页。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