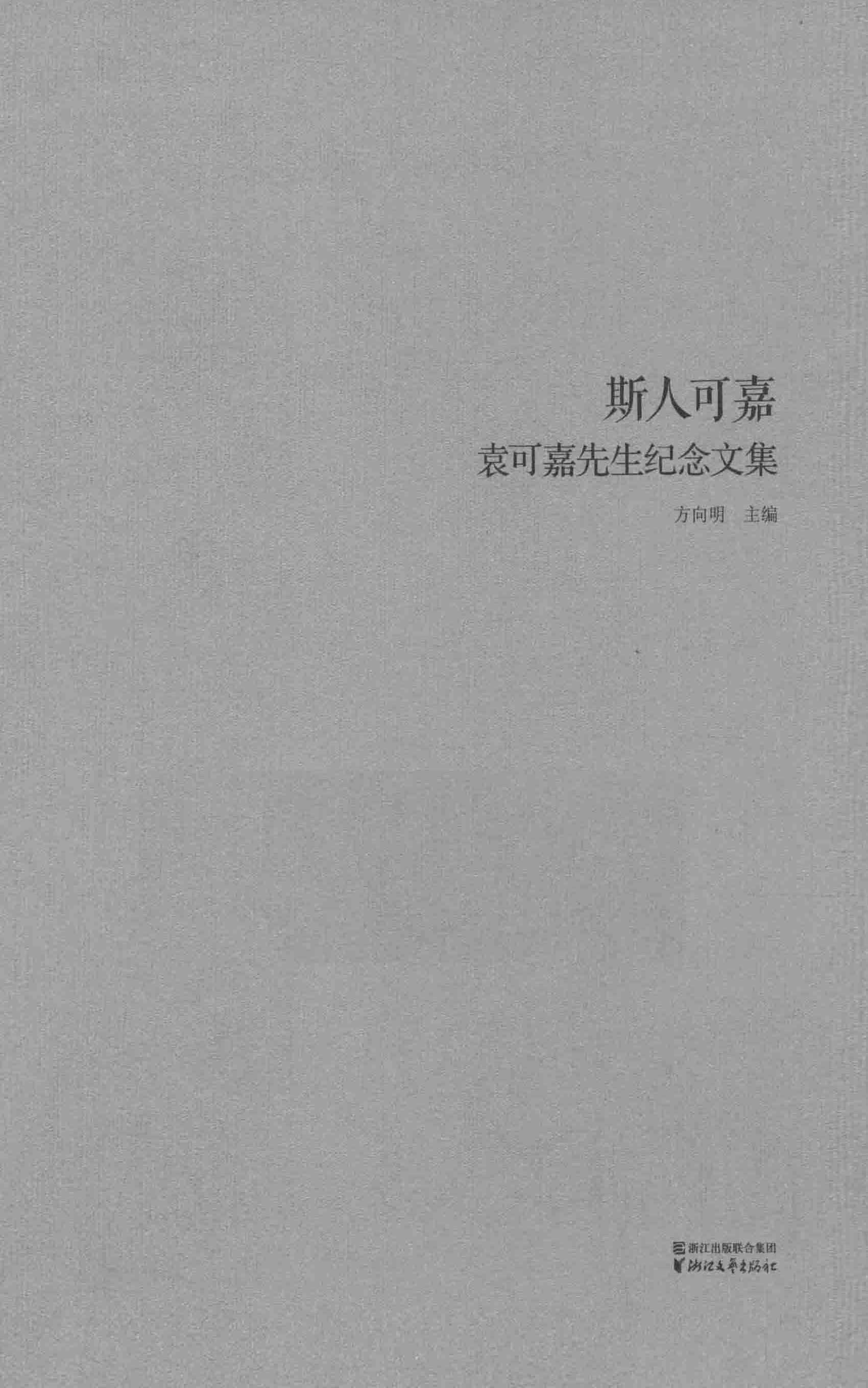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
| 内容出处: | 《斯人可嘉 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4277 |
| 颗粒名称: | 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 |
| 分类号: | K825.6-53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51-260 |
| 摘要: | 袁可嘉在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一个艺术方向上的转变过程,从英国19世纪热爱浪漫主义转向现代派文学,并受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启发,将现实、象征和机智三种因素结合起来,使诗篇带上理性色彩。袁可嘉的诗论在渊源上与瑞恰慈和艾略特有联系。 |
| 关键词: | 评论 文学研究 袁可嘉 |
内容
本文标题如果叫“袁可嘉诗歌批评理论探源”可能更确切,这也是本文的初衷,然而,袁可嘉是因建构九叶派诗论而成名的,而这正是他后来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九叶派诗论的渊源是丰富的,可谓有些“多元”。比如唐湜、陈敬容、杭约赫以及新时期以来的郑敏,都卓有贡献。然而,就时间较早和更有系统性、更完整的更有专门性来说,袁可嘉被公认为九叶派的理论家。
本文拟集中讨论1946年至1948年期间袁可嘉诗论之渊源。他这个时期(二十五至二十七岁)写的诗论文字,后来一直到1988年才汇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1月),这本仅二百五十页的小册子立即引起极大的注意,迄今已成为研究九叶派和中国新诗史的经典性文献。说起来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由于我是新时期以来对九叶派发表评论最早的一两个作者之一(我的论文曾经在几位在京九叶派诗人之中传阅,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定稿于1982年10月,题目为“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初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另一位是古典文学专家严迪昌教授,他的论文《他们歌吟在光明与黑暗交替时》发表于1981年底),袁可嘉先生委托我为他正在汇编的40年代诗论集《论新诗现代化》写序言,并在信中嘱我:“客观地介绍一下这些论文产生的背景和表述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意义,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总以平实中肯为好,也欢迎提出批评意见。”序言写成之后,本拟先在《读书》杂志发表一下,但因为写得太长,后来在编辑时甚至都没有以序言通常的位置放在这本论文集之前面。在这篇序言里,虽然按照袁可嘉先生的嘱咐,着重于这些论文的背景、诗论之要点分析,理论体系及其评价等方面,我仍然提示了这些诗论的渊源。我在序言里明确指出,袁可嘉属于瑞恰慈这类“文学批评家”,把批评作为科学,偏重于美学原理的探究,理论系统的建立,研究重于欣赏,制度化意味甚过一时的兴会感发,他的立论表现出智力与明晰,常常使用“剥笋式”的分析方法。但我也提到袁可嘉对于诗歌文本多有感触和发现,对诗有特殊敏感,而且能从中概括独到看法,因此也兼有艾略特这类“批评文学家”的特长。所有这些话,都有一个用意,即想暗示袁可嘉诗论在渊源上与瑞恰慈和艾略特的联系。时光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一直没有可能把这项已经提出来的课题加以完成,而学术界也没有任何人试图着手去做。旧话重提,朝花夕拾,我认为这个课题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想必仍然为学术界所关注。从选题方向与选题战略说,甚至更应该受到关注了。
根据他的自述,写这些诗论的时候,他正在刚从昆明迁回北京之北京大学西语系任助教。他是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受聘于此。1946年至1948年这两年间,正是九叶派形成风格和臻于成熟的时期。他正是在这个时期发表较多诗作的。这就是说,他是置身于这一诗潮,在其中学习、体验、创作与思考,与此同时,对这一思潮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袁可嘉当年的这些诗论所发表的报刊,主要是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艺周刊》,和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袁可嘉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艺术方向上的转变过程。1941年秋天,他开始就读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大学一年级的那年,他主要沉浸于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他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深受感染,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作他想了。又由于受杨振声教授口衔烟斗,娓娓而讲徐志摩的感染,喜爱上了徐志摩的诗。1942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兴趣从浪漫派文学转向现代派文学。就在这一年,他先后读到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更切近现代人的生活。当时西南联大校园内正刮着一股强劲的现代风,袁可嘉学习现代派诗的象征手法和机智笔触,力求把现实、象征和机智三种因素结合起来,使诗篇带上硬朗的理性色彩。他在奥登《在战时的中国》的启迪下,用不算严格的十四行体,描绘上海、南京和北平几个大都市的外貌和实质,力求用形象突出它们各自的特点。这些有代表性的诗,我都选进了我编选的《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袁可嘉先生在他的1992年12月定稿的《自传》里称这个选本“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九叶派选本”),读者不妨与他的理论文章参照研究。他在1948年大学毕业时用英文撰写的论文《论叶芝的诗》可谓是他写诗论的发轫。
袁可嘉先生后来在七十一岁时回顾说:“三四十年代是西方新诗潮和我国新诗潮相交融,相汇合的年代。在西方,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奥登的影响所向披靡;在我国,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和后来所谓‘九叶’诗人也推动着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走向中国式现代主义。这是一个中西诗交融而产生了好诗的辉煌年代。但截止四十年代中叶,诗歌理论明显地落后于实践,对西方现代诗论虽已有所介绍,可对西方和我国新诗潮的契合点还缺乏理论上的阐明。”(《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这里所说的“诗歌理论”,即在我上文曾经提到的瑞恰慈一类的科学的、体系性的、偏重于美学原理的文学批评,而袁可嘉先生所寻到的“契合点,”就是他那个时期里一再说起的“新诗戏剧化”理论。这个理论,也可以径直叫作“新批评”:袁可嘉曾经把当年那个时期那些诗论以《新批评》为名,收入朱光潜主编的一套诗论丛书,因战乱关系,稿件在投寄途中丢失。对于本文来说甚至显得更重要的,是袁可嘉在这回顾里还说,他所受英美新批评派和现代派启迪的诗论基本观点有以下三点:第一,诗是多种因素结合的有机组织,成败决定于整体效果;第二,诗与主、客观有机联系,不可偏执一端;第三,诗表现手法的现代化问题。这些论述都为本文提供确凿的线索和根据。
在进入袁可嘉诗论的渊源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声明,希望读者不要读过此文之后,下意识地就觉得好像袁可嘉诗论的独创性立刻减少,他们想,呵,原来如此,他的理论都是从别处来的呀。这种情况在很多著名的作家身上都发生过,据我所知,很多作家都不愿意,很不希望看到批评家考据出他的作品受到别人的影响。茅盾说他在写《子夜》之前根本就没有读过左拉的小说《金钱》。曹禺婉转否认别人说《雷雨》受影响于易卜生的《群鬼》和尤金·奥尼尔《榆树下的爱情》,更否认《日出》脱胎于小仲马《茶花女》。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写了篇论文来讨论九叶派诗人杭约赫的抒情长诗《复活的土地》所受艾略特名诗《荒原》的影响,我以为分析得有根据,作者有自己的发现。我兴致勃勃带去杭约赫家里给他看,说这是对于九叶派深入研究后的一个进展。没想到,他一改往日通常的率真和亲切,以一种我很陌生的淡淡的冷淡回应说:过去也有人说我的《复活的土地》受到艾青的《复活的土地》的影响,其实根本没有联系。杭约赫的态度,我印象很深,深感意外和讶异。但当时我无从把他的误解给他加以分析。其实,任何人在进行创造时,都有一个历史背景,同时又在创造,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也都如此。列宁指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西方学者指毛泽东在哲学史上为黑格尔辩证学派。艾略特本人看起来是单枪匹马和作为第一个人,发掘了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其实,在他之前,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也重视英语诗歌的机智传统,他偏爱机智、精练的诗歌,同时也树立起古典主义形式完美的标准。从这两方面看,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约翰逊都可谓艾略特的先驱者。鲁迅则指明《狂人日记》这个题目直接来自果戈里的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是唐湜也用鲁迅的方法指出鲁迅杂文的文体渊源是外来的essay和feuilleton,及魏晋的论辩文章。另外,何乃英还撰写了《〈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袁可嘉先生本人在分析九叶派诗歌卓然独立的特质,并指明它“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和“诗歌气候新的转变”之同时,也还指出了这个“感性革命的萌芽和先驱”,指出了这个先驱就是卞之琳诗中传统感性与象征手法的有效配合,和冯至更富于现代意味的《十四行集》。这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脉络清晰地阐明了九叶派的诗史地位和独创性贡献,尤其是有助于深入分析九叶派是怎样崛起的,用什么样的属于自己所创造的艺术来崛起的。
当然,我写这些话,并不是害怕袁可嘉先生误解,他本人是一个学者,他在自己的论文里其实已经一再提及了他的诗论之渊源,我所做的,只不过对此详加分析就是了。同时,我还注重他在这当中的属于自己的卓越建树,以期对于他这两年时间里所说的“摸索”,作一些进一步的分析和归纳,从而把我们对于现代诗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袁可嘉在40年代后期,即他诗歌理论研究认真起步之时(1946.9.15—1948.
10.30),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文章,1988年全部编入《论新诗现代化》一书,其中有十篇选入他后来在1992年的自选集里,因而相对更重要。但他不是一开始就写了关于“新诗现代化”题旨的重要文章,论新诗现代化的第一篇写于他开始发表诗歌理论文章以来的半年之后,而确认他理论体系并婉转隐藏地为他的理论起名的那篇文章《谈戏剧主义》,发表于1948年6月8日,大约是在经过了两年的摸索之后。因为袁可嘉先生先学写诗,后来转向了理论,因此创作是他的基础。他的第一篇诗论是谈创作的,可以说是谈怎样写诗,不过不是谈自己写诗的经验,而是一些学习诗歌文本过程中的“发现”,题目叫“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第二篇谈及对当时诗坛流行倾向的一个重要观察,并概括为“政治感伤性”。接下来,他谈到了诗的主题、晦涩、道路这些当时诗坛上的比较重要的问题的观感。在谈过现代英诗“从分析到综合”演变历程之后,他开始进入“新诗现代化”这个话题。
《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3.30)是第一篇重要文章。袁可嘉所说“新诗现代化”,是指4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一种新诗,他说这种新诗的出现,无异于一场“改变旧有感性的革命”。他说在这改革活动的后面有七条理论原则,从理论脉络方面看,有理由认为,其中第七条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乃“新传统的寻求”之中心和重点,在这里,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意味着暗示、含蓄,而玄学则表现为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和机智的不时流露。请注意,这里带出来了三个概念:感觉、思想和感情,以及三者在诗里的相互关联。袁可嘉明确指出这个新诗的新传统,它乃来自西方诗现实、象征、玄学新的综合传统。接下来在第二篇论新诗现代化的文章《新诗现代化之再分析》(1947.5.18)里,袁可嘉论述这个新传统在技术方面的四点做法:(l)与貌似坦白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不同,这个新传统要用相应的具体事物表现“思想直觉”;(2)与浪漫派意象的“空洞含糊”不同,新传统的意象要求能惊人、离奇、新颖、丰富,所代表的事物要确切不移,因“情感思想强烈结合”,所以要求所产生的意义复杂;(3)与概念逻辑不同,作者通过想象逻辑对于全诗结构加以注意;(4)与流行的硬性文字不同,新传统要求诗的文字弹性与韧性。这四点做法的中心问题是意象、情感与思想三者的结合。有必要指出,袁可嘉在谈及这个新传统时,曾经说过有几条眼前还无细致复杂的作品可充例证,这句话可以“解构”他所说的“新传统”:既然都还没有作品可以参证,何来的传统呢?原来,袁可嘉所说的传统,并非都从已然的创作里归纳出来,同时也有一些是他本人的主张,或者说暂时还只是西方诗歌的特长。所以他说新传统的“寻求”,而不说新传统之“出现”,这其间的区别意味着,新传统正在被寻求因而也就正在形成之中。他所说的眼前还无作品可充例证的“传统”,有三条:(1)依赖文字通过声音、节奏、意象所能引致的联想;(2)想象逻辑;(3)琐事细节对于全体结构之功效。此三条之中最中心的问题,是想象逻辑。因此,这是袁可嘉诗论所触及的基本问题的第三点。
又经过一年以后,袁可嘉把他所理想的现代化新诗,从创作的角度加以归纳,并针对着当时诗坛的弊端,为回答如何使意志和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提出了“戏剧化”这个名称,这篇文章即题为《新诗戏剧化》(1948年6月,《诗创造》第12期)。概括这篇文章的意思,他所提出的如何克服说教与感伤弊端的要点是:融和思想的成分,从事物深处、本质之中转化自己的经验,而不要在诗里作激情的流露和放任的感情。他进一步详细地解释这样做的三种可能性:(1)如里尔克那样,把搜索自己内心之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打成一片;(2)像奥登那样,利用机智、聪明以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对象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从语气还有比喻的这部分表现,从不坦然裸露;(3)例如像艾略特那样写诗剧,诗剧面对现实时不可或缺的距离,象征功用使得不致过度现实,因此,现代诗剧的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综合的新传统,可谓是最佳选择,而这正是现代诗的主潮所要追求的。袁可嘉把他所理想、所主张的新诗用“戏剧性”一词标识,想必主要也由于受此现代诗剧的启示。这里所讲的里尔克、奥登、艾略特三种略有差别而又有着共同趋向的不同传统所体现出的三种可能性,乃是袁可嘉诗论的第四个基本问题。
与此文差不多同一时候,袁可嘉写成了他全部诗论里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谈戏剧主义》(1948年6月8日《大公报》)。上文刚才分析过的“戏剧化”,是袁可嘉对于他所理想、所归纳的现代化新诗的命名,而“戏剧主义”则是他对于自己批评理论的命名。我曾经在1998年把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命名为“症候分析理论”(《现代文学经典的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把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命名为“诗中主要情感分析理论”(《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5年出版),因此,我想论断说“戏剧主义”是袁可嘉对于自己批评理论的命名。但在1948年他把这些论文结集准备出版时,他用了“新批评”这个命名,1988年重新搜集出版时,用了“论新诗现代化”,这两次他都没有用“戏剧主义批评理论”这个命名。无论从时代和个人原因说,都是因为他想融入时代的文学潮流,不大看重个人的标新立异,或者说希望把个人的标新立异隐藏在时代思潮之深处。《论戏剧主义》这篇更核心、集大成的文章,谈了三个问题:(1)戏剧主义这个命名在心理学、美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的根据;(2)戏剧主义批评的四个特点;(3)戏剧主义批评常用术语。从他论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文里的新鲜内容是对于瑞恰慈“最大量的意识状态”以及“机智”、“讽刺感”两个术语的诠释,这三者也差不多就是戏剧主义批评理论之核了。此乃袁可嘉诗论的第五个基本问题。
以上我从四篇文章里在五个层次上提出五个基本问题。从本文的宗旨来看,这五个基本问题都能找到它的渊源。好在袁可嘉先生在这些论文里,已经一再地为我们探讨这些渊源提供了线索。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有些悲伤,我揣测一定会有人因为我们分析了袁可嘉诗论的渊源就觉得他不那么重要了。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日本故事,故事说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粮食不够吃,父母年纪大了不能再劳动,就由子女背去深山老林让野兽吃掉。可是这个故事里的母亲,害怕的是背他去深山老林的儿子不认识来时路,于是就在儿子背上不时地摘一些树枝扔在地下,让儿子回家时有线索可循。现在我好像成了这个故事里的儿子,循着袁可嘉先生提供的线索,一步一步地把他投向深山老林。然而,这故事结局稍有不同,那儿子因母亲的行为深受感动,最后又把母亲背回了家。为了把为我们提供理论渊源之线索的袁先生背回家,我将在本文结束部分,认真讨论一下他的独创性和卓越贡献。
袁可嘉诗论五个基本问题的理论渊源,我想可以简述如下。在这方面,袁可嘉先生在最早的论文里即已指出,他说现代西洋诗以艾略特为核心,现代西洋诗批评,以瑞恰慈的著作为核心。下面提出的五个方面,皆来自艾略特与瑞恰慈的代表性论著。
一、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里,袁可嘉指出40年代以来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诗歌感性改革活动后面,有七条理论原则,其中心和重点,乃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而这个新诗的新传统,它们来自西方诗歌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袁可嘉一再说过西方现代诗的主潮所追求的正是这个传统,而诗剧正配合这个要求。在诗剧创作方面的情况是,1932年,艾略特企图复活诗剧,写了《大力士斯威尼》作为试验。1935年他发表了第一出诗剧《大教堂中的谋杀》。诗剧之外,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也表现了这个传统。我还不妨解释一下,这里的玄学乃指艾略特所发掘的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传统;象征,指法国19世纪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袁可嘉本人注意及此,乃因为从卞之琳广场创作受到了启示。最后,袁可嘉题目里所谓“新传统”里的“传统”这个词,不是我们通常所谓文学传统的那个传统,而是经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年)里所阐述的那个“传统,”在这里,艾略特对传统这一概念作出了重新评价:在成熟的诗人身上,过去的诗歌是他的个性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也受到现在的修改。真正要做到创新,必须深切意识到不断变化中的“欧洲思想”的存在,并且也意识到自己是它的一部分。为了达到与欧洲诗歌的整体建立有机的联系这一目的,诗人必须树立起消灭自己个性的目标。
二、《新诗现代化再分析》一文在论述“新传统”在技巧方面几点做法时所说的“思想感觉”和“情感思想强烈结合”,均来自艾略特。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1921年)里说,玄学派诗歌是伊丽莎白时代英诗的逻辑发展,应是英诗的主流。他指出玄学派诗歌特点是:形象化的描述极为丰富和具体鲜明,所使用的比喻既具有物体的,也具有理性的涵义,因此能够巧妙地把思想、感情和感觉三个因素结合成一体。这个统一体,17世纪诗人称之为“机智”(wit),机智是能够使“无联系的经验”集合在一起的敏锐的智力。这个诗歌传统具有一种“感觉的机制”,好像熔炉,把思想熔化成为感情的反应。这个“感觉把思想熔化为感情”的特点,不幸在17世纪后半叶消失了。在德莱顿以后的新古典主义诗歌中,出现了感觉的分离,失去了它与感情和感觉的联系,成为今日意义的“机智”:诙谐或戏谑。另一方面,在弥尔顿的诗中,激动的雄辩又和“机智”分离,结果导致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诗歌。
三、也是在《新诗现代化再分析》一文里,袁可嘉在探讨他所说的眼前还暂时无作品可充例证的“传统”时,特别提到“想象逻辑”。这个问题,艾略特和瑞恰慈曾一再论及。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说:诗人的职务只是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没有的感觉。他说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而这些经验在讲实际、爱活动的一种人看来就不会是什么经验。他说这种集中的发生,既非出于自觉,亦非出于思考,诗人仅仅是被动地伺候它们变化而已。这里讲的化炼、集中、被动和与实际经验不同,都是在说“诗想象”是怎么一回事。瑞恰慈在《想象》一文里说,诗想象具有有机的综合能力,在一切艺术中想象表现得明显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把纷乱的、互不联系的各种冲动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有条理的反应。在《诗的经验》一文里,他又说,在文字的运用上,诗歌与科学是相反的。十分确切的思想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选择文字尽量合乎逻辑,而是由于神情、声调、节奏、韵律在我们的兴趣上发生作用,并且使兴趣由无数的可能中选出它所需要的确切而又特别的思想。
四、在《新诗戏剧化》一文里所说“融和思想成分,从事物深处,本质之中转化自己的经验”之三种可能方式:(1)把搜索自己的内心之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打成一片,来自里尔克的《图像集》;(2)利用机智、聪明、语言、比喻、活泼又内敛,来自抗战时期奥登的作品;(3)诗剧方式,来自1935年前后艾略特等的诗剧创作。
五、袁可嘉“戏剧主义批评理论”的三个核心术语之渊源:
(1)“最大量的意识状态”:瑞恰慈在《想象》一文里说,人生价值的高低,完全由它协调不同质量的冲动的能力而决定。冲动协调后的状态,他称之为态度,实际即是心神状态。能调和最大量、最优秀的冲动的心神状态,是人生至境,这就是瑞恰慈所谓“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含义,他认为艺术或诗的创造都具有这种功能。
(2)机智:艾略特、瑞恰慈都有较充分的解释,前引艾略特《玄学派诗人》已经为读者所知了,瑞恰慈在《想象》和《诗的经验》两篇文章里也多有讨论。袁可嘉归纳这些讨论,界定“机智”乃泛指作者在面对某一特定处境时,同时了解这个处境所可以产生的许多不同的复杂态度,它使诗歌意外地生动和丰富。
(3)讽刺感:瑞恰慈在《想象》一文里说,有一种诗歌是经不起用讽刺的态度来观赏的,如济慈的“你的嘴唇,滑溜的幸福”。这里所说的讽刺是把对立的补充的冲动引进来。这就是为什么容易受讽刺的诗不是最高级的诗,而最高级的诗的特点总是讽刺的。袁可嘉先生据此解释说:讽刺感是一种欲望与心情,诗人在指陈自己的态度时,同时希望相反相成的态度,它是争取异己,在诗中为不同于诗中主要情绪的因素。它与机智不同,机智只是消极地承认异己的存在,而讽刺感则积极地争取异己。
最后,由于本文篇幅已经够长了,我想只能直接以结论的形式,说说袁可嘉诗论的独创性与卓越贡献。
一、追踪西方诗歌主潮,思考我国当下诗坛面临的问题。对于西诗主潮追踪,多从艺术本身下功夫,很内行,对于当时诗坛弊端的批评,一针见血,见解独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袁先生正是如此做的,在40年代的诗坛,做得十分成功,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二、瑞恰慈的理论著作,十分晦涩难懂。在此之前,因瑞恰慈1930年前后曾经在中国北平任教,好些人都在他的著作里下过功夫,如李安宅、吴世昌等,但袁可嘉不仅详尽准确地诠释了瑞恰慈,而且用以观察中国诗坛,成就令人瞩目。
三、袁可嘉先生在有渊源有背景的情况下,却不满足于变相编译或照抄,而处处都可见他的深入体会与独创性见解,这些体会与创见,甚至完善和完成了艾略特、瑞恰慈的理论,而对于中国诗坛、中国新诗的发展,其功更不可淹没了。顺便举例来说,比如对于想象逻辑,艾、瑞二人论述比较分散,也不够具体,而袁可嘉先生确切地加以具体归纳,认为所谓想象逻辑,乃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对于诗歌十分重要,它可以结合不同经验,使意义加深、扩大、增重。他又用艾略特长诗作解,认为表现在这些诗里,是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突兀片段,或则扩大某一行或某一意象的蕴意,或则加深某一情绪的起伏、撼荡,或者加速某一观念的辩证引进。又比如他以瑞恰慈理论解释穆旦诗《时感》,说其中两支相反相成的思想主流在每一节都交互环锁、层层渗透,解释杜运燮《露营》和《月》二首,描述其感觉曲线,曲折变易,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都十分精辟而富有创见。
四、袁可嘉先生对于中国当时诗坛“感伤”和“政治感伤性”的深刻观察,对“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的中肯分析,对于晦涩的讨论,以及40年代文学批评方面的种种问题都有十分独特的见解,至今犹值得我们深思。
九叶派诗论的渊源是丰富的,可谓有些“多元”。比如唐湜、陈敬容、杭约赫以及新时期以来的郑敏,都卓有贡献。然而,就时间较早和更有系统性、更完整的更有专门性来说,袁可嘉被公认为九叶派的理论家。
本文拟集中讨论1946年至1948年期间袁可嘉诗论之渊源。他这个时期(二十五至二十七岁)写的诗论文字,后来一直到1988年才汇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1月),这本仅二百五十页的小册子立即引起极大的注意,迄今已成为研究九叶派和中国新诗史的经典性文献。说起来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由于我是新时期以来对九叶派发表评论最早的一两个作者之一(我的论文曾经在几位在京九叶派诗人之中传阅,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定稿于1982年10月,题目为“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初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另一位是古典文学专家严迪昌教授,他的论文《他们歌吟在光明与黑暗交替时》发表于1981年底),袁可嘉先生委托我为他正在汇编的40年代诗论集《论新诗现代化》写序言,并在信中嘱我:“客观地介绍一下这些论文产生的背景和表述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意义,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总以平实中肯为好,也欢迎提出批评意见。”序言写成之后,本拟先在《读书》杂志发表一下,但因为写得太长,后来在编辑时甚至都没有以序言通常的位置放在这本论文集之前面。在这篇序言里,虽然按照袁可嘉先生的嘱咐,着重于这些论文的背景、诗论之要点分析,理论体系及其评价等方面,我仍然提示了这些诗论的渊源。我在序言里明确指出,袁可嘉属于瑞恰慈这类“文学批评家”,把批评作为科学,偏重于美学原理的探究,理论系统的建立,研究重于欣赏,制度化意味甚过一时的兴会感发,他的立论表现出智力与明晰,常常使用“剥笋式”的分析方法。但我也提到袁可嘉对于诗歌文本多有感触和发现,对诗有特殊敏感,而且能从中概括独到看法,因此也兼有艾略特这类“批评文学家”的特长。所有这些话,都有一个用意,即想暗示袁可嘉诗论在渊源上与瑞恰慈和艾略特的联系。时光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一直没有可能把这项已经提出来的课题加以完成,而学术界也没有任何人试图着手去做。旧话重提,朝花夕拾,我认为这个课题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想必仍然为学术界所关注。从选题方向与选题战略说,甚至更应该受到关注了。
根据他的自述,写这些诗论的时候,他正在刚从昆明迁回北京之北京大学西语系任助教。他是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受聘于此。1946年至1948年这两年间,正是九叶派形成风格和臻于成熟的时期。他正是在这个时期发表较多诗作的。这就是说,他是置身于这一诗潮,在其中学习、体验、创作与思考,与此同时,对这一思潮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袁可嘉当年的这些诗论所发表的报刊,主要是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艺周刊》,和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袁可嘉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艺术方向上的转变过程。1941年秋天,他开始就读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大学一年级的那年,他主要沉浸于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他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深受感染,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作他想了。又由于受杨振声教授口衔烟斗,娓娓而讲徐志摩的感染,喜爱上了徐志摩的诗。1942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兴趣从浪漫派文学转向现代派文学。就在这一年,他先后读到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更切近现代人的生活。当时西南联大校园内正刮着一股强劲的现代风,袁可嘉学习现代派诗的象征手法和机智笔触,力求把现实、象征和机智三种因素结合起来,使诗篇带上硬朗的理性色彩。他在奥登《在战时的中国》的启迪下,用不算严格的十四行体,描绘上海、南京和北平几个大都市的外貌和实质,力求用形象突出它们各自的特点。这些有代表性的诗,我都选进了我编选的《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袁可嘉先生在他的1992年12月定稿的《自传》里称这个选本“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九叶派选本”),读者不妨与他的理论文章参照研究。他在1948年大学毕业时用英文撰写的论文《论叶芝的诗》可谓是他写诗论的发轫。
袁可嘉先生后来在七十一岁时回顾说:“三四十年代是西方新诗潮和我国新诗潮相交融,相汇合的年代。在西方,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奥登的影响所向披靡;在我国,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和后来所谓‘九叶’诗人也推动着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走向中国式现代主义。这是一个中西诗交融而产生了好诗的辉煌年代。但截止四十年代中叶,诗歌理论明显地落后于实践,对西方现代诗论虽已有所介绍,可对西方和我国新诗潮的契合点还缺乏理论上的阐明。”(《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这里所说的“诗歌理论”,即在我上文曾经提到的瑞恰慈一类的科学的、体系性的、偏重于美学原理的文学批评,而袁可嘉先生所寻到的“契合点,”就是他那个时期里一再说起的“新诗戏剧化”理论。这个理论,也可以径直叫作“新批评”:袁可嘉曾经把当年那个时期那些诗论以《新批评》为名,收入朱光潜主编的一套诗论丛书,因战乱关系,稿件在投寄途中丢失。对于本文来说甚至显得更重要的,是袁可嘉在这回顾里还说,他所受英美新批评派和现代派启迪的诗论基本观点有以下三点:第一,诗是多种因素结合的有机组织,成败决定于整体效果;第二,诗与主、客观有机联系,不可偏执一端;第三,诗表现手法的现代化问题。这些论述都为本文提供确凿的线索和根据。
在进入袁可嘉诗论的渊源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声明,希望读者不要读过此文之后,下意识地就觉得好像袁可嘉诗论的独创性立刻减少,他们想,呵,原来如此,他的理论都是从别处来的呀。这种情况在很多著名的作家身上都发生过,据我所知,很多作家都不愿意,很不希望看到批评家考据出他的作品受到别人的影响。茅盾说他在写《子夜》之前根本就没有读过左拉的小说《金钱》。曹禺婉转否认别人说《雷雨》受影响于易卜生的《群鬼》和尤金·奥尼尔《榆树下的爱情》,更否认《日出》脱胎于小仲马《茶花女》。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写了篇论文来讨论九叶派诗人杭约赫的抒情长诗《复活的土地》所受艾略特名诗《荒原》的影响,我以为分析得有根据,作者有自己的发现。我兴致勃勃带去杭约赫家里给他看,说这是对于九叶派深入研究后的一个进展。没想到,他一改往日通常的率真和亲切,以一种我很陌生的淡淡的冷淡回应说:过去也有人说我的《复活的土地》受到艾青的《复活的土地》的影响,其实根本没有联系。杭约赫的态度,我印象很深,深感意外和讶异。但当时我无从把他的误解给他加以分析。其实,任何人在进行创造时,都有一个历史背景,同时又在创造,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也都如此。列宁指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西方学者指毛泽东在哲学史上为黑格尔辩证学派。艾略特本人看起来是单枪匹马和作为第一个人,发掘了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其实,在他之前,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也重视英语诗歌的机智传统,他偏爱机智、精练的诗歌,同时也树立起古典主义形式完美的标准。从这两方面看,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约翰逊都可谓艾略特的先驱者。鲁迅则指明《狂人日记》这个题目直接来自果戈里的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是唐湜也用鲁迅的方法指出鲁迅杂文的文体渊源是外来的essay和feuilleton,及魏晋的论辩文章。另外,何乃英还撰写了《〈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袁可嘉先生本人在分析九叶派诗歌卓然独立的特质,并指明它“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和“诗歌气候新的转变”之同时,也还指出了这个“感性革命的萌芽和先驱”,指出了这个先驱就是卞之琳诗中传统感性与象征手法的有效配合,和冯至更富于现代意味的《十四行集》。这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脉络清晰地阐明了九叶派的诗史地位和独创性贡献,尤其是有助于深入分析九叶派是怎样崛起的,用什么样的属于自己所创造的艺术来崛起的。
当然,我写这些话,并不是害怕袁可嘉先生误解,他本人是一个学者,他在自己的论文里其实已经一再提及了他的诗论之渊源,我所做的,只不过对此详加分析就是了。同时,我还注重他在这当中的属于自己的卓越建树,以期对于他这两年时间里所说的“摸索”,作一些进一步的分析和归纳,从而把我们对于现代诗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袁可嘉在40年代后期,即他诗歌理论研究认真起步之时(1946.9.15—1948.
10.30),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文章,1988年全部编入《论新诗现代化》一书,其中有十篇选入他后来在1992年的自选集里,因而相对更重要。但他不是一开始就写了关于“新诗现代化”题旨的重要文章,论新诗现代化的第一篇写于他开始发表诗歌理论文章以来的半年之后,而确认他理论体系并婉转隐藏地为他的理论起名的那篇文章《谈戏剧主义》,发表于1948年6月8日,大约是在经过了两年的摸索之后。因为袁可嘉先生先学写诗,后来转向了理论,因此创作是他的基础。他的第一篇诗论是谈创作的,可以说是谈怎样写诗,不过不是谈自己写诗的经验,而是一些学习诗歌文本过程中的“发现”,题目叫“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第二篇谈及对当时诗坛流行倾向的一个重要观察,并概括为“政治感伤性”。接下来,他谈到了诗的主题、晦涩、道路这些当时诗坛上的比较重要的问题的观感。在谈过现代英诗“从分析到综合”演变历程之后,他开始进入“新诗现代化”这个话题。
《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3.30)是第一篇重要文章。袁可嘉所说“新诗现代化”,是指4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一种新诗,他说这种新诗的出现,无异于一场“改变旧有感性的革命”。他说在这改革活动的后面有七条理论原则,从理论脉络方面看,有理由认为,其中第七条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乃“新传统的寻求”之中心和重点,在这里,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意味着暗示、含蓄,而玄学则表现为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和机智的不时流露。请注意,这里带出来了三个概念:感觉、思想和感情,以及三者在诗里的相互关联。袁可嘉明确指出这个新诗的新传统,它乃来自西方诗现实、象征、玄学新的综合传统。接下来在第二篇论新诗现代化的文章《新诗现代化之再分析》(1947.5.18)里,袁可嘉论述这个新传统在技术方面的四点做法:(l)与貌似坦白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不同,这个新传统要用相应的具体事物表现“思想直觉”;(2)与浪漫派意象的“空洞含糊”不同,新传统的意象要求能惊人、离奇、新颖、丰富,所代表的事物要确切不移,因“情感思想强烈结合”,所以要求所产生的意义复杂;(3)与概念逻辑不同,作者通过想象逻辑对于全诗结构加以注意;(4)与流行的硬性文字不同,新传统要求诗的文字弹性与韧性。这四点做法的中心问题是意象、情感与思想三者的结合。有必要指出,袁可嘉在谈及这个新传统时,曾经说过有几条眼前还无细致复杂的作品可充例证,这句话可以“解构”他所说的“新传统”:既然都还没有作品可以参证,何来的传统呢?原来,袁可嘉所说的传统,并非都从已然的创作里归纳出来,同时也有一些是他本人的主张,或者说暂时还只是西方诗歌的特长。所以他说新传统的“寻求”,而不说新传统之“出现”,这其间的区别意味着,新传统正在被寻求因而也就正在形成之中。他所说的眼前还无作品可充例证的“传统”,有三条:(1)依赖文字通过声音、节奏、意象所能引致的联想;(2)想象逻辑;(3)琐事细节对于全体结构之功效。此三条之中最中心的问题,是想象逻辑。因此,这是袁可嘉诗论所触及的基本问题的第三点。
又经过一年以后,袁可嘉把他所理想的现代化新诗,从创作的角度加以归纳,并针对着当时诗坛的弊端,为回答如何使意志和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提出了“戏剧化”这个名称,这篇文章即题为《新诗戏剧化》(1948年6月,《诗创造》第12期)。概括这篇文章的意思,他所提出的如何克服说教与感伤弊端的要点是:融和思想的成分,从事物深处、本质之中转化自己的经验,而不要在诗里作激情的流露和放任的感情。他进一步详细地解释这样做的三种可能性:(1)如里尔克那样,把搜索自己内心之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打成一片;(2)像奥登那样,利用机智、聪明以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对象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从语气还有比喻的这部分表现,从不坦然裸露;(3)例如像艾略特那样写诗剧,诗剧面对现实时不可或缺的距离,象征功用使得不致过度现实,因此,现代诗剧的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综合的新传统,可谓是最佳选择,而这正是现代诗的主潮所要追求的。袁可嘉把他所理想、所主张的新诗用“戏剧性”一词标识,想必主要也由于受此现代诗剧的启示。这里所讲的里尔克、奥登、艾略特三种略有差别而又有着共同趋向的不同传统所体现出的三种可能性,乃是袁可嘉诗论的第四个基本问题。
与此文差不多同一时候,袁可嘉写成了他全部诗论里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谈戏剧主义》(1948年6月8日《大公报》)。上文刚才分析过的“戏剧化”,是袁可嘉对于他所理想、所归纳的现代化新诗的命名,而“戏剧主义”则是他对于自己批评理论的命名。我曾经在1998年把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命名为“症候分析理论”(《现代文学经典的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把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命名为“诗中主要情感分析理论”(《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5年出版),因此,我想论断说“戏剧主义”是袁可嘉对于自己批评理论的命名。但在1948年他把这些论文结集准备出版时,他用了“新批评”这个命名,1988年重新搜集出版时,用了“论新诗现代化”,这两次他都没有用“戏剧主义批评理论”这个命名。无论从时代和个人原因说,都是因为他想融入时代的文学潮流,不大看重个人的标新立异,或者说希望把个人的标新立异隐藏在时代思潮之深处。《论戏剧主义》这篇更核心、集大成的文章,谈了三个问题:(1)戏剧主义这个命名在心理学、美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的根据;(2)戏剧主义批评的四个特点;(3)戏剧主义批评常用术语。从他论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文里的新鲜内容是对于瑞恰慈“最大量的意识状态”以及“机智”、“讽刺感”两个术语的诠释,这三者也差不多就是戏剧主义批评理论之核了。此乃袁可嘉诗论的第五个基本问题。
以上我从四篇文章里在五个层次上提出五个基本问题。从本文的宗旨来看,这五个基本问题都能找到它的渊源。好在袁可嘉先生在这些论文里,已经一再地为我们探讨这些渊源提供了线索。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有些悲伤,我揣测一定会有人因为我们分析了袁可嘉诗论的渊源就觉得他不那么重要了。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日本故事,故事说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粮食不够吃,父母年纪大了不能再劳动,就由子女背去深山老林让野兽吃掉。可是这个故事里的母亲,害怕的是背他去深山老林的儿子不认识来时路,于是就在儿子背上不时地摘一些树枝扔在地下,让儿子回家时有线索可循。现在我好像成了这个故事里的儿子,循着袁可嘉先生提供的线索,一步一步地把他投向深山老林。然而,这故事结局稍有不同,那儿子因母亲的行为深受感动,最后又把母亲背回了家。为了把为我们提供理论渊源之线索的袁先生背回家,我将在本文结束部分,认真讨论一下他的独创性和卓越贡献。
袁可嘉诗论五个基本问题的理论渊源,我想可以简述如下。在这方面,袁可嘉先生在最早的论文里即已指出,他说现代西洋诗以艾略特为核心,现代西洋诗批评,以瑞恰慈的著作为核心。下面提出的五个方面,皆来自艾略特与瑞恰慈的代表性论著。
一、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里,袁可嘉指出40年代以来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诗歌感性改革活动后面,有七条理论原则,其中心和重点,乃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而这个新诗的新传统,它们来自西方诗歌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袁可嘉一再说过西方现代诗的主潮所追求的正是这个传统,而诗剧正配合这个要求。在诗剧创作方面的情况是,1932年,艾略特企图复活诗剧,写了《大力士斯威尼》作为试验。1935年他发表了第一出诗剧《大教堂中的谋杀》。诗剧之外,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也表现了这个传统。我还不妨解释一下,这里的玄学乃指艾略特所发掘的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传统;象征,指法国19世纪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袁可嘉本人注意及此,乃因为从卞之琳广场创作受到了启示。最后,袁可嘉题目里所谓“新传统”里的“传统”这个词,不是我们通常所谓文学传统的那个传统,而是经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年)里所阐述的那个“传统,”在这里,艾略特对传统这一概念作出了重新评价:在成熟的诗人身上,过去的诗歌是他的个性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也受到现在的修改。真正要做到创新,必须深切意识到不断变化中的“欧洲思想”的存在,并且也意识到自己是它的一部分。为了达到与欧洲诗歌的整体建立有机的联系这一目的,诗人必须树立起消灭自己个性的目标。
二、《新诗现代化再分析》一文在论述“新传统”在技巧方面几点做法时所说的“思想感觉”和“情感思想强烈结合”,均来自艾略特。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1921年)里说,玄学派诗歌是伊丽莎白时代英诗的逻辑发展,应是英诗的主流。他指出玄学派诗歌特点是:形象化的描述极为丰富和具体鲜明,所使用的比喻既具有物体的,也具有理性的涵义,因此能够巧妙地把思想、感情和感觉三个因素结合成一体。这个统一体,17世纪诗人称之为“机智”(wit),机智是能够使“无联系的经验”集合在一起的敏锐的智力。这个诗歌传统具有一种“感觉的机制”,好像熔炉,把思想熔化成为感情的反应。这个“感觉把思想熔化为感情”的特点,不幸在17世纪后半叶消失了。在德莱顿以后的新古典主义诗歌中,出现了感觉的分离,失去了它与感情和感觉的联系,成为今日意义的“机智”:诙谐或戏谑。另一方面,在弥尔顿的诗中,激动的雄辩又和“机智”分离,结果导致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诗歌。
三、也是在《新诗现代化再分析》一文里,袁可嘉在探讨他所说的眼前还暂时无作品可充例证的“传统”时,特别提到“想象逻辑”。这个问题,艾略特和瑞恰慈曾一再论及。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说:诗人的职务只是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没有的感觉。他说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而这些经验在讲实际、爱活动的一种人看来就不会是什么经验。他说这种集中的发生,既非出于自觉,亦非出于思考,诗人仅仅是被动地伺候它们变化而已。这里讲的化炼、集中、被动和与实际经验不同,都是在说“诗想象”是怎么一回事。瑞恰慈在《想象》一文里说,诗想象具有有机的综合能力,在一切艺术中想象表现得明显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把纷乱的、互不联系的各种冲动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有条理的反应。在《诗的经验》一文里,他又说,在文字的运用上,诗歌与科学是相反的。十分确切的思想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选择文字尽量合乎逻辑,而是由于神情、声调、节奏、韵律在我们的兴趣上发生作用,并且使兴趣由无数的可能中选出它所需要的确切而又特别的思想。
四、在《新诗戏剧化》一文里所说“融和思想成分,从事物深处,本质之中转化自己的经验”之三种可能方式:(1)把搜索自己的内心之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打成一片,来自里尔克的《图像集》;(2)利用机智、聪明、语言、比喻、活泼又内敛,来自抗战时期奥登的作品;(3)诗剧方式,来自1935年前后艾略特等的诗剧创作。
五、袁可嘉“戏剧主义批评理论”的三个核心术语之渊源:
(1)“最大量的意识状态”:瑞恰慈在《想象》一文里说,人生价值的高低,完全由它协调不同质量的冲动的能力而决定。冲动协调后的状态,他称之为态度,实际即是心神状态。能调和最大量、最优秀的冲动的心神状态,是人生至境,这就是瑞恰慈所谓“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含义,他认为艺术或诗的创造都具有这种功能。
(2)机智:艾略特、瑞恰慈都有较充分的解释,前引艾略特《玄学派诗人》已经为读者所知了,瑞恰慈在《想象》和《诗的经验》两篇文章里也多有讨论。袁可嘉归纳这些讨论,界定“机智”乃泛指作者在面对某一特定处境时,同时了解这个处境所可以产生的许多不同的复杂态度,它使诗歌意外地生动和丰富。
(3)讽刺感:瑞恰慈在《想象》一文里说,有一种诗歌是经不起用讽刺的态度来观赏的,如济慈的“你的嘴唇,滑溜的幸福”。这里所说的讽刺是把对立的补充的冲动引进来。这就是为什么容易受讽刺的诗不是最高级的诗,而最高级的诗的特点总是讽刺的。袁可嘉先生据此解释说:讽刺感是一种欲望与心情,诗人在指陈自己的态度时,同时希望相反相成的态度,它是争取异己,在诗中为不同于诗中主要情绪的因素。它与机智不同,机智只是消极地承认异己的存在,而讽刺感则积极地争取异己。
最后,由于本文篇幅已经够长了,我想只能直接以结论的形式,说说袁可嘉诗论的独创性与卓越贡献。
一、追踪西方诗歌主潮,思考我国当下诗坛面临的问题。对于西诗主潮追踪,多从艺术本身下功夫,很内行,对于当时诗坛弊端的批评,一针见血,见解独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袁先生正是如此做的,在40年代的诗坛,做得十分成功,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二、瑞恰慈的理论著作,十分晦涩难懂。在此之前,因瑞恰慈1930年前后曾经在中国北平任教,好些人都在他的著作里下过功夫,如李安宅、吴世昌等,但袁可嘉不仅详尽准确地诠释了瑞恰慈,而且用以观察中国诗坛,成就令人瞩目。
三、袁可嘉先生在有渊源有背景的情况下,却不满足于变相编译或照抄,而处处都可见他的深入体会与独创性见解,这些体会与创见,甚至完善和完成了艾略特、瑞恰慈的理论,而对于中国诗坛、中国新诗的发展,其功更不可淹没了。顺便举例来说,比如对于想象逻辑,艾、瑞二人论述比较分散,也不够具体,而袁可嘉先生确切地加以具体归纳,认为所谓想象逻辑,乃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对于诗歌十分重要,它可以结合不同经验,使意义加深、扩大、增重。他又用艾略特长诗作解,认为表现在这些诗里,是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突兀片段,或则扩大某一行或某一意象的蕴意,或则加深某一情绪的起伏、撼荡,或者加速某一观念的辩证引进。又比如他以瑞恰慈理论解释穆旦诗《时感》,说其中两支相反相成的思想主流在每一节都交互环锁、层层渗透,解释杜运燮《露营》和《月》二首,描述其感觉曲线,曲折变易,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都十分精辟而富有创见。
四、袁可嘉先生对于中国当时诗坛“感伤”和“政治感伤性”的深刻观察,对“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的中肯分析,对于晦涩的讨论,以及40年代文学批评方面的种种问题都有十分独特的见解,至今犹值得我们深思。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