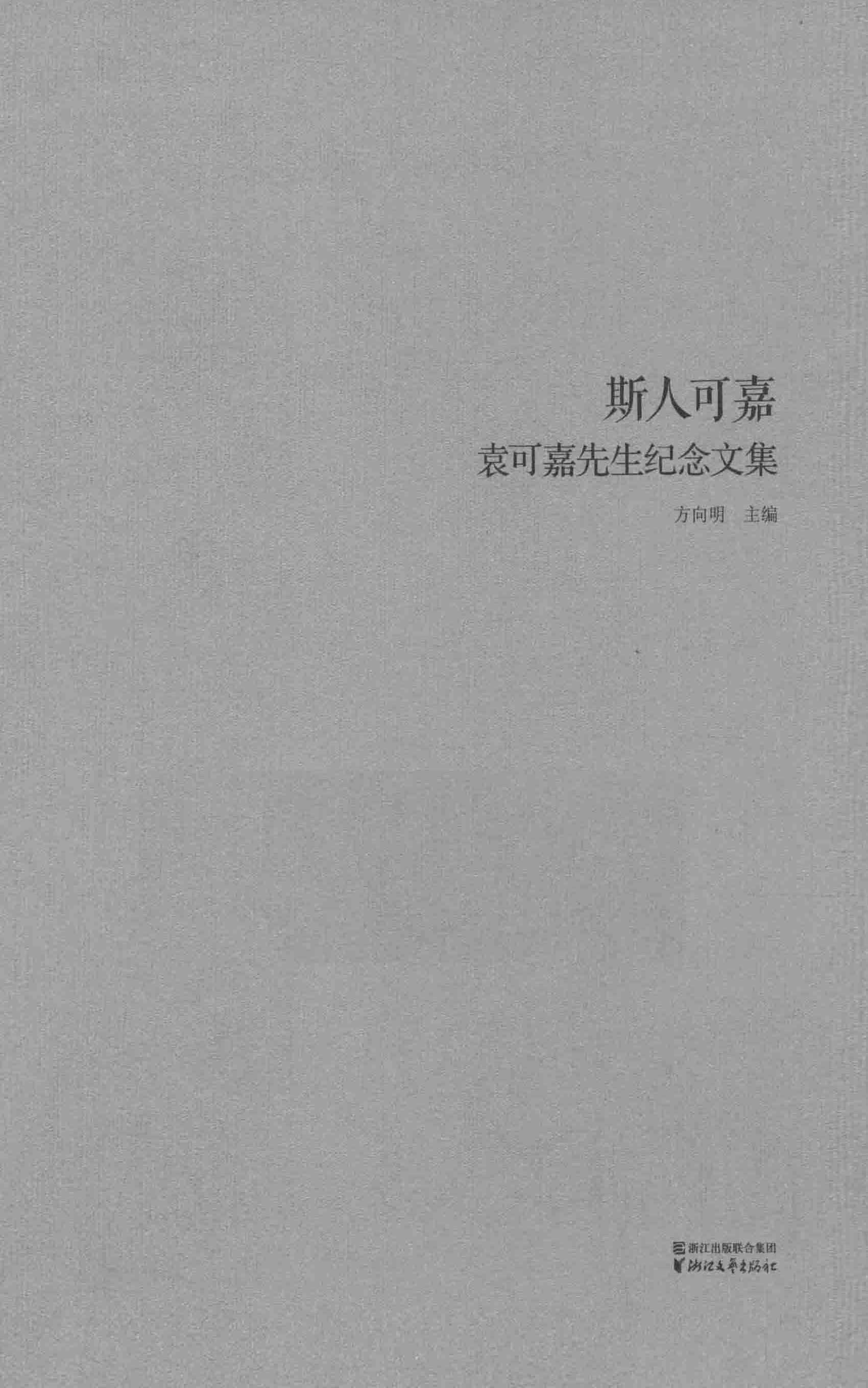照亮和提升:袁可嘉对叶芝的翻译
| 内容出处: | 《斯人可嘉 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4276 |
| 颗粒名称: | 照亮和提升:袁可嘉对叶芝的翻译 |
| 分类号: | K825.6-53 |
| 页数: | 9 |
| 页码: | 242-250 |
| 摘要: | 本文主要讲述了袁可嘉所翻译的叶芝诗歌对于文学青年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当你老了》和《柯尔庄园的野天鹅》这两首诗所带来的照亮和提升。文章认为袁可嘉的译作极其优异,因为只有经过他的翻译,叶芝的诗歌才能被读者真正理解并产生深刻的影响。袁可嘉的译作让我们看到了痛苦而明亮的精神性以及高贵、明澈和精英的气质,并且对于读者的生活和创作有着持久的影响。 |
| 关键词: | 评论 文学研究 袁可嘉 |
内容
对于我们这一代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的文学青年来说,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怎么说也不过分。我是在上大三时第一次从那上面读到卞之琳译的瓦雷里,冯至译的里尔克,穆旦(查良铮)、赵萝蕤译的艾略特,袁可嘉译的叶芝的。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贵,我不仅从中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现代主义艺术洗礼,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那还是一种照亮和提升——尤其是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让我看到了那颗照耀我的星。
在袁先生所译的那一组叶芝诗中,深深影响了我的是《当你老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这两首。《当你老了》这首诗之所以对那时的我那样重要,是因为我一读就感到它已写出了我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中间的两句“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使我深受震动,仿佛就是在那一瞬,我被带向一个更崇高的生命境界,或者说,在这样的诗句中仿佛有某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出现了,而它的出现提升了我,也照亮了我。
我想,这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可称之为“精神性”,它闪耀着精神的元素。正是这种痛苦使理想熠熠生辉,而这也正好应和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某种内在诉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读了也让人难忘,它像木刻一样富有质感,并显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度。这些,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写作都有着持久的影响。
至于《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所体现的那种高贵、明澈和精英的气质,还有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深深打动了我,“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疼心”,这样的诗句我一读就永远记住了。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阅读对我具有“创伤经验”的性质。从此,我只能捂住这样的伤口生活。
这些,就是袁先生所译的叶芝在那时对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正因为读了这样的诗,我们必须像叶芝说的那样,“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这些,我已在一些文章中谈过。现在,我想从翻译的角度具体谈谈袁先生所译的叶芝,因为不经过他那优异的翻译,叶芝就有可能被我们错过,就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看袁先生所译的《茵纳斯弗利岛》:
TheLakeIsleofInnisfree
Iwillariseandgonow,andgotoInnisfree;
Andasmallcabinbuildthere,ofclayandwattlesmade;
NinebeanrowswillIhavethere,ahiveforthehoneybee,
Andlivealoneinthebee-loudglade.
AndIshallhavesomepeacethere,forpeacecomesdroppingslow,
Droppingfromtheveilsofthemorningtowherethecricketsings;
Theremidnight’salla-glimmer,andnoonapurpleglow,
Andeveningfullofthelinner’swings.
Iwillariseandgonow,foralwaysnightandday
Ihearlakewaterlappingwithlowsoundsbytheshore;
WhileIstandontheroadway,oronthepavementsgray,
Ihearitinthedeepheart’score.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露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在谈到翻译时,英国诗人、德语诗歌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这样说:“诗歌的翻译包括两个不同的功能和过程,为着简洁之故,我称之为阅读和写作。阅读指的是对原文的吸收和提炼,从仅仅直觉地把握原文的结构实质,到更有意识地努力把握原文呈现的任何语义或指涉上的困难。写作则指的是用另一种语言重构文本的能力。”①
对照《茵纳斯弗利岛》的原文和译文,我们即会马上感到袁先生所体现的对原文进行透彻读解和“用另一种语言重构文本”的优异能力。
叶芝说他是在怀着乡思走过伦敦舰队街时,听到叮咚的水声而刹那间产生了这首诗,并自认为这是“第一首具有自己的音乐节奏的抒情诗”。而袁先生的译作,不仅深切地把握了这声音的内在起源,也极富有创造性地在汉语中再现了其节奏、韵律和意象。“我就要动身走了……”(“Iwillariseandgonow”),译文一开始就“一锤定音”地确定了全诗的音质,“动身”、“走”和“去”这些动词的运用,也在汉语中重造了诗的姿态和节奏,十分动人。
总的来看,袁先生的翻译是“直译”式的,但正如帕斯所说:“在西班牙文中,我们称字面式翻译为servil(奴性式)……它更接近字典而不是翻译,翻译永远是一种文学活动。”②袁先生的“忠实”也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如对照第一节的最后一句“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Andlivealoneinthebee-loudglade),”就可体会到袁先生的精心处理,且不说音调多么动人,一个原文中没有的“听”,加入得是多么好!
在韵律上,原诗分为三节,每节四行,采用“ababcdcdefef”的交韵形式,在翻译时,袁先生也尽力地保持了这种押韵形式(除了第二节有所变动)。更重要的是,袁先生的整篇译文读起来如此流畅自然,不仅富有节奏感和深长的韵律感,还具有了“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这样的汉语诗歌才具有的对称之美。
这也说明,诗的韵律不单是靠“押韵”来实现的,这是帕斯所说的“一种文学活动”,是一种综合的运作,是一种语言本身的“演奏”——通过像袁先生这样的诗人译者。而这种“演奏”的目的,不单是对应于原作的音韵形式,而是如美国诗人翻译家温伯格所说“应该为翻译出的文本创造出一种新的曲调”。(EliotWeinberger:AnonymousSources:onTranslatorsandTranslation)
袁先生的这首译作之所以如此令人喜爱,就在于他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曲调”。他把一首近一个世纪前的英文诗,变为一首更动人的当代中文诗。“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这其中的“日日夜夜”也是原文中没有的,它加入得多好!多么迫切催人!),的确,读了之后,这样的声音就会时时从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响起!
接下来,我们看袁先生对叶芝《当你老了》的翻译:
WhenYouAreOld
Whenyouareoldandgreyandfullofsleep,
Andnoddingbythefire,takedownthisbook,
Andslowlyread,anddreamofthesoftlook
Youreyeshadonce,andoftheirshadowsdeep;
Howmanylovedyourmomentsofgladgrace,
Andlovedyourbeautywithlovefalseortrue,
Butonemanlovedthepilgrimsoulinyou,
Andlovedthesorrowsofyourchangingface;
Andbendingdownbesidetheglowingbars,
Murmur,alittlesadly,howLovefled
Andpaceduponthemountainsoverhead
Andhidhisfaceamidacrowdofstars.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开篇一句即译得不同寻常,“Whenyouareoldandgreyandfullofsleep”被译作“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两个逗号的顿开,既避免了诗句的冗长,又在中文中再造了一种诗的节奏,而“grey”也被译为“头白了”,让人立刻进入到岁月流逝、人生沧桑的情境之中。人们都知道,这首诗是叶芝写给茅德·冈的名诗之一,诗人一开始就想象了一种“老了”的情境,并从这个视角反观一生。正因为这样一个视角,那经历的漫长一生才呈现在面前,它不仅指向眼神有着“浓重阴影”的青春往昔,更指向了人生中某种致命的“缺席”。这种“缺席”,正是人生忧伤的最根本原因。
但诗人并没有因此减弱或放弃他那灵魂的追求,“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这指的是因为写作对象年轻时代的美丽,在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追求者,而接下来,在袁先生的译文中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出现了:“Butonemanlovedthepilgrimsoulinyou,/Andlovedthesorrowsofyourchangingface”被译为“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里,首先,袁先生增加了原诗没有的“只有”一词,这种有意的强调,使这句诗顿时成为全诗的重心所在:“只有一个人”才能抛开人生的浮华,和她一起朝向那更高的精神事物;“只有一个人”,所强调的更是一种真正的爱的绝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接下来,袁先生又创造性地将“lovedthesorrowsofyourchangingface”译为“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正是这种强调和适度的改写,使这两句诗成为名句,或者说,使一首译作获得了它痛苦的、燃烧的内核。
在该文前面,我也讲了,正是这两句诗使全诗熠熠生辉,使这首诗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性”;使这样的诗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爱情诗,而把爱的追求与人生信仰的建立联系了起来,把真正的、不无痛苦的爱作为对灵魂的拯救。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翻译中的“捕捉”和“强调”:它抓住了原诗中最闪光的东西!
而全诗的结尾也十分耐人寻味:“垂下头来”(“andbendingdown…….”),这看似很忧伤,但消失(或者说错过)的爱并没有真正远离,而是“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这样的结尾真是“意犹未尽”,似乎消逝的爱一边远去,一边还回首对人们抱着期望——就看人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生了!
《当你老了》为叶芝早期代表作之一。在写这首诗时,年轻的诗人似乎已看到了这场恋爱的尽头,看到了某种悲剧性的宿命,这是该诗笼罩着一种忧伤调子的根本原因。但是因为该诗的中间两句“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尤其是经过袁先生在翻译时的种种处理,全诗却有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效果。它使每一个读到它的都受到震动,并由此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生命境界。
曾有人找出译文与原文明显的偏差,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一句,认为袁译不够“忠实”。但正如帕斯在谈翻译时所说:“庞德的诗是否忠实于原作?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作为中文诗的读者,我们都“宁愿”叶芝的原诗是这个样子。如按博尔赫斯的说法,“为什么原文就不能忠实于译文”?
正如一首诗的创作立足于自身的语言法则,一首诗的翻译同样立足于自身的语言法则。袁先生的翻译就这样获得了它自身存在的依据和理由。至于袁先生翻译的叶芝名诗《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则堪称译诗经典,译诗一开始,其语言的清澈就令人惊异:
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
林中的小径很干燥,
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
把寂静的天空映照:
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
五十九只天鹅浮游。
这种语言的清澈其实来自心灵的清澈,来自人生之秋的清澈。这种清澈是来自叶芝还是来自他的汉语的杰出译者?我们已无法分清;但五十九只光辉的野天鹅从此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成为诗的高贵、神秘和美丽的象征。
不仅如此,像“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uponthebrimmingwateramongthestones”,直译成“在石头间满溢的流水上”),还深具一种汉语之美,“盈盈”的运用多美!它更富有感情,也更动人。
而接下来,一种历历在目的语言刻画,使我们犹如身临其境,把我们切实地带入了一种诗的“现场”:
自从我最初为它们计数,
这是第十九个秋天,
我发现,计数还不曾结束,
猛一下飞上了天边,
大声地拍打着翅膀盘旋,
勾画出大而碎的圆圈。
把原文“alsuddenlymount”译为“猛一下飞上了天边”,更口语化,但也更有力量;“andscatterwheelingingreatbrokenrings”译为“勾画出大而碎的圆圈”,准确而又传神,尤其是“大而碎”这种描画,堪称大手笔,令人折服。
如果说叶芝早期带有一种感伤、朦胧、幻想性的诗风,他后来的诗不仅闪现着“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变得更坚实,更有艺术个性了。到了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叶芝说他在庞德的帮助下,“从现代的抽象回到明确而具体的所在”。袁译中这种历历在目的语言刻画,不仅使我们身临其境,也准确再现出叶芝中期的艺术转变和个性的加强。
触动我们的,还有这首译作中那种挽歌的调子,“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心疼”,诗译到这里,可谓一字千钧!叶芝于1897年首次访问格雷戈里夫人的柯尔庄园,1916年重访该地并写下了这首名诗。多年之后,诗人已步入人生的中年,柯尔庄园也即将被强行收归国有,这使叶芝十分感伤。叶芝本来就具有精英意识,在他看来柯尔庄园是一种古老而高贵的文明价值的象征,因此天鹅的光辉会使他“心疼”。他像那些写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中国古诗人一样,在目睹一种高贵的事物在他那个混乱而粗俗的时代消逝。因而袁先生会这样来译:“如今却叫我真心疼”!
同时,天鹅的年轻、美丽、激情和雄心,在它们身上体现的那种“永恒之美”,又引起诗人自己对人生岁月流逝的嗟叹。再接下来,诗的语调又缓和了。在诗的第三节,一个已经步履蹒跚的诗人在回想遥远的过去,而那也是个美丽的黄昏,“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thebell-beatoftheirwingsabovemyhead/trodwithalightertread”。值得留意的是,“”
)在袁译中突出了那时——还有什么比这更动情的回忆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动情的译文吗?如果对照原文和不同的中译本,我们就会感到唯有袁先生的译文才深刻传达出一种来自汉语世界的共鸣。这种诗的共鸣有赖于一种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的心灵“契合”,也有赖于一种精湛的语言功底。我甚至感到,在袁先生晚年翻译叶芝的这首名诗时,他是把他的一生的感慨都放在诗的字里行间了。是他自己还是叶芝在目睹一种高贵的事物在他那个时代消逝?总之,那已是同一个人。
诗的最后一节:“有一天醒来,它们已飞去,/在哪个芦苇丛筑居?/哪一个池边,哪一个湖滨,/取悦于人们的眼睛?”这样一个结尾,不仅使我们惘然,也使我们的视野得以扩展。它使我们从人生的有限和盲目性中“醒来”,而和诗人一起置身于宇宙的无穷中,去体会那世间的变迁和无常。
王佐良在评介叶芝时曾这样说道:叶芝初期的诗“朦胧,甜美而略带忧郁,充满了美丽的词藻,但他很快就学会写得实在、硬朗,而同时仍然保留了许多美丽的东西。他的诗歌语言既明白如话,又比一般白话更高一层,做到了透亮而又深刻”(《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我想,这也恰好是袁先生的翻译最终所达到的境界——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美丽、硬朗、透亮而又深刻的诗歌语言!
布罗茨基在谈翻译时这样说,“翻译是寻找对等物,而不是替代品”①。意思是翻译不应满足于一般的语言转换,而应创造出无愧于原作的对等物。袁先生对叶芝的翻译,就显示了这种一般译者不具备的能力。它显示了袁先生晚期炉火纯青般的翻译技艺和语言功力,它成为袁先生翻译生涯的一种总结。
至于袁先生的翻译诗学,很难挑出某一点来论述。我想起了在其40年代的诗论中,袁先生就希望他和他的同时代诗人能熔铸一种“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我想袁先生也正是这样来把握其翻译的。的确,翻译是一项综合的诗艺和创造活动。在他对叶芝的翻译中,有一种整体的艺术效果,更有照亮和提升。我们深深地感谢这位前辈!
在袁先生所译的那一组叶芝诗中,深深影响了我的是《当你老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这两首。《当你老了》这首诗之所以对那时的我那样重要,是因为我一读就感到它已写出了我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中间的两句“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使我深受震动,仿佛就是在那一瞬,我被带向一个更崇高的生命境界,或者说,在这样的诗句中仿佛有某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出现了,而它的出现提升了我,也照亮了我。
我想,这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可称之为“精神性”,它闪耀着精神的元素。正是这种痛苦使理想熠熠生辉,而这也正好应和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某种内在诉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读了也让人难忘,它像木刻一样富有质感,并显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度。这些,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写作都有着持久的影响。
至于《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所体现的那种高贵、明澈和精英的气质,还有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深深打动了我,“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疼心”,这样的诗句我一读就永远记住了。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阅读对我具有“创伤经验”的性质。从此,我只能捂住这样的伤口生活。
这些,就是袁先生所译的叶芝在那时对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正因为读了这样的诗,我们必须像叶芝说的那样,“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这些,我已在一些文章中谈过。现在,我想从翻译的角度具体谈谈袁先生所译的叶芝,因为不经过他那优异的翻译,叶芝就有可能被我们错过,就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看袁先生所译的《茵纳斯弗利岛》:
TheLakeIsleofInnisfree
Iwillariseandgonow,andgotoInnisfree;
Andasmallcabinbuildthere,ofclayandwattlesmade;
NinebeanrowswillIhavethere,ahiveforthehoneybee,
Andlivealoneinthebee-loudglade.
AndIshallhavesomepeacethere,forpeacecomesdroppingslow,
Droppingfromtheveilsofthemorningtowherethecricketsings;
Theremidnight’salla-glimmer,andnoonapurpleglow,
Andeveningfullofthelinner’swings.
Iwillariseandgonow,foralwaysnightandday
Ihearlakewaterlappingwithlowsoundsbytheshore;
WhileIstandontheroadway,oronthepavementsgray,
Ihearitinthedeepheart’score.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露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在谈到翻译时,英国诗人、德语诗歌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这样说:“诗歌的翻译包括两个不同的功能和过程,为着简洁之故,我称之为阅读和写作。阅读指的是对原文的吸收和提炼,从仅仅直觉地把握原文的结构实质,到更有意识地努力把握原文呈现的任何语义或指涉上的困难。写作则指的是用另一种语言重构文本的能力。”①
对照《茵纳斯弗利岛》的原文和译文,我们即会马上感到袁先生所体现的对原文进行透彻读解和“用另一种语言重构文本”的优异能力。
叶芝说他是在怀着乡思走过伦敦舰队街时,听到叮咚的水声而刹那间产生了这首诗,并自认为这是“第一首具有自己的音乐节奏的抒情诗”。而袁先生的译作,不仅深切地把握了这声音的内在起源,也极富有创造性地在汉语中再现了其节奏、韵律和意象。“我就要动身走了……”(“Iwillariseandgonow”),译文一开始就“一锤定音”地确定了全诗的音质,“动身”、“走”和“去”这些动词的运用,也在汉语中重造了诗的姿态和节奏,十分动人。
总的来看,袁先生的翻译是“直译”式的,但正如帕斯所说:“在西班牙文中,我们称字面式翻译为servil(奴性式)……它更接近字典而不是翻译,翻译永远是一种文学活动。”②袁先生的“忠实”也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如对照第一节的最后一句“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Andlivealoneinthebee-loudglade),”就可体会到袁先生的精心处理,且不说音调多么动人,一个原文中没有的“听”,加入得是多么好!
在韵律上,原诗分为三节,每节四行,采用“ababcdcdefef”的交韵形式,在翻译时,袁先生也尽力地保持了这种押韵形式(除了第二节有所变动)。更重要的是,袁先生的整篇译文读起来如此流畅自然,不仅富有节奏感和深长的韵律感,还具有了“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这样的汉语诗歌才具有的对称之美。
这也说明,诗的韵律不单是靠“押韵”来实现的,这是帕斯所说的“一种文学活动”,是一种综合的运作,是一种语言本身的“演奏”——通过像袁先生这样的诗人译者。而这种“演奏”的目的,不单是对应于原作的音韵形式,而是如美国诗人翻译家温伯格所说“应该为翻译出的文本创造出一种新的曲调”。(EliotWeinberger:AnonymousSources:onTranslatorsandTranslation)
袁先生的这首译作之所以如此令人喜爱,就在于他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曲调”。他把一首近一个世纪前的英文诗,变为一首更动人的当代中文诗。“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这其中的“日日夜夜”也是原文中没有的,它加入得多好!多么迫切催人!),的确,读了之后,这样的声音就会时时从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响起!
接下来,我们看袁先生对叶芝《当你老了》的翻译:
WhenYouAreOld
Whenyouareoldandgreyandfullofsleep,
Andnoddingbythefire,takedownthisbook,
Andslowlyread,anddreamofthesoftlook
Youreyeshadonce,andoftheirshadowsdeep;
Howmanylovedyourmomentsofgladgrace,
Andlovedyourbeautywithlovefalseortrue,
Butonemanlovedthepilgrimsoulinyou,
Andlovedthesorrowsofyourchangingface;
Andbendingdownbesidetheglowingbars,
Murmur,alittlesadly,howLovefled
Andpaceduponthemountainsoverhead
Andhidhisfaceamidacrowdofstars.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开篇一句即译得不同寻常,“Whenyouareoldandgreyandfullofsleep”被译作“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两个逗号的顿开,既避免了诗句的冗长,又在中文中再造了一种诗的节奏,而“grey”也被译为“头白了”,让人立刻进入到岁月流逝、人生沧桑的情境之中。人们都知道,这首诗是叶芝写给茅德·冈的名诗之一,诗人一开始就想象了一种“老了”的情境,并从这个视角反观一生。正因为这样一个视角,那经历的漫长一生才呈现在面前,它不仅指向眼神有着“浓重阴影”的青春往昔,更指向了人生中某种致命的“缺席”。这种“缺席”,正是人生忧伤的最根本原因。
但诗人并没有因此减弱或放弃他那灵魂的追求,“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这指的是因为写作对象年轻时代的美丽,在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追求者,而接下来,在袁先生的译文中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出现了:“Butonemanlovedthepilgrimsoulinyou,/Andlovedthesorrowsofyourchangingface”被译为“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里,首先,袁先生增加了原诗没有的“只有”一词,这种有意的强调,使这句诗顿时成为全诗的重心所在:“只有一个人”才能抛开人生的浮华,和她一起朝向那更高的精神事物;“只有一个人”,所强调的更是一种真正的爱的绝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接下来,袁先生又创造性地将“lovedthesorrowsofyourchangingface”译为“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正是这种强调和适度的改写,使这两句诗成为名句,或者说,使一首译作获得了它痛苦的、燃烧的内核。
在该文前面,我也讲了,正是这两句诗使全诗熠熠生辉,使这首诗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性”;使这样的诗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爱情诗,而把爱的追求与人生信仰的建立联系了起来,把真正的、不无痛苦的爱作为对灵魂的拯救。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翻译中的“捕捉”和“强调”:它抓住了原诗中最闪光的东西!
而全诗的结尾也十分耐人寻味:“垂下头来”(“andbendingdown…….”),这看似很忧伤,但消失(或者说错过)的爱并没有真正远离,而是“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这样的结尾真是“意犹未尽”,似乎消逝的爱一边远去,一边还回首对人们抱着期望——就看人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生了!
《当你老了》为叶芝早期代表作之一。在写这首诗时,年轻的诗人似乎已看到了这场恋爱的尽头,看到了某种悲剧性的宿命,这是该诗笼罩着一种忧伤调子的根本原因。但是因为该诗的中间两句“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尤其是经过袁先生在翻译时的种种处理,全诗却有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效果。它使每一个读到它的都受到震动,并由此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生命境界。
曾有人找出译文与原文明显的偏差,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一句,认为袁译不够“忠实”。但正如帕斯在谈翻译时所说:“庞德的诗是否忠实于原作?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作为中文诗的读者,我们都“宁愿”叶芝的原诗是这个样子。如按博尔赫斯的说法,“为什么原文就不能忠实于译文”?
正如一首诗的创作立足于自身的语言法则,一首诗的翻译同样立足于自身的语言法则。袁先生的翻译就这样获得了它自身存在的依据和理由。至于袁先生翻译的叶芝名诗《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则堪称译诗经典,译诗一开始,其语言的清澈就令人惊异:
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
林中的小径很干燥,
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
把寂静的天空映照:
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
五十九只天鹅浮游。
这种语言的清澈其实来自心灵的清澈,来自人生之秋的清澈。这种清澈是来自叶芝还是来自他的汉语的杰出译者?我们已无法分清;但五十九只光辉的野天鹅从此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成为诗的高贵、神秘和美丽的象征。
不仅如此,像“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uponthebrimmingwateramongthestones”,直译成“在石头间满溢的流水上”),还深具一种汉语之美,“盈盈”的运用多美!它更富有感情,也更动人。
而接下来,一种历历在目的语言刻画,使我们犹如身临其境,把我们切实地带入了一种诗的“现场”:
自从我最初为它们计数,
这是第十九个秋天,
我发现,计数还不曾结束,
猛一下飞上了天边,
大声地拍打着翅膀盘旋,
勾画出大而碎的圆圈。
把原文“alsuddenlymount”译为“猛一下飞上了天边”,更口语化,但也更有力量;“andscatterwheelingingreatbrokenrings”译为“勾画出大而碎的圆圈”,准确而又传神,尤其是“大而碎”这种描画,堪称大手笔,令人折服。
如果说叶芝早期带有一种感伤、朦胧、幻想性的诗风,他后来的诗不仅闪现着“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变得更坚实,更有艺术个性了。到了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叶芝说他在庞德的帮助下,“从现代的抽象回到明确而具体的所在”。袁译中这种历历在目的语言刻画,不仅使我们身临其境,也准确再现出叶芝中期的艺术转变和个性的加强。
触动我们的,还有这首译作中那种挽歌的调子,“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心疼”,诗译到这里,可谓一字千钧!叶芝于1897年首次访问格雷戈里夫人的柯尔庄园,1916年重访该地并写下了这首名诗。多年之后,诗人已步入人生的中年,柯尔庄园也即将被强行收归国有,这使叶芝十分感伤。叶芝本来就具有精英意识,在他看来柯尔庄园是一种古老而高贵的文明价值的象征,因此天鹅的光辉会使他“心疼”。他像那些写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中国古诗人一样,在目睹一种高贵的事物在他那个混乱而粗俗的时代消逝。因而袁先生会这样来译:“如今却叫我真心疼”!
同时,天鹅的年轻、美丽、激情和雄心,在它们身上体现的那种“永恒之美”,又引起诗人自己对人生岁月流逝的嗟叹。再接下来,诗的语调又缓和了。在诗的第三节,一个已经步履蹒跚的诗人在回想遥远的过去,而那也是个美丽的黄昏,“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thebell-beatoftheirwingsabovemyhead/trodwithalightertread”。值得留意的是,“”
)在袁译中突出了那时——还有什么比这更动情的回忆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动情的译文吗?如果对照原文和不同的中译本,我们就会感到唯有袁先生的译文才深刻传达出一种来自汉语世界的共鸣。这种诗的共鸣有赖于一种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的心灵“契合”,也有赖于一种精湛的语言功底。我甚至感到,在袁先生晚年翻译叶芝的这首名诗时,他是把他的一生的感慨都放在诗的字里行间了。是他自己还是叶芝在目睹一种高贵的事物在他那个时代消逝?总之,那已是同一个人。
诗的最后一节:“有一天醒来,它们已飞去,/在哪个芦苇丛筑居?/哪一个池边,哪一个湖滨,/取悦于人们的眼睛?”这样一个结尾,不仅使我们惘然,也使我们的视野得以扩展。它使我们从人生的有限和盲目性中“醒来”,而和诗人一起置身于宇宙的无穷中,去体会那世间的变迁和无常。
王佐良在评介叶芝时曾这样说道:叶芝初期的诗“朦胧,甜美而略带忧郁,充满了美丽的词藻,但他很快就学会写得实在、硬朗,而同时仍然保留了许多美丽的东西。他的诗歌语言既明白如话,又比一般白话更高一层,做到了透亮而又深刻”(《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我想,这也恰好是袁先生的翻译最终所达到的境界——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美丽、硬朗、透亮而又深刻的诗歌语言!
布罗茨基在谈翻译时这样说,“翻译是寻找对等物,而不是替代品”①。意思是翻译不应满足于一般的语言转换,而应创造出无愧于原作的对等物。袁先生对叶芝的翻译,就显示了这种一般译者不具备的能力。它显示了袁先生晚期炉火纯青般的翻译技艺和语言功力,它成为袁先生翻译生涯的一种总结。
至于袁先生的翻译诗学,很难挑出某一点来论述。我想起了在其40年代的诗论中,袁先生就希望他和他的同时代诗人能熔铸一种“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我想袁先生也正是这样来把握其翻译的。的确,翻译是一项综合的诗艺和创造活动。在他对叶芝的翻译中,有一种整体的艺术效果,更有照亮和提升。我们深深地感谢这位前辈!
附注
①米歇尔·汉伯格《保罗·策当诗选》修订扩大版后,纽约PerseaBooks,2002。
②转引自王佐良《另一面镜子:英美人怎样译外国诗》见《论诗的翻译》,王佐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①JosephBrodsky:Lessthanone,FarrarStrausGiroux,1987。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