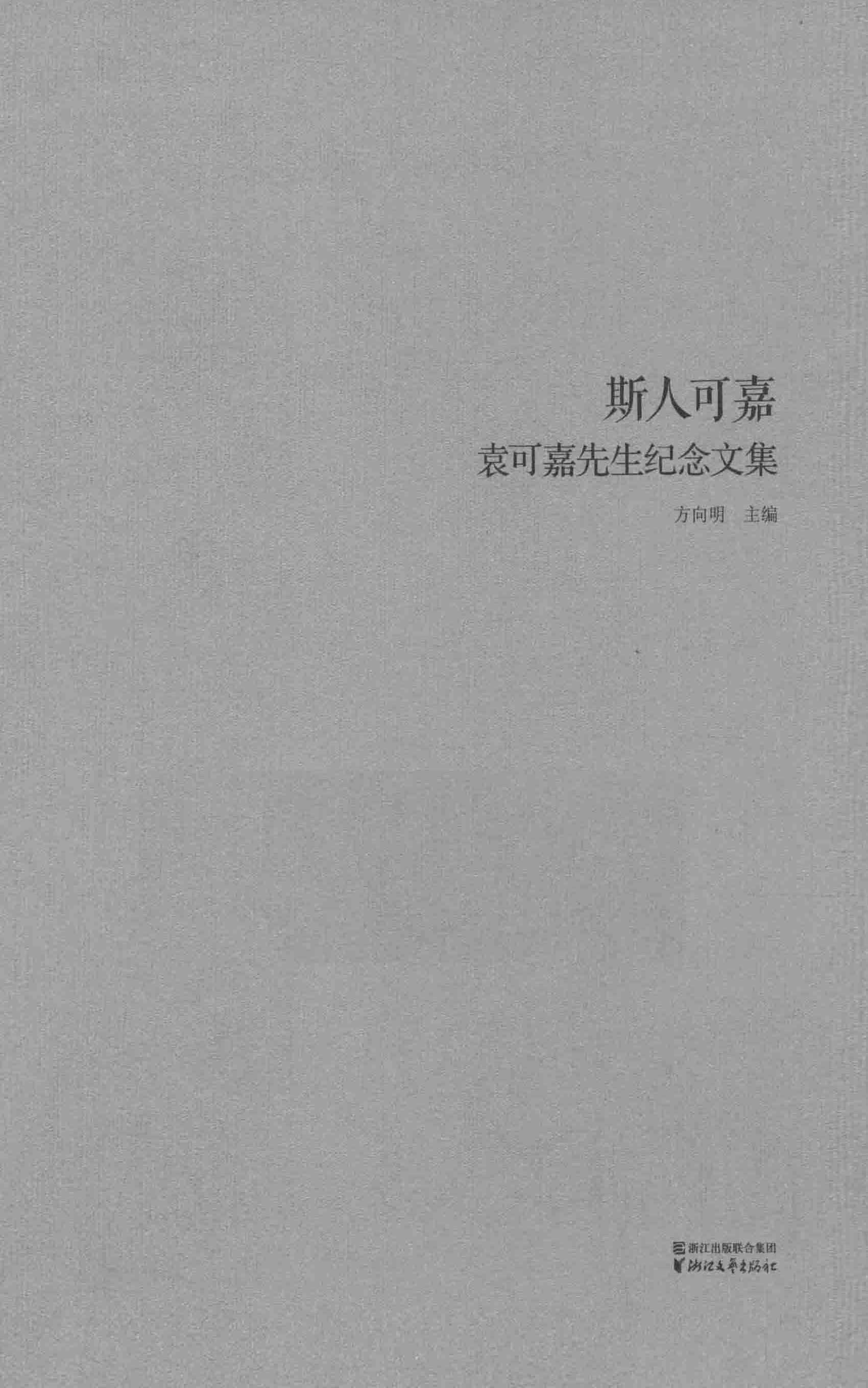斯人可嘉
| 内容出处: | 《斯人可嘉 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4255 |
| 颗粒名称: | 斯人可嘉 |
| 分类号: | K825.6-53 |
| 页数: | 6 |
| 页码: | 132-139 |
| 摘要: | 2008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我在美国参加诗学会议、交游览胜,主要在新英格兰地区,其间曾从华盛顿到波士顿,又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两度经过正好位于这两个中等城市之间的大都会纽约。没承想,在我离开美国正好一个月之后,他竟溘然羽化。这些年,听一些去过纽约的朋友回来说,他年迈体弱、健康欠佳;但我一直想,他心态平和,美国的医疗条件好,又有贤妻和孝女的精心照拂,还不至于出意外。得知噩耗,我还是觉得突然。意外还是出了,而且,据说还是医疗事故,家人送他去医院时,他的病情还不是太严重,医生给他扎了一针,他再也没有缓过来。但最终他恰恰亡殁于所谓的先进的美国医疗。如果有机会见到晓敏,我一定要当面致歉。 |
| 关键词: | 回忆录 文学研究 袁可嘉 |
内容
一、双重愧悔:途经纽约没去探望他
2008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我在美国参加诗学会议、交游览胜,主要在新英格兰地区,其间曾从华盛顿到波士顿,又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两度经过正好位于这两个中等城市之间的大都会纽约。我当然知道袁可嘉先生就在纽约当寓公,也带着他的名片(上面有他在纽约的住址),也曾动过去探望老先生的念头,但由于我在纽约停留的时间太短而终究没有去成。没承想,在我离开美国正好一个月之后(11月8日),他竟溘然羽化。这些年,听一些去过纽约的朋友回来说,他年迈体弱、健康欠佳;但我一直想,他心态平和,美国的医疗条件好,又有贤妻和孝女的精心照拂,还不至于出意外。得知噩耗,我还是觉得突然。意外还是出了,而且,据说还是医疗事故,家人送他去医院时,他的病情还不是太严重,医生给他扎了一针,他再也没有缓过来。记得他曾亲口对我赞美美国的医疗:生病了,只要打个电话或按一下床前的紧急按钮,救护车就会前来接你去医院,就诊后还会送你回家,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最终他恰恰亡殁于所谓的先进的美国医疗。先生去后没多少日子,他的女儿晓敏就曾从纽约给我打电话,但我的手机恰巧在长沙火宫殿吃饭时被偷,因此没有接到;她肯定特别着急,又打电话给我的领导,我才知道。如果有机会见到晓敏,我一定要当面致歉。
我在纽约时,之所以没去探望袁老,还有一个比较隐秘的原因:我有点怕见他。2001年,吴思敬老师说他主编的《诗探索》杂志打算做“袁可嘉研究”专辑,命我分工研究袁可嘉的诗。据我了解,在那之前,关于袁诗的评论文字散见于很多人的很多文章,但专文从未曾有过。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读他几乎所有发表了的诗作,联系跟他有关的中外其他诗人的作品,还联系他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歌翻译。我那时年轻气盛,不懂人情世故。在高度赞誉袁先生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肯定他的诗才尤其早期诗歌的优质的同时,对他的总体诗歌创作成就评价并不高,因为他写得少,而且原创性不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写的,更是散淡而平庸。当然,我更多地分析了他未能诗尽其才的原因,而且更多地归咎于外在的尤其是社会历史的因素。这篇题为“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的论文发表于2001年12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诗探索》杂志。袁先生当然是看到了的,听说他颇为不悦。尽管此文得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好评,如香港《诗网络》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关于袁诗研究的综述文章,有相当大的篇幅是介绍我的那篇“愣头青”论文,并给予了相当赞许的评价,说我对袁诗的价值判断客观、公允而直率。但我还是为自己当时的直率感到内疚。正如钱锺书《吴宓日记·序言》所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挽,真当焚笔砚矣!”“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希望袁老能在某种程度上原谅我一时的鲁莽灭裂。在纽约时,我应该抽出哪怕十分钟的时间,鼓起勇气去向老人家表达愧悔。而我终于没有去,心中的愧悔加倍了。
其实,当我听说袁老为我的文章而耿耿于怀时,曾经公开但委婉地表达过悔意——不是以歉意的方式,而是以敬意的方式。那就是我发表在2005年7月13日《中华读书报》上的随笔《高擎现代派文学之大旗》。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不知道我突然之间写作并发表(而且是发表在读书界影响最大的报纸上)这篇短文的用意。我不知道袁老在美国是否能看到,应该能看到的吧,因为“读书报”上的文章都是即时挂到互联网上的。我当然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我写的全部都是正面的词语:“袁可嘉不仅在新诗领域卓有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更是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心开拓者。”“袁先生思维的开放和敏感是一以贯之的。他不仅写作现代诗,而且重视研究诗论。如果说唐提是‘九叶’评论家,那么,袁先生就是‘九叶’理论家。”关于最后这句话,我想在此补充一句,他之作为“九叶诗派”的理论家,正如闻一多之作为“新月诗派”的理论家、胡风之作为“七月诗派”的理论家。
二、“九叶文库”:他的倡议我执行
袁先生是卞之琳在西南联大时的及门弟子,师生情谊至深。2000年12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原计划为庆祝卞之琳九十华诞而举行专题研讨会,在全家人都反对的情形下,八十高龄、明显老迈的袁先生执意抱病从纽约赶回来,为的是要跟六十年的老师见个面。他下飞机的当日,听到的却是卞老仙逝的噩耗,使他极为悲痛。庆生会变成了追思会。袁先生作为卞之琳的“老学生”头一个发言,他儿度哽咽得不能出声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当天晚上,我陪师兄江弱水去他位于永安南里的住处看望他。他在客厅里接见我们。由于长久没有人住,房子显得异常空落萧瑟。客厅极小,中间支着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餐桌。他念叨着他在1941年跟卞老第一次见面时的尴尬情景:“我初次见到他,冒昧地称他‘卡’先生,他纠正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袁先生的情绪平复了许多,但看着还是很累。我们怕打搅他休息,没有聊多久,就告退了。他送给我们他新出的书,其中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
第二天,我们去八宝山送别卞老之后,我邀请袁先生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因为在文学馆只是个小兵,无权要车接袁老;再则,他不是革命文学的大员,跟中国作家协会又素无关系,所以也不可能受到隆重的接待。我还记得,我和他的大女儿晓敏、江弱水和我的另一位师兄王毅一路陪护着他,他拖着病痛的躯体和哀痛的心灵,从八宝山出发,先乘地铁再打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文学馆。我赶紧找来轮椅,推着他去食堂,吃了点快餐,然后,我推着他去看展览,边走边作讲解。我当时跟沈从文一样,是挂牌的讲解员。我讲到了“卞之琳文库”的情况,虽然还没有真正建立,但由于我那段时间的努力协调,时任馆长舒乙先生已经同意。在文学馆展厅二层举足轻重的“20世纪文学成就展”中,“九叶诗派”占着偌大的版面;袁先生既细看诗友的展品,也看着自己的照片、书影与诗作,感到十分欣慰,这时他甚至变得兴奋起来。随后,我又推着他到舒乙的办公室。袁先生先就“卞之琳文库”的建成向文学馆表达了真挚的谢意;说到自己,他谦逊坦言:以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恐怕没有资格建文库,但问能否以“九叶诗派”集体名义建。舒乙当即拍板:“当然,没问题。”这就是文学馆中唯一一个多人文库的由来。在送走袁老他们之后,我又找到舒乙先生,提议:搞一个“‘九叶文库’建库仪式暨‘九叶诗派’学术研讨会”,由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舒乙又当场答应,但提了两条:一、不叫“建库”,叫“开库”;二、文学馆经费紧张(当时我们的工资都曾被拖欠过),只提供场地,不提供任何费用,这意味着我得去化缘。
第三天晚上,杜运燮先生做东,在袁先生附近的一家粤菜馆,二老请我吃饭,作陪的还有他俩的儿位家人。就在饭桌上,他们各自交给了我一批书,作为“九叶文库”的第一批资料。我郑重承诺,一定全力搞好开库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关于费用问题,杜老给我支招:可以找找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思敬老师,他们那儿的诗歌研究中心有一些经费。
为了把这件有历史意义的不大不小的事做成,我在一个炎热的傍晚找到了吴老师的府上,他爽快地答应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愿意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支持。2001年8月7日,经过我几个月的奔走,在文学馆多功能厅举行了非常像样的开库仪式和学术研讨会。袁先生远在纽约,因行动不便没能与会,但他认真地写了发言稿,由他的女公子晓敏代为宣读。我则代他朗诵了他早年的诗作《沉钟》。袁先生始终关心着“九叶文库”的建设。后来,他还曾从纽约托人带来了《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和《茵纳斯弗利岛》等著译手稿十二件,捐赠给文学馆。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我以诗坛译界晚辈的身份邀请袁先生到文学馆参观,并介绍了文库尤其是“卞之琳文库”,他才倡议建立“九叶文库”。我为自己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而感到高兴。其实,这个文库的建立为文学馆在“非主流”诗歌界提高了声誉、扩大了影响,意义也不可小觑。可惜,我现在的同事(包括领导)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内在价值。
三、回报心理:几乎所有经历写作现代化的作家都感谢他
当然,我这么做也是出于某种回报心理。因为从诗歌因承和代际来说,朦胧诗人是我的“诗父”,“九叶”诗人是我的“诗祖”。我记得,我刚上大学不久,就读了《九叶集》,是从图书馆借的,连借了两次;后来,我有幸结识了时任西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唐祈先生,与“九叶”诗人算是有了切身的接触。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写诗所遵循的一直是袁先生在《九叶集·序》中所概括的“九叶”所走的道路——现实、象征与玄思的结合。我向辛笛、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等学的是写诗,向穆旦、郑敏学的是写诗和译诗,向唐湜学的是写诗和评诗,而向袁可嘉学的是所有这三个方面。曾经有挚友戏说:我的理想是要成为袁先生那样的诗坛三栖人物。我不讳言自己有那样的野心。还是在大学期间,我读完了袁先生几乎所有关于现代派诗歌的著译,如《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等等。《论新诗现代化》收录的是他发表于1946年至1948年期间的诗论文章,共二十六篇。他那时的文笔还不怎么老到,有欧化之嫌,有些地方概念混乱,逻辑不清,词语芜杂,甚至有拗口重复的毛病。但观点新锐,与西方最先进的诗学同步,而且,从谋篇布局到措辞修辞,都有非常具体的设计。他在六十年前就不遗余力地鼓吹现代主义诗歌,而我们扫视当今的诗坛,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现代派?不是袁先生不想教,也不是后来的诗人们不想学,而是被切断了、阻隔了。他的这些文章本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结集了,计划收入朱光潜主编的一套丛书,但是,由于战乱、内乱,直到1988年,才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才重新发挥现代主义启蒙的作用,而那时受教的已经是我这个年龄的人了。
我买书买得最多的是外国诗歌的汉语译本,袁先生的译诗集我几乎全都买了,包括今天一般读者不会再看的《英国宪章派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重印的繁体字版)。这些译本我不仅读学,还研究。我本科时的专业是英语文学。我喜欢读老师一般在课堂上不教的英语诗歌,有看不懂的,读一下译文可能就明白了。我也同时练习着翻译诗歌,碰到翻来覆去还是词不达意的时候,读一下译文会有所启发。当然,我买的一般都是比较好的译本。但我喜欢比较不同的译本,看好翻译到底好在哪里;这样的比较研究对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大有裨益。上诗歌专业的研究生课时,导师邹绛先生是知名翻译家(朱光潜的嫡传)。他最重要的教学法就是这个。由于同级的师兄弟们英语不太灵光,邹先生一般都让我读原文,而且通过对比原文,谈谈不同译本的善与不善。邹先生推崇袁可嘉的翻译,只要有袁译的,他都要找来,让我们琢磨学习。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比较叶芝名作《茵纳斯弗利岛》的不同译本,经过逐字逐句的比较阅读之后,我得出结论:袁先生的是最棒的。比如劈头第一行“我就要起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简洁有力,干净利落,充分展现或者说还原了原作斩钉截铁的决心和毅力(除了专有名词“茵纳斯弗利岛”,叶芝用的几乎全部都是嘎嘣脆的单音节单词)。他的翻译正如他的学生彭予所概括的:“既忠实于原文,又不完全拘泥于原文,有非常好的整体效果。”
以上说的都是袁先生自己的著译,其实他影响中国知识界最大的是他和董衡巽、郑克鲁联合主编的一套大书《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卷八册,选入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十一个流派九十九位作家的一百九十四篇作品或作品片段),这套书总共有三百万字,历时五年才完成。关于此书的价值和意义,袁先生作为主其事者,是极为得意和自信的。他自己曾说:“由于此书是我国20世纪中惟一一部较完整的选本,选题严谨,译文优良,指导思想明确,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外国现代派作家作品,我都是通过这套书才开始接触的,然后,再去找完整的或更多的相关作品。它是窗口、道路、舟楫和指南,而它本身就那么宏富、多样而精当。这套书不仅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影响甚巨,20世纪80年代的读者,尤其是中青年文史读者,不管是诗歌界的、小说界的还是戏剧界的,没有看过这部书的人恐怕很少。因此,我在《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一文中,曾经说,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袁先生最劳苦功高的就是这套书。但这句话后来被《诗探索》的编辑给删掉了,也许那位编辑认为编书不能算什么大成就。但我不这么看。据《深圳商报》2008年12月5日报道,“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电集团等联合举办了“三十年三十本书”文史类读物评选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公众自由推荐、一个月的网络票选及手机短信投票,从三十年来三十万余本出版物中筛选出了一百本候选书目,最终呈交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组成的终审评委团与来自全国十六家知名媒体读书版编辑组成的复审评委团进行评选。在这个显示读物最高影响力的榜单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赫然在焉。
2008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我在美国参加诗学会议、交游览胜,主要在新英格兰地区,其间曾从华盛顿到波士顿,又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两度经过正好位于这两个中等城市之间的大都会纽约。我当然知道袁可嘉先生就在纽约当寓公,也带着他的名片(上面有他在纽约的住址),也曾动过去探望老先生的念头,但由于我在纽约停留的时间太短而终究没有去成。没承想,在我离开美国正好一个月之后(11月8日),他竟溘然羽化。这些年,听一些去过纽约的朋友回来说,他年迈体弱、健康欠佳;但我一直想,他心态平和,美国的医疗条件好,又有贤妻和孝女的精心照拂,还不至于出意外。得知噩耗,我还是觉得突然。意外还是出了,而且,据说还是医疗事故,家人送他去医院时,他的病情还不是太严重,医生给他扎了一针,他再也没有缓过来。记得他曾亲口对我赞美美国的医疗:生病了,只要打个电话或按一下床前的紧急按钮,救护车就会前来接你去医院,就诊后还会送你回家,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最终他恰恰亡殁于所谓的先进的美国医疗。先生去后没多少日子,他的女儿晓敏就曾从纽约给我打电话,但我的手机恰巧在长沙火宫殿吃饭时被偷,因此没有接到;她肯定特别着急,又打电话给我的领导,我才知道。如果有机会见到晓敏,我一定要当面致歉。
我在纽约时,之所以没去探望袁老,还有一个比较隐秘的原因:我有点怕见他。2001年,吴思敬老师说他主编的《诗探索》杂志打算做“袁可嘉研究”专辑,命我分工研究袁可嘉的诗。据我了解,在那之前,关于袁诗的评论文字散见于很多人的很多文章,但专文从未曾有过。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读他几乎所有发表了的诗作,联系跟他有关的中外其他诗人的作品,还联系他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歌翻译。我那时年轻气盛,不懂人情世故。在高度赞誉袁先生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肯定他的诗才尤其早期诗歌的优质的同时,对他的总体诗歌创作成就评价并不高,因为他写得少,而且原创性不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写的,更是散淡而平庸。当然,我更多地分析了他未能诗尽其才的原因,而且更多地归咎于外在的尤其是社会历史的因素。这篇题为“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的论文发表于2001年12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诗探索》杂志。袁先生当然是看到了的,听说他颇为不悦。尽管此文得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好评,如香港《诗网络》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关于袁诗研究的综述文章,有相当大的篇幅是介绍我的那篇“愣头青”论文,并给予了相当赞许的评价,说我对袁诗的价值判断客观、公允而直率。但我还是为自己当时的直率感到内疚。正如钱锺书《吴宓日记·序言》所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挽,真当焚笔砚矣!”“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希望袁老能在某种程度上原谅我一时的鲁莽灭裂。在纽约时,我应该抽出哪怕十分钟的时间,鼓起勇气去向老人家表达愧悔。而我终于没有去,心中的愧悔加倍了。
其实,当我听说袁老为我的文章而耿耿于怀时,曾经公开但委婉地表达过悔意——不是以歉意的方式,而是以敬意的方式。那就是我发表在2005年7月13日《中华读书报》上的随笔《高擎现代派文学之大旗》。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不知道我突然之间写作并发表(而且是发表在读书界影响最大的报纸上)这篇短文的用意。我不知道袁老在美国是否能看到,应该能看到的吧,因为“读书报”上的文章都是即时挂到互联网上的。我当然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我写的全部都是正面的词语:“袁可嘉不仅在新诗领域卓有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更是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心开拓者。”“袁先生思维的开放和敏感是一以贯之的。他不仅写作现代诗,而且重视研究诗论。如果说唐提是‘九叶’评论家,那么,袁先生就是‘九叶’理论家。”关于最后这句话,我想在此补充一句,他之作为“九叶诗派”的理论家,正如闻一多之作为“新月诗派”的理论家、胡风之作为“七月诗派”的理论家。
二、“九叶文库”:他的倡议我执行
袁先生是卞之琳在西南联大时的及门弟子,师生情谊至深。2000年12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原计划为庆祝卞之琳九十华诞而举行专题研讨会,在全家人都反对的情形下,八十高龄、明显老迈的袁先生执意抱病从纽约赶回来,为的是要跟六十年的老师见个面。他下飞机的当日,听到的却是卞老仙逝的噩耗,使他极为悲痛。庆生会变成了追思会。袁先生作为卞之琳的“老学生”头一个发言,他儿度哽咽得不能出声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当天晚上,我陪师兄江弱水去他位于永安南里的住处看望他。他在客厅里接见我们。由于长久没有人住,房子显得异常空落萧瑟。客厅极小,中间支着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餐桌。他念叨着他在1941年跟卞老第一次见面时的尴尬情景:“我初次见到他,冒昧地称他‘卡’先生,他纠正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袁先生的情绪平复了许多,但看着还是很累。我们怕打搅他休息,没有聊多久,就告退了。他送给我们他新出的书,其中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
第二天,我们去八宝山送别卞老之后,我邀请袁先生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因为在文学馆只是个小兵,无权要车接袁老;再则,他不是革命文学的大员,跟中国作家协会又素无关系,所以也不可能受到隆重的接待。我还记得,我和他的大女儿晓敏、江弱水和我的另一位师兄王毅一路陪护着他,他拖着病痛的躯体和哀痛的心灵,从八宝山出发,先乘地铁再打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文学馆。我赶紧找来轮椅,推着他去食堂,吃了点快餐,然后,我推着他去看展览,边走边作讲解。我当时跟沈从文一样,是挂牌的讲解员。我讲到了“卞之琳文库”的情况,虽然还没有真正建立,但由于我那段时间的努力协调,时任馆长舒乙先生已经同意。在文学馆展厅二层举足轻重的“20世纪文学成就展”中,“九叶诗派”占着偌大的版面;袁先生既细看诗友的展品,也看着自己的照片、书影与诗作,感到十分欣慰,这时他甚至变得兴奋起来。随后,我又推着他到舒乙的办公室。袁先生先就“卞之琳文库”的建成向文学馆表达了真挚的谢意;说到自己,他谦逊坦言:以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恐怕没有资格建文库,但问能否以“九叶诗派”集体名义建。舒乙当即拍板:“当然,没问题。”这就是文学馆中唯一一个多人文库的由来。在送走袁老他们之后,我又找到舒乙先生,提议:搞一个“‘九叶文库’建库仪式暨‘九叶诗派’学术研讨会”,由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舒乙又当场答应,但提了两条:一、不叫“建库”,叫“开库”;二、文学馆经费紧张(当时我们的工资都曾被拖欠过),只提供场地,不提供任何费用,这意味着我得去化缘。
第三天晚上,杜运燮先生做东,在袁先生附近的一家粤菜馆,二老请我吃饭,作陪的还有他俩的儿位家人。就在饭桌上,他们各自交给了我一批书,作为“九叶文库”的第一批资料。我郑重承诺,一定全力搞好开库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关于费用问题,杜老给我支招:可以找找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思敬老师,他们那儿的诗歌研究中心有一些经费。
为了把这件有历史意义的不大不小的事做成,我在一个炎热的傍晚找到了吴老师的府上,他爽快地答应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愿意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支持。2001年8月7日,经过我几个月的奔走,在文学馆多功能厅举行了非常像样的开库仪式和学术研讨会。袁先生远在纽约,因行动不便没能与会,但他认真地写了发言稿,由他的女公子晓敏代为宣读。我则代他朗诵了他早年的诗作《沉钟》。袁先生始终关心着“九叶文库”的建设。后来,他还曾从纽约托人带来了《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和《茵纳斯弗利岛》等著译手稿十二件,捐赠给文学馆。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我以诗坛译界晚辈的身份邀请袁先生到文学馆参观,并介绍了文库尤其是“卞之琳文库”,他才倡议建立“九叶文库”。我为自己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而感到高兴。其实,这个文库的建立为文学馆在“非主流”诗歌界提高了声誉、扩大了影响,意义也不可小觑。可惜,我现在的同事(包括领导)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内在价值。
三、回报心理:几乎所有经历写作现代化的作家都感谢他
当然,我这么做也是出于某种回报心理。因为从诗歌因承和代际来说,朦胧诗人是我的“诗父”,“九叶”诗人是我的“诗祖”。我记得,我刚上大学不久,就读了《九叶集》,是从图书馆借的,连借了两次;后来,我有幸结识了时任西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唐祈先生,与“九叶”诗人算是有了切身的接触。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写诗所遵循的一直是袁先生在《九叶集·序》中所概括的“九叶”所走的道路——现实、象征与玄思的结合。我向辛笛、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等学的是写诗,向穆旦、郑敏学的是写诗和译诗,向唐湜学的是写诗和评诗,而向袁可嘉学的是所有这三个方面。曾经有挚友戏说:我的理想是要成为袁先生那样的诗坛三栖人物。我不讳言自己有那样的野心。还是在大学期间,我读完了袁先生几乎所有关于现代派诗歌的著译,如《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等等。《论新诗现代化》收录的是他发表于1946年至1948年期间的诗论文章,共二十六篇。他那时的文笔还不怎么老到,有欧化之嫌,有些地方概念混乱,逻辑不清,词语芜杂,甚至有拗口重复的毛病。但观点新锐,与西方最先进的诗学同步,而且,从谋篇布局到措辞修辞,都有非常具体的设计。他在六十年前就不遗余力地鼓吹现代主义诗歌,而我们扫视当今的诗坛,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现代派?不是袁先生不想教,也不是后来的诗人们不想学,而是被切断了、阻隔了。他的这些文章本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结集了,计划收入朱光潜主编的一套丛书,但是,由于战乱、内乱,直到1988年,才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才重新发挥现代主义启蒙的作用,而那时受教的已经是我这个年龄的人了。
我买书买得最多的是外国诗歌的汉语译本,袁先生的译诗集我几乎全都买了,包括今天一般读者不会再看的《英国宪章派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重印的繁体字版)。这些译本我不仅读学,还研究。我本科时的专业是英语文学。我喜欢读老师一般在课堂上不教的英语诗歌,有看不懂的,读一下译文可能就明白了。我也同时练习着翻译诗歌,碰到翻来覆去还是词不达意的时候,读一下译文会有所启发。当然,我买的一般都是比较好的译本。但我喜欢比较不同的译本,看好翻译到底好在哪里;这样的比较研究对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大有裨益。上诗歌专业的研究生课时,导师邹绛先生是知名翻译家(朱光潜的嫡传)。他最重要的教学法就是这个。由于同级的师兄弟们英语不太灵光,邹先生一般都让我读原文,而且通过对比原文,谈谈不同译本的善与不善。邹先生推崇袁可嘉的翻译,只要有袁译的,他都要找来,让我们琢磨学习。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比较叶芝名作《茵纳斯弗利岛》的不同译本,经过逐字逐句的比较阅读之后,我得出结论:袁先生的是最棒的。比如劈头第一行“我就要起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简洁有力,干净利落,充分展现或者说还原了原作斩钉截铁的决心和毅力(除了专有名词“茵纳斯弗利岛”,叶芝用的几乎全部都是嘎嘣脆的单音节单词)。他的翻译正如他的学生彭予所概括的:“既忠实于原文,又不完全拘泥于原文,有非常好的整体效果。”
以上说的都是袁先生自己的著译,其实他影响中国知识界最大的是他和董衡巽、郑克鲁联合主编的一套大书《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卷八册,选入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十一个流派九十九位作家的一百九十四篇作品或作品片段),这套书总共有三百万字,历时五年才完成。关于此书的价值和意义,袁先生作为主其事者,是极为得意和自信的。他自己曾说:“由于此书是我国20世纪中惟一一部较完整的选本,选题严谨,译文优良,指导思想明确,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外国现代派作家作品,我都是通过这套书才开始接触的,然后,再去找完整的或更多的相关作品。它是窗口、道路、舟楫和指南,而它本身就那么宏富、多样而精当。这套书不仅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影响甚巨,20世纪80年代的读者,尤其是中青年文史读者,不管是诗歌界的、小说界的还是戏剧界的,没有看过这部书的人恐怕很少。因此,我在《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论袁可嘉的诗》一文中,曾经说,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袁先生最劳苦功高的就是这套书。但这句话后来被《诗探索》的编辑给删掉了,也许那位编辑认为编书不能算什么大成就。但我不这么看。据《深圳商报》2008年12月5日报道,“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电集团等联合举办了“三十年三十本书”文史类读物评选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公众自由推荐、一个月的网络票选及手机短信投票,从三十年来三十万余本出版物中筛选出了一百本候选书目,最终呈交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组成的终审评委团与来自全国十六家知名媒体读书版编辑组成的复审评委团进行评选。在这个显示读物最高影响力的榜单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赫然在焉。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