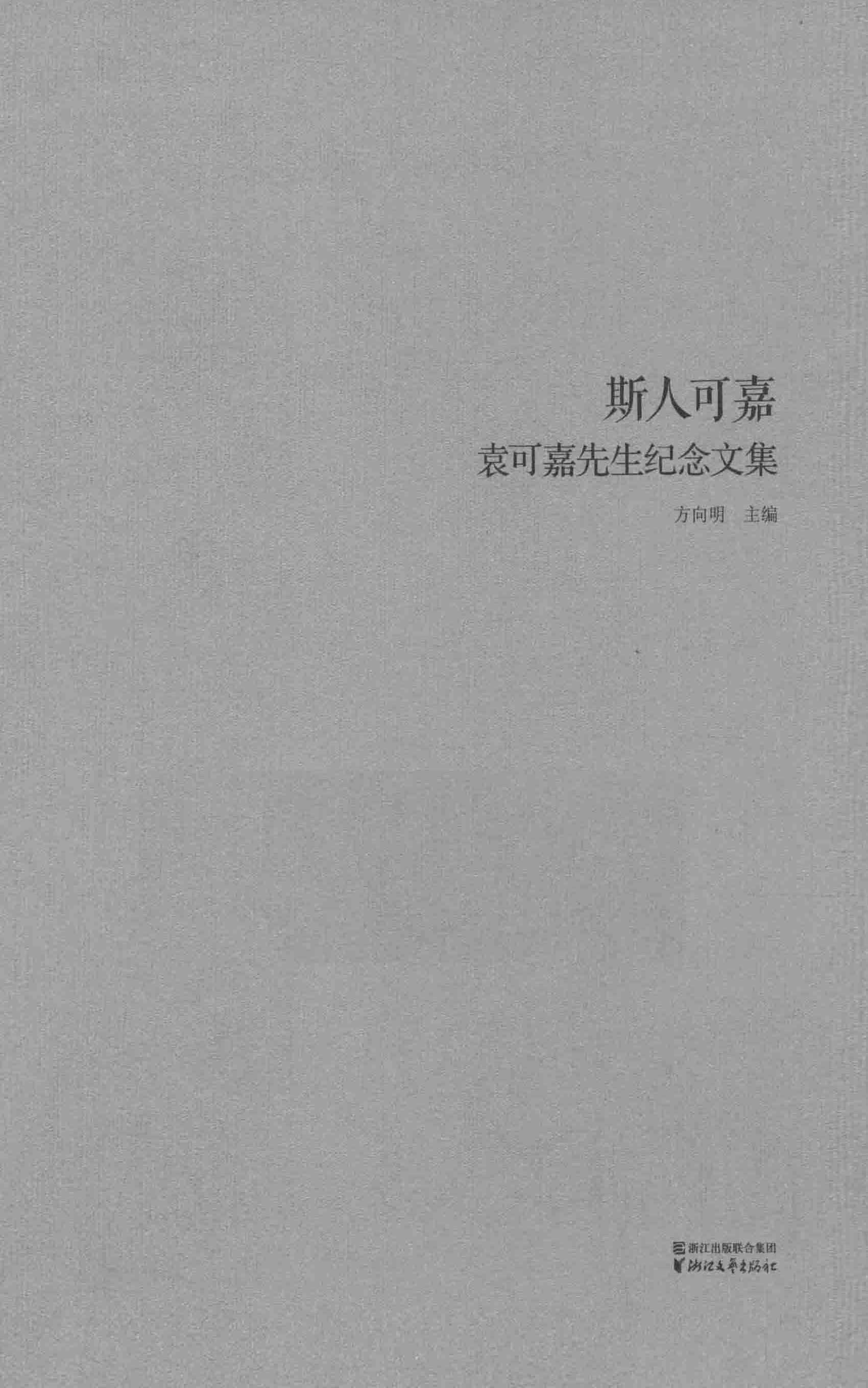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 内容出处: | 《斯人可嘉 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4242 |
| 颗粒名称: |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
| 分类号: | K825.6-53 |
| 页数: | 8 |
| 页码: | 064-071 |
| 摘要: | 11月10日下午,我坐在电脑前翻译着俄国诗人艾基的一首诗《死》,正在字斟句酌地推敲该诗的几个词句时,我突然收到朋友的一个短信:“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8日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八十七岁。”顷刻,我的内心不由得战栗了一下,为如谶的巧合感到了一丝生命的寒冷。数分钟后,接到编辑先生的电话,邀约一篇关于这位诗坛前辈的稿子,我没有任何推辞就答应了。虽说同在一个单位供职,我见到袁可嘉先生的次数并不多。而今获悉噩耗,我自然应该对这位仙逝的诗歌老人表达一份悼念和敬意。平心而论,政治为中国“五四”以降的新诗提供了坚硬的现实性,使政治抒情诗这一文体抵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
| 关键词: | 现代派 文学研究 袁可嘉 |
内容
11月10日下午,我坐在电脑前翻译着俄国诗人艾基的一首诗《死》,正在字斟句酌地推敲该诗的几个词句时,我突然收到朋友的一个短信:“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8日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八十七岁。”顷刻,我的内心不由得战栗了一下,为如谶的巧合感到了一丝生命的寒冷。数分钟后,接到编辑先生的电话,邀约一篇关于这位诗坛前辈的稿子,我没有任何推辞就答应了。
虽说同在一个单位供职,我见到袁可嘉先生的次数并不多。印象较深的是两次,一次是在杭州参加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在会议间隙有过短暂的交谈;另一次是在卞之琳先生的诞辰纪念会上,当时袁先生已移居美国,是专程回国来为老师祝寿的,这让我看到了前辈学者对“师道”的尊崇。而今获悉噩耗,我自然应该对这位仙逝的诗歌老人表达一份悼念和敬意。
就中国现代诗而言,袁可嘉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他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参与者,其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脚印”堪称对中国现代诗最好的丈量。
中国现代诗的复兴基本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算起,谈及这一点,绝不能绕开袁可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的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四卷八本的作品我家中便存有两套,是我和内人在当时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购买的,由此可见,此书在这个时间段成长起来的诗人、作家心目中的地位。正是通过这个重要途径,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较集中地接触到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的流派,知悉了瓦雷里、里尔克、叶芝、奥登、艾略特、勃洛克、洛尔加、卡夫卡、斯特林堡、马利奈蒂、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一大串当时十分陌生的名字和他们颇具启迪意义的写作。因此,说他是中国现代诗写作的“盗火”者绝不为过,其对年轻的中国诗人给予的启迪可谓功莫大焉。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序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背景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文章虽说不得已地留有时代的印痕,但其中的精彩就像褴褛的衣衫遮不住俊朗的身体,袁可嘉先生良好的学养、超人的艺术悟性、敏锐的现代意识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洋溢于字里行间,为读者给出了一张清晰的阅读地图。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成败得失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平心而论,政治为中国“五四”以降的新诗提供了坚硬的现实性,使政治抒情诗这一文体抵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峰。但同时,政治对诗的损伤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先生以西方诗歌作为参照和借鉴,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七项原则,构建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性的新传统。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多次谈到“政治抒情诗”的感伤性问题,颇富预见地指出了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重症。首先,他肯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体生命中诸般因子的“相对相成”,但反对其中任何一种质素或几种质素凌驾于全体之上的倾向。他承认诗与政治有平行的密切关系,“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他认为,这种对自身的束缚不仅会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对个人的生命意义造成伤害。同时,他又指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从属的关系,纯粹地为政治服务其实与另一个极端——“为艺术而艺术”就如硬币的两面,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为此,他重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一些所谓的“政治诗”,将其中的病症命名为“政治感伤性”,它们可怕地缺乏个性,遂导致艺术价值意识的混乱和颠倒,在写作上以“诗情的粗犷”为“唯一表现形式”,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以表达的观念来决定作品价值高下的标准。一首诗的好坏与否并不以艺术为准绳,只以主题作为绝对的判断。联系到作者写作这些文章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不叹服于作者认识之清醒,更为其意见没能得到更多的响应而备感遗憾。
此外,他对当时诗歌“散文化”的弊端,以及对日常语言的迷信、对激情的一味热衷、认定主题高于一切的谬论,等等,都作了独到的剖析和批评,为现代诗的回归本体、建立新的传统起到了一种拨乱反正的作用,迄今仍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
作为出色的翻译家、学者,袁可嘉在学术界内知名度甚高,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恐怕就鲜为人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翻译和研究的名声对他的诗名有着一定的遮蔽,另一方面则跟袁可嘉先生为人的谦逊与低调有关,在他为《九叶集》所作的序言中,他对其余八位诗人的写作特征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逐一给予了精到的评点和知音的赏析,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创作。然而,即以收入《九叶集》和《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的一部分作品而论,细心、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出,袁可嘉在原创性诗歌写作上也有过人的禀赋,其中如《沉钟》《进城》《走近你》《难民》《母亲》等,即便跻身于冯至、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中也毫不逊色,它们激情内敛、意象新奇、诗思隽永,且已粗具20世纪90年代诗人大量运用的“叙事性”、“戏剧化”的质素,堪称是“从分析到综合”的新探索。叶落归根是一种文化的归属感
童蔚
我的这个发言不是学术论文,只是随感,出于我对袁可嘉诗人的尊敬,我喜欢袁先生一些有分量的诗作,崇敬他这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献身事业的精神。
中国有句老话是“叶落归根”,它不是源自常识提炼出的知识,而是对人生的观照与比拟;我想,所谓“叶落归根”也不仅仅暗喻一个人肉体的生命回归故乡,而是指一个人对于文化与文明有着自觉的归属感。虽然,飘逝于异国他乡树下有“九叶”诗人中的一叶,但这片“落叶”仍然会在我们的母语中升起,这即是今天袁先生的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谈论他,也关乎叶落归根的终极意义。
袁老先生一生从事创作、评论、翻译,他的贡献属于这片土地。通过这种文化的根,可以纵向地深入儿千年,也可以横向地向外传播汉语文学以及吸纳西方文明。这是一个旋转的轴,而这位诗人、学者是用一生的岁月来推动的。因此,时间的磨盘上承载着他语言的分量、求索的印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磨盘上的精神食粮使一代读者接受到思想和文化的启迪,这也是我们民族最近的一次精神启蒙。袁先生在特殊年代所作出的贡献来自双方面的给予:即思想、文化匮乏年代读者对西方现代派作品阅读的渴求,这种需求量千载难逢;同时,面对机遇也是诗人、学者必须以自己的文化构成“对应”,肩负起传递的重任。这必然带来时间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也正是基于双方的“给”和“予”,奠定了他著书立说所能达到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80年代,“九叶”不是很红,却充满绿色的创造力,赢得过读者的尊重。袁先生在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包括他后来移居美国还推动、组织这边“九叶”的活动。当这样的曾经的贡献者逝去后,这种根与轴的合力是否依然存在且留有影响,就要看其推动的文化是否还有影响力。袁先生曾以一句诗表达过自己的心声,他说:“你决心献身奇迹。”无论当今的创作者是为了金钱还是奇迹埋首于工作,这样的想法依然还是存在着;而袁老先生不仅曾经期盼过,也敢为人先,承接过历史赋予的重任。
一次,袁先生在与我母亲郑敏乘火车赶赴会议的路途上说:我这一生最后留下的,就是我写的那些诗吧?这当然是一句非常非常谦虚的话,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绝对重视。以我很有限的阅读来看,我发现了他诗作中的个性魅力,就裹挟在对素材的捕捉中,这些生动的“材质”源自40年代的文化土壤,由此孕育出他的诗风——是以思想为中心的感性编织,是恰如其分的汉语与欧式译文美声的交织并且与坚实的诗歌结构相重叠。说到诗歌,我们也许首先看重作品蕴含的精神能量,即使面对一条街巷,诗人的抒写也一定出自灵魂的窗口选取词汇以达成作品的意志力及自由诗文本的质量。虽然,街道在时间的转换中会忽然变得面目全非,但诗人在作品中已经预留了宽广的思考空间,在时间中的阅读又总能返回到写作源头的那一刻,于是,我重读他的诗作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如,写于40年代的那首《难民》当中的诗句:
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
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
死也好,活也好,都只是为了别的,
逃难却成了你们的世代专业;
太多的信任把你们拖到城市,
向贪婪者求乞原是一种讽刺;
饥饿的疯狂掩不住本质的诚恳,
慧黠者却轻轻把诚恳变作资本;
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
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
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需的语言,
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
这些诗句就像经过流水的时光机器一样,在今天读来,仍然让读者感悟到触动,有冲击力。这并非由于政治正确,而是诗歌以语言旋律的调子,传达出诗人在时空中的深思,甚至是坦率、直接的诗意,也能把间隔了儿个历史阶段的现实层面,延展到诗歌的维度中,触及人性永恒的层面。
另一首写于1947年的《出航》,抒发了航海者对于离开土地的担忧以及无意之间涉及了人生的晚年:
航行者离开陆地而怀念陆地,
送行的视线如纤线在后追踪,
人们恐怕从来都不曾想起,
一个多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
年轻的闭上眼描摹远方的面孔,
远行的开始担心身边的积蓄;
老年人不安地看着钟,听听风,
普遍泛滥的是绿得像海的忧郁;
只有小孩们了解大海的欢跃,
破坏以驯顺对抗风浪的嘱咐,
船像摇篮,喜悦得令人惶惑;
大海迎接人们以不安的国度:
像被移植空中的断枝残叶,
航行者夜夜梦着绿色的泥土。
在我与晓敏的一次交谈中,得知她父亲晚年在异乡生活,物质优渥但精神苦闷。由此,我想到,精神世界的苦闷与创作之间的关联从而诞生了词语的奇迹,属于文学史辑录的作家常态。1947年,一个二十六岁的诗人就感知自己晚年的心绪,那是来自未知世界的灵感,当他辅以语言的技艺表达出来时,就是将生命的预感与文学结盟在一起的奇迹;如今,再次阅读,我以为那好比从远方传来的回声:诗人预言了自己的晚年,就像阳光照射在山上,也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语言的声线再次发出振动,这同时印证了语言在时间中的投影作用。
还是在80年代,在一次袁先生主持的诗歌讲座中,他请我朗读艾略特的诗作《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我于讲座前到他在永安里的寓所,品尝了袁伯母烹调的阳春面。在那里,我发现他们家和我们家一样,餐桌就在离门很近的过道上,而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老一辈知识分子都有着嗜书如命的“坏习惯”,至今如此。那个客厅如今浮现在我脑海里,印象就是袁先生要全力推动译介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气势。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是横向的轴,他不仅自己翻译,还组织人员、联系出版,那时他也应邀四处演讲,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向当时的年轻人全力推介现代派文学的理念与创作文本。
那回见面,袁老还跟我讲,你们这代女性非常不容易,要读书、工作,还要做家务,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女生,家庭都比较富裕,所以不用做家务。说这话时,我能觉察到袁老先生对时间的敏感。回首他从事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出其高产的效率是基于中青年时期优厚的积淀,当然,还有勇气。“文革”期间,他与“外面的学者”开始交往,他意识到交流的重要性,也许他还深信“门”最终是要被打开的。但在极为封闭的年代,先行者总是先付出“牺牲”,结果他就被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挨整,隔离审查,还有扫厕所等等体罚,吃了很大的苦。这些特殊的经历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属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烙印之一。“文革”后,大批创作者都属于过度压抑之后的“爆发”,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先抑后扬”。的确,在开放之初,最为前卫的文化创作者,正是在新时代的钟声还没有敲响之前,就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他们对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敏感异常,而且热爱一种文化是发自真心、深入骨髓的,绝非像一件时尚的外套可以随时更换。
不久前,在和晓敏的通话中得知,袁先生有着很深的“九叶”情怀。当晚年接近失明时,他非常惋惜不能和老友们通信了。“九叶”中的一些诗人在早年读书时,彼此就结下了友情。从这一点上说,“九叶”的各位都非常珍惜友情与诗情,他们的相聚是历史中的结缘,而非小团体主义的哥们儿义气。
我母亲说过,她很怕出席类似的活动,因为年事已高,但她会忽然跟我讲:“没关系,我不去还有曹辛之呢!”我想,这种错位的记忆,恰好体现出记忆本身所具有的遗忘与复活的功能。今天她没能来参加会议,但在电话里她非常鼓励袁晓敏出版她父亲的文集,也让我转达她对袁可嘉夫人程其耘女士及女儿们的衷心祝福:祝你们健康、如意!
2009年10月31日
虽说同在一个单位供职,我见到袁可嘉先生的次数并不多。印象较深的是两次,一次是在杭州参加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在会议间隙有过短暂的交谈;另一次是在卞之琳先生的诞辰纪念会上,当时袁先生已移居美国,是专程回国来为老师祝寿的,这让我看到了前辈学者对“师道”的尊崇。而今获悉噩耗,我自然应该对这位仙逝的诗歌老人表达一份悼念和敬意。
就中国现代诗而言,袁可嘉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他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参与者,其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脚印”堪称对中国现代诗最好的丈量。
中国现代诗的复兴基本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算起,谈及这一点,绝不能绕开袁可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的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四卷八本的作品我家中便存有两套,是我和内人在当时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购买的,由此可见,此书在这个时间段成长起来的诗人、作家心目中的地位。正是通过这个重要途径,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较集中地接触到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的流派,知悉了瓦雷里、里尔克、叶芝、奥登、艾略特、勃洛克、洛尔加、卡夫卡、斯特林堡、马利奈蒂、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一大串当时十分陌生的名字和他们颇具启迪意义的写作。因此,说他是中国现代诗写作的“盗火”者绝不为过,其对年轻的中国诗人给予的启迪可谓功莫大焉。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序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背景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文章虽说不得已地留有时代的印痕,但其中的精彩就像褴褛的衣衫遮不住俊朗的身体,袁可嘉先生良好的学养、超人的艺术悟性、敏锐的现代意识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洋溢于字里行间,为读者给出了一张清晰的阅读地图。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成败得失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平心而论,政治为中国“五四”以降的新诗提供了坚硬的现实性,使政治抒情诗这一文体抵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峰。但同时,政治对诗的损伤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先生以西方诗歌作为参照和借鉴,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七项原则,构建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性的新传统。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多次谈到“政治抒情诗”的感伤性问题,颇富预见地指出了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重症。首先,他肯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体生命中诸般因子的“相对相成”,但反对其中任何一种质素或几种质素凌驾于全体之上的倾向。他承认诗与政治有平行的密切关系,“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他认为,这种对自身的束缚不仅会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对个人的生命意义造成伤害。同时,他又指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从属的关系,纯粹地为政治服务其实与另一个极端——“为艺术而艺术”就如硬币的两面,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为此,他重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一些所谓的“政治诗”,将其中的病症命名为“政治感伤性”,它们可怕地缺乏个性,遂导致艺术价值意识的混乱和颠倒,在写作上以“诗情的粗犷”为“唯一表现形式”,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以表达的观念来决定作品价值高下的标准。一首诗的好坏与否并不以艺术为准绳,只以主题作为绝对的判断。联系到作者写作这些文章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不叹服于作者认识之清醒,更为其意见没能得到更多的响应而备感遗憾。
此外,他对当时诗歌“散文化”的弊端,以及对日常语言的迷信、对激情的一味热衷、认定主题高于一切的谬论,等等,都作了独到的剖析和批评,为现代诗的回归本体、建立新的传统起到了一种拨乱反正的作用,迄今仍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
作为出色的翻译家、学者,袁可嘉在学术界内知名度甚高,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恐怕就鲜为人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翻译和研究的名声对他的诗名有着一定的遮蔽,另一方面则跟袁可嘉先生为人的谦逊与低调有关,在他为《九叶集》所作的序言中,他对其余八位诗人的写作特征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逐一给予了精到的评点和知音的赏析,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创作。然而,即以收入《九叶集》和《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的一部分作品而论,细心、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出,袁可嘉在原创性诗歌写作上也有过人的禀赋,其中如《沉钟》《进城》《走近你》《难民》《母亲》等,即便跻身于冯至、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中也毫不逊色,它们激情内敛、意象新奇、诗思隽永,且已粗具20世纪90年代诗人大量运用的“叙事性”、“戏剧化”的质素,堪称是“从分析到综合”的新探索。叶落归根是一种文化的归属感
童蔚
我的这个发言不是学术论文,只是随感,出于我对袁可嘉诗人的尊敬,我喜欢袁先生一些有分量的诗作,崇敬他这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献身事业的精神。
中国有句老话是“叶落归根”,它不是源自常识提炼出的知识,而是对人生的观照与比拟;我想,所谓“叶落归根”也不仅仅暗喻一个人肉体的生命回归故乡,而是指一个人对于文化与文明有着自觉的归属感。虽然,飘逝于异国他乡树下有“九叶”诗人中的一叶,但这片“落叶”仍然会在我们的母语中升起,这即是今天袁先生的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谈论他,也关乎叶落归根的终极意义。
袁老先生一生从事创作、评论、翻译,他的贡献属于这片土地。通过这种文化的根,可以纵向地深入儿千年,也可以横向地向外传播汉语文学以及吸纳西方文明。这是一个旋转的轴,而这位诗人、学者是用一生的岁月来推动的。因此,时间的磨盘上承载着他语言的分量、求索的印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磨盘上的精神食粮使一代读者接受到思想和文化的启迪,这也是我们民族最近的一次精神启蒙。袁先生在特殊年代所作出的贡献来自双方面的给予:即思想、文化匮乏年代读者对西方现代派作品阅读的渴求,这种需求量千载难逢;同时,面对机遇也是诗人、学者必须以自己的文化构成“对应”,肩负起传递的重任。这必然带来时间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也正是基于双方的“给”和“予”,奠定了他著书立说所能达到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80年代,“九叶”不是很红,却充满绿色的创造力,赢得过读者的尊重。袁先生在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包括他后来移居美国还推动、组织这边“九叶”的活动。当这样的曾经的贡献者逝去后,这种根与轴的合力是否依然存在且留有影响,就要看其推动的文化是否还有影响力。袁先生曾以一句诗表达过自己的心声,他说:“你决心献身奇迹。”无论当今的创作者是为了金钱还是奇迹埋首于工作,这样的想法依然还是存在着;而袁老先生不仅曾经期盼过,也敢为人先,承接过历史赋予的重任。
一次,袁先生在与我母亲郑敏乘火车赶赴会议的路途上说:我这一生最后留下的,就是我写的那些诗吧?这当然是一句非常非常谦虚的话,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绝对重视。以我很有限的阅读来看,我发现了他诗作中的个性魅力,就裹挟在对素材的捕捉中,这些生动的“材质”源自40年代的文化土壤,由此孕育出他的诗风——是以思想为中心的感性编织,是恰如其分的汉语与欧式译文美声的交织并且与坚实的诗歌结构相重叠。说到诗歌,我们也许首先看重作品蕴含的精神能量,即使面对一条街巷,诗人的抒写也一定出自灵魂的窗口选取词汇以达成作品的意志力及自由诗文本的质量。虽然,街道在时间的转换中会忽然变得面目全非,但诗人在作品中已经预留了宽广的思考空间,在时间中的阅读又总能返回到写作源头的那一刻,于是,我重读他的诗作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如,写于40年代的那首《难民》当中的诗句:
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
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
死也好,活也好,都只是为了别的,
逃难却成了你们的世代专业;
太多的信任把你们拖到城市,
向贪婪者求乞原是一种讽刺;
饥饿的疯狂掩不住本质的诚恳,
慧黠者却轻轻把诚恳变作资本;
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
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
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需的语言,
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
这些诗句就像经过流水的时光机器一样,在今天读来,仍然让读者感悟到触动,有冲击力。这并非由于政治正确,而是诗歌以语言旋律的调子,传达出诗人在时空中的深思,甚至是坦率、直接的诗意,也能把间隔了儿个历史阶段的现实层面,延展到诗歌的维度中,触及人性永恒的层面。
另一首写于1947年的《出航》,抒发了航海者对于离开土地的担忧以及无意之间涉及了人生的晚年:
航行者离开陆地而怀念陆地,
送行的视线如纤线在后追踪,
人们恐怕从来都不曾想起,
一个多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
年轻的闭上眼描摹远方的面孔,
远行的开始担心身边的积蓄;
老年人不安地看着钟,听听风,
普遍泛滥的是绿得像海的忧郁;
只有小孩们了解大海的欢跃,
破坏以驯顺对抗风浪的嘱咐,
船像摇篮,喜悦得令人惶惑;
大海迎接人们以不安的国度:
像被移植空中的断枝残叶,
航行者夜夜梦着绿色的泥土。
在我与晓敏的一次交谈中,得知她父亲晚年在异乡生活,物质优渥但精神苦闷。由此,我想到,精神世界的苦闷与创作之间的关联从而诞生了词语的奇迹,属于文学史辑录的作家常态。1947年,一个二十六岁的诗人就感知自己晚年的心绪,那是来自未知世界的灵感,当他辅以语言的技艺表达出来时,就是将生命的预感与文学结盟在一起的奇迹;如今,再次阅读,我以为那好比从远方传来的回声:诗人预言了自己的晚年,就像阳光照射在山上,也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语言的声线再次发出振动,这同时印证了语言在时间中的投影作用。
还是在80年代,在一次袁先生主持的诗歌讲座中,他请我朗读艾略特的诗作《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我于讲座前到他在永安里的寓所,品尝了袁伯母烹调的阳春面。在那里,我发现他们家和我们家一样,餐桌就在离门很近的过道上,而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老一辈知识分子都有着嗜书如命的“坏习惯”,至今如此。那个客厅如今浮现在我脑海里,印象就是袁先生要全力推动译介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气势。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是横向的轴,他不仅自己翻译,还组织人员、联系出版,那时他也应邀四处演讲,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向当时的年轻人全力推介现代派文学的理念与创作文本。
那回见面,袁老还跟我讲,你们这代女性非常不容易,要读书、工作,还要做家务,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女生,家庭都比较富裕,所以不用做家务。说这话时,我能觉察到袁老先生对时间的敏感。回首他从事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出其高产的效率是基于中青年时期优厚的积淀,当然,还有勇气。“文革”期间,他与“外面的学者”开始交往,他意识到交流的重要性,也许他还深信“门”最终是要被打开的。但在极为封闭的年代,先行者总是先付出“牺牲”,结果他就被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挨整,隔离审查,还有扫厕所等等体罚,吃了很大的苦。这些特殊的经历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属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烙印之一。“文革”后,大批创作者都属于过度压抑之后的“爆发”,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先抑后扬”。的确,在开放之初,最为前卫的文化创作者,正是在新时代的钟声还没有敲响之前,就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他们对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敏感异常,而且热爱一种文化是发自真心、深入骨髓的,绝非像一件时尚的外套可以随时更换。
不久前,在和晓敏的通话中得知,袁先生有着很深的“九叶”情怀。当晚年接近失明时,他非常惋惜不能和老友们通信了。“九叶”中的一些诗人在早年读书时,彼此就结下了友情。从这一点上说,“九叶”的各位都非常珍惜友情与诗情,他们的相聚是历史中的结缘,而非小团体主义的哥们儿义气。
我母亲说过,她很怕出席类似的活动,因为年事已高,但她会忽然跟我讲:“没关系,我不去还有曹辛之呢!”我想,这种错位的记忆,恰好体现出记忆本身所具有的遗忘与复活的功能。今天她没能来参加会议,但在电话里她非常鼓励袁晓敏出版她父亲的文集,也让我转达她对袁可嘉夫人程其耘女士及女儿们的衷心祝福:祝你们健康、如意!
2009年10月31日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