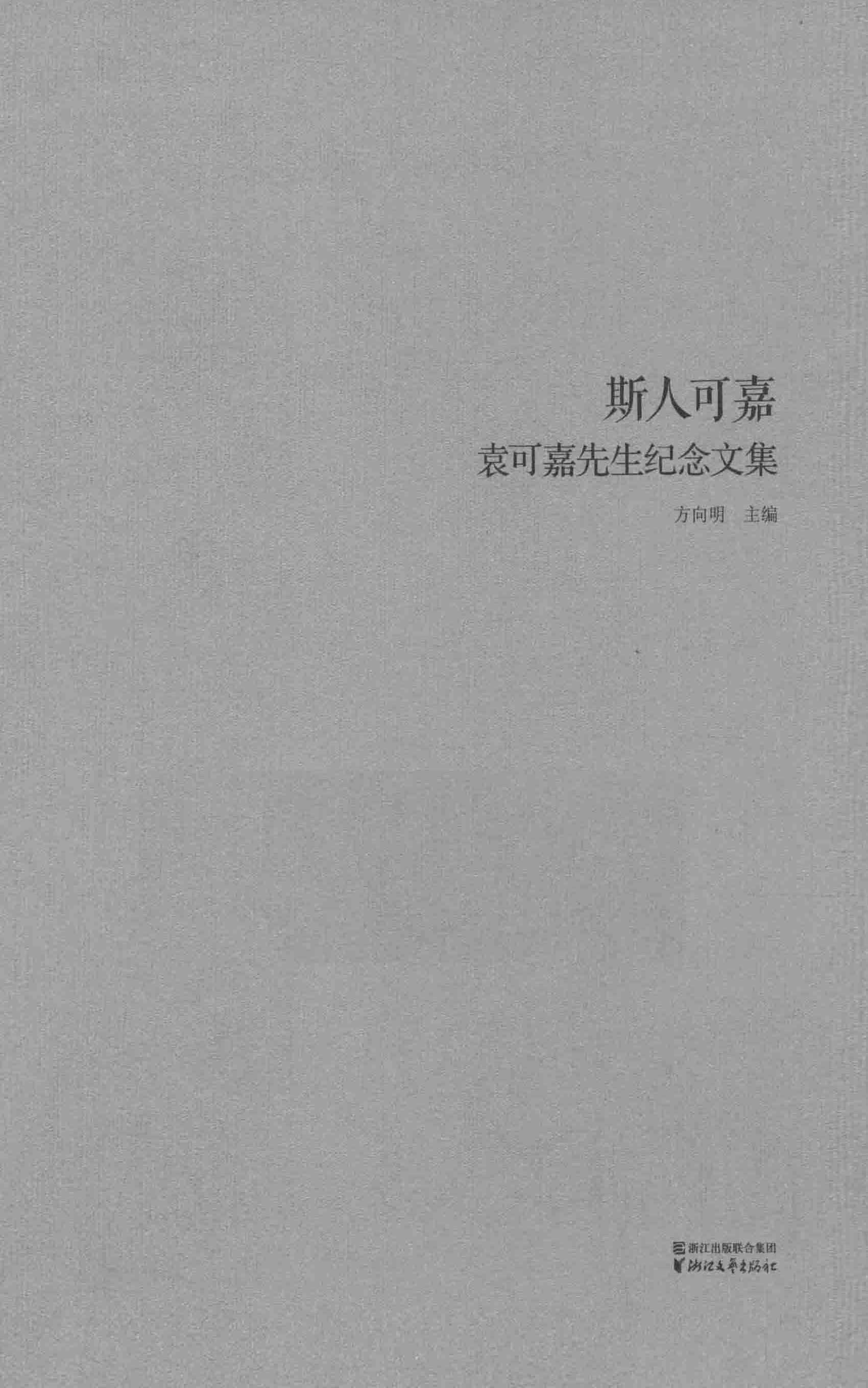森林里的拾薪者
| 内容出处: | 《斯人可嘉 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4240 |
| 颗粒名称: | 森林里的拾薪者 |
| 分类号: | K825.6-53 |
| 页数: | 3 |
| 页码: | 058-060 |
| 摘要: | 我认识袁可嘉先生是在1959年。那年秋天我刚从德国回来,参加国庆十周年接待外宾工作以后,回了一趟家。记得来单位报到,是11月初。我被分配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组做研究实习员。他们都是外国文学界泰斗级人物,分配我与他们一起工作,让我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第二个令我惊讶的现象,是西方文学组有三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卞之琳、袁可嘉、郑敏。尽管他们谦虚地自称为“叶”,甘愿做“花”的陪衬,可我当时还是非常崇拜他们。在我看来,诗歌是文学的精华,写诗的人必然也是文学家中的佼佼者。再说了,年轻人有几个不喜欢诗歌,不崇拜诗人的呢?“没有诗,怎么活呀”,我那时就是这样想的。 |
| 关键词: | 现代派 文学研究 袁可嘉 |
内容
我认识袁可嘉先生是在1959年。那年秋天我刚从德国回来,参加国庆十周年接待外宾工作以后,回了一趟家。记得来单位报到,是11月初。我被分配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组做研究实习员。一进西方组,有两个现象令我惊讶不已,一是西方文学组老专家成堆,除了组长、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卞之琳,还有“五四”老人、易卜生翻译家潘家洵,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专家缪郎山、罗念生,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李健吾、罗大冈,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杨季康。他们都是外国文学界泰斗级人物,分配我与他们一起工作,让我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第二个令我惊讶的现象,是西方文学组有三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卞之琳、袁可嘉、郑敏。后来我才知道,袁可嘉和郑敏都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尽管他们谦虚地自称为“叶”,甘愿做“花”的陪衬,可我当时还是非常崇拜他们。在我看来,诗歌是文学的精华,写诗的人必然也是文学家中的佼佼者。再说了,年轻人有几个不喜欢诗歌,不崇拜诗人的呢?“没有诗,怎么活呀”,我那时就是这样想的。
袁可嘉先生在研究组里地位很特殊,他不属于老专家之列。从年龄来说,他比他们年轻;从资历来说,相差一辈人。可也不同于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年长我们十几岁,资历也长我们一辈。他很尊敬那些老专家,像我们一样尊称他们为“先生”,老专家们称他为“可嘉”,从这个称呼明显听得出老专家们对他的才华的爱戴和尊敬。我到西方组不久发现,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同志”,都称呼袁可嘉先生为“老袁”,我当时心想,他们都是文学所的“元老”,称呼他为“老袁”,口气中透着亲密无间,可我是刚刚毕业的新人,无论如何不敢如此造次。现在想来,我随着老同志称呼他为“老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文革”以前,我在文学所工作的时间不多,刚从国外回来,对60年代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总觉得跟不上趟,只要有机会,我就主动要求下乡去锻炼,与袁可嘉先生交往的机会很少,避免了如何称呼的尴尬。那时尽管与袁先生接触不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相当深刻。袁先生为人极为随和,只要有机会就笑眯眯地与我们年轻人搭话,间或用他那不紧不慢的慈祥语调,与我们开儿句玩笑。这是我后来敢于像老同志一样直呼他“老袁”的原因。
我与袁先生接触较多,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从干校回来以后。那时我们都住在建外宿舍10号楼,低头不见抬头见,不但与袁先生夫妇见面的机会多了,他们的两个女儿小敏、玲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经过他家楼下的时候,常常听见小敏那甜美的歌声:“听奶奶,讲革命……”她的歌声给建外宿舍区的住户平添了许多欢乐。
袁可嘉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研究组里关于西方文学“现代派”问题的议论,有时谈到现代派诗歌,有时谈到小说,1962年以后谈得最多的是“新批评派”文学理论。那时我刚刚毕业,关于西方文学的“现代派”所知甚少,只对个别作家有点印象,例如卡夫卡。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因写文章公开呼吁“把卡夫卡的地下阅读,变成公开阅读,”而遭到民主德国官方舆论批判。我的老师在学术问题上,是个敢为天下先的人。二战以后,是他第一个划清了音乐家瓦格纳与纳粹政权的界限,打破了“瓦格纳禁忌”,为在全德国范围内公演瓦格纳歌剧扫清了思想障碍。50年代中期,他又提出重新评价卡夫卡的问题,试图打破当时的学术禁忌。本来安排他作电台演说,未得到官方允许,改为在《星期日周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界、读书界对卡夫卡的议论热闹起来。我对卡夫卡的了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西方文学现代派的兴趣,还是听了袁可嘉先生的议论,读了他发表的文章和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以后的事情,袁先生是我认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启蒙者之一,我应该感谢他。
不过,对于袁先生向国人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敬仰和感恩之情,是我读过《本雅明日记》以后的事情。德国文学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好朋友,流亡期间,他曾经去丹麦拜访布莱希特,并就卡夫卡评价问题征求他的意见。那时布莱希特一家流亡在丹麦,居住在一个小岛上的一栋茅草房里。本雅明把论卡夫卡的文章交给布莱希特,却三个礼拜不见答复,他几次谈起这篇文章,布莱希特也都避而不答。本雅明好生纳闷,便悄悄地把稿子拿回来。有一天晚上,布莱希特突然说起这篇文章,显然是经过认真思考,有了成熟的想法。
据本雅明在1934年8月5日的日记里记载,为了说明卡夫卡作品的倾向,布莱希特设想了一场老子与其弟子卡夫卡的谈话。从谈话中,老子得出结论,认为卡夫卡是讨厌当前的社会制度、法律形式和经济形态的,他希望自己生活的国家,能有一个信得过的领导人。显然,这是布莱希特对卡夫卡作品社会倾向的理解。不过在他看来,卡夫卡是“从布拉格五光十色的文化泥沼里冒出来的一个气泡”,他的作品里既有“毫不含糊的,非常有趣的”东西,也有“无用的东西”。在他看来,评论家的任务,就是向读者揭示作家作品中那些有用的东西,批判地指出那些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布莱希特援引庄子的“材之患”故事说: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树,粗大结实的,砍来做房梁;不太结实、看起来还顺眼的,用来做箱盖和棺材板;生得奇形怪状、派不上用场的,则躲过了遭砍伐的灾祸。布莱希特援引的这个故事,与庄子的故事用意不同,它并不是提倡“无用之用”,而是提倡一种探索精神。他说:对待卡夫卡的作品,你必须像拾薪者一样,深入森林中去寻找有用的东西。他认为卡夫卡作品中那些比喻的确很好,但对他作品中那些不合理的、神秘莫测的情节,“必须把它们搁置一边”。
布莱希特不赞成卡夫卡的社会观和艺术观,但他并不否定卡夫卡在小说创作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在后来的“表现主义论争”中,他理直气壮地为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的存在理由进行过辩护。布莱希特主张对待卡夫卡这样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评论家要做去粗取精的分析工作,让读者正确理解它们。本雅明听了布莱希特的意见,意识到自己论卡夫卡的文章,并不算成功。不过他日记中的这段记载,为人们理解西方文学中的“现代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袁先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像个深入森林的拾薪者一样,寻寻觅觅,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他的介绍和评论,遵循中国“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尽量做到有分析,实事求是,为国人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出了令人赞美的贡献。袁先生离开我们五年了,他对西方文学的研究成就,像他的音容笑貌一样,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激励着我在有生之年,继续探索那些外国文学的未知领域。
2014年1月20日写于北京车公庄西路坎斋
袁可嘉先生在研究组里地位很特殊,他不属于老专家之列。从年龄来说,他比他们年轻;从资历来说,相差一辈人。可也不同于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年长我们十几岁,资历也长我们一辈。他很尊敬那些老专家,像我们一样尊称他们为“先生”,老专家们称他为“可嘉”,从这个称呼明显听得出老专家们对他的才华的爱戴和尊敬。我到西方组不久发现,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同志”,都称呼袁可嘉先生为“老袁”,我当时心想,他们都是文学所的“元老”,称呼他为“老袁”,口气中透着亲密无间,可我是刚刚毕业的新人,无论如何不敢如此造次。现在想来,我随着老同志称呼他为“老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文革”以前,我在文学所工作的时间不多,刚从国外回来,对60年代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总觉得跟不上趟,只要有机会,我就主动要求下乡去锻炼,与袁可嘉先生交往的机会很少,避免了如何称呼的尴尬。那时尽管与袁先生接触不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相当深刻。袁先生为人极为随和,只要有机会就笑眯眯地与我们年轻人搭话,间或用他那不紧不慢的慈祥语调,与我们开儿句玩笑。这是我后来敢于像老同志一样直呼他“老袁”的原因。
我与袁先生接触较多,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从干校回来以后。那时我们都住在建外宿舍10号楼,低头不见抬头见,不但与袁先生夫妇见面的机会多了,他们的两个女儿小敏、玲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经过他家楼下的时候,常常听见小敏那甜美的歌声:“听奶奶,讲革命……”她的歌声给建外宿舍区的住户平添了许多欢乐。
袁可嘉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研究组里关于西方文学“现代派”问题的议论,有时谈到现代派诗歌,有时谈到小说,1962年以后谈得最多的是“新批评派”文学理论。那时我刚刚毕业,关于西方文学的“现代派”所知甚少,只对个别作家有点印象,例如卡夫卡。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因写文章公开呼吁“把卡夫卡的地下阅读,变成公开阅读,”而遭到民主德国官方舆论批判。我的老师在学术问题上,是个敢为天下先的人。二战以后,是他第一个划清了音乐家瓦格纳与纳粹政权的界限,打破了“瓦格纳禁忌”,为在全德国范围内公演瓦格纳歌剧扫清了思想障碍。50年代中期,他又提出重新评价卡夫卡的问题,试图打破当时的学术禁忌。本来安排他作电台演说,未得到官方允许,改为在《星期日周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界、读书界对卡夫卡的议论热闹起来。我对卡夫卡的了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西方文学现代派的兴趣,还是听了袁可嘉先生的议论,读了他发表的文章和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以后的事情,袁先生是我认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启蒙者之一,我应该感谢他。
不过,对于袁先生向国人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敬仰和感恩之情,是我读过《本雅明日记》以后的事情。德国文学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好朋友,流亡期间,他曾经去丹麦拜访布莱希特,并就卡夫卡评价问题征求他的意见。那时布莱希特一家流亡在丹麦,居住在一个小岛上的一栋茅草房里。本雅明把论卡夫卡的文章交给布莱希特,却三个礼拜不见答复,他几次谈起这篇文章,布莱希特也都避而不答。本雅明好生纳闷,便悄悄地把稿子拿回来。有一天晚上,布莱希特突然说起这篇文章,显然是经过认真思考,有了成熟的想法。
据本雅明在1934年8月5日的日记里记载,为了说明卡夫卡作品的倾向,布莱希特设想了一场老子与其弟子卡夫卡的谈话。从谈话中,老子得出结论,认为卡夫卡是讨厌当前的社会制度、法律形式和经济形态的,他希望自己生活的国家,能有一个信得过的领导人。显然,这是布莱希特对卡夫卡作品社会倾向的理解。不过在他看来,卡夫卡是“从布拉格五光十色的文化泥沼里冒出来的一个气泡”,他的作品里既有“毫不含糊的,非常有趣的”东西,也有“无用的东西”。在他看来,评论家的任务,就是向读者揭示作家作品中那些有用的东西,批判地指出那些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布莱希特援引庄子的“材之患”故事说: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树,粗大结实的,砍来做房梁;不太结实、看起来还顺眼的,用来做箱盖和棺材板;生得奇形怪状、派不上用场的,则躲过了遭砍伐的灾祸。布莱希特援引的这个故事,与庄子的故事用意不同,它并不是提倡“无用之用”,而是提倡一种探索精神。他说:对待卡夫卡的作品,你必须像拾薪者一样,深入森林中去寻找有用的东西。他认为卡夫卡作品中那些比喻的确很好,但对他作品中那些不合理的、神秘莫测的情节,“必须把它们搁置一边”。
布莱希特不赞成卡夫卡的社会观和艺术观,但他并不否定卡夫卡在小说创作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在后来的“表现主义论争”中,他理直气壮地为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的存在理由进行过辩护。布莱希特主张对待卡夫卡这样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评论家要做去粗取精的分析工作,让读者正确理解它们。本雅明听了布莱希特的意见,意识到自己论卡夫卡的文章,并不算成功。不过他日记中的这段记载,为人们理解西方文学中的“现代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袁先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像个深入森林的拾薪者一样,寻寻觅觅,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他的介绍和评论,遵循中国“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尽量做到有分析,实事求是,为国人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出了令人赞美的贡献。袁先生离开我们五年了,他对西方文学的研究成就,像他的音容笑貌一样,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激励着我在有生之年,继续探索那些外国文学的未知领域。
2014年1月20日写于北京车公庄西路坎斋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