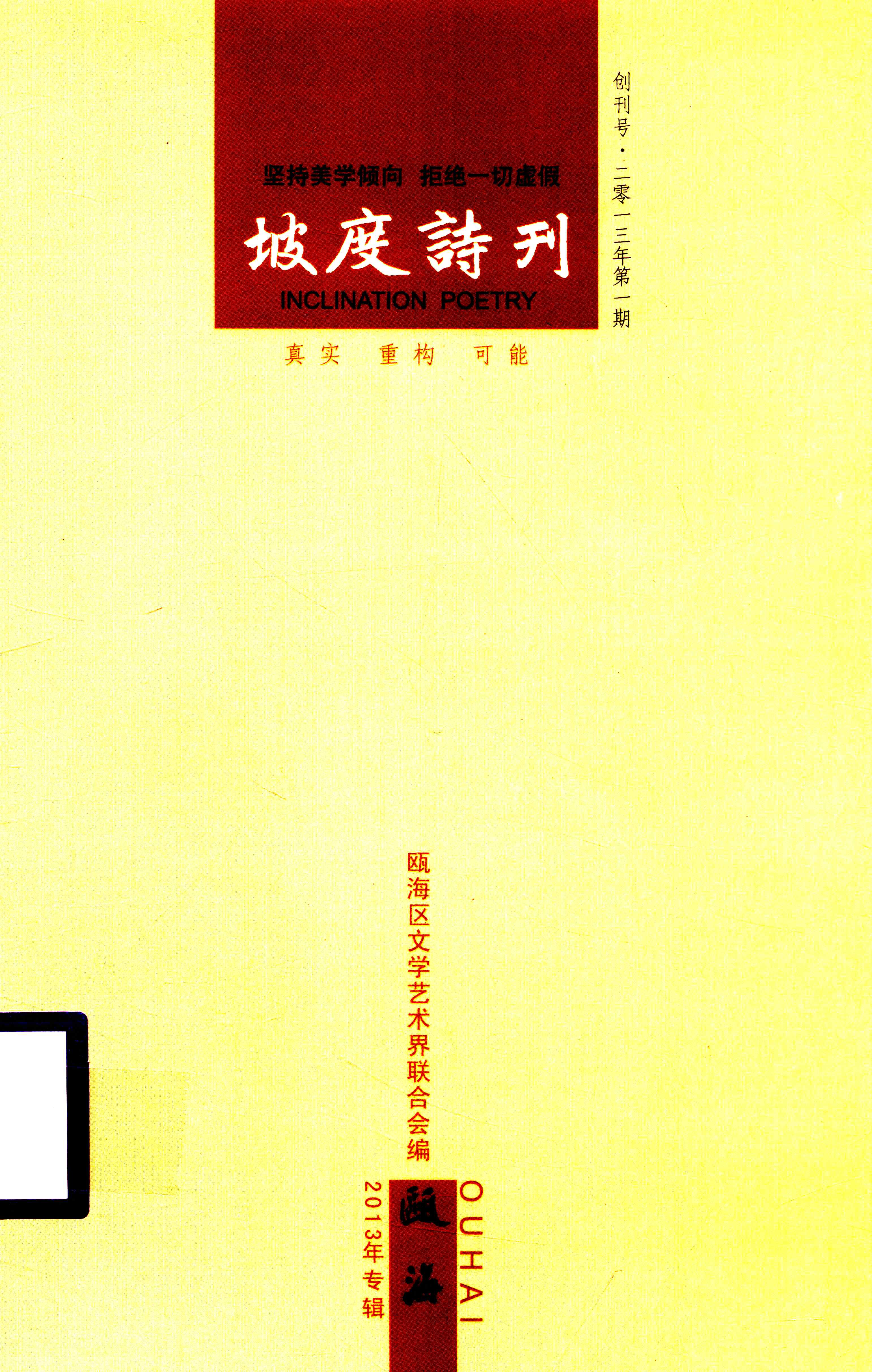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栏目主持:星落河
栏目来稿邮箱:love213052@sina.cn
生长在旷野中的诗歌
——雷平阳《基诺山》部分诗歌选读·吴云望
雷平阳的诗歌生长在旷野之中。以酒浇灌,以灵滋养,以土孕育,成就孤独。它的根向地底深处挖掘真实,感知灵魂,奉行敬畏,然后经由文字的茎叶引渡到现实中,也许开花,也许枯萎。雷平阳的动人之处在于他的粗粝:没有精雕细琢,只在旷野之中,承受着草叶的锋利和野风的诘问,而后俯下身来,捧一口泥水饮下。
《基诺山》,这本孤独的诗集,平静的暗红色封面下涌动着对雨林的向往。封面上诗人的书法,干净、原始。这本集子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回归、土地、生灵和偷渡客的故事,讲述着现代文明的斧镰,云南土地的共情,生命灵魂的触摸和一个偷渡客无法安葬的诉说。一、现代文明的斧镰
在一次访谈之中,雷平阳这样说道:“就在前两年,金沙江上修建几座大电站,大量的老百姓必须搬离故土,被称之为‘移民’。而所有的搬迁,其中第一项就是搬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祖坟,我看见无数的‘不孝子孙’在收取了政府很少的一点补偿金之后,泪流满面地将自己的祖坟一座接一座地挖开,然后将一具具枯骨装入土罐子,先背回家,
放满屋子及院落,祭拜一番之后,又背上它们,匆匆地赶往异乡。这种‘枯骨别’,活活地将活着的人也变成了行尸走肉、孤魂野鬼。”现代文明的潮水涌来,裹挟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如果反抗,就沉入水底,成为冤死的魂,连喊冤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现代文明,它翻搅着埋葬魂灵的土地,把一根根白骨硬生生遣回人世,没有道歉,没有解释,只有耀武扬威的补偿金在鼓吹着社会发展。而那些手无寸铁的“移民”,或者“不孝子孙”,他们连留居故土的权力都被剥夺,又何谈捍卫祖先的安息?冰冷的电站听不见鬼魂的呜咽,而敬鬼的人类,毕竟太弱小,抗衡不了这巨大的机器,只能漂泊异乡,背上枯骨,以安抚祖先。
“江水被开肠破肚之后,一座座电站/就是一座座能量巨大的天堂/上帝的牧羊人,在山中迷路了/赶着羊群,沿着电网的线路向前走/他坚信,任何一种路都存在尽头/而尽头也一定会有村庄和坟墓/他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信徒/却在无意识中把信仰当成了赌注——/当他和羊群途经城市,站在电线的/蜘蛛网下面,他失去了尽头。旷野消失了/陡峭的世界幻化成了魂路图上的魔窟/没有青草和水,人与建筑仿佛/中了魔咒一样冰冷,他与他的羊群/亦听从这魔咒,在屠宰场血腥的流水线上/瞬间就被剥皮抽筋,转世为一堆堆白骨”。雷平阳的诗歌很少出现“电站”一类的现代词语,他固执地驻守着他的寺庙、山野、草木。但是现代化的脚步却不会体谅一个诗人的留恋,电站毫不留情地将江水开肠破肚。“工业文明一来,很多东西都荡然无存了,故乡的灵魂也被抽走了。”这些冷漠的机器将江水的魂抽走,那仍旧流淌的水,成了推动机器运行的奴隶,没有魂。牧羊人没抵达期待的尽头,却走入一片冰冷的屠宰场。电网的线路无法带领他走入村庄和坟墓,只让他遇见冷漠的人和建筑。虔诚的信仰在现代社会成了羁绊和葬送,上帝被直接否定,何谈拯救?这里没有羊群渴食的青草,只有流水线上被剥皮抽筋处理出肥美的人肉。现代的魔咒封存了人和建筑的温暖,上帝如何?佛祖如何?菩萨如何?进入屠宰场,都不过是白骨一堆。
上帝被信徒放逐,金钱被拥上皇位。
“在隆隆的推土机和拆迁队的叫嚣中,一切被‘新时代’视为‘不合法’的事物和景观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消亡。”新时代成为唯一的评判者,土地和山野再没有发言权,只能等待着被屠戮的命运。这是个
充斥着霸权的时代,它肆意地对土地大刀阔斧,没有解释的责任,不需要对谁做交代。一座座高楼大厦崛起,不顾大地的承重;一条条公路被浇筑,封存泥土的呼吸;一座又一座城市被建立,一处又一处荒野被命名;飞速奔跑的高铁企图把神灵也甩在后头;寺庙被拔除或者安插在城市中盈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我们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看似‘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曾经的来路和一代人的命运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歌者,成了新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一个时刻回望并清醒的诗人,只能孤独地用文字拼命坚持,他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将那个与现代化相背离的旷野平移到纸面上。也许是抵抗,也许什么也不能是。
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之下,有被欲望扭曲了的人性,有被经济发展摧残的生命,还有单纯美好的希望被洗去幻想,剩下绝望把人狠狠地抛回去。诗歌中一颗颗变异的灵魂,是这个时代避之不去的躁动与苍凉。
“去年春,我们还在山上争论/农药、化肥与丰收/像埋在泥土里的石头,他不在乎/文明的毒素,只关心/用什么东西可以填饱肚腹/喝酒时,他多喝了两碗/哭着问我,要卖出多少粮食/他才能离开家,满世界去寻找/妻子和女儿。”这是关于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故事。文明的入侵让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让一个只关心用什么东西可以填饱肚腹的父亲,开口去询问粮食的价格;让一个不在乎文明毒素的丈夫,欲图用果腹的粮食去换取金钱,以奢求寻找妻女的希望。妻子和女儿下落不明,这小小的西南一隅,走出去,就是整个世界。满世界的寻找,寻找到了人,也终于寻找不到对土地的死心塌地。问题问出了口,就只剩下悲剧。
雷平阳是一个絮絮叨叨的“遗老”,他对现代化的霸权心知肚明,但他仍旧以他的文字固执地坚守原始。“他诗歌中总是有一种弥漫不散又沉沉坚固的‘土气’。这种特有的味道让人踏实,也让那些被现代性和城市化时代所溺染的人们有恍如隔日之感,未免心生唏嘘。”他以一己之力,游走在孤魂野鬼游荡的山野间,抚摸着云南的每一棵草,把心贴在土地上。
二、云南土地的共情
雷平阳爱云南。这片土地上有他诗歌中一再提及的乌蒙山、基诺山、哀牢山、澜沧江、司徒老寨、安边镇……雷平阳的文字守云南也出云南,他固守住云南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慈悲,又通过泥土的共情把这份慈悲传递出去。一个用膝盖触碰泥土的人,定能体会大地的关怀。
雷平阳对土地是深情的,情深生敬。他对这块土地有着发自肺腑的敬意。“尘土与人永远肌肤相亲。土地是不会自己站起来讨好人类的,这不是所谓的傲慢与尊严,它存在于那儿,人就必须谦卑,把自己贴上去,再贴上去,感到了它的温暖,也就证明你的灵魂和肉体还没有死,你就有资格多活一会。”人类若要真切感受到自己的生,获得活着的资格,就不得不贴近土地,感受土地的温暖,感受这温暖赋予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尊严。然而,这份古来有之的谦卑早已被人类淡忘。人类对土地的忘恩负义最终会把自己推向深渊,只是土地太慈悲,她包容着子女在她身上挖掘堆砌,将她的乳房揉捏进子宫,拖拽出她的肚肠。
“土层中,有替罪羊来不及/刨光的草籽,有披着白色塑料薄膜/播种土豆的怀孕女人的影子/有兽骨,在蚯蚓的蠕动下呻吟/有反复被鞭打的囚犯/在耶稣和释迦牟尼之间左右权衡/不知道自己,该把死亡献给谁……/有一只蟋蟀,尖声鸣叫/声音清凉,干净/仿佛所有的业障,已经消弭”。土层中埋葬着罪恶露出的马脚,包裹着母亲用亲身劳作换取的生存,隐秘着兽骨坚硬的死与蚯蚓柔软的生的碰触,还有那被自己反复鞭打的囚犯,要让自己的死亡成为一场祭献,却不知该献给谁。只有泥土中的蟋蟀发出一只蟋蟀的声音,清凉,干净,是土地的声音,仿佛要消除所有蒙蔽在眼前的业障,以安抚这些可怜的生灵。但终究只是仿佛,心放不下,业障又怎么消除?土地知晓了一切命运,她包容着一切事物的发生,不发表任何评价,只给出真实的反应。假设世上真有全知的上帝存在,那土地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上帝。它仰视着人类,姿态平庸又高贵。
雷平阳诗歌里的云南,早已跳出了“地域性”的框架。说雷平阳是“地方性”诗人,是一种偷懒的评价。正如诗人所说:“我所写的‘云南’,乃是挣扎在工业文明与古老山川之间的一片旷野……”诗人选择
云南这片土地进行创作,因为这片土地野,“礼失求诸野,云南有足够的野,我在其间写作,内心装着千山万水,只想将这野,带到纸上,借以反对猖狂、霸道的诗歌政治学以及暴力般的工业文明。也就是说,我一直对地方性写作这个概念持反对态度,它方便了评论话语谱系中的指称,却有意无意地埋葬了诗歌辽阔的存在空间。”云南之野,是每一寸土地的共性。土地的野性自动站在工业文明和诗歌政治学的对立面,诗人向云南求助的是云南的野性而非名字。如果我们将雷平阳局限在“地方性诗人”的称号之中,我们对他诗歌的解读势必造成困居一处的局限。在他的诗歌里,地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它们可以指代任何一处地方。基诺山和澜沧江在诗人的诗歌中,是以山丘和河流的本来姿态呈现。它们不是名山大川,它们的背后没有文化符号和指称意味,就如同《尽头》中的那颗石头,“抱着石头的本质,彻底断绝了/成为纪念碑的可能性……”诗人力求让山丘只是山丘,河流只是河流,石头只是石头,诗人要呈现的是云南作为一片土地的本来面目,是一片旷野的自性,而不是那个旅游手册中代表着隐居、桃源、安逸种种附加意义的彩云之南。所以从该层面来看,诗人笔下所写的云南,大可以接宇宙,小可以观砂砾。他不再给山水附加其他意义,云南不因为雷平阳而产生其他指称意味。雷平阳将自己放空成一具肉体,让云南魂附,代云南诵诗。
“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远方’的时代。极其吊诡的则是,我们的‘地方’和‘故地’尽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被强行地远离了它。而‘地方’和‘故地’的改变更是可怕和惊人,因此文字空间里携带着精神能量的地理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有之乡。”我们居住的故土在一次次的规划建设中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土地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中失去了自性,触目惊心的是,大多数人面对土地的远离是如此麻木。我们太需要土地的包容和安慰来消弭我们当下的迷惘,故而雷平阳之代山水而吟愈加显得珍贵。三、生命灵魂的触摸
一个关注土地心声的诗人,能够感应到行走在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灵并满怀悲悯之心敬畏它们。诗人对生命的平视来自诗人内心对万物有灵
的信奉:“在我的故乡云南,哈尼族、佤族、布朗族和基诺族等民族,都相信万物有灵,人与各类物种是平等的,动植物是人或鬼神的另一种存活方式,对此我没有异议并乐于遵守其善待之道。这样的观念很自然地深植我心,让我屡屡写到动物和植物,都觉得它们是命,尊严和慈悲通常比人拥有的还要多!”在生命面前,动物和植物,人类和鬼神,都是平等的。在雷平阳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对生命发自肺腑的认同感。不是以一个审判者的角度去品定生命的价值,而是以一个信徒的身份,焚烧诗稿以触摸生命的真实。他没有谄媚的歌颂之辞,他的笔像雕刻的刀,小心翼翼地削出生命的尊严和慈悲,“他不会取巧,即使是对于极其细小的虫草和石块他也必须弯下腰去翻检和察看。”
这个世界太缺少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了。人类太喜欢以救世主自居,妄图重新创世。但其实,我们哪来的资格去重塑自然?我们来自于自然啊,我们和一株草一样羸弱,依附着土地,汲取着她的营养,暴露在白日和黑夜之中,是那么渺小。而可笑的是,我们居然能够顶着正义的名号以战争的形式对同类进行不负责任的屠杀,我们也能够借以发展的目的轻易宣判原始森林的死刑,这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后退?
在《两头大象从我身边经过》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威慑力:“那一瞬,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散发的天生的威慑力、冲击力和统治力/令我内心崩溃,令我眩晕,令我窒息/令我体量缩小,再缩小/他们从我身边经过,视我如无物/我主动示弱,藏身于灌木丛/目送他们远去双手死死抱住自己/像抱着一头侥幸逃生的小野兽/像抱着一棵突然软下来的松树”。自然生长的两头大象,他们生命的威慑力、冲击力和统治力让诗人一瞬间暴露出人类本性的恐惧。在自然法则之中,人类面对大的事物时会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情感。但是,在《肉做的起重机》中,这生命的威慑力却被人类的斧头、刀背和棍棒驯服,成为搬运原木的起重机。他们瘦骨嶙峋,状如标本,断子绝孙。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自以为是:“它们佝偻着/东倒西歪地向前,像拖着整个世界的尊严/连同我内心仅剩的一丝孤傲,偷生人世”。两相对比,触目惊心!人类为了利益,抛弃敬意,让生命在他们胯下偷生。眼见悲凉,才生悲悯。雷平阳在两次访谈中都谈及了他诗作中的悲
悯情感:“‘悲悯’出现在诗中,不是我有意植入,它随命而来,是天生的呼救,是绝命前的最后一次柔软。”、“至于悲悯,蚯蚓具备,田鼠具备,人当然也应该具备,因为它是生命的根本品质。”悲悯之情人皆有之,并非诗人独有。但它却在人群中被淡漠,只能活在诗歌之中。《烧荒》之中,诗人痛挽被火烧惊扰了睡眠的草木、被高温烤熟的幼兽和昆虫、以及逃脱后成为看客的飞禽和巨兽。在另一个世界,个体和独立被荡平。山坡之上那些游荡的灵魂,满世界找物托身。一场烧荒,烧掉了生命,也烧掉了怜悯之心。诗人只能借助附体的蟋蟀,为生命唱出一曲凄厉的挽歌。
万幸的是,还有云南大地上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多的现代文明影响,他们的内心依然虔诚,他们保有人类最初的模样。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现代文明那些丰富多姿的幻象,他们更加清晰、安稳地活着。
“一个女孩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和信物/她的情人找到巫师——/‘我想去阴间看看,问一下/她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巫师给他放魂,却没有将他再收回来/他的身体至今还留在基诺山/每天睡觉,耕种,喝酒/像一部肉做的机器,几十年运转/幽灵一样,沉默寡言”。在基诺山上,人能够和鬼恋爱,爱情不惧怕生死之别。失去了魂的人是人间的幽灵,肉身继续完成人间的路程,像机器一样运转,而被巫师放出的魂魄,可以追随死去的女孩或天国或地狱,相爱不需要依靠肉体死亡来成全。因为相信有灵,爱情得以以最完美的方式实现。
在雷平阳的诗歌中,我看到了生命被奴役的可怖,也看到生命最本初的美妙。正因为这种种现象,我们才更加需要俯下身来,谦卑、诚恳地触摸生命。真诚地感受生命,尊敬生命,是我们对自己的负责。四、偷渡客的孤独与承接
在《基诺山》的序言中,雷平阳把自己定位为偷渡客。他行走在原始与现代、神鬼与人类、天与地之间,他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也是一个坚定的承接者。偷渡客,没有合法性、公共性和透明度,作为连接着两个世界的使者,却同时被两个世界放逐。
偷渡客是孤独的,偷渡客的孤独来自觉醒。他将那些敏感而质朴的
东西从雨林中、佛眼中、巫师的咒语中、野象的身体中偷渡到诗歌里,小心翼翼地低喃着,在土层下蔓延。“面对着在加速度时代即将消逝和早已远逝之物,诗人内心的翻搅杂陈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因为他太觉醒,一般人无法理解、认同,就像是被误认为疯子的天才,又或者,疯子本就是天才。太醒了!醒到求醉死:“‘兄弟,再来一碗,醉死,醉死算了……’”
“他看见过/拍地痛哭的偷渡者,去国前/一页一页地撕吃《诗经》和李白/吃土和啃孔子木雕的人,他也见过/想麻木,麻木不了。这些人过江/坐穴头的独木舟,很多人沉江而亡/只有尸首和泡沫去了异乡,他想麻木/麻木不了。酒一醉,他就充当他们的家人/恶狠狠地向江水要人。”偷渡客,是不得不逃离的一群人。他们热爱着故土的传统文化,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灵魂,却无法解救肉体。意识形态的统一需求容不下他们的清醒,这群觉醒者必将受到驱逐。对面没有《诗经》了,没有李白、孔子了,坐在独木舟上的他们,内心的波涛翻滚胜过江水,离开了故土,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很多人沉江而亡”,万念俱灰,心已死,肉体偷生又有何意义?
“偷渡者所有的遭遇、立场、心态/这时候,全部都汇集到了我的/心上:重压、负罪潜逃、恐慌、去远方/崇洋媚外、贫穷、反抗、弃暗投明/囚禁、贩毒、野心勃勃、冒险、自虐/流亡、赴死、求财、另谋生路……/——在我心里,凭空多出/一座座避难所和集中营,以及缅寺和教堂/他们被我一一想象出来/强压给自己,仿佛自己的内心/真的横亘着一条浊浪滔天的大江/仿佛自己真的是一个偷渡者/身在故土,却一直在流亡/因此,船至对岸,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死里逃生,跪在江边痛哭了一场/”。偷渡客永远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被逮捕,被示众,被作为一种指代,或者符号。而“我”,一个内心没有归属感的人,是精神上的偷渡客。“身在故土,却一直在流亡”。肉体要偷渡,只需要一条船,但精神的偷渡却是永无止息的折磨,这重压没有尽头。“我所奉行的往往就是我内心反对的,而我真正以文字竭力捍卫的东西,却又连说出声的勇气都已丧失。”面对这样的情况,诗人只能用诗歌发声,用“诗歌中的现实”为“现实”超度。
偷渡客,承担着引渡清醒的责任。“或许,我们的诗篇阻挡不了开
们把疼痛诉说。“山川自成体系,人们各得其所,诗人发出声音只是义务和良知,不可能产生权势的功效。社会关怀,是作家永生永世的负载。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渴求权势的宠幸,不为时代写颂词。他的发声出于良知,出于对生命的悲悯,对真相的寻求。他所传达的,是永恒的生命价值,真挚的人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一个清醒的诗人,永生永世都要负载着唤醒的义务,为了唤醒,也为了传承。诗人天生无法沉默,他本能地需要哀鸣,用自己嘶哑的声音为这个荒唐的世界扯开虚荣的伪装:“基诺人认为,蝉是人间通往天国的路边,那些孤魂野鬼的化身,它们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叫,叫到天国和人间的门都打开。我觉得他们说的是诗人。我的写作就是叫,哀鸣。这不是反思的结果,是本能。”
《基诺山》,这本暗红色布面的诗集,最后的一首诗:《我》,以诉说一个诗人的故事结尾。“我是来自雪山的瘸子/不想跟上时间和流水的步伐/我是腾云驾雾的盲人/拒绝放射内心枝状的闪电/我是围墙外徘徊的哑巴/为了紧缩喉咙里的诉状、雷霆和秘密/我是迷宫里的左撇子/醉心于反常理、反多数人/我是流亡路上的驼背,弓着的/背脊,已经习惯了高压/我是住在大海里的聋子/一生的假想敌就是暴雨中的雷霆/我是雨林中修习巫术的六指人/多出来的器官,我把他们献给鬼神/我是六亲不认的傻瓜/反智的年代,喜欢当马戏团的演员/我是理发店里神经质的秃头/偏执地要求手上拿刀的人/数清我满头来历不明的伤口/我是巨人国中心神不宁的侏儒/有人替我挡乱世的子弹,我替人们/收尸、守灵、超度、往返于生死两界之间/我是诗人,一个隐身于众多躯壳中/孤愤而又堕落的残废,健全人拥有的一切/我都没有权利去拥有/就让我站在你们的对立面/一片悬崖之上,向高远的天空/反复投上幽灵般的反对票”。
瘸子、盲人、哑巴、左撇子、驼背、聋子、六指人、傻瓜、秃头、侏儒、诗人。健全的人难以感受到的伤痛,都在一个诗人的血液里涌动。他承受着各种残缺的威胁,亦感激各种残缺的馈赠。他用伤痛去感受这个世界在繁华矫饰之下的屈辱。他会一直站在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把自己隔离在人群之外,隔离在正常之外,弃了理解、认同,拒了崇拜、颂扬,只寻求每一次发声的回归,替山水喊冤,替弱者喊疼。诗人在人世间偷渡,光明正大地躲躲藏藏。
山断水的大型机械,但还是可以替山喊疼,替水流泪。”雷平阳始终怀有一份责任:替山喊疼,替水流泪。他体会山水之痛,给自己义务为他们把疼痛诉说。“山川自成体系,人们各得其所,诗人发出声音只是义务和良知,不可能产生权势的功效。社会关怀,是作家永生永世的负载。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渴求权势的宠幸,不为时代写颂词。他的发声出于良知,出于对生命的悲悯,对真相的寻求。他所传达的,是永恒的生命价值,真挚的人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一个清醒的诗人,永生永世都要负载着唤醒的义务,为了唤醒,也为了传承。诗人天生无法沉默,他本能地需要哀鸣,用自己嘶哑的声音为这个荒唐的世界扯开虚荣的伪装:“基诺人认为,蝉是人间通往天国的路边,那些孤魂野鬼的化身,它们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叫,叫到天国和人间的门都打开。我觉得他们说的是诗人。我的写作就是叫,哀鸣。这不是反思的结果,是本能。”
《基诺山》,这本暗红色布面的诗集,最后的一首诗:《我》,以诉说一个诗人的故事结尾。“我是来自雪山的瘸子/不想跟上时间和流水的步伐/我是腾云驾雾的盲人/拒绝放射内心枝状的闪电/我是围墙外徘徊的哑巴/为了紧缩喉咙里的诉状、雷霆和秘密/我是迷宫里的左撇子/醉心于反常理、反多数人/我是流亡路上的驼背,弓着的/背脊,已经习惯了高压/我是住在大海里的聋子/一生的假想敌就是暴雨中的雷霆/我是雨林中修习巫术的六指人/多出来的器官,我把他们献给鬼神/我是六亲不认的傻瓜/反智的年代,喜欢当马戏团的演员/我是理发店里神经质的秃头/偏执地要求手上拿刀的人/数清我满头来历不明的伤口/我是巨人国中心神不宁的侏儒/有人替我挡乱世的子弹,我替人们/收尸、守灵、超度、往返于生死两界之间/我是诗人,一个隐身于众多躯壳中/孤愤而又堕落的残废,健全人拥有的一切/我都没有权利去拥有/就让我站在你们的对立面/一片悬崖之上,向高远的天空/反复投上幽灵般的反对票”。
瘸子、盲人、哑巴、左撇子、驼背、聋子、六指人、傻瓜、秃头、侏儒、诗人。健全的人难以感受到的伤痛,都在一个诗人的血液里涌动。他承受着各种残缺的威胁,亦感激各种残缺的馈赠。他用伤痛去感受这个世界在繁华矫饰之下的屈辱。他会一直站在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把自己隔离在人群之外,隔离在正常之外,弃了理解、认同,拒了崇拜、颂
扬,只寻求每一次发声的回归,替山水喊冤,替弱者喊疼。诗人在人世间偷渡,光明正大地躲躲藏藏。
读诗是一场自我救赎,诗歌让我终于认清自己,也让我明白,认识一个诗人,不需要恭维和奉承,也千万不要攀附他在人间的虚名。用诚恳的态度,去感知他想传达的一切,以促他完成他用一生去奉行的这场灵魂的偷渡,就是对诗人最好的尊重。
栏目来稿邮箱:love213052@sina.cn
生长在旷野中的诗歌
——雷平阳《基诺山》部分诗歌选读·吴云望
雷平阳的诗歌生长在旷野之中。以酒浇灌,以灵滋养,以土孕育,成就孤独。它的根向地底深处挖掘真实,感知灵魂,奉行敬畏,然后经由文字的茎叶引渡到现实中,也许开花,也许枯萎。雷平阳的动人之处在于他的粗粝:没有精雕细琢,只在旷野之中,承受着草叶的锋利和野风的诘问,而后俯下身来,捧一口泥水饮下。
《基诺山》,这本孤独的诗集,平静的暗红色封面下涌动着对雨林的向往。封面上诗人的书法,干净、原始。这本集子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回归、土地、生灵和偷渡客的故事,讲述着现代文明的斧镰,云南土地的共情,生命灵魂的触摸和一个偷渡客无法安葬的诉说。一、现代文明的斧镰
在一次访谈之中,雷平阳这样说道:“就在前两年,金沙江上修建几座大电站,大量的老百姓必须搬离故土,被称之为‘移民’。而所有的搬迁,其中第一项就是搬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祖坟,我看见无数的‘不孝子孙’在收取了政府很少的一点补偿金之后,泪流满面地将自己的祖坟一座接一座地挖开,然后将一具具枯骨装入土罐子,先背回家,
放满屋子及院落,祭拜一番之后,又背上它们,匆匆地赶往异乡。这种‘枯骨别’,活活地将活着的人也变成了行尸走肉、孤魂野鬼。”现代文明的潮水涌来,裹挟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如果反抗,就沉入水底,成为冤死的魂,连喊冤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现代文明,它翻搅着埋葬魂灵的土地,把一根根白骨硬生生遣回人世,没有道歉,没有解释,只有耀武扬威的补偿金在鼓吹着社会发展。而那些手无寸铁的“移民”,或者“不孝子孙”,他们连留居故土的权力都被剥夺,又何谈捍卫祖先的安息?冰冷的电站听不见鬼魂的呜咽,而敬鬼的人类,毕竟太弱小,抗衡不了这巨大的机器,只能漂泊异乡,背上枯骨,以安抚祖先。
“江水被开肠破肚之后,一座座电站/就是一座座能量巨大的天堂/上帝的牧羊人,在山中迷路了/赶着羊群,沿着电网的线路向前走/他坚信,任何一种路都存在尽头/而尽头也一定会有村庄和坟墓/他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信徒/却在无意识中把信仰当成了赌注——/当他和羊群途经城市,站在电线的/蜘蛛网下面,他失去了尽头。旷野消失了/陡峭的世界幻化成了魂路图上的魔窟/没有青草和水,人与建筑仿佛/中了魔咒一样冰冷,他与他的羊群/亦听从这魔咒,在屠宰场血腥的流水线上/瞬间就被剥皮抽筋,转世为一堆堆白骨”。雷平阳的诗歌很少出现“电站”一类的现代词语,他固执地驻守着他的寺庙、山野、草木。但是现代化的脚步却不会体谅一个诗人的留恋,电站毫不留情地将江水开肠破肚。“工业文明一来,很多东西都荡然无存了,故乡的灵魂也被抽走了。”这些冷漠的机器将江水的魂抽走,那仍旧流淌的水,成了推动机器运行的奴隶,没有魂。牧羊人没抵达期待的尽头,却走入一片冰冷的屠宰场。电网的线路无法带领他走入村庄和坟墓,只让他遇见冷漠的人和建筑。虔诚的信仰在现代社会成了羁绊和葬送,上帝被直接否定,何谈拯救?这里没有羊群渴食的青草,只有流水线上被剥皮抽筋处理出肥美的人肉。现代的魔咒封存了人和建筑的温暖,上帝如何?佛祖如何?菩萨如何?进入屠宰场,都不过是白骨一堆。
上帝被信徒放逐,金钱被拥上皇位。
“在隆隆的推土机和拆迁队的叫嚣中,一切被‘新时代’视为‘不合法’的事物和景观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消亡。”新时代成为唯一的评判者,土地和山野再没有发言权,只能等待着被屠戮的命运。这是个
充斥着霸权的时代,它肆意地对土地大刀阔斧,没有解释的责任,不需要对谁做交代。一座座高楼大厦崛起,不顾大地的承重;一条条公路被浇筑,封存泥土的呼吸;一座又一座城市被建立,一处又一处荒野被命名;飞速奔跑的高铁企图把神灵也甩在后头;寺庙被拔除或者安插在城市中盈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我们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看似‘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曾经的来路和一代人的命运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歌者,成了新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一个时刻回望并清醒的诗人,只能孤独地用文字拼命坚持,他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将那个与现代化相背离的旷野平移到纸面上。也许是抵抗,也许什么也不能是。
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之下,有被欲望扭曲了的人性,有被经济发展摧残的生命,还有单纯美好的希望被洗去幻想,剩下绝望把人狠狠地抛回去。诗歌中一颗颗变异的灵魂,是这个时代避之不去的躁动与苍凉。
“去年春,我们还在山上争论/农药、化肥与丰收/像埋在泥土里的石头,他不在乎/文明的毒素,只关心/用什么东西可以填饱肚腹/喝酒时,他多喝了两碗/哭着问我,要卖出多少粮食/他才能离开家,满世界去寻找/妻子和女儿。”这是关于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故事。文明的入侵让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让一个只关心用什么东西可以填饱肚腹的父亲,开口去询问粮食的价格;让一个不在乎文明毒素的丈夫,欲图用果腹的粮食去换取金钱,以奢求寻找妻女的希望。妻子和女儿下落不明,这小小的西南一隅,走出去,就是整个世界。满世界的寻找,寻找到了人,也终于寻找不到对土地的死心塌地。问题问出了口,就只剩下悲剧。
雷平阳是一个絮絮叨叨的“遗老”,他对现代化的霸权心知肚明,但他仍旧以他的文字固执地坚守原始。“他诗歌中总是有一种弥漫不散又沉沉坚固的‘土气’。这种特有的味道让人踏实,也让那些被现代性和城市化时代所溺染的人们有恍如隔日之感,未免心生唏嘘。”他以一己之力,游走在孤魂野鬼游荡的山野间,抚摸着云南的每一棵草,把心贴在土地上。
二、云南土地的共情
雷平阳爱云南。这片土地上有他诗歌中一再提及的乌蒙山、基诺山、哀牢山、澜沧江、司徒老寨、安边镇……雷平阳的文字守云南也出云南,他固守住云南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慈悲,又通过泥土的共情把这份慈悲传递出去。一个用膝盖触碰泥土的人,定能体会大地的关怀。
雷平阳对土地是深情的,情深生敬。他对这块土地有着发自肺腑的敬意。“尘土与人永远肌肤相亲。土地是不会自己站起来讨好人类的,这不是所谓的傲慢与尊严,它存在于那儿,人就必须谦卑,把自己贴上去,再贴上去,感到了它的温暖,也就证明你的灵魂和肉体还没有死,你就有资格多活一会。”人类若要真切感受到自己的生,获得活着的资格,就不得不贴近土地,感受土地的温暖,感受这温暖赋予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尊严。然而,这份古来有之的谦卑早已被人类淡忘。人类对土地的忘恩负义最终会把自己推向深渊,只是土地太慈悲,她包容着子女在她身上挖掘堆砌,将她的乳房揉捏进子宫,拖拽出她的肚肠。
“土层中,有替罪羊来不及/刨光的草籽,有披着白色塑料薄膜/播种土豆的怀孕女人的影子/有兽骨,在蚯蚓的蠕动下呻吟/有反复被鞭打的囚犯/在耶稣和释迦牟尼之间左右权衡/不知道自己,该把死亡献给谁……/有一只蟋蟀,尖声鸣叫/声音清凉,干净/仿佛所有的业障,已经消弭”。土层中埋葬着罪恶露出的马脚,包裹着母亲用亲身劳作换取的生存,隐秘着兽骨坚硬的死与蚯蚓柔软的生的碰触,还有那被自己反复鞭打的囚犯,要让自己的死亡成为一场祭献,却不知该献给谁。只有泥土中的蟋蟀发出一只蟋蟀的声音,清凉,干净,是土地的声音,仿佛要消除所有蒙蔽在眼前的业障,以安抚这些可怜的生灵。但终究只是仿佛,心放不下,业障又怎么消除?土地知晓了一切命运,她包容着一切事物的发生,不发表任何评价,只给出真实的反应。假设世上真有全知的上帝存在,那土地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上帝。它仰视着人类,姿态平庸又高贵。
雷平阳诗歌里的云南,早已跳出了“地域性”的框架。说雷平阳是“地方性”诗人,是一种偷懒的评价。正如诗人所说:“我所写的‘云南’,乃是挣扎在工业文明与古老山川之间的一片旷野……”诗人选择
云南这片土地进行创作,因为这片土地野,“礼失求诸野,云南有足够的野,我在其间写作,内心装着千山万水,只想将这野,带到纸上,借以反对猖狂、霸道的诗歌政治学以及暴力般的工业文明。也就是说,我一直对地方性写作这个概念持反对态度,它方便了评论话语谱系中的指称,却有意无意地埋葬了诗歌辽阔的存在空间。”云南之野,是每一寸土地的共性。土地的野性自动站在工业文明和诗歌政治学的对立面,诗人向云南求助的是云南的野性而非名字。如果我们将雷平阳局限在“地方性诗人”的称号之中,我们对他诗歌的解读势必造成困居一处的局限。在他的诗歌里,地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它们可以指代任何一处地方。基诺山和澜沧江在诗人的诗歌中,是以山丘和河流的本来姿态呈现。它们不是名山大川,它们的背后没有文化符号和指称意味,就如同《尽头》中的那颗石头,“抱着石头的本质,彻底断绝了/成为纪念碑的可能性……”诗人力求让山丘只是山丘,河流只是河流,石头只是石头,诗人要呈现的是云南作为一片土地的本来面目,是一片旷野的自性,而不是那个旅游手册中代表着隐居、桃源、安逸种种附加意义的彩云之南。所以从该层面来看,诗人笔下所写的云南,大可以接宇宙,小可以观砂砾。他不再给山水附加其他意义,云南不因为雷平阳而产生其他指称意味。雷平阳将自己放空成一具肉体,让云南魂附,代云南诵诗。
“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远方’的时代。极其吊诡的则是,我们的‘地方’和‘故地’尽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被强行地远离了它。而‘地方’和‘故地’的改变更是可怕和惊人,因此文字空间里携带着精神能量的地理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有之乡。”我们居住的故土在一次次的规划建设中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土地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中失去了自性,触目惊心的是,大多数人面对土地的远离是如此麻木。我们太需要土地的包容和安慰来消弭我们当下的迷惘,故而雷平阳之代山水而吟愈加显得珍贵。三、生命灵魂的触摸
一个关注土地心声的诗人,能够感应到行走在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灵并满怀悲悯之心敬畏它们。诗人对生命的平视来自诗人内心对万物有灵
的信奉:“在我的故乡云南,哈尼族、佤族、布朗族和基诺族等民族,都相信万物有灵,人与各类物种是平等的,动植物是人或鬼神的另一种存活方式,对此我没有异议并乐于遵守其善待之道。这样的观念很自然地深植我心,让我屡屡写到动物和植物,都觉得它们是命,尊严和慈悲通常比人拥有的还要多!”在生命面前,动物和植物,人类和鬼神,都是平等的。在雷平阳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对生命发自肺腑的认同感。不是以一个审判者的角度去品定生命的价值,而是以一个信徒的身份,焚烧诗稿以触摸生命的真实。他没有谄媚的歌颂之辞,他的笔像雕刻的刀,小心翼翼地削出生命的尊严和慈悲,“他不会取巧,即使是对于极其细小的虫草和石块他也必须弯下腰去翻检和察看。”
这个世界太缺少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了。人类太喜欢以救世主自居,妄图重新创世。但其实,我们哪来的资格去重塑自然?我们来自于自然啊,我们和一株草一样羸弱,依附着土地,汲取着她的营养,暴露在白日和黑夜之中,是那么渺小。而可笑的是,我们居然能够顶着正义的名号以战争的形式对同类进行不负责任的屠杀,我们也能够借以发展的目的轻易宣判原始森林的死刑,这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后退?
在《两头大象从我身边经过》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威慑力:“那一瞬,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散发的天生的威慑力、冲击力和统治力/令我内心崩溃,令我眩晕,令我窒息/令我体量缩小,再缩小/他们从我身边经过,视我如无物/我主动示弱,藏身于灌木丛/目送他们远去双手死死抱住自己/像抱着一头侥幸逃生的小野兽/像抱着一棵突然软下来的松树”。自然生长的两头大象,他们生命的威慑力、冲击力和统治力让诗人一瞬间暴露出人类本性的恐惧。在自然法则之中,人类面对大的事物时会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情感。但是,在《肉做的起重机》中,这生命的威慑力却被人类的斧头、刀背和棍棒驯服,成为搬运原木的起重机。他们瘦骨嶙峋,状如标本,断子绝孙。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自以为是:“它们佝偻着/东倒西歪地向前,像拖着整个世界的尊严/连同我内心仅剩的一丝孤傲,偷生人世”。两相对比,触目惊心!人类为了利益,抛弃敬意,让生命在他们胯下偷生。眼见悲凉,才生悲悯。雷平阳在两次访谈中都谈及了他诗作中的悲
悯情感:“‘悲悯’出现在诗中,不是我有意植入,它随命而来,是天生的呼救,是绝命前的最后一次柔软。”、“至于悲悯,蚯蚓具备,田鼠具备,人当然也应该具备,因为它是生命的根本品质。”悲悯之情人皆有之,并非诗人独有。但它却在人群中被淡漠,只能活在诗歌之中。《烧荒》之中,诗人痛挽被火烧惊扰了睡眠的草木、被高温烤熟的幼兽和昆虫、以及逃脱后成为看客的飞禽和巨兽。在另一个世界,个体和独立被荡平。山坡之上那些游荡的灵魂,满世界找物托身。一场烧荒,烧掉了生命,也烧掉了怜悯之心。诗人只能借助附体的蟋蟀,为生命唱出一曲凄厉的挽歌。
万幸的是,还有云南大地上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多的现代文明影响,他们的内心依然虔诚,他们保有人类最初的模样。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现代文明那些丰富多姿的幻象,他们更加清晰、安稳地活着。
“一个女孩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和信物/她的情人找到巫师——/‘我想去阴间看看,问一下/她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巫师给他放魂,却没有将他再收回来/他的身体至今还留在基诺山/每天睡觉,耕种,喝酒/像一部肉做的机器,几十年运转/幽灵一样,沉默寡言”。在基诺山上,人能够和鬼恋爱,爱情不惧怕生死之别。失去了魂的人是人间的幽灵,肉身继续完成人间的路程,像机器一样运转,而被巫师放出的魂魄,可以追随死去的女孩或天国或地狱,相爱不需要依靠肉体死亡来成全。因为相信有灵,爱情得以以最完美的方式实现。
在雷平阳的诗歌中,我看到了生命被奴役的可怖,也看到生命最本初的美妙。正因为这种种现象,我们才更加需要俯下身来,谦卑、诚恳地触摸生命。真诚地感受生命,尊敬生命,是我们对自己的负责。四、偷渡客的孤独与承接
在《基诺山》的序言中,雷平阳把自己定位为偷渡客。他行走在原始与现代、神鬼与人类、天与地之间,他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也是一个坚定的承接者。偷渡客,没有合法性、公共性和透明度,作为连接着两个世界的使者,却同时被两个世界放逐。
偷渡客是孤独的,偷渡客的孤独来自觉醒。他将那些敏感而质朴的
东西从雨林中、佛眼中、巫师的咒语中、野象的身体中偷渡到诗歌里,小心翼翼地低喃着,在土层下蔓延。“面对着在加速度时代即将消逝和早已远逝之物,诗人内心的翻搅杂陈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因为他太觉醒,一般人无法理解、认同,就像是被误认为疯子的天才,又或者,疯子本就是天才。太醒了!醒到求醉死:“‘兄弟,再来一碗,醉死,醉死算了……’”
“他看见过/拍地痛哭的偷渡者,去国前/一页一页地撕吃《诗经》和李白/吃土和啃孔子木雕的人,他也见过/想麻木,麻木不了。这些人过江/坐穴头的独木舟,很多人沉江而亡/只有尸首和泡沫去了异乡,他想麻木/麻木不了。酒一醉,他就充当他们的家人/恶狠狠地向江水要人。”偷渡客,是不得不逃离的一群人。他们热爱着故土的传统文化,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灵魂,却无法解救肉体。意识形态的统一需求容不下他们的清醒,这群觉醒者必将受到驱逐。对面没有《诗经》了,没有李白、孔子了,坐在独木舟上的他们,内心的波涛翻滚胜过江水,离开了故土,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很多人沉江而亡”,万念俱灰,心已死,肉体偷生又有何意义?
“偷渡者所有的遭遇、立场、心态/这时候,全部都汇集到了我的/心上:重压、负罪潜逃、恐慌、去远方/崇洋媚外、贫穷、反抗、弃暗投明/囚禁、贩毒、野心勃勃、冒险、自虐/流亡、赴死、求财、另谋生路……/——在我心里,凭空多出/一座座避难所和集中营,以及缅寺和教堂/他们被我一一想象出来/强压给自己,仿佛自己的内心/真的横亘着一条浊浪滔天的大江/仿佛自己真的是一个偷渡者/身在故土,却一直在流亡/因此,船至对岸,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死里逃生,跪在江边痛哭了一场/”。偷渡客永远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被逮捕,被示众,被作为一种指代,或者符号。而“我”,一个内心没有归属感的人,是精神上的偷渡客。“身在故土,却一直在流亡”。肉体要偷渡,只需要一条船,但精神的偷渡却是永无止息的折磨,这重压没有尽头。“我所奉行的往往就是我内心反对的,而我真正以文字竭力捍卫的东西,却又连说出声的勇气都已丧失。”面对这样的情况,诗人只能用诗歌发声,用“诗歌中的现实”为“现实”超度。
偷渡客,承担着引渡清醒的责任。“或许,我们的诗篇阻挡不了开
们把疼痛诉说。“山川自成体系,人们各得其所,诗人发出声音只是义务和良知,不可能产生权势的功效。社会关怀,是作家永生永世的负载。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渴求权势的宠幸,不为时代写颂词。他的发声出于良知,出于对生命的悲悯,对真相的寻求。他所传达的,是永恒的生命价值,真挚的人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一个清醒的诗人,永生永世都要负载着唤醒的义务,为了唤醒,也为了传承。诗人天生无法沉默,他本能地需要哀鸣,用自己嘶哑的声音为这个荒唐的世界扯开虚荣的伪装:“基诺人认为,蝉是人间通往天国的路边,那些孤魂野鬼的化身,它们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叫,叫到天国和人间的门都打开。我觉得他们说的是诗人。我的写作就是叫,哀鸣。这不是反思的结果,是本能。”
《基诺山》,这本暗红色布面的诗集,最后的一首诗:《我》,以诉说一个诗人的故事结尾。“我是来自雪山的瘸子/不想跟上时间和流水的步伐/我是腾云驾雾的盲人/拒绝放射内心枝状的闪电/我是围墙外徘徊的哑巴/为了紧缩喉咙里的诉状、雷霆和秘密/我是迷宫里的左撇子/醉心于反常理、反多数人/我是流亡路上的驼背,弓着的/背脊,已经习惯了高压/我是住在大海里的聋子/一生的假想敌就是暴雨中的雷霆/我是雨林中修习巫术的六指人/多出来的器官,我把他们献给鬼神/我是六亲不认的傻瓜/反智的年代,喜欢当马戏团的演员/我是理发店里神经质的秃头/偏执地要求手上拿刀的人/数清我满头来历不明的伤口/我是巨人国中心神不宁的侏儒/有人替我挡乱世的子弹,我替人们/收尸、守灵、超度、往返于生死两界之间/我是诗人,一个隐身于众多躯壳中/孤愤而又堕落的残废,健全人拥有的一切/我都没有权利去拥有/就让我站在你们的对立面/一片悬崖之上,向高远的天空/反复投上幽灵般的反对票”。
瘸子、盲人、哑巴、左撇子、驼背、聋子、六指人、傻瓜、秃头、侏儒、诗人。健全的人难以感受到的伤痛,都在一个诗人的血液里涌动。他承受着各种残缺的威胁,亦感激各种残缺的馈赠。他用伤痛去感受这个世界在繁华矫饰之下的屈辱。他会一直站在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把自己隔离在人群之外,隔离在正常之外,弃了理解、认同,拒了崇拜、颂扬,只寻求每一次发声的回归,替山水喊冤,替弱者喊疼。诗人在人世间偷渡,光明正大地躲躲藏藏。
山断水的大型机械,但还是可以替山喊疼,替水流泪。”雷平阳始终怀有一份责任:替山喊疼,替水流泪。他体会山水之痛,给自己义务为他们把疼痛诉说。“山川自成体系,人们各得其所,诗人发出声音只是义务和良知,不可能产生权势的功效。社会关怀,是作家永生永世的负载。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渴求权势的宠幸,不为时代写颂词。他的发声出于良知,出于对生命的悲悯,对真相的寻求。他所传达的,是永恒的生命价值,真挚的人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一个清醒的诗人,永生永世都要负载着唤醒的义务,为了唤醒,也为了传承。诗人天生无法沉默,他本能地需要哀鸣,用自己嘶哑的声音为这个荒唐的世界扯开虚荣的伪装:“基诺人认为,蝉是人间通往天国的路边,那些孤魂野鬼的化身,它们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叫,叫到天国和人间的门都打开。我觉得他们说的是诗人。我的写作就是叫,哀鸣。这不是反思的结果,是本能。”
《基诺山》,这本暗红色布面的诗集,最后的一首诗:《我》,以诉说一个诗人的故事结尾。“我是来自雪山的瘸子/不想跟上时间和流水的步伐/我是腾云驾雾的盲人/拒绝放射内心枝状的闪电/我是围墙外徘徊的哑巴/为了紧缩喉咙里的诉状、雷霆和秘密/我是迷宫里的左撇子/醉心于反常理、反多数人/我是流亡路上的驼背,弓着的/背脊,已经习惯了高压/我是住在大海里的聋子/一生的假想敌就是暴雨中的雷霆/我是雨林中修习巫术的六指人/多出来的器官,我把他们献给鬼神/我是六亲不认的傻瓜/反智的年代,喜欢当马戏团的演员/我是理发店里神经质的秃头/偏执地要求手上拿刀的人/数清我满头来历不明的伤口/我是巨人国中心神不宁的侏儒/有人替我挡乱世的子弹,我替人们/收尸、守灵、超度、往返于生死两界之间/我是诗人,一个隐身于众多躯壳中/孤愤而又堕落的残废,健全人拥有的一切/我都没有权利去拥有/就让我站在你们的对立面/一片悬崖之上,向高远的天空/反复投上幽灵般的反对票”。
瘸子、盲人、哑巴、左撇子、驼背、聋子、六指人、傻瓜、秃头、侏儒、诗人。健全的人难以感受到的伤痛,都在一个诗人的血液里涌动。他承受着各种残缺的威胁,亦感激各种残缺的馈赠。他用伤痛去感受这个世界在繁华矫饰之下的屈辱。他会一直站在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把自己隔离在人群之外,隔离在正常之外,弃了理解、认同,拒了崇拜、颂
扬,只寻求每一次发声的回归,替山水喊冤,替弱者喊疼。诗人在人世间偷渡,光明正大地躲躲藏藏。
读诗是一场自我救赎,诗歌让我终于认清自己,也让我明白,认识一个诗人,不需要恭维和奉承,也千万不要攀附他在人间的虚名。用诚恳的态度,去感知他想传达的一切,以促他完成他用一生去奉行的这场灵魂的偷渡,就是对诗人最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