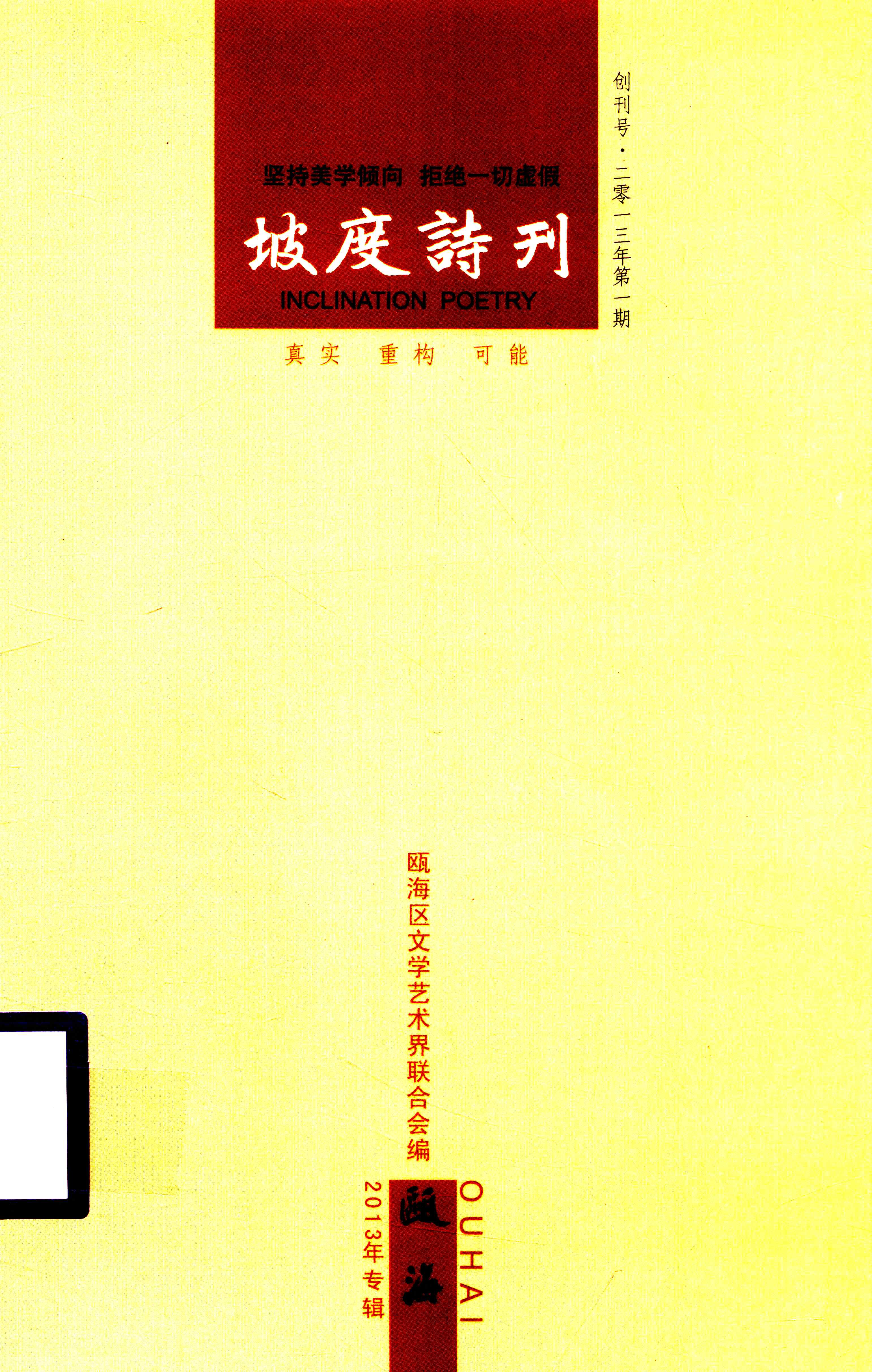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野外诗社选辑
江离
炭马
飞廉
山叶
陈洛
施瑞涛
江离◎对毕达哥拉斯的献辞
博格达峰的雪
——致沈苇
白天多么漫长,到处都是光
悬浮着并且颤动
在飞机的机翼、公路、桦树和杨树的叶片上
也在清真寺的圆顶之上
你陪着我们上街,戴着标志性的平顶帽
你的黑胡须中已掺入了几缕白色
那里面有众多星辰隐匿,仿佛晨昏在交替
一家小面馆门前,狗伸长了舌头
吐着热气,这真是一个酷暑
它的主人在椅子上打盹
街上来往着维吾尔人、汉人、哈萨克人和藏族人
切换着不同的语言交谈
伊斯兰的信徒坐在广场上听经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开斋节
橘色的带着阿拉伯花纹的大巴扎
透着精美典雅
漂亮的维族姑娘们在商铺
向游人介绍薰衣草精油、羊毛围巾和挂毯
这一切让人忘记了
这里曾有过的暴乱和流血
像一场大雾现在已经消散
除了街头戒严的装甲车
和被恐惧与痛苦永远折磨着的幸存者
后来,在你的家中,我们抽着烟
聊了很久:残酷的现实,脆弱的信心
为什么安宁的生活却不可得
透过窗户,你指给我们看
远处的博格达峰和终年不退的积雪
夏日的光照没有融去这些白雪
在峰顶之上,是无与伦比的寂静
那么宏阔,犹如生之奥义
没有沙漠、戈壁、盆地、山脉和城市之别
没有臣服也没有冲突
它教会久历死生的人们
在更迭的征服者的版图中生活的人们
把苦难变成一种必要的坚忍
花木之歌
阳台上有两株月季
是最初宜平从旧居带来的
每过一段时间
她从花店和卡车开来卖的植物中
挑选一两种
鸭掌木、金边瑞香、明月草
有时也有挖来野生的
还有从远方邮寄来的种子
一两个星期后,土壤中
就会出现新芽
有种说不清的奇妙
来自于那一小片移动的土地
无论如何,她有种亲近花木的品性
而我能做的,是从这个小村镇
采集松软的沙土
然后把生长了的花木移到更大的盆里
我看她在木制的花架和阳台
有层次地摆放着这些:
栀子、蔷薇、碰碰香、白色和蓝色的雪花
一个罗列的四季,能感觉到
风在新叶间逗留
就像一个丛林,一个独立的无忧国
一种仅次于创造的照看
带来了清新的回馈
对毕达哥拉斯的献辞
因为无限的少数人都曾追随,
晦明不定的星空的指引,
如同毕达哥拉斯,在他的窗口仰望。
一个无边黑暗中的孤寂旅人,这以后
所有世界的阅读者、巫师、智者、炼金术士,
各自穿过了丛林、黄昏的金色海岸,
历经地狱之苦——
不是为了在一头饥饿的狮子身上
复苏它统治土地的雄心,不是在沙漠之上
建立黄金的国度,
只为在星辰的沙盘上推演,
(在理智认知和未知神明的庇佑下)
我们自身和世界之中,那不可见的统一性。
炭马◎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我想叫上我
我想叫上我
到午夜的大街走走
白天,我们各忙各的
这暗蓝无为的晚上
总算有时间和我
碰个面
去哪里都无所谓
一路慢慢走着就好
有人没人都不要紧
他们只和他们有关
就这样静静走着
在路灯冷静的眼睛里
影子一样摇摆不定
就这样一路无语
或许这样才能更清楚
感到彼此
走得累了
就找一个地方坐下
喝点东西
江河湖海
一杯杯飞渡
直喝到灯阑酒残
直到忘记了彼此
好在出门的时候
我还是跟了上来
我和我就这样摇摇晃晃
继续走着
一前一后
好像谁也不认识谁
直到我差点摔倒
我伸手扶了我一把
我没有说出感谢
因为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彼此
眼中的泪水
春天里
外面,春天一寸一寸在长
簇拥着
一点也不挤
鱼在水里,吐出一串一串词语
喋喋不休
没一句废话
孩子们坐在黑板前,加减乘除
他们一点一点在长
答案没有长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坐在影院里,我突然想到
所有人缅怀的青春
就像一匹用心编织过的锦缎
只在记忆里柔软
不加刀尺
看完电影,街灯已昏黄
妻子和我边走边谈
剧情和人物,不过是我们缅怀青春的
一些似是而非的影子
我们谈到剧中一位叫阮莞的美丽女子
她的青春止于一场意外车祸
那是婚礼前夕,她赶去听多年前
和前男友约定的一场偶像乐队的音乐会
尽管此前她的爱情被多次辜负
她的善良、宽容让人吃惊
她用死保存了青春和美丽
突然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活着,却不知道如何保存
这些易碎的东西
生日
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我们面对的
并非汹汹而来的僵尸
我们一直在和风车作战
飞廉◎岁暮望月
夏日山居
入狱兄弟接连来信,询察世事;
我叹他敲冰求火,遂寄他《老残游记》。
小院,日日读《桃花扇》,
老桐影深,家蝉声楚,似说
明三百年,隳于何人,歇于何地?
天下兴亡,关我何事!我只爱孔尚任
言说之美,扇上的声色风云。
蝉歇,偶有黄鹂、杜鹃短歌一曲;
樟门剥啄,凤仙花开三色,
邻家小女,求花染指甲;
五日后,隔墙酒叟八十大寿,为此
蒋家男婴啼哭不止。
雪夜风雨茅庐
岁暮,伍公山草木苍唐;
时事泥浊,青冥之下,
小民们劳心焦思,障深业重。
偏安在这销金窟,
我游戏琴书,写山水文章。
风雨茅庐,为我发福的中年,
遮挡乱世风雨。
大雪封门,这寒光让我惊遽,
梦寐之际,遂得见阿弥陀佛,
遂愧对东海之浮石,
愧对鲁迅剑锋黑青。
今夜,我把头埋进大雪
今夜,我的笔北风潦冽,
挑亮灯,你我且彻夜著史。
山水
这些年,我观赏过李思训的金碧山水,
“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
三峡闻猿时”的关仝山水。
游历过荆浩的太行山水,
石涛开辟的“黄山派”山水,
黄公望的富春山水,
那偏隅东南的青田山水……
追想过李成山水中的寒林平野,
他醉死在我的故乡,
不曾留下一幅真迹。
而只有凝望倪瓒的《虞山林壑图》,
我才清醒认知,事实上自己
早已死去。郭熙说王羲之喜欢鹅,
纯粹为了观察它们潇洒的脖子,
以练习执笔转腕;这些年,
我徜徉山水,
因我已来到人生中途,
深陷但丁地狱,战战慄慄,
日谨一日。整整八年,
我住进南宋马远的《凤凰山居图》,
空想着贝雅特丽齐。
到处都是魔幻现实主义,
我宁愿隐逸于空想,
“往往整个国家都靠空想才生存下去。”
凤凰山上,电塔林立,
尽管如此,它还是我的贝雅特丽齐;
尽管东西南北,几乎所有
山水都戴上了镣铐,它们也都
还是我的贝雅特丽齐。
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草书益佳,
钱塘江潮水,却让我的生活,越加混乱,
而“混乱已完成了他的杰作!”
岁暮望月
山中,这农业社会的月色,
铁锈在浙赣线上疾驰的辛亥革命的月色,
公元763年,杜甫怀里最后一文钱的月色,
颍水滨14年前,那静坐在我自行车后座的月色,
女孩踢毽子、公鸡变杜鹃、老鼠磨牙、
狸猫偷吃腊肉的月色,
西泠桥边苏小小的碑影开始结冰的月色……
昨晚梦里是刑场,醒来日记是故乡,
罗隐说,所有月色,
都是往事吐下的一地碎甘蔗,
望月则是在《古诗十九首》里照镜子。
头皮屑日夜下雪,几点寒星,萧杀而冷漠。
山叶◎雨后的乡村
一个像雨滴的声音
一个像雨滴的声音,时常在我耳畔响起
有时在清晨,有时是夜晚
当它发出“啪嗒,啪嗒”
我总以为外面在下雨
某日早晨,当我坐在台阶上看书
一位母亲写道,她很想念死去的儿子
终于在梦里见到了他,并告诉她:
“妈妈,您过多的泪水
浇灭了我好不容易点亮的灯盏。”
关于菜园的记忆
仍然是我童年时的菜园
梨花刚谢,苹果叶舒展
向阳处,几排小葱虚妄地朝着田垅长着
右侧的那棵桔子树去年就死了
枝杈干枯,没有再次长出新叶
当作围墙的刺柏长得过高,遮盖了
周围的植物,使它们极少照到阳光
一到春天转暖,父亲就会从深深的黄泥里
挖出一捆捆埋藏过冬的甘蔗
亮紫的表皮上,偶尔会爬着被吵醒的蚯蚓
我和姐姐围着父亲,等着吃
他用柴刀刨削干净的甘蔗
等到真正开春,菜园里会重新种上
一节节带芽的甘蔗
现在,菜园荒废了不少
春天刚到,亮绿的青草火速占据一角
长势凶猛,就像当初曾旺盛生长过的黄花菜
它们中的任何一棵
都有可能成为围绕整座菜园的那枝藤蔓
蚂蚁
快下雨了,两只蚂蚁在一根长水管上
往相反的方向爬行
它们急着赶回家吗,它们的家离这里远吗
家里有妈妈在等着它,还是有怀孕的妻子
要是一不小心,从水管上掉了下去
会不会有热心的同伴来帮忙
要知道,帮助——
这种最原始的表达,在世间已经越来越少
甚至连给予它命名的人类,也对此充满了蔑视
乌桕
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阴冷蔓延
冷空气昨夜降临这个小镇
轻松地驱走了暖冬
乌桕树上挂着去年的果实
隔着雾霾透出点点白光
想起幼时,妈妈曾带我和姐姐
摘过这样的种子
仿佛摘取她怀里满满的乳汁
也在这样薄暮沉沉的溪滩地里
太阳照在不远处的空旷地
如今,我每天都会对着它发一会呆
脑袋空空的。果实每天在减少
现在,我期望看到——
开春之时,它的树下遍地长满
发了芽的种子,即使没有一棵会长大
雨后的乡村
阵雨过后,蝉恢复了鸣叫
它们停在各自的树冠中
有时雨滴坠落,惊慌地飞离树梢
阳光重新打在雨后的石桥上
桥下流水因雨水的加入变得湍急,响亮
水草茂盛,溪鱼追逐
蜻蜓盘旋在高处,它们深知飞行的奥妙
也曾低飞在下雨前的乡间小路上
翅膀从不会被雨水打湿
此时,气温在下降
不断拉低落日在空中的位置
有一刻,余晖疲惫地洒向湿漉漉的山村
电线杆是大自然手中的魔法棒
它把黄昏中的村庄一个一个点亮
陈洛◎在南湖边
傍晚的南宁
大叶榕到过的地方我到过,
蓑衣和细雨到过,这里是我要抵达的故乡。
晚风阔大,暮色里的翅膀越来越暗
父亲,我坠落的一生,
曾经在流水上风光无限。
而这里,是我一路撤退的最后一点尘土。
此刻,傍晚的灯火变幻着暗影,
我每次登楼,
都是为了在老去的时光里虚设脚印。
在牯犒岭
午后的山岚迷乱
树冠静如默悼。这里
四月稀少
我们往林深处探访
步屐停处,察看干瘦的溪流
耳边有无数
灵禽,在溪石间复活
寺院止语,浓荫泽盖的蝉
练习松针织网,有不测深海
它闪耀之处,来自
这个入夏的
喜悦、急躁和死亡面孔
从制高点往北眺望,我遥见
庄子的牯犒山居
有大风掣巨鸟疾走
垂暮,我才认清自己
一只瘦小的松鼠
在松涛密集间栖隐身子
在南湖边
黄昏的光晕调低它的底色
最终落入安静生长的细叶榕上,
蝉在林子里鸣唱
它沉浸于自己的声音,多么悠远。
我在南湖边的草地上独坐
看天空和湖水。密布的麻雀
在我的宇宙里闪过一些往事
有些悲壮,有些快乐。
远处的灯和暮晚的云
擦拭我微信里陌生的温暖,
哦,这多么美好,
一如草地上升起的慢,脱离尘俗。
在舍弃的时光中
没有人领会这种虚构的专注
也没有人和我互道晚安
但神谕般寂静给我带来了久久的颤栗。
莫干山纪游
过滚石瀑,深壑险峻。那蝉声
老气横秋,是我听过最郁闷的长笛。
松月庐,重门深锁。这当年
蒋公憩居之地,夕照下,犹显苍惶。
芦花荡没有芦花。千年冷杉前,
有木牌警示:此处毛虫甚多,不可久留。
月出林低。夜宿武陵村,梦中疑与陶令对饮。
清晨,过剑池,怪石角,朝霞似美女向导。
盛夏山中,竹森,绿净,泉幽。
而我尤爱那只刚爬出草丛的花斑蜗牛。
施瑞涛◎我们常常谈起那个夜晚
那个爱我的男人,老了
隔着门缝,老花镜已经爬上了他的鼻梁
那个爱我的男人,老了
年轻时活跃的思维,偶尔也开始罢工
手臂的关节,也有了衰老的痕迹
那年他亲手种下的桂树,在寒风中
给春天写信,一年瑞雪
花朵可以开得比去年更加芬香
经过客厅,我尽量压低脚步的声音
我怕叫他一声爸爸,会使他的记忆一阵惊慌
隐遁
在黑暗的东方,学习遁术
让晚风吹不进你生锈的身体
人群或者时代中,看不见你
作为空气的象征,你把自己的
内心遮蔽,奔跑在无边的梦境
像一个旁观者,不带色彩地看着
这个世界的哭泣和喜悦
你甚至可以想象,那些被时光吞噬
的灵魂,重新揭穿五月的预言
照亮那个水稻疯长的远方
你爱这个夜晚,以一种隐秘的方式
抵达下一个春天,背对着时代
想起浙西的那片田野
命运以寂静的名义,摘满了
熟透的果实,低处的土地花开两朵
往来的木车轻歌而过
更远处,天空到处都是夕阳
一辆火化车经过,你看见一个人
躺在里面,像你,又不像你
摘苹果记
那时我还年少,易饿的夏天
想摘树上的苹果,红透了的时光
在天空下那么闪亮
未发育的身体,怎么跳也够不着
那个最红的苹果
旁边的凳子梯子,都各有他用
当然那时的我还没学会爬树的技巧
只能仰望着果实,肚子里的舞蹈
和眼神里的渴望
看着伙伴们高高地跳起,苹果在嘴里流汁
回到角落,心中的一万只蚂蚁在集合
我开始学习跳跃的本领
下弯腰,再腾空,那些不眠的夜晚
我开始学习爬树的本领
让自己成为树的一部分,只有月光知道
终于在某个雨夜,我够到了那只苹果
一只虫子从里面探出了头
晚熟的少年,已经没有力气哭泣
坐在地上,握着红色的苹果
一言不发,直到天亮
他睡着了,在远去的路上
满地的落叶飞回到从前
漫山遍野的红苹果
向他跑来,像一个个鲜艳的句号
我们常常谈起那个夜晚
风,一直朝着西边吹
我们不长的头发上
爬满蓝色的时光
月光穿着过冬的衣裳
躺在摇篮上说梦话
我们常常谈起那个夜晚
在一个城边小镇,雨后的广场上
到处都是悦耳的碰杯声
酒精让我们不说谎话
连狗吠,也能穿透黑夜
你爬上桌子,用酒瓶
当话筒,唱跑调的歌
我昂着头,脱了鞋子准备
在明天早晨出发
那棵盛开的丁香树下,就是我的家
他摇晃着身体,眼睛里的波光
越过群山,终究没有把远方看透
只有身旁的姑娘,安静的听我们废话
默默地清理时光的污垢,岁月的残渣
和扫起一地的月光
没有一朵花是干净的
首先我不是干净的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你
一颗种子,从土里逃出
谁能保证这个过程是干净的?
那些被它踩在脚下的种子
那些吸收不到阳光的种子
消失在幽暗的通道里
甚至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雨水总是偏爱柔软的一面
没有一朵花是干净的
一些花朵在开放之前就被践踏
一些花朵被蛇虫所青睐
一些花朵的身上沾满泥巴
没有一朵花是干净的
即使它朝着天空,随风摇摆
装作一副自由的样子
即使它红艳遮日,香飘四方
花托已经腐败得失去信仰
你看,只要一场小小的雨
就让它的虚伪彻底暴露
江离
炭马
飞廉
山叶
陈洛
施瑞涛
江离◎对毕达哥拉斯的献辞
博格达峰的雪
——致沈苇
白天多么漫长,到处都是光
悬浮着并且颤动
在飞机的机翼、公路、桦树和杨树的叶片上
也在清真寺的圆顶之上
你陪着我们上街,戴着标志性的平顶帽
你的黑胡须中已掺入了几缕白色
那里面有众多星辰隐匿,仿佛晨昏在交替
一家小面馆门前,狗伸长了舌头
吐着热气,这真是一个酷暑
它的主人在椅子上打盹
街上来往着维吾尔人、汉人、哈萨克人和藏族人
切换着不同的语言交谈
伊斯兰的信徒坐在广场上听经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开斋节
橘色的带着阿拉伯花纹的大巴扎
透着精美典雅
漂亮的维族姑娘们在商铺
向游人介绍薰衣草精油、羊毛围巾和挂毯
这一切让人忘记了
这里曾有过的暴乱和流血
像一场大雾现在已经消散
除了街头戒严的装甲车
和被恐惧与痛苦永远折磨着的幸存者
后来,在你的家中,我们抽着烟
聊了很久:残酷的现实,脆弱的信心
为什么安宁的生活却不可得
透过窗户,你指给我们看
远处的博格达峰和终年不退的积雪
夏日的光照没有融去这些白雪
在峰顶之上,是无与伦比的寂静
那么宏阔,犹如生之奥义
没有沙漠、戈壁、盆地、山脉和城市之别
没有臣服也没有冲突
它教会久历死生的人们
在更迭的征服者的版图中生活的人们
把苦难变成一种必要的坚忍
花木之歌
阳台上有两株月季
是最初宜平从旧居带来的
每过一段时间
她从花店和卡车开来卖的植物中
挑选一两种
鸭掌木、金边瑞香、明月草
有时也有挖来野生的
还有从远方邮寄来的种子
一两个星期后,土壤中
就会出现新芽
有种说不清的奇妙
来自于那一小片移动的土地
无论如何,她有种亲近花木的品性
而我能做的,是从这个小村镇
采集松软的沙土
然后把生长了的花木移到更大的盆里
我看她在木制的花架和阳台
有层次地摆放着这些:
栀子、蔷薇、碰碰香、白色和蓝色的雪花
一个罗列的四季,能感觉到
风在新叶间逗留
就像一个丛林,一个独立的无忧国
一种仅次于创造的照看
带来了清新的回馈
对毕达哥拉斯的献辞
因为无限的少数人都曾追随,
晦明不定的星空的指引,
如同毕达哥拉斯,在他的窗口仰望。
一个无边黑暗中的孤寂旅人,这以后
所有世界的阅读者、巫师、智者、炼金术士,
各自穿过了丛林、黄昏的金色海岸,
历经地狱之苦——
不是为了在一头饥饿的狮子身上
复苏它统治土地的雄心,不是在沙漠之上
建立黄金的国度,
只为在星辰的沙盘上推演,
(在理智认知和未知神明的庇佑下)
我们自身和世界之中,那不可见的统一性。
炭马◎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我想叫上我
我想叫上我
到午夜的大街走走
白天,我们各忙各的
这暗蓝无为的晚上
总算有时间和我
碰个面
去哪里都无所谓
一路慢慢走着就好
有人没人都不要紧
他们只和他们有关
就这样静静走着
在路灯冷静的眼睛里
影子一样摇摆不定
就这样一路无语
或许这样才能更清楚
感到彼此
走得累了
就找一个地方坐下
喝点东西
江河湖海
一杯杯飞渡
直喝到灯阑酒残
直到忘记了彼此
好在出门的时候
我还是跟了上来
我和我就这样摇摇晃晃
继续走着
一前一后
好像谁也不认识谁
直到我差点摔倒
我伸手扶了我一把
我没有说出感谢
因为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彼此
眼中的泪水
春天里
外面,春天一寸一寸在长
簇拥着
一点也不挤
鱼在水里,吐出一串一串词语
喋喋不休
没一句废话
孩子们坐在黑板前,加减乘除
他们一点一点在长
答案没有长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坐在影院里,我突然想到
所有人缅怀的青春
就像一匹用心编织过的锦缎
只在记忆里柔软
不加刀尺
看完电影,街灯已昏黄
妻子和我边走边谈
剧情和人物,不过是我们缅怀青春的
一些似是而非的影子
我们谈到剧中一位叫阮莞的美丽女子
她的青春止于一场意外车祸
那是婚礼前夕,她赶去听多年前
和前男友约定的一场偶像乐队的音乐会
尽管此前她的爱情被多次辜负
她的善良、宽容让人吃惊
她用死保存了青春和美丽
突然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活着,却不知道如何保存
这些易碎的东西
生日
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我们面对的
并非汹汹而来的僵尸
我们一直在和风车作战
飞廉◎岁暮望月
夏日山居
入狱兄弟接连来信,询察世事;
我叹他敲冰求火,遂寄他《老残游记》。
小院,日日读《桃花扇》,
老桐影深,家蝉声楚,似说
明三百年,隳于何人,歇于何地?
天下兴亡,关我何事!我只爱孔尚任
言说之美,扇上的声色风云。
蝉歇,偶有黄鹂、杜鹃短歌一曲;
樟门剥啄,凤仙花开三色,
邻家小女,求花染指甲;
五日后,隔墙酒叟八十大寿,为此
蒋家男婴啼哭不止。
雪夜风雨茅庐
岁暮,伍公山草木苍唐;
时事泥浊,青冥之下,
小民们劳心焦思,障深业重。
偏安在这销金窟,
我游戏琴书,写山水文章。
风雨茅庐,为我发福的中年,
遮挡乱世风雨。
大雪封门,这寒光让我惊遽,
梦寐之际,遂得见阿弥陀佛,
遂愧对东海之浮石,
愧对鲁迅剑锋黑青。
今夜,我把头埋进大雪
今夜,我的笔北风潦冽,
挑亮灯,你我且彻夜著史。
山水
这些年,我观赏过李思训的金碧山水,
“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
三峡闻猿时”的关仝山水。
游历过荆浩的太行山水,
石涛开辟的“黄山派”山水,
黄公望的富春山水,
那偏隅东南的青田山水……
追想过李成山水中的寒林平野,
他醉死在我的故乡,
不曾留下一幅真迹。
而只有凝望倪瓒的《虞山林壑图》,
我才清醒认知,事实上自己
早已死去。郭熙说王羲之喜欢鹅,
纯粹为了观察它们潇洒的脖子,
以练习执笔转腕;这些年,
我徜徉山水,
因我已来到人生中途,
深陷但丁地狱,战战慄慄,
日谨一日。整整八年,
我住进南宋马远的《凤凰山居图》,
空想着贝雅特丽齐。
到处都是魔幻现实主义,
我宁愿隐逸于空想,
“往往整个国家都靠空想才生存下去。”
凤凰山上,电塔林立,
尽管如此,它还是我的贝雅特丽齐;
尽管东西南北,几乎所有
山水都戴上了镣铐,它们也都
还是我的贝雅特丽齐。
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草书益佳,
钱塘江潮水,却让我的生活,越加混乱,
而“混乱已完成了他的杰作!”
岁暮望月
山中,这农业社会的月色,
铁锈在浙赣线上疾驰的辛亥革命的月色,
公元763年,杜甫怀里最后一文钱的月色,
颍水滨14年前,那静坐在我自行车后座的月色,
女孩踢毽子、公鸡变杜鹃、老鼠磨牙、
狸猫偷吃腊肉的月色,
西泠桥边苏小小的碑影开始结冰的月色……
昨晚梦里是刑场,醒来日记是故乡,
罗隐说,所有月色,
都是往事吐下的一地碎甘蔗,
望月则是在《古诗十九首》里照镜子。
头皮屑日夜下雪,几点寒星,萧杀而冷漠。
山叶◎雨后的乡村
一个像雨滴的声音
一个像雨滴的声音,时常在我耳畔响起
有时在清晨,有时是夜晚
当它发出“啪嗒,啪嗒”
我总以为外面在下雨
某日早晨,当我坐在台阶上看书
一位母亲写道,她很想念死去的儿子
终于在梦里见到了他,并告诉她:
“妈妈,您过多的泪水
浇灭了我好不容易点亮的灯盏。”
关于菜园的记忆
仍然是我童年时的菜园
梨花刚谢,苹果叶舒展
向阳处,几排小葱虚妄地朝着田垅长着
右侧的那棵桔子树去年就死了
枝杈干枯,没有再次长出新叶
当作围墙的刺柏长得过高,遮盖了
周围的植物,使它们极少照到阳光
一到春天转暖,父亲就会从深深的黄泥里
挖出一捆捆埋藏过冬的甘蔗
亮紫的表皮上,偶尔会爬着被吵醒的蚯蚓
我和姐姐围着父亲,等着吃
他用柴刀刨削干净的甘蔗
等到真正开春,菜园里会重新种上
一节节带芽的甘蔗
现在,菜园荒废了不少
春天刚到,亮绿的青草火速占据一角
长势凶猛,就像当初曾旺盛生长过的黄花菜
它们中的任何一棵
都有可能成为围绕整座菜园的那枝藤蔓
蚂蚁
快下雨了,两只蚂蚁在一根长水管上
往相反的方向爬行
它们急着赶回家吗,它们的家离这里远吗
家里有妈妈在等着它,还是有怀孕的妻子
要是一不小心,从水管上掉了下去
会不会有热心的同伴来帮忙
要知道,帮助——
这种最原始的表达,在世间已经越来越少
甚至连给予它命名的人类,也对此充满了蔑视
乌桕
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阴冷蔓延
冷空气昨夜降临这个小镇
轻松地驱走了暖冬
乌桕树上挂着去年的果实
隔着雾霾透出点点白光
想起幼时,妈妈曾带我和姐姐
摘过这样的种子
仿佛摘取她怀里满满的乳汁
也在这样薄暮沉沉的溪滩地里
太阳照在不远处的空旷地
如今,我每天都会对着它发一会呆
脑袋空空的。果实每天在减少
现在,我期望看到——
开春之时,它的树下遍地长满
发了芽的种子,即使没有一棵会长大
雨后的乡村
阵雨过后,蝉恢复了鸣叫
它们停在各自的树冠中
有时雨滴坠落,惊慌地飞离树梢
阳光重新打在雨后的石桥上
桥下流水因雨水的加入变得湍急,响亮
水草茂盛,溪鱼追逐
蜻蜓盘旋在高处,它们深知飞行的奥妙
也曾低飞在下雨前的乡间小路上
翅膀从不会被雨水打湿
此时,气温在下降
不断拉低落日在空中的位置
有一刻,余晖疲惫地洒向湿漉漉的山村
电线杆是大自然手中的魔法棒
它把黄昏中的村庄一个一个点亮
陈洛◎在南湖边
傍晚的南宁
大叶榕到过的地方我到过,
蓑衣和细雨到过,这里是我要抵达的故乡。
晚风阔大,暮色里的翅膀越来越暗
父亲,我坠落的一生,
曾经在流水上风光无限。
而这里,是我一路撤退的最后一点尘土。
此刻,傍晚的灯火变幻着暗影,
我每次登楼,
都是为了在老去的时光里虚设脚印。
在牯犒岭
午后的山岚迷乱
树冠静如默悼。这里
四月稀少
我们往林深处探访
步屐停处,察看干瘦的溪流
耳边有无数
灵禽,在溪石间复活
寺院止语,浓荫泽盖的蝉
练习松针织网,有不测深海
它闪耀之处,来自
这个入夏的
喜悦、急躁和死亡面孔
从制高点往北眺望,我遥见
庄子的牯犒山居
有大风掣巨鸟疾走
垂暮,我才认清自己
一只瘦小的松鼠
在松涛密集间栖隐身子
在南湖边
黄昏的光晕调低它的底色
最终落入安静生长的细叶榕上,
蝉在林子里鸣唱
它沉浸于自己的声音,多么悠远。
我在南湖边的草地上独坐
看天空和湖水。密布的麻雀
在我的宇宙里闪过一些往事
有些悲壮,有些快乐。
远处的灯和暮晚的云
擦拭我微信里陌生的温暖,
哦,这多么美好,
一如草地上升起的慢,脱离尘俗。
在舍弃的时光中
没有人领会这种虚构的专注
也没有人和我互道晚安
但神谕般寂静给我带来了久久的颤栗。
莫干山纪游
过滚石瀑,深壑险峻。那蝉声
老气横秋,是我听过最郁闷的长笛。
松月庐,重门深锁。这当年
蒋公憩居之地,夕照下,犹显苍惶。
芦花荡没有芦花。千年冷杉前,
有木牌警示:此处毛虫甚多,不可久留。
月出林低。夜宿武陵村,梦中疑与陶令对饮。
清晨,过剑池,怪石角,朝霞似美女向导。
盛夏山中,竹森,绿净,泉幽。
而我尤爱那只刚爬出草丛的花斑蜗牛。
施瑞涛◎我们常常谈起那个夜晚
那个爱我的男人,老了
隔着门缝,老花镜已经爬上了他的鼻梁
那个爱我的男人,老了
年轻时活跃的思维,偶尔也开始罢工
手臂的关节,也有了衰老的痕迹
那年他亲手种下的桂树,在寒风中
给春天写信,一年瑞雪
花朵可以开得比去年更加芬香
经过客厅,我尽量压低脚步的声音
我怕叫他一声爸爸,会使他的记忆一阵惊慌
隐遁
在黑暗的东方,学习遁术
让晚风吹不进你生锈的身体
人群或者时代中,看不见你
作为空气的象征,你把自己的
内心遮蔽,奔跑在无边的梦境
像一个旁观者,不带色彩地看着
这个世界的哭泣和喜悦
你甚至可以想象,那些被时光吞噬
的灵魂,重新揭穿五月的预言
照亮那个水稻疯长的远方
你爱这个夜晚,以一种隐秘的方式
抵达下一个春天,背对着时代
想起浙西的那片田野
命运以寂静的名义,摘满了
熟透的果实,低处的土地花开两朵
往来的木车轻歌而过
更远处,天空到处都是夕阳
一辆火化车经过,你看见一个人
躺在里面,像你,又不像你
摘苹果记
那时我还年少,易饿的夏天
想摘树上的苹果,红透了的时光
在天空下那么闪亮
未发育的身体,怎么跳也够不着
那个最红的苹果
旁边的凳子梯子,都各有他用
当然那时的我还没学会爬树的技巧
只能仰望着果实,肚子里的舞蹈
和眼神里的渴望
看着伙伴们高高地跳起,苹果在嘴里流汁
回到角落,心中的一万只蚂蚁在集合
我开始学习跳跃的本领
下弯腰,再腾空,那些不眠的夜晚
我开始学习爬树的本领
让自己成为树的一部分,只有月光知道
终于在某个雨夜,我够到了那只苹果
一只虫子从里面探出了头
晚熟的少年,已经没有力气哭泣
坐在地上,握着红色的苹果
一言不发,直到天亮
他睡着了,在远去的路上
满地的落叶飞回到从前
漫山遍野的红苹果
向他跑来,像一个个鲜艳的句号
我们常常谈起那个夜晚
风,一直朝着西边吹
我们不长的头发上
爬满蓝色的时光
月光穿着过冬的衣裳
躺在摇篮上说梦话
我们常常谈起那个夜晚
在一个城边小镇,雨后的广场上
到处都是悦耳的碰杯声
酒精让我们不说谎话
连狗吠,也能穿透黑夜
你爬上桌子,用酒瓶
当话筒,唱跑调的歌
我昂着头,脱了鞋子准备
在明天早晨出发
那棵盛开的丁香树下,就是我的家
他摇晃着身体,眼睛里的波光
越过群山,终究没有把远方看透
只有身旁的姑娘,安静的听我们废话
默默地清理时光的污垢,岁月的残渣
和扫起一地的月光
没有一朵花是干净的
首先我不是干净的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你
一颗种子,从土里逃出
谁能保证这个过程是干净的?
那些被它踩在脚下的种子
那些吸收不到阳光的种子
消失在幽暗的通道里
甚至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雨水总是偏爱柔软的一面
没有一朵花是干净的
一些花朵在开放之前就被践踏
一些花朵被蛇虫所青睐
一些花朵的身上沾满泥巴
没有一朵花是干净的
即使它朝着天空,随风摇摆
装作一副自由的样子
即使它红艳遮日,香飘四方
花托已经腐败得失去信仰
你看,只要一场小小的雨
就让它的虚伪彻底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