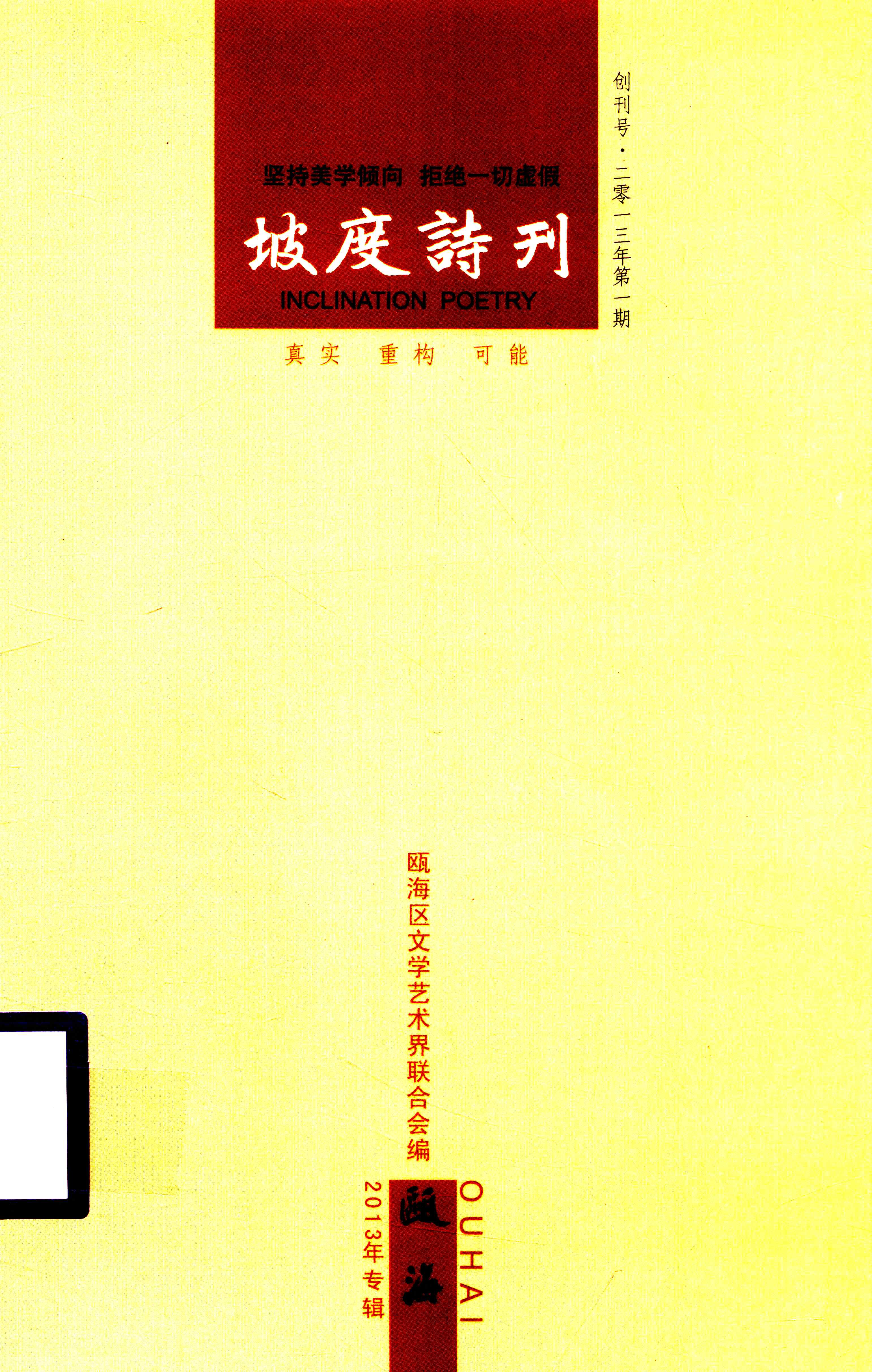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福建诗人初探之新秀篇(1)
·五线谱
张漫青吴银兰祝俊
冰儿米拉
·三行书
海约年微漾上官灿亮
●张漫青/我从来不是你
空虚不可戳穿
空虚不可戳穿
我写下这个题目
目光扫过你
扫来扫去
还没发射就丧失了耐心
你的这件衣裳像另一件
很不错的那种
衣领像衣领
袖口像袖口
纽扣像纽扣
眼睛像眼睛
伤口像伤口
唯有睡眠不可辜负
我的生活不是活着这件事
是我想象出来的其他事
那些事游荡在夜空
构成夜晚
不要取笑夜晚
虽然它黑
虽然它安静得像一块黑蛋糕
我睡着或醒着
它都那么黑
一心一意地黑
没羞没臊地黑
我就利用这些黑
来想你
有时候想得太厉害
头发飞了起来
但我看不见
我摸黑爬起
单手抓空气
几乎就能优雅地呕吐
你们爱自己
你们都爱自己
在淘宝挑选打折的名牌
在咖啡馆小心翼翼端起一杯奶茶
有时在黑暗中辨认陌生人的发型
有时瞧一瞧镜子,抚摸新鲜的眼袋
我放心,至少你们爱自己
至少会周末去健身房
至少会流泪,会吃垃圾食品
会在朋友圈晒一晒忧伤
你们计算过幸福指数
也渴望结婚生子
我放心,至少你们在春节挤上了回乡的列车
至少老父老母老泪纵横
至少肉体在床单留下皱褶
至少早餐在餐桌上,至少衰老一步一个脚印
你们要爱自己,要让我放心
别像我,我是这个星球的旅客
我的故乡在天上
我从来不是你
一个人戒了烟
那些抽烟的日子就都死了
一个人不再恋爱
那些恋爱中的日子就都死了
放心我不是你
我不去旅行
我对艳遇没有胃口
寻欢作乐不是问题
没有问题是问题
我穿过一个又一个
黑黑的夜晚
宇宙苍茫,人类匆忙
这让我感到幸福
●吴银兰/只写两首
在路上遇见我
在路上遇见我,我是平凡的路人
在工作的路上,去买菜途中
漫无目的闲散无事之人
在路上遇见的我
不可能画着精致让你喜欢的妆容
我尽力装扮成靠谱的路人甲乙丙丁
尽量不引人注意
尽量像不存在一样存在着
尽量做一个没有故事
表情冷漠内心空洞的人
在路上遇见我,你也可以撞死我
看我鲜血染在污泥上。
不停地使用
我不停不停地使用眼睛,
看尽繁花似锦,看尽人间沧桑
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不停不停地使用耳朵,
听尽花落流水,听尽你说爱我
直到什么也听不见。
我不停不停地使用思绪,
想尽悲欢离合,
想着什么也不必多想
直到什么也不想想。
我不停不停地使用时间,
不停不停地使用欢乐,
不停不停地使用悲伤,
不停不停地使用我,
直到再也一无可用,
直到一无可用。
爱
雨都停了,
门外渐显荒凉之意
远方的远方有远方
你知道,相爱像烽火硝烟
短兵相见
相爱太难,有视死如归的悲凉。
我和我
我是我的敌人
用于和自己过不去
朝自己下手
和自己反抗
人生漫漫太无聊
我必须放胆折腾自己
弄出声响
在愤怒里解体
最后一团和气,重整
彼此修炼
敷衍余生
只写两首
今天的诗,我只想写两首,
一首满是孤单,一首满是寂寞。
它们脉络清晰,长短不一。
●祝俊/大欢喜
一截枯木
一截枯木
正好容下我的身体
那是在克兰大峡谷
一个夏日的午后
溪水顺着太阳落去的方向缓缓流着
白桦树宁静而安详
对面悬崖上的积雪似乎千万年来从未变过
我躺在这截枯木里
闭上双眼
那里又是繁星满天
我感觉自己就这样飞了起来
带着人间荒地里的一缕芳香
在上天赐给我的悬棺里飞了起来
多么愉悦,没有疲倦
待繁星散尽
这悬棺便停在了悬崖上
那腹中之芳香,竟开出一朵鲜艳欲滴的花
自此,我才明白为何
在人间遇上热爱之物
心便会隐隐作痛
雪落之时
雪落之时
烟火已成灰烬
北方寒风料峭
南方枝繁叶茂
我提着松子来
我提着冰凌来
我提着轻飘飘的影子与虚幻的肉身来
两手空空
我离自己很远很远
往前一步就是悬崖
绝壁之上
影子与肉体毫无两样
绝壁之上
青松与白雪毫无两样
西硖山
那年冬天
因为怨恨自己
我便去了西硖山
那时云层凌乱
漫山落叶
我无忧伤
只有无可把握的悲哀
第二天
便下雪了
我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冬天
一个冬天里漫山都是雪
从此
我心里再也没有了怨恨
饮酒诗,致叶来
——兼致威格、颜非、舒城、海约诸友
“叶来是个坏人。”对此,我深信不疑。
说这话时,春天刚过,晚霞染透了大半个厦门城。
那时,人们还不习惯把厦门叫做厦门,叫宝岛。
海水湛蓝,螃蟹在沙滩上恣意爬行,有条种鱼,吐吐烟圈
就能让大海怀孕。有位青年,在安徽,在舒城
头枕大江大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时,天边泛起的红晕像熟透了的葡萄酒
小海约光着屁股丫子,躲进杯子里,练习游泳
他把自己的身姿,想象成他喜欢的女人。
对此,已无据可考,无究可考。
恍惚间,厦门已然成为厦门,成为最牛X的城市。
大海已不能怀孕,当年迎着浪花翻滚作乐的螃蟹
已遁化成一位发如雪,心如莲的老人。
至此,天空羞涩得再也泛不起红晕
人生已无大事,喝酒成了头等大事。
推杯间,大江大河,风生水起;
换盏时,祖国各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面对每天迅雷不及掩耳的新闻报道
世上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算作是事。
台风过境,一群在黑夜中呼啸而聚的人
一群越喝越清醒的人,一群内心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
而要求只能越来越少的人,都只能算作是鸟人。
其中最鸟的人说:“叶来是个坏人。”
说这话时,他的忧伤,仿佛不在眼中
在大江大河,在祖国各地,在人生南北。
大欢喜
我绝望。我有大欢喜。
虫子。野草。列车的轰隆声。
远方就在远方,前方指向前方,困顿而清醒。
天空阔大。河流阔大。黑夜阔大。冥思阔大。
一个思往过度的人,在时间的纱布上咯血。
咯出的不是血,是苍狗分分秒秒的巫术。
月光无尽呵,缺缺圆圆了那么多年,似乎也老了。
弹指一挥,灰还是灰,尘还是尘。
世间是精彩的。它的疏朗,忧郁和毒
同人类一样古老,而执拗。无数个绚烂躯体
不轻,不重。够轻轻的来,够去。
茫然是徒劳的,抓紧什么也是不易的。
从无关的痛痒到有序的分裂与磨损
从简单到永恒,从琐碎到坚持,从过程中分离出焦躁不安
并加以抚慰。从黑夜中移走一束光——掘墓,坐毙,洞悉。
无关生活的,都是生活。活色生香的生活。
如此,咬牙切齿也好,黯然神伤也罢
滚烫的车轮顺从不了心迹,我们顺从不了自己。
如此,我们离虚空甚远,离极致甚远,离生的悲悯与痛楚甚远。
如此,我们的血液每秒每度都在流淌,我们的骨骼在废弃的沙
砾中咯咯作响。
因此绝望。
因此赏心悦目的注视这世间万般风景。
因此我有大欢喜。
●冰儿/眼镜
豹子
每一座人迹罕至的雪山
都有一条崭新的栈道通向它
途中鲜花盛开,流水潺潺
但我们不能独自去到那里
像一把突然亮起的手电筒
现在正是它需要充电的时候
它用爪子刨开表层的积雪
抓起深处从未有人动过的雪块大口吃着
它就是依靠这些补给度过了一个个寒冬
每吃一口雪,它身上皮毛的亮度就增加一分
逐渐变成一团燃烧的火球
向雪山深处蔓延
火势越来越大,燃烧的范围越来越广
灌木在风中噼啪作响。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
也映照出豹子的灼热
它像一道闪电在冰层深处行动着
开辟着一条全新的生命通道
它不能停止,它要一直这样深挖下去
去撕咬大地深处的某种东西
蝉蜕
天色快暗下来的时候。蝉却从壳里探出了身子
亮晶晶的羽翼,照亮了周围一小片天空
透过低矮的灌木丛。能看见树叶在簌簌往下掉落
像微弱的火苗
它要就着火光穿过下面的小径
去存放身上的一件东西
那东西已经成熟。逐渐饱满
像一筐沉甸甸的谷粒
那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山谷一片通红
它的身躯也融入其中。成为一道光
能感觉到它在动。身体的一部分像潜水艇在下沉
另一部分却正在上升。仿佛长出了翅膀
在它飞翔与降落的间隙。我们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注入到了空气中
四周的物体轻微地抖动
那只蝉,一直在飞。在卸下什么
在将死亡带到另一个世界
留在视野中的图像越来越小
越来越模糊。一团黑乎乎的影子
完全消失了
月亮正缓缓从山谷升起。静谧中
很多事物也许都和它们一样
在荒野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到达了新的高度
跑道
七月。太阳用十万枚钢针抵住大地上一条跑道
它要打通那里所有的穴道
疏散身体里的火
它太烫了。它需要像一台发动机带动皮带运转那样
来消耗身上多余的热能
它不会粉碎什么也很难有新的东西产生
它宁愿被一条皮带缠得透不过气也不停止
我们围着它。绕了一圈又一圈
毫无办法。我们自己也像一只充血的动物
穿越远古的雪崩和火山来到这里
年复一年。用结满茧子的脚
磨损着这条星空下的跑道
人到中年。我们不再为旁边足球场有人进球而激动驻足
当初我们也是带着这样远征的信念
和它一起勇敢地投入这片活着的海中
没有船只。没有救生圈
只有那些波浪在大海深处呼唤着我们,推动着我们
把我们带到一个火焰之外的世界
一群叫不出名字的生物中间
去搏斗,去呼喊
眼镜
有一种人,必须带上眼镜才觉得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安全的
一层薄薄的玻璃,为他的眼球挡住了灰尘
也挡住了穿透力极强的紫外线
出于对自我的保护,他一直带着眼镜生存
带着眼镜与这个世界发生或深或浅的联系
他感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眼镜了
那些不同材质,不同造型的眼镜
给他带来的新鲜刺激
远远超过了他自身近视的需求
而眼球也早已适应了透过不同的镜片去观察不同的人
它甚至已经能敏锐地捕捉到
一朵进入视野中的油菜花在一只蜜蜂身下
摇曳舒展的幅度和频率
那时,风吹过来,田野上一片翻滚的金黄
它因为眼前突然的明亮而瞳孔放大,布满血丝
像一只愤怒的动物
好在有眼镜。将那些危险因素完整地
拦截在了玻璃内部
篮球场
一段时间的弓腰过程中,保持手的运动
等球逐渐适应了某种节奏
猛然弹跳,跃起
像豹子一样将它稳稳送进球框后
球场沸腾了。他也感到全身轻松
那颗球像他身上结出的果实。成熟很久了
有些提前发育的,迟迟等不到人来
腐烂在枝头
留下来的,继续在阳光下发酵
有时,午夜的房间里。你会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果子熟透后
浓郁的果香。仿佛来到了一座果园
你伸手摸摸这颗,捏捏那颗
因为大自然珍贵的馈赠而感动得想哭
但你忍住了。如这些果实一样
它们的一生都在黑暗内部秘密酿造着各自的汁液
现在,一颗颗带着即将被采摘的颤栗
悬挂在月光下
既无需安慰,也无需分享
●米拉/我只站在这里
舞蹈与酒
在镜子里,我完全不是我
我的双臂在空气中向上伸展,伸展
它带着我的心来到一条幽径
有人说,天下虚无度日不过如此
我冷笑。我的双脚根植于大地
世间混沌于我,只是阴谋而已
此刻我置身在这里舞蹈,月光出没
哪怕身体垂暮,心已足矣!
我不能矫情,只不过身体变得柔软
再想想,把舞蹈、情感、酒量纠缠起来
这一招一式使我想起了那年的日月
只有醉酒人在如泣如诉,而这原来便有的
音符又在催情。我不能呼吸过快
抓一杯酒,无论名字与名字之间
是否添了酒味,只要一弯又一弯的月光还在
今晚,我们便能不醉不归!
致牌桌上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相聚又别离,别离又相聚
有时默默无语,记忆长满苔藓
四个男人便用牌语交谈
甩牌的动作惊醒了夜晚潜伏的风
只有那些女人,从沉默的世界
来到更加沉默的世界
她们如往常般坐在男人们的身边
柔和的光亮里,她们看到满天繁星
她们并不安于世间的一切
她们柔美、平静、脉脉的双眸
在夜半更深闪耀出一句句诗行
除此,她们仍需改变日子的颜色
春天的蝴蝶路过她们的花园
花粉传播着男男女女天真的秘密
我们需要将纸牌再洗一洗
以便洗净我们的重逢和离别
玩具车上的男人
你穿着暗色衣服,神情淡然
夜晚的火焰穿过你的眼神
温热腐蚀着春天的痕迹
我们忘却了悲喜,相坐无言
你像婴孩一般坐在玩具车上
它支撑着大地般的身躯
深邃的眼眸,童年在默默告别
夜晚的身影还在晃动,黎明很遥远
颓墙在抗衡,我们疲于反抗
只有闪烁的灯光在念念有词
只有一只无家可归的蚊子
悄悄打出了血淋淋的饱嗝
我们在眺望。从田野望向高山
从少年望向中年,这些过往
是云烟、是火苗、是未知的冷暖
直至我们与别离相遇
我只站在这里
这个夏天,黎明托付于我
如若星星点点的梦境与你们相遇
我要带上摇曳的名字和鲜花
悄悄地邀约远方的鸽群
受惊的孩子和飞鸟并未长大
只有白云穿透永生的静寂
只有狂风在雨中颤栗
只有炊烟在吟唱童年的歌声
岩石和树枝长出厚厚的影子
把双脚扎进深沉的土地
这里有冰冷的白雪和陌生人
来自我们的世界之外
于是,我长成了一株植物
历尽悲喜也要站在这片大地上啊
黎明沉默了。这一生
不离不弃,我只站在这里
于她
沿着空旷之地,她来了
她的眼眸已植入春天的玫瑰
她的语言缠绕着永恒的黎明
这只是自身的影子或是风的故事
风起时,我们是这般诧异
穿过静默的土壤,我们彼此面对
她的容颜仿佛与秘密一致
对她而言,时间只是目光的相遇
太明净的季节带来了流水淙淙
生命倾泻。我们朝着一切欢乐走去
如果深情的歌者还在海边歌唱
黄昏看上去,何止只是一场夜色
她的一生被迷雾织成森林
这是隐秘的风景,只有风沿路奔跑
仿佛一种力量从苍穹迢迢而来
若不是如此,我们将一无所知
●海约/隐秘世界
在鼓浪屿。雷雨如期而至
在鼓浪屿
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
雷雨如期而至。我们却希望
树木能够
捉住一些影子。甚至
于尘嚣之上
在静寂中逆光而行。
以至,在节节败退的海浪声中
仿佛听见一曲古琴音就像
六月未结的果
落入大地。
而逆光而行的人
一直都在自己的影子里
寻找光
以及,闪电。
从溪流生出的小树
这是在七月
风就要压垮额头那滴汗珠。
从溪流生出的小树,弱不禁风的样子
有那么一阵,我以为
它会被连根拔起刮跑在奔波的人群
最后被忙碌的表象所吞没
而它没有。
这从溪流生出的小树
安静,逆着风生长。哪怕在七月
风的温度
高出溪面许多
水流一直被疼痛的尖叫覆盖
生活因疲惫,有些难堪
而我还是看见了那些树根紧抓着泥巴
抗拒着死亡。
我们自始至终奔波在死亡的漩涡
欢愉地拨开双手
摸向光处。
在虚度中消耗自我
事物间的更替
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面对每天周而复始的白与黑
不再悲喜。一天之中
从阳光明媚
到乌云笼罩甚至暴雨倾泻
更像是一念之间。
何必奢望于天空会一直晴朗
同样对这些潦草的生活亦不必绝望
没有人会一直活着
没有人会一直难堪地活着。
乌云终会散去
雨会停
黑夜会按时到来
那时,我们守着一个空洞的肉体
虚度自我消耗自我
直到虚无。
生病记
咳嗽像野兽
奔突而来,占住山头
而嘴里叼着的烟,看上去很像
一株枯木
它燃烧的姿势
隐秘,以至你未能发现
浓烟裹着的身体
渗出的忧伤
是一截有着足够温度的时光
摇晃着这铁制的床
恍若人世间那些转瞬即逝
的事物。
为了维持一种平衡
我用冰凉的左手握住持续高烧的右手
让它们相互抵抗
彼此相爱。
隐秘世界
视野之外,万物生长
也有草缓缓枯死
春风吹又生。
所谓的平衡
充满生机以及死亡,甚至
遍布未知。
因此,我们开始
相信根部以下深藏着一个隐秘世界
那些我们未曾到达的
黑暗,可能
一直都在放射光芒
那些我们不曾触及的生活
宽阔,并充满了善意
而我们,如此
希望能够打开那扇隐秘之门
就像羊群跨过栅栏
●年微漾/江湖曲
在潮汕平原
多么辽阔,田野、江面和初夏
构成了故土的全部
不会有革命,来到这里惊扰她
也不会有异乡
反驳她的柔美。春夏之交适合建造
修筑的村庄
都纵横分明,在山海之间。浪花抖动和声
与朝阳相和
所有草木用尽全力
往四月里绿。她用温水和茶叶
展开听觉
用冷却下来的苦涩,启示人们
重新擦亮修辞
在这部皇皇的家史中,万物各有所指
遗憾我不被允许
有过多的时间,用来相聚和别离
九百里韩江昼夜流淌
九百里韩江昼夜流淌。不可以太急
太急就会骤变成行军,士兵背起了南宋
壮烈地沉入元朝。亦不能太缓
祭文一日未抵,鳄鱼就继续趴在
头盖骨上,啃食艳阳。太清就柔弱无骨
柳枝取代木棉,太浊就穷凶极恶
广济门竹木门上水门下水门,通通形同虚设
祖先的英灵,因为后裔们四处迁徙
要遭受第二次车裂之苦。它应像织布机
舒缓地流,有节奏地流,带着木头的关节
在流,也暗藏金属的质地在流。它不止
流向反叛和抵抗,也流向回归与顺从
它把雨季织成一段一段的江面,把过客
认作满脸泪水的义子。我曾在江边
入住的三个昼夜,令人记忆深刻,令我拒绝
更多的人,把此间当成故乡。我像个囚徒
对它怀有专制的迷恋,我的爱就是破坏
地图上虚无的祖国,道路旁错误的远方
还有瓜架间多余的花海,只留下方言
给故交写信,劝他们回家,在某个雨天
九百里韩江昼夜流淌,水温适中而生计简朴
我住在江边,易生荣归故里的满足
女人忙于生子,男人要去市集,他等待天晴
如同此刻孩子在摇篮里等待一个姓名
在普宁
南嫁的燕子,每经过一片水域
就要换掉一件倒影,整个天地
都是她的裁缝铺。荔枝木落籍他乡
最终穿上一身灰烬,在风中跳皂隶之舞
长者从篝火中,摸出一袭带褶皱的年纪
死后成为山神,城隍庇佑过王师
御赐黄袍加身。他们的父母
久居于乡下,盖着一床比阴天
更粗厚的姓氏,那姓氏就是潮汐
月亮兜售的绸缎,被用于缝制
国家的补丁,不同的故乡骨肉分离
彼时尚在襁褓。洪阳镇的月光
此刻像兴化湾上空的月光的谐音
兴化湾上空的月光,此刻悲悯地
照着那些被掏空了声音的钟
江湖曲
闹钟又来到某个深刻的时辰
一杯开水,在桌面
自然冷却。窗外,是雨后初晴
春末立夏
你所深爱的每一天,其实都是理所当然
都是公车卸下道路
回归湖边的车站。都是昨夜
单曲循环的音乐
到了清晨,还在继续吟唱
五月开满了蓝花楹
透过玻璃
看到它们,就像在一篇散文里
读出蓝色的字句
花开时是爱人,花落后
就成了药方,在寻找相适的病症
寻找旧年
草书上的国家,处处飘曳着
小楷般的旗纛
我的兄弟何其年少,他的亡妻正当芳龄
江湖儿女,本应垂老于江湖
愿流水舒缓
倒影静止,时光赐予他们不失体面的归降
潮汕之秋
乡间的音乐柔软,篱笆、稻穗
和八月,都含着乐句
你在一辆单车上,要去到江边
那里正在下雨
雨声像沙子铺满了河床
你抚摸它们,如同抚摸一台
童年的手风琴
琴面落满灰尘,弹奏时会留下
幼稚的签名
我突然感到窒息,不敢用力呼吸
说不清是因为爱你
还是爱这平静的流逝
时间在莫比乌斯带上,缓缓移动
去年的秋天,眼看就要成为
今年的秋天
●上官灿亮/三角梅
要藏,干脆就一头扎进一滴雨里去
从此,再也没有一滴雨可以打击我,再也没有人
妄想读到一首无字之诗
那一束束雷电
狞狰地闪过
以及雷电下面人世间丑陋的面目
我从此将不再看到
我不爱的人,我也不再惦记
再也不
我隐藏在一滴雨里
像一个浑沌的胎儿
沁心的凉意养育着我
我坚决不再长大
终生随着这滴雨
与更多的雨汇合
流经小溪或者下水道,拐弯抹角
终归回到大海
身上粘染了阳光的人
青筋暗下去。几粒羞怯的痘痘
像小星星罗列其间,这两条
硕壮而修长的大腿,手臂以及长脖子
因这个季节猛烈的气候而散发出
阳光的迷人的味道
又黑又肥
像是非洲的母亲
而阳光无法照到的部位
隶属于私人领地
因她的极力守护至今仍然
可以用冰清玉洁来形容
三角梅
今天,我看见一株三角梅
开了整整一树的花
昨天还是浑身的刺
这也太奢侈了,大手大脚地
开出这么多花
我该说什么好呢?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含刺的花
就像
就像后院那个冷漠的人
忽然咧开嘴,大声笑了出来
就像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从来就不曾这么美好过
喉咙痛是不是叫咽喉肿痛
水已泼出去,两粒
胶囊就免了吧
石膏凉了
我得罪过一些人。喉咙的痛
已渐入佳境,仿佛就
从未痛过
我羞耻于这难过的一天
发炎是这么一回事
如此迅速地康复
又是另一回事
无题
台风过境,将雨
一路的蚂蚁列队,加班
筑巢,搬家
这焦急的生活
这水深火热的物种
冒似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
我将带上丰厚的面包屑
赴宴它们苦逼的
乔迁之喜
·五线谱
张漫青吴银兰祝俊
冰儿米拉
·三行书
海约年微漾上官灿亮
●张漫青/我从来不是你
空虚不可戳穿
空虚不可戳穿
我写下这个题目
目光扫过你
扫来扫去
还没发射就丧失了耐心
你的这件衣裳像另一件
很不错的那种
衣领像衣领
袖口像袖口
纽扣像纽扣
眼睛像眼睛
伤口像伤口
唯有睡眠不可辜负
我的生活不是活着这件事
是我想象出来的其他事
那些事游荡在夜空
构成夜晚
不要取笑夜晚
虽然它黑
虽然它安静得像一块黑蛋糕
我睡着或醒着
它都那么黑
一心一意地黑
没羞没臊地黑
我就利用这些黑
来想你
有时候想得太厉害
头发飞了起来
但我看不见
我摸黑爬起
单手抓空气
几乎就能优雅地呕吐
你们爱自己
你们都爱自己
在淘宝挑选打折的名牌
在咖啡馆小心翼翼端起一杯奶茶
有时在黑暗中辨认陌生人的发型
有时瞧一瞧镜子,抚摸新鲜的眼袋
我放心,至少你们爱自己
至少会周末去健身房
至少会流泪,会吃垃圾食品
会在朋友圈晒一晒忧伤
你们计算过幸福指数
也渴望结婚生子
我放心,至少你们在春节挤上了回乡的列车
至少老父老母老泪纵横
至少肉体在床单留下皱褶
至少早餐在餐桌上,至少衰老一步一个脚印
你们要爱自己,要让我放心
别像我,我是这个星球的旅客
我的故乡在天上
我从来不是你
一个人戒了烟
那些抽烟的日子就都死了
一个人不再恋爱
那些恋爱中的日子就都死了
放心我不是你
我不去旅行
我对艳遇没有胃口
寻欢作乐不是问题
没有问题是问题
我穿过一个又一个
黑黑的夜晚
宇宙苍茫,人类匆忙
这让我感到幸福
●吴银兰/只写两首
在路上遇见我
在路上遇见我,我是平凡的路人
在工作的路上,去买菜途中
漫无目的闲散无事之人
在路上遇见的我
不可能画着精致让你喜欢的妆容
我尽力装扮成靠谱的路人甲乙丙丁
尽量不引人注意
尽量像不存在一样存在着
尽量做一个没有故事
表情冷漠内心空洞的人
在路上遇见我,你也可以撞死我
看我鲜血染在污泥上。
不停地使用
我不停不停地使用眼睛,
看尽繁花似锦,看尽人间沧桑
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不停不停地使用耳朵,
听尽花落流水,听尽你说爱我
直到什么也听不见。
我不停不停地使用思绪,
想尽悲欢离合,
想着什么也不必多想
直到什么也不想想。
我不停不停地使用时间,
不停不停地使用欢乐,
不停不停地使用悲伤,
不停不停地使用我,
直到再也一无可用,
直到一无可用。
爱
雨都停了,
门外渐显荒凉之意
远方的远方有远方
你知道,相爱像烽火硝烟
短兵相见
相爱太难,有视死如归的悲凉。
我和我
我是我的敌人
用于和自己过不去
朝自己下手
和自己反抗
人生漫漫太无聊
我必须放胆折腾自己
弄出声响
在愤怒里解体
最后一团和气,重整
彼此修炼
敷衍余生
只写两首
今天的诗,我只想写两首,
一首满是孤单,一首满是寂寞。
它们脉络清晰,长短不一。
●祝俊/大欢喜
一截枯木
一截枯木
正好容下我的身体
那是在克兰大峡谷
一个夏日的午后
溪水顺着太阳落去的方向缓缓流着
白桦树宁静而安详
对面悬崖上的积雪似乎千万年来从未变过
我躺在这截枯木里
闭上双眼
那里又是繁星满天
我感觉自己就这样飞了起来
带着人间荒地里的一缕芳香
在上天赐给我的悬棺里飞了起来
多么愉悦,没有疲倦
待繁星散尽
这悬棺便停在了悬崖上
那腹中之芳香,竟开出一朵鲜艳欲滴的花
自此,我才明白为何
在人间遇上热爱之物
心便会隐隐作痛
雪落之时
雪落之时
烟火已成灰烬
北方寒风料峭
南方枝繁叶茂
我提着松子来
我提着冰凌来
我提着轻飘飘的影子与虚幻的肉身来
两手空空
我离自己很远很远
往前一步就是悬崖
绝壁之上
影子与肉体毫无两样
绝壁之上
青松与白雪毫无两样
西硖山
那年冬天
因为怨恨自己
我便去了西硖山
那时云层凌乱
漫山落叶
我无忧伤
只有无可把握的悲哀
第二天
便下雪了
我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冬天
一个冬天里漫山都是雪
从此
我心里再也没有了怨恨
饮酒诗,致叶来
——兼致威格、颜非、舒城、海约诸友
“叶来是个坏人。”对此,我深信不疑。
说这话时,春天刚过,晚霞染透了大半个厦门城。
那时,人们还不习惯把厦门叫做厦门,叫宝岛。
海水湛蓝,螃蟹在沙滩上恣意爬行,有条种鱼,吐吐烟圈
就能让大海怀孕。有位青年,在安徽,在舒城
头枕大江大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时,天边泛起的红晕像熟透了的葡萄酒
小海约光着屁股丫子,躲进杯子里,练习游泳
他把自己的身姿,想象成他喜欢的女人。
对此,已无据可考,无究可考。
恍惚间,厦门已然成为厦门,成为最牛X的城市。
大海已不能怀孕,当年迎着浪花翻滚作乐的螃蟹
已遁化成一位发如雪,心如莲的老人。
至此,天空羞涩得再也泛不起红晕
人生已无大事,喝酒成了头等大事。
推杯间,大江大河,风生水起;
换盏时,祖国各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面对每天迅雷不及掩耳的新闻报道
世上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算作是事。
台风过境,一群在黑夜中呼啸而聚的人
一群越喝越清醒的人,一群内心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
而要求只能越来越少的人,都只能算作是鸟人。
其中最鸟的人说:“叶来是个坏人。”
说这话时,他的忧伤,仿佛不在眼中
在大江大河,在祖国各地,在人生南北。
大欢喜
我绝望。我有大欢喜。
虫子。野草。列车的轰隆声。
远方就在远方,前方指向前方,困顿而清醒。
天空阔大。河流阔大。黑夜阔大。冥思阔大。
一个思往过度的人,在时间的纱布上咯血。
咯出的不是血,是苍狗分分秒秒的巫术。
月光无尽呵,缺缺圆圆了那么多年,似乎也老了。
弹指一挥,灰还是灰,尘还是尘。
世间是精彩的。它的疏朗,忧郁和毒
同人类一样古老,而执拗。无数个绚烂躯体
不轻,不重。够轻轻的来,够去。
茫然是徒劳的,抓紧什么也是不易的。
从无关的痛痒到有序的分裂与磨损
从简单到永恒,从琐碎到坚持,从过程中分离出焦躁不安
并加以抚慰。从黑夜中移走一束光——掘墓,坐毙,洞悉。
无关生活的,都是生活。活色生香的生活。
如此,咬牙切齿也好,黯然神伤也罢
滚烫的车轮顺从不了心迹,我们顺从不了自己。
如此,我们离虚空甚远,离极致甚远,离生的悲悯与痛楚甚远。
如此,我们的血液每秒每度都在流淌,我们的骨骼在废弃的沙
砾中咯咯作响。
因此绝望。
因此赏心悦目的注视这世间万般风景。
因此我有大欢喜。
●冰儿/眼镜
豹子
每一座人迹罕至的雪山
都有一条崭新的栈道通向它
途中鲜花盛开,流水潺潺
但我们不能独自去到那里
像一把突然亮起的手电筒
现在正是它需要充电的时候
它用爪子刨开表层的积雪
抓起深处从未有人动过的雪块大口吃着
它就是依靠这些补给度过了一个个寒冬
每吃一口雪,它身上皮毛的亮度就增加一分
逐渐变成一团燃烧的火球
向雪山深处蔓延
火势越来越大,燃烧的范围越来越广
灌木在风中噼啪作响。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
也映照出豹子的灼热
它像一道闪电在冰层深处行动着
开辟着一条全新的生命通道
它不能停止,它要一直这样深挖下去
去撕咬大地深处的某种东西
蝉蜕
天色快暗下来的时候。蝉却从壳里探出了身子
亮晶晶的羽翼,照亮了周围一小片天空
透过低矮的灌木丛。能看见树叶在簌簌往下掉落
像微弱的火苗
它要就着火光穿过下面的小径
去存放身上的一件东西
那东西已经成熟。逐渐饱满
像一筐沉甸甸的谷粒
那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山谷一片通红
它的身躯也融入其中。成为一道光
能感觉到它在动。身体的一部分像潜水艇在下沉
另一部分却正在上升。仿佛长出了翅膀
在它飞翔与降落的间隙。我们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注入到了空气中
四周的物体轻微地抖动
那只蝉,一直在飞。在卸下什么
在将死亡带到另一个世界
留在视野中的图像越来越小
越来越模糊。一团黑乎乎的影子
完全消失了
月亮正缓缓从山谷升起。静谧中
很多事物也许都和它们一样
在荒野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到达了新的高度
跑道
七月。太阳用十万枚钢针抵住大地上一条跑道
它要打通那里所有的穴道
疏散身体里的火
它太烫了。它需要像一台发动机带动皮带运转那样
来消耗身上多余的热能
它不会粉碎什么也很难有新的东西产生
它宁愿被一条皮带缠得透不过气也不停止
我们围着它。绕了一圈又一圈
毫无办法。我们自己也像一只充血的动物
穿越远古的雪崩和火山来到这里
年复一年。用结满茧子的脚
磨损着这条星空下的跑道
人到中年。我们不再为旁边足球场有人进球而激动驻足
当初我们也是带着这样远征的信念
和它一起勇敢地投入这片活着的海中
没有船只。没有救生圈
只有那些波浪在大海深处呼唤着我们,推动着我们
把我们带到一个火焰之外的世界
一群叫不出名字的生物中间
去搏斗,去呼喊
眼镜
有一种人,必须带上眼镜才觉得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安全的
一层薄薄的玻璃,为他的眼球挡住了灰尘
也挡住了穿透力极强的紫外线
出于对自我的保护,他一直带着眼镜生存
带着眼镜与这个世界发生或深或浅的联系
他感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眼镜了
那些不同材质,不同造型的眼镜
给他带来的新鲜刺激
远远超过了他自身近视的需求
而眼球也早已适应了透过不同的镜片去观察不同的人
它甚至已经能敏锐地捕捉到
一朵进入视野中的油菜花在一只蜜蜂身下
摇曳舒展的幅度和频率
那时,风吹过来,田野上一片翻滚的金黄
它因为眼前突然的明亮而瞳孔放大,布满血丝
像一只愤怒的动物
好在有眼镜。将那些危险因素完整地
拦截在了玻璃内部
篮球场
一段时间的弓腰过程中,保持手的运动
等球逐渐适应了某种节奏
猛然弹跳,跃起
像豹子一样将它稳稳送进球框后
球场沸腾了。他也感到全身轻松
那颗球像他身上结出的果实。成熟很久了
有些提前发育的,迟迟等不到人来
腐烂在枝头
留下来的,继续在阳光下发酵
有时,午夜的房间里。你会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果子熟透后
浓郁的果香。仿佛来到了一座果园
你伸手摸摸这颗,捏捏那颗
因为大自然珍贵的馈赠而感动得想哭
但你忍住了。如这些果实一样
它们的一生都在黑暗内部秘密酿造着各自的汁液
现在,一颗颗带着即将被采摘的颤栗
悬挂在月光下
既无需安慰,也无需分享
●米拉/我只站在这里
舞蹈与酒
在镜子里,我完全不是我
我的双臂在空气中向上伸展,伸展
它带着我的心来到一条幽径
有人说,天下虚无度日不过如此
我冷笑。我的双脚根植于大地
世间混沌于我,只是阴谋而已
此刻我置身在这里舞蹈,月光出没
哪怕身体垂暮,心已足矣!
我不能矫情,只不过身体变得柔软
再想想,把舞蹈、情感、酒量纠缠起来
这一招一式使我想起了那年的日月
只有醉酒人在如泣如诉,而这原来便有的
音符又在催情。我不能呼吸过快
抓一杯酒,无论名字与名字之间
是否添了酒味,只要一弯又一弯的月光还在
今晚,我们便能不醉不归!
致牌桌上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相聚又别离,别离又相聚
有时默默无语,记忆长满苔藓
四个男人便用牌语交谈
甩牌的动作惊醒了夜晚潜伏的风
只有那些女人,从沉默的世界
来到更加沉默的世界
她们如往常般坐在男人们的身边
柔和的光亮里,她们看到满天繁星
她们并不安于世间的一切
她们柔美、平静、脉脉的双眸
在夜半更深闪耀出一句句诗行
除此,她们仍需改变日子的颜色
春天的蝴蝶路过她们的花园
花粉传播着男男女女天真的秘密
我们需要将纸牌再洗一洗
以便洗净我们的重逢和离别
玩具车上的男人
你穿着暗色衣服,神情淡然
夜晚的火焰穿过你的眼神
温热腐蚀着春天的痕迹
我们忘却了悲喜,相坐无言
你像婴孩一般坐在玩具车上
它支撑着大地般的身躯
深邃的眼眸,童年在默默告别
夜晚的身影还在晃动,黎明很遥远
颓墙在抗衡,我们疲于反抗
只有闪烁的灯光在念念有词
只有一只无家可归的蚊子
悄悄打出了血淋淋的饱嗝
我们在眺望。从田野望向高山
从少年望向中年,这些过往
是云烟、是火苗、是未知的冷暖
直至我们与别离相遇
我只站在这里
这个夏天,黎明托付于我
如若星星点点的梦境与你们相遇
我要带上摇曳的名字和鲜花
悄悄地邀约远方的鸽群
受惊的孩子和飞鸟并未长大
只有白云穿透永生的静寂
只有狂风在雨中颤栗
只有炊烟在吟唱童年的歌声
岩石和树枝长出厚厚的影子
把双脚扎进深沉的土地
这里有冰冷的白雪和陌生人
来自我们的世界之外
于是,我长成了一株植物
历尽悲喜也要站在这片大地上啊
黎明沉默了。这一生
不离不弃,我只站在这里
于她
沿着空旷之地,她来了
她的眼眸已植入春天的玫瑰
她的语言缠绕着永恒的黎明
这只是自身的影子或是风的故事
风起时,我们是这般诧异
穿过静默的土壤,我们彼此面对
她的容颜仿佛与秘密一致
对她而言,时间只是目光的相遇
太明净的季节带来了流水淙淙
生命倾泻。我们朝着一切欢乐走去
如果深情的歌者还在海边歌唱
黄昏看上去,何止只是一场夜色
她的一生被迷雾织成森林
这是隐秘的风景,只有风沿路奔跑
仿佛一种力量从苍穹迢迢而来
若不是如此,我们将一无所知
●海约/隐秘世界
在鼓浪屿。雷雨如期而至
在鼓浪屿
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
雷雨如期而至。我们却希望
树木能够
捉住一些影子。甚至
于尘嚣之上
在静寂中逆光而行。
以至,在节节败退的海浪声中
仿佛听见一曲古琴音就像
六月未结的果
落入大地。
而逆光而行的人
一直都在自己的影子里
寻找光
以及,闪电。
从溪流生出的小树
这是在七月
风就要压垮额头那滴汗珠。
从溪流生出的小树,弱不禁风的样子
有那么一阵,我以为
它会被连根拔起刮跑在奔波的人群
最后被忙碌的表象所吞没
而它没有。
这从溪流生出的小树
安静,逆着风生长。哪怕在七月
风的温度
高出溪面许多
水流一直被疼痛的尖叫覆盖
生活因疲惫,有些难堪
而我还是看见了那些树根紧抓着泥巴
抗拒着死亡。
我们自始至终奔波在死亡的漩涡
欢愉地拨开双手
摸向光处。
在虚度中消耗自我
事物间的更替
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面对每天周而复始的白与黑
不再悲喜。一天之中
从阳光明媚
到乌云笼罩甚至暴雨倾泻
更像是一念之间。
何必奢望于天空会一直晴朗
同样对这些潦草的生活亦不必绝望
没有人会一直活着
没有人会一直难堪地活着。
乌云终会散去
雨会停
黑夜会按时到来
那时,我们守着一个空洞的肉体
虚度自我消耗自我
直到虚无。
生病记
咳嗽像野兽
奔突而来,占住山头
而嘴里叼着的烟,看上去很像
一株枯木
它燃烧的姿势
隐秘,以至你未能发现
浓烟裹着的身体
渗出的忧伤
是一截有着足够温度的时光
摇晃着这铁制的床
恍若人世间那些转瞬即逝
的事物。
为了维持一种平衡
我用冰凉的左手握住持续高烧的右手
让它们相互抵抗
彼此相爱。
隐秘世界
视野之外,万物生长
也有草缓缓枯死
春风吹又生。
所谓的平衡
充满生机以及死亡,甚至
遍布未知。
因此,我们开始
相信根部以下深藏着一个隐秘世界
那些我们未曾到达的
黑暗,可能
一直都在放射光芒
那些我们不曾触及的生活
宽阔,并充满了善意
而我们,如此
希望能够打开那扇隐秘之门
就像羊群跨过栅栏
●年微漾/江湖曲
在潮汕平原
多么辽阔,田野、江面和初夏
构成了故土的全部
不会有革命,来到这里惊扰她
也不会有异乡
反驳她的柔美。春夏之交适合建造
修筑的村庄
都纵横分明,在山海之间。浪花抖动和声
与朝阳相和
所有草木用尽全力
往四月里绿。她用温水和茶叶
展开听觉
用冷却下来的苦涩,启示人们
重新擦亮修辞
在这部皇皇的家史中,万物各有所指
遗憾我不被允许
有过多的时间,用来相聚和别离
九百里韩江昼夜流淌
九百里韩江昼夜流淌。不可以太急
太急就会骤变成行军,士兵背起了南宋
壮烈地沉入元朝。亦不能太缓
祭文一日未抵,鳄鱼就继续趴在
头盖骨上,啃食艳阳。太清就柔弱无骨
柳枝取代木棉,太浊就穷凶极恶
广济门竹木门上水门下水门,通通形同虚设
祖先的英灵,因为后裔们四处迁徙
要遭受第二次车裂之苦。它应像织布机
舒缓地流,有节奏地流,带着木头的关节
在流,也暗藏金属的质地在流。它不止
流向反叛和抵抗,也流向回归与顺从
它把雨季织成一段一段的江面,把过客
认作满脸泪水的义子。我曾在江边
入住的三个昼夜,令人记忆深刻,令我拒绝
更多的人,把此间当成故乡。我像个囚徒
对它怀有专制的迷恋,我的爱就是破坏
地图上虚无的祖国,道路旁错误的远方
还有瓜架间多余的花海,只留下方言
给故交写信,劝他们回家,在某个雨天
九百里韩江昼夜流淌,水温适中而生计简朴
我住在江边,易生荣归故里的满足
女人忙于生子,男人要去市集,他等待天晴
如同此刻孩子在摇篮里等待一个姓名
在普宁
南嫁的燕子,每经过一片水域
就要换掉一件倒影,整个天地
都是她的裁缝铺。荔枝木落籍他乡
最终穿上一身灰烬,在风中跳皂隶之舞
长者从篝火中,摸出一袭带褶皱的年纪
死后成为山神,城隍庇佑过王师
御赐黄袍加身。他们的父母
久居于乡下,盖着一床比阴天
更粗厚的姓氏,那姓氏就是潮汐
月亮兜售的绸缎,被用于缝制
国家的补丁,不同的故乡骨肉分离
彼时尚在襁褓。洪阳镇的月光
此刻像兴化湾上空的月光的谐音
兴化湾上空的月光,此刻悲悯地
照着那些被掏空了声音的钟
江湖曲
闹钟又来到某个深刻的时辰
一杯开水,在桌面
自然冷却。窗外,是雨后初晴
春末立夏
你所深爱的每一天,其实都是理所当然
都是公车卸下道路
回归湖边的车站。都是昨夜
单曲循环的音乐
到了清晨,还在继续吟唱
五月开满了蓝花楹
透过玻璃
看到它们,就像在一篇散文里
读出蓝色的字句
花开时是爱人,花落后
就成了药方,在寻找相适的病症
寻找旧年
草书上的国家,处处飘曳着
小楷般的旗纛
我的兄弟何其年少,他的亡妻正当芳龄
江湖儿女,本应垂老于江湖
愿流水舒缓
倒影静止,时光赐予他们不失体面的归降
潮汕之秋
乡间的音乐柔软,篱笆、稻穗
和八月,都含着乐句
你在一辆单车上,要去到江边
那里正在下雨
雨声像沙子铺满了河床
你抚摸它们,如同抚摸一台
童年的手风琴
琴面落满灰尘,弹奏时会留下
幼稚的签名
我突然感到窒息,不敢用力呼吸
说不清是因为爱你
还是爱这平静的流逝
时间在莫比乌斯带上,缓缓移动
去年的秋天,眼看就要成为
今年的秋天
●上官灿亮/三角梅
要藏,干脆就一头扎进一滴雨里去
从此,再也没有一滴雨可以打击我,再也没有人
妄想读到一首无字之诗
那一束束雷电
狞狰地闪过
以及雷电下面人世间丑陋的面目
我从此将不再看到
我不爱的人,我也不再惦记
再也不
我隐藏在一滴雨里
像一个浑沌的胎儿
沁心的凉意养育着我
我坚决不再长大
终生随着这滴雨
与更多的雨汇合
流经小溪或者下水道,拐弯抹角
终归回到大海
身上粘染了阳光的人
青筋暗下去。几粒羞怯的痘痘
像小星星罗列其间,这两条
硕壮而修长的大腿,手臂以及长脖子
因这个季节猛烈的气候而散发出
阳光的迷人的味道
又黑又肥
像是非洲的母亲
而阳光无法照到的部位
隶属于私人领地
因她的极力守护至今仍然
可以用冰清玉洁来形容
三角梅
今天,我看见一株三角梅
开了整整一树的花
昨天还是浑身的刺
这也太奢侈了,大手大脚地
开出这么多花
我该说什么好呢?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含刺的花
就像
就像后院那个冷漠的人
忽然咧开嘴,大声笑了出来
就像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从来就不曾这么美好过
喉咙痛是不是叫咽喉肿痛
水已泼出去,两粒
胶囊就免了吧
石膏凉了
我得罪过一些人。喉咙的痛
已渐入佳境,仿佛就
从未痛过
我羞耻于这难过的一天
发炎是这么一回事
如此迅速地康复
又是另一回事
无题
台风过境,将雨
一路的蚂蚁列队,加班
筑巢,搬家
这焦急的生活
这水深火热的物种
冒似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
我将带上丰厚的面包屑
赴宴它们苦逼的
乔迁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