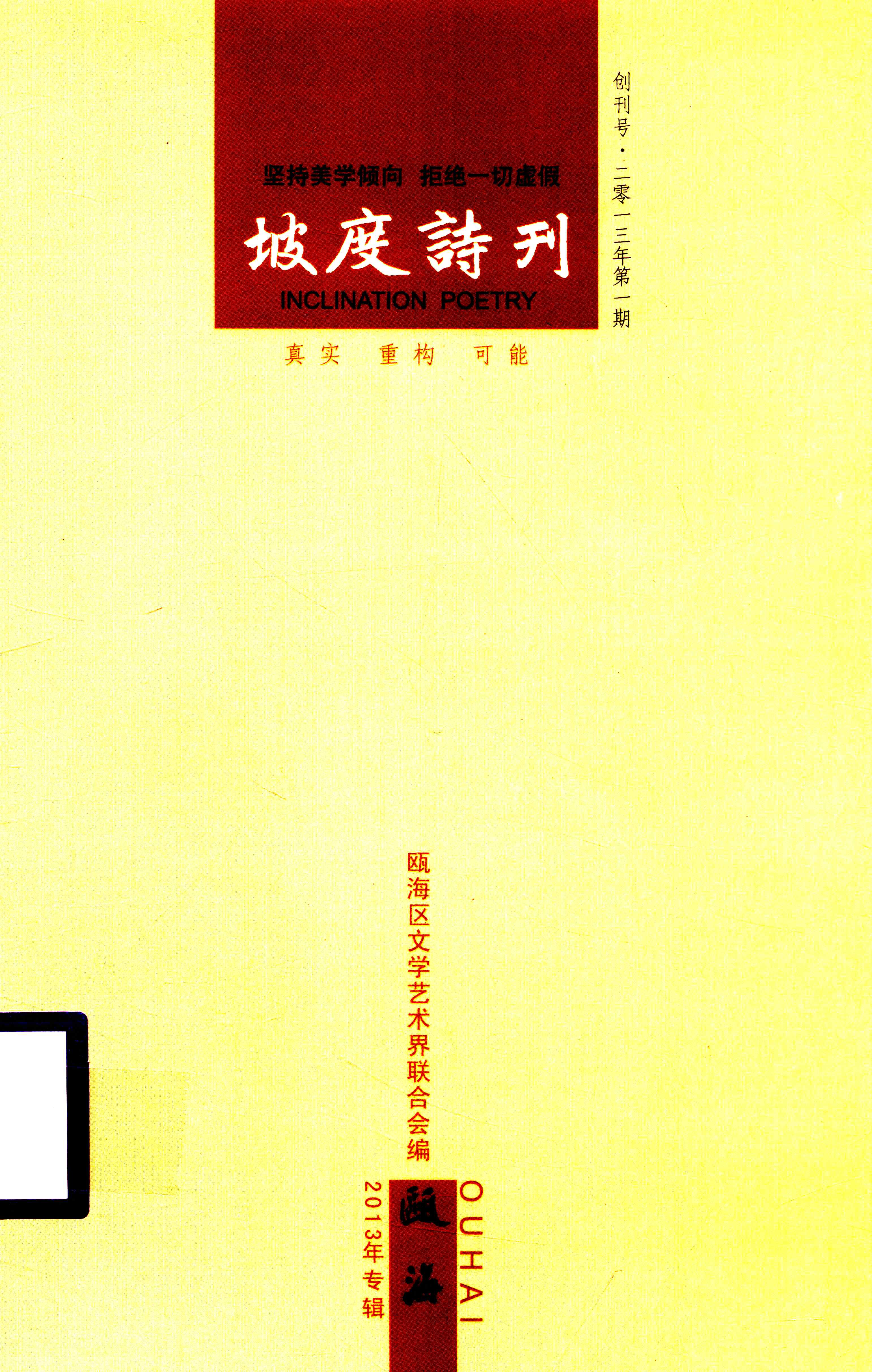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我知道慕白是一个诗人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情了。2006年,《温州文学》作了“诗歌专号”,邀我作一篇概观性质的文章。这次的“诗歌专号”里有慕白的诗歌,所以有机会第一次读到了慕白的诗歌。彼时,我对慕白的“诗歌是一个人内心的河流”之说很认同,所以特地阐释了“河流”的启示性和“河流”的传统。但那时,我和诗人还未曾谋面。
“慕白”的名字似乎是被人多次谈及,诗人自己也在那篇“跋”文《慕白,慕不白,白慕》中特地做了坦白:先从儿子小学语文书上看到大诗人李白的介绍——继而想到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宏论——又加上对自己的牙齿黑的不满,于是“一举三得”的大名“慕白”,“开张营业”。诗人对自己笔名的“散讲”,很是“油滑”,不过“文坛登龙术”该是有点暗示。就像想上“星光大道”的乡村艺人都希望有个“毕姥爷”一样,“乡村”诗人,我想,也希望有个“白姥爷”作为自己诗歌道路上的“引路人”。何况慕白和李白一样,也是位“经常走在路上,四处流觞”、“甚嚣尘上,倦于世网尘劳”的诗人。
不过,对于“乡村”诗人来说,“白姥爷”这个巨大的“引路人”留下的最激励的诗句可能还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慕白虽自称是浙南文成的“土著”,也表白文成是他“全部的故乡”,
“是一个理想的、田园的、诗意的栖息地”,但“田园”和“现代”是不合的,做一个“世界性的人”强烈想法,必定会让诗人发现这理想的故乡是一个“闭塞的地方”,所以他必定是要做一个“在路上”的“行者”。诗人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在路上》和《行者》,就是要说明:一个“世界性的人”,必定不安于一隅。“出门”的欲望一直轰响在慕白内心。需要说明的是,诗人的故乡文成就已经有一位出门者刘基。这位明代的大人物给诗人的故乡永久性地留下的名字。我想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慕白,口中说出“我是文成的土著”中,当然也有一份来自“刘文成公”的激励。
一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慕白诗歌中的“包山底”,甚至有不少的诗评家将“包山底”看成是慕白诗歌中的“关键词”。正如上文所说,慕白需要“出门”,从包山底走出去,是慕白写作的一个最大动机。但“出门”需要一个“故园”作为出发地,在我看来,慕白所有的“包山底”的诗句,就是建筑一个“故园”。这个“故园”可以保证他在行走的途中,一旦遇到挫折和伤害,可以给予诗人一些必要的安慰和基于内心的保护。慕白写包山底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地域诗人”,慕白也无意写一个文学上的“包山底”,他对“包山底”的一次次的言说,只不过是一次次地确认“走”的可能性。
在《行者》这本诗集里,诗人特地留了一辑“包山底志”。这一辑的诗篇中,有炙热的抒情性特征,包山底也在这抒情性的书写中获得了位置——“躺在我灵魂的版图上”(《我出生在一个叫“包山底”的地方》)。但很快诗人就“把故乡弄丢了”,成了一个“欠着故乡的债”“无家可归的人”。诗人显然知道包山底的局限——“包山底的文字/只写些平易的庄稼”,所以他似乎有些愤怒地宣称:
那些深奥玄乎的文字
早被衣帽光鲜的城里人穿走了
乡间的农民儿子包山底买不起漂亮的字典
包山底要告诉山里邻家的孩子
告诉自己的孩子告诉战争中的孩子
告诉非洲苦难的孩子
只有种在泥土上的汉字
才能枝叶茂盛,才能光芒万丈(《包山底》)
但这首诗歌中强烈的城乡对比意识和“非洲苦难”的第三世界存在感,都实实在在表明诗人的“前现代性”。当然诗歌最后一句中的“光芒万丈”也再次说明了“慕白”的“野心”。不过,诗人的这种愤怒不会是“坚固”的,毕竟慕白或多或少了然人间本相——“上帝看着不顾/阎王记着不管”(《自画像》)。本质上,他还是个“内心长着一颗羞愧的灵魂”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愤怒青年。这一辑里不断出现的“归故乡”诗——比如《我该从哪儿回家》《游子吟》《儿童相问》《回乡偶书》等等——也足以说明“包山底”不是慕白的诗歌国度。这些故乡抒情性书写,不过是诗人不断行走中的慰藉。
还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并不现代的“乡村诗人”并不需要“精神返乡”。慕白的前驱诗人不是荷尔德林这样的“朝霞诗人”。或许,中国当代诗人都不可能有一次真正的现代性意义的“精神返乡”书写。说到底,我们还未“现代”,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白昼时代”的“诸神隐退”所带来的现代性焦虑并没有在中国出现,我们还在现代的路上。既不曾现代,何来返乡?慕白也可能未曾明了昆德拉所说的“世界性的人”背后的宗教背景,他慕的是“白”,而不是幽暗的“林间”。
《城中村纪事:告别春天》是一个隐秘的文本。一般来说,一首“告别”诗,都不只是作者的一个小手段,用来表达他因一次小刺痛而产生的偶然情绪;它一定是用来表达诗人对“告别”这个现象本身的思考。它或许只是一次经验,但足可以在书写经验中丧失私人经验,从而获得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我愿意把这首诗歌看成是慕白对“告别”的一次有意味的经验。
诗人在深夜读书发短信作札记,虽然感叹“新盖的楼房”,“挡住了我探向远方的视线”。但真正侵扰他的是那只“咬了我一口”、“流着我的血液的蚊子”。蚊子的叮咬,让诗人的额头上“迅速起了一个小小的肿包/又痛又痒的,和我童年时在包山底的记忆一模一样”。我想,包山底就是那个“又痛又痒”的诗人之肿。它能让诗人在深夜独居的时候,拿出一瓶珍藏三十年的老酒,和那只蚊子对饮——因为这只蚊子有着和我一样的“自己的方言”。但,包山底方言是“他们”,现代都市“流行播种的是普通话与时髦的广东语”。在“深圳和北京”,包山底的方言,“这些山里来的种子,散落在出租屋,制衣厂,打磨车间”,虽然“方言是一个人返乡的通行证。/其实,它们不是死在故乡就是死在路上”(《包山底方言:他们》)。所以诗人虽然在“告别春天”时候和蚊子对饮,也遥祝那只不甚酒力、从“纱窗漏洞里急急忙忙飞走”的小虫子,“别忘记来时的方向和返乡的路”。但我想,诗人不会不明白,蚊子的所谓“返乡路”,不过是有一天被拍死在路上。当然只有在路上,这只在夜晚扰人的蚊子,才有被孤独的“诗人”邀请来饮酒;只有在路上,诗人才有体验到这卑微的虫子“身体里留着我的血液的蚊子”有着与自己相似的“方言”。他们所来自的乡村都“日渐消瘦”。当然,这只“身上长着翅膀的家伙”,端地可以是诗人的自喻——卑微、脆弱却能飞翔;“分不清南北西东”,在天空中迷失,却可以让城里发短信写札记的文明人刺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会飞的夏虫,也可以是诗歌在一个急速异质的世界中的形象。但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需要的是“告别”春天的恬谧,接受即将到来的世界之酷热和不安。
当然,行走本身就是意味着拒绝成为“闭塞世界”的存在物。“行走”也意味着从纱窗的漏洞里飞出去,即便有可能消失在世界中,慕白也拒绝成为一个在浙南山区隐居的“小诗人”。“包山底”不是慕白的尽头,乡村也不是诗人的界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要求慕白必须明白这个世界的“深奥玄乎”。如果他终此一生都没有体验到世界的“深奥玄乎”,只在朴素中经验地活着,他的诗歌可能只能是“具体、质朴”的句子,而不会成为“朴素的诗歌”。“朴素的诗歌”风格“文雅”,和“自然的本质”相关,像布罗姆说的那样,是“留住大地根基”的诗歌。它态度公正,超然,虽可嘲讽,却有柔韧的质地,生动俏皮中却明确有力。不过从《大解之解》这首芜杂的诗歌中,我有理由相信慕白已经开始可以“执白守黑”,触摸这世界之玄。
二
中国成语:“父母在,不远游”。对于一个执意“在路上”的诗人,可能需要解决“行走”和“父亲”的关系。如果说,“故园”可以在行者受伤时给予“内心的慰藉”,“父亲”当可以成为行走者的障碍。按照那位晦暗的写作者卡夫卡的说法,“父亲”是“我丈量世界的尺度”。在谈到观念世界的不同时,这位作家说:“小男孩的观念是,他必须伸直脖子,以便刚好能够看到放在桌子上的苹果;而父亲的观念呢,他拿起苹果,随心所欲地递给同桌者。”在某种意义上,男孩成长则意味着一场事先张扬的观念上弑父行为。“父母在,不远游”,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就必须解决“父亲”。
慕白诗集《行者》中有一首《月下独酌》:
灯光真的醉了,满脸通红
身影歪斜的厉害,小店的那个女的老板
在柜台用算盘炒着花生米,噼里啪啦响着
令人作呕,乌鸦一样地呱噪
瓶中的酒明显被兑了水,喝起来越来越寡味
父亲,这个名词,空气一样
不请自来,坐在我的对面一直微笑,没有举杯
也没有动一下筷子
这个死去多年的老家伙大概也喝醉了
突然动起来,用眼睛和我划拳
老家伙明显输了,却耍赖
抚摸着我的头,教训我:你个小王八犊子……
我还想和他在干两杯,把老家伙灌醉
举起杯,碰到的却是我眼角
早已埋伏的一群泪水……
对比慕白所慕的那位叫做“白”的伟大醉酒者的同名作品,居于现代的当下的诗人似乎不够飘逸和洒脱。虽然都是“月下独酌”,一个在花间,一个在昏暗的小酒馆:一个邀月共舞作“及春”之“行乐”,一个却只能喝着“明显兑了水”的酒,忍受着小店里女老板“噼里啪啦”拨弄算盘的“令人作呕”聒噪声。如果仅仅从“月下独酌”这个有意味的“境”来说,慕白这首诗歌第一节就解构了伟大醉酒者的诗意——让“独酌”从“孤独审美”变成了一次不折不扣的“俗世恶心”。不过,我想仅仅从解构出发,这首诗歌最终的内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注意。在我看来,李白“月下独酌”是一次“邀影”的自恋行为,而慕白的“月下独酌”却是“自我确认失败”的行为。诗歌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不请自来”的已经死去多年的父亲的亡魂。
显然,在如此“俗世之恶”的时间里,并不适合一场招魂仪式。但我选择确认,这次月下独酌事件是可以是“真”。我无意冒犯慕白这首诗歌对他父亲的亡魂所经历的一次的复杂哀伤的情感:因为诗人的“眼角早已埋伏的一群泪水”。不过艾略特提醒我们:“艺术和事件之间的区别永远是绝对的”。一次酒后与“父亲”亡魂的遭遇,并不必然进入诗歌。但此一事件一进入诗歌,就会作为艾略特所说的“一个化合起来的总体”,也就不会必然比那位著名的丹麦王子和他父亲亡魂的遭遇事件简单,如果彼时写作的慕白拥有莎士比亚的心灵。可惜的是,慕白还没有达到莎士比亚的“普遍性”高度,他轻易地把这一次亡魂的造访改变成了一次俗世伦理的较量,以及较量之后的抒情。诗人在认证父亲喝酒耍赖之后熟稔地让眼泪从眼角——这人类的弱点的集中地,倾泻而出。不过,我还是提醒读者的是这首诗歌中的“诗人和父亲的较量”行为,在这种较量中,“父亲”作为偶像和禁忌已经破碎,诗人已经在观念上和父亲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了“随意”地处理苹果——他不但熟练地和父亲划拳,也对父亲的耍赖行为心知肚明,甚者,可以举起杯,“把老家伙灌醉”。这足可以见出“行者”已经解决的他出行的障碍了。他可以上路了,去迎接他的世界,虽然这世界可能还没有准备拥抱他,毕竟,女老板的算盘还在“噼里啪啦”的响。
慕白的“父亲”书写,最直接的当然是《父亲的墓志铭》和《墓志铭:没有别的》。我没有考证过这两首诗歌的写作时间,但显然可以将《墓志铭:没有别的》看成是《父亲的墓志铭》的改写。《父亲的墓志铭》既是对“父亲”从生到死的一生的“简介”,也是对“父亲”的一次“盖棺”定论:“他的一生/活着是卑微/精神和肉体/忍受着双重的屈辱”。不过就像前文所说,每一首“告别”诗歌都不仅是作者的一个手段,“悼亡”作为最终极的“告别”,“多多少少可以用来表达作者对死亡这个现象本身的总体思考”(布罗茨基),所引慕白的“墓志铭”的诗句,和他亲睐的当代诗人雷平阳的名诗《祭父帖》的名句“他的一生,因为疯狂地/向往着生,所以他有着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卑贱”十分相似。而《墓志铭:没有别的》和《祭父帖》也有相似的构架。与其说,这是慕白对雷平阳诗作的仿写,我宁愿相信这两位诗人都把握住了经历过共和国历史的“一代的父亲”共同的精神病症。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这“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卑贱”的特征“父亲”,是60—70年代生人共同的“父亲”形象,慕白的诗作,不过是在雷平阳之后再次确认了这一代人的“父亲”病理特征,墓碑上的刻痕得到了重新的加深。正如艾略特说所说,“诗人的任务不是并不是寻找新的感情,而是运用普遍的情感,去把它们综合加工成诗歌”。艾略特所说是诗歌的“个人和传统”话题,但对于写作者来说,“父亲”就是“传统”,“传统”必然是“父亲”。当然比之于雷平阳,慕白笔下的“父亲”书写要单纯的多,就像前文所说,慕白还没有能力驾驭一种“普遍性”。相对的,雷平阳是一位具备“普遍性”品格的诗人,可笑的是当代那些诗歌批评者或许还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云南的“地域性”诗人。我曾在私下里说,与其说雷平阳是一位“地域性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位“地狱性诗人”——他的诗歌具备了地狱所要求的“深渊性质”、“凛冽风格”和“启示性”,也具备朴素的伟大作品所必备的两种特征——“明显的缺陷”和“丰富的芜杂”。《祭父帖》中的“父亲”书写,慕白可能只能领受其中某一种维度。
延伸一点,慕白正是在《月下独酌》,解决了“父亲”这个障碍,我们可能看到《行者》一集中,慕白有些肆无忌惮地对诗歌史上的“前驱者”的名诗进行一次“再写作”。比如《姚家源独坐》对之《独坐敬亭山》、《霞山喜雨》对之《春夜喜雨》、《宿衢江上》对之《宿建德江》等等。更有甚者,有些诗作的题目都懒得改:如前文所引《月下独酌》,相同是还有《回乡偶书》《游子吟》《过故人庄》等等。这些具有“同题诗”性质的书写,是《行者》这个诗集的最明显的特点了。当然,慕白的这些“有意味的同题书写”,在我看来,它不是一种和李白们的“较技”行为,也不是像布罗姆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愤怒派诗人”对传统的“解构”和“戏拟”性书写。他好像只安于一个后来者的“识取”,把那些诗歌史上的“前驱者诗作”一一“请”到桌子上来,和他对饮。更准确一点,慕白的这种写作也不能看成是“请”——“请”具备“仪式”的庄严和肃穆感。他的这种写作很随意,但也不是“有意冒犯”。好像这些“诗题”就像《月下独酌》里所说的那个父亲的亡魂,是“不请自来”的。和我同桌,但它既不举杯,也不动筷子,只是“用眼睛和我划拳”,所以诗人虽然自我确认父亲“明显输了”,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依然可以“教训我”。那一声“小王八犊子”,是我和父亲之间的“暧昧的感情”。
需要指出的是,慕白不仅在诗歌题目上玩这种“不请自来”的“识取”,而且在具体的诗句中也经常性的“识取”,不仅“识取”旧诗的句子——比如《在李骞家吃杀猪饭》里的“山歌祝酒且为乐”“乌蒙磅礴等闲”“但愿长醉”;也毫不客气的“识取”现代乃至当代诗歌的名句——比如《两棵杨树》里的“首师大17号楼公寓的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白杨树,另一棵还是白杨树”,以及上文所引的《父亲的墓志铭》中的“他的一生/活着是卑微/精神和肉体/忍受着双重的屈辱”。慕白的这些“识取”的诗题、诗句绝大多数都很“安静”——大概他已经很好地领受了艾略特所说的“个人和传统”之间的的论述,抑或是如他在这本诗集的《序》里引张耒所说的话“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完全不顾及那些巨大的前驱者的压力?
三
有评论者注意到《行者》一集中的“智慧的顿悟”,笔者认为慕白的“智慧的顿悟”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的“wit”(机智),当然这主要集中在他对诗歌技术处理的“wit”上。《行者》中特别标出一辑“文非一体”,自然是因为这一辑中的诗作不能归到“行者”这一词汇所要求的“游走”和“客居”以及“返乡”等范畴中去,所以别归一辑为“文非一体”了。不过,我特别喜欢此一辑中的《大解之解》。在我看来,这首诗歌用简单的词语汇集和解释,就解决了“好的诗歌”中的“柔韧的反讽”和“生动的确定”。它的确诙谐或者说戏谑,但诗歌最后一句“大解一辈子只要一种念法/大解的解只读xie”却端端正正,将前面四处奔走的诗句一一收好。四种读音的“解”字归结到那唯一一种写法中去,文字“应声而落”,诗人大解也在这唯一的声音的引领之下归位。诗人将毫无联系的经验,“机智”地结合到一起,成就了一首姿态非凡的诗歌。
很多评论者都说到了慕白的“真”,把“诗之真”提到“诗之美”之前加以确认。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对。但我觉得“诗之真”可能更应该在“肆意”这一层面上来讨论:真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看到,《行者》一集中,诗人既是在祖国的大地上毫无障碍的“游荡”“闲坐”,也在诗歌的领域中肆意地“识取”。慕白的“智慧的顿悟”或者“经验性的机智”使得《行者》这本诗集具备了足够独特的个性,也使得阅读者即便仅仅为了乐趣的阅读也会有一种“美感享受”。我充分赞同商震先生说的“这本诗集中的作品,是对他过去诗歌的否定,是它展开羽翅准备翱翔的练习”。我诚恳地邀请慕白在打破禁忌之后,在肆无忌惮的同时,让“诗性的记忆”和“传统中骇人的思想““相认”并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基础性的诗歌”,像弗莱切所说的那样。
“慕白”的名字似乎是被人多次谈及,诗人自己也在那篇“跋”文《慕白,慕不白,白慕》中特地做了坦白:先从儿子小学语文书上看到大诗人李白的介绍——继而想到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宏论——又加上对自己的牙齿黑的不满,于是“一举三得”的大名“慕白”,“开张营业”。诗人对自己笔名的“散讲”,很是“油滑”,不过“文坛登龙术”该是有点暗示。就像想上“星光大道”的乡村艺人都希望有个“毕姥爷”一样,“乡村”诗人,我想,也希望有个“白姥爷”作为自己诗歌道路上的“引路人”。何况慕白和李白一样,也是位“经常走在路上,四处流觞”、“甚嚣尘上,倦于世网尘劳”的诗人。
不过,对于“乡村”诗人来说,“白姥爷”这个巨大的“引路人”留下的最激励的诗句可能还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慕白虽自称是浙南文成的“土著”,也表白文成是他“全部的故乡”,
“是一个理想的、田园的、诗意的栖息地”,但“田园”和“现代”是不合的,做一个“世界性的人”强烈想法,必定会让诗人发现这理想的故乡是一个“闭塞的地方”,所以他必定是要做一个“在路上”的“行者”。诗人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在路上》和《行者》,就是要说明:一个“世界性的人”,必定不安于一隅。“出门”的欲望一直轰响在慕白内心。需要说明的是,诗人的故乡文成就已经有一位出门者刘基。这位明代的大人物给诗人的故乡永久性地留下的名字。我想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慕白,口中说出“我是文成的土著”中,当然也有一份来自“刘文成公”的激励。
一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慕白诗歌中的“包山底”,甚至有不少的诗评家将“包山底”看成是慕白诗歌中的“关键词”。正如上文所说,慕白需要“出门”,从包山底走出去,是慕白写作的一个最大动机。但“出门”需要一个“故园”作为出发地,在我看来,慕白所有的“包山底”的诗句,就是建筑一个“故园”。这个“故园”可以保证他在行走的途中,一旦遇到挫折和伤害,可以给予诗人一些必要的安慰和基于内心的保护。慕白写包山底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地域诗人”,慕白也无意写一个文学上的“包山底”,他对“包山底”的一次次的言说,只不过是一次次地确认“走”的可能性。
在《行者》这本诗集里,诗人特地留了一辑“包山底志”。这一辑的诗篇中,有炙热的抒情性特征,包山底也在这抒情性的书写中获得了位置——“躺在我灵魂的版图上”(《我出生在一个叫“包山底”的地方》)。但很快诗人就“把故乡弄丢了”,成了一个“欠着故乡的债”“无家可归的人”。诗人显然知道包山底的局限——“包山底的文字/只写些平易的庄稼”,所以他似乎有些愤怒地宣称:
那些深奥玄乎的文字
早被衣帽光鲜的城里人穿走了
乡间的农民儿子包山底买不起漂亮的字典
包山底要告诉山里邻家的孩子
告诉自己的孩子告诉战争中的孩子
告诉非洲苦难的孩子
只有种在泥土上的汉字
才能枝叶茂盛,才能光芒万丈(《包山底》)
但这首诗歌中强烈的城乡对比意识和“非洲苦难”的第三世界存在感,都实实在在表明诗人的“前现代性”。当然诗歌最后一句中的“光芒万丈”也再次说明了“慕白”的“野心”。不过,诗人的这种愤怒不会是“坚固”的,毕竟慕白或多或少了然人间本相——“上帝看着不顾/阎王记着不管”(《自画像》)。本质上,他还是个“内心长着一颗羞愧的灵魂”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愤怒青年。这一辑里不断出现的“归故乡”诗——比如《我该从哪儿回家》《游子吟》《儿童相问》《回乡偶书》等等——也足以说明“包山底”不是慕白的诗歌国度。这些故乡抒情性书写,不过是诗人不断行走中的慰藉。
还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并不现代的“乡村诗人”并不需要“精神返乡”。慕白的前驱诗人不是荷尔德林这样的“朝霞诗人”。或许,中国当代诗人都不可能有一次真正的现代性意义的“精神返乡”书写。说到底,我们还未“现代”,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白昼时代”的“诸神隐退”所带来的现代性焦虑并没有在中国出现,我们还在现代的路上。既不曾现代,何来返乡?慕白也可能未曾明了昆德拉所说的“世界性的人”背后的宗教背景,他慕的是“白”,而不是幽暗的“林间”。
《城中村纪事:告别春天》是一个隐秘的文本。一般来说,一首“告别”诗,都不只是作者的一个小手段,用来表达他因一次小刺痛而产生的偶然情绪;它一定是用来表达诗人对“告别”这个现象本身的思考。它或许只是一次经验,但足可以在书写经验中丧失私人经验,从而获得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我愿意把这首诗歌看成是慕白对“告别”的一次有意味的经验。
诗人在深夜读书发短信作札记,虽然感叹“新盖的楼房”,“挡住了我探向远方的视线”。但真正侵扰他的是那只“咬了我一口”、“流着我的血液的蚊子”。蚊子的叮咬,让诗人的额头上“迅速起了一个小小的肿包/又痛又痒的,和我童年时在包山底的记忆一模一样”。我想,包山底就是那个“又痛又痒”的诗人之肿。它能让诗人在深夜独居的时候,拿出一瓶珍藏三十年的老酒,和那只蚊子对饮——因为这只蚊子有着和我一样的“自己的方言”。但,包山底方言是“他们”,现代都市“流行播种的是普通话与时髦的广东语”。在“深圳和北京”,包山底的方言,“这些山里来的种子,散落在出租屋,制衣厂,打磨车间”,虽然“方言是一个人返乡的通行证。/其实,它们不是死在故乡就是死在路上”(《包山底方言:他们》)。所以诗人虽然在“告别春天”时候和蚊子对饮,也遥祝那只不甚酒力、从“纱窗漏洞里急急忙忙飞走”的小虫子,“别忘记来时的方向和返乡的路”。但我想,诗人不会不明白,蚊子的所谓“返乡路”,不过是有一天被拍死在路上。当然只有在路上,这只在夜晚扰人的蚊子,才有被孤独的“诗人”邀请来饮酒;只有在路上,诗人才有体验到这卑微的虫子“身体里留着我的血液的蚊子”有着与自己相似的“方言”。他们所来自的乡村都“日渐消瘦”。当然,这只“身上长着翅膀的家伙”,端地可以是诗人的自喻——卑微、脆弱却能飞翔;“分不清南北西东”,在天空中迷失,却可以让城里发短信写札记的文明人刺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会飞的夏虫,也可以是诗歌在一个急速异质的世界中的形象。但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需要的是“告别”春天的恬谧,接受即将到来的世界之酷热和不安。
当然,行走本身就是意味着拒绝成为“闭塞世界”的存在物。“行走”也意味着从纱窗的漏洞里飞出去,即便有可能消失在世界中,慕白也拒绝成为一个在浙南山区隐居的“小诗人”。“包山底”不是慕白的尽头,乡村也不是诗人的界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要求慕白必须明白这个世界的“深奥玄乎”。如果他终此一生都没有体验到世界的“深奥玄乎”,只在朴素中经验地活着,他的诗歌可能只能是“具体、质朴”的句子,而不会成为“朴素的诗歌”。“朴素的诗歌”风格“文雅”,和“自然的本质”相关,像布罗姆说的那样,是“留住大地根基”的诗歌。它态度公正,超然,虽可嘲讽,却有柔韧的质地,生动俏皮中却明确有力。不过从《大解之解》这首芜杂的诗歌中,我有理由相信慕白已经开始可以“执白守黑”,触摸这世界之玄。
二
中国成语:“父母在,不远游”。对于一个执意“在路上”的诗人,可能需要解决“行走”和“父亲”的关系。如果说,“故园”可以在行者受伤时给予“内心的慰藉”,“父亲”当可以成为行走者的障碍。按照那位晦暗的写作者卡夫卡的说法,“父亲”是“我丈量世界的尺度”。在谈到观念世界的不同时,这位作家说:“小男孩的观念是,他必须伸直脖子,以便刚好能够看到放在桌子上的苹果;而父亲的观念呢,他拿起苹果,随心所欲地递给同桌者。”在某种意义上,男孩成长则意味着一场事先张扬的观念上弑父行为。“父母在,不远游”,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就必须解决“父亲”。
慕白诗集《行者》中有一首《月下独酌》:
灯光真的醉了,满脸通红
身影歪斜的厉害,小店的那个女的老板
在柜台用算盘炒着花生米,噼里啪啦响着
令人作呕,乌鸦一样地呱噪
瓶中的酒明显被兑了水,喝起来越来越寡味
父亲,这个名词,空气一样
不请自来,坐在我的对面一直微笑,没有举杯
也没有动一下筷子
这个死去多年的老家伙大概也喝醉了
突然动起来,用眼睛和我划拳
老家伙明显输了,却耍赖
抚摸着我的头,教训我:你个小王八犊子……
我还想和他在干两杯,把老家伙灌醉
举起杯,碰到的却是我眼角
早已埋伏的一群泪水……
对比慕白所慕的那位叫做“白”的伟大醉酒者的同名作品,居于现代的当下的诗人似乎不够飘逸和洒脱。虽然都是“月下独酌”,一个在花间,一个在昏暗的小酒馆:一个邀月共舞作“及春”之“行乐”,一个却只能喝着“明显兑了水”的酒,忍受着小店里女老板“噼里啪啦”拨弄算盘的“令人作呕”聒噪声。如果仅仅从“月下独酌”这个有意味的“境”来说,慕白这首诗歌第一节就解构了伟大醉酒者的诗意——让“独酌”从“孤独审美”变成了一次不折不扣的“俗世恶心”。不过,我想仅仅从解构出发,这首诗歌最终的内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注意。在我看来,李白“月下独酌”是一次“邀影”的自恋行为,而慕白的“月下独酌”却是“自我确认失败”的行为。诗歌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不请自来”的已经死去多年的父亲的亡魂。
显然,在如此“俗世之恶”的时间里,并不适合一场招魂仪式。但我选择确认,这次月下独酌事件是可以是“真”。我无意冒犯慕白这首诗歌对他父亲的亡魂所经历的一次的复杂哀伤的情感:因为诗人的“眼角早已埋伏的一群泪水”。不过艾略特提醒我们:“艺术和事件之间的区别永远是绝对的”。一次酒后与“父亲”亡魂的遭遇,并不必然进入诗歌。但此一事件一进入诗歌,就会作为艾略特所说的“一个化合起来的总体”,也就不会必然比那位著名的丹麦王子和他父亲亡魂的遭遇事件简单,如果彼时写作的慕白拥有莎士比亚的心灵。可惜的是,慕白还没有达到莎士比亚的“普遍性”高度,他轻易地把这一次亡魂的造访改变成了一次俗世伦理的较量,以及较量之后的抒情。诗人在认证父亲喝酒耍赖之后熟稔地让眼泪从眼角——这人类的弱点的集中地,倾泻而出。不过,我还是提醒读者的是这首诗歌中的“诗人和父亲的较量”行为,在这种较量中,“父亲”作为偶像和禁忌已经破碎,诗人已经在观念上和父亲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了“随意”地处理苹果——他不但熟练地和父亲划拳,也对父亲的耍赖行为心知肚明,甚者,可以举起杯,“把老家伙灌醉”。这足可以见出“行者”已经解决的他出行的障碍了。他可以上路了,去迎接他的世界,虽然这世界可能还没有准备拥抱他,毕竟,女老板的算盘还在“噼里啪啦”的响。
慕白的“父亲”书写,最直接的当然是《父亲的墓志铭》和《墓志铭:没有别的》。我没有考证过这两首诗歌的写作时间,但显然可以将《墓志铭:没有别的》看成是《父亲的墓志铭》的改写。《父亲的墓志铭》既是对“父亲”从生到死的一生的“简介”,也是对“父亲”的一次“盖棺”定论:“他的一生/活着是卑微/精神和肉体/忍受着双重的屈辱”。不过就像前文所说,每一首“告别”诗歌都不仅是作者的一个手段,“悼亡”作为最终极的“告别”,“多多少少可以用来表达作者对死亡这个现象本身的总体思考”(布罗茨基),所引慕白的“墓志铭”的诗句,和他亲睐的当代诗人雷平阳的名诗《祭父帖》的名句“他的一生,因为疯狂地/向往着生,所以他有着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卑贱”十分相似。而《墓志铭:没有别的》和《祭父帖》也有相似的构架。与其说,这是慕白对雷平阳诗作的仿写,我宁愿相信这两位诗人都把握住了经历过共和国历史的“一代的父亲”共同的精神病症。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这“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卑贱”的特征“父亲”,是60—70年代生人共同的“父亲”形象,慕白的诗作,不过是在雷平阳之后再次确认了这一代人的“父亲”病理特征,墓碑上的刻痕得到了重新的加深。正如艾略特说所说,“诗人的任务不是并不是寻找新的感情,而是运用普遍的情感,去把它们综合加工成诗歌”。艾略特所说是诗歌的“个人和传统”话题,但对于写作者来说,“父亲”就是“传统”,“传统”必然是“父亲”。当然比之于雷平阳,慕白笔下的“父亲”书写要单纯的多,就像前文所说,慕白还没有能力驾驭一种“普遍性”。相对的,雷平阳是一位具备“普遍性”品格的诗人,可笑的是当代那些诗歌批评者或许还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云南的“地域性”诗人。我曾在私下里说,与其说雷平阳是一位“地域性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位“地狱性诗人”——他的诗歌具备了地狱所要求的“深渊性质”、“凛冽风格”和“启示性”,也具备朴素的伟大作品所必备的两种特征——“明显的缺陷”和“丰富的芜杂”。《祭父帖》中的“父亲”书写,慕白可能只能领受其中某一种维度。
延伸一点,慕白正是在《月下独酌》,解决了“父亲”这个障碍,我们可能看到《行者》一集中,慕白有些肆无忌惮地对诗歌史上的“前驱者”的名诗进行一次“再写作”。比如《姚家源独坐》对之《独坐敬亭山》、《霞山喜雨》对之《春夜喜雨》、《宿衢江上》对之《宿建德江》等等。更有甚者,有些诗作的题目都懒得改:如前文所引《月下独酌》,相同是还有《回乡偶书》《游子吟》《过故人庄》等等。这些具有“同题诗”性质的书写,是《行者》这个诗集的最明显的特点了。当然,慕白的这些“有意味的同题书写”,在我看来,它不是一种和李白们的“较技”行为,也不是像布罗姆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愤怒派诗人”对传统的“解构”和“戏拟”性书写。他好像只安于一个后来者的“识取”,把那些诗歌史上的“前驱者诗作”一一“请”到桌子上来,和他对饮。更准确一点,慕白的这种写作也不能看成是“请”——“请”具备“仪式”的庄严和肃穆感。他的这种写作很随意,但也不是“有意冒犯”。好像这些“诗题”就像《月下独酌》里所说的那个父亲的亡魂,是“不请自来”的。和我同桌,但它既不举杯,也不动筷子,只是“用眼睛和我划拳”,所以诗人虽然自我确认父亲“明显输了”,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依然可以“教训我”。那一声“小王八犊子”,是我和父亲之间的“暧昧的感情”。
需要指出的是,慕白不仅在诗歌题目上玩这种“不请自来”的“识取”,而且在具体的诗句中也经常性的“识取”,不仅“识取”旧诗的句子——比如《在李骞家吃杀猪饭》里的“山歌祝酒且为乐”“乌蒙磅礴等闲”“但愿长醉”;也毫不客气的“识取”现代乃至当代诗歌的名句——比如《两棵杨树》里的“首师大17号楼公寓的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白杨树,另一棵还是白杨树”,以及上文所引的《父亲的墓志铭》中的“他的一生/活着是卑微/精神和肉体/忍受着双重的屈辱”。慕白的这些“识取”的诗题、诗句绝大多数都很“安静”——大概他已经很好地领受了艾略特所说的“个人和传统”之间的的论述,抑或是如他在这本诗集的《序》里引张耒所说的话“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完全不顾及那些巨大的前驱者的压力?
三
有评论者注意到《行者》一集中的“智慧的顿悟”,笔者认为慕白的“智慧的顿悟”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的“wit”(机智),当然这主要集中在他对诗歌技术处理的“wit”上。《行者》中特别标出一辑“文非一体”,自然是因为这一辑中的诗作不能归到“行者”这一词汇所要求的“游走”和“客居”以及“返乡”等范畴中去,所以别归一辑为“文非一体”了。不过,我特别喜欢此一辑中的《大解之解》。在我看来,这首诗歌用简单的词语汇集和解释,就解决了“好的诗歌”中的“柔韧的反讽”和“生动的确定”。它的确诙谐或者说戏谑,但诗歌最后一句“大解一辈子只要一种念法/大解的解只读xie”却端端正正,将前面四处奔走的诗句一一收好。四种读音的“解”字归结到那唯一一种写法中去,文字“应声而落”,诗人大解也在这唯一的声音的引领之下归位。诗人将毫无联系的经验,“机智”地结合到一起,成就了一首姿态非凡的诗歌。
很多评论者都说到了慕白的“真”,把“诗之真”提到“诗之美”之前加以确认。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对。但我觉得“诗之真”可能更应该在“肆意”这一层面上来讨论:真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看到,《行者》一集中,诗人既是在祖国的大地上毫无障碍的“游荡”“闲坐”,也在诗歌的领域中肆意地“识取”。慕白的“智慧的顿悟”或者“经验性的机智”使得《行者》这本诗集具备了足够独特的个性,也使得阅读者即便仅仅为了乐趣的阅读也会有一种“美感享受”。我充分赞同商震先生说的“这本诗集中的作品,是对他过去诗歌的否定,是它展开羽翅准备翱翔的练习”。我诚恳地邀请慕白在打破禁忌之后,在肆无忌惮的同时,让“诗性的记忆”和“传统中骇人的思想““相认”并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基础性的诗歌”,像弗莱切所说的那样。
相关人物
崔勇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