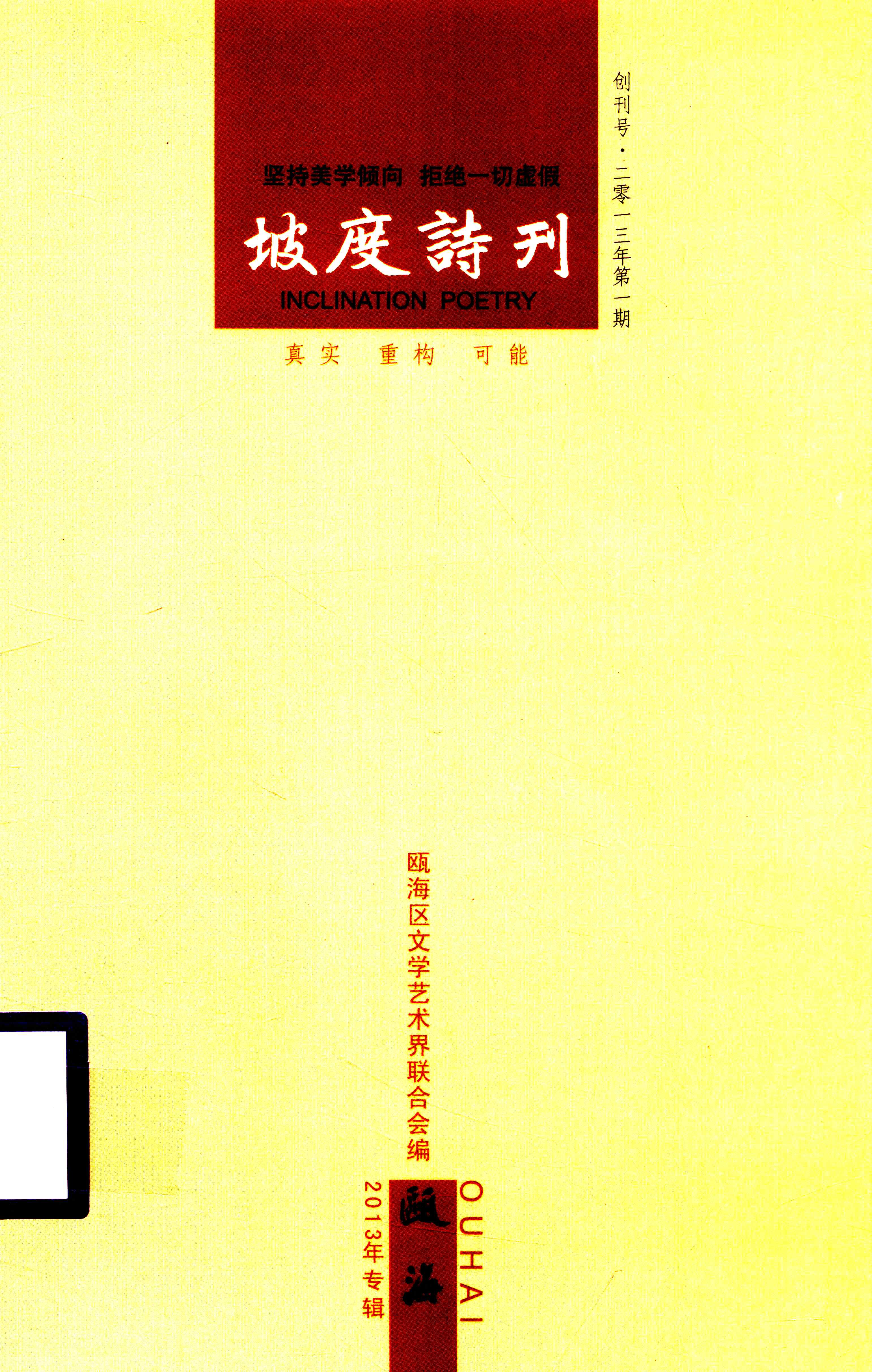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离离,曾从事教师职业,她还有-个身份是诗人。
土地和母亲,哺育了离离;离离,用诗歌馈赠她深爱的物和人。
离离是生活的歌者,她唱生活的虚伪:“如今我回来了,我将与你为敌/与整个村子为敌,在面对面的一刻”(《关于蓝的记忆》),也唱对生活的热爱:"说我恋旧,热爱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失》);离离的诗也透露出她的智慧,既有对生活的妥协与退让:“我像和上帝妥协的/苹果/渐渐呈现出/淡淡的无知”(《在新华书店》),也有着一种臻于知足的生活境界:“我对生活要求不多/能预见黄澄澄的收成/我已满足“(《这些就够了》),而我最钟情的,还是她笔下那些歌唱爱的诗句。
离离在《像一种思想》中写到,“她剥着桔子/用双手分开/十一月的黄昏/这个更大的桔子/在窗外泛着橘黄的光/她继续剥/顺着伤痕”,在常人而言,剥橘子是为了吃橘子,而离离写剥橘子的过程更让人觉得她是在解剖自己,把自己的前世今生赤裸裸地呈现在众人面前,毫无遮掩和矫饰。“很多年来/每次剥橘子/她都会想起第一次吃橘子/那时/橘子的周围/很多亲人都在”,当人们重复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理所当然地想起第一次的情景,剥橘子也是一场值得回忆的过去。而我猜,橘子的周围或许就是离离她自身的周围,离离就是那颗被自己剥离的橘子。第一次吃橘子的时候,是馨悦的,那个时候,相爱的人们都还健在,且触手可及,那是种幸福溢出杯口的感觉。但后来,一切都晦暗了。“因为橘子/她仓皇而逃/一直逃了这么多年/直到他们都不在了”,她不敢面对爱的人,那么多人都不在了,都离她远去了,可是橘子还在,自己还在。她以为,如果出逃,如果疏远,那就不会失去了。可是当她蓦然回首,才发现所有人都已不在了。她把自己流放在时间之外,只因不忍失去,却错过了更多。
"有时候/她再次咬破橘皮/还是那么苦/那些亲人/就会顺着汁水挤出来/一瓣一瓣/靠在手心里/慢慢坐下。”这是几行有温度、会说话的诗,胜过炙热的告白。那些死去的亲人,肉体不在,但在离离的心里,他们的生命并未消逝,而是或在云里小憩,在青草里冬眠,也可以在橘子的汁水里复活,“靠在手心里,慢慢坐下”。这听起来并不惊悚,相反,却是出奇得温暖。我们多么希望自己逝去的亲人能死而复生,离离把这份希冀寄托在了橘子上。她曾因橘出逃,终是因橘生爱,而她挚爱的亲人幻化成另一种生命的形态,重又复活团圆。
有人在写离离时讲到,“如果诗人逃离了生活,也便逃离了诗;如果诗人拥抱了生活,诗便把诗人抱得更紧。”是啊,生活之于诗人,犹如水对于鱼一样不可或缺。离离就是这样一位在诗歌中还原生活本来面貌的诗人,这颗坦诚直率的“橘子”就是这样一次次抒写悲暖的离歌。她的诗歌没有血肉分离的生硬痛楚,没有生命轮回的夸张痕迹,而是和朱自清一样,用生活中最简单的“橘子”娓娓诉说着心底里那份最刻骨铭心的温存。
离离的诗歌中不乏类似于《像一种思想》的诗歌:“一直以来/我善良的亲人/一个个离去/他们灰暗的皮肤/渐渐贴在大地上/他们的气息已经成为小草的气息/他们的名字已成为植物的根茎/他们/已属于某一科某一属/开黄花的春天和秋天/更多的时候/我贴着大地坐下来/不只是和植物在一起”(《钝器》)。
“更多的时候,我贴着大地坐下来,不只是和植物在一起”,更是在寻觅逝去亲人的呼吸、心跳和脉搏。在诗人的眼中,肉体的消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灵魂的堕落才是生命的地狱。那些善良的亲人,即使离去了,也甘愿把自己剩下的全部贞献给土地。我想,他们滋养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或许也是存着小小的私心,是为了能够在某个落叶的秋日再一次和记得自己的人相遇。
对亲人的追忆和爱恋,是生活之常情,也是离离诗歌割舍不下的一部分。有了亲情,诗歌就顿时有了可以填充的血与肉、灵与魂。离离的诗歌里,最触动我的是她对父母的骨肉之情。因为我们做子女的都对父母怀揣着复杂的感情,而离离把这种难以启齿的感情用文字写成了一行行的诗歌。
如《乳房》一诗。母羊供给她奶水,给予她活下去的可能。母亲赐予她生命,提供给她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后来,两位母亲,一位“被别人牵走”,而“我”只能站在墙角哭泣,无能为力;而另一位母亲,恩赐她生命,把自己的青春投注在她身上,却被时间带走了美丽和自信,羞于把身体暴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孩子曾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母亲看自己孩子的身体就像欣赏一件自己创作的完美的艺术品,而诗人衰老的母亲在盛年的女儿面前沐浴时表露出来的羞涩,着实让人心痛和不忍。而其实,母亲在离离的眼里是这样的一“她白天叫我女儿,晚上睡在我孩子的摇篮里/她就成了一个/一丝不挂的婴儿”(《母亲》)。这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表白。
诗的最后,诗人发出“它们在衰老的时候/都是离我那么远”的悲号,喊出了所有真心为人子女的心声。一个孩子理当仰视哺育她的人或物。“用手轻轻摸它身上的毛,也轻轻摸过为我挤出奶的地方”,这是对母羊最起码的尊重和感恩。“不敢去碰”,感情更是升华为对无私奉献却垂垂老矣的母亲的敬仰。
离离在《槐花》中:“槐树的叶子很茂盛/几乎完全罩住了母亲藏着病灶的身体/只露出槐花一样盛开的他们正在上高中的女儿”。一个是羸弱的母亲,被病魔纠缠,一个是风华正茂,如槐花般美好的女孩儿,两相对比,不仅突出了母亲的虚弱和不幸,更凸显了作为女儿对母亲的愧疚和深沉的爱意。善良的诗人宁愿生病的是自己,也不愿看见生养她的母亲受病痛的折磨。近于絮语的倾诉,娓娓道来,蕴含了极为丰富复杂的情感,形成一股悲喜交加的暖流,使我们感受到说不出的苦与乐的生活之味。
再者如《橘子》,和《像一种思想》有所不同。“没人注意到/你在吃橘子时露出的白发/除了我/你的苍老无法让人说清”。“没人注意到”,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沧桑中,无暇顾及别人的老化,只有细心的子女会有心思去关注父母额头上是否比前天多了一道皱纹,两鬓又添了几丝银发,牙齿脱落了几颗。或者说,在年少无知的时候,在不懂得母亲、不懂得父亲的年纪,在只顾自己玩耍放肆的青春期里,我们根本不会注意父母亲细微的变化。等到某一天,真的成长了,在突然间,就会发现母亲脸上出现了老年斑,不复当年俏丽模样,而其实,母亲的老年斑在几年前就已经有占据她的面庞了,只是当时你还沉湎于失恋的悲伤中无法自拔。
而“除了我,你的苍老无法让人说清”,只有我们温暖的诗人能说清她所爱之人的苍老,清楚得知道那一缕白发是为何而掉,眼角的鱼尾纹又是因谁落泪而起。在《光》里,离离写到“他们都去了哪里/像儿根白发从这个世界消失/那天妈妈说/她老了/干不动了/我突然看见妈妈头上的白发/越来越粗/越来越清晰”,诗人是早就注意着母亲衰老的表征的,她之前就观察到了母亲的白发,并不说这一瞬突然发现。此刻她“突然看到”的,是妈妈头上白发“越来越粗,越来越清晰”。时间并没有同情母亲的衰老而放过母亲,母亲衰老的速度在离离的眼里变得越来越快,尤其是当她全神贯注凝视着妈妈头上的白发时,她心里害怕失去母亲的恐惧也愈发被放大了。人们总是在拥有某样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害怕失去它的习惯。
只有真正懂得品尝生活的诗人,才能把生活在诗里写活,写的像样,读的人才能读出生活的味道。离离把她深爱的人写进诗里,没有生离死别,就像是讲故事那般纯粹而温暖。
“还是那张床/只是换了新的床单和被套/还是那件屋子/地面被反复扫过/甚至看不见一根掉下的白发丝/光从窗口涌进来/照见的还是两个人/一个70岁/在轻轻擦拭桌子/另一个/在桌子上的相框里/听她反反复复絮叨”(《这便是爱》)。所有的爱情继续到老的时候,就升华成为亲情。这首诗简直就是个故事。以一位后辈的口吻在讲述她长辈的故事,而听的人也不禁簌簌落下泪来。屋子里一切的物件都还是它们最初的模样,该做什么用就做什么用,但使用者呢?起初读到“照见的还是两个人”,所有人都会理所当然的想到这是一对相濡以沫的老人,他们饱经风霜却依然在一起。但事情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折,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个竟是在相框里。于是我们感慨,啊,不在了啊。我猜,这对老人或许是离离的父母,或许是离离编织的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简单的语句,纯净的只有感情。我们都期望得到这样的爱情,在年轻的时候和一个人相爱,然后和他一起慢慢老去。
读到《他们终于分开了》,我知道《这便是爱》中的主角就是离离的父母。
“他们终于分开了/距离比想象中要远不管爱或者不爱/他们终于分开了/这两个做我父亲和母亲的人。”离离用柔软的笔触写父母的生死相隔,她怀揣着对父母的深沉的爱诉说着两人的过往。“之前没完没了的吵架/摔东西/甚至厮打过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他们彼此孤独/已无法回到从前。”或许这对夫妻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爱情,相处的日子里矛盾多过和平,但毕竟他们陪伴彼此度过了一生。
无论是对逝去亲人的追思,对母亲的尊敬和爱恋还是对父母深沉的情感,离离的诗歌道出了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真谛,那就是——爱。与其说她是用笔在纸上耕耘,不如说她用心唱岀了生活和生命中的爱。好的诗歌不需要华丽粉饰的语言,也不需要惊世骇俗的题材,只要有一双善于挖掘生活的慧眼和一颗真诚如镜的心。而离离,一位真实而善良的诗人,曾是一位崇高而平凡的教师,我想,做一位心中有爱的诗人的学生,该是多么幸福和美好的事情。
土地和母亲,哺育了离离;离离,用诗歌馈赠她深爱的物和人。
离离是生活的歌者,她唱生活的虚伪:“如今我回来了,我将与你为敌/与整个村子为敌,在面对面的一刻”(《关于蓝的记忆》),也唱对生活的热爱:"说我恋旧,热爱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失》);离离的诗也透露出她的智慧,既有对生活的妥协与退让:“我像和上帝妥协的/苹果/渐渐呈现出/淡淡的无知”(《在新华书店》),也有着一种臻于知足的生活境界:“我对生活要求不多/能预见黄澄澄的收成/我已满足“(《这些就够了》),而我最钟情的,还是她笔下那些歌唱爱的诗句。
离离在《像一种思想》中写到,“她剥着桔子/用双手分开/十一月的黄昏/这个更大的桔子/在窗外泛着橘黄的光/她继续剥/顺着伤痕”,在常人而言,剥橘子是为了吃橘子,而离离写剥橘子的过程更让人觉得她是在解剖自己,把自己的前世今生赤裸裸地呈现在众人面前,毫无遮掩和矫饰。“很多年来/每次剥橘子/她都会想起第一次吃橘子/那时/橘子的周围/很多亲人都在”,当人们重复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理所当然地想起第一次的情景,剥橘子也是一场值得回忆的过去。而我猜,橘子的周围或许就是离离她自身的周围,离离就是那颗被自己剥离的橘子。第一次吃橘子的时候,是馨悦的,那个时候,相爱的人们都还健在,且触手可及,那是种幸福溢出杯口的感觉。但后来,一切都晦暗了。“因为橘子/她仓皇而逃/一直逃了这么多年/直到他们都不在了”,她不敢面对爱的人,那么多人都不在了,都离她远去了,可是橘子还在,自己还在。她以为,如果出逃,如果疏远,那就不会失去了。可是当她蓦然回首,才发现所有人都已不在了。她把自己流放在时间之外,只因不忍失去,却错过了更多。
"有时候/她再次咬破橘皮/还是那么苦/那些亲人/就会顺着汁水挤出来/一瓣一瓣/靠在手心里/慢慢坐下。”这是几行有温度、会说话的诗,胜过炙热的告白。那些死去的亲人,肉体不在,但在离离的心里,他们的生命并未消逝,而是或在云里小憩,在青草里冬眠,也可以在橘子的汁水里复活,“靠在手心里,慢慢坐下”。这听起来并不惊悚,相反,却是出奇得温暖。我们多么希望自己逝去的亲人能死而复生,离离把这份希冀寄托在了橘子上。她曾因橘出逃,终是因橘生爱,而她挚爱的亲人幻化成另一种生命的形态,重又复活团圆。
有人在写离离时讲到,“如果诗人逃离了生活,也便逃离了诗;如果诗人拥抱了生活,诗便把诗人抱得更紧。”是啊,生活之于诗人,犹如水对于鱼一样不可或缺。离离就是这样一位在诗歌中还原生活本来面貌的诗人,这颗坦诚直率的“橘子”就是这样一次次抒写悲暖的离歌。她的诗歌没有血肉分离的生硬痛楚,没有生命轮回的夸张痕迹,而是和朱自清一样,用生活中最简单的“橘子”娓娓诉说着心底里那份最刻骨铭心的温存。
离离的诗歌中不乏类似于《像一种思想》的诗歌:“一直以来/我善良的亲人/一个个离去/他们灰暗的皮肤/渐渐贴在大地上/他们的气息已经成为小草的气息/他们的名字已成为植物的根茎/他们/已属于某一科某一属/开黄花的春天和秋天/更多的时候/我贴着大地坐下来/不只是和植物在一起”(《钝器》)。
“更多的时候,我贴着大地坐下来,不只是和植物在一起”,更是在寻觅逝去亲人的呼吸、心跳和脉搏。在诗人的眼中,肉体的消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灵魂的堕落才是生命的地狱。那些善良的亲人,即使离去了,也甘愿把自己剩下的全部贞献给土地。我想,他们滋养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或许也是存着小小的私心,是为了能够在某个落叶的秋日再一次和记得自己的人相遇。
对亲人的追忆和爱恋,是生活之常情,也是离离诗歌割舍不下的一部分。有了亲情,诗歌就顿时有了可以填充的血与肉、灵与魂。离离的诗歌里,最触动我的是她对父母的骨肉之情。因为我们做子女的都对父母怀揣着复杂的感情,而离离把这种难以启齿的感情用文字写成了一行行的诗歌。
如《乳房》一诗。母羊供给她奶水,给予她活下去的可能。母亲赐予她生命,提供给她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后来,两位母亲,一位“被别人牵走”,而“我”只能站在墙角哭泣,无能为力;而另一位母亲,恩赐她生命,把自己的青春投注在她身上,却被时间带走了美丽和自信,羞于把身体暴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孩子曾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母亲看自己孩子的身体就像欣赏一件自己创作的完美的艺术品,而诗人衰老的母亲在盛年的女儿面前沐浴时表露出来的羞涩,着实让人心痛和不忍。而其实,母亲在离离的眼里是这样的一“她白天叫我女儿,晚上睡在我孩子的摇篮里/她就成了一个/一丝不挂的婴儿”(《母亲》)。这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表白。
诗的最后,诗人发出“它们在衰老的时候/都是离我那么远”的悲号,喊出了所有真心为人子女的心声。一个孩子理当仰视哺育她的人或物。“用手轻轻摸它身上的毛,也轻轻摸过为我挤出奶的地方”,这是对母羊最起码的尊重和感恩。“不敢去碰”,感情更是升华为对无私奉献却垂垂老矣的母亲的敬仰。
离离在《槐花》中:“槐树的叶子很茂盛/几乎完全罩住了母亲藏着病灶的身体/只露出槐花一样盛开的他们正在上高中的女儿”。一个是羸弱的母亲,被病魔纠缠,一个是风华正茂,如槐花般美好的女孩儿,两相对比,不仅突出了母亲的虚弱和不幸,更凸显了作为女儿对母亲的愧疚和深沉的爱意。善良的诗人宁愿生病的是自己,也不愿看见生养她的母亲受病痛的折磨。近于絮语的倾诉,娓娓道来,蕴含了极为丰富复杂的情感,形成一股悲喜交加的暖流,使我们感受到说不出的苦与乐的生活之味。
再者如《橘子》,和《像一种思想》有所不同。“没人注意到/你在吃橘子时露出的白发/除了我/你的苍老无法让人说清”。“没人注意到”,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沧桑中,无暇顾及别人的老化,只有细心的子女会有心思去关注父母额头上是否比前天多了一道皱纹,两鬓又添了几丝银发,牙齿脱落了几颗。或者说,在年少无知的时候,在不懂得母亲、不懂得父亲的年纪,在只顾自己玩耍放肆的青春期里,我们根本不会注意父母亲细微的变化。等到某一天,真的成长了,在突然间,就会发现母亲脸上出现了老年斑,不复当年俏丽模样,而其实,母亲的老年斑在几年前就已经有占据她的面庞了,只是当时你还沉湎于失恋的悲伤中无法自拔。
而“除了我,你的苍老无法让人说清”,只有我们温暖的诗人能说清她所爱之人的苍老,清楚得知道那一缕白发是为何而掉,眼角的鱼尾纹又是因谁落泪而起。在《光》里,离离写到“他们都去了哪里/像儿根白发从这个世界消失/那天妈妈说/她老了/干不动了/我突然看见妈妈头上的白发/越来越粗/越来越清晰”,诗人是早就注意着母亲衰老的表征的,她之前就观察到了母亲的白发,并不说这一瞬突然发现。此刻她“突然看到”的,是妈妈头上白发“越来越粗,越来越清晰”。时间并没有同情母亲的衰老而放过母亲,母亲衰老的速度在离离的眼里变得越来越快,尤其是当她全神贯注凝视着妈妈头上的白发时,她心里害怕失去母亲的恐惧也愈发被放大了。人们总是在拥有某样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害怕失去它的习惯。
只有真正懂得品尝生活的诗人,才能把生活在诗里写活,写的像样,读的人才能读出生活的味道。离离把她深爱的人写进诗里,没有生离死别,就像是讲故事那般纯粹而温暖。
“还是那张床/只是换了新的床单和被套/还是那件屋子/地面被反复扫过/甚至看不见一根掉下的白发丝/光从窗口涌进来/照见的还是两个人/一个70岁/在轻轻擦拭桌子/另一个/在桌子上的相框里/听她反反复复絮叨”(《这便是爱》)。所有的爱情继续到老的时候,就升华成为亲情。这首诗简直就是个故事。以一位后辈的口吻在讲述她长辈的故事,而听的人也不禁簌簌落下泪来。屋子里一切的物件都还是它们最初的模样,该做什么用就做什么用,但使用者呢?起初读到“照见的还是两个人”,所有人都会理所当然的想到这是一对相濡以沫的老人,他们饱经风霜却依然在一起。但事情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折,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个竟是在相框里。于是我们感慨,啊,不在了啊。我猜,这对老人或许是离离的父母,或许是离离编织的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简单的语句,纯净的只有感情。我们都期望得到这样的爱情,在年轻的时候和一个人相爱,然后和他一起慢慢老去。
读到《他们终于分开了》,我知道《这便是爱》中的主角就是离离的父母。
“他们终于分开了/距离比想象中要远不管爱或者不爱/他们终于分开了/这两个做我父亲和母亲的人。”离离用柔软的笔触写父母的生死相隔,她怀揣着对父母的深沉的爱诉说着两人的过往。“之前没完没了的吵架/摔东西/甚至厮打过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他们彼此孤独/已无法回到从前。”或许这对夫妻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爱情,相处的日子里矛盾多过和平,但毕竟他们陪伴彼此度过了一生。
无论是对逝去亲人的追思,对母亲的尊敬和爱恋还是对父母深沉的情感,离离的诗歌道出了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真谛,那就是——爱。与其说她是用笔在纸上耕耘,不如说她用心唱岀了生活和生命中的爱。好的诗歌不需要华丽粉饰的语言,也不需要惊世骇俗的题材,只要有一双善于挖掘生活的慧眼和一颗真诚如镜的心。而离离,一位真实而善良的诗人,曾是一位崇高而平凡的教师,我想,做一位心中有爱的诗人的学生,该是多么幸福和美好的事情。
相关人物
张泸萍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