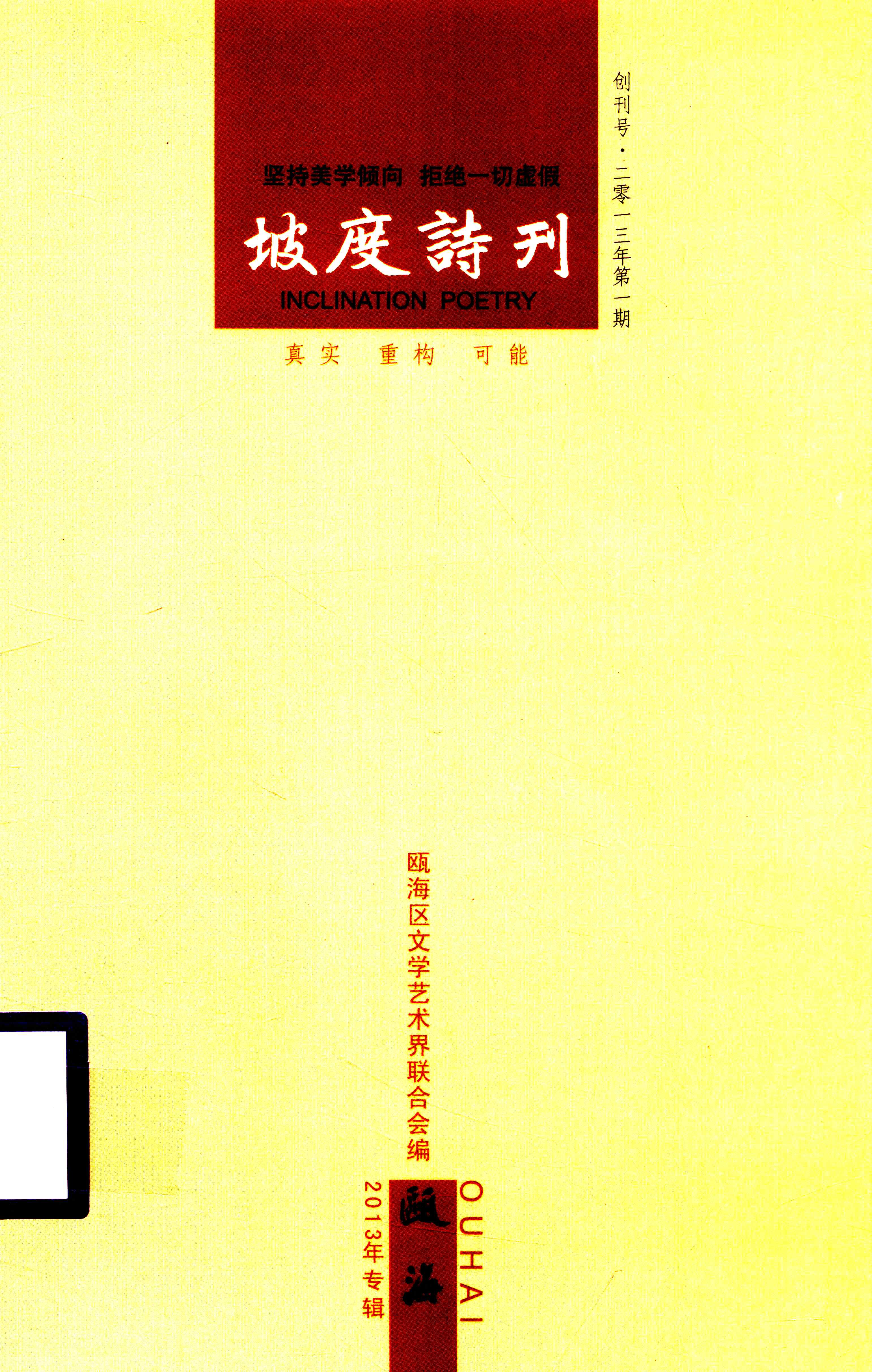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2013年7月,冯娜参加第二十九届“青春诗会”,并因此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在随后出版的一系列青春诗会诗丛中,冯娜的诗集《寻鹤》在封面摘录了一节诗:
“牛羊藏在草原的阴影中
巴音布鲁克我遇见一个养鹤的人
他有长喙一般的脖颈
断翅一般的腔调
鹤群掏空落在水面的九个太阳
他让我觉得草原应该另有模样”
这位来自云南的白族女诗人,就如同这些诗句,如同那群被寻找的鹤,翩然而至,降落在诗歌的高原之上。
《寻鹤》一诗,窃以为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无论是富含游牧气息的“牛羊”、“草原”这些意象,区别于汉语音系的“巴音布鲁克”这个地名,抑或神秘如通灵者的“养鹤人”这份古老的职业,都体现着冯娜诗歌中明晰且浓厚的地域特色——云南。在冯娜的诗中,这些云南意象俯拾皆是,构成了一个意象群,而这些意象群中所具有的真正的云南精神气质,又得以组成她的诗中一批具有真正风情的“云南诗群”。《寻鹤》一诗,从词语的表面肌理到语句间弥漫的意境,从诗艺到内质,都体现出云南情致的饱满和一致,又具有对云南般爱情的探寻,使得它得以成为冯娜“云南诗群”中的一种典范。这些优秀的云南诗群给冯娜的诗作抹上浓烈的地域色彩。《寻鹤》、《澜沧江》、《云南的声响》、《沿着高原的河流》等一批诗作,构架了冯娜诗中令人神往的另一个空间,那里弥漫着浓郁且典型的云南况味,栖息着聪颖的自然生灵与少数民族的契约。而你也不得不把冯娜一这位自如地呈现这一切的诗人,与那个充满灵性与秘密的地方紧密相连。“云南诗人”就这样成为她所惯有的标签。
然而,仅以地域解冯娜,或许会遗失她诗歌中的另一些广阔与丰富。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一位天生有灵性的母亲,天生孕育有灵性的灵魂。它为这些灵魂打开感知世界万物的能力,并成为其感知之旅的起点。然而,感知之旅一旦开启,决不会仅局限于出发地。细读冯娜的诗歌,可以发现其对世界多种角度和层面的感知与探寻。它们在诗歌中各自独立地存在,并都具备蓬勃的内蕴和生发。它们构成了冯娜诗歌中的多种生命形式。
好的诗歌必定产生于诗人对万物生动而深入的感知,这种感知得益于诗人的天赋,并决定了他们与世界独特的交流方式。冯娜正是一个具备独特感知天赋的人。在诗歌中,这天赋则体现为诸多意象所具备的一种神灵气质与生命形式。而这些“神灵”们,便形成了她诗歌的第一种生命形式。冯娜善于以拟人与联想相结合的方式,赋予山川河流,花鸟虫鱼,草树木甚至是平凡的物件以灵魂和感知力。它们以人的形态发声,具备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它们或见证人类的人生,或自身便拥有丰沛的经历与情感。她在《莲花》中写道:“一卷经书放在窗上夜里感到寒冷”。这是经书日常的遭遇。在《龙山公路旁小憩》中:“近处有松树苦楝树我不知道名字的阔叶树/它们高高低低交错生长又微妙地相让”。这是属于所有树木们的契约。《龙山坝的夜》中她写:“黄昏过后/坝子的尽头无数星辰将要分娩”。这是接近神的意志。这样的诗句在她的诗集中俯拾皆是。《夜过增城》中:'‘粤水怀有十二个罗汉的慈悲/荔枝因为一个人缺席而推迟成熟”;《卡若拉冰川》中:“在山上你在苔薛间按灭烟蒂/大地轻轻颤栗了一下/所有云朵都动荡不安”;《晚安》中:“大病初愈的月光白戚戚地并膝坐在台阶上”。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时,都无法不被这样的句子触动到自己恻隐的触角。这些诗句已然不是简单的拟人手法便可轻易制造,动人的诗句中藏匿的向来是属于诗歌内部的生命,而这生命诞生于一个有思想、有天赋的诗人的真挚与情意。一个眼中万物皆有灵的诗人,或许已掌握了与这个世界交流的秘密。她给予世间一切的万物以同等的目光,注视和平等相待,世间万物便是她的旅伴。这些神灵穿梭在冯娜诗句的字里行间,让一本诗集于沉静而无人的语言中见出丰沛的魂魄。又或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诗集中的冯娜在日常的行走中,寻找到千万个藏匿于万物的另一个自己。此时,她本人就是云南(或更多大千风光)之中的一部分,是万千“带着翅膀的事物”之一(《如何遇见带翅膀的事物》)。
冯娜惯于以这种方式,将自己化入自然万物之中,倾听它们的故事,承担它们的情绪。这些有灵魂的生灵,一类体现为旁观世间的崇山静水,它们像生长了千万年的长者,却不曾失去过锐觉和生机,每年春天,它们都重复拥有青春。如冯娜在《群山》中写道:
“群山涉水多年而不渡
蜂巢引发耳鸣 这寂寞忽远忽近
春天随之带来痼疾
迫使大地拧开胶囊中的粉末
相互传染的痒
让它们遍体花束 如象群的墓冢”
韩作荣曾在《候车室》一诗中这样写:“只有椅子稳重地站立着/有腿而不远行/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过客”,二者在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群山在“不渡”的静态中,对比“涉水”和他人的“渡”两种动态;椅子在“不远行”的静态中,对比“有腿”和他人的“远行”两种动态,二者都在动与静的二重对比中,形成时间的长度和旁观的姿态,并产生一种绝妙的回响,给人以忘年之感。在挨弃时间的轮回之后,于群山而言,春天是每年必染的一样“痼疾”,浑身开满鲜花是周期性过敏般的症状,让人不禁感觉有花在肌肤上盛开,而读者则得以拥有身为群山的体验,这是此诗的妙处。又如《龙山的女儿》:“龙山在干净渐暖的风中白发簌簌凋零/我看着他流尽整座山峦的眼泪”,龙山的款款深情同样在四季变迁中同步地表露端倪。在《菩提树》中她写道:“第一次路过它们用手碰了碰树干/植物的回应是一只受惊的鸟……我们都一屁股坐在它的脚趾上”;在《金沙江》中她写道,那块“黑色的礁石”,是“我静静没入水中殉情的女人”(诗人的二个远方姐姐殉情于金沙江)。在诗人笔下,这些自然景物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秘密。在大千世界中,它们或许为冯娜这样的人所关注,或许更多的是被熟视无睹,但这都无碍于它们生活的丰富,晏如,与世无争。而冯娜的书写,得以为读者搭建彼此感知的桥梁。
冯娜诗中的有一类生灵,与女人具有特殊的联系。在《桂花树》中,桂花树脱离了单纯的植物形态,而是娴静而隐忍的女人,怀有女性的羞涩和端庄,具有天下女人普遍怀有的苦楚和忍耐。桂树传说生长于月亮,月亦是女性的象征。诗人眼中,她们原本都是来自月亮的纯洁之物。然为何被贬下凡去了?生长在凡间的泥土中,从此怎么也去不了那“趾缝里泄漏的泥腥气”。何时不曾想返乡呢,在这里,她们把梦和念想隐藏得很深,隐姓埋名,你我谁会记得把它和遥远的月相关联,香气四溢时,人们只当作是她的美满,理所当然;她亦把苦楚只留给自己,独自忍受从来是女人应备的品德。大地上的女人们,何尝不是把万千的美好和远行的梦都拾掇好,在归作别人家后,忙碌于市井庸常,只在无人的夜中,追忆心之所向。桂花树正是天下女性这些最典型又最为动人的形态。冯娜也曾在《在生命里》写道:“我窥探一株植物的奥秘一个女人的魂灵/它们的肌肤雷同/高贵脆弱如死之静谧和坚强”。植物和女性在灵魂上的相通之处可见一斑。
每个地域的诗人,尤其是来自少数民族的诗人,或许都带有书写家族的使命感。冯娜本人是白族人,按她的话说,她的母亲“属于典型的白族女人”,她的祖辈“怀揣许多迁徙琉璃的故事”。冯娜诗歌中来自云南深处的传说和风俗,构成了第二种生命形式。冯娜曾在2013年的组诗《他耳普子情歌》集中描写了白族的一些风俗和往事。那些祝酒词、巫师、族谱、牧歌、祭司、水鬼……是不为人所熟知的、神秘的生命群体。他们存在于云南深处。而在冯娜的诗歌中,他们并不讳莫如深,而是以性格中的生机、深情、隐忍、热情、誓言与人形成共鸣。在《一个白族人的祝酒辞》诗中,三行排比句见出白族人的豁达和热情,在命运与他留河的交互中见出这一民族对人生的洞然。在《晨歌或风水》中,山水,晨雾,太阳和雪山,牛羊和晨起洗漱,这是他留人安宁的生活图景。他留人的河流被冠以种族的名字《他留河》,河水是他留人流淌的根脉,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留下彼此依存的深情。在他留人中,象征爱情的是马缨花(《马缨花》:我的爱情藏进马缨花的雌蕊)。他们的婚礼有陶罐、铜镜、黑蛇和族谱(《夜歌》)。族人间饮酒时,上前斟酒如“手持一把柯尔特手枪”,醉酒时如豹子“应声倒地”般壮硕(《与彝族人喝酒》)。而他留人的牧歌里,唱着"世间的猛兽良禽虫豸”(《他留人牧歌》)。这一民族群体的生命形式,是具有勃勃生机的。
冯娜诗歌中的第三种生命形式,则是以她自身的情感与思索为基点,探寻人类生命的一些共性。在2014年9月王威廉对冯娜的釆访中,她提到:“一个诗人各个成长阶段的诗歌理应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我愿意看到它缓慢沉着,自觉但不刻意的变化。……近年来,我将目光投向这些情感记忆在现实中的际遇、在人类命运中的共鸣、在时间中的恒定和变幻,试图获得一种更新的、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眼光。”冯娜近几年的创作中,逐渐岀现了区别于之前的诗作。
冯娜的一首献给父亲的诗《隔着时差的城市》曾在多处被刊登。她也曾在公众诗歌活动中朗诵了这首诗。这是冯娜仅有的六首献诗(《九月,是写献诗的季节(组诗)》)中的一首,可见她对父亲的情感。诗中所包含的真挚,读来让人心疼。“父亲,我是否应该将光阴对折/剪去那些属于南方的迷/……/我有你盛怒之下的灰烬/你何尝想过吧,成为-个女人的父亲是如此艰辛”。一个长大后的女儿在重解当年与父亲的心结时,会承担更多的感喟。“父亲,额尔齐斯河的水一直往下流/一个又一个迁徙者的命运/我和你一样,竟没有把多余的爱憎留在岸上”。当女儿成长到能够与父亲一同谈论今生的命运,彼时白发对青丝,竟发现自己这一生的秉性和道路,从父辈就已有预示和痕迹——代代注定把多余的爱憎携带一生。在“目光呆滞,默不作声"的沉默中,那弥漫着的宿命感无关悲伤,反而是亲情间的相互呼应和抚慰。在岁月里与父亲逐渐达到同歩、甚至超越的过程中,亲情愈加丰富厚重,几近迫人心痛。一句句的“父亲”,如若呼唤。在2013年,冯娜又写了一首《与父亲掰手腕》:“我不能察觉他在老去/我不能总让他赢/我必须伺机在他突然的疏忽中/扳回一局”。诗歌里,在女儿与父亲角色对调的过程中,有一种轻柔的、童趣的、温情的爱。冯娜也有过写母亲的诗。在《母亲》一诗中,她重复写道:“她经历许多,来做我的母亲”。在一次次的反复中,显现的是对母亲不易的了然,和无以言说的感恩。而在诗句中可以看出,冯娜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铺展,只消这样的一句恰好的概述,就已足够让人懂得那些无力多说,也不必多说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概述背后,必定是冯娜长久的感知和富有洞察力与穿透力的眼光。在《接站的母亲》中,她写道:“每一趟车都掠起一阵风/只有她不被吹拂/……/我站在天空底下/一只鹰沉默地飞向旗云/它的心事我都听见”。冯娜的诗歌中,亲情仿佛平静且不动声色,不具有特殊性或戏剧性。然而,以平静之力所表述出的亲情中的永恒一面,却更能摇动万千人的心灵。
冯娜诗中自然也不乏爱情。《橙子》一诗可谓是小巧玲珑而韵味丰满。“我舍不得切开你艳丽的心痛/粒粒都藏着向阳时零星的甜蜜/我提着刀来/自然是不再爱你了”。全诗仅四句,如刀一般短,然而刀中有爱与不爱的秘密。在《生活》中,冯娜看到爱情让女人做梦、沉醉,自我欺骗与自我宽慰彼此相互颠而复使。在《隐居》中她写道:“你静静走着也不问起我/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隐居——/活在你的爱里却从不现身”。这是爱情假想者所向往的爱情模式的一种。此外,在她的笔下,也出现过别人的爱情。如《白蛇》中:"……白蛇/你拿几百年修行来做美人/和我在下午怀念面容模糊的旧情人/一样光阴虚掷”。这是一针见血的自我解嘲,又是必然的义无反顾。而族人间的爱情,会"藏进马缨花的雌蕊”(《马缨花》)。在《江山或每人的侧影》中她写道:“男人死于江山/女人死于爱情”。在冯娜看来,男人与女人之于爱情的真相,即是如此。在冯娜的诗中,爱情保留着优雅的疯狂与理想,有一笔文艺,有一笔成熟,又有一笔清新。
然而,冯娜诗中目前最能奠定与证明她诗歌能力的作品,当属近年来诸多以抽象的哲理与命运与时间等为内容的诗歌作品,如11、12年的《红桃A》、《私人心愿》,13年的《如何……》、《黃夜》、《乡村公路上》、《乘船去孤山》,14年的《春天的树》,以及《词语》等等。从内容上,这些诗作由外部转向对内在的深入,由平流的风景转向起伏的深刻,由外在的感知,转向对内质的追寻。这一转向,或许便是所谓“经验”写作的伊始。这一行为,让诗作本身就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并非人人都可驾驭。而诗歌中字句的张弛有度,简洁丰富,也可以见出诗人对语词更为优秀与进步的控制力,和作品更为成熟的诗风。在《私人心愿》中,作者已在谈论光明,庙宇(信仰),死亡,分离,生命……这些人类间的共鸣。在《黃夜》中她写道:"大西洋用水重复它的夜/我在另一个人的头上看见你发间的白霜/……/苍老是比死亡更有耐心的/……/而这夜/是一枚投入泉眼的硬币/老人们到死的时候还惦记着/——不能把运气一下子用光”。这是在深夜谈论死亡。在冯娜14年的几首新作中,这些谈论显得更为成熟与自如。如《春天的树》,即便仍是以植物为写作对象,此时的冯娜在融合对恋情的感知和玄想后,生发出了一些人类生命中对于恋爱之初的情感共性,由此,春天的树已不仅是具备神灵气质的植物,而是具有爱情之初的本质与流变的象征意义。在语言上,也具有一种更为高能的碰撞和迸发。而《词语》一诗则更为抽象,在这里,冯娜开始谈论符号——词语的意义。这或许是诗人在这么长久的写作中对于自己的文字进行的一场抒情和总结,而这样的总结往往意味着一个阶段的回顾,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启。
这些具有哲学和人类命运层度的诗作,对冯娜诗歌的第三重生命形式进行了更高意义上的升华。从这一角度,或许冯娜正将从一个“体验”的写作,过渡到更为纯粹、流畅的“经验”中去。而当下这些刚令读者们感到惊奇的、渐渐难以追逐的诗歌,大概正是冯娜诗歌未来更多重生命形式的新开始!
“牛羊藏在草原的阴影中
巴音布鲁克我遇见一个养鹤的人
他有长喙一般的脖颈
断翅一般的腔调
鹤群掏空落在水面的九个太阳
他让我觉得草原应该另有模样”
这位来自云南的白族女诗人,就如同这些诗句,如同那群被寻找的鹤,翩然而至,降落在诗歌的高原之上。
《寻鹤》一诗,窃以为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无论是富含游牧气息的“牛羊”、“草原”这些意象,区别于汉语音系的“巴音布鲁克”这个地名,抑或神秘如通灵者的“养鹤人”这份古老的职业,都体现着冯娜诗歌中明晰且浓厚的地域特色——云南。在冯娜的诗中,这些云南意象俯拾皆是,构成了一个意象群,而这些意象群中所具有的真正的云南精神气质,又得以组成她的诗中一批具有真正风情的“云南诗群”。《寻鹤》一诗,从词语的表面肌理到语句间弥漫的意境,从诗艺到内质,都体现出云南情致的饱满和一致,又具有对云南般爱情的探寻,使得它得以成为冯娜“云南诗群”中的一种典范。这些优秀的云南诗群给冯娜的诗作抹上浓烈的地域色彩。《寻鹤》、《澜沧江》、《云南的声响》、《沿着高原的河流》等一批诗作,构架了冯娜诗中令人神往的另一个空间,那里弥漫着浓郁且典型的云南况味,栖息着聪颖的自然生灵与少数民族的契约。而你也不得不把冯娜一这位自如地呈现这一切的诗人,与那个充满灵性与秘密的地方紧密相连。“云南诗人”就这样成为她所惯有的标签。
然而,仅以地域解冯娜,或许会遗失她诗歌中的另一些广阔与丰富。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一位天生有灵性的母亲,天生孕育有灵性的灵魂。它为这些灵魂打开感知世界万物的能力,并成为其感知之旅的起点。然而,感知之旅一旦开启,决不会仅局限于出发地。细读冯娜的诗歌,可以发现其对世界多种角度和层面的感知与探寻。它们在诗歌中各自独立地存在,并都具备蓬勃的内蕴和生发。它们构成了冯娜诗歌中的多种生命形式。
好的诗歌必定产生于诗人对万物生动而深入的感知,这种感知得益于诗人的天赋,并决定了他们与世界独特的交流方式。冯娜正是一个具备独特感知天赋的人。在诗歌中,这天赋则体现为诸多意象所具备的一种神灵气质与生命形式。而这些“神灵”们,便形成了她诗歌的第一种生命形式。冯娜善于以拟人与联想相结合的方式,赋予山川河流,花鸟虫鱼,草树木甚至是平凡的物件以灵魂和感知力。它们以人的形态发声,具备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它们或见证人类的人生,或自身便拥有丰沛的经历与情感。她在《莲花》中写道:“一卷经书放在窗上夜里感到寒冷”。这是经书日常的遭遇。在《龙山公路旁小憩》中:“近处有松树苦楝树我不知道名字的阔叶树/它们高高低低交错生长又微妙地相让”。这是属于所有树木们的契约。《龙山坝的夜》中她写:“黄昏过后/坝子的尽头无数星辰将要分娩”。这是接近神的意志。这样的诗句在她的诗集中俯拾皆是。《夜过增城》中:'‘粤水怀有十二个罗汉的慈悲/荔枝因为一个人缺席而推迟成熟”;《卡若拉冰川》中:“在山上你在苔薛间按灭烟蒂/大地轻轻颤栗了一下/所有云朵都动荡不安”;《晚安》中:“大病初愈的月光白戚戚地并膝坐在台阶上”。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时,都无法不被这样的句子触动到自己恻隐的触角。这些诗句已然不是简单的拟人手法便可轻易制造,动人的诗句中藏匿的向来是属于诗歌内部的生命,而这生命诞生于一个有思想、有天赋的诗人的真挚与情意。一个眼中万物皆有灵的诗人,或许已掌握了与这个世界交流的秘密。她给予世间一切的万物以同等的目光,注视和平等相待,世间万物便是她的旅伴。这些神灵穿梭在冯娜诗句的字里行间,让一本诗集于沉静而无人的语言中见出丰沛的魂魄。又或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诗集中的冯娜在日常的行走中,寻找到千万个藏匿于万物的另一个自己。此时,她本人就是云南(或更多大千风光)之中的一部分,是万千“带着翅膀的事物”之一(《如何遇见带翅膀的事物》)。
冯娜惯于以这种方式,将自己化入自然万物之中,倾听它们的故事,承担它们的情绪。这些有灵魂的生灵,一类体现为旁观世间的崇山静水,它们像生长了千万年的长者,却不曾失去过锐觉和生机,每年春天,它们都重复拥有青春。如冯娜在《群山》中写道:
“群山涉水多年而不渡
蜂巢引发耳鸣 这寂寞忽远忽近
春天随之带来痼疾
迫使大地拧开胶囊中的粉末
相互传染的痒
让它们遍体花束 如象群的墓冢”
韩作荣曾在《候车室》一诗中这样写:“只有椅子稳重地站立着/有腿而不远行/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过客”,二者在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群山在“不渡”的静态中,对比“涉水”和他人的“渡”两种动态;椅子在“不远行”的静态中,对比“有腿”和他人的“远行”两种动态,二者都在动与静的二重对比中,形成时间的长度和旁观的姿态,并产生一种绝妙的回响,给人以忘年之感。在挨弃时间的轮回之后,于群山而言,春天是每年必染的一样“痼疾”,浑身开满鲜花是周期性过敏般的症状,让人不禁感觉有花在肌肤上盛开,而读者则得以拥有身为群山的体验,这是此诗的妙处。又如《龙山的女儿》:“龙山在干净渐暖的风中白发簌簌凋零/我看着他流尽整座山峦的眼泪”,龙山的款款深情同样在四季变迁中同步地表露端倪。在《菩提树》中她写道:“第一次路过它们用手碰了碰树干/植物的回应是一只受惊的鸟……我们都一屁股坐在它的脚趾上”;在《金沙江》中她写道,那块“黑色的礁石”,是“我静静没入水中殉情的女人”(诗人的二个远方姐姐殉情于金沙江)。在诗人笔下,这些自然景物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秘密。在大千世界中,它们或许为冯娜这样的人所关注,或许更多的是被熟视无睹,但这都无碍于它们生活的丰富,晏如,与世无争。而冯娜的书写,得以为读者搭建彼此感知的桥梁。
冯娜诗中的有一类生灵,与女人具有特殊的联系。在《桂花树》中,桂花树脱离了单纯的植物形态,而是娴静而隐忍的女人,怀有女性的羞涩和端庄,具有天下女人普遍怀有的苦楚和忍耐。桂树传说生长于月亮,月亦是女性的象征。诗人眼中,她们原本都是来自月亮的纯洁之物。然为何被贬下凡去了?生长在凡间的泥土中,从此怎么也去不了那“趾缝里泄漏的泥腥气”。何时不曾想返乡呢,在这里,她们把梦和念想隐藏得很深,隐姓埋名,你我谁会记得把它和遥远的月相关联,香气四溢时,人们只当作是她的美满,理所当然;她亦把苦楚只留给自己,独自忍受从来是女人应备的品德。大地上的女人们,何尝不是把万千的美好和远行的梦都拾掇好,在归作别人家后,忙碌于市井庸常,只在无人的夜中,追忆心之所向。桂花树正是天下女性这些最典型又最为动人的形态。冯娜也曾在《在生命里》写道:“我窥探一株植物的奥秘一个女人的魂灵/它们的肌肤雷同/高贵脆弱如死之静谧和坚强”。植物和女性在灵魂上的相通之处可见一斑。
每个地域的诗人,尤其是来自少数民族的诗人,或许都带有书写家族的使命感。冯娜本人是白族人,按她的话说,她的母亲“属于典型的白族女人”,她的祖辈“怀揣许多迁徙琉璃的故事”。冯娜诗歌中来自云南深处的传说和风俗,构成了第二种生命形式。冯娜曾在2013年的组诗《他耳普子情歌》集中描写了白族的一些风俗和往事。那些祝酒词、巫师、族谱、牧歌、祭司、水鬼……是不为人所熟知的、神秘的生命群体。他们存在于云南深处。而在冯娜的诗歌中,他们并不讳莫如深,而是以性格中的生机、深情、隐忍、热情、誓言与人形成共鸣。在《一个白族人的祝酒辞》诗中,三行排比句见出白族人的豁达和热情,在命运与他留河的交互中见出这一民族对人生的洞然。在《晨歌或风水》中,山水,晨雾,太阳和雪山,牛羊和晨起洗漱,这是他留人安宁的生活图景。他留人的河流被冠以种族的名字《他留河》,河水是他留人流淌的根脉,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留下彼此依存的深情。在他留人中,象征爱情的是马缨花(《马缨花》:我的爱情藏进马缨花的雌蕊)。他们的婚礼有陶罐、铜镜、黑蛇和族谱(《夜歌》)。族人间饮酒时,上前斟酒如“手持一把柯尔特手枪”,醉酒时如豹子“应声倒地”般壮硕(《与彝族人喝酒》)。而他留人的牧歌里,唱着"世间的猛兽良禽虫豸”(《他留人牧歌》)。这一民族群体的生命形式,是具有勃勃生机的。
冯娜诗歌中的第三种生命形式,则是以她自身的情感与思索为基点,探寻人类生命的一些共性。在2014年9月王威廉对冯娜的釆访中,她提到:“一个诗人各个成长阶段的诗歌理应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我愿意看到它缓慢沉着,自觉但不刻意的变化。……近年来,我将目光投向这些情感记忆在现实中的际遇、在人类命运中的共鸣、在时间中的恒定和变幻,试图获得一种更新的、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眼光。”冯娜近几年的创作中,逐渐岀现了区别于之前的诗作。
冯娜的一首献给父亲的诗《隔着时差的城市》曾在多处被刊登。她也曾在公众诗歌活动中朗诵了这首诗。这是冯娜仅有的六首献诗(《九月,是写献诗的季节(组诗)》)中的一首,可见她对父亲的情感。诗中所包含的真挚,读来让人心疼。“父亲,我是否应该将光阴对折/剪去那些属于南方的迷/……/我有你盛怒之下的灰烬/你何尝想过吧,成为-个女人的父亲是如此艰辛”。一个长大后的女儿在重解当年与父亲的心结时,会承担更多的感喟。“父亲,额尔齐斯河的水一直往下流/一个又一个迁徙者的命运/我和你一样,竟没有把多余的爱憎留在岸上”。当女儿成长到能够与父亲一同谈论今生的命运,彼时白发对青丝,竟发现自己这一生的秉性和道路,从父辈就已有预示和痕迹——代代注定把多余的爱憎携带一生。在“目光呆滞,默不作声"的沉默中,那弥漫着的宿命感无关悲伤,反而是亲情间的相互呼应和抚慰。在岁月里与父亲逐渐达到同歩、甚至超越的过程中,亲情愈加丰富厚重,几近迫人心痛。一句句的“父亲”,如若呼唤。在2013年,冯娜又写了一首《与父亲掰手腕》:“我不能察觉他在老去/我不能总让他赢/我必须伺机在他突然的疏忽中/扳回一局”。诗歌里,在女儿与父亲角色对调的过程中,有一种轻柔的、童趣的、温情的爱。冯娜也有过写母亲的诗。在《母亲》一诗中,她重复写道:“她经历许多,来做我的母亲”。在一次次的反复中,显现的是对母亲不易的了然,和无以言说的感恩。而在诗句中可以看出,冯娜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铺展,只消这样的一句恰好的概述,就已足够让人懂得那些无力多说,也不必多说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概述背后,必定是冯娜长久的感知和富有洞察力与穿透力的眼光。在《接站的母亲》中,她写道:“每一趟车都掠起一阵风/只有她不被吹拂/……/我站在天空底下/一只鹰沉默地飞向旗云/它的心事我都听见”。冯娜的诗歌中,亲情仿佛平静且不动声色,不具有特殊性或戏剧性。然而,以平静之力所表述出的亲情中的永恒一面,却更能摇动万千人的心灵。
冯娜诗中自然也不乏爱情。《橙子》一诗可谓是小巧玲珑而韵味丰满。“我舍不得切开你艳丽的心痛/粒粒都藏着向阳时零星的甜蜜/我提着刀来/自然是不再爱你了”。全诗仅四句,如刀一般短,然而刀中有爱与不爱的秘密。在《生活》中,冯娜看到爱情让女人做梦、沉醉,自我欺骗与自我宽慰彼此相互颠而复使。在《隐居》中她写道:“你静静走着也不问起我/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隐居——/活在你的爱里却从不现身”。这是爱情假想者所向往的爱情模式的一种。此外,在她的笔下,也出现过别人的爱情。如《白蛇》中:"……白蛇/你拿几百年修行来做美人/和我在下午怀念面容模糊的旧情人/一样光阴虚掷”。这是一针见血的自我解嘲,又是必然的义无反顾。而族人间的爱情,会"藏进马缨花的雌蕊”(《马缨花》)。在《江山或每人的侧影》中她写道:“男人死于江山/女人死于爱情”。在冯娜看来,男人与女人之于爱情的真相,即是如此。在冯娜的诗中,爱情保留着优雅的疯狂与理想,有一笔文艺,有一笔成熟,又有一笔清新。
然而,冯娜诗中目前最能奠定与证明她诗歌能力的作品,当属近年来诸多以抽象的哲理与命运与时间等为内容的诗歌作品,如11、12年的《红桃A》、《私人心愿》,13年的《如何……》、《黃夜》、《乡村公路上》、《乘船去孤山》,14年的《春天的树》,以及《词语》等等。从内容上,这些诗作由外部转向对内在的深入,由平流的风景转向起伏的深刻,由外在的感知,转向对内质的追寻。这一转向,或许便是所谓“经验”写作的伊始。这一行为,让诗作本身就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并非人人都可驾驭。而诗歌中字句的张弛有度,简洁丰富,也可以见出诗人对语词更为优秀与进步的控制力,和作品更为成熟的诗风。在《私人心愿》中,作者已在谈论光明,庙宇(信仰),死亡,分离,生命……这些人类间的共鸣。在《黃夜》中她写道:"大西洋用水重复它的夜/我在另一个人的头上看见你发间的白霜/……/苍老是比死亡更有耐心的/……/而这夜/是一枚投入泉眼的硬币/老人们到死的时候还惦记着/——不能把运气一下子用光”。这是在深夜谈论死亡。在冯娜14年的几首新作中,这些谈论显得更为成熟与自如。如《春天的树》,即便仍是以植物为写作对象,此时的冯娜在融合对恋情的感知和玄想后,生发出了一些人类生命中对于恋爱之初的情感共性,由此,春天的树已不仅是具备神灵气质的植物,而是具有爱情之初的本质与流变的象征意义。在语言上,也具有一种更为高能的碰撞和迸发。而《词语》一诗则更为抽象,在这里,冯娜开始谈论符号——词语的意义。这或许是诗人在这么长久的写作中对于自己的文字进行的一场抒情和总结,而这样的总结往往意味着一个阶段的回顾,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启。
这些具有哲学和人类命运层度的诗作,对冯娜诗歌的第三重生命形式进行了更高意义上的升华。从这一角度,或许冯娜正将从一个“体验”的写作,过渡到更为纯粹、流畅的“经验”中去。而当下这些刚令读者们感到惊奇的、渐渐难以追逐的诗歌,大概正是冯娜诗歌未来更多重生命形式的新开始!
相关人物
周小琳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