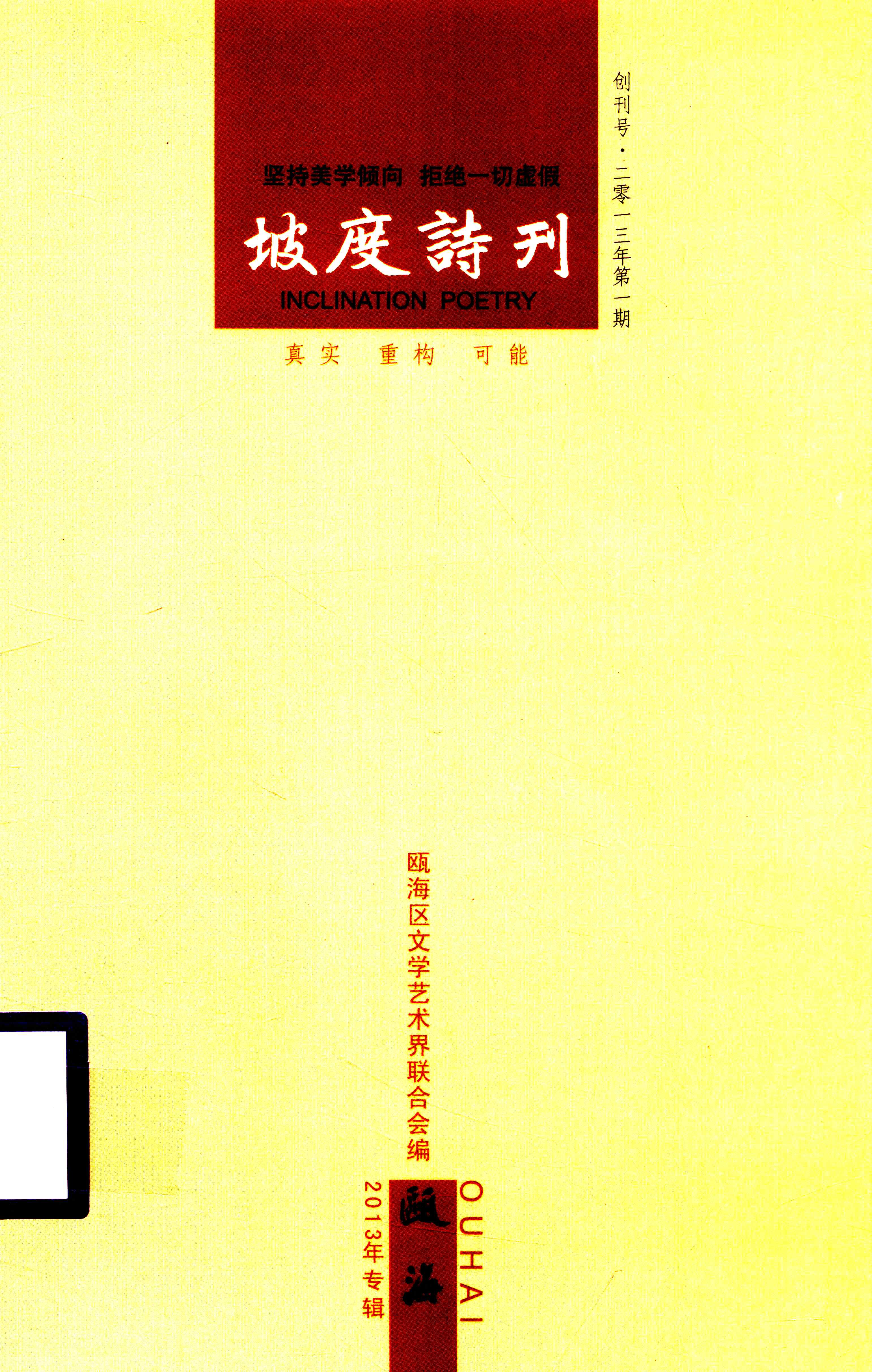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察:温州的诗人是安静的,他们关注诗歌,不大参与诗歌活动。诗歌是他们所有的诗歌活动。
但这次,诗歌活动来了。
青年诗人郑仁光把这一次活动的诗歌汇集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嘱我写一些文字,着实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一则,这些年来,我只是动口,几乎没有动过笔或者键盘,关于诗歌的动口,也只在我的课堂上;再则,除了马叙池凌云慕白的诗歌,我也没有看过更多的其他温州诗人的诗作。现在,我只能说,郑仁光的固执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让我“两手空空”也可以“混在你的宾客之中”,一如夏鼎铭在《为什么太阳在白昼而月亮在夜晚发光》所写。
“为什么太阳在白昼而月亮在夜晚发光”?这是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吗?不,它首先不是个问题,这只是诗歌的一种说话方式。在我看来,这样的诗歌说话方式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足以确认在这个仪式上的所有言说,使得“诗人和读者都会以一种极细微但又很本质的方式远离发生过的事情,失去正在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感觉。”(谢尔摩·希尼)我想,诗歌活动也可以达到希尼说的小细节——这古老的诗歌技术遗迹——的作用。它将召唤出所有对这种“仪式”有记忆的人。郑仁光介绍说,这次诗歌活动将是努力汇集温州诗人的一次聚会。说这话时,
他的身上仿佛流动着古老的酒杯,有一股“兰亭”气息。奥登说:“在任何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背后,都有三个主要愿望:制造某种东西的愿望;感知某种东西的愿望:还有跟别人交流这些感知的愿望。”一场诗歌聚会,无疑,就意味一场诗歌“感知”的酒杯四处碰撞的历程。这次聚会的所有的“酒”——诗歌,现在都摆在我的面前。实在是该谢谢这种固执的美德,使我提前畅饮这次诗歌盛宴的美酒。
耶鲁学者哈罗德·布罗姆说:“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当然,这位精湛的诗歌阅读者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比喻性的修辞。他看中的不是“比喻”,而是诗歌语言基于比喻“锋利”。在我看来,一首诗歌如果拥有“锋利的词语”,它就会给阅读者带来“词语的疼痛”。比如诗人池凌云的诗歌《玛丽娜在深夜写诗》
在孤独中入睡,在寂寞中醒来
上帝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玛丽娜
你从贫穷中汲取,你歌唱
让已经断送掉的一切重新回到椅子上。
你把暗红的碳火藏在心里
像一轮对夜色倾身的月亮。
可是你知道黑暗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眼睛除了深渊已没有别的。
没有魔法师,没有与大海谈心的人
亲爱的,一百年以后依然如此
篝火已经冷却。没有人可以让我们快乐
“人太多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
为此我悄悄流泪,在深夜送上问候。
除此之外,只有又甘甜又刺痛的漆黑的柏树
只有耀眼的刀尖,那宁静而奔腾的光。
显然,这首诗歌首先是池凌云对自己的“前驱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致敬。诗人和她的前驱诗人之间的纠葛关联,布罗姆在他的《影响的焦虑》里有很好的阐释,我就不多说了。我所着迷的是“宁静而奔腾的光”
这样的锋利词语。我以为,它是一种直抵光的本质的表达——光的本质就是“宁静和奔腾”的;正是这样对光的本质抵达的词语,使得“光”从我们混沌的日常经验中被召唤出来了。本质性的光一旦被召唤出来,世界之暗就得以敞开和澄明,从而我们才能知晓“黑暗是怎么一回事”。托马斯·卡莱尔说“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或者更可以说,未曾知悉光的人,不足以语暗夜。所以此“宁静而奔腾”同时使得世界之暗和世界之光涌现,从而诗人在暗夜的“悄悄流泪”也得到了根基;那些“已经断送掉的一切”也可以“重新回到椅子上”。这丰盛的修辞,使得诗和思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无法将这两种过程分
开。不能不说池凌云的这首小诗拥有“微妙的感性”和“完整的品质”的美德。
词语的锋利,其本质上可看成是现代诗自兰波以来所要求的“新语言”使然。考虑到布罗姆的耶鲁背景,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形式主义诗歌批评常常提到的“词语的陌生”。在他们看来有“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张力”可以带来“震惊”(Shock)。要知道“震惊”在兰波之后已经是现代诗学的一个专门术语。不过,在我看来,诗歌词语的锋利性说法,现在已经很“寻常”了。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可能在“即事名篇,无所依傍”的寻常之中成为诗人的常识。
我很不安,诗人马叙的《浮世集》还没有完整的看过,这委实是我的过错。但即便是对马叙诗歌的有限阅读,也使得我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位诗人的沉稳。我判断,马叙大概只有带着强大的自信和平静,才有可能走进《浮世集》这样的断片性质的写作。要知道,《浮世集》这样的命名,已经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隐喻背景,邀请进了诗歌。但这样的命名,也同时宣告了世界的碎片性。也就是说“浮世集”这样的命名,首先就暗示了这是“一个无限补缀而成的作品”;同时它也意味着这部作品的“未完成性”。在这种碎片性质的写作中,“世界作为采样:样本是一些特性,是从一系列普通的成分中提取出的显著而且不能被总体化的局部。”只有这样“浮世集”才可能保证“世界作为异质性的各个部分成为一个集合”(吉尔·德勒兹)显然,如果写作者对世界的碎片
性没有很好的体验,这样的写作是危险的。因为,它极有可能将世界作
为“哲理对象”,从而诗歌变成格言,成为冰心的《春水》《繁星》式的格言小集,作为整体的背景世界被低践。马叙不是冰心!我所阅读到的《浮世集》,没有格言。
他远远地走来,三月,他的形象春天一样塌陷。
他身边的那么多小事物也都分别穿上了春天的衣服。
他塌陷,它们也跟着塌陷。
这些春天的衣裳,靓丽,混乱,淫荡,虚无。
它们被一阵清风带向云端。
他只带一副骨架走进夏天。
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他因此更多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墨汁。
他伸进手。触及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
那里,一个沉睡已久的事物跳起来
——此时,他已经漆黑一团
“他塌陷,它们跟着塌陷。”这样的句子,可以保证在这样的碎片性质的写作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被发明出来。当然,在这首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歌信徒的马叙,一如既往地辨认出了现代世界的黑暗性和荒诞感。“世界就这样告终/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嘘的一声”(艾略特《空心人》),塌陷得毫无悲壮感,只有日常生活的庸常性。整个《浮世集》“即事名篇,无所依傍”的寻常自有它的不寻常。“他只带一副骨架走进夏天”,大概只有落尽浮世上的“浮华”,才有可能让这幅“骨架”“漆黑一团”。
按照惯常的理解,诗歌的工作常常会帮助我们“成为自己的自由艺术家”(布罗姆)。所谓“成为自己的自由艺术家”,就是体验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去完成它。马叙这只诗歌的“鳄鱼”现在已经从“渐渐稀薄”的“晨雾”中,“从水中爬出”,“聚合一生的事件”,去完
成他“冷静、质朴的第二次显现”。(马叙《鳄鱼醒来》)
在我看来,诗歌的工作也是一次次的生活训练。在这些训练中,熟
了诗歌,成了诗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有限的赞同诗歌艺术来源于生活的陈旧的判断。但生活的芜杂不可以直接进入诗歌,哪怕是依托着“抒情”这个古老的诗歌技艺。我曾私下里思考过“朦胧诗”的流弊,觉得当代诗歌的写作应该告别“喉咙”的歌唱性质,不必要在诗歌里刻意寻求“刻在石头上的诗句”。要知道“写在沙子上的诗句”,足可见证海边嬉戏的纯粹。“刻在石头的诗句”是灵魂通神后的启示,“写在沙子上的诗句”也是人与世界的亲在的敞开。
写一首诗,有些时候是因了一句“刻在石头上的诗句”。然后左冲右突,渐渐打开。这样的写作常是“苦吟”。“苦吟”当是对诗歌的敬意,它本身就是对诗歌这种“神圣的文字艺术”的一种宗教般的情怀。故此,这种“从一个句子开始”的写作,也惯会产生令人敬畏的诗歌。比如郑仁光的那首《病中代书》:
再见,陌生人
在愚昧和惯性支配的世界
你们一如街市上哭泣的婴童
盲目的人无所不知
他们尚有勇气试探幽暗
我住在人世下游,自甘堕落之乡
行过险恶,只希望和死相见不会太晚
诗人海子曾说:“回忆和遗忘都是久远的。对着这块千百年来始终沉默的天空,我们不回答,只生活。这是老老实实的,悠长的生活。磨难中句子变得简洁而短促。”“我住在人世下游”,就是这样“简洁而短促”。要多么久的幽暗以及多大的从这幽暗游出的勇气,才会得到这样灾难性质的句子的亲赖。
比起这些灾难性质的诗歌,我比较愿意看到那些“写在沙子上的诗句”。“写在沙子上的诗句”,在我看来,可以接通卡尔维诺说的“未来艺术”“轻”的本质。在他看来,“重”来源于“轻”,“沉重的世界是建立在微尘之上”。诗人的言此及彼的轻言反讽,极可能撬动世界,但也可能加固世界之基。布罗姆举例说:“我们听到哈姆雷特说‘我谦
卑地感谢你’或之类的话的时候会不寒而栗,因为这位王子毫无谦卑和感激的意思。”
这一次汇集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不寒而栗”的“轻”,比如花药兰,比如部分的星落河,和部分的卓铁锋。
以致
世界成为一坨黏稠的液体
并虚构出我的生活
就如梦中的鱼
飞翔于水偶尔露出
梦外的一个头颅(花药兰《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客人》)
某种意义上,世界开始于男性的那一坨黏稠的液体(精液);男权世界的基础也就是建立在这黏稠的液体之上。但当“世界成为一坨黏稠的液体”之后,被虚构出来的“露出来的头颅”就不再是梦之轻了。
世界之“轻”,也在灰烬上。诗人海子有诗:“我已走到人类的尽头/那里是一片灰烬”;我曾和诗人池凌云谈论过她的诗歌里的“灰烬”意象,说“灰烬是火的遗迹”。后来者得以从灰烬中知晓那里曾经有过燃烧,有过炙热的篝火。这一次汇集的“九山诗人”的诸多诗篇就可以看成是曾经燃烧过后的灰烬。今天阅读九山诗人的这些诗歌,我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在九山湖畔曾经炙热的燃烧。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曾经是那么近的接近了同时代的高峰,现在却星散在各处。也许,诗歌可以在这些逐渐冷却的诗篇上认证:“诗歌即是青春之战”,只是任谁也没有想到,这战争会挥霍掉那么多的勇气和荣耀。
不过,温州年轻的诗人大概还是比较习惯于“歌唱”。歌唱固然会撩人心绪,但歌唱的又会因了调子的缘故,不知不觉地会使诗句缠绕。新诗人废名在谈到自由诗的时候,特地指出一个“滑”字。他认为,由于自由诗没有一般旧体诗的形式上的约束,可以自由的来写。但这种自
由的来写,对于自由诗的天才诗人来说,“有时反而不能加以帮助,好
比冰场上溜冰一样,本来是没有阻碍的,但滑就是阻碍,随便的滑一下,
自己觉着,别人也看着你滑一脚了,好像气力不够似的。”废名的这些
话,诚是见道之言。
这雨水磅礴狂风肆虐的夜
没有鲜花,没有爱情,没有雪
山路似乎一条隐秘的时空隧道
沿永远的河流盘旋上山
沿古老的村庄慢行至灵魂暗处
沿我沉睡的记忆到达你
一千棵轻舞的草木飘扬
一千种悦耳的鸟鸣婉转
一千朵蘑菇在深厚的植被里繁衍
一千羽蒲公英夜风中飞翔
——在山谷,展开记忆
像黝黑的岩石展开山的重量
诗人朱淑洁的这首《四海山之夜》,第一句“这雨水磅礴狂风肆虐的夜”,神完气足。第三节的几句也可观。似乎她没有注意到“这雨水磅礴狂风肆虐的夜”,本就渊渟岳峙,来不得半点拖沓,诗歌的第二节的“滑”,让这首诗歌变得“不完全”了。或许正是这种“不完全”,才可能让诗人“继续生长”。祝福那些还在写诗的人!
但这次,诗歌活动来了。
青年诗人郑仁光把这一次活动的诗歌汇集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嘱我写一些文字,着实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一则,这些年来,我只是动口,几乎没有动过笔或者键盘,关于诗歌的动口,也只在我的课堂上;再则,除了马叙池凌云慕白的诗歌,我也没有看过更多的其他温州诗人的诗作。现在,我只能说,郑仁光的固执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让我“两手空空”也可以“混在你的宾客之中”,一如夏鼎铭在《为什么太阳在白昼而月亮在夜晚发光》所写。
“为什么太阳在白昼而月亮在夜晚发光”?这是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吗?不,它首先不是个问题,这只是诗歌的一种说话方式。在我看来,这样的诗歌说话方式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足以确认在这个仪式上的所有言说,使得“诗人和读者都会以一种极细微但又很本质的方式远离发生过的事情,失去正在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感觉。”(谢尔摩·希尼)我想,诗歌活动也可以达到希尼说的小细节——这古老的诗歌技术遗迹——的作用。它将召唤出所有对这种“仪式”有记忆的人。郑仁光介绍说,这次诗歌活动将是努力汇集温州诗人的一次聚会。说这话时,
他的身上仿佛流动着古老的酒杯,有一股“兰亭”气息。奥登说:“在任何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背后,都有三个主要愿望:制造某种东西的愿望;感知某种东西的愿望:还有跟别人交流这些感知的愿望。”一场诗歌聚会,无疑,就意味一场诗歌“感知”的酒杯四处碰撞的历程。这次聚会的所有的“酒”——诗歌,现在都摆在我的面前。实在是该谢谢这种固执的美德,使我提前畅饮这次诗歌盛宴的美酒。
耶鲁学者哈罗德·布罗姆说:“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当然,这位精湛的诗歌阅读者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比喻性的修辞。他看中的不是“比喻”,而是诗歌语言基于比喻“锋利”。在我看来,一首诗歌如果拥有“锋利的词语”,它就会给阅读者带来“词语的疼痛”。比如诗人池凌云的诗歌《玛丽娜在深夜写诗》
在孤独中入睡,在寂寞中醒来
上帝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玛丽娜
你从贫穷中汲取,你歌唱
让已经断送掉的一切重新回到椅子上。
你把暗红的碳火藏在心里
像一轮对夜色倾身的月亮。
可是你知道黑暗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眼睛除了深渊已没有别的。
没有魔法师,没有与大海谈心的人
亲爱的,一百年以后依然如此
篝火已经冷却。没有人可以让我们快乐
“人太多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
为此我悄悄流泪,在深夜送上问候。
除此之外,只有又甘甜又刺痛的漆黑的柏树
只有耀眼的刀尖,那宁静而奔腾的光。
显然,这首诗歌首先是池凌云对自己的“前驱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致敬。诗人和她的前驱诗人之间的纠葛关联,布罗姆在他的《影响的焦虑》里有很好的阐释,我就不多说了。我所着迷的是“宁静而奔腾的光”
这样的锋利词语。我以为,它是一种直抵光的本质的表达——光的本质就是“宁静和奔腾”的;正是这样对光的本质抵达的词语,使得“光”从我们混沌的日常经验中被召唤出来了。本质性的光一旦被召唤出来,世界之暗就得以敞开和澄明,从而我们才能知晓“黑暗是怎么一回事”。托马斯·卡莱尔说“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或者更可以说,未曾知悉光的人,不足以语暗夜。所以此“宁静而奔腾”同时使得世界之暗和世界之光涌现,从而诗人在暗夜的“悄悄流泪”也得到了根基;那些“已经断送掉的一切”也可以“重新回到椅子上”。这丰盛的修辞,使得诗和思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无法将这两种过程分
开。不能不说池凌云的这首小诗拥有“微妙的感性”和“完整的品质”的美德。
词语的锋利,其本质上可看成是现代诗自兰波以来所要求的“新语言”使然。考虑到布罗姆的耶鲁背景,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形式主义诗歌批评常常提到的“词语的陌生”。在他们看来有“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张力”可以带来“震惊”(Shock)。要知道“震惊”在兰波之后已经是现代诗学的一个专门术语。不过,在我看来,诗歌词语的锋利性说法,现在已经很“寻常”了。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可能在“即事名篇,无所依傍”的寻常之中成为诗人的常识。
我很不安,诗人马叙的《浮世集》还没有完整的看过,这委实是我的过错。但即便是对马叙诗歌的有限阅读,也使得我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位诗人的沉稳。我判断,马叙大概只有带着强大的自信和平静,才有可能走进《浮世集》这样的断片性质的写作。要知道,《浮世集》这样的命名,已经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隐喻背景,邀请进了诗歌。但这样的命名,也同时宣告了世界的碎片性。也就是说“浮世集”这样的命名,首先就暗示了这是“一个无限补缀而成的作品”;同时它也意味着这部作品的“未完成性”。在这种碎片性质的写作中,“世界作为采样:样本是一些特性,是从一系列普通的成分中提取出的显著而且不能被总体化的局部。”只有这样“浮世集”才可能保证“世界作为异质性的各个部分成为一个集合”(吉尔·德勒兹)显然,如果写作者对世界的碎片
性没有很好的体验,这样的写作是危险的。因为,它极有可能将世界作
为“哲理对象”,从而诗歌变成格言,成为冰心的《春水》《繁星》式的格言小集,作为整体的背景世界被低践。马叙不是冰心!我所阅读到的《浮世集》,没有格言。
他远远地走来,三月,他的形象春天一样塌陷。
他身边的那么多小事物也都分别穿上了春天的衣服。
他塌陷,它们也跟着塌陷。
这些春天的衣裳,靓丽,混乱,淫荡,虚无。
它们被一阵清风带向云端。
他只带一副骨架走进夏天。
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他因此更多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墨汁。
他伸进手。触及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
那里,一个沉睡已久的事物跳起来
——此时,他已经漆黑一团
“他塌陷,它们跟着塌陷。”这样的句子,可以保证在这样的碎片性质的写作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被发明出来。当然,在这首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歌信徒的马叙,一如既往地辨认出了现代世界的黑暗性和荒诞感。“世界就这样告终/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嘘的一声”(艾略特《空心人》),塌陷得毫无悲壮感,只有日常生活的庸常性。整个《浮世集》“即事名篇,无所依傍”的寻常自有它的不寻常。“他只带一副骨架走进夏天”,大概只有落尽浮世上的“浮华”,才有可能让这幅“骨架”“漆黑一团”。
按照惯常的理解,诗歌的工作常常会帮助我们“成为自己的自由艺术家”(布罗姆)。所谓“成为自己的自由艺术家”,就是体验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去完成它。马叙这只诗歌的“鳄鱼”现在已经从“渐渐稀薄”的“晨雾”中,“从水中爬出”,“聚合一生的事件”,去完
成他“冷静、质朴的第二次显现”。(马叙《鳄鱼醒来》)
在我看来,诗歌的工作也是一次次的生活训练。在这些训练中,熟
了诗歌,成了诗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有限的赞同诗歌艺术来源于生活的陈旧的判断。但生活的芜杂不可以直接进入诗歌,哪怕是依托着“抒情”这个古老的诗歌技艺。我曾私下里思考过“朦胧诗”的流弊,觉得当代诗歌的写作应该告别“喉咙”的歌唱性质,不必要在诗歌里刻意寻求“刻在石头上的诗句”。要知道“写在沙子上的诗句”,足可见证海边嬉戏的纯粹。“刻在石头的诗句”是灵魂通神后的启示,“写在沙子上的诗句”也是人与世界的亲在的敞开。
写一首诗,有些时候是因了一句“刻在石头上的诗句”。然后左冲右突,渐渐打开。这样的写作常是“苦吟”。“苦吟”当是对诗歌的敬意,它本身就是对诗歌这种“神圣的文字艺术”的一种宗教般的情怀。故此,这种“从一个句子开始”的写作,也惯会产生令人敬畏的诗歌。比如郑仁光的那首《病中代书》:
再见,陌生人
在愚昧和惯性支配的世界
你们一如街市上哭泣的婴童
盲目的人无所不知
他们尚有勇气试探幽暗
我住在人世下游,自甘堕落之乡
行过险恶,只希望和死相见不会太晚
诗人海子曾说:“回忆和遗忘都是久远的。对着这块千百年来始终沉默的天空,我们不回答,只生活。这是老老实实的,悠长的生活。磨难中句子变得简洁而短促。”“我住在人世下游”,就是这样“简洁而短促”。要多么久的幽暗以及多大的从这幽暗游出的勇气,才会得到这样灾难性质的句子的亲赖。
比起这些灾难性质的诗歌,我比较愿意看到那些“写在沙子上的诗句”。“写在沙子上的诗句”,在我看来,可以接通卡尔维诺说的“未来艺术”“轻”的本质。在他看来,“重”来源于“轻”,“沉重的世界是建立在微尘之上”。诗人的言此及彼的轻言反讽,极可能撬动世界,但也可能加固世界之基。布罗姆举例说:“我们听到哈姆雷特说‘我谦
卑地感谢你’或之类的话的时候会不寒而栗,因为这位王子毫无谦卑和感激的意思。”
这一次汇集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不寒而栗”的“轻”,比如花药兰,比如部分的星落河,和部分的卓铁锋。
以致
世界成为一坨黏稠的液体
并虚构出我的生活
就如梦中的鱼
飞翔于水偶尔露出
梦外的一个头颅(花药兰《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客人》)
某种意义上,世界开始于男性的那一坨黏稠的液体(精液);男权世界的基础也就是建立在这黏稠的液体之上。但当“世界成为一坨黏稠的液体”之后,被虚构出来的“露出来的头颅”就不再是梦之轻了。
世界之“轻”,也在灰烬上。诗人海子有诗:“我已走到人类的尽头/那里是一片灰烬”;我曾和诗人池凌云谈论过她的诗歌里的“灰烬”意象,说“灰烬是火的遗迹”。后来者得以从灰烬中知晓那里曾经有过燃烧,有过炙热的篝火。这一次汇集的“九山诗人”的诸多诗篇就可以看成是曾经燃烧过后的灰烬。今天阅读九山诗人的这些诗歌,我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在九山湖畔曾经炙热的燃烧。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曾经是那么近的接近了同时代的高峰,现在却星散在各处。也许,诗歌可以在这些逐渐冷却的诗篇上认证:“诗歌即是青春之战”,只是任谁也没有想到,这战争会挥霍掉那么多的勇气和荣耀。
不过,温州年轻的诗人大概还是比较习惯于“歌唱”。歌唱固然会撩人心绪,但歌唱的又会因了调子的缘故,不知不觉地会使诗句缠绕。新诗人废名在谈到自由诗的时候,特地指出一个“滑”字。他认为,由于自由诗没有一般旧体诗的形式上的约束,可以自由的来写。但这种自
由的来写,对于自由诗的天才诗人来说,“有时反而不能加以帮助,好
比冰场上溜冰一样,本来是没有阻碍的,但滑就是阻碍,随便的滑一下,
自己觉着,别人也看着你滑一脚了,好像气力不够似的。”废名的这些
话,诚是见道之言。
这雨水磅礴狂风肆虐的夜
没有鲜花,没有爱情,没有雪
山路似乎一条隐秘的时空隧道
沿永远的河流盘旋上山
沿古老的村庄慢行至灵魂暗处
沿我沉睡的记忆到达你
一千棵轻舞的草木飘扬
一千种悦耳的鸟鸣婉转
一千朵蘑菇在深厚的植被里繁衍
一千羽蒲公英夜风中飞翔
——在山谷,展开记忆
像黝黑的岩石展开山的重量
诗人朱淑洁的这首《四海山之夜》,第一句“这雨水磅礴狂风肆虐的夜”,神完气足。第三节的几句也可观。似乎她没有注意到“这雨水磅礴狂风肆虐的夜”,本就渊渟岳峙,来不得半点拖沓,诗歌的第二节的“滑”,让这首诗歌变得“不完全”了。或许正是这种“不完全”,才可能让诗人“继续生长”。祝福那些还在写诗的人!
相关人物
崔勇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