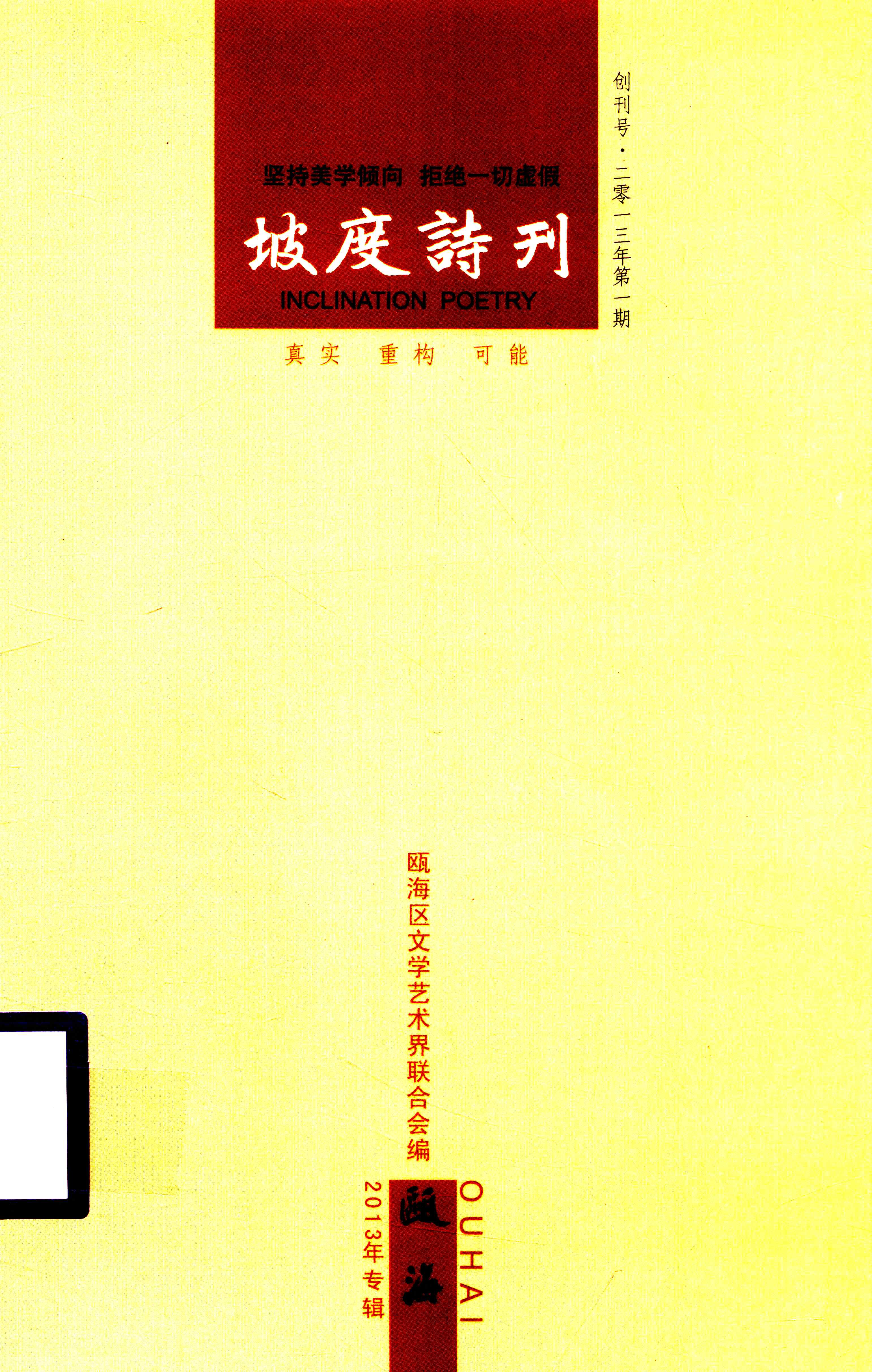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我如何去回答酒桶兄在最近几个文本所呈露出来的清晰和慵懒呢?现在我往往更多地注意到审美形态上的气韵和意境,而对中国更早期审美形态,即“中和”,已有了一种岁月的遗忘。但《物象》所彰显出来的理性,却催促我从更深层次去了解酒桶近期的创作特点和境界。
物象在当下的美学话语习惯中,多数会被纳入“意境说”中的事物,并作为思维空间内的具体对象化构成物。如此,我必须首先分开“意境”和“中和”的区别。中国早期的审美形态是"中和”,而并非“意境”。
“中和”之后是“气韵”,到唐代意境学说才有所发端。但这样划分是机械的,“中和”经常与后两者交织在一起,并始终贯穿和参与中国审美活动的历史中。
要想绝对地划分“中和”与“意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可以相对地把中和与意境作出区别,以便对人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有更清晰的认识。人类最早的世界观通常都是神话中的物活论,而相伴随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因为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人的理性作用在那时还显得很弱小。所以早期的巫术文化,充满了人类对自然的各种激烈的情感反映,人们无法通过其蒙昧的理性的认知能力,对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人与社会等关系,有更多的认识和把握。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力逐步提高,一个伟大的理性时代开始发端——近古哲学。哲学对神话的胜利,是人类理性的胜利,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胜利,对神怀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造就了人类第一批智者。
朴素唯物主义强调"客观的再现”,正所谓“感天地而化生万物”,这在西方被解释为对自然“模仿说”。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两个相当靠近的邻居,甚至人在对世界抱持一种唯物的世界观的时候,朴素的辩证主义便几乎同时降临在人类的思想史中。它们都是理性的产物,只不过唯物主义在“再现”的意识的毛坯基础上,洞彻了人与自然存在的关系,于是人学在悖论中强调“中和”,合题对立的统一意义。而中和的表述最早可见于《周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它强调的是人与客观现实的统一和折中。
那么我就回答了带有“中和”的审美活动和现实的关系,也同时分出了意境和中和的根本区别。“中和"作为审美活动,它与现实世界是相结合的,而意境则不然。意境的主客统一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审美世界,那个世界作为审美理想的文学典型,往往具有乌托邦性质。而中和则不是,中和强调人与现实自然的和谐,而意境则更强调审美理想的意义,并带有更强烈的人化功能。于是我似乎回答了作者的“慵懒”,他更多地满足在人和现实的自然和谐中,并反映这种和谐与现实。
结合诗歌《物象》的5个小节进行分析,我看到了作者在“情感上的适中”,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审美形态,即“中和”的审美心理特点。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究其原因中和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强调合适的尺度和分寸。悖论分属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合”之则“中”,“中”又生“和”,所以你很难看到作者内在思绪有太多的起伏。而意境则不然,意境带有强烈的对审美理想的求诉,所以越纯粹的人心之境像,就越带有冲突性,人的主观因素强烈地介入审美活动中。按佛罗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存在主义的说法,那就叫能量的贯注,并通过“起立”在脑海生成物象和承载物象的思维空间一一大地。所以“情感的适中”作为艺术观,也就是理性对情感的控制,并自觉地把握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使情感不至于失控和泛滥,而达到一种宁静、平和与渐进的愉悦。
因此,我把作者文学图景的清晰归于唯物观的反映论,而把作者在文本表露出的宁静,归于他与现实之间的中和态度。他强调与现实的一种和平共处,并重视忠实于生活的原貌,使人从平凡中获得对存在意义的抵达,而不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革。所以那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作为物质、命运、自然和义理,其在作者“中和”的审美意识和态度中,带出了普遍的完整效果,呈现一种总体的心智平衡。这种完整性本就是调和与包含,并在多样性统一中,使作者对生活外来的因素和差异性都能善于吸纳,并化解其所得。
要知道“中和”作为人性的修养,在中国先秦时代就发展出优美、高尚、细腻和雅致的文化气质和特点。所以我们也看到酒桶诗歌中各种现实场景和事件,虽然来自非常平凡的生活,但在作者的语境下呈现出诗的贵族光辉。现在我更具体说说文本。
《物象》:“1//一台拖拉机/吃力地/从山脚下/往上爬/司机叼着一根纸烟/火星子/在风里乱飞/萤火虫/都跑得远远的”。第一个文本作者在兼顾审美对象情趣和鲜活的同时,也不忘记拖拉机的力量之美。他通过劳动解释人生的严肃意义时,也不忘记通过司机叼烟的动作,暗示生命的艰难和盲目,进而使司机的粗陋现出一种可爱,并与萤火虫的轻盈获得一种异质同构。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描绘拖拉机、司机的动作时,在揭示劳动的意义时,也不忘记自然的破坏。而这些多样性分明统一在作者平静的陈述中,究其原因就正是作者“天人合一”的中和思想。
“2//幺妹/仍然坐在门槛边上/面前/还堆着/一小堆豆角/两只公鸡/溜远了/黄狗趴在鸡窝/旁边/只是偶尔/张一下/眼睛”。第二个文本作者对“天人合一”的满足感,呈现在乡村生活的自明中。除了“幺妹”的一些细微生活动作,其他不想了,混沌了。于是他解释了生活真实面目的幸福感,而在过去静态的生活和世界观,曾经日日夜夜地陪伴着人类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完全没有我们现在都市生活的繁华和激烈的节奏。
“3//夜宵摊子/躲在马路的拐弯处/一个说安徽话的/20岁出头的/女孩子/穿着白色围裙/一会儿/把锅盖盖子/拎起来/一会儿/把锅盖放上去/偶尔拿根铁丝/往笨重的/蜂窝煤炉子里/捅几下/冒着热气的锅沿/是干净的/这是冬天/深夜11点/马路上/偶尔有人/从自行车上/下来/站着吃碗/小馄饨”。第三个文本理解起来很容易,即通过一个被人们经常接触,而又经常所忽略的事件,来陈诉底层生活人们的苦难。作者的叙述动作非常细腻,在审美对象机械的动作中,饱含了他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对人民的同情、热爱和恩情感。当然也包括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依赖和交流。
“4〃一只苍鹰/静静地/飞过去/蹲在一棵大柏树顶上/大柏树/站立在/一大片水田的/中央/水田上面/有一层薄薄餉雾气/太阳才刚出来/一个挂着猎枪的人/站在田境上/嘴上叼着烟杆/正不停地/划火柴”。第四个文本是一幅风景画,苍鹰和柏树呈露出自然的壮美、开阔和古朴,水田是农耕文明的温暖意义,而阳光把猎人神秘的存在揭示出来。所以猎人的具体含义非常值得玩味,他带有一种现代的解构,甚至是破坏的意义,并又是一幅事不关己的神态。所以这个文本更多属于意境的人心之象的范畴,碍于评论的篇幅,我就不再分析"中和”与“意境”的交织之处了。
“5//公路横亘在半山上/两部车/一前一后/紧追不舍/身后跟着两朵黄色的云/一条静止的大河/卧在山谷里/阳光/直射着它”。第五个文本作者回到“中和”对现实的复制,两台追赶的车是人化世界的事物,所以它们暗含了冲动的危险意味,而自然则是永恒的,并独立和无待于人。因此我依然把文本视为作者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审视,并藏下了作者对人学强烈的危机感。
最后我对作者“慵懒”也要给以一定劝告,那就是中和容易消泯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发展过度会造成对个人才情的严重束缚,甚至会扼杀人的积极意义和生存态度。当然这只是从创作观中去解读作者,而实际一个鲜活的人,他的意义肯定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价值观上来说,人的历史己经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小国寡民的静态的生活样式中了,除了挽歌,我们还是要朝前走。过去我们受到自然的庇护,也受到自然的威胁,历史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供过一种自然的乌托邦。
物象在当下的美学话语习惯中,多数会被纳入“意境说”中的事物,并作为思维空间内的具体对象化构成物。如此,我必须首先分开“意境”和“中和”的区别。中国早期的审美形态是"中和”,而并非“意境”。
“中和”之后是“气韵”,到唐代意境学说才有所发端。但这样划分是机械的,“中和”经常与后两者交织在一起,并始终贯穿和参与中国审美活动的历史中。
要想绝对地划分“中和”与“意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可以相对地把中和与意境作出区别,以便对人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有更清晰的认识。人类最早的世界观通常都是神话中的物活论,而相伴随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因为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人的理性作用在那时还显得很弱小。所以早期的巫术文化,充满了人类对自然的各种激烈的情感反映,人们无法通过其蒙昧的理性的认知能力,对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人与社会等关系,有更多的认识和把握。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力逐步提高,一个伟大的理性时代开始发端——近古哲学。哲学对神话的胜利,是人类理性的胜利,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胜利,对神怀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造就了人类第一批智者。
朴素唯物主义强调"客观的再现”,正所谓“感天地而化生万物”,这在西方被解释为对自然“模仿说”。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两个相当靠近的邻居,甚至人在对世界抱持一种唯物的世界观的时候,朴素的辩证主义便几乎同时降临在人类的思想史中。它们都是理性的产物,只不过唯物主义在“再现”的意识的毛坯基础上,洞彻了人与自然存在的关系,于是人学在悖论中强调“中和”,合题对立的统一意义。而中和的表述最早可见于《周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它强调的是人与客观现实的统一和折中。
那么我就回答了带有“中和”的审美活动和现实的关系,也同时分出了意境和中和的根本区别。“中和"作为审美活动,它与现实世界是相结合的,而意境则不然。意境的主客统一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审美世界,那个世界作为审美理想的文学典型,往往具有乌托邦性质。而中和则不是,中和强调人与现实自然的和谐,而意境则更强调审美理想的意义,并带有更强烈的人化功能。于是我似乎回答了作者的“慵懒”,他更多地满足在人和现实的自然和谐中,并反映这种和谐与现实。
结合诗歌《物象》的5个小节进行分析,我看到了作者在“情感上的适中”,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审美形态,即“中和”的审美心理特点。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究其原因中和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强调合适的尺度和分寸。悖论分属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合”之则“中”,“中”又生“和”,所以你很难看到作者内在思绪有太多的起伏。而意境则不然,意境带有强烈的对审美理想的求诉,所以越纯粹的人心之境像,就越带有冲突性,人的主观因素强烈地介入审美活动中。按佛罗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存在主义的说法,那就叫能量的贯注,并通过“起立”在脑海生成物象和承载物象的思维空间一一大地。所以“情感的适中”作为艺术观,也就是理性对情感的控制,并自觉地把握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使情感不至于失控和泛滥,而达到一种宁静、平和与渐进的愉悦。
因此,我把作者文学图景的清晰归于唯物观的反映论,而把作者在文本表露出的宁静,归于他与现实之间的中和态度。他强调与现实的一种和平共处,并重视忠实于生活的原貌,使人从平凡中获得对存在意义的抵达,而不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革。所以那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作为物质、命运、自然和义理,其在作者“中和”的审美意识和态度中,带出了普遍的完整效果,呈现一种总体的心智平衡。这种完整性本就是调和与包含,并在多样性统一中,使作者对生活外来的因素和差异性都能善于吸纳,并化解其所得。
要知道“中和”作为人性的修养,在中国先秦时代就发展出优美、高尚、细腻和雅致的文化气质和特点。所以我们也看到酒桶诗歌中各种现实场景和事件,虽然来自非常平凡的生活,但在作者的语境下呈现出诗的贵族光辉。现在我更具体说说文本。
《物象》:“1//一台拖拉机/吃力地/从山脚下/往上爬/司机叼着一根纸烟/火星子/在风里乱飞/萤火虫/都跑得远远的”。第一个文本作者在兼顾审美对象情趣和鲜活的同时,也不忘记拖拉机的力量之美。他通过劳动解释人生的严肃意义时,也不忘记通过司机叼烟的动作,暗示生命的艰难和盲目,进而使司机的粗陋现出一种可爱,并与萤火虫的轻盈获得一种异质同构。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描绘拖拉机、司机的动作时,在揭示劳动的意义时,也不忘记自然的破坏。而这些多样性分明统一在作者平静的陈述中,究其原因就正是作者“天人合一”的中和思想。
“2//幺妹/仍然坐在门槛边上/面前/还堆着/一小堆豆角/两只公鸡/溜远了/黄狗趴在鸡窝/旁边/只是偶尔/张一下/眼睛”。第二个文本作者对“天人合一”的满足感,呈现在乡村生活的自明中。除了“幺妹”的一些细微生活动作,其他不想了,混沌了。于是他解释了生活真实面目的幸福感,而在过去静态的生活和世界观,曾经日日夜夜地陪伴着人类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完全没有我们现在都市生活的繁华和激烈的节奏。
“3//夜宵摊子/躲在马路的拐弯处/一个说安徽话的/20岁出头的/女孩子/穿着白色围裙/一会儿/把锅盖盖子/拎起来/一会儿/把锅盖放上去/偶尔拿根铁丝/往笨重的/蜂窝煤炉子里/捅几下/冒着热气的锅沿/是干净的/这是冬天/深夜11点/马路上/偶尔有人/从自行车上/下来/站着吃碗/小馄饨”。第三个文本理解起来很容易,即通过一个被人们经常接触,而又经常所忽略的事件,来陈诉底层生活人们的苦难。作者的叙述动作非常细腻,在审美对象机械的动作中,饱含了他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对人民的同情、热爱和恩情感。当然也包括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依赖和交流。
“4〃一只苍鹰/静静地/飞过去/蹲在一棵大柏树顶上/大柏树/站立在/一大片水田的/中央/水田上面/有一层薄薄餉雾气/太阳才刚出来/一个挂着猎枪的人/站在田境上/嘴上叼着烟杆/正不停地/划火柴”。第四个文本是一幅风景画,苍鹰和柏树呈露出自然的壮美、开阔和古朴,水田是农耕文明的温暖意义,而阳光把猎人神秘的存在揭示出来。所以猎人的具体含义非常值得玩味,他带有一种现代的解构,甚至是破坏的意义,并又是一幅事不关己的神态。所以这个文本更多属于意境的人心之象的范畴,碍于评论的篇幅,我就不再分析"中和”与“意境”的交织之处了。
“5//公路横亘在半山上/两部车/一前一后/紧追不舍/身后跟着两朵黄色的云/一条静止的大河/卧在山谷里/阳光/直射着它”。第五个文本作者回到“中和”对现实的复制,两台追赶的车是人化世界的事物,所以它们暗含了冲动的危险意味,而自然则是永恒的,并独立和无待于人。因此我依然把文本视为作者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审视,并藏下了作者对人学强烈的危机感。
最后我对作者“慵懒”也要给以一定劝告,那就是中和容易消泯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发展过度会造成对个人才情的严重束缚,甚至会扼杀人的积极意义和生存态度。当然这只是从创作观中去解读作者,而实际一个鲜活的人,他的意义肯定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价值观上来说,人的历史己经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小国寡民的静态的生活样式中了,除了挽歌,我们还是要朝前走。过去我们受到自然的庇护,也受到自然的威胁,历史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供过一种自然的乌托邦。
相关人物
夏日的果
责任者